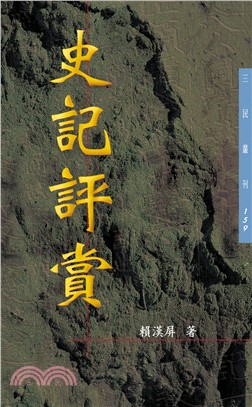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本書收錄十二年前出版的《縫》,加入新作四篇,重新問世。
十二個短篇故事,十二種罪與罰。
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張耀升是敏銳而勇敢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彷彿看見他用深情而哀傷的眼光在撿拾這個世界的破片,然後還用顫抖的雙手細細地縫補著。
-袁哲生
張耀升擅長從黑暗著手,實則藏不住小說家的同理心與悲憫情懷。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說故事好手,情節詭誕,引人入勝,卻又入情入理,令人折服。他的手法犀利如手術刀,刀刀見骨,絕不鄉愿,這在台灣作家中誠屬少見。
-林靖傑
名家推薦
小野(作家)、丁允恭(作家)、甘耀明(作家)、朱宥勳(小說家、文化評論者)、宋澤萊(作家)、伊格言(作家)、李金蓮(資深文化人)、吳曉樂(作家)、林靖傑(導演)、林書宇(導演)、易智言(導演)、紀培慧(演員)、袁哲生(作家)、桂綸鎂(演員)、陳國偉(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陳玉勳(導演)、陳柏青(作家)、黃河(演員)、曹麗娟(作家)、葉佳怡(作家)、楊佳嫻(作家、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廖玉蕙(作家)、廖苡喬(演員)、劉克襄(作家)、鄭明娳(作家)、鄭順聰(作家)、關詩敏(歌手) 熱烈推薦
壓縮在記憶底層的童年鬼魅、校園裡流傳的鬼故事、被霸凌而後自殺的少年灰影、彷彿一起生活的祖母其實早已死去、年輕時深愛過自己的人換了樣貌出現眼前……
這些被壓迫,被驅離的弱者躲在黑暗中,
在包容一切艱難的黑暗裡,他們無須羞愧自己的髒污。.
如果你願意,請一起走進縫隙中,
說不定,你會赫然發現,這裡正說著你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太乾淨明亮,因此張耀升劈開了一道縫,讓無家可歸的幽魂得以在此棲息。他表面上說著異常可怕的故事,實則低目垂眉,守護那些被驅離的、被棄置的、乃至不被承認的惡,在黑暗中等待著轉化的可能。
「黑,是最溫暖的顏色。」張耀升這麼說。
十二個短篇故事,十二種罪與罰。
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張耀升是敏銳而勇敢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彷彿看見他用深情而哀傷的眼光在撿拾這個世界的破片,然後還用顫抖的雙手細細地縫補著。
-袁哲生
張耀升擅長從黑暗著手,實則藏不住小說家的同理心與悲憫情懷。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說故事好手,情節詭誕,引人入勝,卻又入情入理,令人折服。他的手法犀利如手術刀,刀刀見骨,絕不鄉愿,這在台灣作家中誠屬少見。
-林靖傑
名家推薦
小野(作家)、丁允恭(作家)、甘耀明(作家)、朱宥勳(小說家、文化評論者)、宋澤萊(作家)、伊格言(作家)、李金蓮(資深文化人)、吳曉樂(作家)、林靖傑(導演)、林書宇(導演)、易智言(導演)、紀培慧(演員)、袁哲生(作家)、桂綸鎂(演員)、陳國偉(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陳玉勳(導演)、陳柏青(作家)、黃河(演員)、曹麗娟(作家)、葉佳怡(作家)、楊佳嫻(作家、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廖玉蕙(作家)、廖苡喬(演員)、劉克襄(作家)、鄭明娳(作家)、鄭順聰(作家)、關詩敏(歌手) 熱烈推薦
壓縮在記憶底層的童年鬼魅、校園裡流傳的鬼故事、被霸凌而後自殺的少年灰影、彷彿一起生活的祖母其實早已死去、年輕時深愛過自己的人換了樣貌出現眼前……
這些被壓迫,被驅離的弱者躲在黑暗中,
在包容一切艱難的黑暗裡,他們無須羞愧自己的髒污。.
如果你願意,請一起走進縫隙中,
說不定,你會赫然發現,這裡正說著你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太乾淨明亮,因此張耀升劈開了一道縫,讓無家可歸的幽魂得以在此棲息。他表面上說著異常可怕的故事,實則低目垂眉,守護那些被驅離的、被棄置的、乃至不被承認的惡,在黑暗中等待著轉化的可能。
「黑,是最溫暖的顏色。」張耀升這麼說。
作者簡介
張耀升
小說家,影像創作者。
張耀升使用文字與影像,一如用咒,為種種混沌無明一一安放其名,使之降伏。他擅長與黑暗相處,黑暗中躲著怪獸,等著他一一將它們的故事說出,彷彿如此才能得到安息。藉著他的故事召喚出的幻象,我們觀看他人的艱難,好得知自己命運的真相。
本書收錄二○○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縫》,並加入近年新作數篇。張耀升曾於二○一○年執行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至日本在地旅行三個月,此後決定重返人間,二○一一年出版長篇小說《彼岸的女人》(本事文化)與散文集《告別的年代:再見!左營眷村!》。二○一四年出版電影小說《行動代號:孫中山》(導演及故事:易智言)。
小說家,影像創作者。
張耀升使用文字與影像,一如用咒,為種種混沌無明一一安放其名,使之降伏。他擅長與黑暗相處,黑暗中躲著怪獸,等著他一一將它們的故事說出,彷彿如此才能得到安息。藉著他的故事召喚出的幻象,我們觀看他人的艱難,好得知自己命運的真相。
本書收錄二○○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縫》,並加入近年新作數篇。張耀升曾於二○一○年執行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至日本在地旅行三個月,此後決定重返人間,二○一一年出版長篇小說《彼岸的女人》(本事文化)與散文集《告別的年代:再見!左營眷村!》。二○一四年出版電影小說《行動代號:孫中山》(導演及故事:易智言)。
序
走進人性幽微處----讀張耀升《縫》
鄭明娳
張耀升短篇小說《縫》主要關懷當前台灣三大領域:家庭親子關係、中學校園生態與愛情尋覓之路。其間同時帶出社會(如求職)、軍中(如請假)等各種問題,幾乎囊括業已扭曲/失衡/冷冽/異化的台灣生態,人性在此負空間無限地往前進展,渾沌者隨波逐流,清醒者墜入絕望的黑洞。
全書收尾之作〈鼠〉文的時代背景回到日據時代,幾乎成為整本小說象徵性上的「楔子」,台灣的歷史如果從這一頁讀起,那麼小說最後一句「昭和二十年,炸毀岸內糖廠的那群砲彈,便在此時如一陣雷雨般落下來。」非常具有象徵意味地呈現日據時台灣人民在二戰時的悲慘境遇:主角在喪失丈夫、親人、工作、食物……所有東西之後,更面臨炮彈全面性的毀滅。她是否能「絕處逢生」,〈鼠〉文沒寫就戛然而止,但《縫》一書其他篇章替這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島內人民做了後續詮釋。
全書並非依賴題材引起讀者注意,而是對人性內在極幽微之處掌握得絲絲入扣,讀來讓人膽戰心驚。
是縫合還是縫死?家庭中的糾葛鬥爭
首篇〈縫〉從兒童(孫子)視角瞻望祖母(地位可以上推到祖先,代表整個民族傳統的父母霸權)地位的崩解。孫子沒機會看到過去祖母如何教養父親,但讀者看到這家「老字號西服店」,就知道父親承襲祖父母的職業,當客人挑選衣料時,祖母必然在父親背後提出各種意見。可見父親從小就時時被祖母耳提面命教育成今天的裁縫師。〈縫〉文未寫出的家庭教育,很可以用蘇紹連詩〈七尺布〉來補白:母親買回七尺布替兒子裁衣,兒子說八尺才夠。母親堅持按「舊尺碼在布上畫了一個我,然後用剪刀慢慢地剪,我慢慢地哭,啊!把我剪破,把我剪開,再用針線縫我,補我……使我成人。」同樣呈現我們種族的家庭傳統教育,父母有權力把子女形塑成他們預設的職業/形象,可以用暴力(剪刀)裁破兒女的/心,再用針線依照他們的期望去縫補,最後「縫」成父母預設的成人(恰恰被孔子定義的「成人」所嘲諷)。〈縫〉裡的父親被調教成:「身體捆在保守強硬的四肢線條框架下……。」想來,在成長過程裡,必如前詩中也哭過、求過、忍耐過,結果都失敗,直到祖母年邁仍然不放棄指揮他。
〈縫〉更進一步書寫兒子對傳統家教的反撲;他讓母親有多不堪,就表示他對過去的教育有多怨恨。母親去世時,他把母親的壽衣和皮膚縫在一起,看來真像他自己「身體捆在保守強硬的四肢線條框架下」啊。
親子的人間鬥爭方才落幕,祖母彷彿立刻從陰間回來報仇,這意味著在滴水不漏的傳統觀念下,天下絕對沒有不是的父母;所以,她讓兒子如天譴般地自殘殘人乃至發瘋。
與其說是祖母回陽間報仇,不如說是父親潛意識裡孝/順/叛逆的糾葛鬥爭,那不斷出現的縫紉聲音及父親眼前揮之不去的(祖母)影子,既暗示潛意識想要縫合親情的裂縫;但更多的是意識層面要把對方如布料般以利針縫(釘)死。母子間一生的愛恨情仇盤根錯節地糾纏難解,以致兒子內在人格不斷地分裂流血……。
〈敲門〉、〈螳螂〉、〈縫〉裡的孫子都跟祖母感情融洽,這又是傳統社會裡祖輩溺愛孫輩的寫照。重新出版的《縫》新增的〈秘密〉寫子女棄養,但〈回家〉出現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眷戀情愫,則呈現當前社會的親子關係有了多樣的組合。
死亡才得以重生,校園裡的幽暗面
〈藍色項圈〉、〈友達〉、〈暘城〉以及〈鮮肉餅〉顯示作者對台灣中學校園的高度關懷,前兩篇非常具體地顯示學校唯升學主義是瞻,不惜用盡各種虐待學生的方法,讓學生自相殘殺拚第一名。作者很技巧的不白描校長、教師種種嘴臉/行為,而是直搗龍穴指向盡頭:學生被壓力逼迫到投繯自盡(這是一個層次)/死而後生(脫胎換骨又是一個層次)的惡性循環裡。凡是能拚到死的人,脖子就會留下「藍色項圈」印記,回到陽間、回到教室成績就躍居第一。這不是鬼魅小說,只是象徵學生必須付出生命的全部代價才能拚到學校的要求。許多學生都不得不走上這條路,因而第一名像打牌一樣會輪莊,學生也只好再度上吊,故許多學生其實帶著多條「藍色項圈」,用來象徵「死去活來」,多麼殘酷!
學校只在乎成績,其他一概放牛,學生互相傾軋鬥爭,校園比監獄還不堪。至於〈暘城〉與〈鮮肉餅〉,更是近年校園常見青少年人格墮落,霸凌弱勢,並牽涉到單親/弱勢家庭的悲劇、家長/學校/社會扭曲的價值觀,種種亂象不遑細舉。
被壓抑的必定反撲,愛情裡的黑洞
表面看,〈伊卡勒斯〉是唯一書寫愛情之作,其實還要加上〈洞〉。
初讀〈洞〉時,筆者不斷回想它與〈伊卡勒斯〉對愛情本質的詮釋頗為接近而且互補,沒想到結尾竟然出現主角要寫的小說題目是「伊卡勒斯」!
〈伊卡勒斯〉書寫同性之愛,〈洞〉是異性之愛;只要是愛情,同性跟異性無何差別。〈伊卡勒斯〉充滿許多雙關的敘述文字,例如忠哥在頂樓圍(危)牆彈吉他,稍為一仰就可能墮落樓下,雙關他把自己「放」在一個危險的處境。他在此彈唱的感人歌曲的內容是一場絕望的戀愛,也雙關他的愛情經過與結局。
忠哥愛上同住一年的「我」,而「我」完全享受著被愛,卻絲毫不在乎對方,他幾乎利用忠哥的愛來照顧自己、寵壞自己,忠哥都無怨無悔;但他用冷漠來回應忠哥的愛撫,使忠哥絕望而消失,「我」卻以為忠哥是死於日本的樹海。十年後,忠哥再次出現,仍然熱情地愛著「我」,忠哥其實一直偷偷地看著「我」,知道對方很依賴他,他用十年來等待愛情發芽。然而,重逢後的「我」依然如故。一切急轉直下回到原點,忠哥永遠消失。
〈洞〉裡的戀情也發生在同住一戶公寓的高中男女。男主角寫了很多情書,卻沒有給對方,都藏在自家房間衣櫃後面牆上的洞裡。這是一場沒有發生情節的愛情,男主角受不了自我壓抑終於不告而別,對方則在大學聯考後自殺。「洞」指涉許多「昨日被壓抑的一切,他日必定會帶著更強大的力量反撲。」他終於決定把壓抑在心底黑洞的種種書寫出來,結尾是「一切黯黑便化成光。」有精神解脫、有創作自負,讓人擊節稱賞!
愛情需要兩人互動才能進行,以上兩篇小說都因為其中一位角色「愛無能」而造成非死即分的殘愛。
一本為所有折翼人物而寫的小說
重新出版的《縫》增加四篇小說,是對原本三大主題的補強。就全部小說的主題來說:人類都希望能擁有伊卡勒斯般的翅膀自由地飛翔自己的人生。然而,幾乎每個人都因種種原因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折翼。沒有人能真正飛翔起來,可能因先天後天存在著無法綴補的「縫」,是渺小的人類所無能為力的。
《縫》書各篇經常交織使用夢/夢魘/幻想/魔幻等手法,以致於虛寫與寫實界線模糊,有時看似一個平常的夢境,原來是經常流盪心中的幻覺;有時像是主角的幻覺,之後才發現那是經常出現的夢魘,不斷搗亂主角內心;更甚者,主角甚至讀者也分不清那是實境還是幻境─實際上那不正是現代人生/人性/人心的寫實嗎?同時,也因為這樣的手法使得各篇之間,可以互相呼應與連結(例如〈洞〉文結尾要寫的小說題目是「伊卡勒斯」,並非指〈伊卡勒斯〉一篇而已,是指深藏在心洞中的所有折翼的人物,增加整本小說廣大的詮釋空間,成為《縫》引人注目的魅力之一。
鄭明娳。曾獲國家文藝理論獎、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中山文藝散文創作獎等十一項獎。著有《古典小說藝術新探》等二十八種、編有《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等三十種。
鄭明娳
張耀升短篇小說《縫》主要關懷當前台灣三大領域:家庭親子關係、中學校園生態與愛情尋覓之路。其間同時帶出社會(如求職)、軍中(如請假)等各種問題,幾乎囊括業已扭曲/失衡/冷冽/異化的台灣生態,人性在此負空間無限地往前進展,渾沌者隨波逐流,清醒者墜入絕望的黑洞。
全書收尾之作〈鼠〉文的時代背景回到日據時代,幾乎成為整本小說象徵性上的「楔子」,台灣的歷史如果從這一頁讀起,那麼小說最後一句「昭和二十年,炸毀岸內糖廠的那群砲彈,便在此時如一陣雷雨般落下來。」非常具有象徵意味地呈現日據時台灣人民在二戰時的悲慘境遇:主角在喪失丈夫、親人、工作、食物……所有東西之後,更面臨炮彈全面性的毀滅。她是否能「絕處逢生」,〈鼠〉文沒寫就戛然而止,但《縫》一書其他篇章替這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島內人民做了後續詮釋。
全書並非依賴題材引起讀者注意,而是對人性內在極幽微之處掌握得絲絲入扣,讀來讓人膽戰心驚。
是縫合還是縫死?家庭中的糾葛鬥爭
首篇〈縫〉從兒童(孫子)視角瞻望祖母(地位可以上推到祖先,代表整個民族傳統的父母霸權)地位的崩解。孫子沒機會看到過去祖母如何教養父親,但讀者看到這家「老字號西服店」,就知道父親承襲祖父母的職業,當客人挑選衣料時,祖母必然在父親背後提出各種意見。可見父親從小就時時被祖母耳提面命教育成今天的裁縫師。〈縫〉文未寫出的家庭教育,很可以用蘇紹連詩〈七尺布〉來補白:母親買回七尺布替兒子裁衣,兒子說八尺才夠。母親堅持按「舊尺碼在布上畫了一個我,然後用剪刀慢慢地剪,我慢慢地哭,啊!把我剪破,把我剪開,再用針線縫我,補我……使我成人。」同樣呈現我們種族的家庭傳統教育,父母有權力把子女形塑成他們預設的職業/形象,可以用暴力(剪刀)裁破兒女的/心,再用針線依照他們的期望去縫補,最後「縫」成父母預設的成人(恰恰被孔子定義的「成人」所嘲諷)。〈縫〉裡的父親被調教成:「身體捆在保守強硬的四肢線條框架下……。」想來,在成長過程裡,必如前詩中也哭過、求過、忍耐過,結果都失敗,直到祖母年邁仍然不放棄指揮他。
〈縫〉更進一步書寫兒子對傳統家教的反撲;他讓母親有多不堪,就表示他對過去的教育有多怨恨。母親去世時,他把母親的壽衣和皮膚縫在一起,看來真像他自己「身體捆在保守強硬的四肢線條框架下」啊。
親子的人間鬥爭方才落幕,祖母彷彿立刻從陰間回來報仇,這意味著在滴水不漏的傳統觀念下,天下絕對沒有不是的父母;所以,她讓兒子如天譴般地自殘殘人乃至發瘋。
與其說是祖母回陽間報仇,不如說是父親潛意識裡孝/順/叛逆的糾葛鬥爭,那不斷出現的縫紉聲音及父親眼前揮之不去的(祖母)影子,既暗示潛意識想要縫合親情的裂縫;但更多的是意識層面要把對方如布料般以利針縫(釘)死。母子間一生的愛恨情仇盤根錯節地糾纏難解,以致兒子內在人格不斷地分裂流血……。
〈敲門〉、〈螳螂〉、〈縫〉裡的孫子都跟祖母感情融洽,這又是傳統社會裡祖輩溺愛孫輩的寫照。重新出版的《縫》新增的〈秘密〉寫子女棄養,但〈回家〉出現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眷戀情愫,則呈現當前社會的親子關係有了多樣的組合。
死亡才得以重生,校園裡的幽暗面
〈藍色項圈〉、〈友達〉、〈暘城〉以及〈鮮肉餅〉顯示作者對台灣中學校園的高度關懷,前兩篇非常具體地顯示學校唯升學主義是瞻,不惜用盡各種虐待學生的方法,讓學生自相殘殺拚第一名。作者很技巧的不白描校長、教師種種嘴臉/行為,而是直搗龍穴指向盡頭:學生被壓力逼迫到投繯自盡(這是一個層次)/死而後生(脫胎換骨又是一個層次)的惡性循環裡。凡是能拚到死的人,脖子就會留下「藍色項圈」印記,回到陽間、回到教室成績就躍居第一。這不是鬼魅小說,只是象徵學生必須付出生命的全部代價才能拚到學校的要求。許多學生都不得不走上這條路,因而第一名像打牌一樣會輪莊,學生也只好再度上吊,故許多學生其實帶著多條「藍色項圈」,用來象徵「死去活來」,多麼殘酷!
學校只在乎成績,其他一概放牛,學生互相傾軋鬥爭,校園比監獄還不堪。至於〈暘城〉與〈鮮肉餅〉,更是近年校園常見青少年人格墮落,霸凌弱勢,並牽涉到單親/弱勢家庭的悲劇、家長/學校/社會扭曲的價值觀,種種亂象不遑細舉。
被壓抑的必定反撲,愛情裡的黑洞
表面看,〈伊卡勒斯〉是唯一書寫愛情之作,其實還要加上〈洞〉。
初讀〈洞〉時,筆者不斷回想它與〈伊卡勒斯〉對愛情本質的詮釋頗為接近而且互補,沒想到結尾竟然出現主角要寫的小說題目是「伊卡勒斯」!
〈伊卡勒斯〉書寫同性之愛,〈洞〉是異性之愛;只要是愛情,同性跟異性無何差別。〈伊卡勒斯〉充滿許多雙關的敘述文字,例如忠哥在頂樓圍(危)牆彈吉他,稍為一仰就可能墮落樓下,雙關他把自己「放」在一個危險的處境。他在此彈唱的感人歌曲的內容是一場絕望的戀愛,也雙關他的愛情經過與結局。
忠哥愛上同住一年的「我」,而「我」完全享受著被愛,卻絲毫不在乎對方,他幾乎利用忠哥的愛來照顧自己、寵壞自己,忠哥都無怨無悔;但他用冷漠來回應忠哥的愛撫,使忠哥絕望而消失,「我」卻以為忠哥是死於日本的樹海。十年後,忠哥再次出現,仍然熱情地愛著「我」,忠哥其實一直偷偷地看著「我」,知道對方很依賴他,他用十年來等待愛情發芽。然而,重逢後的「我」依然如故。一切急轉直下回到原點,忠哥永遠消失。
〈洞〉裡的戀情也發生在同住一戶公寓的高中男女。男主角寫了很多情書,卻沒有給對方,都藏在自家房間衣櫃後面牆上的洞裡。這是一場沒有發生情節的愛情,男主角受不了自我壓抑終於不告而別,對方則在大學聯考後自殺。「洞」指涉許多「昨日被壓抑的一切,他日必定會帶著更強大的力量反撲。」他終於決定把壓抑在心底黑洞的種種書寫出來,結尾是「一切黯黑便化成光。」有精神解脫、有創作自負,讓人擊節稱賞!
愛情需要兩人互動才能進行,以上兩篇小說都因為其中一位角色「愛無能」而造成非死即分的殘愛。
一本為所有折翼人物而寫的小說
重新出版的《縫》增加四篇小說,是對原本三大主題的補強。就全部小說的主題來說:人類都希望能擁有伊卡勒斯般的翅膀自由地飛翔自己的人生。然而,幾乎每個人都因種種原因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折翼。沒有人能真正飛翔起來,可能因先天後天存在著無法綴補的「縫」,是渺小的人類所無能為力的。
《縫》書各篇經常交織使用夢/夢魘/幻想/魔幻等手法,以致於虛寫與寫實界線模糊,有時看似一個平常的夢境,原來是經常流盪心中的幻覺;有時像是主角的幻覺,之後才發現那是經常出現的夢魘,不斷搗亂主角內心;更甚者,主角甚至讀者也分不清那是實境還是幻境─實際上那不正是現代人生/人性/人心的寫實嗎?同時,也因為這樣的手法使得各篇之間,可以互相呼應與連結(例如〈洞〉文結尾要寫的小說題目是「伊卡勒斯」,並非指〈伊卡勒斯〉一篇而已,是指深藏在心洞中的所有折翼的人物,增加整本小說廣大的詮釋空間,成為《縫》引人注目的魅力之一。
鄭明娳。曾獲國家文藝理論獎、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中山文藝散文創作獎等十一項獎。著有《古典小說藝術新探》等二十八種、編有《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等三十種。
目次
名家推薦
推薦序 走進人性幽微處 鄭明娳
傷害,作為書寫倫理 陳國偉
縫
暘城
藍色項圈
友達
鮮肉餅
秘密
敲門
螳螂
回家
伊卡勒斯
洞
鼠
編者的話
推薦序 走進人性幽微處 鄭明娳
傷害,作為書寫倫理 陳國偉
縫
暘城
藍色項圈
友達
鮮肉餅
秘密
敲門
螳螂
回家
伊卡勒斯
洞
鼠
編者的話
書摘/試閱
鮮肉餅
一到下午第三堂課,他就會開始想像校門口鮮肉餅的味道。
他喜歡先在周圍一圈油亮白皮上咬一小口,啜飲裡頭熱燙香麻的肉汁,再稍微大口地含住鮮肉餅上下兩面焦黃的底,喀嚓一聲,咬進內餡,胡椒、孜然、薑、蔥、蒜,各式辛香料從粉紅色的肉餡中奔騰而起,衝入鼻腔,連同肉汁在他口中流竄,讓他連吸帶吮吞下一塊肉。
那是每天放學時,他唯一期待的事情,雖說校門口鮮肉餅的攤販車要等到第七堂課快結束時才會將鍋蓋掀開,只有那些與管理員交情特殊或油條到師長視而不見的學生能比所有人都早走出校門,取得第一批剛起鍋的鮮肉餅。而他總是最後離開,鮮肉餅的老闆早已將攤販車清潔完畢,等他經過,才從保麗龍箱子裡拿出最後一個包著鮮肉餅的紙袋,也不多看他一眼,任憑他將零錢放到攤販車上拾起鮮肉餅離開。
最後一個鮮肉餅往往已經失溫,且特別油膩,遠不如剛出爐的好吃。很久以前他曾吃過剛出爐的鮮肉餅,並一直念念不忘,但如今的他沒有辦法。放學前,前後左右四個同學便斜眼揪著他,不許他離開。下課後,四個同學將他圍住,帶往操場後方的空地,輪番虐待他。
原本他們還是一群好朋友,時常玩在一起,有說有笑,但有天他們聊起家庭成員,他說自己是單親家庭,母親撫養他長大,他沒見過也沒聽母親提起過父親。
隔天,附近的同學躲著他竊竊私語,下課前,後面傳來一張紙條:「我媽說你爸是殺人兇手。」放學後,前後左右四個同學面無表情地將他帶往廁所,有的手一撐將他壓在牆上,有的揪著他的衣領,陸續替他填補空白的父親形象。
計程車司機、酒駕、衝撞放學的國小學童、車頭全毀、三死六傷、刑事訴訟、棄保潛逃、通緝。
偶爾有人要進來上廁所,便被把風的同學擋住,說:「裡面有事情在處理。」
之後,「處理」就沒有在放學後間斷過。總是等到所有人都離開校園,他才從地上爬起,緩緩走出學校,與正準備離開的鮮肉餅老闆視線相對。
老闆看他的樣子,問他要不要緊,他搖搖頭。
老闆從保麗龍箱子拿出一個鮮肉餅,說:「哪,這個給你,別太難過。」
回家路上,他咬下一口鮮肉餅,突然感到唇齒間一陣巨痛,才發現其中一顆牙齒被打落。
鮮肉餅上滿是他口中的血,鮮血混著肉汁佈滿粉紅色的肉餅,再從外圍白亮的餅皮中垂涎到地面,彷彿鮮肉餅本身便是一個淌著血的傷口。
母親問他怎麼了,他反問父親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之後他們有了一段各說各話的爭吵,並開始在家裡減少交談與眼神接觸的機會。
第二天,當老闆又遞給他最後一個鮮肉餅,他突然意識到欺負他的同學先他離開校門,也必定跟老闆買了鮮肉餅。他拒絕老闆的施捨,從口袋掏出零錢丟到攤販車上。
一切都會變成常態。家中的冷戰,學校的霸凌,老闆的施惠,他的倔強。常態而後成為日常。在看似不變的日常中,唯一改變的,只有他不斷累積的怨恨。從早自習起,他便在腦中想像同學的死狀,整整一天下來,細節足夠讓他以為門口的老闆殺了這四個同學,而後支解,吊起手臂與大腿,將臀部與排骨分開排放於桌上,半月形的屠刀打鼓般地落在砧板上,而後和入香料,做成鮮肉餅。
所以肉餡與他受傷後癒合的傷口一樣,是粉紅色。
他逐漸對老闆產生一份親切感,有時候,拿起鮮肉餅,猶豫地站在攤販車前想說幾句話。老闆好奇地抬起頭,他看見老闆的臉,眉毛粗短,顴骨高嘴唇薄,雙頰被頭頂的路燈打出陰影,像牆上的一副塗鴉,輪廓粗糙、面無表情。
回家路上,透過脹紅的雙眼望出去,沿路與他路過的每個人都長著那樣的臉,那個拐彎後險些與他撞上的母親與她牽著的小孩、公園長椅上的醉漢,以及見他一臉癡呆站在路邊而放慢速度靠過來的計程車司機,都和老闆一樣,在陰影中對他張開如裂縫般的一雙眼。
他開始有意地在老闆面前展示身上的瘀青,開始與欺負他的同學保持一段看得出關聯的距離走出校門,期望老闆能看出他的委屈。他意外地發現老闆從未將鮮肉餅賣給那四位同學,而是假裝賣完,等他經過才拿出事先藏好的鮮肉餅。
他於是更加篤定老闆與自己之間有著某種聯繫,某種認同,某種理解。他想像老闆有過一個早夭的兒子,想像老闆感受到他身上某種同屬於殺人兇手後代的氣質,他們是同類。有一天,在必要的刺激下,老闆會替他報仇。
暑假來臨前,他偷走母親抽屜的積蓄,塞在鞋底帶到學校,挺過放學後的折磨,脫下鞋子,走向鮮肉餅老闆,將一疊鈔票往老闆桌上一丟,沒拾起鮮肉餅便朝開往校門口的公車一撞。
整個夏天,他都在醫院度過。來看他的同學慶幸他能從車禍中醒來,並告知他這個夏天實在可怕,在他車禍的隔天,原本坐在他前後左右的四個同學,在回家路上跨越平交道,集體被火車碾過,屍塊四散,有的散落數十公尺遠,至今仍無法拼湊出完整的軀體。
同學離開後,他告訴母親,想吃鮮肉餅,校門口那間的,剛出爐的,愈多愈好。
在身體逐漸康復的過程中,他有時會感覺到四位同學的存在,尤其當他獨自在病房浴室洗手抬上放滿水,彎腰低頭潑水洗臉,他便感到心慌,深怕後方會有一雙手將他的後腦杓壓入水面。幾次他在昏沉與恍惚間錯覺似地看見四個同學面無表情地站在他的病床邊,甚至感到四肢就此失去知覺,胸口沉悶無法呼吸。
最恐怖的不是惡夢,而是他想像四位同學的車禍慘狀,淋漓盡致的屍首散落各地,誰的頭與誰的手滾落軌道上而誰與誰的內臟混成肉泥,他撐著柺杖走到醫院走廊的公用電話,撥了一通電話到帶頭欺負他的同學家裡。
他想起小時候幫媽媽對發票,不過是對到一張四千塊的中獎發票,他跟媽媽往後幾天都不斷興奮地拿出那張發票重複對獎,此刻的他是同樣的心情,甚至更激動難耐,直到他在電話中說出同學的名字,問他在不在,然後竊笑著等待聽見同學家長的痛哭失聲。
「等一下喔,喂,有你的電話!」
他嚇得掛上電話,半响,又拿起話筒撥給另一個同學,電話一接通,另一頭一傳來他熟悉的聲音,他便掛上電話。在斜射的午後陽光下,他將上著石膏的手舉高,仔細察看上面所有同學的簽名,在他不容易看到的手肘外側,潦草但清楚地簽著霸凌他的四位同學的名字。
他哭倒在走廊上,隨即又為自己的軟弱感到氣餒,軟弱殺人犯的後代,果然只有軟弱的內心。在暑氣蒸騰的醫院裡,他翻閱報紙,確認意外死亡的四個同學與霸凌他的同學無關,他偷走一份放在護理站櫃臺上的病歷表,扯下幾頁,用盡全身之力努力控制酸動的手腕,大大寫下四個同學的名字,將這張紙折疊再折疊,收進口袋,假裝散步偷偷離開醫院。
他在校門口附近下車,一步一步往前,這次他要清楚指定四個同學的名字。
他回想老闆的臉,粗短的眉毛、薄唇、細窄的鼻梁、凹陷的兩頰,他不自覺皺眉、抿嘴,將老闆的面容複製到自己臉上。
夕陽將來往車輛的影子都長長地貼在校門口那條上坡路的地面,他吃力地撐著柺杖,看路面上的影子漸淡,而後路燈亮起。
他走到寫著「鮮肉餅」的招牌前。
招牌上多了一行小字:「即日起停止營業。」
眼前沒有老闆,也沒有四位同學的鬼影,他環顧四周,覺得耳邊有千萬輛火車疾駛而過。
晚風順著校門口的上坡路吹上來,溫暖潮濕,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超越過去他所承受的霸凌痛苦,他覺得自己應該要哭,但雙眼乾澀刺痛,他開始明白老闆與他之間,不過是他個人因過度寂寞而起的妄想,事實上沒有人會理解他,沒有人會同情他,被欺負到角落的他與這個世界之間只剩淡然隱約的薄弱聯繫,像微雨的湖面上的漣漪,早就已經一圈圈逐漸淡去。
一到下午第三堂課,他就會開始想像校門口鮮肉餅的味道。
他喜歡先在周圍一圈油亮白皮上咬一小口,啜飲裡頭熱燙香麻的肉汁,再稍微大口地含住鮮肉餅上下兩面焦黃的底,喀嚓一聲,咬進內餡,胡椒、孜然、薑、蔥、蒜,各式辛香料從粉紅色的肉餡中奔騰而起,衝入鼻腔,連同肉汁在他口中流竄,讓他連吸帶吮吞下一塊肉。
那是每天放學時,他唯一期待的事情,雖說校門口鮮肉餅的攤販車要等到第七堂課快結束時才會將鍋蓋掀開,只有那些與管理員交情特殊或油條到師長視而不見的學生能比所有人都早走出校門,取得第一批剛起鍋的鮮肉餅。而他總是最後離開,鮮肉餅的老闆早已將攤販車清潔完畢,等他經過,才從保麗龍箱子裡拿出最後一個包著鮮肉餅的紙袋,也不多看他一眼,任憑他將零錢放到攤販車上拾起鮮肉餅離開。
最後一個鮮肉餅往往已經失溫,且特別油膩,遠不如剛出爐的好吃。很久以前他曾吃過剛出爐的鮮肉餅,並一直念念不忘,但如今的他沒有辦法。放學前,前後左右四個同學便斜眼揪著他,不許他離開。下課後,四個同學將他圍住,帶往操場後方的空地,輪番虐待他。
原本他們還是一群好朋友,時常玩在一起,有說有笑,但有天他們聊起家庭成員,他說自己是單親家庭,母親撫養他長大,他沒見過也沒聽母親提起過父親。
隔天,附近的同學躲著他竊竊私語,下課前,後面傳來一張紙條:「我媽說你爸是殺人兇手。」放學後,前後左右四個同學面無表情地將他帶往廁所,有的手一撐將他壓在牆上,有的揪著他的衣領,陸續替他填補空白的父親形象。
計程車司機、酒駕、衝撞放學的國小學童、車頭全毀、三死六傷、刑事訴訟、棄保潛逃、通緝。
偶爾有人要進來上廁所,便被把風的同學擋住,說:「裡面有事情在處理。」
之後,「處理」就沒有在放學後間斷過。總是等到所有人都離開校園,他才從地上爬起,緩緩走出學校,與正準備離開的鮮肉餅老闆視線相對。
老闆看他的樣子,問他要不要緊,他搖搖頭。
老闆從保麗龍箱子拿出一個鮮肉餅,說:「哪,這個給你,別太難過。」
回家路上,他咬下一口鮮肉餅,突然感到唇齒間一陣巨痛,才發現其中一顆牙齒被打落。
鮮肉餅上滿是他口中的血,鮮血混著肉汁佈滿粉紅色的肉餅,再從外圍白亮的餅皮中垂涎到地面,彷彿鮮肉餅本身便是一個淌著血的傷口。
母親問他怎麼了,他反問父親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之後他們有了一段各說各話的爭吵,並開始在家裡減少交談與眼神接觸的機會。
第二天,當老闆又遞給他最後一個鮮肉餅,他突然意識到欺負他的同學先他離開校門,也必定跟老闆買了鮮肉餅。他拒絕老闆的施捨,從口袋掏出零錢丟到攤販車上。
一切都會變成常態。家中的冷戰,學校的霸凌,老闆的施惠,他的倔強。常態而後成為日常。在看似不變的日常中,唯一改變的,只有他不斷累積的怨恨。從早自習起,他便在腦中想像同學的死狀,整整一天下來,細節足夠讓他以為門口的老闆殺了這四個同學,而後支解,吊起手臂與大腿,將臀部與排骨分開排放於桌上,半月形的屠刀打鼓般地落在砧板上,而後和入香料,做成鮮肉餅。
所以肉餡與他受傷後癒合的傷口一樣,是粉紅色。
他逐漸對老闆產生一份親切感,有時候,拿起鮮肉餅,猶豫地站在攤販車前想說幾句話。老闆好奇地抬起頭,他看見老闆的臉,眉毛粗短,顴骨高嘴唇薄,雙頰被頭頂的路燈打出陰影,像牆上的一副塗鴉,輪廓粗糙、面無表情。
回家路上,透過脹紅的雙眼望出去,沿路與他路過的每個人都長著那樣的臉,那個拐彎後險些與他撞上的母親與她牽著的小孩、公園長椅上的醉漢,以及見他一臉癡呆站在路邊而放慢速度靠過來的計程車司機,都和老闆一樣,在陰影中對他張開如裂縫般的一雙眼。
他開始有意地在老闆面前展示身上的瘀青,開始與欺負他的同學保持一段看得出關聯的距離走出校門,期望老闆能看出他的委屈。他意外地發現老闆從未將鮮肉餅賣給那四位同學,而是假裝賣完,等他經過才拿出事先藏好的鮮肉餅。
他於是更加篤定老闆與自己之間有著某種聯繫,某種認同,某種理解。他想像老闆有過一個早夭的兒子,想像老闆感受到他身上某種同屬於殺人兇手後代的氣質,他們是同類。有一天,在必要的刺激下,老闆會替他報仇。
暑假來臨前,他偷走母親抽屜的積蓄,塞在鞋底帶到學校,挺過放學後的折磨,脫下鞋子,走向鮮肉餅老闆,將一疊鈔票往老闆桌上一丟,沒拾起鮮肉餅便朝開往校門口的公車一撞。
整個夏天,他都在醫院度過。來看他的同學慶幸他能從車禍中醒來,並告知他這個夏天實在可怕,在他車禍的隔天,原本坐在他前後左右的四個同學,在回家路上跨越平交道,集體被火車碾過,屍塊四散,有的散落數十公尺遠,至今仍無法拼湊出完整的軀體。
同學離開後,他告訴母親,想吃鮮肉餅,校門口那間的,剛出爐的,愈多愈好。
在身體逐漸康復的過程中,他有時會感覺到四位同學的存在,尤其當他獨自在病房浴室洗手抬上放滿水,彎腰低頭潑水洗臉,他便感到心慌,深怕後方會有一雙手將他的後腦杓壓入水面。幾次他在昏沉與恍惚間錯覺似地看見四個同學面無表情地站在他的病床邊,甚至感到四肢就此失去知覺,胸口沉悶無法呼吸。
最恐怖的不是惡夢,而是他想像四位同學的車禍慘狀,淋漓盡致的屍首散落各地,誰的頭與誰的手滾落軌道上而誰與誰的內臟混成肉泥,他撐著柺杖走到醫院走廊的公用電話,撥了一通電話到帶頭欺負他的同學家裡。
他想起小時候幫媽媽對發票,不過是對到一張四千塊的中獎發票,他跟媽媽往後幾天都不斷興奮地拿出那張發票重複對獎,此刻的他是同樣的心情,甚至更激動難耐,直到他在電話中說出同學的名字,問他在不在,然後竊笑著等待聽見同學家長的痛哭失聲。
「等一下喔,喂,有你的電話!」
他嚇得掛上電話,半响,又拿起話筒撥給另一個同學,電話一接通,另一頭一傳來他熟悉的聲音,他便掛上電話。在斜射的午後陽光下,他將上著石膏的手舉高,仔細察看上面所有同學的簽名,在他不容易看到的手肘外側,潦草但清楚地簽著霸凌他的四位同學的名字。
他哭倒在走廊上,隨即又為自己的軟弱感到氣餒,軟弱殺人犯的後代,果然只有軟弱的內心。在暑氣蒸騰的醫院裡,他翻閱報紙,確認意外死亡的四個同學與霸凌他的同學無關,他偷走一份放在護理站櫃臺上的病歷表,扯下幾頁,用盡全身之力努力控制酸動的手腕,大大寫下四個同學的名字,將這張紙折疊再折疊,收進口袋,假裝散步偷偷離開醫院。
他在校門口附近下車,一步一步往前,這次他要清楚指定四個同學的名字。
他回想老闆的臉,粗短的眉毛、薄唇、細窄的鼻梁、凹陷的兩頰,他不自覺皺眉、抿嘴,將老闆的面容複製到自己臉上。
夕陽將來往車輛的影子都長長地貼在校門口那條上坡路的地面,他吃力地撐著柺杖,看路面上的影子漸淡,而後路燈亮起。
他走到寫著「鮮肉餅」的招牌前。
招牌上多了一行小字:「即日起停止營業。」
眼前沒有老闆,也沒有四位同學的鬼影,他環顧四周,覺得耳邊有千萬輛火車疾駛而過。
晚風順著校門口的上坡路吹上來,溫暖潮濕,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超越過去他所承受的霸凌痛苦,他覺得自己應該要哭,但雙眼乾澀刺痛,他開始明白老闆與他之間,不過是他個人因過度寂寞而起的妄想,事實上沒有人會理解他,沒有人會同情他,被欺負到角落的他與這個世界之間只剩淡然隱約的薄弱聯繫,像微雨的湖面上的漣漪,早就已經一圈圈逐漸淡去。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