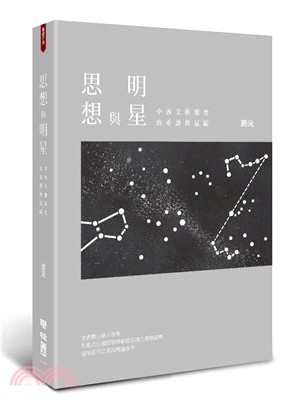商品簡介
標示華人學界對當代法國哲學與歐陸思潮之理解詮釋、
運用延伸之最高理論水平。
一個人必須在自身中懷有混沌,為了誕生一個跳舞的明星!
跳吧,麥可!在天河璀燦的酷炫
表面上,成為自己所創造的事件的兒子!
跳吧,思想!化身燦爛起舞的群星,畫出理念的星圖,照亮群眾運動的軌跡,召喚一個未來人民的影子!
思想需要明星,明星需要思想!思想是一種高度與深度;明星是一種形象與魅力。思想需要明星的形象與魅力來感動群眾,凝聚人心,明星需要思想的高度與深度來引領群眾,提升人性!思想與明星的結合才能推動一個真正精采健康的文藝盛世!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思想與明星的分離,知識分子與群眾的分離,文藝學術與娛樂消費的分離!群眾陷入「無思想狀態」,思想則自限於抽象蒼白的象牙塔!正如尼采的預言:看啊,這個時代正在來臨,當人不再產生任何明星。看啊,最令人蔑視者的時代正在來臨,注意!我將向你展示這最後一人。
本書之旨趣:在一個沒有思想也沒有明星的時代,讓思想與明星重新遭遇邂逅,勾畫不同的思想體系與明星形象如何遭遇碰撞,排列組合出新的思想形象與理念星圖:
羅蘭巴特的《明室》遇見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攝影的「刺點」逼顯出現代私密主體的「點狀自我」;傅柯的《性史I》遇見賈木許的《羅馬之夜》,「將性置於言說」的現代「性設置」庸俗化為當代八卦媒體的自我真理儀式;巴迪悟的愛情本體論遇見張愛玲與杜哈絲的〈愛〉以及王國維與蘇東坡的〈蝶戀花〉;麥可‧傑可森的月球漫步遇見路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夢遊仙境》以及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杜甫的兩句詩「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遇見康德的先驗時空形式以及現代「漫遊」文學;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作為一種「我們說」的「可能世界」遇見德勒茲的「他們說」的精神分裂之流;迦達瑪詮釋學的「時效性歷史意識」遇見董仲舒的今文經學,指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大視域融合。
作者簡介
路況
哲學家,詩人,文化評論家。巴黎第八大學美學及造型藝術博士。現任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作 : 《王子——從馬基維利「君王論」回到孔孟「王道」》,《德勒茲•巴洛克•全球化》,《冥王星民主——反太陽花小手冊》,《台灣當代藝術大系:社會•世俗篇》,《五月之磚——巴黎學派68思想》,《鼠儒主義》,《犬儒圖》,《虛無主義書簡》,《後╱現代及其不滿》。翻譯 :《藝術與哲學》。計畫撰寫:《王子Ⅲ 軸心——中國的崛起與第三軸心時代的來臨》,《王子Ⅱ3P——卷一 People/Prince/Power之政治本體論與權力拓璞學╱卷二 「五才」形上學: 天、地、人、鬼、神》,《美學經濟學批判大綱及美學產業現象學》,《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形上學小手冊》。
序
序:思想需要明星,明星需要思想
在什麼地方可以遇見那麼多璀璨的明星,看到那麼多目眩神馳,精采絕倫的事件與奇觀?唯有在無限開展的思想平面上,在穿梭時空的思想光速中,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遇見眾星雲集的銀河盛宴!李商隱〈碧城〉詩云:「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思想是一種不設限的運動,一個猝不及防的事件,一場不可能的遭遇邂逅!有什麼比不可能的遭遇邂逅更令人興奮莫名,幸福無比!《詩經》唐風〈綢缪〉: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簡直幸福到不知道該怎麼辦!思想的遭遇是一場不可能的激情邂逅。沒有激情的思想是抽象無力的,沒有思想的激情是盲目空轉的,思想必須成為一場不可能的激情邂逅,激情也必須成為一場猝不及防的思想遭遇!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這個邂逅就叫做思想;今夕何夕,見此粲者!這個粲者就叫做明星!生命就是一連串純屬偶然的「今夕何夕」,等待思想與明星的璀璨邂逅!
將近一個世紀之前,民初文人夏丏尊《平屋雜文》的〈阮玲玉的死〉一文寫道:「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眾轟動,主要原因就在大眾對她有認識,有好感,換句話說,她十年來體會大眾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是曾能滿足大眾要求的。」「不論音樂繪畫文學或是什麼,凡是真正的藝術,照理說都該以大眾為對象,努力和大眾發生交涉的。藝術家的任務就在於用了他的天分體會大眾的心,用了他的技巧滿足大眾的要求。好的藝術家,必和大眾接近,同時為大眾所認識所愛戴。」「他們一向不忘記大眾,一切作為都把大眾放在心目中,所以大眾也不忘記他們,把他們放在心目中。這情形不但藝術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業上,學問上都一樣。凡是心目中沒有大眾的,任憑他議論怎樣巧,地位怎樣高,聲勢怎樣盛,大眾也不會把他放在心目中。」「中國自古有過許多傑出的文人,現在也有不少好的文人,可是大眾之中認識他們,愛戴他們的有多少呢?中國文人死的時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眾轟動的,過去固然不曾有過,最近的將來也決不會有吧。這可是使我們作文人的愧殺的。」
一個世紀之後,敢問今日的台灣文人: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古流!難道不更感到「愧殺」?
夏丏尊在大眾媒體還只初露端倪的民國時代,就已跳出傳統文人的視野格局,預見了當代社會的明星現象與媒體奇觀,並且直接戳破傳統文人的「自我感覺良好」:文人如果心中沒有大眾,無法感動大眾,拿什麼去跟一個電影明星比!真乃先知灼見。更不同凡響的是,夏丏尊平實近人的筆調竟然呼應了尼采的超人思想,《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寫道:
偉大的明星啊!什麼將是你的快樂,如果沒有那些為你所照耀的人們?
除了一點:其實中國古代文人也產生過不少超級巨星:從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直到屈原,陶淵明,杜甫,蘇東坡,皆是照耀一代代人民大眾的文星北斗!
思想需要明星,明星需要思想!思想是一種高度,一種深度;明星是一種形象,一種魅力。思想需要明星的形象與魅力來感動群眾,凝聚人心,明星需要思想的高度與深度來引領群眾,提升人心!思想呼喚明星,明星呼喚思想!
怎樣才能成就一個黃金時代,文藝盛世?就是思想化身為明星的形象與魅力,明星也發射出思想的光芒與文采!借用德勒茲的講法,這是一個「思想變成明星,明星變成思想」(thought-becoming-star, star-becoming-thought)的雙重變化過程!這就叫「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思想與理念必須化身為明星的形象與魅力,才足以感動號召人心,為茫茫大塊的群眾照亮時代的大方向。披頭四走紅時,約翰藍儂說:「我們比耶穌更受歡迎!」耶穌必須成為流行巨星,流行巨星也必須成為思想的啟蒙者!「啟蒙運動」就是「思想變成明星,明星變成思想」所啟發照亮的群眾運動,畫出理念的星圖,召喚未來人民的影子。
思想與明星的結合才能推動一個真正精采健康的文藝盛世,黃金時代!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思想與明星的分離,知識分子與群眾的分離,文藝學術與娛樂消費的分離!群眾陷入「無思想狀態」,思想則自限於抽象蒼白的象牙塔狀態!這正是台灣目前的文化學術狀態:一種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感覺,更沒有激情,極度乏善可陳的無趣沉悶狀態!為什麼呢?因為沒有明星,沒有魅力!所以不再有遭遇,不再有事件,不再有運動!
思想的問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文化的問題則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因為政治是眾人之事,人民之事,思想與文化也應該是眾人之事,人民之事。在這意義下,一個文人或藝術家和一個政治人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要為人民謀福利,說出人民的心聲,都要盡最大努力去感動人民,提升人民!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滿口人民福利與社會正義,實則假公濟私,公器私用,會被人民唾棄為「政客」,那麼,當今台灣文人最擅於凝視撫摸自己的肚臍眼,發而為張愛玲所說的「肚臍眼文學」佔據媒體版面,此一假借媒體公器公然自看自摸,自戀自溺的自慰之姿,難道不是比政客更等而下之的「公器私用」!
( 麥克魯漢說:「媒介是人的延伸。」每種媒介都是人體某一器官的延伸。所以以肚臍眼為中心,可以延伸放射出各種私密的器官書寫,身體書寫,疾病書寫,情慾書寫,飲食書寫,寵物書寫,收藏書寫,電玩書寫…,族繁不及備載,但萬變不離其宗,最後都要指回那既私密又可公然暴露的肚臍眼。偉哉肚臍!一統台灣當代的所有書寫系譜!)
正如尼采所預言的:
看啊,這個時代正在來臨,當人不再產生任何明星。看啊,最令人蔑視者的時代正在來臨,注意!我將向你展示這最後一人。
這最令人蔑視的最後一人的時代就是一個沒有思想,也沒有明星的時代!
真正的思想產生於遭遇邂逅一個明星,所以真正的明星都是思想的明星,文化的偶像,同時啟發與塑造群眾的思想與激情!而遭遇邂逅是純屬偶然的機遇碰撞,偶然機遇之總和就叫做「混沌」(chaos)。
尼采寫道:我告訴你:一個人必須在自身中懷有混沌,為了誕生一個跳舞的明星。我告訴你:你必須在你自身中懷有混沌。
為什麼從混沌中可以誕生一個跳舞的明星?馬拉梅詩云:「所有的思想都是骰子一擲。」思想作為骰子一擲,就是純粹偶然機遇之排列組合。偶然機遇是混沌的星雲,但思想的骰子一擲所呈現之點數必然構成一個排列組合的星座與星圖(constellation),這個星座就是跳舞的群星!思想就是從混沌星雲中躍出的跳舞群星,是群星之舞排列組合而成的星圖,這個星圖叫做「理念」!
思想不只是要去遭遇邂逅跳舞的明星,更要讓那許多不可能遭遇邂逅的明星遭遇邂逅,燦爛起舞!每個明星都已然是一個星座與星圖,思想的遭遇就是讓不同星座遭遇碰撞,燦爛起舞,重新排列組合,連結布局,畫出新的星座與星圖!
所以,本書之旨趣就是思想與明星的重新連結:在一個沒有思想也沒有明星的時代,面對一個沒有遭遇,沒有事件,沒有運動,乏味無趣之至的學術文化狀況,試圖讓思想與明星重新遭遇邂逅,勾畫不同的思想體系與明星形象如何遭遇碰撞,排列組合出新的思想形象與理念星圖:
羅蘭巴特的《明室》遇見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春光乍洩》,攝影的「刺點」逼顯出現代私密主體的「點狀自我」;傅柯的《性史I》遇見賈木許的電影《羅馬之夜》,「將性置於言說」的現代「性設置」庸俗化為當代八卦媒體的自我真理儀式;巴迪悟的愛情本體論遇見張愛玲與杜哈絲的〈愛〉以及王國維與蘇東坡的〈蝶戀花〉;波特萊爾的「時尚現代性」遇見韓波、馬拉梅、賀德林、克利的「詩意現代性」;麥可‧傑可森的月球漫步遇見路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夢遊仙境》以及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德勒茲的美學方法遇見司馬中原的「江北荒原」以及黃春明的「蘭陽平原」;杜甫的兩句詩「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遇見康德的先驗時空形式以及現代「漫遊」文學;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作為一種「我們說」的「可能世界」遇見德勒茲的「他們說」的精神分裂之流;迦達瑪詮釋學的「時效性歷史意識」遇見董仲舒的今文經學,指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大視域融合。
偶然看到一句運動球鞋的廣告詞:Nothing is impossible.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沒有什麼思想體系與明星形象不可能遭遇邂逅,交會融合!
一個人必須在自身中懷有混沌,為了誕生一個跳舞的明星!
跳吧,麥可!在天河璀燦的酷炫表面上,成為自己所創造的事件的兒子!
跳吧,思想!化身燦爛起舞的群星,畫出理念的星圖,照亮群眾運動的軌
跡,召喚一個未來人民的影子!
目次
目次
卷首題詩:最快的人
序:思想需要明星,明星需要思想
卷一 現代私密主體系譜學
第一章 從羅蘭巴特《明室》的「現代私密主體」看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
第二章 從傅柯的「性設置」論現代私密主體系譜學與當代的「性話語生產」
附錄1 我是一個有錢有品味的人-從米克‧傑格的〈同情惡魔〉看金融海嘯
附錄2 二十一世紀的推銷員之死-從鮑伯·狄倫的〈像一顆滾石〉看美國債信危機
卷二 愛情、時尚、詩意的現代性
第三章 運動、遭遇、宣言—巴迪悟的愛情本體論與現代性三法則
附錄:懷人——代擬臉書戀歌一首
第四章 從波特萊爾的「時尚現代性」走向現代藝術的四種「詩意現代性」
第五章 「表面」的昇華與崩潰—麥可‧傑可森作為一個「愛麗絲童話事件」
附錄1 黃色小鴨:「玩這麼大」的兒童鏡像
附錄2 圓仔與黃小鴨的「可愛現象學」
附錄3 冰桶名人效應的「上流美」奇觀與「誇富宴」人類學
卷三 溝通與詮釋的兩個模型
第六章 「溝通」理論的兩個模型--從哈伯瑪斯的理性「對話」到德勒茲的「自由間接表述」之精神分裂
附錄1 從「書寫」的「語用學」看「文言文」的重要性
附錄2 菜英文現象:從「翻譯」到「格義」
附錄3 查理事件是語言暴力, 不是言論自由
第七章 歷史,道統,平台--從「時效性歷史意識」看今古文經學之爭
附錄1 「全球化」作為「視域融合」的「詮釋學經驗」
附錄2 台灣人文學術的「I級/埃及化」--從國科會到科技部
卷四 漫遊,疆域,星座
第八章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從兩句杜詩論康德時空觀與現代「漫遊」文學
附錄:可能世界的戲劇性—分析一首自己的詩〈空門〉
第九章 小說作為一種「美學方法」:「感覺體」的「組構」與「疆域性」的「表現」——司馬中原與黃春明的鄉土小說
附錄:兒童相識盡,宇宙此生浮——紀念段彩華
第十章 左翼男性主體之重振雄風--趙剛《橙紅的早星》的「星座」方法學
附錄1 阮玲玉與卡夫卡
附錄2 二十一世紀是文化革命的世紀
卷五 宗師,奇觀,體制
第十一章 王家衛為何無法成為一代宗師?
第十二章 野月滿庭隅-試論陳庭詩抽象藝術的時代文化意義
附錄1 「客形」的回返-走向「後抽象/後觀念」的繪畫本體論
附錄2 星沈海底當窗見-西方「繪畫性」在東海的軌跡與系譜
第十三章 當代藝術作為一種「奇觀」或「體制」?
附錄 威尼斯參展名單荒謬事件簿--台灣策展人機制的「官僚化」與「買辦化」
卷六 「軸心」之「興」
第十四章 走向「興」的詩學本體論--從陳世驤的〈原興〉與德勒茲的「差異 哲學」
附錄1 世界盃啟示錄
附錄2 北韓存在的正面啟示
第十五章 儒學文藝復興與第三軸心時代的來臨
附錄1 盧梭是哪國人?
附錄2 虯髯客精神與大亞洲理念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從羅蘭巴特《明室》的「現代私密主體」看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
巴特的《明室》提出了一套「攝影現象學」,同時勾畫出某種「現代私密主體」的系譜學。此私密主體是照片中某個偶然「刺點」穿透文化符碼之「知面」所喚起的「強度的點狀自我」,而逼顯出社會所無法面對處理的「瘋狂真理」。
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春光乍洩》亦觸及到「刺點」的問題。《明室》與《春光乍洩》的相互對照,見證了攝影的「瘋狂」與「睿智」。
壹、導言
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的名片《Blow up》(1966),中譯《春光乍洩》,透過一名英國時尚攝影師的觀點來批判西方消費社會的影像文化,已成新浪潮電影的經典之作。故事背景在二十世紀六○年代的倫敦,安東尼奧尼雖是義大利人,卻充分捕捉了倫敦當時特有的前衛普普風、搖滾樂與青少年叛逆文化的時代氛圍。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明室》(La Chambre Claire, 1980)是生前所出版的最後一本書,已成當代攝影理論不可略過的經典之作。但《明室》對攝影的探索,其實已延伸涵蓋到整個現代社會之影像文化的普遍批判省思。
而我們發現,《明室》更深刻的文化內涵,則是巴特透過對攝影影像的「現象學」描述,卻同時揭露反顯出某種「私人」與「內在」的現代主體形象。〔關於「現代私密主體」之界定,我們將根據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的《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Sources of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1989)一書之主要論點「西方現代人之同一性(identity)之形成是一個內在化過程」,做進一步之釐清,詳見本論文「肆、現代私密主體的點狀自我」〕。
巴特之創見在於將此「現代私密主體」關連到十九世紀攝影發明時,西方社會所面臨的死亡儀式的式微沒落,並迴溯此「現代私密主體」之起源直至中世紀末期的私人祈禱儀式。可以說,巴特的「攝影現象學」同時蘊含著一套獨樹一格的「現代私密主體」的文化系譜學。
我們更發現,透過《明室》之「現代私密主體」的觀點來看《春光乍洩》,實有相映成趣,相互印證之妙。在此,我們並不是要借助或引用巴特的「攝影理論」來談論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作品」,因為巴特的《明室》不只是一部理論著作,更充滿散文隨筆與自傳寫作的文學風格,其「創作性」並不亞於其「理論性」。反之,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雖是劇情片,卻充滿新浪潮電影反思批判影像機制自身的典型「後設」意味,其「理論性」亦並不亞於「創作性」。所以我們並不是透過一套「攝影理論」來談論一部「電影作品」,而是讓《明室》與《春光乍洩》這兩套關於「攝影╱影像」的「理論╱創作」體系在相互對照印證之中,達到更深刻的相互理解與相互啟發。
《春光乍洩》最後一幕著名的寓言場景:攝影師觀看一群波希米亞的無稽年輕人以默劇式肢體動作模擬打網球,而若有所悟。《明室》最後一節指出現代社會如何馴化「攝影的瘋狂」的兩種方式,而對整個影像消費文化提出最激進澈底的省思批判。我們將看到,透過《春光乍洩》最後一幕與《明室》最後一節的相互對照印證,更能澄清照明安東尼奧尼與巴特的核心思想之曲折、深刻、微妙。
貳、現象學反符號學
眾所周知,巴特嘗以符號學(sémiologie)方法之文本分析,而聞名於法國學界與西方思壇。但在《明室》中,為了探索攝影經驗之特殊本質,巴特的研究進路採取了明顯的「方法學轉向」:從符號學轉向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甚至於有反符號學之意味。關於巴特此一「方法學轉向」,先提出幾點基本說明:
一、 攝影之本質就是一種與「指涉對象」(référent)不可分離的影像,符號學則是一門只研究符號系統之「符碼」,而可以完全不涉及「指涉對象」的科學。所以符號學無法觸及攝影之本質。
二、 巴特採取胡賽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現象學對於「意向性」活動(intentionnalité)之「能思╱所思」(noèse/noème)結構之分析來理解掌握攝影之「指涉對象」在吾人經驗中所呈現之本質性意義。
三、 巴特並進一步採取與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早期著作《論想像》(L’Imginaire)關於想像力與意象(image)之現象學分析相類似的風格來描述分析攝影影像之本質,所以《明室》的卷首題詞是「向沙特的《論想像》致敬」(En hommage à L’Imginaire de Sartre)。
四、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方法學轉向」,同時蘊含了從「知面」(Studium)到「刺點」(Punctum)這兩種攝影本體論元素之重新置定。符號學只能處理攝影之「知面」,現象學才觸及攝影之「刺點」。唯有「刺點」才逼顯出攝影不可言說之本質與真理。而我們將看到,關於攝影之真理的「不可言說性」,巴特不只是訴諸現象學,還更進一步訴諸精神分析。
以下試詳論之。
符號學,從它的創立者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開始,就是專事探討符號之「能指」(signifiant)與「所指」(signifié)之「指意關係」(signification)的一門科學。決定「指意關係」之規則,稱為符碼(code)。符號之意義完全由符碼所決定,可以和指涉對象完全無關。換言之,符號學是一門只研究符號系統之「符碼」,而不涉及「指涉對象」的科學。
而《明室》一開使就界定攝影是一種與其「指涉對象」不可分離的影像。在所有的影像與藝術形式當中,這是獨一無二的。
結果,如此這般的一張照片從來都無法與其指涉對象相區別(與其所再現之對象)……據說照片總是隨身攜帶著它的指涉對象,二者遭受同樣致命不動的一擊,無論這是戀愛的或悲痛的一擊,在運動著的世界之核心:他們彼此黏貼,肢體交纏……好像被永恆的交媾結成一體。
攝影之指向指涉對象,有如窗玻璃之指向風景,欲望之指向對象。
此一對指涉對象的執抝固著(entetement)構成了攝影的本質。可以有一套攝影的符號學,研究各種類型攝影之符碼,但它觸及不到攝影最核心的本質:指涉對象。攝影之指向指涉對象,是一個最原始簡單的事實,如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用手指指著某物說這個、那個!
一張照片總是位於此手勢所指之處,它說: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樣!沒有別的意思;一張照片無法被哲學地轉化說明,它被填滿偶然性,它只是包圍此偶然性之透明與輕盈的封套。
要掌握攝影此一最原始簡單的指涉動作,巴特訴諸胡賽爾的現象學關於「意向性」結構的描述分析。現象學方法就是透過對意識經驗之描述來理解事物或對象之本質。吾人之意識經驗顯示為「意識總是意識到某物」的「意向性」活動,由此導出「意向性」活動的雙重結構:「意向性」所意識到的「某物」,所指向的對象,胡賽爾稱之為「所思」(noème),「意向性」活動本身則稱之為「能思」(noèse)。可以這麼說,巴特以胡賽爾現象學之「能思╱所思」的「意向性」結構取代索緒爾符號學之「能指╱所指」的「指意」結構,來探索攝影經驗之本質。
然則,相對於胡賽爾將現象學視為奠立所有科學之堅實基礎的「嚴格科學」,巴特承認自己採用的毋寧是一種寬鬆的(vague)、瀟灑不拘的(desinvolte),有點出格的現象學。這是將現象學當成一種廣義的思考模式與思想風格,而巴特的法蘭西文采更使現象學方法從胡賽爾的「嚴格科學」成為一種交織著哲理思辨與抒情體驗的「書寫風格」(style de l’écriture)。
為什麼要以現象學反符號學?因為攝影之本質就在於每張照片總是指向某個實際存在的指涉對象,這個指涉對象是一種拒絕符碼,超越符碼的狀態。借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與瓜達利(Félix Guattari, 1930-1992)的術語,巴特在《明室》中所做的,無非是對攝影的「去符碼化」(décodage),將攝影從「符碼化」的狀態釋放出來,逼顯出攝影拒絕被符碼化的核心本質。
參、「知面」與「刺點」
所以,符號學與現象學作為兩種方法學,兩種觀看照片的「認知方式」,同時也界定了攝影的兩種「存在方式」,巴特由此推演出一套二元對立元素的「攝影存有學」,巴特以拉丁文的兩個詞來命名這兩個對立元素:「知面」(Studium)與「刺點」〔Punctum(按照許綺玲之中譯)〕。「知面」(對應於符號學方法)是照片中可解讀的各種知識、文化、社會成規;以「知面」的觀點看照片,便是將照片符碼化,套入社會或文化的公式。相對的,「刺點」則是照片中拒絕符碼化,無法符碼化的某個偶然細節,有如處於知識、文化、社會之外的不可規範者。
「知面」與「刺點」雖彼此對立,但又可並存共現於同一照片中(co-présence des deux éléments)。「知面」是一種廣度量的延伸(studium-étendue),「刺點」則是干擾、穿透「知面」的瞬間的強烈一擊(punctum-point):
刺點將擾亂知面,它是此一偶然,指向我刺穿我,給我致命一擊。
我們發現,巴特思考「知面╱刺點」訴諸這樣一種「面的延伸╱點的穿透」的二元圖像,其實借用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與德勒茲的「廣度╱強度」(extension/intensité)二元論。而二氏之「強度╱廣度」二元圖像則是延伸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心 ╱物」二元論之「思維╱廣延」(pensée/étendue)二元圖像。廣度是外在的,空間的,物質的;強度是內在的,時間的,精神的。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指出:「能量學以兩種要素的組合來界定能量:強度與廣度。經驗顯示,強度不可分離於某一廣度,此廣度將之關連於某一外延〔廣延體(étendue)〕」。
綜合言之,巴特的「刺點╱知面」二元圖像延續了笛卡爾「思維╱廣延」二元圖像,同時亦吸納融入了柏格森與德勒茲更為形象鮮明的「強度╱廣度」二元圖像。職是之故,笛卡爾「心 ╱物」二元論所蘊含的「現代世界觀」之基本架構:「主體 ╱客體」、「內在╱外在」、「自我╱世界」,皆延伸納入現代人的攝影經驗領域,並將之「存在主義化」,「強度/廣度」乃轉化成現代人面對攝影的存在體驗。
所以巴特借用英文中的love與like來說明「刺點╱知面」之「強度╱廣度」的差別。「知面」作為一種「廣度」,就是社會一般人所認可的「廣泛的興趣喜好」,它是一種like,卻往往是不痛不癢、無所謂、不起勁(nonchalant, indifférent)的欲望。「刺點」則是一種「強度」穿透的love,雖然只是一個偶然意外的細節,沒什麼理由,卻可以刺醒我,穿透我,干擾我,有如一道傷口。「刺點」之「強度」,就如中文常講的「錐心泣血」、「刻骨銘心」。
「刺點」究竟是什麼?就是某個偶然細節喚起我們意識到照片中的對象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事實。所以巴特的攝影現象學所逼顯的「所思」就是「此曾在」(ça-a-été):照片中的這個對象曾經存在過。攝影的指涉對象隱含兩層意義:它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它已成過去。它存在於過去時空的某一點。
《明室》的卷首題詞:「向沙特的《論想像》致敬」(En hommage à L’Imginaire de Sartre),並非無謂的客套虛語。沙特在這本早期著作中對吾人「想像」意識呈現之意象(image)所做的現象學描述:「意象包圍著某種確定的虛無。一個意象即使如此生動、感人、強烈,……它給予它的對象如同缺席不在。」預示了巴特以「此曾在」來界定攝影的「所思」。更耐人尋味的是,沙特論「記憶」時所舉的例子:「在罕見的例子中,一個記憶意象維持著無名性:突然間,我重見到一座憂傷的花園在灰色的天空下,我不可能知道在何時何地我曾看過這花園。」而巴特在母親去世後不久,翻閱母親舊照,發現母親五歲時在某個冬季花園與她哥哥的一張合照。巴特看到「某些事物如同攝影之本質,浮動在這張個別照片中」,這張平凡的冬季花園照乃成為巴特探索影像迷宮的阿麗安(Ariane)之線。沙特的「灰色天空下的無名花園」的記憶意象與巴特的「母親童年的冬季花園照」,也許就是這兩個例子純屬巧合的奇異呼應共鳴,使得《明室》的卷首題詞要向沙特致敬。
那麼,什麼是攝影的「能思」?巴特並未直接回答,但很明顯的,對巴特而言,攝影的「能思」絕非不痛不癢、冷漠無謂的意識狀態,而是愛,欲望,情感。為什麼「此曾在」會成為攝影的核心本質,因為照片中的這個對象是我所愛,我所欲望的對象。他曾經存在過,同時也已成過去,所以攝影的「能思」是愛,欲望,情感,同時也是一種「痛失所愛」,無可排遣的哀傷,悲痛,憂鬱。所以「此曾在」的簡單事實會成為「無法處理」「無法面對」者(l’Intraitable),如同精神分析之創傷場景或死亡原理。巴特的攝影現象學乃指向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與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精神分析式之「不可思議」與「無法言詮」的極端弔詭。
但一切弔詭都開始於平常的生活經驗。現象學的運作方式,就是暫時懸置一切既有的成見與理論預設,回到最基本的生活經驗,讓對象在吾人意識中顯現出最本然的意義。例如,什麼是「死亡」?讓我們暫且懸置科學或宗教上關於死亡的界定,提出一生活世界的「死亡現象學」。在日常經驗中,當我們說某某人「死了」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這個人「不在」(absent)了,再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永遠「消失」、「缺席」了。所以當某個熟人老友很久不見,又突然出現,我們常打趣道:「你死到哪去了!」一個嬰兒看到母親離去,從自己的視野中消失,會號啕大哭,因為他以為母親已經死了。這個嬰兒其實是一個現象學家,體驗到「死亡」即「消失」、「不在」的本質性意義。
巴特的攝影現象學也始於懸置攝影師的專業經驗與各種攝影理論的預設觀點,回歸到一般人的看照片經驗與被拍照經驗,所以巴特寫道:「一般而言,票友(l’amateur)被界定為藝術家的不成熟狀態:某些人不能也不願自我提升到專業的掌控。但在攝影實踐的領域,票友反而是專業的昇華,因為票友更接近攝影之本質」。
從這票友式的看照片經驗與被拍照經驗,巴特卻導出了一套極端弔詭的「死亡現象學」,甚至「幽靈現象學」:作為被拍照者,「我感覺攝影創造了我的身體,或將之死體化(le mortifie)」「既非主體,亦非客體,而是一個感覺自己變成客體的主體:我經歷一種死亡的微觀經驗(micro-experience de la mort),我變成幽靈魅影」。
攝影作為一個死去對象的生動影像(image vivante d’une chose morte),不是使之栩栩如生(faire vivant),而是使之不動如死者、屍體:「攝影是不動影像,因為它們出不了框,它們被麻醉、釘死,像蝴蝶標本。」
所以,「死亡是此一照片之本質」(l’eidos),一個對象已消失不在,它的影像卻留存下來,這不就是古代人所認為的鬼魂、幽靈?攝影是扮演死者回返的死亡儀式與奇觀。所有的照片都是死者的遺照,都是死而復返的魅影幢幢。
巴特有另一個講法比較不那麼陰鬱:「攝影在實質上是指涉對象的流出物(émanation du référent)。從一個曾存在於彼處的真實物體,其幅射的光線觸及在這裡的我;傳遞時間的長短並不重要,那已消失對象的照片觸及到我,就如一顆星發出的光延遲到達」。
但無論是比擬為天上的星光還是死者的幽靈魅影,「此曾在」是攝影無可駁斥的「實在」(réalité, reality)。面對此一「實在」,吾人不能多贊一詞。而這就是攝影的「真理」(vérité, truth):就是這樣(c’est-ça),就是如此(c’est tel),無話可說,沒什麼好說的(rien à dire)。
整部《明室》就是在訴說這無話可說的「真理」。巴特認為,攝影之「天才」就是將「實在」與「真理」混同疊合為一。怎麼說呢?最簡單的理解是,「實在」是指實際存在之事實狀況,「真理」則是對事實狀況的理解或詮釋。例如,自然現象是一種「實在」,牛頓的運動定律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則是理解詮釋自然現象的某種「真理」。那麼,一般的科學與藝術所追求的「真理」都不只是對「實在」的直接呈現。唯有攝影,它對「實在」的直接呈現就是它的「真理」!它告訴吾人:此曾在!就是這樣!不容吾人多贊一詞。
巴特從一張死刑犯的照片解讀出「此曾在」的弔詭時態:他將要死去,他已經死去!這就是刺點!每一張照片都是預知死亡紀事:「不管照片中的主體是否已死去,所有的攝影都是此一死劫終局(catastrophe)」。這是一種時間的壓碎覆滅(un écrasment du Temps),這已經死了,這將要死去!攝影的「此曾在」的時光隧道是沒有出口,沒有未來的。每一張照片都是「沒有明天」。這就是攝影的「憂鬱」。被帶入此一沒有未來,沒有出口的時間迴路中的看照片的人,只能是一個絕對憂鬱的主體,連哀悼都不可能。因為哀悼是一種「工作」(travail du deuil),一種「辯證法」式的勞動,透過種種紀念與儀式,將痛失所愛的哀傷予以轉化超越,揚棄昇華,就如一般人常講的「節哀順變」,「化悲痛為力量」。
攝影的真理「就是這樣!」則拒絕任何辯證法的轉化超越。死了就是死了,就是這樣,沒什麼好說的!也沒什麼好做的(rien à faire)!此一「非辯證」的真理逼顯出一種陷入絕對憂鬱的主體,絕對的無能與無言!
巴特指出攝影作為一個新的人類學對象,應關聯到十九世紀下半開始的「死亡的危機」,這意味著:在一個宗教與儀式式微消退的現代社會,死亡失去了原有的象徵意義與位置,變成一種非象徵性的平板死亡(la mort plate),一種無深度的字面意義的死亡(Mort littérale):死了就是死了!沒什麼好說的!簡言之,這是死亡的「去符碼化」,死亡失去了社會與文化的定位,變成一個平板的事實。而攝影正是一種沒有符碼,沒有深意的扁平影像:「我必須承認此法則:我無法深化、穿透照片。我只能掃視它如一平展的表面。照片是扁平的(plate),就扁平一詞的所有意義」。
巴特對攝影的定義,乍看如素樸的寫實主義:「寫實主義者,我是其中之一,我總已是,一旦我肯定攝影是一種沒有符碼的影像。」但此素樸的寫實主義卻可導出盧梭式(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反社會,反文化的極端結論:「我是一個野蠻人,一個兒童,或一個狂噪症患者;我攆走所有的知識,所有的文化」。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