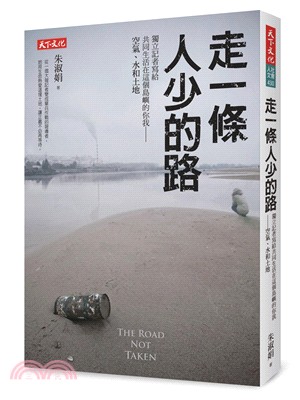走一條人少的路:獨立記者寫給共同生活在這個島嶼的你我-空氣、水和土地
商品資訊
系列名:社會人文
ISBN13:9789869310390
替代書名:The Road Not Taken
出版社:天下文化
作者:朱淑娟
出版日:2016/05/27
裝訂/頁數:平裝/256頁
規格:21cm*14.8cm*2.1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610【九年級】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2009年,一個大報記者在媒體業不景氣的縮編計畫裡,
她被迫離開「機構記者」工作;
2010年,她以「獨立記者」之姿,一口氣拿下三座具份量的
「卓越新聞獎」與「曾虛白新聞獎」。
她,是獨立記者朱淑娟。
十七年來,朱淑娟的獨立報導之路見證了公民社會的覺醒,
走過「十年大旱」、「要命的空氣」,我們不能只看重經濟發展思維,
而忽略了環境永續與生存正義。
讀她的報導,縱使在最陰暗的角落,
都有著一群無私無我、為正義付出行動的人──隱姓埋名或無懼曝光──
一同參與為台灣未來而奮鬥的熱情。
朱淑娟讓環境議題不再是冷冰冰的數字與抗爭,她筆下有官員、學者、農民、環團……,
是一群與你我共同生活在島嶼的手足──這當中沒有旁觀者。
「沒有你的支持,我不可能來到這裡。我要向你致上一百萬個謝謝。」她說。
「然後遙望遠方微弱的亮光,繼續前行。」
作者簡介
朱淑娟/著
記者生涯十七年,前十年在《聯合報》,後七年做獨立記者,成立「環境報導」(greennews.tw),致力於環境新聞深度報導,並為國內多家重要媒體撰稿。
2010年以中科三期、中科四期、南部水資源(與公視合作)報導獲得三座「卓越新聞獎,2015年再以「大旱望雨」報導獲得第四座卓新獎。期許自己以報導做為社會參與的方法,搭起溝通橋樑、促進社會進步。
記者生涯十七年,前十年在《聯合報》,後七年做獨立記者,成立「環境報導」(greennews.tw),致力於環境新聞深度報導,並為國內多家重要媒體撰稿。
2010年以中科三期、中科四期、南部水資源(與公視合作)報導獲得三座「卓越新聞獎,2015年再以「大旱望雨」報導獲得第四座卓新獎。期許自己以報導做為社會參與的方法,搭起溝通橋樑、促進社會進步。
序
穹頂之下,廢水之邊/一個不從屬於任何機構的記者
夏珍
「假如沒有對人的真正的關切,就不能成為記者;假如僅僅停留在對人的關切,而不是對問題的求解上,就不會成為一個好記者。」──柴靜
我不認識柴靜,但早在她的作品《看見》繁體版在台灣出版前,我就讀了這本書的簡體版。當台灣的女主播們動輒犯上「進行一個動作」的「語詞錯誤」,而備受譏嘲時,我非常好奇這個以調查新聞聞名的「小女生」,為什麼能用這麼漂亮的文字書寫她的工作?最重要的,她的文字有疑問、有思考,即便未必有答案,但她對群眾問題的感情完全到位,這讓她的報導不必渲染就有十足的感染力。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前三十年你們拚命毀文化,後三十年你們拚命毀物質。夜以繼日地挖取地下資源賤賣掉,強拆地面的民房,汙染河流空氣,用高稅賦和低工資榨乾百姓,我們的子孫沒有了生存資源。你們的子孫移民走了。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這麼恨這個國家,毀之唯恐不及。」可想而知,在中國調查環保議題、處理礦區驚人的空氣與水汙染,而能講出這段話,是多麼不容易。直到去年(二○一五年),柴靜製作一部紀錄片《穹頂之下》,創造瞬間破億的點擊之後,她也立刻成為大陸封殺的「獨立記者」。
很奇特,每次觀看《穹頂之下》,看到站在螢幕前的柴靜,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朱淑娟。
台灣比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快了三十年,我們也曾經歷只要經濟發展不知環保為何物的年代,做為「環保記者」,朱淑娟當然不是第一代。早在政治開放前後,台灣環保新聞即蓬勃如火,五輕抗爭得以關廠,到六輕抗爭得到回饋,彷彿是一種預示。在民主社會走在環保抗爭的前沿,報導沒有政治壓力,卻難免業務干擾;沒有生命安危,卻難免精神耗弱,因為所有的問題都不可能一時半刻得到解決。人,就在歲月流轉中,老了,或累了。
七年,淑娟就成為圈內知名的「獨立記者」,獲獎無數。如果她還在新聞機構之中,或許並不特殊,她的特殊就在於她的「獨立」──不從屬於任何新聞機構。機構之於記者,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後靠」,你知道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支撐你的信念,支持你的工作,至少和新聞對象吵架的時候,還有人可以幫腔;但是,七年來,朱淑娟離開《聯合報》,憑藉的只有她自己的一枝筆(鍵盤),柴靜被大陸同行譽為「環保先行者」,淑娟應該是「新媒先行者」。在主流媒體還在嘗試網媒的時候,她自己就架起了網站,開始「一人工坊」──而且,沒有固定收入。最近幾年才流行所謂的「自媒體」,而她早就不再是「部落客」,而是專業的「自媒體」。
這幾年媒體生態無限惡化,許多媒體老人糾結於去留之間(包括我自己),淑娟義無反顧,走了就走了,奇特的是,太陽升起時,她照樣跑新聞!而且,一跑七年,如此專注不嘩眾,絕不跟著熱鬧走。對每一篇稿子,她都慎而重之,一再查核,總在現場,不論現場有沒有其他記者在,她鎖定議題就窮追到底,中科三、四期的前因後果,大概沒人比她更清楚。看到她寫前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拍著她肩膀問,「你為什麼老跟我做對?」我笑了,這就是淑娟,這就是「記者」。
記者,是一個特殊的行當,擁有比一般人多一點「接近真相」的權力或詛咒。說「詛咒」,因為真相就像是巨大的黑洞,一旦接近就無可避免地被吸引,無從逃避的一再探底,深,還要挖更深。從這個角度看,此刻眼下的多數射後不理的追風同業,到底稱不稱得上「記者」是有問題的,但我們多數人(同樣包括我自己),可能都失去了探底的好奇心或勇氣。我們常告訴自己「莫忘初衷」,卻不太回望、反省自己的初衷到底是什麼?
「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還記得自己為什麼出發嗎?其實,絕大多數人踏入這行的時候,沒什麼天大的信念和原因,或為工作故只得賣力做,但只要祖師爺真要賞你這口飯吃,總會碰到一個時刻,如靈光一閃,剎時就懂了:就是為了這個!一路能走下去,「這個」肯定不是名與利,掌聲或獎金。柴靜製作《穹頂之下》還有個起心動念,是為了她先天有缺陷的女兒;早在柴靜之前,朱淑娟已經呼喊PM2.5不知多少年了,新聞獎或許可能是她馬拉松式的「跑新聞」過程中,為她打氣的一瓶水,卻不是關鍵動力。
在媒體崩壞的年代,淑娟某種程度算是一種特殊存在的「物種」,當人人皆曰媒體可罵,她安靜地站穩媒體亦可敬的一個角落。
一百多年前,馬克吐溫就譏笑過記者:「輿論雖有令人生畏的力量,但它是由一群無知而自鳴得意的傻瓜營造出來的。我認識幾百個記者,其中大多數人的個人之見並不值錢,但當他們在報紙上說話,就成了報紙的意見,於是,他們的話就成了震撼社會、雷鳴般的預言。」這段話,擺在今日依舊適用,但對淑娟這樣的「獨立記者」而言,她早就脫離依靠(新聞)機構營造意見的階段,當然也就擺脫了來自業務干擾的可能,她的專業和敬業,贏得新聞對象的敬重。
網路世代興起,傳統媒體是否勢將消亡?或許不必太早定論,但相信遲早有一天,最著名新聞獎創辦人普立茲對「新聞媒體」下的定義要改寫為:
「一個記者(原文:機構,意指新聞機構)應該永遠為進步和改革而戰,永不容忍不公和腐敗;應該永遠向各政黨和煽動行為宣戰,絕不從屬於任何政黨和機構(原文只有政黨);應該永遠反對特權階層和魚肉百姓的人,永不對貧窮的人漠然不顧;應該永遠對社會福利事業忠誠不渝,絕不滿足於只顧刊登新聞;應該永遠竭力維護獨立自主,永不懼怕打擊錯誤行為,不管它是來自掠奪成性的富豪集團還是來自淪於劫掠貧困的人們。」
(附上原文:An institutaion should always fight for progress and reform, never tolerate injustice or corruption, always fight demagogues of all parties, never belong to any party, always oppose privileged classes and public plunders, never lack sypathy with the poot, always remain devoted to the public welfare, never be satisfied with merely printing news, always be drastically independent, never be afraid attack wrong, whether by predatory plutocracy or predatory poverty.)
(本文作者為「風傳媒」總主筆)
夏珍
「假如沒有對人的真正的關切,就不能成為記者;假如僅僅停留在對人的關切,而不是對問題的求解上,就不會成為一個好記者。」──柴靜
我不認識柴靜,但早在她的作品《看見》繁體版在台灣出版前,我就讀了這本書的簡體版。當台灣的女主播們動輒犯上「進行一個動作」的「語詞錯誤」,而備受譏嘲時,我非常好奇這個以調查新聞聞名的「小女生」,為什麼能用這麼漂亮的文字書寫她的工作?最重要的,她的文字有疑問、有思考,即便未必有答案,但她對群眾問題的感情完全到位,這讓她的報導不必渲染就有十足的感染力。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前三十年你們拚命毀文化,後三十年你們拚命毀物質。夜以繼日地挖取地下資源賤賣掉,強拆地面的民房,汙染河流空氣,用高稅賦和低工資榨乾百姓,我們的子孫沒有了生存資源。你們的子孫移民走了。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這麼恨這個國家,毀之唯恐不及。」可想而知,在中國調查環保議題、處理礦區驚人的空氣與水汙染,而能講出這段話,是多麼不容易。直到去年(二○一五年),柴靜製作一部紀錄片《穹頂之下》,創造瞬間破億的點擊之後,她也立刻成為大陸封殺的「獨立記者」。
很奇特,每次觀看《穹頂之下》,看到站在螢幕前的柴靜,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朱淑娟。
台灣比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快了三十年,我們也曾經歷只要經濟發展不知環保為何物的年代,做為「環保記者」,朱淑娟當然不是第一代。早在政治開放前後,台灣環保新聞即蓬勃如火,五輕抗爭得以關廠,到六輕抗爭得到回饋,彷彿是一種預示。在民主社會走在環保抗爭的前沿,報導沒有政治壓力,卻難免業務干擾;沒有生命安危,卻難免精神耗弱,因為所有的問題都不可能一時半刻得到解決。人,就在歲月流轉中,老了,或累了。
七年,淑娟就成為圈內知名的「獨立記者」,獲獎無數。如果她還在新聞機構之中,或許並不特殊,她的特殊就在於她的「獨立」──不從屬於任何新聞機構。機構之於記者,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後靠」,你知道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支撐你的信念,支持你的工作,至少和新聞對象吵架的時候,還有人可以幫腔;但是,七年來,朱淑娟離開《聯合報》,憑藉的只有她自己的一枝筆(鍵盤),柴靜被大陸同行譽為「環保先行者」,淑娟應該是「新媒先行者」。在主流媒體還在嘗試網媒的時候,她自己就架起了網站,開始「一人工坊」──而且,沒有固定收入。最近幾年才流行所謂的「自媒體」,而她早就不再是「部落客」,而是專業的「自媒體」。
這幾年媒體生態無限惡化,許多媒體老人糾結於去留之間(包括我自己),淑娟義無反顧,走了就走了,奇特的是,太陽升起時,她照樣跑新聞!而且,一跑七年,如此專注不嘩眾,絕不跟著熱鬧走。對每一篇稿子,她都慎而重之,一再查核,總在現場,不論現場有沒有其他記者在,她鎖定議題就窮追到底,中科三、四期的前因後果,大概沒人比她更清楚。看到她寫前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拍著她肩膀問,「你為什麼老跟我做對?」我笑了,這就是淑娟,這就是「記者」。
記者,是一個特殊的行當,擁有比一般人多一點「接近真相」的權力或詛咒。說「詛咒」,因為真相就像是巨大的黑洞,一旦接近就無可避免地被吸引,無從逃避的一再探底,深,還要挖更深。從這個角度看,此刻眼下的多數射後不理的追風同業,到底稱不稱得上「記者」是有問題的,但我們多數人(同樣包括我自己),可能都失去了探底的好奇心或勇氣。我們常告訴自己「莫忘初衷」,卻不太回望、反省自己的初衷到底是什麼?
「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還記得自己為什麼出發嗎?其實,絕大多數人踏入這行的時候,沒什麼天大的信念和原因,或為工作故只得賣力做,但只要祖師爺真要賞你這口飯吃,總會碰到一個時刻,如靈光一閃,剎時就懂了:就是為了這個!一路能走下去,「這個」肯定不是名與利,掌聲或獎金。柴靜製作《穹頂之下》還有個起心動念,是為了她先天有缺陷的女兒;早在柴靜之前,朱淑娟已經呼喊PM2.5不知多少年了,新聞獎或許可能是她馬拉松式的「跑新聞」過程中,為她打氣的一瓶水,卻不是關鍵動力。
在媒體崩壞的年代,淑娟某種程度算是一種特殊存在的「物種」,當人人皆曰媒體可罵,她安靜地站穩媒體亦可敬的一個角落。
一百多年前,馬克吐溫就譏笑過記者:「輿論雖有令人生畏的力量,但它是由一群無知而自鳴得意的傻瓜營造出來的。我認識幾百個記者,其中大多數人的個人之見並不值錢,但當他們在報紙上說話,就成了報紙的意見,於是,他們的話就成了震撼社會、雷鳴般的預言。」這段話,擺在今日依舊適用,但對淑娟這樣的「獨立記者」而言,她早就脫離依靠(新聞)機構營造意見的階段,當然也就擺脫了來自業務干擾的可能,她的專業和敬業,贏得新聞對象的敬重。
網路世代興起,傳統媒體是否勢將消亡?或許不必太早定論,但相信遲早有一天,最著名新聞獎創辦人普立茲對「新聞媒體」下的定義要改寫為:
「一個記者(原文:機構,意指新聞機構)應該永遠為進步和改革而戰,永不容忍不公和腐敗;應該永遠向各政黨和煽動行為宣戰,絕不從屬於任何政黨和機構(原文只有政黨);應該永遠反對特權階層和魚肉百姓的人,永不對貧窮的人漠然不顧;應該永遠對社會福利事業忠誠不渝,絕不滿足於只顧刊登新聞;應該永遠竭力維護獨立自主,永不懼怕打擊錯誤行為,不管它是來自掠奪成性的富豪集團還是來自淪於劫掠貧困的人們。」
(附上原文:An institutaion should always fight for progress and reform, never tolerate injustice or corruption, always fight demagogues of all parties, never belong to any party, always oppose privileged classes and public plunders, never lack sypathy with the poot, always remain devoted to the public welfare, never be satisfied with merely printing news, always be drastically independent, never be afraid attack wrong, whether by predatory plutocracy or predatory poverty.)
(本文作者為「風傳媒」總主筆)
目次
第一部 獨立記者‧環境報導
前言:在獨立的路上
第一章:我做了記者
第二章:成為獨立記者
第三章:從事件中成長
第四章:與故鄉的連結
第五章:獨立工作守則
第二部:天空的顏色‧是國家進步的象徵
前言:仰望藍天
第六章:PM2.5來敲門
第七章:彰化醫生的故鄉守護
第八章:空汙的總量
第九章:汙染之城
第十章:被遺忘的城市
第十一章:共享一口好空氣
第三部 大旱望雨‧尋找幸福的水台灣
前言:大旱望雨
第十二章:十年大旱,缺水的台灣
第十三章:無雨的年代,休耕的農田
第十四章:控管耗水產業,用水才能零成長
第十五章:節水三法通過,水資源改革的契機
第十六章:草山水道,傳承水資源教育
後語:不只環境正義,而是永續正義 朱增宏
誌謝 我還會留在地球上
前言:在獨立的路上
第一章:我做了記者
第二章:成為獨立記者
第三章:從事件中成長
第四章:與故鄉的連結
第五章:獨立工作守則
第二部:天空的顏色‧是國家進步的象徵
前言:仰望藍天
第六章:PM2.5來敲門
第七章:彰化醫生的故鄉守護
第八章:空汙的總量
第九章:汙染之城
第十章:被遺忘的城市
第十一章:共享一口好空氣
第三部 大旱望雨‧尋找幸福的水台灣
前言:大旱望雨
第十二章:十年大旱,缺水的台灣
第十三章:無雨的年代,休耕的農田
第十四章:控管耗水產業,用水才能零成長
第十五章:節水三法通過,水資源改革的契機
第十六章:草山水道,傳承水資源教育
後語:不只環境正義,而是永續正義 朱增宏
誌謝 我還會留在地球上
書摘/試閱
【導讀】在獨立的路上
一個科技學院畢業生,在偶然的機會裡成為記者,在主流媒體十年後,一個部落格、一張名片成為獨立記者。七年內,部落格累積一千兩百多篇文章,獲得四座卓越新聞獎,見證網路時代獨立記者已能獨立發聲。
獨立記者因擁有較多自主性,可以堅持自己的理想。但少了組織的支援,獨立記者也有自己的困難要突破。而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是一件幸福的事,珍惜機緣,努力向前,一步一腳印。
【後記】永遠懷抱希望
這本書總共有三部。第一部談我如何從一個科技學院畢業生,變成記者、再變成獨立記者的過程。這之間有機緣巧合,也有自己的選擇。機緣是動力,選擇是關鍵,雖然我們無法左右機緣,但卻可以掌握選擇權。
回想自己這七年來的獨立記者生涯,真的很幸運能夠堅持下來,選擇相信自己,也給自己機會。沒有浪費太多時間在自怨自艾,或指責別人,而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於處理挫折、甚至超越挫折。當然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牽絆而無法自由選擇,但我想請你在可能的情況下,永遠不要放棄選擇權。
歲月匆匆,人生苦短,柴米油鹽、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也經常讓我們心情黯淡。但如果你對生活懷抱一絲理想與目標,這些生活中的種種瑣碎也就變得比較能夠忍受,那會讓我們即使身處黑暗,也能看見光明。
這七年來,我不斷被問到什麼是獨立記者、什麼是公民記者。雖然記者的名稱好像變多,但最後兩個字一定是「記者」,工作內容、任務並無不同。一定要分的話,只有「在公司上班」的記者、跟「沒在公司上班」的記者。
獨立記者、公民記者就是屬於「沒在公司上班」的記者,基本上獨立記者是全職,公民記者則是兼職,因為關心某些議題而無償工作。當然這是「基本上」,獨立記者也會無償寫稿,而公民記者的作品有時也可以變有償。
至於認定的問題,台灣本來就沒有「記者證」這種東西,公司記者很容易識別,只要認就職公司發給他的「工作證」就好。獨立記者或公民記者就從他的「實質工作內容」來認定。例如我有自己的新聞網站、也為幾個媒體寫稿,「實質」做的就是記者工作。我沒有「工作證」(要自己做一張也可以),但沒有人會說我不是記者,可見這種認定法一點都不困難。
而不論什麼名稱的記者,還有其他法律可以規範其行為,也有社會輿論的事後監督。如果有人假借記者名義,很快就會被拆穿。例如某記者在一個地方出現很久,但總是沒看到他寫什麼,以後還有人會給他採訪嗎?
見證公民社會軌跡
我做獨立記者以來,不斷在說這些觀念,也腳踏實地去印證,漸漸的,社會大眾、採訪對象也能接受這個觀念,說起來,面對質疑,最好的化解之道,就是親自去做給人家看。台灣人民真的很了不起,總是用開放的態度接受新觀念,對獨立記者及公民記者的友善就是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台灣獨立記者及公民記者的百花齊放、各種不同的觀點彙集,正是台灣民主社會的見證。
而這只是表面上的分法,獨立記者最大的意義還在於「獨立」兩個字,行動獨立、思考獨立,因為關心這件事所以去採訪、去寫報導。機構記者則因職責所在,有些時候的行動都是被指派,並非出自關心。出於主動或被動,工作的熱誠、意願及動力就會差別很大。
從這個角度來看,獨立記者的工作本身就有另一層意義,是做為公民社會與權力的一座橋樑,透過報導,讓政府、人民本來各站一邊的兩群人,開始互相看見、理解並溝通。我們常講「公民參與」,這個參與不是單向的,而是兩邊人都要走到另外一邊去參與對方,才能讓公民社會更邁開大步往前走。
就因為如此,我始終認為記者是一種「希望工程」,用報導牽起社會溝通的橋樑,促進社會良善的對話,讓社會往更好的方向前進。不只記者,任何工作都會找到其意義,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樣,看見工作價值,就會感覺非凡。
第二部是寫這四年來台灣細懸浮微粒PM2.5的影響及治理過程。我之所以特別挑空氣、水資源來寫,主要原因是這兩項不但攸關永續,而且牽涉到環境正義、生存正義。書中所提的例子都是我這些年來親自採訪過的,只屬於個人的經驗及觀點,不代表所有環境事件。雖然寫的是事,但在寫作的同時,卻也發現寫的其實是人,是一群跟你我共同生活在這個島嶼的手足。
寫環境議題特別會碰觸到社會的陰暗面,看見經濟私益下被犧牲的人、環境、甚至集體的未來。但另一方面,總是在陰暗的角落看見一群人,無私無我、毫無畏懼為正義付出行動,趕走黑暗、帶進陽光,深深覺得台灣社會還是充滿善的力量。
第三部是寫從二○一四年秋天到二○一五年春季,發生在台灣的嚴重枯旱,基於這些年來我對水資源缺乏的焦慮,當下即決定要追蹤這件事的發展。希望提出台灣水資源的種種困境,然後大家一起想想,不論你在哪個位置,能夠一起努力維護我們、以及下一代充足及安全的水源。
在這八個月追蹤枯旱期間,我總計寫了五十四篇報導,分別刊在環境報導、《商業周刊》、風傳媒,即時報導的目的是希望在事件當下就能發揮影響力。在枯旱結束後,為了將這個過程更有系統的紀錄下來,我重新再寫一遍,於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完成,總計三萬字,刊登在環境報導網站,當年十一月這套作品獲得「第十四屆卓越新聞獎—平面類專題新聞獎」。書中完整收錄這套作品,因部分事件有異動,遂一併更新或補正。
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非常多,沒有你們的支持,我絕對無法走到這裡。無以為報,只能更努力做出好的報導回報大家。深深感謝。
朱淑娟
二○一六年六月
獲獎的正義
二○一○年十二月我以中科三期的系列報導獲得「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導獎」,這似乎讓后里農民相當欣慰。廖明田有一次跟我說,他的孫子在我得獎隔天很興奮地跟他說:「阿公,你們那個抗議有得獎耶」,當時他搞不清楚得什麼獎,後來知道是我得獎,他說起這件事的神采飛揚讓我深受感動。
這個獎也讓曾經參與中科三期的許多人非常振奮,力量之大恐怕連頒獎給我的「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都想不到。其中一直以來協助這個案子的靜宜大學生態系教授鍾丁茂來信:「淑娟,妳得獎讓我高興的不得了,苦幹、深入、貼近台灣人民、台灣土地、台灣生態的報導,應該得獎。」
鍾老師那時因病人生已到了盡頭,收到他的信讓我熱淚盈眶。他臨終前的某一天,我接到台中張豐年醫師的電話,他說鍾老師希望我能去看他一次。二○一一年七月十八日天氣持續因颱風影響而不穩定,鍾老師選在這一天,邀請他的好朋友在台中榮總參加「樂動生命」創作曲音樂發表會。
自從兩年前發現自己得了肺腺癌第四期後,他的太太林淑惠才知道原來鍾老師會作曲,他決定在生命最後用創作的台語彌撒曲來榮耀天主。那天,當音樂響起,躺在病牀上的鍾老師時而舉起右手跟著節拍而搖動,時而跟遠道而來的朋友微笑點頭。在安寧病房中,透著一股隱藏在寧靜下的躁鬱。
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莊秉潔、廖本全、廖明田、後龍灣寶的洪箱、陳幸雄等多位農民都來了。中科三期、後龍科技園區案,第一時間站出來幫助農民的就是鍾老師。后里農民王婉盈提到,二○○五年鍾老師到她家裡吃了果園的梨子後說:「這麼好吃的梨子,怎麼可以徵收給中科蓋聯外道路?」
音樂會最後唱到「求主賜我善渡一生」時,鍾老師拿起麥克風說:「我太太要我謝謝大家。」隨後即進入病房,他太太要我也跟著進去,他偏著頭看到我來,舉起右手對我豎起大姆指。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最後中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與后里農民達成協議,官司合解,結束這場長達八年的行政訴訟。或許后里農民無法對抗龐大的政府機器,但天下不會有白費的戰役,農民們展現的堅毅生命力、無私的護土情懷,同時促成各界對環境法律的重視、以及人民對環境權的覺醒,更是深遠流長。
中科四期今安在?
中科三期之後,國科會又提出中科四期,什麼時候政治人物才能擺脫以科學園區做為政見的習慣?中科四期更是史上最荒唐的科學園區,它的失敗說穿了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是總統的政見」。二○○八年馬英九總統提出競選政見「愛台十二建設」,中科四期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是總統的政見,行政機關傾國傾城去實踐,如今中科四期在投入五百二十億建設經費、犧牲六百三十一公頃優良農地後,只有一家二‧六八公頃的廠商進駐,示範了什麼是政見的災難。
這個總統級的政見也變成地方選舉的籌碼,二○○八年八月在三天內現勘了七個地點後,選中彰化縣二林鎮做為園區地點。二○○九年十二月彰化縣長卓伯源順利連任。而國科會從未交代,為何把一個高汙染、高耗水的光電園區,選在一個地層下陷、缺水、而且是中部重要農業生產地帶的精華區?
這個園區是為了友達光電量身定製,但早在二○○八年十一月友達就已透露面板業不景氣,建廠計畫至少延後半年。但國科會無視這個警訊,照樣進行基礎建設,還說做好後就等友達公司隨時進駐。
連副總統吳敦義(已卸任)都可以跑來為廢水排放方式背書。為了搶過環評,國科會什麼承諾什麼都敢答應,然後在核備半年後又反悔承諾做不到,提出多達五項環評變更,公部門在替廠商示範「頭過身就過」的環評詐術。
在這之間,國科會主委幾番更替,中科四期也在多年政策糾纏下,到了一個誰都無法收拾的情況。二○一二年友達宣布不來了,國科會主委朱敬一(現已卸任)宣布轉型機械園區,他認為轉型後,用水、汙染都降低,對土地更友善,理當受到肯定。但我卻期待中科四期應重新檢討,而不是只做枝節調整而已。
有一次國科會的記者會結束後,只有我還在收攝影器材,朱敬一本來已經回到辦公室,不知為什麼又轉進來,看到我說:「你為什麼老是跟我作對?」
我對他說:「主委,我們最大的差異就是,我認為中科四期應該從頭來過,但站在你的位子你只能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他聽完後拍拍我的肩膀沒再說什麼,在那個空曠的會議室中,那一刻或許是我們相互理解的開始。
後來他在一場記者會中說了一段話:「我名義上的老闆是行政院長,但我實質上的老闆是台灣的土地跟人民……我今年二月六日才上任,但政府是永續的,我沒辦法從原點規劃二林園區,只能在現有基礎上做最大、最好的改善。這不會是一百分的方案,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多元和包容。」
我並沒有懷疑他的用心跟善意,但一如我剛剛說的,中科四期已經到了誰都改變不了的狀態,朱敬一應該也是盡力了。果然又四年過去了,國科會升格為科技部,他跟副主委賀陳宏都離開行政機關,他們當初一腔熱血宣布要做的精密機械園區,到現在連個影子都沒有。
所以當二○一五年九月,蔡英文的總統競選政見提出在台南高鐵站旁的沙崙農場打造一千一百一十八公頃的創新綠能科技園區時,第一個浮上來的念頭就是「又來了」。過沒多久趁一個到台南的機會,我刻意去現場看看。那一大片平整的農地上種了許多作物,農地接連天空,除了風聲,只有鳥鳴聲,而且聽聲音就知道牠從這個方向飛到了另一個方向。
這讓我想起二○○九年五月我因為給公共電視拍中科四期節目,跟攝影記者陳慶鍾到二林農場的情景,沙崙農場就跟當時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樣。而今中科四期安在?或許因為中科四期是我當獨立記者第一個追的事件,涉入許多私人情感,即便過了這麼多年,想起來還是非常心痛。
在這過程中,彰化農漁民經歷了一場生死保衛戰,投入人生多少血汗淚水。園區內相思寮的阿公阿嬤也在一場驚天動地的土地徵收後遷離四散。卻有人可以從二林園區得到政治利益,友達也不必為一個承諾負起什麼責任。
〈節錄自第三章:從事件中成長〉
一個科技學院畢業生,在偶然的機會裡成為記者,在主流媒體十年後,一個部落格、一張名片成為獨立記者。七年內,部落格累積一千兩百多篇文章,獲得四座卓越新聞獎,見證網路時代獨立記者已能獨立發聲。
獨立記者因擁有較多自主性,可以堅持自己的理想。但少了組織的支援,獨立記者也有自己的困難要突破。而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是一件幸福的事,珍惜機緣,努力向前,一步一腳印。
【後記】永遠懷抱希望
這本書總共有三部。第一部談我如何從一個科技學院畢業生,變成記者、再變成獨立記者的過程。這之間有機緣巧合,也有自己的選擇。機緣是動力,選擇是關鍵,雖然我們無法左右機緣,但卻可以掌握選擇權。
回想自己這七年來的獨立記者生涯,真的很幸運能夠堅持下來,選擇相信自己,也給自己機會。沒有浪費太多時間在自怨自艾,或指責別人,而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於處理挫折、甚至超越挫折。當然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牽絆而無法自由選擇,但我想請你在可能的情況下,永遠不要放棄選擇權。
歲月匆匆,人生苦短,柴米油鹽、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也經常讓我們心情黯淡。但如果你對生活懷抱一絲理想與目標,這些生活中的種種瑣碎也就變得比較能夠忍受,那會讓我們即使身處黑暗,也能看見光明。
這七年來,我不斷被問到什麼是獨立記者、什麼是公民記者。雖然記者的名稱好像變多,但最後兩個字一定是「記者」,工作內容、任務並無不同。一定要分的話,只有「在公司上班」的記者、跟「沒在公司上班」的記者。
獨立記者、公民記者就是屬於「沒在公司上班」的記者,基本上獨立記者是全職,公民記者則是兼職,因為關心某些議題而無償工作。當然這是「基本上」,獨立記者也會無償寫稿,而公民記者的作品有時也可以變有償。
至於認定的問題,台灣本來就沒有「記者證」這種東西,公司記者很容易識別,只要認就職公司發給他的「工作證」就好。獨立記者或公民記者就從他的「實質工作內容」來認定。例如我有自己的新聞網站、也為幾個媒體寫稿,「實質」做的就是記者工作。我沒有「工作證」(要自己做一張也可以),但沒有人會說我不是記者,可見這種認定法一點都不困難。
而不論什麼名稱的記者,還有其他法律可以規範其行為,也有社會輿論的事後監督。如果有人假借記者名義,很快就會被拆穿。例如某記者在一個地方出現很久,但總是沒看到他寫什麼,以後還有人會給他採訪嗎?
見證公民社會軌跡
我做獨立記者以來,不斷在說這些觀念,也腳踏實地去印證,漸漸的,社會大眾、採訪對象也能接受這個觀念,說起來,面對質疑,最好的化解之道,就是親自去做給人家看。台灣人民真的很了不起,總是用開放的態度接受新觀念,對獨立記者及公民記者的友善就是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台灣獨立記者及公民記者的百花齊放、各種不同的觀點彙集,正是台灣民主社會的見證。
而這只是表面上的分法,獨立記者最大的意義還在於「獨立」兩個字,行動獨立、思考獨立,因為關心這件事所以去採訪、去寫報導。機構記者則因職責所在,有些時候的行動都是被指派,並非出自關心。出於主動或被動,工作的熱誠、意願及動力就會差別很大。
從這個角度來看,獨立記者的工作本身就有另一層意義,是做為公民社會與權力的一座橋樑,透過報導,讓政府、人民本來各站一邊的兩群人,開始互相看見、理解並溝通。我們常講「公民參與」,這個參與不是單向的,而是兩邊人都要走到另外一邊去參與對方,才能讓公民社會更邁開大步往前走。
就因為如此,我始終認為記者是一種「希望工程」,用報導牽起社會溝通的橋樑,促進社會良善的對話,讓社會往更好的方向前進。不只記者,任何工作都會找到其意義,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樣,看見工作價值,就會感覺非凡。
第二部是寫這四年來台灣細懸浮微粒PM2.5的影響及治理過程。我之所以特別挑空氣、水資源來寫,主要原因是這兩項不但攸關永續,而且牽涉到環境正義、生存正義。書中所提的例子都是我這些年來親自採訪過的,只屬於個人的經驗及觀點,不代表所有環境事件。雖然寫的是事,但在寫作的同時,卻也發現寫的其實是人,是一群跟你我共同生活在這個島嶼的手足。
寫環境議題特別會碰觸到社會的陰暗面,看見經濟私益下被犧牲的人、環境、甚至集體的未來。但另一方面,總是在陰暗的角落看見一群人,無私無我、毫無畏懼為正義付出行動,趕走黑暗、帶進陽光,深深覺得台灣社會還是充滿善的力量。
第三部是寫從二○一四年秋天到二○一五年春季,發生在台灣的嚴重枯旱,基於這些年來我對水資源缺乏的焦慮,當下即決定要追蹤這件事的發展。希望提出台灣水資源的種種困境,然後大家一起想想,不論你在哪個位置,能夠一起努力維護我們、以及下一代充足及安全的水源。
在這八個月追蹤枯旱期間,我總計寫了五十四篇報導,分別刊在環境報導、《商業周刊》、風傳媒,即時報導的目的是希望在事件當下就能發揮影響力。在枯旱結束後,為了將這個過程更有系統的紀錄下來,我重新再寫一遍,於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完成,總計三萬字,刊登在環境報導網站,當年十一月這套作品獲得「第十四屆卓越新聞獎—平面類專題新聞獎」。書中完整收錄這套作品,因部分事件有異動,遂一併更新或補正。
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非常多,沒有你們的支持,我絕對無法走到這裡。無以為報,只能更努力做出好的報導回報大家。深深感謝。
朱淑娟
二○一六年六月
獲獎的正義
二○一○年十二月我以中科三期的系列報導獲得「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導獎」,這似乎讓后里農民相當欣慰。廖明田有一次跟我說,他的孫子在我得獎隔天很興奮地跟他說:「阿公,你們那個抗議有得獎耶」,當時他搞不清楚得什麼獎,後來知道是我得獎,他說起這件事的神采飛揚讓我深受感動。
這個獎也讓曾經參與中科三期的許多人非常振奮,力量之大恐怕連頒獎給我的「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都想不到。其中一直以來協助這個案子的靜宜大學生態系教授鍾丁茂來信:「淑娟,妳得獎讓我高興的不得了,苦幹、深入、貼近台灣人民、台灣土地、台灣生態的報導,應該得獎。」
鍾老師那時因病人生已到了盡頭,收到他的信讓我熱淚盈眶。他臨終前的某一天,我接到台中張豐年醫師的電話,他說鍾老師希望我能去看他一次。二○一一年七月十八日天氣持續因颱風影響而不穩定,鍾老師選在這一天,邀請他的好朋友在台中榮總參加「樂動生命」創作曲音樂發表會。
自從兩年前發現自己得了肺腺癌第四期後,他的太太林淑惠才知道原來鍾老師會作曲,他決定在生命最後用創作的台語彌撒曲來榮耀天主。那天,當音樂響起,躺在病牀上的鍾老師時而舉起右手跟著節拍而搖動,時而跟遠道而來的朋友微笑點頭。在安寧病房中,透著一股隱藏在寧靜下的躁鬱。
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莊秉潔、廖本全、廖明田、後龍灣寶的洪箱、陳幸雄等多位農民都來了。中科三期、後龍科技園區案,第一時間站出來幫助農民的就是鍾老師。后里農民王婉盈提到,二○○五年鍾老師到她家裡吃了果園的梨子後說:「這麼好吃的梨子,怎麼可以徵收給中科蓋聯外道路?」
音樂會最後唱到「求主賜我善渡一生」時,鍾老師拿起麥克風說:「我太太要我謝謝大家。」隨後即進入病房,他太太要我也跟著進去,他偏著頭看到我來,舉起右手對我豎起大姆指。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最後中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與后里農民達成協議,官司合解,結束這場長達八年的行政訴訟。或許后里農民無法對抗龐大的政府機器,但天下不會有白費的戰役,農民們展現的堅毅生命力、無私的護土情懷,同時促成各界對環境法律的重視、以及人民對環境權的覺醒,更是深遠流長。
中科四期今安在?
中科三期之後,國科會又提出中科四期,什麼時候政治人物才能擺脫以科學園區做為政見的習慣?中科四期更是史上最荒唐的科學園區,它的失敗說穿了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是總統的政見」。二○○八年馬英九總統提出競選政見「愛台十二建設」,中科四期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是總統的政見,行政機關傾國傾城去實踐,如今中科四期在投入五百二十億建設經費、犧牲六百三十一公頃優良農地後,只有一家二‧六八公頃的廠商進駐,示範了什麼是政見的災難。
這個總統級的政見也變成地方選舉的籌碼,二○○八年八月在三天內現勘了七個地點後,選中彰化縣二林鎮做為園區地點。二○○九年十二月彰化縣長卓伯源順利連任。而國科會從未交代,為何把一個高汙染、高耗水的光電園區,選在一個地層下陷、缺水、而且是中部重要農業生產地帶的精華區?
這個園區是為了友達光電量身定製,但早在二○○八年十一月友達就已透露面板業不景氣,建廠計畫至少延後半年。但國科會無視這個警訊,照樣進行基礎建設,還說做好後就等友達公司隨時進駐。
連副總統吳敦義(已卸任)都可以跑來為廢水排放方式背書。為了搶過環評,國科會什麼承諾什麼都敢答應,然後在核備半年後又反悔承諾做不到,提出多達五項環評變更,公部門在替廠商示範「頭過身就過」的環評詐術。
在這之間,國科會主委幾番更替,中科四期也在多年政策糾纏下,到了一個誰都無法收拾的情況。二○一二年友達宣布不來了,國科會主委朱敬一(現已卸任)宣布轉型機械園區,他認為轉型後,用水、汙染都降低,對土地更友善,理當受到肯定。但我卻期待中科四期應重新檢討,而不是只做枝節調整而已。
有一次國科會的記者會結束後,只有我還在收攝影器材,朱敬一本來已經回到辦公室,不知為什麼又轉進來,看到我說:「你為什麼老是跟我作對?」
我對他說:「主委,我們最大的差異就是,我認為中科四期應該從頭來過,但站在你的位子你只能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他聽完後拍拍我的肩膀沒再說什麼,在那個空曠的會議室中,那一刻或許是我們相互理解的開始。
後來他在一場記者會中說了一段話:「我名義上的老闆是行政院長,但我實質上的老闆是台灣的土地跟人民……我今年二月六日才上任,但政府是永續的,我沒辦法從原點規劃二林園區,只能在現有基礎上做最大、最好的改善。這不會是一百分的方案,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多元和包容。」
我並沒有懷疑他的用心跟善意,但一如我剛剛說的,中科四期已經到了誰都改變不了的狀態,朱敬一應該也是盡力了。果然又四年過去了,國科會升格為科技部,他跟副主委賀陳宏都離開行政機關,他們當初一腔熱血宣布要做的精密機械園區,到現在連個影子都沒有。
所以當二○一五年九月,蔡英文的總統競選政見提出在台南高鐵站旁的沙崙農場打造一千一百一十八公頃的創新綠能科技園區時,第一個浮上來的念頭就是「又來了」。過沒多久趁一個到台南的機會,我刻意去現場看看。那一大片平整的農地上種了許多作物,農地接連天空,除了風聲,只有鳥鳴聲,而且聽聲音就知道牠從這個方向飛到了另一個方向。
這讓我想起二○○九年五月我因為給公共電視拍中科四期節目,跟攝影記者陳慶鍾到二林農場的情景,沙崙農場就跟當時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樣。而今中科四期安在?或許因為中科四期是我當獨立記者第一個追的事件,涉入許多私人情感,即便過了這麼多年,想起來還是非常心痛。
在這過程中,彰化農漁民經歷了一場生死保衛戰,投入人生多少血汗淚水。園區內相思寮的阿公阿嬤也在一場驚天動地的土地徵收後遷離四散。卻有人可以從二林園區得到政治利益,友達也不必為一個承諾負起什麼責任。
〈節錄自第三章:從事件中成長〉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