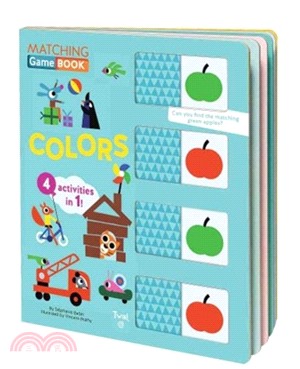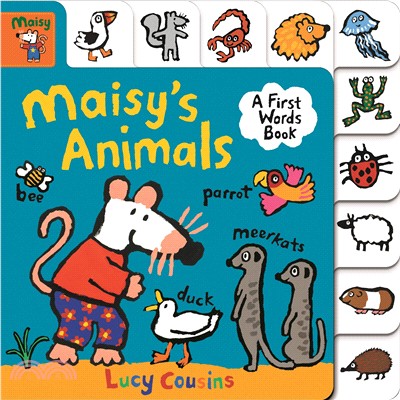定價
:NT$ 350 元優惠價
:90 折 315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9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如果有一張藥方,按時服用,日久可得自由,你願意一試嗎?
城市病了,氣血不通,諸脈堵塞,浮城心煩意亂,前路一片迷茫。
人病醫病,城市有病,要說望聞問切,從何入手?人心又如何能得到自由?
面對城市崩壞的無力感,朱順慈寫下了《自由之方》,她在自序中寫道:
「念念不忘的,終究是自身的處境。香港病了,病在哪?如何醫?」
《自由之方》是一則城市病變的寓言,以一起失踪事件作序幕。原本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流動中醫徐啟寧,一夜之間,遇上連串奇人奇事,還因此多了一個醫術比他高明、功力莫測高深的助手小張。兩個中醫,一個有牌,一個無牌,同被捲入李家三女子的病史。失踪事件讓徐啟寧化身醫療偵探,由外在環境的線索,走進病人的生活,追查病源,由身體的病追踪至心的病,醫人也醫治了自己。
各有各的病,醫人的就醫的,無一倖免,越深入病源,不禁自問:人生而為人,怎樣才能得到自由?
徐啟寧是自由身的流動中醫,他的朋友對他說:
「挺羨慕你的工作,很自由。不像我,朝九晚六,營營役役的,每天瞎忙,然後一年一年過去。」然後又說道:「像你這樣來來去去,表面很自在,骨子裡不都跟我們一樣,手停口停。我一直想起你,想到有點擔心,你這日子真過得下去嗎?」
作者自言很少看西醫,對博大精深的中醫理論十分著迷,小說把養生常識結合在角色的塑造和情節的佈局中:
給一位心有千千結的病者的處方──
這是都市人常見的氣機病,你要注意養肝,肝很重要,我們靠肝來藏血,但同時要留意適時疏洩,處理好肝,其他都是小問題。想生氣時,不要鬱
在心裡。
給一位失眠多時的患者的處方──
神歸心,魂歸肝,魄歸肺,意歸脾,志藏腎,恕我直言,你是心肝脾肺腎都亂作一團,神魂魄意志都要調理,弄好了,自然睡得香甜。
到最後失踪事件留下的線索,也跟中醫藥材有關,開給大家的一道謎題 ──
君無遠志
未竟黃蓮
待汝首烏
朝夕當歸
由《現在未來式》的城市未來寓言,到《自由之方》的當下人心病變,朱順慈念念不忘她土生土長的城市,字裡行間充滿集體的感情回憶── 地方街道的變遷,食物味覺的懷念,經典流行曲的洗禮。讀《自由之方》,我們隨著流動中醫二人組到不同地區出診,與他們一起重遊城市,以至城市記憶的某個角落,感情是內歛而不喧嘩的,因為感嘆是來自每天的生活,磨人也是細水長流的。
在《自由之方》裡,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你知道星巴克咖啡賣到幾錢一杯?租一個小房間要多少錢?我交完租就開不了飯,難道這又算正常?香港本來就不正常。」
「有道理。」她幽幽嘆一口氣。「整個城市都病入膏盲。」
愛之深,關之切。朱順慈看著城市崩壞,覺得一切無可挽回的無力,以兩個流動中醫寄託感情,給自己打氣。這只是故事的開端,兩位流動中醫將繼續在城市出診,追本逐源,治病,也治心,在流動中尋索安穩,在風雨中抱緊自由。
推薦人語:
「《自由之方》正是朱順慈為社會把把脈, 來一點清熱排毒, 加一劑保胃健脾的「廿四味」。
我鼓勵對前途迷茫的年輕人看這書,推薦對香港失望的成年人看這書, 也介紹對今天社會問題磨拳擦掌的有心人看這書。讓大家一起來替我們獅子山下的母親治治病罷。
——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城市病了,氣血不通,諸脈堵塞,浮城心煩意亂,前路一片迷茫。
人病醫病,城市有病,要說望聞問切,從何入手?人心又如何能得到自由?
面對城市崩壞的無力感,朱順慈寫下了《自由之方》,她在自序中寫道:
「念念不忘的,終究是自身的處境。香港病了,病在哪?如何醫?」
《自由之方》是一則城市病變的寓言,以一起失踪事件作序幕。原本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流動中醫徐啟寧,一夜之間,遇上連串奇人奇事,還因此多了一個醫術比他高明、功力莫測高深的助手小張。兩個中醫,一個有牌,一個無牌,同被捲入李家三女子的病史。失踪事件讓徐啟寧化身醫療偵探,由外在環境的線索,走進病人的生活,追查病源,由身體的病追踪至心的病,醫人也醫治了自己。
各有各的病,醫人的就醫的,無一倖免,越深入病源,不禁自問:人生而為人,怎樣才能得到自由?
徐啟寧是自由身的流動中醫,他的朋友對他說:
「挺羨慕你的工作,很自由。不像我,朝九晚六,營營役役的,每天瞎忙,然後一年一年過去。」然後又說道:「像你這樣來來去去,表面很自在,骨子裡不都跟我們一樣,手停口停。我一直想起你,想到有點擔心,你這日子真過得下去嗎?」
作者自言很少看西醫,對博大精深的中醫理論十分著迷,小說把養生常識結合在角色的塑造和情節的佈局中:
給一位心有千千結的病者的處方──
這是都市人常見的氣機病,你要注意養肝,肝很重要,我們靠肝來藏血,但同時要留意適時疏洩,處理好肝,其他都是小問題。想生氣時,不要鬱
在心裡。
給一位失眠多時的患者的處方──
神歸心,魂歸肝,魄歸肺,意歸脾,志藏腎,恕我直言,你是心肝脾肺腎都亂作一團,神魂魄意志都要調理,弄好了,自然睡得香甜。
到最後失踪事件留下的線索,也跟中醫藥材有關,開給大家的一道謎題 ──
君無遠志
未竟黃蓮
待汝首烏
朝夕當歸
由《現在未來式》的城市未來寓言,到《自由之方》的當下人心病變,朱順慈念念不忘她土生土長的城市,字裡行間充滿集體的感情回憶── 地方街道的變遷,食物味覺的懷念,經典流行曲的洗禮。讀《自由之方》,我們隨著流動中醫二人組到不同地區出診,與他們一起重遊城市,以至城市記憶的某個角落,感情是內歛而不喧嘩的,因為感嘆是來自每天的生活,磨人也是細水長流的。
在《自由之方》裡,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你知道星巴克咖啡賣到幾錢一杯?租一個小房間要多少錢?我交完租就開不了飯,難道這又算正常?香港本來就不正常。」
「有道理。」她幽幽嘆一口氣。「整個城市都病入膏盲。」
愛之深,關之切。朱順慈看著城市崩壞,覺得一切無可挽回的無力,以兩個流動中醫寄託感情,給自己打氣。這只是故事的開端,兩位流動中醫將繼續在城市出診,追本逐源,治病,也治心,在流動中尋索安穩,在風雨中抱緊自由。
推薦人語:
「《自由之方》正是朱順慈為社會把把脈, 來一點清熱排毒, 加一劑保胃健脾的「廿四味」。
我鼓勵對前途迷茫的年輕人看這書,推薦對香港失望的成年人看這書, 也介紹對今天社會問題磨拳擦掌的有心人看這書。讓大家一起來替我們獅子山下的母親治治病罷。
——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作者簡介
朱順慈
土生土長香港人。小時候希望長大從事電影工作,後來發現真正想做的是一個會說故事的人,現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讓講堂變成故事聚散的舞台。
2013年,靜極思動,召集親朋好友襄助,製作了以中文大學為背景的獨立電影《佳釀》,作為送給自己和學生的禮物。
著有《現在未來式》。
朱偉昇 (攝影)
朱偉昇,從事設計多年,年青時一心做好花紙包裝世界,人到中年,風流褪色,灰白的心欲尋千里以外的顏色。
土生土長香港人。小時候希望長大從事電影工作,後來發現真正想做的是一個會說故事的人,現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讓講堂變成故事聚散的舞台。
2013年,靜極思動,召集親朋好友襄助,製作了以中文大學為背景的獨立電影《佳釀》,作為送給自己和學生的禮物。
著有《現在未來式》。
朱偉昇 (攝影)
朱偉昇,從事設計多年,年青時一心做好花紙包裝世界,人到中年,風流褪色,灰白的心欲尋千里以外的顏色。
序
推薦序
為社會把把脈/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出自《國語•晉語》的「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我們都會聽過。 意思是最出色的醫生醫國患,建設國家。其次 要做好醫人的工作,如建立公共醫療系統,做好預防措施,資源分配,甚或者做教導者和教師,健體育人。不要追求做醫病的而不明病理的醫生。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治病而不治根源的乃是下醫。
在《自由之方》這本寓言小説裡, 作者巧妙地以兩個中醫師的故事, 道出今天香港的隱疾。香港社會的問題, 政治的紛亂, 有些人認為是無病呻吟, 作繭自縛, 有些卻認為是先天不足, 病人膏肓。但大概没有人不同意香港是病了, 而且病得久, 病得深。要解決現在社會的問題, 中醫的辨症論治, 固本培元, 似乎比起西醫用猛藥抑制或手術開刀, 更溫和, 更奏效。由《現在未來式》對城市未來的寓言,到《自由之方》的當下人心病變, 作者念念不忘孕育她成長的香港,字裡行間充滿感情和集體的回憶, 像我這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此書帶出絲絲情懷, 勾起無限感慨。
認識朱順慈差不多五年了, 從沒有校長與教職員的隔膜。她活潑的笑容, 開朗的性格, 成了大學𥚃難得的開心果。順慈的創作力和想像力, 亦是吸引我的地方。中文大學的《花節》, 《漂書》, 和《中大有晴》, 都是她的「鬼主意」, 卻深受校內外師生的歡迎。她善長利用音樂, 藝術, 祥和的氣氛, 把人文精神, 正面的價值帶出來。是位難得的老師,更是學生的福氣。雖然近年社會充斥著矛盾和紛爭, 她的招牌微笑和肩膀的一縮, 往往成為一道清泉, 叫人悶氣全消。《自由之方》正是順慈為社會把把脈, 來一點清熱排毒, 加一劑保胃健脾的「廿四味」。
我鼓勵對前途迷茫的年青人看這書,推薦對香港失望的成年人看這書, 也介紹對今天社會問題磨拳擦掌的有心人看這書。讓大家一起來替我們獅子山下的母親治治病罷。
作者自序
在崩壞中追尋自由/朱順慈
起初我想寫一個關於女人看中醫的故事。不論年齡、學歷、職業、身高、體重、喜好,反正身邊有很多女人在交換各門各路的中醫資料。她們像說著某種神秘宗教,而那些把個脈便知道你前世今生的醫師,是教主,是先知,是沙漠的綠洲,是無垠人生的救命草。
醫不醫得好,不是重點。
工作以來,我幾乎不看西醫,普通傷風感冒,好好睡一覺比吃抗生素好。相對醫治,我更相信調理,中醫說的「治未病」。我看過很多中醫,誰比誰高明,我不知道,但在那些望聞問切的常規中,我漸漸熟習了一套語言,由是接觸到一種世界觀,或者一種界定「健康」的思路。
彼世界奧妙精奇,病是病,病非病,五臟六腑,奇經八脈,各司其職又環環相扣。有病醫病,無病養生。養生養甚麼?精、氣、神。精氣神又是甚麼?如何量度基準?如何判辨消長?一路追問下去,玄之又玄。末了,卻又不過是「健康」兩字。
構思有了,以為會交出一個愛情故事,然後,一如那些不斷重複自己的作者,兜兜轉轉之間,我又丟失了愛情,念念不忘的,終究是自身的處境。香港病了,病在哪?如何醫?醫生大抵不會斷然說出「你沒救了」的狠話,但在水深火熱的時刻,總無法按捺悲觀,因著眼前各種崩壞,只覺一切無力挽回,返魂乏術。
最終寫了這麼一個為自己打氣的故事,翻了很多書,麻煩了好幾個中醫朋友,謹在此致以最真摯的謝意。希望可以繼續寫徐醫師和小張的江湖歷險,由妙手回春,待我終於寫到慵懶自在的冬日,或能領會流動中醫所嚮往的自由,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只不知到那時,我城是死是活,還是苟延殘喘。
為社會把把脈/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出自《國語•晉語》的「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我們都會聽過。 意思是最出色的醫生醫國患,建設國家。其次 要做好醫人的工作,如建立公共醫療系統,做好預防措施,資源分配,甚或者做教導者和教師,健體育人。不要追求做醫病的而不明病理的醫生。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治病而不治根源的乃是下醫。
在《自由之方》這本寓言小説裡, 作者巧妙地以兩個中醫師的故事, 道出今天香港的隱疾。香港社會的問題, 政治的紛亂, 有些人認為是無病呻吟, 作繭自縛, 有些卻認為是先天不足, 病人膏肓。但大概没有人不同意香港是病了, 而且病得久, 病得深。要解決現在社會的問題, 中醫的辨症論治, 固本培元, 似乎比起西醫用猛藥抑制或手術開刀, 更溫和, 更奏效。由《現在未來式》對城市未來的寓言,到《自由之方》的當下人心病變, 作者念念不忘孕育她成長的香港,字裡行間充滿感情和集體的回憶, 像我這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此書帶出絲絲情懷, 勾起無限感慨。
認識朱順慈差不多五年了, 從沒有校長與教職員的隔膜。她活潑的笑容, 開朗的性格, 成了大學𥚃難得的開心果。順慈的創作力和想像力, 亦是吸引我的地方。中文大學的《花節》, 《漂書》, 和《中大有晴》, 都是她的「鬼主意」, 卻深受校內外師生的歡迎。她善長利用音樂, 藝術, 祥和的氣氛, 把人文精神, 正面的價值帶出來。是位難得的老師,更是學生的福氣。雖然近年社會充斥著矛盾和紛爭, 她的招牌微笑和肩膀的一縮, 往往成為一道清泉, 叫人悶氣全消。《自由之方》正是順慈為社會把把脈, 來一點清熱排毒, 加一劑保胃健脾的「廿四味」。
我鼓勵對前途迷茫的年青人看這書,推薦對香港失望的成年人看這書, 也介紹對今天社會問題磨拳擦掌的有心人看這書。讓大家一起來替我們獅子山下的母親治治病罷。
作者自序
在崩壞中追尋自由/朱順慈
起初我想寫一個關於女人看中醫的故事。不論年齡、學歷、職業、身高、體重、喜好,反正身邊有很多女人在交換各門各路的中醫資料。她們像說著某種神秘宗教,而那些把個脈便知道你前世今生的醫師,是教主,是先知,是沙漠的綠洲,是無垠人生的救命草。
醫不醫得好,不是重點。
工作以來,我幾乎不看西醫,普通傷風感冒,好好睡一覺比吃抗生素好。相對醫治,我更相信調理,中醫說的「治未病」。我看過很多中醫,誰比誰高明,我不知道,但在那些望聞問切的常規中,我漸漸熟習了一套語言,由是接觸到一種世界觀,或者一種界定「健康」的思路。
彼世界奧妙精奇,病是病,病非病,五臟六腑,奇經八脈,各司其職又環環相扣。有病醫病,無病養生。養生養甚麼?精、氣、神。精氣神又是甚麼?如何量度基準?如何判辨消長?一路追問下去,玄之又玄。末了,卻又不過是「健康」兩字。
構思有了,以為會交出一個愛情故事,然後,一如那些不斷重複自己的作者,兜兜轉轉之間,我又丟失了愛情,念念不忘的,終究是自身的處境。香港病了,病在哪?如何醫?醫生大抵不會斷然說出「你沒救了」的狠話,但在水深火熱的時刻,總無法按捺悲觀,因著眼前各種崩壞,只覺一切無力挽回,返魂乏術。
最終寫了這麼一個為自己打氣的故事,翻了很多書,麻煩了好幾個中醫朋友,謹在此致以最真摯的謝意。希望可以繼續寫徐醫師和小張的江湖歷險,由妙手回春,待我終於寫到慵懶自在的冬日,或能領會流動中醫所嚮往的自由,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只不知到那時,我城是死是活,還是苟延殘喘。
書摘/試閱
4 急症
救護車不消五分鐘就來到,香港式效率,總是令人嘆服。對我來說,這五分鐘卻像一個世紀那麼長。小兄弟在我眼前昏厥過去的一刻,我想也沒想就掏出電話打九九九,電話接通,我跑到最近的燈柱,報上號碼,前後不需三十秒。一收線,聽到李知而在旁邊嘀咕:「自己不也是行醫的嗎?」
她聲線壓得低,我還是毫無遺漏地聽入耳了。這話如當頭棒喝,她確沒說錯,我完全沒想過自己也可以為他急救,枉我學醫多年,前面明擺著一個病人,我只知盡好市民之責,渾忘了另一個身分。
我假裝沒聽見她的說話。小兄弟面色蒼白,嘴角有白沫,平躺石壆上,我定一定心神,上前探他鼻息,好消息是未斷氣,壞消息是呼吸極微弱,手背放上額頭,感覺冰涼,顯然是體溫下降。這是牛飲啤酒的現眼報,酒醉一般不會死人,但飲到昏厥,另作別話。我解下背包,輕抬起他雙腳,用背包墊高,然後脫下風衣,放他胸上。我感到身後李知而銳利的目光。「你不要這樣盯著我好不好?」我沒回頭,看不到她的反應,半响,她說:「你們不是會按穴道嗎?這管用不管用?」
她這麼一問,我先想到太沖穴,不過又要脫鞋脫襪,太麻煩,情勢緊急,不如直接按勞宮穴?我背包有針,可以在人中和合谷施針,但轉念之間,又擔心這樣大動作,待救護員來到,怕解釋不了那麼多。為著這個念頭,我暗暗慚愧 – 我是貨真價實的中醫,救急扶危是天職,居然畏首畏尾,我到底在怕甚麼?
李知而哪裡知道我心內這麼多盤算,見我不回話,逕自走到小兄弟面前,二話不說,拇指對準人中穴壓下去。
我跑上前,輕輕抬起他的頭,示意李知而加大力度捏。
沒捏多久,小兄弟指尖抖了一下,未幾,悠悠醒轉。不遠處,兩個救護員急步跑來,我和李知而忙退下。這時才有空看一看錶,一時零五分。
救護員的一身白制服在深宵很亮眼,見到他們滿有信心,不慌不忙,我心完全安定下來。
「返來呀!返來……」小兄弟醒來,念念不忘的還是同一句話。
「你們認識的嗎?」其中一名救護員問。
「不認識。」李知而搶答似的回答。
我連她也說不上認識,孤獨都市,寂寞夜晚,滿街陌生人。
這時,警察也來了,對講機的沙沙聲,頓時增添了懸疑感。「誰人報案?」
我舉起手,像個笨笨的小學生。李知而忍不住笑了出來,說:「我們剛路過。」
警察看了我倆一眼,問:「那你倆又是甚麼關係?」
我幾乎沒衝口而出說 「關你甚麼事」,李知而先是呆了一下 ,過了一會才說:「朋友」。
警察再看了我們一眼,走近救護員,問:「情況如何呀手足?」
「醉酒,短暫昏迷,血壓偏低,但無大礙。他神智未清,要送院。」
警察彎下身,正對著小兄弟,問道:「哥仔,你叫甚麼名字?」「返來呀。」「拿身份證來看看。」「返來呀。」「你想要誰返來?他幾號電話號碼?」「返來呀。」
「返來哥」一件單衫,褲袋看來空空如也,搞不好連錢包也沒有。警察沒好氣,轉身對著對講機交代一些甚麼,救護員打開輪椅,我以為這段西灣河小插曲到此為止,沒料到在他們扶「返來哥」上輪椅的一刻,他忽然甩開了兩人,跌跌撞撞的撲到我跟前,一把抱住了我。
「不要離開我。」
他滿身酒氣,環抱我的雙手軟弱無力,頭埋進我的頸,嘴唇貼上來時,我大力推開了他。兩個救護員上前把他扶穩了,他睜開了眼睛,定睛看著我,又說了一遍:「不要離開我。」
不過是一瞬,但我肯定他眼神堅定,更肯定這不可能出現在一個酩酊大醉的人的臉上。但也只是一瞬,他又閉上眼,渾身無力的靠倒在救護員身上。
我像被甚麼懾住了,整個世界靜了下來,只重複聽見「不要離開我」五個字。
三分鐘後,我登上了救護車,車開走時,我看見李知而一臉不解跟我揮別。
小兄弟睡得香甜,救護員自顧自聊天,從沒上過白車的我,在搖晃中漸漸清醒過來:天啊,我在做甚麼?
凌晨時分的急症室比想像中多人。醫院的白光管,典型世界光,看上去是一片光明,但浮泛在候診病人頭上臉上的慘白,足以令我生起立即逃離的心。醫院最危險了,細菌病毒和病氣,應有盡有,打開背包想找個口罩,找不到,不意摸出了一條餐巾,拿來一看,上面歪歪斜斜的寫了幾行字:「小醫治病,中醫治人,大醫治國,上醫治心」。
我愣了一下,這東西,誰放進來的?
忽然人聲鼎沸,回頭看,兩個救護員分列兩旁,把一個滿身鮮血的男人架在膀子上。男人還能自己走路,可血從哪裡冒出我真的不敢看,他們經過我身邊時,我聽到幾下痛苦低吟。我別過頭不敢看,腦袋倒沒閒下來,我幻想他來自黑幫,午夜過後跟仇家狹路相逢,一言不合互劈起來,那會劈在身上哪部位呢?剛才飛快看了一眼,肩和腿都沒事,難道劈中了胸口?江湖格鬥,這樣下手會不會太兇殘?抑或這其實是工傷?說不定這男的在廚房工作,不小心弄傷了自己?但要搞出這麼大面積的傷口,那會是甚麼樣的工種?總不會宰豬殺牛時遇到反抗吧?我胡思亂想,總算暫時忘記那一大灘血,心神甫定,後面又傳來新一波鼎沸的人聲。我忍不住又回頭看,這一回,兩個神色慌張的少女急步跑上前來,前後左右合共四個警員,後頭拖著一大堆人,有人拿攝影機,估計是電視台,更多人只舉起了手機。劇情看來又有變了,看牌面,男傷者是爸爸,少女是女兒,那誰斬人呢?答案呼之欲出是她們的媽。我杜撰完這堆亂七八糟的情節,心定了。
少女被擋在診室外,記者旋即有默契地左右包抄,把兩個少女圍在中間。我在圍外看熱鬧,恨不得伸長耳朵聽足本問答。
「可不可以說說你們的感受?」
「接下來有甚麼計劃?」
這是甚麼蠢問題?為甚麼不直接問她們發生甚麼事?我更好奇了,從外圍擠進內圍,擠近一看,她倆薄施脂粉,輪廓分明,眼睛尤其大,看來有點眼熟,再看一會,想起來了,她們是樂壇新進組合,改了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叫「試管嬰兒」。前兩天在巴士上,我站在電視機前,被逼聽她們用可愛到叫人起雞皮的腔調解釋組合名字:「啊呀,公司覺得我們是新人,我們之前明明不認識,但又一起出道一起發展,就像試管一樣啦,又似BB啦,哈哈哈,所以就叫試管嬰兒囉。」
如果不是念在她們還算有三分姿色,這麼沒頭沒腦的訪問,誰看得下去?
真想不到,如今她們真人實物原大站在我面前。
「好亂,我個心好亂。」嬰兒一號說。
「好亂,我個心好亂。」嬰兒二號說。輪到我個心好亂,她們是試管嬰兒,又不是孖生嬰兒。
「究竟剛才發生了甚麼事?」終於有人問了一個我想問的問題。
「我們on show,有一個fan屎走來,想我們簽名,然後,然後……」嬰兒一號一派花容失色,說不下去。
嬰兒二號摟住一號的肩,深呼吸一口氣,說:「他拿出一把刀,然後,Michael,Michael就倒下了。」說到這裡,二號也崩潰了。
一個會帶刀找歌手簽名的人算不算fan屎?為何他拿出刀而Michael會自動倒下?說是倒下,為何入院時還會行會走,連擔架床也沒有?對嬰兒來說,這已經是極其艱深的邏輯問題。少女猶在慌失失,同一時間,一個穿了三吋高跟鞋的女人從走廊另一端碎步跑過來,人未到,鞋跟落地的聲音先到,我的注意力立即給轉移了。這女的上身一件黑色絲背心,頸上一串珍珠項鍊,米色四個骨褲,白色高跟鞋,這身打扮,在中環金鐘是常態,來到急症室就一反常態,我不禁多看兩眼,不看猶可,細看竟然又覺得眼熟,我之前在哪裡見過這人?
她看上去三十出頭,驟眼看算是眉清目秀,但眼神太鋒利,嘴唇特別薄,樣子兇巴巴的,一副生人勿近的戰鬥格局。她擋在試管嬰兒前面,嘴角向上翹,顯然是一個假笑。
「多謝記者朋友關心,由於案件已經交由警方處理,我們現階段沒有其他補充。兩個BB需要休息,希望大家幫幫手,給予她們空間,好不好?謝謝大家,謝謝!」
記者也沒追問下去,閃光燈對著哭泣的嬰兒又狂閃了一會,大概甚麼角度都齊全了,圍著的人陸續散開,不久,只剩我一人,呆呆的站在三個女人面前。
少女還在抽泣,惡女人邊安慰她們,邊滿有戒心的盯著我看。這張臉孔,我到底在哪兒見過?我病人才那幾十個,她長得還算標緻,真的幫她看過病,沒可能記不住她。會不會是那些從未打過招呼的鄰居?大學同過班但叫不出名字的同學甲乙丙丁戊?實在想不起,我也不慣跟陌生人這樣子互盯,正準備轉身離去時,不知一號還是二號驚叫了一下,旁邊那個渾身乏力昏倒在叫的人的懷裡,惡女人上前幫忙,力有不逮,眼看一號還是二號要掉在地上,我忙踏前一步,把她接住,順勢執起她的右手,在虎口位置大力按捏了幾下,她即醒過來,當發現整個人靠在我身上時,手還給我牽著,忙不及甩開我,腳步不穩的掙扎著站直身子。我扶著她在附近長椅坐下,為免被誤會是色狼,我正色道: 「我是中醫,請你放心,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幫你把一把脈。」嬰兒不愧是嬰兒,明明每個字都聽明白,就是不會自己做決定,只懂看著惡女人,惡女人點頭默許,她才怯生生地把手遞給我。
聽脈時,惡女人繼續緊盯著我,看得我心煩,表面上,我無論如何強裝鎮定,聽完左手聽右手,慢慢來。
沒把出甚麼異象,方才空氣不流通,她們又受了驚,呼吸不暢順,一時缺氧暈倒也很正常。把脈時,幾個醫護人員走過,向我們投以奇異目光,陪著她們進來的警察,竊竊私語,我隱約聽到有人說:「傻的嗎?中醫看急症?」
傻的嗎?以前未有西醫,人有急病時,還不是中醫給醫治?要說中醫不能看急症,你們以為中醫是甚麼?
我放下少女的手,溫言道:「別擔心,你身體很不錯,不過是受了一點驚,可以的話,待會喝一杯熱的玫瑰花茶,今晚會睡得好一點。」惡女人目睹一切,眼神放柔和了,主動在我身旁坐下,說:「謝謝你,未請教。」我伸手和她握了一下,答道:「小姓徐,徐啟寧。」她看進我雙眼裡去,問:「你真的是有牌中醫嗎?」難道我半夜三更來醫院玩角色扮演嗎?我沒好氣,打開背包,本來要找名片盒,手先碰到的卻是那張不知何時放進來的餐巾。飛快瞥一眼,先看到「小醫治病」四個字,這夜太多奇怪事了,心頭浮上一陣不安。
找到了名片,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多了的是公司名 – 流動中醫。
她拿著名片研究了好一會,再說話時,第一句就是:「你這樣子生存得到嗎?」
我當場啞了。我看來像死人嗎?我不是好端端在呼吸在生存是甚麼?
「可以的,那你呢?未請教。」
她這才如夢初醒的打開她的小皮包,抽出一張名片,雙手遞上時自我介紹:「我叫李知然,你可以叫我Sophia。」
李知然?這名字怎地那麼熟?我接過名片,全天后唱片公司,策略推廣總監,李知然。
我抬眼看李知然一眼,老天不是想跟我開甚麼玩笑吧?一小時前,我認識了一位李知而,一小時後,眼前出現了一位李知然,就算不是親姐妹,至少是堂姐妹。我想起李知而說,妹妹比她快活自由,因為她一年只見阿媽三次。
「徐醫師為甚麼在這裡?」李知然一言驚醒了我,是的,我為甚麼在這裡?
我記起了,我來,是因為那個叫我不要離開他的返來哥。擾攘了這麼一大輪,他現在在哪裡了?
我匆匆告別了李知然,來到詢問處探問,這才發現自己連問都不會問,姓甚名誰不知道,年齡不知道,身份證號碼更不會知道,我總不成問人,那個喝醉酒的返來哥在哪?
太多人看病,返來哥去向根本無人顧念,我倆萍水相逢,連話都沒講過一句,我竟然跟白車來了急症室,也夠匪夷所思。
站在慘白的燈光下,不知為何有點失落,打開背包,拿出那張餐巾。
小醫治病,中醫治人,大醫治國,上醫治心。
翻轉餐巾,背面有八個數目字,這是誰的電話號碼?我掏出手機,凌晨一時四十分,這鐘點打電話給人,會不會太像叫人起身尿尿的整蠱電話?
救護車不消五分鐘就來到,香港式效率,總是令人嘆服。對我來說,這五分鐘卻像一個世紀那麼長。小兄弟在我眼前昏厥過去的一刻,我想也沒想就掏出電話打九九九,電話接通,我跑到最近的燈柱,報上號碼,前後不需三十秒。一收線,聽到李知而在旁邊嘀咕:「自己不也是行醫的嗎?」
她聲線壓得低,我還是毫無遺漏地聽入耳了。這話如當頭棒喝,她確沒說錯,我完全沒想過自己也可以為他急救,枉我學醫多年,前面明擺著一個病人,我只知盡好市民之責,渾忘了另一個身分。
我假裝沒聽見她的說話。小兄弟面色蒼白,嘴角有白沫,平躺石壆上,我定一定心神,上前探他鼻息,好消息是未斷氣,壞消息是呼吸極微弱,手背放上額頭,感覺冰涼,顯然是體溫下降。這是牛飲啤酒的現眼報,酒醉一般不會死人,但飲到昏厥,另作別話。我解下背包,輕抬起他雙腳,用背包墊高,然後脫下風衣,放他胸上。我感到身後李知而銳利的目光。「你不要這樣盯著我好不好?」我沒回頭,看不到她的反應,半响,她說:「你們不是會按穴道嗎?這管用不管用?」
她這麼一問,我先想到太沖穴,不過又要脫鞋脫襪,太麻煩,情勢緊急,不如直接按勞宮穴?我背包有針,可以在人中和合谷施針,但轉念之間,又擔心這樣大動作,待救護員來到,怕解釋不了那麼多。為著這個念頭,我暗暗慚愧 – 我是貨真價實的中醫,救急扶危是天職,居然畏首畏尾,我到底在怕甚麼?
李知而哪裡知道我心內這麼多盤算,見我不回話,逕自走到小兄弟面前,二話不說,拇指對準人中穴壓下去。
我跑上前,輕輕抬起他的頭,示意李知而加大力度捏。
沒捏多久,小兄弟指尖抖了一下,未幾,悠悠醒轉。不遠處,兩個救護員急步跑來,我和李知而忙退下。這時才有空看一看錶,一時零五分。
救護員的一身白制服在深宵很亮眼,見到他們滿有信心,不慌不忙,我心完全安定下來。
「返來呀!返來……」小兄弟醒來,念念不忘的還是同一句話。
「你們認識的嗎?」其中一名救護員問。
「不認識。」李知而搶答似的回答。
我連她也說不上認識,孤獨都市,寂寞夜晚,滿街陌生人。
這時,警察也來了,對講機的沙沙聲,頓時增添了懸疑感。「誰人報案?」
我舉起手,像個笨笨的小學生。李知而忍不住笑了出來,說:「我們剛路過。」
警察看了我倆一眼,問:「那你倆又是甚麼關係?」
我幾乎沒衝口而出說 「關你甚麼事」,李知而先是呆了一下 ,過了一會才說:「朋友」。
警察再看了我們一眼,走近救護員,問:「情況如何呀手足?」
「醉酒,短暫昏迷,血壓偏低,但無大礙。他神智未清,要送院。」
警察彎下身,正對著小兄弟,問道:「哥仔,你叫甚麼名字?」「返來呀。」「拿身份證來看看。」「返來呀。」「你想要誰返來?他幾號電話號碼?」「返來呀。」
「返來哥」一件單衫,褲袋看來空空如也,搞不好連錢包也沒有。警察沒好氣,轉身對著對講機交代一些甚麼,救護員打開輪椅,我以為這段西灣河小插曲到此為止,沒料到在他們扶「返來哥」上輪椅的一刻,他忽然甩開了兩人,跌跌撞撞的撲到我跟前,一把抱住了我。
「不要離開我。」
他滿身酒氣,環抱我的雙手軟弱無力,頭埋進我的頸,嘴唇貼上來時,我大力推開了他。兩個救護員上前把他扶穩了,他睜開了眼睛,定睛看著我,又說了一遍:「不要離開我。」
不過是一瞬,但我肯定他眼神堅定,更肯定這不可能出現在一個酩酊大醉的人的臉上。但也只是一瞬,他又閉上眼,渾身無力的靠倒在救護員身上。
我像被甚麼懾住了,整個世界靜了下來,只重複聽見「不要離開我」五個字。
三分鐘後,我登上了救護車,車開走時,我看見李知而一臉不解跟我揮別。
小兄弟睡得香甜,救護員自顧自聊天,從沒上過白車的我,在搖晃中漸漸清醒過來:天啊,我在做甚麼?
凌晨時分的急症室比想像中多人。醫院的白光管,典型世界光,看上去是一片光明,但浮泛在候診病人頭上臉上的慘白,足以令我生起立即逃離的心。醫院最危險了,細菌病毒和病氣,應有盡有,打開背包想找個口罩,找不到,不意摸出了一條餐巾,拿來一看,上面歪歪斜斜的寫了幾行字:「小醫治病,中醫治人,大醫治國,上醫治心」。
我愣了一下,這東西,誰放進來的?
忽然人聲鼎沸,回頭看,兩個救護員分列兩旁,把一個滿身鮮血的男人架在膀子上。男人還能自己走路,可血從哪裡冒出我真的不敢看,他們經過我身邊時,我聽到幾下痛苦低吟。我別過頭不敢看,腦袋倒沒閒下來,我幻想他來自黑幫,午夜過後跟仇家狹路相逢,一言不合互劈起來,那會劈在身上哪部位呢?剛才飛快看了一眼,肩和腿都沒事,難道劈中了胸口?江湖格鬥,這樣下手會不會太兇殘?抑或這其實是工傷?說不定這男的在廚房工作,不小心弄傷了自己?但要搞出這麼大面積的傷口,那會是甚麼樣的工種?總不會宰豬殺牛時遇到反抗吧?我胡思亂想,總算暫時忘記那一大灘血,心神甫定,後面又傳來新一波鼎沸的人聲。我忍不住又回頭看,這一回,兩個神色慌張的少女急步跑上前來,前後左右合共四個警員,後頭拖著一大堆人,有人拿攝影機,估計是電視台,更多人只舉起了手機。劇情看來又有變了,看牌面,男傷者是爸爸,少女是女兒,那誰斬人呢?答案呼之欲出是她們的媽。我杜撰完這堆亂七八糟的情節,心定了。
少女被擋在診室外,記者旋即有默契地左右包抄,把兩個少女圍在中間。我在圍外看熱鬧,恨不得伸長耳朵聽足本問答。
「可不可以說說你們的感受?」
「接下來有甚麼計劃?」
這是甚麼蠢問題?為甚麼不直接問她們發生甚麼事?我更好奇了,從外圍擠進內圍,擠近一看,她倆薄施脂粉,輪廓分明,眼睛尤其大,看來有點眼熟,再看一會,想起來了,她們是樂壇新進組合,改了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叫「試管嬰兒」。前兩天在巴士上,我站在電視機前,被逼聽她們用可愛到叫人起雞皮的腔調解釋組合名字:「啊呀,公司覺得我們是新人,我們之前明明不認識,但又一起出道一起發展,就像試管一樣啦,又似BB啦,哈哈哈,所以就叫試管嬰兒囉。」
如果不是念在她們還算有三分姿色,這麼沒頭沒腦的訪問,誰看得下去?
真想不到,如今她們真人實物原大站在我面前。
「好亂,我個心好亂。」嬰兒一號說。
「好亂,我個心好亂。」嬰兒二號說。輪到我個心好亂,她們是試管嬰兒,又不是孖生嬰兒。
「究竟剛才發生了甚麼事?」終於有人問了一個我想問的問題。
「我們on show,有一個fan屎走來,想我們簽名,然後,然後……」嬰兒一號一派花容失色,說不下去。
嬰兒二號摟住一號的肩,深呼吸一口氣,說:「他拿出一把刀,然後,Michael,Michael就倒下了。」說到這裡,二號也崩潰了。
一個會帶刀找歌手簽名的人算不算fan屎?為何他拿出刀而Michael會自動倒下?說是倒下,為何入院時還會行會走,連擔架床也沒有?對嬰兒來說,這已經是極其艱深的邏輯問題。少女猶在慌失失,同一時間,一個穿了三吋高跟鞋的女人從走廊另一端碎步跑過來,人未到,鞋跟落地的聲音先到,我的注意力立即給轉移了。這女的上身一件黑色絲背心,頸上一串珍珠項鍊,米色四個骨褲,白色高跟鞋,這身打扮,在中環金鐘是常態,來到急症室就一反常態,我不禁多看兩眼,不看猶可,細看竟然又覺得眼熟,我之前在哪裡見過這人?
她看上去三十出頭,驟眼看算是眉清目秀,但眼神太鋒利,嘴唇特別薄,樣子兇巴巴的,一副生人勿近的戰鬥格局。她擋在試管嬰兒前面,嘴角向上翹,顯然是一個假笑。
「多謝記者朋友關心,由於案件已經交由警方處理,我們現階段沒有其他補充。兩個BB需要休息,希望大家幫幫手,給予她們空間,好不好?謝謝大家,謝謝!」
記者也沒追問下去,閃光燈對著哭泣的嬰兒又狂閃了一會,大概甚麼角度都齊全了,圍著的人陸續散開,不久,只剩我一人,呆呆的站在三個女人面前。
少女還在抽泣,惡女人邊安慰她們,邊滿有戒心的盯著我看。這張臉孔,我到底在哪兒見過?我病人才那幾十個,她長得還算標緻,真的幫她看過病,沒可能記不住她。會不會是那些從未打過招呼的鄰居?大學同過班但叫不出名字的同學甲乙丙丁戊?實在想不起,我也不慣跟陌生人這樣子互盯,正準備轉身離去時,不知一號還是二號驚叫了一下,旁邊那個渾身乏力昏倒在叫的人的懷裡,惡女人上前幫忙,力有不逮,眼看一號還是二號要掉在地上,我忙踏前一步,把她接住,順勢執起她的右手,在虎口位置大力按捏了幾下,她即醒過來,當發現整個人靠在我身上時,手還給我牽著,忙不及甩開我,腳步不穩的掙扎著站直身子。我扶著她在附近長椅坐下,為免被誤會是色狼,我正色道: 「我是中醫,請你放心,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幫你把一把脈。」嬰兒不愧是嬰兒,明明每個字都聽明白,就是不會自己做決定,只懂看著惡女人,惡女人點頭默許,她才怯生生地把手遞給我。
聽脈時,惡女人繼續緊盯著我,看得我心煩,表面上,我無論如何強裝鎮定,聽完左手聽右手,慢慢來。
沒把出甚麼異象,方才空氣不流通,她們又受了驚,呼吸不暢順,一時缺氧暈倒也很正常。把脈時,幾個醫護人員走過,向我們投以奇異目光,陪著她們進來的警察,竊竊私語,我隱約聽到有人說:「傻的嗎?中醫看急症?」
傻的嗎?以前未有西醫,人有急病時,還不是中醫給醫治?要說中醫不能看急症,你們以為中醫是甚麼?
我放下少女的手,溫言道:「別擔心,你身體很不錯,不過是受了一點驚,可以的話,待會喝一杯熱的玫瑰花茶,今晚會睡得好一點。」惡女人目睹一切,眼神放柔和了,主動在我身旁坐下,說:「謝謝你,未請教。」我伸手和她握了一下,答道:「小姓徐,徐啟寧。」她看進我雙眼裡去,問:「你真的是有牌中醫嗎?」難道我半夜三更來醫院玩角色扮演嗎?我沒好氣,打開背包,本來要找名片盒,手先碰到的卻是那張不知何時放進來的餐巾。飛快瞥一眼,先看到「小醫治病」四個字,這夜太多奇怪事了,心頭浮上一陣不安。
找到了名片,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多了的是公司名 – 流動中醫。
她拿著名片研究了好一會,再說話時,第一句就是:「你這樣子生存得到嗎?」
我當場啞了。我看來像死人嗎?我不是好端端在呼吸在生存是甚麼?
「可以的,那你呢?未請教。」
她這才如夢初醒的打開她的小皮包,抽出一張名片,雙手遞上時自我介紹:「我叫李知然,你可以叫我Sophia。」
李知然?這名字怎地那麼熟?我接過名片,全天后唱片公司,策略推廣總監,李知然。
我抬眼看李知然一眼,老天不是想跟我開甚麼玩笑吧?一小時前,我認識了一位李知而,一小時後,眼前出現了一位李知然,就算不是親姐妹,至少是堂姐妹。我想起李知而說,妹妹比她快活自由,因為她一年只見阿媽三次。
「徐醫師為甚麼在這裡?」李知然一言驚醒了我,是的,我為甚麼在這裡?
我記起了,我來,是因為那個叫我不要離開他的返來哥。擾攘了這麼一大輪,他現在在哪裡了?
我匆匆告別了李知然,來到詢問處探問,這才發現自己連問都不會問,姓甚名誰不知道,年齡不知道,身份證號碼更不會知道,我總不成問人,那個喝醉酒的返來哥在哪?
太多人看病,返來哥去向根本無人顧念,我倆萍水相逢,連話都沒講過一句,我竟然跟白車來了急症室,也夠匪夷所思。
站在慘白的燈光下,不知為何有點失落,打開背包,拿出那張餐巾。
小醫治病,中醫治人,大醫治國,上醫治心。
翻轉餐巾,背面有八個數目字,這是誰的電話號碼?我掏出手機,凌晨一時四十分,這鐘點打電話給人,會不會太像叫人起身尿尿的整蠱電話?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