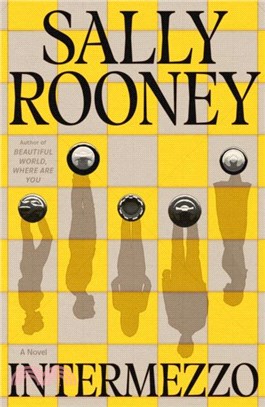遠藤周作短篇小說集
商品資訊
系列名:新世紀叢書
ISBN13:9789863600657
替代書名:えんどうしゅうさくたんぺんしょうせつしゅう
出版社:立緒文化
作者:遠藤周作
譯者:林水福
出版日:2016/08/05
裝訂/頁數:平裝/304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版次:1
定價
:NT$ 350 元優惠價
:90 折 315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9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完整記錄遠藤周作之創作脈絡
既溫暖又憂傷的短篇小說選
生之意義的探尋
愛會傷人――在那瞬間,連「祂」也選擇了沉默
遠藤的小說就像汩汩滲血的痂,
那是一種名為「遺憾」的心傷。
「我寫短篇小說往往是長篇小說的伏線,或者是長篇小說的試作。如果長篇小說是太陽,那麼它前後的短篇小說就是環繞太陽的幾個衛星。」遠藤周作如是言。本書所輯選的短篇小說,便是構成整個遠藤文學太陽系的點點繁星。
遠藤一生創作皆離不開宗教與人性的探索,本書亦不離此主軸。在描述不同主角與母親、父親之間的情感互動,以及夫婦、情人之間的關係牽絆中,將精湛出色的人物描寫與其對宗教信仰的情懷合而為一,帶出自父性中脫胎蛻變,轉移成尋求日本宗教「母性」本質的心路歷程,在多篇小說中均可看出作者之用心著墨。
遠藤曾經因肺病而度過一段長期住院的日子,這段與死神搏鬥的病中歲月亦被轉化為小說創作的養分。生病往往是人心最脆弱無助的時刻,也最能顯露出赤裸的人性,以此為基礎,遠藤的文字不僅糅合了自身經驗的實際描述,更在深入挖掘人性陰暗面的同時,不忘努力映照出人性的光明面,即使是在冰冷殘酷的醫院病房中,世間暖流始終會從各種艱難的夾縫中挹注,撫慰人心。
愛與病,世上最折磨人的兩樣東西,在這本短篇小說集中有了完整且多面向的體現,同時也是人心的照鏡,照出了慾望、貪婪、自私之惡,也映出了同情、理解、悲憫之善,這是遠藤周作向來關注且拿手的主題――探尋生之意義,透過作者沉著而犀利的筆鋒,挑動著讀者每一絲憂傷與感動。
各篇小說的主角與場景或許予人似曾相識之感,但聚焦主題卻截然不同,如同作者所言,是長篇小說的伏線或試作,亦可看出遠藤身為一位專業小說家,在取材與設定上是如何不斷嘗試諸多可能性,若稍加留意,便可窺見其長篇大作的創作軌跡。而做為一本短篇小說選輯,各獨立篇章之間看似纏繞實則無涉,看似無關卻又互為表裡的,讀之更令人完全沉浸於遠藤的小說世界。
※本書文章選錄自《海與毒藥》(2006年版)並重新校訂。
既溫暖又憂傷的短篇小說選
生之意義的探尋
愛會傷人――在那瞬間,連「祂」也選擇了沉默
遠藤的小說就像汩汩滲血的痂,
那是一種名為「遺憾」的心傷。
「我寫短篇小說往往是長篇小說的伏線,或者是長篇小說的試作。如果長篇小說是太陽,那麼它前後的短篇小說就是環繞太陽的幾個衛星。」遠藤周作如是言。本書所輯選的短篇小說,便是構成整個遠藤文學太陽系的點點繁星。
遠藤一生創作皆離不開宗教與人性的探索,本書亦不離此主軸。在描述不同主角與母親、父親之間的情感互動,以及夫婦、情人之間的關係牽絆中,將精湛出色的人物描寫與其對宗教信仰的情懷合而為一,帶出自父性中脫胎蛻變,轉移成尋求日本宗教「母性」本質的心路歷程,在多篇小說中均可看出作者之用心著墨。
遠藤曾經因肺病而度過一段長期住院的日子,這段與死神搏鬥的病中歲月亦被轉化為小說創作的養分。生病往往是人心最脆弱無助的時刻,也最能顯露出赤裸的人性,以此為基礎,遠藤的文字不僅糅合了自身經驗的實際描述,更在深入挖掘人性陰暗面的同時,不忘努力映照出人性的光明面,即使是在冰冷殘酷的醫院病房中,世間暖流始終會從各種艱難的夾縫中挹注,撫慰人心。
愛與病,世上最折磨人的兩樣東西,在這本短篇小說集中有了完整且多面向的體現,同時也是人心的照鏡,照出了慾望、貪婪、自私之惡,也映出了同情、理解、悲憫之善,這是遠藤周作向來關注且拿手的主題――探尋生之意義,透過作者沉著而犀利的筆鋒,挑動著讀者每一絲憂傷與感動。
各篇小說的主角與場景或許予人似曾相識之感,但聚焦主題卻截然不同,如同作者所言,是長篇小說的伏線或試作,亦可看出遠藤身為一位專業小說家,在取材與設定上是如何不斷嘗試諸多可能性,若稍加留意,便可窺見其長篇大作的創作軌跡。而做為一本短篇小說選輯,各獨立篇章之間看似纏繞實則無涉,看似無關卻又互為表裡的,讀之更令人完全沉浸於遠藤的小說世界。
※本書文章選錄自《海與毒藥》(2006年版)並重新校訂。
作者簡介
遠藤周作
近代日本文學大家。一九二三年生於東京,慶應大學法文系畢業,別號狐狸庵山人,曾先後獲芥川獎、谷崎潤一郎獎等多項日本文學大獎,一九九五年獲日本文化勳章。遠藤承襲了自夏目漱石、經芥川龍之介至崛辰雄一脈相傳的傳統,在近代日本文學中居承先啟後的地位。
生於東京、在中國大連度過童年的遠藤周作,於一九三三年隨離婚的母親回到日本;由於身體虛弱,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未被徵召入伍,而進入慶應大學攻讀法國文學,並在一九五○年成為日本戰後第一批留學生,前往法國里昂大學留學達二年之久。
回到日本之後,遠藤周作隨即展開了他的作家生涯。作品有以宗教信仰為主的,也有老少咸宜的通俗小說,著有《母親》、《影子》、《醜聞》、《海與毒藥》、《沉默》、《武士》、《深河》、《深河創作日記》等書。一九九六年九月辭世,享年七十三歲。
近代日本文學大家。一九二三年生於東京,慶應大學法文系畢業,別號狐狸庵山人,曾先後獲芥川獎、谷崎潤一郎獎等多項日本文學大獎,一九九五年獲日本文化勳章。遠藤承襲了自夏目漱石、經芥川龍之介至崛辰雄一脈相傳的傳統,在近代日本文學中居承先啟後的地位。
生於東京、在中國大連度過童年的遠藤周作,於一九三三年隨離婚的母親回到日本;由於身體虛弱,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未被徵召入伍,而進入慶應大學攻讀法國文學,並在一九五○年成為日本戰後第一批留學生,前往法國里昂大學留學達二年之久。
回到日本之後,遠藤周作隨即展開了他的作家生涯。作品有以宗教信仰為主的,也有老少咸宜的通俗小說,著有《母親》、《影子》、《醜聞》、《海與毒藥》、《沉默》、《武士》、《深河》、《深河創作日記》等書。一九九六年九月辭世,享年七十三歲。
序
導讀 遠藤文學的太陽與衛星╱林水福
本書收錄的短篇小說,皆與遠藤周作的宗教信仰和療養生活有關。
遠藤一輩子以宗教為主題創作小說,很長一段時間思考基督宗教在日本紮根的問題。對於明治時代的思想家、宗教家內村鑑三強調聖經中的「父性」──對於犯錯的孩子嚴加處罰,不輕易寬恕──部分,遠藤認為有礙基督宗教的傳播,因此,特別強調聖經另一面的「母性」──孩子犯錯時給予安慰,幫孩子在父親面前講話,取得寬恕、原諒──部分。
一九六九年一月發表於《新潮》雜誌的〈母親〉,是將日本人在宗教中追求的精神志向「母性」,與自身對母親的懷念、憧憬,和信仰的軌跡重疊的傑作。末尾部分「……在日本隱匿的天主教徒中,不知何時他們拋棄了不合適的規條,把它轉變成純日本式的宗教之本質──即對母親的思慕。那時,我也想起自己的母親,而母親灰色的影子也正在我身旁,不是拉小提琴的姿態,也不是捏著念珠的姿態,而是站著兩手交叉胸前,用微帶哀傷的眼神注視著我。」
〈母親〉是將人物描寫與宗教信仰問題融合為一的傑作。
與八哥有關的有兩篇,即〈男人與八哥〉和〈四十歲的男人〉。兩篇裡出現的八哥,與其他短篇中出現的狗,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動物形象的鳥與狗,而是雙重或多重形象的重疊與融合。
一九六○年遠藤過著長期住院的療養生活,翌年,肺部動過兩次手術失敗後,遠藤買了八哥飼養。深夜醒過來,在黑暗中注視著八哥,而八哥也歪著頭看他,宛如信徒對神父告解般。有的晚上八哥扮演神父的角色,有的晚上八哥是遠藤信仰動搖、疑惑的唯一傾訴者。第三次手術成功,總算把遠藤從鬼門關召回,然而等到他回到病房時,發現八哥已死,因此,遠藤直覺認為八哥是替他而死的。尤其是〈男人與八哥〉中,遠藤藉著飼養八哥過程,運用諷刺筆調,描繪人性的自私和自己信仰的動搖,也隱約透露出遠藤獨特的「母性宗教」觀。
〈雜樹林中的醫院〉係〈我.拋棄了的.女人〉的試作之一,但兩者之間揭示的理念、思想顯然不同,筆調當然不同。〈我.拋棄了的.女人〉中,作者重點擺在森田蜜身上,透過她平凡卻坎坷的一生,道出真正的愛是什麼?無瑕的愛是什麼?最後,她到達了凡人無可企及的崇高境界。作品中對神職人員修女並無責難之意。而〈雜樹林中的醫院〉中,顯然作者並未安排明顯的主角,而是以「病房」為故事的舞臺,以諷刺手法描繪人的自私與不必要的炫耀心理,從而呼籲人應分擔他人的痛苦與悲傷。對病房的管理者──修女,有所針砭。作者反諷的手法跟芥川龍之介的〈手巾〉有點類似。
遠藤童年時代非自願的受洗,在往後的人生當中,有好幾次甚至想拋棄它。〈歸鄉〉與〈大病房〉表面上素材雖然不同,但追尋母性基督的痛苦步履則一。〈歸鄉〉的最後一段:
走出十六號館,耀眼的陽光照射到我的眼睛。我忍耐著輕微的暈眩,從巴士和高中生之間穿過,妹妹還呆呆地站在剛才的樹蔭下。我感到疲倦,可是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襪子已緊緊地黏在腳底上了。
最後一句,「襪子已緊緊地黏在腳底上了」,並非只是單純的表面上的事實描寫,它的背後透露出主角對自己的信仰,經過一番追尋、掙扎之後,儘管感覺上並不那麼舒服,但是他知道無論如何是拋棄不了的;在看似無奈的語氣中,透露出堅定而執著的訊息。
〈童話〉與〈我的東西〉同為遠藤描繪信仰生活動搖不安的作品。尤其是〈我的東西〉中,透露出作者受洗的動機和經過,對非自由意志下選擇的信仰的痛苦,有鮮活而確切的描述。〈童話〉中背叛母親的烏鴉,到了〈我的東西〉中的勝呂,為了不想背叛母親,因此違背父意選擇別的女人為妻,理由是「不是因為喜歡才選擇她,而是因為懦弱才和她結婚的」。如果將兩篇作品一起閱讀,或許會產生主角的感情從父親轉移到母親身上的感覺,事實上遠藤想表達的是他從父性轉移到母性的宗教觀。
遠藤短篇小說的素材常取材自自己的私生活,但絕非「私小說」。素材不能與作品畫上等號,讀者參考年表,即可看出哪些是事實,哪些是加以改造的。再者,有些素材或似曾相識,但仔細閱讀可發現作者想要表達的主題不同,寫作手法也不一!由此可以瞭解遠藤創作的軌跡以及從短篇發展成為長篇的過程與經營的苦心。
遠藤周作曾談到他自己的長篇與短篇之間的關係,他說:「我寫短篇小說往往是長篇小說的伏線,或者是長篇小說的試作。如果長篇小說是太陽,那麼它前後的短篇小說就是環繞太陽的幾個衛星。」
太陽固然燦爛奪目,而環繞太陽的幾個衛星亦各擅勝場,值得瀏覽。以整個遠藤周作太陽系文學而言,太陽與衛星皆為構成分子,不容忽略。
本書收錄的短篇小說,皆與遠藤周作的宗教信仰和療養生活有關。
遠藤一輩子以宗教為主題創作小說,很長一段時間思考基督宗教在日本紮根的問題。對於明治時代的思想家、宗教家內村鑑三強調聖經中的「父性」──對於犯錯的孩子嚴加處罰,不輕易寬恕──部分,遠藤認為有礙基督宗教的傳播,因此,特別強調聖經另一面的「母性」──孩子犯錯時給予安慰,幫孩子在父親面前講話,取得寬恕、原諒──部分。
一九六九年一月發表於《新潮》雜誌的〈母親〉,是將日本人在宗教中追求的精神志向「母性」,與自身對母親的懷念、憧憬,和信仰的軌跡重疊的傑作。末尾部分「……在日本隱匿的天主教徒中,不知何時他們拋棄了不合適的規條,把它轉變成純日本式的宗教之本質──即對母親的思慕。那時,我也想起自己的母親,而母親灰色的影子也正在我身旁,不是拉小提琴的姿態,也不是捏著念珠的姿態,而是站著兩手交叉胸前,用微帶哀傷的眼神注視著我。」
〈母親〉是將人物描寫與宗教信仰問題融合為一的傑作。
與八哥有關的有兩篇,即〈男人與八哥〉和〈四十歲的男人〉。兩篇裡出現的八哥,與其他短篇中出現的狗,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動物形象的鳥與狗,而是雙重或多重形象的重疊與融合。
一九六○年遠藤過著長期住院的療養生活,翌年,肺部動過兩次手術失敗後,遠藤買了八哥飼養。深夜醒過來,在黑暗中注視著八哥,而八哥也歪著頭看他,宛如信徒對神父告解般。有的晚上八哥扮演神父的角色,有的晚上八哥是遠藤信仰動搖、疑惑的唯一傾訴者。第三次手術成功,總算把遠藤從鬼門關召回,然而等到他回到病房時,發現八哥已死,因此,遠藤直覺認為八哥是替他而死的。尤其是〈男人與八哥〉中,遠藤藉著飼養八哥過程,運用諷刺筆調,描繪人性的自私和自己信仰的動搖,也隱約透露出遠藤獨特的「母性宗教」觀。
〈雜樹林中的醫院〉係〈我.拋棄了的.女人〉的試作之一,但兩者之間揭示的理念、思想顯然不同,筆調當然不同。〈我.拋棄了的.女人〉中,作者重點擺在森田蜜身上,透過她平凡卻坎坷的一生,道出真正的愛是什麼?無瑕的愛是什麼?最後,她到達了凡人無可企及的崇高境界。作品中對神職人員修女並無責難之意。而〈雜樹林中的醫院〉中,顯然作者並未安排明顯的主角,而是以「病房」為故事的舞臺,以諷刺手法描繪人的自私與不必要的炫耀心理,從而呼籲人應分擔他人的痛苦與悲傷。對病房的管理者──修女,有所針砭。作者反諷的手法跟芥川龍之介的〈手巾〉有點類似。
遠藤童年時代非自願的受洗,在往後的人生當中,有好幾次甚至想拋棄它。〈歸鄉〉與〈大病房〉表面上素材雖然不同,但追尋母性基督的痛苦步履則一。〈歸鄉〉的最後一段:
走出十六號館,耀眼的陽光照射到我的眼睛。我忍耐著輕微的暈眩,從巴士和高中生之間穿過,妹妹還呆呆地站在剛才的樹蔭下。我感到疲倦,可是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襪子已緊緊地黏在腳底上了。
最後一句,「襪子已緊緊地黏在腳底上了」,並非只是單純的表面上的事實描寫,它的背後透露出主角對自己的信仰,經過一番追尋、掙扎之後,儘管感覺上並不那麼舒服,但是他知道無論如何是拋棄不了的;在看似無奈的語氣中,透露出堅定而執著的訊息。
〈童話〉與〈我的東西〉同為遠藤描繪信仰生活動搖不安的作品。尤其是〈我的東西〉中,透露出作者受洗的動機和經過,對非自由意志下選擇的信仰的痛苦,有鮮活而確切的描述。〈童話〉中背叛母親的烏鴉,到了〈我的東西〉中的勝呂,為了不想背叛母親,因此違背父意選擇別的女人為妻,理由是「不是因為喜歡才選擇她,而是因為懦弱才和她結婚的」。如果將兩篇作品一起閱讀,或許會產生主角的感情從父親轉移到母親身上的感覺,事實上遠藤想表達的是他從父性轉移到母性的宗教觀。
遠藤短篇小說的素材常取材自自己的私生活,但絕非「私小說」。素材不能與作品畫上等號,讀者參考年表,即可看出哪些是事實,哪些是加以改造的。再者,有些素材或似曾相識,但仔細閱讀可發現作者想要表達的主題不同,寫作手法也不一!由此可以瞭解遠藤創作的軌跡以及從短篇發展成為長篇的過程與經營的苦心。
遠藤周作曾談到他自己的長篇與短篇之間的關係,他說:「我寫短篇小說往往是長篇小說的伏線,或者是長篇小說的試作。如果長篇小說是太陽,那麼它前後的短篇小說就是環繞太陽的幾個衛星。」
太陽固然燦爛奪目,而環繞太陽的幾個衛星亦各擅勝場,值得瀏覽。以整個遠藤周作太陽系文學而言,太陽與衛星皆為構成分子,不容忽略。
目次
導讀――遠藤文學的太陽與衛星╱林水福
1 童話
2 六天的旅行
3 手指
4 歸鄉
5 雜種狗
6 耽擱
7 母親
8 我的東西
9 化妝後的世界
10 男人與八哥
11 四十歲的男人
12 大病房
13雜樹林中的醫院
遠藤周作年表
1 童話
2 六天的旅行
3 手指
4 歸鄉
5 雜種狗
6 耽擱
7 母親
8 我的東西
9 化妝後的世界
10 男人與八哥
11 四十歲的男人
12 大病房
13雜樹林中的醫院
遠藤周作年表
書摘/試閱
母親
還記得向母親撒過謊話。
現在想來,我的謊言是出自對母親的情結(complex)。被丈夫拋棄的痛楚,除了藉信仰得到慰藉之外,別無他法的母親,把曾為了尋找一個小提琴音符的熱誠,轉移到對神的真誠;現在我已能夠瞭解那種執著的心情,可是,當時的我,卻感到透不過氣來。她越要求我信奉和她相同的信仰,我就更像溺水的少年,為了抵抗水壓而更加努力掙扎。
同學中有個叫田村的,是西宮煙花巷的兒子。肚子老是纏著髒兮兮的繃帶,經常請假;或許從那時起就患了肺結核,我接近被好學生瞧不起的他,的確是出自對母親嚴厲管教的反抗心情。
田村第一次教我抽菸時,我感覺像犯了滔天大罪似的。在學校的射箭場後面,田村邊注意著周遭的動靜,邊從制服的口袋裡,偷偷掏出一包皺巴巴的香菸。
「先用力吸,等受不了時,再噴出來!」
我咳嗽了,菸味刺激鼻子和喉嚨,很難受。那一瞬間眼前又浮現母親的容顏,那是在微暗中從被窩起來,捏著念珠祈禱的臉。為了驅走那張臉,我更用力吸起菸來。
從學校的回家途中溜去看電影,也是跟田村學的。跟在田村的後面,躲躲閃閃地進入在西宮阪神火車站附近的二番館。館內黑漆漆的,也不知從哪裡飄來廁所的臭味。在小孩的哭聲、老人的咳嗽聲中,聽得到放映機旋轉的單調音律。我腦子裡只盡想著母親現在在做什麼呢?「我們回去吧!」
催了田村好幾次,他生氣了。
「囉哩八嗦的傢伙,要回去,你自個兒回去好了!」
走出電影院,載滿下班人潮的阪神電車,從我們面前經過。
「怕老媽怕成那樣子!」田村嘲笑似地聳聳肩。「編個故事不就得了!」
和他分開後,我卻還編不出謊話來。
「因為學校補課,還有,考試的日期也近了。」
我屏住氣息,一口氣說出來,看到母親相信的樣子,我心裡一陣疼痛,但同時也有一種滿足感。
說老實話,我根本沒有真正的信仰,母親要我上教會,我只是交叉著手,裝出祈禱的樣子,心裡卻想些別的事情,想到後來和田村一起去看電影,裡面出現的種種鏡頭;有一次眼前甚至浮現出某日田村偷偷讓我看的春宮照片。禮拜堂內,信徒們一會兒跪下、一會兒起立,跟著主持彌撒的神父祈禱。我試著不去胡思亂想,它卻嘲諷似地拚命在我眼前晃漾。
我不知道母親為何會相信這樣的東西,感覺上,神父的話、《聖經》的故事和十字架,都和自己沒什麼關係,就像是沒有真實感的往事。我懷疑一到星期日,大家聚集到這裡來,一邊咳嗽一邊斥責孩子,雙手合掌時的心情,有時,我對那樣的自己感到懊惱,也覺得對不起母親;我祈禱要是真有神存在,希望也能賜給我那樣的信仰精神,可是,這祈禱並沒有改變我的心情。
最後,我停止了每天早上的彌撒,我的藉口是要準備考試。從那時起,總會若無其事地躺在床上,聽患有心臟病的母親,即使在冬天的清晨,也一個人出門上教會的腳步聲。不久之後,連一星期非去一次不可的週日彌撒也開溜了!母親後腳一踏出家門,我就跑到西宮購物人潮聚集的鬧區閒逛,看電影院的廣告招牌消磨時間。
從那時候起,母親經常感到呼吸困難。走在路上,有時會用一隻手按著胸部,蹙著眉站立不動,我根本沒把它當一回事,對十六歲的少年而言,想像不出死亡的恐怖,而且發作只是暫時性的,五分鐘過後,又恢復正常,因此認為不是什麼大病;事實上,那是長期的痛苦與疲勞,使她的心臟變得衰弱。儘管如此,母親仍舊每天早晨五點起床,拖著沉重的步伐,在毫無人跡的路上,走到電車站,教會在搭上電車的第二站。
一個星期六,我抗拒不了誘惑,在上學途中下車,溜到鬧區。把書包寄放在那時和田村常去的咖啡屋。到電影開演為止,還有段相當長的時間,口袋裡有一張一圓的鈔票,那是幾天前從母親的錢包裡拿的。我養成了有時自己開母親錢包的習慣。看電影直至黃昏,然後若無其事地踏上歸途。
打開玄關,沒想到母親就站在那裡,一句話也沒說,直盯著我看,突然,她的臉慢慢扭曲,在那扭曲的臉頰上眼淚緩緩地掉下,我知道從學校來的電話,把一切都洩露出去了。那一晚,母親在鄰室一直啜泣到深夜,我用手指塞住耳朵,盡量不去聽那聲音,可是,母親的哭泣聲仍然傳到鼓膜來,我並不後悔,反而想著怎麼收拾這場面才好。
請人帶我到村公所觀賞出土物時,窗外已開始泛白,抬頭仰望天空,雨似乎已停了。
「到學校那邊去,或許可以看到東西吧!」
站在旁邊名叫中村的村長助理擔心地問。他的表情有如在說這裡什麼都沒有是他自己的責任似的。村公所和小學裡有的東西,都不是我想看的隱匿天主教徒的遺物,只不過是小學老師們挖掘出來的上代的土器破片罷了。
「譬如他們的念珠或十字架等,都沒有嗎?」
中村惶恐地搖搖頭。
「隱匿的天主教徒喜歡隱密,因此除了直接去找他們之外,別無他法。那一票人都是些乖僻的傢伙!」
和次郎一樣,我從中村的話裡也聽得出他對隱匿的天主教徒,有種輕蔑的心態。
去打聽天氣狀況的次郎回來了。
「已經恢復正常了,明天沒有問題嗎?這樣的話,我們現在去岩島瀏覽一下好嗎?」他慫恿我,因為在這之前,即在「切支丹」墳墓那兒時,我就曾請他想辦法帶我去岩島。
助理馬上打電話給漁業公會;這種時候村公所就很方便了,公會很快就派出一艘裝有馬達的小船。
向中村借了雨衣,連同次郎三個人趕到港口,有一位漁師準備好船,在被雨淋濕的木板上,鋪上草蓆讓我坐,腳下污水淤積,水中漂著一條死了的銀色小魚。
馬達發出聲響,船向波濤洶湧的海上出發,漸漸激烈地搖晃起來,浪頭高揚時,有種輕微的快感,可是海浪翻落,胃好像突然被束緊。
「岩島是很好的釣魚場哦!我們經常在假日去,您是否也釣魚呢?」
我搖搖頭,助理就趕忙向沮喪著臉的次郎和漁師吹噓曾釣到大黑鯛的得意事。
雨衣全給水花打濕了,海風很冷,從剛剛開始,我一直緊閉著嘴巴。是啊,剛剛還是鉛色的海面,到了這裡卻變成黑色,似乎很冷。我想起四世紀之前,被綁成珠串的信徒在這裡被拋入海中,自己要是生在那個時代,也沒有信心一定能忍受得了那樣的刑罰。我突然憶起母親;在西宮的鬧區遊蕩,向母親撒謊時的自己,又在心中甦醒過來。
岩島逐漸近了,果如其名,到處都是岩石的小島,山頂上有少許的灌木。問了助理,才知道這裡除了郵政部的職員偶爾會來巡視一下之外,只能當村民的釣魚場。
約有十隻烏鴉,在頭頂上盤旋,發出沙啞的叫聲,撕開了灰濛濛的雨空,荒涼的景象,令人覺得不舒暢。可以清楚地看到岩石的裂痕和凹凸怪狀,波浪撞擊岩石發出激烈的聲音,揚起白色的浪花。
我問信徒們被推下海的斷崖在哪裡,助理和次郎都不知道。或許不是固定的一個地方,而是從各個地方推下去的吧!
「好恐怖的事!」
「現在無論如何想像不出。」
我從剛剛一直思考的事,在同樣是天主教徒的助理和次郎的意識上,似乎並未浮現過。
「這個洞穴有很多蝙蝠,只要一接近,就可聽到吱吱的叫聲。」
「真是奇妙!牠們飛得那麼快,就是不會碰在一起,身上好像有雷達之類的東西。」
「我們是否繞一圈之後回去呢?」
白色的波浪凶暴地侵蝕著島的裡側,雲散雨停,島上小山的山腹逐漸清晰可辨。
「隱匿的天主教部落就在那一帶。」
助理指著那座山的方向,和昨夜神父指的方向一致。
「現在和他們也有來往嗎?」
「欸!學校裡的一個工友就是,叫下村,是那部落的人,不過,就是有點討厭,話談不來!」
根據兩人的說法,村裡的天主教信徒不太願意和隱匿的天主教徒來往或結婚,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不同,不如說是心理上的對立所產生的。隱匿的天主教徒彼此互相通婚,否則就維持不了自己的信仰,這種習慣使大家把他們當成特殊份子看待,即使現在亦如此。
一半在雲霧覆罩下的那座山之山腹,三百年來隱匿的天主教徒們,跟其他躲藏的部落一樣,決定「挑水」、「輸送」、「聯絡」等工作人員,對外絕不洩露他們的組織祕密,一直遵守著他們信仰;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傳給兒子,一代一代地傳下「祈禱」,在黑暗的倉庫中,奉祀著他們的信仰。我用看某種荒涼景象的心情,在山腹中尋找那孤立的部落;當然,從這個位置是看不到的。
「對那些乖僻的傢伙,您怎麼會感興趣呢?」
助理覺得很奇怪地問我,我隨便敷衍過去。
是一個秋晴的日子,拿著菊花上墳,母親的墳墓在府中市天主教墓地。從學生時代開始,在通往墓地的路上,不知來回幾趟。從前,路的兩側有一大片栗子和橡的雜樹林跟麥田,春天到來時,是很好的散步小道;可是,現在已變成筆直的大馬路,商店櫛比鱗次,連那時孤立墓地前的一間小石屋,如今都改建成兩層樓的建築物了。每次來這裡,往事浮湧心頭。大學畢業的那天也來上墳;到法國留學上船的前一天也來過;生了大病回到日本的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這裡來;結婚時、入院時,都不忘回到這裡。現在有時還瞞著妻子來掃墓,因為這裡是我不想對任何人提起的、母親和我談話的地方,內心深處甚且希望即使是親人,也不要常來打擾。穿過小路,墓地正中央有聖母像,四周有一列排列非常整齊的石墓碑,這是屍骨葬在日本的修女墓地,以此為中心,有白色的十字架和石墓,明亮的陽光照耀著,寂靜包圍了所有的墳墓。
母親的墳墓很小,看到那小小的墓石,心裡一陣抽痛。拔除四周的雜草,蟲在我的旁邊飛來飛去,發出拍翅的聲音。除了蟲聲之外,聽不到其他任何聲音。
在墓碑上澆水,跟往常一樣,想起母親去世的那一天,對我來說,那是極為難堪的回憶。母親心臟病發作倒在走廊上,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我並不在她身旁,那時,我在田村家做著母親若看到一定會傷心的事。
那時田村從自己的抽屜,拿出用報紙包著、像明信片的東西,然後臉上浮現出要偷偷告訴我什麼的那種淺笑。
「這跟一般賣的東西不一樣!」
報紙裡大約有十張照片,可能是洗得不好的關係,邊緣已經轉黃了,照片中男人黑色身體和女人白色身體重疊,女的眉毛皺在一起,似乎很痛苦。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一張又一張反覆地看。
「助平,看夠了吧!」
不知哪裡響起電話鈴聲,有人接電話,隨後傳來跑步聲,田村迅速把照片藏在抽屜裡。一個女子的聲音叫著我的名字。
「趕快回去!你母親病倒了!」
「怎麼了?!」
「怎麼了?」我的眼光仍然停留在抽屜上。「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呢?」
比起母親病倒,對為什麼知道我在這裡的事,更感到不安,母親知道田村他父親經營妓女戶,所以禁止我去田村家;何況,最近母親因心臟病發作,躺在床上的次數越來越多。不過,每次吃下醫生給的白色藥丸,藥名已忘了,病情又給壓制下來。
我在陽光仍很強的內巷,慢吞吞地走回去。野外堆積著寫有「土地出售」的生鏽廢鐵,旁邊有村工,工地裡不知在敲打些什麼,傳出鈍重而有規律的聲音。有個男子騎著自行車迎面而來,在長滿雜草的空地上停車小便。
已看到家了,跟往常一樣,我房間的窗子半開著,附近的小孩在家門前玩耍,一切和平常一樣,絲毫也沒有出事的感覺。教會的神父站在玄關前面。
「你母親……剛才死了。」
他一個字一個字輕輕說出來,那聲音,連我這個懵懂的中學生,也聽得出是壓抑著感情的聲音;那聲音,連我這個無知的中學生,也聽得出其中隱含了諷刺的意味。
附近的鄰居和教會的信徒們,背彎曲坐著,把躺在八帖大房間的母親遺體包圍起來,沒有人理睬我,也沒有人向我打招呼,我知道那些人堅硬的背,都在責備我。
母親的臉白得像牛乳,眉宇之間還透著痛心的樣子,那時我輕浮地想起剛剛那幽暗照片中女人的表情,這時,我才明白自己是為了什麼而哭泣。
澆完一桶水,把菊花插進綁在墓碑的花瓶裡,剛才在臉四周飛翔的蟲馬上飛到花上,埋葬著母親的土是武藏野特有的黑土,哪一天,我也會在這裡,跟少年時代一樣,和母親兩個人住在這裡呢?
還記得向母親撒過謊話。
現在想來,我的謊言是出自對母親的情結(complex)。被丈夫拋棄的痛楚,除了藉信仰得到慰藉之外,別無他法的母親,把曾為了尋找一個小提琴音符的熱誠,轉移到對神的真誠;現在我已能夠瞭解那種執著的心情,可是,當時的我,卻感到透不過氣來。她越要求我信奉和她相同的信仰,我就更像溺水的少年,為了抵抗水壓而更加努力掙扎。
同學中有個叫田村的,是西宮煙花巷的兒子。肚子老是纏著髒兮兮的繃帶,經常請假;或許從那時起就患了肺結核,我接近被好學生瞧不起的他,的確是出自對母親嚴厲管教的反抗心情。
田村第一次教我抽菸時,我感覺像犯了滔天大罪似的。在學校的射箭場後面,田村邊注意著周遭的動靜,邊從制服的口袋裡,偷偷掏出一包皺巴巴的香菸。
「先用力吸,等受不了時,再噴出來!」
我咳嗽了,菸味刺激鼻子和喉嚨,很難受。那一瞬間眼前又浮現母親的容顏,那是在微暗中從被窩起來,捏著念珠祈禱的臉。為了驅走那張臉,我更用力吸起菸來。
從學校的回家途中溜去看電影,也是跟田村學的。跟在田村的後面,躲躲閃閃地進入在西宮阪神火車站附近的二番館。館內黑漆漆的,也不知從哪裡飄來廁所的臭味。在小孩的哭聲、老人的咳嗽聲中,聽得到放映機旋轉的單調音律。我腦子裡只盡想著母親現在在做什麼呢?「我們回去吧!」
催了田村好幾次,他生氣了。
「囉哩八嗦的傢伙,要回去,你自個兒回去好了!」
走出電影院,載滿下班人潮的阪神電車,從我們面前經過。
「怕老媽怕成那樣子!」田村嘲笑似地聳聳肩。「編個故事不就得了!」
和他分開後,我卻還編不出謊話來。
「因為學校補課,還有,考試的日期也近了。」
我屏住氣息,一口氣說出來,看到母親相信的樣子,我心裡一陣疼痛,但同時也有一種滿足感。
說老實話,我根本沒有真正的信仰,母親要我上教會,我只是交叉著手,裝出祈禱的樣子,心裡卻想些別的事情,想到後來和田村一起去看電影,裡面出現的種種鏡頭;有一次眼前甚至浮現出某日田村偷偷讓我看的春宮照片。禮拜堂內,信徒們一會兒跪下、一會兒起立,跟著主持彌撒的神父祈禱。我試著不去胡思亂想,它卻嘲諷似地拚命在我眼前晃漾。
我不知道母親為何會相信這樣的東西,感覺上,神父的話、《聖經》的故事和十字架,都和自己沒什麼關係,就像是沒有真實感的往事。我懷疑一到星期日,大家聚集到這裡來,一邊咳嗽一邊斥責孩子,雙手合掌時的心情,有時,我對那樣的自己感到懊惱,也覺得對不起母親;我祈禱要是真有神存在,希望也能賜給我那樣的信仰精神,可是,這祈禱並沒有改變我的心情。
最後,我停止了每天早上的彌撒,我的藉口是要準備考試。從那時起,總會若無其事地躺在床上,聽患有心臟病的母親,即使在冬天的清晨,也一個人出門上教會的腳步聲。不久之後,連一星期非去一次不可的週日彌撒也開溜了!母親後腳一踏出家門,我就跑到西宮購物人潮聚集的鬧區閒逛,看電影院的廣告招牌消磨時間。
從那時候起,母親經常感到呼吸困難。走在路上,有時會用一隻手按著胸部,蹙著眉站立不動,我根本沒把它當一回事,對十六歲的少年而言,想像不出死亡的恐怖,而且發作只是暫時性的,五分鐘過後,又恢復正常,因此認為不是什麼大病;事實上,那是長期的痛苦與疲勞,使她的心臟變得衰弱。儘管如此,母親仍舊每天早晨五點起床,拖著沉重的步伐,在毫無人跡的路上,走到電車站,教會在搭上電車的第二站。
一個星期六,我抗拒不了誘惑,在上學途中下車,溜到鬧區。把書包寄放在那時和田村常去的咖啡屋。到電影開演為止,還有段相當長的時間,口袋裡有一張一圓的鈔票,那是幾天前從母親的錢包裡拿的。我養成了有時自己開母親錢包的習慣。看電影直至黃昏,然後若無其事地踏上歸途。
打開玄關,沒想到母親就站在那裡,一句話也沒說,直盯著我看,突然,她的臉慢慢扭曲,在那扭曲的臉頰上眼淚緩緩地掉下,我知道從學校來的電話,把一切都洩露出去了。那一晚,母親在鄰室一直啜泣到深夜,我用手指塞住耳朵,盡量不去聽那聲音,可是,母親的哭泣聲仍然傳到鼓膜來,我並不後悔,反而想著怎麼收拾這場面才好。
請人帶我到村公所觀賞出土物時,窗外已開始泛白,抬頭仰望天空,雨似乎已停了。
「到學校那邊去,或許可以看到東西吧!」
站在旁邊名叫中村的村長助理擔心地問。他的表情有如在說這裡什麼都沒有是他自己的責任似的。村公所和小學裡有的東西,都不是我想看的隱匿天主教徒的遺物,只不過是小學老師們挖掘出來的上代的土器破片罷了。
「譬如他們的念珠或十字架等,都沒有嗎?」
中村惶恐地搖搖頭。
「隱匿的天主教徒喜歡隱密,因此除了直接去找他們之外,別無他法。那一票人都是些乖僻的傢伙!」
和次郎一樣,我從中村的話裡也聽得出他對隱匿的天主教徒,有種輕蔑的心態。
去打聽天氣狀況的次郎回來了。
「已經恢復正常了,明天沒有問題嗎?這樣的話,我們現在去岩島瀏覽一下好嗎?」他慫恿我,因為在這之前,即在「切支丹」墳墓那兒時,我就曾請他想辦法帶我去岩島。
助理馬上打電話給漁業公會;這種時候村公所就很方便了,公會很快就派出一艘裝有馬達的小船。
向中村借了雨衣,連同次郎三個人趕到港口,有一位漁師準備好船,在被雨淋濕的木板上,鋪上草蓆讓我坐,腳下污水淤積,水中漂著一條死了的銀色小魚。
馬達發出聲響,船向波濤洶湧的海上出發,漸漸激烈地搖晃起來,浪頭高揚時,有種輕微的快感,可是海浪翻落,胃好像突然被束緊。
「岩島是很好的釣魚場哦!我們經常在假日去,您是否也釣魚呢?」
我搖搖頭,助理就趕忙向沮喪著臉的次郎和漁師吹噓曾釣到大黑鯛的得意事。
雨衣全給水花打濕了,海風很冷,從剛剛開始,我一直緊閉著嘴巴。是啊,剛剛還是鉛色的海面,到了這裡卻變成黑色,似乎很冷。我想起四世紀之前,被綁成珠串的信徒在這裡被拋入海中,自己要是生在那個時代,也沒有信心一定能忍受得了那樣的刑罰。我突然憶起母親;在西宮的鬧區遊蕩,向母親撒謊時的自己,又在心中甦醒過來。
岩島逐漸近了,果如其名,到處都是岩石的小島,山頂上有少許的灌木。問了助理,才知道這裡除了郵政部的職員偶爾會來巡視一下之外,只能當村民的釣魚場。
約有十隻烏鴉,在頭頂上盤旋,發出沙啞的叫聲,撕開了灰濛濛的雨空,荒涼的景象,令人覺得不舒暢。可以清楚地看到岩石的裂痕和凹凸怪狀,波浪撞擊岩石發出激烈的聲音,揚起白色的浪花。
我問信徒們被推下海的斷崖在哪裡,助理和次郎都不知道。或許不是固定的一個地方,而是從各個地方推下去的吧!
「好恐怖的事!」
「現在無論如何想像不出。」
我從剛剛一直思考的事,在同樣是天主教徒的助理和次郎的意識上,似乎並未浮現過。
「這個洞穴有很多蝙蝠,只要一接近,就可聽到吱吱的叫聲。」
「真是奇妙!牠們飛得那麼快,就是不會碰在一起,身上好像有雷達之類的東西。」
「我們是否繞一圈之後回去呢?」
白色的波浪凶暴地侵蝕著島的裡側,雲散雨停,島上小山的山腹逐漸清晰可辨。
「隱匿的天主教部落就在那一帶。」
助理指著那座山的方向,和昨夜神父指的方向一致。
「現在和他們也有來往嗎?」
「欸!學校裡的一個工友就是,叫下村,是那部落的人,不過,就是有點討厭,話談不來!」
根據兩人的說法,村裡的天主教信徒不太願意和隱匿的天主教徒來往或結婚,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不同,不如說是心理上的對立所產生的。隱匿的天主教徒彼此互相通婚,否則就維持不了自己的信仰,這種習慣使大家把他們當成特殊份子看待,即使現在亦如此。
一半在雲霧覆罩下的那座山之山腹,三百年來隱匿的天主教徒們,跟其他躲藏的部落一樣,決定「挑水」、「輸送」、「聯絡」等工作人員,對外絕不洩露他們的組織祕密,一直遵守著他們信仰;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傳給兒子,一代一代地傳下「祈禱」,在黑暗的倉庫中,奉祀著他們的信仰。我用看某種荒涼景象的心情,在山腹中尋找那孤立的部落;當然,從這個位置是看不到的。
「對那些乖僻的傢伙,您怎麼會感興趣呢?」
助理覺得很奇怪地問我,我隨便敷衍過去。
是一個秋晴的日子,拿著菊花上墳,母親的墳墓在府中市天主教墓地。從學生時代開始,在通往墓地的路上,不知來回幾趟。從前,路的兩側有一大片栗子和橡的雜樹林跟麥田,春天到來時,是很好的散步小道;可是,現在已變成筆直的大馬路,商店櫛比鱗次,連那時孤立墓地前的一間小石屋,如今都改建成兩層樓的建築物了。每次來這裡,往事浮湧心頭。大學畢業的那天也來上墳;到法國留學上船的前一天也來過;生了大病回到日本的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這裡來;結婚時、入院時,都不忘回到這裡。現在有時還瞞著妻子來掃墓,因為這裡是我不想對任何人提起的、母親和我談話的地方,內心深處甚且希望即使是親人,也不要常來打擾。穿過小路,墓地正中央有聖母像,四周有一列排列非常整齊的石墓碑,這是屍骨葬在日本的修女墓地,以此為中心,有白色的十字架和石墓,明亮的陽光照耀著,寂靜包圍了所有的墳墓。
母親的墳墓很小,看到那小小的墓石,心裡一陣抽痛。拔除四周的雜草,蟲在我的旁邊飛來飛去,發出拍翅的聲音。除了蟲聲之外,聽不到其他任何聲音。
在墓碑上澆水,跟往常一樣,想起母親去世的那一天,對我來說,那是極為難堪的回憶。母親心臟病發作倒在走廊上,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我並不在她身旁,那時,我在田村家做著母親若看到一定會傷心的事。
那時田村從自己的抽屜,拿出用報紙包著、像明信片的東西,然後臉上浮現出要偷偷告訴我什麼的那種淺笑。
「這跟一般賣的東西不一樣!」
報紙裡大約有十張照片,可能是洗得不好的關係,邊緣已經轉黃了,照片中男人黑色身體和女人白色身體重疊,女的眉毛皺在一起,似乎很痛苦。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一張又一張反覆地看。
「助平,看夠了吧!」
不知哪裡響起電話鈴聲,有人接電話,隨後傳來跑步聲,田村迅速把照片藏在抽屜裡。一個女子的聲音叫著我的名字。
「趕快回去!你母親病倒了!」
「怎麼了?!」
「怎麼了?」我的眼光仍然停留在抽屜上。「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呢?」
比起母親病倒,對為什麼知道我在這裡的事,更感到不安,母親知道田村他父親經營妓女戶,所以禁止我去田村家;何況,最近母親因心臟病發作,躺在床上的次數越來越多。不過,每次吃下醫生給的白色藥丸,藥名已忘了,病情又給壓制下來。
我在陽光仍很強的內巷,慢吞吞地走回去。野外堆積著寫有「土地出售」的生鏽廢鐵,旁邊有村工,工地裡不知在敲打些什麼,傳出鈍重而有規律的聲音。有個男子騎著自行車迎面而來,在長滿雜草的空地上停車小便。
已看到家了,跟往常一樣,我房間的窗子半開著,附近的小孩在家門前玩耍,一切和平常一樣,絲毫也沒有出事的感覺。教會的神父站在玄關前面。
「你母親……剛才死了。」
他一個字一個字輕輕說出來,那聲音,連我這個懵懂的中學生,也聽得出是壓抑著感情的聲音;那聲音,連我這個無知的中學生,也聽得出其中隱含了諷刺的意味。
附近的鄰居和教會的信徒們,背彎曲坐著,把躺在八帖大房間的母親遺體包圍起來,沒有人理睬我,也沒有人向我打招呼,我知道那些人堅硬的背,都在責備我。
母親的臉白得像牛乳,眉宇之間還透著痛心的樣子,那時我輕浮地想起剛剛那幽暗照片中女人的表情,這時,我才明白自己是為了什麼而哭泣。
澆完一桶水,把菊花插進綁在墓碑的花瓶裡,剛才在臉四周飛翔的蟲馬上飛到花上,埋葬著母親的土是武藏野特有的黑土,哪一天,我也會在這裡,跟少年時代一樣,和母親兩個人住在這裡呢?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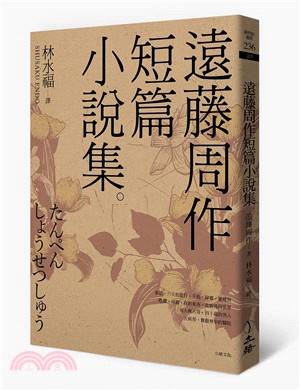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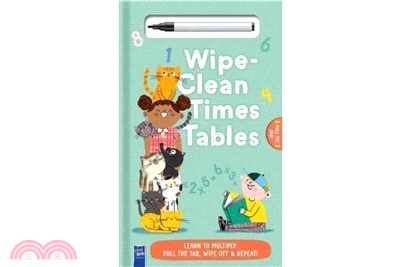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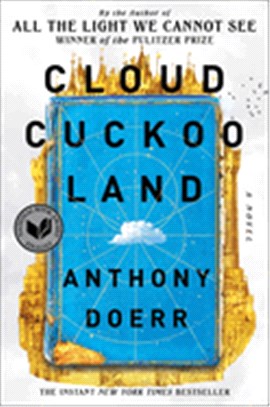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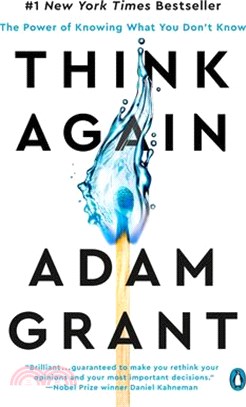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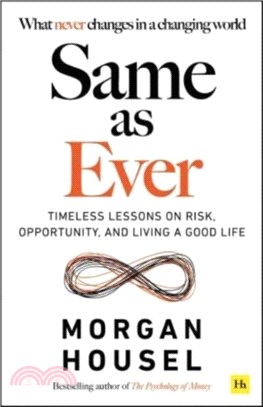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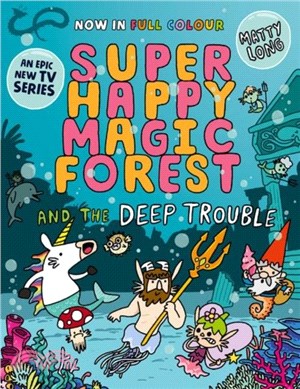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