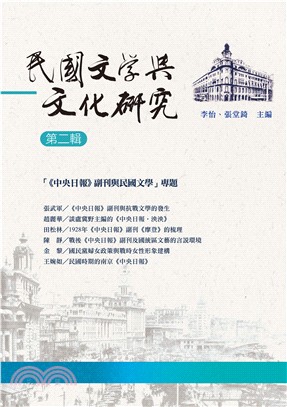商品簡介
華人世界第一份民國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刊物
開啟重返民國歷史現場的文學研究運動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從二○一五年末開始出版,為新一創辦的學術叢書,預計每半年出版一冊,由李怡、張堂錡兩人主編。
本輯推出「《中央日報》副刊與民國文學」專題,特別收錄張武軍、趙麗華、田松林、陳靜等多位學者針對歷年來《中央日報》副刊對於民國文學的發展有何推進性貢獻所發表的精采論文。
並且,為使讀者可以審思「民國文學」一直以來的發展與歷史脈絡,「經典重刊」專欄收錄丁帆的「『民國文學風範』在台灣的再思考」文章與李怡與張中良對於「民國文學」的若干質疑與追問。
另外更特別收錄由封德屏主持,秦賢次、黃美娥、張中良、蔡登山、劉福春等學者參與出席對於「民國史料與文學」的圓桌座談珍貴記錄。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創辦,是為了提倡一種返回民國歷史現場進行文學研究的學術理念。堅持學術立場、文學本位、開放思想則是本刊的宗旨。我們認為,在「民國框架」下討論問題,不僅可以積累一批被忽略的史料,而且最終也有助於形成與現代漢語文學相適應的研究思路和學術模式,從而擺脫長期以來受制於歐美學術範式的宿命,並與西方學界進行平等對話。
「民國文學」作為一個學樹的生長點,其意義與價值已經得到學界的肯定。現代文學的研究,在經過早期對「現代性」的思索與追求之後,發展到對「民國性」的探討與深究,應該說也是符合現代文學史發展規律的一次深化與超越。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深信,學術界將可以在這方面開展更多的合作機制與對話空間。
本書特色
√ 是華人世界第一份有關民國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刊物。
√ 政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堂錡、北京師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怡共同主編。
√ 透過這份刊物,建立一個對話的平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發展與突破將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和重要貢獻。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李怡
四川重慶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學術集刊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詩歌、魯迅及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批判的批判》、《七月派作家評傳》、《魯迅的精神世界》、《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作為方法的「民國」》等十餘種。
張堂錡
台灣新竹人。文學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撰、專刊組組長、政大華語文教學學程主任。目前執教於政治大學中文系,並任政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台灣散文及澳門文學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黃遵憲的詩歌世界》、《白馬湖作家群論稿》、《個人的聲音 ──抒情審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現代文學百年回望》、《民國文學中的邊緣作家群體》等十餘種。
目次
【觀念交鋒】
陳芳明/台灣作家與魯迅
李怡/在「民國」發現「史料」
劉福春/民國文學文獻:搶救與整理─一個民國文獻工作者的一些零碎感想
【經典重刊】
丁帆/「民國文學風範」在台灣的再思考
李怡/「民國文學」與「民國機制」三個追問
張中良/回答關於民國文學的若干質疑
【專題論文 《中央日報》副刊與民國文學】
張武軍/主持人語
張武軍/《中央日報》副刊與抗戰文學的發生
趙麗華/「建文」理念與「泱泱」氣象─談盧冀野主編的《中央日報•泱泱》
田松林/黨報如何摩登─1928 年《中央日報》副刊《摩登》的梳理
陳靜/短暫的民主─戰後《中央日報》副刊及國統區文藝的言說環境
金黎/國民黨婦女政策與戰時女性形象建構─以《中央日報》副刊為考察對象
王婉如/民國時期的南京《中央日報》
【一般論文】
周質平/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
黃文輝/穆旦詩歌慣用語及悖論修辭探討
陳信元/陳儀、許壽裳與台灣省編譯館
張俐璇/「民國」對台灣意味著什麼?─以戰後初期「民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交鋒為例
【書評書論】
張堂錡/回到文學史常識的學術嘗試─對《民國文學史論》的觀察與思考
袁昊/撥雲見日,別開新境─論《民國歷史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出版的學術史意義
【圓桌座談 民國史料與民國文學】
封德屏/時移事往,從歷史罅隙覓研究良帖
秦賢次/條分縷析辨源頭,蛛絲馬跡尊史料
黃美娥/「台灣」看「民國」的重層鏡像,延續?斷裂?嫁接?
張中良/史料再掘,意義重啟
蔡登山/咬定線索不放鬆,千磨萬仞再解構
劉福春/樂以無窮,為有新詩活水來
封德屏/民國文學、史料研究的欣樂與創發
【新銳園地】
汪時宇、曹育愷、盧靖/論王平陵與民國文學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稿約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撰稿體例
第三輯主題徵稿:國民黨文藝政策與民國文學
第四輯主題徵稿:日記中的抗戰與文學
編後記
書摘/試閱
【「民國文學」與「民國機制」三個追問】
■李怡
「民國文學」的設想最早是從事現代史料工作的陳福康教授在1997年提出來的, 但是似乎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2003年,張福貴先生再次提出以「民國文學」取代「現代文學」的設想,希望文學史敘述能夠「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 不過,響應者依然寥寥。沉寂數年之後,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即將結束的時候,終於有更多的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特別是最近兩三年,主動進入這一研究的學者大量增加,國內期刊包括《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海南師範大學學報》、《鄭州大學學報》、《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都先後發表了大量論文,《文藝爭鳴》與《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等還定期推出了專欄討論,張中良先生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民國史視角」問題,我本人也在宣導「文學的民國機制」研究,當然,也有不少的學者從這樣那樣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在我看來,「民國文學」研究的興起和隨之而來的質疑都十分正常,它們都顯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之後一次重要學術自覺和學術深化,並且與在此之前的幾次發展不同,這一次的理論開拓和質疑並不是外來學術思潮衝擊和感應的結果,從總體上看屬於中國學術在自我反思中的一種成熟。
正因為如此,我覺得很有必要以這些爭論和質疑為契機,對因「民國文學」而生的種種分歧和疑問作出認真分析和回應,從根本上說,這與其說是為了說服他人,毋寧說是為了更好地自我清理、將討論的問題引向深入。準確地說,這是一次自我的追問,我追問的問題有三:提出「民國」的文學而不是繼續簡單沿用「現代」的文學,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意義,「民國」何謂?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概念,所謂的「民國文學」究竟可以推進文學研究的什麼?即「民國文學」何為?最後,我本人致力於宣導文學的民國機制,這樣的研究方式究竟來自哪裡?
〔一、「民國」何謂?]
新文學、近代/現代/當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我們今天已經有了這些成熟的概念,繼續提出「民國文學」,還有特殊的意義嗎?雖然以上概念或有不足,但究竟約定俗成,至於更多的弊端也可能在遙遠的未來顯現,今天的「新論」,是不是一種替未來人作無謂的操心呢?
的確,作為對百年來中國文學史的描述,「現代文學」常常是可以替代「民國文學」的;「現代文學」如果是在「現代性」意義上理解,使用時間更長,還包括了當代,這樣,「民國文學」概念可以使用的地方幾乎都可以使用「現代文學」。至少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五四以後的這一段文學,既理所當然屬於我們過去所謂的「現代文學」,又無疑可以稱作是「民國文學」。就是1911-1917這一段過去屬於「近代文學」一部分的文學,除了今天可以冠名「民國文學」,但同樣稱呼「現代文學」其實也沒有什麼絕對不可以的──既然我們可以在「現代性」的取向中廣泛使用「現代文學」到當代,那麼在今天,我們似乎也沒有必然的理由拒絕繼續將「現代」的概念向前延伸,涵蓋1911-1917甚至更早,就像今天的「現代文學史」寫作不斷將「現代」的起點前移一樣。
所以,如果不是特別所指,我對百年來文學現象的描繪還是常常使用「現代文學」,例如主編的叢書名曰「民國歷史與文學」研究,承擔課題是「民國歷史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這裡,顯然與「民國」更緊密的聯繫是那一段獨特的「歷史文化」,而定義「文學」的常常還不得不是「現代」──雖然這「現代」的含義充滿矛盾和歧義,但究竟已經約定俗成,也就成為我們表達的最方便的一個概念吧。
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認為,提出「民國」概念作為「文學」的修飾與限定,卻有著它特殊的意指,在我們的「現代」長期以來不加分別地覆蓋一切的時候,這種意指微妙卻重要,需要仔細辨析。
「現代文學」依託的「現代」屬於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昭示了中國文學對世界性歷史過程的一種回應和融入;但是,作為一種獨立的精神形式,中國作家肯定不是簡單以世界歷史的動向為材料書寫自我的,更激盪他們心靈的是中國歷史自身的種種情形與生命體驗,這就產生了一個「現代」的中國意義的問題,仔細討論,用中國對世界歷史的被動回應也許並不能說明「中國現代」的真正源起,中國的「現代」是中國這個國家自己的歷史遭遇所顯現的。在這個意義上,特定的國家歷史情境才是影響和決定「中國文學」之「現代」意義的根本力量。這一國家歷史情境所包孕的各種因素便可以借用這個概念──民國。
民國從表面上看屬於特定政權的概念,或者說是以政權概念命名的歷史階段的概念,就如同兩漢文學、魏晉文學、唐宋文學、元代文學、宋代文學一樣,但是由於民國所代表的這一段歷史恰恰遭逢了巨大的歷史變遷(千年帝制的結束、中外文化的空前融會等等),所以它的確有自己值得挖掘和辨析的歷史性質──雖然漢代文學不一定有如此強烈的漢代性、唐代文學不一定有鮮明的唐代性,但我們卻可以說民國時期的文學有值得挖掘的「民國性」,「民國性」就是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現代性」的真正的落實和呈現。從民國社會歷史的種種特性出發理解和闡述文學現象就是對中國自身歷史文化的深切觀察和尊重,中國的現代趨向自然理所當然就是民國生長的歷史現象,這裡並不存在一個邏輯上的外來的「現代性」價值轉化認證的問題,事實上也沒有中國作家將西方文學現代性的動向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它就是中國作家生存、發展於民國時代的種種社會歷史感受的自然表達的過程,中國文學的「現代」在「民國」的概念框架中獲得了最自然最妥帖的醞釀和表達。
在這個時候,使用「民國文學」一說不就是對文學歷史的一種十分自然的命名方式麼?
至少在以下兩種情形下,使用「民國文學」一說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其一是突出歷史從晚清至以後一段時間的演變,例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陸續出版的《晚清民國小說研究叢書》,團結出版社推出的《晚清民國小說珍本叢刊》、學術論著《清末民國小說史論》 、《晚清民國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 、《清末民初漢譯法國文學研究,1897-1916》 《清末民國兒童文學教育發展史論》 及學位論文如《清末民初文學作品中的甲午戰爭──以歷史小說為中心》 等等。這些名稱都與近年出現的重寫「民國文學」的思潮關係不大,屬於對歷史階段的樸素而真實的命名,就如同「民國」概念進入歷史學界,並早已經成為歷史領域的基本概念一樣。在呈現歷史階段的基本事實的時候,樸素的「民國」比糾纏於各種意識形態色彩的「現代」更為貼切。所謂「晚清盡頭是民國」,這本來就是一個無需爭論的事實。
其二是在需要特別強調這一時期文學與國家歷史的某些特點之時,使用「民國文學」就更能傳神,比如我們考察1930年代的國家經濟政策與文學的關係,這個時候籠統使用「現代文學」不如稱其為「民國文學」 ;發掘建國前數十年的自然災害與文學書寫的關係, 研究國民黨政治文化與書報檢查制度對文學的影響, 或者,考察民國時期的某些獨特的文化與文學現象如民國小報,這個時候取名「民國文學」顯然也更合適…… 總之,但凡涉及民國社會歷史與國家制度等具有明確標識性意義的文學考察,為了加以更明晰的描述,都不妨直接使用「民國文學」。同理,在我們需要突出某種現代世界的共同遭遇在中外文學歷史的對比性呈現之時,如全球資本主義文化對文學的影響,也可以繼續冠名「中國現代文學」。
考慮到目前學界對「現代文學」的廣泛使用,為了不因為概念的糾纏而干擾我們對問題本身的討論,我自己常常採取折中方案,即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民國時期」,或者加強修飾語「民國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民國時期歷史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種種」關係等等。當然,我知道這是權宜之計,歷史的發展總是在不斷擴大過去的「相似」而認定當下的「特殊」,未來─百年或者更長時間,「現代」沒有理由永遠延長,到那時,以國家社會形態的具體演變時段標示文學,或者就自然而然了、無需爭議了。
〔二、「民國文學」何為?]
另外一個關於「民國文學」概念的使用爭論就是它的價值取向問題。回首歷史,我們必須看到,「民國文學」之說在一開始就是本著「價值中立」的角度加以引入的。最早提出「民國文學」設想的陳福康就有這樣的主張, 後來相當多的「民國文學」宣導者也有大體相同的看法,他們都先後討論了舊體詩詞、通俗文學無法進入「現代文學」的現實,希望借助「民國文學」的框架予以解決,這裡有一個假定:民國文學是一個價值中立的闡述框架。
這似乎暗示了「民國文學」研究的一種可能:暫時擱置先進/落後,新/舊,現代/傳統之辨,在一個更寬闊的視域內闡述的文學現象,取得比「現代文學」敘述更豐富的成果。
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式,我基本上認同這樣多方位多層面的展開努力,不過,在我看來,這裡依然存在兩種不同的思路,其所謂「價值中立」的情形也並不相同,需要我們加以辨析。
一是文學史寫作的思路,也就是說,我們提出「民國文學」就是為了完成一部新的《民國文學史》,作為「重寫文學史」的最新的厚重的成果。在我看來,真正文學史的敘述實際上都有著自己的價值基礎,絕對的「價值中立」其實並不存在,在當前,強調文學的「民國」意義,其主要目標是為了那些為「現代」敘述所遮蔽的文學現象入史,問題在於,被「現代」所遮蔽的文學現象主要是什麼呢?是「非現代」的傳統文學樣式嗎?在我看來,這些「非現代」的傳統文學樣式固然也存在被遮蔽的現實,但是更大的被遮蔽卻存在於對整個文學史演變細節的認識和理解之中,無論是來自前蘇聯的革命史「現代觀」還是來自今日西方現代性知識話語的「現代觀」,都形成了對中國社會具體歷史情境的種種忽視。
例如前者的「反封建」之說─問題在於,中國歷史的進程本身就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並不存在近似於西歐中世紀式的「封建制」,秦帝國形成的一直延續到晚清乃至在民國依然影響深刻的專制集權統治與思維的「封建專制」並不是一回事,封土建國的「封建」時期是在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制之前,尤其是西周,到了東周時期,諸侯小國逐步被兼併成大國,直到秦國併吞六國,建立的是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制,早在晚清一代覺悟的知識分子那裡,與其說是要「反封建」不如說是「反秦制」,譚嗣同的名言是:「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與其說民國的「現代」意義是「反封建」,毋寧說就是從實施秦政的「帝國」走向「民國」之後,以「三民主義」、「憲政理想」為旗幟的走出傳統專制主義的努力,當然也包括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反對國民黨獨裁壓迫、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努力,「反封建」一說雖然源遠流長,影響深遠,但是嚴格說來,依然似是而非。
後者如現代性批判中的「兩種現代性」之說,但在事實上,這樣的分類在中國文學中卻是混沌不清的,李歐梵先生一方面正確地指出:在中國,基本上找不到「兩種現代性」的區別,大多數中國作家「確實將藝術不僅看作目的本身,而且經常同時(或主要)將它看作一種將中國(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中國詩歌)從黑暗的過去導致光明的未來的集體工程的一部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卻對中國文學在「五四」時代所追求的這種現代性缺乏足夠的同情與認同:「中國『五四』的思想模式幾乎要不得的,這種以『五四』為代表的現代性為什麼走錯了路?就是它把西方理論傳統裡面產生的一些比較懷疑的那些傳統也引進來。」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其實就是我們還不能真正回到民國歷史的現場。置身於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情景中,我們就會知道,單純運用這些「現代性」知識是無法準確描繪中國文學獨特遭遇與選擇,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輸入了一個什麼抽象的「現代」觀念,而是如郁達夫所說「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 如果說西方現代作家是在超越世俗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了精神的同一性,那麼中國現代作家卻正是在重新建構自己的世俗文化的基礎之上體現了某種精神的同一性。在反抗專制、建設「民國」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要同等重要,批判專制文化的「傳統」與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同等重要,這裡所呈現的價值需求、文化分割與資源依託都與西方完全不同,像這樣從西方的「現代性」概念出發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方式,其實並沒有為中國文學的問題敞露更多的細節。在這些地方,包括在與受西方知識體系影響的海外漢學的商榷方面,都還需要在民國歷史的發展中辨認我們自己的「價值」。
當然,提出「民國文學」也存在對民國時期的文學現象加以研究、闡發的思路。在這個時候,大量的文學現象的確都可以成為我們整理、分析的目標,而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去除遮蔽,釋放被掩蓋資訊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將那些為「現代」遮蔽的「非現代」文學現象加以發掘自然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而且在「民國文學」現場情況並不清楚的今天,各類文學材料的挖掘整理實在必不可少。
在這個意義上,我主張目前對「民國文學」的研究目標持一個寬容的態度:既大力提倡返回民國歷史現場,重新梳理中國文學重要事實的學術,也需要盡可能窮究各種文學現象的學術,對於一段長期被壓抑、被混淆的歷史,目前最缺乏的是學術界一致的努力,既要有理論建構,也要有史料發掘,既要有歷史觀的辨析,又要有大量文本的再解讀,既要有新的價值體系的建立,也要有最基礎的被遺忘的材料的梳理,既需要個性鮮明的思想開拓,也需要同舟共濟的奮力並行,只有這樣,一個新的學術空間才能夠出現並逐漸邁向成熟,而更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包括有份量的《民國文學史》的問世,都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成熟而富有對話機制的學術空間當中。
〔三、「民國機制」何求?]
民國時期文學值得我們挖掘和剖析的「民國性」我稱之為「文學的民國機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範式之反思〉一文中,我將發掘「民國機制」的思路概括為「在具體的國家歷史情態中考察中國文學的民國特性」, 顯然,從大的方面說,這種歷史文化的批評依然屬於傳統的文學社會學的研究方式。於是,有對「民國文學」概念有所質疑的學人表達了這樣的困惑:既然已經有了傳統的研究,為什麼還要提出「民國機制」的研究?
在我看看,恰恰因為傳統的歷史文化批判存在種種的問題,所以需要在進一步的文學研究中加以完善和調整,針對中國現代文學提出的「民國機制」首先就是一種有效的完善方式。
《孟子‧萬章下》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就是今天人們常常說到的「知人論世」閱讀與批評方法。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對此進一步解釋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 按照這個說法,中國文學的歷史文化批評「古已有之」,而強調文學與社會歷史的聯繫似乎就是一個由來已久的顛撲不破的道理,未來一切相似的理論包括來自西方的文化批評都統統可以納入這個範疇。但問題在於,所謂的「知人論世」其實本身相當的籠統和模糊,朱自清《詩言志辨》就曾經指出,孟子的「知人論世」,「並不是說詩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 ,當代學者也指出,孟子之說「實際上只是一種隨感式的評論,缺乏嚴密的內在邏輯性,因此,『知人論世』研究範式本身的理論內涵便隱含著三重意義指向:其一,讀者經由『頌其詩,讀其書』,然後才『知其人』;或讀者經由『頌其詩,讀其書』而達到『論其世』;或讀者經由『頌其詩,讀其書』,從而『知其人』,並進而『論其世』。其二,與之相反,讀者因為先『知其人』,然後才由『頌其詩,讀其書』;或讀者為『論其世』而『頌其詩,讀其書』;或讀者為『論其世』、『知其人』,而去『頌其詩,讀其書』。其三,以上兩種兼而有之。」在實際操作中,「『知人論世』的文學研究範式便先天性地秉賦了兩種痼疾:首先,它往往導致一種先入為主的文學闡釋活動,讀者不惜淡化其應有的審美感受,並忽略作品文本獨具的審美特性,而直接地將對作者或對社會的先驗理解用於對作品的解讀,以求得到一種貌似符合邏輯的有序的推理,和一種『終極審判』式的獨斷定論。」 例如,在儒家「詩教」觀照下,「知人」往往被簡單化為一種道德評價,「論世」則淪為線性因果的政治決定論。
進入現當代以後,對我們思維產生決定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也一向強調社會歷史之於個人精神創造的巨大決定作用,所謂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等。所以早在新時期到來之前,文學的社會歷史批評幾乎就是我們唯一的研究方式。法國著名文學社會學家雅克‧萊納爾德指出:「從19世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給了文學方面的社會學研究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但是,眾所周知,在那個「唯一」的時代,我們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社會學與庸俗社會學混為一談,將文學的豐富性簡化為階級鬥爭政治直接反映,不是深化了對文學的認識反倒是造成了對文學的諸多傷害。
1980年代,西方古典的社會學研究傳入中國,包括維柯的「特定時代、特定方式」說、斯達爾夫人的「民族精神」說、丹納的「種族、時代、環境」三動因說和聖伯甫的傳記批評等,對新時期中國文學研究界影響巨大。借助對「文化」的寬泛理解,各種「文化」現象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都成了我們學術研究的新課題,諸如政治文化與文學、區域文化與文學、宗教文化與文學、校園文化與文學等等,這些研究連同1990年代以後興起的文學體制、文學制度研究一起,從根本上衝破了「唯一」時代的庸俗社會學的藩籬,將中國文學研究帶入到一個生機勃勃的新天地。在這個時候,「文化」扮演的是與建國後前三十年庸俗的政治批判相對立的角色,正如當時有學者所說:「『走出文學』就是注重文學的外部特徵,強調文學研究與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民族學、心理學、歷史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倫理學等學科的聯繫,統而言之,從文化角度,而不只是從政治角度來考察文學。」 不過,類似的文化研究在取得自己顯著的成績之時卻也相對忽略了對作家主體性的深入挖掘,彷彿就是這林林總總的「文化」直接造就了作家的創作,形成了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基本面貌,作家自身生命感受的複雜性、藝術創造的可選擇性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簡化了,社會文化、歷史過程與文學之間的若干「仲介」環節往往不甚分明。
1990年代至今,又從西方傳入了「文化研究」,並逐漸成為我們學術的主流趨向之一。如果說,前述的各種「文化視角」的研究主要還是透過文化來觀察文學的發展演變,即運用各種文化學說的成果來剖析文學的品質和趣味,那麼如今的「文化研究」則是打破了文學與各種社會文化之間的間隔,將文學作為社會文化關係版圖中的有機元素,其重點不在品味文學的審美個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義」,特別是熱衷挖掘社會結構中種種的階級、權力、性別與民族的關係。這顯然大大地拓寬了我們的眼界,為我們關注尋覓文學細節與歷史細節之內在聯繫打通了思路。不過,「文化研究」理論的西方淵源也註定了它的一些關注中心(如後殖民主義批判、文化/權力關係批判、種族與性別問題、大眾文化問題、身分政治學等)與我們的「中國問題」之間並不都能夠重合。
從總體上看,我們宣導發掘「民國文學機制」,就是在汲取以上社會歷史的批評方法各自優勢的基礎上實現新的學術的超越。這種超越的方式有二:
通過充分返回民國歷史現場、潛入歷史細節實現對各種外來理論「異質關注」的超越。無疑,我們觀察、思考的諸多角度都會得益於1980年代以降的「文化視角」、1990年代至今的「文化研究」,還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等等,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返回到中國國家社會的情境─民國社會歷史的具體場景之中,經過自己的體驗感受到中國文學自己的問題,並以此為基礎實現對外來理論中自然存在的「異質關注」的過濾,過濾之後的歷史文化批評一個最大程度地貼合於中國社會歷史的細節,或者說是在中國社會歷史元素的醞釀之中「再生長」的結果。
通過充分返回中國作家的精神世界、發掘其創造機能實現對文學的「外部研究」的超越,努力將「文學之內」與「文學之外」充分地結合起來。「民國文學機制」一方面要充分展示文化視角研究及文化研究的所長,但另外一方面,它又不同於純粹的文學外部研究,「機制」不等同於「體制」和「制度」,「機制」之中除了有「體制」和「制度」因素外,還有人主觀努力的因素,或者說中國作家努力實現自己創造力的因素。從「體制」的角度研究文學,我們考察的是政治、法律、經濟對於文學形態(內容和形式)的影響,從「機制」的角度剖析文學,需要我們留意的則不僅是作家如何「適應」政治、法律與經濟而創作,重要的還包括他們如何反抗這些政治、法律與經濟而創作,並且在反抗中確立和發展自己的精神追求。民國時代的政治、經濟危機促進了左翼作家的現實批判,批判現實的黑暗絕不僅僅是現實政治與經濟的簡單「反映」,它更是中國作家主動的、有意識的選擇;民國時代的書報檢查相當嚴苛,大批「不合時宜」的文學成為反覆掃蕩的對象,但顯而易見,民國文學並不是這些掃蕩的殘餘之物,掃蕩的間隙,產生了異樣的「鑽網」的文學,生成了倔強的呼喚自由的「魔羅詩力」。
研討文學的民國機制,將帶來中國文學歷史文化研究的全新格局。
(本文發表於《理論學刊》,2013年5月)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