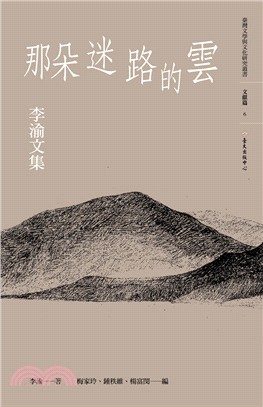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
商品資訊
系列名: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
ISBN13:9789863501947
替代書名:That Missing Cloud: Collected Works of Li Yu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作者:李渝
出版日:2016/11/15
裝訂/頁數:軟精裝/550頁
規格:23cm*15cm*3.6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754【高於十二年級】
商品簡介
透過蒐整小說家李渝未集結的珍貴文章,
將她的生命遭逢、文學觀點與美學理念,一一輯錄其中。
文字以寬宏視角體察人間幽微,包容生命悲喜,
一如月印萬川,酣靜綿長。
李渝是二十一世紀華文小說最為傑出的作家之一,然小說出版之外,李渝同時也撰寫散文雜文、人物傳記、文學與電影的評論,惟因不曾結集,這些作品至今仍鮮為人知。
本書編者透過一手文獻的蒐整,將李渝散見報刊雜誌的文字匯結成冊,全書共分:「那朵迷路的雲」、「重獲的志願」、「莽林裡的烏托邦」、「視者的世界」、「尋找一種敘述方式」等五輯,依序帶領當代讀者,理解李渝文學不可撼動的經典性。
從本書討論女性意識與學生運動的意見,以及有關翻譯與創作、電影與文學、現代與古典的辯證,能讓讀者對於李渝小說的獨特觀點,乃至她所奉行實踐的文學理念,有更具縱深且遼闊的認識。
【名家推薦】
白先勇(文學家、臺大講座教授)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柯慶明(臺大中文系所及臺文所名譽教授)
陳怡蓁(趨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暨執行長)
蘇偉貞(作家、成大中文系教授)
林俊穎(作家)
童偉格(作家)
楊佳嫻(作家、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
李渝跟她先生郭松棻曾經是《現代文學》的撰稿者,深受「現代主義」的影響,她以小說集《溫州街的故事》著名,這部小說集敘述早年從大陸飄零來台知識分子的命運,應該在台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014年,李渝不幸逝世,她在台灣大學的學生同事楊富閔、鍾秩維以及梅家玲教授,為了紀念她,遍搜各大圖書館,將李渝未結集的作品輯成《那朵迷路的雲》,這是對一位傑出的作家一份禮敬。
──白先勇(文學家、臺大講座教授)
李渝散文有如天光雲影,造像萬端。溫潤有時,沉鬱有時,超拔有時。
雲彩不曾迷路,只是永不休止。雲彩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不回來。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李渝
一九四四~二○一四,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藝術史碩、博士。曾任教於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系,擔任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與台灣大學白先勇文學講座。著有小說集《溫州街的故事》、《應答的鄉岸》、《夏日踟躕》、《賢明時代》與《九重葛與美少年》;長篇小說《金絲猿的故事》;小說與藝術評論《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行動中的藝術家》和《拾花入夢記》;畫家評傳《任伯年》;翻譯《現代畫是什麼》、《中國繪畫史》。
【編者簡介】
梅家玲
台大中文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兼括中國近現代文學、台灣文學與漢魏六朝文學。曾先後擔任捷克查理大學、中國清華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嶺南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性別,還是家國?──五○與八、九○年代臺灣小說論》、《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等。
鍾秩維
台大政治系、台大台文所碩士班畢業,目前為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研究員。研究興趣:台灣文學、現代主義、華語語系研究、文化研究與媒介研究。
楊富閔
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文學寫作與教育、台灣文學史料。二〇一〇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新秀作家、二〇一三台灣文學年鑑焦點人物;入圍二〇一一、二〇一四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出版小說《花甲男孩》、散文《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休書──我的臺南戶外寫作生活》、《書店本事:在你心中的那些書店》。
序
導讀/無限山川:李渝的文學視界(摘錄)
梅家玲(台大中文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根據年表資料,可看出李渝其實很早就有志於文學創作。中學時期,即在父親主編的《中國一周》「青年園地」發表多篇文章。她畢生的文學志業及人生關懷,似乎在早年的〈我的志願〉一文中,便可見端倪:
一個人既生存世上,就不能不有一個對於將來的希望,以發揚生命的光輝,充實生命的意義。
我的希望是將來成為一個女作家。
假如說人生是一片荒涼的沙漠,那麼文學便是我尋覓的綠洲!是它滋潤了我枯乾的心靈,是它為我帶來生命的曙光。
成為「女作家」,意味著致力於文學寫作的同時,意識到了自己「女性」的性別身分;而它又與「發揚生命的光輝,充實生命的意義」互為表裡。《李渝文集》雖依文章性質,分為「小說」、「散文隨筆」、「民國的細訴」、「文學與電影評論」、「文學教室」等幾個不同專輯,但綜觀全書,女性、寫作,以及以文學為人生之寄託與救贖的觀點幾乎無所不在。正是三者的相互呼應,彼此生發,共同開顯出李渝的文學視界。
一、女性的故事
眾所周知,李渝的「現代主義」書寫開始於大學時代,當時文學中的性別意識還並不明顯。其後,她因投入保釣運動與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與評論,一度中輟寫作;十餘年後,才又重新提筆,回到文學。她的女性關懷,也同時出現於各類書寫之中。一九八○年,她重返文壇的第一篇小說〈返鄉〉在復刊後的《現代文學》刊出,小說女主角「純子」早年投身海外學生運動,歷經情感幻滅、學業挫折,最後學成返國,選擇赴台灣偏鄉從事教育工作。一九八三年榮獲時報文學小說首獎的〈江行初雪〉,藉由玄江菩薩與幾個不同女性的故事,投射對歷史與人類命運的反思。這兩篇小說中的各類女性形象,雖然多少來自於李渝自身之所聞見,然所呈顯的女性觀照,其實正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李渝的女性(主義)意識。
八○年代之初,台灣女性主義思潮方興未艾,身為女性作家的李渝,同樣就此發表不少論述。所觸及的論題,從畫作中的女性形象,到女明星女演員;從談女動物學家和猩猩的故事,到娜拉的選擇;多元豐富,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她從西蒙.波娃《第二性》出發,強調「女性意識」必得奠基於「存在意識」。念茲在茲的,不是性別之間的對抗,而是超越昇華。她期許女性「不但要從卑屬奴從於男人的處境裡脫身,達到兩性平等的地位,更要把自己當做一個『人』,由自由的意志從而建立自己成為一種更好的個人」。也因此,「更有效的婦運的命題,也許要從男女平等昇進到女性的自由選擇權利――不是以男性,而是以更好的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遠景為指標,為自己的存在做出自由選擇的權利。」
落實在對於各女性人物的具體評論上,她會很自然地安慰離婚的友人阿惠「既非輸家,更非弱者」,因為這將會使她「獲得一個從來不曾有過的認識自己的機會;以自己的力量重建生活,再肯定自己」。她認為大家讚揚法國女演員珍.蒙若,「不僅只是認可她的藝術成就而已;這讚揚裡還包涵了她作一個個人,作一個上進的女性的敬意。她以行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成就了今日的地位。在她從演而導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女性的努力。」當然,談到女作家,她便以獲得諾貝爾獎的南非作家葛蒂瑪為例,強調她雖然寫政治小說,卻不讓政治干涉小說,脫離了政治小說;雖然寫南非,她不黑白二分,超越了本土觀和地域性,達到了評論家們所讚揚的「人類的幅度」。因此,在身為女作家方面,她也走出了「女」作家的局限,表現了她反抗意識的另一面成就。
但更饒有興味的,應是她對於《伊甸思絮――我在婆羅洲與橙色猿生活的年月》(Reflections of Eden: My years with the Orangutans of Borneo)一書的評論。該書作者比魯特.葛爾荻卡斯(Birutė Galdikas),是一位是祖籍立陶宛的女性類人猿學(Primatology)家。她在一九七一年獲得原始人類學名學者路易.李奇(Louis Leakey)的贊助,來到印尼的原始森林,就此和猿群以及原住民生活下來,不只調查研究,還「成為猿群們的一分子,作孤兒猿的代理媽媽,受傷和受危害者的看護,把牠們養育成長後再放回森林裡去」。她以謙卑的態度對待猿群,與牠們建立「熟悉而親昵」的友誼,後來成為類人猿學著名的三位女性學者之一。這本書視原始森林為伊甸園,它寫橙色猿,也寫自己的生平。橙色猿(Orangutan)是生長在南亞洲的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的長臂猿,毛為棕紅色,中國大陸譯為「印度尼西亞猩猩」,或「橙色長臂猿」。姑不論此一「橙色猿」是否即是《金絲猿的故事》「金絲猿」之所本,通過這部被李渝視為「女性主義書籍」的作品,她其實想說的是:傳統科學向來由白種男性主持,穿上雪白冰涼的白色研究衣,冷靜又嚴峻。男性科學家注重客觀歸納思考分析,有具體的假設和先論,規則的過程,數據決定結論,指數、籌碼、電腦化一切,高高在上。他們懷著強勢者的態度和征服目的,要自然就範,御為人類的隸屬。然而「女性科學」卻不是這樣的,女性在人類史上本來就是受欺壓的弱勢者,「從自己的經歷而知道同情和愛護,用弱者的謙卑親和來呵護,用自己的身體去接觸、撫摸和擁抱」。正是此一具有女性氣質的科學研究,「宇宙和生命才能和睦綿延悠長」,因為,它的特質是:
介入的,親身感受的、移情的、給予的、承受的、人化的、和自然共處共分同享的、抒情的。
事實上,對於李渝而言,「親身感受的」、「人化的、和自然共處共分同享的、抒情的」態度,遠不止於女性科學研究而已,它同時是李渝的夫子自道。經由此,我們乃得以進一步深入她的創作理念與文學人生。
後記二 季節交換的時候 (摘錄)
楊富閔(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
二○一○年九月,季節交換的台北,因文學院白先勇文學講座,妳應聘回母校授課一學期,開設「文學與繪畫」「小說閱讀和書寫」課程。前者最初課名是「從羽人到旅人──中國古典文學和繪畫」,係屬研究生專業課程;後者設成大學部通識,初選人數高達一千三百人,只收十五人。
美術我完全外行,小說也是門外漢,作為妳的助教我實在不夠聰穎,我的絕活大概是逗妳開心。一次繪畫課,妳隨機問了在座學生:中國四大美女是誰?幾乎沒有思考我橫空接了一句是李渝。妳笑了將近三分鐘,妳說富閔嘴最甜。
台文所口譯教室聽妳談畫,談漢代壁畫中的羽人、顧愷之的〈洛神賦圖〉與〈女史箴圖〉、趙幹〈江行初雪〉與徽宗〈瑞鶴圖〉;我們也到故宮看畫,妳就著展示中的夏圭〈溪山清遠圖〉說,經過幾百年時間,畫作仍浮泛著光絲。我跟著妳彎腰看光在哪裡?我沒有慧根,真的不夠用功;也談到任柏年系列名為〈關河一望蕭索〉的畫作,尤其要我們注意水邊、漠地、山徑的一旅人一馬匹,天與地之間,踽踽行者的回首,到底看到了什麼?
新生大樓五○四教室,每週三早上十點聽妳講授小說:〈一顆簡單的心〉、〈在斯萬家那邊〉、〈紅葉〉,學期進行一半,課綱從西方急轉五四:(妳是選在五四那天離開的嗎?)魯迅的〈在酒樓上〉、〈影的告別〉,沈從文的〈靜〉,施蟄存的〈將軍底頭〉,蕭紅的〈手〉、〈生死場〉,妳想提升學生的歷史感,對當前文學生態妳的感觸是架空。
課中妳帶我們一句句析讀沈從文〈丈夫〉,我翻出當時課堂錄述的筆記──小說家同情筆下人物,氣氛布置好了,形容詞要配合;把尖銳給磨掉、細節細節、層次層次。妳常說:人一墮落文字跟著墮落,拔昇很難,墮落是over night的事。
妳從不站上講台說話,只為與學生平起平坐;妳進教室一定彎腰道聲早,多麼親切nice的老師。五○四教室後方窗外生著一成排菩提樹,陽光落在菩提樹、陽光落在一張張青春稚嫩的少年臉側,本是提升創作風氣的課程,妳老是提醒大家:寫小說很辛苦──
教與學的過程寫成〈那天,椰林裡有小金絲猿〉,已發表在二○一一年七月號《文訊》,又本該全程錄影存檔的兩門課,都因妳覺得沒必要成為憾事,僅有的一次我恰好請假,影音中不熟機器操作的妳,瞇眼在螢幕前移著滑鼠、尋找播放投影片的杯狀按鍵。聽到妳說:啊!富閔今天不在。多想再聽一次妳叫我的名字。
那時我到台北滿一年,從中文到台文學科轉換調適並不OK,身與心承受的壓力來到極限,灰心之餘將自己封鎖在史料文獻,常常在圖書館二樓碰到忙於掃描紅樓圖錄的妳。
肅穆的、挑高的台大圖書館,一陣風似、我總衝到妳面前大叫:「老師,妳在幹嘛!」發現妳操作儀器碰上困難,不等妳回話、挽起袖子:「別擔心,我來!」其實我也不會使用那些高科技,只是製造混亂、站在妳的身邊當妳的定心丸。半年的相處,漸漸我感覺除了課堂的互動,日常各個方面其實妳都需要幫忙。
有天在圖書館外邊的飯廳巧遇妳正晚餐,妳吃簡單的自助餐,且快吃完了,只是路過的我,因著妳一句:「吃了沒?」、妳還說:「我等你吃。」我匆匆忙忙去點餐,搖搖晃晃很快端回一碗香菇雞湯,妳又說:「只喝湯,吃太少!」其實我是怕點太複雜的食物讓妳等太久,以及心理迫不及待要跟妳一同共食,飯中的談話環繞在我的起居與作息,太瘦、都吃拉機食物;我想跟妳談心,又怕增加妳的負擔,那是唯一一次與妳單獨吃飯,飯後本要陪妳走回宿舍,我說:「妳會迷路。」妳想了一下:「反正沿圍牆走到辛亥路就對了。」我也不知對不對,第二年了在台大我仍會走失,而現在校園地景地貌畢竟也與四十年前大不相同了。目送妳走向燈照不足的校路,我多想跑向前說:還是陪妳吧!
目次
圖輯
導讀 無限山川:李渝的文學視界 梅家玲
那朵迷路的雲──小說
〈那朵迷路的雲〉
〈返鄉〉
〈簷雨〉
〈六時之靜〉
重獲的志願──散文隨筆
〈我的志願〉
〈五月淺色的日子〉
〈華盛頓廣場〉
〈女明星.女演員〉
〈五個東歐婦人〉
〈女性的故事〉
〈並非敗者〉
〈重逢〉
〈娜拉的選擇〉
〈永遠不失去希望〉
〈六月是花開的季節〉
〈追憶似水年華〉
〈禮物〉
〈來自伊甸園的消息──女動物學家和猩猩的故事〉
〈忘憂〉
〈風定〉
〈交腳菩薩〉
〈寫作外一章──怎麼活過來的?〉
〈飼虎〉
〈胖妹,妳在哪裡?〉
〈美豔校長〉
〈春深回家〉
〈美好時代〉
〈戰後少年〉
〈重獲金鈴子──向聶華苓老師致敬〉
〈敬念高居翰老師〉
莽林裡的烏托邦──民國的細訴
〈漢奸和共匪的情史──多情漢子汪精衛和楊虎城〉
〈美人和野獸──張學良的幽禁/悠靜生活〉
〈父與女──抑鬱的陳布雷與叛逆的陳璉〉
〈戒愛不戒色──張愛玲與她筆下人物〉
〈在莽林裡搭建烏托邦──中國才子瞿秋白〉
〈以浪漫的自豪走過歷史橋樑──梁思成和林徽因找尋中國古建築〉
視者的世界──文學與電影評論
〈童年雖然「愚騃」也永遠存在──評影片《城南舊事》〉
〈又荒唐.又蒼涼──從馬奎茲到台灣鄉土文學〉
〈童年和童年的失落──影片《童年往事》看了以後所想起的〉
〈童年的再失落──電影評論的多元性〉
〈月印萬川──再識沈從文〉
〈宮闈電影的聯想──歷史與個人〉
〈夢的王國梁山泊──女性和夢在《水滸》裡的位置〉
〈夢歸呼蘭──談蕭紅的敘述風格〉
〈文藝失憶史〉
〈情愛豪豔〉
〈呼喚美麗言語〉
〈多一點想像力就多一些傳奇〉
〈葛蒂瑪的《朱利的族人》和她對「女作家」的看法〉
〈跋扈的自戀──張愛玲〉
〈被遺忘的族類〉
〈抖抖擻擻過日子──夏志清教授和《中國現代小說史》〉
〈悄吟和三郎──蕭紅與蕭軍的情愛和文學生活〉
尋找一種敘述方式──李渝文學教室
〈翻譯並非次等事〉
〈模仿與獨創〉
〈尋找一種敘述方式〉
〈敘述觀點新奇的小說〉
〈翻譯比創作更重要〉
〈莊嚴〉
〈創作無疆界〉
〈漂流的意願,航行的意志〉
附錄一 「小說閱讀和書寫」課程及「文學與繪畫」課程
附錄二 李渝創作.評論.翻譯年表初編
後記一 啟引 鍾秩維
後記二 季節交換的時候 楊富閔
書摘/試閱
月印萬川──再識沈從文(摘錄)
近數年沈從文的地位從被誤解誣衊埋沒而至重見天日,甚至直入中國小說和世界小說上的最高位置,高齡八十五歲的作家能夠親眼見到這變化,猜想晚年的心情是安慰的。讀者的我從完全不知作家是誰,隨環境的改變和年齡的增長而一步步認識,回想這很長的過程,其實無非也就是慢慢地明白了一些文學是什麼的過程。這裡或者可以把因沈從文的去世而一時間湧上來的比較個人的思索作一整理,再識一次作家的意義吧。
在台灣時的我是從來沒有看過沈從文的作品的。愚蠢的政治為了自身的利益硬把傳統截斷,使在台灣長大的人有三十餘年的時間,竟連自己有什麼作家作品都不知道。五四運動促生了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上的第一代,可惜還沒有盡情發揮潛力,這第一代就被局勢分割成了兩半。來到台灣的部分,如果以作品論成就,要比留在大陸的差一些。可是對五○、六○年代的少年來說,這是中國現代文藝的唯一現實了。記得幼年時也並不是不愛看中文著作的;父親在文化界工作,經常帶回家來當時的文藝雜誌或書籍,家裡走動的父親的朋友們中也有不少是文人。但是這些出版的內容(張秀亞的散文或許是個例外)和老一輩文人的「風範」不但從來沒有打動過白紙般的稚幼心靈,反而使它對自己的背景反感起來,以至於以後越發遠離,竟要等待一連串古怪的外國作家的名字來啟蒙,而啟蒙以後更越發憎恨起自己的傳統了。
時間沉澱心情,帶來鑑識的能力,也許今天重看台灣一九五○年代文學會對它有比較中肯的了解,會看出它的成就,認識出它對文學史也有一樣重要的貢獻。然而在這件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渴望著的年輕的心的確曾經不滿足過,這或許是所謂「盲目西化」底下的真相之一吧。
所幸以後終於看到了魯迅。記得當時的禁書為了傳閱安全常撕去封面,看了五○作品再來看沒有作者名字的〈影的告別〉和〈狂人日記〉,驚奇之下,還以為是外國翻譯過來的小說呢;所幸在更以後又看到了沈從文。
初看時拿起的是〈邊城〉,印象卻不好,覺得很囉嗦,寫的事好像也十分瑣碎。看了〈邊城〉反倒放下了沈從文也是意料中的事;那時是閱讀卡謬卡夫卡沙特貝克特等存在主義虛無主義荒謬劇場的年代,如何看得下溫馨的田野紀事?現在回想,覺得當時的心情固然不對,選擇〈邊城〉也是個錯誤。它雖是沈從文最常被提到的名著,卻不是他的好作品。他鬆長的句法和緩慢的節奏用在諸如〈菜園〉、〈靜〉、〈燈〉、〈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等中能夠成為獨特的代表風格,在〈邊城〉裡卻行走得十分累贅。不知沈從文而從〈邊城〉入門,比較容易產生錯誤的印象,以為他是位「田園詩人」。
柏克萊是個開放明朗的學生城,我來念書時正值各種運動風起雲湧。言論自由運動、學生權力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左派運動等等,已經進入學生和持槍憲兵警察對立的階段。演說示威遊行每天都在進行,校內外一片彈石煙硝,人潮洶湧。一個從極權國家出來的青年眼見這種景象,從閉封的世界驟然落身到新天地中,不消說,那種心情是很興奮的;緩慢安靜的沈從文被忘記。不久中國留學生自己也爆發了保釣運動,以及因釣運而起的,意義的長遠在當時未曾料到的重識中國現代史的活動。對一個學文藝史的學生來說,便是重讀(或者第一次讀)三○文學了。
如上繮的馬,已經在騰躍,魯迅立刻成為精神的前導。記得《戰報》第一期第二期抄寫時,篇頁相接處都是以抄錄魯迅的句子為填白的。沉鬱狂熱的魯迅是怎樣地在激勵著浪漫的民族主義學生們。
身在運動之中不知時間的飛逝,保釣用去了十年時光。一轉身,距離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示威竟也已十七年,多麼令人驚愕。保釣運動教育了扭轉了許多想法,改變了許多方向和路程。有一天,希望時間終於培養出距離和觀點,而使這一段寶貴的經驗能夠蛻變而成文學。十年保釣,從單純的學生愛國運動演變成複雜的政治活動,是在這過程裡,學院裡的青年第一次獲得了了解現實與人的機會。
左派理論有它崇高的精神層面,例如反剝削反壓迫,建立平等共享的大同世界等,落在二十餘歲的心裡,無疑是烏托邦能在世上出現的保證了。釣運初發在陽光常照的城市,理想是美好的,因共分理想和工作而建立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難得,這些都容易使人覺得生活充滿遠景;人是好的,就是不好的地方也可以變好,運動是一種洗禮。從柏克萊來到紐約,運動進入人物眾多目的複雜利益交錯的政治性的後期,一瞬間,才明白前時的想法是多麼幼稚可笑。這才是真正的、現實的世界,一切都在按照實利法則在進行遊戲,何況是政治。許多事令人不安和畏懼,崇高的理論被運作成銳利的武器來制壓打擊或「奪權」。人與人對立敵立一切昇級為「兩條路線的鬥爭」。所幸地,這是紐約,而非中國的某個城鄉,否則私刑已經使用,人頭已經落地。許多年後,回想當時的一些事端,覺得雖都以政治理由來執行,其實隱藏在最深處的最真實的那動機,無非來自人的最原始的權力欲望或嫉恨心理。
洗禮的事可遇而不可求;所有政治活動的欺騙性和為實利而背叛原則的本質都一樣,無論大如文革或者小如釣運。人性是很黑暗的,黑暗部分的持久和有力遠非光明部分能比擬。當釣運能從人性而非政治性的層次來被了解以後,卻未料到在似非而是的情況下,它的缺點或真相竟給人帶來了無數的益處。
從學生運動到政治活動到官僚體系,越走越難走,我想很多人都不是這條路上的人,只是意外地走來了這條路。有一段時間精神有些散漫,目的有些恍惚,勉強收拾心情,想起了因運動而放下了的文學,才明白,在黯淡的甬道中,文學有如執燈的神祇,由祂手中發出幽靜的光,原來始終在等待著。
離開運動而逐漸安定,人事糾紛都遠去了。拿起筆,想可以寫點什麼,這一瞬間,才全然又徹底地茫然了起來:可以寫些什麼呢?運動使我看到了先入為主的強大意識,例如民族主義社會意識階級立場本土精神等等,如果強納入文字,容易架出空妄的姿態,嚇跑了文學。但是一路意識型態先行已經使它們變成唯知的主題,高昂的筆調已成為唯一熟悉的寫法──我能寫些什麼呢?
是在這樣惘然的情形下重新拿起了沈從文。
在從沈從文那兒獲得的無數好處中,最使這時的我受益的,莫過於讓人明白了謙虛或卑微之為力量。或者說,以卑微的觀點來進行敘述所能產生的巨大的動力。
以小人物小事件為素材並不特別,三○年代以至現在的寫小說的人大約都知道「小中現大」的道理。但是敘述者把自己壓抑(對沈從文來說當然不是壓抑)到這樣低微,甚至比人物還要低微的身位上來進行敘述,卻是奇異的。以魯迅為例,雖然阿Q、孔乙己、閏土等都是很微小的人物,作者的觀點卻立在一個高點上,所以敘述處處顯示了反思內省闡釋的性質。魯迅有他的功力,把他自己所選取的觀點運行到了風格的最高峰,無懈可擊。高視角用在較次的手中,例如茅盾或巴金,往往會出現解說或發議論的片段,時時會有「正義之聲」來鞭撻現象或者訓導讀者。
揭露、批判、譴責、抗議、教訓等等,這些因高視點而產生的有稜角的詞語都不適用於沈從文;沈從文是柔軟的、謙虛的、溫和的、渺小的,沒有地位,甚至是懦弱無能的,然而就是在這懦弱之中隱藏了巨大的情感和人的精神,在近百年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幾成為獨一的現象。
我們來看看這觀點低到了什麼地步,在〈丈夫〉中有一位妻子到城裡去做妓女來維持生計。男人因為想念了,便換上乾淨的衣裳,包了妻愛吃的栗子來城裡看望。把沾泥的鞋子留在護板上,坐在艙尾等妻作完她的生意。這樣的事多少要叫人悶氣和寂寞,後來便鬧了點彆扭,要早回家去。妻把一把新買的胡琴塞到他手裡。不說話,他把琴擱在膝上,低頭調起了弦──
或者〈靜〉裡的小女孩從晒樓下來,到房裡看剛吐了血的病床上的母親。女兒和母親交換了些勉強的高興話,母親叫女兒站在那邊莫動,讓她看看,說,「這個月你又長高了,簡直像個大人了。」
還有著名的蕭蕭,被花狗糊塗地弄大了肚子,什麼自盡的事都想過了,「究竟是年紀太小,捨不得死,卻不曾做。」伯父沒念過「子曰」,也不忍把她照規矩沉潭。「好像極其自然」,「倒又像不甚要緊」,大家反而釋然了。等蕭蕭生下了兒子,大家把兩人照料得好好的,吃雞吃酒燒紙謝神。十二歲時兒子也接了親,新娘在轎中哭著的時候,「忙壞了那個祖父、曾祖父」。
隨手選幾個例子,都是既不知批判也不知抗議的「懦弱無能」的典型的沈從文人物;敘述的基線不能放得再低了,可是從基線的底下油生出從來沒有這樣從容和堅韌的耐性;有一雙眼睛靜置在敘述的後邊,包容了體諒了悲喜全體。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沈從文的觀點有點像佛眼,又有點接近中國繪畫中的俯瞰透視,隱藏在某處的無所不見的寬宏的視角,容納下了無限山川。
似乎是什麼事都沒有說,然而每件事都說了都發生了;似乎是冷酷而無可救藥的現實,無可救藥之中卻讓同情和希望永遠存在;文藝裡有一種抒情的,人的品質,是超越在一切標準之上的,有一種水平是一切理論都無法界範的。這樣的作品自豐自足,無須外在或附加的文字來打擾。遇到了這樣的作品,口與筆或者都應該停下來,因為月印萬川,這是酣靜的時刻。
一個柔弱但強韌而持續的聲音開始從文字後邊傳過來,使每一個人物和情節都生出了意義,使每一次再閱讀都能獲得新的訊息。它說的都是人與生活的故事,並不以文學或社會來教導,但是一旦有了前者,後者卻在不知覺中出現了。我暫時跳過保釣,試著回到文學啟蒙最前時──
近幾年台灣的政運、民運發展得十分快速,遠比當日的釣運要激烈廣泛和實際,許多人都投入了運動,包括了不少原來是從事文學的。這些人中,我在想,會不會也逐漸生出我前邊提到的感覺,在若干年後分享與我類似的經驗,終於領悟到政治或社教活動是與文學活動絕然不同的,而兩者之間只能有一個選擇呢?
很靜的夜,酣睡的時刻,在暗中萬物仍舊滋長,據說在子卯兩個時辰你甚至可以聽到滋長的聲音,朔朔地從地面抽上來。沈從文一生不曾擁護過勢力,就是在最險惡的時刻也不曾放棄過生活和藝術上的原則,智慧的光輝現在將與祖國其他的先聖先賢們一同照耀著世紀。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