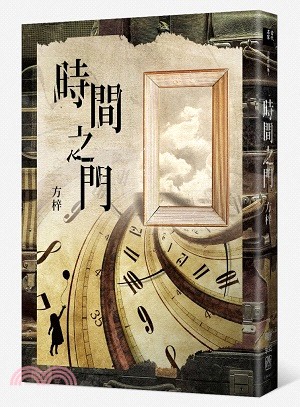時間之門
商品資訊
系列名:當代名家‧方梓作品集
ISBN13:9789570848267
出版社:聯經
作者:方梓
出版日:2016/11/17
裝訂/頁數:平裝/256頁
規格:21cm*14.8cm*1.8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555【七年級】
定價
:NT$ 280 元優惠價
:90 折 252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時間之門》最明確的屬性是時間和空間,
是我寫過往的年代事物與人的故事,
以及走過的地景書寫,
是故,我以時間的橫線和空間縱支去架構,
張開成集成書。
以疏雅清新文風見長的方梓,字裡行間擅用譬喻象徵且頗富哲思。不管是餐館、咖啡廳的飲食,或是田野、公園的野花野菜,都是她「寫作時間」的一部分。《時間之門》集結摭拾過去未曾收錄成冊的篇章,說城鄉、憶舊往、談飲食、觀日常,方梓說:「我把城市當成一座田園,把行道樹看成一片森林,樹木花草便會對我回望,我樂於成為植物的言說者。」輕淡的筆調藏有濃郁的感懷,平實地呈現世故人情,使看似細瑣的時間與空間交織成溫潤且剔透的光暈。
延伸閱讀:
蔡詩萍,《回不去了。然而有一種愛》
西零,《家在巴黎》
是我寫過往的年代事物與人的故事,
以及走過的地景書寫,
是故,我以時間的橫線和空間縱支去架構,
張開成集成書。
以疏雅清新文風見長的方梓,字裡行間擅用譬喻象徵且頗富哲思。不管是餐館、咖啡廳的飲食,或是田野、公園的野花野菜,都是她「寫作時間」的一部分。《時間之門》集結摭拾過去未曾收錄成冊的篇章,說城鄉、憶舊往、談飲食、觀日常,方梓說:「我把城市當成一座田園,把行道樹看成一片森林,樹木花草便會對我回望,我樂於成為植物的言說者。」輕淡的筆調藏有濃郁的感懷,平實地呈現世故人情,使看似細瑣的時間與空間交織成溫潤且剔透的光暈。
延伸閱讀:
蔡詩萍,《回不去了。然而有一種愛》
西零,《家在巴黎》
作者簡介
方梓
本名林麗貞。
台灣花蓮人,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總編輯、全國文化總會學術研究組企畫、《自由時報‧自由副刊》副主編、總統府專門委員,及大學兼任講師。
著有《人生金言》、《他們為什麼成功》、《傑出女性的宗教觀》、《第四個房間》、《采采卷耳》、《來去花蓮港》、《野有蔓草:野菜書寫》等。
本名林麗貞。
台灣花蓮人,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總編輯、全國文化總會學術研究組企畫、《自由時報‧自由副刊》副主編、總統府專門委員,及大學兼任講師。
著有《人生金言》、《他們為什麼成功》、《傑出女性的宗教觀》、《第四個房間》、《采采卷耳》、《來去花蓮港》、《野有蔓草:野菜書寫》等。
序
序:
時間有門
時間在物理定義是純量,藉由時間,以昨天、今天、明天的序列將「時間」量度確定;時間也是空間,過去、現在、未來看起來是時間的區隔,卻也是空間的指涉,就像歐洲的歷史、台灣的歷史、台北的發展歷史,怎麼看都是時間,但最大的議題還是在空間,或者說,時間空間是纏綁難以切割。
時間於我,也是空間,所以時間有門,那一扇門是人腦中的思考,用來描述事物變化的程度╱過程。
二○○一年《采采卷耳》出版之後,我並沒有「乘勝追擊」再出版散文集,而是癱陷在研究所的英美文學,碩士拿到後,離開工作十多年的副刊場域,跑到一個完全和文學無關的地方上班,於是我有藉口十年不寫,只做和文學無關的事情,只寫和文學無關的文字。
二○○八年結束爾虞我詐的工作,時間之門讓我再度進入寫作的行列,擺脫以往嫻熟的散文,挑戰於我完全陌生的長篇小說的構思和書寫,另騰出一線縫隙書寫人到中年的回憶和正興盛的地誌╱空間描繪。一篇一篇緩慢的敲鍵盤,連同更早的作品,十年龜速爬行也積累成書。
幾乎所有的書寫都是透過時間之門。
十年、二十年,小孩會長大,大人會變老,三十年、五十年空間會傾頹消失,找不回的時間,想不起來的樣貌唯有進出時間之門,去翻箱倒篋,行走在一條條模糊的道路,一棟棟頹圮的屋舍,一塊塊仍舊翠綠的田園,一一拉出某個物品,某個人,不堪或溫馨的情節,還有一張張稚嫩或青春的面貌,轉化成文字讓他們重生。
時間有門,文字無限,書寫得以重生、療癒;我在時間之門重塑以及建構過去、現在,甚至未來。
《時間之門》是十多年來彙集的作品,主軸在時間與空間的敘述。感謝金倫、逸華的費心,感謝宗翰銳眼鞭辟入裡的訪談。
時間有門
時間在物理定義是純量,藉由時間,以昨天、今天、明天的序列將「時間」量度確定;時間也是空間,過去、現在、未來看起來是時間的區隔,卻也是空間的指涉,就像歐洲的歷史、台灣的歷史、台北的發展歷史,怎麼看都是時間,但最大的議題還是在空間,或者說,時間空間是纏綁難以切割。
時間於我,也是空間,所以時間有門,那一扇門是人腦中的思考,用來描述事物變化的程度╱過程。
二○○一年《采采卷耳》出版之後,我並沒有「乘勝追擊」再出版散文集,而是癱陷在研究所的英美文學,碩士拿到後,離開工作十多年的副刊場域,跑到一個完全和文學無關的地方上班,於是我有藉口十年不寫,只做和文學無關的事情,只寫和文學無關的文字。
二○○八年結束爾虞我詐的工作,時間之門讓我再度進入寫作的行列,擺脫以往嫻熟的散文,挑戰於我完全陌生的長篇小說的構思和書寫,另騰出一線縫隙書寫人到中年的回憶和正興盛的地誌╱空間描繪。一篇一篇緩慢的敲鍵盤,連同更早的作品,十年龜速爬行也積累成書。
幾乎所有的書寫都是透過時間之門。
十年、二十年,小孩會長大,大人會變老,三十年、五十年空間會傾頹消失,找不回的時間,想不起來的樣貌唯有進出時間之門,去翻箱倒篋,行走在一條條模糊的道路,一棟棟頹圮的屋舍,一塊塊仍舊翠綠的田園,一一拉出某個物品,某個人,不堪或溫馨的情節,還有一張張稚嫩或青春的面貌,轉化成文字讓他們重生。
時間有門,文字無限,書寫得以重生、療癒;我在時間之門重塑以及建構過去、現在,甚至未來。
《時間之門》是十多年來彙集的作品,主軸在時間與空間的敘述。感謝金倫、逸華的費心,感謝宗翰銳眼鞭辟入裡的訪談。
目次
目次:
序╱時間有門
輯一
花蓮之翼
我的宜蘭拼圖
泉水汨汨的礁坑
台北寅時
陽光和星星交織的城市
日裡的陽光,夜裡的燈
湖與山的綺麗
秋天的Pupusas 和jocote
黑名單之旅
輯二
上學
與童年對唱
回溯崇拜
衣櫃的祕密
迷宮的芭樂園
爬樹的小孩
轉角的柚子樹
遺失的翅膀
擺盪在後山與山前
貧乏與豐富的年代
玩物不成癮
時間之門
恐懼的潮汐
聆聽,黑暗中的聲音
輯三
也是一種後現代飲食──白斬雞
銅鍋與筍干
小人國的鹼粽
讀寫日誌
附錄:
模糊、曖昧也是文學之必要
序╱時間有門
輯一
花蓮之翼
我的宜蘭拼圖
泉水汨汨的礁坑
台北寅時
陽光和星星交織的城市
日裡的陽光,夜裡的燈
湖與山的綺麗
秋天的Pupusas 和jocote
黑名單之旅
輯二
上學
與童年對唱
回溯崇拜
衣櫃的祕密
迷宮的芭樂園
爬樹的小孩
轉角的柚子樹
遺失的翅膀
擺盪在後山與山前
貧乏與豐富的年代
玩物不成癮
時間之門
恐懼的潮汐
聆聽,黑暗中的聲音
輯三
也是一種後現代飲食──白斬雞
銅鍋與筍干
小人國的鹼粽
讀寫日誌
附錄:
模糊、曖昧也是文學之必要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台北寅時
認識台北從微光開始。
那一年高四重考生,白天曲蜷在館前路的補習班,晚上窩在窄仄宿舍,見到陽光的時間實在不多。第一次離家,害怕黃昏一盞盞點亮的路燈,也畏於家家戶戶窗內溫暖的光暈,晚膳的時間讓人覺得被遺落在孤島,家在數百里之外。華燈初上,台北的夜,對我是一種思鄉的折磨。
我常在清晨前醒來,像鴿子籠的宿舍沒有窗,細微亮光來自走道,走道的窗外是一小方天井,初秋寅時,天微微透光,像一張水墨,重重的灰青色渲染著,然後逐漸變淡轉亮,薄而弱的陽光灑入天井,天就亮了。
有時,坐在大門內的階梯上,從上方玻璃窗看見街道巷弄從黑夜走到天亮,從寂靜到嘈雜;天漸漸光是我認識台北最深沉的方式。爾後,我屢屢在子時到天微光才肯撇下濃夜的台北就寢。其實,來台北的前幾日,我也在天漸漸光中告別花蓮。
大學聯考完後幾天,幾個死黨聚集在月蘭海濱街的家,聊的都是茫茫的前程,五個人中只有純慈把握有學校唸,她在乎的只是國立或私立,瑤華想考夜大,錦秀要考三專,月蘭想找工作,我什麼都沒想,而且也篤定考不上任何大學。那個年代,高中的我們還不敢明目張膽的談戀愛,能聊的只有暗戀的對象或喜歡什麼類型的男友,五個女生談聯考、談大學、談毫無經驗的感情想像……聊著聊著,墨夜轉灰黑,天再過不久就會亮了。
走!去看日出。
幾分鐘後我們來到海邊的堤防。灰黑的夜色我們看不太清楚浪花刷洗沙岸的影像,然海潮一波波襲擊沙岸的聲音,在謐靜的夜裡,像竹扁籃篩豆子,每顆豆子滾動的音節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們走下堤防坐在一點點潮濕的海沙上。沒有人說話,安靜的等待日頭從太平洋的海面蹦跳出來,也彷彿在進行一種儀式,告別家鄉的日出海祭。再過些時日,我們將從蘇花公路或橫貫公路到異地工作或求學,把最純真質樸的人生留在此地,以海以日為鑑。
黑灰的天色轉為青灰,另一頭的沙岸有幾個人影,細細輕輕幾句交談聲,日出的祭典不宜喧譁,似乎成了默契。日頭宛如一顆火球從遙遠的下坡往上翻滾;從一點點光影亮在海面上,然後是一小片,繼續擴展成半圓,光影再奮力拉長拓展,沒有告知似的如一顆煮熟的湯圓,蹦!一顆火球冒出在滾燙的海面。哇的一片聲響,熱烈的話語紛紛落在沙灘上。
然後,我們真的各奔前程。
我在太陽升起後搭金馬號走蘇花公路、換火車走北宜線來到台北館前路的補習班,走出車站,紅紅大大的太陽低掛在西邊樓與樓之間的隙縫。
是那方天井的微光影響?爾後,我經常流連在台北的微光,晝日與睡神搏鬥。
多年後到報社工作,世紀末與世紀初,藉著夜晚工作,我名正言順的從子時流連到寅時,越夜越美麗,天色微亮才就寢。
台北有很多面貌,晝夜各有精彩。子時後的台北是另一種繁華;忠孝東路四段另一群人彷彿剛甦醒過來,車聲、攤販聲沸沸揚揚,買東西、看電影、吃消夜,子夜場的生活正式開演,復興南路的白粥滾熱著,KTV樓下的人進人出,烤香腸的氣味濃烈,敦化路的酒店霓虹燈熾豔,計程車、黑頭車來來去去,一個個敞開西裝拉歪領帶的男人,像煮熟的蝦子硬被塞進車子裡。
或者夜還淺一點,我下班離開南京東路二段的報社,第一批應酬結速的人背上貼著疲憊,車子乏力的往回家的路行駛。有時,我走路回家,從二段走到五段,路上行人愈來愈少,店家的燈一盞一盞的暗滅,有一種荒涼,猶如一條被棄置的街道,一棟棟人去樓空的建築。這條路布滿銀行、證券公司,白天汲汲營營的人群此時躲在夢裡安穩沉眠或煢煢孑立在夢中尋富迷失?屬於白晝生活的這群人正在安眠,這裡的夜已吹熄燈號,繁華黯然失色;白天翻騰的就讓暗黑來沉澱,白日的挫敗、煩悶就讓夜來舒緩撫慰。
回到家裡,讀小學的女兒已就寢,屋裡如遭竊一團雜亂,我像海螺女在子時前打掃整理、準備丈夫和女兒隔日的晚餐。審視女兒熟睡的臉後,燈火升起,我的夜才開始。
深夜裡有很多事可以做,也可以什麼都不做;有時寫作,有時閱讀,看電視或觀賞影片,夜雖暗沉,時間流動卻是快速的。寫作時,整個台北城我似乎只聽到敲打鍵盤的聲音,答‧答‧答篤篤脆亮的敲字聲響彷彿和心應答,是我的最愛。偶爾救護車或救火車的尖銳聲響刺破沉寂,隨即黑夜再度閉合沒了聲響,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
和文字交纏直到天色微光,幾聲脆亮的鳥叫聲,隱約可聽到公園早起人的招呼。我不捨的關了電腦、電視,合了書,拉開窗簾小縫隙,望著正在甦醒的街道,美麗的夜結束在寅時的微光中。熄燈就寢,在另一半的鼾聲中努力入睡。
有時,真的什麼都不做,不打字寫稿,不翻書,不看電視,坐著或站著,想事情或發呆,聽夜的流動,看光影的變化;燈光的城市沒有純粹墨黑的夜,總暈染著燈影顯得空洞寂寥,不似白天的燦亮翻騰。從橙黯的黑到深灰暗,再到青灰,燈光逐漸漸被稀弱,喧鬧的一天就要開始。
經常,我就坐在烏暗的夜裡,聽台北城最微弱的心跳,仿如叛逆者或過動兒終於酣睡的祥和呼吸聲。有時,也想起十八歲那年,在花蓮微光的海灘等待日出,那份質樸的心。從沉夜到天色微光,是我觀察一個城市最直接的方式;疲憊或酣睡的夜與人最貼近。
天漸漸光,是我一天的開始,也是結束。
轉角的柚子樹
永遠記得那兩條小徑,那是我的童年世界,邁著剛會走路的小短腿從這頭進入,高瘦的身軀從另一端走出來,快樂的童年就這麼結束了。
外婆的家園十分廣衮,千坪的果園圍繞著宅屋,對一個三、四歲的小孩來說,穿梭在果園中,簡直是走進一座森林。兩條小徑呈L型從家園中間穿過,是對外的通道;一邊的出口是溪邊,小阿姨洗衣服的地方,一邊通往大阿姨婆家的小路。兩條小徑交接的轉角有一棵樹,樹下有一顆被坐到發亮如圓桌的大石頭。鄰居的阿桑常搬個小凳子和外婆在樹下挑菜,有時她十四歲的養女阿月大剌剌跨坐在石頭上,和我說著阿桑如何虐待她,四、五歲的我不知道什麼是虐待。外婆的宅園附近就我們兩處住家,阿月的工作是餵豬、做飯和洗衣服,偶爾空閒的她大概也只能同我說話吧,儘管我完全不是她說話的對象。後來加入外婆果園的弟弟最喜歡爬上那顆大石頭再跳下來,經常摔得鼻青臉腫,甚至一次跳下來骨折,他卻樂此不疲。轉角的樹是柚子樹,外婆說和其他的果樹一樣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自己長出來的,在母親小時候就有了,也許有人吃了果實掉下的種籽,或是鳥、昆蟲叼了過來。是一棵老柚子樹,大半的時候它是引不起人注意的,即使最常在它樹下乘涼的阿桑和外婆,也從不關注它,不像園中的蓮霧,在端午節時外婆拿了柴刀朝樹幹底砍了幾道,掛上一串吃完粽子的粽繩,說是提醒花葉茂盛的蓮霧要如粽子般果實纍纍。也不像釋迦要稍折彎它的枝椏,免得過高不好採摘釋迦果。
外婆的宅園各種「自己長出來」的水果,四季交替的開花結實;春天才開始,楊桃垂掛黃綠色如同燈籠、土芭樂和野草莓一顆一顆的成熟;摘土芒果幼果是清明節;初夏早熟的蓮霧也可以摘來吃了,看到龍眼大概知道七月半的普渡要到了,接下來是柚子和柿子提醒中秋節來了,然後是那棵矮小的酸橘子紅了,過年轉眼就到了。還有滿園的釋迦,彷彿大半年都可以吃得到。
在外婆果園中我最喜歡柚子,不是它好吃,是它好玩。
柚子的好玩得從春夏開始。過了清明,柚子開花,白色的花蕊非常清香,香氣直逼玉蘭花,風輕輕拂盪柚子花似雪花般飄墜,整條小徑迴盪著花香,阿月撿起掉落的柚子花撒滿她的髮上,她說新娘子都戴花,有時偷偷拿著針線串成一條花鍊,我總央她也串一條給我。白色的柚子花鍊的確非常漂亮,且香氣繚繞,可惜戴了一個下午全掉光了。
夏天,整樹的小柚子如拳頭般大小,一個颱風常颳下一半的果實,我撿起落果當球玩,阿月拿著小柚子在髮上猛搓,她說柚子皮有油可以讓頭髮「烏金」。有時我們嘴饞,阿月硬是剝開柚子皮,柚肉細又硬,酸澀得讓我們只咬一口便扔了。
抵擋過颱風的柚子愈來愈大愈圓,也漸漸由深綠色轉為綠黃。外婆家的柚子不是文旦,圓形皮圓滑,淡粉色的果肉細小汁多但略酸。在還未吃過文旦之前,我以為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柚子。
貧窮匱乏的年代不做興賞月,中秋月圓不圓是其次,重要是有月餅可享用,而月餅的種類也極簡單,絕大多數是綠豆凸,蛋黃酥或蓮蓉月餅如同舶來品。直到我讀小學四、五年級,小姑姑到台北做事,中秋節帶回有著彩色玻璃紙包著的蓮蓉豆沙月餅,我們才知道原來中秋月餅不只是綠豆凸。
中秋節的綠豆凸比起其他節慶的糕餅或粿粽要來得稀罕,因為糕餅或粿粽都是阿嬤、母親動手做的,唯綠豆凸是買的。花錢買的東西絕對不會多,有配額限制,一年當中也只有中秋節才有,因此中秋節吃綠豆凸就顯得珍貴而慎重。
比起綠豆凸,柚子就平易近人,也不限定中秋節當天。
大約中秋節的前半個月左右,柚子約略成熟了。摘柚子是小孩最愛的事,站在樹下看著大人摘下後,我和弟弟及表弟妹搶著指定要哪一顆柚子,不是搶著吃柚肉,而是要那頂柚子皮。每次大概摘個五、六個柚子,也剛好是我們幾個小孩的數量,每人其實都會有一頂柚子皮帽,柚子也大同小異,只是先搶到的好像就是最好的。
剝柚子皮,台語是「刣柚仔」,大人用刀間隔劃開柚皮和瓤綿,取下柚肉,柚瓤皮就成了一頂六到八瓣膜左右的柚皮帽,戴在小孩的頭上十分合適,那個沒什麼稀奇玩具也無帽子可戴的我們,頂個柚皮帽覺有趣而新鮮,想像頭上頂著真正的帽子。切開後柚皮的香氣飄散著,泌出的柚皮油大人要我們抹在頭髮上,據說可以讓髮質烏亮柔順。
吃柚子的季節極短,因為就只限轉角那棵柚子,二十來顆,摘個三、四次就結束了,想要再吃就得等來年了。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種上一、二棵柚子,果實多不多或好不好吃不重要,不必花錢買才是主要考量,而會買柚子的都是花蓮市區「街仔路」的人。如果那年颱風來得多(五、六○年代颱風每年颳向花蓮,有時一個夏天好幾次。),柚子所剩無幾,甚至一顆也沒有,那麼那一年的中秋節就必然沒有柚子。
柚子樹比不上後院龍眼和柿子樹的高大,也不像釋迦的茂盛;或許因為那樣稀罕著柚子,或是它就在兩條小徑的轉角處,或是樹下是阿月和我玩耍的地方,是阿桑和外婆閒話家常的地方,它卻是外婆宅園中數十棵果樹中最重要也最顯眼。
走過了轉角,走過柚子樹,那個仰頭關注柚子抽長的小女孩輕聲細步,不知不覺走出小徑的另一頭,走出柚子樹的童年。
讀高中那一年,舅舅賣掉了宅園搬到市區;果樹被砍伐殆盡鋪上水泥成了一棟棟公寓,果園的樹開始在夢裡滋長延生,尤其轉角那棵柚子樹,樹下那顆磨得發亮的大石頭,風起時柚花飛舞如雪片飄落……。
和女兒談中秋節,談月餅談柚子還有他們最關心的烤肉。她說最滑稽的是讀小學前,我老是強迫她們戴柚子皮的帽子,硬生生把我的童年移植到她的頭上。我能移植的大概也只有那頂柚子皮帽,至於柚子樹下的童年往事,不是成天電腦前的他們能分享感受的。
比起女兒的童年有玩不完的玩具和豐盛的物資,我則有一棵柚子樹,豐富了我的童年。
台北寅時
認識台北從微光開始。
那一年高四重考生,白天曲蜷在館前路的補習班,晚上窩在窄仄宿舍,見到陽光的時間實在不多。第一次離家,害怕黃昏一盞盞點亮的路燈,也畏於家家戶戶窗內溫暖的光暈,晚膳的時間讓人覺得被遺落在孤島,家在數百里之外。華燈初上,台北的夜,對我是一種思鄉的折磨。
我常在清晨前醒來,像鴿子籠的宿舍沒有窗,細微亮光來自走道,走道的窗外是一小方天井,初秋寅時,天微微透光,像一張水墨,重重的灰青色渲染著,然後逐漸變淡轉亮,薄而弱的陽光灑入天井,天就亮了。
有時,坐在大門內的階梯上,從上方玻璃窗看見街道巷弄從黑夜走到天亮,從寂靜到嘈雜;天漸漸光是我認識台北最深沉的方式。爾後,我屢屢在子時到天微光才肯撇下濃夜的台北就寢。其實,來台北的前幾日,我也在天漸漸光中告別花蓮。
大學聯考完後幾天,幾個死黨聚集在月蘭海濱街的家,聊的都是茫茫的前程,五個人中只有純慈把握有學校唸,她在乎的只是國立或私立,瑤華想考夜大,錦秀要考三專,月蘭想找工作,我什麼都沒想,而且也篤定考不上任何大學。那個年代,高中的我們還不敢明目張膽的談戀愛,能聊的只有暗戀的對象或喜歡什麼類型的男友,五個女生談聯考、談大學、談毫無經驗的感情想像……聊著聊著,墨夜轉灰黑,天再過不久就會亮了。
走!去看日出。
幾分鐘後我們來到海邊的堤防。灰黑的夜色我們看不太清楚浪花刷洗沙岸的影像,然海潮一波波襲擊沙岸的聲音,在謐靜的夜裡,像竹扁籃篩豆子,每顆豆子滾動的音節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們走下堤防坐在一點點潮濕的海沙上。沒有人說話,安靜的等待日頭從太平洋的海面蹦跳出來,也彷彿在進行一種儀式,告別家鄉的日出海祭。再過些時日,我們將從蘇花公路或橫貫公路到異地工作或求學,把最純真質樸的人生留在此地,以海以日為鑑。
黑灰的天色轉為青灰,另一頭的沙岸有幾個人影,細細輕輕幾句交談聲,日出的祭典不宜喧譁,似乎成了默契。日頭宛如一顆火球從遙遠的下坡往上翻滾;從一點點光影亮在海面上,然後是一小片,繼續擴展成半圓,光影再奮力拉長拓展,沒有告知似的如一顆煮熟的湯圓,蹦!一顆火球冒出在滾燙的海面。哇的一片聲響,熱烈的話語紛紛落在沙灘上。
然後,我們真的各奔前程。
我在太陽升起後搭金馬號走蘇花公路、換火車走北宜線來到台北館前路的補習班,走出車站,紅紅大大的太陽低掛在西邊樓與樓之間的隙縫。
是那方天井的微光影響?爾後,我經常流連在台北的微光,晝日與睡神搏鬥。
多年後到報社工作,世紀末與世紀初,藉著夜晚工作,我名正言順的從子時流連到寅時,越夜越美麗,天色微亮才就寢。
台北有很多面貌,晝夜各有精彩。子時後的台北是另一種繁華;忠孝東路四段另一群人彷彿剛甦醒過來,車聲、攤販聲沸沸揚揚,買東西、看電影、吃消夜,子夜場的生活正式開演,復興南路的白粥滾熱著,KTV樓下的人進人出,烤香腸的氣味濃烈,敦化路的酒店霓虹燈熾豔,計程車、黑頭車來來去去,一個個敞開西裝拉歪領帶的男人,像煮熟的蝦子硬被塞進車子裡。
或者夜還淺一點,我下班離開南京東路二段的報社,第一批應酬結速的人背上貼著疲憊,車子乏力的往回家的路行駛。有時,我走路回家,從二段走到五段,路上行人愈來愈少,店家的燈一盞一盞的暗滅,有一種荒涼,猶如一條被棄置的街道,一棟棟人去樓空的建築。這條路布滿銀行、證券公司,白天汲汲營營的人群此時躲在夢裡安穩沉眠或煢煢孑立在夢中尋富迷失?屬於白晝生活的這群人正在安眠,這裡的夜已吹熄燈號,繁華黯然失色;白天翻騰的就讓暗黑來沉澱,白日的挫敗、煩悶就讓夜來舒緩撫慰。
回到家裡,讀小學的女兒已就寢,屋裡如遭竊一團雜亂,我像海螺女在子時前打掃整理、準備丈夫和女兒隔日的晚餐。審視女兒熟睡的臉後,燈火升起,我的夜才開始。
深夜裡有很多事可以做,也可以什麼都不做;有時寫作,有時閱讀,看電視或觀賞影片,夜雖暗沉,時間流動卻是快速的。寫作時,整個台北城我似乎只聽到敲打鍵盤的聲音,答‧答‧答篤篤脆亮的敲字聲響彷彿和心應答,是我的最愛。偶爾救護車或救火車的尖銳聲響刺破沉寂,隨即黑夜再度閉合沒了聲響,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
和文字交纏直到天色微光,幾聲脆亮的鳥叫聲,隱約可聽到公園早起人的招呼。我不捨的關了電腦、電視,合了書,拉開窗簾小縫隙,望著正在甦醒的街道,美麗的夜結束在寅時的微光中。熄燈就寢,在另一半的鼾聲中努力入睡。
有時,真的什麼都不做,不打字寫稿,不翻書,不看電視,坐著或站著,想事情或發呆,聽夜的流動,看光影的變化;燈光的城市沒有純粹墨黑的夜,總暈染著燈影顯得空洞寂寥,不似白天的燦亮翻騰。從橙黯的黑到深灰暗,再到青灰,燈光逐漸漸被稀弱,喧鬧的一天就要開始。
經常,我就坐在烏暗的夜裡,聽台北城最微弱的心跳,仿如叛逆者或過動兒終於酣睡的祥和呼吸聲。有時,也想起十八歲那年,在花蓮微光的海灘等待日出,那份質樸的心。從沉夜到天色微光,是我觀察一個城市最直接的方式;疲憊或酣睡的夜與人最貼近。
天漸漸光,是我一天的開始,也是結束。
轉角的柚子樹
永遠記得那兩條小徑,那是我的童年世界,邁著剛會走路的小短腿從這頭進入,高瘦的身軀從另一端走出來,快樂的童年就這麼結束了。
外婆的家園十分廣衮,千坪的果園圍繞著宅屋,對一個三、四歲的小孩來說,穿梭在果園中,簡直是走進一座森林。兩條小徑呈L型從家園中間穿過,是對外的通道;一邊的出口是溪邊,小阿姨洗衣服的地方,一邊通往大阿姨婆家的小路。兩條小徑交接的轉角有一棵樹,樹下有一顆被坐到發亮如圓桌的大石頭。鄰居的阿桑常搬個小凳子和外婆在樹下挑菜,有時她十四歲的養女阿月大剌剌跨坐在石頭上,和我說著阿桑如何虐待她,四、五歲的我不知道什麼是虐待。外婆的宅園附近就我們兩處住家,阿月的工作是餵豬、做飯和洗衣服,偶爾空閒的她大概也只能同我說話吧,儘管我完全不是她說話的對象。後來加入外婆果園的弟弟最喜歡爬上那顆大石頭再跳下來,經常摔得鼻青臉腫,甚至一次跳下來骨折,他卻樂此不疲。轉角的樹是柚子樹,外婆說和其他的果樹一樣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自己長出來的,在母親小時候就有了,也許有人吃了果實掉下的種籽,或是鳥、昆蟲叼了過來。是一棵老柚子樹,大半的時候它是引不起人注意的,即使最常在它樹下乘涼的阿桑和外婆,也從不關注它,不像園中的蓮霧,在端午節時外婆拿了柴刀朝樹幹底砍了幾道,掛上一串吃完粽子的粽繩,說是提醒花葉茂盛的蓮霧要如粽子般果實纍纍。也不像釋迦要稍折彎它的枝椏,免得過高不好採摘釋迦果。
外婆的宅園各種「自己長出來」的水果,四季交替的開花結實;春天才開始,楊桃垂掛黃綠色如同燈籠、土芭樂和野草莓一顆一顆的成熟;摘土芒果幼果是清明節;初夏早熟的蓮霧也可以摘來吃了,看到龍眼大概知道七月半的普渡要到了,接下來是柚子和柿子提醒中秋節來了,然後是那棵矮小的酸橘子紅了,過年轉眼就到了。還有滿園的釋迦,彷彿大半年都可以吃得到。
在外婆果園中我最喜歡柚子,不是它好吃,是它好玩。
柚子的好玩得從春夏開始。過了清明,柚子開花,白色的花蕊非常清香,香氣直逼玉蘭花,風輕輕拂盪柚子花似雪花般飄墜,整條小徑迴盪著花香,阿月撿起掉落的柚子花撒滿她的髮上,她說新娘子都戴花,有時偷偷拿著針線串成一條花鍊,我總央她也串一條給我。白色的柚子花鍊的確非常漂亮,且香氣繚繞,可惜戴了一個下午全掉光了。
夏天,整樹的小柚子如拳頭般大小,一個颱風常颳下一半的果實,我撿起落果當球玩,阿月拿著小柚子在髮上猛搓,她說柚子皮有油可以讓頭髮「烏金」。有時我們嘴饞,阿月硬是剝開柚子皮,柚肉細又硬,酸澀得讓我們只咬一口便扔了。
抵擋過颱風的柚子愈來愈大愈圓,也漸漸由深綠色轉為綠黃。外婆家的柚子不是文旦,圓形皮圓滑,淡粉色的果肉細小汁多但略酸。在還未吃過文旦之前,我以為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柚子。
貧窮匱乏的年代不做興賞月,中秋月圓不圓是其次,重要是有月餅可享用,而月餅的種類也極簡單,絕大多數是綠豆凸,蛋黃酥或蓮蓉月餅如同舶來品。直到我讀小學四、五年級,小姑姑到台北做事,中秋節帶回有著彩色玻璃紙包著的蓮蓉豆沙月餅,我們才知道原來中秋月餅不只是綠豆凸。
中秋節的綠豆凸比起其他節慶的糕餅或粿粽要來得稀罕,因為糕餅或粿粽都是阿嬤、母親動手做的,唯綠豆凸是買的。花錢買的東西絕對不會多,有配額限制,一年當中也只有中秋節才有,因此中秋節吃綠豆凸就顯得珍貴而慎重。
比起綠豆凸,柚子就平易近人,也不限定中秋節當天。
大約中秋節的前半個月左右,柚子約略成熟了。摘柚子是小孩最愛的事,站在樹下看著大人摘下後,我和弟弟及表弟妹搶著指定要哪一顆柚子,不是搶著吃柚肉,而是要那頂柚子皮。每次大概摘個五、六個柚子,也剛好是我們幾個小孩的數量,每人其實都會有一頂柚子皮帽,柚子也大同小異,只是先搶到的好像就是最好的。
剝柚子皮,台語是「刣柚仔」,大人用刀間隔劃開柚皮和瓤綿,取下柚肉,柚瓤皮就成了一頂六到八瓣膜左右的柚皮帽,戴在小孩的頭上十分合適,那個沒什麼稀奇玩具也無帽子可戴的我們,頂個柚皮帽覺有趣而新鮮,想像頭上頂著真正的帽子。切開後柚皮的香氣飄散著,泌出的柚皮油大人要我們抹在頭髮上,據說可以讓髮質烏亮柔順。
吃柚子的季節極短,因為就只限轉角那棵柚子,二十來顆,摘個三、四次就結束了,想要再吃就得等來年了。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種上一、二棵柚子,果實多不多或好不好吃不重要,不必花錢買才是主要考量,而會買柚子的都是花蓮市區「街仔路」的人。如果那年颱風來得多(五、六○年代颱風每年颳向花蓮,有時一個夏天好幾次。),柚子所剩無幾,甚至一顆也沒有,那麼那一年的中秋節就必然沒有柚子。
柚子樹比不上後院龍眼和柿子樹的高大,也不像釋迦的茂盛;或許因為那樣稀罕著柚子,或是它就在兩條小徑的轉角處,或是樹下是阿月和我玩耍的地方,是阿桑和外婆閒話家常的地方,它卻是外婆宅園中數十棵果樹中最重要也最顯眼。
走過了轉角,走過柚子樹,那個仰頭關注柚子抽長的小女孩輕聲細步,不知不覺走出小徑的另一頭,走出柚子樹的童年。
讀高中那一年,舅舅賣掉了宅園搬到市區;果樹被砍伐殆盡鋪上水泥成了一棟棟公寓,果園的樹開始在夢裡滋長延生,尤其轉角那棵柚子樹,樹下那顆磨得發亮的大石頭,風起時柚花飛舞如雪片飄落……。
和女兒談中秋節,談月餅談柚子還有他們最關心的烤肉。她說最滑稽的是讀小學前,我老是強迫她們戴柚子皮的帽子,硬生生把我的童年移植到她的頭上。我能移植的大概也只有那頂柚子皮帽,至於柚子樹下的童年往事,不是成天電腦前的他們能分享感受的。
比起女兒的童年有玩不完的玩具和豐盛的物資,我則有一棵柚子樹,豐富了我的童年。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