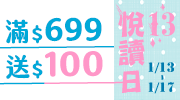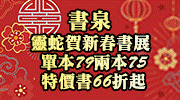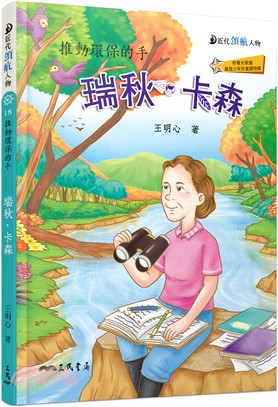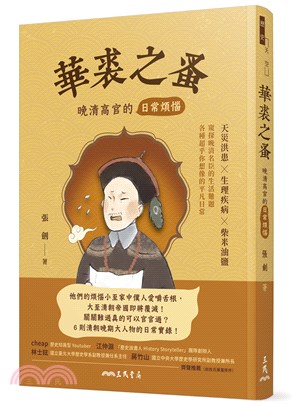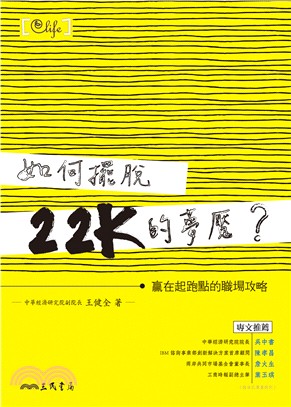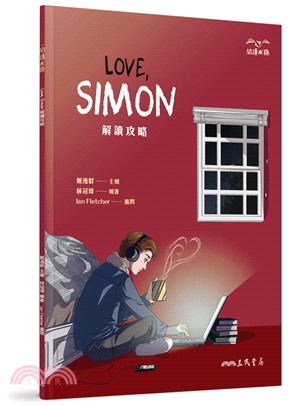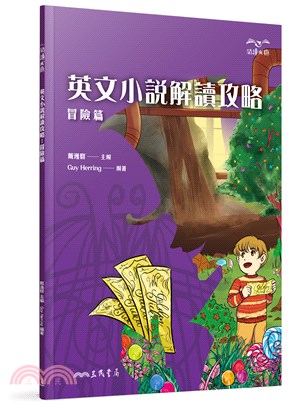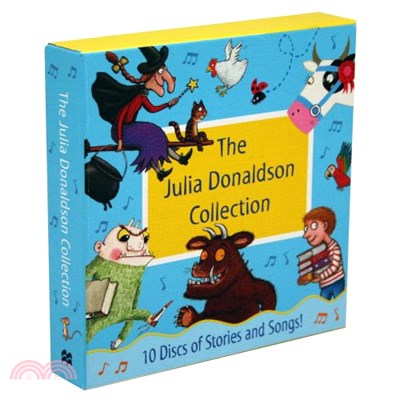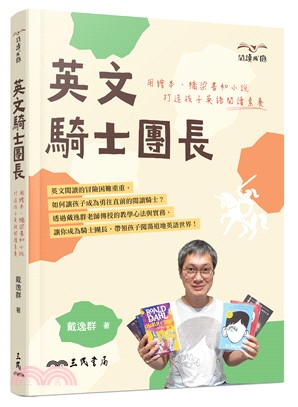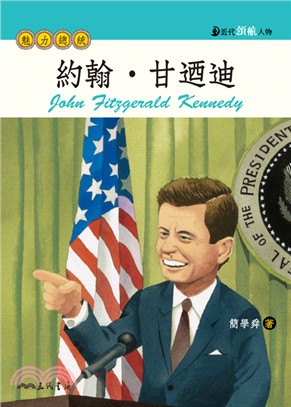臺北女生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本書獻給曾經如此渴望改變的我們,以及改變成真的以後——
苗博雅 專文推薦
小野、林達陽、羅毓嘉齊聲力挺
這些文字教我想起換季時節的臺北的河,想起河上巨大的連外橋,橋上能看見美麗的白芒花,花草上有風,風裡有許多願望,和失望。我曾為了許多事情沮喪,也曾努力變得頑強。可惜青春只有一回,沒有誰能經歷全部。謝謝菁芳,替我、我們,經歷了更痛但更好的可能。
——林達陽
「臺北」是讓很多臺灣人又愛又恨的地方;「女生」夾在時代的縫隙也是進退維谷。「臺北」加「女生」,則是集各種羨慕嫉妒恨的大成。……這種金光閃閃的菁英剖開內心世界,根本是絕對的政治錯誤呀!這種書,簡直是不知民間疾苦到了極點!因此,我願意推薦這本書。
——苗博雅
「這首都的願景與創新被老男人們佔據了版面。可其實,
臺北的輝煌繁華都是臺北女生撐起來的。」
臺北令人疲倦,蒼白,潮濕,臺北吞噬人的靈魂。多數人看臺北女生是一個女生,但其實是臺北讓人變成了臺北女生。來自島嶼各地,臺北女生們在這城裡拿青春搏鬥;從島嶼的首都畢業,臺北女生紛飛去世界爭一席之地。
她如她愛的島,都有獨立的姓名,自由的靈魂。
許菁芳的生命經驗是關於「獨立」的反省:從憤怒與迷惘的青春裡獨立,從既定的性別結構中獨立,從世界對臺灣的定義裡獨立。
過去數年間,臺灣的公民社會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這一輩臺灣青年曾經經歷過失望與憤怒,但像她一樣的臺灣青年也都在挫折裡傾心相愛,愛他們共同的島,組成共同體的人。
她紀錄了成長過程中的痛,痛的必要性,痛中有無數甜蜜。方年滿三十的她筆下所映照出的,不僅是她自身的,更是這一整個世代的青春、一個時代翻轉後的自我釐清,與終究會到來的成長。
她說:「在以為沒有以後的以後裡,我們繼續愛,繼續奮鬥。」
苗博雅 專文推薦
小野、林達陽、羅毓嘉齊聲力挺
這些文字教我想起換季時節的臺北的河,想起河上巨大的連外橋,橋上能看見美麗的白芒花,花草上有風,風裡有許多願望,和失望。我曾為了許多事情沮喪,也曾努力變得頑強。可惜青春只有一回,沒有誰能經歷全部。謝謝菁芳,替我、我們,經歷了更痛但更好的可能。
——林達陽
「臺北」是讓很多臺灣人又愛又恨的地方;「女生」夾在時代的縫隙也是進退維谷。「臺北」加「女生」,則是集各種羨慕嫉妒恨的大成。……這種金光閃閃的菁英剖開內心世界,根本是絕對的政治錯誤呀!這種書,簡直是不知民間疾苦到了極點!因此,我願意推薦這本書。
——苗博雅
「這首都的願景與創新被老男人們佔據了版面。可其實,
臺北的輝煌繁華都是臺北女生撐起來的。」
臺北令人疲倦,蒼白,潮濕,臺北吞噬人的靈魂。多數人看臺北女生是一個女生,但其實是臺北讓人變成了臺北女生。來自島嶼各地,臺北女生們在這城裡拿青春搏鬥;從島嶼的首都畢業,臺北女生紛飛去世界爭一席之地。
她如她愛的島,都有獨立的姓名,自由的靈魂。
許菁芳的生命經驗是關於「獨立」的反省:從憤怒與迷惘的青春裡獨立,從既定的性別結構中獨立,從世界對臺灣的定義裡獨立。
過去數年間,臺灣的公民社會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這一輩臺灣青年曾經經歷過失望與憤怒,但像她一樣的臺灣青年也都在挫折裡傾心相愛,愛他們共同的島,組成共同體的人。
她紀錄了成長過程中的痛,痛的必要性,痛中有無數甜蜜。方年滿三十的她筆下所映照出的,不僅是她自身的,更是這一整個世代的青春、一個時代翻轉後的自我釐清,與終究會到來的成長。
她說:「在以為沒有以後的以後裡,我們繼續愛,繼續奮鬥。」
作者簡介
許菁芳
高雄人,臺灣大學法律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律碩士,現居多倫多。文字作品散見於網路媒體,女人迷Womany專欄作家。
少時懞懞懂懂地做憤青,成人後是半調子文青。正職從事知識生產工作,關心東亞法治與民主。平日讀書寫字,跑步,摸貓,看電影。日常宅裡實踐女性主義,做獨立的人,做自由的臺灣人。
高雄人,臺灣大學法律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律碩士,現居多倫多。文字作品散見於網路媒體,女人迷Womany專欄作家。
少時懞懞懂懂地做憤青,成人後是半調子文青。正職從事知識生產工作,關心東亞法治與民主。平日讀書寫字,跑步,摸貓,看電影。日常宅裡實踐女性主義,做獨立的人,做自由的臺灣人。
序
【專文推薦】臺北不只是臺北,女生不只是女生 文/苗博雅
這本書,從書名就很大膽。
第一次聽到許菁芳的名字,是還在臺大法律讀書時。我是個把時間都拿去戀愛、運動、讀書的死大學生,許菁芳是校園學生自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
依稀記得那次學生會長選舉,雙方廝殺過程裡,出現了「許菁芳是民進黨派來的啦」的耳語,我覺得這種攻擊有點好笑(難道學生自治的參與者要對現實政治完全無知嗎),也直覺式地認為,這個敢在馬英九正夯、陳水扁正黑的年代,被貼上民進黨的標籤,還一直往前走的人,心臟還滿大顆的。
雖然當時沒去投票,後來也記不得「許菁芳」後來做了些什麼,但這個名字就此留在我的記憶裡。
放耳語的人都繪聲繪影地說,這些搞學生自治的,不單純,都是為了謀求自己的利益,以後就會去當幕僚、蹲地方、選議員、找機會往上跳,變成政客。
後來的後來,許菁芳出國讀書,走上學者的路(我知道,你可能會說學者就是政客的預備軍)。她開始更廣泛地寫作,寫人生、寫留學、寫性別、寫小故事、寫政治、寫愛情、寫分手、寫台灣、寫在一起、寫中國。
如果,她是那些人所說的,政客預備軍,那麼,這樣的寫作對她是危險的。她永遠不會知道,這些年累積的字,何時會變成對手(或自己人)拿來插在她背上的箭。
她持續地寫作,累積成專欄作家,累積成一本書。
而且這本書叫「臺北女生」。
「臺北」是讓很多臺灣人又愛又恨的地方;「女生」夾在時代的縫隙也是進退維谷。「臺北」加「女生」,則是集各種羨慕嫉妒恨的大成。臺大法律夠菁英吧?還是芝加哥大學、柏克萊大學雙碩士?還住在加拿大?!還敢說自己是「臺北女生」!這種金光閃閃的菁英剖開內心世界,根本是絕對的政治錯誤呀!這種書,簡直是不知民間疾苦到了極點!
因此,我願意推薦這本書。
這個年頭,想好好當個「人」都不容易;想讓各種人的疑難、自我質疑、自卑、自信、痛苦、快樂被看見、被承認,都不容易。越是擁有菁英的表象,越難讓外界認知到,「她/他也只不過,是個(ㄍㄜ˙)人」。
菁英臺北女生,必須是個女性主義者,但也不能是個女性主義者,要很溫柔、很包容、很博學、很精確、胸懷天下、關心弱勢、勇敢正直、善解人意。一旦不小心顯露笨拙、平凡、普通、自利,只不過是像個平凡人,難免就會得到「哈哈哈,UCCU」的迴音。
我願意拿掉那副批判菁英臺北女生的眼鏡,將這本書當成一個「人」的輕聲細語(有時也會提高音量),一個「人」的所見所思。
讀這本書,我可以沒有負擔地看到一個被視為菁英的臺北女生,她的人生、愛情、政治,她沒有要推銷你任何東西,在這本書裡,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個「人」。許菁芳的身分,集結了許多形成「易被酸體質」的要素,她曾經搞過學生自治、曾經得罪很多人、她應該要做得更好、應該要完美。這年頭,哪裡找得到這種敢公然傷春悲秋、稍微裸露內心小劇場的年輕女性知識分子呢。
我的推薦,不只是因為文字,更是因為許菁芳選擇了一條有趣的進路。一種在生活中實踐與庶民溝通的風格、一種學院菁英敢寫通俗作品任同儕以嚴厲眼光檢視的勇氣。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我知道這麼做,不簡單、不輕鬆,我由衷感到佩服。
【跋】以後 文/許菁芳
我們都不知道,會不會有以後
這本書寫於二零零九到二零一六年,紀錄著我以為沒有以後的以後。
第一次失戀的時候覺得人生沒有以後了,心如死木,再不能愛。國民黨復辟的時候也覺得台灣沒有以後了,自甘沈落的島。島上的人不知是愚昧或者無情無義,輕易把民主的成果承諾放煞。
但居然還有以後。有一天,胃痛停了,睡眠開始了。哭得再慘也還是獨立起來,收拾行李去更遠的地方。雪融的時候,跟人喝一杯啤酒,彷彿又有愛的可能。以後裡面國民黨居然輸慘了,不當黨產條例通過了,冤枉的死囚提起上訴。年輕人都醒了,美麗的女人們坐在街頭。資本家有一天,偶爾,不是每一次,必須低頭。台北的房價居然也跌了。
太陽花運動後的縣市長選舉,我在凌晨四點起床看開票,票開好,天也亮了。我去學校跑步,跑著跑著,眼淚流下臉頰,風吹在臉上很涼。終於贏了,我真沒想到我能看到這一天。自少時就徒勞無功推行的石頭突然推上山頂,定睛一看,竟然有這許多人不知不覺地站到身邊。偏過頭對妳一笑。瞬間春暖花開,像是愛了很久的初戀,突然回頭愛妳。
這愛裡諸多不順依舊,比方說工時還是太長,政府繼續拆人房子,帝國的陰影持續傾斜;而我的體脂還是很高。然而信心逐漸生長出來。我見識過了這島的生命力,黑色的莓旺盛地繁衍,金色的花頂天立地開放。心碎後柔軟粉嫩的新生觸感留在手心。
以後還會有以後。以後可能黑暗還是會籠罩世界。地震颱風可能再次使天崩地裂,威權可能會以更加幽微偽善的臉孔出現。但以後還會有以後。我留下了見證的文字。有一天如果失望再臨,再傷心、再度輕言放棄,願這本書裡碎碎暖暖的記憶流金,提醒我們:我們曾經有過以後。以後裡我們繼續愛,繼續奮鬥。
這些文字從二十三歲寫到三十歲,很快就不能再說自己是憤青了。但憤怒張狂的青春以後,還愛這島,與島上的人。
這本書,從書名就很大膽。
第一次聽到許菁芳的名字,是還在臺大法律讀書時。我是個把時間都拿去戀愛、運動、讀書的死大學生,許菁芳是校園學生自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
依稀記得那次學生會長選舉,雙方廝殺過程裡,出現了「許菁芳是民進黨派來的啦」的耳語,我覺得這種攻擊有點好笑(難道學生自治的參與者要對現實政治完全無知嗎),也直覺式地認為,這個敢在馬英九正夯、陳水扁正黑的年代,被貼上民進黨的標籤,還一直往前走的人,心臟還滿大顆的。
雖然當時沒去投票,後來也記不得「許菁芳」後來做了些什麼,但這個名字就此留在我的記憶裡。
放耳語的人都繪聲繪影地說,這些搞學生自治的,不單純,都是為了謀求自己的利益,以後就會去當幕僚、蹲地方、選議員、找機會往上跳,變成政客。
後來的後來,許菁芳出國讀書,走上學者的路(我知道,你可能會說學者就是政客的預備軍)。她開始更廣泛地寫作,寫人生、寫留學、寫性別、寫小故事、寫政治、寫愛情、寫分手、寫台灣、寫在一起、寫中國。
如果,她是那些人所說的,政客預備軍,那麼,這樣的寫作對她是危險的。她永遠不會知道,這些年累積的字,何時會變成對手(或自己人)拿來插在她背上的箭。
她持續地寫作,累積成專欄作家,累積成一本書。
而且這本書叫「臺北女生」。
「臺北」是讓很多臺灣人又愛又恨的地方;「女生」夾在時代的縫隙也是進退維谷。「臺北」加「女生」,則是集各種羨慕嫉妒恨的大成。臺大法律夠菁英吧?還是芝加哥大學、柏克萊大學雙碩士?還住在加拿大?!還敢說自己是「臺北女生」!這種金光閃閃的菁英剖開內心世界,根本是絕對的政治錯誤呀!這種書,簡直是不知民間疾苦到了極點!
因此,我願意推薦這本書。
這個年頭,想好好當個「人」都不容易;想讓各種人的疑難、自我質疑、自卑、自信、痛苦、快樂被看見、被承認,都不容易。越是擁有菁英的表象,越難讓外界認知到,「她/他也只不過,是個(ㄍㄜ˙)人」。
菁英臺北女生,必須是個女性主義者,但也不能是個女性主義者,要很溫柔、很包容、很博學、很精確、胸懷天下、關心弱勢、勇敢正直、善解人意。一旦不小心顯露笨拙、平凡、普通、自利,只不過是像個平凡人,難免就會得到「哈哈哈,UCCU」的迴音。
我願意拿掉那副批判菁英臺北女生的眼鏡,將這本書當成一個「人」的輕聲細語(有時也會提高音量),一個「人」的所見所思。
讀這本書,我可以沒有負擔地看到一個被視為菁英的臺北女生,她的人生、愛情、政治,她沒有要推銷你任何東西,在這本書裡,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個「人」。許菁芳的身分,集結了許多形成「易被酸體質」的要素,她曾經搞過學生自治、曾經得罪很多人、她應該要做得更好、應該要完美。這年頭,哪裡找得到這種敢公然傷春悲秋、稍微裸露內心小劇場的年輕女性知識分子呢。
我的推薦,不只是因為文字,更是因為許菁芳選擇了一條有趣的進路。一種在生活中實踐與庶民溝通的風格、一種學院菁英敢寫通俗作品任同儕以嚴厲眼光檢視的勇氣。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我知道這麼做,不簡單、不輕鬆,我由衷感到佩服。
【跋】以後 文/許菁芳
我們都不知道,會不會有以後
這本書寫於二零零九到二零一六年,紀錄著我以為沒有以後的以後。
第一次失戀的時候覺得人生沒有以後了,心如死木,再不能愛。國民黨復辟的時候也覺得台灣沒有以後了,自甘沈落的島。島上的人不知是愚昧或者無情無義,輕易把民主的成果承諾放煞。
但居然還有以後。有一天,胃痛停了,睡眠開始了。哭得再慘也還是獨立起來,收拾行李去更遠的地方。雪融的時候,跟人喝一杯啤酒,彷彿又有愛的可能。以後裡面國民黨居然輸慘了,不當黨產條例通過了,冤枉的死囚提起上訴。年輕人都醒了,美麗的女人們坐在街頭。資本家有一天,偶爾,不是每一次,必須低頭。台北的房價居然也跌了。
太陽花運動後的縣市長選舉,我在凌晨四點起床看開票,票開好,天也亮了。我去學校跑步,跑著跑著,眼淚流下臉頰,風吹在臉上很涼。終於贏了,我真沒想到我能看到這一天。自少時就徒勞無功推行的石頭突然推上山頂,定睛一看,竟然有這許多人不知不覺地站到身邊。偏過頭對妳一笑。瞬間春暖花開,像是愛了很久的初戀,突然回頭愛妳。
這愛裡諸多不順依舊,比方說工時還是太長,政府繼續拆人房子,帝國的陰影持續傾斜;而我的體脂還是很高。然而信心逐漸生長出來。我見識過了這島的生命力,黑色的莓旺盛地繁衍,金色的花頂天立地開放。心碎後柔軟粉嫩的新生觸感留在手心。
以後還會有以後。以後可能黑暗還是會籠罩世界。地震颱風可能再次使天崩地裂,威權可能會以更加幽微偽善的臉孔出現。但以後還會有以後。我留下了見證的文字。有一天如果失望再臨,再傷心、再度輕言放棄,願這本書裡碎碎暖暖的記憶流金,提醒我們:我們曾經有過以後。以後裡我們繼續愛,繼續奮鬥。
這些文字從二十三歲寫到三十歲,很快就不能再說自己是憤青了。但憤怒張狂的青春以後,還愛這島,與島上的人。
目次
目錄
臺北女生
中國前男友
臺大男生
少年阿寶
甜蜜垃圾話
林佩瑩
天天
生活在他方
經院路之始
寂寞美好
A Proper Farewell
獨立・運動
研討會
艾蜜莉
女博士
分手Final Push
分手Heartache Attack
分手To Part
擇偶條件
我與我的想像共同體
運味
我如何成為女性主義者
1106自由之夏
建築在死亡上的青春與愛
跋—以後 許菁芳
專文推薦—臺北不只是臺北,女生不只是女生 苗博雅
臺北女生
中國前男友
臺大男生
少年阿寶
甜蜜垃圾話
林佩瑩
天天
生活在他方
經院路之始
寂寞美好
A Proper Farewell
獨立・運動
研討會
艾蜜莉
女博士
分手Final Push
分手Heartache Attack
分手To Part
擇偶條件
我與我的想像共同體
運味
我如何成為女性主義者
1106自由之夏
建築在死亡上的青春與愛
跋—以後 許菁芳
專文推薦—臺北不只是臺北,女生不只是女生 苗博雅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臺北女生
難得沒事做,躺在沙發上聽了一個晚上的徐佳瑩。好久不關心台灣流行音樂,徐佳瑩居然已經出到第四張專輯了。滿好聽的:不只是她仍然從詞曲間隱隱透出的才華洋溢,許多編曲也做得很有味道。讓人得轉過身去正面看著她,要看著她,專心聽她說故事那種引人入勝。
她出道的超級星光大道也就是我唯一追過的一季。看流行歌曲比賽不是我的嗜好,甚至本來是有點鄙視的。但其他朋友在學生會辦公室裏看了起來,我也從善如流跟著看──哎呀,好好看啊。立刻折服成戲迷。女孩們都非常喜歡李伯恩,林芯儀的台語歌,一開口就征服所有南部小孩。我們跟著小胖老師、黃韻玲點評得頭頭是道。而親眼目睹、第一次聽見徐佳瑩的成名作《身騎白馬》,當然可以算是我們世代集體記憶之一了吧。沒有人能否認她那無法被錯認的才華和光彩,立刻就讓她變成她自己了。
五年後她累積了好多作品。Youtube上的自動播放清單轉呀轉,一口氣轉了十幾首歌,貓咪都聽到睡著了。
徐佳瑩變得好像是台北女生呀。畫了眼線畫了長長的睫毛,長長的腿長長的頭髮,在瀏海後抬眼靜靜定定地看著你。明明很在乎,但也知道在乎沒有用,誰在乎誰傷心,抱著這種心情進進出出感情間。在感情裡打死也不要吃虧。但真問她為什麼那麼怕吃虧,她也說不出所以然。睜著大大的眼睛,很有個性地,很美麗但很倔強地不要吃虧那樣。也可以喝酒也可以跳舞也可以帥氣地刷卡也可以跟男生回家也可以流浪在雙人床間。但她感冒時妳拎著熱湯去看她時,她很憔悴地坐在妳為她擺好的餐具前,怔怔流下淚來。妳作為一個好朋友,輕輕拍拍她的背。那樣的台北女生。
台北女生通常不真的是台北女生。台北女生往往有一個不是台北的家,在過年過節的時候要回去。她會從小小的租屋處,光鮮亮麗地拉著行李去搭捷運,搭到台北車站,在複雜的地下道間穿梭,上高鐵,坐下來,喝一口小七買的咖啡,聽哀鳳裡的音樂。她盡力維持那從都會區回到家鄉的形象。她不會離開台北很久,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好的收入可以四處旅行。也沒有那麼久的假期。而假期要節省起來去聽起來比較異國風味的歐洲。即使不去歐洲,也想去京都吃甜點看楓葉。比較標新立異的台北女生會去印度、泰國、柬埔寨。台北女生在鏡頭前笑得很美,分不清楚他在對誰笑,但她在那樣的角色扮演當中是得笑,就該那麼笑,很美地笑。
台北女生不想結婚但也不想單身。台北女生有能力-無論是經濟或智識上的-抵抗要把她捕捉回潛留在現代化城市下的父權暗流。那被寫好的,議程改都不能改的文化霸權。長輩說話不回嘴,老公晚歸做宵夜。彷彿她少也賤而多能鄙事的十八般武藝,在婚姻市場上都不算數,她孓然一身只剩下生育與照護的價值,任三姑六婆品頭論足。台北女生不是很喜歡單身,眼光也不是那麼高,她想找的是可以一起在人生裡旅行的伴侶,出現的卻總是想透過擁有她來證明自己是人生勝利組的男孩們。在玩具箱裡少一個漂亮能幹女朋友的男孩們。
「你是要我,還是要一個會認真聽你說話、陪伴你,跟你朋友家人處得來的有陰道的人類?」台北女生常常在心裡這樣默默地質問躺在身邊的男朋友們。
男朋友們都說現在女生沒有公主病最好了。但當台北女生皺著眉頭談論稅務、房地產或市長選舉的時候,台北女生好像又不可愛了。可愛到底是什麼?是馬尾,還是雙馬尾?是笑起來的時候會先抿一下嘴唇?是看電影的時候會被嚇一跳讓男生握住她的手?為什麼可愛總與激起雄性保護欲有正相關呢?但我覺得我的台北女生朋友們最可愛的時候是她們在熱炒店喝了啤酒大聲說「幹馬英九下台」。
真正的台北女生有軟弱的時候-城市是這樣一個會吞噬掉靈魂的黑洞啊-但她真的需要妳的時候她不是落難的公主。她是不得志的白居易,被一份雞肋般的工作勒得看不見出路,而台北居大不易。
這首都的願景與創新被老男人們佔據了版面。可其實,台北的輝煌繁華都是台北女生撐起來的。她們在城市機器裡做大大小小的螺絲釘,編織人群成政經網絡。在台北女生的手下,高樓從平地興起,夢想從遠方降落。她照料著百工在市井間穿梭,餵飽鰥寡孤獨,扶穩了改朝換代。台北女生老了的時候,還得走進政治人物的藉口裡,扮成淡水阿嬤叫人選總統。哎,真正的台北女生才不會叫人選總統。治大國如烹小鮮,她從廚房走出來可以直接走進總統府裡。後來選上總統的不就是個台北女生。
多數人看台北女生是一個女生,但我總覺得是台北讓人變成了台北女生。這城苦她心志,勞她筋骨,雖是咬著牙奮鬥卻仍然笑咪咪地,別人輕賤她卻還是心懷大志。
我聽了一個晚上的徐佳瑩。她問,「我們是不是比從前完整?和誰過著理想的人生?」我想著我曾經做過台北女生。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從台北畢業。我沒有跟誰一起過理想的人生。不過,幸好,我倒也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天降大任於斯,是那城裡讓我成了台北女生,終究能了人所不能。
------------
建築在死亡上的青春與愛
我始終覺得,對這島嶼有愛的年輕生命,註定了要經驗許多死亡與暴力。
**
首知陳文成博士之死,是在台大裡,就在他死去的草地旁。我是大二學生,鎮日睡到自然醒後去社團裡練舞,不怎麼上課。某天被學姊動員去參加學生會舉辦的紀念活動,本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坐在台下聽了半個多小時突然意會過來。台上他們在說的是:有一個人死在台大校園裡,是國民黨殺了他。
後來演講的老師跟學姊帶著大家穿出活動中心的側門,到陳文成博士當時的陳屍地點。我懵懵懂懂地跟在人群後面,人群的氣氛很奇怪。大約是那樣溫暖的春天夜裡,大學校園青春活潑的氣息太強盛了,怎樣都無法與陳文成的悲劇之死連結在一起。我默默看著草木旺盛的研究生圖書館邊際,實在無法想像,這裡曾經躺著一句被自殺的屍體。概念上知道是一件沈痛的事,但那時候我與死亡的交會非常少,白色恐怖的故事還躺在歷史課本裡,不在我的生活經驗裡,因此也沒有辦法體會痛苦的重量。
過了幾年,國民黨復辟了,台灣社會轉了個彎,我的生活也轉了個彎,進入了運動不斷的旋渦當中。大學最後一個學期的春天是鄭南榕自焚二十週年。我其實不太確定一開始是怎麼讀到鄭南榕的故事,只記得自己早在那場紀念活動之前就已經知道鄭南榕經營黨外雜誌,多次被停刊,仍然不斷出刊。國民黨威脅說將查封雜誌社並逮捕他,鄭南榕說,「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隨即在雜誌社開始自囚,囤積數桶瓦斯,準備在最後抓捕時刻引火自焚,慷慨成仁。鄭南榕在許多人的文字記錄中都非常鮮明突出,他抽很多煙,從大學時刻就是怪咖,因為拒絕修習三民主義因此沒有拿到台大畢業證書。他愛妻愛家,追求葉菊蘭的時候非常瘋狂,婚後生了一個女兒名為竹梅,也非常疼愛女兒,常常宣稱是跟別人的太太約會。
鄭南榕的死亡尖銳地擊中我。他的死亡如一場精心策劃的落櫻祭。因為他有渾然天成的神氣,他甘願拿他自己熠熠生光的靈魂獻祭。國民黨是一部殺人機器,他迎向前去,自燃成一股火焰在黑暗的歷史尾聲照亮道路。他燃燒自己血肉的時候必定是錐心的痛吧,我不斷想像著,其實也無法體會那肉體的痛,只感覺到心痛緩緩共鳴。他走了,餘下一世人面對還沒有獨立的台灣。
我記得自己一個人在宿舍電腦前看鄭南榕得意萬分的演講錄影片段。他用台語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他的手舉起來,說完後放下,自信地停頓著等待台下的掌聲。我也記得我讀了胡慧玲寫的紀念文,她說鄭南榕的女兒寫了一首詩。說鄭南榕是她的太陽,卻是她叫不回的太陽,太陽不見了,她覺得好冷好冷。我也記得我忍不住搜尋鄭南榕自焚照片,被焚燒焦黑的屍體,雙手仍然高舉。我當然也記得鄭南榕並不是唯一一個選擇自焚的烈士,還有在鄭南榕出殯當日奔向總統府,在拒馬前燃燒自己的詹益樺。詹益樺說,「鄭南榕是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
其實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鄭竹梅與葉菊蘭本人。我是女人,我總是忍不住搜尋歷史裡輕描淡寫帶過的女人。竹梅有略微方正的下巴,像是照片裡鄭南榕的輪廓;葉菊蘭竟然一點政治氣息都沒有,戴著一條長絲巾,像是氣質優雅的鄰居阿姨。參加完學生主辦的紀念活動之後,她坐在我們之間,跟我們說故事。她說,鄭南榕自焚那天她還有去上班,她在很大的廣告公司上班,是很帥氣專業的女強人,穿著高高的跟鞋急匆匆趕去雜誌社現場。她記得自己跟鞋踩在階梯上的聲音,很快很急。我後來默默跟蹤葉菊蘭的政治生涯,看了很多影片。鄭南榕死後她有一次公開講話,「我很愛很愛鄭南榕,我也很尊敬他,因為他愛的不是一個小小的太太,一個小孩,而是全台灣,他愛的是全台灣這一千九百多萬的人民。他今天為了台灣獨立,為了言論自由,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不看自己的太太,不看自己的小孩!」她說話的時候聲嘶力竭,因為她的眼淚一邊流著,聲音被哽咽住了,但她很清楚自己要說什麼,必須要說,因此她用盡力氣說。
我常想如果葉菊蘭不是葉菊蘭,鄭南榕還會不會是鄭南榕?烈士死了成了歷史,烈士的妻子繼續活著寫歷史。她與鄭南榕,一生一死,她的生與鄭南榕的死,力量是一樣強悍的;鄭南榕的死有多壯烈,她的生就有多強韌。
**
其實為台灣而死的人很多,實在是太多了,而且沒有被記得就被遺忘。大學時代啟蒙以來我困惑不已,為何我們如此善於遺忘?勇於遺忘難道不正是助長不義?
遺忘與記憶是歷史學家的課題,但如何面對記憶卻是每個公民必須做出的選擇。二零一四年,我剛進博士班。二二八前幾天中央社報導一場座談會,會中講者指稱二二八事件沒有元兇,甚至,日本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臉友們轉貼這篇報導,驚恐不已。已經七十年了,這樣的言論還能夠蟄伏在人們認知的邊緣,以話術將事實一筆勾銷。彷彿大批移動來台的飛機與軍隊,都是憑空出現;被捉捕與處決的人們,也都是憑空消失。槍枝與刀械在台灣人身上留下的傷口與血跡被掩埋在人們的記憶裡,不敢說也不敢想。
全世界的獨裁政權似乎都覺得,如果屠殺只存在在記憶裡,就不算是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沒有指揮官需要對暗夜的號哭與恐懼負責。
隔了幾天,讀歷史的朋友 F 寫了一篇文章紀念陳澄波。陳澄波是傑出的畫家,來自殖民地的平凡學徒,靠著天份與勤力,一躍而上日本帝國的藝術舞台。他的畫筆下有澄澈的淡水海波,有林木蓊鬱的嘉義公園。家人在他筆下有樸拙勤實的古風,孩子穿著胖胖的棉襖,戴瓜皮小帽。年夜飯時人們聚集在餐桌邊,畫家的眼是全視角,將全家人都包納進去。但陳澄波也是國民黨軍隊槍口下的犧牲者。作為地方仕紳,又因少時遊歷能說流利的北京話,人們仰賴他。在二二八的混亂之中,他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與政府對話的責任,穿戴好整齊的西裝前往水上機場與軍隊談判。
他挺直背脊,直挺挺地走進去;他的背脊也直挺挺地躺著出來。
他躺在那裡,直挺挺地躺著,死不瞑目的僵直著。我在許多場合都一再看見陳澄波躺在木板上的遺容。實在不好看,委屈橫死的,如何能好看。但我也逼著我自己看,不只是他,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輕易跳過那一張張死前凝視鏡頭、死後七竅流血的照片。因為死亡的面目如此,獨裁政權的本質如此。這塊土地承載過這些鮮血。此政權後來所宣稱的現代化與經濟奇蹟裡,還有一群被迫沈默的幽魂在背景遊蕩。後面世世代代也都沈默著,任憑教育與媒體一層層覆蓋上權力者的觀點,為著下一代不要心懷恐懼。無知便可以不恐懼。
但無知不是無所畏懼,無知只是無知。擁有知識才可能擁有無懼的勇氣。在真理面前人才能自由。這麼多年後,我們可以面對死亡的來龍去脈。
F 說:「終於我們活在了一個可以自由談論陳澄波的時代,終於我們對於這些過往,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心懷恐懼。我們可以記得他們,記得陳澄波,還有那些平白消失在歷史的人們。所以我們要一直記得。」
**
歷史裡的死亡其實沒有很遙遠,歷史裡的死亡往往在當下。台灣幾乎處處都是田野現場,一伸手就能觸碰到時代巨輪。
出國前後,中學歷史課綱的修改議題還沒有如野火般一發不可收拾,只是溫溫地悶燒在學術工作者之間。我追蹤這個議題許久,閱讀會議側記,相關的報導與部落格文看了很多,每有新發展也都抓空與身邊朋友討論。
無庸置疑,歷史的形塑是權力的展演 (The making of history is no doubt a political project)。歷史課綱的問題開始受到學者矚目,出身法國的高格孚教授來多倫多演講,開場白的第一句就這麼說。我坐在台下,心裡一驚。我是政治學的學生,我也看見了這歷史的書寫裡權力再赤裸不過。眼前浮起會議側記裡王曉波舌戰群雄的紀錄,又想起課綱比較表格中被粗暴改寫的移民觀點,清清楚楚,鬥爭就在跟前。
現時的鬥爭決定對過去的理解,爭的是過去,改變的卻是未來。歷史又遠又近。
不久後全台遍地烽火,高中生挺身而出接下反課綱大纛,正面迎擊教育部。從暮春到仲夏,我默默看著官僚閃爍其詞,避重就輕,對比學生簡單鮮明的訴求反差極大。可嘆年輕的時候,呼喊都是沒有回音的,奮力出擊徒遭反噬傷身。即使扛著再清晰不過的旗幟不斷吶喊,不斷捶打——權力者的身形卻穩如金湯。他揮一揮衣袖,年輕的生命墜落,他還是繼續揮一揮衣袖。
參與運動學生的自殺訊息傳來時,我正在比利時旅行。這頭是涼爽優美的布魯日,那頭卻是炎熱悲傷的台北。布魯日的美如夢似幻,據說是歐洲最適合度蜜月的浪漫城市之一。可我所經驗的那一天夏日是傷心欲絕的顏色。坐在民宿的大木桌邊,我看了學生與教育部官員會面的直播,心情低落。媒體鏡頭追著年輕的運動者跑,他們一出門就蹲坐在牆邊抱頭痛哭起來,我不忍看,感覺心裡有什麼埋藏得很好的傷痕也隱隱抽痛,拉著我也紅了眼眶。在運動裡,迷惘與挫敗都沒有盡頭,放眼望去只見得冷冷的世界萬頭鑽動。
**
為何體驗到權力邊界存在時,總是伴隨著巨量的淚水?國家是建立在死亡與暴力之上的,我逐漸理解。
博士班以來我每年都教同一門政治學導論。春季的授課教授品味很奇特,傳統的政治科學主題不太談,反而長篇大論地討論種族滅絕、猶太人大屠殺、優生學與絕育。偏鋒奇招的路數讓助教們很頭痛,這些題目很難讓十八九歲的大一新生起共鳴,討論課上大眼瞪小眼。我本來不明白老師究竟要透過這樣的討論帶我們去哪裡,有一天備課時卻突然恍然大悟:政治學是關於權力的學問,權力的本質正是暴力。與其歌頌讚揚國家的光輝,不如深入挖掘那光芒的核心。國家的過去掩蓋了許多死亡,必須要直視那死亡的形狀與樣貌,才能理解政治輪廓的來龍去脈。
這幾年來,我緩慢但有系統地閱讀學院對國家與社會的討論。國家是什麼?國家是壟斷正當武力使用的實體,韋伯說。在特定領土與人口裡,只有國家可以宣稱自己使用的武力是正當的,而且也只有國家擁有最強大的武力可以將其宣稱付諸實行。
說得更直白一點,國家就是勒索保護費的流氓,提供武力保護以交換稅收,這是提利 (Charles Tilly) 的一針見血。所謂戰爭創造國家正是如此:當權者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使土地上的人民甘心交出收入,必須以武力擊退內外威脅建立保護傘。隨著軍隊編制擴大,需要更多收入,現代治理制度逐漸成形以管理稅收與處置紛爭。頻繁的對外戰爭則加速、深化了這個過程,現代國家遂成型。
當然,戰爭的功能不只於此。戰爭是動員民族情感,劃下國家邊界的最好時刻。暴力清楚地分割出一條線,我們在線裡,他們在線外。線裡的是自己人,保護的是我的國家。
剛到加拿大,十一月初,發現許多同學的外套上都配戴紅色罌粟花,地鐵站裡有穿著制服的退伍軍人捧著盒子販售。罌粟花是戰亡將士紀念日的象徵,一開始只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殉亡士兵,後來衍伸到所有殉國服役者。加拿大始終沒有完全獨立離開大英國協,她的國家認同是循序漸進發展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她在國際上以獨立姿態展露頭角的重要經歷。
罌粟花的象徵來自於加拿大籍隨軍醫師 John McCrae 的詩作《在法蘭德斯戰場》:
罌粟花迎風在法蘭德斯戰場
綻放在十字架間,一排排一行行
標示我們死去的位置
天上雲雀仍在勇敢地歌唱,飛翔
人們充耳未聞,槍砲驟響
我們是死者,但在數天前
我們還活著,感受晨曙與夕陽
我們愛著也被愛著,但我們現在躺下了
在法蘭德斯戰場
輪到你們接手與敵人的戰鬥
從我們失敗的雙手中接過
火炬是你的了,高舉它
若辜負我們死去的信仰
我們將難以安息,即使罌粟花仍然生長
在法蘭德斯戰場
或許是因為是他國的死亡,或許因為其他原因,我對深秋四處飛揚的紅色罌粟花隱隱不安。我默默地想,為何國家認同總是建立在浪漫化的死亡上?不只有人得死,還必須有人再製那死亡。罌粟花飛揚在砲聲隆隆的壕溝間是多麽搶眼的對比畫面,然而戰士缺手斷腿的血腥死亡,卻在詩作裡巧妙地缺席。
為國家而死,是事實還是詮釋?是當權者的,還是人民的詮釋?
我逐漸捉摸清楚少時聽聞陳文成、鄭南榕之死的震動。沿著政治權力的浩浩川流,人的死亡被一分為二:逆者亡,順者昌。有利於當權者的死亡被吸納成國家的論述,殉戰者成烈士,史書記載英名,孩童在學校裡傳唱;而反抗政治權力的死亡,則被歷史遺忘,生存遺跡由國家的手塗乾抹淨。
死亡本身是事實,死亡的意義卻需要理解與詮釋。令我震動的死亡往往是反抗當權者的死亡。那樣的螳臂擋車的死亡,為著追求超乎個人與現實之外的理想。即使以後世的眼光看來是不切實際的嚮往,是缺乏基礎的執著,但不可錯認的是:死者眼裡看見了其他人看不見的遠方。並且坦然以生命做賭注前往。死亡原來是因為超越死亡的能量才有感動人心的力量。
他們死了,只是死了。但我若記得他的死亡,承擔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便有生命。
**
說來慚愧,我一直要到大學畢業之後才去了綠島。帶著兩個台美混血兒朋友去的,一行四人在船上吐得亂七八糟。走在小島上很熱,我們參觀監獄,吃海鮮,掛上泳鏡浮潛,兩個美國人興沖沖地試騎摩托車。我站在礁石磊磊的太平洋邊,藍色的海一望無際。迎面而來的海風黏黏鹹鹹,我的海島魂瞬間覺醒。
啊,我是海島的孩子無誤。
然而這溫暖豐富的熱帶島嶼景色,實在看不出來曾經承載了怎樣悲傷無望的暗夜。這海浪不知道吞吐了多少冤魂,有多少無名的冤魂曾經吞吐過我此時平靜呼息的空氣。
那段時間我非常排斥愛台灣這件事——我覺得我是真愛她,但我真是不得不愛這塊土地。我討厭那不得不。知道那些故事,碰觸過那些死亡與暴力,我不得不愛,不得不也拿出自己的心給她。畢業之後我做著一份貢獻於台灣的工作,但很不快樂。我常想,如果我不是出生在台灣,我應該可以更加理直氣壯、心無旁騖地選擇與追求個人的成功與快樂。但我終究是個台灣人,這塊土地生我育我,我沒辦法不憐惜她過去受的傷,沒辦法不欽佩她的掙扎與奮鬥,也沒辦法輕易地別過頭去,拒絕加入她對民主自由的百年追求。我必須愛她。
但是,如果有選擇,妳願意做台灣人嗎?我始終無法給自己一個問心無愧的答案。
二十歲下半局,在沒有盡頭的異國流浪之中,我很久不再追問這個問題。但從那漫長的沈默甦醒過來,我卻好像有了答案。
承擔肯認這塊土地上的死亡與暴力,是建立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年輕的時候,初識國家之惡總是恐懼,感覺自己孤身一人面對龐大的、死亡的陰影,它緊追在我背後。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學會:轉過身來,陽光就跟著眼光照進黑暗裡。
若我傾聽瘖啞者,以我的聲音訴說她的故事;若我為盲者見證,我們的凝視就能看見更遠的烏托邦。我是一個人,但是若我懷抱著前人的死亡與苦痛,我便不只是一個人。在這世界上,人不是獨立於歷史社會之外的存有,而是因為有了他人的給予與受付才有了生命的趣味。好好做人,做一個快樂的人,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也就是做個對過去有愛、對未來有希望的人。
過去與未來,愛與希望,都有根,環繞著我心有所向的台灣。
我選擇做堂堂正正的台灣人。如同小王子選擇了他的玫瑰一般,我也選擇了台灣。因為台灣是我從年少時就傾心相愛的,是我用身體與行動保護起來的。因為我以眼淚澆灌她,看顧她,因為我除滅她身上的毛蟲。我願意飛過高山海洋為她投下一票,帶她往公平正義的方向前進。我傾聽她的抱怨和自吹自擂,有時候也聽著她的沈默。她是獨一無二的——曾有人為她而死,我們願為她而死。而也不為什麼,只因為她是我們的玫瑰。
漢納鄂蘭說,「對於人類而言,思考過去的事物物意味著向深層境界移動,意味著扎根,讓自己穩定下來,使他們不至於被任何可能發生的事物席捲而去,不管那是所謂時代精神、大歷史,或者就只是單純的誘惑。」
經歷過暴力與死亡,我們的愛才有了絕對的方向。這塊土地必須更好。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做一個愛台灣的年輕人,註定要經歷眼淚與死亡了。因為黑暗裡光明是最明顯的,而愛在仇恨與壓迫裡才更加清晰。走過死亡的蔭谷,我們倚賴著彼此與對這塊土地的感情,成為堅強而溫柔的人,成為無所畏懼的台灣人。
這島的死亡歷歷,在那之上青春與愛茂盛生長。這塊土地必須更好,我願以青春護航。
臺北女生
難得沒事做,躺在沙發上聽了一個晚上的徐佳瑩。好久不關心台灣流行音樂,徐佳瑩居然已經出到第四張專輯了。滿好聽的:不只是她仍然從詞曲間隱隱透出的才華洋溢,許多編曲也做得很有味道。讓人得轉過身去正面看著她,要看著她,專心聽她說故事那種引人入勝。
她出道的超級星光大道也就是我唯一追過的一季。看流行歌曲比賽不是我的嗜好,甚至本來是有點鄙視的。但其他朋友在學生會辦公室裏看了起來,我也從善如流跟著看──哎呀,好好看啊。立刻折服成戲迷。女孩們都非常喜歡李伯恩,林芯儀的台語歌,一開口就征服所有南部小孩。我們跟著小胖老師、黃韻玲點評得頭頭是道。而親眼目睹、第一次聽見徐佳瑩的成名作《身騎白馬》,當然可以算是我們世代集體記憶之一了吧。沒有人能否認她那無法被錯認的才華和光彩,立刻就讓她變成她自己了。
五年後她累積了好多作品。Youtube上的自動播放清單轉呀轉,一口氣轉了十幾首歌,貓咪都聽到睡著了。
徐佳瑩變得好像是台北女生呀。畫了眼線畫了長長的睫毛,長長的腿長長的頭髮,在瀏海後抬眼靜靜定定地看著你。明明很在乎,但也知道在乎沒有用,誰在乎誰傷心,抱著這種心情進進出出感情間。在感情裡打死也不要吃虧。但真問她為什麼那麼怕吃虧,她也說不出所以然。睜著大大的眼睛,很有個性地,很美麗但很倔強地不要吃虧那樣。也可以喝酒也可以跳舞也可以帥氣地刷卡也可以跟男生回家也可以流浪在雙人床間。但她感冒時妳拎著熱湯去看她時,她很憔悴地坐在妳為她擺好的餐具前,怔怔流下淚來。妳作為一個好朋友,輕輕拍拍她的背。那樣的台北女生。
台北女生通常不真的是台北女生。台北女生往往有一個不是台北的家,在過年過節的時候要回去。她會從小小的租屋處,光鮮亮麗地拉著行李去搭捷運,搭到台北車站,在複雜的地下道間穿梭,上高鐵,坐下來,喝一口小七買的咖啡,聽哀鳳裡的音樂。她盡力維持那從都會區回到家鄉的形象。她不會離開台北很久,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好的收入可以四處旅行。也沒有那麼久的假期。而假期要節省起來去聽起來比較異國風味的歐洲。即使不去歐洲,也想去京都吃甜點看楓葉。比較標新立異的台北女生會去印度、泰國、柬埔寨。台北女生在鏡頭前笑得很美,分不清楚他在對誰笑,但她在那樣的角色扮演當中是得笑,就該那麼笑,很美地笑。
台北女生不想結婚但也不想單身。台北女生有能力-無論是經濟或智識上的-抵抗要把她捕捉回潛留在現代化城市下的父權暗流。那被寫好的,議程改都不能改的文化霸權。長輩說話不回嘴,老公晚歸做宵夜。彷彿她少也賤而多能鄙事的十八般武藝,在婚姻市場上都不算數,她孓然一身只剩下生育與照護的價值,任三姑六婆品頭論足。台北女生不是很喜歡單身,眼光也不是那麼高,她想找的是可以一起在人生裡旅行的伴侶,出現的卻總是想透過擁有她來證明自己是人生勝利組的男孩們。在玩具箱裡少一個漂亮能幹女朋友的男孩們。
「你是要我,還是要一個會認真聽你說話、陪伴你,跟你朋友家人處得來的有陰道的人類?」台北女生常常在心裡這樣默默地質問躺在身邊的男朋友們。
男朋友們都說現在女生沒有公主病最好了。但當台北女生皺著眉頭談論稅務、房地產或市長選舉的時候,台北女生好像又不可愛了。可愛到底是什麼?是馬尾,還是雙馬尾?是笑起來的時候會先抿一下嘴唇?是看電影的時候會被嚇一跳讓男生握住她的手?為什麼可愛總與激起雄性保護欲有正相關呢?但我覺得我的台北女生朋友們最可愛的時候是她們在熱炒店喝了啤酒大聲說「幹馬英九下台」。
真正的台北女生有軟弱的時候-城市是這樣一個會吞噬掉靈魂的黑洞啊-但她真的需要妳的時候她不是落難的公主。她是不得志的白居易,被一份雞肋般的工作勒得看不見出路,而台北居大不易。
這首都的願景與創新被老男人們佔據了版面。可其實,台北的輝煌繁華都是台北女生撐起來的。她們在城市機器裡做大大小小的螺絲釘,編織人群成政經網絡。在台北女生的手下,高樓從平地興起,夢想從遠方降落。她照料著百工在市井間穿梭,餵飽鰥寡孤獨,扶穩了改朝換代。台北女生老了的時候,還得走進政治人物的藉口裡,扮成淡水阿嬤叫人選總統。哎,真正的台北女生才不會叫人選總統。治大國如烹小鮮,她從廚房走出來可以直接走進總統府裡。後來選上總統的不就是個台北女生。
多數人看台北女生是一個女生,但我總覺得是台北讓人變成了台北女生。這城苦她心志,勞她筋骨,雖是咬著牙奮鬥卻仍然笑咪咪地,別人輕賤她卻還是心懷大志。
我聽了一個晚上的徐佳瑩。她問,「我們是不是比從前完整?和誰過著理想的人生?」我想著我曾經做過台北女生。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從台北畢業。我沒有跟誰一起過理想的人生。不過,幸好,我倒也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天降大任於斯,是那城裡讓我成了台北女生,終究能了人所不能。
------------
建築在死亡上的青春與愛
我始終覺得,對這島嶼有愛的年輕生命,註定了要經驗許多死亡與暴力。
**
首知陳文成博士之死,是在台大裡,就在他死去的草地旁。我是大二學生,鎮日睡到自然醒後去社團裡練舞,不怎麼上課。某天被學姊動員去參加學生會舉辦的紀念活動,本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坐在台下聽了半個多小時突然意會過來。台上他們在說的是:有一個人死在台大校園裡,是國民黨殺了他。
後來演講的老師跟學姊帶著大家穿出活動中心的側門,到陳文成博士當時的陳屍地點。我懵懵懂懂地跟在人群後面,人群的氣氛很奇怪。大約是那樣溫暖的春天夜裡,大學校園青春活潑的氣息太強盛了,怎樣都無法與陳文成的悲劇之死連結在一起。我默默看著草木旺盛的研究生圖書館邊際,實在無法想像,這裡曾經躺著一句被自殺的屍體。概念上知道是一件沈痛的事,但那時候我與死亡的交會非常少,白色恐怖的故事還躺在歷史課本裡,不在我的生活經驗裡,因此也沒有辦法體會痛苦的重量。
過了幾年,國民黨復辟了,台灣社會轉了個彎,我的生活也轉了個彎,進入了運動不斷的旋渦當中。大學最後一個學期的春天是鄭南榕自焚二十週年。我其實不太確定一開始是怎麼讀到鄭南榕的故事,只記得自己早在那場紀念活動之前就已經知道鄭南榕經營黨外雜誌,多次被停刊,仍然不斷出刊。國民黨威脅說將查封雜誌社並逮捕他,鄭南榕說,「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隨即在雜誌社開始自囚,囤積數桶瓦斯,準備在最後抓捕時刻引火自焚,慷慨成仁。鄭南榕在許多人的文字記錄中都非常鮮明突出,他抽很多煙,從大學時刻就是怪咖,因為拒絕修習三民主義因此沒有拿到台大畢業證書。他愛妻愛家,追求葉菊蘭的時候非常瘋狂,婚後生了一個女兒名為竹梅,也非常疼愛女兒,常常宣稱是跟別人的太太約會。
鄭南榕的死亡尖銳地擊中我。他的死亡如一場精心策劃的落櫻祭。因為他有渾然天成的神氣,他甘願拿他自己熠熠生光的靈魂獻祭。國民黨是一部殺人機器,他迎向前去,自燃成一股火焰在黑暗的歷史尾聲照亮道路。他燃燒自己血肉的時候必定是錐心的痛吧,我不斷想像著,其實也無法體會那肉體的痛,只感覺到心痛緩緩共鳴。他走了,餘下一世人面對還沒有獨立的台灣。
我記得自己一個人在宿舍電腦前看鄭南榕得意萬分的演講錄影片段。他用台語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他的手舉起來,說完後放下,自信地停頓著等待台下的掌聲。我也記得我讀了胡慧玲寫的紀念文,她說鄭南榕的女兒寫了一首詩。說鄭南榕是她的太陽,卻是她叫不回的太陽,太陽不見了,她覺得好冷好冷。我也記得我忍不住搜尋鄭南榕自焚照片,被焚燒焦黑的屍體,雙手仍然高舉。我當然也記得鄭南榕並不是唯一一個選擇自焚的烈士,還有在鄭南榕出殯當日奔向總統府,在拒馬前燃燒自己的詹益樺。詹益樺說,「鄭南榕是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
其實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鄭竹梅與葉菊蘭本人。我是女人,我總是忍不住搜尋歷史裡輕描淡寫帶過的女人。竹梅有略微方正的下巴,像是照片裡鄭南榕的輪廓;葉菊蘭竟然一點政治氣息都沒有,戴著一條長絲巾,像是氣質優雅的鄰居阿姨。參加完學生主辦的紀念活動之後,她坐在我們之間,跟我們說故事。她說,鄭南榕自焚那天她還有去上班,她在很大的廣告公司上班,是很帥氣專業的女強人,穿著高高的跟鞋急匆匆趕去雜誌社現場。她記得自己跟鞋踩在階梯上的聲音,很快很急。我後來默默跟蹤葉菊蘭的政治生涯,看了很多影片。鄭南榕死後她有一次公開講話,「我很愛很愛鄭南榕,我也很尊敬他,因為他愛的不是一個小小的太太,一個小孩,而是全台灣,他愛的是全台灣這一千九百多萬的人民。他今天為了台灣獨立,為了言論自由,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不看自己的太太,不看自己的小孩!」她說話的時候聲嘶力竭,因為她的眼淚一邊流著,聲音被哽咽住了,但她很清楚自己要說什麼,必須要說,因此她用盡力氣說。
我常想如果葉菊蘭不是葉菊蘭,鄭南榕還會不會是鄭南榕?烈士死了成了歷史,烈士的妻子繼續活著寫歷史。她與鄭南榕,一生一死,她的生與鄭南榕的死,力量是一樣強悍的;鄭南榕的死有多壯烈,她的生就有多強韌。
**
其實為台灣而死的人很多,實在是太多了,而且沒有被記得就被遺忘。大學時代啟蒙以來我困惑不已,為何我們如此善於遺忘?勇於遺忘難道不正是助長不義?
遺忘與記憶是歷史學家的課題,但如何面對記憶卻是每個公民必須做出的選擇。二零一四年,我剛進博士班。二二八前幾天中央社報導一場座談會,會中講者指稱二二八事件沒有元兇,甚至,日本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臉友們轉貼這篇報導,驚恐不已。已經七十年了,這樣的言論還能夠蟄伏在人們認知的邊緣,以話術將事實一筆勾銷。彷彿大批移動來台的飛機與軍隊,都是憑空出現;被捉捕與處決的人們,也都是憑空消失。槍枝與刀械在台灣人身上留下的傷口與血跡被掩埋在人們的記憶裡,不敢說也不敢想。
全世界的獨裁政權似乎都覺得,如果屠殺只存在在記憶裡,就不算是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沒有指揮官需要對暗夜的號哭與恐懼負責。
隔了幾天,讀歷史的朋友 F 寫了一篇文章紀念陳澄波。陳澄波是傑出的畫家,來自殖民地的平凡學徒,靠著天份與勤力,一躍而上日本帝國的藝術舞台。他的畫筆下有澄澈的淡水海波,有林木蓊鬱的嘉義公園。家人在他筆下有樸拙勤實的古風,孩子穿著胖胖的棉襖,戴瓜皮小帽。年夜飯時人們聚集在餐桌邊,畫家的眼是全視角,將全家人都包納進去。但陳澄波也是國民黨軍隊槍口下的犧牲者。作為地方仕紳,又因少時遊歷能說流利的北京話,人們仰賴他。在二二八的混亂之中,他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與政府對話的責任,穿戴好整齊的西裝前往水上機場與軍隊談判。
他挺直背脊,直挺挺地走進去;他的背脊也直挺挺地躺著出來。
他躺在那裡,直挺挺地躺著,死不瞑目的僵直著。我在許多場合都一再看見陳澄波躺在木板上的遺容。實在不好看,委屈橫死的,如何能好看。但我也逼著我自己看,不只是他,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輕易跳過那一張張死前凝視鏡頭、死後七竅流血的照片。因為死亡的面目如此,獨裁政權的本質如此。這塊土地承載過這些鮮血。此政權後來所宣稱的現代化與經濟奇蹟裡,還有一群被迫沈默的幽魂在背景遊蕩。後面世世代代也都沈默著,任憑教育與媒體一層層覆蓋上權力者的觀點,為著下一代不要心懷恐懼。無知便可以不恐懼。
但無知不是無所畏懼,無知只是無知。擁有知識才可能擁有無懼的勇氣。在真理面前人才能自由。這麼多年後,我們可以面對死亡的來龍去脈。
F 說:「終於我們活在了一個可以自由談論陳澄波的時代,終於我們對於這些過往,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心懷恐懼。我們可以記得他們,記得陳澄波,還有那些平白消失在歷史的人們。所以我們要一直記得。」
**
歷史裡的死亡其實沒有很遙遠,歷史裡的死亡往往在當下。台灣幾乎處處都是田野現場,一伸手就能觸碰到時代巨輪。
出國前後,中學歷史課綱的修改議題還沒有如野火般一發不可收拾,只是溫溫地悶燒在學術工作者之間。我追蹤這個議題許久,閱讀會議側記,相關的報導與部落格文看了很多,每有新發展也都抓空與身邊朋友討論。
無庸置疑,歷史的形塑是權力的展演 (The making of history is no doubt a political project)。歷史課綱的問題開始受到學者矚目,出身法國的高格孚教授來多倫多演講,開場白的第一句就這麼說。我坐在台下,心裡一驚。我是政治學的學生,我也看見了這歷史的書寫裡權力再赤裸不過。眼前浮起會議側記裡王曉波舌戰群雄的紀錄,又想起課綱比較表格中被粗暴改寫的移民觀點,清清楚楚,鬥爭就在跟前。
現時的鬥爭決定對過去的理解,爭的是過去,改變的卻是未來。歷史又遠又近。
不久後全台遍地烽火,高中生挺身而出接下反課綱大纛,正面迎擊教育部。從暮春到仲夏,我默默看著官僚閃爍其詞,避重就輕,對比學生簡單鮮明的訴求反差極大。可嘆年輕的時候,呼喊都是沒有回音的,奮力出擊徒遭反噬傷身。即使扛著再清晰不過的旗幟不斷吶喊,不斷捶打——權力者的身形卻穩如金湯。他揮一揮衣袖,年輕的生命墜落,他還是繼續揮一揮衣袖。
參與運動學生的自殺訊息傳來時,我正在比利時旅行。這頭是涼爽優美的布魯日,那頭卻是炎熱悲傷的台北。布魯日的美如夢似幻,據說是歐洲最適合度蜜月的浪漫城市之一。可我所經驗的那一天夏日是傷心欲絕的顏色。坐在民宿的大木桌邊,我看了學生與教育部官員會面的直播,心情低落。媒體鏡頭追著年輕的運動者跑,他們一出門就蹲坐在牆邊抱頭痛哭起來,我不忍看,感覺心裡有什麼埋藏得很好的傷痕也隱隱抽痛,拉著我也紅了眼眶。在運動裡,迷惘與挫敗都沒有盡頭,放眼望去只見得冷冷的世界萬頭鑽動。
**
為何體驗到權力邊界存在時,總是伴隨著巨量的淚水?國家是建立在死亡與暴力之上的,我逐漸理解。
博士班以來我每年都教同一門政治學導論。春季的授課教授品味很奇特,傳統的政治科學主題不太談,反而長篇大論地討論種族滅絕、猶太人大屠殺、優生學與絕育。偏鋒奇招的路數讓助教們很頭痛,這些題目很難讓十八九歲的大一新生起共鳴,討論課上大眼瞪小眼。我本來不明白老師究竟要透過這樣的討論帶我們去哪裡,有一天備課時卻突然恍然大悟:政治學是關於權力的學問,權力的本質正是暴力。與其歌頌讚揚國家的光輝,不如深入挖掘那光芒的核心。國家的過去掩蓋了許多死亡,必須要直視那死亡的形狀與樣貌,才能理解政治輪廓的來龍去脈。
這幾年來,我緩慢但有系統地閱讀學院對國家與社會的討論。國家是什麼?國家是壟斷正當武力使用的實體,韋伯說。在特定領土與人口裡,只有國家可以宣稱自己使用的武力是正當的,而且也只有國家擁有最強大的武力可以將其宣稱付諸實行。
說得更直白一點,國家就是勒索保護費的流氓,提供武力保護以交換稅收,這是提利 (Charles Tilly) 的一針見血。所謂戰爭創造國家正是如此:當權者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使土地上的人民甘心交出收入,必須以武力擊退內外威脅建立保護傘。隨著軍隊編制擴大,需要更多收入,現代治理制度逐漸成形以管理稅收與處置紛爭。頻繁的對外戰爭則加速、深化了這個過程,現代國家遂成型。
當然,戰爭的功能不只於此。戰爭是動員民族情感,劃下國家邊界的最好時刻。暴力清楚地分割出一條線,我們在線裡,他們在線外。線裡的是自己人,保護的是我的國家。
剛到加拿大,十一月初,發現許多同學的外套上都配戴紅色罌粟花,地鐵站裡有穿著制服的退伍軍人捧著盒子販售。罌粟花是戰亡將士紀念日的象徵,一開始只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殉亡士兵,後來衍伸到所有殉國服役者。加拿大始終沒有完全獨立離開大英國協,她的國家認同是循序漸進發展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她在國際上以獨立姿態展露頭角的重要經歷。
罌粟花的象徵來自於加拿大籍隨軍醫師 John McCrae 的詩作《在法蘭德斯戰場》:
罌粟花迎風在法蘭德斯戰場
綻放在十字架間,一排排一行行
標示我們死去的位置
天上雲雀仍在勇敢地歌唱,飛翔
人們充耳未聞,槍砲驟響
我們是死者,但在數天前
我們還活著,感受晨曙與夕陽
我們愛著也被愛著,但我們現在躺下了
在法蘭德斯戰場
輪到你們接手與敵人的戰鬥
從我們失敗的雙手中接過
火炬是你的了,高舉它
若辜負我們死去的信仰
我們將難以安息,即使罌粟花仍然生長
在法蘭德斯戰場
或許是因為是他國的死亡,或許因為其他原因,我對深秋四處飛揚的紅色罌粟花隱隱不安。我默默地想,為何國家認同總是建立在浪漫化的死亡上?不只有人得死,還必須有人再製那死亡。罌粟花飛揚在砲聲隆隆的壕溝間是多麽搶眼的對比畫面,然而戰士缺手斷腿的血腥死亡,卻在詩作裡巧妙地缺席。
為國家而死,是事實還是詮釋?是當權者的,還是人民的詮釋?
我逐漸捉摸清楚少時聽聞陳文成、鄭南榕之死的震動。沿著政治權力的浩浩川流,人的死亡被一分為二:逆者亡,順者昌。有利於當權者的死亡被吸納成國家的論述,殉戰者成烈士,史書記載英名,孩童在學校裡傳唱;而反抗政治權力的死亡,則被歷史遺忘,生存遺跡由國家的手塗乾抹淨。
死亡本身是事實,死亡的意義卻需要理解與詮釋。令我震動的死亡往往是反抗當權者的死亡。那樣的螳臂擋車的死亡,為著追求超乎個人與現實之外的理想。即使以後世的眼光看來是不切實際的嚮往,是缺乏基礎的執著,但不可錯認的是:死者眼裡看見了其他人看不見的遠方。並且坦然以生命做賭注前往。死亡原來是因為超越死亡的能量才有感動人心的力量。
他們死了,只是死了。但我若記得他的死亡,承擔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便有生命。
**
說來慚愧,我一直要到大學畢業之後才去了綠島。帶著兩個台美混血兒朋友去的,一行四人在船上吐得亂七八糟。走在小島上很熱,我們參觀監獄,吃海鮮,掛上泳鏡浮潛,兩個美國人興沖沖地試騎摩托車。我站在礁石磊磊的太平洋邊,藍色的海一望無際。迎面而來的海風黏黏鹹鹹,我的海島魂瞬間覺醒。
啊,我是海島的孩子無誤。
然而這溫暖豐富的熱帶島嶼景色,實在看不出來曾經承載了怎樣悲傷無望的暗夜。這海浪不知道吞吐了多少冤魂,有多少無名的冤魂曾經吞吐過我此時平靜呼息的空氣。
那段時間我非常排斥愛台灣這件事——我覺得我是真愛她,但我真是不得不愛這塊土地。我討厭那不得不。知道那些故事,碰觸過那些死亡與暴力,我不得不愛,不得不也拿出自己的心給她。畢業之後我做著一份貢獻於台灣的工作,但很不快樂。我常想,如果我不是出生在台灣,我應該可以更加理直氣壯、心無旁騖地選擇與追求個人的成功與快樂。但我終究是個台灣人,這塊土地生我育我,我沒辦法不憐惜她過去受的傷,沒辦法不欽佩她的掙扎與奮鬥,也沒辦法輕易地別過頭去,拒絕加入她對民主自由的百年追求。我必須愛她。
但是,如果有選擇,妳願意做台灣人嗎?我始終無法給自己一個問心無愧的答案。
二十歲下半局,在沒有盡頭的異國流浪之中,我很久不再追問這個問題。但從那漫長的沈默甦醒過來,我卻好像有了答案。
承擔肯認這塊土地上的死亡與暴力,是建立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年輕的時候,初識國家之惡總是恐懼,感覺自己孤身一人面對龐大的、死亡的陰影,它緊追在我背後。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學會:轉過身來,陽光就跟著眼光照進黑暗裡。
若我傾聽瘖啞者,以我的聲音訴說她的故事;若我為盲者見證,我們的凝視就能看見更遠的烏托邦。我是一個人,但是若我懷抱著前人的死亡與苦痛,我便不只是一個人。在這世界上,人不是獨立於歷史社會之外的存有,而是因為有了他人的給予與受付才有了生命的趣味。好好做人,做一個快樂的人,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也就是做個對過去有愛、對未來有希望的人。
過去與未來,愛與希望,都有根,環繞著我心有所向的台灣。
我選擇做堂堂正正的台灣人。如同小王子選擇了他的玫瑰一般,我也選擇了台灣。因為台灣是我從年少時就傾心相愛的,是我用身體與行動保護起來的。因為我以眼淚澆灌她,看顧她,因為我除滅她身上的毛蟲。我願意飛過高山海洋為她投下一票,帶她往公平正義的方向前進。我傾聽她的抱怨和自吹自擂,有時候也聽著她的沈默。她是獨一無二的——曾有人為她而死,我們願為她而死。而也不為什麼,只因為她是我們的玫瑰。
漢納鄂蘭說,「對於人類而言,思考過去的事物物意味著向深層境界移動,意味著扎根,讓自己穩定下來,使他們不至於被任何可能發生的事物席捲而去,不管那是所謂時代精神、大歷史,或者就只是單純的誘惑。」
經歷過暴力與死亡,我們的愛才有了絕對的方向。這塊土地必須更好。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做一個愛台灣的年輕人,註定要經歷眼淚與死亡了。因為黑暗裡光明是最明顯的,而愛在仇恨與壓迫裡才更加清晰。走過死亡的蔭谷,我們倚賴著彼此與對這塊土地的感情,成為堅強而溫柔的人,成為無所畏懼的台灣人。
這島的死亡歷歷,在那之上青春與愛茂盛生長。這塊土地必須更好,我願以青春護航。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