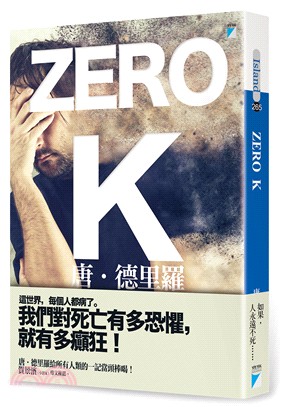定價
:NT$ 350 元優惠價
:90 折 315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這世界,每個人都病了。
我們對死亡有多恐懼,就有多癲狂!
唐‧德里羅給所有人類的一記當頭棒喝!
賀景濱(小說家)專文推薦。
這部小說,是一柄閃著寒光的利刃,輕輕挪移近我們的脖子。
我在我的跛腿中看見自己,也在我培養這跛腿的方法中看見自己。
但每回父親帶我參觀自然史博物館,
我便會把跛腿殺死。
億萬富翁羅斯正祕密投資一項驚人的事業──將人「冷凍保存」,直到未來不治之症找到治療方式,人們再從沉睡狀態甦醒過來。他患重症的年輕妻子,成了實驗者,而當妻子做了這決定後,羅斯也決定追隨。
只是,當與前妻所生下的兒子傑佛瑞的出現,卻動搖了羅斯。
羅斯在傑佛瑞13歲那一年離家,從那一刻起,傑佛瑞咬著舌頭說話,拖著腳步走路,把頭中間一片頭髮由前到後剃光。傑佛瑞說,他是他父親個人的反對者。
心懷對兒子的愧疚與愛,羅斯會踩煞車?還是永生不死的欲求,會驅策羅斯踏上「冷凍保存」之路?
我們對死亡有多恐懼,我們就有多癲狂,而當死亡愈是逼近,我們為了逃避死亡所願意付出的代價,比起死亡本身,往往更令人瞠目結舌。
在這部美國當代文學巨擘唐‧德里羅最新創作的小說裡,一再揭示著毛骨聳然的事實──人類,本身就是一個恐怖的世界,而當我們完全成為自己欲望的囚鳥時,不待全球愈來愈頻繁的災難與恐攻,我們早已讓自己滅頂。
※本書特色:
◎繼鉅作《白躁音》、《毛二世》、《身體藝術家》之後,唐‧德里羅最新諷喻人類生存恐懼與無盡欲望的警世力作。
◎亞馬遜網站2016年五月好書。
◎「於是我們在《ZERO K》看到的是:
一、一個卡繆筆下的疏離異鄉人……
二、漫遊在卡夫卡式的奇詭城堡裡……
三、用貝克特式的語言觀察敘述……
四、叩問著菲利浦.K.迪克的疑惑……
五、時不時冒出波赫士那樣般靈光……」──賀景濱
◎「這本充滿冷感的小說中唯一的溫情就是兩父子重逢的對話和幽默,但是他們很快就產生分歧。傑佛瑞沒有辦法認同作為時代勝利者的父親羅斯,但是同樣沒有辦法改變父親自我冷凍的決定。兩父子之間南轅北轍的世界觀正是《ZERO K》這部小說最強的張力,亦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
──宋子江(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統籌主任)
※本書重要書評:
◎在這部充滿思考性的小說底下,唐‧德里羅偷渡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一個兒子試圖跟父親重新連結的故事。──《出版人週刊》
◎唐‧德里羅的新作《ZERO K》令人低迴不已,可說是自從一九九七年驚人的大師傑作《地獄》之後,最有說服力的作品,也是一部將自己與《白噪音》區隔開來的作品:其沉鬱而冷靜的未來主義風格,讓他的早期作品顯得像是諷刺性的黑色喜劇……這些年來,在唐‧德里羅的小說中出現過的所有主題,不管是從科技和大眾傳播媒體帶來的誘惑,到金錢的力量,以及對混亂的恐懼……皆貫穿交織於這部小說中。──角谷美智子(《紐約時報》書評家)
◎對於長期關注唐‧德里羅的讀者來說,《ZERO K》是一本最神祕,最感動人心,又最有回饋的作品……你完全無法預期這部小說會如此深深打動你。讀完這部小說後,我既震撼,又深覺感激。──約書亞‧費瑞斯(小說家,《紐約客雜誌》專欄作家)
我們對死亡有多恐懼,就有多癲狂!
唐‧德里羅給所有人類的一記當頭棒喝!
賀景濱(小說家)專文推薦。
這部小說,是一柄閃著寒光的利刃,輕輕挪移近我們的脖子。
我在我的跛腿中看見自己,也在我培養這跛腿的方法中看見自己。
但每回父親帶我參觀自然史博物館,
我便會把跛腿殺死。
億萬富翁羅斯正祕密投資一項驚人的事業──將人「冷凍保存」,直到未來不治之症找到治療方式,人們再從沉睡狀態甦醒過來。他患重症的年輕妻子,成了實驗者,而當妻子做了這決定後,羅斯也決定追隨。
只是,當與前妻所生下的兒子傑佛瑞的出現,卻動搖了羅斯。
羅斯在傑佛瑞13歲那一年離家,從那一刻起,傑佛瑞咬著舌頭說話,拖著腳步走路,把頭中間一片頭髮由前到後剃光。傑佛瑞說,他是他父親個人的反對者。
心懷對兒子的愧疚與愛,羅斯會踩煞車?還是永生不死的欲求,會驅策羅斯踏上「冷凍保存」之路?
我們對死亡有多恐懼,我們就有多癲狂,而當死亡愈是逼近,我們為了逃避死亡所願意付出的代價,比起死亡本身,往往更令人瞠目結舌。
在這部美國當代文學巨擘唐‧德里羅最新創作的小說裡,一再揭示著毛骨聳然的事實──人類,本身就是一個恐怖的世界,而當我們完全成為自己欲望的囚鳥時,不待全球愈來愈頻繁的災難與恐攻,我們早已讓自己滅頂。
※本書特色:
◎繼鉅作《白躁音》、《毛二世》、《身體藝術家》之後,唐‧德里羅最新諷喻人類生存恐懼與無盡欲望的警世力作。
◎亞馬遜網站2016年五月好書。
◎「於是我們在《ZERO K》看到的是:
一、一個卡繆筆下的疏離異鄉人……
二、漫遊在卡夫卡式的奇詭城堡裡……
三、用貝克特式的語言觀察敘述……
四、叩問著菲利浦.K.迪克的疑惑……
五、時不時冒出波赫士那樣般靈光……」──賀景濱
◎「這本充滿冷感的小說中唯一的溫情就是兩父子重逢的對話和幽默,但是他們很快就產生分歧。傑佛瑞沒有辦法認同作為時代勝利者的父親羅斯,但是同樣沒有辦法改變父親自我冷凍的決定。兩父子之間南轅北轍的世界觀正是《ZERO K》這部小說最強的張力,亦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
──宋子江(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統籌主任)
※本書重要書評:
◎在這部充滿思考性的小說底下,唐‧德里羅偷渡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一個兒子試圖跟父親重新連結的故事。──《出版人週刊》
◎唐‧德里羅的新作《ZERO K》令人低迴不已,可說是自從一九九七年驚人的大師傑作《地獄》之後,最有說服力的作品,也是一部將自己與《白噪音》區隔開來的作品:其沉鬱而冷靜的未來主義風格,讓他的早期作品顯得像是諷刺性的黑色喜劇……這些年來,在唐‧德里羅的小說中出現過的所有主題,不管是從科技和大眾傳播媒體帶來的誘惑,到金錢的力量,以及對混亂的恐懼……皆貫穿交織於這部小說中。──角谷美智子(《紐約時報》書評家)
◎對於長期關注唐‧德里羅的讀者來說,《ZERO K》是一本最神祕,最感動人心,又最有回饋的作品……你完全無法預期這部小說會如此深深打動你。讀完這部小說後,我既震撼,又深覺感激。──約書亞‧費瑞斯(小說家,《紐約客雜誌》專欄作家)
作者簡介
唐.德里羅 Don DeLillo
美國四大名家之一,多次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且呼聲極高。他也是「美國藝術與文學科學院」院士,迄今已出版十餘本長篇小說和三本劇作,另著有諸多短篇小說和隨筆。有評論因他對後現代生存境遇的描繪,而稱他是「另一種類型的巴爾扎克」。
唐.德里羅於1936年出生在紐約一個義大利移民家庭,童年時隨父母遷居賓州。大學時期學習神學、哲學和歷史,但他並不喜歡學校生活,倒是從現代派繪畫、爵士樂、歐洲電影和格林威治村的先鋒藝術獲得樂趣和教益。1958年大學畢業後,唐.德里羅就職於一家廣告代理公司,並在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
他的小說先後獲得「哥根哈姆獎」、「美國藝術與文學科學院文學獎」。1985年出版的《白噪音》,是他奠定文壇地位的重要作品。此書不但摘下該年度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入選「時代雜誌100大小說」,更被譽為美國後現代主義文學最具經典性的代表作。學者馬克.奧斯蒂恩稱譽此書為「美國死亡之書」。
1989年,唐.德里羅突發奇想要寫何梅尼,1992年,他便以這部名為《毛二世》的小說榮獲「國際筆會/福克納獎」。而後在1997年,他出版一部八百多頁的巨著《地獄》,描繪了二十世紀整整後半個世紀的美國社會,對美國和世界文壇産生了巨大的震撼。這部作品不同於其他議題嚴肅的小說,很意外地,成了國際第一暢銷書。
唐.德里羅的作品所造成的影響力是全面性的,不僅大學課堂講授他的《白噪音》,當今許多美國名家以他為師,流行歌手寫歌稱頌他,保羅.奧斯特更將《巨獸》及《沒落之鄉》獻給他以表崇敬之意,而英國文學大師馬丁.艾米斯則推崇他是「美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他的著作已跨越了時間與地域的藩籬,在數十年來,始終緊貼著現代人的生活脈動且影響了無數讀者;而唐.德里羅這個名字,亦將會永遠屹立在世界文學史的不朽地位。
美國四大名家之一,多次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且呼聲極高。他也是「美國藝術與文學科學院」院士,迄今已出版十餘本長篇小說和三本劇作,另著有諸多短篇小說和隨筆。有評論因他對後現代生存境遇的描繪,而稱他是「另一種類型的巴爾扎克」。
唐.德里羅於1936年出生在紐約一個義大利移民家庭,童年時隨父母遷居賓州。大學時期學習神學、哲學和歷史,但他並不喜歡學校生活,倒是從現代派繪畫、爵士樂、歐洲電影和格林威治村的先鋒藝術獲得樂趣和教益。1958年大學畢業後,唐.德里羅就職於一家廣告代理公司,並在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
他的小說先後獲得「哥根哈姆獎」、「美國藝術與文學科學院文學獎」。1985年出版的《白噪音》,是他奠定文壇地位的重要作品。此書不但摘下該年度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入選「時代雜誌100大小說」,更被譽為美國後現代主義文學最具經典性的代表作。學者馬克.奧斯蒂恩稱譽此書為「美國死亡之書」。
1989年,唐.德里羅突發奇想要寫何梅尼,1992年,他便以這部名為《毛二世》的小說榮獲「國際筆會/福克納獎」。而後在1997年,他出版一部八百多頁的巨著《地獄》,描繪了二十世紀整整後半個世紀的美國社會,對美國和世界文壇産生了巨大的震撼。這部作品不同於其他議題嚴肅的小說,很意外地,成了國際第一暢銷書。
唐.德里羅的作品所造成的影響力是全面性的,不僅大學課堂講授他的《白噪音》,當今許多美國名家以他為師,流行歌手寫歌稱頌他,保羅.奧斯特更將《巨獸》及《沒落之鄉》獻給他以表崇敬之意,而英國文學大師馬丁.艾米斯則推崇他是「美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他的著作已跨越了時間與地域的藩籬,在數十年來,始終緊貼著現代人的生活脈動且影響了無數讀者;而唐.德里羅這個名字,亦將會永遠屹立在世界文學史的不朽地位。
書摘/試閱
【推薦序】如何享用唐‧德里羅/賀景濱(小說家)
或者意識,或者無意識,我們一生,所做所為,隱隱約約,都在為死亡做準備。
唐‧德里羅在他最新的小說《ZERO K》裡,則以更簡潔的句子宣告:
人人都想擁有世界末日。
為什麼?
再用一句唐‧德里羅的話來說,那就是:
難道迫在眉睫的死亡,不是最能鼓勵最深的自欺嗎?
所以,唐‧德里羅以八十高齡完成的這部長篇小說,是談論死亡之書嗎?的確,歐美有些書評把它當成一個老人在黃昏時對死亡的冥思。但死亡有什麼好談論的。我們的語言只能想像死亡,想像地獄或天堂,我們的語言根本無力談論死亡。唐‧德里羅當然不會掉入這個陷阱。這書描繪的,其實是人面對死亡時,會做出何種怪誕行為的末日景象。就像有人為了避免乳癌,會先割除乳房;有人為了永生,會先自行冷凍。
故事從羅斯.洛克哈特這個億萬富翁的奇謀開始。他在哈薩克斯坦的某處沙漠,創建了神祕又龐大的地下碉堡,專門用來「深層冷凍」那些得了絕症或是企求永生的人體,以等待未來生物科技的救贖;甚至,期待奈米科技會讓那些解凍的細胞得到更強大的力量。
熟知唐‧德里羅的讀者不難看出這位羅斯的原型,八成來自富可敵國的索羅斯。唐‧德里羅經常拿社會名流做為他小說人物的原型。例如《毛二世》裡那位萬人擁戴的教主,顯然來自統一教的文鮮明。又如《身體藝術家》裡那位探討身體極限和想像的女主角,總是讓人一再想起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就連短篇小說〈錘子與鐮刀〉,德里羅也不忘拿史上最大詐財案的主角、前納斯達克主席伯納.馬多夫來開刀。
還需要更多佐證嗎?這十多年來,我們看到多少矽谷的富豪,毫不猶豫地投擲大把錢給生物科技。所謂深層冷凍、低溫保存,分明就是超級富豪追求永生的遊戲。我們不會把這本作品錯看成未來主義的科幻小說,但把埃及的金字塔搬到矽谷,我們看到的是沙漠裡地下碉堡的反諷。
是的,對照與反諷。雖然唐‧德里羅的文風一向以曖昧難明出名,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這本小說的結構是以對照形式的反諷構成的。書中提到四次死亡事件,正是兩兩對照的的明證。先是羅斯摰愛的年輕妻子、考古學家阿蒂絲的死亡,對照的是被羅斯遺棄,甚至連名字都忘了的元配之死。一富一貧、一貴一賤,昭然若揭。其次是兩年後,羅斯受不了摰愛離去的孤獨,決定追隨阿蒂絲成為未來的木乃伊。此時的對照組,是我們的敘述者傑佛瑞,在無意中目睹了女友失蹤的孩子戰死烏克蘭的畫面。一老一少,兩人各自為了所愛(更精準地說,是為了自己愛的意識型態),選擇並自認擁有了自己的世界末日。
類似的反諷和對照在書中屢見不鮮。羅斯的姓Lockhart(心房上鎖?)是反諷,阿蒂絲的名字Artis也是反諷,而考古學家選擇成為明日的木乃伊,本身就是最大的反諷。十三歲的傑佛瑞在做三角函數時,被父親羅斯遺棄;與此對照的是傑佛瑞女友領養的小孩,最終還是遺棄了自己的養父母。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大放厥詞的史丹馬克兄弟與沉默的「僧人」是對照組,書中上半部描述的服裝人偶,到了下半部被人體標本取代,也是一組對照。最後,傑佛瑞在紐約街頭發現了一個像身體藝術家的神祕女人,我們似乎看到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又陰魂不散回來了。
從表面看,《ZERO K》的主題仍是唐‧德里羅窮後半生關注的議題,洪水、地震、饑荒、戰火、恐攻,所有天災人禍的意象幾乎瀰漫全書。那是唐‧德里羅對現代社會的觀察。但一個作家的偉大,並不是來自他書寫的主題。讓唐‧德里羅脫穎而出成為後現代的大師,在於他不像一般的小說家專注於情節的策劃,或是經營角色的情感。
於是我們在《ZERO K》看到的是:
一、一個卡繆筆下的疏離異鄉人,他會把頭髮從中剃光,他永遠在對抗世俗的父親,他總是冷冷地看待親人和非親人的死亡……
二、漫遊在卡夫卡式的奇詭城堡裡,總是有數不盡的同樣式的房間,還有無止盡的長廊,以及隨時會突然垂掛下來的大銀幕,播放著放不完的死亡畫面……
三、用貝克特式的語言觀察敘述,主角總是試著在為新出現的人物命名,或者為舊事物下新定義,意符和意旨完全斷裂了……
四、叩問著菲利浦.K.迪克的疑惑,冷凍之後的意識會存在於哪個階層?岩石在,但它們不存在?對一個死人來說,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死而不死……
五、時不時冒出波赫士那樣般靈光,「你們正在失去自主權,正在被虛擬化,被你們隨時隨地帶在身上的裝置虛擬化。在劫難逃。所有你們使用的編碼脈衝都在約束著你們……」
說真的,哪個熱愛唐‧德里羅的讀者,會在意他的情節精不精采,或人物生不生動呢?唐‧德里羅最讓人迷醉的,就是那些迷死人不償命的句子,那些三不五時就會跳出來撞擊你心房的句子,那些你忍不住想在旁邊劃線做記號的句子。他很少採用意識流的手法表達角色的情感和思緒,他運用的是他獨家的「觀看」。書中有大半的篇幅來自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觀看,奇妙的是在那冷冰冰的觀看底下,卻能讓你感到有一股情感和思緒在流動著。他觀看母親的死亡,父親的永凍,直到最後,他看到的是紐約摩天大樓正中央又圓又大又紅的落日,那輪讓小男孩敬畏到哭出聲的餘暉。但即使在通篇冷酷異境的腔調下,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對生命、對家庭、對大自然的愛與不捨。
也許文化論者會把那些到處流竄的珠磯句子當做後現代的碎片。那是詩嗎?那不是詩。那是哲思嗎?那也不是哲思。那是散文詩與哲思的奇美拉(Chimera),是獅首羊頭蛇尾噴火獸的嵌合體。
所以閱讀《ZERO K》的最佳方式,應是準備一杯精心濾泡的莊園咖啡,在緩緩降溫的過程中,細細捕捉那些捉摸不定的句子。因為,據說在降溫時更能嚐出咖啡的回甘。
然後那些高談後現代後殖民的人終將明白:我們最終的殖民主人,是死神。
【內文試閱】
一
人人都想擁有世界末日。
我父親如是說。他站在大方格窗旁邊,地點是他的紐約辦公室(業務涵蓋私人財富管理、豪門財產信託和投資新興市場)。 我們正在分享一個罕有時刻,一個沉思時刻。他戴著的復古太陽眼鏡把黑夜帶進了室內,讓這時刻更形完整。我打量辦公室裡擺設的各種不同抽象藝術品,開始明白他語畢後的良久沉默無關我或他。我想到他太太,我指的是第二任太太,那個女考古學家。她的心靈和油盡燈枯的身體很快便會按照原定計畫,漂浮進入太虛。
幾個月後,在半個地球之外,我回憶起上述時刻。我坐在一輛掀背式防彈轎車後座,兩邊的磨砂玻璃車窗都落了窗簾。司機穿著足球衣和運動長褲,髖部隆起一塊,明顯帶著傢伙。在崎嶇道路行駛一小時以後,車子停定,司機對領口的裝置說了些什麼。然後他頭向右後偏轉四十五度角,而我相信,這表示我應該解開安全帶,推門下車。
這趟行車是我的馬拉松式旅程的最後一程。車外的高溫嚇人一跳。我拿著旅行袋向前走出幾步,然後站住一會兒,感到身體鬆懈開來。我聽見引擎發動聲,轉身觀看。汽車朝私人飛機跑道的方向開回去,是極目之內唯一正在移動的東西,過不久便會被大地或黯淡下來的日光或地平線吞沒。
我慢慢把四周打量了一遍。舉目都是鹽灘和碎石,除幾座低矮結構體之外,一片空蕩蕩。那些結構體可能是彼此相連,幾乎和漂白過似的地貌無法區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對我要來的這個目的地,我原先只知道它位處極其偏遠,其他一無所知。不難想像,當我父親站在辦公室窗邊說出那句話時,心裡是想著這片荒涼地貌和融合於其中的幾何形狀結構體。
他現在就在這裡,兩個都在這裡。我是說我的父親和繼母。我來,是為進行一次最短暫的探望和道一個不確定的再見。
從我的位置,很難確定結構體一共是幾座。兩座、四座、七座或九座都有可能。但也可能只有一座,由一個中央部分相連著若干附屬部分構成。我把它想像為一個註定會在未來時代被發現的城市——這城市一應俱全、沒有名字而保存良好,由一個不為人知的遷移文化所棄置。
熱浪讓我感覺身體正在皺縮,但我想要再停留一下,多看幾眼。這些是躲起來的建築,密封在曠野恐懼症裡。它們是一些盲的建築,肅靜而陰森,開著看不見的窗子,是設計來等待電影播放到數位垮陷的一刻自我摺疊起來的。
我順著一條石頭道路走到一個寬闊的入口。有兩個男人守在那裡,身穿與司機不同款式的足球衣,髖部照樣是隆起一塊。他們背後有一排防撞桿,用來阻止汽車進入。
在入口的最邊邊處,奇怪地站著兩個女人,她們一動不動,從頭到腳包裹在伊斯蘭黑色長袍裡。
二
父親新蓄了一把落腮鬍。我為之嚇了一跳。鬍子比他的頭髮略灰白,把他的凝視襯托得更加濃烈。蓄這鬍子是不是反映出他殷殷盼望進入一個新的信仰向度?
「什麼時候進行?」我問。
「正在研究是哪一天幾點幾分。快了。」他說。
這個叫羅斯.洛克哈特的男人六十多,快七十歲,寬肩而動作敏捷。他的墨鏡放在他前面的辦公桌上。我習慣在他分布各地的辦公室和他見面。現在這間是臨時拼揍的,擺設有好幾個螢幕、好幾副鍵盤和其他設備。這讓我意識到,他把大把鈔票投入到這個稱為「匯聚」的運作或努力中。這辦公室是一種回報、禮遇,方便他可以和他的眾多公司、代理人、基金、受託管理財產、基金會、辛迪加(註:一種局部的市場壟斷機制)、公社和氏族保持聯繫。
「阿蒂絲怎樣了?」
「她完全準備好了。沒有絲毫猶豫或需要再考慮的跡象。」
「我們談的不是屬靈生命的永生。這事情是關於身體的。」
「身體將會冷凍起來。深冷保存法。」他說。
「然後等待來日。」
「對,等待醫學想出辦法消滅那些會搞垮身體的因素。屆時心靈和身體將會回春,重得生命。」
「這不是什麼新鮮構想。我說得對不對?」
「是不新,但卻是直至今日才邁向全面實現。」
我暈頭轉向。現在是早上,是我來到這地方的第一個全天。坐在辦公桌對面的人是我父親,但不管是這裡的環境、建築或那個蓄落腮鬍的男人,都不是我熟悉的。來得及消化這一切之前,我已在回家路上。
「你完全信任這計畫。」
「完全信任,不管是它的醫學部分、技術部分,還是哲學部分。」
「別人只會冷凍寵物。」我說。
「這裡不是這樣的。這裡沒有什麼事情是空想的。沒有什麼事情是異想天開或膚淺的。它是關於男人和女人,關於死亡和生命。」
他的語氣不疾不徐,帶有向我挑戰的味道。
「進行的時候我可以在場嗎?」
「我極端懷疑。」他說。
他太太阿蒂絲患有好幾種重症。我知道讓她日漸衰竭的禍首是多發性硬化症。我父親在這裡是要見證她的死亡和保存。她的身體將會受到保存,以待幾十年後可以安全醒過來時再讓它轉醒。
「我在入口遇到兩個佩槍的隨扈。他們對我徹底搜身,然後帶我到房間,全程幾乎不發一語。這個機構的名字很有宗教意味。」
「那是一種以信仰為基礎的科技。這是它的本質。它信奉的是另一種神,但嚴格來說和從前其他神無甚差別。不同處只在於祂是真的,會履行應許。」
「死後生命的應許。」
「對,最終會落實。」
「『匯聚』。」
「對。」
「匯聚是個數學名詞。」
「還是個生物學名詞。還是個生理學名詞。(原文為convergence,數學中譯為「收斂」,生物學中譯為「收斂」或「輻合」或「會合」。)這不重要。」他說。
我媽是在家裡過世,死時我守在床邊。在場的還有她的一個朋友——一個女人,拄著拐杖,站在房門。這就是我對當時的記憶。回憶起這一幕時,出現的總是簡化過的畫面:一個躺在床上的女人、一個站在門口的女人、床本身和金屬拐杖。
羅斯說:「我有時會下去安寧療護區走走,看看那些準備接受程序的人。他們的心情交雜著期盼和敬畏。對,期盼和敬畏要遠多於害怕或忐忑。他們是連枝同氣的,一起處於某種遠大於他們所能想像的東西。他們感受到一種共同使命, 共同天命。我不期然聯想起中世紀供朝聖者住宿的落腳處。」
「朝聖者,真棒。我們是回到舊日的宗教去了。我有可能到安寧療護區走走嗎?」
「八成不行。」他說。
他給我戴上一條腕帶,上面附著個小圓盤。他說它的作用類似電子腳鐐,可以讓我的行蹤無所遁形。我只被容許在這一層樓和上一層樓走動,其他地方一律止步。我一脫下腕帶就會驚動保全系統。
「別對你看見和聽見的事情遽下結論。這地方是由嚴肅認真的人所設計。請尊敬他們的理念,尊敬這個環境本身。阿蒂絲說我們應該把它視為施工中的土方藝術或地景藝術。它是從大地之中打造而起再沉回大地之中,目的是讓人無法進入。不管是這裡的人或環境都是由靜止所定義的。它同時也有一點類似墓穴。『土』是這裡的指導原則。出於土而歸於土。」
我沿著一條條長廊散步以消磨時間。每條長廊都近乎空無一人,期間我只分別遇到過三個人。我對他們點頭,但他們只沒好氣地瞧我一眼。牆壁髹成不同的綠色調。走完一條寬闊的長廊後,轉個彎會進入另一條。空白的牆,沒有窗戶,門與門之間間隔很寬,所有門都緊閉。門與牆是同一色系,但略淡些。我懷疑這種色彩的遞嬗是不是有什麼深意。這是我遇到任何新環境都會做的事:設法在其中注入意義,好讓整個地方變得融貫,至少是好讓我自己可以在其中找到定位,以印證我的不自在。
最後一條長廊盡頭的天花板有一條長縫,露出一片螢幕的底邊。螢幕在我走近時開始下降,寬度及於兩面牆,完全下降後離地板不遠。我慢慢走近。起初,畫面裡淨是水。有快速漫過林地的水和溢出河岸的水,有暴雨打在梯田的畫面。有好長一陣子就只看見雨,然後是四處奔逃的人,還有些人無助地坐著小舟,在急流裡搖搖晃晃。然後是一些水淹的廟宇,一些滑下山坡的房屋。我看著大水在城市街道不斷漲起,把汽車和駕駛全數淹沒。螢幕的大尺寸製造出遠非電視新聞報導可比擬的效果。一切都被放大,而且每一幕的持續時間遠超過一般新聞畫面。然後,我看見一個真人大小的女人坐在椅子裡,連同房子一起被土石流沖走。事情就發生在我眼前,近在咫尺。然後一張男人的臉在水下面瞪著我看。我嚇得退後一步,但繼續觀看。我無法不觀看。最後,我轉過頭,想看見有個人從長廊另一頭走過來,站在我旁邊,一起見證影像的堆積和箍箝。
螢幕只有畫面,沒有聲音。
三
阿蒂絲單獨待在她和羅斯住的套房裡。她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穿著睡袍和拖鞋,看來正在打盹。
我要說些什麼呢?該怎樣開啟話題?
妳好漂亮,我想這樣說。她確實漂亮,只可嘆這漂亮已被疾病稀釋。消瘦的臉,沒梳理的灰金色頭髮,雙手交疊在大腿上。我以前都把她看成「父親的第二個太太」,然後是看成繼母,然後才是考古學家。最後一個標籤沒那麼有否定性,這主要是因為我當時對她終於有所了解。我喜歡把她想像為一個苦行僧科學家,常會在簡陋營地住一段時間,隨時準備好適應新的不饒人環境。
為什麼父親要求我到這裡來呢?
他希望阿蒂絲死去時有我陪在他旁邊。
我坐在一張鑲墊長凳,看著和等著,不多久心思便離開了那個靜悄悄坐在扶手椅裡的人,在微型化的心靈空間裡看見了羅斯,看見了我和他。
他是個由金錢形塑的人。他最早的名氣來自他對自然災難如何影響獲利的分析。他喜歡教我金錢方面的知識。但我媽卻說:你應該教他性方面的知識,那才是他需要懂的。金錢遊戲的語言很複雜,他會向我定義名詞,畫出圖表以助解釋。他似乎全時間生活在緊急狀態,大部分日子一天待在辦公室十或十二小時,不然就是趕飛機或為演講準備。在家裡,他會站在全身鏡前面背誦談論風險偏好或離岸司法管轄權的演講稿,邊背邊精練手勢動作和面部表情。他和一個辦公室臨時僱員有過一腿。他參加過波士頓馬拉松賽跑。
我又都是做些什麼呢?我咬著舌頭說話,拖著腳步走路,把頭中間一片頭髮由前到後剃光。我是他個人的反對者。
他在我十三歲那一年離家。他向我告別時,我正在寫學校的三角函數作業。他坐在小桌子另一頭(桌上玻璃罐裡總是插著削尖的鉛筆),而我在他說話時繼續做功課。我翻看課本裡的公式,然後在筆記本裡一遍又一遍寫上同樣幾個字:正弦餘弦正切。
我父親為什麼會離開我媽?
兩人都從未解釋。
一些年後,我一個人住在上曼哈頓一間出租小套房。有一晚,我看見父親出現在電視螢幕上。那是個冷門頻道,收訊不良,影像有點重疊。羅斯正在日內瓦發表演講,用的是法語。我以前知道父親懂法語嗎?我又敢肯定電視上的人是我父親嗎?從字幕,我得知他談到什麼失業生態學。我看著他崛起。
但阿蒂絲現在卻置身這個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的地方,這個沙漠中的幽靈之地,很快就會成為一具被保存在巨大墳室裡的冷凍屍體。然後,她會有一個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未來。時間、命運、機會、不朽——這些字眼光想到便夠讓人肅然起敬。但我想到的卻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往事,一些我不能自已、要喚起的瞬間。我會不能自已,是因為這些瞬間是我的,無法看不見或不去感覺。也因為它們是自己從環繞著我的每面牆壁裡爬出來的。……(未完)
【後記】科幻與永生——導賞唐•德里羅《ZERO K》/宋子江(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統籌主任)
最近有科學家準備進行換頭手術的試驗,即把一個活人的頭切開,嫁接到另一個人的脖子上。如果他成功的話,人的身體不斷衰敗,甚至壞死都沒有關係。換頭科技可以幫人續命,這種科技的產生固然會讓人擔心人類會不會陷入倫理困境,但是科技能否逆轉生死有時的宿命?這個問題關係到人類命運之休戚,無論是流行文化,還是嚴肅文學都難以繞過。近幾年,美國科幻電影如《機械姬》(Ex Machina)、《雲端情人》(Her)、《明日邊界》(Edge of Tomorrow)、《啟動原始碼》(Source Code)等等從不同面向觸及過這個議題。美國小說家也不遑多讓,二○一三年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寫出了《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而今年唐•德里羅(Don Dellilo)出版了《ZERO K》。
品欽和唐‧德里羅分別成名於一九六○和七○年代,他們都是美國當代最優秀小說家,近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他們都在賠率榜單上。雖然他們往往被貼上「後現代小說家」的標籤,但是幾十年後,當他們在寫出文學教授、小說評論家和書評家都無法輕易下判斷的科幻作品,讀者不禁想問,「後現代」的前面究竟要加上多少個「後」字,才能體現兩位小說大師天馬行空的構想。品欽的小說愈寫愈厚,並以此著稱,據聞出版社甚至考慮過改換紙質來控制成本。而唐‧德里羅自從一九九七年出版《地下世界》(Underworld)之後,他的小說則愈寫愈薄,愈寫愈黑暗,愈寫愈冷峻,愈寫愈晦澀,今年出版的《ZERO K》還不足三百頁,有些嚴謹的書評家一讀再讀,仍沒有輕易下任何結論。
《ZERO K》的題材引人注目:「人體超低溫保存」,即通過超低溫保持技術,把絕症患者的身體保存在比膠囊旅館還要小的人體膠囊裝置裡,以期有朝一日醫學技術能夠克服該絕症時,再將人體解凍並進行治療。我們在科幻電影中曾經看過許多試圖超越人類感覺時間,甚至超越生死的科技,例如宇航員可以在生命維持裝置中睡掉整個航程,而他們的生理年齡卻不會增長;人可以將自己的大腦信息轉化成數據,存在於數碼世界之中,又或者下載到另一具軀體。可以說,「人體超低溫保存」已並不是那麼新穎的科學構想。唐‧德里羅並沒有去深究倫理上的問題,而是將此原本不得已而為之的技術變成人類的選擇。
唐‧德里羅各部小說的內容互相穿插,形成斑駁多姿的小說世界。要談《ZERO K》,須從他出版於一九八五年的小說《白噪音》(White Noise)談起。《白噪音》的敘述者傑克和他的太太芭蓓有一場頗為浪漫的對話。兩人在談論死亡的問題時,都願意成為先死的那位,而且他們給出的原因也是一樣的:他們都深愛著對方,無法忍受自己的生活中沒有對方的存在。兩人可說是一體兩面。日常生活中的情侶或者夫妻也會進行這種對話,如果一個人選擇後死,因為他不願意愛人去忍受失去摯愛的孤獨和悲痛,這又何嘗不是愛呢?諷刺的是,傑克在一段內心獨白承認,他自己不想先死,他真正想要的是兩人都能苦樂與共,長生不死。這在現實中當時是不可能的,而在小說中,傑克也沒有選擇,因為唐‧德里羅為這部小說設置了宿命:「所有的情節終於死亡」(all plots end in death),因此它的結局可以說是早已註定。
《ZERO K》也講到一對恩愛的夫妻,羅斯和阿蒂絲。羅斯是億萬富翁,六十幾歲,身體健康,而阿蒂絲已病入膏肓,必須進行人體冷凍技術以暫時「保存」性命。與《白噪音》中沒有選擇的傑克不同,《ZERO K》的羅斯有了選擇的自由。他決定把自己也冷凍了,一方面他想要在無盡的黑暗和睡眠中陪伴自己的太太,另一方面他不願意一個人孤零零地面對妻子冷凍後的日子。冷凍在人體膠囊裝置裡的人都集中存放在一個叫「Convergence」的收集中心,大部分都是由於客觀原因而被迫冷凍的,而小部分自願被冷凍的人則放在一個叫做《ZERO K》的單位。
實際上,比起《白噪音》,《ZERO K》對生死狀態的探索讓讀者更加覺得陰森可怖。一個人進入冷凍狀態,他就像進入一個最深層的無夢之眠,雖說保存了生命,卻又最接近死亡。只要沒有人拔掉插頭,那麼在這個狀態中,Immortality(永生)和Mortality(死亡)已經是同一回事,前綴「Im-」可有可無,又無法完全消失。科技既讓人觸碰到超越生死的界線,又無法讓人完全超越。人靜靜地躺在生死的界線上,與界線一同成就永恆。當然,這是筆者猜想的文字遊戲,但是這種解讀有更深一層的意義。「Im-」無疑會讓人想起「I’m」,即「I am」的縮寫,於是「我存在」變成一種模糊曖昧的狀態。筆者認為,這就是《ZERO K》整本小說所探討的核心。
如果唐‧德里羅單方面去寫羅斯,小說就不會具有說服力了。羅斯故意召回他和前妻生的兒子傑佛瑞,並打算把自己的生意交給他,而傑佛瑞正是這本小說的敘事者。傑佛瑞是一個存在感極弱的人,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麻木,但是對身邊的小事情卻十分執著。他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在大時代中浮沉的小人物。選擇他做敘事者,或許是一招險著,例如他會執著於機場安檢諸如此類的小事上,並從中闡發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讀起來有點像黑色幽默,但又不是完全如此。小說中最顯著的一幕莫過於他在紐約計程車上和女朋友滔滔不絕地講身邊「定義我們的小事物」(minor matters that define us),但是他說話的聲音又不得不被馬路上的車聲和電視螢幕上的新聞報導穿插。傑佛瑞終究是個平凡的美國人,既服膺於時代,又不得不對抗時代,一個對抗現實的現實主義者。
這本充滿冷感的小說中唯一的溫情就是兩父子重逢的對話和幽默,但是他們很快就產生分歧。傑佛瑞沒有辦法認同作為時代勝利者的父親羅斯,但是同樣沒有辦法改變父親自我冷凍的決定。兩父子之間南轅北轍的世界觀正是《ZERO K》這部小說最強的張力,亦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羅斯帶著一種冰寒的浪漫情調試圖征服生死之限,傑佛瑞則維持一副尖刻的現實至上的面孔。三十多歲的傑佛瑞對現實的見解仍未夠深刻。其實再往下一步去想,他的父親羅斯進入冷凍狀態以後,就不再能夠被傑佛瑞所說的身邊的小事物所定義。羅斯不僅不能被定義,由於進入冷凍狀態後便失去意識,這些小事物以及傑佛瑞的敘述根本無法對他生效。不是羅斯否定了現實,就是現實否定了羅斯。
《ZERO K》是一部典型唐‧德里羅晚期風格的作品。當然讀者也可以從科學哲學、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角度去批評這部長篇小說對科學倫理的探究不夠深刻,幾乎無視女性的存在,資產階級玩弄尖端科技之不公不義,但是唐‧德里羅晚期風格就是一面多稜鏡,讀他的小說或許更不能被單一理論框架所限吧。
或者意識,或者無意識,我們一生,所做所為,隱隱約約,都在為死亡做準備。
唐‧德里羅在他最新的小說《ZERO K》裡,則以更簡潔的句子宣告:
人人都想擁有世界末日。
為什麼?
再用一句唐‧德里羅的話來說,那就是:
難道迫在眉睫的死亡,不是最能鼓勵最深的自欺嗎?
所以,唐‧德里羅以八十高齡完成的這部長篇小說,是談論死亡之書嗎?的確,歐美有些書評把它當成一個老人在黃昏時對死亡的冥思。但死亡有什麼好談論的。我們的語言只能想像死亡,想像地獄或天堂,我們的語言根本無力談論死亡。唐‧德里羅當然不會掉入這個陷阱。這書描繪的,其實是人面對死亡時,會做出何種怪誕行為的末日景象。就像有人為了避免乳癌,會先割除乳房;有人為了永生,會先自行冷凍。
故事從羅斯.洛克哈特這個億萬富翁的奇謀開始。他在哈薩克斯坦的某處沙漠,創建了神祕又龐大的地下碉堡,專門用來「深層冷凍」那些得了絕症或是企求永生的人體,以等待未來生物科技的救贖;甚至,期待奈米科技會讓那些解凍的細胞得到更強大的力量。
熟知唐‧德里羅的讀者不難看出這位羅斯的原型,八成來自富可敵國的索羅斯。唐‧德里羅經常拿社會名流做為他小說人物的原型。例如《毛二世》裡那位萬人擁戴的教主,顯然來自統一教的文鮮明。又如《身體藝術家》裡那位探討身體極限和想像的女主角,總是讓人一再想起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就連短篇小說〈錘子與鐮刀〉,德里羅也不忘拿史上最大詐財案的主角、前納斯達克主席伯納.馬多夫來開刀。
還需要更多佐證嗎?這十多年來,我們看到多少矽谷的富豪,毫不猶豫地投擲大把錢給生物科技。所謂深層冷凍、低溫保存,分明就是超級富豪追求永生的遊戲。我們不會把這本作品錯看成未來主義的科幻小說,但把埃及的金字塔搬到矽谷,我們看到的是沙漠裡地下碉堡的反諷。
是的,對照與反諷。雖然唐‧德里羅的文風一向以曖昧難明出名,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這本小說的結構是以對照形式的反諷構成的。書中提到四次死亡事件,正是兩兩對照的的明證。先是羅斯摰愛的年輕妻子、考古學家阿蒂絲的死亡,對照的是被羅斯遺棄,甚至連名字都忘了的元配之死。一富一貧、一貴一賤,昭然若揭。其次是兩年後,羅斯受不了摰愛離去的孤獨,決定追隨阿蒂絲成為未來的木乃伊。此時的對照組,是我們的敘述者傑佛瑞,在無意中目睹了女友失蹤的孩子戰死烏克蘭的畫面。一老一少,兩人各自為了所愛(更精準地說,是為了自己愛的意識型態),選擇並自認擁有了自己的世界末日。
類似的反諷和對照在書中屢見不鮮。羅斯的姓Lockhart(心房上鎖?)是反諷,阿蒂絲的名字Artis也是反諷,而考古學家選擇成為明日的木乃伊,本身就是最大的反諷。十三歲的傑佛瑞在做三角函數時,被父親羅斯遺棄;與此對照的是傑佛瑞女友領養的小孩,最終還是遺棄了自己的養父母。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大放厥詞的史丹馬克兄弟與沉默的「僧人」是對照組,書中上半部描述的服裝人偶,到了下半部被人體標本取代,也是一組對照。最後,傑佛瑞在紐約街頭發現了一個像身體藝術家的神祕女人,我們似乎看到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又陰魂不散回來了。
從表面看,《ZERO K》的主題仍是唐‧德里羅窮後半生關注的議題,洪水、地震、饑荒、戰火、恐攻,所有天災人禍的意象幾乎瀰漫全書。那是唐‧德里羅對現代社會的觀察。但一個作家的偉大,並不是來自他書寫的主題。讓唐‧德里羅脫穎而出成為後現代的大師,在於他不像一般的小說家專注於情節的策劃,或是經營角色的情感。
於是我們在《ZERO K》看到的是:
一、一個卡繆筆下的疏離異鄉人,他會把頭髮從中剃光,他永遠在對抗世俗的父親,他總是冷冷地看待親人和非親人的死亡……
二、漫遊在卡夫卡式的奇詭城堡裡,總是有數不盡的同樣式的房間,還有無止盡的長廊,以及隨時會突然垂掛下來的大銀幕,播放著放不完的死亡畫面……
三、用貝克特式的語言觀察敘述,主角總是試著在為新出現的人物命名,或者為舊事物下新定義,意符和意旨完全斷裂了……
四、叩問著菲利浦.K.迪克的疑惑,冷凍之後的意識會存在於哪個階層?岩石在,但它們不存在?對一個死人來說,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死而不死……
五、時不時冒出波赫士那樣般靈光,「你們正在失去自主權,正在被虛擬化,被你們隨時隨地帶在身上的裝置虛擬化。在劫難逃。所有你們使用的編碼脈衝都在約束著你們……」
說真的,哪個熱愛唐‧德里羅的讀者,會在意他的情節精不精采,或人物生不生動呢?唐‧德里羅最讓人迷醉的,就是那些迷死人不償命的句子,那些三不五時就會跳出來撞擊你心房的句子,那些你忍不住想在旁邊劃線做記號的句子。他很少採用意識流的手法表達角色的情感和思緒,他運用的是他獨家的「觀看」。書中有大半的篇幅來自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觀看,奇妙的是在那冷冰冰的觀看底下,卻能讓你感到有一股情感和思緒在流動著。他觀看母親的死亡,父親的永凍,直到最後,他看到的是紐約摩天大樓正中央又圓又大又紅的落日,那輪讓小男孩敬畏到哭出聲的餘暉。但即使在通篇冷酷異境的腔調下,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對生命、對家庭、對大自然的愛與不捨。
也許文化論者會把那些到處流竄的珠磯句子當做後現代的碎片。那是詩嗎?那不是詩。那是哲思嗎?那也不是哲思。那是散文詩與哲思的奇美拉(Chimera),是獅首羊頭蛇尾噴火獸的嵌合體。
所以閱讀《ZERO K》的最佳方式,應是準備一杯精心濾泡的莊園咖啡,在緩緩降溫的過程中,細細捕捉那些捉摸不定的句子。因為,據說在降溫時更能嚐出咖啡的回甘。
然後那些高談後現代後殖民的人終將明白:我們最終的殖民主人,是死神。
【內文試閱】
一
人人都想擁有世界末日。
我父親如是說。他站在大方格窗旁邊,地點是他的紐約辦公室(業務涵蓋私人財富管理、豪門財產信託和投資新興市場)。 我們正在分享一個罕有時刻,一個沉思時刻。他戴著的復古太陽眼鏡把黑夜帶進了室內,讓這時刻更形完整。我打量辦公室裡擺設的各種不同抽象藝術品,開始明白他語畢後的良久沉默無關我或他。我想到他太太,我指的是第二任太太,那個女考古學家。她的心靈和油盡燈枯的身體很快便會按照原定計畫,漂浮進入太虛。
幾個月後,在半個地球之外,我回憶起上述時刻。我坐在一輛掀背式防彈轎車後座,兩邊的磨砂玻璃車窗都落了窗簾。司機穿著足球衣和運動長褲,髖部隆起一塊,明顯帶著傢伙。在崎嶇道路行駛一小時以後,車子停定,司機對領口的裝置說了些什麼。然後他頭向右後偏轉四十五度角,而我相信,這表示我應該解開安全帶,推門下車。
這趟行車是我的馬拉松式旅程的最後一程。車外的高溫嚇人一跳。我拿著旅行袋向前走出幾步,然後站住一會兒,感到身體鬆懈開來。我聽見引擎發動聲,轉身觀看。汽車朝私人飛機跑道的方向開回去,是極目之內唯一正在移動的東西,過不久便會被大地或黯淡下來的日光或地平線吞沒。
我慢慢把四周打量了一遍。舉目都是鹽灘和碎石,除幾座低矮結構體之外,一片空蕩蕩。那些結構體可能是彼此相連,幾乎和漂白過似的地貌無法區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對我要來的這個目的地,我原先只知道它位處極其偏遠,其他一無所知。不難想像,當我父親站在辦公室窗邊說出那句話時,心裡是想著這片荒涼地貌和融合於其中的幾何形狀結構體。
他現在就在這裡,兩個都在這裡。我是說我的父親和繼母。我來,是為進行一次最短暫的探望和道一個不確定的再見。
從我的位置,很難確定結構體一共是幾座。兩座、四座、七座或九座都有可能。但也可能只有一座,由一個中央部分相連著若干附屬部分構成。我把它想像為一個註定會在未來時代被發現的城市——這城市一應俱全、沒有名字而保存良好,由一個不為人知的遷移文化所棄置。
熱浪讓我感覺身體正在皺縮,但我想要再停留一下,多看幾眼。這些是躲起來的建築,密封在曠野恐懼症裡。它們是一些盲的建築,肅靜而陰森,開著看不見的窗子,是設計來等待電影播放到數位垮陷的一刻自我摺疊起來的。
我順著一條石頭道路走到一個寬闊的入口。有兩個男人守在那裡,身穿與司機不同款式的足球衣,髖部照樣是隆起一塊。他們背後有一排防撞桿,用來阻止汽車進入。
在入口的最邊邊處,奇怪地站著兩個女人,她們一動不動,從頭到腳包裹在伊斯蘭黑色長袍裡。
二
父親新蓄了一把落腮鬍。我為之嚇了一跳。鬍子比他的頭髮略灰白,把他的凝視襯托得更加濃烈。蓄這鬍子是不是反映出他殷殷盼望進入一個新的信仰向度?
「什麼時候進行?」我問。
「正在研究是哪一天幾點幾分。快了。」他說。
這個叫羅斯.洛克哈特的男人六十多,快七十歲,寬肩而動作敏捷。他的墨鏡放在他前面的辦公桌上。我習慣在他分布各地的辦公室和他見面。現在這間是臨時拼揍的,擺設有好幾個螢幕、好幾副鍵盤和其他設備。這讓我意識到,他把大把鈔票投入到這個稱為「匯聚」的運作或努力中。這辦公室是一種回報、禮遇,方便他可以和他的眾多公司、代理人、基金、受託管理財產、基金會、辛迪加(註:一種局部的市場壟斷機制)、公社和氏族保持聯繫。
「阿蒂絲怎樣了?」
「她完全準備好了。沒有絲毫猶豫或需要再考慮的跡象。」
「我們談的不是屬靈生命的永生。這事情是關於身體的。」
「身體將會冷凍起來。深冷保存法。」他說。
「然後等待來日。」
「對,等待醫學想出辦法消滅那些會搞垮身體的因素。屆時心靈和身體將會回春,重得生命。」
「這不是什麼新鮮構想。我說得對不對?」
「是不新,但卻是直至今日才邁向全面實現。」
我暈頭轉向。現在是早上,是我來到這地方的第一個全天。坐在辦公桌對面的人是我父親,但不管是這裡的環境、建築或那個蓄落腮鬍的男人,都不是我熟悉的。來得及消化這一切之前,我已在回家路上。
「你完全信任這計畫。」
「完全信任,不管是它的醫學部分、技術部分,還是哲學部分。」
「別人只會冷凍寵物。」我說。
「這裡不是這樣的。這裡沒有什麼事情是空想的。沒有什麼事情是異想天開或膚淺的。它是關於男人和女人,關於死亡和生命。」
他的語氣不疾不徐,帶有向我挑戰的味道。
「進行的時候我可以在場嗎?」
「我極端懷疑。」他說。
他太太阿蒂絲患有好幾種重症。我知道讓她日漸衰竭的禍首是多發性硬化症。我父親在這裡是要見證她的死亡和保存。她的身體將會受到保存,以待幾十年後可以安全醒過來時再讓它轉醒。
「我在入口遇到兩個佩槍的隨扈。他們對我徹底搜身,然後帶我到房間,全程幾乎不發一語。這個機構的名字很有宗教意味。」
「那是一種以信仰為基礎的科技。這是它的本質。它信奉的是另一種神,但嚴格來說和從前其他神無甚差別。不同處只在於祂是真的,會履行應許。」
「死後生命的應許。」
「對,最終會落實。」
「『匯聚』。」
「對。」
「匯聚是個數學名詞。」
「還是個生物學名詞。還是個生理學名詞。(原文為convergence,數學中譯為「收斂」,生物學中譯為「收斂」或「輻合」或「會合」。)這不重要。」他說。
我媽是在家裡過世,死時我守在床邊。在場的還有她的一個朋友——一個女人,拄著拐杖,站在房門。這就是我對當時的記憶。回憶起這一幕時,出現的總是簡化過的畫面:一個躺在床上的女人、一個站在門口的女人、床本身和金屬拐杖。
羅斯說:「我有時會下去安寧療護區走走,看看那些準備接受程序的人。他們的心情交雜著期盼和敬畏。對,期盼和敬畏要遠多於害怕或忐忑。他們是連枝同氣的,一起處於某種遠大於他們所能想像的東西。他們感受到一種共同使命, 共同天命。我不期然聯想起中世紀供朝聖者住宿的落腳處。」
「朝聖者,真棒。我們是回到舊日的宗教去了。我有可能到安寧療護區走走嗎?」
「八成不行。」他說。
他給我戴上一條腕帶,上面附著個小圓盤。他說它的作用類似電子腳鐐,可以讓我的行蹤無所遁形。我只被容許在這一層樓和上一層樓走動,其他地方一律止步。我一脫下腕帶就會驚動保全系統。
「別對你看見和聽見的事情遽下結論。這地方是由嚴肅認真的人所設計。請尊敬他們的理念,尊敬這個環境本身。阿蒂絲說我們應該把它視為施工中的土方藝術或地景藝術。它是從大地之中打造而起再沉回大地之中,目的是讓人無法進入。不管是這裡的人或環境都是由靜止所定義的。它同時也有一點類似墓穴。『土』是這裡的指導原則。出於土而歸於土。」
我沿著一條條長廊散步以消磨時間。每條長廊都近乎空無一人,期間我只分別遇到過三個人。我對他們點頭,但他們只沒好氣地瞧我一眼。牆壁髹成不同的綠色調。走完一條寬闊的長廊後,轉個彎會進入另一條。空白的牆,沒有窗戶,門與門之間間隔很寬,所有門都緊閉。門與牆是同一色系,但略淡些。我懷疑這種色彩的遞嬗是不是有什麼深意。這是我遇到任何新環境都會做的事:設法在其中注入意義,好讓整個地方變得融貫,至少是好讓我自己可以在其中找到定位,以印證我的不自在。
最後一條長廊盡頭的天花板有一條長縫,露出一片螢幕的底邊。螢幕在我走近時開始下降,寬度及於兩面牆,完全下降後離地板不遠。我慢慢走近。起初,畫面裡淨是水。有快速漫過林地的水和溢出河岸的水,有暴雨打在梯田的畫面。有好長一陣子就只看見雨,然後是四處奔逃的人,還有些人無助地坐著小舟,在急流裡搖搖晃晃。然後是一些水淹的廟宇,一些滑下山坡的房屋。我看著大水在城市街道不斷漲起,把汽車和駕駛全數淹沒。螢幕的大尺寸製造出遠非電視新聞報導可比擬的效果。一切都被放大,而且每一幕的持續時間遠超過一般新聞畫面。然後,我看見一個真人大小的女人坐在椅子裡,連同房子一起被土石流沖走。事情就發生在我眼前,近在咫尺。然後一張男人的臉在水下面瞪著我看。我嚇得退後一步,但繼續觀看。我無法不觀看。最後,我轉過頭,想看見有個人從長廊另一頭走過來,站在我旁邊,一起見證影像的堆積和箍箝。
螢幕只有畫面,沒有聲音。
三
阿蒂絲單獨待在她和羅斯住的套房裡。她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穿著睡袍和拖鞋,看來正在打盹。
我要說些什麼呢?該怎樣開啟話題?
妳好漂亮,我想這樣說。她確實漂亮,只可嘆這漂亮已被疾病稀釋。消瘦的臉,沒梳理的灰金色頭髮,雙手交疊在大腿上。我以前都把她看成「父親的第二個太太」,然後是看成繼母,然後才是考古學家。最後一個標籤沒那麼有否定性,這主要是因為我當時對她終於有所了解。我喜歡把她想像為一個苦行僧科學家,常會在簡陋營地住一段時間,隨時準備好適應新的不饒人環境。
為什麼父親要求我到這裡來呢?
他希望阿蒂絲死去時有我陪在他旁邊。
我坐在一張鑲墊長凳,看著和等著,不多久心思便離開了那個靜悄悄坐在扶手椅裡的人,在微型化的心靈空間裡看見了羅斯,看見了我和他。
他是個由金錢形塑的人。他最早的名氣來自他對自然災難如何影響獲利的分析。他喜歡教我金錢方面的知識。但我媽卻說:你應該教他性方面的知識,那才是他需要懂的。金錢遊戲的語言很複雜,他會向我定義名詞,畫出圖表以助解釋。他似乎全時間生活在緊急狀態,大部分日子一天待在辦公室十或十二小時,不然就是趕飛機或為演講準備。在家裡,他會站在全身鏡前面背誦談論風險偏好或離岸司法管轄權的演講稿,邊背邊精練手勢動作和面部表情。他和一個辦公室臨時僱員有過一腿。他參加過波士頓馬拉松賽跑。
我又都是做些什麼呢?我咬著舌頭說話,拖著腳步走路,把頭中間一片頭髮由前到後剃光。我是他個人的反對者。
他在我十三歲那一年離家。他向我告別時,我正在寫學校的三角函數作業。他坐在小桌子另一頭(桌上玻璃罐裡總是插著削尖的鉛筆),而我在他說話時繼續做功課。我翻看課本裡的公式,然後在筆記本裡一遍又一遍寫上同樣幾個字:正弦餘弦正切。
我父親為什麼會離開我媽?
兩人都從未解釋。
一些年後,我一個人住在上曼哈頓一間出租小套房。有一晚,我看見父親出現在電視螢幕上。那是個冷門頻道,收訊不良,影像有點重疊。羅斯正在日內瓦發表演講,用的是法語。我以前知道父親懂法語嗎?我又敢肯定電視上的人是我父親嗎?從字幕,我得知他談到什麼失業生態學。我看著他崛起。
但阿蒂絲現在卻置身這個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的地方,這個沙漠中的幽靈之地,很快就會成為一具被保存在巨大墳室裡的冷凍屍體。然後,她會有一個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未來。時間、命運、機會、不朽——這些字眼光想到便夠讓人肅然起敬。但我想到的卻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往事,一些我不能自已、要喚起的瞬間。我會不能自已,是因為這些瞬間是我的,無法看不見或不去感覺。也因為它們是自己從環繞著我的每面牆壁裡爬出來的。……(未完)
【後記】科幻與永生——導賞唐•德里羅《ZERO K》/宋子江(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統籌主任)
最近有科學家準備進行換頭手術的試驗,即把一個活人的頭切開,嫁接到另一個人的脖子上。如果他成功的話,人的身體不斷衰敗,甚至壞死都沒有關係。換頭科技可以幫人續命,這種科技的產生固然會讓人擔心人類會不會陷入倫理困境,但是科技能否逆轉生死有時的宿命?這個問題關係到人類命運之休戚,無論是流行文化,還是嚴肅文學都難以繞過。近幾年,美國科幻電影如《機械姬》(Ex Machina)、《雲端情人》(Her)、《明日邊界》(Edge of Tomorrow)、《啟動原始碼》(Source Code)等等從不同面向觸及過這個議題。美國小說家也不遑多讓,二○一三年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寫出了《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而今年唐•德里羅(Don Dellilo)出版了《ZERO K》。
品欽和唐‧德里羅分別成名於一九六○和七○年代,他們都是美國當代最優秀小說家,近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他們都在賠率榜單上。雖然他們往往被貼上「後現代小說家」的標籤,但是幾十年後,當他們在寫出文學教授、小說評論家和書評家都無法輕易下判斷的科幻作品,讀者不禁想問,「後現代」的前面究竟要加上多少個「後」字,才能體現兩位小說大師天馬行空的構想。品欽的小說愈寫愈厚,並以此著稱,據聞出版社甚至考慮過改換紙質來控制成本。而唐‧德里羅自從一九九七年出版《地下世界》(Underworld)之後,他的小說則愈寫愈薄,愈寫愈黑暗,愈寫愈冷峻,愈寫愈晦澀,今年出版的《ZERO K》還不足三百頁,有些嚴謹的書評家一讀再讀,仍沒有輕易下任何結論。
《ZERO K》的題材引人注目:「人體超低溫保存」,即通過超低溫保持技術,把絕症患者的身體保存在比膠囊旅館還要小的人體膠囊裝置裡,以期有朝一日醫學技術能夠克服該絕症時,再將人體解凍並進行治療。我們在科幻電影中曾經看過許多試圖超越人類感覺時間,甚至超越生死的科技,例如宇航員可以在生命維持裝置中睡掉整個航程,而他們的生理年齡卻不會增長;人可以將自己的大腦信息轉化成數據,存在於數碼世界之中,又或者下載到另一具軀體。可以說,「人體超低溫保存」已並不是那麼新穎的科學構想。唐‧德里羅並沒有去深究倫理上的問題,而是將此原本不得已而為之的技術變成人類的選擇。
唐‧德里羅各部小說的內容互相穿插,形成斑駁多姿的小說世界。要談《ZERO K》,須從他出版於一九八五年的小說《白噪音》(White Noise)談起。《白噪音》的敘述者傑克和他的太太芭蓓有一場頗為浪漫的對話。兩人在談論死亡的問題時,都願意成為先死的那位,而且他們給出的原因也是一樣的:他們都深愛著對方,無法忍受自己的生活中沒有對方的存在。兩人可說是一體兩面。日常生活中的情侶或者夫妻也會進行這種對話,如果一個人選擇後死,因為他不願意愛人去忍受失去摯愛的孤獨和悲痛,這又何嘗不是愛呢?諷刺的是,傑克在一段內心獨白承認,他自己不想先死,他真正想要的是兩人都能苦樂與共,長生不死。這在現實中當時是不可能的,而在小說中,傑克也沒有選擇,因為唐‧德里羅為這部小說設置了宿命:「所有的情節終於死亡」(all plots end in death),因此它的結局可以說是早已註定。
《ZERO K》也講到一對恩愛的夫妻,羅斯和阿蒂絲。羅斯是億萬富翁,六十幾歲,身體健康,而阿蒂絲已病入膏肓,必須進行人體冷凍技術以暫時「保存」性命。與《白噪音》中沒有選擇的傑克不同,《ZERO K》的羅斯有了選擇的自由。他決定把自己也冷凍了,一方面他想要在無盡的黑暗和睡眠中陪伴自己的太太,另一方面他不願意一個人孤零零地面對妻子冷凍後的日子。冷凍在人體膠囊裝置裡的人都集中存放在一個叫「Convergence」的收集中心,大部分都是由於客觀原因而被迫冷凍的,而小部分自願被冷凍的人則放在一個叫做《ZERO K》的單位。
實際上,比起《白噪音》,《ZERO K》對生死狀態的探索讓讀者更加覺得陰森可怖。一個人進入冷凍狀態,他就像進入一個最深層的無夢之眠,雖說保存了生命,卻又最接近死亡。只要沒有人拔掉插頭,那麼在這個狀態中,Immortality(永生)和Mortality(死亡)已經是同一回事,前綴「Im-」可有可無,又無法完全消失。科技既讓人觸碰到超越生死的界線,又無法讓人完全超越。人靜靜地躺在生死的界線上,與界線一同成就永恆。當然,這是筆者猜想的文字遊戲,但是這種解讀有更深一層的意義。「Im-」無疑會讓人想起「I’m」,即「I am」的縮寫,於是「我存在」變成一種模糊曖昧的狀態。筆者認為,這就是《ZERO K》整本小說所探討的核心。
如果唐‧德里羅單方面去寫羅斯,小說就不會具有說服力了。羅斯故意召回他和前妻生的兒子傑佛瑞,並打算把自己的生意交給他,而傑佛瑞正是這本小說的敘事者。傑佛瑞是一個存在感極弱的人,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麻木,但是對身邊的小事情卻十分執著。他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在大時代中浮沉的小人物。選擇他做敘事者,或許是一招險著,例如他會執著於機場安檢諸如此類的小事上,並從中闡發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讀起來有點像黑色幽默,但又不是完全如此。小說中最顯著的一幕莫過於他在紐約計程車上和女朋友滔滔不絕地講身邊「定義我們的小事物」(minor matters that define us),但是他說話的聲音又不得不被馬路上的車聲和電視螢幕上的新聞報導穿插。傑佛瑞終究是個平凡的美國人,既服膺於時代,又不得不對抗時代,一個對抗現實的現實主義者。
這本充滿冷感的小說中唯一的溫情就是兩父子重逢的對話和幽默,但是他們很快就產生分歧。傑佛瑞沒有辦法認同作為時代勝利者的父親羅斯,但是同樣沒有辦法改變父親自我冷凍的決定。兩父子之間南轅北轍的世界觀正是《ZERO K》這部小說最強的張力,亦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羅斯帶著一種冰寒的浪漫情調試圖征服生死之限,傑佛瑞則維持一副尖刻的現實至上的面孔。三十多歲的傑佛瑞對現實的見解仍未夠深刻。其實再往下一步去想,他的父親羅斯進入冷凍狀態以後,就不再能夠被傑佛瑞所說的身邊的小事物所定義。羅斯不僅不能被定義,由於進入冷凍狀態後便失去意識,這些小事物以及傑佛瑞的敘述根本無法對他生效。不是羅斯否定了現實,就是現實否定了羅斯。
《ZERO K》是一部典型唐‧德里羅晚期風格的作品。當然讀者也可以從科學哲學、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角度去批評這部長篇小說對科學倫理的探究不夠深刻,幾乎無視女性的存在,資產階級玩弄尖端科技之不公不義,但是唐‧德里羅晚期風格就是一面多稜鏡,讀他的小說或許更不能被單一理論框架所限吧。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