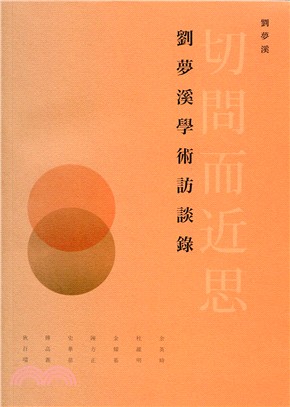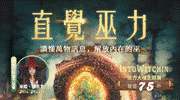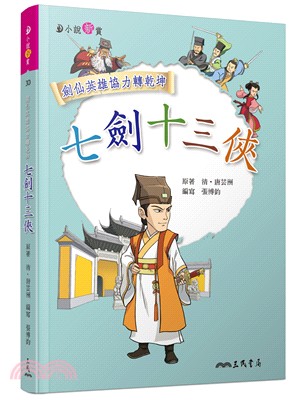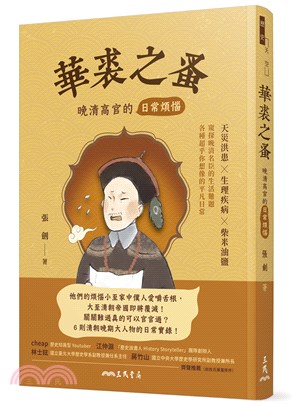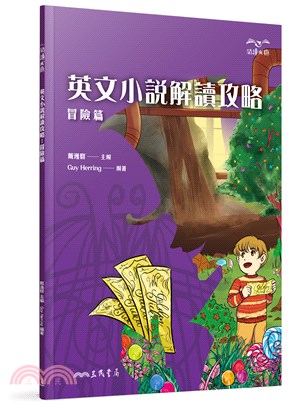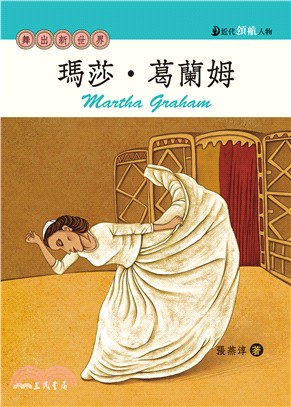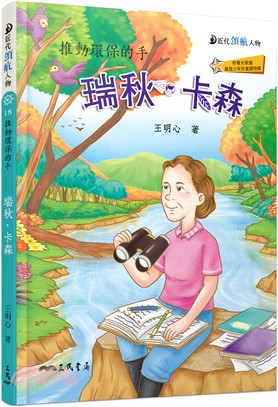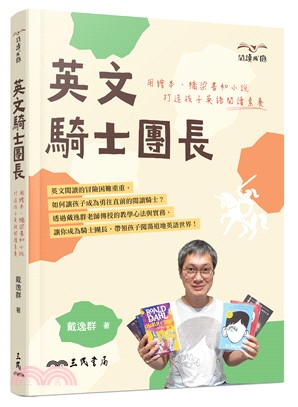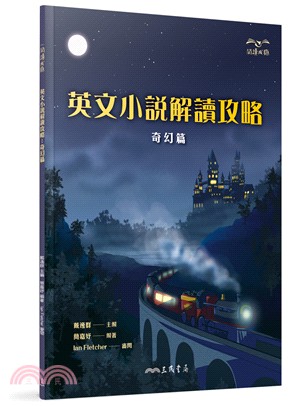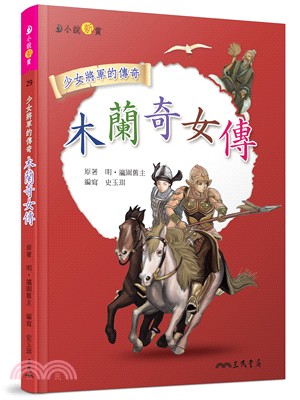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所收之與余英時、史華慈、金耀基、杜維明、狄百瑞、傅高義、陳方正諸先生的訪談,堪稱思想盛宴,其中余英時的真切通明、史華慈的深邃沉醉、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維明的理性低迴,狄百瑞的陳異獨斷,傅高義的親切闊朗,陳方正的科學思維都在書中全然展現。
訪談發生在二十世紀末,涵蓋了社會、文化、現代性等重大議題,其中一些研判已成為事實,甚至在時間的流逝中已逐漸成為歷史。二十餘年過去,大的社會環境與小的敘述語境無疑都變了。無論是內地,還是訪談中多次被提及的香港,也在這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選擇重新回味那場思想盛宴,是因為我們相信訪談錄中的學者絕非一時人物,而是到今天仍不減影響力的思想大家;更是因為我們相信訪談中迸發的思想,是他們一生思想的結晶,足以永恆。回頭再時,依舊感到新鮮。
作者簡介
序
香港版跋語 本書初版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距今已經十年了。中間不乏出版機構找我商談再版事宜,中華也一直有重印的計劃。主要是我一時騰不出手來,來不及對初版重新作一次系統校訂。等到我想重印了,又因余英時先生的名字遭遇朦朧的禁忌,欲再版者變成唯唯否否。一位從事出版的業者向我建議,索性刪去訪談余先生這篇,應該就沒有障礙了。此議固然。但在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遙憶清光緒九年,也就是1883年,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任浙江臬司不到四個月,就因王樹汶案蒙冤去職。陳寶箴的態度是:「一官去耳,輕如鴻毛。」至於一書的出與不出,對一個學者而言,簡直等於無,豈能因一書而忘情忘義哉。實際上,如果沒有1992年我與余英時先生的對坐忘年,後來的那些訪談對話,就無從說起。 世間事,語默動靜無非緣法。有一次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過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先生聽說我與傅有故人之情,便安排了一次小聚。席間我將《訪談錄》一書持呈給傅,他是我的最重要的對話人之一。同時也送給李昕先生一冊。李先生看後,立即說此書應該重印。於是此書便輾轉到了香港三聯書店。中國的體制真是特而不凡,北方不亮南方亮,此地辦不成的事情,易地南移,還真的辦成了。不僅辦成了,而且再過幾個月,就要付梓了。我該向香港的讀者說些什麼悄悄話呢?書中兩位與我對話的主人公,金耀基先生、陳方正先生,他們就佈道耕耘於斯。我想他們會喜歡港版書的風格。余英時先生從大陸出來,首站就是香港,且曾獲任新亞書院院長。此地比較重大的學術活動,我的許多訪談對象都應邀前來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據我所知,他們都喜歡香港。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在1992年,記憶猶新。當時還沒有回歸。結識金耀基先生就是在那一次。我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潘耀明先生主編的《明報月刊》上,題目叫《初讀香港》。這裏不妨摘錄幾段,以明我的香港觀。其中一段寫道:
這是另一個中國,一個社會未被破壞的中國。近百年來中國戰亂頻仍,運動不斷,要麼和別人鬥,要麼和自己鬥,總之沒有消閒過。亂鬥的結果,文化破壞了,社會解體了,這是最難醫治的創傷。香港雖然不能完全逃離這種內鬥外鬥的影響,但社會卻保持了完形,文化也未遭到根本的破壞,這是香港的真正的優勢。文化一詞,人們耳熟能詳,說得口滑,但文化以社會作為自己的依託物,社會不存,文化安在哉?
文章的另一段寫道:
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犧牲品,是大英帝國強佔的中國領土,是中國的南大門,是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樑,是臨時的政治飛地,是繁榮的東方通都大邑,是世界金融與貿易的中心,1997年以後是一國兩制的實驗場。但比所有這一切都重要的應該是:香港是中國人的驕傲!她向世界表明,在社會不被破壞的情況下,中國人能創造怎樣的現代經濟與文明的奇跡。沒有深圳經濟特區,談不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而沒有香港,便不會有深圳經濟特區,也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思路。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最明了。五十年不變,如果是歷史的思考,何必如此吝嗇?我相信是舉成數。甚或如《周易》所示,五十乃大衍之數,麗象繁垂,時空變幻,盡在其中。(載香港《明報月刊》1993年第3期)
我說這些話的背景,至今已過去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後來又多次去過香港,既見證了各盡其職的安寧,也看到了哀愁與紛擾。我的《學術訪談錄》在這個時候南移覓知音,簡直是不識時務。不過與我對話的諸位碩學,可不是等閒人物,更不是一時的人物,而是直到現在仍不減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思想,是一生思理學問的結晶,今天重新驗看,仍然感到新鮮。《21世紀經濟報導》的編者,就是因為看到我與金耀基先生的對話,雖然已是十年之後,還是感到新鮮得如同即時所寫。因此毫不猶豫,立即在報紙上以多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其實訪談金先生的這篇文字,我的手寫筆記回北京後竟然失蹤,撰寫時用的是內子的極簡略的記錄,以及我的盡可能的記憶,所以遺漏舛誤多多。書中的這篇定稿,是經過耀基先生全文修改補充的文稿。此點是必須再次向讀者交代的。這就是何以此篇文字顯得格外系統完整的緣由。
訪談對話,非學術之堂奧,就寫作而言,亦小術也。可是它們在我的學術經歷中所佔的位置,卻有不可輕看的意涵。本書序言寫道:「所收之與余英時、與史華慈、與金耀基、與杜維明、與傅高義、與狄百瑞、與陳方正諸先生的訪談,無異於躬逢思想的饗會,真是非經過者不知也。史華慈的深邃沉醉,余英時的真切洞明,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維明的理性低徊,傅高義的親切闊朗,狄百瑞的陳義獨斷,陳方正的科學思維,都無法淡化的留在我的心裏。」而陳方正離開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位置,學術天地豁然大開,文思泉湧,每年都有新作。特別是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的他的《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一書,成為人文學界口耳相傳的大著述。本人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近年連續多期有方正先生的文字,為拙編大光篇幅。
因此本書的出版,協同書中的這些泰山北斗再次降臨香港,應不止是寂寞學林的一道小風景。《論語.憲問》記孔子之言曰:「作者七人矣。」然則本書的真正作者,應該是余英時、史華慈、傅高義、金耀基、杜維明、狄百瑞、陳方正「七人」,我只是他們思想的追尋者和記錄者。雖然我也是這些訪談的設計者。如果不是當時,移在今天,相信他們和我本人都不具有如此傾心長談的興趣。也許連如此傾談的精神和體力,我和他們都同樣地不具備了。史華慈教授已經作古。余英時先生已是望九之年。
本來還有兩位於我也是亦師亦友的學問大家—張光直先生和李亦園先生,也該留下和他們訪談的記錄。其實還有許倬雲先生,我們在南京曾談得彼此下淚。可惜這些都完全無此可能。許先生應該很難再離開匹茲堡了。
感謝李昕先生推薦本書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感謝責編李斌先生的辛勤勞作。諸家之小傳係及門黃彥偉博士整理編寫,在此一併致意。余英時先生的名字在此地可以不朦朧,也令我感到欣慰。眇予小書,但它充滿了榮光。
劉夢溪
目次
序言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金耀基教授訪談錄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現代方向/陳方正教授訪談錄
現代性與跨文化溝通/史華慈教授訪談錄
哈佛的中國學與美國的中國學/傅高義教授訪談錄
經典會讀與文明對話/狄百瑞教授訪談錄
中華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傳遞/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後記
香港版跋語
書摘/試閱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
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引言 1992年9月,我赴哈佛大學出席「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應余英時教授的邀請,順訪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先生是我最服膺的學者,早在七十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他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當即為之一震。從此我知道世間有余英時其名。他的文章寫於1973年,但我讀到,已是1979年了。自此我便到處找余先生的書,找到一本讀一本,到1988年,凡是能找到的余著我都讀過了。古人說:「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沒想到1992年的秋天,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們第一次在哈佛見面就忘了時間,從晚上10時一直談到第二天清晨5點。然後一起去普林斯頓,在列車上繼續交談。到普大後再談。我們前後談話的時間,大約有三十多個小時。主題則是圍繞中國學術思想與中國文化,追尋的目標是為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重建。
我們談話的方式,更多的時候,是無題漫議,興致所至,想到哪裏,談到哪裏。有時則是我提出問題,英時先生給予解答;解答中遇到問題,我進一步深摳,他再加以闡證。也有時是兩個人對談,各自取證,互相證發。古人所謂談講之樂,盡在其中矣。談話過程中,我徵得英時先生同意,隨手作了簡單記錄。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現場記錄的再整理。小標題自然是整理時所加。整理稿經英時先生過目,有些地方他作了補正。
因此,這既是一篇訪談錄,又可以看作是一篇對話體的文章。只不過作者應該是英時先生。巴爾札克有一句名言:「法蘭西是要成為歷史家的,我只是她的書記。」余英時先生是人所共知的歷史學家,巴爾札克老人這句話對於此時此刻的我,比用之於他本人更合適。
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劉夢溪:您的《錢穆與新儒家》一文,我看得很仔細,前後看了三遍,為的是能準確地寫內容提要。文章刊載在《中國文化》第六期上,香港版已經出來了,大陸三聯版還要一些時間。我揣想您這篇文章,開始時並沒有計劃寫這麼大規模,而是寫著寫著,不能自已,圍繞這個問題的所有觀點便傾瀉而出了。
余英時:也可以這麼說。錢穆先生逝世以後,臺灣、香港、大陸刊出了許多紀念文章。我也寫了兩篇悼念文字,一是《猶記風吹水上鱗》,發表在臺北的《中國時報》;另一篇是《一生為故國招魂》,發表在《聯合報》。但這兩篇文章都有所局限,前者是一篇雜憶,主要記述在香港時期我和錢先生的師生之誼;後者雖然意在說明他的學術精神,也只是簡單勾勒他的民族文化意識的根結,沒有對錢先生的學術思想作深入的闡發。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了《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當然是有所為而寫的。作為錢先生的學生,我不能看到對錢先生的曲解而置若罔聞。
劉夢溪:可是您寫起來就不以澄清問題為限了,我相信這是您近年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似乎是第一次系統表述您對新儒家的看法,因此學術界非常重視。我來美之前接到好多電話,問第六期《中國文化》何時出來。我注意到,您雖然不贊同把錢穆先生置於新儒家的旗幟之下,但您對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儒學傳統並沒有任何輕忽,甚至對錢穆先生的儒學態度和儒學關懷,也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余英時:是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思想像儒家思想這樣,能夠維持得這麼長久,延續了兩千多年,成為中國人的基本價值系統。在做人方面,我最同情儒家了。今天全面恢復儒學做不到,但基本道德,離開儒學其他思想不能代替。比如說,作為一個人,怎麼能不講信義呢?基督教不能代替儒家思想。事實上,我們也不可能把基督教思想完全搬過來。儒學的關鍵在做,不做沒有用。中國沒有傳教士,過去做地方官的,一面管理行政事務,一面傳教佈道,而且是在沒有人指令要他做的情況下,本人自覺自願做的。要說政教合一,這種合一並沒有什麼不好。錢穆先生的儒學觀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歷史事實的層次,一個是信仰的層次。就後者而言,可以說儒家是他終身遵奉的人生信仰,始終堅信儒家價值系統對社會對個人都有潛移默化的積極功能。這一點,我在文章中作了比較詳盡的論述。但錢穆先生決不是新儒家,又必須加以澄清。我認為把新儒家的名號加在錢先生身上,並不是褒揚錢先生,而是局限了錢先生。所以我在文章一開始特別提出學術與門戶以及學問的宗主問題。
劉夢溪:這就不僅是為錢先生辯了,而且提出了學術史的大問題。我個人是最不贊成學術研究有門戶之見的。我認為學派可以有,家法也可以有,就是不應該有門戶之見。一涉及門戶,難免有人為的因素摻入,也就在學問中摻進了偏私之心。而學術領域最容不得一曲之私。《中國文化》創刊,我特地在發刊詞中申明「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辦刊宗旨。章學誠《文史通義》有「言公」篇,道理講得很透闢。特別是站在史學立場上的學者,一般都反對用門戶來自限和限人。
余英時:是這樣。錢穆先生的史學立場很鮮明,《國史大綱》、《秦漢史》、《史記地名考》等乙部範圍內的著作不必說,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諸子繫年》、《論語新解》、《莊子纂箋》、《朱子新學案》等子部著述,也貫穿著史學精神。史學家面對的是客觀世界,歷史陳跡是客觀的東西,如何再現歷史事實的真相,在歷史陳跡中發現歷史精神,已傷透了歷史家的腦筋,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緒去建立門戶的壁壘。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錢先生是浩博寬豁的通儒,不是在牛角尖裏作文章的酸腐書生,這也使他從來與門戶無緣。但治學不立門戶,卻不能沒有宗主。錢先生治學的宗主,我認為就是立志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這一精神貫穿於他的全部著述之中。
劉夢溪:您在文章中講錢穆先生的學問宗主一節,提到了陳寅恪和湯用彤兩位先生,是不是您認為錢、陳、湯三人的學問宗主有相同的取向?
余英時:如果不是完全一樣,也有重要的共同之處。至少他們的學術路向與當時的主流派是相背的。另外,他們都不宗主一家。陳寅恪宗主哪一家呢?國內學術界這一家那一派之間的筆墨官司固然為他所看輕,外國的互為畛域的學術紛爭他也不放在眼裏。他在歐洲、日本那麼多年,主要為的是兩件事:一是接觸原始資料,二是掌握治學工具,特別是語言工具。
劉夢溪:是的,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自主性非常強。他在國外前後有十多年的經歷,對外域的知識學問熟悉得不得了,卻很少在自己的著述中露出痕跡,以致於讓人發生錯覺,以為他使用的是舊方法。
余英時:當然不是舊方法。他是舊中有新、似舊彌新。錢先生也是這樣。所以我在文章中引他《國史新論》裏的話:「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這和陳寅恪的觀點如出一轍。
劉夢溪:您對新儒家的評價是否有些偏低?新儒家把文化作為一種信仰,那種誠篤執著的精神,也是非常令人感佩的。
余英時:應該說新儒家是在提倡一種有信仰的文化,在舉世滔滔之時,他把人的精神作了高度肯定,其取徑值得同情,所作所為是另一回事。我在文章結尾部分有一段話講得很明確:「根據我個人的了解,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製的哲學語言來宣傳一種特殊的信仰。在這個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新儒家如果能發揮一點起信的功用,哪怕僅僅限於三五徒眾,仍然有益於社會秩序。我個人不但不反對,而且十分願意樂觀其成。」這個評價不能算偏低,恐怕已經相當高了。
劉夢溪:那麼您對「第三期」儒學的發展前景是不是比較悲觀?余英時:我認為「第三期」儒學僅僅是個假說。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余英時:講任何問題都不能承認某個人擁有特權。尤其在學術領域裏,在科學面前,更沒有特權的位置。對於某個問題,不能說只有我看到了,別人都看不到。宣稱自己掌握了規律、看到了本質,是荒唐的。科學都不能隨便談,何況規律。一個人如果宣稱自己看到了全部規律,那他就是上帝,他可以洞察萬世。
可以有偏好,但不應有特權。比如研究思想史,研究者當然有自己的觀點,但不能脫離開制度史,不能脫離開社會。在知識面前,在學術面前,在認識面前,誰都沒有特權。如果強調一定要「有慧根」,才能躋身某個領域,那就是要確立一部分人在這個領域的特權。這就是要求特權。先儒裏面,孔子平易,不追求特權。孟子的氣勢高人一等,給人以「捨我其誰」的印象,但還說不上要求特權。如果再進一步,從思想的特權發展到社會特權,危害就大了。
劉夢溪:所謂特權,實際上是試圖把非本體的職分添加到本體上來,無限制地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學術也劃勢力範圍,已經離開學術了。讀書治學,重要的是守持得住自己,為本色學問,做本色人。最要不得的是時不時地到處做出位之思,對什麼問題都發表言說。
余英時:胡適早就說過,要各盡其職。在今天,就思想而言,我主張寧低勿高。
劉夢溪:可是時尚相反,很多人喜歡自高位置,以似乎真理在手自居,聽不得不同意見的商榷。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思想領域一度流行假、大、空的高調,影響所及,也感染了學術界,包括文風、文體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影響。思想的高調尚且無益,學術的高調就更加可憎了。
余英時:思想和學術的高調,我以為與過分要求思想一致、思想統一有關。思想怎麼能夠統一呢?馮友蘭過去強調「大一統」,翻譯他的書的人站出來反對,說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社會需要和諧,但不需要整齊劃一。《易經》裏講:「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個思想很好。司馬光也反復講過這個意思。中國傳統思想是不獨斷的。《論語》平易,不獨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思想太重要了,非常合情合理。
劉夢溪:是的,《論語》已經把大道理化作了日用常行,親切易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能守此道,人與人之間、社會結構內部可以減少很多衝突。「忠恕」,還有仁愛,也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給以理解,應該是流播四海、傳之萬世而不滅的思想資源。
余英時:現在唸《論語》,人們喜歡摘引「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劉夢溪:孔子這句話有不同的解釋,有的把「女」解釋為「汝」,未免過於牽強。其實這是個大判斷,包含有孔子的閱世經驗在內。有意思的是,他對何以「難養」的說明—「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不能說他講得沒有人情世態的理據。
余英時:「君子」「小人」的概念,依我的看法,道德意義高於社會地位。如果看作是單純社會階級地位的劃分,就離開孔子原意了。孔子下判斷,經驗的成分是很大的,好處是他不強加於人。對自己堅持的東西,就說別人不懂,這就是認知上的特權思想。認知特權,對主體是危險的,對客體是有害的。否定的工作是破壞性的工作。否定本身是一種破壞性思維,作為群體的思維定式,在中國是近代衍生出來的。魯迅的長處是深刻。所謂深刻是能夠發現更深在的根源。但光看到壞處,那是尖刻。陳寅恪和魯迅,到底哪個深?純負面的不可能是深刻的。只告知社會是惡,並不能解決問題。
劉夢溪:作家與社會的關係與學者對社會的態度是否有所不同?
余英時: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來看,應該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關懷的方式。作家情感的成分要多一些,而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家,則需要盡量汰除情感。換句話說,作家的主觀性強一些,學者作科學研究則需要客觀。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余英時:我講學術不允許有特權,也包含做學問的人一定要遵守學術紀律。
劉夢溪:這正是我要請教的。我由於編《中國文化》,與各種年齡層的人文學者都有一定接觸,經常收到各種各樣的稿件,因此對一篇論文以及一部學術著作的寫作過程比較留心。同時我本人也是過來人。我深感在國內學術失範是個很嚴重的問題。這有各方面的原因:一是五十年代以後,非學術的因素對學術的影響甚大,致使到底什麼是學術變得不那麼好鑒定;二是長時期以來正常的學術活動不能無間斷地進行,出現了學術斷層;三是由此產生的中青年一代學人缺乏系統的學術訓練;四是與國際社會進行學術交流還很不夠等等。學術失範,也就是學術紀律得不到遵守,是阻礙國內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余英時:的確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學術紀律其實是一種治學的通則,誰都不能違反的。大學的基本訓練裏面,掌握學術規則是其中的內容之一。學術規則很多,例如引用資料一定要真實可靠、要重視第一手材料、要尊重前人成果、不能隱瞞證據等等。不過這都是一些具體規則,更重要的是對待學術要有一個科學態度。就史學而言,第一位的是根據翔實可靠的史料建立自己的觀念,這是個前提。
劉夢溪:您在北美執教、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很長,西方學術界的狀況您非常了解。我很想知道美國漢學界在學術規範方面有哪些特殊的設定?美國漢學,或者說研究中國這一塊,與歐洲漢學有什麼分別?
余英時:西方學術界一般是比較嚴格的,美國也不例外。主要是重視通則。對論文、對著作有一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就通不過。當然由於平時重視訓練,因為不符合學術規則通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很多。至於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以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為職志的專門學者,學風都是很謹嚴的。這與西方的科學傳統有關。要麼做別的事情,只要進入學術領域,就要按慣常的規則辦,已經成為一種職業習慣了,你不讓他這樣做也辦不到。因此遵守學術紀律就像遵守交通規則一樣,如果僅僅意識到不應違反學術規則,還是初步的,應更進一步,變成一種習慣,想不遵守也不行。
劉夢溪:東西方的學術規則是不是也有不同之處?
余英時:規則、紀律應該是相同的,但學術傳統確有不同。我在《錢穆與新儒家》最後一節講「良知的傲慢」和「知性的傲慢」,實際上接觸到了這個問題。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傾向於把自然科學置於社會—人文科學之上,是理論的偏頗;而新儒家使道德主義的意識形態得到完善,用回歸主觀的「道體」代替客觀的「真理性」,其結果不是遵守而是在擺脫學術紀律的路上愈走愈遠。就拿熊十力來說,他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隨意性是很大的。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有一段話,說「今日之談中國哲學史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
劉夢溪:這段話主要是批評當時的墨學研究。
余英時:是的。不過他接下去說的「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呼廬成廬,喝雉成雉之比」,所指就不只是墨學研究了。至少新儒家某些人由於不講究訓詁,他們對古典的態度,與陳先生批評的沒有什麼兩樣。
劉夢溪:不過熊十力的性格堅強,思想執著,也很獨到,有自己的體系,對「六經」、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是有貢獻的。
余英時:熊是特立獨行之士,他的價值在己出。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