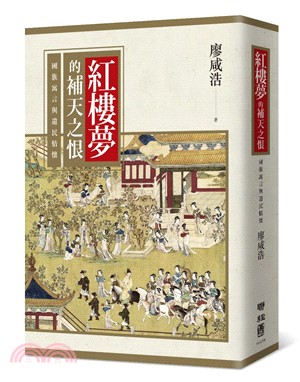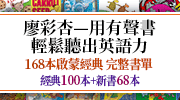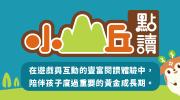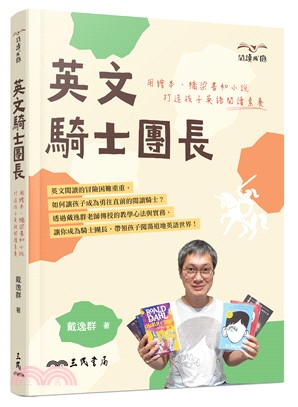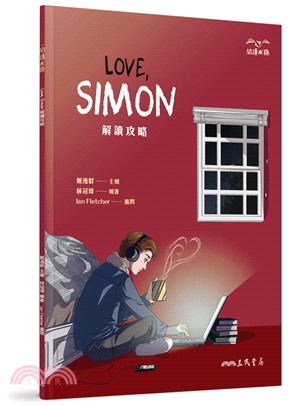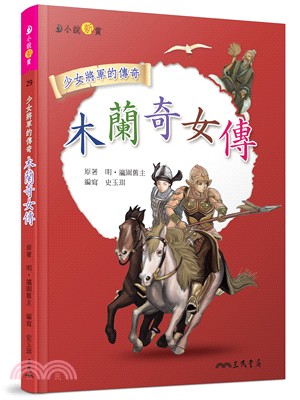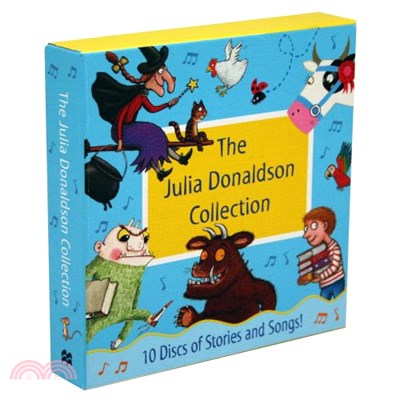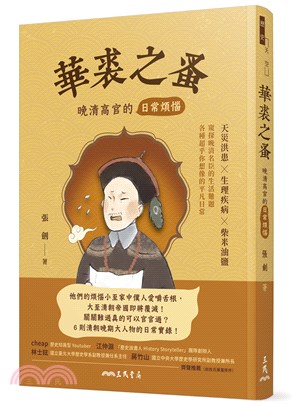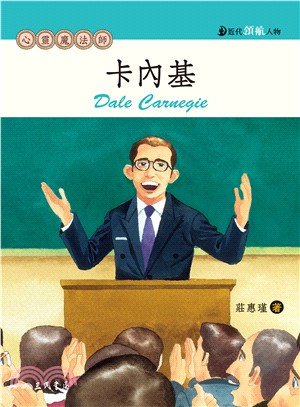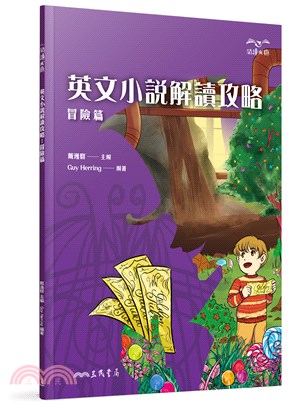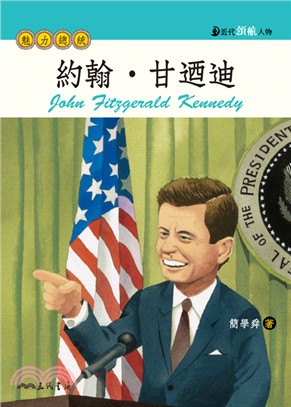商品簡介
以「遺民情懷」作為重詮《紅樓夢》的密碼
從文字迷宮中發掘「隱微書寫」的政治意義
將當代理論導入紅學研究,重審「反清悼明」或「排滿興漢」的議題
學者廖咸浩新作《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將紅樓夢中「心學」與「理學」的對抗現象,
還原為遺民情懷與清代籠絡政策的抗衡,展開關於本書題旨的鉤沉。
這個重詮的過程主要以後設小說、國族寓言及精神分析理論貫穿。從紅樓夢以兩種神話二度開展的現象,勾勒出其後設小說架構,並以「不看正面,應看反面」的寓言閱讀,窺看其對明清易代之巨變下國族命運的省思,再由精神分析理論剖析遺民之「另我」(寶玉)如何在以《大義覺迷錄》為高潮的清廷籠絡政策壓力下,經由重履崇禎殉國至南明覆滅的歷史,以堅其不仕二主之志。最後,《紅樓夢的補天之恨》更經由此一易代的悲劇,探索紅樓夢如何轉化興起於明清之際的本土現代性因滿人入關所遭致的挫敗。
文學研究中的寓言式閱讀在中西文學傳統中都源遠流長,而當代的「國族寓言」式的閱讀,更可謂結合了傳統寓言式閱讀、當代後結構主義理論及後殖民理論,對文學作品中被忽略的國族宰制關係給予了全新的關注。《紅樓夢的補天之恨》的寫作即是從這樣一個視角出發,對遺民情懷應成為一種「具正當性」的紅學研究議題,提供一點淺見。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廖咸浩《紅樓夢的補天之恨》開宗明義,點出目前「紅學」研究的局限在於執著文本內部(人物、文字、象徵)研究,以致見樹不見林,忽略《紅樓》真正宗旨:這是一本反清復明的國族寓言,是一本政治小說。我們任何對木石前緣的矜惜,對補天遺恨的喟嘆,都必須以作者的遺民情懷為前提。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延續了蔡元培、潘重規的「紅學」論述,力圖「正本清源」,為《紅樓》民族大義再做解說。廖咸浩秉持《紅樓夢》作為寓言小說的信念,將全書視為一龐大細膩的遺民密碼結構,不僅自己抽絲剝繭,也號召讀者有志一同,參與解密工作。在以往蔡元培、潘重規式的解讀方法外,他又能操作西學理論,從拉岡(Lacan)到布希亞(Baudrillard)、紀傑克(Žižek),從創傷論到國族論、後殖民論,發展出個人的詮釋體系。作者一方面是解密,但另一方面因為援引、發揮繁複理論資源,其實又成為「加密」的嘗試。由此形成微妙的論述張力,最是可觀。
廖咸浩將《紅樓夢》再還原至歷史情境,認為《紅樓夢》成書背景雖然已是雍乾盛世,卻也是文字獄的高峰期。根據小說種種蛛絲馬跡,作者認為上述三重世界觀和遺民論述息息相關。太虛論依違程朱理學,其實投射清廷懷柔漢人的一套思想邏輯;大荒論指向明室正統覆亡後,天崩地裂的絕對荒涼情境;而大觀論則暗示遺民一往情深,追懷前朝而不可得的烏托邦結晶。
作者簡介
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美國史丹福大學文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曾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中外文學》月刊社長兼發行人、《英美文學評論》總編輯、Studies i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總編輯、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台灣大學主任祕書、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執行長。並曾受邀至美國西雅圖大學任客座教授,捷克查爾斯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任特約講座教授,至美國普林斯頓、芝加哥、澳洲墨爾本、香港中文、南京等大學任訪問學人。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逢甲大學特約講座教授。
公餘曾在港台主要報刊如《聯合文學》、《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香港《明報》擔任專欄作家,以及幼獅電台《苦澀的成長》、公共電視「閱讀天下」的節目主持人。
研究範圍包括:文學/文化理論(精神分析、後殖民理論、全球化與跨國主義、新物質主義理論、後人類理論)、文化政策、比較詩學、英美文學、紅樓夢、電影詩學、道家美學、華人離散、台灣文學及文化等。在創作上寫過詩、散文與小說。
著有散文集《迷蝶》(印刻),評論集《愛與解構》(聯合文學)、《美麗新世紀》(印刻),編有《八十四年度小說選》(爾雅)、《臺北學(Ⅰ)》、《臺北學(Ⅱ)》。另有專書《後台灣文學:認同、現代性、後殖民》、《我是別人:台灣電影中主體的僵局與超越》、《德勒茲與中國思維》,及中、英文詩集即將出版。
序
王德威
《紅樓夢》是古典小說經典中的經典,自一七九一年問世後傾倒歷代無數讀者,影響所及,於是有了「紅學」研究。最近白先勇教授再詳《紅樓夢》,力捧程乙本,又掀起另一波解讀熱潮。在台灣學院傳統中研究《紅樓夢》,我們多半側重文本欣賞。曹雪芹所經營的神話架構、敘事手法、寫實技巧、人物造型、象徵隱喻早為識者津津樂道,更不提小說對生命的感喟和啟悟。
是在這樣豐富的研究傳統之外,廖咸浩教授別有所見,寫出《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全書開宗明義,點出目前「紅學」研究的局限在於執著文本內部(人物,文字,象徵)研究,以致見樹不見林,忽略《紅樓》真正宗旨:這是一本反清復明的國族寓言,是一本政治小說。我們任何對木石前緣的矜惜,對補天遺恨的喟嘆,都必須以作者的遺民情懷為前提。
早期「紅學」研究其實不乏對文本外圍的注意。從胡適一九二一年的《紅樓夢考證》起,到日後俞平伯、周汝昌、趙剛等,都對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鑽研甚深,以致「紅學」又發展出「曹學」。但考證外另有索隱一派,最重要的人物首推蔡元培。早在一九一五年蔡即發表《石頭記索隱》,勾勒全書反清復明的寓言脈絡;論「紅」樓的「朱」色隱喻,「金陵」的地理影射等,只是最明白的例子。索隱派研究以潘重規先生的著述達到高潮。一九五一年潘在台大中文系演講《紅樓夢》血淚史,解析寶黛深情下的興亡遺恨,滿座為之動容,自有彼時的歷史寄託。
廖咸浩教授的新著延續了蔡元培、潘重規這一系統的「紅學」論述,力圖「正本清源」,為《紅樓》民族大義再作解說。但在新世紀重拾政治寓言的話題,廖教授必須面臨如下的考驗。「紅學」研究汗牛充棟,唯自一九八一年余英時先生《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專論以後,我們基本承認《紅樓夢》作為歷史與虛構小說的多義性,無須在考證索隱方面亦步亦趨。畢竟文學作品本身有其自律範疇,不應為掛一漏萬的實證研究所抹殺。其次,廖教授出身比較文學專業,對現當代西學理論極其熟悉。尤其後現代風潮席捲下,探問作品始源意義,似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而追根究柢,《紅樓夢》作者設下重重「假語村言」機關,早在寫作過程中自行解構了。
面對這些考驗,廖教授力圖化阻力為助力,寫出《紅樓夢的補天之恨》。他秉持《紅樓夢》作為寓言小說的信念,將全書視為一龐大細膩的遺民密碼結構,不僅自己抽絲剝繭,也號召讀者有志一同,參與解密工作。在以往蔡元培、潘重規式的解讀方法外,他又能操作西學理論,從拉岡(Lacan)到布希亞(Baudrillard)、紀傑克(Žižek),從創傷論到國族論、後殖民論,發展出他個人的詮釋體系。他的工作一方面是解密,但另一方面因為援引、發揮繁複理論資源,其實又成為「加密」的嘗試。由此形成微妙的論述張力,最是可觀。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基本建構在廖教授所發現的三個世界觀,或三套敘述模式上:太虛論,大荒論,大觀論。我們一般的閱讀多半從太虛論進入,對《紅樓》人物和情事的真假虛實做出辯證式探討,而以警幻仙子的教訓,「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為焦點。但太虛論之外有大荒論,那就是宇宙洪荒,無因果、斷循環的莽莽乾坤。大荒論的偶然觀與太虛論的天命觀成為強烈對照。太虛論之內又有大觀論,在其中「情」之為物成為唯一的生命意義。太虛、大荒、大觀的三重世界觀因此超越余英時先生的二重世界論,指向小說更複雜的形式/觀念結構。
但廖教授有意將此(接近康德的)形式/觀念的典範政治化,將《紅樓夢》再還原至歷史情境。《紅樓夢》成書背景雖然已是雍乾盛世,卻也是文字獄的高峰期。華夷之辨、滿漢防閒的風波從查嗣庭案、呂留良案到胡中水案牽連動輒千百人。乾隆一朝文字獄高達百件,遠遠超過前朝。曹雪芹生逢其時,不可能不感受到巨大壓力。在綿密的文網裡生存,任何心懷正朔的作者下筆為文必將真事隱去,託付村言。所謂「欲彰則蓋,欲語還休」,這是一個語言即政治的時代。
根據小說種種蛛絲馬跡,廖認為上述三重世界觀和遺民論述息息相關。太虛論依違程朱理學,其實投射清廷懷柔漢人的一套思想邏輯;大荒論指向明室正統覆亡後,天崩地裂的絕對荒涼情境;而大觀論則暗示遺民一往情深,追懷前朝而不可得的烏托邦結晶。賈寶玉作為有情主體,所懷抱的不只是木石之情,更是難以言傳的黍離之情。他一心求得釵黛兼美(原初的政治完滿性),但卻落得面對白茫茫一片的大荒絕境。歷劫之後,他將何去何從?
以此,廖教授指出清初遺民論述的黑洞。作為遺民主體人物的賈寶玉必須分辨(被屈從壓抑的)民族大義,或是(被清廷攫取收編的)文化大義,更不提內裡(被異化和創傷化的)真情實意。套用拉岡對「大義物」(The Other,大他者)的認知,廖認為無論如何,遺民「大義」總已是時過境遷的後設相像,總已是矛盾反覆的欲望糾結。而《紅樓夢》最終要處理的是,如何面對這一論述的黑洞,給予一個自圓其說的可能,或啟動另一想像循環。
我以為這是廖教授專著和以往索隱派研究不同之處。他當然也論證出種種似乎相應對照的遺民人物和抉擇。如黛玉的反清復明的理想主義,妙玉的逃禪避世的遁世主義,湘雲見風轉舵的機會主義,寶釵守理衷情的妥協主義等,以及大量情節影射的可能。這些考證固然提供猜謎遊戲般的樂趣,也難免望文生義的誘惑。但與其說廖教授只在乎想當然耳的索隱考證,毋寧說他更企圖將故事「接著講下去」。
我在《後遺民寫作》(二○○七)一書中曾指出,「遺民」的「遺」充滿複雜意義,可以指的是失去(遺「失」),是痕跡(「殘」遺),也可以指的是餽贈(遺「留」)。究其極,遺民情懷之所以如是,正是在於「我們回不去了」:復原已經無望,真相不可能大白。剩下的是殘山剩水,是荒山頑石,是心酸淚、荒唐言。「遺民」作為論述方法既不能完,也完不了。我以為,唯有延續這一層次的弔詭,才能繼續欣賞《紅樓夢的補天之恨》的理論意涵:它必須是自覺地「補遺」、「加密」、「虛構」之作,而非昭告天下的詳夢之書。
如此,書中所援用的大量西方理論也就不妨視為「說故事」的方法。在討論上述太虛、大荒、大觀的三重世界觀之後,廖指出三者之間的矛盾導向遺民敘事的僵局。但《紅樓夢》最終畢竟提出令人意外的轉折,因此為遺民敘事提供了不解之結。他援引拉岡晚期的「叁統」(sinthome)論,認為小說最後不再汲汲於「大義物」(或曰明正朔)的再現,轉而承認日常生活本身延展,也衍異,那一言難盡、不堪回首的民族大義與家國真情。是以全書的關鍵不是寶玉雪夜拜別,歸向大荒─那仍然太理想化了;而是蔣玉函以寶玉的民間分身姿態,與花襲人結合,隱入尋常百姓人家。換句話說,曾經滄海的遺民意識經過一再創傷與試煉後,並不一了百了,而是化為生活本身的症候群,點點滴滴融入穿衣吃飯的生命之流,不絕如縷。
廖教授的理論資源基本來自一九八○年代流行一時的後現代論述,拉岡尤其得到青睞。事實上,他也可以在古典主義學者如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1)的著作如《迫害與寫作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1952)找到共鳴。史特勞斯認為文本的意義從來有表面與深層的分別,相互依存,端賴有心讀者的細讀。古代哲人身處君王與宗教之間,時時可能因言賈禍,因此必須將自己的思想隱藏在字裡行間。一直到十八世紀,言行獨特的哲人都是在政治迫害的威脅下,將書寫化為一種陳倉暗渡、借此喻彼的技藝─「隱微書寫」(esoteric writing)。後之來者的解讀因此也必須理解這一技藝,抽絲剝繭,體會文本所承載的政治風險,並由此體會微言大義的苦心。廖教授的觀點其實與此不謀而合。他以遺民意識作為《紅樓夢》書寫的前提,也期望從研究中發掘「隱微書寫」的政治意義。
目次
大義與微言 王德威
第一章 緒論:絳樹兩歌──《紅樓夢》研究的新方向
第二章 青埂與幻境──《紅樓夢》的兩種起源
一、警幻仙子何事「亦腐矣」?
二、程朱八股與新舊大義
三、不從正面看,要從反面看
四、《紅樓夢》的兩種神話起源論
五、補天遺民與游離秀氣
六、塵緣偶結與前緣天定
七、化石為玉,大觀獨上紅樓
八、三層架構與三種人生
第三章 少年與成人──《紅樓夢》的兩種世界
一、西方成長小說與現代性矛盾
二、理學分化與心一元論
三、情的再生與少年的誕生
四、才子佳人與紅樓迷情
五、程朱杜撰與王門後學
六、赤子之心是否不忍天倫
七、寶珠不明與寶珠已死
第四章 天命與意外──《紅樓夢》的兩種記憶
一、血淚辛酸與二手記憶
二、紅樓殘夢與國族寓言
三、警幻收編與遺民不移
四、自傳他作與人生藝想
五、個人獨創或追求本源?
六、搜奇檢怪,不離本來面目
七、以「詩樂園」重建「失樂園」?
第五章 可親與應憐──《紅樓夢》的兩種中國
一、英蓮迷失與「山崩地陷」
二、可卿猝死與甲申之變
三、「英蓮書寫」與「可卿書寫」
四、遺民心之所繫:女性世界
五、迤邐迷宮與攀天金字塔
六、尋國族救贖於庶民智慧
第六章 意淫與肉淫──《紅樓夢》的兩種耽溺
一、肉淫的欲與意淫的情
二、淫的治療:不可能的任務
三、父之名背後:淫穢與至情
四、意淫至極,「除明明德外無書」
五、「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
六、雙美兼具或男女平衡?
第七章 兼美與警幻──《紅樓夢》的兩種平衡
一、兼美退位,寶釵崛起
二、神祕繡春囊與朗朗會真記
三、主陽奴陰「方是人的規矩」
四、仙子警幻,雍正覺迷
五、清之大義破明之至情
六、以天命呼之,以倫理範之
第八章 真情與假義──《紅樓夢》的兩種本體
一、假如何作真,無如何變有?
二、大觀真情與太虛假義
三、南邊之情與北邊之清
四、「水國」台灣的「漢南」情緣
五、「保今王」者終究「白雪紅梅」
六、更高層次的真與假
第九章 逃禪與日常──《紅樓夢》的兩種禪宗
一、佛家思想與紅樓幻夢
二、禪宗勘破與入世人生
三、清初遺民與逃禪策略
四、精神逃禪與週轉空間
五、遺民主體最後的依託
六、「現代創傷」與中國現代性
七、禪宗與儒家一衣帶水
第十章 覺迷與致命──《紅樓夢》的兩種誘惑
一、誘惑赴死的祕密命運
二、飛升太虛或回歸大荒
三、保守的夢與激進的玉
四、困頓於木石與金玉之間
五、拋棄富貴路,重回傷心地
六、遺民的末世與順民的聖世
第十一章 今聖與後王──《紅樓夢》的雙重視野
一、婚與不婚的遺民困境
二、以出家為名的身分交換
三、「事二主否」誠千古艱難
四、始於「保國」,終於「保天下」
五、「期待後王」與遺民思想普世化
七、興亡有迭代,中華無不復
第十二章 結論:黃華二牘──《紅樓夢》與身分認同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第一章 緒論:絳樹兩歌──《紅樓夢》研究的新方向
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紅樓夢》的詮釋都不斷因自詡是「文學」的研究,而極力迴避書中的「政治」面向。倒不是說與政治相關的元素都無法被接納;階級鬥爭、宮廷鬥爭等元素仍被一定程度允許。被排除的元素主要是國族鬥爭相關的遺民情懷(即反清悼明或排滿興漢的意趣)。原因眾人皆知是來自胡適對早期索隱派的致命一擊。當胡適考據出曹雪芹為作者之後,他生活的年代及包衣的背景似乎意味著他不可能有任何遺民情懷。然而書中俯拾皆是的疑似遺民情懷的線索,卻又無法輕易納入現有的所謂「文學」的詮釋架構,以至於以傳統索隱為方法的「在野」研究不但從未止息,甚至可謂春風吹而又生。
但胡適催生的是曹學,而紅學研究之所以會「純文學化」或「去政治化」,追根究柢還是肇因於不少紅學研究在方法論上停滯於一種「前新批評」的所謂「文學」研究。這類的研究對新批評忽視脈絡,頗有認知,但其因應方式卻是回到新批評所大力批判的傳記派研究(biographical literary study),對作者背景及生活細節津津樂道並以之為研究的根據,並在不知不覺間與曹學一定程度的互為體用。然而值此同時,新批評對文本細讀的要求也因此而遭到忽略。更遺憾的是自新批評迄今的大多數新思潮幾乎等於都不存在於紅學研究的領域。而在當代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已成為基本的文學研究方法時,「遺民情懷」這種與被殖民經驗極為相近的經驗竟常被斥為無稽,尤其令人扼腕。於是,紅學的無限空間遂被收束在極為傳統的所謂「文學」研究,而無法坦然面對書中與殖民統治相似的政治面向,當然也就無法掌握小說的「生產條件」(conditions of production)。典範早該轉移卻猶自踟躕。
現行對《紅樓夢》所謂「文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另一個基本缺失則是,少有論者將《紅樓夢》當作「一本」小說來研究,多數研究對小說並無「我注六經」般的慎重其事,而更像是「六經注我」式的各取所需;論者只顧選取對自己論證有利的細節,而忽略其他不利的細節。嚴格講,這種研究甚至稱不上「文學」研究,或只能稱為私密的讀後感而已。
然而,對書中遺民情懷的探討,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接受傳統索隱派的方法論。本書無意為索隱派辯駁,畢竟傳統索隱的閱讀在方法論上確有瑕疵,但這卻不意味著「反清悼明」或「排滿興漢」的遺民情懷便因此應束之高閣。文學研究中的寓言式閱讀在中西文學傳統中都源遠流長,而當代的「國族寓言」式的閱讀,更可謂結合了傳統寓言式閱讀、當代後結構主義理論及後殖民理論,對文學作品中被忽略的國族宰制關係給予了全新的關注。本書的寫作即是從這樣一個視角出發,對遺民情懷應成為一種「具正當性」的紅學研究議題,提供一點淺見。
本書欲自《紅樓夢》鉤沉的遺民情懷,非單指具遺民身分之作者所流露於作品中的情懷,更非如索隱派企圖在書中做歷史人物之一對一的指認。而是指本書乃是具有「反清悼明」乃至「排滿懷漢」之廣義遺民情懷的作品。這時作者可以是遺民,也可能是曾經仕清的前朝士人,甚至可能生於易代之後。這種情懷其實是清初眾多作品或隱或顯所共有的特質。《桃花扇》、《長生殿》二劇作可謂最為人所津津樂道、具遺民情懷的作品。但不少其他凸顯忠烈之作品(包括以建文帝靖難為主題的書寫),往往都隱含遺民情懷,差別僅在隱顯;然一隱一顯之間,作者與作品之命運可謂有天壤之別。隱顯之選擇往往與時代之氛圍(主要是文網之寬緊)及作者之判斷有關。
如康熙朝之《桃花扇》、雖明白與悼明相涉,最終且為統治者不容,卻未足以死。而乾隆朝以詩作婉轉托寓時,甚至雖無其事但可茲聯想,則往往立遭構陷,並處以極刑。不過,事實上自清初始文網已相當緊密,而致具遺民情懷的知識分子雖亟欲一抒塊壘,卻不敢直剖胸臆,故普遍使用自創的「隱語系統」,以輾轉言志、迂迴論事。因此,後人鉤沉遺民情懷,就不得不對當時這些「因人因事而異」的隱語系統,進行余英時所謂的「譯解暗碼」(decoding)的工作。然而,可以想像的是,若為避文網而藏之過深,則作者雖或能倖存,寓意卻可能因時間的流逝而湮滅。《紅樓夢》就可能是這樣的例子。
具遺民情懷之作品就文類而言,幾乎詩作、小說、劇作皆有重大的產出。就詩而言,如收入於卓爾堪所輯《明遺民詩》中有作者四百餘人,詩文近三千首皆屬此類。而日後遭構文字獄者部分詩作也確透露出遺民情懷的蛛絲馬跡,如乾隆朝與《紅樓夢》著作年代相近的「徐述夔案」(案發於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即為一例。徐氏(一七三八年中舉,案發時去世十多年)的詩文中仍看到強烈的弔明之意(如「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諧「胡兒」)擱半邊」、「毀我衣冠真恨事,搗除巢穴在明朝」等)。
就劇作而言,除先前提到的《桃花扇》及《長生殿》或因作者出生於易代之後較無警覺,而渾不避人耳目,有更多作品則欲語還休,尤其情緒較澎湃者,壓抑尤重、隱藏尤深。如王夫之的《龍舟會》改寫唐傳奇謝小娥報父親與丈夫遭賊殺害之仇,實則深藏遺民湔雪國恥之欲望與無力回天之憾恨。其餘如丁耀亢〈化人遊〉、黃星周〈人天樂〉、尤侗〈讀離騷〉、〈桃花源〉、〈鈞天樂〉、〈弔琵琶〉、吳偉業的〈秣陵春〉、〈通天臺〉、〈臨春閣〉都有類似意趣。另外,以靖難為主題的作品如李玉〈千忠錄〉、朱佐朝〈血影石〉、葉時章〈遜國疑〉、邱園〈一合相〉,也無一不以各自的隱語系統輾轉流露出不同程度的遺民情懷。
小說部分,鄭振鐸早在〈清初到中葉的長篇小說的發展〉一文中已點明:「董說的《西遊補》、陳忱的《水滸後傳》、丁耀亢的《續金瓶梅》、西周生的《醒世姻緣傳》、錢采的《精忠傳》都是頗可注意的長篇。他們都是『有所為』而作的,不是為寫小說而寫小說的。他們都是要以『古人酒杯澆自己的塊壘』的。所以在『遺民文學』的這個特殊意義上是有了很光榮的收穫的。」這些作品皆透過托寓的方式暗涉弔明反滿之情。其中陳忱的《水滸後傳》尤其是各方津津樂道的例子,作者陳忱在序中明言以本書來表達「古宋遺民之心」,而魯迅及胡適的閱讀都斷言其遺民情懷。小說中亦有藉靖難喻易代者,如《女仙外史》便是。
在遺民的著作中,張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就遺民之衷情未著一字,卻透過隱語言簡意賅的道盡遺民無可補天之悵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與《紅樓夢》有著極相似的修辭: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張岱所寫之往事雖在明亡之前(一六三二),但晚年書此文時雖距明亡已二三十年,卻仍用崇禎年號,文中復特別點出湖心所遇係客居於此的「金陵人氏」,再銜接最後二句舟子之言「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中的「痴」字,完成了本文隱語系統所烘托的寓意:其「痴」應屬遺民感復國無望只能孤高離俗之「痴」。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句與《紅樓夢》的表達方式緊密的呼應: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第一回)
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痴!(第一二○回)
此處的舟子正是「遺民圈外人」,故不解相公之「痴」。而紅樓夢此二回所指涉之狀況也極類似;「都云」及「休笑」的主詞都意指類似「舟子」的「非遺民人士」,彼等因不知「由來同一夢」,故「不解其中味」,遂如舟子對相公一般,訕笑遺民(世人)之痴。
胡適之後的紅學研究之所以難以有新的突破,正是因為書中可能的隱語系統已被束之高閣。隱語必涉托寓,或西方理論所謂的「寓言」(allegory),故捨隱語則失托寓。這正是後胡適紅學研究的大罩門:徒孜矻於文字的表面,而棄托寓於不顧。然而,紅樓夢開宗明義「真事隱去假語存言」,無非是要提醒我們,不可執著於文字的表面,而應深入文字的背後。而且,通篇各種雙關語、謎語,及婉轉指涉,又更透露出小說另有寓意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實有所指。因此,回到《紅樓夢》的隱語系統,鉤沉其被掩埋的寓意,才是還此書以公道的關鍵門徑。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