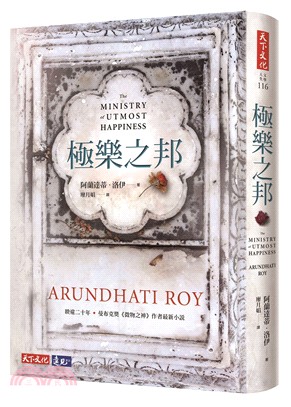商品簡介
● 暌違20年.曼布克獎《微物之神》作者最新小說
● 亞馬遜2017年6月選書.文學小說暢銷榜冠軍
● 李明璁.紀大偉.郭強生 齊聲推薦
「我與書中角色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他們對身分、性別、國家、民族、信仰、家庭、母親、死亡與愛,有著迷亂的歸類與概念,而我自己也是。」
——阿蘭達蒂.洛伊
在這片土地,戰爭就是和平,和平就是戰爭。
經過二十年漫長等待,我們再次走進印度,張開驚奇的眼……
婕冰小姐二世降生於太平盛世的午夜,
東方有百萬顆星星迎接她的到來。
她在不受期待下出生,備受期待下成長。
婕冰小姐二世是三個母親的孩子,
安竺和蒂洛都宣稱是她的母親。
被困在雌雄莫辨軀體裡的安竺,
畢生追尋棲身之所,改變肉體,
心靈卻不知該何去何從;
周旋於三位愛慕者的蒂洛,
在最危險的愛情裡孤注一擲,
同樣需要慰藉。
故事從印度這片土地長出,
美麗、荒謬而支離破碎的世界,
圍繞著充滿矛盾、苦痛與哀愁的男人和女人,
迷亂的身分、徬徨的愛,如波斯地毯般華麗展開……
媒體讚譽
洛伊筆下的故事具有電影特質,深刻動人。她以詩意的筆法描繪出愛與歸屬的複雜公式……從親眼目睹的悲劇中萃取希望。
——角谷美智子,《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洛伊的小說是今夏不可錯過的作品。內容洞悉人性,角色令人難忘,文字活色生香,果然值得二十年的等待。
——莎拉.貝格禮(Sarah Begley),《時代雜誌》(Time)
故事既私密又有國際視野……洛伊的文字有一股魔力,不像印在紙上的字,而是浮在水上的墨。書中火熱的憤怒和深深的憐憫都將使你動容。
——榮恩.查爾斯(Ron Charles)《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這部小說融合溫柔與殘暴、神話與新聞頭條……透過洛伊之眼,我們看到一個美麗、矛盾且支離破碎的世界。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作者簡介
阿蘭達蒂.洛伊 Arundhati Roy/著
1959年生,現居新德里。首部長篇小說《微物之神》即獲1997年曼布克獎,震驚世界文壇。《微物之神》長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數十週,全球售出四十餘種語言,銷量破千萬冊。此後,洛伊投身社會運動,關注人民、政治、環境與正義,發表數十篇散文及評論文章。經過二十年醞釀,全球書迷引領期盼的第二部小說《極樂之邦》終於問世。
廖月娟/譯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獲誠品好讀報告2006年度最佳翻譯人、2007年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2008年吳大猷科普翻譯銀籤獎。翻譯生涯逾二十年,作品近百冊,期許自己畢生以「科學的熱情和詩之精確」來翻譯。譯作包括《狼廳》、《雅各的千秋之年》、《謝謝你遲到了》、《灰犀牛》、《人生思考題》、《不整理的人生魔法》等。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文】一切終歸「極樂」 / 郭強生
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洛伊二十年前以小說處女作《微物之神》一舉拿下曼布克文學獎,不僅作品全球熱賣,成為新英語文學的代表,她本人亦成為媒體寵兒,被《時人》(People)雜誌選為全世界最美麗人物之一。但是她顯然對此深感抗拒,之後身體力行投入政治運動,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反印度核武、反美國出兵阿富汗……敢言直言,每一個抗爭現場幾乎都看得見她的身影。她的讀者們不禁都要懷疑,那個文字瑰麗神祕又擅長說故事的阿蘭達蒂,是否早已改弦易轍,與文學漸行漸遠了?
時隔二十年後,阿蘭達蒂終於推出了她的第二部小說《極樂之邦》,甫出版就入圍了曼布克獎,讓關注她的讀者們都鬆了一口氣:那個天生的說故事人又回來了!只不過,這回她要述說的,不是童年那個洋溢著幻想與人情之美的印度,而是在上世紀末一度被視為金磚四國、經濟起飛,事實上因宗教衝突、政治貪腐、種姓制度不公而陷入動盪不安的二十一世紀印度國內真相。
這本《極樂之邦》或許也可看做這二十年來,阿蘭達蒂在四處奔走、拍攝紀錄片、穿梭於不同黨派為受壓迫者發聲的一個縮影,她所支持與反對的情勢都一一成為了她這部小說的背景。她的憤怒與痛心在字裡行間清晰可見,但是,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她仍未失去一位小說家欲以文字,為一場場血腥暴動中的死者安魂的敏感與真誠。《極樂之邦》這本書的書封設計乃以一幕碑為圖。或許,面對人類的盲目、瘋狂、貪婪、愚蠢,阿蘭達蒂最後還是選擇用藝術之眼,文學之筆,為人類留下另一種珍貴的紀錄。以「極樂之邦」為名,看似反諷,但何嘗不是為了喚醒人類的良知?
全書以一場發生在二○○二年印度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衝突為主要背景,這場起因是載滿印度教徒的火車疑遭穆斯林恐攻,之後印度教徒對穆斯林展開瘋狂報復殘殺的動亂,直到今日仍餘波盪漾。做為身在台灣的讀者,多數人也許長年對國際大事無感,也可能對這場死傷千餘的人間慘劇一無所知。阿蘭達蒂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窗口,讓我們目賭看似遠在天邊的動亂,其中隱隱有著多少我們似曾相識的因果脈絡。
目次
2 夢之宮
3 降生
4 阿薩德.巴堤亞博士
5 追蹤覓影
6 未來會出現的問題
7 房東
8 房客
9 婕冰小姐一世的早夭
10 極樂之邦
11 房東
12 糞金龜
書摘/試閱
婕冰小姐一世的早夭
自從她長大到開始有自己的主見,就堅持每一個人都要叫她婕冰小姐。只有叫她這個名字,她才會回應。「小姐」這個稱呼是在喀什米爾谷地發生動亂早期開始流行的,早熟的婕冰小姐從此奉行不輟。突然間,所有追求時髦的女孩都堅持別人稱她們為小姐,特別是住在城裡的。
可惜婕冰小姐早夭,沒能長大成人成為護士,甚至沒機會溜直排輪。
她最先被埋在烈士墓園。墓園大門入口上方鑄鐵做的拱形標示牌上,用兩種文字寫了一句話:「為了你們的明日,我們獻出今日。」鑄鐵已經生鏽,綠漆也變得斑駁。然而,經過了這麼多年,那鑄鐵標示牌仍在,就像一塊綠蕾絲,鑲嵌在藍天和白雪皚皚的鋸齒狀山頭。
那標示牌還在。
標示牌上面的字句是行政委員會決定的。無限正義的代數極其霸道,沒徵詢任何人,就把她列為獨立運動年紀最小的烈士。她就葬在母親亞里法.亞斯威的旁邊,一顆子彈取走這對母女的性命。子彈從婕冰小姐的左邊太陽穴穿入她的頭部,穿出後再進入她母親的心臟。她生命的最後一張照片中,子彈在她左耳上方留下一團紅紅的血,像是一朵盛夏玫瑰。下葬前,幾片花瓣飄落在她的白色裹屍布上。
烈士墓園裡,婕冰小姐和她母親的墳相鄰。穆沙.亞斯威為他太太的墓碑刻了下面文字:
亞里法.亞斯威
1968.9.12-1995.12.22
穆沙.亞斯威的愛妻
接著有兩行詩句:
Ab wahan khaak udhaati hai khizaan
Phool hi phool jahaan the pehle
此刻,塵埃在秋風中飛揚,
曾經風華正茂,今已香消玉殞。
婕冰小姐的墓碑上的字則是:
婕冰小姐
1992.1.1-1995.12.22
亞里法和穆沙.亞斯威的愛女
所有看穆沙.亞斯威埋葬妻女的人,都注意到他的靜默。從他的臉,你看不到悲傷。他看起來孤僻而且心不在焉,似乎人在心不在,他最後可能因此被捕。或許是因為他的心跳,他的心跳太快或太慢,因此不是無辜的平民。惡名昭彰的檢查哨士兵有時會把耳朵貼在年輕人的胸膛上,傾聽他們的心跳。據說,有些士兵甚至帶著聽診器。他們說:「這個人的心跳,是爭取自由的節奏。」
穆沙不是在檢查哨被逮捕。葬禮過後,士兵去他家捉拿他。在自己妻女的葬禮上過於平靜是不可能逃過任何人的耳目的。他們總是在一定的時間找人——凌晨四點。他早已醒來,在書桌前寫信。他走到門口,兩個士兵持槍分別站在他的左右兩側,把他押上車。穆沙沒被上手銬,也沒被布袋套頭。出租車駛向冰凍、滑溜的街道。
希哈茲電影院改建的聯合審訊中心裡面有營房和軍官辦公室,周遭防護極為嚴密。出租車戴著穆沙很快就通過檢查哨。顯然,軍方已經知道這件事。車子直接從中庭開到主要入口。穆沙和護送他的兩名士兵沒在登記處停留,像皇室成員大搖大擺地直接走進去,從旋轉樓梯走到皇后包廂。
安瑞克.辛格少校從桌子後方站起來迎接穆沙。
「我把你帶來這裡,是表示我的歉意和最深刻的哀悼之意。」
喀什米爾實在腐敗到了極點,安瑞克.辛格才會渾然不知這麼做有多諷刺。一個人的妻女才剛被槍殺,竟然叫士兵拿著武器在凌晨四點把他押到審訊中心,只是為了表示同情!
「發生在你身上的,不該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你必然受到驚嚇。來,吃點脆餅。這種脆餅很好吃,一半是糖,一半是鹽。」
穆沙不語。
安瑞克.辛格喝完茶,穆沙那杯一口也沒喝。
「你是學工程的,不是嗎?」
「不是,是建築。」
「我想幫你。你知道,軍方正在招募工程師。有很多工程可做,待遇很好。邊境柵欄啦、孤兒院啦,他們還計劃為年輕人興建娛樂中心、體育館,就連這塊地方也需要整修……我可以幫你爭取到條件不錯的合約。至少,這是我們該彌補你的。」
穆沙沒抬起頭來看他。
「我被捕了嗎?還是我可以走了?」
因為他一直沒抬頭,所以沒看到安瑞克.辛格眼中浮現一層透明的憤怒。那憤怒來得很快,而且悄然無聲,就像一隻貓倏地躍過矮牆。
「你可以走了。」
穆沙站起來,離開房間。安瑞克.辛格一直坐在椅子上。他按鈴,請人護送穆沙出去。
天色漸亮。鴿子灰的天空出現一抹玫瑰紅。穆沙走在死寂的街道上。出租車與他保持安全距離,在後頭慢慢開。司機一邊用無線電連絡檢查哨,要他們讓穆沙通行。
他走進家門時,肩膀上有積雪。天氣再怎麼冷,也比不上他的心寒。他的父母、姊妹看到他的臉,就知道最好什麼也別問。他回到書桌,繼續寫信。先前被帶走時,他只寫了一半。他用烏爾都語寫,寫得很快,有如這是他最後的任務,也像是在跟寒冷賽跑,必須在身體的熱散發光前趕緊寫完。或許,這是一封永遠也寫不完的信。
他是寫給婕冰小姐的。
親愛的寶貝,
你想,我會想你嗎?你錯了。我才不會想你呢,因為你永遠跟我在一起。
你要我講真實的故事給你聽,但我再不知道什麼是真實了。從前的真實故事,也就是我過去說的那些,現在聽起來就像愚蠢的童話故事,你應該無法忍受。我現在確知的是:在喀什米爾,死者將永遠活著,而生者則假裝自己是死人。
下禮拜,我們要幫你製作一張身分證。親愛的,如你所知,現在身分證比我們本人來得重要。這張小小的卡片比什麼都要珍貴,勝過最漂亮的地毯、最柔軟暖和的披肩、最大的花園或是我們谷地所有的櫻桃和胡桃。你能想像嗎?我的身分證字號是M108672J。你說,這是個幸運號碼,因為M是「Miss」(小姐),而J代表你的名字「Jebeen」(婕冰)。真是這樣,我應該很快就會跟你與你最親愛的媽咪相會,你準備好好在天堂做功課吧。如果我告訴你,有十萬人參加你的葬禮,又有什麼意義?你只會數到五十九吧?我是說數數兒嗎?我指的是叫喊,你只能叫喊到五十九。不管你現在在哪裡,我都希望你別大吼大叫。你要學習輕聲細語,像淑女一樣說話,至少有時候必須這樣。我要如何為你解釋十萬呢?這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我們用季節的概念來想,好嗎?想想,春天的時候,樹上有多少葉子,冰雪融化後,溪裡有多少鵝卵石?想想原野上有多少紅罌栗花。如此一來,你應該對十萬是多少有一個粗淺的概念。秋天,我帶你去大學校園散步,法桐樹葉子被你踩得沙沙作響,好多好多的葉子。
不管怎麼說,再回到我們方才討論的數字:十萬。你還可想想在冬天從空中飄下的片片雪花。還記得我們是怎麼數嗎?你不是曾伸手,想抓住那些雪花?在你葬禮上出現的那些人就是這麼多。他們像雪花,覆蓋所有的地面。你能想像嗎?好。而那些只是人群,還沒算從山上溜下來的懶熊、從樹林中窺視的馬鹿、在雪中留下爪印的雪豹、在空中盤旋監督的栗鳶。總而言之,那個場面太壯觀了。我知道,你應該很會很開心,因為你喜歡人群。我們早就知道,你應該會變成都會女孩。現在,該你了。告訴爸爸——
最後那句才寫一半,穆沙不敵寒意,就此停筆。他把信紙折疊,放進口袋。這封信他一直沒寫完,但總是帶在身上。
他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他必須搶先安瑞克.辛格一步,先發制人。他所知的人生已經完結,他知道他已被喀什米爾吞噬,在喀什米爾的胃腸中。
他花了一天時間完成該做的事:付清他欠的菸錢、撕掉一些文件、把愛不釋手或是所需之物放在袋子裡。翌日清晨,他家人醒來,他已離去。接著,他轉往地下活動,不再拋頭露面。這段時日持續了九個月,就像懷孕,只是結果和懷孕完全相反,最後是以死亡做為終結,而非迎來新生命。
他變得更冷漠、安靜。他的人頭價碼愈來愈高,本來只有十萬盧比,現在已高達三十萬盧比。九個月過去後,蒂洛來到喀什米爾。
● ● ●
一艘艘船屋緊挨著停泊在對岸,湖畔漆黑、空蕩蕩的。
沙欣號是最小,也最破爛的一艘。蒂洛的船靠近岸邊時,一個裹著及膝棕色大衣、個子矮小的男人前來迎接她。後來,蒂洛才知道他名叫古爾瑞茲。他好像很了解蒂洛,有如她這輩子都住在這裡,只是去市場買點東西。男人的頭很大,脖子很細,肩膀寬闊。他帶蒂洛走進船屋,經過小小的餐廳,從一條鋪著地毯的狹窄走道進到臥屋。她聽到貓咪在喵喵叫。他像個驕傲的父親露出燦爛的笑容,兩顆眼睛就像綠寶石那樣迷人、閃亮。
房間只比一張雙人床略大。床上有件繡花床罩,床頭桌上擺了一個花朵圖案的塑膠托盤,盤子上有個精美的鐘形金屬水壺,兩個彩色玻璃杯和一部小小的CD播放器。地板上花色繁複的地毯有幾個地方已經磨破,衣櫃的門刻工較粗,天花板有蜂巢裝飾,混凝紙漿做的垃圾桶也有複雜的花紋。蒂洛覺得眼花撩亂,想找一個沒有圖案、繡花、雕刻或精工裝飾的地方,讓眼睛休息一下。由於遍尋不著,她心中湧現一股焦慮。她打開木窗,但是只看得到隔壁船屋的緊閉木窗,空菸盒和菸蒂在兩艘船屋間的水面上飄浮。她把行李放下,走到門廊點了根菸。
第二天,她都在船上等,看著古爾瑞茲用雞毛撣子撣一塵不染的家具,看他在船後方堤岸上的菜園跟他種的紫茄和甘藍說話。兩個人吃了簡便的午餐,碗盤清理完後,他拿出一個機場免稅店的大型黃色購物袋,展示收藏的東西給她看。這就是他的待客之道。
蒂洛以吞吞吐吐的印地語跟他聊天,他則用結結巴巴的烏爾都語說。蒂洛發現,他說的「穆札卡克」應該就是穆沙。他拿出一份烏爾都語報紙的剪報給蒂洛看,上面有婕冰小姐跟她母親遭到槍擊的照片。他不斷地親吻報上的照片,指著上面的小女孩和年輕女子。蒂洛慢慢拼湊,大概得知是怎麼一回事:那女子是穆沙的妻子,而那小女孩是他們的女兒。照片印得很模糊,沒能看清她們的五官,因此不知這對母女是否相像。古爾瑞茲為了讓蒂洛了解,他雙手合掌,頭斜斜地靠在手上,像孩子一樣閉上眼睛,然後指著天空。
她們上天堂了。
蒂洛不知道穆沙結婚了。
他沒告訴她。
他該跟她說嗎?
她該在意嗎?
當初是她離開他的。
但她的確在意。
不是因為他結婚,而是他沒告訴她,他結婚了。
她不知道為何知道穆沙結婚,她竟有如此怪異的反應。也許,這是因為她的腦子裡在下暴雨。也許,這是心靈的生存策略,以免去想為何她和穆沙的惡夢會錯綜複雜地糾纏在一起。
沒有任何導遊告訴她喀什米爾的惡夢如此雜亂。這些惡夢是最偉大的突襲者,會背叛你,任意闖入你的夢境,且不接受任何管束。沒有任何碉堡、圍籬可抵擋這些惡夢的入侵。在喀什米爾,你只能像擁抱老朋友一樣擁抱那些惡夢,像面對老敵人一樣應付。蒂洛很快就知道了。
她坐在船屋門廊有軟墊的座椅上,看著第二個日落。
穆沙突然靜悄悄地從船尾上船,古爾瑞茲正要上菜。
「對不起,久等了。」
他沒多解釋。他的樣子似乎沒多大改變,只是看起來有點憔悴,但蒂洛幾乎認不出他來。他的鬍子長了,眼神似乎一下明亮、一下黯淡,像是有一個顏色被洗得褪色,另一個顏色還在。他那棕綠色的瞳孔外圍多了一圈黑色,蒂洛記得他以前的眼睛不是這樣。她看到他的輪廓、他在這個世界的樣子,那輪廓已經變得模糊不清。因此,他更容易融入周圍的環境。他脫下羊毛帽,蒂洛發現他的頭髮多了一道銀色線條。他知道蒂洛正在看他的頭髮,手指像有自覺似的,撫弄自己的頭髮。那指頭強韌有力,是畫馬的手指,食指扣扳機的地方長了繭。他和她同年,三十一歲。
兩人彼此的靜默像手風琴的響聲,時而宏大,時而微小。這首寂靜之歌只有他們倆才聽得到。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的一切,他們之間就是這樣,無聲勝有聲。
古爾瑞茲用托盤端茶過來。他和穆沙沒有客套話,但蒂洛感覺得到兩人關係親密。穆沙叫他「古爾卡克」或「獨活者」(Mout),為他帶來耳藥水。古爾瑞茲點了藥,耳朵裡的冰層就化了。
「他耳朵發炎。他很害怕,怕死了。」穆沙解釋說。
「會痛嗎?一整天下來,他似乎還好。」
「他不是怕痛。他不會痛,他怕被槍打中。他說,他耳朵不好,擔心到檢查哨士兵命令說站住時,他沒聽清楚。有時,他們會放你通行,接著又叫你站住。萬一沒聽到……」
古爾瑞茲感覺到房裡的氣氛有點緊張,為了化解,他剎有其事地跪在地上,臉頰靠在穆沙膝上,耳朵像向日葵一樣朝上,讓穆沙幫他點耳藥水。兩朵向日葵都得到藥水的滋潤後,穆沙用棉花塞住瓶口,把藥水瓶給他。
「小心保管。我不在這裡的時候,你可以請她幫忙,她是我朋友。」
古爾瑞茲很想要這個有塑膠噴嘴的小瓶子。儘管如此,他還是乖乖地把這瓶藥水交給蒂洛,對她燦然一笑。那一刻,這三人就像一家人:熊爸爸、熊媽媽和熊寶貝。
最開心的就是熊寶貝。他準備了五道有肉的佳肴:辣肉球加乳酪、香料羊肉球、奶油醬肉、沙米烤肉漢堡和雞湯。
「這麼多吃的……」蒂洛說。
「牛肉、山羊肉、雞肉、綿羊肉……只有奴隸會這樣狼吞虎嚥。」穆沙盛了一大堆到自己的盤子裡,說:「我們的胃是墳墓。」
蒂洛不敢相信熊寶貝一個人包辦了這頓盛宴。
「我看他一整天都在跟茄子說話,跟貓咪玩耍,沒看到他在煮東西。」
「他肯定在你來之前就準備妥當。他很會煮菜呢!是專業廚師。」
「為什麼他一個人待在這裡?」
「他不是一個人。他的周圍有很多眼睛、耳朵,還有很多顆心。他不能住在村子裡……對他來說,那裡太危險了。古爾卡克是我們所說的獨活者,他活在自己的世界,有他自己的規則。從某個角度來看,有點像你。」穆沙抬起頭來,一臉嚴肅地看著蒂洛。
「你是說,他是個傻子吧。村子裡的一個傻子?」蒂洛也板起臉孔看著他。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一個受到庇佑的人。」
「受什麼庇佑?這種庇佑還真是他媽的變態。」
「因為他有美麗的靈魂。因此,這裡每一個人都很尊敬他。」
穆沙很久沒聽到這樣的謾罵,特別是出自女人之口。那話語像板球,輕輕擊中他緊揪的心,讓他想起他為什麼愛蒂洛,如何愛她,多麼愛她──這回憶已是塵封許久的檔案。
穆沙看著蒂洛擱在桌上的手。他太熟悉這雙手了,甚至勝過自己的手。她還戴著他多年前送她的銀戒指。那時,他還是另一個人。
晚餐過後,他們到門廊抽菸。
一點風也沒有,湖面平靜,船屋安穩,但這寂靜教人不安。
「你愛她嗎?」
「我愛她。我原本就打算告訴你的。」
「為什麼?」
穆沙抽完一根菸,又點了一根。
「不知道,跟名聲有關吧。你的、我的,還有她的。」
「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我不知道。」
「這是父母安排的婚事嗎?」
「不是。」
他坐在她身旁呼吸,覺得自己像門窗緊密的空屋出現一道縫隙,困在裡面的鬼魂得以溜出來。他再度開口,像在對夜空說話,說給山巒聽。
「我在最恐怖的情況下遇見了她……恐怖但很美……只有我們這裡才可能發生這種事。那是一九九一年春天,混亂之年……每天都有槍戰、爆炸,每天都有人死在警察或士兵槍下。武裝分子大搖大擺在街上行走,炫耀手中武器……」
穆沙的話語停在嘴邊,為自己的聲音感到不安。他還不習慣,蒂洛沒鼓勵他說出來。她有點不想聽穆沙即將告訴她的故事,一方面則慶幸他沒說得太仔細。
「無論如何,那年——我在那年遇見她。那時我剛找到一份工作,應該大有可為的,可惜什麼地方都關了。法院、大學、學校……所有的機構都關閉,正常生活完全瓦解……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那種瘋狂……你看到的都可以搶,搶劫、綁架、謀殺層出不窮,還有集體考試作弊,這是最好笑的。在戰亂那一年,突然每個人都想通過學校考試,因為這樣就可以用較低的利率從政府那裡借到錢……我知道有一家三代,爺爺、爸爸和兒子一起去學校參加期末考。想想看,所有的農夫、工人、賣水果的都來考試,只要抄參考手冊,就可得高分。他們連每一頁最下面『請翻下頁』的手指圖示都照抄——還記得那個圖示吧?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我們要嘲笑某人是笨蛋,就會說:『你是不是九○年代拿到畢業證書的?』」
蒂洛知道他故意講些有的沒的,因為他真正要說的難以啟齒,蒂洛聽了想必也不好受。
「你是九一年那批的嗎?」穆沙呵呵笑。他雖嘲笑同鄉,但你可從他的笑聲聽出他是愛他們的。
蒂洛一直愛穆沙這點,他完全屬於一個族群。他愛他們,嘲笑他們,抱怨他們,也會咒罵他們,但無論如何,他都無法與他們分開。也許蒂洛就愛他這點,因為她自己辦不到,她獨來獨往,不屬於任何群體。
很久以前,她認為穆沙跟她是「同一國」的。但自從他們分道揚鑣後,就沒有人跟她是同一國的了。
雖然說到一半,他就在此打住。「進去了,Babajaana,這裡變冷了。」
Babajaana。吾愛,這個親暱的稱呼從他口中自然溜出。她注意到了,但他似乎覺得沒什麼。外面其實不冷,但他們還是進去了。
那晚,在沙欣船屋,交歡少,悲傷多。他們的傷痕有些年代過於久遠,有些太新,而且大不相同,或許太深,乃至無法療癒。
不管如何,穆沙給她的愛安撫了她。她側躺,用手肘把頭撐起來。
「跟我說話……」
「我們不是說了一大堆嗎?」
「那只是前話……」
她用臉頰摩娑他的鬍渣,然後躺下,頭靠在枕頭上。
「你要聽什麼?」
「我什麼都要聽,巨細靡遺地告訴我吧。」
她點了兩根菸。
「我要聽另一個故事……那個既恐怖但很美的故事……愛情故事。告訴我那個真實故事吧。」
蒂洛不知道這句話哪裡觸動了穆沙,他把她抱得更緊。他別過頭去,眼裡有淚光。他緊緊擁抱她,似乎他一放手,就會沒命。穆沙告訴她婕冰小姐的故事,說起她如何要求每一個人稱呼她婕冰小姐,她每晚都要說的床邊故事,還有她種種調皮的事。也告訴她,他和亞里法在斯里納加一家文具店初次相遇的事。
蒂洛和穆沙可以這樣討論第三者,因為他們同時是戀人,也是前度,情同兄弟姊妹,曾經是手足,是同學,是過去的同窗。他們彼此互相信賴,即使曾因此受到傷害,但他們都相信,不管另一個人愛的是誰,那人必然是值得愛的。
她抬起頭來看著他,他握著她的手,親吻她戴的銀戒指。
「很高興看到你還戴著這個戒指。」
「戒指卡住,拿不下來了。」
穆沙微笑。他們靜靜地抽著菸,抽完後,她把菸灰缸拿到窗邊,把菸蒂倒在水裡,和其他菸蒂一起飄浮。她抬頭看著天空,然後回到床上。
「對不起,我亂倒菸蒂。」
穆沙在她額頭上輕輕一吻,之後站起來。
「你要走了?」
「是的。有艘船正在等我,船上有菠菜、香瓜、紅蘿蔔和蓮藕。我將變成以船為家的漢茲族人,在水上市場賣果菜。我將削價競爭,跟家庭主婦討價還價,然後趁亂溜走。」
「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你?」
「我會派一個叫卡蒂嘉的女人來找你。你可以相信她,跟她走。你們將一起旅行。我希望你看到一切,了解一切。你會安全的。」
「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你?」
「比你想的要快,我會找到你的。願神保佑你。」
他就這麼走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