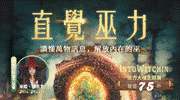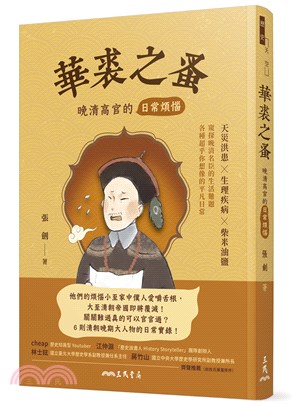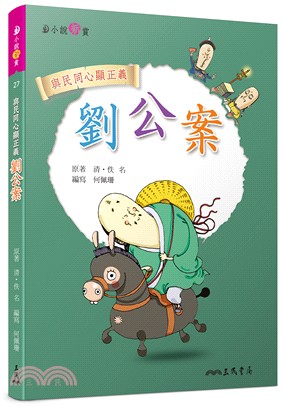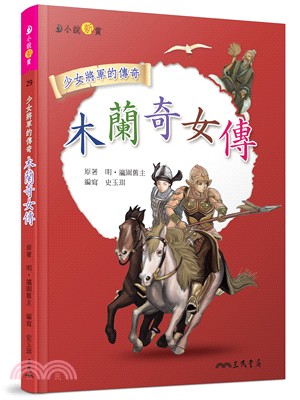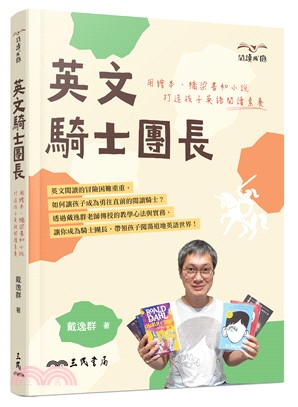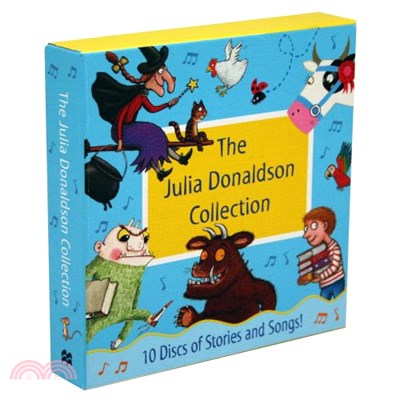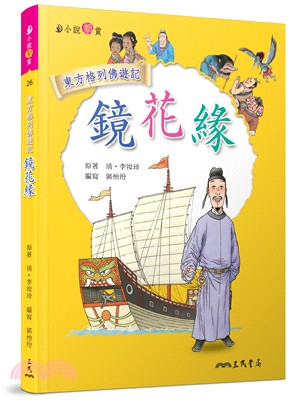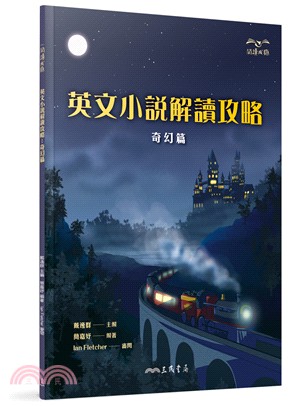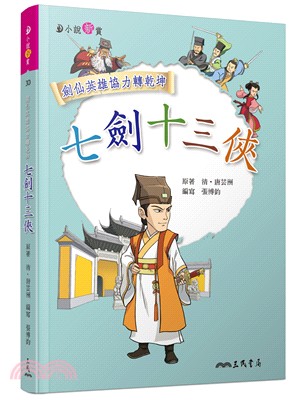商品簡介
「我之所以犯下殺人罪,是因為對於想像力的恐懼」這是村上龍當時正在撰寫的小說〈味噌湯裡〉的主角殺人魔說的話。因為社會真正發生了犯罪事件,而讓村上龍感到「憂鬱」,但他憂鬱的並不是小說與現實的真實性,而是我們真的從現實中失去了想像力了!
在村上龍創作的歷程中,「想像力」是他不顧一切全力捍衛的珍貴財富,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把駭人聽聞的現實事件用文字透析人的存在意義。
追溯日本結束現代化的過程,卻成了找不到個人生存的價值觀遊魂,所有人失去了終極奮鬥的目標。在富裕的國家,女高中生要賣淫,因為寂寞。中年男子買春,因為寂寞。少年殺人,因為寂寞。
過去如果有「心理創傷」很快就會被「要填飽肚子」而忘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回,那麼日本在現代化完成的空檔中所形成的寂寞創傷,要如何復元?
在短短八千多字的敘述,字字句句簡潔提煉出許多問題與反思,小說家不以「人性失序」來譴責少年殺人事件,也不以因為環境問題,教育問題來搪塞。一個創作者,他看到整個日本的進化,成了一個龐大的寂寞國體,在這個充滿寂寞因子的民族裡,持續富裕,持續進步,持續禮貌待人,卻渾然不知自我的持續寂寞……
作者簡介
村上龍
有人說他是暴力和頹廢的解剖大師;
有人盛讚他是繼三島由紀夫之後,最具代表性的當代超級行動派作家;
村上春樹曾經說「他的好奇心像鯊魚一般」;
而村上龍自己說,保持活力與熱情,最重要的是做自己最喜歡的事。
1952年生於長崎縣佐世保市,本名龍之介的村上龍,一直抱持著「不重複用同一個方法」創作作品,第一部小說《接近無限透明的藍》即獲得第19屆群像新人獎、第75屆芥川獎,作品的尺度在當時引起不小的社會騷動,這一位天才作家在喧囂與出類拔萃的資質中,初試啼聲便於日本文壇擁有了屹立不搖的文學地位。
過去曾被宣稱是日本「年輕一代的旗手」,村上龍拒絕「被定位」,活躍於電影、電視、廣告、音樂、旅行的他,永遠敏感觸摸時代核心,將社會脈動化成筆下一部部緊扣人心的奇異作品。
譯者簡介 張智淵
台北人,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課程修畢,從事翻譯十餘年,譯有《愛之國》、《55歲開始的Hello Life》等五十餘本小說,以及《麥肯錫新人邏輯思考5堂課》、《女子的人間關係》等四十餘本實用書等三十餘本實用書,現為專職譯者。
名人/編輯推薦
各方推薦
當人有了自由和資源,卻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為了什麼活著,就陷入生命意義危機。村上龍描述的日本是這樣,其實台灣的近一代也是這樣。
──朱家安\沃草公民學院主編
我們已經不能談集體主義,也不能談極端的個人主義,個人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不論自我的決定是成就自己、存活下去,還是毀了一切,其契機都存在於人際關係。關懷自己,然後據此及於他人,進而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尋獲自我。這或許是村上於此篇散文中,所欲表達的事物。
──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村上龍的散文有著漆黑中緩慢下著雨的濕冷滲透力,他沒有在浪嘆感懷中逃避問題,反倒是把問題提煉得更加清晰—不管你贊成或是反對他的觀點,他都提供了明確的論辯基底。我認為這是種值得提倡的散文態度。這本《寂寞國殺人》篇幅雖然不長,但他的觀察力與筆觸是把鑰匙。或者說,是本製造鑰匙的說明書。
──溫朗東╲鳴人堂專欄作者‧評論人
我非常同意村上龍先生在《寂寞國殺人》對日本社會充斥矛盾、衝突等而暗自引爆重大犯罪事件的反省;反觀我們台灣,媒體重複、幾近病態的報導更加凸顯類似問題,媒體過度渲染台灣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衝突、敵對、仇恨等負面消息,可能也是蓄積社會不滿、不公、不義現況的壓力源,直到「最後的一根稻草」「導火線」出現,終爆發殘酷隨機殺人的重大刑案,如此巨觀的社會對立氛圍,也可能是情境因素密切相關的環境負因,這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與省思的。
──鄧煌發╲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任教授
序
後記
我如今也清楚記得,在寫日後集結成本書的散文時的事情。我接受《文藝春秋》正刊當時的總編輯—平尾隆弘的委託,當時是採取採訪的形式。我一面回答平尾的問題,一面思考、彙整日本社會的狀況,但是閱讀文稿之後,我認為口頭回答還不夠,必須寫成散文。接著,我從神戶的十四歲少年引發的離奇案件開始寫起,如今也清晰記得開始寫時的憂鬱心情,而且那股憂鬱在十幾年後的如今,也沒有消失。
《寂寞國殺人》的主題是對於變化的不適應。明明現代化和高度成長早已結束,但是制度和思考方式依舊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樣。能夠列舉《NHK紅白歌合戰》,作為其文化象徵。《NHK紅白戰合戰》誕生於清晰留下戰爭爪痕的時代,成為國民娛樂。代表日本的男女歌手分成紅白兩隊,比拚歌曲、歌唱實力和受歡迎程度,是一個內容單純的節目,但是療癒因為戰爭而受傷的人民,撫慰了邁向高度成長的勞工家庭。
但即使如今,戰爭造成的傷痛,以及令人驚訝的經濟發展這個國民共通的悲傷和亢奮消失,人們不再團結一心,變成了伴隨差異的多元時代,《NHK紅白歌合戰》還是持續著。在沒有一首暢銷曲是所有階層的人民都會唱的時代,沒有回顧原本的目的,持續進行不自然的「國民娛樂」,象徵著如今的日本社會。
具體而言,適應變化是停止什麼,開始某種新的事情。主要在政治等官方領域,以及媒體,持續著維持既有路線這種愚蠢行為。我在寫《寂寞國殺人》時,下意識地預感到,日本社會今後應該也無法接受、適應改變。我的預感儼然成真,那是憂鬱沒有消失的理由,也是我鮮明地記得撰寫《寂寞國殺人》時的理由。
於橫濱 村上龍
目次
005 寂寞國殺人
068 後記
074 推薦
-生命的意義沒有標準答案╲朱家安
-從他人的眼光尋獲自我╲李茂生
-製造鑰匙的說明書╲溫朗東
-孤寂、毀滅正在無聲無息地啃蝕我們的世界╲鄧煌發
書摘/試閱
電視新聞報導,遭到逮捕的是一名十四歲的國中生,不久之後,住在北海道的妺妹為了另一件事打電話來。形式性地說完事情之後,聊到遭到逮捕的十四歲少年,妹妹身為三個女兒的母親,說:「名嘴左一句社會不好,右一句學校不好,我聽都聽膩了。」妹妹說:「乾脆說十四歲的少年因為預謀殺人的嫌疑,遭到逮捕不就得了。」
我認為,妹妹的意見大部分正確。
少年遭到逮捕的那一晚,我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一位音樂家朋友。
電子郵件的內容是:
「一名十四歲的少年身為神戶須磨區命案的嫌犯,遭到逮捕。或許不只是家庭模式和家庭成員出了問題,搞不好人性開始失序了。」
寄出之後,我對於「人性開始失序」這種說法耿耿於懷。我總覺得哪裡不對。
我懷著憂鬱的心情,在寫《讀賣新聞》晚報的連載稿子。這篇名為〈味噌湯裡〉的長篇小說,旨在描述一個名叫法蘭克的美籍殺人魔來到日本,在日本也殺人無數,最後接觸到不明確的日式善意,但卻沒有洗心革面。當然,法蘭克被設定為在日本是異類,晚報正好連載到他即將向主角—日籍導遊,坦誠訴說自己至今的大半輩子。大致來說,浮現於故事中的是,病態得無可救藥卻又不失真實性的法蘭克,以及毫無美國特有危機意識的日籍導遊之間的鮮明對比。
法蘭克在新宿歌舞伎町展開大屠殺時,正好發生了神戶的案件。法蘭克以細長尖刀割下中年男子耳朵的那一天,被害者的部分遺體被人發現,讀賣新聞文化部收到了大批讀者抗議:「為何在這種時候,刊載這種小說?」話說回來,〈味噌湯裡〉始於一名女高中生遭人肢解的屍體,在新宿歌舞伎町的垃圾場被人發現。屍體的軀幹部分塞進了一張紙條,上頭寫著:「神明不會饒恕。」
十四歲的少年遭到逮捕那一晚,我正在寫連載小說,我之所以憂鬱,倒不是因為擔心這麼一來,抗議或許又會蜂擁而至。抗議對我的工作不會造成絲毫影響。
我之所以憂鬱,是因為我總覺得想像力受限於真實的案件。我心想,法蘭克訴說自己身為殺人魔大半輩子的自白,會因為這起真實的案件,難以光憑想像力而成立。畢竟小說家並非模仿真實案件,而是運用想像力,與現實抗衡。
法蘭克自白的第一句話是:
「我之所以犯下殺人罪,是因為對於想像力的恐懼。」
「想像力令我萌生『我搞不好會殺人』這種想法,這令我極度恐懼。消除這種想像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實際殺人。」
我為了描寫法蘭克的自白而做筆記,覺得他和神戶命案的十四歲少年之間,有相異之處,又有相同之處。而想像力這三個字在我的心中一再反覆出現,我知道我寄給音樂家的電子郵件,內容哪裡錯了。
我再次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
「我之前寫了『人性開始失序』這句身為小說家所不該寫的話。日本士兵在長官的一聲令下,以日本刀砍下外國人腦袋而受到褒獎,不過是短短數十年前的事。人性原本就失序。有史以來,人們以各種事物掩蓋、粉飾這一點。其代表性的事物是家庭和法律,以及理念、藝術與宗教等。我在想的並非它們沒有發揮功能,是什麼讓十四歲的少年去殺人,而是無法阻止他動手的是什麼。」
-------
從他人的眼光尋獲自我
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村上龍在《寂寞國殺人》這短篇散文中,透過神戶少年殺人事件表達了他對日本社會價值轉變過程中缺失的憂慮。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將國家目標訂定在增加財富、讓生活富裕之上,然而在這個代表國家大目標的現代化已經完成了之後,卻沒有辦法將價值觀轉型到個人應「如何正確地去享受這個得來的富裕」。成人們除了面對已經達成的國家目標,感覺到繼續努力也不會有更大的成就外,根本就沒有辦法獲得協助,繼續創造新的價值,所以在整個的人際關係上,日益感到寂寞,也逐漸喪失存在價值。
村上認為這種「大人」,無法引領下一代找尋出自我活存的意義,而年輕的世代在沒有他人的指引下,只能一味地尋求物質上的暫時快感。同時年輕世代的人也因為傳統堅實目標的虛偽以及現實上沒有指引的空泛,而感受到迷惘,進一步發揮其「(錯誤的)想像力」,並導致悲劇。
這個想像力所創造出來的虛幻,到底有何意涵?其實村上並沒有提出任何答案。讀者頂多僅能從其散文的內容中,模糊地察覺到這是一種不願意當透明人,想從他人的眼光中得到自己存在意義的驅力。
然而,物質上一時快感的尋覓與人生價值的空泛,真的會引起殺人事件嗎?大部分的人應該是就這樣墮落下去吧。醉生夢死,不也是一種生活態度的選擇嗎?或許會犯下這種無可挽回的大錯的人,才是真正敏感到覺得自己無法在這個社會孤寂中尋求到自我存在意義的人吧。
村上對於神戶殺人事件中少年A的心境的解讀或許過於粗糙,終究社會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兒童所附加的壓力,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大。姑不論少年A的自傳─《絕歌》是否道盡了其自身的想像,少年A有著性方面的精神疾病,而且最終其也自我解析,認為親密的人際關係會造成自己的痛苦,據此不再尋求清澈、無垢的聖域(終極的人際關係),反倒是將自己與他人間的關係一律斬除,不斷地切割自己與社會間的關係,想將自己隱藏到群眾陰影下,並在這種痛苦(想與群眾接觸,但又不能接觸)下贖罪。比諸神戶少年A事件,村上所描繪的現實毋疑是展現在秋葉原事件中的佳藤智大身上。
成人錯誤地在他身上附加了悲情的時代任務,但是現代化既已成遂,佳藤無法在人際關係中尋覓虛幻的成就,但同時也沒有辦法得到他人的協助,形塑新的自我。因為無法感受到在社群中自己的存在意義,進而透過想像,想毀了一切。換句話說,想自殺,又無能力自殺,結果只好借國家權力來自殺,順便拉幾個人來墊背。這個才是一般人所感受到的寂寞,也才是荒唐憾事的淵藪。
許多人都感受到了傳統人生目標的虛幻,也認知到現在於團體中,於人際關係中尋求自我的困難。這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但是會走上絕路,應該是有一個關鍵性的契機。而這個契機就存在於現存的人際關係中。我們已經不能談集體主義,也不能談極端的個人主義,個人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不論自我的決定是成就自己、存活下去,還是毀了一切,其契機都存在於人際關係。關懷自己,然後據此及於他人,進而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尋獲自我。這或許是村上於此篇散文中,所欲表達的事物。
製造鑰匙的說明書
溫朗東╲鳴人堂專欄作者‧評論人
這是個濕淋淋的傍晚,我正要搭公車前往公司的尾牙。其實我不是正職員工,只是簽了約,固定做點公共議題的節目。之所以會去,可能是因為同事主管熱情的邀約,也可能是我想要感受一些團體感。
大部分的時候,我對團體關係感到抗拒,不願意為了融入團體而削去身上的邊角。卻也偶爾,需要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人,需要確認自己站在人群旁邊。
下班時間的公車有點擠,沒有到密不透氣,但已經超出了舒適的範圍。公車在車陣中走走停停,需要費點力氣才能好好站著。站牌前停車又發車的時候,我聽到一個不陌生的華語腔調。等一下,她說。
車子還是往前開了一點。
等一下,她說。這名看似東南亞看護的中年女子,攙扶著老人緩慢移動,終究趕不及下車。老人撐著助行器,臉上的皺紋深到看不出表情,好像已經無法準確地說話了。女子為了無法扶老人下車而著急。乘客紛紛喊說:「等一下」「有人要下車」。
我們總能在日常中看到一些溫馨、美德或者說是正義感。這令人欣慰。
卻也有些時候,這種「正向的力量」會展現出它的暴力性。對犯罪嫌疑人的追打、對鞭刑的狂熱、對從事登山或是派對受災者的責難⋯⋯我們的團體意識,還停留在現代化之前的素樸狀態。我們的主流道德,跟百年前差異不大—大多數人相信,人的本性是怠惰失序的,唯有透過家庭的教養、法律的約束,才有機會維持「安定社會」的狀態。
如果一個人犯了罪,那就是他的家人沒把他教好,就是法律的刑罰不夠峻;如果一個人受了傷,他必須是個好人、必須從事著主流且有明顯經濟效益的活動,不然那就是「自找的」「不值得同情」。
大部分的人,不相信自己能夠影響政策,也不願意為理解公共議題付出寶貴的精神力。他們相信努力工作,就能獲得對等的回報。沒有被剝削,只有能力不夠。公共生活並不完美,卻不可能也沒必要改善它。
村上龍認為日本的社會問題,來自於「現代化完成後的寂寞」。也就是說,當日本人從二戰後艱困地站起,這過程中雖然辛苦,卻也產生了整個世代的「不這麼賣力,整個國家就會一起下沉」的共感。但隨著日本的現代化,這個共感的時代回不去了。作為社會規訓前哨站的家庭,意義也隨之崩解。
當社會失去了集體的目標,轉向追求個人化的發展時,活在集體制度中的個體,會感受到強烈的不適,會感到孤單並且失去尊嚴。這種氣氛在家庭中由上往下傳遞,拉開家長跟孩子之間的距離。「在家裡聽話,出社會找個大公司,一輩子認真工作」的價值觀在現代化完成後被鬆動了。
長輩覺得孩子越來越不聽話:「我們那個時代那麼苦,還是努力打拚。你過得這麼幸福卻不知感恩。」孩子也覺得長輩不再是仿效的典範:「只會擺架子,道理早就過時了。只會工作不會生活,看起來過得不開心。我以後不想過這樣的人生。」
這些現代化後,經濟發展趨緩、集體目標喪失、人們開始追求個體性的現象,對台灣人來說並不陌生。可以說在某個面向上,台灣也面臨了跟二十年前的日本一樣的問題。
但台灣的處境比日本更複雜艱難。國族議題在整個東亞史裡向來難解。社會的主流聲音傾向於迴避衝突,而不是正視它的艱難而尋求解決。社會氣氛傾向於「租屋心態」,總覺得台灣這所房子不是自己的,拒絕去做大規模的裝修、結構強化甚至於重建。偷工減料的工程、殘害健康的食品、剝削勞工的企業、善於仿效但缺乏研發創新的氣氛⋯⋯我們有種「賺快錢」的集體共識。如果無法長住久安,至少要積累出移民的本錢。
對集體光榮感的需求卻沒有停止。我們渴求各式各樣的「台灣之光」。即使是非主流的事業,只要能獲得世界的肯定,也就能獲得島內的肯定。在獲得世界肯定之前,我們對非主流從業者的支持少之又少。只注重收成,不在乎灌溉。我們始終胸懷著素樸的溫柔與正義感,但多數人並未擁有現代化的、尊重個體自由選擇的道德。對生命的可能性也缺乏想像力。
村上龍的散文有著漆黑中緩慢下著雨的濕冷滲透力,他沒有在浪嘆感懷中逃避問題,反倒是把問題提煉得更加清晰—不管你贊成或是反對他的觀點,他都提供了明確的論辯基底。我認為這是種值得提倡的散文態度。
我想,我們並不缺乏「團體感的需求」或是「公義的本能」。在一道道糾結的關卡面前,缺少的是解答難題的嘗試與典範。這本《寂寞國殺人》篇幅雖然不長,但他的觀察力與筆觸是把鑰匙。或者說,是本製造鑰匙的說明書。
「停下來」的叫喊聲好像沒讓司機聽到,車子繼續往前。我們又叫喊了起來。司機也在擁擠的車上吼說:「我是要靠邊停一點。」大家才安靜下來,看著女子扶著老人下車,各自回到對抗車陣走停的崗位上。
雨還在安靜地下著。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