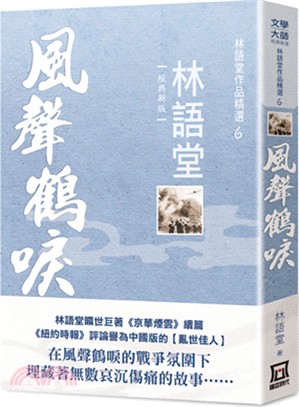庫存:1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6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風聲鶴唳》是林語堂《京華煙雲三部曲》之一
《紐約時報》評論譽為中國版的【亂世佳人】
在風聲鶴唳的戰爭氛圍下,埋藏著無數哀沉傷痛的故事……
在中國抗戰史上,三月二十七日的漢口空襲只是幾千次空襲之一。
但人事卻不像統計那麼簡單。
人生複雜得不可思議。
幾個大阪製造的炸彈,用美國石油飛運,落在武昌的一堆岩石上,卻對丹妮、老彭和伯牙的一生造成極大的轉變……
殘酷的戰火持續著,北平成為淪陷區。
北平王爺園的姚家,已有妻室的伯牙,戀上了一個背景神秘複雜的女子媚玲。然而戰時一切的變化都來得突然,媚玲與伯牙好友老彭為避開日本人的搜索,不得不先行離開北平,穿越戰區,前往上海。路上,他們與一位不知自己懷上的是已逝丈夫的骨肉,抑或日本鬼子的孽種而徬徨不安的女子玉梅結伴同行。
此時,渾然不知狀況的伯牙,赫然得知他愛上的女子,竟是天津某要人捲款潛逃的小妾!誤會、猜疑、難言的過去,橫亙在伯牙和媚玲之間……
戰爭就像大風暴,掃著千百萬落葉般的男女和小孩,把他們颳得四處飄散,讓他們在某一個安全的角落躺一會兒,直到新的風暴又把他們捲入另一旋風裏……這段中國抗戰史和所有偉大運動的歷史一樣,銘刻在這一代的腦海和身心裏。五十年或一百年後,茶樓閒話和老太太聊天時,一定會把幾千個風飄弱絮的故事流傳下去。風中的每一片葉子都是有心靈、有感情、有熱望、有夢想的個人,每個人都一樣重要!
我們此處的任務是追溯戰爭對一個女人的影響,她也是千百萬落葉之一。
「如果你看到路邊殘斷的少年屍體,枯槁的農婦屍身,一個面孔朝下,一個面孔朝上,你會有什麼感覺?他們做了什麼事,應該遇害呢?小孩、婦女、老人、青年,全村的人都無家可歸,在路上流浪,不知道該去哪裏!你對自己說,這些可憐、和平的受難者造了什麼孽?你答不出來。你只好不去想。所以我就回來了。一定要替他們想想辦法。」──書中主角老彭
歷史上最大的移民開始了。
數百萬人由海岸湧到內地,拋棄家園和故鄉,跋山涉水,在難以理解的敵人侵略中逃避大屠殺的命運。
敵人的鞭笞太可怕了。但恐怖的不是戰爭、砲彈、坦克、槍枝和手榴彈。上帝造人以來,人眼從沒見過狂笑的士兵把嬰兒拋入空中,用刺刀接住,而當作一種運動;也沒有遮住眼睛的囚犯站在壕溝邊,被當作殺人教育中刺刀練習的標靶。兩個軍人由蘇州到南京一路追殺中國的潰兵,打賭誰先殺滿一百人……
《紐約時報》評論譽為中國版的【亂世佳人】
在風聲鶴唳的戰爭氛圍下,埋藏著無數哀沉傷痛的故事……
在中國抗戰史上,三月二十七日的漢口空襲只是幾千次空襲之一。
但人事卻不像統計那麼簡單。
人生複雜得不可思議。
幾個大阪製造的炸彈,用美國石油飛運,落在武昌的一堆岩石上,卻對丹妮、老彭和伯牙的一生造成極大的轉變……
殘酷的戰火持續著,北平成為淪陷區。
北平王爺園的姚家,已有妻室的伯牙,戀上了一個背景神秘複雜的女子媚玲。然而戰時一切的變化都來得突然,媚玲與伯牙好友老彭為避開日本人的搜索,不得不先行離開北平,穿越戰區,前往上海。路上,他們與一位不知自己懷上的是已逝丈夫的骨肉,抑或日本鬼子的孽種而徬徨不安的女子玉梅結伴同行。
此時,渾然不知狀況的伯牙,赫然得知他愛上的女子,竟是天津某要人捲款潛逃的小妾!誤會、猜疑、難言的過去,橫亙在伯牙和媚玲之間……
戰爭就像大風暴,掃著千百萬落葉般的男女和小孩,把他們颳得四處飄散,讓他們在某一個安全的角落躺一會兒,直到新的風暴又把他們捲入另一旋風裏……這段中國抗戰史和所有偉大運動的歷史一樣,銘刻在這一代的腦海和身心裏。五十年或一百年後,茶樓閒話和老太太聊天時,一定會把幾千個風飄弱絮的故事流傳下去。風中的每一片葉子都是有心靈、有感情、有熱望、有夢想的個人,每個人都一樣重要!
我們此處的任務是追溯戰爭對一個女人的影響,她也是千百萬落葉之一。
「如果你看到路邊殘斷的少年屍體,枯槁的農婦屍身,一個面孔朝下,一個面孔朝上,你會有什麼感覺?他們做了什麼事,應該遇害呢?小孩、婦女、老人、青年,全村的人都無家可歸,在路上流浪,不知道該去哪裏!你對自己說,這些可憐、和平的受難者造了什麼孽?你答不出來。你只好不去想。所以我就回來了。一定要替他們想想辦法。」──書中主角老彭
歷史上最大的移民開始了。
數百萬人由海岸湧到內地,拋棄家園和故鄉,跋山涉水,在難以理解的敵人侵略中逃避大屠殺的命運。
敵人的鞭笞太可怕了。但恐怖的不是戰爭、砲彈、坦克、槍枝和手榴彈。上帝造人以來,人眼從沒見過狂笑的士兵把嬰兒拋入空中,用刺刀接住,而當作一種運動;也沒有遮住眼睛的囚犯站在壕溝邊,被當作殺人教育中刺刀練習的標靶。兩個軍人由蘇州到南京一路追殺中國的潰兵,打賭誰先殺滿一百人……
作者簡介
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漳州)人。譜名和樂,17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改名玉堂。28歲獲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學位。1923年獲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返國後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兼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講師。開始以語堂為名發表文章。
以人生為課本的林語堂,聲稱自己從老媽子黃媽身上習得中國女教的良好思想,即便是個隨口罵人的蘇州船娘,都能教導他一段人生哲學,品味生活的藝術。他是一位以英文書寫而揚名海外的中國作家,更是具哲學家、文學家、旅遊家以及發明家於一身的近代中國學者。他的作品充滿了赤子之心,代表著他亦莊亦諧的生活態度,也闡釋了他獨特的生活藝術。他以《京華煙雲》三大家族的故事,勾勒出庚子義和團拳亂至抗戰時代四十年來的中國輪廓,並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以《風聲鶴唳》描寫抗日時期的民間百態;以《朱門》及《紅牡丹》描述女子勇於突破舊有傳統;以《武則天》與《蘇東坡傳》重新詮釋一代女皇及才子蘇東坡;以《賴柏英》紀念其初戀情人,並對中西文化差異、男女對感情的看法,有獨到的描寫。以《生活的藝術》、《吾土與吾民》向國外講述中國人的生活哲學,曾高踞美國暢銷書籍排行榜第一名長達一年,為林語堂在西方文壇的成名作,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強力推薦。
以人生為課本的林語堂,聲稱自己從老媽子黃媽身上習得中國女教的良好思想,即便是個隨口罵人的蘇州船娘,都能教導他一段人生哲學,品味生活的藝術。他是一位以英文書寫而揚名海外的中國作家,更是具哲學家、文學家、旅遊家以及發明家於一身的近代中國學者。他的作品充滿了赤子之心,代表著他亦莊亦諧的生活態度,也闡釋了他獨特的生活藝術。他以《京華煙雲》三大家族的故事,勾勒出庚子義和團拳亂至抗戰時代四十年來的中國輪廓,並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以《風聲鶴唳》描寫抗日時期的民間百態;以《朱門》及《紅牡丹》描述女子勇於突破舊有傳統;以《武則天》與《蘇東坡傳》重新詮釋一代女皇及才子蘇東坡;以《賴柏英》紀念其初戀情人,並對中西文化差異、男女對感情的看法,有獨到的描寫。以《生活的藝術》、《吾土與吾民》向國外講述中國人的生活哲學,曾高踞美國暢銷書籍排行榜第一名長達一年,為林語堂在西方文壇的成名作,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強力推薦。
書摘/試閱
下午兩點半,凱男坐在櫃台邊捲頭髮。不知怎麼,她有點氣自己的髮型。問題是她臉很長,輪廓寬,濃眉大眼的。她留短頭髮,整個向後攏。媚玲有一頭披肩的鬈髮,與她圓圓的小臉相得益彰。凱男想把頭髮散在腦後,但是這樣似乎更擴大了她的臉型。如果伯牙肯勸她在耳後弄幾撮鬈髮,效果一定不錯。但是伯牙不在乎,而她又不像羅拉和媚玲懂得女性打扮的祕訣,她簡直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她站在落地鏡前方,顯得比平常更高了。
伯牙回來,還想著媚玲,不知道該怎麼瞭解她。他對太太有一種異樣的罪惡感,以前他由八大胡同的花街柳巷回來,從來就不覺得歉疚,這在他是完全陌生的感覺。他只不過帶媚玲去看祖祠,和她略微調情一番;但是他在心裏已經和她談戀愛了,結果和真正戀愛差不多。他為媚玲著迷,自己也很意外。
「你回來啦,」凱男顯出驚喜的態度。
「是啊,媚玲要看紅玉的畫像。她很感動哩。」
凱男丟下髮梳,走向一張椅子,拿起雜誌卻不打算翻閱。「你以為她真的對我們家那麼感興趣?她不是同宗也不是親戚。」
「我怎麼知道?我想羅拉舅媽對她說過紅玉的故事,她想要親自看看。」
「她到底是誰?」
「我不知道。她是羅拉的客人。我只知道她的姓氏和名字。」
「她要在這兒住多久?」
「我不知道。她一直想去上海。她也許會和我們一塊兒去。」
凱男抬頭看看伯牙。「你以為她真的那麼無依無靠嗎?沒有家的女孩通常會照顧自己。」
「你怎麼知道她沒有家?」
「她有家沒家不關我的事,」凱男壓住了火氣說。「不過一個人好客是有限度的。我們要去南方,等我們走了以後,她可以陪羅拉住在這座園子裏,愛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我不願意和那個女人一起出門。」
伯牙發火了。「你不願意?喔,我願意。」
伯牙是個冷酷的丈夫。凱男不輕易對別人屈服,但是伯牙看不起她,她對他似乎一點力量都沒有。她巴不得他動手打人,她好指責他,但是他始終保持冷靜自如的態度,才真是氣死人呢。
凱男站起身,氣沖沖走出房間。伯牙回來,一心想和顏悅色對待她,因為他覺得歉疚,又相信他不久就自由了。但是凱男的話激怒了他,他說話又顯出唐突、優越的態度來。
凱男的心情就像一般幽怨的少婦,結婚三、四年,才發現自己的婚姻失敗了。她嫁給伯牙是北京大學女友間的一大勝利,當時伯牙和她都在北大念書,伯牙功課並不好。他頭兩年曾在西郊的清華大學就讀,後來改變主意,轉到北大。北大的學生比較窮,年齡也大些,有些人已是鄉下小學的老師或校長,早已結婚生子。伯牙身為「王爺園」園主之孫,年輕英俊,舉止瀟灑,在學生羣中非常突出,被女同學看作白馬王子。凱男是籃球隊員,她優美的身材吸引了伯牙的注意。最後一學期,他們交往一段日子就結婚了。
伯牙看上她,有幾個理由。第一,他這段時期的理想是找一個高大、健康的女人,他自己也很高;第二,凱男功課不好,人卻很愉快、活潑,參加了不少活動;第三,她名叫「凱男」,包含有女性挑戰的意味,這一點頗能吸引伯牙。他需要一個和他並肩工作的妻子;這是他年輕時代理想主義的一部分,凱男在適當的時期來到,正合乎他的理想。最後主要的理由是凱男憑著現實的本能,伯牙追她,她也追伯牙。追逐期間她自由自在,毫不忌諱什麼,伯牙還以為這是她真正現代化的訊號。所以他向她求婚,她就拒絕別人而接受了他。這是很輕鬆的決定,女友們都說她「掘到了金礦」。當時伯牙的祖父姚老爺還在,伯牙問他,他說:「我贊成。她是一個強壯、健康的女子。大屁股代表多兒多女——強壯、健康的小孩。我們的民族必須強身。你看西方國家,他們的女人多徤壯、多自由!」
雖然姚老爺曾說過這一番話,他們卻沒有子女。幾個月後,丈夫和妻子都發現對方脾氣很倔強,通常總是女方讓步的多。
珊瑚姑姑死後,伯牙抽上了日本鴉片,變得瘦削異常。凱男照顧他,有一段時間伯牙對太太又恢復了溫柔的態度。等他恢復健康,他不知不覺又冷淡下來。凱男不懂他為什麼不滿意。她愈是盡力注意衣著打扮,伯牙似乎愈是疏遠她。他朋友很多,常和他們出去,也曾酗酒,愛上一個名伶遏雲。凱男息事寧人,認為這是富家子正常的舉動。他回來總帶著酒味。他是紙牌、麻將、搳拳的能手,風流韻事可不只他告訴太太的那幾樁。他陪老學究們逛風化區;回到家不愛說話,只管讀詩、讀藝術、讀他祖父書齋的珍本,一直讀到凌晨。空閒的時候,他就研究顧炎武的一百二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是受了北京地質測量學會會長的影響,他畢業後曾和那個機構有過兩年的接觸。會長是留英的地質學家,也是傑出的學者,曾研究現代戰爭的武器來消遣。在他的影響下,伯牙變成自封的「戰略家」,也曾研究歷史戰役,但是家境太好,從來不在雜誌上發表著作。他多才多藝,會彈鋼琴,還背誦了不少曲子。
凱男安心過著社交女主人的生活,以宴會來彌補失歡於丈夫的空虛,繼續享受她嫁入姚家所得到的財富。就在這段期間,伯牙變得憤世嫉俗,常常用粗話諷刺她:「你和你那批討厭的珠寶、勢利的朋友!你的女性主義和女權呢?還叫凱男哩!」但是凱男已經不在乎他的辱罵,還繼續在富有的女伴間巧笑揚威。她耿耿於自己的身分,早就為修指甲而放棄了運動,她對美白、軟化肌膚非常感興趣,也做得很成功。只有最近北平淪陷後,她才感到寂寞和無聊。她不再請客,大部分朋友也已離開本市。他們的汽車被馮舅公所謂的「當局」接收了。所以她一直要伯牙帶她到上海去。
但是伯牙很清楚,他為什麼對太太不滿意。他發現他的神仙祖父料錯了。凱男不但沒生下一男半女,而且他那一套壯女人值得娶的理論也完全粉碎了。他發現一個在學校操場吸引他注意的女運動員,並不是理想的妻子和伴侶。她甚至不會燒菜和理家,因為大學教育沒有敎這些課程。伯牙對外表和研究非常拘泥,凱男卻邋邋遢遢,把他的東西亂丟一氣;她對他心愛的骨董和藝術珍藏一點感情都沒有。他結交八大胡同文靜、柔和、優雅的女性,他對女性的理想就開始改觀了。凱男的一身肌肉令他厭煩。他現在相信運動對女人不好,因為她們會失去身心兩方面的女性氣質。運動使女人肌肉硬化,聲音變粗,而且他覺得似乎還鈍化了她的神經末梢,使她腦袋變笨了。身心似乎是一體的,粗劣的身體內不可能存有細緻的心靈。這個信念是他和八大胡同的風塵女人接觸的結果,那邊招待和追求制度首先就要求文雅和秀氣。他對太太有反感,也開始討厭所有高大的女人,喜歡嬌小玲瓏的尤物。
八大胡同往往使夫妻們不必吵架,但也使他們不必和好。伯牙並不原諒自己去那兒,也不找藉口。他只接受一個事實,他和太太合不來。他優雅的本性和教養使他需要理想的女人,需要身心合一,這是他本能的要求。他不像一般好丈夫,願意忍受二流的貨色,只因為已經娶了一個女人,就好好對待她。但是他外面的風流韻事耗光了他對女性的愛戀,必然會污損夫妻愛的清泉——保有精力才能滋養快樂的婚姻。
他對女性的理想一改觀,他太太的性格也變了。凱男接受了新的安排,不願意冒離婚的大險,伯牙也看出她性格全變了,可見她的大學教育全是假的。結婚頭一年,她還假意跟隨他對書本和政治的討論。現在她除了畫報和電影雜誌,什麼都不讀,自己也坦白不害臊,以社交地位、珠寶首飾、有機會對客人炫耀大宅院而自滿。伯牙想起她那女權運動家的名字,不覺大笑,厭惡就化為輕視了。他是一個情緒平衡的人,不愛動粗,於是保持冷淡的譏諷態度,在言語中表現出來,更令人生氣。
他坐立不安,找到了另一項逃避的嗜好。北大的影響深深刻在他身上,和他心智的發展息息相關。他曾經在最好的教授門下修過中國文學。北大的教授中有不少全國知名的學者,還有一座最好的圖書館。但是它那不可名狀的自由氣氛和學術自由更使他心智成長,造成獨有的傾向。有的學生住在宿舍,有的住在公立招待所,過著富裕、多變、自由的生活。學校有許多組織,半文藝半政治,還有不少師生發表作品的刊物。這些雜誌上的討論題目有時候會帶到課堂上。戰爭前幾年,北平生活在日本人不斷侵略的陰影中,有人成立了「察哈爾——河北政治會」的半自治組織,避免日本和中央政府直接衝突,國事自然佔據了學生主要的心思。伯牙晚上喜歡到煤山東邊的馬勝廟圍場去聽激烈的政治討論;那兒有保守派,也有激進派,有人主張立刻宣戰,有人贊成磨時間的政策,有人懷疑蔣介石是否備戰,有人則相信蔣氏是唯一能帶領中國度過艱險的領袖。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歧見更大,而國民黨支持者又分成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兩派。後者被左派人士稱為「法西斯黨」。就在戰前左翼和右翼學生的熱烈討論下,大家仔細權衡「焦土政策」的輕重,伯牙自己的戰略也初步成形。
伯牙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但是他非常佩服蔣介石,隨著戰事的發展,後來簡直變成偶像崇拜了。他的分析能力使他看出幾年後的許多事情,而不看重一般人注意的小節。他蒐集蔣介石的一切資料,觀察、研究、分析他。他由內戰時期開始研究蔣氏的功勳,看他瓦解、壓服、打贏實力雄厚的軍閥,最後全國統一復興,又研究這次抵禦外侮的戰爭。他開始看出老文化和古典傳統對蔣氏的影響。伯牙具有分析和史家的頭腦,他和許多歷史家一樣,對控制整段發展期的英雄人物深深著迷。所以他閱讀蔣氏發表的一切著作,愈研究現階段的當代史,心中愈佩服蔣氏。他沒有參加國民黨,天生不愛行動——也可以說,因為家境的關係根本不需要行動——只把心靈當作一面鏡子,照出他心目中的英雄影像和動作。他的心靈也很藝術化,所以他用自己的註釋來增添觀察的色彩,他心目中的蔣氏幻象(他從來沒見過他)一天天美化、加強,簡直像一座泥土雕像,在大雕刻家的指縫間愈來愈壯、愈來愈美了。
在愛情和政治間,伯牙有許多事可忙,完全和他太太分道揚鑣。他不安的心靈在美女聲色和純理智的政治興趣中來回擺盪,兩者似乎有互補的作用。他喜歡秩序,也見過家中幸福的婚姻,譬如他叔叔阿非和寶芬,還有他姑姑木蘭和莫愁的婚姻都很成功,這些印象老是留在腦海裏。他迷戀媚玲,似乎自己也覺得很不平常,他不知道和自己的太太戀愛是什麼滋味。
今天下午和媚玲見面,他更快活了。他知道自己想正式抛棄太太,實在很自私,不過他的憤世主義又使他相信,自私是人類一切行為真正的動力。
那天晚上他依約去看媚玲,發現她對馮劍很友善,覺得很好玩。他的自尊不容許吃醋,因為她曾經發表過她對馮劍的想法,而且她一邊說話一邊還偷眼看他呢。和大夥兒坐在牌桌上,媚玲不隨便賣弄風情。伯牙碰碰媚玲的雙腳,她沒有反應。但是她總是低頭看牌,慢慢開闔眼皮,靜觀四周的動靜。大家笑,她也笑,彷彿要掩飾心中的念頭。有時候一片死寂,但是在伯牙眼中,每一個動靜似乎都表示他們之間祕密的瞭解。
忠敏堂之行和媚玲的談話已經迷住了伯牙。他決心向她示愛。第二天下午,伯牙又來找媚玲,邀她去散步,也邀羅拉一起去,因為不請她似乎不太好。她同意了,三個人就穿過西邊的月形拱門,來到通往桃園的假山邊。秋風漸涼,桃樹已經落下了葉子。媚玲說她很冷,想回去拿一件毛衣。
「我去替你拿,」羅拉笑笑說。「你們在這邊等我,」她快快活活對伯牙和媚玲說道。
媚玲和伯牙留下來。伯牙看看她,她連忙轉頭,似乎不好意思。她穿著低跟的中國絲拖鞋。她靜靜站著,伯牙激動地走來走去,石道上只聽到他那雙外國皮鞋的響聲。不久一個女僕拿媚玲的毛衣來,說少奶奶有針線活兒要做,叫他們自己去。
「怎麼?」媚玲發窘說。「我們該不該回去?」
「告訴少奶奶,我們馬上回來,」伯牙對女傭說。
他轉向媚玲,幫她穿上毛衣;那是一件深棕色的大針毛衣,只到腰部。媚玲把下襬扣上,在和風中甩甩頭髮。他的眼光使她很不自在。人一緊張,眼睛的斜視加深了,但是並不覺得礙眼,反而替她的面孔平添一種異樣的魔力,正如輕微的南方口音加深了她聲音的魅力。棕色毛衣顏色單純,強調了她的細腰,也襯出她優美的身材。
「好啦?」伯牙無話可說,就轉身扶她經過花園。他一直希望有機會和她單獨談談,他相信羅拉是故意走開的。
「伯牙,」媚玲說,「真奇怪,我在戰亂中認識你……只遺憾我們相見太晚了。」這是新朋友的客套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也許不該說出口,因此就帶有特殊的含義了。
「是啊,可惜我們沒有早一點認識。也許還不太晚吧。」她的眼光和他相迎。
他們步調緩下來。媚玲有點不好意思。開始一路摘花摘葉子。
「你為什麼這樣糟蹋花葉?會折壽的。」
「我就是喜歡嘛。真的會折壽嗎?」媚玲嘻笑著問他。
「不,只是一種說法。你愛摘多少就摘多少,我不在乎。」
幾步外有一棵盛開的大木蘭。媚玲一陣衝動,跑上去折下三、四根小枝,她聽到樹枝劈啪響,不覺大笑。伯牙也跟著笑。
「喏!」她把木蘭花交給他。「這樣會縮短我幾年的壽命?」
「別那樣說——我只是開玩笑罷了。」他引一句名詩說,「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媚玲馬上明白這句影射青春和愛情的名詩,她噘噘嘴。「這些花要怎麼辦?」她說。
「我替你拿著。」
「我想我真的做錯了,」媚玲懊悔地說,面孔也突然變了。「我不該這樣……沒有人教我別這樣……反正女人做的事情沒有一樣是對的。」她悲哀地說。
她嘻笑的心情馬上嚴肅起來。
「你怎麼說這種話呢?」伯牙深感困惑。
「你不覺得這是實話——女孩子做的事情老是不對。」
「為什麼?」
「譬如我和你在這兒約會。我想不太應該,大家永遠責備女方。」
「我不相信,」伯牙熱烈否認。
「你從來沒當過女孩子。」
傷心的表情過去了,她又恢復活潑的態度。他們繼續穿過庭院,進入池塘前的「暗香齋」,然後沿著封閉的迴廊來到有頂的小徑。伯牙指出,渠道由此向南彎,他們其實是站在跨水的有頂橋面上。媚玲在木板上頓腳,為吱吱嘎嘎的響聲而大笑,然後又俯身看水,把舌頭伸出來。她那天真的興致和頑皮的笑容使伯牙覺得很有趣。她的眼睛比平常更亮,笑容更真摯,聲音也更清脆了。伯牙看過她高興,也看過她臉上罩著一層哀思,但是從來沒見過她這麼盡興、這麼快活。
他們走出有頂的橋面,媚玲輕輕跑上土墩的台階。伯牙跟在後面,看她慢慢喘氣,用快樂挑戰的眼神回頭看他。他走上去,抓住她的小手說,「我逮到你了。」
「可是我沒有跑呀。你不是在追我吧?」
「是……」
他還沒說完,她就抽出雙手,跑下土墩的北側。石階很窄,彎來彎去的,她一會兒就不見了。伯牙慢下來,走到一個通往洞穴的岔路口。他止步聆聽,又沿台階走下去。他剛到低處,媚玲突然在他身後的暗道尾端爆出一陣大笑。伯牙一轉身,她又不見了。洞穴的走道只有十一、二呎長,伯牙折回台階上,在另一端等她。他剛走近,突然看見她大叫一聲衝出來,跑上台階,她踉蹌了一下,一隻拖鞋掉下來,但她仍然往前跑,伯牙撿起她的絲拖鞋,把戰利品握在手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向她走去。
她用單腳站著,半倚在岩石上。
「看我沒收了什麼?」伯牙說。
「拜託,」媚玲哀求道,「拖鞋還我!」
「要依我的條件才行。」
「什麼條件?」
「把腳伸出來,我替你穿。」
「喏!」媚玲伸出玉足,修長、豐潤,曲線美極了。伯牙跪下來抓住她的小腳。他正為她穿鞋,附近有腳步聲走過。「噓!」媚玲蹲下來,「如果有人看到我們,」她低聲說。她帶著戲謔的笑容往下滑,背部挨著石塊。他們就用這樣的怪姿勢躲在那兒,最後終於聽到腳步聲越過土墩。媚玲的小臉上有一種天真恐懼和好玩的表情。等腳步聲聽不見了,伯牙說:「坐在地上吧。挺乾淨的。你今天為什麼這樣高興?」
她把頭靠向身後的岩石,午後的陽光完全映在她臉上。
「我一生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她說。
「我很高興。」
「愛、笑、生活。人一生中真正快樂的時候並不多。」
剛才伯牙完全被媚玲的笑聲迷住了。現在他的臉上一霎時又顯出懶洋洋的神色,掩蓋了輕浮的表情。
「媚玲,你會不會對我好?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的女孩子。你身上具有我所不瞭解的氣質。你為什麼說女孩子做的事情永遠不對勁?」
「不是嗎?」
「我不知道。你憑什麼說這種話呢?」
「憑我的經驗,」媚玲慢慢答道。
「什麼經驗?」
她抬起密密的睫毛,眼睛以挑戰的神色和伯牙相望。然後她慢慢垂下雙眼,一句話也不說。午後的陽光映在她脆弱的小臉上,使她顯得又清新又溫柔。
「媚玲,談談你自己吧,我希望更瞭解你。」
「談我自己?」
「你是誰?你的父母呢?」
「喔,我是媚玲,我姓崔。」
「我知道。我是指你的身世。」
「沒什麼好說的,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別那麼神祕嘛。你父母是誰?」
「我沒有父母。」
「你怎麼認識羅拉的?她是你的同學嗎?」
「不,我沒有上過學校,只上過很短的時間。」
「你不告訴我,羅拉也不肯告訴我。我把我家的一切都告訴你了,你卻不肯談談你家。」
「我的身分對你很重要嗎?」
「是的……很重要。媚玲,我們能不能做好朋友——真心的朋友?」
媚玲把頭轉向矮花樹,手指一片片拔著乾葉子。伯牙還在等她答腔,她頭髮向後一甩,似乎專心理順她的髮絲,這個動作使她胸部的曲線更明顯了。
這個迷人的姿態使伯牙更想知道這位女人的神祕。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小鳥偶然輕唱幾聲。她臉上一片紅潮,帶著困惑和發窘的神色。她迅速抬眼看他說,「嗯,怎麼?」露出一個女人打算被愛的微笑。「你想要知道我哪一點呢?」
「我一定要多瞭解你一些。你有父母。你總不是像仙女一般由天上掉下來的吧?」
媚玲折下一根乾樹枝。她聲音有點發抖,臉上也有遲疑的表情,似乎要吐露一項祕密。「喔,我父親是一個軍國主義者;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崔是母姓。」
「你是在講神話故事?」
「隨你怎麼想,我父親拋棄了我母親,我們在貧苦中度日。我十七歲那年母親死了……」她突然打住。
「咦,說下去嘛。」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父親被人暗殺了。」
「暗殺!誰幹的?」
「我不能告訴你。你會知道太多。很多人都恨他。他殺過不少人。」
「你對你父親好像沒什麼感情。」
「一點都沒有。我怎麼會有呢?……夠了吧?」
「不,再多談一點。」
「後來我孤單單一個人,有人愛上了我……喔,我的遭遇太怪了。你不會相信的。」
「我相信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孤單單一個人,一定會有某些奇遇。」
「伯牙兄,你覺得我吃過苦嗎?」
「看你不覺得,你今年幾歲?」
「二十五,」媚玲停下來。盯著他,然後又說,「我如果告訴你,我結過婚呢?」
伯牙停了半晌才說,「那你就更迷人了。有人要娶你,我毫不意外。」
「他說要送我上學,又天天來看我,最後我被學校開除了。你有興趣嗎?」
「說下去。然後呢?」
「然後就是地獄!他父親介入我們之間。我嫁給他,並沒有得到他父親的認可。我們起初很快樂——頭幾個月……他是一家輪船公司買辦的兒子,他父親發現了我的身分。他恨我父親,他說我父親曾經把他關入監牢,他花了十萬元才保住性命。他要報復,就移恨在我身上。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孤零零的少女又能怎麼辦呢?老頭子沒有一絲悲憫。我是傻瓜,如此而已。」
「是他暗殺你父親的?」
「不,另有別人,我父親樹敵很多。」
「兇手有沒有公開審判?」
「沒有。大家的言論都支持他。你不相信我父親替日本人做事吧?」
「但是你沒有說你父親是誰呀。」
「對,我想我發昏了……反正對我也無關緊要。一切都很複雜。我從來不關心我父親。我母親也恨他,但是我的公公卻把一切推到我身上,叫我『漢奸種』。我該不該為我父親辯護呢?他起先氣他兒子,因為他恨我,然後他又改變了心意,叫他兒子把我帶入他家,否則要脫離父子關係,我就去了,一連幾周被關在我丈夫家裏。我相信他的目的是逼我自殺。我見不到我丈夫,常常哭累了朦朧睡去……後來他母親可憐我,對老頭子說,『她父親不對,反正現在人也死了。何必責備他的女兒呢?你若不喜歡蓮兒,最好把她送走,叫我們兒子再娶一個……』」
「蓮兒?」
「喔,那是我的名字,我後來改名了。」
「那個老太太真好心。」
「是的,她是一個佛教徒。她對丈夫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還是少造陰孽——神明知道的。」
「後來呢?」
「他父親叫他再娶,他就照辦了。我算什麼——非馬非牛,非妻非妾……這位新婦嫉妒心很強。那時我對丈夫早已失去了敬意,也不在乎了。不過老天總會留給人一條生路。有一天我婆婆傍晚進入我房間,遞給我一個紙包說,『蓮兒,自從你來到我們家,我心裏沒有一刻平安過。男人心狠,他們不肯聽我的話,把這個帶著,裏面有六百元,自己去想辦法。離開本市到別的地方去,我來和他們父子商量,叫他們別再打擾你……』」
媚玲的聲音突然打住了,然後一面扭手絹一面慢慢說,「世界上也有好心人,要不是那位老太太,我說不定早就死嘍,」年輕的面孔上露出平靜的表情,一切受苦的痕跡都消失了。
伯牙看她,顯得很意外。「看到你,絕對想不到你有這些遭遇。後來你怎麼辦呢?」
「我說得夠多了,別再問下去。」
伯牙靠近些,抓住她的小手,她也捏了捏他,使他整個神經都興奮起來。
「別告訴別人,」媚玲說。
伯牙又靠近些,兩個人手緊握在一起。媚玲很沉默。伯牙撫弄她的頭髮,她也不說話,眼睛俯視地面,胸前微微起伏。他雙手捧住她的小臉,捧到他面前,發現她眼睛充滿狂熱的激情。
「媚玲,這就是我們的愛情,」他說。
他親吻她,她也激動地報以熱吻。他覺得她的一雙手臂環著他,暖烘烘的。
「我一直渴望愛情,」他說,「這份愛情。婚姻內或婚姻外倒無關緊要。就算是一種婚姻吧。兩個人身心結合的婚姻——你知道我的意思……兩者似乎融合在一起,你分不出哪個是哪個了,就是這樣。」
媚玲一動也不動。
「你不說話?」
「我只是快樂……什麼也不想說。」
「我也很快樂。」
他們就這樣躺了兩三分鐘,「蓮兒……蓮兒——我喜歡那個名字。」
「別這樣叫我。」
「為什麼?」
「這是我童年的名字……不然——你可以叫我,但只能在沒有人的時候偷叫。這個名字讓我想起母親。」
「好的,蓮兒,」他們一起大笑。
「我該叫你什麼?」媚玲問道。
「就叫我伯牙好了,我的俊丫頭。」
「怎麼這樣叫我?」
「我不知道,我們北平就這樣叫法。」伯牙等於叫她「我美麗的女奴」。
「喔!」媚玲天真地點點頭,這是她某一方面單純的表現,「為什麼同一個名字可以罵人,也可以表示親密?」
「是這樣的: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可以叫他任何名字,聽起來還是很甜蜜。」
「為什麼我們說俊丫頭,而不說美丫頭呢?」
「美就是美。俊卻代表『美麗和聰明』。我不知道丫頭為什麼會比太太漂亮機靈,但事實往往如此。」
一聽到「太太」這個名詞,媚玲臉色變了,她沉默下來。
「你在想什麼?」伯牙問她。
媚玲悲哀的開口了。「社會永遠站在妻子這一邊。一個聰明的女人永遠不對勁。但是女人聰明又有什麼辦法呢?社會從來不責備男人一次次有艷遇。逢場作戲嘛,他們說。但是女孩子鬧戀愛呢?婚姻對女人比男人重要,因為她一生都受婚事影響。她甚至不能尋樂。假如她婚姻不幸——她又有什麼辦法?她要裝聾作啞,忍受下去嗎?如果她有了艷史,社會將要說什麼?假如有人發現我們在這裏——誰知道是你追我,還是我追你?但是大家會責備我,不會責備你,於是我又錯了。」
她說出這一段意外的見解,伯牙眼睛一直盯著她,心裏並沒有絲毫不高興。
「你為什麼說『又錯了』?你以前錯過嗎?」
「這不關你的事,」媚玲說。「就連那次結婚,大家都說是我勾引那個年輕人,不是他勾引我,他家人怪我嫁入父親的仇家——那是『無恥』——不然就像他父親,說我是漢奸種。老頭子常說,他家前世欠了我家一筆債。你相不相信一個人的罪孽會還報到子女身上?」
「我不知道。我想,我們體內流著先人的血液,我們都為先人的行為而受苦。」
伯牙抓起媚玲的小手,在午後的陽光下欣賞她臂上精巧的血管和若隱若現的汗毛。
「我真心愛你,媚玲。」伯牙說。
「蓮兒,」媚玲高高興興糾正說。「你以前曾經這樣愛過一個女人嗎?」
「沒有。總覺得缺了些什麼。漂亮的人很多,但是不久就看厭了。你知道,我總覺得漂亮的女人天生愚蠢,聰明的女子外貌又令人討厭,太聰明,太骨感,太不舒服。所以男人才魂不守舍。」
媚玲快活地聽他這一套女人論。
「我是心智愚蠢還是外貌令人討厭,哪一種?」她咯咯笑著說。
「媚玲——蓮兒——我是在談其他的女人,」伯牙大笑。
「我不要人恭維。請你坦白告訴我。你喜歡我哪一點?我希望這是永遠的,永遠不變。我要盡一切力量來討你歡心。告訴我,我算哪一種——愚蠢還是討厭?」
「我沒法分析你。你似乎好年輕、好清新,但是你卻有這麼多遭遇,你當然不討人厭。」
「謝謝你。」
「你也不可能愚蠢。」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聰明的女子為什麼討人厭嗎?」
「為什麼?」媚玲說。
「聰明的女子話太多了。她鋒芒畢露,使男人很不舒服。」
「做一個討人歡心的女孩子一定很難,」媚玲彷彿嚇壞了。
「但是這兒有一個完美的女性,她的智慧外露同時又內斂,那就是你。你令人興奮,也令人靜下來。」
「喔,伯牙,」媚玲喃喃說。「我不能讓你失望,我真怕了。你很難侍候嗎?我要盡一切力量來討你歡心。如果你要我,我願意做你的情婦。」
伯牙看看她賞心悅目的面孔,「你覺得一個女人可以同時做妻子和情婦嗎?」
「怎麼?」
「妻子就是妻子,她握有一張結婚證書,她受到保護,所以什麼都不在乎。她是某某太太,就像凱男吧,社交上她是姚太太,她只對這件事感興趣。情婦可沒有這種便利,因此她會盡力討男人歡心,你能想像一個太太像情婦般做人、愛人和被愛嗎?你聽過一句諺語:『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著』。」
媚玲大笑,「我要記住這句話。我是不是在偷你?」
「你知道我不愛凱男,她比你更明白這一點。」
「我是不是真的把你偷來了……?如果是,我很幸福,你打算怎麼辦?」
「你知道她一直想去上海。」
「能不能帶我去?她會不會反對?」
「她不是已經反對你留在這兒了嗎?那不是問題。」
「那又是什麼呢?」
「她要回娘家,這樣最好。她很不幸,也很不快活,我一直對她冷冷的。」
媚玲專心聽著,想像自己和他住一起。「你肯不肯帶我去?只要有了你,是偷是妾是妻,我都無所謂。」
伯牙滿面愁色,沒有答腔。
「伯牙,我自由自在,孑然一身,我願意跟你到任何地方,只要愛你就成了。」
「真的?現在是戰時,你知道。」
「我願意跟你到天涯海角。」
「真的?」伯牙盯著她,彷彿想瞭解這個女孩子,她的身世還半掩在神祕中呢。「把你的一切告訴我。」
「為什麼我必須說出一切呢?」
「因為我愛你。」
「我告訴你的已經比任何人要多了。」
媚玲臉上也現出一片陰霾。
「喔,好吧。我想這樣就夠了,我愛的就是你這個人。」
媚玲說,「你告訴女傭,我們馬上回去。現在太陽都快下山了。」
伯牙扶她起來。「來吧!」他說。
他扶她穿過果園,回到她的院落,手臂環在她腰上,還沒到月形拱門,兩人慢慢逛著,他覺得一切來得太突然了,但是他知道自己今天是存心來向她求愛的,不免為輕鬆的勝利而滿面通紅。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到我們這邊來?」媚玲現在已非常平靜。
「我要來,只為了看看你,不過我們若想一起到南方去,一定要表現得自然些。」
「真像作賊。喔,我喜歡偷你的感覺,沒有人知道,」她貼近他耳語說。
「你要不要讓羅拉知道?」伯牙問她。
「不,」媚玲堅定地說。
「你不笨嘛,」伯牙說道。
「我不告訴任何人,還沒到上海之前,這件事必須完全保密,我們之間的祕密。」
伯牙當時當地就覺得想偷媚玲了。「偷不著」會更刺激。他喜歡這樣,於是
伯牙回來,還想著媚玲,不知道該怎麼瞭解她。他對太太有一種異樣的罪惡感,以前他由八大胡同的花街柳巷回來,從來就不覺得歉疚,這在他是完全陌生的感覺。他只不過帶媚玲去看祖祠,和她略微調情一番;但是他在心裏已經和她談戀愛了,結果和真正戀愛差不多。他為媚玲著迷,自己也很意外。
「你回來啦,」凱男顯出驚喜的態度。
「是啊,媚玲要看紅玉的畫像。她很感動哩。」
凱男丟下髮梳,走向一張椅子,拿起雜誌卻不打算翻閱。「你以為她真的對我們家那麼感興趣?她不是同宗也不是親戚。」
「我怎麼知道?我想羅拉舅媽對她說過紅玉的故事,她想要親自看看。」
「她到底是誰?」
「我不知道。她是羅拉的客人。我只知道她的姓氏和名字。」
「她要在這兒住多久?」
「我不知道。她一直想去上海。她也許會和我們一塊兒去。」
凱男抬頭看看伯牙。「你以為她真的那麼無依無靠嗎?沒有家的女孩通常會照顧自己。」
「你怎麼知道她沒有家?」
「她有家沒家不關我的事,」凱男壓住了火氣說。「不過一個人好客是有限度的。我們要去南方,等我們走了以後,她可以陪羅拉住在這座園子裏,愛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我不願意和那個女人一起出門。」
伯牙發火了。「你不願意?喔,我願意。」
伯牙是個冷酷的丈夫。凱男不輕易對別人屈服,但是伯牙看不起她,她對他似乎一點力量都沒有。她巴不得他動手打人,她好指責他,但是他始終保持冷靜自如的態度,才真是氣死人呢。
凱男站起身,氣沖沖走出房間。伯牙回來,一心想和顏悅色對待她,因為他覺得歉疚,又相信他不久就自由了。但是凱男的話激怒了他,他說話又顯出唐突、優越的態度來。
凱男的心情就像一般幽怨的少婦,結婚三、四年,才發現自己的婚姻失敗了。她嫁給伯牙是北京大學女友間的一大勝利,當時伯牙和她都在北大念書,伯牙功課並不好。他頭兩年曾在西郊的清華大學就讀,後來改變主意,轉到北大。北大的學生比較窮,年齡也大些,有些人已是鄉下小學的老師或校長,早已結婚生子。伯牙身為「王爺園」園主之孫,年輕英俊,舉止瀟灑,在學生羣中非常突出,被女同學看作白馬王子。凱男是籃球隊員,她優美的身材吸引了伯牙的注意。最後一學期,他們交往一段日子就結婚了。
伯牙看上她,有幾個理由。第一,他這段時期的理想是找一個高大、健康的女人,他自己也很高;第二,凱男功課不好,人卻很愉快、活潑,參加了不少活動;第三,她名叫「凱男」,包含有女性挑戰的意味,這一點頗能吸引伯牙。他需要一個和他並肩工作的妻子;這是他年輕時代理想主義的一部分,凱男在適當的時期來到,正合乎他的理想。最後主要的理由是凱男憑著現實的本能,伯牙追她,她也追伯牙。追逐期間她自由自在,毫不忌諱什麼,伯牙還以為這是她真正現代化的訊號。所以他向她求婚,她就拒絕別人而接受了他。這是很輕鬆的決定,女友們都說她「掘到了金礦」。當時伯牙的祖父姚老爺還在,伯牙問他,他說:「我贊成。她是一個強壯、健康的女子。大屁股代表多兒多女——強壯、健康的小孩。我們的民族必須強身。你看西方國家,他們的女人多徤壯、多自由!」
雖然姚老爺曾說過這一番話,他們卻沒有子女。幾個月後,丈夫和妻子都發現對方脾氣很倔強,通常總是女方讓步的多。
珊瑚姑姑死後,伯牙抽上了日本鴉片,變得瘦削異常。凱男照顧他,有一段時間伯牙對太太又恢復了溫柔的態度。等他恢復健康,他不知不覺又冷淡下來。凱男不懂他為什麼不滿意。她愈是盡力注意衣著打扮,伯牙似乎愈是疏遠她。他朋友很多,常和他們出去,也曾酗酒,愛上一個名伶遏雲。凱男息事寧人,認為這是富家子正常的舉動。他回來總帶著酒味。他是紙牌、麻將、搳拳的能手,風流韻事可不只他告訴太太的那幾樁。他陪老學究們逛風化區;回到家不愛說話,只管讀詩、讀藝術、讀他祖父書齋的珍本,一直讀到凌晨。空閒的時候,他就研究顧炎武的一百二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是受了北京地質測量學會會長的影響,他畢業後曾和那個機構有過兩年的接觸。會長是留英的地質學家,也是傑出的學者,曾研究現代戰爭的武器來消遣。在他的影響下,伯牙變成自封的「戰略家」,也曾研究歷史戰役,但是家境太好,從來不在雜誌上發表著作。他多才多藝,會彈鋼琴,還背誦了不少曲子。
凱男安心過著社交女主人的生活,以宴會來彌補失歡於丈夫的空虛,繼續享受她嫁入姚家所得到的財富。就在這段期間,伯牙變得憤世嫉俗,常常用粗話諷刺她:「你和你那批討厭的珠寶、勢利的朋友!你的女性主義和女權呢?還叫凱男哩!」但是凱男已經不在乎他的辱罵,還繼續在富有的女伴間巧笑揚威。她耿耿於自己的身分,早就為修指甲而放棄了運動,她對美白、軟化肌膚非常感興趣,也做得很成功。只有最近北平淪陷後,她才感到寂寞和無聊。她不再請客,大部分朋友也已離開本市。他們的汽車被馮舅公所謂的「當局」接收了。所以她一直要伯牙帶她到上海去。
但是伯牙很清楚,他為什麼對太太不滿意。他發現他的神仙祖父料錯了。凱男不但沒生下一男半女,而且他那一套壯女人值得娶的理論也完全粉碎了。他發現一個在學校操場吸引他注意的女運動員,並不是理想的妻子和伴侶。她甚至不會燒菜和理家,因為大學教育沒有敎這些課程。伯牙對外表和研究非常拘泥,凱男卻邋邋遢遢,把他的東西亂丟一氣;她對他心愛的骨董和藝術珍藏一點感情都沒有。他結交八大胡同文靜、柔和、優雅的女性,他對女性的理想就開始改觀了。凱男的一身肌肉令他厭煩。他現在相信運動對女人不好,因為她們會失去身心兩方面的女性氣質。運動使女人肌肉硬化,聲音變粗,而且他覺得似乎還鈍化了她的神經末梢,使她腦袋變笨了。身心似乎是一體的,粗劣的身體內不可能存有細緻的心靈。這個信念是他和八大胡同的風塵女人接觸的結果,那邊招待和追求制度首先就要求文雅和秀氣。他對太太有反感,也開始討厭所有高大的女人,喜歡嬌小玲瓏的尤物。
八大胡同往往使夫妻們不必吵架,但也使他們不必和好。伯牙並不原諒自己去那兒,也不找藉口。他只接受一個事實,他和太太合不來。他優雅的本性和教養使他需要理想的女人,需要身心合一,這是他本能的要求。他不像一般好丈夫,願意忍受二流的貨色,只因為已經娶了一個女人,就好好對待她。但是他外面的風流韻事耗光了他對女性的愛戀,必然會污損夫妻愛的清泉——保有精力才能滋養快樂的婚姻。
他對女性的理想一改觀,他太太的性格也變了。凱男接受了新的安排,不願意冒離婚的大險,伯牙也看出她性格全變了,可見她的大學教育全是假的。結婚頭一年,她還假意跟隨他對書本和政治的討論。現在她除了畫報和電影雜誌,什麼都不讀,自己也坦白不害臊,以社交地位、珠寶首飾、有機會對客人炫耀大宅院而自滿。伯牙想起她那女權運動家的名字,不覺大笑,厭惡就化為輕視了。他是一個情緒平衡的人,不愛動粗,於是保持冷淡的譏諷態度,在言語中表現出來,更令人生氣。
他坐立不安,找到了另一項逃避的嗜好。北大的影響深深刻在他身上,和他心智的發展息息相關。他曾經在最好的教授門下修過中國文學。北大的教授中有不少全國知名的學者,還有一座最好的圖書館。但是它那不可名狀的自由氣氛和學術自由更使他心智成長,造成獨有的傾向。有的學生住在宿舍,有的住在公立招待所,過著富裕、多變、自由的生活。學校有許多組織,半文藝半政治,還有不少師生發表作品的刊物。這些雜誌上的討論題目有時候會帶到課堂上。戰爭前幾年,北平生活在日本人不斷侵略的陰影中,有人成立了「察哈爾——河北政治會」的半自治組織,避免日本和中央政府直接衝突,國事自然佔據了學生主要的心思。伯牙晚上喜歡到煤山東邊的馬勝廟圍場去聽激烈的政治討論;那兒有保守派,也有激進派,有人主張立刻宣戰,有人贊成磨時間的政策,有人懷疑蔣介石是否備戰,有人則相信蔣氏是唯一能帶領中國度過艱險的領袖。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歧見更大,而國民黨支持者又分成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兩派。後者被左派人士稱為「法西斯黨」。就在戰前左翼和右翼學生的熱烈討論下,大家仔細權衡「焦土政策」的輕重,伯牙自己的戰略也初步成形。
伯牙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但是他非常佩服蔣介石,隨著戰事的發展,後來簡直變成偶像崇拜了。他的分析能力使他看出幾年後的許多事情,而不看重一般人注意的小節。他蒐集蔣介石的一切資料,觀察、研究、分析他。他由內戰時期開始研究蔣氏的功勳,看他瓦解、壓服、打贏實力雄厚的軍閥,最後全國統一復興,又研究這次抵禦外侮的戰爭。他開始看出老文化和古典傳統對蔣氏的影響。伯牙具有分析和史家的頭腦,他和許多歷史家一樣,對控制整段發展期的英雄人物深深著迷。所以他閱讀蔣氏發表的一切著作,愈研究現階段的當代史,心中愈佩服蔣氏。他沒有參加國民黨,天生不愛行動——也可以說,因為家境的關係根本不需要行動——只把心靈當作一面鏡子,照出他心目中的英雄影像和動作。他的心靈也很藝術化,所以他用自己的註釋來增添觀察的色彩,他心目中的蔣氏幻象(他從來沒見過他)一天天美化、加強,簡直像一座泥土雕像,在大雕刻家的指縫間愈來愈壯、愈來愈美了。
在愛情和政治間,伯牙有許多事可忙,完全和他太太分道揚鑣。他不安的心靈在美女聲色和純理智的政治興趣中來回擺盪,兩者似乎有互補的作用。他喜歡秩序,也見過家中幸福的婚姻,譬如他叔叔阿非和寶芬,還有他姑姑木蘭和莫愁的婚姻都很成功,這些印象老是留在腦海裏。他迷戀媚玲,似乎自己也覺得很不平常,他不知道和自己的太太戀愛是什麼滋味。
今天下午和媚玲見面,他更快活了。他知道自己想正式抛棄太太,實在很自私,不過他的憤世主義又使他相信,自私是人類一切行為真正的動力。
那天晚上他依約去看媚玲,發現她對馮劍很友善,覺得很好玩。他的自尊不容許吃醋,因為她曾經發表過她對馮劍的想法,而且她一邊說話一邊還偷眼看他呢。和大夥兒坐在牌桌上,媚玲不隨便賣弄風情。伯牙碰碰媚玲的雙腳,她沒有反應。但是她總是低頭看牌,慢慢開闔眼皮,靜觀四周的動靜。大家笑,她也笑,彷彿要掩飾心中的念頭。有時候一片死寂,但是在伯牙眼中,每一個動靜似乎都表示他們之間祕密的瞭解。
忠敏堂之行和媚玲的談話已經迷住了伯牙。他決心向她示愛。第二天下午,伯牙又來找媚玲,邀她去散步,也邀羅拉一起去,因為不請她似乎不太好。她同意了,三個人就穿過西邊的月形拱門,來到通往桃園的假山邊。秋風漸涼,桃樹已經落下了葉子。媚玲說她很冷,想回去拿一件毛衣。
「我去替你拿,」羅拉笑笑說。「你們在這邊等我,」她快快活活對伯牙和媚玲說道。
媚玲和伯牙留下來。伯牙看看她,她連忙轉頭,似乎不好意思。她穿著低跟的中國絲拖鞋。她靜靜站著,伯牙激動地走來走去,石道上只聽到他那雙外國皮鞋的響聲。不久一個女僕拿媚玲的毛衣來,說少奶奶有針線活兒要做,叫他們自己去。
「怎麼?」媚玲發窘說。「我們該不該回去?」
「告訴少奶奶,我們馬上回來,」伯牙對女傭說。
他轉向媚玲,幫她穿上毛衣;那是一件深棕色的大針毛衣,只到腰部。媚玲把下襬扣上,在和風中甩甩頭髮。他的眼光使她很不自在。人一緊張,眼睛的斜視加深了,但是並不覺得礙眼,反而替她的面孔平添一種異樣的魔力,正如輕微的南方口音加深了她聲音的魅力。棕色毛衣顏色單純,強調了她的細腰,也襯出她優美的身材。
「好啦?」伯牙無話可說,就轉身扶她經過花園。他一直希望有機會和她單獨談談,他相信羅拉是故意走開的。
「伯牙,」媚玲說,「真奇怪,我在戰亂中認識你……只遺憾我們相見太晚了。」這是新朋友的客套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也許不該說出口,因此就帶有特殊的含義了。
「是啊,可惜我們沒有早一點認識。也許還不太晚吧。」她的眼光和他相迎。
他們步調緩下來。媚玲有點不好意思。開始一路摘花摘葉子。
「你為什麼這樣糟蹋花葉?會折壽的。」
「我就是喜歡嘛。真的會折壽嗎?」媚玲嘻笑著問他。
「不,只是一種說法。你愛摘多少就摘多少,我不在乎。」
幾步外有一棵盛開的大木蘭。媚玲一陣衝動,跑上去折下三、四根小枝,她聽到樹枝劈啪響,不覺大笑。伯牙也跟著笑。
「喏!」她把木蘭花交給他。「這樣會縮短我幾年的壽命?」
「別那樣說——我只是開玩笑罷了。」他引一句名詩說,「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媚玲馬上明白這句影射青春和愛情的名詩,她噘噘嘴。「這些花要怎麼辦?」她說。
「我替你拿著。」
「我想我真的做錯了,」媚玲懊悔地說,面孔也突然變了。「我不該這樣……沒有人教我別這樣……反正女人做的事情沒有一樣是對的。」她悲哀地說。
她嘻笑的心情馬上嚴肅起來。
「你怎麼說這種話呢?」伯牙深感困惑。
「你不覺得這是實話——女孩子做的事情老是不對。」
「為什麼?」
「譬如我和你在這兒約會。我想不太應該,大家永遠責備女方。」
「我不相信,」伯牙熱烈否認。
「你從來沒當過女孩子。」
傷心的表情過去了,她又恢復活潑的態度。他們繼續穿過庭院,進入池塘前的「暗香齋」,然後沿著封閉的迴廊來到有頂的小徑。伯牙指出,渠道由此向南彎,他們其實是站在跨水的有頂橋面上。媚玲在木板上頓腳,為吱吱嘎嘎的響聲而大笑,然後又俯身看水,把舌頭伸出來。她那天真的興致和頑皮的笑容使伯牙覺得很有趣。她的眼睛比平常更亮,笑容更真摯,聲音也更清脆了。伯牙看過她高興,也看過她臉上罩著一層哀思,但是從來沒見過她這麼盡興、這麼快活。
他們走出有頂的橋面,媚玲輕輕跑上土墩的台階。伯牙跟在後面,看她慢慢喘氣,用快樂挑戰的眼神回頭看他。他走上去,抓住她的小手說,「我逮到你了。」
「可是我沒有跑呀。你不是在追我吧?」
「是……」
他還沒說完,她就抽出雙手,跑下土墩的北側。石階很窄,彎來彎去的,她一會兒就不見了。伯牙慢下來,走到一個通往洞穴的岔路口。他止步聆聽,又沿台階走下去。他剛到低處,媚玲突然在他身後的暗道尾端爆出一陣大笑。伯牙一轉身,她又不見了。洞穴的走道只有十一、二呎長,伯牙折回台階上,在另一端等她。他剛走近,突然看見她大叫一聲衝出來,跑上台階,她踉蹌了一下,一隻拖鞋掉下來,但她仍然往前跑,伯牙撿起她的絲拖鞋,把戰利品握在手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向她走去。
她用單腳站著,半倚在岩石上。
「看我沒收了什麼?」伯牙說。
「拜託,」媚玲哀求道,「拖鞋還我!」
「要依我的條件才行。」
「什麼條件?」
「把腳伸出來,我替你穿。」
「喏!」媚玲伸出玉足,修長、豐潤,曲線美極了。伯牙跪下來抓住她的小腳。他正為她穿鞋,附近有腳步聲走過。「噓!」媚玲蹲下來,「如果有人看到我們,」她低聲說。她帶著戲謔的笑容往下滑,背部挨著石塊。他們就用這樣的怪姿勢躲在那兒,最後終於聽到腳步聲越過土墩。媚玲的小臉上有一種天真恐懼和好玩的表情。等腳步聲聽不見了,伯牙說:「坐在地上吧。挺乾淨的。你今天為什麼這樣高興?」
她把頭靠向身後的岩石,午後的陽光完全映在她臉上。
「我一生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她說。
「我很高興。」
「愛、笑、生活。人一生中真正快樂的時候並不多。」
剛才伯牙完全被媚玲的笑聲迷住了。現在他的臉上一霎時又顯出懶洋洋的神色,掩蓋了輕浮的表情。
「媚玲,你會不會對我好?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的女孩子。你身上具有我所不瞭解的氣質。你為什麼說女孩子做的事情永遠不對勁?」
「不是嗎?」
「我不知道。你憑什麼說這種話呢?」
「憑我的經驗,」媚玲慢慢答道。
「什麼經驗?」
她抬起密密的睫毛,眼睛以挑戰的神色和伯牙相望。然後她慢慢垂下雙眼,一句話也不說。午後的陽光映在她脆弱的小臉上,使她顯得又清新又溫柔。
「媚玲,談談你自己吧,我希望更瞭解你。」
「談我自己?」
「你是誰?你的父母呢?」
「喔,我是媚玲,我姓崔。」
「我知道。我是指你的身世。」
「沒什麼好說的,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別那麼神祕嘛。你父母是誰?」
「我沒有父母。」
「你怎麼認識羅拉的?她是你的同學嗎?」
「不,我沒有上過學校,只上過很短的時間。」
「你不告訴我,羅拉也不肯告訴我。我把我家的一切都告訴你了,你卻不肯談談你家。」
「我的身分對你很重要嗎?」
「是的……很重要。媚玲,我們能不能做好朋友——真心的朋友?」
媚玲把頭轉向矮花樹,手指一片片拔著乾葉子。伯牙還在等她答腔,她頭髮向後一甩,似乎專心理順她的髮絲,這個動作使她胸部的曲線更明顯了。
這個迷人的姿態使伯牙更想知道這位女人的神祕。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小鳥偶然輕唱幾聲。她臉上一片紅潮,帶著困惑和發窘的神色。她迅速抬眼看他說,「嗯,怎麼?」露出一個女人打算被愛的微笑。「你想要知道我哪一點呢?」
「我一定要多瞭解你一些。你有父母。你總不是像仙女一般由天上掉下來的吧?」
媚玲折下一根乾樹枝。她聲音有點發抖,臉上也有遲疑的表情,似乎要吐露一項祕密。「喔,我父親是一個軍國主義者;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崔是母姓。」
「你是在講神話故事?」
「隨你怎麼想,我父親拋棄了我母親,我們在貧苦中度日。我十七歲那年母親死了……」她突然打住。
「咦,說下去嘛。」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父親被人暗殺了。」
「暗殺!誰幹的?」
「我不能告訴你。你會知道太多。很多人都恨他。他殺過不少人。」
「你對你父親好像沒什麼感情。」
「一點都沒有。我怎麼會有呢?……夠了吧?」
「不,再多談一點。」
「後來我孤單單一個人,有人愛上了我……喔,我的遭遇太怪了。你不會相信的。」
「我相信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孤單單一個人,一定會有某些奇遇。」
「伯牙兄,你覺得我吃過苦嗎?」
「看你不覺得,你今年幾歲?」
「二十五,」媚玲停下來。盯著他,然後又說,「我如果告訴你,我結過婚呢?」
伯牙停了半晌才說,「那你就更迷人了。有人要娶你,我毫不意外。」
「他說要送我上學,又天天來看我,最後我被學校開除了。你有興趣嗎?」
「說下去。然後呢?」
「然後就是地獄!他父親介入我們之間。我嫁給他,並沒有得到他父親的認可。我們起初很快樂——頭幾個月……他是一家輪船公司買辦的兒子,他父親發現了我的身分。他恨我父親,他說我父親曾經把他關入監牢,他花了十萬元才保住性命。他要報復,就移恨在我身上。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孤零零的少女又能怎麼辦呢?老頭子沒有一絲悲憫。我是傻瓜,如此而已。」
「是他暗殺你父親的?」
「不,另有別人,我父親樹敵很多。」
「兇手有沒有公開審判?」
「沒有。大家的言論都支持他。你不相信我父親替日本人做事吧?」
「但是你沒有說你父親是誰呀。」
「對,我想我發昏了……反正對我也無關緊要。一切都很複雜。我從來不關心我父親。我母親也恨他,但是我的公公卻把一切推到我身上,叫我『漢奸種』。我該不該為我父親辯護呢?他起先氣他兒子,因為他恨我,然後他又改變了心意,叫他兒子把我帶入他家,否則要脫離父子關係,我就去了,一連幾周被關在我丈夫家裏。我相信他的目的是逼我自殺。我見不到我丈夫,常常哭累了朦朧睡去……後來他母親可憐我,對老頭子說,『她父親不對,反正現在人也死了。何必責備他的女兒呢?你若不喜歡蓮兒,最好把她送走,叫我們兒子再娶一個……』」
「蓮兒?」
「喔,那是我的名字,我後來改名了。」
「那個老太太真好心。」
「是的,她是一個佛教徒。她對丈夫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還是少造陰孽——神明知道的。」
「後來呢?」
「他父親叫他再娶,他就照辦了。我算什麼——非馬非牛,非妻非妾……這位新婦嫉妒心很強。那時我對丈夫早已失去了敬意,也不在乎了。不過老天總會留給人一條生路。有一天我婆婆傍晚進入我房間,遞給我一個紙包說,『蓮兒,自從你來到我們家,我心裏沒有一刻平安過。男人心狠,他們不肯聽我的話,把這個帶著,裏面有六百元,自己去想辦法。離開本市到別的地方去,我來和他們父子商量,叫他們別再打擾你……』」
媚玲的聲音突然打住了,然後一面扭手絹一面慢慢說,「世界上也有好心人,要不是那位老太太,我說不定早就死嘍,」年輕的面孔上露出平靜的表情,一切受苦的痕跡都消失了。
伯牙看她,顯得很意外。「看到你,絕對想不到你有這些遭遇。後來你怎麼辦呢?」
「我說得夠多了,別再問下去。」
伯牙靠近些,抓住她的小手,她也捏了捏他,使他整個神經都興奮起來。
「別告訴別人,」媚玲說。
伯牙又靠近些,兩個人手緊握在一起。媚玲很沉默。伯牙撫弄她的頭髮,她也不說話,眼睛俯視地面,胸前微微起伏。他雙手捧住她的小臉,捧到他面前,發現她眼睛充滿狂熱的激情。
「媚玲,這就是我們的愛情,」他說。
他親吻她,她也激動地報以熱吻。他覺得她的一雙手臂環著他,暖烘烘的。
「我一直渴望愛情,」他說,「這份愛情。婚姻內或婚姻外倒無關緊要。就算是一種婚姻吧。兩個人身心結合的婚姻——你知道我的意思……兩者似乎融合在一起,你分不出哪個是哪個了,就是這樣。」
媚玲一動也不動。
「你不說話?」
「我只是快樂……什麼也不想說。」
「我也很快樂。」
他們就這樣躺了兩三分鐘,「蓮兒……蓮兒——我喜歡那個名字。」
「別這樣叫我。」
「為什麼?」
「這是我童年的名字……不然——你可以叫我,但只能在沒有人的時候偷叫。這個名字讓我想起母親。」
「好的,蓮兒,」他們一起大笑。
「我該叫你什麼?」媚玲問道。
「就叫我伯牙好了,我的俊丫頭。」
「怎麼這樣叫我?」
「我不知道,我們北平就這樣叫法。」伯牙等於叫她「我美麗的女奴」。
「喔!」媚玲天真地點點頭,這是她某一方面單純的表現,「為什麼同一個名字可以罵人,也可以表示親密?」
「是這樣的: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可以叫他任何名字,聽起來還是很甜蜜。」
「為什麼我們說俊丫頭,而不說美丫頭呢?」
「美就是美。俊卻代表『美麗和聰明』。我不知道丫頭為什麼會比太太漂亮機靈,但事實往往如此。」
一聽到「太太」這個名詞,媚玲臉色變了,她沉默下來。
「你在想什麼?」伯牙問她。
媚玲悲哀的開口了。「社會永遠站在妻子這一邊。一個聰明的女人永遠不對勁。但是女人聰明又有什麼辦法呢?社會從來不責備男人一次次有艷遇。逢場作戲嘛,他們說。但是女孩子鬧戀愛呢?婚姻對女人比男人重要,因為她一生都受婚事影響。她甚至不能尋樂。假如她婚姻不幸——她又有什麼辦法?她要裝聾作啞,忍受下去嗎?如果她有了艷史,社會將要說什麼?假如有人發現我們在這裏——誰知道是你追我,還是我追你?但是大家會責備我,不會責備你,於是我又錯了。」
她說出這一段意外的見解,伯牙眼睛一直盯著她,心裏並沒有絲毫不高興。
「你為什麼說『又錯了』?你以前錯過嗎?」
「這不關你的事,」媚玲說。「就連那次結婚,大家都說是我勾引那個年輕人,不是他勾引我,他家人怪我嫁入父親的仇家——那是『無恥』——不然就像他父親,說我是漢奸種。老頭子常說,他家前世欠了我家一筆債。你相不相信一個人的罪孽會還報到子女身上?」
「我不知道。我想,我們體內流著先人的血液,我們都為先人的行為而受苦。」
伯牙抓起媚玲的小手,在午後的陽光下欣賞她臂上精巧的血管和若隱若現的汗毛。
「我真心愛你,媚玲。」伯牙說。
「蓮兒,」媚玲高高興興糾正說。「你以前曾經這樣愛過一個女人嗎?」
「沒有。總覺得缺了些什麼。漂亮的人很多,但是不久就看厭了。你知道,我總覺得漂亮的女人天生愚蠢,聰明的女子外貌又令人討厭,太聰明,太骨感,太不舒服。所以男人才魂不守舍。」
媚玲快活地聽他這一套女人論。
「我是心智愚蠢還是外貌令人討厭,哪一種?」她咯咯笑著說。
「媚玲——蓮兒——我是在談其他的女人,」伯牙大笑。
「我不要人恭維。請你坦白告訴我。你喜歡我哪一點?我希望這是永遠的,永遠不變。我要盡一切力量來討你歡心。告訴我,我算哪一種——愚蠢還是討厭?」
「我沒法分析你。你似乎好年輕、好清新,但是你卻有這麼多遭遇,你當然不討人厭。」
「謝謝你。」
「你也不可能愚蠢。」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聰明的女子為什麼討人厭嗎?」
「為什麼?」媚玲說。
「聰明的女子話太多了。她鋒芒畢露,使男人很不舒服。」
「做一個討人歡心的女孩子一定很難,」媚玲彷彿嚇壞了。
「但是這兒有一個完美的女性,她的智慧外露同時又內斂,那就是你。你令人興奮,也令人靜下來。」
「喔,伯牙,」媚玲喃喃說。「我不能讓你失望,我真怕了。你很難侍候嗎?我要盡一切力量來討你歡心。如果你要我,我願意做你的情婦。」
伯牙看看她賞心悅目的面孔,「你覺得一個女人可以同時做妻子和情婦嗎?」
「怎麼?」
「妻子就是妻子,她握有一張結婚證書,她受到保護,所以什麼都不在乎。她是某某太太,就像凱男吧,社交上她是姚太太,她只對這件事感興趣。情婦可沒有這種便利,因此她會盡力討男人歡心,你能想像一個太太像情婦般做人、愛人和被愛嗎?你聽過一句諺語:『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著』。」
媚玲大笑,「我要記住這句話。我是不是在偷你?」
「你知道我不愛凱男,她比你更明白這一點。」
「我是不是真的把你偷來了……?如果是,我很幸福,你打算怎麼辦?」
「你知道她一直想去上海。」
「能不能帶我去?她會不會反對?」
「她不是已經反對你留在這兒了嗎?那不是問題。」
「那又是什麼呢?」
「她要回娘家,這樣最好。她很不幸,也很不快活,我一直對她冷冷的。」
媚玲專心聽著,想像自己和他住一起。「你肯不肯帶我去?只要有了你,是偷是妾是妻,我都無所謂。」
伯牙滿面愁色,沒有答腔。
「伯牙,我自由自在,孑然一身,我願意跟你到任何地方,只要愛你就成了。」
「真的?現在是戰時,你知道。」
「我願意跟你到天涯海角。」
「真的?」伯牙盯著她,彷彿想瞭解這個女孩子,她的身世還半掩在神祕中呢。「把你的一切告訴我。」
「為什麼我必須說出一切呢?」
「因為我愛你。」
「我告訴你的已經比任何人要多了。」
媚玲臉上也現出一片陰霾。
「喔,好吧。我想這樣就夠了,我愛的就是你這個人。」
媚玲說,「你告訴女傭,我們馬上回去。現在太陽都快下山了。」
伯牙扶她起來。「來吧!」他說。
他扶她穿過果園,回到她的院落,手臂環在她腰上,還沒到月形拱門,兩人慢慢逛著,他覺得一切來得太突然了,但是他知道自己今天是存心來向她求愛的,不免為輕鬆的勝利而滿面通紅。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到我們這邊來?」媚玲現在已非常平靜。
「我要來,只為了看看你,不過我們若想一起到南方去,一定要表現得自然些。」
「真像作賊。喔,我喜歡偷你的感覺,沒有人知道,」她貼近他耳語說。
「你要不要讓羅拉知道?」伯牙問她。
「不,」媚玲堅定地說。
「你不笨嘛,」伯牙說道。
「我不告訴任何人,還沒到上海之前,這件事必須完全保密,我們之間的祕密。」
伯牙當時當地就覺得想偷媚玲了。「偷不著」會更刺激。他喜歡這樣,於是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