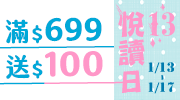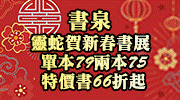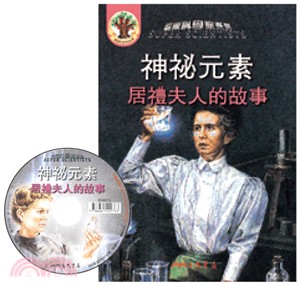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特色
假死逃離皇宮的小麟子回來了!回復女兒身,藉著秀女選拔再次回到了有楚鄒在的深深皇宮。她回來的原因除了報仇,還有為了多年未見的故人們……
晉江名家[玉胡蘆]細細述說紫禁城內的宮闈秘事,文辭細膩,讀來令人如歷其境、如聞其人。
內容
天家緣薄,情意難深,縱然後宮三千的天子無數,他楚鄒,偏要做這紫禁城唯娶一人的皇帝!
四皇子復起,原以為皇儲之路已無波折,卻因著錦秀為先皇淑女的身分大明,陸梨竟成了皇族血脈,再與楚鄒便是亂常違綱,就又硬生生地將二人分開,斷了孽緣。
被派去浙江辦差的楚鄒並不知曉,他思念萬分的女子在遙遠的皇宮裡面臨著什麼樣的困境與磨難。紅花落不下堅強的孩子,陸梨便悄悄地在冷宮中孕育長大,如同當年的小尿炕子,嘻嘻哈哈地不知人間憂愁。
楚鄒回宮,那早該懸了梁的錦秀竟還是在宮中呼風喚雨,捏著優柔的棋子小九,一心想連同戚世忠將他與陸梨盡除。
驚天大案接連降臨皇宮,一向被冷落的皇子暗地裡蓄勢待發,密謀著推翻自己的父皇。早知此事的楚鄒將會如何應對?他與陸梨,在最終又能獲得什麼樣的結局?
作者簡介
《作者》
玉胡蘆
作者玉胡蘆,久居福建東南隅,射手座,喜好隨性,思緒天馬行空。私認為寫文是一種修煉,同時亦希望筆下故事得到你的喜愛,看完若能留於心中,則為榮幸。本篇《太子妃花事記》源於一次故宮之行,在完結後又動筆了現言《非正式戀愛》,不同風格,期待閱讀。
《繪者》
殼中蠍
暱稱是蠍子~喜歡畫畫、看劇和玩遊戲的認證宅女,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夠睡到自然醒。做為一個半路出家插畫師,喜歡各種畫風並樂於嘗試,目前古風作品比較多。如果你喜歡我的畫,我會感到很榮幸,你也可以通過上述社交網站找到我的更多作品( =?ω?= )。
目次
第二章 腌臢齷齪
第三章 寶兒天佑
第四章 險象環生
第五章 驚天貪案
第六章 東窗事發
第七章 元宵宮變
第八章 東宮大火
第九章 天災人禍
第十章 大奕之危
書摘/試閱
八月的紫禁城,碧瓦飛甍,雕梁畫棟,金黃的老樹襯著朱漆的宮牆,秋意甚濃。戊戌日那天,完顏霍領著二子、三子與九郡主完顏嬌從東華門進宮朝貢。
算算其五子完顏辰被俘,已過去了四個多月。完顏霍此次入漢,除卻用三座城換回兒子外,還贈了一把漢代失傳的名劍赤霄,又把愛女帶在身邊似有意聯姻,可見還是誠意滿滿。
大奕王朝建國近兩百載,國運淵遠流長,那天的場面很是浩瀚。奉天殿前文武百官著藍的紅的大襟斜領朝服,沿須彌座往三十九級台階層層而下。兩排錦衣衛在東華門下開道,領著完顏霍一行過了內金水橋。按說仗原本是老二打贏的,但這樣的風光皇帝卻沒有讓楚鄺出面,卻叫了楚鄒與完顏霍對接。
萬里蒼穹之下風輕雲淡,楚鄒頭戴金漆九旒冕,那日的禮服甚為考究,原本普通皇子因著青衣,他卻穿了更上一階的玄色,刺繡亦不與普通皇子一般規制,但又比東宮皇儲少了一點飾物。如此這般看在朝臣們眼裡,想來離東宮復位已是不遠了。
完顏霍五十上下年紀,兩個兒子亦都是土生土長的謖真血種,不比被俘虜的漢妃之子完顏辰清朗。十五歲的九郡主完顏嬌乃是正室嫡出,身條兒高且勻稱,臉上也像能望見白雲似的。楚鄒那時站在奉天門場院裡迎候,完顏嬌乍然與他一對視,不禁怔然恍了神,又認真地再看了一眼。
楚鄒卻是沒注意她的,只按制伸手把路一引,然後垂袖上了漢白玉台階。
微風拂著他的袍服輕揚,小九楚鄎站在左翼門廊簷下,不禁看得滿目崇拜,對身旁的陸梨感慨道:「他看起來終於是好了。」
陸梨開解道:「殿下好起來,小九爺應當感到高興才是。大公主和壽昌王出宮建府了,唯有殿下陪著小九爺在宮裡,殿下好了,便可在前頭為小九爺擋風遮雨,這是血緣親情斬不斷的。」
楚鄎聽了便想到錦秀和她肚子裡的那個小團。已是三十有一的錦秀孕起來似乎特別辛苦,近日肚子也像掩不住了,忽然地微隆起來。宮人們都在等著看她的蕭條,楚鄎每日過去請安,錦秀卻兀自與他笑顏以對。她若是臉上露出些愁苦倒還好,證明她有過掙扎;她這般溫柔親善,倒叫他覺著她對那團小肉的費心掩護。
楚鄎默了一默,便吁口氣,「我聽懂了。我前陣子夢見我母后了,我看見她的臉竟不覺得陌生,像從前就看見過很多回似的。她對我笑得慈祥,說真抱歉沒能夠好好抱過我。」忽而頓了一下,又繼續道:「我從此不會繼續怪我四哥,我會一直站在他身後,他是我母后生下的親四哥。」
體仁閣裡一前一後走出兩條人影。十四歲的宋玉柔著一襲玉白纏枝底團領袍,髮束脂玉冠,打扮得萬般臭美又俊俏,邊走邊道:「宋玉妍說她大後兒也得去。」
剛從廟裡回來那幾天叫著「我姐」,這才沒過多久又開始直呼名字了。
年已三十八九的宋岩依舊高健而挺拔,將一襲正一品仙鶴補服襯得威武翩翩,聽了話應道:「去哪兒,馬場嗎?不是病得厲害?就在家養著。」
「那她這回準得一哭二鬧三上吊了。」宋玉柔不禁頹唐地吐舌頭。那姐兒哪裡有病,她是痴迷二皇子痴迷成癲,最近聽說老二要和戶部尚書左瑛的千金議親,這便急著天天在家裡鬧進宮。
眼看著太子就要起來了,年歲亦相當,皇帝又已暗示過這門親事,哪容她胡鬧。宋岩也不理會,只繼續往前走路。
宋玉柔愁巴巴地跟著走了兩步,忽而桃花眼一抬,便瞥見側對面廊簷下站著的陸梨。
清風拂著她丹櫻色的裙襬,那長開的模樣總叫他看得心生疑惑,宋玉柔不禁吶吶地慢下步子。
宋岩等不到兒子隨上來,順著視線側頭一看,便也看到陸梨了。晌午的光景之下,那姑娘十四五歲,眼睛也像掬著水兒,在風中遠眺著,朦朧如絕世美人。宋岩只這般看一眼,便生生地記起來久遠的另一張臉。
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幕,有個女人站在親屬探視的玄武門下,那個女人應該叫朴玉兒。
此刻看著陸梨那張相似的臉龐,不禁又想起朴玉兒當年遺下的卑賤小太監,一時只覺得心底有些膈,宋岩便冷漠地收回眼神。
宋玉柔發現爹爹也在看陸梨,跟上幾步問道:「聽說她與我同歲,父親可是也覺得她像一個人,像那個小太監?」說著把手勾上宋岩的袖子,一種自然而然的父子親情。
宋岩卻是料不到兒子也會往這方面想的,他的這個兒子說來還有一樁故事。
當年楚妙生下的龍鳳胎男嬰將要不行,皇覺寺因為常年得宋家的香火,便偷偷托人帶口信說寺廟裡撿著個孩子。夫婦倆沒兩日便瞞著家中老人上了山,真該是一個續了一個的緣,那男嬰就在到廟門口的時候嚥了氣。方丈把宋玉柔抱出來,廟裡的山水將他養得白嫩可人,正在吐舌頭,竟和那個死去的孩子長得差不離,一看到楚妙,就伸出粉嫩的小手輕輕撫她的臉。楚妙當即眼淚就下來了。
親生子後來叫方丈化了,骨灰就收在廟中佛像的背後,盼望得著佛經的仁慈普渡,早早能夠托生投胎,亦為著能夠保佑宋玉柔替他續命。
抱回來的宋玉柔,也像是天生該與宋岩做父子似的,連午睡時伸出的小胳膊、仰臥的姿勢都學著宋岩一模一樣,長大後飲食上的一些喜好更是如出一轍。彼時夫婦倆以才做完法事不便開門見人為由,把宋玉柔藏著養了半個月,後便替了那個短命的男嬰。
楚妙因著孩子與丈夫有緣,在悲痛之餘總算得了些安慰,因此對待宋玉柔便越發視若性命,好像要把對死去那個的愛與虧欠雙重地加諸在他身上。是以當年小麟子死後,宋玉柔因為中了晦氣去了半條命,那幾年楚妙便狠狠心把他送去廟裡,只因想要得著那「死去的」庇佑,以保他能續命活著。
只是宋岩卻料不到時間過去了這麼多年,兒子竟依舊對那小太監念念不忘,明明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太卑賤的命,他不喜從自己兒子口中提及,便冷沉地道一句:「提那些過去的做什麼。不是說沒見過北蠻韃子嗎,這就帶你去瞧瞧。」說著又把陸梨看一眼,一道袍服翩翩上了台階。
◎
景仁宮裡熏香清幽,沈嬤嬤勾頭跪在地上,邊上站兩個威風的嬤嬤,張貴妃雍容華貴地端坐在上頭,拖長著嗓音道:「沈妙翠,這可是本宮第二次召妳了,妳說是不說,全看妳自個兒的造化。妳本名叫沈妙華,十四年前本就該死的人,可巧妳在宮裡的堂姐沈妙翠,生得與妳一般微胖不起眼,因為在浣衣局落了癆病將死,便生生把妳藏了三月,病死後叫妳替了她名字活著。倒是差事卑微,竟無誰瞧得出來。
「本宮查雖查了,但也不打算為難。只這裡問妳一件舊事,當年妳在東筒子闈院裡伺候著一個高麗進貢的淑女,那淑女名字有冊卷可查,叫作朴玉兒。那院裡與她同住的還有一個,卻生生被劃空了去,本宮這就問問妳,她叫的是什麼名字?」
沈嬤嬤料不到,時間過去了十多年,張貴妃卻忽然尋出自己問起這檔子事,因怕把陸梨牽扯出來,只是默著不敢應話。
張貴妃勾唇冷笑,又繼續道:「妳可以選擇不說,本宮既能問妳這句話,那便是心中早已有了數,妳說與不說,都不妨礙本宮把她鬥倒。但妳該知道的是,她也在暗中找妳,妳今日說了,本宮尚能發發慈悲保妳一命,否則等到她把妳揪出來,那時下場妳自己想像。
「聽說妳老家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算算年紀也都是膝下兒孫滿堂了,最年長的大孫子歲初剛當爹,說起來也是四世同堂。妳進宮前的同郡相好李大壯,當初為了救妳被折斷了條腿,娶了門妻難產死了,幾十年也都一直鰥著。妳今兒若說出名字,回頭給本宮在皇帝爺跟前做個證,事成後本宮賞臉放妳出宮回鄉,妳還有二三十年好活。妳不說,本宮也一樣有法子鬥倒她,可妳還有多少日子活頭?是進是退,妳自己掂量。」
她故意不提及朴玉兒生孩子一事,只把矛頭指向錦秀,話說著便端起邊上的銀耳羹,輕輕舀了一小勺。
沈嬤嬤果然聽得眉間一顫,到底那宮外頭久遠的煙火人情漫上來。她默了很長時間,最後便雙手伏地不再抬起。張貴妃揮揮手,命身旁一干人等摒退出去。
秋天吳爸爸易火燥睡不安穩,陸梨去御膳房給吳全有送了一摞配好的茶包,回來一腳跨進咸安門,就看見沈嬤嬤抱著包袱從廊簷下迎面過來,她就好奇地住了步子,「嬤嬤這是要去哪兒?」
清脆的少女嗓音,聽得沈嬤嬤詫然抬頭,略微現出一絲慌亂。但想想又還好,畢竟宮裡無人曉得朴玉兒還生了個女嬰,早點把錦秀鬥倒了還安妥。
她便鞠了鞠腰,答道:「原是老奴該辭行了,四年前貴妃娘娘把老奴安排在殿下身邊,如今殿下在前朝風光無限,身邊又有了姑娘照應,老奴的差事也就無甚要緊,這就還回去歸貴妃安置。」她故意這麼說,把自己說得好像是張貴妃的人,是不願勞陸梨再惦記。
陸梨前些天原看見過沈嬤嬤從外頭悄悄回來,當年楚鄒跟前的人皆是張貴妃安排的,此刻聽了倒也不覺得意外,她便不好挽留,只說道:「嬤嬤人好著哩,這些年殿下禁在這廢宮裡,身子又時時不好,得虧嬤嬤悉心照拂。殿下是個記著好的善心人,將來嬤嬤若遇了難處,便托口信回來。」
沈嬤嬤睇了眼陸梨的手,又想起當年她剛出生時洗澡的模樣,小手嫩嫩的,攥得像個小肉球,哭得哀哀。她便忽然下了一個決定,停步喚道:「姑娘留步。」
陸梨回過頭來,「耶?嬤嬤可是有話要說?」翦水般的眸瞳裡噙著笑。
沈嬤嬤說:「姑娘可曉得一個叫朴玉兒的女人?」
「朴?」陸梨聽得一愣,這樣的姓倒不像是漢人的姓,便搖搖頭,滿臉茫然。
沈嬤嬤看得有些不忍,但還是慢聲道:「姑娘不曉得也正常。這話說來就長了,十八年前高麗進貢兩百多名淑女,朴玉兒就是裡頭頂頂美貌的,也是紅顏該遭人嫉,萬禧把她安排在東筒子盡頭的闈院裡,一住就住了四年,老奴也就在她身邊伺候了四年。剛來的時候與妳一般大年紀,連漢話都說得磕磕巴巴。可惜啊是個傻女人,那個男人的身家地位可是她能高攀得上的?生下一對龍鳳胎,身子還沒捂暖呢,最後自個兒就先死了。姑娘別誤會,這不是在影射姑娘,太子爺對妳是情真意切的,姑娘他日必貴不可言。我這麼說,是因為看見姑娘的臉想起她來了,日後姑娘若記著這個名字,想知道她長什麼模樣,便拿起手邊鏡子照照,那鏡子的就是她的樣子了。」
說著堆起眼角幾絲魚尾紋,慈善地把陸梨再看看,便欠了欠身子往外走。
陸梨乍聽得回不了神,什麼叫往鏡子裡看看……龍鳳胎……心中莫名略過幾許空悵,待要再問那個男人是誰,沈嬤嬤一道微胖的老婦身影卻已往門外台階矮下去。
她回到自己的屋子,看到床面安靜地擱著個銀鐲子還有一枚小三角的掛飾,像是由原本一個玉珮打碎成了兩片,然後各自用繩子穿起來,而她這個只是其中一片。她怎麼多看了兩眼,心裡就奇怪地揪著不舒服。
那天晚上的陸梨便入了夢魘,彷彿被擱放在一個漆黑的炕頭,正在嗚哇著小嘴大哭,似乎有什麼非常渴望的東西正在向自己靠近,帶著徹骨的不捨與愛憐,她也渴望它。陸梨的心就重重一顫,猛地從夢中驚醒過來。
八月中秋,月亮掛在天空,將春禧殿打出幽藍的光影,然後就看到身旁楚鄒沉睡的樣子,似是因為白日裡負荷了太多,睡夢中也像斂著一絲沉鬱,叫人看了忍不住疼惜。
陸梨撫著楚鄒精緻的薄唇,夜風透過被褥的縫隙吹進來,使得腰背有些涼,近陣子被他要得勤了,原本早該到的月事過了四五天還不見影。陸梨心裡無底,不由將身子往楚鄒邊上靠了靠,想要取他的暖。
◎
謖真王完顏霍此次朝貢還算心誠,皇帝也就以禮相待。八月十五那天宮中設了招待宴席,十六請了戲班子連唱兩天,十八日遊萬壽山,到十九那天便去了郊外的馬場秋狩。留了張貴妃與德妃、淑妃在宮中掌事,連同懷孕的孫凡真和李蘭蘭也帶上了。
原本康妃錦秀是沒旨意去的,皇帝並未叫她。只楚鄎在出發前一天過去請安時,對錦秀說了一句:「我明兒要和四哥學騎馬了,太祖皇帝在馬背上打下的江山,我身為大奕王朝的龍子皇孫,可不得這般怯弱,我得學著克服它。」
錦秀聽了便從屜子裡取出一副嶄新的護膝與護肘,然後撫著腰蹲下來道:「九兒不說,錦秀也有這樣的意思。從前倒是總想叫你學,可殿下那時的眼睛……身邊也無有妥帖人照應。如今有四爺在,倒是叫我放心了。」看著楚鄎白俊的小臉蛋,目中幾許滄瑟與憐愛。
錦秀那天沒上妝,稱呼也時而不自覺地謙卑下來,不再用「本宮」與「小九兒」,而改叫「殿下與錦秀」了。楚鄎本是有意叫她聽出自己與四哥親近,不再依附她,怎的真被她聽出來了,心中又頓生空落。他依舊是顧念著錦秀的,眼睛卻不自覺地往她的肚子那裡看。
錦秀似察覺了,低下頭一默,又抬起頭暈開笑顏,「算起來,進宮已有十七年,宮裡不倒的是牆,唯人情卻是最短最留不住。我近來時常在夢中見到從前的夥伴,只是聽說常夢見死人不好,夜半醒來心頭空空的,就好像被她們召喚,怕再看不見我們小九兒……呀,瞧瞧我,這都說了些什麼,殿下自去玩得開心就好。」她說著潸然地拭了一下眼角。
楚鄎立在旁邊看,竟一瞬很怕她會因為父皇的失寵而自殺,便一意求了父皇的旨意,央著拖著錦秀一塊兒去了。怎知蒼天便偏在那天給了她一個機緣,讓她把肚子裡的去得轟轟烈烈。
是辰時初從東華門開始出發的,一向身子骨甚好的九郡主完顏嬌不曉得早膳用了什麼,半道上頻頻泛胃酸,皇帝便叫楚鄒和楚鄺護了宮嬪與年幼的皇子公主們先走,自己留下一部分人馬,與完顏霍父子在路邊亭子下暫作休憩。
秋日乾燥,侍衛們都往亭子旁的茶棚裡討水喝,卻忽然從暗處閃出百數名黑衣套頭蒙面人,聽一聲沙啞高麗暗語,各個便手持利劍與鋒弓包抄過來,行舉凶猛且招招致命。待楚昂發現不對勁時侍衛們多已飲水中毒。
刺客應是衝著完顏霍與皇帝去的,陸梨本護著楚鄎躺倒在車廂板上,眼看著呼嘯的利箭射向楚昂,怕再失去父皇,八歲的楚鄎忽然心中鈍痛,便掙扎著爬起來衝向對面。
錦秀就是在那個當口從角落裡撲過來,不顧一切地護住他們父子倆,然後一支利箭便險險地擦過楚昂的臂膀,另一支射中錦秀的肩背,是帶著毒的。等楚鄒帶著人馬從前頭率兵趕來救駕時,便看到錦秀已經緩緩地從父皇後脊剝離,然後躺倒在一片汪洋似的血水中。
那麼多的血,刺目鮮紅,就恍如五歲那年御花園裡的一幕,刺得他的眼睛生疼。
刺客是高麗派來的死士,楚鄒率一部羽林衛救駕後便迅速挽回局面。應是事前經過嚴密的布置,在隨後戚世忠與東廠趕來之際,便齊齊咬毒自刎了,其中有個動作稍慢一瞬,被楚鄒一個劍鞘扔過去打歪了下頜骨,沒死成,叫戚世忠帶回去拷問。
彼時的路程已走大半,因為康妃滑胎生死未卜,許多人亦都受了傷,便繼續前往馬場宿了一夜。東廠拷打的酷刑果然無堅不摧,戚世忠在大約兩個時辰後便摳出了結果,那個高麗死士淌著血水沙啞地吐了兩個字:「亡月。」然後便翻白眼嚥了氣。
除此之外只從他身上搜出一塊褐木令牌,上刻「單暮」二字,「單暮」乃是高麗民間最為亡命也最為昂貴的殺手組織,只「亡月」不解其意。戚世忠便拿了令牌站在皇帝跟前請罪。
「亡月」為主,合起來便是「望」。楚昂這一輩的皇嗣,旁人也許不知道,可那「望」乃是遠在高麗的齊王楚曎小名。彼時楚昂的父皇仁宗身體已見不好,許惠妃尚懷著老十二在肚子裡,便給起了這個「望」字小名,然而還未望到他出生,孝帝便已歸天了。這些楚昂也是在幼年聽隆豐偶間提過一次。
若果然是他楚曎假託名字雇人幹的,他今番這般咄咄逼人,只怕是擔心完顏霍與大奕聯盟,那頭老高麗王驚慌了將他遣送回來,這便使了個破釜沉舟的伎倆妄圖刺殺自己。
明間裡燭火跳躍,魏老太醫正在給楚昂包紮手臂。楚昂伸手接過腰牌大略一掃,隨後就冷淡道一句:「先下去吧,此事回宮後再議。」
「是。」戚世忠把腰一哈,連忙躬身後退出門。
中秋過後天氣一日比一日轉涼,這荒郊野外的比皇城還要更清冷些。小花園旁可攏著不少人,都在議論著今兒那一遭生死奪命的突襲,正心有餘悸,對面第四間廡房下走出來兩個太醫和藥童,身後幾個嬤嬤端著紅木盆子尾隨而出,看神色一個個都是凝重,一時間不由噤了聲。
那廡房裡安置的乃是康妃,康妃流產了。
先頭宮裡雖暗暗傳她懷了孕,到底只是猜測,今兒這般一重創,可什麼也瞞不住了。聽說被太監抬回來時整身宮袍都浸得黑紅,人更是氣息奄奄。她本是後宮多年盛眷的寵妃,懷了骨肉卻瞞著,可見這個孩子並不受皇帝的歡迎。
安置後皇帝有過來瞧了一眼,在床邊站了站便漠著臉出去了。倒是九皇子楚鄎,從頭到尾坐在跟前守著。聽進去當差的奴才們說,康妃的臉白得像一張紙,肚子亦平復下去,一直沒睜開眼睛,九皇子抓著她的手,時而在她手心裡撓撓,兩嘴片子就跟著顫一顫。九皇子這是把她當養母哩,這般敬孝,皇帝不肯容她懷上子嗣想來也在情理之中。
酉末的京郊馬場,日頭漸漸沉了,一片光影昏黃。今兒夜裡四皇子與二王爺換了鎧甲親自輪流值守,四面場院時時可聽見羽林衛馬蹄聲踢踏作響。
一直被關在雲明樓裡的完顏霍第五子完顏辰亦受了傷。白天二公主楚池為了躲箭,下意識栽進他胸膛裡躲避,完顏辰為了救她,肩膀被刀劃破。楚池帶了藥去探望,又恐怕禮儀忌諱,便拖了討梅一道去。春綠不知道獨自上哪兒傷神去了,陸梨找不到她,便坐在石桌旁聽著眾人議論。
許是她心思狹了,怎的仔細把前頭後尾來回琢磨,總覺得哪兒似有些微妙,一時卻又琢磨不到點,見一排當差的迎面過來,便暗自斂回心緒。
皇帝為了安撫眾下,派膳房給大夥送來了安神的補給,奴才們的是蓮子大棗粥,主子們的是蟲草花煲雞湯下長壽麵。陸梨的和小主們是一樣的,太監把湯給她呈上,還附帶一小荷包的香烤鵪鶉蛋。她猜著就是楚鄒給她的「特例」了,曉得她從小愛吃這口,心裡頭不禁泛過暖意。
如今倒是換他處處學會疼人了。
舀著勺兒才吃了幾口,孫凡真便搭著兔毛領披風盈盈碎步過來,看她在喝湯,倒好像故意坐在她身旁攪擾似的,手上拿著支笛子,把穗子尾巴一甩便甩進陸梨的湯裡,又似才發現,回頭道:「喲,瞧這風吹的,髒了妳的湯,也油了我的穗子。看妳像餓得不行,把本宮這份賞妳便是了。」
自從上次湯盅被人下毒之後,皇帝便時常留宿在孫凡真這裡,就連同住長春宮的李蘭蘭和沈妃都遠遠不得她的頻,現下被調養得丰韻潤澤,眼睛裡都像含著光,看著便越發傲慢了。
陸梨一直不篤定她上次是發了慈心不查,還是將計就計用來爭寵的,若那次想查,只須把每個人的頭髮比對過去,也能抓出幾個相似的,反正宮裡頭處置宮女從來不稀罕個數。
但她和孫凡真向來不對盤,那碗湯後來也就不吃了。
孫凡真是在許久之後才告訴陸梨,那湯裡被下了毒。她在來的路上看到了,一個宮女拐進林子裡,然後撒下一小包藥粉,一路隨過來,果然看到端去的是給陸梨。
但當時的陸梨並不知道,只當作是那湯裡燜了太多黃酒,又或者是著了涼,怎的走了兩步竟忽然有些頭暈,路上撞見個太監,說夜涼了,殿下叫送件披風過去,在大梧桐樹下等著。
從白天遇襲起,因著場面混亂,皇帝又受了傷,兩個人就都沒怎麼正經碰過面說過話。陸梨因為記起楚鄒當時掛了傷,便帶上藥粉和夜宵,攜著披風一道去了。
一路往小徑深處走,過了窄長一條石頭路,之後便是秋日枯澀的荒草拂動。怎麼走著走著眼睛有點花,嗓子亦顯得乾渴起來,但神志還是清醒的,看到大梧桐樹下坐著道寬健的身影,墨髮用玉冠高束著垂散下來,肩膀似乎比楚鄒厚實些,怎的身邊還有一只酒壺。
她便狐疑地吶了聲:「那位可是爺?把披風給爺送來了。」
楚鄺聽聞熟悉的動聽嗓兒,吭聲冷笑:「不是和那小子睡了嗎?兩個如膠似漆,何故又把爺叫來這裡寒磣?肯回心轉意了?」他說著便轉過臉來,眼睛有些紅,嗓子亦恁地澀啞。
陸梨那時才察覺出不對,她根本沒找過楚鄺,然而想要轉身走,卻已經來不及。
那天的楚鄺應該也是被下了藥的,兩個人被套進一個局,這個局的目的便是為了讓楚鄒失去陸梨,只是彼時的陸梨並不能知。
自己拚了性命打贏的仗,父皇卻讓他老四在前朝接洽使臣展盡風光,白日救駕又讓他先行一步占了上風,楚鄺的嫉恨與怒鬱無從沖泄。喝醉酒的他,把陸梨猛地抵在身後的樹上,他說:「爺費盡心思攀爬,最後什麼好處都他媽讓他老四沾去了!妳不是多麼心甘情願為他捨身為他付出嗎?那便把他欠下爺的也一併還了吧!」
一邊說著一邊混亂地去解陸梨的裙裾。隔著秋日的馬面裙,陸梨都已能感到鈍痛逼近的生疼。「放開我!二爺你是瘋了!」拚盡力打著楚鄺的肩背,可楚鄺卻一意要往她的裙下試探。
彼時,春綠因為思鄉正在草叢裡抹眼淚,驀地站起來被場面嚇昏了頭,在把石子砸向楚鄺後頸時也未顧及太多,楚鄺原本熱血上湧,懵然間便暈眩在地上。
陸梨牽著春綠的手往回跑,兩個人分開後,春綠發現母親留給自己的翡翠鐲子掉了,只得又匆忙跑回去找,瞧見鐲子掉在老二身旁,便掂著裙子邁過去撿。就這樣,在轉身的時候被醒來的楚鄺忽然拖住了腳踝……
一個多時辰後,被巡夜的羽林衛路過發現。彼時春綠已痛得昏厥過去好幾回,討梅給她上藥時裙子和那裡都已經破得不成樣了。皇帝得知後盛怒不已,在這般緊要關頭身為堂堂皇子竟不勤於值守,還這般穢亂後宮。因為不想叫完顏霍聽去丟了王朝的臉面,便把老二關了一晚的禁閉,第二天天不亮就叫張福派一隊人馬押送回京城。
楚鄒本是不知道此事的,陸梨也沒有告訴他。那天晚上他回屋的時候已經過了子時,身上沾著夜的濕氣與血的腥殺,要換作平時,陸梨一定趕他下去洗了再上來。可那夜始一上床,陸梨便把腕子環上他的頸貼近他不放。中秋的深夜寒涼,被窩裡沾了她少女的馨香與暖熱,他還只當她忽然體貼自己,直生出滿腔的柔情。
第二天楚鄒才知道老二對陸梨未遂的那件事,彼時兄弟倆除卻嚼穿齦血的仇惡,心中對陸梨的自疚自責業已幾近崩潰。
因為完顏霍與他的兩個兒子也都受了輕傷,馬場狩獵便沒了興致,隊伍次日傍晚便打道歸程。回宮後皇帝便大步往乾清宮洶洶然而去,隨後張貴妃也緊忙地跟著過來。楚鄺是在這天早上才認真看過春綠的,聽說春綠昨兒半夜上吊,被人揪了下來。她是不愛慕二皇子的,至今想起來都是痛與怕,哭得眼睛腫得像兩個水泡。楚鄺也從酒醉中清醒,剛俊的臉龐上一夜之間冒出青茬,顯得很是頹靡憔悴,這時把春綠定睛一凝,也不想說什麼了,只是垂下頭噤語。
皇帝陰鬱著臉,端坐在正中銅黃的影壁之下。這件事可大可小,往小了說是皇子與淑女生情,往大了說可就是淫亂皇帝的後宮了。張貴妃萬萬沒料到事情會突生變故,又聽說錦秀竟是為救皇帝父子才滑了胎,後來便叫人把劉廣慶從衍祺門喊了來。
那天早上的陸梨穿一身淺水紅的斜襟褂子,正坐在春禧殿前的矮凳上洗衣裳。辰時的朝陽打著淡暖的黃暈,楚鄒端坐在內殿條案上寫字。然後匆匆忙忙來了一個太監,也不知道說了什麼,楚鄒便換上袍服出去了。
又過了半個多時辰,小路子也來了。平時見人就笑,嘴也暢快,那天的臉色卻有些莫名,沉語一句:「梨子,妳跟我來一趟。」簡簡短短的話,說完便自在前頭走路。一襲森綠曳撒撲簌撲簌著,似屢屢想回頭過來問些什麼,又始終沒有說。
陸梨的心便隱隱地有些鬱亂的兆頭。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