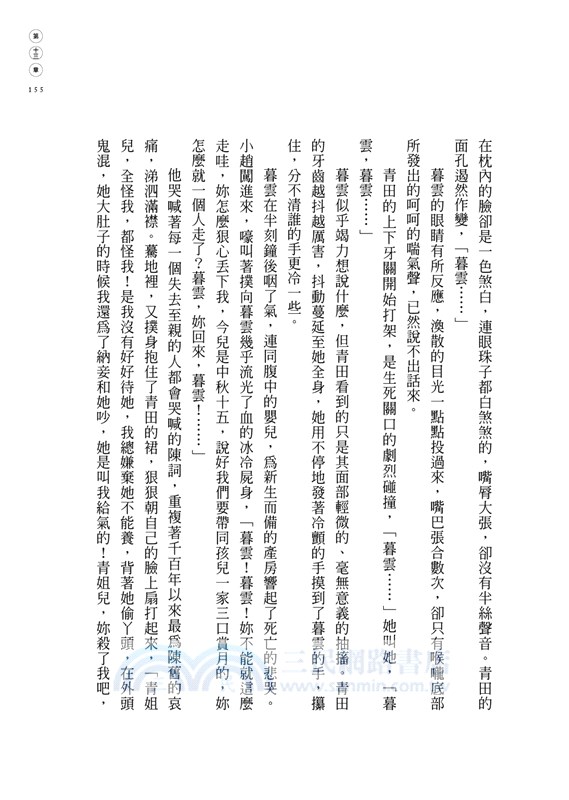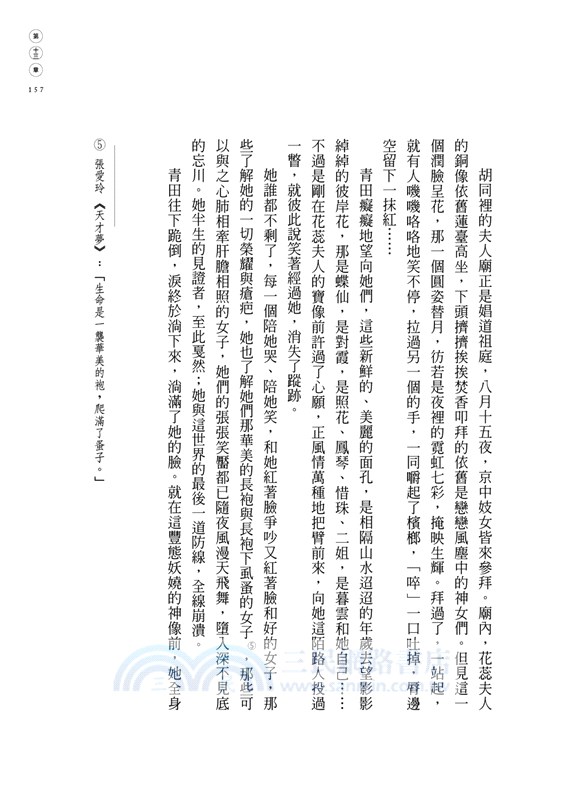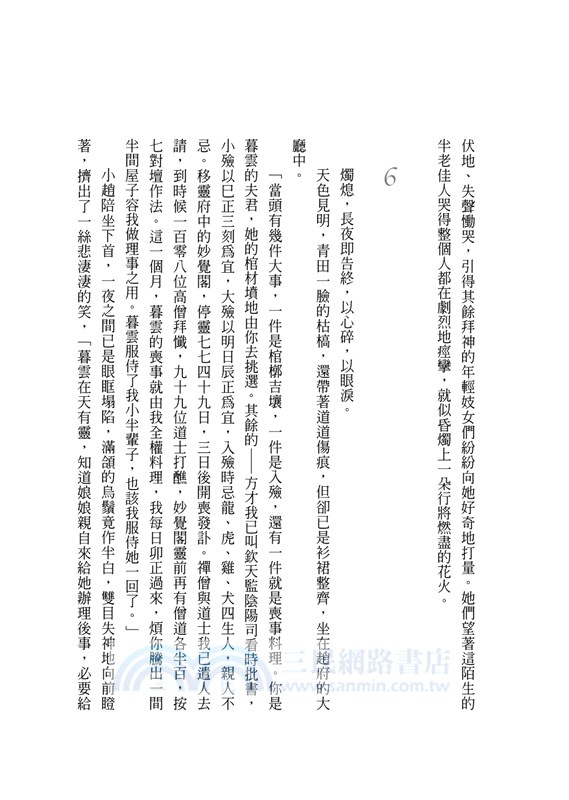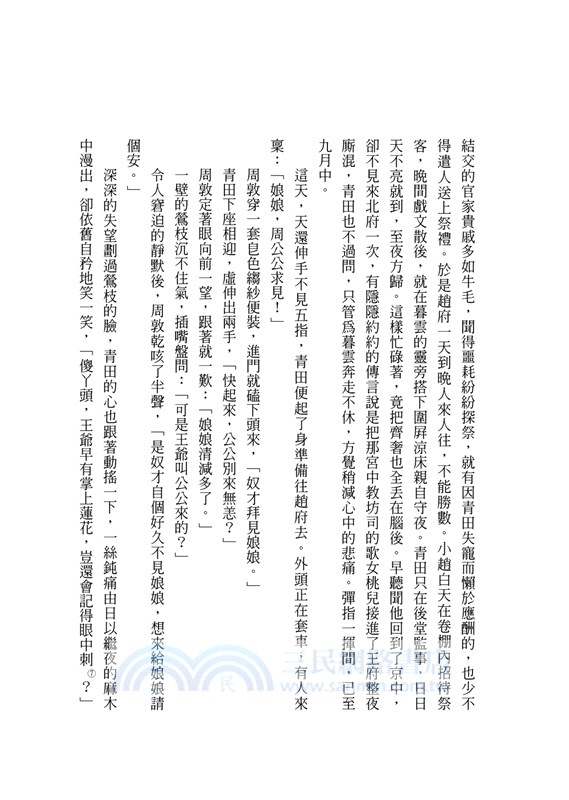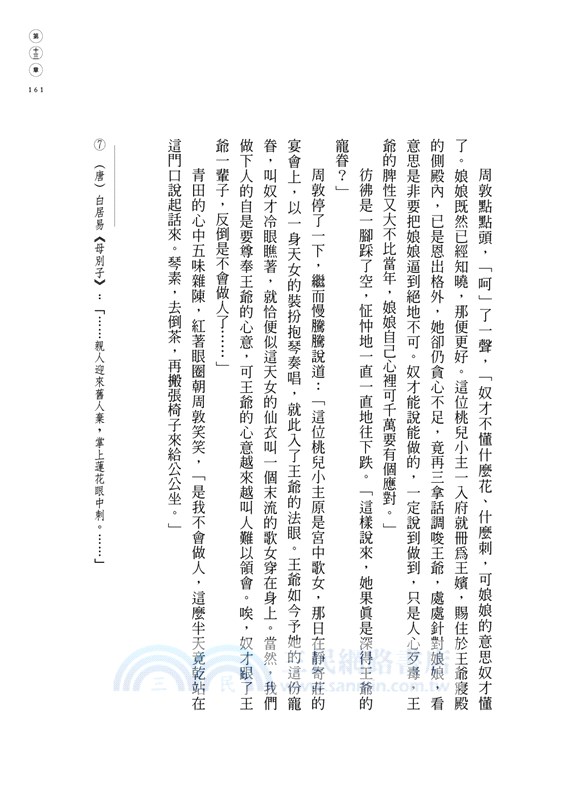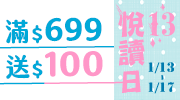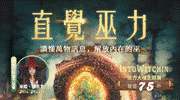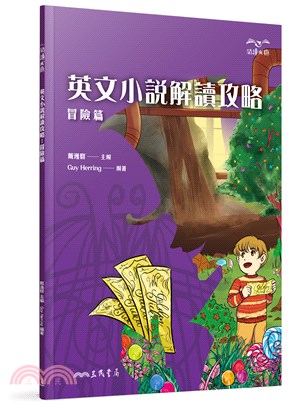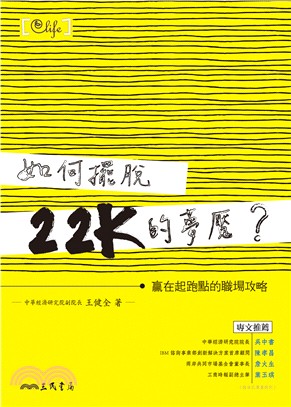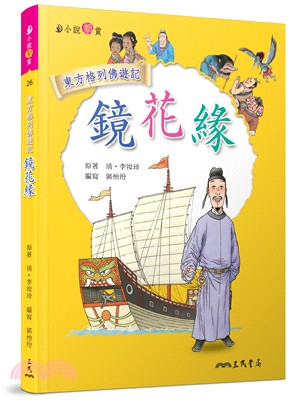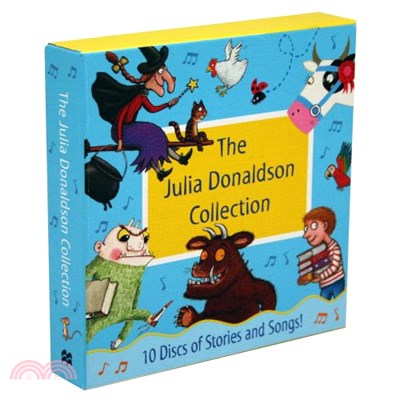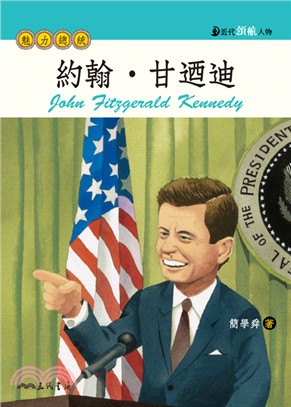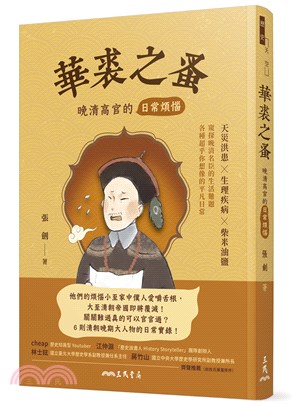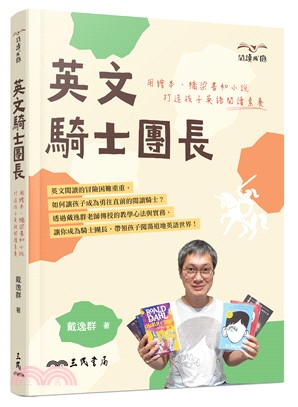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悲歡離合金匣起,死生契闊人面終
她從青樓名利場到宮廷生死局
他從金燦燦龍庭到白茫茫大地
絕代倌人與亂世帝王
貴賤是天塹,愛情是天梯
身分與生理各有殘缺的兩人,該如何跨越彼此心中的檻?
她刻苦地學習每一項技能,尤其是如何嗲聲嗲氣地抱著人,用從裡到外的柔軟騙取堅硬的金與銀,為他去買一個把手中的剪刀換做筆的機會。男人們伏在她身上,一個又一個,她大張著眼躺在最深的爛泥底,含笑仰望著一株花,抽芽吐穗,在紅綃帳頂上慢慢地開……
她是九十九地之下,追歡賣笑的花榜狀元。他是三十三天之上,操縱著陰謀陽謀的帝國主宰。一支帶著血腥色的朱筆,拐彎抹角地輾轉著,於命運的考卷上,把他們連到了一起。即使他在萬人矚目中高不可攀,即使她是人群裡的塵下塵,穿越萬丈紅塵,他們也要在靈魂裡相擁。
伊人望吾鄉,兩心永團圓
――匣子緩緩地關閉,在故事的結尾,在一個心的故事裡,他們會永遠地在一起。
齊奢的大半輩子都活在他的父親、兄長,甚至是他的子侄的陰影下,這些皇帝輪番欺侮,他忍辱負重,甚至願意放下仇恨,當一位忠賢良臣,卻因為一場貪婪的風暴,捲起一陣名為「復仇」的狂風──那是齊奢長期以來的渴望,他不要再任人宰割,這次,他要親自主宰皇帝的命運。
然而,就在齊奢成為暴君後,青田也隨之成了怨婦。他冷落她、嘲諷她,看見她,就彷若看見兒時的自己,於是齊奢決定將青田拖下煉獄,讓自己的每一天也都在煉獄之門來回進出……在這渾沌的亂世中,本是一體的兩人真能捨下彼此,就此漸行漸遠嗎?
【本書特色】
★網路最受矚目,9.9分高評價,才華洋溢的人氣女神開創古言小說新局,影視化熱烈啟動中
★從青樓名利場到宮廷生死局,絕代倌人與亂世帝王的曠世虐戀
★當當網六千多則佳評,讀者爭相推薦!
「畫面感極強,閱讀的過程就如同看了一部電影!」
「是我看過唯一一部可以和《甄嬛傳》齊頭的小說!」
「愛恨交織的故事,值得去看,值得去想,如匣子一般,裝滿了酸楚和歡笑。」
「這本《匣心記》確實不同《延禧宮略》《甄嬛傳》風格,有新,有質,有巧,確實難得。」
「特別是不落俗套!作者別出心裁,用青樓女子做主角,偏還能於濁世中見真情,高,實在是高!」
「這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小說,無論人物還是情節。跌宕起伏、陰謀詭計、愛恨情仇都十分齊全,閱讀很有暢酣淋漓之感,是本好書。」
「人都有陰暗的一面,也沒有完美的人生,人性刻畫的比較豐滿,感覺是有血有肉的,不像許多言情小說主角都是頭頂金光、完美無缺、無所不能的非人類!」
★《劍魂如初》作者/懷觀、歐巴桑系網路插畫家/鼻妹 痴心推薦
【好評推薦】
「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美麗的文字,細緻的考據,構成了這部青樓女子的血淚風情史。
權傾天下的王爺對上冶豔入骨的名妓,人前都光鮮亮麗,心底均千瘡百孔。兩個殘缺的靈魂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圓滿,結局好不好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推薦給古言迷,作者能用文字帶你進入某個時空下的街坊妓院、宮廷殿堂,看盡世間炎涼。
──《劍魂如初》作者 懷觀
她從青樓名利場到宮廷生死局
他從金燦燦龍庭到白茫茫大地
絕代倌人與亂世帝王
貴賤是天塹,愛情是天梯
身分與生理各有殘缺的兩人,該如何跨越彼此心中的檻?
她刻苦地學習每一項技能,尤其是如何嗲聲嗲氣地抱著人,用從裡到外的柔軟騙取堅硬的金與銀,為他去買一個把手中的剪刀換做筆的機會。男人們伏在她身上,一個又一個,她大張著眼躺在最深的爛泥底,含笑仰望著一株花,抽芽吐穗,在紅綃帳頂上慢慢地開……
她是九十九地之下,追歡賣笑的花榜狀元。他是三十三天之上,操縱著陰謀陽謀的帝國主宰。一支帶著血腥色的朱筆,拐彎抹角地輾轉著,於命運的考卷上,把他們連到了一起。即使他在萬人矚目中高不可攀,即使她是人群裡的塵下塵,穿越萬丈紅塵,他們也要在靈魂裡相擁。
伊人望吾鄉,兩心永團圓
――匣子緩緩地關閉,在故事的結尾,在一個心的故事裡,他們會永遠地在一起。
齊奢的大半輩子都活在他的父親、兄長,甚至是他的子侄的陰影下,這些皇帝輪番欺侮,他忍辱負重,甚至願意放下仇恨,當一位忠賢良臣,卻因為一場貪婪的風暴,捲起一陣名為「復仇」的狂風──那是齊奢長期以來的渴望,他不要再任人宰割,這次,他要親自主宰皇帝的命運。
然而,就在齊奢成為暴君後,青田也隨之成了怨婦。他冷落她、嘲諷她,看見她,就彷若看見兒時的自己,於是齊奢決定將青田拖下煉獄,讓自己的每一天也都在煉獄之門來回進出……在這渾沌的亂世中,本是一體的兩人真能捨下彼此,就此漸行漸遠嗎?
【本書特色】
★網路最受矚目,9.9分高評價,才華洋溢的人氣女神開創古言小說新局,影視化熱烈啟動中
★從青樓名利場到宮廷生死局,絕代倌人與亂世帝王的曠世虐戀
★當當網六千多則佳評,讀者爭相推薦!
「畫面感極強,閱讀的過程就如同看了一部電影!」
「是我看過唯一一部可以和《甄嬛傳》齊頭的小說!」
「愛恨交織的故事,值得去看,值得去想,如匣子一般,裝滿了酸楚和歡笑。」
「這本《匣心記》確實不同《延禧宮略》《甄嬛傳》風格,有新,有質,有巧,確實難得。」
「特別是不落俗套!作者別出心裁,用青樓女子做主角,偏還能於濁世中見真情,高,實在是高!」
「這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小說,無論人物還是情節。跌宕起伏、陰謀詭計、愛恨情仇都十分齊全,閱讀很有暢酣淋漓之感,是本好書。」
「人都有陰暗的一面,也沒有完美的人生,人性刻畫的比較豐滿,感覺是有血有肉的,不像許多言情小說主角都是頭頂金光、完美無缺、無所不能的非人類!」
★《劍魂如初》作者/懷觀、歐巴桑系網路插畫家/鼻妹 痴心推薦
【好評推薦】
「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美麗的文字,細緻的考據,構成了這部青樓女子的血淚風情史。
權傾天下的王爺對上冶豔入骨的名妓,人前都光鮮亮麗,心底均千瘡百孔。兩個殘缺的靈魂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圓滿,結局好不好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推薦給古言迷,作者能用文字帶你進入某個時空下的街坊妓院、宮廷殿堂,看盡世間炎涼。
──《劍魂如初》作者 懷觀
作者簡介
伍倩
生於夏天,太陽獅子,月亮天蠍。北京大學法語文學博士,現在大學任教。
鍾愛文字與故事。惟願自己能一字字講述好每一個故事,這些故事自冥冥之中找到我,藉我的筆墨降臨人間,帶給我歡笑與眼淚、光明與黑暗。
你想歡笑?想流淚?想永生難忘一個故事?我和我的故事都在等著你,希望能在書裡碰到你,也希望你可以在書裡,和你自己迎頭相遇。
生於夏天,太陽獅子,月亮天蠍。北京大學法語文學博士,現在大學任教。
鍾愛文字與故事。惟願自己能一字字講述好每一個故事,這些故事自冥冥之中找到我,藉我的筆墨降臨人間,帶給我歡笑與眼淚、光明與黑暗。
你想歡笑?想流淚?想永生難忘一個故事?我和我的故事都在等著你,希望能在書裡碰到你,也希望你可以在書裡,和你自己迎頭相遇。
目次
第十二章 碎金盞
他的父親、兄長、子侄⋯⋯
他大半輩子都在被皇帝們輪番欺侮,
這是他漂亮的復仇――再沒有皇帝能抄他齊奢的家,
現在,是他齊奢,在抄皇帝的家。
第十三章 剔銀燈
她依舊是美麗的,只是多了一分惴惴的倉皇。
就彷彿在這張臉周圍,有成群的豺狼環伺。
這些豺狼,齊奢明白,叫時間。
第十四章 望吾鄉
他離她、離這所有的一切是這樣近,
近到只需邁一步、伸出手就夠得到,
齊奢覺得不公平,不公平極了,就差這麼一丁點兒。
煞尾 永團圓
在一個關於心的故事裡,
他們總是會,永遠地在一起。
他的父親、兄長、子侄⋯⋯
他大半輩子都在被皇帝們輪番欺侮,
這是他漂亮的復仇――再沒有皇帝能抄他齊奢的家,
現在,是他齊奢,在抄皇帝的家。
第十三章 剔銀燈
她依舊是美麗的,只是多了一分惴惴的倉皇。
就彷彿在這張臉周圍,有成群的豺狼環伺。
這些豺狼,齊奢明白,叫時間。
第十四章 望吾鄉
他離她、離這所有的一切是這樣近,
近到只需邁一步、伸出手就夠得到,
齊奢覺得不公平,不公平極了,就差這麼一丁點兒。
煞尾 永團圓
在一個關於心的故事裡,
他們總是會,永遠地在一起。
書摘/試閱
這便是紫禁城中齊奢的一天,青田在北府的一天則全然不同。 齊奢離去後很久,她才由魚戲荷葉的繡被中探出一雙藕臂,因幽歡密愛而微有些發腫的脣角笑意濃濃,「鶯枝―」 繼而,便聽得門一響,伴著恰恰鶯聲。 「可算醒啦,這都快大晌午了。王爺朝乾夕惕,有人卻只睡個不夠。」一張容長臉兒上稚氣皆消,疏疏的眉,小小一隻膽鼻,雙目卻又圓又大,滿室間一睞,秋水為神。聲音比幼時更加地清亮和緩,彷彿金豆子一粒一粒、數得清清楚楚地掉落在銀盆裡。 青田一面笑,一面攬被坐起身,「妳這小呆子,我只說妳是個老實的,這兩年也學會弄嘴兒了,『有人』是誰啊?」 鶯枝低鬟一笑:「奴婢卻也不知道『有人』是誰。」 青田端過盤上的薄荷香茶,另一手就往鶯枝滿垂細髮的額前一彈,「罰妳吃個榧子!」 主僕倆正笑著,另有一群侍婢手中各捧著銀盆盥巾也進得房來,有的輕如浣雪,有的秀若餐霞,正是就花居中的十琴婢―去了一個琴竹,現今只剩下九個。從前王府裡的曉鏡、月魄幾人皆已婚配,除去鶯枝,便是這九琴近身服侍青田。彼時洗漱即畢,琴盟、琴畫和琴素三婢捧來了胭脂與水粉,開了梳頭盒子。其中琴畫是梳頭丫頭,正拿著牙梳替青田攏頭髮,琴語走了來,妍妍一笑,「娘娘,大理寺少卿左夫人來了,已在外頭等了娘娘小半個時辰了。」 北府常有命婦造訪,大小丫鬟都對各位官眷如數家珍。青田聽了這一位,單以兩指拈起一束髮絲來,在指尖繞幾繞, 「我猜猜,八成是大理寺卿新近出缺,王爺一時沒找到合適的人選,暫叫左大人『署理』,左太太就上我這兒來興師問罪了。」 梳頭丫頭琴畫手最巧,嘴巴也最厲害,一面替青田把長髮在頭頂盤做個單螺,一面洋洋一笑,「她哪裡敢興師問罪,負荊請罪還差不多。這左夫人總仗著娘家是建國公馮家,在娘娘面前也擺出一副世族小姐的嘴臉,動不動就把她那家世表白一番,最討人厭的。娘娘不喜歡左夫人,王爺自然就不喜歡左大人。這麼多年,同榜的做到大學士的都有,左大人卻還在大理寺少卿的位置上苦熬著。這回好容易趕上正職遺缺,依資歷而論,由左大人升補乃是天經地義之事,誰想仍是個『署理』。左夫人再不來求求娘娘大發慈悲,怕左大人這輩子都別想『扶正』了。」 「小蹄子少瞎講,」那廂琴盟呈上了首飾匣,青田指了指一把草蟲啄針,由鏡中瞟琴畫一眼,「同我有什麼關係?左大人官聲雖不算太壞,可才具平庸,又欠謹飭,王爺向來瞧不上眼,不過看在他是個老資格的分上,他還癡心妄想呢!左夫人來了也是白來。」 鶯枝在一壁揀出一支珠母簪,往青田的鬢邊一比,青田搖了搖手,她便又放下,溫言慢語道:「娘娘既不想見,推了便罷。琴素―」 後頭的琴素忙將手裡的一只大盤捧上,盤中是十餘樣各色鮮花,「請娘娘簪花。」 鶯枝由花盤內選出一莖晚香玉,為青田簪於髻頂,「府裡新從外頭買了兩個小戲,一個叫佩瑤,一個叫仲瑤,前兒奴婢撞見她們排演《長生殿》,當真是纖音遏雲,唱盡天寶風流,有年頭沒見著這麼好的孩子了,不如叫進來給娘娘來兩齣?不比聽左夫人吐苦水強嗎?」 青田一手扶鬢,攬鏡自照,「也好。」 就花居外的過廳,一張雕梅花紅木椅上坐著位穿紅緞繡金衣裙的貴婦,便是左夫人。眉目算得上清明,鼻子兩邊高高地撐起兩塊顴骨,下巴高揚著,顯得十分焦急。後廂秀簾輕動,婢女琴語婷婷地走出,「左太太,娘娘剛起,覺著身子有些不適,想是不能見您了,太太先回吧。」 左夫人的腮幫子一耷拉,滿目失望。只好敷衍了幾句請娘娘保重的話,帶著幾名侍女悻悻離開。 走到垂花門外時,見迎面來了一對十一二歲的女童,看打扮是府裡的伶官,跟著個丫鬟往裡頭去了。左夫人心下一轉,謊稱掉了手絹,重新尋回了客廳,就聽見一陣清唱自後堂傳來,還有咯咯的笑聲。左夫人回身而出,一面同貼身侍婢咬著牙根地咬耳根:「不舒服還有勁頭聽曲?哼,連那邊王府的繼妃娘娘也要顧念我的出身,格外優容,她倒把架子端上天了。且罷,容她得意,我就不信一個花街出來的下等貨色能在我這樣的世家之女跟前得意一世!走著瞧吧。」 妝房內,青田聽著小戲們一曲清歌繞梁韻,無端剎那間,憶起多年前在懷雅堂被豪客馮公爺召之即來,此刻卻閒坐王庭,將他的孫女揮之即去。人世轉際,不外如此。 舊事仍未下心頭,卻有故人登門。 「娘娘,左夫人去了,外頭又來了一位黃夫人求見。」琴語去而折返,輕將羅袖撲一撲,「以前沒見過的,說是新任河道總督的夫人,剛從南邊進京。」 「黃夫人?」揚州,瘦西湖,安廬―青田喜色一動,「行了停吧,別唱了。快請夫人進來。」 黃夫人依然是灑脫精幹的模樣,攜十來名侍女麗妝而來,「娘娘!妾身拜見娘娘。」 青田忙以兩手相攙,「夫人快請起。」 黃夫人仰面含笑端詳一番說:「娘娘這一頭頭髮可全長好了。」 青田掩頰笑一聲:「是了,在揚州那時候成日價都要戴著帽子,醜死人了。」 「娘娘怎麼樣都好看,只現今妝扮起來更如謫仙似的。喲,這是鶯枝大姑娘吧?」 鶯枝含著笑,從青田身後走上前幾步,壓身向黃夫人一禮。 黃夫人拉過了她的手道:「果然娘娘會調理人,幾年不見,出落得水蔥一樣。」 青田笑出了聲來,「可不是?轉眼也成了大姑娘了。夫人裡頭坐。琴盟,去沖一壺密雲龍。」她將黃夫人延請至小客室內的軟榻上坐下,十分親熱,「許久不見,我很想念夫人。早聽王爺說有意把黃大人調回京中,今年總算成行了。我還特意問,是不是攜了家眷一道?這下可好,夫人能常來同我說說話了。」 黃夫人亦是春容滿面,「只要娘娘不嫌煩,妾身天天來請安。」 「北上走的是水路吧?可還順利?」 「託王爺和娘娘的洪福,風足帆飽。對了,這一趟走得急,也沒帶什麼,只有一些風土特產,還有幾件玩物,想著娘娘還看得上眼。」黃夫人手一招,身邊一名丫鬟就托上了一份大紅禮單。 青田接來,稱謝不已,「當年在府上叨擾一場,也沒什麼謝禮,今日反倒叫夫人破費,如何敢當?」 二人客套了一回,一道吃了午飯,青田方才送客出門。歪在躺椅上盹一晌,與鶯枝說了半日閒話,又將黃夫人送來的禮物揀選一番,也就到了晚飯。用完飯,傳伶官佩瑤和仲瑤將上午唱了一半的戲唱完,已覺得眼皮打架,卻還不見齊奢。差了個小太監去打聽,原來人早已經回府,不過一直待在「退軒」―就花居在北府的北頭,往南有一帶假山所隔的院落,正殿的二進是一座二層閣樓,即為退軒,乃齊奢接見臣僚之地。 「王爺在那兒同誰說到這麼晚?」青田倚窗逗弄著鸚鵡飛卿,替牠把翎毛梳了又梳。 一簾之外的小太監圓領襴衫,眉眼低垂而答:「回娘娘,王爺一個人待著看書呢。」 「哦。」輕綾長裙窸窣一響,青田扭轉腰肢,一身的豐似多肌、柔若無骨,「鶯枝,那妳去叫人把那屏風抬上,跟我一道到退軒去。」 兩刻鐘之後青田就進了退軒的門,直上二樓。樓廊九曲闌干,正中擺放著一面水晶大鏡,正照遠處的什剎海。畫船燈火、星影螢光,連泠泠的船歌也倒映在鏡中,悠遠動人。青田借杵於鏡前的兩掛風燈對鏡理了理紗緞領,向後輕擲一聲:「小心些啊。」 等裡間的齊奢得著通報時,青田已跨進門了,一進門就嬌笑如鈴道:「爺為國操勞辛苦了,給爺送禮來了。」 齊奢坐在張花梨大桌後,把手間的一本書捏起,只見青田與一群侍婢後,還跟著五六個太監合擔著一件酸枝插屏。插屏中是一塊厚約一尺的水晶玻璃,中空注水,水中竟游弋著一群通體油綠的活魚。機巧絕倫,似真似幻。 「這兒,就擺這兒。」青田一壁督人擺設,一壁笑吟吟地拍拍手,「怎麼樣?你一直抱怨說書房裡少一件像樣的插屏,這件好不好?這是今兒黃夫人送來的,倒是別出心裁,裡頭是黑龍江的竹魚,你批文批倦了瞧上兩眼,滿目清―怎麼了?」青田的聲音小下來,插屏業已擺好,她的手腳卻不知該怎樣擺放。 以往也有幾回,她心血來潮當他獨處時探望,他總笑臉相迎,充其量邊笑邊皺起眉,「正忙正忙,別瞎打岔。」她就安靜地退守一隅,為他烹一道新茶。但青田從未見過齊奢對她的不期而至有當下的反應:活像一頭領地被入侵的獸,凶光畢露。 她略顯失措地立在屏邊,連忙道歉:「可是擾到你了?對不住。」 齊奢從座位上起立,瞪起兩眼惡聲惡氣道:「以後沒我的許可,不准擅自上樓。」 青田把身上的白銀條衫兒揪弄兩下,「以前不都隨便來去,你也沒說過什麼。」 「現在我說『以後』。」 青田定睛朝齊奢端量一番,放柔了語調:「你今兒是怎麼了?心情這麼壞?」 「心情好得很,」他高仰起下頜,「只是教妳守點兒規矩。」 二人間偶爾也拌拌嘴,可鮮少有如此冥頑不靈之態。青田自覺顏面有損,即時頂回去:「我沒規矩,爺又不是第一天知道,突然新興起來,卻也不知為了什麼。」 齊奢直接把手內的書往旁邊牆上「啪啦」一摜,震聲暴喝:「混帳!」 青田冷哼半聲:「你在外頭跟誰置了骯髒氣,只管找他發去,少衝我撒野。」言訖將鏤金裙一掣,足下生風而去。使女太監誰也不敢吱聲,悄然跟出。 可等亥末敲過,青田見齊奢仍未歸寢,就不由生出了絲絲悔意,對住鶯枝長歎一聲:「都怪我,他一定是為什麼事煩惱,我還和他頂嘴,當著那麼多人叫他下不來臺。唉,我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沉不住氣了?」 鶯枝傍於一側,盈然一笑,「王爺也算自食苦果,誰讓他總慣著娘娘,可不把娘娘這副脾氣越慣越大?」 青田笑啐一口,「妳也是叫我給慣的,說話越沒個分寸。行啦,陪我走一遭吧。」 當即又乘一座二人肩輿重回退軒。樓上的西廂內有一間用作小憩的臥室,兩邊夾道立滿了守更的人,周敦和何無為都在,說王爺已睡下了。青田晃了晃手不叫他們出聲,接過鶯枝手中的一盞小燈,自個躡足踏入進間。 靠著牆,一張筆管大架子床羅帳低垂,青田把燈放去了床頭的八角臺上,掛起一面帳子。床裡的人手腳大攤,氣咻咻地濃眉緊皺,卻不聞一絲鼾聲。她只道齊奢佯睡,笑著扒住他兩肩,氣息如蘭,「哎,哎,還生我的氣呀?好了,是我不好。這麼些年什麼時候也沒分床睡過,沒你在身邊,我睡不好,跟你賠禮道歉,回去睡吧,要不我在這裡陪你?那給騰個地方,哎,哎,別再裝啦,好啦……」 她扯住他一隻手,細笑撒嬌,誰知他卻猛地裡將手一甩,手背正撩在她鼻端,似塊石頭般又重又硬,一下就叫她跌落床腳。另一頭,齊奢則在夢中咒駡了一句什麼,翻身向內。 過了許久―或許並沒多久,鼻眼之間那刺心的辣痛方才減退,青田捧著臉坐在地下,滿手都是被酸出的婆娑淚水。她知道這感覺很荒誕,也很不公平,他睡著了,他不是有意的,但她仍感到似乎是回到了某張擺放在記憶深處的、落滿了塵灰的床邊;與這床和床上的男人們相伴的,是永恆的痛苦和恥辱。 她擦拭著亂淚把頭抬起,几上的小燈冷眼旁觀,看床內那壯碩的背軀動了兩動,發出了齁齁的鼾聲。 後來青田回想起,變化就始於這一夜。 這一夜,她強抑下滿心委屈退回就花居中,一場昏夢後早早就醒來,整個白天都怏怏不樂,只等著夜晚。但等到夜幕沉沉也沒見齊奢的蹤影,她開始如坐針氈,直至派出探訪的太監回說王爺已在那邊的王府歇息,她才上床安眠,但擔憂卻並未隨之消解。毫無因由的夜不歸宿,這是他第一次這樣對待她,但青田很快就會明白,這絕不是最後一次。 第二天很晚的時候,齊奢倒是回來了,滿面的煞氣。青田見狀便咽下了一肚子的話,只不痛不癢一句:「用過飯沒有?」 一頓飯齊奢都不怎麼出聲,連看也很少看她一眼,而對她所有的問話,也只以點頭或搖頭作答。這樣的疏離在他們間絕無僅有,青田確定,絕不因前夜他們爭吵了幾句。發生了什麼,很嚴重的什麼。 「你沒事吧?」 她的耐心是一根柔韌的蠶絲,直等到就寢,才以近乎纏綿的語氣輕問。 「沒事。」他簡斷似刀。 於是青田伸出手,隔衣撫著他硬邦邦的腱子肉,以期繞指柔融化那百煉鋼,「三哥……」 齊奢忽一下坐起,薄綢寢衣擦過她面頰,微微的涼。「來人!來人!」 門外守夜的是琴宜和琴靜,二人急急忙忙地應道:「王爺有何吩咐?」 「去跟周敦說,讓他傳阿古拉去角觝房―現在!」 現在是深夜裡丑時,而齊奢要離開溫柔鄉去同韃靼武士摔角。被拋下的青田,在錦帳銀床間,迷亂而不解地抱住了雙肩。 接下來的日子裡,青田一遍又一遍地問著齊奢同一個問題:「你有愁思?」開始她在枕邊問,抱摟著他的腰;後來她試著只在他看起來心情不錯時提起,用熨帖而專注的語氣,凝視著他的眼睛;再後來她裝作渾不在意,邊問邊笑著往他嘴裡塞一顆杏脯。而齊奢給她的答案每次都一樣:「沒有。」最後一次他沒開口,只一把撥開她正替他繫衣紐的手,眼光極其陰冷地往下盯了她一盯,旋身走掉了。青田懷著無限的心事度過了一個長長的白日,到夜裡頭亥時還沒有見到人,也只好睡下,但哪裡睡得穩?正魂夢無著處,聽見外頭的人聲嘈嘈,忙披了衣起來看,可不是齊奢? 她攏了攏衣襟,輕歎一聲:「回來這麼晚?」 丫鬟們正服侍著齊奢更衣,他一手將她們一攔,就朝這邊梗起了脖子,「忙,不行嗎?妳有什麼意見?」 青田見他行止乖專,自己的態度自然就放得極力謙讓,「我並沒有什麼意見,不過看你這一段格外忙,想提醒你一句身體要緊,能早些回來,還是早些回來休息的好。」 「妳少拿這幌子來壓我,妳當我不知道?妳日日派了人在外頭盤查我的行動,怎麼樣,查到了什麼?」 「怎麼能叫『盤查』?你向來不是在我這兒,就是回繼妃娘娘那兒去,每次回去也都提前和我打好招呼。可你現在老是突然一下子就沒了影兒,又不對我說明,我心裡頭擔心,還不能叫人出去打聽一聲嗎?你若嫌我多事,那我以後不問就是。」 「妳想問儘管問,能問得出來算妳本事。」 「你既不想我知道,我又何必招你討厭?反正你總是忙正事就對了。」 「妳這話拐彎抹角地損誰呢?」 「我說的是正話,你自己偏要反著聽。你不去忙正事,難道去忙邪事不成?」 齊奢摸了摸上脣的兩撇小鬍子,「我忙什麼不用妳來操心,總之我沒工夫在這裡守著妳就是。」 青田本就有些頭疼,眼下這疼痛更是一下下在頭腦裡鑽刺,她扶住了額角喘上幾口氣,「三爺,咱們不這麼一句趕一句的行不行?我哪裡有做得不到的去處,或有什麼對不住你的所在,總之請你明明白白地告訴我,我也好改過。老像這樣見了面就吵嘴,日子還怎麼往下過?」 齊奢把肩膀往上扛了扛,「妳句句都指著我的不是,妳還有什麼好改過的?」 「我哪一句指著你的不是?」 「我忙了一天,這才剛進門衣服都沒脫妳就衝出來責問我晚了,這不是存心挑眼是什麼?」 「我就事論事,說一句晚了,怎麼就成了挑眼呢?你自己看看什麼時候了,不是晚了,竟是早了不成?」 「愛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我還告訴妳,我樂意早回來就早回來,樂意晚回來就晚回來,妳能干涉得了我嗎?」 來來去去只是越說越擰,青田不覺一陣心冷,把臉扭去了一邊,「就是你不回來,我能干涉得了你嗎?」 齊奢冷笑了兩聲,「說了半天妳只這一句說到了點子上,我現在就要出去,妳倒是再派人來刺探我行蹤啊。」說完從丫鬟手裡頭搶回了外衣,一跺腳就走出去。 這一走又足足走了四五天,自這次後,青田當面再不對齊奢多過問一句。私下把周敦找來了密詢,周敦對著她一拍雙手,「最近苗疆鬧騰得厲害,王爺定是為這個犯愁。」有時卻又為難地抓著後腦勺,「嘶,前年撤銷關停的礦山似乎又偷開了幾家,要不就是為這個?」可大多數時候,周敦也只不過苦笑著搖搖頭,「實在沒什麼,風調雨順、四海昇平,奴才想破腦袋也想不出王爺還能為什麼煩心。唉,忍吧!這來得突然,沒准去得也突然,過一陣就好嘍。」 青田聽從了周敦的勸告,她選擇了忍耐,而忍耐則是她前半世最為扎實的修行。只不過前半世,她忍耐的是許多男人的輕浮與狂熱,現在,她所需要忍耐的是一個男人的輕慢和冷漠。由仲春至仲夏,情形每況愈下。齊奢晚歸與不歸的次數越來越頻繁,人變得越來越陰鬱。他開始公然地挑剔她、指責她,她對月傷心,他冷冷一句:「做什麼哭喪著一張臉?」如果她強作歡顏,他又會暴躁地濃眉一揪,「有什麼可瞎高興的!」她講話稍微多一些,他就會流露出一臉的焦躁,要麼就乾脆起身走開。在她的軟磨硬泡下,他才肯陪她一起進餐,結果卻摔了筷子,砸碎了兩只碗。她化起年輕時篩酒待客的宴妝,琵琶與小曲,百般柔情蜜意,他卻只把她輕輕放來他大腿內側打圈的手重重地捏住,拽出來壓在膝蓋上。他已很久不同她交歡,屈指可數的幾次,是生硬地粗暴地將她一把摁倒在桌面或地毯上,過程中一個字也不說,只是純粹拿她來洩火―生理的和心理的,他現在像隨時都對她怒火衝衝。身體秋毫無犯的夜晚,他睡在她枕邊,她做夢,夢到了在御,哭著醒來,也吵醒了他。就在不久前,他還會哄小貓一般揉揉拍拍,哄著她再次入睡,或把自己先哄得打起鼾,但這一夜,「還嫌我不夠累怎麼著?專等我睡著了號喪。」他翻過身,背對她。齊奢完完全全換了一個人,只除了那一具因經年的弓馬操練而始終保持年輕緊實的軀殼。青田的軀殼則經歷著一場巨變,她迅速地憔悴下去:色斑與細紋,失去閃光與水分的肌膚……每一個中年女子都逃不過的,她也一樣沒有逃過。 就花居的夏花盛放時,段娘娘失寵的新聞就傳遍了北京城。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