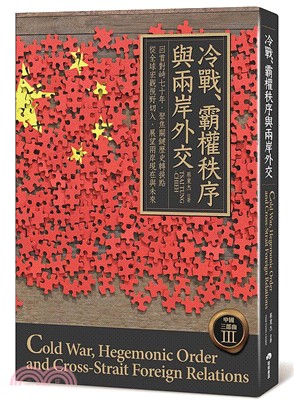冷戰、霸權秩序與兩岸外交
商品資訊
定價
:NT$ 380 元優惠價
:90 折 342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0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中國三部曲 THE CHINA TRILOGY
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們既須探究其內涵,更需要積極尋找更有意義的客觀切入點,纔能深入理解其未來前景。
本系列將透過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之不同長度視野,由「大歷史」角度重構中國歷史進程。
本書即為此系列之第三部,將目光拉至最近的過去,兩岸關係雖是中國問題核心所在,實則卻僅是全球結構下的因變數。本書將嘗試解析以下疑惑:究竟冷戰如何奠下當前兩岸互動之基礎?以美國為中心的冷戰秩序又如何影響其間曲折起伏?我們又應如何放眼未來?
回首對峙七十年,聚焦關鍵歷史轉捩點
從全球宏觀視野切入,展望兩岸現在與未來
起自一九四九年之中國外交史(或兩岸之對外關係)所以具有特殊性,至少直到二十世紀末為止,原因主要來自兩岸之間因競逐單一主權與正統性所引發的對立、衝突與相互牽制。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承緒中國自清季以來的國際弱勢地位,此期間之衝突緣由,最初雖基於不同政治團體為爭取統治權所致,外部因素(特別是若干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強權國家)所佔之關鍵地位實不容忽視。
隔海相望七十年,除了就是兩岸關係,還能從甚麼角度脈絡來觀察?與兩岸分治同時開展的全球冷戰,提供了何種時代背景?作為戰後雙強,美國與蘇聯的對抗又扮演何種角色?隨著冷戰終結,兩岸面對的又是甚麼樣新結構?本書將透過若干關鍵轉折,娓娓細數這一段漫長曲折之歷史進程。
列寧(Vladimir Lenin):
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
羅素(Bertrand Russell):
既然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而即使中國人不對其他國家人民產生影響,中國問題本身也是個意義深遠的問題。
杜魯門(Harry Truman):
除非我們強烈支持中國,否則蘇聯將在遠東取代日本的地位。
毛澤東(Mao Zedong):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尼克森(Richard Nixon):
美國的任何亞洲政策,都必須切實掌握中共存在的事實。從長遠觀點看來,不能永遠讓中共隔離於國際社會之外。
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們既須探究其內涵,更需要積極尋找更有意義的客觀切入點,纔能深入理解其未來前景。
本系列將透過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之不同長度視野,由「大歷史」角度重構中國歷史進程。
本書即為此系列之第三部,將目光拉至最近的過去,兩岸關係雖是中國問題核心所在,實則卻僅是全球結構下的因變數。本書將嘗試解析以下疑惑:究竟冷戰如何奠下當前兩岸互動之基礎?以美國為中心的冷戰秩序又如何影響其間曲折起伏?我們又應如何放眼未來?
回首對峙七十年,聚焦關鍵歷史轉捩點
從全球宏觀視野切入,展望兩岸現在與未來
起自一九四九年之中國外交史(或兩岸之對外關係)所以具有特殊性,至少直到二十世紀末為止,原因主要來自兩岸之間因競逐單一主權與正統性所引發的對立、衝突與相互牽制。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承緒中國自清季以來的國際弱勢地位,此期間之衝突緣由,最初雖基於不同政治團體為爭取統治權所致,外部因素(特別是若干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強權國家)所佔之關鍵地位實不容忽視。
隔海相望七十年,除了就是兩岸關係,還能從甚麼角度脈絡來觀察?與兩岸分治同時開展的全球冷戰,提供了何種時代背景?作為戰後雙強,美國與蘇聯的對抗又扮演何種角色?隨著冷戰終結,兩岸面對的又是甚麼樣新結構?本書將透過若干關鍵轉折,娓娓細數這一段漫長曲折之歷史進程。
列寧(Vladimir Lenin):
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
羅素(Bertrand Russell):
既然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而即使中國人不對其他國家人民產生影響,中國問題本身也是個意義深遠的問題。
杜魯門(Harry Truman):
除非我們強烈支持中國,否則蘇聯將在遠東取代日本的地位。
毛澤東(Mao Zedong):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尼克森(Richard Nixon):
美國的任何亞洲政策,都必須切實掌握中共存在的事實。從長遠觀點看來,不能永遠讓中共隔離於國際社會之外。
作者簡介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迄今著作甚豐,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迄今著作甚豐,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目次
從莫斯科到遠東 一九一八─一九四九
新時代、新蘇聯與新中國
國共的合作與分流
大戰陰影與安內攘外之挑戰
平壤之秋 一九四九─一九五四
猶豫不決的超級強權
屈從現實壓力的革命家
柳暗花明又一村
獨立與依賴 一九五五─一九六○
主權合法性競賽
歧路:走向獨立與深化依賴
三角關係質變及其影響
第三世界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
美蘇兩極結構之鬆動
升溫中的邦交戰
不平靜的南方邊界
北京與曼哈頓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布拉格、珍寶島與華盛頓
國際地位大逆轉
從兩條線到一大片
關係正常化 一九七六─一九八一
後強人時期來臨
三角關係再度質變與重塑
兩岸外交消長之深化
巨變前夕 一九八二─一九八九
向錢看與外交理性化
冷戰三角最後一幕
統一問題之進展與挑戰
後冷戰 一九八九─二○○七
陰影下的新時代
慢慢走出去
另一場最漫長的戰爭
邁向戰國時代 二○○八迄今
畫上句點之冷戰秩序
中國崛起與美中區域對抗
不確定之世界均勢
後記
新時代、新蘇聯與新中國
國共的合作與分流
大戰陰影與安內攘外之挑戰
平壤之秋 一九四九─一九五四
猶豫不決的超級強權
屈從現實壓力的革命家
柳暗花明又一村
獨立與依賴 一九五五─一九六○
主權合法性競賽
歧路:走向獨立與深化依賴
三角關係質變及其影響
第三世界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
美蘇兩極結構之鬆動
升溫中的邦交戰
不平靜的南方邊界
北京與曼哈頓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布拉格、珍寶島與華盛頓
國際地位大逆轉
從兩條線到一大片
關係正常化 一九七六─一九八一
後強人時期來臨
三角關係再度質變與重塑
兩岸外交消長之深化
巨變前夕 一九八二─一九八九
向錢看與外交理性化
冷戰三角最後一幕
統一問題之進展與挑戰
後冷戰 一九八九─二○○七
陰影下的新時代
慢慢走出去
另一場最漫長的戰爭
邁向戰國時代 二○○八迄今
畫上句點之冷戰秩序
中國崛起與美中區域對抗
不確定之世界均勢
後記
書摘/試閱
從莫斯科到遠東 / 一九一八─一九四九
起自一九四九年之中國外交史(或兩岸之對外關係)所以具有特殊性,至少直到二十世紀末為止,原因主要來自兩岸之間因競逐單一主權與正統性所引發的對立、衝突與相互牽制。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承緒中國自清季以來的國際弱勢地位,此期間之衝突緣由,最初雖基於不同政治團體為爭取統治權所致,外部因素(特別是若干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強權國家)所佔之關鍵地位實不容忽視。至於相較多數人或更關切美國扮演的角色,此處則試圖將起點拉到一九一七年後開始發生質變的中蘇關係上。如同毛澤東的名言一般,「十月革命砲聲一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斯列寧主義」,事實上,俄國革命送來的絕不只是思想,更是一個歷史轉捩點。
新時代、新蘇聯與新中國
國際結構重組與革命浪潮 兩岸之分裂與競爭固然源自冷戰,但所謂冷戰絕不單單只是由於美蘇雙方利益存在不可妥協之處罷了。為了更深入理解其來龍去脈,我們需要一個更宏觀敘事之框架來加以指引,至於其起點則是在一次大戰摧毀舊秩序後,未來混沌未明又充滿各種可能的一九二○年代。
一九二○年代的世界顯然正邁向一個嶄新的階段。由於其具有之特殊意義,個人將它稱之為「一個重整的時代」(a re-constructed era)。前述名詞帶有兩個重要的描述性意涵:首先是「舊世界」(特別指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在經歷第一次大戰創傷後,試圖重建自身結構及社會價值秩序之過程;其次則是「新世界」(歐洲以東的地區,包括俄國和整個亞洲)藉此契機努力思索自我轉型之道,希冀能拉近與進步西方的距離。至於美國,此際不啻是蟄伏在側、猶豫不決但伺機而動的旁觀者。
與歐洲在十五、六世紀自視為舊大陸不同,在此所謂「新舊」之分,是指在邁向現代時期(Modern Age)後,歐洲以其「先驅者」角色首先進入產業革命階段,繼之又以十九世紀一連串社會主義思潮及政治改革措施重組其社會結構,最終使得以歐洲為首的區域,加上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形成具有一定「文化凝聚力」的世界核心地帶,從而扮演著推動全球化浪潮的火車頭。相對於歐洲,後起的俄國與亞洲不啻是新加入的夥伴。儘管前者自十九世紀以來始終被視為是歐洲權力平衡體系的一員,實則在認知上始終是西歐眼中的「他者」。它們普遍具有傳統的社會特徵,例如農民仍佔據人口絕大多數,缺乏足夠中產階級,以及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甚至還未工業化)等,和工業革命前歐洲的發展狀況頗為類似。無論如何,在十九世紀末葉,部分農民由於內部政治動亂而自願或被迫地脫離解體中的農村,加入並成為城市工人先驅,創造了有限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則正逐漸萌芽。
為了解決歐洲資本滲透與內部社會動盪所帶來的壓力,部分「新世界」國家紛紛推動制度變革以圖自救,俄羅斯與中國都不例外。不過,如同托克維爾的真知灼見,「經驗告訴我們,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革命往往並非爆發於被苛政折磨最深之時,而是情況開始改善,人們有了呼吸空間、開始省思、相互溝通想法,並依據過去狀況來衡量自己的權利與苦痛之際,桎梏雖已減輕,反而顯得更加讓人難以忍受。」這段文字雖針對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卻與十九世紀末俄羅斯與中國統治者的處境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在中國於一九一一年迎來一個「意外成功的革命」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則為俄國轉型提供了關鍵催化劑。
從某個角度看來,俄國革命看來也不無意外性,如同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所言,至少針對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這場起事沒有計劃,未經協調,連職業革命家也只能跟在後面隨波逐流」,當城市底層平民自發性走上聖彼得堡街頭時,當時流亡瑞士蘇黎世的列寧,如同一九一一年在紐約獲知武昌起義訊息的孫文,瞬間都恍然有些超現實感受,但他隨即掌握情勢,高喊「土地、和平、麵包、自由」口號,結合了相對剝奪感與戰爭挫折,領導多數農民起而推翻控有全國一半以上土地,並擁有政治權力的地主(約僅兩萬人左右),同時企圖以激烈而從未被嘗試過的手段(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設法加快社會轉型以趕上西方舊世界。於此同時,歐戰也暫時抑止了西方對中國繼續經濟滲透與傾銷,使其得以藉此契機擴大工業化腳步,一方面創造出少量城市工人,另則一股社會主義潮流也逐漸在知識界蔓延開來。
概言之,這也是個「變革的時代」,只不過西方社會是「由上而下」地在穩定方面下工夫,而東方的新世界則期盼「由下而上」去重建結構,並嘗試一種具挑戰性的,甚或全新的生活方式。
蘇聯的世界觀及其中國政策 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理想主義者在一九一七年成功建立起一個新國家,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國家,也是某種高度「烏托邦式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在現實中首次被大規模地實踐。
但列寧及其同伴的野心並不止於此,其目標是全世界。
俄國革命者高舉的大旗是,「行將到來的我們是其前鋒隊的世界革命,……屆時各國人民將聯合成一個大家庭。」這和馬克思主義終極目標基本上一致,相較過去幾個世紀聚焦「西方中心」之狹隘歷史觀,這亦是第一個將目光投射至全球範圍的思想。正如列寧在全俄羅斯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中所言:「我們不但善於英勇地進攻,也善於英勇地退卻,等到國際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幫助我們,我們就要在世界範圍內開始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由此,「第三國際」於焉誕生,列寧也進一步闡釋其目標,「第一國際奠定了對資本主義革命之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第二國際雖繼續推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但投機取向終究拉低了它的革命水準,至於第三國際則致力去除投機主義、社會沙文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垃圾,從而確實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目的是領導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單就馬克思(Karl Marx)本人而言,其內在思想雖隱含有「世界革命」的擴張性,目光毋寧還是注視著歐洲的,但面對一九二○年代「舊世界」透過各種福利措施重整社會結構,此起彼落的共產運動紛紛歸於失敗,於是迫使第三國際的領導者必須重估其革命道路。無論列寧在一九一三年所言「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抑或托洛斯基的看法「歐洲的革命看來已經退到幕後,毫無疑問,我們本身也已經從西方退到東方;……國際形勢正以這樣的方式表現得十分明顯,即通往巴黎和倫敦的道路在於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一些城鎮」,都代表了蘇共領袖對其主義擴散路徑之反省,以及對人口明顯眾多且深具潛力之東方亞洲世界的重視。
雖然對歐洲外交仍舊是重中之重,為貫徹前述戰略想法,革命後的蘇聯對中國採取了「雙軌外交」政策,首先是以「宣言攻勢」爭取好感,另則以實際談判來維護固有利權。據此,蘇聯首先由外務委員會委員翟趣林(G. V. Chicherin)在一九一八年宣稱:「蘇俄自願放棄沙皇政府在滿州地區的掠奪所得,恢復中國在此地區的主權,……蘇俄同意放棄俄羅斯人在中東、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權,並準備放棄一切賠款,……如若獲得與中國之協議,蘇俄擬放棄中東路之特權,並將南滿支線售予日本。」這段話基本上延續了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和平命令》的政策精神,也是加拉罕日後宣言的張本,但具體意義不大,原因之一是它並非正式對外政策,其次則中國方面早在六個月前便已接收中東路並進行改組。不過,蘇聯仍在一九一九年趁「五四運動」民情輿論激昂之際展開第二波攻勢,加拉罕發表〈致中國國民及北方與南方政府宣言〉,此即所謂〈第一次對華宣言〉,強調蘇聯政府「即將俄皇政府自行侵奪,或偕日本及其他聯盟國共同侵奪之中國人民之所有者,一概歸還中國人民。……將中東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產及他種產業,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放棄中國因一九○○年拳匪之亂而負欠之賠款」。儘管北京政府遲至一九二○年三月才得到該文件的抄本,此宣言仍得到蘇聯預期的反應。例如北京的全國學生聯合會隨即致電蘇聯政府:「你們這次的大舉動,足為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我們自當盡我們所能,與貴國恢復邦交。」《天津益世報》稱:「此實為世界人類從來未有之義舉。」《上海救國日報》也說:「這封通牒,恐怕是要開世界之先例,……如果把這些話都實行盡致了,我們中國在國際上所受不平允的待遇,一定可以擺脫。」
就在中國內部這種熱烈應和的氣氛下,加拉罕再於一九二○年九月草擬了〈第二次對華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他雖重申了首次宣言之重要內容,但至少存在兩點差異:首先是前次宣言性質較廣泛,對象是「中國人民及南、北政府」,此次目標則直指「中國外交部」,特別是受各國法律承認的北京政府,因之政治意涵愈濃;其次,相較前次宣言強調「無條件歸還」與「毫不索償」,這次則轉稱「由中俄兩國政府商定專約」,對中東路問題也非無條件歸還。
伴隨著加拉罕「宣言攻勢」的是另一條談判路線,第一個主角則是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Ignatius L. Yourin)。該國乃是蘇聯在東方所成立的臨時性緩衝國,主要任務有三,首先是追擊並徹底殲滅白俄勢力,其次是與國際交涉,促使日本自西伯利亞東部撤軍,最後則是與中國作試探性接觸,以解決中東路與外蒙問題。上述第三個目標正是優林於一九二○年來華時欲解決的首要任務,但沒有任何具體結論,且隨著該國與蘇聯合併,此一任務乃由巴意開斯、越飛與加拉罕等來自莫斯科的代表接手。在談判中,中東路爭議與外蒙問題乃焦點所在。中東路向來是舊俄經營北滿地區的生命線,且經南滿支線亦可打開前往北京的通道,因此具有經濟和軍事雙重價值。至於蒙古也一直是俄國南下主要發展對象之一,因其進則可窺略東北、新疆和黃河流域,退則又可藉戈壁沙漠自保,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汲汲於帝國主義者固有利益不免與蘇共理想邏輯相矛盾,若從革命政權對於政治穩定性之追求看來,蘇聯正因堅持意識形態異端(共產主義)而遭到西方刻意冷落孤立,此際莫斯科對獲得外國承認和國內支持的殷切需求,當有助於瞭解其行為。可以這麼說,為拉攏中國,於是有翟趣林和兩次加拉罕宣言,而為了爭取自身民眾的支持,又必須堅持在中東路和外蒙的立場。
蘇聯與孫文之接觸嘗試 儘管根據保障利益之短期角度,蘇聯主要交涉對象乃北京的直系政府與東北的奉系軍閥,但它在此同時嘗試與廣州孫文政權接觸,對未來中國歷史顯然埋下更關鍵的影響。
一九一九年底,亟欲外援的孫文在上海與俄籍軍官波布夫(Popoff)交換意見。翌年,吳廷康也會晤孫氏並嘗試交流若干合作可能。接著是一九二一年在桂林與孫文碰面的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後者向其解釋蘇聯正進行之計劃性新經濟政策,建議國民黨改組並建立軍校,且約略提到與中共合作事宜。最後是一九二二年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達林(Serge Dalin)建議國共組成聯合陣線。儘管馬林與達林的「合共」建議都被拒絕了,蘇聯拉攏孫文之意圖仍極為明顯,理由則大致有三項:第一,孫中山乃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革命領袖;第二,中共初期組織發展相當薄弱,改組中的國民黨不啻提供一個可資合作與利用的政治軀殼;第三,共產黨與孫文之間存在「反軍閥」的共同目標。因此,即便孫文尚躊躇未決,中共仍在第三國際核准下於一九二二年通過下列決議:「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必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由另一層面視之,此決議顯然有「聯絡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意味,因為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畢竟仍是個「資產階級」意識頗濃的政黨。
儘管如此,若欲瞭解此時期蘇聯與孫文密切互動之背景,或還是得對當時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環境進行深入觀察才行。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年的訪華之行雖褒貶不一,他在回國後仍做出如下結論,「既然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而即使中國人不對其他國家人民產生影響,中國問題本身也是個意義深遠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事態發展,無論如何都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未來兩百年歷史將表明,中國人何去何從,將是影響整個世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儘管此一睿智「預言」迄今已逐漸證明其前瞻性,一九二○年代的中國顯然正面臨著巨大的衝擊與挑戰,變化主要呈現在兩個面向上:首先是軍閥持續混戰所引起的上層政治結構解體,其次則是隨著戰火、肆意掠奪、橫徵戰費、交通混亂與市場秩序破壞所帶來的農村崩潰。正如小島晉治與丸山松幸指出:「民族產業的凋蔽,造成失業和勞動條件降低,強迫勞動者做更大的犧牲。並且由於廉價和有利關稅大增的外國製日常用品(約佔總輸入七成)侵透到農村,給予副業的手工業以重大的打擊,把農村經濟不容分辯地納入世界商品市場。隨著農民物資購買率上升,上升的比率部分就造成經濟農產物。多為小規模經營,又為苛捐、酷稅與債務所逼迫的農民,不能不以任人擺佈的價格將農產賣了出去。以棉花大豆為首,中國農村變成低廉原料供應地的趨勢愈來愈顯著。」
中國的農村基礎本即不甚穩固,尤其經過太平天國蹂躪及外國勢力介入後,傳統結構即非蕩然無存,至少已不復原有風貌,換言之,中國的「舊社會」正面臨著無可避免的崩潰命運。若進一步檢視,不難發現崩潰的根源乃由於體系本身自我控制機制失調所致:當中國的「農業-官僚」結構與西方的「商業-資本」體系接觸後,舊社會顯得脆弱且不堪一擊。即便如此,「社會主義式的階級覺醒」未必應運而生,因為它還少了點催化的種子。直到一九一七年後,隨著這粒種子在遙遠的俄國生根發芽,中國也在一九二○年代掀起了一股思想狂潮,非但「以社會主義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乃當時許多自由派學者希望所繫,各種相關專欄論文、雜誌專號、口號和學術團體亦紛紛出籠,結果使全國上下「有若著了瘋魔一般」。究其原委,首先自然是俄國革命成功的刺激,其次則一次戰後日本同樣社會主義思潮澎湃,隨後經譯作而影響中國亦不容忽視,最後,中國學界在長久沉悶後,亦藉此於困境中尋找抒發出口。
就某方面看來,這種風潮或不過是象牙塔中的宣言,對當時處於分裂中的國家並無裨益。除一九一九年上海南北和平會議最後終歸失敗之外,北方也隨即爆發了兩次軍閥混戰(一九二○年直皖戰爭與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最後,南方的孫文一度在一九一八年被改組為「七總裁制」的軍政府架空權力,北走上海,但不久又藉陳炯明之助回粵,與舊皖系段祺瑞以及奉系張作霖共組「三角同盟」以圖北伐。不過,上述這些起落浮沉雖支配了一九二○年代前期的中國政治,畢竟只是歷史軌跡上的小插曲,真正的重頭戲則正在醞釀當中:一九二二年,受到陳炯明叛變所激的孫文,決定改組國民黨並創建黨軍,而蘇聯勢力也正藉中共有計劃地深入中國,於是對中國現代史影響深遠的兩大政治組織(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了首度交集。必須這麼說,交集的表面是個政治事件,其內涵卻根植於社會轉型的巨大力量中,至於結果則影響了其後半個世紀以上中國與東亞的發展,甚至迄今猶存。
起自一九四九年之中國外交史(或兩岸之對外關係)所以具有特殊性,至少直到二十世紀末為止,原因主要來自兩岸之間因競逐單一主權與正統性所引發的對立、衝突與相互牽制。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承緒中國自清季以來的國際弱勢地位,此期間之衝突緣由,最初雖基於不同政治團體為爭取統治權所致,外部因素(特別是若干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強權國家)所佔之關鍵地位實不容忽視。至於相較多數人或更關切美國扮演的角色,此處則試圖將起點拉到一九一七年後開始發生質變的中蘇關係上。如同毛澤東的名言一般,「十月革命砲聲一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斯列寧主義」,事實上,俄國革命送來的絕不只是思想,更是一個歷史轉捩點。
新時代、新蘇聯與新中國
國際結構重組與革命浪潮 兩岸之分裂與競爭固然源自冷戰,但所謂冷戰絕不單單只是由於美蘇雙方利益存在不可妥協之處罷了。為了更深入理解其來龍去脈,我們需要一個更宏觀敘事之框架來加以指引,至於其起點則是在一次大戰摧毀舊秩序後,未來混沌未明又充滿各種可能的一九二○年代。
一九二○年代的世界顯然正邁向一個嶄新的階段。由於其具有之特殊意義,個人將它稱之為「一個重整的時代」(a re-constructed era)。前述名詞帶有兩個重要的描述性意涵:首先是「舊世界」(特別指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在經歷第一次大戰創傷後,試圖重建自身結構及社會價值秩序之過程;其次則是「新世界」(歐洲以東的地區,包括俄國和整個亞洲)藉此契機努力思索自我轉型之道,希冀能拉近與進步西方的距離。至於美國,此際不啻是蟄伏在側、猶豫不決但伺機而動的旁觀者。
與歐洲在十五、六世紀自視為舊大陸不同,在此所謂「新舊」之分,是指在邁向現代時期(Modern Age)後,歐洲以其「先驅者」角色首先進入產業革命階段,繼之又以十九世紀一連串社會主義思潮及政治改革措施重組其社會結構,最終使得以歐洲為首的區域,加上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形成具有一定「文化凝聚力」的世界核心地帶,從而扮演著推動全球化浪潮的火車頭。相對於歐洲,後起的俄國與亞洲不啻是新加入的夥伴。儘管前者自十九世紀以來始終被視為是歐洲權力平衡體系的一員,實則在認知上始終是西歐眼中的「他者」。它們普遍具有傳統的社會特徵,例如農民仍佔據人口絕大多數,缺乏足夠中產階級,以及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甚至還未工業化)等,和工業革命前歐洲的發展狀況頗為類似。無論如何,在十九世紀末葉,部分農民由於內部政治動亂而自願或被迫地脫離解體中的農村,加入並成為城市工人先驅,創造了有限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則正逐漸萌芽。
為了解決歐洲資本滲透與內部社會動盪所帶來的壓力,部分「新世界」國家紛紛推動制度變革以圖自救,俄羅斯與中國都不例外。不過,如同托克維爾的真知灼見,「經驗告訴我們,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革命往往並非爆發於被苛政折磨最深之時,而是情況開始改善,人們有了呼吸空間、開始省思、相互溝通想法,並依據過去狀況來衡量自己的權利與苦痛之際,桎梏雖已減輕,反而顯得更加讓人難以忍受。」這段文字雖針對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卻與十九世紀末俄羅斯與中國統治者的處境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在中國於一九一一年迎來一個「意外成功的革命」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則為俄國轉型提供了關鍵催化劑。
從某個角度看來,俄國革命看來也不無意外性,如同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所言,至少針對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這場起事沒有計劃,未經協調,連職業革命家也只能跟在後面隨波逐流」,當城市底層平民自發性走上聖彼得堡街頭時,當時流亡瑞士蘇黎世的列寧,如同一九一一年在紐約獲知武昌起義訊息的孫文,瞬間都恍然有些超現實感受,但他隨即掌握情勢,高喊「土地、和平、麵包、自由」口號,結合了相對剝奪感與戰爭挫折,領導多數農民起而推翻控有全國一半以上土地,並擁有政治權力的地主(約僅兩萬人左右),同時企圖以激烈而從未被嘗試過的手段(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設法加快社會轉型以趕上西方舊世界。於此同時,歐戰也暫時抑止了西方對中國繼續經濟滲透與傾銷,使其得以藉此契機擴大工業化腳步,一方面創造出少量城市工人,另則一股社會主義潮流也逐漸在知識界蔓延開來。
概言之,這也是個「變革的時代」,只不過西方社會是「由上而下」地在穩定方面下工夫,而東方的新世界則期盼「由下而上」去重建結構,並嘗試一種具挑戰性的,甚或全新的生活方式。
蘇聯的世界觀及其中國政策 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理想主義者在一九一七年成功建立起一個新國家,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國家,也是某種高度「烏托邦式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在現實中首次被大規模地實踐。
但列寧及其同伴的野心並不止於此,其目標是全世界。
俄國革命者高舉的大旗是,「行將到來的我們是其前鋒隊的世界革命,……屆時各國人民將聯合成一個大家庭。」這和馬克思主義終極目標基本上一致,相較過去幾個世紀聚焦「西方中心」之狹隘歷史觀,這亦是第一個將目光投射至全球範圍的思想。正如列寧在全俄羅斯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中所言:「我們不但善於英勇地進攻,也善於英勇地退卻,等到國際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幫助我們,我們就要在世界範圍內開始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由此,「第三國際」於焉誕生,列寧也進一步闡釋其目標,「第一國際奠定了對資本主義革命之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第二國際雖繼續推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但投機取向終究拉低了它的革命水準,至於第三國際則致力去除投機主義、社會沙文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垃圾,從而確實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目的是領導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單就馬克思(Karl Marx)本人而言,其內在思想雖隱含有「世界革命」的擴張性,目光毋寧還是注視著歐洲的,但面對一九二○年代「舊世界」透過各種福利措施重整社會結構,此起彼落的共產運動紛紛歸於失敗,於是迫使第三國際的領導者必須重估其革命道路。無論列寧在一九一三年所言「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抑或托洛斯基的看法「歐洲的革命看來已經退到幕後,毫無疑問,我們本身也已經從西方退到東方;……國際形勢正以這樣的方式表現得十分明顯,即通往巴黎和倫敦的道路在於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一些城鎮」,都代表了蘇共領袖對其主義擴散路徑之反省,以及對人口明顯眾多且深具潛力之東方亞洲世界的重視。
雖然對歐洲外交仍舊是重中之重,為貫徹前述戰略想法,革命後的蘇聯對中國採取了「雙軌外交」政策,首先是以「宣言攻勢」爭取好感,另則以實際談判來維護固有利權。據此,蘇聯首先由外務委員會委員翟趣林(G. V. Chicherin)在一九一八年宣稱:「蘇俄自願放棄沙皇政府在滿州地區的掠奪所得,恢復中國在此地區的主權,……蘇俄同意放棄俄羅斯人在中東、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權,並準備放棄一切賠款,……如若獲得與中國之協議,蘇俄擬放棄中東路之特權,並將南滿支線售予日本。」這段話基本上延續了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和平命令》的政策精神,也是加拉罕日後宣言的張本,但具體意義不大,原因之一是它並非正式對外政策,其次則中國方面早在六個月前便已接收中東路並進行改組。不過,蘇聯仍在一九一九年趁「五四運動」民情輿論激昂之際展開第二波攻勢,加拉罕發表〈致中國國民及北方與南方政府宣言〉,此即所謂〈第一次對華宣言〉,強調蘇聯政府「即將俄皇政府自行侵奪,或偕日本及其他聯盟國共同侵奪之中國人民之所有者,一概歸還中國人民。……將中東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產及他種產業,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放棄中國因一九○○年拳匪之亂而負欠之賠款」。儘管北京政府遲至一九二○年三月才得到該文件的抄本,此宣言仍得到蘇聯預期的反應。例如北京的全國學生聯合會隨即致電蘇聯政府:「你們這次的大舉動,足為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我們自當盡我們所能,與貴國恢復邦交。」《天津益世報》稱:「此實為世界人類從來未有之義舉。」《上海救國日報》也說:「這封通牒,恐怕是要開世界之先例,……如果把這些話都實行盡致了,我們中國在國際上所受不平允的待遇,一定可以擺脫。」
就在中國內部這種熱烈應和的氣氛下,加拉罕再於一九二○年九月草擬了〈第二次對華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他雖重申了首次宣言之重要內容,但至少存在兩點差異:首先是前次宣言性質較廣泛,對象是「中國人民及南、北政府」,此次目標則直指「中國外交部」,特別是受各國法律承認的北京政府,因之政治意涵愈濃;其次,相較前次宣言強調「無條件歸還」與「毫不索償」,這次則轉稱「由中俄兩國政府商定專約」,對中東路問題也非無條件歸還。
伴隨著加拉罕「宣言攻勢」的是另一條談判路線,第一個主角則是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Ignatius L. Yourin)。該國乃是蘇聯在東方所成立的臨時性緩衝國,主要任務有三,首先是追擊並徹底殲滅白俄勢力,其次是與國際交涉,促使日本自西伯利亞東部撤軍,最後則是與中國作試探性接觸,以解決中東路與外蒙問題。上述第三個目標正是優林於一九二○年來華時欲解決的首要任務,但沒有任何具體結論,且隨著該國與蘇聯合併,此一任務乃由巴意開斯、越飛與加拉罕等來自莫斯科的代表接手。在談判中,中東路爭議與外蒙問題乃焦點所在。中東路向來是舊俄經營北滿地區的生命線,且經南滿支線亦可打開前往北京的通道,因此具有經濟和軍事雙重價值。至於蒙古也一直是俄國南下主要發展對象之一,因其進則可窺略東北、新疆和黃河流域,退則又可藉戈壁沙漠自保,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汲汲於帝國主義者固有利益不免與蘇共理想邏輯相矛盾,若從革命政權對於政治穩定性之追求看來,蘇聯正因堅持意識形態異端(共產主義)而遭到西方刻意冷落孤立,此際莫斯科對獲得外國承認和國內支持的殷切需求,當有助於瞭解其行為。可以這麼說,為拉攏中國,於是有翟趣林和兩次加拉罕宣言,而為了爭取自身民眾的支持,又必須堅持在中東路和外蒙的立場。
蘇聯與孫文之接觸嘗試 儘管根據保障利益之短期角度,蘇聯主要交涉對象乃北京的直系政府與東北的奉系軍閥,但它在此同時嘗試與廣州孫文政權接觸,對未來中國歷史顯然埋下更關鍵的影響。
一九一九年底,亟欲外援的孫文在上海與俄籍軍官波布夫(Popoff)交換意見。翌年,吳廷康也會晤孫氏並嘗試交流若干合作可能。接著是一九二一年在桂林與孫文碰面的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後者向其解釋蘇聯正進行之計劃性新經濟政策,建議國民黨改組並建立軍校,且約略提到與中共合作事宜。最後是一九二二年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達林(Serge Dalin)建議國共組成聯合陣線。儘管馬林與達林的「合共」建議都被拒絕了,蘇聯拉攏孫文之意圖仍極為明顯,理由則大致有三項:第一,孫中山乃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革命領袖;第二,中共初期組織發展相當薄弱,改組中的國民黨不啻提供一個可資合作與利用的政治軀殼;第三,共產黨與孫文之間存在「反軍閥」的共同目標。因此,即便孫文尚躊躇未決,中共仍在第三國際核准下於一九二二年通過下列決議:「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必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由另一層面視之,此決議顯然有「聯絡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意味,因為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畢竟仍是個「資產階級」意識頗濃的政黨。
儘管如此,若欲瞭解此時期蘇聯與孫文密切互動之背景,或還是得對當時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環境進行深入觀察才行。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年的訪華之行雖褒貶不一,他在回國後仍做出如下結論,「既然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而即使中國人不對其他國家人民產生影響,中國問題本身也是個意義深遠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事態發展,無論如何都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未來兩百年歷史將表明,中國人何去何從,將是影響整個世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儘管此一睿智「預言」迄今已逐漸證明其前瞻性,一九二○年代的中國顯然正面臨著巨大的衝擊與挑戰,變化主要呈現在兩個面向上:首先是軍閥持續混戰所引起的上層政治結構解體,其次則是隨著戰火、肆意掠奪、橫徵戰費、交通混亂與市場秩序破壞所帶來的農村崩潰。正如小島晉治與丸山松幸指出:「民族產業的凋蔽,造成失業和勞動條件降低,強迫勞動者做更大的犧牲。並且由於廉價和有利關稅大增的外國製日常用品(約佔總輸入七成)侵透到農村,給予副業的手工業以重大的打擊,把農村經濟不容分辯地納入世界商品市場。隨著農民物資購買率上升,上升的比率部分就造成經濟農產物。多為小規模經營,又為苛捐、酷稅與債務所逼迫的農民,不能不以任人擺佈的價格將農產賣了出去。以棉花大豆為首,中國農村變成低廉原料供應地的趨勢愈來愈顯著。」
中國的農村基礎本即不甚穩固,尤其經過太平天國蹂躪及外國勢力介入後,傳統結構即非蕩然無存,至少已不復原有風貌,換言之,中國的「舊社會」正面臨著無可避免的崩潰命運。若進一步檢視,不難發現崩潰的根源乃由於體系本身自我控制機制失調所致:當中國的「農業-官僚」結構與西方的「商業-資本」體系接觸後,舊社會顯得脆弱且不堪一擊。即便如此,「社會主義式的階級覺醒」未必應運而生,因為它還少了點催化的種子。直到一九一七年後,隨著這粒種子在遙遠的俄國生根發芽,中國也在一九二○年代掀起了一股思想狂潮,非但「以社會主義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乃當時許多自由派學者希望所繫,各種相關專欄論文、雜誌專號、口號和學術團體亦紛紛出籠,結果使全國上下「有若著了瘋魔一般」。究其原委,首先自然是俄國革命成功的刺激,其次則一次戰後日本同樣社會主義思潮澎湃,隨後經譯作而影響中國亦不容忽視,最後,中國學界在長久沉悶後,亦藉此於困境中尋找抒發出口。
就某方面看來,這種風潮或不過是象牙塔中的宣言,對當時處於分裂中的國家並無裨益。除一九一九年上海南北和平會議最後終歸失敗之外,北方也隨即爆發了兩次軍閥混戰(一九二○年直皖戰爭與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最後,南方的孫文一度在一九一八年被改組為「七總裁制」的軍政府架空權力,北走上海,但不久又藉陳炯明之助回粵,與舊皖系段祺瑞以及奉系張作霖共組「三角同盟」以圖北伐。不過,上述這些起落浮沉雖支配了一九二○年代前期的中國政治,畢竟只是歷史軌跡上的小插曲,真正的重頭戲則正在醞釀當中:一九二二年,受到陳炯明叛變所激的孫文,決定改組國民黨並創建黨軍,而蘇聯勢力也正藉中共有計劃地深入中國,於是對中國現代史影響深遠的兩大政治組織(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了首度交集。必須這麼說,交集的表面是個政治事件,其內涵卻根植於社會轉型的巨大力量中,至於結果則影響了其後半個世紀以上中國與東亞的發展,甚至迄今猶存。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