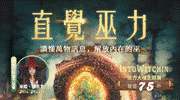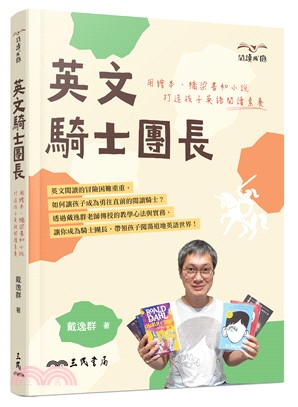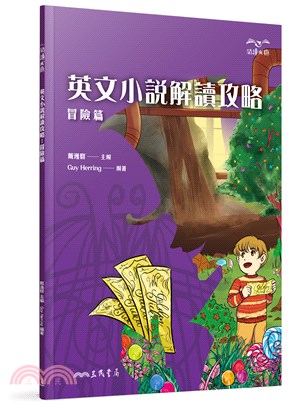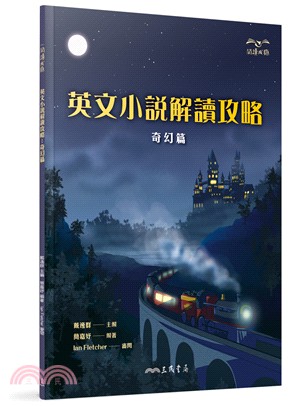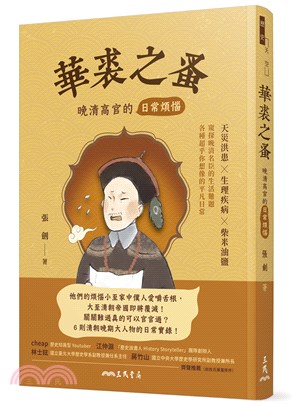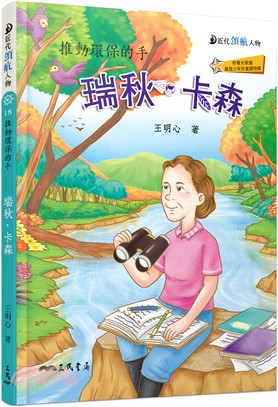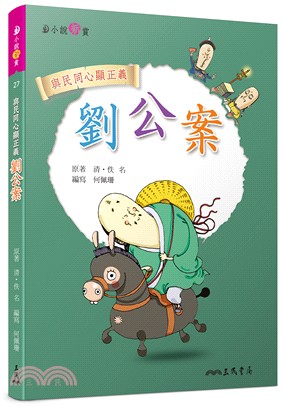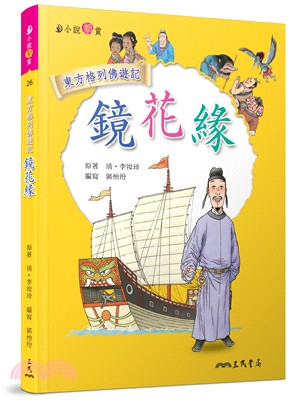商品簡介
啟動未來文學無限時鐘
時間與零的迷宮競走賽事,此刻開始
字母T到Z狀擬文學對時空之創生潛能。時間的每一刻皆測不準,猶如世界任何一處都無關此在,由是書寫自未知處張開全新眼界,捕捉沃林格式動態生機,萬籟之音穿透生命的單義性齊聲奏鳴,作品從無有處裂生而出,再於終/起點歸零時刻返抵未來。
《字母會:從零度到未來》屬於字母會實驗寫作計畫的最終一部分成果,字母A到字母S過去曾部分在《短篇小說》刊登,且已陸續出版成冊。本次春山出版將發行的是T到Z七冊,這七冊是作家在近三年來最新的創作成果,此次出版將銜接上七年前字母會開始的那一刻,意味著字母會實驗寫作計畫之終了,但它正是文學的意義上的真正開始。《字母會:從零度到未來》為T到Z七冊限量套書,特別在專屬書盒上燙上流水序號,且在最後一冊《字母會Z零》書中,邀請全程參與二十六個字母寫作計畫的核心八位成員親筆簽名。
《字母會:從零度到未來》套書七冊內容如下:
字母會T時間
楊凱麟—策畫/胡淑雯、張亦絢、陳雪、童偉格、黃崇凱、駱以軍、顏忠賢—小說/潘怡帆—評論
有事件,是因為有著使事件暴長而出的時間,有流變,因為有使流變湧現竄逃的時間……,如果有作品,是因為有使其成為可能的獨特時間性。
時間在文學裡一刻與恆常互文見義。張亦絢描述女同志洞見金箔時光,燼滅後自我祝福的餘生;黃崇凱捕捉網友與炮友間並非全無真意,卻總錯時落拍的時光間隙;陳雪躲進婚與愛乾涸後,現實擠壓出的每個十分鐘;胡淑雯筆下的小女孩預習「姦殺」二字,來複習權力的黑色暴力;童偉格取徑一通告知母親自殺緊急電話,抵達家鄉橫看生死兩面的碑塚山頭;駱以軍描繪從火柴盒般房子到廢墟之間的時光,只是如看紀錄片般考古與拾遺;顏忠賢寫困於幻聽與法會之人,持續在業與夢中擺盪壞掉的生命指針。
字母會U單義性
楊凱麟—策畫/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黃崇凱、駱以軍、顏忠賢—小說/潘怡帆—評論
每個存在物都表達差異的聲音,經驗分歧而零亂,嘩嘩響著龐大的聲浪,毫不相同亦毫不同調,但這些聲音其實都傾訴著「存有被訴說的單一意義」。
文學的單義是無窮的收納術。胡淑雯剪歪女孩頭髮,凸顯建制與權利只不過是可笑歪曲了的規矩;童偉格讓離婚者結婚、生者託孤,顯現結合與分離不可能各如其義;駱以軍以基因改造種子失去傳統種子的繁殖能力,猶如初戀之吻一去不返,無靈光之物即便存在無異於消失;黃崇凱使工傷被輾斷手臂的少年娶先天殘疾之妻,漸漸習慣了生活退讓,無異於先天缺乏;顏忠賢描述大樓自來水斷水引出焦慮,如嗅到自身內在乾涸的惡臭;陳雪進入夢中與舊情人爭吵,述說愛與痛的完了與未完並進。
字母會V 虛擬
楊凱麟—策畫/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黃崇凱、駱以軍、顏忠賢—小說/潘怡帆—評論
不可見卻又決定現實的虛擬分子雲霧才是小說中的真正誘惑,文學在此直抵事物的創造性潛能。
虛擬張開一個絕不實存卻得以進入的世界。駱以軍讓被稱為精神分裂者的說故事,再以AI關機使故事說之不盡;黃崇凱描述神愛世人卻不愛同性戀,此可釋義教徒的「愛」說一套做一套;胡淑雯收下老同學的無緣無故送的香水,而在閨香酒醇之間嗅出騙子的真意;陳雪以約炮及錯聊一個月情色電話,投射出渴忘愛情的自我形變;顏忠賢寫在治痛的短暫夢境內,重歷畢生的痛與劫;童偉格通過小說化島津、太宰治與蕭紅展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學性指向」,因其就是虛擬本身。
字母會W沃林格
楊凱麟—策畫/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黃崇凱、駱以軍、顏忠賢—小說/潘怡帆—評論
沃林格使得完全不同於古典心靈的另類生命成為獨特的美學問題,從此生命成為一種怪異的、高張力與高動態的表達,充滿暈眩……
沃林格闡揚哥德式大教堂落地後仍鎮日鼓動,文學則是擱筆後始生機蓬勃。陳雪將失憶的女人帶至陌生的城市,再由被騙的情人揭露其自身謊言;黃崇凱的夢中列車載著長日所思入夜再搖晃而出;胡淑雯以對性的未知與坦然,逼騷擾者掉入困窘的沉默;童偉格在停靈的家屋貼糊滿滿舊報,而人們徒勞地注視往故與流散;駱以軍點亮空總的廢墟,使絢爛與鬼火皆再次搖曳;顏忠賢描寫游泳入迷者,帶著其一生的偏執與不安在池底湧竄。
字母會X 未知
楊凱麟—策畫/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黃崇凱、駱以軍、顏忠賢—小說/潘怡帆—評論
對於小說應該問:什麼是這本小說所重新問題化且總是變幻無踪的「事物=X」?
未知數X幻化文學題式與解答。顏忠賢筆下小說家X拚命代入偉大作家,卻在自己的作品裡碎裂;黃崇凱使〈在畢加島〉流亡者們在不可能的時刻就地歸返;童偉格描寫在客運順行公路與操場練跑迴圈中目送生命光景;駱以軍在哥們聊著將迎接的機械狗時,忽然淚憶故犬,以此哀悼無法寄存於科技的文明;陳雪前往男色酒吧買賣春色,意外拾起破碎心裡尚存的溫柔;胡淑雯的性服務者在限時開放的洞口,試圖為失性者探索生命未至的疆域。
字母會Y 眼
楊凱麟—策畫/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黃崇凱、駱以軍、顏忠賢—小說/潘怡帆—評論
特異之眼(或耳)內建於作品中,文學賦予我們所沒有的陌異之眼,我們由此開始觀看。
文學之眼從全新觀看點看出絕無僅有的光景。黃崇凱進入印傭客家華僑女子的身體,攬看關於閩客、性別、移工種種歧見;胡淑雯以女童的眼光,觀照外婆被國家剝奪丈夫的病痛與寂苦;陳雪鋪陳如鏡對照的美好青少男女純情,如何在自我逼視中起火燃盡;駱以軍將班級鬥戰拆成漫畫式分鏡,使一瞬可無限次重播重演;顏忠賢看著陰陽眼與乩身中層疊太多交錯的身世,過度張開了眼而無力闔上;童偉格寄存人們離去前對著山谷家屋的拜別,當神靈不再遶境、賽鴿盤桓遠颺、一切隱沒之時,唯一張開動態的即小說之眼。
字母會Z零
楊凱麟—策畫/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黃崇凱、駱以軍、顏忠賢—小說/潘怡帆—評論
書寫的零度是解放的預感,文學的時代總是由此重新揭開,零。
零度意味著起點、開始與歸零、重新開始,文學須從未知的路徑全新出發,並在完成時再度歸零。童偉格描寫護送一顆母親自栽的西瓜,繞經清明節後無可回返的事物後重獲時序;陳雪在女同志伴侶人工受孕的對話裡勾出腦海深處墮掉仍存活的嬰孩;駱以軍以字母B曾被讀書會以零票評價的事件反手轉出字母會投給未來宇宙的片言;顏忠賢將肛門視為肉身的零點、破洞與盡頭,須將死物排空以抵達未來;胡淑雯讓小女孩成熟於看穿掠奪者裝作若無其事地拿取,不若真正的給予者不說半分;黃崇凱筆下日本姪子欲描寫作家伯父,試圖理解臺日情結與語文藩籬,然在作品裡互為虛構,一切必得從零開始。
作者簡介
胡淑雯
一九七○年生,臺北人。著有長篇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短篇小說《哀豔是童年》;歷史書寫《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主編、合著);主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合編)。
張亦絢
一九七三年生於臺北木柵。著有長篇小說《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等
陳雪
一九七○年生,臺中人。著有長篇小說《無父之城》、《摩天大樓》、《迷宮中的戀人》、《附魔者》、《無人知曉的我》、《陳春天》、《橋上的孩子》、《愛情酒店》、《惡魔的女兒》等。
童偉格
一九七七年生,萬里人。著有長篇小說《西北雨》、《無傷時代》;短篇小說《王考》;散文《童話故事》;舞臺劇本《小事》。
黃崇凱
一九八一年生,雲林人。著有長篇小說《文藝春秋》、《黃色小說》、《壞掉的人》、《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短篇小說《靴子腿》。
駱以軍
一九六七年生,臺北人,祖籍安徽無為。著有長篇小說《明朝》、《匡超人》、《女兒》、《西夏旅館》等。
顏忠賢
一九六五年生,彰化人。
策畫簡介 楊凱麟
評論簡介 潘怡帆
目次
《字母會T時間》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Temps
T如同「時間」――楊凱麟
時間――張亦絢
黃崇凱
陳雪
胡淑雯
童偉格
駱以軍
顏忠賢
T評論――潘怡帆
《字母會U單義性》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Univocité
U如同「單義性」――楊凱麟
單義性――胡淑雯
童偉格
駱以軍
黃崇凱
顏忠賢
陳雪
U評論――潘怡帆
《字母會V虛擬》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Virtuel
V如同「虛擬」――楊凱麟
虛擬――駱以軍
黃崇凱
胡淑雯
陳雪
顏忠賢
童偉格
V評論――潘怡帆
《字母會W沃林格》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W. Worringer
W如同「沃林格」――楊凱麟
沃林格――陳雪
黃崇凱
胡淑雯
童偉格
駱以軍
顏忠賢
W評論――潘怡帆
《字母會X未知》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X
X如同「未知」――楊凱麟
未知――顏忠賢
黃崇凱
童偉格
駱以軍
陳雪
胡淑雯
X評論――潘怡帆
《字母會Y眼》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Yeux
Y如同「眼」――楊凱麟
眼――顏忠賢
黃崇凱
童偉格
駱以軍
陳雪
胡淑雯
Y評論――潘怡帆
《字母會Z零》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Zéro
Z如同「零」――楊凱麟
零――顏忠賢
黃崇凱
童偉格
駱以軍
陳雪
胡淑雯
Z評論――潘怡帆
書摘/試閱
《字母會Z零》L’abécédaire de la littérature: Zéro
〈Z評論〉――潘怡帆
字母終局,盡皆歸零。零,暗示前二十五個字母所築起的精神與思考都都需抹除,而後重置。然而零亦不是徹頭至尾皆沒有,因為無感於零,則零不存在。必須接連二十五次的積累才有抹除的可能。於是所有的努力無非為了歸零,為了棄絕一切,推倒積累,堅定地說「沒有」。因為文學創造無關建樹,而是從典範離開。彌賽亞以毀滅帶來新世界的希望,諾亞方舟航行在世界淹沒不在的洪水上,張無忌棄絕張三丰演練的劍法,才練就太極劍的奧義;盡逝後能重新開始,拋棄即創造的起源。脫離太陽神阿波羅奠定的白晝律法,迎向酒神的璀璨毀滅。零,因而是最劇烈的運動,為了從究極的寂靜中引爆最震攝人心的狂喜,於是,歸零。
童偉格的字母Z逆向起跑,撥轉歸零,敘事各自由結局倒行原初,從母親托送西瓜講回主角與姊在此前的矛盾,已然葬身海底的阿明爬回海面,逆溯生前。死亡一路倒轉往出生前,小說裡的所有運動都成為結局已定的徒勞掙扎,阿明再返來也無法取消自己的死亡,描述父親無法換回活生生的他,就像《獵人格拉庫斯》即使馬不停蹄地移動也無從離開死亡之域。童偉格從零度鑿出無法納入計算的時間倒敘,召喚運動不可能的芝諾詭論,使開始一再退回開始的開始,永遠無法真正踏出零度以外。小說主角把母親的西瓜送往姊姊的處所,恍如薛西弗斯推石的純粹勞動並不增加任何收穫,或如海角母親們將稻田囤積成工廠,再將荒壞工廠收拾成游滿蝦蟹的溝渠農地,彷彿工廠從未存在;看電視的姊姊每逢廣告時間,便拿出清潔滾輪悠哉沾粘四處毛屑,廣告結束她爬回電視機前,像廣告或清潔的時光未曾有過。童偉格縫合重複(農田、連續劇),摺入差異(工廠、廣告、清潔)成不可見的內襯。小說提醒,冬天的海絕不單調,而是將「非洲草原那萬獸聚集的氣魄」覆蓋在表面無事的零度空間底下。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輕》裡提到,「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像壓根兒沒有發生過」,童偉格則在字母I說:「發生過兩次以上的事,會等於沒發生過」;昆德拉認為,差異若不經重複的辨識而命名,那麼,不被認識的差異最終將無法存在,然而童偉格提醒我們,必須經由重複來命名的差異,將指認重複而非差異,並且最終取消差異,等於「沒發生過」。差異不可知,即零度,它或無法辨識,或因重複而質變,由是我們理解了小說中對羅蘭巴特二次喪母的引用。巴特發覺自己注定喪母兩次,初次是母親過世,第二次則是「當她遁回無可記憶那刻。」巴特回顧死去母親的一生,他一路反向追索母親的舊照,從中年、結婚、少女退回最初時刻,此前再無,感到母親再度消亡。完整圈寫的生命史弔詭地並未使巴特擁有全部的母親,反而導致二度喪失,因為當母親以一個總體形象被蓋棺論定時,正意味著她的結束,就像唯有當時代告終時,我們才能為之命名。古典時期宣告著古典的滅亡,浪漫派的歸類敲響浪漫派的喪鐘,小說裡的阿明必須回家兩次才能終結人子的任務,父親的亡故必須經歷兩次葬禮(埋葬與撿骨再葬)來確認。巴特母親的死亡不在於肉體的消亡,而在回顧她一生後;當我們回顧二十五個字母,最終必然走向歸零的道路:「我們不外乎,都是她[母親]已消亡的後裔。」消亡並非結束,而如普魯斯特所謂地質斷層的變動,那必然誕生與前不同的後裔們,踩著過去的養分,長出全然異質的新芽,就像童偉格在字母G對維柯《新科學》的引用,我們終將成為養分,壯大未來。因而歸零不是結束,而是為了更新世界,為了打開新思考而結束一種思考。字母Z由童偉格打頭陣,帶著字母會對未來文學的祝福,唯有「背過一切人為的荒漠,第一次,他們才看見從未見識過的海洋」。從字母零之後,字母會與所有的讀者「就是兩名獲有時序的正常人了」,迎向另一個將臨的文學時刻。
童偉格按下倒數計時的碼錶,啟動回顧歸零的最後程序,接棒的陳雪提出古典與當代小說的形式交接,以對話體與意識流書寫展開零的二重性:零的胎動與歸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小說開場於幾對拉子好友討論著人工生殖的懷孕計畫,用科幻與夢幻壯大純屬女子間密謀的求子計畫。對話讓虛空的子宮逐漸隆起,開始受孕:美國來的精子,郵寄到柬埔寨診所待命,先到婦產科檢查,再用中藥調養身體,冒著事後爭奪小孩的風險跟男同志形式婚姻,拉子之間還有誰的卵和誰生的問題,生一個好還是兩個都生?簡單一點就到酒吧一夜求子,複雜的程度也能擴延至操控小孩的血統、品種、星座,還有如何教養小孩等問題。不存在的寶寶纏祟著你來我往的話語空間,愈描摹愈具體,他尚未存在卻已長成帶著華裔面孔的混血兒、A型血、雙子座,已被未來的母親深愛,亦深陷不被歡迎,反對兼恐嚇的家族風暴中。寶寶不在,卻從對話中分娩出來,他以缺席的方式現身,既是又不只是零而蠢蠢欲動。主角「她」以意識流的思考切換眾人嘩啦啦的對話產子,她曾人工流產一個孩子,於是思想運動開始從飽脹想像的胎動轉向墮胎歸零的程序。已經在三年前摘除子宮再不能生兒育女的「她」回想起徹底歸零以前的人生,「她不可能生育不可能撫養不可能結婚不可能的愛情繼續著只因為無法停止,說不定只是因為賀爾蒙作祟費落蒙起乩因為男人總不愛保險套可是他們也不愛小孩到底用了沒用保險套自己也弄不清楚……她愛著不能分開也無法好好相處的男人她不能生下他的孩子」。不同於表面積極實則謹小慎微的計劃生子,意識流則將翻騰巨浪掩藏在無波瀾的如鏡大海下。主角「微笑著續聽朋友們交談準備生養製造一個孩子必須耗盡所有存款五十萬八十萬一百萬到底夠不夠能不能製造一個生命」,同時憶起迫使歸零的前導節奏正是愈來愈高升與一無反顧的瘋狂。那種翻覆天地,不容片刻喘息、遲疑或反省的強迫,將在旋起所有瘋狂、愛欲、死亡與災難後直撲歸零。在熱烈往來對話中受孕的孩子,被蜷曲於內心不可見的意識流世界默默斬殺,奔騰的話流最終只為了完成一個最終與自己切斷關係的零。由是,陳雪通過意識流凸顯歸零前的徒勞運動,潛藏於意識卻四處亂竄的意義不斷湧現,五味雜陳卻無法一以貫之地簡單道出,千頭萬緒狂風驟雨般的拚命說,同時亦是什麼也沒說的逕自沉默。由是,歸零並非徹頭至尾不曾易改的平靜,而是主角不動聲色底下的波濤洶湧,是陳雪關門前留下空無一物的巨大迴聲:「沒有也存在。」
陳雪講述無存在的迴聲,駱以軍則展演凌空探物的文學手勢。小說描寫一個文學讀書會對《字母會B巴洛克》中諸篇小說進行投票討論,敘事者寫的那篇出乎意料地得到零分。「零」經由投票的單刀直入被賦予平板的印象:瞬間判死、取消存在的任何一絲價值、毫不猶豫的把迴圈封死的零,換言之,一個無厚度且無足輕重的點。然而這些關於「零」的意義,卻與敘事者在書寫過程中投注作品的意象毫無半點接近:「我的書寫琴弦,在編織繃緊並鎖上各個金屬絲的螺絲時,我洋溢著書寫的歡悅……那篇作品在書寫時光,架備情節,驅動想像,賦予魔術……經過手工藝,使之存在於某種活物的神祕流動。」毫無負重,宛如初生的零精確標誌或兌換一樁處心積慮的計算,純手工搭字配詞,通過離開慣習的詞組而切割出能塞入更多想像的字距空隙,流暢的閱讀隱藏著讓字詞無法安分的鋪排,由是鬆動方塊字,揚落一身塵土,漫開滿室飛旋錯落的意義群落。無盡膨脹的寫作宇宙究竟如何在瞬間塌縮為零?極大極小的反差結構成循環的無限運動。敘事者回憶二十年寫作一再復始的經驗,每次從「虛妄拉出一座空中閣樓、時間簡史、不存在的大冒險」,就會有一次不同模式的「密室裡的震爆、率然臨之的罪名,讓我驚駭莫名,欲辯忘言――事實上,我學習寫小說之初,完全沒有學習,如何在小說之外,小說寫完拋擲出去之後,替自己的作品、人格、敗德、惡行……辯解」,然而,盡滅歸零的時刻總已不由分說地降臨。極致繁複而後系統盡滅的一再重演,驗證「零」毫不輕薄,並非初生而無知的開始,而是「開始總已重新開始」。就像阿茲特克文明建起的「神之城」等待被殖民者破壞殆盡成荒土,或在語言發明前,一切的生物,所有蠕蟲、海中魚群、蝴蝶、蜥蜴、烏龜、鳥、斑馬、巤狗、獅子、長頸鹿、甚至狒狒……在那幾百萬、幾千萬、幾億年間,努力的交配、覓食、演化,全是活在一種「等語言出現,最後這一切都要被取消活著」。由是,歸零總已通過重啟,同時承擔了洗掉幾億年間的積累或精密文明的沉重,它有別於無知或興之所致地開始,而是在通曉自己將爆破的世界是何等龐大後,仍決定一意孤行且承擔一切的勇氣。小說提到,每一個零度都內在凹摺著一個宇宙大小:「宇宙是從單一的點爆發而產生,這個點的大小大概和一個原子差不多。我們所知的一切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都以超乎想像的密度一且塞在這單一的點中」;每一次的關閉都超載著把一個族群壓扁成零的重量,「那些痞子西班牙人,轉過身,將大批眼前轉瞬死亡的奴隸,挖鑿的銀礦,轉運回歐洲,那持續發展成後來的故事,我們現在置身其中的世界。」因而沒有無辜的零,只有將文明踐踏成廢墟而就地重建,踩著被侮辱被損害之人的「殘骸、血水,吃著從他們以哀號交換過來的這個文明美食」那樣滿身罪孽(而非輕薄如無物)的零,那樣幾近不可承受的零。而面對字母會那二十五次層疊築起的奇景怪境,與即將爆破的歸零,敘事者唯一提請「謙遜」,對於即將展開與過去摧毀的,提請慎重地記憶。班雅明的天使面向過去,倉皇且沉重地重新回到零的開始。
倘若駱以軍將字母會編寫成魔幻寫實的Z劇場,顏忠賢則以肛門象形,展開字母Z的肉身戲仿(parodie)。巴代伊在《太陽肛門》(L’Anus solaire)中提到:「生命是戲仿的,且短缺了解釋。」戲仿出於調侃、嘲諷、遊戲或致敬等目的,使兩個不相干的事物彼此相連。每個事物都是對另一事物的戲仿,一旦它們被繫動詞「是」接連成句子,便激活大腦反思,旋出燒腦的循環,生命由此暴動而繁衍:繫動詞(copule)是性交(copulation),大腦是赤道,零是肛門。繫動詞「是」成為性愛到極致激狂的連接體,指認想像生命的起源。然而,由戲仿展開的生殖無非是腦內風暴,無名火的狂躁,沒有任何事物會被實質認出,一再變形的戲仿,構成無處棲居的純粹遊牧。循環的起點亦是終點,所有的出發都是為了折返,反摺回空洞,從肛門反摺回零。小說遊走在一個接一個的灌腸經驗,肛門來往於收縮又舒張的展演,從零度通向另一個零度:灌腸藥水進入後,必須HOLD住,「沒有忍住太快拉出來所有的藥就沒用了」,因而必須零洩出地絕對收縮。然而,一旦洞口敞開,肛門亦盡瀉不留,禁食、瀉藥,加上灌水水療,只出不進的無盡歸零,以便抵達「饑餓的狀態迴響出的最底層回聲」。空無一物與回聲,像鳥鳴盤繞出幽谷,回聲是對一無長物的再確認。敘事由拉肚子、排泄、大腸水療築成一道不斷掏空的洩洪通道,跟著療程同時吐露的一切心聲、過往、羞恥感、心灰意冷、匪夷所思的細節、惡夢、好奇與諸多疑慮成為遺留在通道上,必須徹底淨空而即將報廢的言說。因而小說裡的言說無非是為了拋棄,為了歸零所必須卸下的障礙與廢棄物,它們偽裝成臟器而乍看像作品,其實是作品的剩餘,就像小說提到,第一次見到宿便的驚奇:「看到嚇一跳因為像是拉出自己一段腸子……就像自己退化的殘體局部……破器官。」水療患者開始紛紛道出各自關於肛門宿疾的史前史,雷同的經歷沒有因為重複而被抑制,周而復始的節奏呼應著巫師對修行者的反覆忠告:「用心想像用你的肛門來修行……把心拿走。」剔除核心,剩下空殼,顏忠賢把肛門從慾望的心理學名詞凹折成禁絕一切的苦修鍛鍊,從盈滿生育力的巴代伊轉進無腔調的貝克特,展演了布朗肖意義下的中性言說(parole neutre):重複而無人在聽的話、無法停止一再說起的話,亦是使所有言說陷入永恆拒絕言說而歸零的貝克特之言。
顏忠賢用滔滔不絕的說展演言說缺席,胡淑雯則掏空核心而歸零。小說開篇提到:「假如你真心掛念一個人,那個人會變成一團謎,化身為各種意想不到的樣子或『沒有樣子』,襲卷任何可能的符號與意象而來,讓困惑隨思念與遺忘一併加深。假如你一點也不在乎那個人,他反而必須老老實實的,以寫實主義的文法現身,方便你指認出來。」這個區辨奠定了小說的法則:被寫下來的將不是重要的,無法被寫下來的,才是敘事者真正在意的事。敘事者娓娓講述小學五年級時遭受隔壁班導性騷擾的過程。在公車上老師身上噴得香香的,飽含關懷與讚美的語言幻術,用修長手指乾乾淨淨的步步逼近,敘事者耐心等候老師犯罪意圖的落實,以便拋棄尊師重道的倫理綁架,理直氣壯地離開現場。她三番兩次改換上學路線與時間,不願接受老師用來賄賂她成為性共犯的作弊……,在屏氣凝神與老師對戰之間,敘事者絲毫不顯怯懦或驚恐,因為這一切毫無新鮮而且都已曾經發生:「四、五歲的時候,住在博愛院的單身老兵做過,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美術老師在地下室也做過,他們的方法,手感與氣息都差不多。」隔壁班導只是一個「二手貨帶來的二手經驗」,連讚美都只是二手的。重複與二手的反覆提醒,一再削弱做為小說主軸的性傷害的重要性,凸顯那通過表面重複勞動的運輸中,被差異賦予的知識啟蒙,就像書寫重述事件,使更深刻的反省從字裡行間浮現。重複的傷害使敘事者能置身事外地學會更重要的事,那是藉由出手與惡意所領悟的「一旦」、「卑鄙」與「愛」的深意。「一旦你起手犯規,我就知道怎麼辦了……當即將成為現在」,便一翻兩瞪眼的讓曖昧不明著床成黑白分明的判斷;「將過期的禮品轉贈給僕傭」無非就是卑鄙;而真正的愛,是父親「透過無盡的勞動,將每一分所得奉獻給小孩……字詞困在剛強的下巴之中,被洶湧的羞澀阻斷」。胡淑雯以一則故事的軀殼提請我們注意,真正重要的不在表面。表面,是終於歸零的字母Z,然而真正重要的是那尚未被言明的重新啟程。開始在乍初時刻無法被察覺或訴說,必須經由事件才能定錨開端,因而開始總已是對開始的回溯,開始總已重新開始。開始的開始至關重要(它將導引整個事件)卻又無法言說,因為開始在它所不在之處,在開始結束後開始。開始總已經開始,因此,開始只能通過與之不符的結束來指認,而結束總已施放開始的信號彈。由是,字母會在第二十六個字詞之後,歸零。
經歷五位作者的先後歸零,壓陣的黃崇凱描摹一位關門的入門弟子,呼應字母Z。字母會的最後一字,黃崇凱並未呈顯幾經努力終於修得正果的恢宏氣勢,相反,敘事者以寫作見習生的身分出場,由是,結尾並非結束,而是等待進場。敘事者開始構思一樁寫作計畫,尚未啟動的作品將填塞入過去的材料:「我一直想找個比較適切的角度來寫伯父」。已發生被尚未發生重新包裹,就像呈顯於鴨仔蛋內外兩重不一致的時間,還未啟動的時間零度由是並非沒有時間,而是裝載著另一種時間的流湧,誠如楊凱麟對此篇的描述,在一則未來的歷史中,時空對稱凹摺的中心是過去,「字母Z除了有故事的多重塞進摺入之外(字母P的迴返),更以一種時態上的『先未來式』(futur antérieur)從事時間的複式疊加。小說中的小說各自持存在臺、日的不同時間與生命處境之中……每一則小說於是都成為其他小說的鏡像,都同時已經「塞進」所有小說的處境,也都已經是另一則小說敘事者說出的故事。」伯父舊日的作品將構成敘事者未來寫作的素材,已完成之作重新成為生產新作的原料,通過未來的寫作轉世出另一重面貌。然而,像輪迴般既是零也不是零的重生,弔詭地,並未被安排成垂直的繼承,而是旁系橫移。敘事者要重寫的對象不是父親,而是伯父,他在伯父舊作裡找到的並非伯父,而是「以我父親為原型角色的」父親。乍看一脈相承的香火開始錯亂。敘事者的父親像所有日本父親一樣,是個沉默寡言的臺灣移民,敘事者通過伯父短篇小說裡的敘事,臨摹父親的心境,然而,敘事者同時提到:「父親與伯父不算特別親近,平常各過各的生活,偶爾才交換、更新一些近況。」其實不了解哥哥的父親,就像總是搞錯弟弟職業的伯父,他們無太多交集的生命使伯父指認父親的可信度存疑。敘事者曾就伯父一篇撰寫弟弟找他商量選日本名字的小說,向父親求證內容,父親「確實有請伯父幫忙想姓名,不過伯父並未如小說寫的那樣熱切幫父親擬出備選清單」。此外,伯父〈宇都宮〉裡描繪了像是臺灣省道旁的豪華升級版的賣廠商家,「但事實上,宇都宮郊區周邊的道路景觀,就像日本其他地方城鎮,到處是那些了無生趣的連鎖店家、便利超商和大型柏青哥店,並不通往什麼豪華升級的版本。」作品於是並非事實的原樣再現,伯父的作品不通往父親或伯父,更甚,敘事者描述與研究的並非與己直接共時的伯父的新作,而是間隔十五年的舊作。小說末了「早就過氣」的震撼彈說明這不僅不是一脈相傳的連續繼承,而是左拐右彎的枝節旁生,與被空檔時間割裂的斷代繼承。旁系、錯認與代溝把非正統、不一致、不對等與不均勻的思考注入敘事者,使他具有關門的入門弟子的核心意涵。在關門前入門,意味著弟子親蒞見證的並非最輝煌的鼎盛時期,而是煙花散盡的殘餘,是為了寫下結論前來的最末之人。然而弟子的見習無非從灰燼中掘出已逝的繁華榮景,從廢墟中虛擬塔頂的天際線,敘事者從未看過伯父創作,卻想由中斷書寫十五年、對話不超過二十句的尋常臺南人身上召喚作家伯父。所見與所是的分歧就像臺灣父親到日本落地生根,日本兒子回臺灣寫小說,伯父查看讀不懂的日文書,姪兒研習著不可逆溯的歷史,四面八方的錯接,編織起這幅讓見習生反覆臨摹,卻實際上有別於原圖重現的系譜想像圖像。只能擁抱殘餘與幻象的關門弟子,就像楊凱麟所言:「幽靈般的文學存有模式似乎是悲觀的。」然而,弟子所關上的將不會是任何既存的原件,因此關上總已重啟創造。霍伯葛里耶(Robbe-Grillet)於是能向我們宣告,一個特別可悲的時代同時特別可期,繼承的系統已破舊,熵質已盡,便迎來了一個新發明的世代。
楊凱麟以「未來」吹響字母會的號角,以「零」揮動文學革命的旗幟。經歷二十六個字母之後,文學將再度碎片四射,迎向不可重複的文學景觀。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