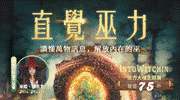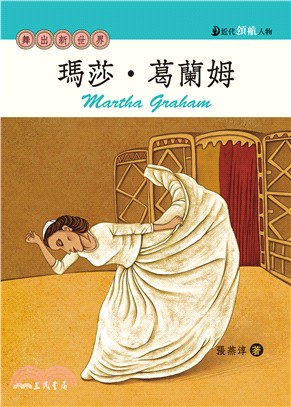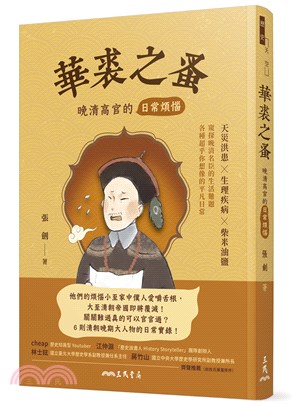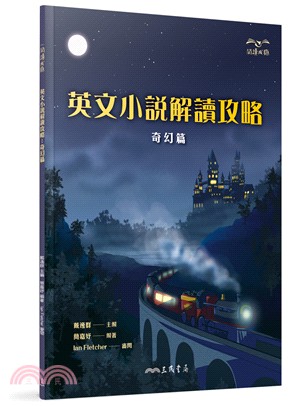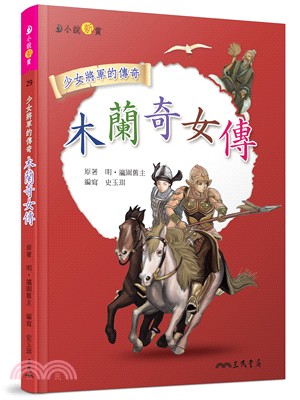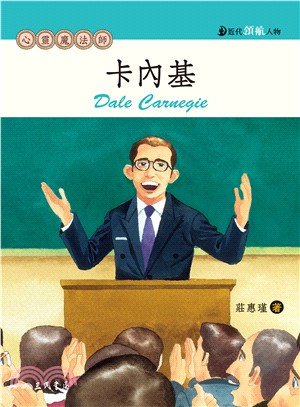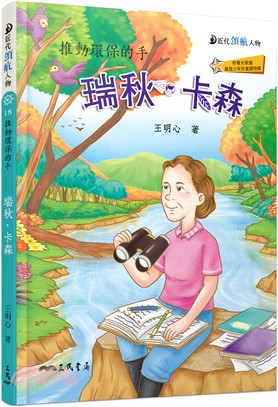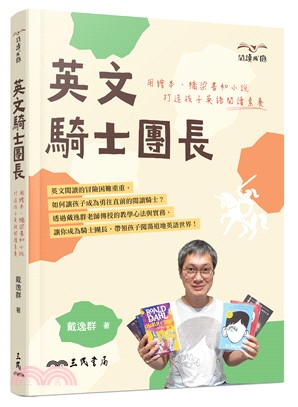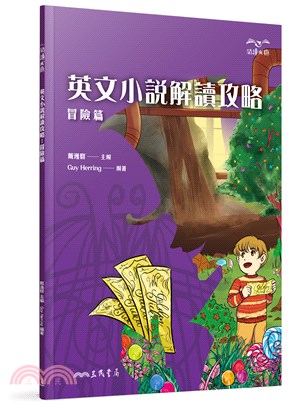阿鼻劍前傳卷一:封印重啟
商品資訊
系列名:Dala Plus
ISBN13:9789866634994
替代書名:ABI-SWORD: Prequel Volume One
出版社:大辣
作者:馬利MA LI
出版日:2020/02/06
裝訂/頁數:平裝/416頁
規格:21cm*15cm*3.1cm (高/寬/厚)
重量:581克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542【七年級】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阿鼻劍前傳》小說╱暫定3冊
編劇馬利醞釀30年的大作
和鄭問一起獻給《阿鼻劍》所有讀者
鄭問《阿鼻劍》漫畫,從一九八九年問世,前後出版過兩集之後,不只從此成為武俠漫畫的經典,也給眾多讀者留下漫長的等待。
勿生到底想起了什麼前世?他和阿鼻第九使者到底是什麼關係?阿鼻劍到底是什麼來歷?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過去三十年,大家不斷在詢問。
現在,《阿鼻劍前傳》的小說,終於開始和大家見面了。
《阿鼻劍》漫畫版的第三集有過短暫的兩回。當時是把勿生回憶起的前世,和他的現世交錯進行。
而小說版的《阿鼻劍前傳》,則是集中寫前世,寫阿鼻劍的由來,寫勿生如何由摩訶劍的大護法轉變為阿鼻使者,甚至再成為尊者。整個故事則透過阿鼻第九使者的旁觀和回憶來敘述。
小說的背景,在五代十國的亂世。人間與地獄難分的亂世。
十九歲的平川,從一個在客棧裡跑堂的少年,抱著夢想,想要見識外面的天地,一步步走入人生的險境,但也有了平常人畢生難求的奇遇。
他在走投無路要自殺的時候,遇上了讓他生命得以昇華的嬋兒。
他在殺了第一個人之後,遇上了愛他如痴的小青。
小說的第一個脈絡,是在講平川的少年成長,逐步如何遇上勿生,成為阿鼻第九使者。
小說的第二個脈絡,則是在講摩訶劍莊大護法勿生,如何由各方的正派人物遭到暗算,不得已走上自己迴避多年的路,重啟阿鼻劍封印,大開殺戒,震動四方。
小說的第三個脈絡,則是阿鼻劍的由來,為什麼和勿生有眾多糾結,以及勿生如何封印,又要花上如何代價重啟封印。
漫畫版裡的司劍、十八惡道,也都在前傳中紛紛亮相。
看過漫畫版的讀者,一定會因為看到這些脈絡的展現而興奮!
沒看過漫畫版的讀者,也會因為故事本身的曲折引人而入迷!
《阿鼻劍前傳》目前暫定三卷。
2020年2月出版的是〈卷一:封印重啟〉。
這是一本武俠小說。
這是一本愛情小說。
這也是一本青春與成長的小說。
《阿鼻劍》漫畫的由來
鄭問第一部黑白水墨作品
一九八九年郝明義決定創辦《星期漫畫》,找了導演楊德昌當監製,並且頭陣作家鎖定了三位:麥仁杰、曾正忠,以及鄭問。麥仁杰以《鳥人》,曾正忠以《花心赤狐》,鄭問以《阿鼻劍》,又曾經是《刺客列傳》的讀者,所以他給自己留了一個和漫畫家鄭問共同合作的機會,以筆名「馬利」化身劇作家,這就是阿鼻劍的起源……
鄭問畫風融合中國水墨技法與西方繪畫技巧,細膩而大膽,作品充滿豪邁灑脫的豪情俠意。一九九○年受日本重要漫畫出版社講談社的邀請,在日本發表描繪中國歷史故事的《東周英雄傳》,引起轟動。一九九一年更獲得日本漫畫家協會「優秀賞」,他是這個大獎二十年來第一位非日籍的得獎者。日本《朝日新聞》讚嘆他是漫畫界二十年內無人能出其右的「天才、鬼才、異才」,日本漫畫界更譽為「亞洲至寶」。
極具詩意的武俠漫畫
《阿鼻劍》是國內漫畫創作的傳奇之一,也是鄭問的漫畫創作轉捩點,他獨特的水墨畫法,將武俠漫畫帶入了新的層次;而編劇馬利則將原本武俠小說的元素精采地串連重組,並融入發人深省的佛義,使得這部武俠漫畫有別於一般武俠的刀光劍影,有了更深的意涵。
編劇馬利表示,一開始,《阿鼻劍》就有「前世」、「今生」的設計。我和鄭問合作的兩部《阿鼻劍》,第一部〈尋覓〉、第二部〈覺醒〉,都是「今生」的前半段。我的想法是:先用這兩部來讓今生的「何勿生」登場,然後回頭講他的前世,最後再來講他覺醒之後,今生要執行的是什麼。這樣,我和鄭問合作,而有了三十年前出版的兩部《阿鼻劍》漫畫。
編劇馬利醞釀30年的大作
和鄭問一起獻給《阿鼻劍》所有讀者
鄭問《阿鼻劍》漫畫,從一九八九年問世,前後出版過兩集之後,不只從此成為武俠漫畫的經典,也給眾多讀者留下漫長的等待。
勿生到底想起了什麼前世?他和阿鼻第九使者到底是什麼關係?阿鼻劍到底是什麼來歷?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過去三十年,大家不斷在詢問。
現在,《阿鼻劍前傳》的小說,終於開始和大家見面了。
《阿鼻劍》漫畫版的第三集有過短暫的兩回。當時是把勿生回憶起的前世,和他的現世交錯進行。
而小說版的《阿鼻劍前傳》,則是集中寫前世,寫阿鼻劍的由來,寫勿生如何由摩訶劍的大護法轉變為阿鼻使者,甚至再成為尊者。整個故事則透過阿鼻第九使者的旁觀和回憶來敘述。
小說的背景,在五代十國的亂世。人間與地獄難分的亂世。
十九歲的平川,從一個在客棧裡跑堂的少年,抱著夢想,想要見識外面的天地,一步步走入人生的險境,但也有了平常人畢生難求的奇遇。
他在走投無路要自殺的時候,遇上了讓他生命得以昇華的嬋兒。
他在殺了第一個人之後,遇上了愛他如痴的小青。
小說的第一個脈絡,是在講平川的少年成長,逐步如何遇上勿生,成為阿鼻第九使者。
小說的第二個脈絡,則是在講摩訶劍莊大護法勿生,如何由各方的正派人物遭到暗算,不得已走上自己迴避多年的路,重啟阿鼻劍封印,大開殺戒,震動四方。
小說的第三個脈絡,則是阿鼻劍的由來,為什麼和勿生有眾多糾結,以及勿生如何封印,又要花上如何代價重啟封印。
漫畫版裡的司劍、十八惡道,也都在前傳中紛紛亮相。
看過漫畫版的讀者,一定會因為看到這些脈絡的展現而興奮!
沒看過漫畫版的讀者,也會因為故事本身的曲折引人而入迷!
《阿鼻劍前傳》目前暫定三卷。
2020年2月出版的是〈卷一:封印重啟〉。
這是一本武俠小說。
這是一本愛情小說。
這也是一本青春與成長的小說。
《阿鼻劍》漫畫的由來
鄭問第一部黑白水墨作品
一九八九年郝明義決定創辦《星期漫畫》,找了導演楊德昌當監製,並且頭陣作家鎖定了三位:麥仁杰、曾正忠,以及鄭問。麥仁杰以《鳥人》,曾正忠以《花心赤狐》,鄭問以《阿鼻劍》,又曾經是《刺客列傳》的讀者,所以他給自己留了一個和漫畫家鄭問共同合作的機會,以筆名「馬利」化身劇作家,這就是阿鼻劍的起源……
鄭問畫風融合中國水墨技法與西方繪畫技巧,細膩而大膽,作品充滿豪邁灑脫的豪情俠意。一九九○年受日本重要漫畫出版社講談社的邀請,在日本發表描繪中國歷史故事的《東周英雄傳》,引起轟動。一九九一年更獲得日本漫畫家協會「優秀賞」,他是這個大獎二十年來第一位非日籍的得獎者。日本《朝日新聞》讚嘆他是漫畫界二十年內無人能出其右的「天才、鬼才、異才」,日本漫畫界更譽為「亞洲至寶」。
極具詩意的武俠漫畫
《阿鼻劍》是國內漫畫創作的傳奇之一,也是鄭問的漫畫創作轉捩點,他獨特的水墨畫法,將武俠漫畫帶入了新的層次;而編劇馬利則將原本武俠小說的元素精采地串連重組,並融入發人深省的佛義,使得這部武俠漫畫有別於一般武俠的刀光劍影,有了更深的意涵。
編劇馬利表示,一開始,《阿鼻劍》就有「前世」、「今生」的設計。我和鄭問合作的兩部《阿鼻劍》,第一部〈尋覓〉、第二部〈覺醒〉,都是「今生」的前半段。我的想法是:先用這兩部來讓今生的「何勿生」登場,然後回頭講他的前世,最後再來講他覺醒之後,今生要執行的是什麼。這樣,我和鄭問合作,而有了三十年前出版的兩部《阿鼻劍》漫畫。
作者簡介
馬利MA LI
本名郝明義,1956年出生於韓國。現任大塊文化與Net and Books 董事長。
著有:《工作DNA》(增訂三卷)、《故事》、《那一百零八天》、《他們說》、《越讀者》、《一隻牡羊的金剛經筆記》、《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大航海時刻》、《尋找那本神奇的書》。譯著:《如何閱讀一本書》、《2001太空漫遊》。
與鄭問共同創作《阿鼻劍》漫畫,擔任編劇,以及2018年企畫《人物風流:鄭問的世界與足跡》。2019年幫鄭問點評三國人物在台灣全新出版《鄭問之三國演義畫集》。
個人網站:rexhow.com
facebook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rexhow.dna
本名郝明義,1956年出生於韓國。現任大塊文化與Net and Books 董事長。
著有:《工作DNA》(增訂三卷)、《故事》、《那一百零八天》、《他們說》、《越讀者》、《一隻牡羊的金剛經筆記》、《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大航海時刻》、《尋找那本神奇的書》。譯著:《如何閱讀一本書》、《2001太空漫遊》。
與鄭問共同創作《阿鼻劍》漫畫,擔任編劇,以及2018年企畫《人物風流:鄭問的世界與足跡》。2019年幫鄭問點評三國人物在台灣全新出版《鄭問之三國演義畫集》。
個人網站:rexhow.com
facebook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rexhow.dna
序
前言
火,在竄騰。
影子像巨大的黑色波浪,緩吞而落,又急升而上。
空中有一幅畫在飛盪。
畫中,黑鬚金角、全身墨綠的龍,和一條赤紅的巨蟒在歙張廝殺。
也在糾纏交配。
巨斧和銅撾交擊。
帶著雷鳴的劍影轟然而過。
一切歸於寂滅。
只有勿生的臉,在火熖閃動中時明時暗。
而他最後一句話氣息低弱,卻清楚:「等到我再醒來。」
是的。
等到他再醒來。三百三十年。
他交付我的任務。
沒有死亡,長生不老。
對此刻已經活了兩百八十七年的我來說,這個常人祈求不得的願望卻成了無從擺脫的糾纏。
不是任務。更像懲罰。
其實,幾乎就在看著他死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錯了。
我不該答應他的。
一起經歷過那些事情之後,我應該和他一起死在那裡的。
生命結束在那裡,才是善終。起碼,和他一起結束在那裡。
鐘鼓齊發,百樂琤琮之後,只剩孤弦單音,太寂寞,也太空洞。
空洞到錯亂。
起初,時間是快的。
快到只剩下眨動。一年如一日的眨動。
北風的呼嘯,夏夜的蛙鳴,都在眨動中更替。
再逐漸,時間是慢的。
慢到春日草葉上的露珠成了永恒的飽滿。
飽滿到讓人難以喘息。
還好,是進入第一百二十年吧,我找到這座洞窟,有了遁逃的去處。
不見任何光亮的山洞好找。沒有任何聲響的,難。
黑暗有了動靜,就會透出層次。
有了層次,就會波動。
而我只要靜止。
我需要在絕對的靜止中定坐。
坐到不知自己是從岩石中虯結而出,還是從地縫鑽入無邊的虛空。
我總想告訴自己:這就是死亡的面目。
或者,最接近死亡的距離。
但知道都不是。
因為最後,我還是會聽到一個潮浪般的聲音。
我的心跳。
將近三百年的光陰,把許多回憶的河道阻塞,留下模糊的水面。
隨著潮聲在水面浮起的殘木,像是指引,也像讓我攀附的依託。
所以,不是我找到記憶,而是記憶找到我。
但,又有什麼關係?
畢竟,如果他答應的日子沒錯,只要再過四十三年,就是我們重逢之日。
我也到了需要把記得的都整理一遍的時候。
我和勿生的相逢。
他之成為尊者。
風起八千里的征戰。
那最後一夜的到來。
以及為什麼要等待他復活的理由。
身為阿鼻第九使者,我所記得的。
跋
《阿鼻劍》漫畫,從一九八九年問世,前後出版過兩集之後,不只從此成為武俠漫畫的經典,也給眾多讀者留下漫長的等待。
勿生到底想起了什麼前世?他和阿鼻第九使者到底是什麼關係?阿鼻劍到底是什麼來歷?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過去三十年,大家不斷在詢問。
現在,《阿鼻劍前傳》,終於以小說的形式開始和大家見面了。
會寫成小說,開始是偶然的因素。
二○○八年,因為我和鄭問一直各有忙碌的事情,中斷的合作總是陰錯陽差而沒法接續,所以當時就動念先來嘗試寫小說看看。
但畢竟因為我從沒有寫過小說,那之前身為編劇和鄭問的合作經驗又太愉快,所以寫了沒多久就想偷懶,覺得還是先擱下,等未來再繼續和鄭問合作漫畫才是正道。
但是三年前鄭問去世,我們的合作再也不可能,於是要把接下來的故事寫成小說,就成了必然。
把這個三十年來一直在腦中斷續發展的故事,以小說形式寫出來,成了唯一的選擇。不只為了向讀者,也為了向鄭問有一個交待。
真正開始寫,是去年年初的事。寫到四月左右,一度很順手。但是接下來遇到瓶頸。中斷到七月底,才又接續。只是再不久,就又卡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鄭問所畫的漫畫版本《阿鼻劍》實在太精采了。
鄭問在《阿鼻劍》的跋裡說,因為兩人分工,有我在編劇,所以他可以把構思劇情的力量全部轉移到畫面的處理上,融入各種插畫理論與技法,發展出《阿鼻劍》獨樹一格的魅力。
同樣地,對身為編劇的我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兩人分工,有鄭問這樣的絕頂高手在繪圖,所以我不需要構思畫面的細節,而只要發展故事的脈絡、氛圍,在情節上可以跳躍前進。
然而,一旦我自己寫小說,挑戰就完全不一樣了。除了故事的脈絡、氛圍、情節,我必須自己照顧所有的畫面細節,而所有這些都是要用文字進行的。我必須用文字經營所有的畫面和細節,一如鄭問用圖像經營所有的畫面和細節。
我才嘗試寫第一本小說,覺得沒法做到鄭問那麼好。
在半夜的掙扎裡,我經常問鄭問:「為了不要破壞大家對《阿鼻劍》的印象,我還是不要寫下去了。該成為絕響的,就絕響如何?」
鄭問沒有回答過我。
但我畢竟還是不能放棄。
這麼多人等了這麼多年,他們總該知道一些事情到底怎麼了。
去年十一月,在我們的image3 非常圖像空間,有一位先生過來找我,指指他的頭髮,說是已經從濃黑等到花白。他說:他知道鄭問已經過世,但希望我另想辦法,讓他趁眼睛還行的時候,可以把這個故事看完。
於是,一次又一次地掙扎著,我還是一點點寫下去了。
能寫去的動力,也還是因為鄭問所畫的漫畫版本《阿鼻劍》實在太精采了。
雖然力有未逮,但我想那還是鼓勵,或者刺激我要把小說設法再寫好一點的動力。
所以我在寫的過程裡,還是會問鄭問問題。但換一種問法。
每寫到一個場面,我會停下來想一想他在處理漫畫的某些場面,問一下他:「你看如何?這樣還可以吧?」
當然,有時候我也會跟他說:「鄭問,幫我一下!別讓小說漏漫畫的氣啊!」
這樣,我努力著把《阿鼻劍前傳》的卷一〈封印重啟〉完成了。
《阿鼻劍》漫畫版的第三集有過短暫的兩回。當時是把勿生回憶起的前世,和他的現世交錯進行。
而小說版的《阿鼻劍前傳》,則是集中寫前世,寫阿鼻劍的由來,寫勿生如何由摩訶劍的大護法轉變為阿鼻使者,甚至再成為尊者。整個故事則透過阿鼻第九使者的旁觀和回憶來敘述。
時代的背景,則放在五代。
五代不只是亂世,不只有烽火,各種殘暴凶惡之事,不可思議。
我覺得那是一個人世和地獄的界限難分的年代,很適合阿鼻劍的情節發展。
要感謝的人很多。
專研五代史的陳弱水教授,和他的高足黃庭碩,費心指點我許多那個時空的細節;曾孜榮的校閱;大辣編輯洪雅雯、設計師楊啟巽在最後階段的全力配合;黃健和秉持三十年前漫畫版催稿的精神持續催生,都在此致謝。
尤其三十年來所有《阿鼻劍》的讀者,沒有各位一直的鼓勵,這本書也就不會出現。
這本小說,是我和鄭問一起獻給各位的。
火,在竄騰。
影子像巨大的黑色波浪,緩吞而落,又急升而上。
空中有一幅畫在飛盪。
畫中,黑鬚金角、全身墨綠的龍,和一條赤紅的巨蟒在歙張廝殺。
也在糾纏交配。
巨斧和銅撾交擊。
帶著雷鳴的劍影轟然而過。
一切歸於寂滅。
只有勿生的臉,在火熖閃動中時明時暗。
而他最後一句話氣息低弱,卻清楚:「等到我再醒來。」
是的。
等到他再醒來。三百三十年。
他交付我的任務。
沒有死亡,長生不老。
對此刻已經活了兩百八十七年的我來說,這個常人祈求不得的願望卻成了無從擺脫的糾纏。
不是任務。更像懲罰。
其實,幾乎就在看著他死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錯了。
我不該答應他的。
一起經歷過那些事情之後,我應該和他一起死在那裡的。
生命結束在那裡,才是善終。起碼,和他一起結束在那裡。
鐘鼓齊發,百樂琤琮之後,只剩孤弦單音,太寂寞,也太空洞。
空洞到錯亂。
起初,時間是快的。
快到只剩下眨動。一年如一日的眨動。
北風的呼嘯,夏夜的蛙鳴,都在眨動中更替。
再逐漸,時間是慢的。
慢到春日草葉上的露珠成了永恒的飽滿。
飽滿到讓人難以喘息。
還好,是進入第一百二十年吧,我找到這座洞窟,有了遁逃的去處。
不見任何光亮的山洞好找。沒有任何聲響的,難。
黑暗有了動靜,就會透出層次。
有了層次,就會波動。
而我只要靜止。
我需要在絕對的靜止中定坐。
坐到不知自己是從岩石中虯結而出,還是從地縫鑽入無邊的虛空。
我總想告訴自己:這就是死亡的面目。
或者,最接近死亡的距離。
但知道都不是。
因為最後,我還是會聽到一個潮浪般的聲音。
我的心跳。
將近三百年的光陰,把許多回憶的河道阻塞,留下模糊的水面。
隨著潮聲在水面浮起的殘木,像是指引,也像讓我攀附的依託。
所以,不是我找到記憶,而是記憶找到我。
但,又有什麼關係?
畢竟,如果他答應的日子沒錯,只要再過四十三年,就是我們重逢之日。
我也到了需要把記得的都整理一遍的時候。
我和勿生的相逢。
他之成為尊者。
風起八千里的征戰。
那最後一夜的到來。
以及為什麼要等待他復活的理由。
身為阿鼻第九使者,我所記得的。
跋
《阿鼻劍》漫畫,從一九八九年問世,前後出版過兩集之後,不只從此成為武俠漫畫的經典,也給眾多讀者留下漫長的等待。
勿生到底想起了什麼前世?他和阿鼻第九使者到底是什麼關係?阿鼻劍到底是什麼來歷?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過去三十年,大家不斷在詢問。
現在,《阿鼻劍前傳》,終於以小說的形式開始和大家見面了。
會寫成小說,開始是偶然的因素。
二○○八年,因為我和鄭問一直各有忙碌的事情,中斷的合作總是陰錯陽差而沒法接續,所以當時就動念先來嘗試寫小說看看。
但畢竟因為我從沒有寫過小說,那之前身為編劇和鄭問的合作經驗又太愉快,所以寫了沒多久就想偷懶,覺得還是先擱下,等未來再繼續和鄭問合作漫畫才是正道。
但是三年前鄭問去世,我們的合作再也不可能,於是要把接下來的故事寫成小說,就成了必然。
把這個三十年來一直在腦中斷續發展的故事,以小說形式寫出來,成了唯一的選擇。不只為了向讀者,也為了向鄭問有一個交待。
真正開始寫,是去年年初的事。寫到四月左右,一度很順手。但是接下來遇到瓶頸。中斷到七月底,才又接續。只是再不久,就又卡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鄭問所畫的漫畫版本《阿鼻劍》實在太精采了。
鄭問在《阿鼻劍》的跋裡說,因為兩人分工,有我在編劇,所以他可以把構思劇情的力量全部轉移到畫面的處理上,融入各種插畫理論與技法,發展出《阿鼻劍》獨樹一格的魅力。
同樣地,對身為編劇的我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兩人分工,有鄭問這樣的絕頂高手在繪圖,所以我不需要構思畫面的細節,而只要發展故事的脈絡、氛圍,在情節上可以跳躍前進。
然而,一旦我自己寫小說,挑戰就完全不一樣了。除了故事的脈絡、氛圍、情節,我必須自己照顧所有的畫面細節,而所有這些都是要用文字進行的。我必須用文字經營所有的畫面和細節,一如鄭問用圖像經營所有的畫面和細節。
我才嘗試寫第一本小說,覺得沒法做到鄭問那麼好。
在半夜的掙扎裡,我經常問鄭問:「為了不要破壞大家對《阿鼻劍》的印象,我還是不要寫下去了。該成為絕響的,就絕響如何?」
鄭問沒有回答過我。
但我畢竟還是不能放棄。
這麼多人等了這麼多年,他們總該知道一些事情到底怎麼了。
去年十一月,在我們的image3 非常圖像空間,有一位先生過來找我,指指他的頭髮,說是已經從濃黑等到花白。他說:他知道鄭問已經過世,但希望我另想辦法,讓他趁眼睛還行的時候,可以把這個故事看完。
於是,一次又一次地掙扎著,我還是一點點寫下去了。
能寫去的動力,也還是因為鄭問所畫的漫畫版本《阿鼻劍》實在太精采了。
雖然力有未逮,但我想那還是鼓勵,或者刺激我要把小說設法再寫好一點的動力。
所以我在寫的過程裡,還是會問鄭問問題。但換一種問法。
每寫到一個場面,我會停下來想一想他在處理漫畫的某些場面,問一下他:「你看如何?這樣還可以吧?」
當然,有時候我也會跟他說:「鄭問,幫我一下!別讓小說漏漫畫的氣啊!」
這樣,我努力著把《阿鼻劍前傳》的卷一〈封印重啟〉完成了。
《阿鼻劍》漫畫版的第三集有過短暫的兩回。當時是把勿生回憶起的前世,和他的現世交錯進行。
而小說版的《阿鼻劍前傳》,則是集中寫前世,寫阿鼻劍的由來,寫勿生如何由摩訶劍的大護法轉變為阿鼻使者,甚至再成為尊者。整個故事則透過阿鼻第九使者的旁觀和回憶來敘述。
時代的背景,則放在五代。
五代不只是亂世,不只有烽火,各種殘暴凶惡之事,不可思議。
我覺得那是一個人世和地獄的界限難分的年代,很適合阿鼻劍的情節發展。
要感謝的人很多。
專研五代史的陳弱水教授,和他的高足黃庭碩,費心指點我許多那個時空的細節;曾孜榮的校閱;大辣編輯洪雅雯、設計師楊啟巽在最後階段的全力配合;黃健和秉持三十年前漫畫版催稿的精神持續催生,都在此致謝。
尤其三十年來所有《阿鼻劍》的讀者,沒有各位一直的鼓勵,這本書也就不會出現。
這本小說,是我和鄭問一起獻給各位的。
目次
前言
一 紅袍彎刀
二 我的名字
三 書生
四 出門
五 官兵的啟示
六 摩訶劍莊
七 盲者之杖
八 入獄
九 風中的刀鋒
十 初遇勿生
十一 燕子錢東這麼說
十二 流民
十三 蕭聲如水
十四 但願重來
十五 花花春日奇
十六 星空之下
十七 取劍
十八 過招
十九 都是你
二十 祭劍
二一 鮮衣怒馬走春風
二二 且聽一曲菩薩蠻
二三 等一下來找我
二四 全滅的驛舍
二五 阿嬤說的話
二六 你會記得我嗎
二七 無顏無言
二八 且過江
二九 秋獵日
三十 怒弓直拉
三一 如是我見
三二 清之明之
三三 卻遇水惡
三四 卻會如此
三五 寒冰之福
三六 重逢
三七 成長與休養
三八 回憶中
三九 六家村
四十 孫手
四一 向南走
四二 歌聲與劍名
四三 迎接
四四 長樂府
四五 阿鼻劍
四六 開鋒
四七 封劍
四八 七天法會
四九 智覺寺
五十 眾生眾生
五一 劍的因緣
五二 拿不起來
五三 不能插手我的事
五四 連續的聲音
五五 誰都不許走
五六 呼喚你的劍
五七 劍鳴
五八 刀陣
五九 青春之戰
六十 地獄
六一 鬼戰
跋
書摘/試閱
一 紅袍彎刀
都快立秋了,怎麼還有這種潑灑而下的雨勢,我站在那裡納悶。
本來,小小草棚,如果不是擠了好幾撥的人,就算看雨發愣也無妨。現在可不。
右手最外邊,最晚進來,大半身都蹲在棚外的,是三個莊稼漢。看來是附近的人趕了集回來,寧可淋雨,也不濕了一車東西。
裡面點,一個人道袍道冠,手裡可不見拂塵。大概淋得比較濕,一直把兩手寬袖東抖抖西抖抖。
比道士再早點進來的人,書生模樣。他個子小,又不時打個噴嚏,連腳邊放的包裹都顯得大。
左手邊,是一對男女。他們和我前後腳進的棚子。男的高挺,手裡拎了個竹條編的箱子,看來像個行商,可他精亮的眼神又透著不只如此。他進來的時候瞄了我一眼,之後就一直盯著棚外。
女的是他老婆吧,坐在棚子裡僅有的一張凳子上。一身綠,蔥綠的上衣配著草綠的裙。隔著她漢子,又低垂著頭,只看到她的雲髻和雪白的頸子,看不清面貌。
她旁邊,則是一頭她剛才騎的毛驢。
我,被這些人擠在中間。
麻煩事在後頭。
那年我十九歲。前一天在路上吃壞了肚子,早上才好些,卻又趕在這個當兒折騰起來。
雨大,棚子裡沒人還好辦。這會兒擠在人堆裡可不知怎麼是好。
我跟五臟廟不斷地說要行行好,別跟自己過不去。
肚子沒理岔,土地公卻可能聽進去了。雨勢漸小。望過書生跟道士,我打量到去處。
對面有個林子,可以遮雨,又隱密。我抄起東西,嘟囔了一聲「借過」就衝出去。雨水比剛才淋到的時候要涼多了。我跑得快,一頭栽進去。
在一棵樹下,我花了一盞茶功夫。
好在從林木間隙看著越下越小的雨,和棚子裡剛才一起避雨的那夥人,不算無聊。
就在差不多要起身的時候,雨中,路的遠處,出現了一個光影。
有那麼一會兒,我搞不明白那是什麼,怎麼會是那個顏色,那種動作。
稍微近了,才看出那是一個人。
穿了一身大紅袍。
秃著個腦袋,穿了一身酒紅色大袍的人。
他走路的步伐很快,姿勢又很詭異。
先只是搖搖晃晃得怪。等到再看清楚一點,脊梁刷地一涼。
他的秃頭上,竟然看不到五官。雞蛋似的光滑一片。我的頭皮轟然一陣發麻。
還好,下一刻,我看明白了。
他是倒著走路。我看到的是他的後腦勺。
那人左右搖晃著,卻像是腦後長了眼睛似的,越來越快地往棚子走過去了。
應該說,奔過去。
雨更細了。
棚子裡的人,三個莊稼漢還是蹲者,其他人仍然坐著的坐著,站著的站著。明明是朝著紅袍秃子的方向,看著他一路急速倒奔而來,每個人都視而未見的樣子。
我望了一眼那個綠衣綠裙的女人。她還是低著頭。
眼看紅袍秃子就要衝進棚子裡,他卻在不遠處猛然煞住腳步。住腳太急,只看他全身往後一傾,卻又靠釘在地上似的兩隻腳把身子拉了回來,筆直立定。
細雨突然沒了。
我稍微挪動了一下,就著一個方向,頭一次打量到紅袍秃子的長相。
一個瘦削的腦袋上,不見任何毛髮,連眉毛都沒有。看不出歲數。細眼,眼角高高地吊著,看來似睡未睡。嘴脣薄薄的,翹著兩邊,似笑不笑。兩隻耳朵,則大得毫不含糊地稱得上是招風耳。
我打了個寒噤,把頭埋更低了些。
棚子裡的人還是沒有動靜。偶爾聽到書生打個噴嚏。
旁人路過,還可能以為他們是同一夥人,正朝著同一個方向張望雨後的天空呢。
「把.人.交.出.來。」
尖尖細細的聲音,一字一字地響了起來。聲音也怪。
我看紅袍秃子。他還是那似笑不笑的模樣立定在那裡,沒見他嘴巴怎麼動。
接著,棚子裡的人動了起來。
最先是那個東抖抖西抖抖的道士。他寬袖長袍,卻輕靈地一眨眼就出了棚子,手裡有一道黑影往秃子的後背招呼過去。
書生差不多時間。他從斜地裡竄出,踮了個腳就騰起空中,直刺秃子。剛看他個子小、打噴嚏,怎麼也想不到有這麼俐落的身手。
一陣金鐵交鳴。道士被格開,他手裡是一方鐵尺。書生也從空中被擋落到紅袍人的前方。紅袍人還是沒有面對他們,雙手垂著,袖子寬長,看不到握著什麼。顯然是短兵器。
新加入了幾個人,從另一個方向圍住了秃子。是那三個莊稼漢,手裡長短兵器不一。
我暗叫了一聲。完全沒看出他們是練家子。更沒料到他們是一夥人,分頭過來避雨。
「名門正派都是喜歡打群架的嗎?」陰細的聲音又響起。他把話連起來說,就更怪腔怪調,不容易聽明白。似笑不笑的嘴巴還是看不出有怎麼動。
「對付惡人,哪有什麼講究。」高壯的漢子走出了棚子。綠衣女人本來垂著的頭稍微抬高了一些,像是在看前方地上什麼東西。
「嗤嗤嗤嗤。」紅袍秃子的笑聲更細。「早給晚給都是要給,幹嘛硬要送命呢。」
「你要什麼人,我們哪知道!」一個莊稼漢悶聲道。
紅袍秃子還是沒有轉身:「那你們裝什麼熊來護駕啊,就是你們天健莊少奶奶嘛。」他雖然背對著棚子,但是眼睛吊得更瞇,嘴角也翹得更高,好像女人就在他面前似的。
「放肆!」一個綠影帶著道白光從棚子裡射出。
噹!
秃子仍然是頭也沒回就伸手擋開女人的劍光。
女人冷著臉孔,依然看得出形貌清麗。她也有一身本領,難怪剛才不動聲色。
秃子這次露出了手裡的兵器,是一把月牙形的小彎刀。「好俊的身手,我喜歡!」他又嗤嗤笑了一聲。
高壯男子暴喝一聲,緊接著一劍攻上。道士也把鐵尺舞起,從旁招呼過去。接下來的場面難忘。
紅袍秃子不像是在打鬥,倒像是在進進退退,左左右右地踩著舞步。他左右兩手一邊一把小彎刀,閃著金光,東擋西擋,響著叮叮噹噹,一派輕鬆。
然後,再過了一會兒,我就看著他一聲「著!」把道士的喉嚨割開,噴出一片血霧。又一聲「喝!」把書生的心口剜出個窟窿。
三個莊稼漢,都是胸腹之間被切開。
高壯男子的脖子被砍開大口子。這也是秃子臉上血濺得最多的一刀。
綠衣女子撐到最後,應該說是被讓到最後。
她看到男人被殺的剎那,尖叫一聲,回劍直刺自己的喉嚨。秃子左手的彎刀早已伸過去打掉,再騰身一指點了她的穴道。
女人一癱。秃子撈起她,噹啷一聲兩把彎刀落地。
他桀桀一笑,猛力扯開她的衣服,一個雪白的奶子迸了出來。他沒有任何停頓,血手一捏,低頭咬上去。
秃子的大紅袍展開,把女人整個包了進去。
躺了一地屍首的地上,大紅袍子弓在地上像個小丘,一直在蠕動,蠕動。
老半天之後,紅袍人起身,立了一會兒,走了。這次沒有倒著走,左右搖晃依舊,逐漸走遠。
而他剛才弓身蠕動的地方,白晃晃的肉歪七扭八地攤在血水中。
棚子裡,小毛驢不知何時也不見了。
林子裡的鳥在啾啾地叫,林外的天空出現了一道彩虹,眼前的草葉上水珠晶瑩。
我這才意識到不知什麼時候,整個人都趴在地上了,有點哆嗦,全身冷汗濕透。
雖然和我日後見過的殺戮場面比起來,這絲毫不算什麼,但卻是回憶經常浮現的一幕。
那是我第一次和十八惡道相遇。
我看到的是「女惡」。
專挑名門閨秀,尤其身上有功夫的女人下手的女惡。
二 我的名字
我有過兩個名字。
先從第一個說起吧。
我姓平,名川。筆劃簡單,寫起來容易,意思也好,在亂世裡可以保個順當。這是算命先生跟我爹說的。
我爹娘就沒有那麼順當。
我家是北方人,逃難來鄱陽城投奔早年過來的堂叔。可千辛萬苦才到,我爹就死了。那年我四歲。
開客棧的堂叔收留我們,加上我娘做些針線活兒,倒也把我拉拔大。可是到我十二歲那年,剛可以跑堂侍候客人,她也過世了。若不是她過世前一個晚上交代我事情的印象深刻,都不記得她的模樣了。可我堂嬸常說,我和我娘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我沒難過多久,也就適應了孤身一人的日子。
侍候客人從早到晚,夜裡累癱,沒力氣多想。加上南來北往的人多,客棧裡來吃的來住的,脾氣好的凶的,什麼樣的客人都有,每天都得些新奇見聞,也轉移了注意。
那是後來人稱五代的年頭。
說是亂世,可我長大的時候沒覺得。相對於北方還在殺得烽火連天,江淮之間不同。
我所在的吳國,是原先唐朝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東征西討,一手打下的基礎。楊行密身後,大政為徐溫把持。徐溫死後,他的養子徐知誥大權獨攬。
和北方不同的是,吳國宮廷裡的權鬥雖然未歇,但是民間未經兵燹。加上從楊行密到徐溫再到徐知誥,都是幹練的人。在他們的持續治理下,因而有後人所說「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的成果。鄱陽大湖,水陸要衝,尤其富饒。
所以跑堂的時候,雖然我也聽到其他地方戰火肆虐的慘狀,總覺得遙遠。來往做生意的人,吃香喝辣,倒是看得真切。
從北方走藥材、羊馬下來的人,從南方走瓷器、茶葉上去的人,還有從更南邊運香料來的人。他們真給了我不少賞錢。鄱陽城裡出門發財的人也不少。有個運木材的張胖子,他回來大宴賓客的闊氣,讓人羨慕。
老早以來,就有個現象。當官的瞧不起平民,不論你多富有,也都是賤民。有錢人,當然又不把窮人當人看。
我在客棧裡最好侍候的,是南來北往的行商、過客,最怕碰上的,是在地有錢人。出門在外的人,通常都比較知道收歛一些。在地的有錢人,飛揚跋扈起來,不可一世。他們遇到當官的吃的癟,通通發作到沒錢人身上。
不過,沒錢的人,身上如果有武藝,就不一樣了。
那時候,身上有兩下子的武人,跟生意人一樣,出路很多。常聽說什麼人去當了哪個節度使的牙兵,扶搖直上;有人去哪個莊園帶起團練;還有嘛,就是拉起一幫人當了盗賊,說起來也就是去「上山」了,沒那麼難聽。畢竟,官逼民反,黃巢之後,盗賊之能為大,大家都早有見識。何況,英雄不怕出身低,當年楊行密自己也是盗賊。
堂叔是個胖墩墩的人。我們客棧裡賣吃的,別的菜倒也還好,就是幾道醬肘子、滷味特別好。不只住店的客人愛吃,在城裡也知名,遠近都來。這就是堂叔的絕活。
堂嬸個子比堂叔高一截,說話也快一截。她看我拿賞錢,就說都幫我存起來拿走了。
他們有個兒子,大我三歲。從來不搭理我。小時候他都是出去跟街坊的小孩玩,大了之後也是出去聽曲、鬥雞,沒看他做過什麼正經事。他常得意地說,他爹那幾道醬滷味的祕方別人不傳,一定會留給他,他也只要做好那幾道菜就夠了。
而我,看來也就是一輩子跑堂,跟另外兩個夥計一起繼續給他當下人了。
可是聽多了這個人發財,那個人發跡的故事,我還是不免做起白日夢。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出去走走呢?跟著什麼人出去做買賣?
聽客人聊各地的景緻,最讓我動心的,有南,有北。
南邊,閩國來的人說,他們的福州改名長樂府之後,日日夜夜有多少新奇華麗。跟新羅、日本、南洋來往的船,帶來多少珍異貨物。
那人說起大海,我問他海長什麼樣子。他形容了半天,我說我們鄱陽湖也是水天一色啊。「你懂什麼!」他嗤笑。
北邊,是關外的大草原。說話的人,講他騎著馬跑幾天,東南西北都不見邊際。我聽多了北方的戰亂可怕,還有胡人的兇猛,可是那麼大的草原,聽得我怎麼都沒法想像到底是什麼模樣。草原和大海哪個比較大呢?
想著,我心中波濤起伏。
做到第五年的時候最難捱,真想央著哪個客人帶我走。反正孤身一人,外頭的風險再大,總比這麼一輩子強吧。何況,搞不好也可以輪到我揚眉吐氣?
後來,時間再過去,也就明白這都是妄想,又慢慢沉靜下來。
再過一年,我死心塌地這輩子就當一個跑堂了。再聽客人講些天南地北的事,也就只是當故事聽了。
有個客人會講謎語。其中有個我記得很清楚:「有樣東西,扛得了重,可是走不了。它的頭就是它的尾。有時候你看見它在彎腰,有時候在伸腰。」大家都猜不到,答案是橋。
還有客人講一個會法術的人。說他仗著法術什麼壞事都做,叫人逮到也不怕。因為抓了他砍腦袋都沒用。砍一個長一個。後來才知道,要破他的法,得在夜裡把他綁到月亮底下,朝他地上的影子噴三口水,先砍他影子的頭一刀。這樣他的腦袋掉下來,才再也長不出來。
日子就這樣,有點事也沒什麼事地過去了。
可那天,客棧裡來了一個書生。
三 書生
那是個瘦䠷的讀書人,帶著一個箱匣。路上就有了病,到客棧說要歇息兩天就走,結果卻發起燒,走不動了。
他先說自己懂點醫道,開了方子找人去配藥。不見好,堂叔又找了個大夫來看。也沒見效。這下子病就拖下去。等他盤纏用完,病情越發嚴重。
堂叔翻翻他箱匣裡只有一把劍和幾本書,沒什麼好氣。出來跟我說:「還好有把劍可以拿去當了、賣了抵一抵。」
眼看他逐漸是挺著等死,客棧又來了幫皮毛商人,客房不夠,我就乾脆把他接到我住的柴房去。
我來照料。能好過來,是他的造化。好不了,也沒有死在客房裡那麼晦氣。
還真做對了。把他搬到柴房之後,日裡夜裡多顧著他一些,情況當真慢慢好轉。頭十天,多了口氣。再半個月,精神好多了。等到快要入伏的時候,他已經起身走動自如。
有天中午,我幫他送了些吃的過去,看到他拿著一本書,在吚吚哦哦地唸著什麼。
聽不懂,卻挺有意思的。晚上就問他。
「唔?」他看看我:「你怎麼會想知道這個?」
我臉刷一下紅了。我只跟著堂叔認識一些帳單上的字。
他看出我的窘態:「不,我是問你,你是聽出什麼意思嗎?」
我跟他說沒有,只是覺得唸起來聲調真好,又好像有什麼意思在裡面。
他哈哈一笑,就把他唸的那首詩講給我聽了。多好的詩啊。我聽到著迷。不,是激動。
東海有勇婦
何慚蘇子卿
學劍越處子
超然若流星
捐軀報夫仇
萬死不顧生
白刃耀素雪
蒼天感精誠
十步兩躩躍
三呼一交兵
斬首掉國門
蹴踏五藏行
……………
他跟我說,那是一個叫李白的人寫的詩。
詩裡的句子,把一個識字不多的孩子攪得心情翻騰,眼前模糊。
講詩的人問:「你哭什麼呢?」
我答不上來。
過了一天之後,我才跟他說:「我哭自己活得連一個女人家都不如。」
書生多看了我一會兒。他的人瘦,眼睛卻大,左眼角有顆紅痣。
「我想學劍。」我鼓起勇氣跟他說。
他問我:「你有什麼仇家嗎?」
我搖搖頭。
他想了想問我:「那是想有了本領出去闖蕩?」
我搖搖頭,點點頭,又搖搖頭。「我就是想學。」
書生微微一笑,沒再說什麼。
第二天早上,箱匣還在,他卻不見了。
失蹤了。連著十來天。
有天夜裡我聽到動靜醒來,他回來了。他看著我,大眼睛在黑暗中閃著光:「你真的想學劍嗎?」
就這樣我有了一個教劍、也教字的人。
書生說:「不識字的人學不好劍。」
我求他寫給我的第一張識字的字帖,就是李白的那首詩。
但他堅決不肯收我為徒:「你照顧我一場,救了我一命。我教你一點東西,只是一點回報,不成心意。」
我跪下來給他磕了三個頭。他攔不住我,也作了三個長揖,說:「不敢當。」
接下來一個月,他教了我一套劍法,和打拳、吐納練氣的方法。也透露了點自己的事。
他姓馮。到這裡是尋仇的。在大病一場康復之後,他溜出去查了仇人的狀況,卻發現對方就在這段時間暴病而亡。
既然事情已經這般,他也就接受天意如此,決定回來教我點東西。
「我的仇家沒了,劍也沒有用了,就送給你吧。」他說。
我接過劍的那一刻,永遠如在眼前。
劍鞘、劍柄一色暗紅。劍身是三尺三,比一般略長。在燭光下,劍鋒亮得晃眼。
後來我摸過再多的好劍,也沒有像那一把難忘。
有天晚上,書生說我學得有些眉目,離別的時候到了。
他也第一個告訴我「平川」這個名字不只有「順當」的意思。
「平川浩蕩,」他說:「氣派很大。」
平川不只是順當。還有浩蕩的意思。這讓我震動很大。
第二天睡醒,他消失不見。
我惆悵了很久,為了和這個人再無相逢的機會。
當然,我不知道,命運已經安排了我們再見之日。並且是那個情況。
四 出門
書生走了。但,我的人生再也不同。
接下來,我每天練習所學。
書生說過,因為他不收我為徒,不想別人看出我的師承,只能教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所以除了馬步,還有一套連名字都沒有的拳路和吐納運氣之法外,他教我一套十分常見,無所謂師門的「三才劍法」。
書生說,正因為太通俗了,很多人不覺新奇,大半不肯仔細練,很容易走樣,以訛傳訛。而他教我的,就是一套還原歸本,乾乾淨淨的「三才劍法」。不但容易入手,用心練必會受益,將來有緣再學別的,也比較容易上手。
他還跟我說,練拳不要只練招式,要練到有一天可以感覺到「體隨氣動」。
「所以你要認真打坐,吐納運氣久了,你有了內功,要打拳,要使劍,就都不一樣。」書生說。
他也給我誇讚。「我看你學劍很聰明,使劍很輕靈,有天分,一定會練出火候。」
不過,他也告訴我另一件事,「不管練拳和練劍,練是一回事,真正和人家動起手來,又是另一回事。」書生說。「練熟的招會用得上,可更多時候,你得臨機應變。」
我問他如何臨機應變。
書生哈哈笑起來,說他講得出來就不是臨機應變了。
我記住他的話,朝夕苦練。
不管冷熱,找得出空的時候。不只是武功,還有他寫下來留給我的三百個字的字帖。
有時候,起得晚了,會吃堂叔狠狠的排頭。但是我不在乎。一天天覺得自己越來越有進展,很享受。有些不知名的期待,也在心底隱約地蔓延、游移著。
書生告訴我,劍要藏著,不要外露。我聽他的話做了,但是卻沒有藏住我的夢想。
我不要只是窩在這裡過太平日子。
我也想出去做買賣,看看外頭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劇變不斷。
我遇上書生那年,北方石敬塘跟契丹借兵,滅了後唐,改朝晉。我所在的吳國,徐知誥也進一步廢了楊家天下,先是改吳為齊,以昇元為年號。等到北方的後唐滅亡,徐知誥自稱是唐憲宗的後代,所以回歸李姓,改名昪,同時又再改國號為唐。也就是後來大家所說的南唐。
雖然出門總是不平靜,可我們唐國比起北方中原可說是富庶又太平,何不一試?
終於,有一天,那游移的期待具形迸現了。
有個每年總會經過一趟的茶葉商人,和另一幫喝醉了酒的客人起了衝突。先是口角,後來鬧起來。
茶葉商人本來有個年輕的隨從,這次沒看見。那些人看他孤單,就要欺負他。
我過去勸解,一個塊頭很大的傢伙瞪了我一眼:「你算什麼東西!」一把推來。
說起來,我都分不清到底是被他趾高氣揚的那句話激怒,還是早就準備要出手,總之,我反手一格,再一拳打到他腰眼上。
大塊頭一下子癱倒在地上。
其他人要上來,我簡單俐落地撂倒兩個之後,就都安靜了。
「要欺負人到別處去!」我跟他們吼了一聲。
我堂叔瞪大了眼睛在看我。
那天晚上,堂叔把我找去,問我怎麼會了拳腳。
我一五一十地說了。
堂叔聽我有了一把劍,眼睛瞪得更大,跟銅鈴一般。那時候,律法亂,一般人私有刀劍,是可大可小的事。我本來擔心會挨一頓罵,可他沒說什麼就叫我回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堂叔和堂嬸一起叫我過去,劈頭一句輪到我瞪大眼睛。
「以前常聽你說能出去走走多好,現在還想嗎?」堂叔問,聲音很輕柔。
接著他跟我說,茶葉商人這次身體微恙沒有隨從,是因為那個年輕人在路上得了痢疾,一病不起。
「他是我們的老客人了。我看他這樣在路上沒有人陪是不行。你想的話,我來幫你問問。」他說。
堂嬸一向話多又快,那天早上在旁邊一直只是看著我,沒出聲。
事情很快就談妥了。
茶葉商人本來就知道我,再加上昨天幫他解圍,一聽堂叔建議他帶我出去,沉吟了一下,也就同意。
唐朝時候,出門做生意,路過關津,都得有「過所」,也就是通關文牒。不但商人自己,隨行的姓名也得註明清楚,檢查嚴格。等到了五代,天下大亂,各國之間的關防之地防備固嚴,國境之內的通行就看情況,鬆緊不一。
茶葉商人說他回去之後就要收手不再出門了。所以帶我去不了多遠的地方,能教我多少買賣的事也說不準。但如果我真想出門看看,還是樂意帶我。路上如果碰上盤查的時候,只要記得報上他原來那個隨從的姓名,也就可以了。
他直跟我堂叔道謝:「這也是幫我的忙。他跟著我,我放心,你也可以放心。」
忽然,多年的夢想,早就埋起來的夢想亮了起來,像是有個新的天地在我眼前打開。
生平跟人第一次打架,竟然就有這麼美好的獎賞?我都不敢相信。
我才不管茶葉商人回去之後就不出門了怎麼辦。只要能先出門就好。出了門,自然有新的機會。我很有把握。
這樣,沒幾天,等茶葉商人料理好他的事,我就可以跟他走了。
堂嬸把這幾年幫我存的賞錢給我,有一貫錢,約一千文錢。倒是堂叔說我出遠門,身上要有點錢,慷慨地給了我一些盤纏。他知道茶葉商人要去的方向之後,還推薦我有需要可以去一座縣城找他的朋友。
他對我的態度也和過去完全不同。之前,堂叔看我的時候,多半拉著臉。那幾天他可一直都是笑臉。
連他兒子,以前從不正眼看我,也跟我點點頭,閃過不知是羨慕還是什麼的眼神。
我帶著一把劍和一個小包裹,和茶葉商人上路。
和堂叔不捨地告別後,出了客棧走遠一點再回望,看到他帶著從沒有過的輕鬆笑容跟別人朝我指指點點,心頭最後一丁點牽掛也全部放下。
我出發了。
都快立秋了,怎麼還有這種潑灑而下的雨勢,我站在那裡納悶。
本來,小小草棚,如果不是擠了好幾撥的人,就算看雨發愣也無妨。現在可不。
右手最外邊,最晚進來,大半身都蹲在棚外的,是三個莊稼漢。看來是附近的人趕了集回來,寧可淋雨,也不濕了一車東西。
裡面點,一個人道袍道冠,手裡可不見拂塵。大概淋得比較濕,一直把兩手寬袖東抖抖西抖抖。
比道士再早點進來的人,書生模樣。他個子小,又不時打個噴嚏,連腳邊放的包裹都顯得大。
左手邊,是一對男女。他們和我前後腳進的棚子。男的高挺,手裡拎了個竹條編的箱子,看來像個行商,可他精亮的眼神又透著不只如此。他進來的時候瞄了我一眼,之後就一直盯著棚外。
女的是他老婆吧,坐在棚子裡僅有的一張凳子上。一身綠,蔥綠的上衣配著草綠的裙。隔著她漢子,又低垂著頭,只看到她的雲髻和雪白的頸子,看不清面貌。
她旁邊,則是一頭她剛才騎的毛驢。
我,被這些人擠在中間。
麻煩事在後頭。
那年我十九歲。前一天在路上吃壞了肚子,早上才好些,卻又趕在這個當兒折騰起來。
雨大,棚子裡沒人還好辦。這會兒擠在人堆裡可不知怎麼是好。
我跟五臟廟不斷地說要行行好,別跟自己過不去。
肚子沒理岔,土地公卻可能聽進去了。雨勢漸小。望過書生跟道士,我打量到去處。
對面有個林子,可以遮雨,又隱密。我抄起東西,嘟囔了一聲「借過」就衝出去。雨水比剛才淋到的時候要涼多了。我跑得快,一頭栽進去。
在一棵樹下,我花了一盞茶功夫。
好在從林木間隙看著越下越小的雨,和棚子裡剛才一起避雨的那夥人,不算無聊。
就在差不多要起身的時候,雨中,路的遠處,出現了一個光影。
有那麼一會兒,我搞不明白那是什麼,怎麼會是那個顏色,那種動作。
稍微近了,才看出那是一個人。
穿了一身大紅袍。
秃著個腦袋,穿了一身酒紅色大袍的人。
他走路的步伐很快,姿勢又很詭異。
先只是搖搖晃晃得怪。等到再看清楚一點,脊梁刷地一涼。
他的秃頭上,竟然看不到五官。雞蛋似的光滑一片。我的頭皮轟然一陣發麻。
還好,下一刻,我看明白了。
他是倒著走路。我看到的是他的後腦勺。
那人左右搖晃著,卻像是腦後長了眼睛似的,越來越快地往棚子走過去了。
應該說,奔過去。
雨更細了。
棚子裡的人,三個莊稼漢還是蹲者,其他人仍然坐著的坐著,站著的站著。明明是朝著紅袍秃子的方向,看著他一路急速倒奔而來,每個人都視而未見的樣子。
我望了一眼那個綠衣綠裙的女人。她還是低著頭。
眼看紅袍秃子就要衝進棚子裡,他卻在不遠處猛然煞住腳步。住腳太急,只看他全身往後一傾,卻又靠釘在地上似的兩隻腳把身子拉了回來,筆直立定。
細雨突然沒了。
我稍微挪動了一下,就著一個方向,頭一次打量到紅袍秃子的長相。
一個瘦削的腦袋上,不見任何毛髮,連眉毛都沒有。看不出歲數。細眼,眼角高高地吊著,看來似睡未睡。嘴脣薄薄的,翹著兩邊,似笑不笑。兩隻耳朵,則大得毫不含糊地稱得上是招風耳。
我打了個寒噤,把頭埋更低了些。
棚子裡的人還是沒有動靜。偶爾聽到書生打個噴嚏。
旁人路過,還可能以為他們是同一夥人,正朝著同一個方向張望雨後的天空呢。
「把.人.交.出.來。」
尖尖細細的聲音,一字一字地響了起來。聲音也怪。
我看紅袍秃子。他還是那似笑不笑的模樣立定在那裡,沒見他嘴巴怎麼動。
接著,棚子裡的人動了起來。
最先是那個東抖抖西抖抖的道士。他寬袖長袍,卻輕靈地一眨眼就出了棚子,手裡有一道黑影往秃子的後背招呼過去。
書生差不多時間。他從斜地裡竄出,踮了個腳就騰起空中,直刺秃子。剛看他個子小、打噴嚏,怎麼也想不到有這麼俐落的身手。
一陣金鐵交鳴。道士被格開,他手裡是一方鐵尺。書生也從空中被擋落到紅袍人的前方。紅袍人還是沒有面對他們,雙手垂著,袖子寬長,看不到握著什麼。顯然是短兵器。
新加入了幾個人,從另一個方向圍住了秃子。是那三個莊稼漢,手裡長短兵器不一。
我暗叫了一聲。完全沒看出他們是練家子。更沒料到他們是一夥人,分頭過來避雨。
「名門正派都是喜歡打群架的嗎?」陰細的聲音又響起。他把話連起來說,就更怪腔怪調,不容易聽明白。似笑不笑的嘴巴還是看不出有怎麼動。
「對付惡人,哪有什麼講究。」高壯的漢子走出了棚子。綠衣女人本來垂著的頭稍微抬高了一些,像是在看前方地上什麼東西。
「嗤嗤嗤嗤。」紅袍秃子的笑聲更細。「早給晚給都是要給,幹嘛硬要送命呢。」
「你要什麼人,我們哪知道!」一個莊稼漢悶聲道。
紅袍秃子還是沒有轉身:「那你們裝什麼熊來護駕啊,就是你們天健莊少奶奶嘛。」他雖然背對著棚子,但是眼睛吊得更瞇,嘴角也翹得更高,好像女人就在他面前似的。
「放肆!」一個綠影帶著道白光從棚子裡射出。
噹!
秃子仍然是頭也沒回就伸手擋開女人的劍光。
女人冷著臉孔,依然看得出形貌清麗。她也有一身本領,難怪剛才不動聲色。
秃子這次露出了手裡的兵器,是一把月牙形的小彎刀。「好俊的身手,我喜歡!」他又嗤嗤笑了一聲。
高壯男子暴喝一聲,緊接著一劍攻上。道士也把鐵尺舞起,從旁招呼過去。接下來的場面難忘。
紅袍秃子不像是在打鬥,倒像是在進進退退,左左右右地踩著舞步。他左右兩手一邊一把小彎刀,閃著金光,東擋西擋,響著叮叮噹噹,一派輕鬆。
然後,再過了一會兒,我就看著他一聲「著!」把道士的喉嚨割開,噴出一片血霧。又一聲「喝!」把書生的心口剜出個窟窿。
三個莊稼漢,都是胸腹之間被切開。
高壯男子的脖子被砍開大口子。這也是秃子臉上血濺得最多的一刀。
綠衣女子撐到最後,應該說是被讓到最後。
她看到男人被殺的剎那,尖叫一聲,回劍直刺自己的喉嚨。秃子左手的彎刀早已伸過去打掉,再騰身一指點了她的穴道。
女人一癱。秃子撈起她,噹啷一聲兩把彎刀落地。
他桀桀一笑,猛力扯開她的衣服,一個雪白的奶子迸了出來。他沒有任何停頓,血手一捏,低頭咬上去。
秃子的大紅袍展開,把女人整個包了進去。
躺了一地屍首的地上,大紅袍子弓在地上像個小丘,一直在蠕動,蠕動。
老半天之後,紅袍人起身,立了一會兒,走了。這次沒有倒著走,左右搖晃依舊,逐漸走遠。
而他剛才弓身蠕動的地方,白晃晃的肉歪七扭八地攤在血水中。
棚子裡,小毛驢不知何時也不見了。
林子裡的鳥在啾啾地叫,林外的天空出現了一道彩虹,眼前的草葉上水珠晶瑩。
我這才意識到不知什麼時候,整個人都趴在地上了,有點哆嗦,全身冷汗濕透。
雖然和我日後見過的殺戮場面比起來,這絲毫不算什麼,但卻是回憶經常浮現的一幕。
那是我第一次和十八惡道相遇。
我看到的是「女惡」。
專挑名門閨秀,尤其身上有功夫的女人下手的女惡。
二 我的名字
我有過兩個名字。
先從第一個說起吧。
我姓平,名川。筆劃簡單,寫起來容易,意思也好,在亂世裡可以保個順當。這是算命先生跟我爹說的。
我爹娘就沒有那麼順當。
我家是北方人,逃難來鄱陽城投奔早年過來的堂叔。可千辛萬苦才到,我爹就死了。那年我四歲。
開客棧的堂叔收留我們,加上我娘做些針線活兒,倒也把我拉拔大。可是到我十二歲那年,剛可以跑堂侍候客人,她也過世了。若不是她過世前一個晚上交代我事情的印象深刻,都不記得她的模樣了。可我堂嬸常說,我和我娘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我沒難過多久,也就適應了孤身一人的日子。
侍候客人從早到晚,夜裡累癱,沒力氣多想。加上南來北往的人多,客棧裡來吃的來住的,脾氣好的凶的,什麼樣的客人都有,每天都得些新奇見聞,也轉移了注意。
那是後來人稱五代的年頭。
說是亂世,可我長大的時候沒覺得。相對於北方還在殺得烽火連天,江淮之間不同。
我所在的吳國,是原先唐朝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東征西討,一手打下的基礎。楊行密身後,大政為徐溫把持。徐溫死後,他的養子徐知誥大權獨攬。
和北方不同的是,吳國宮廷裡的權鬥雖然未歇,但是民間未經兵燹。加上從楊行密到徐溫再到徐知誥,都是幹練的人。在他們的持續治理下,因而有後人所說「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的成果。鄱陽大湖,水陸要衝,尤其富饒。
所以跑堂的時候,雖然我也聽到其他地方戰火肆虐的慘狀,總覺得遙遠。來往做生意的人,吃香喝辣,倒是看得真切。
從北方走藥材、羊馬下來的人,從南方走瓷器、茶葉上去的人,還有從更南邊運香料來的人。他們真給了我不少賞錢。鄱陽城裡出門發財的人也不少。有個運木材的張胖子,他回來大宴賓客的闊氣,讓人羨慕。
老早以來,就有個現象。當官的瞧不起平民,不論你多富有,也都是賤民。有錢人,當然又不把窮人當人看。
我在客棧裡最好侍候的,是南來北往的行商、過客,最怕碰上的,是在地有錢人。出門在外的人,通常都比較知道收歛一些。在地的有錢人,飛揚跋扈起來,不可一世。他們遇到當官的吃的癟,通通發作到沒錢人身上。
不過,沒錢的人,身上如果有武藝,就不一樣了。
那時候,身上有兩下子的武人,跟生意人一樣,出路很多。常聽說什麼人去當了哪個節度使的牙兵,扶搖直上;有人去哪個莊園帶起團練;還有嘛,就是拉起一幫人當了盗賊,說起來也就是去「上山」了,沒那麼難聽。畢竟,官逼民反,黃巢之後,盗賊之能為大,大家都早有見識。何況,英雄不怕出身低,當年楊行密自己也是盗賊。
堂叔是個胖墩墩的人。我們客棧裡賣吃的,別的菜倒也還好,就是幾道醬肘子、滷味特別好。不只住店的客人愛吃,在城裡也知名,遠近都來。這就是堂叔的絕活。
堂嬸個子比堂叔高一截,說話也快一截。她看我拿賞錢,就說都幫我存起來拿走了。
他們有個兒子,大我三歲。從來不搭理我。小時候他都是出去跟街坊的小孩玩,大了之後也是出去聽曲、鬥雞,沒看他做過什麼正經事。他常得意地說,他爹那幾道醬滷味的祕方別人不傳,一定會留給他,他也只要做好那幾道菜就夠了。
而我,看來也就是一輩子跑堂,跟另外兩個夥計一起繼續給他當下人了。
可是聽多了這個人發財,那個人發跡的故事,我還是不免做起白日夢。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出去走走呢?跟著什麼人出去做買賣?
聽客人聊各地的景緻,最讓我動心的,有南,有北。
南邊,閩國來的人說,他們的福州改名長樂府之後,日日夜夜有多少新奇華麗。跟新羅、日本、南洋來往的船,帶來多少珍異貨物。
那人說起大海,我問他海長什麼樣子。他形容了半天,我說我們鄱陽湖也是水天一色啊。「你懂什麼!」他嗤笑。
北邊,是關外的大草原。說話的人,講他騎著馬跑幾天,東南西北都不見邊際。我聽多了北方的戰亂可怕,還有胡人的兇猛,可是那麼大的草原,聽得我怎麼都沒法想像到底是什麼模樣。草原和大海哪個比較大呢?
想著,我心中波濤起伏。
做到第五年的時候最難捱,真想央著哪個客人帶我走。反正孤身一人,外頭的風險再大,總比這麼一輩子強吧。何況,搞不好也可以輪到我揚眉吐氣?
後來,時間再過去,也就明白這都是妄想,又慢慢沉靜下來。
再過一年,我死心塌地這輩子就當一個跑堂了。再聽客人講些天南地北的事,也就只是當故事聽了。
有個客人會講謎語。其中有個我記得很清楚:「有樣東西,扛得了重,可是走不了。它的頭就是它的尾。有時候你看見它在彎腰,有時候在伸腰。」大家都猜不到,答案是橋。
還有客人講一個會法術的人。說他仗著法術什麼壞事都做,叫人逮到也不怕。因為抓了他砍腦袋都沒用。砍一個長一個。後來才知道,要破他的法,得在夜裡把他綁到月亮底下,朝他地上的影子噴三口水,先砍他影子的頭一刀。這樣他的腦袋掉下來,才再也長不出來。
日子就這樣,有點事也沒什麼事地過去了。
可那天,客棧裡來了一個書生。
三 書生
那是個瘦䠷的讀書人,帶著一個箱匣。路上就有了病,到客棧說要歇息兩天就走,結果卻發起燒,走不動了。
他先說自己懂點醫道,開了方子找人去配藥。不見好,堂叔又找了個大夫來看。也沒見效。這下子病就拖下去。等他盤纏用完,病情越發嚴重。
堂叔翻翻他箱匣裡只有一把劍和幾本書,沒什麼好氣。出來跟我說:「還好有把劍可以拿去當了、賣了抵一抵。」
眼看他逐漸是挺著等死,客棧又來了幫皮毛商人,客房不夠,我就乾脆把他接到我住的柴房去。
我來照料。能好過來,是他的造化。好不了,也沒有死在客房裡那麼晦氣。
還真做對了。把他搬到柴房之後,日裡夜裡多顧著他一些,情況當真慢慢好轉。頭十天,多了口氣。再半個月,精神好多了。等到快要入伏的時候,他已經起身走動自如。
有天中午,我幫他送了些吃的過去,看到他拿著一本書,在吚吚哦哦地唸著什麼。
聽不懂,卻挺有意思的。晚上就問他。
「唔?」他看看我:「你怎麼會想知道這個?」
我臉刷一下紅了。我只跟著堂叔認識一些帳單上的字。
他看出我的窘態:「不,我是問你,你是聽出什麼意思嗎?」
我跟他說沒有,只是覺得唸起來聲調真好,又好像有什麼意思在裡面。
他哈哈一笑,就把他唸的那首詩講給我聽了。多好的詩啊。我聽到著迷。不,是激動。
東海有勇婦
何慚蘇子卿
學劍越處子
超然若流星
捐軀報夫仇
萬死不顧生
白刃耀素雪
蒼天感精誠
十步兩躩躍
三呼一交兵
斬首掉國門
蹴踏五藏行
……………
他跟我說,那是一個叫李白的人寫的詩。
詩裡的句子,把一個識字不多的孩子攪得心情翻騰,眼前模糊。
講詩的人問:「你哭什麼呢?」
我答不上來。
過了一天之後,我才跟他說:「我哭自己活得連一個女人家都不如。」
書生多看了我一會兒。他的人瘦,眼睛卻大,左眼角有顆紅痣。
「我想學劍。」我鼓起勇氣跟他說。
他問我:「你有什麼仇家嗎?」
我搖搖頭。
他想了想問我:「那是想有了本領出去闖蕩?」
我搖搖頭,點點頭,又搖搖頭。「我就是想學。」
書生微微一笑,沒再說什麼。
第二天早上,箱匣還在,他卻不見了。
失蹤了。連著十來天。
有天夜裡我聽到動靜醒來,他回來了。他看著我,大眼睛在黑暗中閃著光:「你真的想學劍嗎?」
就這樣我有了一個教劍、也教字的人。
書生說:「不識字的人學不好劍。」
我求他寫給我的第一張識字的字帖,就是李白的那首詩。
但他堅決不肯收我為徒:「你照顧我一場,救了我一命。我教你一點東西,只是一點回報,不成心意。」
我跪下來給他磕了三個頭。他攔不住我,也作了三個長揖,說:「不敢當。」
接下來一個月,他教了我一套劍法,和打拳、吐納練氣的方法。也透露了點自己的事。
他姓馮。到這裡是尋仇的。在大病一場康復之後,他溜出去查了仇人的狀況,卻發現對方就在這段時間暴病而亡。
既然事情已經這般,他也就接受天意如此,決定回來教我點東西。
「我的仇家沒了,劍也沒有用了,就送給你吧。」他說。
我接過劍的那一刻,永遠如在眼前。
劍鞘、劍柄一色暗紅。劍身是三尺三,比一般略長。在燭光下,劍鋒亮得晃眼。
後來我摸過再多的好劍,也沒有像那一把難忘。
有天晚上,書生說我學得有些眉目,離別的時候到了。
他也第一個告訴我「平川」這個名字不只有「順當」的意思。
「平川浩蕩,」他說:「氣派很大。」
平川不只是順當。還有浩蕩的意思。這讓我震動很大。
第二天睡醒,他消失不見。
我惆悵了很久,為了和這個人再無相逢的機會。
當然,我不知道,命運已經安排了我們再見之日。並且是那個情況。
四 出門
書生走了。但,我的人生再也不同。
接下來,我每天練習所學。
書生說過,因為他不收我為徒,不想別人看出我的師承,只能教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所以除了馬步,還有一套連名字都沒有的拳路和吐納運氣之法外,他教我一套十分常見,無所謂師門的「三才劍法」。
書生說,正因為太通俗了,很多人不覺新奇,大半不肯仔細練,很容易走樣,以訛傳訛。而他教我的,就是一套還原歸本,乾乾淨淨的「三才劍法」。不但容易入手,用心練必會受益,將來有緣再學別的,也比較容易上手。
他還跟我說,練拳不要只練招式,要練到有一天可以感覺到「體隨氣動」。
「所以你要認真打坐,吐納運氣久了,你有了內功,要打拳,要使劍,就都不一樣。」書生說。
他也給我誇讚。「我看你學劍很聰明,使劍很輕靈,有天分,一定會練出火候。」
不過,他也告訴我另一件事,「不管練拳和練劍,練是一回事,真正和人家動起手來,又是另一回事。」書生說。「練熟的招會用得上,可更多時候,你得臨機應變。」
我問他如何臨機應變。
書生哈哈笑起來,說他講得出來就不是臨機應變了。
我記住他的話,朝夕苦練。
不管冷熱,找得出空的時候。不只是武功,還有他寫下來留給我的三百個字的字帖。
有時候,起得晚了,會吃堂叔狠狠的排頭。但是我不在乎。一天天覺得自己越來越有進展,很享受。有些不知名的期待,也在心底隱約地蔓延、游移著。
書生告訴我,劍要藏著,不要外露。我聽他的話做了,但是卻沒有藏住我的夢想。
我不要只是窩在這裡過太平日子。
我也想出去做買賣,看看外頭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劇變不斷。
我遇上書生那年,北方石敬塘跟契丹借兵,滅了後唐,改朝晉。我所在的吳國,徐知誥也進一步廢了楊家天下,先是改吳為齊,以昇元為年號。等到北方的後唐滅亡,徐知誥自稱是唐憲宗的後代,所以回歸李姓,改名昪,同時又再改國號為唐。也就是後來大家所說的南唐。
雖然出門總是不平靜,可我們唐國比起北方中原可說是富庶又太平,何不一試?
終於,有一天,那游移的期待具形迸現了。
有個每年總會經過一趟的茶葉商人,和另一幫喝醉了酒的客人起了衝突。先是口角,後來鬧起來。
茶葉商人本來有個年輕的隨從,這次沒看見。那些人看他孤單,就要欺負他。
我過去勸解,一個塊頭很大的傢伙瞪了我一眼:「你算什麼東西!」一把推來。
說起來,我都分不清到底是被他趾高氣揚的那句話激怒,還是早就準備要出手,總之,我反手一格,再一拳打到他腰眼上。
大塊頭一下子癱倒在地上。
其他人要上來,我簡單俐落地撂倒兩個之後,就都安靜了。
「要欺負人到別處去!」我跟他們吼了一聲。
我堂叔瞪大了眼睛在看我。
那天晚上,堂叔把我找去,問我怎麼會了拳腳。
我一五一十地說了。
堂叔聽我有了一把劍,眼睛瞪得更大,跟銅鈴一般。那時候,律法亂,一般人私有刀劍,是可大可小的事。我本來擔心會挨一頓罵,可他沒說什麼就叫我回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堂叔和堂嬸一起叫我過去,劈頭一句輪到我瞪大眼睛。
「以前常聽你說能出去走走多好,現在還想嗎?」堂叔問,聲音很輕柔。
接著他跟我說,茶葉商人這次身體微恙沒有隨從,是因為那個年輕人在路上得了痢疾,一病不起。
「他是我們的老客人了。我看他這樣在路上沒有人陪是不行。你想的話,我來幫你問問。」他說。
堂嬸一向話多又快,那天早上在旁邊一直只是看著我,沒出聲。
事情很快就談妥了。
茶葉商人本來就知道我,再加上昨天幫他解圍,一聽堂叔建議他帶我出去,沉吟了一下,也就同意。
唐朝時候,出門做生意,路過關津,都得有「過所」,也就是通關文牒。不但商人自己,隨行的姓名也得註明清楚,檢查嚴格。等到了五代,天下大亂,各國之間的關防之地防備固嚴,國境之內的通行就看情況,鬆緊不一。
茶葉商人說他回去之後就要收手不再出門了。所以帶我去不了多遠的地方,能教我多少買賣的事也說不準。但如果我真想出門看看,還是樂意帶我。路上如果碰上盤查的時候,只要記得報上他原來那個隨從的姓名,也就可以了。
他直跟我堂叔道謝:「這也是幫我的忙。他跟著我,我放心,你也可以放心。」
忽然,多年的夢想,早就埋起來的夢想亮了起來,像是有個新的天地在我眼前打開。
生平跟人第一次打架,竟然就有這麼美好的獎賞?我都不敢相信。
我才不管茶葉商人回去之後就不出門了怎麼辦。只要能先出門就好。出了門,自然有新的機會。我很有把握。
這樣,沒幾天,等茶葉商人料理好他的事,我就可以跟他走了。
堂嬸把這幾年幫我存的賞錢給我,有一貫錢,約一千文錢。倒是堂叔說我出遠門,身上要有點錢,慷慨地給了我一些盤纏。他知道茶葉商人要去的方向之後,還推薦我有需要可以去一座縣城找他的朋友。
他對我的態度也和過去完全不同。之前,堂叔看我的時候,多半拉著臉。那幾天他可一直都是笑臉。
連他兒子,以前從不正眼看我,也跟我點點頭,閃過不知是羨慕還是什麼的眼神。
我帶著一把劍和一個小包裹,和茶葉商人上路。
和堂叔不捨地告別後,出了客棧走遠一點再回望,看到他帶著從沒有過的輕鬆笑容跟別人朝我指指點點,心頭最後一丁點牽掛也全部放下。
我出發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