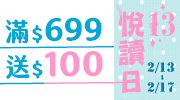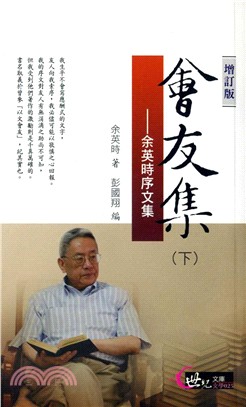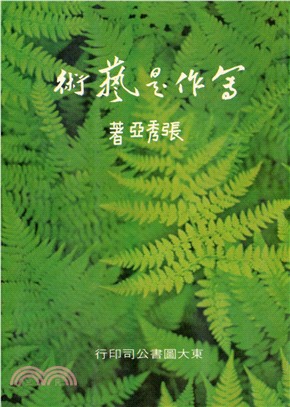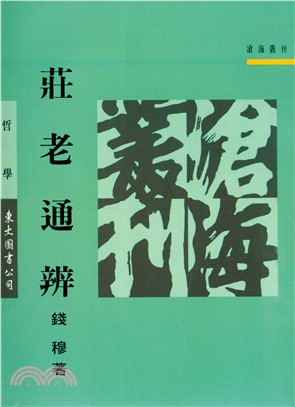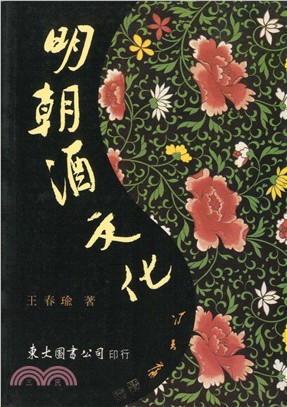商品簡介
小街、古都、天子腳下
紅樓、五四、反帝百年
流亡者蘇曉康回眸當年
崇禎上吊自盡御花園
青年毛澤東打工閱覽室
中共創始西齋廂房
文革狂飆沙灘大院
學生運動百年迴圈
我在那「五四紅樓」旁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一直不知道它與我們「新中國一代」有何關係,直到八○年代我偶然走進那裡,才發現「歷史」整個兒是一個騙局。
——蘇曉康
他的文字掃過景山東街,彷彿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郭沫若、梁漱溟、錢穆的身影還在流動
再進紅樓大院,依稀仍有陸定一、周揚、江青、戚本禹等留下的蹤跡
新文化發源地曾是皇家馬廄
皇城根已是明清兩朝絢爛的屍骨
世界獨有八公里長古都中軸線隕落
古城牆改建為「北京的瓔珞」夢碎
林徽因吟唱古城樓在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梁思成悲史」摹寫千年燕京淒涼的毀滅
這個最「文化」的地方恰是百年劇變漸成文化沙漠的策源地
「沙灘」上構建造反神話新人譜系「戀父」愛黨
「孑民堂」出產革命經典偷換大眾想像
「瘋婆婆」匿名攻擊「副統帥」
「閻王殿」終成屠場傾巢無完卵
好一個白茫茫大地
一把辛酸淚恰似《紅樓》
筆直的街道,蘇曉康執筆如火燭,帶著我們走入其中
作者簡介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詰問華夏歷史,悲歎文明衰微。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凡三十年,未止思索,筆耕不綴。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1989-2019》等。
序
一個人的少年,常常到中年之後只剩下濕漉漉鵝卵石的雨夜迷濛,或者清晨瀰漫在胡同裡勾魂的炊煙,然而我的少年卻是另外一種,雖然也同一條小街藕斷絲連著,雖然那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一條小街,沿街有副食店、理髮館、煤球場、小飯鋪等等,來來往往的也都是表面上只為柴米油鹽的升斗小民,但是那彷彿只是一個錯覺─這條街的西頭,緊靠明清兩朝的皇宮後苑,於是這尋常巷陌,沒有一絲過渡就銜接了「黃瓦紅牆」,一種優美的古典,而黎民晨起暮伏於其間,並未覺察城牆、樹木、街道的美妙襯托、銜接,別具一格。
我要到青年時代,才從一位建築師的描述中追憶這美妙:「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築。天然的材料經人的聰明建造,再受時間的洗禮,成美術與歷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鑑賞者一種特殊的靈性的融合、神志的感觸。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廢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這段文字取自梁思成一九三二年寫的《平郊建築雜錄》,據說這優美的文字其實出自他的妻子林徽因,極富盛名的民國才媛,新月派詩人,寫得一手極品散文。她那句「時間上的漫不可信」,恰好叫人遠溯到一千年前的另一句話:「很早以前,一個遙遠的國家曾有一座迷人的城市。那裡有金碧輝煌的宮殿,莊嚴的廟宇,華麗的牌樓,優美恬靜的園林以及由成千上萬座灰色瓦房組成的幽靜的四合院。」這是一個義大利人說的,他叫馬可.波羅。
少年從南方來北京,我還些許能感覺到一種古帝都的氣派,那黃瓦紅牆、嶙峋城樓、廟宇殿群,是隨時隨地觸目可見的;不過我後來從書上讀到的、當時梁思成對周恩來動情描述的「帝王廟牌樓在夕陽跌墜,漸落西山背景下的高度美的畫面」,則是壓根兒無緣見識了。這座古都最終沒有倖存下來,是我們追懷這些文字之際最為痛徹的。八○年代我在報告文學創作的初期,曾挖掘一部建築史與政治史交織在一起的「梁思成悲史」,四九年北平改名為北京,梁思成就建議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避免毀掉古都,求得新舊兩全,但是遭到蘇聯專家的反對,他們主張將中央行政區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毛澤東支持後者。接下來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陸續被拆除。所以北京在五六○年代是有一種歷史性的擠壓發生了,讓你處處覺得有一個驕橫的粗人,肆無忌憚地躺在
明清兩朝絢爛的屍骨上撒潑,你或許可以聽到那屍骨的呻吟。
這裡是所謂「天子腳下」的地方,古皇城的邊緣,至今留著一個地名叫「皇城根」,還分東西兩段。我剛來時很久都不懂這個「根」字是什麼意思,北京人喊它時又添了一個輕飄飄的「兒」的尾音,讓我覺得更怪。其實我從杭州來,杭州話本多「兒」音,只是那「兒」一下的位置,與北京話多不在同一處。哪裡還有什麼皇城?皇城該是個何等模樣?只聽老北京說,至少大清時的皇城範圍是沒有百姓居住的,以現代北京城從東四到西四這麼大一塊地方無人居住,那情形我是想像不出來的。六○年代初,也就是「文革」前的北京城,這一帶的氣象,是中央機關的衙門、宿舍糾纏在港汊般胡同裡的民居之間,設若一個做腳力的搬運夫,全家五六口住在胡同裡幾米見方的破屋裡,出門來拉著他的板車從這「皇城根」逶迤西去,途經紫禁城外的護城河時,就會穿過許多從前的王府大門,裡面如今都住上了坐紅旗轎車的元帥或副總理什麼的,搬運夫的兒子永遠不會同那深宅大院裡的某個公子哥兒,在路邊彈玻璃球或踢毽子,也絕不會一道去逛景山的;過了故宮再往西一兩里多,上得一座橋來,便有鐵欄杆和佩槍的士兵了,橋一側是悠悠的白塔,另一側便是中南海,猶如一口不斷釋放出風暴來的深潭,平日裡卻總是靜靜的……不過連販夫走卒都很清楚,有一個他們稱之為「救星」(不再叫「天子」)的人住在那裡面,他若起心動念或者脾氣不對勁,那可是不得了。有野史也稱,梁思成對中央機關設在中南海有意見,認為不應該在皇家花園這樣旅遊的地方辦公,建議到北京東南朝陽門外日壇一帶搞政府大院辦公,則北京市民不僅可以到北海划船,也可以划到中南海去,毛聞之不悅,說這不是要把我趕出去?
再回到那小街。上面我說了小街西頭連接的古代和古典,終於隕落了,然而小街的東頭,卻奇妙地連接著現代,因為那裡坐落著近百年中國人無法拒絕的兩棟建築物,一是舉世聞名的北大紅樓(即北洋時期的北京大學一院,也就是文學院),二是紅樓後面的大操場上四九年後蓋起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的辦公大樓,是淡紅色的。於是,這條小街的西頭,就怪誕地連接著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個風暴眼:「五四」和「文革」,而從這條街上走過的那些身影裡,必定會有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郭沫若、梁漱溟、錢穆等,還有那個當年寒酸卻野心勃勃的毛澤東,以及六○年代初在文革舞臺上顯赫一時的諸多「文痞」..於是你可以發現,小街西頭古典的隕落,究其因果,多少又同小街的東頭有關。
這條小街叫景山東街。此地緊挨皇宮,從清朝中期以來都屬於一座公主府,晚清改為京師大學堂,那時仍沿用舊稱叫馬神廟,但廟址不存;張中行老先生對它的描繪最簡潔:「馬神廟是景山山頭直向東看的一條街」。到北洋時代學堂改為北大,街名亦更新為景山東街,直到上世紀六○年代我去那裡的時候還叫這個街名,現在好像改稱沙灘後街了,大概因為這一帶俗稱「沙灘」。少年時剛到那裡,我就很奇怪如此繁華的地方怎會叫「沙灘」這麼個荒涼的地名,有人解釋說北京在遠古不過是渤海灣淤沙堆積而成,所以留下這個稱呼。我慢慢長成大人的歲月裡,越是回味這個稱呼便越發覺得它再貼切不過:這個最「文化」的地方,可不就是中國經百年劇變漸成文化沙漠的一塊策源地嗎?曾經踏上這條小街連同掩隱在它後面的那種歷史,沒有半點值得誇耀之處,我只驚異自己居然那樣貼近過釀成這種「失去」的歷史源頭。
再交代幾句方位。這裡還借張中行先生,一位老北大也是老沙灘的文字,他寫在《負暄瑣話》裡的一句:「紅樓是多方面的中心。形勢四通八達:東接東四牌樓,西接西四牌樓;南行不遠是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北行不遠是地安門、鼓樓,風景也好,西行幾百步就是故宮、景山、三海。」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磚木結構,坐北向南,到六○年代,已是北京鳳毛麟角的西洋化建築,樓前一條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貫通北京東西城的幾路電車均必經此站,站名在「文革」時改為「五四大街」,可人潮洶湧之中,會有幾人還知道「五四」聖殿就是這棟紅樓?
這「五四」紅樓,文革前幾年搬進去了國家文物局,我家則一直住在緊挨它的那棟沙灘大院「紅前樓」裡,到八○年代初才搬走。日後每每路經那個繁忙車站,我都忍不住要觀望那紅樓的門簾一眼,它旁邊那個郵局當年是「未名社」的遺址呢。接近八○年代尾聲,我製作那部流產的電視片《五四》之際,要說一說現代中國之開幕式的這場運動裡的一個小故事,又跟這紅樓有關,而「五四」歷史著作中很少提到它,記得我們還特意進國家文物局裡面,拍了一組鏡頭。故事要講的是,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遂安伯胡同,他計畫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要召集北大學生班長和代表,把巴黎和會的噩耗告訴大家,號召學生奮起救國,可是五月四日(「五四」)那天早上,他卻匆匆趕到馬神廟北大一院,即這棟「五四紅樓」,去勸阻學生上街遊行!他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被視為異端,若再鬧出事來,恐怕首先遭難;他甚至說學生因救國而犧牲學業,其損失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然而蔡元培也難挽狂瀾於既倒,「五四」運動還是發生了。這個細節的歷史張力實在太大了,而「五四」公案,說它是「斬斷中國傳統」之大禍,拿它上比拳亂下附紅衛兵造反一鍋熬,指它抑啟蒙而揚救亡,至今眾說紛紜。
還要惋惜的是,我想拍的電視片《五四》,也因七十年後驟起於天安門廣場的另一場學生運動而夭折,其間我也曾去廣場紀念碑下勸說學生撤退,即五月十四日「十二名知識分子上廣場」,自然我們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畢竟模仿是笨拙的,儘管是模仿七十年前的蔡元培。那學運後來潰散於血泊之中,我也因此倉皇辭國,不覺已然三十年流逝,到此刻二○一九年我來寫「沙灘」,距離「五四」已整整一百年。
目次
引子
上 闋│皇城根上
「西齋夜雨聲」
歪脖老槐樹
萬春亭
中軸線
紫禁城
筒子河
雪池胡同
紅學家
文華殿曹雪芹展覽
「記住老師說的話」
孑民堂
楊家有女
中 闋│景山東街
景山公園清道夫
明清猶在
三海
四十五號院
後海一水榭
「感情說」大將
銀錠橋
「北河沿的路燈」
東華門
隆福寺
下 闋│紅樓大院
圖書館抄寫員
爬窗溜進審片室
白毛女
東方紅
忠叛之辯
刀筆吏
瘋姥姥
「閻王殿」
電影處長
劫餘
老夫子
筆墨之禍
煤山斜暉
書摘/試閱
「西齋夜雨聲」
御花園景山東側,黃瓦紅牆之外,幾步之遙便有一個門臉,影壁後面是一個深院。過來人回憶,門口傳達室的校工,閒聊某某官宦、某某教授、某某名人,如白頭宮女說玄宗─這如數家珍,說的「五四」時代。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內務府奉旨修復馬神廟和嘉公主府作為大學堂校舍;一九○四年又在其附院修建了十四排大屋頂平房,由南向北一路排下去,每排四間,該院即「西齋」,張中行稱之為最早的中國大學男生宿舍。他談「沙灘的住」,說男生宿舍「量」多,計有東齋、西齋、三齋、四齋。「齋」的古意,指文人的書齋,唐詩〈錢塘青山題李隱居西齋〉:「小隱西齋為客開,翠蘿深處遍青苔」;晚清龔自珍有「門前報有關山客,來聽西齋夜雨聲」之句,我取來做題這一節,只是覺得有意境,也可知遲至「五四」時代,西化的新學堂還不甘心用新詞「宿舍」取代古雅的「齋」字呢。
相傳西齋十二號(也有說四號)宿舍裡,住著兩個學生,一個叫顧頡剛,另一個是剛來的,叫傅斯年,兩人討論要不要趕走一個叫胡適的教授,因為這位從美國回來的教授講哲學史不講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開講,這樣的人怎配來北京大學登堂授業?顧頡剛覺得胡先生有新意,希望傅斯年作個評價。所以西齋所在的馬神廟一帶,因北大的緣故,可謂「出入皆鴻儒,往來無白丁」。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接掌由京師大學堂改名而來的北京大學,「北大紅樓」要到次年才落成,他就在西齋辦公。一九二一年他批准在西齋辟兩間屋子,成立「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德文「共產主義」的譯音。發起人羅章龍後來回憶,這兩間寬敞的房子既是圖書室又是翻譯室,還做辦公室。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兩邊貼著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上句是陳獨秀的話,下句是北方人李大釗與南方青年學生們在一起吟詠的詩句。所以當代中國有一個源頭,倘若把它從上海法租界和嘉興南湖的一條絲網船,挪移到北平一座公主府的附院廂房裡,至少要古典一點吧?這不是杜撰,上述史料便是證據。直到一九五二年北大才由沙灘搬去西郊燕園,這三十年間很少有人提及西齋了,以致一九四九年春,得手天下而在西柏坡喊了一聲「進城趕考去」的毛澤東,到香山見一個北大學生時問道:「西齋還在嗎?」
我生在杭州,十一歲那年父親從省報,被調到《紅旗》雜誌社當編輯,於是全家順京滬線去了北京,住進沙灘景山東街西頭的這個「西齋」。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近百戶人家擠在一起的一個大雜院,院內沙丁魚罐頭似的一溜兒十幾排密密麻麻的平房,排與排之間,相隔約五六米的空地,栽著大樹,枝冠茂盛。我在南方沒見過這種房子,也絲毫沒有不少人在回憶錄裡盛讚西齋如何「窗明几淨」的感覺─我家在杭州住的是「竹竿巷那間三面都是玻璃窗的房子」(父親後來的描述),我從小在西湖之畔,晨夕兩頭都跟湖上的朝霧晚霞相遇,而霧化在心裡的某種「蘇杭優越感」,有點視幽燕為「苦寒之地」;坊間也有一個傳說,中國文改之父周有光原住上海,胡愈之動員他來北京,他不願意,說北京雨水少,風沙大,春風一颳起來,到處髒兮兮的。最後他還是搬來了,就住西齋隔壁。
我只習慣南方那種鵝卵石小巷子的生活─即使清早一派涮馬桶的聲音,那涮出的髒水又隨地就潑─卻久久習慣不了北京胡同裡那種共用露天水池和廁所的風俗,比如我們住的西齋,並非一個胡同,卻也是兩三排平房的七八戶人家,共用那兩樣,水池是冬天凍住了要拿開水去澆,廁所則總是污穢滿地。記得媽媽有半年都沉著臉,怨爸爸不該來北京。我們江南的孩子到北京,還要遭兩樣罪,一是春天乾燥風烈,嘴唇龜裂瘀血,二是寒冬手腳長凍瘡,也會破裂化膿,不過就像牛痘,一般得過就免疫,一季而終。
我十一歲那年是一九六○年,正值饑荒年饉。江南好像沒那麼慘烈,我們在杭州,大概因為有舟山漁場,報社食堂裡一日三餐吃帶魚,吃倒了胃口,但是我沒有飢餓的記憶。到了北京才發現,肉、油、細糧(白麵、大米)都要憑證,蔬菜極少。那時媽媽總讓我去買東西,記得她把那些票證藏得很嚴實,比錢還金貴,每次撕給我一張,總是只買二兩肉,細細的一條,家家戶戶如此,因為每月按人頭只供應半斤豬肉。大家在肉鋪排隊,老遠就盯著那割肉的,看他下刀割到哪裡,輪到自己是肥是瘦,若是白花花的一條肥肉,你連燒碗麵都不行,於是就會有人同那賣肉的吵架,誰敢同他吵,下回還讓你白花花拎一條走。剛到京城那年,好像是連豬肉也沒有的。春節前我們小孩子的一大任務,是兄弟姊妹輪班到大菜市場排隊辦年貨,無非是買些包餃子的肉和菜,卻要從半夜排起。我們那一帶最大的菜市場,在朝陽門附近,對面就是文化部大樓,記得那年我排了整整一天,凍得孫子似的,買來的居然是一塊馬肉,媽媽把它燉了,我只嘗了一口,很粗糙,還一股土腥味。
這西齋早已失去昔日的光環,像一個被遺棄的婢女,無人問津。話說北大遷往燕園之後,一九五四年中直機關事務管理局接管「沙灘大院」,分配給中央宣傳部使用,必定那時也將西齋劃歸過來了,此後沙灘大院大興土木,在當年的「民主廣場」北端興建了五層辦公樓和一批宿舍,西齋則一直沉睡著。這裡住的都是中宣部和《紅旗》雜誌社的人員嗎?我家住在好像是第七排的兩間房子裡。
「嗨,我叫渡江,住後排,你叫什麼?」一張笑咪咪的鵝蛋臉。
看上去就是樂天少心眼的一個男孩,在水池邊上跟我搭腔。名叫「渡江」,便是四九年春共產黨渡江攻打南京時生人,比我大幾個月。他們一家人住在後面的第八排,他是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孩童年歲的小弟弟。我似乎從未見過他的父親露面,只有他的媽媽,一個高個子大嗓門的婦人,好像脾氣暴烈,常常厲聲責罵孩子們,或指桑罵槐什麼,看得出來這家人發生了什麼,鄰里無人議論。渡江人緣好,跟西齋男孩們玩在一起,或去景山漫坡撒野,或去筒子河遛彎,並無芥蒂。忽一日,只聽見後排渡江媽媽爆發式的嚎啕大哭,原來他爸爸被發配新疆。幾個西齋男孩,默默來找渡江:
「咱們去北海划船,給你送行!」
我們出了西齋,從景山東門洞穿到西門,再往西走過一條幽靜小街,兩側皆深宅大院,出來就是北海東門了。這門叫陟山門,隔門相望,那座喇嘛教形制的白塔,頃刻就在眼前。再跨過一座陟山橋,便上了瓊島,沿湖畔小徑,往北繞到漪瀾堂。這裡在前清就是一個帝后們遊園泛舟的碼頭,末代皇帝退位後,幾個御廚跑來開了一家「仿膳」,聞名京城。漪瀾堂水面,氣派闊大,跟前就是租船碼頭。那天已是黃昏時分,大家駕船下水,還唱起歌來,划船能唱的歌只有一支,就是那首〈讓我們蕩起雙槳〉,我在杭州西湖划船也唱過它,歌詞有如「紅領巾迎著太陽/陽光灑在海面上/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盡是一些標準的五十年代「幸福雞湯」,來北京後才知道,這首著名歌謠,是新中國第一部兒童電影《祖國的花朵》主題曲,就是在北海公園拍攝的。渡江自然再也唱不出這種歌詞,只奮勇划槳,而其他人也絲毫沒覺得尷尬、諷刺。湖面上風急浪大,大家吼著划著,只見渡江淚水滿臉,忽而大家也跟著哭成一團。這北海划船,彷彿歃血為盟,結拜弟兄,西齋男孩們做了一回死黨。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渡江的父親叫李之璉,中宣部祕書長,他的劫難,竟然是跟中國文壇巨案「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有染。那是一九五五年反右前,中國作家協會的文藝官僚劉白羽等,代表中宣部陸定一、周揚來管文學,跟以丁玲為首的創作實力派之間發生一場權力爭奪,當然丁玲落敗,被打成右派;而丁玲背後似又有胡喬木的支持,一九五八年再向中宣部遞交申訴,李之璉僅僅因為職位之故,恰好由他接手處理,也由此遭恨於陸定一、周揚,而在一九五八年被他們劃為「極右分子」。這是我十幾歲到京城裡看到的第一樁政治險惡,曉得周揚這廝在文壇的霸道;誰知快三十年後,中國大小報刊上圍剿我的《河殤》和報告文學的大批判中,最積極的打手,還是劉白羽這老頭。弔詭的是,丁玲在延安就說過「黨管文學」的話,她自己最後被黨管到死,她跟周揚之間,難道真有是非嗎?而中國的文學至今也沒有逃出黨的牢籠。文革後李之璉獲平反、復職,但是我再也沒有見到渡江。
筒子河
故宮四四方方一塊,四角各有一座角樓。這角樓,雖不是午門、神武門那一類巍峨城樓(形制均如同天安門),卻精巧得多,彷彿雕梁畫棟都縮小了尺寸,而樣樣俱在。每座角樓立於護城河轉彎的直角頂端,跳開大城樓自成孤獨一景,常常在夕陽下散發出一股難言的惆悵。東南角上的那一座,離我家住的西齋,僅幾步之遙,對我而言,皇宮鋪天蓋地一如莫測的金色大湖,唯有這孑然一身的角樓可以寄託少年時的徬徨。
皇宮旁小街人生的開始,忽有一種極大的壓抑感降臨,叫我知道辛稼軒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並不貼切,西湖邊上的年少爛漫、無心和「不知愁滋味」竟是帶不過來的,而少年有愁但不會描述才是真的。愁什麼?如今去回想,張嘴就帶南方口音,不會說京腔兒,在京城會被歧視,上課最怕老師提問,是很現實的一樁。我放學回家,每天路經故宮東南角樓,常常由不得止步,靠一棵樹幹眺望它,或趴到護城河的石岸端詳它。直到今天,那餘暉中的角樓身影還時常會在夢裡浮現。
這筒子河繞紫禁城一周,離城牆根兒其實很遠,這裡本來有宮牆外所謂「紅鋪三十六」,護衛故宮的森嚴兵丁值房,現在成了一條青翠的林帶,晨曦薄暮之際,乃是人們晨練、散步、戀愛的地方,演員在這裡吊嗓子,樂手吊他們的小號黑管,學生們則背書,某日清晨,我也開始在這裡背俄文,應付考試;黃昏時節也可以來這裡遛彎。多年後我才讀到老舍的一段感慨文字:「北京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的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閒的地方……。」北京話「喘氣兒」很有空間的神韻,物質精神都囊括了。據說老舍常常面對積水潭,背靠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心中安適寧靜,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孩睡在搖籃裡─曾經有過那樣舒坦的一個北京,但可以想見失去那種北京的老舍,日後是逃不脫要跳進太平湖的。
故宮城牆,其實就是小了一號的北京城牆;換言之,我在筒子河青翠林帶曾享受的空間神韻,是可以建構到北京巨大的城牆上下的,而這恰好是梁林伉儷的一個絕妙設計和夢想。他們在禮贊了故宮、中軸線等等之後寫道:
但是一件極重要而珍貴的文物,竟然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視,那就是偉大的北京城牆……它的樸實雄厚的壁壘,宏麗嶙峋的城門樓、箭樓、角樓,也正是北京體形環境中不可分離的藝術構成部分,我們還需要首先特別提到,蘇聯人民稱斯摩林斯克的城牆為蘇聯的頸鏈,我們北京的城牆,加上那些美麗的城樓,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華人民的瓔珞了。
城牆上面面積寬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種花草,安設公園椅,每隔若干距離的敵臺上可建涼亭,供人遊息。由城牆或城樓上俯視護城河,與郊外平原,遠望西山遠景或禁城宮殿,它將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園之一─一個全長達三九點七五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
後世稱它是林徽因設計的「北京的項鍊」,但是在她自己的文字裡,她使用的詞更典雅:「瓔珞」。
梁林伉儷第一想完整保護古都不被政治中心擠壓,第二就想挽救天安門「T」字型宮廷廣場,與蘇聯專家激烈爭辯,負責首都改建的副市長吳晗斥責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當場痛哭失聲。毛澤東聞訊說道:「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天安門外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一九五二年拆除,中華門一九五九年拆除。接下來梁林又竭力挽救起城牆來。一九五三年林徽因為了保住永定門城樓,指著吳晗的鼻子說:「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時你們再蓋的就是假古董!」兩年後林徽因病逝。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牆:中央是宮城(故宮),第二層是皇城,第三層是京城─分為內城、外城(即南城)。裡應外合的三道城牆,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林徽因說的「瓔珞」,就是最外層的京城,「新王朝」決定拆除它,梁思成五○年撰文力陳城牆存廢之得失,他說:「北京城牆除去內外各有厚約一米為磚皮外,內心全是『灰土』,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堅硬如同岩石,粗估約一千二百萬噸,堆積起來等於十二個景山,用二十節車皮需要八十五年才能運完。」然而,這位大師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深挖洞」的文革時代,不過是小菜一碟,輕而易舉就解決了。
昏日。人海。塵霧。一九六九年冬春之交,復興門城牆邊。
城牆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蘆,黑壓壓的人群像是那趴滿糖葫蘆的螞蟻。在昏黃的陽光下,北京市民從四面八方撲向城牆,用鍁鎬撬扛支解這條奄奄一息的長龍。從它身上剝下來的鱗片─那一米多長的方磚,被各種卡車、三輪車、板車、馬車、排子車和手推車,源源不斷地運到全市各個角落去砌防空洞。北京人拆得極為瘋狂,各單位飆著勁幹,比誰的裝備多、人力強。在那塵埃漫漫、萬斧霍霍之中,同那個時代非常對味兒的一種破壞欲支配著人們,使他們除了冷酷和殘忍的競賽之外,絲毫不會想到這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
……扛撬錘擊,夜以繼日。城牆雖然出乎意料的堅固,但終於崩潰了。被剝盡了鱗片之後,她就像一個扒光了裙衫的老嫗,露出了千瘡百孔、慘不忍睹的軀體。在她身邊,剝下來的鱗片堆成小山,標上某某單位或個人所有的記號;暫時運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當全市「深挖洞」,和居民蓋小房的原料基本滿足後,「拆磚熱」漸漸冷卻,人們便不再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只有清華園裡還有個老人在為她哭泣。梁思成在報紙上看到,拆西直門時發現裡面還抱著一個元代的小城門,這時林徽因已經不在了,他央求續弦林洙:「你看他們會保留這個元代的城門嗎?」
林洙在回憶錄中寫道:
他懷著僥倖的心情對我說,「你能不能到西直門去看看,照一張像片回來給我?」他像孩子般地懇求我。
「幹嗎?跑到那兒去照像,你想讓人家把我這個『反動權威』的老婆揪出來示眾嗎?」……
一九五三年左安門拆除,一九五四年慶壽寺雙塔拆除,一九五六年中華門拆除,一九五七年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朝陽門拆除,一九五八年右安門拆除,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門、元城牆拆除。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被拆除。只有正陽門、德勝門、鐘樓得以部分保存。
一九七二年元月九日,梁思成在北京醫院含屈而逝。
文華殿曹雪芹展覽
說到《紅樓夢》,其實我是勉強讀完前八十回,就不要讀它了,大概文化低、鑑賞力差,以後對海內外的種種「紅學熱」我也一向很淡。然而在少年時代,我還真的飽受一次「紅樓夢」的視覺衝擊,終身難忘。
那是在不大吃得飽的一九六三年,故宮舉辦了一次曹雪芹展覽,是他的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在紫禁城東側的文華殿展出,展品多達兩千多件,皆為康雍乾時代的服式、器物、園林建築,有六個展室,琳琅滿目。這文華殿,要繞到東華門進入,離西齋也不遠,順北池子大街一遛彎就到了。
我至今還有印象,整個展覽會最奪目的,是一件大紅猩猩氈斗篷,也就是書中賈寶玉身上老披著的那一件,它是展覽主辦人錢杏酲(阿英)在故宮地庫裡「淘寶」淘出來的,令他喜出望外;他還淘出一件俄羅斯毛裘,元春歸省時穿的那件,非常得意,說:「我也未曾想到,還真有這樣的毛裘!它是用孔雀毛撚成線,再加金線縷織成的」─跟曹雪芹在書中描寫的細節完全吻合。
「紅學」裡面,有一門通俗紅學,也就是從《紅樓夢》衍生出來的繪畫、戲曲、說唱藝術等等,阿英是這方面的專家,出版過《〈紅樓夢〉版畫集》、《紅樓夢書話》兩本書。六三年他著手籌辦這個展覽,選了兩個助手:一個是畫家黃苗子,管史料;一個是漫畫家丁聰,負責裝潢布置。兩個人都是「摘帽右派」。
展覽會從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到《紅樓夢》的各種版本、著述,一覽無遺。至於《紅樓夢》時代的參考文物,他們從故宮文物庫裡,精心挑選出康雍兩朝頒發給曹雪芹祖先的誥命,曹寅、曹頫給康熙、雍正的奏摺,還有曹頫、李煦被革職抄家的檔案史料等,甚至《紅樓夢》裡描繪的聯珠帳、琥珀杯、金玉如意等,都找出來展覽。
有一方二寸多長的石硯,在二千件展品中鶴立雞群,即那件薛素素的脂硯,是張伯駒的藏品,據說展前張伯駒將此硯讓周汝昌鑒賞,周建議他送展,脂硯可能是第一次面世。我後來在網上看到,一九六六年脂硯由外地展出返京時神祕失蹤,至今下落不明。這方名硯,幾百年裡都是蹤跡神祕。史傳,它最早由明萬曆間名妓薛素素所藏;康熙晚年,由余之儒從薛氏後人手中購得,旋贈與曹寅。此後歲月倥傯,至一九五三年,此硯被重慶金石家黃笑芸在一舊貨攤上發現,以二十五元買下;一九六○年張伯駒鑑定此硯乃薛素素舊物,遂以一千二百元購下收藏。
展覽會還有一個亮點,是幾幅大畫,但是我記不真切細節了。所幸在網上偶見一篇文字〈想起曹雪芹〉,作者鄉公,竟也是當年的一位觀展者,且極有用心的隨身帶了一個小本子,記下三十四頁紀錄,其中提到:
曹雪芹的生平及家事,記得這部分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介紹文字,而是幾幅大畫,是由劉旦宅、賀友直、林鍇分別創作的。現在依手中資料,可知畫共十一幅,分別是:豪門公子、似水流年、家遭巨變、宗學就食、舊恨新愁、山村著書、廢寺留詩、畫石寄傲、佩刀質酒、十年辛苦、淚盡絕筆。當時只覺幅幅精彩,給人震撼,三位畫家身手不凡,當年三位正精力旺盛之時,想必也是他們自已稱心之作。
林鍇的一幅曹雪芹巨像,給我印象尤深,雪芹青袍冉冉而立,手持玉管,圓顱豐頰,天庭飽滿,身後一枝寒梅,背景似展現「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圖景……。
這個展覽吸引了二十一萬人次參觀,盛況空前。展覽結束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了紀錄影片《紀念曹雪芹》。接下來,又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紅學」熱,六三年發表的紀念曹雪芹的紅學研究文章多達一百三十六篇,撰稿人包括沈雁冰、楊絳、何其芳等。
這次展覽,是經周恩來批准,由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和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一九六三年是什麼年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現在有人稱之為「五年大饑荒」,中國餓死幾千萬人,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一九六二年初有一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作了檢討,此後開始包產到戶、農村救命;城市裡開始了「票證時代」,什麼肥皂票、火柴票、煙筒票、鐵爐子票、鐵鍋票、鋁壺票、生爐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還有大衣櫃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圓桌票、鬧鐘票、手錶票、電燈泡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等,北京市一九六一年度憑票供應物品達六十九種。
後來有人回憶起來,把極流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首歌改成這樣:
嘿,九十號!九十號呀,九十號,九十號!
煙號票,酒號票,豆瓣兒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買半塊,火柴兩盒慢慢燒。
媽媽記,娃娃抄,號票不能搞混了。
所以京城裡弄個「紅學熱」,也是為了鬆弛、調劑吧?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