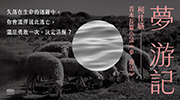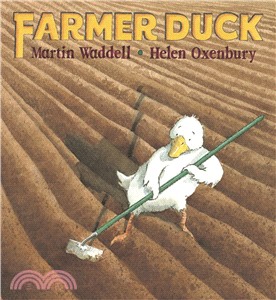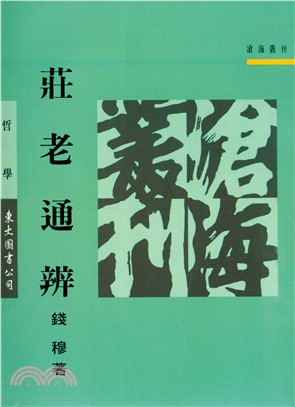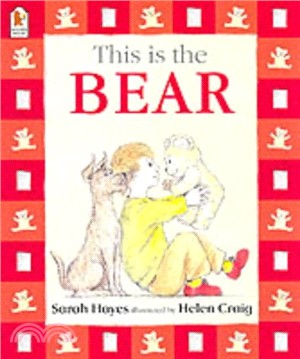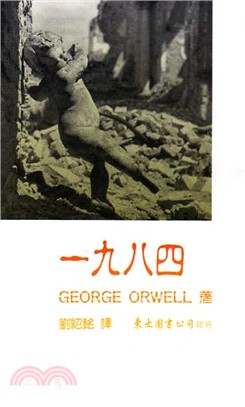誰是葛里歐
商品資訊
系列名:當代名家‧方梓作品集
ISBN13:9789570854701
出版社:聯經
作者:方梓
出版日:2020/04/06
裝訂/頁數:平裝/360頁
規格:21cm*15cm*2.5cm (高/寬/厚)
版次:1
定價
:NT$ 380 元優惠價
:90 折 342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0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深入自然地域的奇幻書寫
演繹山海神話與部落生態
方梓化身葛里歐
是角色的故事
是「創作者」祛邪的過程
是女人們互助、遷徙、尋找桃花源的自我人生
葛里歐,源自西非傳統部落,集吟遊詩人、讚美歌者、口述歷史傳誦者於一身的特殊職業,是部落慶典不可或缺的表演者,也是喪葬悼亡至關重要的致詞者。
活了幾百歲的老母龜阿綠和樹齡超過千歲的胖茄冬,自從相識後每幾年便會脫殼神遊,見面敘舊。這一回她們發現,居然有人看得到她們?!
自幼便欲和原住民文化切割的拉候,沒想到婚後試圖一步步找回傳統和習俗;離鄉背井嫁到外地的純麗,因為婚後家人的冷落,感覺正一點一滴地老去……;長期在雜誌社擔任人物採訪撰稿的女子闕沛盈,喜歡挖掘每個人背後的故事和題材;蘇玉映則是從女工變成國際知名化妝品牌創辦人的成功人士;英鳳早年赴美求學,在女兒出事和丈夫臨終後,隻身一人回台度過餘生。
這五位女人因緣聚會下相聚,決定要來一場屬於她們的東部漫遊,
沒想到竟然遇見一棵會移動的樹和一隻會說話的烏龜?!
方梓繼《來去花蓮港》、《時間之門》後又一力作,透過文字葛里歐之口,讓角色娓娓道出自己的神話和傳說,進而改寫自己的結局。
聯手推薦
郝譽翔(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郭強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廖玉蕙(作家)
(依姓氏筆畫排序)
★本書獲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演繹山海神話與部落生態
方梓化身葛里歐
是角色的故事
是「創作者」祛邪的過程
是女人們互助、遷徙、尋找桃花源的自我人生
葛里歐,源自西非傳統部落,集吟遊詩人、讚美歌者、口述歷史傳誦者於一身的特殊職業,是部落慶典不可或缺的表演者,也是喪葬悼亡至關重要的致詞者。
活了幾百歲的老母龜阿綠和樹齡超過千歲的胖茄冬,自從相識後每幾年便會脫殼神遊,見面敘舊。這一回她們發現,居然有人看得到她們?!
自幼便欲和原住民文化切割的拉候,沒想到婚後試圖一步步找回傳統和習俗;離鄉背井嫁到外地的純麗,因為婚後家人的冷落,感覺正一點一滴地老去……;長期在雜誌社擔任人物採訪撰稿的女子闕沛盈,喜歡挖掘每個人背後的故事和題材;蘇玉映則是從女工變成國際知名化妝品牌創辦人的成功人士;英鳳早年赴美求學,在女兒出事和丈夫臨終後,隻身一人回台度過餘生。
這五位女人因緣聚會下相聚,決定要來一場屬於她們的東部漫遊,
沒想到竟然遇見一棵會移動的樹和一隻會說話的烏龜?!
方梓繼《來去花蓮港》、《時間之門》後又一力作,透過文字葛里歐之口,讓角色娓娓道出自己的神話和傳說,進而改寫自己的結局。
聯手推薦
郝譽翔(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郭強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廖玉蕙(作家)
(依姓氏筆畫排序)
★本書獲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作者簡介
方梓
本名林麗貞。
台灣花蓮人,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總編輯、全國文化總會學術研究組企畫、《自由時報‧自由副刊》副主編、總統府專門委員,及大學兼任講師。
著有《人生金言》、《他們為什麼成功》、《傑出女性的宗教觀》、《第四個房間》、《采采卷耳》、《來去花蓮港》、《野有蔓草:野菜書寫》、《時間之門》、《誰是葛里歐》等。
本名林麗貞。
台灣花蓮人,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總編輯、全國文化總會學術研究組企畫、《自由時報‧自由副刊》副主編、總統府專門委員,及大學兼任講師。
著有《人生金言》、《他們為什麼成功》、《傑出女性的宗教觀》、《第四個房間》、《采采卷耳》、《來去花蓮港》、《野有蔓草:野菜書寫》、《時間之門》、《誰是葛里歐》等。
序
自序
她在小說的世界挑釁我
法國評論家狄伯德把小說讀者分為普通讀者與精讀者;精讀者,可謂小說的生活者,是在小說世界如真實世界般行走坐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精讀者,然而,讀閱或不閱讀時,腦海裡或現實生活中常出現小說的場景、人物,有時是某些物品;在從大樓走出的婦人中,我想她是不是那個優雅的刺蝟?在河津搭上公車往天城山的沿途,想像著八十多年前川島跟著踊子阿薫和我相錯的路線。有時,在郊區的平交道等火車通過,轟轟的火車經過,腦子竟然浮現安娜.卡列妮娜,心頭不免一驚;搭火車經過羅東,偶爾還是會想到阿蒼說:「我真的買魚回來了。」
在寫小說時,腦海裡全是真實或虛構的人物、情節、場地,就連吃飯、睡覺、工作頭上彷彿頂個電影院,這些情節人物也如影隨形般跟在我的前後,小說寫完了這些人事物全都付印在紙上,各就各位,放映結束,連電影院也消失無蹤。
不寫小說的三、四年,頭上沒有電影院,也不必拖著一群人,覺得身心很輕盈。雖然有時會看到小說人物走在街頭,或在書房,我知道那是一種「殘影」,是我不經意想起那些我虛構的人物。
準備寫第二部長篇小說,在書桌前列大綱、人物,我隱隱約約聽到:「我呢?」我聽到我心裡的聲音,一個很熟悉的聲音,我確信是我不是她。我的這部小說不會有她!
這部小說一開始就不順遂。才寫一萬字,母親大病入院,我每週二一下課便搭火車回花蓮,週六日才再回台北。爾後,母親的身體不斷出現各種併發症,過了七、八個月才好轉。在照顧母親,在買菜的市場我又聽到熟悉的聲音:「我呢?」雖然小說停頓了,但我確定小說裡不會有她。
母親的狀況好轉,我恢復往常每個月回花蓮一趟,也開始續寫小說,偶爾母親有狀況,我又得常回花蓮。寫寫停停小說就以拼圖的方式一小塊一小塊的寫。當然「那個聲音」出現得更頻繁,意圖更明顯「我呢?你不能把我丟在那個沒結局的地方。」我看到她經常圍繞在我身邊。她,我在上一部小說《來去花蓮港》中的闕沛盈,她說她不要四十歲就關在一個沒有結局的小說裡。
於是,闕沛盈跑到我正在寫的小說中呼朋引伴挑釁我,告訴我「誰才是說故事的人」。
其實,這是一群女人的故事,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命運,寫著寫著有了叉路,有時停滯,有時不甚滿意,三年來不斷受著這幾個女人的圍繞,她們彷彿看穿我,她們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敵人,她們「演」久了,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像神怪似的拓展她們的能力或者法術,去完成我貧乏的想像。
這是以神話或神怪方式曝寫小說的創作過程的雛型,以未完成的形式留給角色們鋪成。當然,這仍是女人們的遷徙尋找桃花源的故事。
葛里歐(Griot),非洲一個以傳頌各家族歷史,書寫各朝代戰爭的故事為生的人。寫作,其實就是葛里歐,只是在神話的國度,角色們才是葛里歐,不是作者。最終,葛里歐飯店矗立在花蓮東海岸,面對著太平洋。一定得在花蓮,她是我的故鄉。
她在小說的世界挑釁我
法國評論家狄伯德把小說讀者分為普通讀者與精讀者;精讀者,可謂小說的生活者,是在小說世界如真實世界般行走坐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精讀者,然而,讀閱或不閱讀時,腦海裡或現實生活中常出現小說的場景、人物,有時是某些物品;在從大樓走出的婦人中,我想她是不是那個優雅的刺蝟?在河津搭上公車往天城山的沿途,想像著八十多年前川島跟著踊子阿薫和我相錯的路線。有時,在郊區的平交道等火車通過,轟轟的火車經過,腦子竟然浮現安娜.卡列妮娜,心頭不免一驚;搭火車經過羅東,偶爾還是會想到阿蒼說:「我真的買魚回來了。」
在寫小說時,腦海裡全是真實或虛構的人物、情節、場地,就連吃飯、睡覺、工作頭上彷彿頂個電影院,這些情節人物也如影隨形般跟在我的前後,小說寫完了這些人事物全都付印在紙上,各就各位,放映結束,連電影院也消失無蹤。
不寫小說的三、四年,頭上沒有電影院,也不必拖著一群人,覺得身心很輕盈。雖然有時會看到小說人物走在街頭,或在書房,我知道那是一種「殘影」,是我不經意想起那些我虛構的人物。
準備寫第二部長篇小說,在書桌前列大綱、人物,我隱隱約約聽到:「我呢?」我聽到我心裡的聲音,一個很熟悉的聲音,我確信是我不是她。我的這部小說不會有她!
這部小說一開始就不順遂。才寫一萬字,母親大病入院,我每週二一下課便搭火車回花蓮,週六日才再回台北。爾後,母親的身體不斷出現各種併發症,過了七、八個月才好轉。在照顧母親,在買菜的市場我又聽到熟悉的聲音:「我呢?」雖然小說停頓了,但我確定小說裡不會有她。
母親的狀況好轉,我恢復往常每個月回花蓮一趟,也開始續寫小說,偶爾母親有狀況,我又得常回花蓮。寫寫停停小說就以拼圖的方式一小塊一小塊的寫。當然「那個聲音」出現得更頻繁,意圖更明顯「我呢?你不能把我丟在那個沒結局的地方。」我看到她經常圍繞在我身邊。她,我在上一部小說《來去花蓮港》中的闕沛盈,她說她不要四十歲就關在一個沒有結局的小說裡。
於是,闕沛盈跑到我正在寫的小說中呼朋引伴挑釁我,告訴我「誰才是說故事的人」。
其實,這是一群女人的故事,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命運,寫著寫著有了叉路,有時停滯,有時不甚滿意,三年來不斷受著這幾個女人的圍繞,她們彷彿看穿我,她們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敵人,她們「演」久了,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像神怪似的拓展她們的能力或者法術,去完成我貧乏的想像。
這是以神話或神怪方式曝寫小說的創作過程的雛型,以未完成的形式留給角色們鋪成。當然,這仍是女人們的遷徙尋找桃花源的故事。
葛里歐(Griot),非洲一個以傳頌各家族歷史,書寫各朝代戰爭的故事為生的人。寫作,其實就是葛里歐,只是在神話的國度,角色們才是葛里歐,不是作者。最終,葛里歐飯店矗立在花蓮東海岸,面對著太平洋。一定得在花蓮,她是我的故鄉。
目次
序曲
拉候回到Makotaay
氣味
百日關的女孩
有點忙的女人
她是葛理歐(Griot)
究竟有沒有神
我的故事很精彩(一)───是特工不是特攻隊
暴食
那一場豐年祭
誰懂肚臍眼
不能說的秘密
她和她的夢
看得到我們嗎
去海邊
終於回來了
有關我們的傳說
我的神話你的傳說
我的故事很精彩(二)
蛇郎君和石頭公
我的故事很精彩(三)
她的故事
把記憶留在夏天
我的神話家鄉
來去花蓮
造反與封神榜
他要刪改小說
葛里歐飯店
拉候回到Makotaay
氣味
百日關的女孩
有點忙的女人
她是葛理歐(Griot)
究竟有沒有神
我的故事很精彩(一)───是特工不是特攻隊
暴食
那一場豐年祭
誰懂肚臍眼
不能說的秘密
她和她的夢
看得到我們嗎
去海邊
終於回來了
有關我們的傳說
我的神話你的傳說
我的故事很精彩(二)
蛇郎君和石頭公
我的故事很精彩(三)
她的故事
把記憶留在夏天
我的神話家鄉
來去花蓮
造反與封神榜
他要刪改小說
葛里歐飯店
書摘/試閱
序曲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镸差】丘,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镸差】丘北。
奢比屍國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屍在大人北。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熏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屍北。
──《山海經》之〈海外東經〉
海浪不斷拍打著礁岸,激起一叢又一叢的浪花,海面上一艘漁船緩緩移動,夕陽從山巔迤邐灑下,石榴色的霞光漫漶在海面,灰藍的海面鋪上一層薄薄的橙紗,使得冬日嚴峻的海溫柔許多。
老母龜阿綠伸出頭來,深深的吸口氣,一整日的冬陽曬得龜殼暖烘烘的,洞穴也乾爽許多。老母龜阿綠望著眼前遼闊的海,幾百年來的海浪洶湧,嚎吼的東北風似乎也被日頭暖化許多,海風習習吹著。阿綠轉頭回看山崖上的林樹和山土,嘆了口氣。這幾十年來,山土不斷流失,不管根淺根深的樹一棵棵倒掉,連起碼二、三百年的樹都不見,想找個說話對象也沒有。那個老樹精胖茄冬,也有二、三年沒來了。
老樹精胖茄冬知道阿綠道行淺,只有幾百年,得再一百年才能真正脫殼神遊遠處,現在就在鄰近上上下下的。這一百年來,都是胖茄冬來找阿綠。阿綠只知道胖茄冬遠從深山裡過來,胖茄冬說那個地方車子到不了,人也很難到達,否則她們這些老樹精早就被砍光了。
阿綠正想著,一陣陣咻咻咻的聲音從遠處飄來,阿綠知道胖茄冬來了,這個聲音得道行三百年以上才聽得到看得到。二千年的胖茄冬見多識廣,很多趣事、稀奇的人和動植物她都見過,說起故事來又生動,讓阿綠聽入神,巴不得胖茄冬日日來。胖茄冬一年遊歷台灣一圈,這數十年卻不敢橫越太平洋或黑水溝到其他地方。胖茄冬說海洋太遼闊了沒得歇腳,跟山裡的土地不一樣很不踏實,現在竟有心理障礙試過幾次都無法到海的另一端,索性放棄在島的山上山下四處遊歷。
而且每遊一日得養精神兩三日,所以胖茄冬每次脫樹幹殼神遊一百天得回到樹身養神二百日,每年就遊這麼一次。
「老東西,好久不見了。」胖茄冬學人類老婦女稱呼鄰居或朋友叫老東西(妯娌),有年歲漸去,情誼瀝存的感覺。
「這二年妳去了哪裡?這麼久沒來?」阿綠看看胖茄冬有些疲憊的臉色。
「前幾年神遊太久了,傷了精神,這兩年就養著精神不敢四處跑。又看到樹仔僅存的那截根頭完全腐爛了,有些難過也就愈發不愛出門。」胖茄冬眼神迷濛看著海。
樹仔也是一棵茄冬,是胖茄冬的丈大,年齡相當,兩棵樹並肩而立,日日耳鬢廝磨,是樹群中一對恩愛的夫妻。五百多年前來了一株含苞阿娜柔弱的藤蔓蘭,沒多久藤蔓蘭就纏繞在樹仔的身上,完全不顧胖茄冬的制止與警告,樹仔耽溺在藤蔓蘭溫柔的撫觸、纏繞,胖茄冬氣得神遊出遠門,眼不見為淨。
三個月後,胖茄冬回來,只見樹仔的枝葉全都枯乾掉落滿地,被藤蔓蘭纏繞只露出一點點天靈蓋,無力悲悽的看著胖茄冬,胖茄冬得養神無力幫他,眼睜睜的望著他斷氣,藤蔓蘭卻益發得豐茂潤澤,正蠢蠢欲動去勾引其他的樹精。一日大雷噼叭響,一道火光直劈向枯死的樹仔。轟的一聲全樹著火,連藤蔓蘭也燒得一乾二淨,只剩樹仔一截根頭焦黑的立著。
儘管怨樹仔移情,然而連焦黑的根頭都沒了對胖茄冬彷彿是僅存的一點記憶都要抹去了。
阿綠沒有回話,她知道胖茄冬表面看來無所謂,這五百多年來可是一直記著樹仔的好。
「有歲啊,我都兩千歲啊,真正老囉。」胖茄冬經常穿梭在人群市廛,講話的語氣和樣貌愈來愈像老婦人。
「那我算年輕的,還不到一千歲。」阿綠想轉換胖茄冬沉悶的心情,刻意裝活潑。
胖茄冬望了一眼阿綠,仍是望著海。
「最近有什麼有趣的事?」阿綠想挑起胖茄冬說話的興致。
「哪有什麼有趣的事,都是一群愚蠢的人,害我的親朋好友一批批的變成漂流木。啊有啦,剛剛過來時經過立在東海岸的『人定勝天』碑被大浪打到不見蹤影。
「啊,人勝不了天的,怎麼拿走就怎麼還。我記得你說過好像叫什麼火山女神的,
「是啊,那是夏威夷的基拉韋厄火山女神佩蕾的傳說。這塊『人定勝天』碑不見了,整座山的林樹、石土和動物都高興,立碑在那裡是跟天挑釁,哪天惹天發怒,遭殃的可是我們啊。」胖茄冬半瞇著眼,阿綠很清楚胖茄冬近二千歲的修行,到過很多國家、城市,看過很多山林、河海。
「是啊,有一次颱風大量土石流,淹沒一些房子,人類說是天災,其實有些過度開墾,把一切推給上天了。」阿綠記得那次強大土石流的狀況,她早在幾年前看過人類不斷讓挖土機開腸破肚的挖山砍樹田,種了高冷蔬菜,沒有一點著力的土壤遇大風雨當然要崩。
「我喜歡台灣的地圖是橫躺著的樣子,傳說中的台灣是一隻大鯨魚,中央山脈是脊椎,肥沃的嘉南平原是肚腹。」胖茄冬望著海面上的暈紅的霞光。
「說到鯨魚,你知道嗎?虎鯨呢是喜歡飆髒話,就像人類不爽時也會說的一樣。還有,下午我打算上岸時,在海面聽到海豚聊八卦,很好玩。」提起有趣的事,阿綠想起今天下午在海面上看到的聽到趣事。
「海豚會聊八卦?都說些什麼?」胖茄冬知道花草樹木也會聊天傳情,不知海裡的魚蝦蟹會說些什麼。
「說誰勾引誰,誰又太瘦、太醜的,交頭接耳的說。海豚一向很享受說是非聊八卦。」阿綠年輕時遇到挑釁的烏賊,還噴她墨汁,她也飆了一連串的髒話,只有烏賊才聽得懂。
「真有趣,植物也會但沒有聲音,只有我們同類才看得懂。對了,大半人類都認為植物沒有感覺更沒有感知,其實植物有記憶的,也知道痛和害怕。」胖茄冬想起樹仔最後的眼神,也想起許許多被砍倒的大樹最後的顫抖。
「其實植物跟動物都一樣,只是動物可以發出聲音。聽說大象的記憶是最久的,可以二十多年還記得當時照顧過牠們的主人。」阿綠知道龜和鮭魚都會「返鄉」產卵,這也是一種記憶吧。
「對,人類還未必記得起來,動物只是迫於生存即使明知是陷井也會重蹈覆轍。植物則是無法動彈,只能靠所謂的命運。我呢就屬於人類所說的『大而無用』才能活這麼久。慶幸我活過千年才能免於害怕雖然有可能被砍或被雷劈。」胖茄搖頭像要摔掉不好的念頭似的。
「一千多年前的台灣是什麼樣子?」阿綠很早就想問胖茄冬在她出現前的台灣。
「都是樹,只有一些矮小黝黑的人住著,我看過幾次,都是男的,腰下綁著樹皮或獸皮,裸著上身,手上拿著石刀和木棍,大都一個人。都是夏天才經過,大概冬天太冷有霜雪阻擋了。我住的森林裡有不少很奇怪的動物,狗頭豬身的動物,有人類惋惜已經消失的雲犳,還有一種四不像的鹿、草草猛獁…有的被獵殺,有的因為天災逐漸滅種了。」胖茄冬閉著眼睛回想她剛發芽長葉及茁壯的年代。
「海底也是,這幾百年來也有很多海底動植物絕種了。」阿綠想起她剛跑進海底及長大後在海底的狀況。
「台灣早在幾萬年前就有人居住,有一次我不是帶你去瑞穗舞鶴看掃叭石柱,那也有三千年了,是Sakiraya族的時代,那麼大那麼重的石柱,怎麼想都不可能是當時的人類能投運過來。早期我在森林裡看到人類的機會不多,但我看到的再大的力氣,再多的人都不可能做到。我倒是常看到奇怪的動物,只是太久了有些都忘記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概我才十多歲,不算矮小枝葉也茂盛,那時有一隻三頭的蟒蛇很愛在我樹榦上纏繞,壓得我很不舒服。牠們很愛吵架,每吵就互相咬啄,卻常啄在我身上,那時我的樹皮還嫰,經常是布滿三頭蛇的牙洞。後來就不見了,我想大概被人類捕捉或被其他獸類吃了。」胖茄冬看著阿綠,這個她相識十年的朋友。
「為什麼三千年的巨石沒有變成精或什麼石頭公的?」阿綠突想起她和胖茄冬都因為年歲關係而成「精」。
「誰知道呢?也許道行比我們高不讓我們看或知道吧?」胖茄冬也不過只看過掃叭巨石二次,也許也跟她一樣剛好出遊呢?
「也許有一天我族類也會消失吧?不過也都要經過幾百幾千年吧?」阿綠望著愈來愈暗黑的海面。
「有可能幾十年或幾百年,有些物種會消失的,像花蓮光復鄉拉索埃湧泉還不是被土石流給填埋了。誰知道一千年,或數百年後這塊土地會變什麼樣,一千年前的人類看到現今台灣的樣子大概會嚇死吧。」胖茄冬回望山上的叢樹群,那個她生長的地方。
「我記得那個湧泉,你說過有很美麗的傳說,也是千年以上的泉水,不過三、四十年就可以被消失。」阿綠想起拉索埃湧泉和阿美族人美麗的傳說。
阿綠和胖茄冬靜靜的望著海面上一點點的浪光沒再說話。
胖茄冬想起她滿千歲,可以出竅初始歷遊台灣西部的情形。她看到有一群人住在一起,用茅草、竹子搭蓋的小屋,女人用麻纖編成衣服和裙子。她還看到綠魢的石塊被做成戴在手上的玉?,男人手上有鐵做的刀。有些小路兩旁樹很多,有些小路卻乾涸全是沙石。那是胖茄冬第一次見到人類的「家」。後來胖茄冬才知道,這就是台灣人類的鐵器時代,她就是從那時開始遊歷台灣。
黑色如一匹布整個蓋住了海,也蓋住了山林。胖茄終和阿綠走入山洞,沒有月亮的海邊,兩個巨大的黑影移動著。
內文選摘(節錄)
氣味
寂靜的午後,整個屋子完全沒有聲音。屋裡靜悄悄得有點詭異,彷彿將電視或電影調成靜音,整個屋子像一部默片。
純麗從廚房走到客廳,她豎著耳朵專心聽著,沒有任何聲響,她故意跺跺腳,連拖鞋拍擊著地板都沒有發出聲響。她打開電視,沒有任何畫面,螢幕全佈滿黑白細細的粒子,應該要有沙沙的聲音,但還是沒有。她走到兒子的臥房,早上整理過了,兩張床都很乾淨整潔,兩張書桌上除了小兒子桌上有參考書,都沒有雜物。她跺到主臥房,早上擦過地板,橡木的地板閃著亮光,床上放著睡衣,她的睡衣。她到浴室,打開水龍頭,水無聲無息的流出來,她看著鏡子,她的臉泛著微微的油光,擠出洗面乳和著水搓出泡沬,抹在臉上然後沖乾淨,還是沒有一丁點兒聲音。
坐在床上,她想起曾看過的一部電影《把愛找回來》那個音樂小神童,走到哪兒,聽到什麼都是聲音,風鈴聲,煙囪排出濃厚灰煙的聲音,地下鐵捷運經過的聲音,樹葉的聲音。
純麗想她的世界是無聲的,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也不會有聲音。她好害怕,不斷用食指挖耳朵,拉耳垂,希望能聽到一點點的聲音。剛洗過的臉不斷冒著汗水。她看著床頭櫃上的電話,來電燈閃著好像很急促,有人打電話來。顯示號碼盤上她看到是陌生的號碼,她接起電話,她聽不到任何聲音,也發不出聲音。她慌亂的扔了電話,跑到陽台,打開紗窗想大聲的吼叫,可是,不管麼用力就是發不出聲音,彷彿被人堵塞或是掐住喉嚨。她拚命的吼,拚命的想發出聲音。
突然一陣刺耳的電話鈴響。純麗汗涔涔從睡夢中驚醒,她接起床頭櫃上的電話。
「晚上跟廠商吃飯,會晚點回去,不用準備我的晚餐。」電話裡丈夫溫溫的說著。
純麗想這是這週第四個晚上不回家吃飯,今天是周五。
窗外公園的暮蟬嘶叫著,有小孩子的嘻笑聲。望了梳妝台的鬧鐘五點半,今天的午睡睡過頭了。她打開電視,一個料理的節目,主持人和做菜的人不知為什麼笑個不停,她聽得到聲音,幸好是做夢。
今晚又是一個人晚餐,應該說是一個人午、晚餐。純麗嘆了一口氣,到廚房把要煮湯的白蘿蔔,要炒的空心菜放入冰箱,擱在冷藏層四天的絞肉和黃魚放到冷凍層裡。然後,拿出一碗泡麵放在餐桌上,這是她的晚餐,中午是餛飩湯,昨天是從市場買了炒米粉。
純麗很懷念兒子還小時,廚房裡充滿著味道;很少有空間像廚房那樣充滿著複雜與多樣性氣味;臥室充滿著香水、保養品和衣櫃內防潮、薰衣劑交混的氣味;書房新書的墨香和舊書的霉味;衛浴是各種洗潔品的味道。
純麗最喜歡廚房不同時間不同食物飄散的各種味道,是生活、飲食,散發出生命真實厚重的氣息;早上烤吐司、麵包、奶油、荷包蛋、火腿、牛奶、咖啡,看著丈夫和兩個兒子在餐桌上匯集了一天能量的開始;中午,讀小二的大兒子和讀幼稚園半天班的小兒子會回來,十一點她洗米先煮飯,電鍋裡一陣陣炊飯的米食香氣迴盪著。然後,魯肉、炒蔬菜、辛香料在熱鍋裡煎逼出的濃烈嗆味;有時是一鍋湯麵,大兒子靈敏的嗅覺偶爾能分辨出幾種食材;晚餐總是較豐盛,中式或西式的,增加了煎、蒸或紅燒的魚類、湯品、甜點、水果。
純麗喜歡在用餐結束後,抹乾最後一滴水漬,流理台泛著洗潔劑淡淡的檸檬香。茶湯初沸,彷彿完結的儀式,然在香碟上點上一根檀香,濃郁的檀香收攏所有的氣味,脾胃塵世的需求暫時告一段落。
自從兩個兒子讀國、高中,丈夫應酬愈來愈多後,廚房的味道愈來愈淡,或者愈來愈單一,最後他們連早餐都不吃了,說是睡過頭趕時間。一個人吃飯,純麗不想費事,不是外買,就是簡單的麵食,她最喜歡餛飩,是台灣式的扁食,她到市場買包好的,煮熟了加個青菜及油蔥酥和芹菜末。純麗喜歡煮餛飩的味道,她想應該就是油蔥酥的味道,這個味道讓她想起小時候父親偶爾帶她到小麵攤吃麵的情形。不管是陽春麵、雜菜麵或扁食,煮麵的婦人都會加一匙的油蔥酥到湯裡,整碗麵,不,是整個麵攤都充滿著油蔥酥的香氣。
父親說,沒有油蔥酥氣味的麵,就不是麵。純麗記得她剛讀大學時,父親帶她到台北的學校註冊,幫她買些日用品搬進宿舍後,他們到學校旁的小吃街吃午餐,兩家小小的自助餐店擠滿了人,賣陽春麵、餛飩的麵館門口一長排的人等著吃麵。最後他們來到小街的最尾端一家小麵館,賣水餃、酢醬麵、打魯麵等。父親不喜歡吃沒有油蔥酥的麵,所以點了三十個水餃,她偏愛打魯麵再加點醋。她喜歡外省麵食,父親說還是切仔麵最好吃。
純麗出社會的第一個工作上班快一年,父母親來台北看她,她帶他們去當時很流行的台菜餐廳,除了台菜還幫父親點了切仔麵。他們吃得很高興,可是當他們知道這一餐花了純麗好幾天的薪水,從此來台北只吃麵攤,直到純麗結婚。
十多年前父母親相繼過世,一個人的午餐,純麗開始買餛飩或是陽春麵,她懷念那股濃郁的油蔥酥味道。現在廚房最常有的氣味就是油蔥酥。
純麗看過電影《香水》,她沒有葛奴乙過人靈敏的嗅覺,但她也喜歡氣味,且多數是在廚房,這些氣味可以很塵俗,像食物的氣味;也可以空靈,像剛沖泡的綠茶,難怪廚房多半屬於女人的空間,只有女人對氣味特別敏感吧。
真的是敏感嗎?純麗最近老是聞到一股腥味,這股腥味宛如一尾蛇四處流竄,有時在客廳,有時在浴室、在臥房、在廚房。兩個兒子都說沒有聞到,丈夫也沒有,這股腥只有她聞到?後來純麗更確定,這股腥味像水腥,陰陰濕濕的,或者,真是一尾蛇,一尾濕濕腥腥的蛇?純麗害怕得四處找尋,櫥櫃下、沙發下、床下,所有陰暗見不得光,還有潮濕的地方,她都尋遍了,為此她還在這些地方塞了木炭、灑了石灰。
腥味消失了幾天,又再回來,周而復始,後來純麗竟然習慣了,雖然不喜歡卻也習慣了那股腥味的存在。其實,純麗很清楚,那腥來自哪裡,她從來都不問,不想問也不敢問。
因為腥味,純麗開始聞自已身上的氣味。純麗想起讀大學時和初戀情人並肩走在校園,初戀情人總是說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她想應該是香皂、洗髮精吧,後來她才知道那是青春少女特有的香氣。
純麗從腋下聞起,流過汗的腋下有一點汗酸味,再久一點是酸腐味,那股酸腐味有些熟悉,她想起好像是阿嬤的味道,或者說是老女人的味道。她老了嗎?再一年就五十歲算老了嗎?她已有更年期的輕微症狀,怕熱多汗,經期的量不是很多就是很少。她不喜歡做完家事的汗臭,夏天她經常一天沖好幾次澡。
純麗想起母親,那是她婚後第二年,帶著剛滿月的大兒子回娘家,母親為了歡迎女兒和女婿,整治了一桌菜,要他們上桌吃飯,自己卻躲進浴室洗澡。母親說,一身汗不舒服。那時母親五十四歲,正值更年期,老嚷著身子不舒服,父親說母親一天洗好幾次澡,因為覺得身上有味道。一向不化妝也不保養的母親竟然嚅嚅的問她可不可以幫她買一瓶香水。爾後,每次回娘家純麗就帶一瓶香水給母親。
現在她終於了解了,那是邁入老年的味道,就好像食物從最新鮮逐漸要腐壞的味道。
後來,母親生病了,純麗週週抽空回家。父親跟她抱怨母親很虛弱,連走路都不穩,卻是一天三、四次嚷著要洗澡。她俯身幫母親擦拭額上因疼痛不斷冒出的汗水,確實聞到因癌末引起的腐臭味。純麗想一向愛乾淨的母親一定也聞到自己身上散出的味道。母親過世前還問自己身上是不是很臭?純麗搖搖頭,然後跑到廁所大哭。入殮時,純麗灑了些香水在母親的壽衣上,還將這瓶香水放在母親的身旁。純麗想母親應該會喜歡香香的出門。
純麗終於體會到什麼是空巢期,大兒子在南部讀大一,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小兒子高三不是學校就是補習班。早上兒上學、補習,丈夫上班、永遠開不完的會、加班和應酬,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後,純麗幾乎都是一個人,她發現一天中竟然是和市場的攤販講最多話。就像電影畫面一樣,原是一群人走動、生活的家,一個一個消逝身影,原本顯得擁擠的空間,逐漸清空,突然她覺得房子好空曠,說話都有回音。那個永遠被玩具占滿、老是踩到積木、機器人、小汽車的客廳,現在暢通得可以溜冰,那兩個仰著頭和她說話的小男孩,現在比她高出一個頭。老是纏著她,拉她裙裾的小男孩都不見了。
純麗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全家唯一會發出聲音的只有電視,她日日看電視,和電視對話。純麗很喜歡看電影頻道,有時她覺得電影裡有她生活的影子,電影播映了她部分過去的生活,也預告了她未來的人生。《豐富之旅》裡的華特太太有個故鄉可以思念,有個初戀情人可以緬懷,純麗想她的故鄉呢?十四年前父母親相繼過世,哥哥賣了田產跑到大陸消息全無,她就沒有故鄉可以回去了。
純麗聽大堂姊說老宅和田園,全成了一排透天厝。電影裡華特太太雖然沒見著初戀情人的最後一面,至少還看到破舊的故居。純麗是連一片磚瓦也看不到。大三那年初戀情人因癌症過世,她有十年走不出來,直到遇見當時還是同事的丈夫。
純麗很羡慕別人有遇見舊情人的機會和情況,她的舊情人走了。記得蒙古人說人死了靈魂會寄託在某一隻駱駝的毛上,她記得初戀情人送她一個萬年青的小盆栽,有好長一段時間,她相信初戀情人的靈魂是附在萬年青的葉子上面的。那盆萬年青純麗養了五年,從大學到上班工作,夜夜和它講話,說說一天的讀書和工作情形,即使回家過年過節她都帶著它。萬年青的葉子純麗日日擦得晶亮,早上葉尖常沾著水珠,她想是初戀情人的淚水嗎?是憐惜她的孤單嗎?萬年青長得很好,從只有書本的高度,從書桌上的小盆栽一直攀爬到頂著天花板的書架上。
有一次回家過年七天,純麗忘了帶著,回到寓居,萬年青竟然枯黃,葉子全掉在書桌上,她澆了水也回天乏術,幾天後整株枯黃。她想,初戀情人的靈魂走了,他去投胎了。
其實,純麗很少夢見初戀情人,只有在他剛過世時夢過幾次,初戀情人總是站在很遠或很暗的地方,身影面貌都模糊不清楚。純麗想他大概不想讓她看到他病得皮包骨的模樣吧。初戀情人發現得癌症,初始還上課,到了寒假就休學住院化療,然後回家休養,開學後純麗去探望幾次,頭髮都掉光,本來就清瘦的身軀更顯得單薄,純麗輕輕柔柔的擁抱他,小心的握他的手,深怕一用力就碰碎他的胸骨,或是折斷他的手腕。暑假,初戀情人告訴純麗家人要送他去美國,他的姑媽在美國幫他找到權威的醫生。開學沒多久,初戀情人回到台灣,兩天後就過世了。純麗沒有見到初戀情人最後一面。
年輕時上班、結婚、照顧兒子,太累了經常睡眠不足,純麗很少做夢,或許有夢醒來她都不記得了。最近卻常常做夢,午睡做夢,晚上也做夢,而且老是夢些光怪陸離的景象或事情。就像昨夜,純麗又夢見自己繞著一間大屋子,四處找尋廁所。
近來,純麗經常做這樣的夢,有時是在小學學校,有時是在公共場所。明明有很多間廁所,多半找尋的結果是一無所獲,即使找到了,不是有人,就是一間髒噁無比的廁所,或是一個不能使用的馬桶。
夢見尋找廁所,是一種壓力,或者就如佛洛依德說的,回到口腔或肛門期?純麗想或者最有可能的是女性生理期的焦慮,是因為生育功能即將結束的潛藏憂慮?還是,尋覓一個真正隱秘、安全、乾淨的感情、婚姻?她很不喜歡這樣的夢,醒來總是胸口鬱悶或莫名的難過、低潮。純麗望著梳妝台鏡中的自己,白晰卻不光滑的皮膚,眼尾有點下垂,嘴角也不像年輕時上仰,淺淺的木偶線。這張日日看的臉,仔細端詳竟有些陌生,轉頭時從眼角餘光中她好像看到母親的臉,純麗覺得她愈來愈像母親了。從小到大,純麗都覺得自己像父親,母親也這麼認為,大哥像母親,她的五官連身材都比較像父親。
現在,純麗覺得自己愈來愈像母親了,動作和神情都像過世前的母親。純麗想這是不是就要老了,就要慢慢變成老女人了?
有時無夢,一夜難眠,純麗靜靜躺著,所的光影都被黑暗吞沒了,留下細碎的聲音,在暗烏中,她聽著身旁丈夫的打呼聲,從打呼聲的高低和頻率,她可以猜測丈夫今天是不是太累了;丈夫的打呼聲有高有低,有時很急促,有時低緩。偶爾丈夫會磨牙,聽說那是白天的壓力和焦慮造成。純麗也聽過丈夫睡夢中的囈語,含糊不清像叫一個人的名字,也像和某人說話,但她都沒聽清楚是什麼。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镸差】丘,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镸差】丘北。
奢比屍國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屍在大人北。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熏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屍北。
──《山海經》之〈海外東經〉
海浪不斷拍打著礁岸,激起一叢又一叢的浪花,海面上一艘漁船緩緩移動,夕陽從山巔迤邐灑下,石榴色的霞光漫漶在海面,灰藍的海面鋪上一層薄薄的橙紗,使得冬日嚴峻的海溫柔許多。
老母龜阿綠伸出頭來,深深的吸口氣,一整日的冬陽曬得龜殼暖烘烘的,洞穴也乾爽許多。老母龜阿綠望著眼前遼闊的海,幾百年來的海浪洶湧,嚎吼的東北風似乎也被日頭暖化許多,海風習習吹著。阿綠轉頭回看山崖上的林樹和山土,嘆了口氣。這幾十年來,山土不斷流失,不管根淺根深的樹一棵棵倒掉,連起碼二、三百年的樹都不見,想找個說話對象也沒有。那個老樹精胖茄冬,也有二、三年沒來了。
老樹精胖茄冬知道阿綠道行淺,只有幾百年,得再一百年才能真正脫殼神遊遠處,現在就在鄰近上上下下的。這一百年來,都是胖茄冬來找阿綠。阿綠只知道胖茄冬遠從深山裡過來,胖茄冬說那個地方車子到不了,人也很難到達,否則她們這些老樹精早就被砍光了。
阿綠正想著,一陣陣咻咻咻的聲音從遠處飄來,阿綠知道胖茄冬來了,這個聲音得道行三百年以上才聽得到看得到。二千年的胖茄冬見多識廣,很多趣事、稀奇的人和動植物她都見過,說起故事來又生動,讓阿綠聽入神,巴不得胖茄冬日日來。胖茄冬一年遊歷台灣一圈,這數十年卻不敢橫越太平洋或黑水溝到其他地方。胖茄冬說海洋太遼闊了沒得歇腳,跟山裡的土地不一樣很不踏實,現在竟有心理障礙試過幾次都無法到海的另一端,索性放棄在島的山上山下四處遊歷。
而且每遊一日得養精神兩三日,所以胖茄冬每次脫樹幹殼神遊一百天得回到樹身養神二百日,每年就遊這麼一次。
「老東西,好久不見了。」胖茄冬學人類老婦女稱呼鄰居或朋友叫老東西(妯娌),有年歲漸去,情誼瀝存的感覺。
「這二年妳去了哪裡?這麼久沒來?」阿綠看看胖茄冬有些疲憊的臉色。
「前幾年神遊太久了,傷了精神,這兩年就養著精神不敢四處跑。又看到樹仔僅存的那截根頭完全腐爛了,有些難過也就愈發不愛出門。」胖茄冬眼神迷濛看著海。
樹仔也是一棵茄冬,是胖茄冬的丈大,年齡相當,兩棵樹並肩而立,日日耳鬢廝磨,是樹群中一對恩愛的夫妻。五百多年前來了一株含苞阿娜柔弱的藤蔓蘭,沒多久藤蔓蘭就纏繞在樹仔的身上,完全不顧胖茄冬的制止與警告,樹仔耽溺在藤蔓蘭溫柔的撫觸、纏繞,胖茄冬氣得神遊出遠門,眼不見為淨。
三個月後,胖茄冬回來,只見樹仔的枝葉全都枯乾掉落滿地,被藤蔓蘭纏繞只露出一點點天靈蓋,無力悲悽的看著胖茄冬,胖茄冬得養神無力幫他,眼睜睜的望著他斷氣,藤蔓蘭卻益發得豐茂潤澤,正蠢蠢欲動去勾引其他的樹精。一日大雷噼叭響,一道火光直劈向枯死的樹仔。轟的一聲全樹著火,連藤蔓蘭也燒得一乾二淨,只剩樹仔一截根頭焦黑的立著。
儘管怨樹仔移情,然而連焦黑的根頭都沒了對胖茄冬彷彿是僅存的一點記憶都要抹去了。
阿綠沒有回話,她知道胖茄冬表面看來無所謂,這五百多年來可是一直記著樹仔的好。
「有歲啊,我都兩千歲啊,真正老囉。」胖茄冬經常穿梭在人群市廛,講話的語氣和樣貌愈來愈像老婦人。
「那我算年輕的,還不到一千歲。」阿綠想轉換胖茄冬沉悶的心情,刻意裝活潑。
胖茄冬望了一眼阿綠,仍是望著海。
「最近有什麼有趣的事?」阿綠想挑起胖茄冬說話的興致。
「哪有什麼有趣的事,都是一群愚蠢的人,害我的親朋好友一批批的變成漂流木。啊有啦,剛剛過來時經過立在東海岸的『人定勝天』碑被大浪打到不見蹤影。
「啊,人勝不了天的,怎麼拿走就怎麼還。我記得你說過好像叫什麼火山女神的,
「是啊,那是夏威夷的基拉韋厄火山女神佩蕾的傳說。這塊『人定勝天』碑不見了,整座山的林樹、石土和動物都高興,立碑在那裡是跟天挑釁,哪天惹天發怒,遭殃的可是我們啊。」胖茄冬半瞇著眼,阿綠很清楚胖茄冬近二千歲的修行,到過很多國家、城市,看過很多山林、河海。
「是啊,有一次颱風大量土石流,淹沒一些房子,人類說是天災,其實有些過度開墾,把一切推給上天了。」阿綠記得那次強大土石流的狀況,她早在幾年前看過人類不斷讓挖土機開腸破肚的挖山砍樹田,種了高冷蔬菜,沒有一點著力的土壤遇大風雨當然要崩。
「我喜歡台灣的地圖是橫躺著的樣子,傳說中的台灣是一隻大鯨魚,中央山脈是脊椎,肥沃的嘉南平原是肚腹。」胖茄冬望著海面上的暈紅的霞光。
「說到鯨魚,你知道嗎?虎鯨呢是喜歡飆髒話,就像人類不爽時也會說的一樣。還有,下午我打算上岸時,在海面聽到海豚聊八卦,很好玩。」提起有趣的事,阿綠想起今天下午在海面上看到的聽到趣事。
「海豚會聊八卦?都說些什麼?」胖茄冬知道花草樹木也會聊天傳情,不知海裡的魚蝦蟹會說些什麼。
「說誰勾引誰,誰又太瘦、太醜的,交頭接耳的說。海豚一向很享受說是非聊八卦。」阿綠年輕時遇到挑釁的烏賊,還噴她墨汁,她也飆了一連串的髒話,只有烏賊才聽得懂。
「真有趣,植物也會但沒有聲音,只有我們同類才看得懂。對了,大半人類都認為植物沒有感覺更沒有感知,其實植物有記憶的,也知道痛和害怕。」胖茄冬想起樹仔最後的眼神,也想起許許多被砍倒的大樹最後的顫抖。
「其實植物跟動物都一樣,只是動物可以發出聲音。聽說大象的記憶是最久的,可以二十多年還記得當時照顧過牠們的主人。」阿綠知道龜和鮭魚都會「返鄉」產卵,這也是一種記憶吧。
「對,人類還未必記得起來,動物只是迫於生存即使明知是陷井也會重蹈覆轍。植物則是無法動彈,只能靠所謂的命運。我呢就屬於人類所說的『大而無用』才能活這麼久。慶幸我活過千年才能免於害怕雖然有可能被砍或被雷劈。」胖茄搖頭像要摔掉不好的念頭似的。
「一千多年前的台灣是什麼樣子?」阿綠很早就想問胖茄冬在她出現前的台灣。
「都是樹,只有一些矮小黝黑的人住著,我看過幾次,都是男的,腰下綁著樹皮或獸皮,裸著上身,手上拿著石刀和木棍,大都一個人。都是夏天才經過,大概冬天太冷有霜雪阻擋了。我住的森林裡有不少很奇怪的動物,狗頭豬身的動物,有人類惋惜已經消失的雲犳,還有一種四不像的鹿、草草猛獁…有的被獵殺,有的因為天災逐漸滅種了。」胖茄冬閉著眼睛回想她剛發芽長葉及茁壯的年代。
「海底也是,這幾百年來也有很多海底動植物絕種了。」阿綠想起她剛跑進海底及長大後在海底的狀況。
「台灣早在幾萬年前就有人居住,有一次我不是帶你去瑞穗舞鶴看掃叭石柱,那也有三千年了,是Sakiraya族的時代,那麼大那麼重的石柱,怎麼想都不可能是當時的人類能投運過來。早期我在森林裡看到人類的機會不多,但我看到的再大的力氣,再多的人都不可能做到。我倒是常看到奇怪的動物,只是太久了有些都忘記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概我才十多歲,不算矮小枝葉也茂盛,那時有一隻三頭的蟒蛇很愛在我樹榦上纏繞,壓得我很不舒服。牠們很愛吵架,每吵就互相咬啄,卻常啄在我身上,那時我的樹皮還嫰,經常是布滿三頭蛇的牙洞。後來就不見了,我想大概被人類捕捉或被其他獸類吃了。」胖茄冬看著阿綠,這個她相識十年的朋友。
「為什麼三千年的巨石沒有變成精或什麼石頭公的?」阿綠突想起她和胖茄冬都因為年歲關係而成「精」。
「誰知道呢?也許道行比我們高不讓我們看或知道吧?」胖茄冬也不過只看過掃叭巨石二次,也許也跟她一樣剛好出遊呢?
「也許有一天我族類也會消失吧?不過也都要經過幾百幾千年吧?」阿綠望著愈來愈暗黑的海面。
「有可能幾十年或幾百年,有些物種會消失的,像花蓮光復鄉拉索埃湧泉還不是被土石流給填埋了。誰知道一千年,或數百年後這塊土地會變什麼樣,一千年前的人類看到現今台灣的樣子大概會嚇死吧。」胖茄冬回望山上的叢樹群,那個她生長的地方。
「我記得那個湧泉,你說過有很美麗的傳說,也是千年以上的泉水,不過三、四十年就可以被消失。」阿綠想起拉索埃湧泉和阿美族人美麗的傳說。
阿綠和胖茄冬靜靜的望著海面上一點點的浪光沒再說話。
胖茄冬想起她滿千歲,可以出竅初始歷遊台灣西部的情形。她看到有一群人住在一起,用茅草、竹子搭蓋的小屋,女人用麻纖編成衣服和裙子。她還看到綠魢的石塊被做成戴在手上的玉?,男人手上有鐵做的刀。有些小路兩旁樹很多,有些小路卻乾涸全是沙石。那是胖茄冬第一次見到人類的「家」。後來胖茄冬才知道,這就是台灣人類的鐵器時代,她就是從那時開始遊歷台灣。
黑色如一匹布整個蓋住了海,也蓋住了山林。胖茄終和阿綠走入山洞,沒有月亮的海邊,兩個巨大的黑影移動著。
內文選摘(節錄)
氣味
寂靜的午後,整個屋子完全沒有聲音。屋裡靜悄悄得有點詭異,彷彿將電視或電影調成靜音,整個屋子像一部默片。
純麗從廚房走到客廳,她豎著耳朵專心聽著,沒有任何聲響,她故意跺跺腳,連拖鞋拍擊著地板都沒有發出聲響。她打開電視,沒有任何畫面,螢幕全佈滿黑白細細的粒子,應該要有沙沙的聲音,但還是沒有。她走到兒子的臥房,早上整理過了,兩張床都很乾淨整潔,兩張書桌上除了小兒子桌上有參考書,都沒有雜物。她跺到主臥房,早上擦過地板,橡木的地板閃著亮光,床上放著睡衣,她的睡衣。她到浴室,打開水龍頭,水無聲無息的流出來,她看著鏡子,她的臉泛著微微的油光,擠出洗面乳和著水搓出泡沬,抹在臉上然後沖乾淨,還是沒有一丁點兒聲音。
坐在床上,她想起曾看過的一部電影《把愛找回來》那個音樂小神童,走到哪兒,聽到什麼都是聲音,風鈴聲,煙囪排出濃厚灰煙的聲音,地下鐵捷運經過的聲音,樹葉的聲音。
純麗想她的世界是無聲的,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也不會有聲音。她好害怕,不斷用食指挖耳朵,拉耳垂,希望能聽到一點點的聲音。剛洗過的臉不斷冒著汗水。她看著床頭櫃上的電話,來電燈閃著好像很急促,有人打電話來。顯示號碼盤上她看到是陌生的號碼,她接起電話,她聽不到任何聲音,也發不出聲音。她慌亂的扔了電話,跑到陽台,打開紗窗想大聲的吼叫,可是,不管麼用力就是發不出聲音,彷彿被人堵塞或是掐住喉嚨。她拚命的吼,拚命的想發出聲音。
突然一陣刺耳的電話鈴響。純麗汗涔涔從睡夢中驚醒,她接起床頭櫃上的電話。
「晚上跟廠商吃飯,會晚點回去,不用準備我的晚餐。」電話裡丈夫溫溫的說著。
純麗想這是這週第四個晚上不回家吃飯,今天是周五。
窗外公園的暮蟬嘶叫著,有小孩子的嘻笑聲。望了梳妝台的鬧鐘五點半,今天的午睡睡過頭了。她打開電視,一個料理的節目,主持人和做菜的人不知為什麼笑個不停,她聽得到聲音,幸好是做夢。
今晚又是一個人晚餐,應該說是一個人午、晚餐。純麗嘆了一口氣,到廚房把要煮湯的白蘿蔔,要炒的空心菜放入冰箱,擱在冷藏層四天的絞肉和黃魚放到冷凍層裡。然後,拿出一碗泡麵放在餐桌上,這是她的晚餐,中午是餛飩湯,昨天是從市場買了炒米粉。
純麗很懷念兒子還小時,廚房裡充滿著味道;很少有空間像廚房那樣充滿著複雜與多樣性氣味;臥室充滿著香水、保養品和衣櫃內防潮、薰衣劑交混的氣味;書房新書的墨香和舊書的霉味;衛浴是各種洗潔品的味道。
純麗最喜歡廚房不同時間不同食物飄散的各種味道,是生活、飲食,散發出生命真實厚重的氣息;早上烤吐司、麵包、奶油、荷包蛋、火腿、牛奶、咖啡,看著丈夫和兩個兒子在餐桌上匯集了一天能量的開始;中午,讀小二的大兒子和讀幼稚園半天班的小兒子會回來,十一點她洗米先煮飯,電鍋裡一陣陣炊飯的米食香氣迴盪著。然後,魯肉、炒蔬菜、辛香料在熱鍋裡煎逼出的濃烈嗆味;有時是一鍋湯麵,大兒子靈敏的嗅覺偶爾能分辨出幾種食材;晚餐總是較豐盛,中式或西式的,增加了煎、蒸或紅燒的魚類、湯品、甜點、水果。
純麗喜歡在用餐結束後,抹乾最後一滴水漬,流理台泛著洗潔劑淡淡的檸檬香。茶湯初沸,彷彿完結的儀式,然在香碟上點上一根檀香,濃郁的檀香收攏所有的氣味,脾胃塵世的需求暫時告一段落。
自從兩個兒子讀國、高中,丈夫應酬愈來愈多後,廚房的味道愈來愈淡,或者愈來愈單一,最後他們連早餐都不吃了,說是睡過頭趕時間。一個人吃飯,純麗不想費事,不是外買,就是簡單的麵食,她最喜歡餛飩,是台灣式的扁食,她到市場買包好的,煮熟了加個青菜及油蔥酥和芹菜末。純麗喜歡煮餛飩的味道,她想應該就是油蔥酥的味道,這個味道讓她想起小時候父親偶爾帶她到小麵攤吃麵的情形。不管是陽春麵、雜菜麵或扁食,煮麵的婦人都會加一匙的油蔥酥到湯裡,整碗麵,不,是整個麵攤都充滿著油蔥酥的香氣。
父親說,沒有油蔥酥氣味的麵,就不是麵。純麗記得她剛讀大學時,父親帶她到台北的學校註冊,幫她買些日用品搬進宿舍後,他們到學校旁的小吃街吃午餐,兩家小小的自助餐店擠滿了人,賣陽春麵、餛飩的麵館門口一長排的人等著吃麵。最後他們來到小街的最尾端一家小麵館,賣水餃、酢醬麵、打魯麵等。父親不喜歡吃沒有油蔥酥的麵,所以點了三十個水餃,她偏愛打魯麵再加點醋。她喜歡外省麵食,父親說還是切仔麵最好吃。
純麗出社會的第一個工作上班快一年,父母親來台北看她,她帶他們去當時很流行的台菜餐廳,除了台菜還幫父親點了切仔麵。他們吃得很高興,可是當他們知道這一餐花了純麗好幾天的薪水,從此來台北只吃麵攤,直到純麗結婚。
十多年前父母親相繼過世,一個人的午餐,純麗開始買餛飩或是陽春麵,她懷念那股濃郁的油蔥酥味道。現在廚房最常有的氣味就是油蔥酥。
純麗看過電影《香水》,她沒有葛奴乙過人靈敏的嗅覺,但她也喜歡氣味,且多數是在廚房,這些氣味可以很塵俗,像食物的氣味;也可以空靈,像剛沖泡的綠茶,難怪廚房多半屬於女人的空間,只有女人對氣味特別敏感吧。
真的是敏感嗎?純麗最近老是聞到一股腥味,這股腥味宛如一尾蛇四處流竄,有時在客廳,有時在浴室、在臥房、在廚房。兩個兒子都說沒有聞到,丈夫也沒有,這股腥只有她聞到?後來純麗更確定,這股腥味像水腥,陰陰濕濕的,或者,真是一尾蛇,一尾濕濕腥腥的蛇?純麗害怕得四處找尋,櫥櫃下、沙發下、床下,所有陰暗見不得光,還有潮濕的地方,她都尋遍了,為此她還在這些地方塞了木炭、灑了石灰。
腥味消失了幾天,又再回來,周而復始,後來純麗竟然習慣了,雖然不喜歡卻也習慣了那股腥味的存在。其實,純麗很清楚,那腥來自哪裡,她從來都不問,不想問也不敢問。
因為腥味,純麗開始聞自已身上的氣味。純麗想起讀大學時和初戀情人並肩走在校園,初戀情人總是說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她想應該是香皂、洗髮精吧,後來她才知道那是青春少女特有的香氣。
純麗從腋下聞起,流過汗的腋下有一點汗酸味,再久一點是酸腐味,那股酸腐味有些熟悉,她想起好像是阿嬤的味道,或者說是老女人的味道。她老了嗎?再一年就五十歲算老了嗎?她已有更年期的輕微症狀,怕熱多汗,經期的量不是很多就是很少。她不喜歡做完家事的汗臭,夏天她經常一天沖好幾次澡。
純麗想起母親,那是她婚後第二年,帶著剛滿月的大兒子回娘家,母親為了歡迎女兒和女婿,整治了一桌菜,要他們上桌吃飯,自己卻躲進浴室洗澡。母親說,一身汗不舒服。那時母親五十四歲,正值更年期,老嚷著身子不舒服,父親說母親一天洗好幾次澡,因為覺得身上有味道。一向不化妝也不保養的母親竟然嚅嚅的問她可不可以幫她買一瓶香水。爾後,每次回娘家純麗就帶一瓶香水給母親。
現在她終於了解了,那是邁入老年的味道,就好像食物從最新鮮逐漸要腐壞的味道。
後來,母親生病了,純麗週週抽空回家。父親跟她抱怨母親很虛弱,連走路都不穩,卻是一天三、四次嚷著要洗澡。她俯身幫母親擦拭額上因疼痛不斷冒出的汗水,確實聞到因癌末引起的腐臭味。純麗想一向愛乾淨的母親一定也聞到自己身上散出的味道。母親過世前還問自己身上是不是很臭?純麗搖搖頭,然後跑到廁所大哭。入殮時,純麗灑了些香水在母親的壽衣上,還將這瓶香水放在母親的身旁。純麗想母親應該會喜歡香香的出門。
純麗終於體會到什麼是空巢期,大兒子在南部讀大一,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小兒子高三不是學校就是補習班。早上兒上學、補習,丈夫上班、永遠開不完的會、加班和應酬,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後,純麗幾乎都是一個人,她發現一天中竟然是和市場的攤販講最多話。就像電影畫面一樣,原是一群人走動、生活的家,一個一個消逝身影,原本顯得擁擠的空間,逐漸清空,突然她覺得房子好空曠,說話都有回音。那個永遠被玩具占滿、老是踩到積木、機器人、小汽車的客廳,現在暢通得可以溜冰,那兩個仰著頭和她說話的小男孩,現在比她高出一個頭。老是纏著她,拉她裙裾的小男孩都不見了。
純麗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全家唯一會發出聲音的只有電視,她日日看電視,和電視對話。純麗很喜歡看電影頻道,有時她覺得電影裡有她生活的影子,電影播映了她部分過去的生活,也預告了她未來的人生。《豐富之旅》裡的華特太太有個故鄉可以思念,有個初戀情人可以緬懷,純麗想她的故鄉呢?十四年前父母親相繼過世,哥哥賣了田產跑到大陸消息全無,她就沒有故鄉可以回去了。
純麗聽大堂姊說老宅和田園,全成了一排透天厝。電影裡華特太太雖然沒見著初戀情人的最後一面,至少還看到破舊的故居。純麗是連一片磚瓦也看不到。大三那年初戀情人因癌症過世,她有十年走不出來,直到遇見當時還是同事的丈夫。
純麗很羡慕別人有遇見舊情人的機會和情況,她的舊情人走了。記得蒙古人說人死了靈魂會寄託在某一隻駱駝的毛上,她記得初戀情人送她一個萬年青的小盆栽,有好長一段時間,她相信初戀情人的靈魂是附在萬年青的葉子上面的。那盆萬年青純麗養了五年,從大學到上班工作,夜夜和它講話,說說一天的讀書和工作情形,即使回家過年過節她都帶著它。萬年青的葉子純麗日日擦得晶亮,早上葉尖常沾著水珠,她想是初戀情人的淚水嗎?是憐惜她的孤單嗎?萬年青長得很好,從只有書本的高度,從書桌上的小盆栽一直攀爬到頂著天花板的書架上。
有一次回家過年七天,純麗忘了帶著,回到寓居,萬年青竟然枯黃,葉子全掉在書桌上,她澆了水也回天乏術,幾天後整株枯黃。她想,初戀情人的靈魂走了,他去投胎了。
其實,純麗很少夢見初戀情人,只有在他剛過世時夢過幾次,初戀情人總是站在很遠或很暗的地方,身影面貌都模糊不清楚。純麗想他大概不想讓她看到他病得皮包骨的模樣吧。初戀情人發現得癌症,初始還上課,到了寒假就休學住院化療,然後回家休養,開學後純麗去探望幾次,頭髮都掉光,本來就清瘦的身軀更顯得單薄,純麗輕輕柔柔的擁抱他,小心的握他的手,深怕一用力就碰碎他的胸骨,或是折斷他的手腕。暑假,初戀情人告訴純麗家人要送他去美國,他的姑媽在美國幫他找到權威的醫生。開學沒多久,初戀情人回到台灣,兩天後就過世了。純麗沒有見到初戀情人最後一面。
年輕時上班、結婚、照顧兒子,太累了經常睡眠不足,純麗很少做夢,或許有夢醒來她都不記得了。最近卻常常做夢,午睡做夢,晚上也做夢,而且老是夢些光怪陸離的景象或事情。就像昨夜,純麗又夢見自己繞著一間大屋子,四處找尋廁所。
近來,純麗經常做這樣的夢,有時是在小學學校,有時是在公共場所。明明有很多間廁所,多半找尋的結果是一無所獲,即使找到了,不是有人,就是一間髒噁無比的廁所,或是一個不能使用的馬桶。
夢見尋找廁所,是一種壓力,或者就如佛洛依德說的,回到口腔或肛門期?純麗想或者最有可能的是女性生理期的焦慮,是因為生育功能即將結束的潛藏憂慮?還是,尋覓一個真正隱秘、安全、乾淨的感情、婚姻?她很不喜歡這樣的夢,醒來總是胸口鬱悶或莫名的難過、低潮。純麗望著梳妝台鏡中的自己,白晰卻不光滑的皮膚,眼尾有點下垂,嘴角也不像年輕時上仰,淺淺的木偶線。這張日日看的臉,仔細端詳竟有些陌生,轉頭時從眼角餘光中她好像看到母親的臉,純麗覺得她愈來愈像母親了。從小到大,純麗都覺得自己像父親,母親也這麼認為,大哥像母親,她的五官連身材都比較像父親。
現在,純麗覺得自己愈來愈像母親了,動作和神情都像過世前的母親。純麗想這是不是就要老了,就要慢慢變成老女人了?
有時無夢,一夜難眠,純麗靜靜躺著,所的光影都被黑暗吞沒了,留下細碎的聲音,在暗烏中,她聽著身旁丈夫的打呼聲,從打呼聲的高低和頻率,她可以猜測丈夫今天是不是太累了;丈夫的打呼聲有高有低,有時很急促,有時低緩。偶爾丈夫會磨牙,聽說那是白天的壓力和焦慮造成。純麗也聽過丈夫睡夢中的囈語,含糊不清像叫一個人的名字,也像和某人說話,但她都沒聽清楚是什麼。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