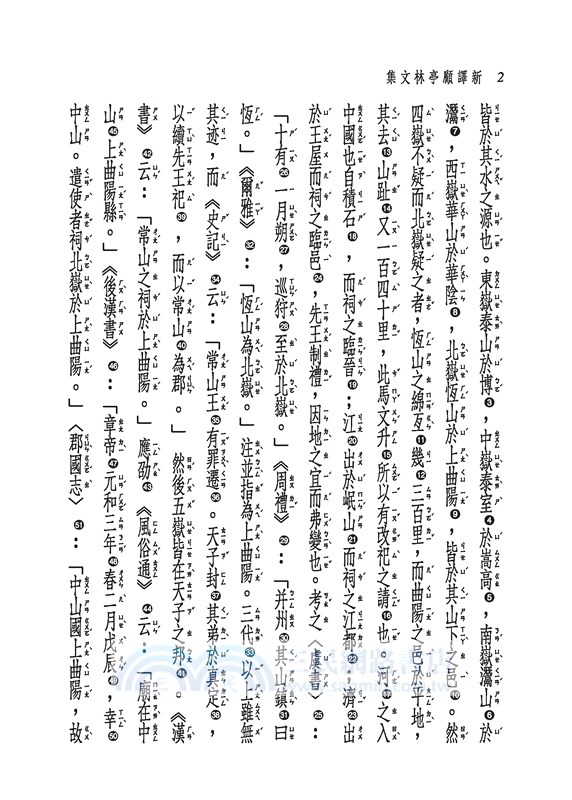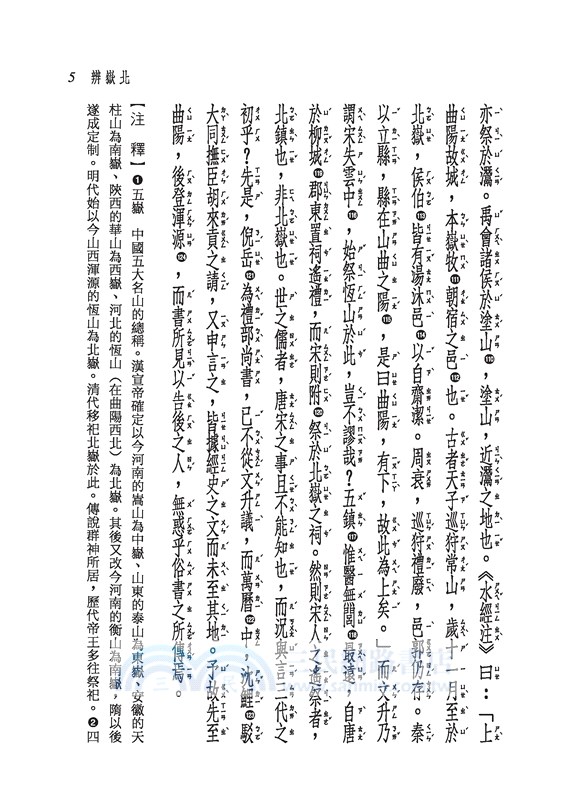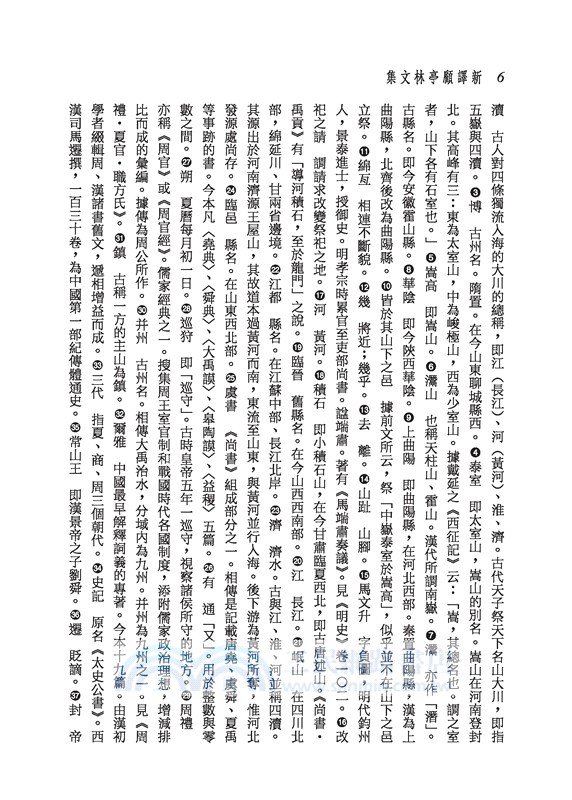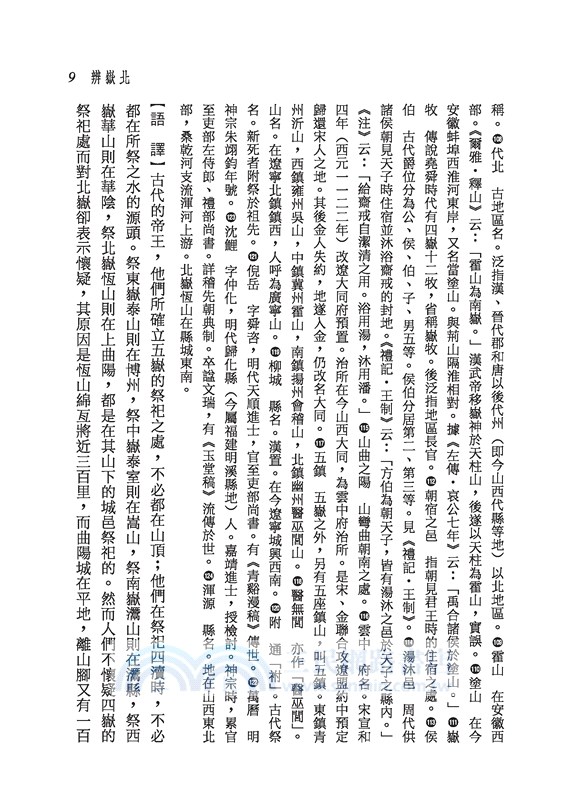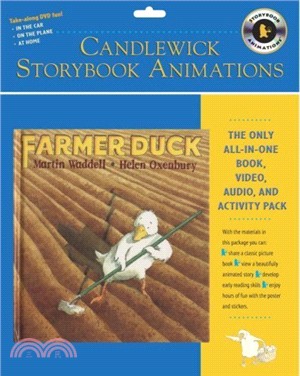一、顧炎武的家世及其生平
顧氏的先世在吳郡(今江蘇東南部),為江東四大姓之一。在三國東吳孫權朝,就有一位名叫顧雍的任過丞相(參見〈與毛錦銜〉)。五代時,顧氏遷居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縣)。南宋時,有名顧慶的,從滁州遷居海門姚劉沙(今上海市崇明縣)。顧慶的次子伯善,又從姚劉沙遷居崑山縣(今屬江蘇)的花浦邨,其後又移家到千墩,顧氏便定居下來。
從顧伯善傳十一世到顧濟,是顧炎武的高祖。顧濟字舟卿,號思軒,是明代正德年間的進士,官至江西饒州知府,著有《諫垣疏》一卷。曾祖顧章志,字子行,號觀海,是嘉靖癸丑年間的進士,官至南京兵部侍郎;性極清介,獨愛藏書(見〈鈔書自序〉)。本祖父顧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丁丑年的進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著有《寶庵集》十二卷。《靜志居詩話》稱他「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孟襄陽、高蘇門者」。嗣祖父顧紹芾,字德甫,號蠡源,是太學生。他天才俊逸,工詩及古文,奇奧秀拔;尤善於書法,極為董其昌所稱許(見《崑新合志》)。本生父顧同應,字仲從,官蔭生;性極闊達,好施與;善詩文,其詩「詞澹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冷然之致」(見《明詩綜》引王平仲語)。著有《藥房》、《秋嘯》等集(見《蘇州府志》)。嗣父顧同吉,早卒,聘王氏,是太僕寺卿王宇的孫女,諸生王述的女兒。她十七歲未婚守節,因此以顧炎武為後嗣,性極孝,曾斷指以療姑病;又「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有奩田五十畝,歲所入,悉以散之三族」(見〈先妣王碩人行狀〉)。上述家世,無疑對顧炎武的成長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顧炎武生於明代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年),卒於清代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初名絳,字忠清,明朝亡後,他就改名炎武,字寧人;又曾叫圭年,別號蔣山傭;學者稱他為亭林先生。
顧炎武由其嗣祖父顧蠡源、嗣母王氏撫養成人。他自幼性情耿介,落落有大志。十四歲時,與同里友人歸莊參加主張改良政治的知識分子組織復社;因其瞳子中白邊黑,相貌怪異,時人稱他和歸莊為「歸奇顧怪」。他雖年少,但詩文俱佳,在當時的文士中頗有聲名(見〈答原一、公肅兩甥書〉)。二十七歲時,秋試被廢除,於是「退而讀書」,遍覽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以及公移邸鈔之類共千餘部,輯錄有關材料,旁推互證,撰寫《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兩書。這兩部書,前者著重於記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後者詳細記錄了各地疆域、形勝、水利、兵防、物產、賦稅等資料。
西元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渡過長江,顧炎武糾合同志,發動義兵,堅守蘇州,但最後歸於失敗,他的友人大多戰死,他自己也差點喪命。此戰失敗後,他並沒有放棄抗清的行動,而是扮作商賈模樣,奔走於江、浙,來往於山東、河北、陝西等地,聯絡抗清志士,觀察中原地理形勢,以圖恢復明室。他在北方結識了李中孚、王宏撰等愛國人士。曾經六次往謁昌平的明十三陵和五次往謁南京的明孝陵。他的活動受到清政府的注意。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年)二月,他被山東姜元衡告發入獄,後因李中孚、朱彝尊等人的盡力營救,才被釋放。後來定居於陝西的華陰,因為他認為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見〈與三姪書〉)。在華陰,他置田五十畝自給,並在他處開墾荒地,其收入則另外存儲,以備恢復之用。其矢志不渝,由此可見。
顧炎武在奔走南北,遊覽九州五嶽過程中,閱歷更加豐富,視野更加開闊,這有助於他的學術研究。他所撰寫的《音學五書》、《日知錄》、《金石文字記》、《石經考》等數十種著作,涉及到諸多學術領域,對清代學者產生過極大影響,直至今天,人們仍然不只是把他視為明清之際的著名愛國者,更推崇他是中國近代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和國學大師。
二、顧炎武的民主思想及愛國精神
顧炎武具有強烈的民主主義思想,這不僅表現在他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這部批判封建君主制的著作的推崇上,更表現在他的一系列政論文中。他寫了九篇〈郡縣論〉,其中首先對封建君主的專制行為予以揭露,他說:「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見〈郡縣論〉一)同時又提出了改革郡縣制的主張,他說:「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見〈郡縣論〉一)他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其實質就是分權地方,實行宗法自治。他說:「人君之於天下,不能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閏門之內。」(見《日知錄‧愛百姓故刑罰中》)又說:「惟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見《日知錄‧鄉亭之職》)「尊令長之秩,而予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矣。」(見〈郡縣論〉一)他的這種主張,著眼於「厚民生,強國勢」,在當時可能不失為救弊之良劑,在今天則可看出它與現代民主精神有相合之處。
顧炎武的民主思想還表現在他對當時一些經濟政策的看法上。比如,清初陝西關中一帶的田賦,是向農民徵收銀錢。由於道路不通,關中本來就銀少錢貴,農民為了繳納稅銀,只得以低價賣出糧食,去換取銀兩,從而導致穀賤銀貴,農民貧困日甚一日,以致到了豐年賣子的境地。針對這種情形,顧炎武寫了〈錢糧論〉,深刻揭露其弊病,同時又考證了歷代經濟政策的得與失,對那些使民窮而姦吏富的作法進行了嚴厲的抨擊。
顧炎武的愛國精神也表現得相當突出,這從我們對他的生平的介紹中已經可以得到證明。他的這種愛國精神,與他遵循嗣母遺訓分不開。他的嗣母王氏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剛烈女子。當清兵南下,崑山城破時,她絕食十五天而死,臨死前對顧炎武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瞑目於地下!」(見〈先妣王碩人行狀〉)對於嗣母的這些叮囑,顧炎武銘刻在心。他一生都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就在清廷因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時,朝中大臣屢次想推薦,都被他嚴辭拒絕。他曾對朋友說,如果真的強他出仕,就準備「以身殉之」(見〈與葉訒菴書〉)。可見他不違母訓、忠於先朝的態度是何等堅決。
三、顧炎武的學術觀點及治學方法
顧炎武生在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時代。他認為明代的滅亡,與明代道學先生空談「明心見性」直接有關。他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亂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見《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他把明朝的滅亡歸之於道學先生的空談,未免言之過重,但也有其合理之處。基於這種看法,他從實用的觀點出發,對做學問與寫文章的目的,表明了自己的主張。他說:「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事,何流極而至於斯,則思起而極之。」(見〈與潘次耕書〉)又說:「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事之務者,一切不為。」(見〈與人書〉三)「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見《日知錄‧文須有益於天下》)他的這種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對儒學所謂「文以載道」的傳統觀念的繼承,但是另一方面則與他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不無關係。他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又說:「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與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見〈病起與薊門當事書〉)顧炎武一生之所以重實學,輕空談,雖著作等身,而無一虛妄之文,應當能夠從他的這些話中得到可靠的解答。
與上述學術觀點相一致的是,顧炎武採取了注重實際調查和確切證據的治學方法。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說:「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車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顧炎武在談到自己撰述《金石文字記》一書的經過時也說:「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 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經過了如此艱苦的探尋工作之後,顧炎武又對此書所錄漢以後碑刻三百餘種各綴跋語,述其本末源流,辨其譌誤,極為精核。
顧炎武是清代學風的開山祖師,他的考證方法被清代乾嘉以後的學者充分繼承和大力發揚。顧炎武不僅在對漢代經學及古代音讀的研究上成功地運用考證方法,從而糾正了前人理解上的諸多錯誤,而且在地理、風俗乃至禮儀等等方面的辨析中,也因考證有力而澄清了許多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在〈北嶽辨〉中,針對前人懷疑古代帝王祭北嶽恆山於上曲陽這一問題,先從先秦的〈虞書〉考證起,隨後依次引述《周禮》、《爾雅》、《史記》、《漢書》、《後漢書》、《郡國志》、《水經注》、《魏書》、《隋書》、《唐書》等史籍的有關記載予以博證,最後才得出結論說:「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因為據史而論,引證充分,所以他的結論也就成了毋庸置疑的定論。
《顧亭林文集》有康熙原刻本存世。本書則以此為底本,遇有字句脫誤之處,則據《蔣山傭殘稿》及清光緒張修府、董金鑑諸刻本(見《學古齋金石叢書》)參校補正。
對本書各篇的研析,本著有話則言、無話則免的原則予以處理。在作研析時,或談其思想內容,或談其藝術特色,或談其所體現出的作者的人格精神、治學態度等等,沒有定規。
《顧亭林文集》至今無人進行過完整的注釋和翻譯。本人才疏學淺,在從事這一工作時又無從借鑑,若有錯誤,懇請讀者指正。
劉九洲 於二千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