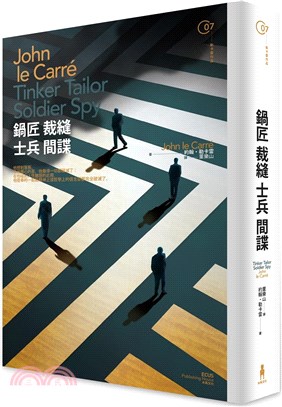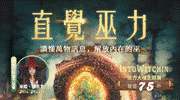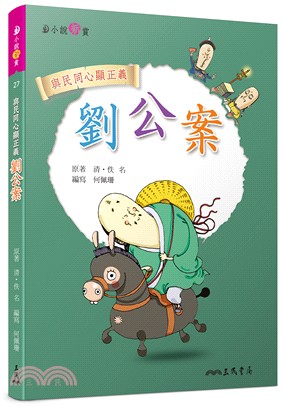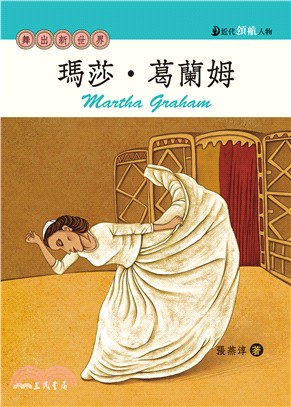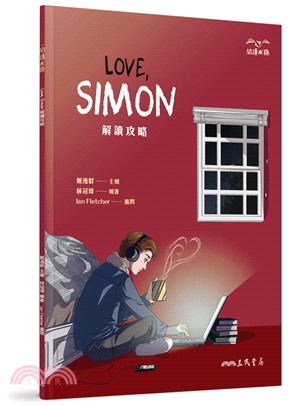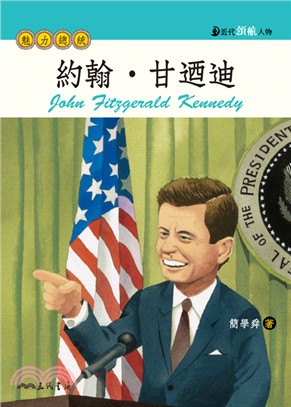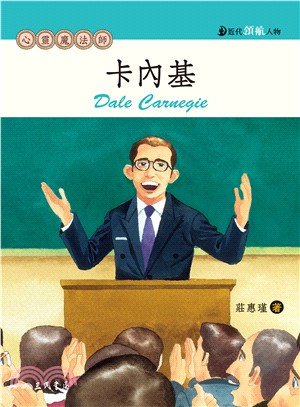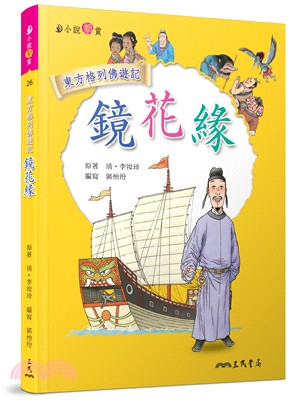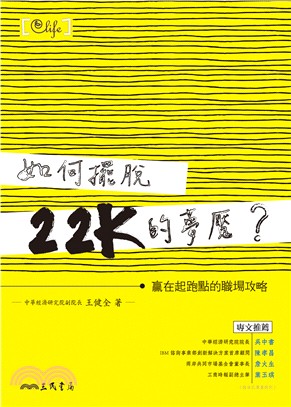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商品資訊
系列名:勒卡雷作品
ISBN13:9789863598657
替代書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約翰・勒卡雷
譯者:董樂山
出版日:2021/02/09
裝訂/頁數:平裝/424頁
規格:21cm*14.8cm*2.6cm (高/寬/厚)
重量:589克
版次:2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對你們這種人,真不知道究竟何時該相信,何時又不該。
你們有截然不同的標準,是不是?」
約翰・勒卡雷 『自認最好的作品』。―― 英國《衛報》
軍情六處的老總懷疑,蘇聯在這個英國情報單位高層裡暗藏了一名間諜。他以「鍋匠、裁縫、士兵、窮人、乞丐」作為對五個懷疑對象的代稱,並暗中策劃一場遠在捷克的行動,要從當地某名將軍口中得知叛徒的身分,揪出藏在圓場裡的這隻「地鼠」。
然而老總遭到設局,計劃失敗,他黯然病死,圓場也面臨徹底的人事重整。
原本因此而被逐出情報單位的史邁利受到白廳私下委託,開始重啟調查。在愛徒貴蘭姆的協助下,史邁利得從圓場成堆舊檔案裡的跡證,和當初被迫離職的單位舊識口中,逐步拼湊出這場陰謀的可能全貌。
這個代號「傑拉德」的雙面間諜究竟是誰?
史邁利發現,他面對的是一個陷阱,一個「非常聰明的巧結」,而這細密如蛛網的計謀,正來自他終極的死敵、謎般的俄國情報頭子卡拉……
你們有截然不同的標準,是不是?」
約翰・勒卡雷 『自認最好的作品』。―― 英國《衛報》
軍情六處的老總懷疑,蘇聯在這個英國情報單位高層裡暗藏了一名間諜。他以「鍋匠、裁縫、士兵、窮人、乞丐」作為對五個懷疑對象的代稱,並暗中策劃一場遠在捷克的行動,要從當地某名將軍口中得知叛徒的身分,揪出藏在圓場裡的這隻「地鼠」。
然而老總遭到設局,計劃失敗,他黯然病死,圓場也面臨徹底的人事重整。
原本因此而被逐出情報單位的史邁利受到白廳私下委託,開始重啟調查。在愛徒貴蘭姆的協助下,史邁利得從圓場成堆舊檔案裡的跡證,和當初被迫離職的單位舊識口中,逐步拼湊出這場陰謀的可能全貌。
這個代號「傑拉德」的雙面間諜究竟是誰?
史邁利發現,他面對的是一個陷阱,一個「非常聰明的巧結」,而這細密如蛛網的計謀,正來自他終極的死敵、謎般的俄國情報頭子卡拉……
作者簡介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英國著名小說家,原名大衛・康威爾(David Cornwell),一九三一年生於英國,十八歲便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後於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並於伊頓公學教授德文及法文。一九五八年進入英國軍情五處(MI5)工作,兩年後轉調至軍情六處(MI6),先後派駐德國波昂及漢堡,並在任職期間寫下《死亡預約》、《上流謀殺》,以及首部暢銷全球之作《冷戰諜魂》。
勒卡雷在一九六四年離開軍情六處後,即全心投入寫作,作品不僅廣受全球讀者喜愛及各大媒體推崇,更因充滿戲劇懸疑張力,已有十餘部改編為電視劇及電影。
勒卡雷一生獲獎無數,最重要的包括一九六五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Edgar Awdars、一九六四年獲得英國Somerset Maugham Award、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一九八八年更獲頒英國犯罪作家協會CWA終身成就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其內斂而深沉的寫作風格更是確立了他在二十世紀類型文學領域的崇高地位。
二○一六年,他以《此生如鴿》一書細膩講述個人經歷,是瞭解勒卡雷其人和其筆下諜報世界、人物及各部作品的精彩回憶自傳。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勒卡雷逝於英國。
英國著名小說家,原名大衛・康威爾(David Cornwell),一九三一年生於英國,十八歲便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後於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並於伊頓公學教授德文及法文。一九五八年進入英國軍情五處(MI5)工作,兩年後轉調至軍情六處(MI6),先後派駐德國波昂及漢堡,並在任職期間寫下《死亡預約》、《上流謀殺》,以及首部暢銷全球之作《冷戰諜魂》。
勒卡雷在一九六四年離開軍情六處後,即全心投入寫作,作品不僅廣受全球讀者喜愛及各大媒體推崇,更因充滿戲劇懸疑張力,已有十餘部改編為電視劇及電影。
勒卡雷一生獲獎無數,最重要的包括一九六五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Edgar Awdars、一九六四年獲得英國Somerset Maugham Award、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一九八八年更獲頒英國犯罪作家協會CWA終身成就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其內斂而深沉的寫作風格更是確立了他在二十世紀類型文學領域的崇高地位。
二○一六年,他以《此生如鴿》一書細膩講述個人經歷,是瞭解勒卡雷其人和其筆下諜報世界、人物及各部作品的精彩回憶自傳。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勒卡雷逝於英國。
名人/編輯推薦
「間諜小說家第一人。」――格雷安・葛林 Graham Greene
「文學巨人,人道主義者的心靈。」――史蒂芬・金 Stephen King
「不只是偉大作家,更深富卓識遠見。」―― 保羅・科爾賀 Paulo Coelho
「勒卡雷正是間諜小說書寫領域的如此奇蹟,他的規格、視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所有間諜小說書寫者……」―― 唐諾
「文學巨人,人道主義者的心靈。」――史蒂芬・金 Stephen King
「不只是偉大作家,更深富卓識遠見。」―― 保羅・科爾賀 Paulo Coelho
「勒卡雷正是間諜小說書寫領域的如此奇蹟,他的規格、視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所有間諜小說書寫者……」―― 唐諾
目次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導讀
勒卡雷・不只是間諜小說的第一人而已――唐諾
寓批判於間諜小說中――南方朔
關於《鍋匠裁縫士兵間諜》――郭重興
• 第二部
• 第三部
• 導讀
勒卡雷・不只是間諜小說的第一人而已――唐諾
寓批判於間諜小說中――南方朔
關於《鍋匠裁縫士兵間諜》――郭重興
書摘/試閱
(節選自第三章)
在這種前提的慰藉下,史邁利到了國王路,他在人行道上停了一會兒,好像要過馬路似的。馬路兩邊都是華麗的精品商店。在他前面是自己住的貝瓦特街,一條死巷子,他從頭走到底,總共只有一百一十七步。他當初搬到這裡時,這些喬治時期的建築有一種敗落敝舊的美,年輕的夫婦靠十五鎊過一星期,在地下室裡還不敢聲張收個不付稅的房客。可是現在卻有鐵欄杆保護下層的窗戶,每幢屋子的路邊都擠著停了三輛汽車。史邁利出於長期養成的習慣,走過去時一一看了一眼,哪輛是熟悉的,哪輛不然;不熟悉的汽車中,有哪輛又是安裝了天線和多一面鏡子,哪輛是監視者喜歡的那種無窗小貨車。他這麼做,部分原因是要考驗自己的記憶力,為了保持頭腦不至於因為退休而萎縮,就像以前他在往大英博物館的公車上熟記沿途的商店門牌號碼一樣;也正如他背得出自己家中每層樓梯共有多少級,十二扇門每一扇朝什麼方向開一樣。
但是史邁利這麼做還有第二個原因,那就是他害怕,這是職業間諜到死都甩不開的祕密恐懼。由於過去經歷那樣複雜,連自己也記不清結下了多少怨仇,總有一天仇人會找上門來跟他算帳。
在這條街的盡頭,有個鄰居帶狗出來散步;她看到他,抬起頭來說了一句不知什麼的話,但是他沒有理她,心裡知道大概又是關於安的話。他穿過馬路。他的房子一片漆黑,窗簾仍像他出門時那樣拉上。他爬上六級台階,來到門口。自從安走了以後,他把打掃屋子的女人也給辭退了:除了安之外,沒有別人有鑰匙。門上有兩道鎖,一道是班漢牌死鎖,一道是朱伯牌管匙鎖,還有兩片他自製的小木片, 只有指甲那麼大,一片塞在上面門梁縫裡,一片塞在班漢鎖的下面。這是他在出外勤時留下的習慣。最近,不知什麼原因,他又開始使用;也許是為了不要因為她突然回來而吃一驚。他用指尖一摸,兩片小木片都在那裡。於是他開了門鎖,推了進去,腳下碰到中午塞進來躺在地毯上的郵件。
他心想,是什麼雜誌到期了?《德國生活與文學》?《語言學》?他想應該是《語言學》,這早就到期了。他打開門廊的電燈,彎身翻看了一下郵件。一封是他的裁縫寄來的帳單,記的是一套他沒有訂製的衣服,他懷疑很可能那衣服正穿在安情人的身上;一封是亨萊一個加油站寄來的汽油帳單(才十月九號就沒錢了,他們在萊亨幹什麼呀);一封是銀行來信,說的是關於密德蘭銀行伊明翰分行為安.史邁利夫人開戶取款的事。
他對著這封信問,他媽的這兩個人在伊明翰幹什麼?真是天曉得,誰會去伊明翰跟姘頭幽會?這伊明翰是在哪裡?
他正在思量這個問題時,目光卻落在傘架上一把沒見過的雨傘上,這是一把綢傘,傘把上有手工縫製的皮套,上面有一個金環,但是沒有物主的姓名縮寫。他的腦袋裡很快閃過一個念頭:既然這把傘是乾的,那麼一定是在六點十五分下雨前就放在那裡了,因為架上也沒有水跡。而且這把傘很講究,雖然不新,傘尖不鏽鋼包頭還沒有擦劃過的痕跡。因此,這把傘屬於一個行動敏捷的人,甚至是年輕人, 像安最近的一個情人。但是既然這個傘主人知道門上塞的木片,又知道進屋以後放回原處,而且還頗為機靈,在推門打亂了(而且無疑也讀了)郵件以後,又把信放在門邊靠著,那麼他極有可能也認識史邁利;他不是安的情人,而是一個像他自己那樣的職業特務,一度跟他親密共事過,而且就像行話所說的那樣,認得出他的「筆跡」。
客廳的門虛掩著。他輕輕地又推開了一點。
「彼得?」他問道。
他從門縫裡看進去,靠外面路燈的光,看到沙發一頭伸著一雙穿著麂皮鞋子的腳,懶洋洋地交疊在一起。
「我要是你,喬治,我就不脫大衣了,老兄,」說話的聲音很親切,「我們還要趕遠路呢。」
五分鐘後,穿著一件寬大的棕色旅行大衣,喬治.史邁利鬱鬱不樂地坐在彼得.貴蘭姆的敞篷跑車的客座上。那件大衣是安送他的禮物,是他唯一乾燥的大衣。原來彼得把車停在附近另一個廣場上,所以他先前沒有發現。他們的目的地是阿斯科特,那是個以女人和賽馬著稱的地方。不過做為內閣辦公室奧立佛.拉孔先生的宅邸所在,就不太有人知道。拉孔先生是各類不同委員會的高級顧問、諜報事務的總監督。或者,用貴蘭姆那有失尊敬的話來說,是白廳的管家。
(節選自第十章)
這幢房子一面是練習騎馬的小圍場,另一面是草地網球場,隱藏在樹林中間。球場不是太好,沒有常割草。春天時,草地被冬季的積水浸透,沒有陽光照進來把它曬乾。到了夏天,球飛出去也會消失在樹葉叢中。今天早上,從整個花園裡掃進球場來的結霜落葉,厚可沒腳。但是在場外,在順著長方形的鐵絲網外的山毛櫸間,有一條小徑,史邁利和拉孔就在這條小徑上漫步。史邁利披上了他的旅行大衣, 拉孔卻只穿他那套破舊的衣服。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的步子邁得又大又快,每一步都走在史邁利前面,因此不得不停步等個子矮的史邁利趕上。一趕上來,他又急著邁步,結果又走在前頭,他們這樣趕了兩次,拉孔終於打破沉默。
「一年前,你為了一個類似的想法來見我,我幾乎把你攆了出去。我想現在應該向你道歉。當時我太大意。」他沉默了一會,想著自己那次的失職,「我那時指示你停止所有調查。」
「你對我說,這種調查違憲。」史邁利也遺憾地說,彷彿也想起那個可悲的錯誤。
「我是這麼說的嗎?我的天,我真是太誇大其詞了。」
屋子那裡傳來潔姬不斷的哭聲。
「你從來沒有過吧,是不是?」拉孔馬上問,頭轉向哭聲傳來的方向。
「你說什麼?」
「我是說孩子,你和安沒有孩子吧?」
「沒有。」
「姪子、外甥呢?」
「只有一個姪子。」
「你的?」
「她的。」
史邁利環顧四周的玫瑰花叢,斷了的鞦韆、潮濕的沙坑、在晨光中醒目刺眼的紅房子,他心想,我彷彿從來沒離開過這裡,我們從上次談話後彷彿一直都還在這裡。
拉孔又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說,我不是完全信任你的動機?你瞧,我當時心裡想,是老總指使你來見我的。這是他戀棧不去,想排擠派西.艾勒林的辦法―」他又向前跨出大步,手腕向外揮著。
「不是,我可以向你保證,老總根本不知道。」
「我現在明白了。但我當時不明白。對你們這種人,真不知道究竟何時該相信,何時又不該。你們有截然不同的標準,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們不得不那樣。這一點,我是同意的。我無意妄下斷語。畢竟我們的目標一致,即便方法不同。」―他跳過一個小溝―「有一次,我聽人說,道德規範就是方法。這種看法你同意嗎?我想你大概不會同意。我想,你會說,道德規範就寄託在目標之中。但是很難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問題就在這裡,尤其你若是英國人的話。我們不能要求你們這些人來為我們決定政策,是不是?我們只能要求你們推行政策,對不對?又很微妙吧?」
史邁利不再追著他走。他一屁股坐在一個生鏽的搖椅上,把大衣裹得更緊了,於是拉孔只好回來, 欠著身子坐在他身旁。他們兩人一起跟著下面的彈簧咯吱咯吱地搖著。
「為什麼她選中塔爾?」拉孔終於自言自語道,撥弄著他纖長的手指,「要找一個人聽她的懺悔, 我看沒有比這個人更不合適的了。」
「我看,這個問題你得去問女人,問我們沒有用。」史邁利的心裡又在想伊明翰究竟位在哪裡。
「唉,是啊。」拉孔馬上同意道,「這一切都是個謎。我十一點要去見大臣,」他低聲告訴史邁利,「我得讓他知道,他是你在議會的表兄弟。」他又補充了一句,勉強加上這個涉及私人的笑話。
「比爾.海頓也是安的表兄?我們倫敦站那位傑出的站長?」他們以前也已經開過這個玩笑了。
「是啊,根據另一條家系,比爾也是她的表兄。」他完全沒必要地補上一句,「她出身一個古老的家族,這個家族有很穩固的政治傳統。年代久遠,也就分布得更廣了。」
「傳統?」拉孔喜歡把含糊其詞的話搞清楚。
「家族。」
史邁利聽見樹林外面汽車駛過的聲音。整個世界就在這樹林之外,然而拉孔卻有這個紅色的城堡和基督教的倫理觀,後者能給他的不過是個爵士的封號、同輩的尊敬、優厚的年金和一、兩家大公司理事的掛名差使。
「我反正要在十一點鐘去見他。」拉孔站了起來,他們又在一起走了。史邁利忽然覺得在早晨新鮮的空氣中飄來「埃利斯」的名字。有那麼一陣子,像坐在貴蘭姆的車裡一樣,一種奇怪的不安感襲上他的心頭。
「畢竟,」拉孔說道,「我們倆的立場都很光明正大。你認為埃利斯被出賣了,因此要求追查。大臣和我認為這件事完全是老總辦事無能―說得客氣點,這也是外交部的看法―因此我們要換一把新掃帚。」
「唉,我相當理解你兩難的處境。」史邁利這句話與其說是說給拉孔聽的,不如說是說給自己聽的。
「那我很高興。喬治,可別忘了:你是老總的人。老總喜歡你,不喜歡海頓,他後來失去自制,幹這件特別冒險的事時,是你給他撐門面的。不是別人,是你,喬治。諜報組織的頭頭和捷克人打私仗, 可不是常見的事。」舊事重提顯然還是令人不快。「要不是那樣,我想倒楣的也許就是海頓了,但是你正好首當其衝,而―」
「而派西.艾勒林正好是大臣的人。」史邁利的聲音很輕,拉孔只好放慢腳步來聽他說。
「你也知道,要是你有個懷疑對象,就不是那樣了!你沒有指出任何人!沒有具體目標而進行調查,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而新掃帚掃得更乾淨些。」
「你是說派西.艾勒林?總而言之,他做得很好。他拿出來的是諜報,不是醜聞。他嚴格遵守職責,博得顧客信任。據我所知,他還沒有侵犯捷克領土。」
「有比爾.海頓替他防守,誰不會?」
「老總就不會。」拉孔的這一拳很有力。
他們走到一個空游泳池前停了下來,站在那裡看著深的那一頭。從黑漆漆的深處,史邁利好像覺得又聽見羅迪.馬丁台爾含沙射影的話:「海軍部裡的機密文件閱覽室裡,用各種古里古怪名稱成立的小組委員會裡……」
「派西的那個情資特別來源還活躍嗎?」史邁利問道,「叫什麼巫術資料或什麼的?」
「我不知道你也在名單上,」拉孔說得一點也不高興,「既然你問起,我就告訴你吧,仍舊活躍。巫師情資來源是我們的主要依靠,他的情資仍用巫術這個名稱。圓場好多年沒交來這麼好的資料了。根據我的記憶,可說從來沒有過。」
「還是需要經過那套特殊處理嗎?」
「當然,但現在發生這件事,我想我們無疑要採取更嚴格的預防措施。」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這麼做。傑拉德可能嗅出味道不對。」
「這就是關鍵,不是嗎?」拉孔馬上回說。史邁利心想,這人精力過人,不可想像。剛才還像個連腰板都挺不直的瘦弱拳擊手,戴著一副過大的拳擊手套;這會兒他卻出拳把你打到場邊的繩圈上,帶著基督徒的同情眼光看著你。「我們不能動手。我們不能著手調查,因為調查手段全都掌控在圓場手上, 甚至可能就在地鼠傑拉德的手裡。我們不能監視、偷聽、拆信。要做這些事情,得用艾斯特海斯手下點路燈的力量,而艾斯特海斯本人就跟別人一樣也是嫌疑對象。我們不能訊問,我們不能限制某個人查閱機密資料。這些舉動會有讓地鼠心生警戒的危險。喬治,這是個最古老的問題:誰能充當偵查間諜的間諜?誰能打草不驚蛇?」他開了一個笨拙的玩笑:「只有地鼠。」說的是內心的旁白。
史邁利一時來了勁,往前跨步,在通向小騎馬場的那條小徑上,走在拉孔的前頭。
「那麼就找圓場的競爭對手,」他回頭大聲說,「找安全部門。他們是專家,會幫你忙。」
「大臣不會同意的。你很明白,他和艾勒林對這個競爭對手有什麼看法。也難怪他們。如果讓一些前殖民地官員來檢查圓場的文件,不如讓陸軍來調查海軍算了!」
「根本不能這樣比。」史邁利不同意。
但是拉孔這個模範公務員卻已準備好了他的第二個隱喻:「那麼好吧,大臣寧可屋漏,也不願意讓外人來把他的堡壘拆掉。這麼說總行吧?喬治,他有充分的理由。我們有情報員在外面,一旦保安部門的人插手進來,他們就完了。」
現在史邁利放慢腳步了。
「有多少?」
「六百上下。」
「鐵幕後面呢?」
「估計是一百二十。」凡是數字,凡是各種各樣的事實,拉孔從來不含糊,這是他工作的本錢,從灰色的官僚主義大地中挖出來的黃金。「從財務報告來看,目前他們幾乎都很活躍。」他跨了一大步, 「那麼,我可以告訴他你願意幹,是不是?」他相當輕快地說,好像這個問題僅僅是形式,在適當的方格裡打個勾就行了,「你願意擔任這整頓內部的工作?對以前的、以後的,採取必要的措施?這畢竟是你這一代的,這是你的責任。」
史邁利已經推開小騎馬場的柵欄門,進去之後又隨手關上。他們兩人就在搖搖晃晃的欄杆兩邊面對著。拉孔臉上有些紅暈,帶著一種依賴的笑容。
「我為什麼要說埃利斯?」他找話說,「那個可憐的傢伙明明是叫普里多,我為什麼說埃利斯事件?」
「埃利斯是他工作的名字。」
「當然了,那些日子裡不斷出事,讓人連細節都給忘了,」他停了一會,揮著右臂向外一甩,「他是海頓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
「他們戰前一起念牛津。」
「後來戰時和戰後一直是圓場的同伴。出了名的海頓― 普里多搭檔。我的前輩不斷提到他們。」他又問,「你跟他從來沒親近過?」
「普里多?不。」
「我是說,不是表兄?」
「拜託,」史邁利粗聲粗氣地叫道。
拉孔又顯得尷尬起來,但是他另有目的,因此目光死盯著史邁利。「沒有感情上的原因或其他原因,讓你覺得不適合擔任這個工作吧?喬治,你一定得說清楚。」他有些擔心地要求,好像他最不希望人家說清楚似的。他等了一會,就又不在乎了,「不過我看不出有什麼真正理由。我們總有一部分是屬於公家的,不是嗎?社會契約互相都有約束力,我相信你一直都知道。普里多也是。」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唉,喬治,他中了槍,背上中了一槍,即使在你們的圈子裡,這也是很大的犧牲吧。」
在這種前提的慰藉下,史邁利到了國王路,他在人行道上停了一會兒,好像要過馬路似的。馬路兩邊都是華麗的精品商店。在他前面是自己住的貝瓦特街,一條死巷子,他從頭走到底,總共只有一百一十七步。他當初搬到這裡時,這些喬治時期的建築有一種敗落敝舊的美,年輕的夫婦靠十五鎊過一星期,在地下室裡還不敢聲張收個不付稅的房客。可是現在卻有鐵欄杆保護下層的窗戶,每幢屋子的路邊都擠著停了三輛汽車。史邁利出於長期養成的習慣,走過去時一一看了一眼,哪輛是熟悉的,哪輛不然;不熟悉的汽車中,有哪輛又是安裝了天線和多一面鏡子,哪輛是監視者喜歡的那種無窗小貨車。他這麼做,部分原因是要考驗自己的記憶力,為了保持頭腦不至於因為退休而萎縮,就像以前他在往大英博物館的公車上熟記沿途的商店門牌號碼一樣;也正如他背得出自己家中每層樓梯共有多少級,十二扇門每一扇朝什麼方向開一樣。
但是史邁利這麼做還有第二個原因,那就是他害怕,這是職業間諜到死都甩不開的祕密恐懼。由於過去經歷那樣複雜,連自己也記不清結下了多少怨仇,總有一天仇人會找上門來跟他算帳。
在這條街的盡頭,有個鄰居帶狗出來散步;她看到他,抬起頭來說了一句不知什麼的話,但是他沒有理她,心裡知道大概又是關於安的話。他穿過馬路。他的房子一片漆黑,窗簾仍像他出門時那樣拉上。他爬上六級台階,來到門口。自從安走了以後,他把打掃屋子的女人也給辭退了:除了安之外,沒有別人有鑰匙。門上有兩道鎖,一道是班漢牌死鎖,一道是朱伯牌管匙鎖,還有兩片他自製的小木片, 只有指甲那麼大,一片塞在上面門梁縫裡,一片塞在班漢鎖的下面。這是他在出外勤時留下的習慣。最近,不知什麼原因,他又開始使用;也許是為了不要因為她突然回來而吃一驚。他用指尖一摸,兩片小木片都在那裡。於是他開了門鎖,推了進去,腳下碰到中午塞進來躺在地毯上的郵件。
他心想,是什麼雜誌到期了?《德國生活與文學》?《語言學》?他想應該是《語言學》,這早就到期了。他打開門廊的電燈,彎身翻看了一下郵件。一封是他的裁縫寄來的帳單,記的是一套他沒有訂製的衣服,他懷疑很可能那衣服正穿在安情人的身上;一封是亨萊一個加油站寄來的汽油帳單(才十月九號就沒錢了,他們在萊亨幹什麼呀);一封是銀行來信,說的是關於密德蘭銀行伊明翰分行為安.史邁利夫人開戶取款的事。
他對著這封信問,他媽的這兩個人在伊明翰幹什麼?真是天曉得,誰會去伊明翰跟姘頭幽會?這伊明翰是在哪裡?
他正在思量這個問題時,目光卻落在傘架上一把沒見過的雨傘上,這是一把綢傘,傘把上有手工縫製的皮套,上面有一個金環,但是沒有物主的姓名縮寫。他的腦袋裡很快閃過一個念頭:既然這把傘是乾的,那麼一定是在六點十五分下雨前就放在那裡了,因為架上也沒有水跡。而且這把傘很講究,雖然不新,傘尖不鏽鋼包頭還沒有擦劃過的痕跡。因此,這把傘屬於一個行動敏捷的人,甚至是年輕人, 像安最近的一個情人。但是既然這個傘主人知道門上塞的木片,又知道進屋以後放回原處,而且還頗為機靈,在推門打亂了(而且無疑也讀了)郵件以後,又把信放在門邊靠著,那麼他極有可能也認識史邁利;他不是安的情人,而是一個像他自己那樣的職業特務,一度跟他親密共事過,而且就像行話所說的那樣,認得出他的「筆跡」。
客廳的門虛掩著。他輕輕地又推開了一點。
「彼得?」他問道。
他從門縫裡看進去,靠外面路燈的光,看到沙發一頭伸著一雙穿著麂皮鞋子的腳,懶洋洋地交疊在一起。
「我要是你,喬治,我就不脫大衣了,老兄,」說話的聲音很親切,「我們還要趕遠路呢。」
五分鐘後,穿著一件寬大的棕色旅行大衣,喬治.史邁利鬱鬱不樂地坐在彼得.貴蘭姆的敞篷跑車的客座上。那件大衣是安送他的禮物,是他唯一乾燥的大衣。原來彼得把車停在附近另一個廣場上,所以他先前沒有發現。他們的目的地是阿斯科特,那是個以女人和賽馬著稱的地方。不過做為內閣辦公室奧立佛.拉孔先生的宅邸所在,就不太有人知道。拉孔先生是各類不同委員會的高級顧問、諜報事務的總監督。或者,用貴蘭姆那有失尊敬的話來說,是白廳的管家。
(節選自第十章)
這幢房子一面是練習騎馬的小圍場,另一面是草地網球場,隱藏在樹林中間。球場不是太好,沒有常割草。春天時,草地被冬季的積水浸透,沒有陽光照進來把它曬乾。到了夏天,球飛出去也會消失在樹葉叢中。今天早上,從整個花園裡掃進球場來的結霜落葉,厚可沒腳。但是在場外,在順著長方形的鐵絲網外的山毛櫸間,有一條小徑,史邁利和拉孔就在這條小徑上漫步。史邁利披上了他的旅行大衣, 拉孔卻只穿他那套破舊的衣服。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的步子邁得又大又快,每一步都走在史邁利前面,因此不得不停步等個子矮的史邁利趕上。一趕上來,他又急著邁步,結果又走在前頭,他們這樣趕了兩次,拉孔終於打破沉默。
「一年前,你為了一個類似的想法來見我,我幾乎把你攆了出去。我想現在應該向你道歉。當時我太大意。」他沉默了一會,想著自己那次的失職,「我那時指示你停止所有調查。」
「你對我說,這種調查違憲。」史邁利也遺憾地說,彷彿也想起那個可悲的錯誤。
「我是這麼說的嗎?我的天,我真是太誇大其詞了。」
屋子那裡傳來潔姬不斷的哭聲。
「你從來沒有過吧,是不是?」拉孔馬上問,頭轉向哭聲傳來的方向。
「你說什麼?」
「我是說孩子,你和安沒有孩子吧?」
「沒有。」
「姪子、外甥呢?」
「只有一個姪子。」
「你的?」
「她的。」
史邁利環顧四周的玫瑰花叢,斷了的鞦韆、潮濕的沙坑、在晨光中醒目刺眼的紅房子,他心想,我彷彿從來沒離開過這裡,我們從上次談話後彷彿一直都還在這裡。
拉孔又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說,我不是完全信任你的動機?你瞧,我當時心裡想,是老總指使你來見我的。這是他戀棧不去,想排擠派西.艾勒林的辦法―」他又向前跨出大步,手腕向外揮著。
「不是,我可以向你保證,老總根本不知道。」
「我現在明白了。但我當時不明白。對你們這種人,真不知道究竟何時該相信,何時又不該。你們有截然不同的標準,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們不得不那樣。這一點,我是同意的。我無意妄下斷語。畢竟我們的目標一致,即便方法不同。」―他跳過一個小溝―「有一次,我聽人說,道德規範就是方法。這種看法你同意嗎?我想你大概不會同意。我想,你會說,道德規範就寄託在目標之中。但是很難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問題就在這裡,尤其你若是英國人的話。我們不能要求你們這些人來為我們決定政策,是不是?我們只能要求你們推行政策,對不對?又很微妙吧?」
史邁利不再追著他走。他一屁股坐在一個生鏽的搖椅上,把大衣裹得更緊了,於是拉孔只好回來, 欠著身子坐在他身旁。他們兩人一起跟著下面的彈簧咯吱咯吱地搖著。
「為什麼她選中塔爾?」拉孔終於自言自語道,撥弄著他纖長的手指,「要找一個人聽她的懺悔, 我看沒有比這個人更不合適的了。」
「我看,這個問題你得去問女人,問我們沒有用。」史邁利的心裡又在想伊明翰究竟位在哪裡。
「唉,是啊。」拉孔馬上同意道,「這一切都是個謎。我十一點要去見大臣,」他低聲告訴史邁利,「我得讓他知道,他是你在議會的表兄弟。」他又補充了一句,勉強加上這個涉及私人的笑話。
「比爾.海頓也是安的表兄?我們倫敦站那位傑出的站長?」他們以前也已經開過這個玩笑了。
「是啊,根據另一條家系,比爾也是她的表兄。」他完全沒必要地補上一句,「她出身一個古老的家族,這個家族有很穩固的政治傳統。年代久遠,也就分布得更廣了。」
「傳統?」拉孔喜歡把含糊其詞的話搞清楚。
「家族。」
史邁利聽見樹林外面汽車駛過的聲音。整個世界就在這樹林之外,然而拉孔卻有這個紅色的城堡和基督教的倫理觀,後者能給他的不過是個爵士的封號、同輩的尊敬、優厚的年金和一、兩家大公司理事的掛名差使。
「我反正要在十一點鐘去見他。」拉孔站了起來,他們又在一起走了。史邁利忽然覺得在早晨新鮮的空氣中飄來「埃利斯」的名字。有那麼一陣子,像坐在貴蘭姆的車裡一樣,一種奇怪的不安感襲上他的心頭。
「畢竟,」拉孔說道,「我們倆的立場都很光明正大。你認為埃利斯被出賣了,因此要求追查。大臣和我認為這件事完全是老總辦事無能―說得客氣點,這也是外交部的看法―因此我們要換一把新掃帚。」
「唉,我相當理解你兩難的處境。」史邁利這句話與其說是說給拉孔聽的,不如說是說給自己聽的。
「那我很高興。喬治,可別忘了:你是老總的人。老總喜歡你,不喜歡海頓,他後來失去自制,幹這件特別冒險的事時,是你給他撐門面的。不是別人,是你,喬治。諜報組織的頭頭和捷克人打私仗, 可不是常見的事。」舊事重提顯然還是令人不快。「要不是那樣,我想倒楣的也許就是海頓了,但是你正好首當其衝,而―」
「而派西.艾勒林正好是大臣的人。」史邁利的聲音很輕,拉孔只好放慢腳步來聽他說。
「你也知道,要是你有個懷疑對象,就不是那樣了!你沒有指出任何人!沒有具體目標而進行調查,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而新掃帚掃得更乾淨些。」
「你是說派西.艾勒林?總而言之,他做得很好。他拿出來的是諜報,不是醜聞。他嚴格遵守職責,博得顧客信任。據我所知,他還沒有侵犯捷克領土。」
「有比爾.海頓替他防守,誰不會?」
「老總就不會。」拉孔的這一拳很有力。
他們走到一個空游泳池前停了下來,站在那裡看著深的那一頭。從黑漆漆的深處,史邁利好像覺得又聽見羅迪.馬丁台爾含沙射影的話:「海軍部裡的機密文件閱覽室裡,用各種古里古怪名稱成立的小組委員會裡……」
「派西的那個情資特別來源還活躍嗎?」史邁利問道,「叫什麼巫術資料或什麼的?」
「我不知道你也在名單上,」拉孔說得一點也不高興,「既然你問起,我就告訴你吧,仍舊活躍。巫師情資來源是我們的主要依靠,他的情資仍用巫術這個名稱。圓場好多年沒交來這麼好的資料了。根據我的記憶,可說從來沒有過。」
「還是需要經過那套特殊處理嗎?」
「當然,但現在發生這件事,我想我們無疑要採取更嚴格的預防措施。」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這麼做。傑拉德可能嗅出味道不對。」
「這就是關鍵,不是嗎?」拉孔馬上回說。史邁利心想,這人精力過人,不可想像。剛才還像個連腰板都挺不直的瘦弱拳擊手,戴著一副過大的拳擊手套;這會兒他卻出拳把你打到場邊的繩圈上,帶著基督徒的同情眼光看著你。「我們不能動手。我們不能著手調查,因為調查手段全都掌控在圓場手上, 甚至可能就在地鼠傑拉德的手裡。我們不能監視、偷聽、拆信。要做這些事情,得用艾斯特海斯手下點路燈的力量,而艾斯特海斯本人就跟別人一樣也是嫌疑對象。我們不能訊問,我們不能限制某個人查閱機密資料。這些舉動會有讓地鼠心生警戒的危險。喬治,這是個最古老的問題:誰能充當偵查間諜的間諜?誰能打草不驚蛇?」他開了一個笨拙的玩笑:「只有地鼠。」說的是內心的旁白。
史邁利一時來了勁,往前跨步,在通向小騎馬場的那條小徑上,走在拉孔的前頭。
「那麼就找圓場的競爭對手,」他回頭大聲說,「找安全部門。他們是專家,會幫你忙。」
「大臣不會同意的。你很明白,他和艾勒林對這個競爭對手有什麼看法。也難怪他們。如果讓一些前殖民地官員來檢查圓場的文件,不如讓陸軍來調查海軍算了!」
「根本不能這樣比。」史邁利不同意。
但是拉孔這個模範公務員卻已準備好了他的第二個隱喻:「那麼好吧,大臣寧可屋漏,也不願意讓外人來把他的堡壘拆掉。這麼說總行吧?喬治,他有充分的理由。我們有情報員在外面,一旦保安部門的人插手進來,他們就完了。」
現在史邁利放慢腳步了。
「有多少?」
「六百上下。」
「鐵幕後面呢?」
「估計是一百二十。」凡是數字,凡是各種各樣的事實,拉孔從來不含糊,這是他工作的本錢,從灰色的官僚主義大地中挖出來的黃金。「從財務報告來看,目前他們幾乎都很活躍。」他跨了一大步, 「那麼,我可以告訴他你願意幹,是不是?」他相當輕快地說,好像這個問題僅僅是形式,在適當的方格裡打個勾就行了,「你願意擔任這整頓內部的工作?對以前的、以後的,採取必要的措施?這畢竟是你這一代的,這是你的責任。」
史邁利已經推開小騎馬場的柵欄門,進去之後又隨手關上。他們兩人就在搖搖晃晃的欄杆兩邊面對著。拉孔臉上有些紅暈,帶著一種依賴的笑容。
「我為什麼要說埃利斯?」他找話說,「那個可憐的傢伙明明是叫普里多,我為什麼說埃利斯事件?」
「埃利斯是他工作的名字。」
「當然了,那些日子裡不斷出事,讓人連細節都給忘了,」他停了一會,揮著右臂向外一甩,「他是海頓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
「他們戰前一起念牛津。」
「後來戰時和戰後一直是圓場的同伴。出了名的海頓― 普里多搭檔。我的前輩不斷提到他們。」他又問,「你跟他從來沒親近過?」
「普里多?不。」
「我是說,不是表兄?」
「拜託,」史邁利粗聲粗氣地叫道。
拉孔又顯得尷尬起來,但是他另有目的,因此目光死盯著史邁利。「沒有感情上的原因或其他原因,讓你覺得不適合擔任這個工作吧?喬治,你一定得說清楚。」他有些擔心地要求,好像他最不希望人家說清楚似的。他等了一會,就又不在乎了,「不過我看不出有什麼真正理由。我們總有一部分是屬於公家的,不是嗎?社會契約互相都有約束力,我相信你一直都知道。普里多也是。」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唉,喬治,他中了槍,背上中了一槍,即使在你們的圈子裡,這也是很大的犧牲吧。」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