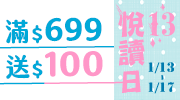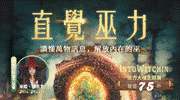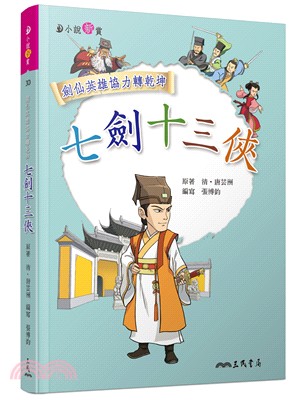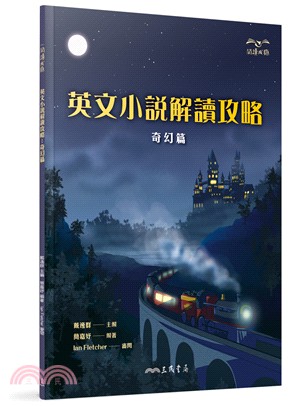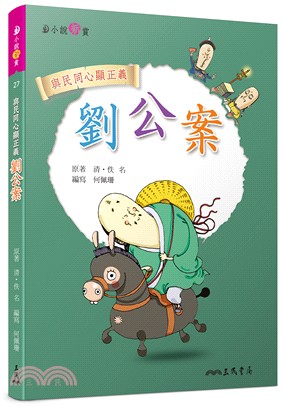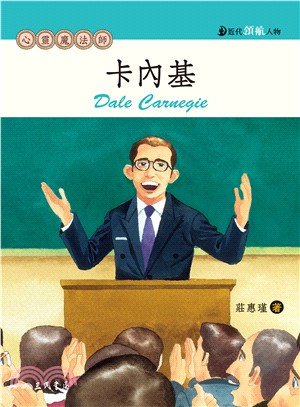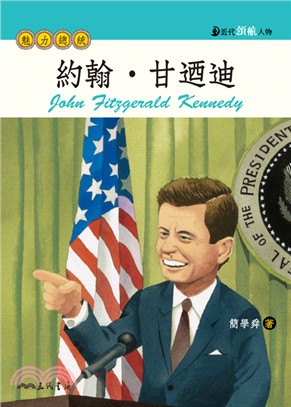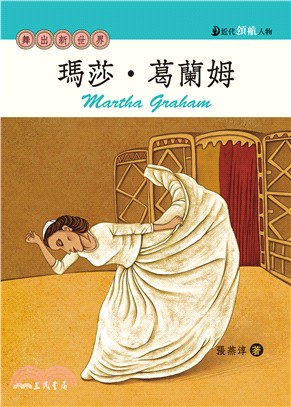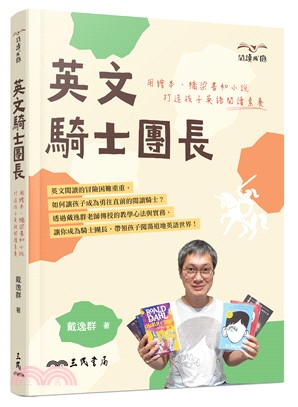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蕭朔說:「我自幼見你,一眼便已記牢……當年我本想趕去邊城同你說,以生死祭朝暮,卻陰差陽錯。既然朝暮不可祭,我轉求百年。」
雲琅說:「我同蕭朔無非生死一處而已,不論百年,不算朝暮,我心裡裝著他,於是便活著兩個人的命,他活一個時辰,我便不敢早進墳塋一刻。」
情竇初開、互訴衷腸的兩人雖情話講得好聽,但一個話本沒看懂,一個話本沒看全,一邊磕磕絆絆地談戀愛,一邊聯手調查當年滅門血案的真相。
雲琅想闖入機關密布的玉英閣裡找一份血誓,兩人歷經九死一生才終於驚險找到關鍵證據,得知當年還是皇子的當今皇上,是跟誰密謀奪朝。
也因此打草驚蛇,兩人察覺京中開始出現微小的蹊蹺反常,面對朝堂的緊逼,他們步步踩在刀尖上,若哪一處差了半分,就搏不出一條血路。
春節將至,各方看似平靜得近乎詭異,其下卻暗流洶湧,只怕險灘已至……
誰歸於誰,並無分別,總歸攜手百年,來世仍做眷侶
「將軍夫人不好,不威風。小王妃多厲害,回頭你給我弄一個王妃大印。」
不論叫蕭朔將軍夫人,還是叫雲琅小王妃,
雲琅都是單人獨騎便能力挽狂瀾的少將軍。
他的少將軍。
★口是心非的冰山小王爺X正經不超過五秒的俠氣小將軍
★晉江積分3.3億、6.4萬書評、11萬收藏、VIP強推古風耽美文,看過都按讚
★開窗書衣設計概念:
書中常出現「窗戶」這個元素,以此為概念,書衣畫出大理寺內機關密布的玉英閣外觀,透過窗戶能看到封面上正在玉英閣裡歷經九死一生的蕭朔和雲琅。
★隨書好禮大方送:
第一重:隨書贈送精美留言卡
第二重:作者獨冢專訪-2,暢談創作緣由
第三重:首刷加送開窗書衣,書衣的窗戶能左右打開,透過玉英閣的外窗,能看到閣內互相倚靠的兩人正處於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
第四重:書衣上有燙金的作者簽名
雲琅說:「我同蕭朔無非生死一處而已,不論百年,不算朝暮,我心裡裝著他,於是便活著兩個人的命,他活一個時辰,我便不敢早進墳塋一刻。」
情竇初開、互訴衷腸的兩人雖情話講得好聽,但一個話本沒看懂,一個話本沒看全,一邊磕磕絆絆地談戀愛,一邊聯手調查當年滅門血案的真相。
雲琅想闖入機關密布的玉英閣裡找一份血誓,兩人歷經九死一生才終於驚險找到關鍵證據,得知當年還是皇子的當今皇上,是跟誰密謀奪朝。
也因此打草驚蛇,兩人察覺京中開始出現微小的蹊蹺反常,面對朝堂的緊逼,他們步步踩在刀尖上,若哪一處差了半分,就搏不出一條血路。
春節將至,各方看似平靜得近乎詭異,其下卻暗流洶湧,只怕險灘已至……
誰歸於誰,並無分別,總歸攜手百年,來世仍做眷侶
「將軍夫人不好,不威風。小王妃多厲害,回頭你給我弄一個王妃大印。」
不論叫蕭朔將軍夫人,還是叫雲琅小王妃,
雲琅都是單人獨騎便能力挽狂瀾的少將軍。
他的少將軍。
★口是心非的冰山小王爺X正經不超過五秒的俠氣小將軍
★晉江積分3.3億、6.4萬書評、11萬收藏、VIP強推古風耽美文,看過都按讚
★開窗書衣設計概念:
書中常出現「窗戶」這個元素,以此為概念,書衣畫出大理寺內機關密布的玉英閣外觀,透過窗戶能看到封面上正在玉英閣裡歷經九死一生的蕭朔和雲琅。
★隨書好禮大方送:
第一重:隨書贈送精美留言卡
第二重:作者獨冢專訪-2,暢談創作緣由
第三重:首刷加送開窗書衣,書衣的窗戶能左右打開,透過玉英閣的外窗,能看到閣內互相倚靠的兩人正處於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
第四重:書衣上有燙金的作者簽名
作者簡介
【作者】
三千大夢敘平生
專職做夢,副業寫作,睡眠重度困難戶。
熱愛漫長的行走,熱愛觀察和記錄,理想是成為一個能把故事講好的人。
有三千場夢,三千段講不完的故事,和三千顆不同味道的水果糖。
【封面繪圖】
蓮花落
繪手一枚,喜歡古風,尤其鍾愛武俠,武俠是初心也是白月光。
因為太懶無法走萬里路,所以讓想像縱馬於江湖之間,可以自由持一竹杖任行逍遙。
希望某天筆能長大到畫出喜歡的花草鳥獸和各種好看瀟灑男人,但筆往往不受控是最大的煩惱。
三千大夢敘平生
專職做夢,副業寫作,睡眠重度困難戶。
熱愛漫長的行走,熱愛觀察和記錄,理想是成為一個能把故事講好的人。
有三千場夢,三千段講不完的故事,和三千顆不同味道的水果糖。
【封面繪圖】
蓮花落
繪手一枚,喜歡古風,尤其鍾愛武俠,武俠是初心也是白月光。
因為太懶無法走萬里路,所以讓想像縱馬於江湖之間,可以自由持一竹杖任行逍遙。
希望某天筆能長大到畫出喜歡的花草鳥獸和各種好看瀟灑男人,但筆往往不受控是最大的煩惱。
目次
【第一章】恕老僕直言,您的話本看得沒比王爺強到哪裡去
【第二章】我從未這般高興,高興我此番追你,竟來得及
【第三章】你我不是他人手中刀,君若成刀,我自為鞘
【第四章】叫他下不了榻,叫他乖,叫他哭不出聲
【第五章】多虧小王爺沉穩,接了當頭一鍋,轉手砸了侍衛司一個跟頭
【第六章】這是哪家道理,哪處話本上是這般寫的?
【第七章】不論什麼事,小王爺回來,叫他在窗戶底下蹲著
【第八章】小王爺,這些年你這麼忙,大理寺卿知道嗎?
【第九章】琰王殿下,你將雲氏餘孽自法場劫回府中,究竟是為的什麼?
【第十章】今日一戰,我只聽喊殺聲便恨不能與你並肩
【特別收錄】作者紙上訪談第三彈,角色性格分析
【第二章】我從未這般高興,高興我此番追你,竟來得及
【第三章】你我不是他人手中刀,君若成刀,我自為鞘
【第四章】叫他下不了榻,叫他乖,叫他哭不出聲
【第五章】多虧小王爺沉穩,接了當頭一鍋,轉手砸了侍衛司一個跟頭
【第六章】這是哪家道理,哪處話本上是這般寫的?
【第七章】不論什麼事,小王爺回來,叫他在窗戶底下蹲著
【第八章】小王爺,這些年你這麼忙,大理寺卿知道嗎?
【第九章】琰王殿下,你將雲氏餘孽自法場劫回府中,究竟是為的什麼?
【第十章】今日一戰,我只聽喊殺聲便恨不能與你並肩
【特別收錄】作者紙上訪談第三彈,角色性格分析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第十章】今日一戰,我只聽喊殺聲便恨不能與你並肩
蕭朔是進宮來做什麼的,洪公公看不透,都虞候和連勝看不透,就連皇上預設立場、百般揣摩,只怕也想不明白。
宮變凶險,禍福難料。蕭朔慣了走一步看三步,縱然有九成九的把握,也要為了那一分,將後路替他鋪設妥當。
只要能叫皇上相信雲琅能替他守住當年事,便有可能叫皇上動搖,此時壓上蕭朔的立場,皇上無人可用,為安撫蕭朔,多半會選赦了雲琅死罪。
若今日能將雲琅身上的死罪推了……不論用什麼辦法,縱然明日不幸,蕭小王爺死在這宮變之中,雲琅也再不需王府庇佑。
蕭朔不攔雲琅同死同穴,卻要為了這一分可能,寧肯兵行險著,也要讓雲琅能以少將軍之名去北疆。
蕭朔要保證,縱然琰王今日身死,他的少將軍也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領他的兵、奪他的城。
「少將軍……好軍威。」蕭朔抬手,在雲琅眼尾輕輕一碰,「訓人竟也能將自己訓成這般架式。」
雲琅用力閉上眼睛,將眼底熱意逼回去,惡狠狠威脅,「再說一句。」
蕭朔及時住了口,靜了片刻,又輕聲道:「只是慣了思慮,將事做得周全些,你不必多想。」
雲少將軍不爭氣,又想起來時見蕭朔那一笑,徹底沒了半分軍威,緊閉著眼睛轉了個身。
「知錯了。」蕭朔輕撫他頸後,「如何能哄少將軍消氣?」
「去找你六大爺,叫他赦了我。」雲琅悶聲:「打一仗給你看軍威。」
蕭朔微啞,正要開口,殿外傳來極輕的兩下敲門聲。
「殿下。」隔了一息,洪公公的聲音自門外響起,「文德殿方才派人傳旨,說宗正寺來報,尋著了一封過往宗室玉牒。」
「天章閣閣老與虔國公親自辨認,上用玉璽,是先帝筆跡。」洪公公輕聲道:「玉牒上所載……是前雲麾將軍雲琅。」
雲琅:「……」
蕭朔靜坐著,掌心仍覆著他脖頸,看不清神色。
雲琅方才澎湃的心神漸漸熄了,心情有些複雜,撐坐起來。
兩人忙活半宿,為的無非就是這個,自然猜得到皇上會妥協設法赦他死罪。
死罪並不難免,雲琅只是受親族牽連,若非當年親手燒了豁罪明詔,為換琰王府安寧將性命親手交進了六皇子手中,這罪分明早就該一筆勾銷。
如今皇上既不得已退讓這一步,找個今年高興、大赦天下的藉口,罪便也免乾淨了。
誰也沒想起來……居然還有這個辦法。
雲琅還記著先帝那句「皇后養子」,一時心裡也頗沒底,訥訥:「小王爺。」
蕭朔坐得紋絲不動。
雲琅有點心虛,乾咳一聲,扯扯他袖子,「小皇孫。」
蕭朔坐得一片巍然。
雲琅鼓足勇氣,「大侄……」
蕭朔:「雲琅。」
雲琅當即牢牢閉嘴。
蕭朔深吸口氣,將一把火燒了祖廟的念頭壓下去,按按眉心,起身下榻開門,去接了那一封玉牒。
他也早已忘了此事,更想不到蔡太傅竟當真去找了,此時只覺分外頭痛,蹙緊眉打開看了一眼,卻忽然微怔。
雲琅輩分飄忽不定,頗為緊張,「寫的什麼?」
蕭朔看他一眼,將玉牒合上。
雲琅:「啊?」
蕭小王爺沒有心。雲琅火急火燎,自榻上跳下來,「給我看一眼!怎麼回事,莫非將我寫成端王養孫了?你怎麼還往高舉你這人……」
洪公公及時關了門,看著兩人鬧在一處爭搶那份玉牒,再壓不住笑意,欣然向後退了退。
雲琅蹦著高,眼看便要搶到那一封玉牒,神色忽然微變,鬆開手回過身。
洪公公一愣,「小侯爺,可是出了什麼事?」
蕭朔走到窗邊,將窗戶推開。
宮中仍寧靜,天邊卻一片通明,隱約可見耀眼爆竹焰色。
蕭朔與雲琅對視一眼,神色微沉,「是鼇山的爆竹聲。」
「大抵是我們這位皇上到底沉不住氣,打草驚蛇了……無妨,來得及。」
雲琅道:「我本想著今日在宮裡陪你一天,外頭安排好了,隨時能用。」
雲琅入宮前便已整頓好了殿前司,兩家親兵也並在一處,隨時待命。開封尹早備好了滅火活水、衙役各方守牢,虔國公的私兵也守在了京郊,隨時馳援。
本想有備無患,陰差陽錯,竟碰在了一處。
侍衛司異動,朝臣深夜入宮,終歸還是驚動了虎視眈眈的襄王,竟將宮變提前了整整一日。
此時正好盡數用上。
「不耽擱了,回頭同你說。」雲琅摸過蒙面巾,「你那盔甲穿好,流矢無眼,千萬當心。」
「小侯爺!」洪公公隱約聽明白了情形,心頭一懸,「您不可不披甲,宮中有盔甲,老奴帶您去。」
「不必。」雲琅一笑,「我剛從製衣局過來,一不小心,看見了套上好的雲錦短打,配的薄鐵淬火明光甲。」
雲琅已有了主意,緊了緊腕間袖箭機栝,「蕭朔。」
蕭朔點了點頭,緩聲道:「凡事謹慎,多加小心。」
「話還給你,多加小心。」雲琅笑道:「有件事我沒對你說過……我在御史臺獄,曾做過個夢。」
雲琅:「夢見我穿著那一身雲錦戰袍,去北疆打了一場仗,萬箭穿心,死在了北疆。」
蕭朔眼底光芒一悸,抬頭望他。
「我就剩了一個煙花,本想等到死而無憾的時候,給自己聽個響。」雲琅道:「放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居然有憾,還憾大發了……我惦記一個人,竟連他一眼都沒看見。」
雲琅:「若他在,我說一句疼,他定來哄我。」
「戰事在即。」蕭朔啞聲道:「不說這些。」
「就得說這些,老主簿說了,要說什麼等打完仗回來就把我扛回你府裡當小王妃之類的話,這就叫插旗。」
雲琅飛快含混道:「你聽我說,蕭朔。」
蕭朔叫他握住手,輕攥了下,抬起視線。
「我攀扯你,在刑場胡言亂語,是忽然想通了。」雲琅道:「我若死在你府上,就能有個歸處,半夜還能在你床底下睡覺。」
蕭朔靜了靜,抬頭道:「戰事在即……」
「我知道。」雲琅扯扯嘴角,低聲飛快道:「我今夜調息,又做了那個夢,夢裡有諸多不同。我想過是什麼兆頭,也想同你研究研究,後來見你醒來朝我笑,忽然想透了……蕭朔。」
窗外漆黑,夜色下蟄伏的凶險還尚未顯露,天邊明暗吞吐,雜著爆竹的鳴聲。
雲琅單手一撐,坐在窗沿上。
雲琅看著蕭朔,眼底已是一片刀光劍影的明銳鋒芒,卻又分明映著他的影子,「過來,這次輪到你。」
蕭朔靜看他良久,走過去。
雲琅握住他手臂用力一扯,伸手將蕭朔牢牢抱住,迎著夜風,肆無忌憚地吻他。
蕭朔胸口滾燙熱血轟鳴,氣息一滯,閉上眼睛。
雲少將軍輕薄了琰王殿下,笑意明淨,深深看了蕭朔一眼,再不廢話,擰身扎進了茫茫夜色。
**************
臘月廿九,大儺驅逐疫癘之鬼,焚天香於戶外。
消災祈福,除舊布新
鼇山轟鳴點亮的一刻,文德殿內也跟著一時靜寂。朝臣面面相覷,神色都隱約微變。
皇上用力按了按眉心,深吸口氣,慢慢呼出來。
高繼勳死得突然,蕭朔接掌侍衛司,原本也是此時唯一一條出路。
只是按照原本預計,赦了雲琅以安撫蕭朔,明早再勉勵一番,調動妥當從容安排,一日的時間恰好足夠。
襄王一黨偏偏在今夜點亮鼇山,勢成騎虎,待兵戈一起,再無退路。
「京城情勢與北疆不同,雲琅已多年沒帶過兵,未必能勝,不便執掌兵事。」皇上壓了壓念頭,「宣琰王……來文德殿吧。」
一刻後,琰王披掛入殿,奉了侍衛司銅牌令。
「非常之時,朕信不過旁人。」皇上穿過群臣,親手將蕭朔扶起,「禁軍各處皆已調配妥當,只缺人居中調動,你可有把握?」
「臣不知兵。」蕭朔道:「拚命而已。」
皇上頓了下,神色不變,緩聲道:「朕用人不疑,既用了你,便是信你能替朕剿除逆黨。」
話音未盡,又一聲震耳轟鳴。
方才那一聲在城中,離得尚遠,此時這一響震得地皮像是都跟著顫了一顫,竟彷彿近在咫尺。
窗外夜沉如水,仍靜得彷彿一片風平浪靜,夜風流動,卻飄來隱約炙烤的火藥氣息。
皇上倏而轉身,牢牢盯著窗外,神色驟沉。
蕭朔道:「上朝時,大都過宣德門、端禮門,再入文德門方到文德殿。可要來文德殿最便利的,其實並不是這幾座門。」
眾人面面相覷,對視一眼,臉色都不由變了變。
「情勢有變,臣請兵符。」蕭朔道:「右承天門若破,要毀文德殿,只要一把火。」
他語氣冷淡漠然,與平日無異,說出的話卻已在殿中掀開一片焦躁惶恐。
「你……你如何知道,他們會從右承天門殺進來?」樞密使顫巍巍道:「那裡不是正門,外有護城塹溝,城高牆深,區區叛軍如何進得來……」
「大人。」蕭朔慢慢道,「真正的叛軍,是不會裹挾幾個禁軍嘩變,在寢宮前鬧一場了事的。」
他此言對著樞密使,皇上的臉色卻忽然狠狠一白,沉聲道:「夠了,不必說了!」
蕭朔回身,垂頭拱手。
皇上深深盯他半晌,終歸將侍衛司的腰牌兵符取出來,遞給金吾衛,交在了蕭朔手中。
*****************
汴梁城中,火光四起。
開封尹未著官服,親自帶人撲火滅煙,身上已處處煙灰餘燼,「不可聚在一處,四處照應!敲淨街梆……」
話到一半,一條梁柱燒得毀去大半,當頭劈砸下來。
護衛撲救已來不及,喊劈了嗓子,要捨身撲過去,忽然聽見身後清亮馬嘶。
馬上將領白袍銀甲,掠過殘垣,一槍挑飛了仍烈烈燒著的梁柱,扯著開封尹衣領,拋進護衛群中。
開封尹被人七手八腳匆忙攙扶,倉促站穩,「雲將軍!」
「有勞。」雲琅勒馬,「叛軍在何處?」
開封尹定了定神,「四方都有,朝城西匯攏。方才聽見傳令,要破右承天門。」
雲琅:「百姓如何?」
「依將軍所言,這幾夜淨街宵禁。」開封尹道:「大都在家中,只是有民居燒毀,開封府正設法安置。」
雲琅心中大致有數,點了下頭,勒了勒手中馬韁。
開封尹是文人,不是戰將,能顧到這一步已是極限。如今在阻攔叛軍,與之激戰的,應當是周邊駐紮的禁軍。
禁軍布置他看過一圈,當年端王遺留下來的布防圖,水潑不透,若戰力足夠,叛軍理當束手無策。
若戰力足夠。
雲琅隨手拋了搶來的長槍,解下鞍後繫著的勁弓,握在手裡,凝神將城中各方布置戰力盤過一遍。
宮中忌憚蕭朔,卻又不得不用蕭朔,縱然交出侍衛司,也不會放蕭朔出城。
城中禁軍各自為戰,沒有將領主持,成了遊兵散勇。
「殿前司守在金水門!」開封尹忽然想起一事,上前一步急道:「是琰王留給將軍的部下,將軍若見了他們,便有兵了!」
「不急。」雲琅道:「金水門緊要,不可輕離。」
開封尹一怔,「可是……」
「衛大人斯文些,擦一擦臉。」雲琅朝他一笑,調轉馬頭,「我做將軍,幾時還沒有兵帶了?」
開封尹怔忡立著,不及開口,雲琅已揚鞭催馬,沒入了黑黢黢的夜色。
城中亂成一片,沿街門戶緊閉,越向西走,越見戰後狼藉。
血色刺目,混著硫磺火藥,在風裡熱熱刺著人的嗓子。
花燈碾爛了,毀去大半,破開精緻外膛,亮出一點細弱燭火。
侍衛司叫黑鐵騎兵絞著,一觸即潰,猶有勉力拚殺的,也已不比風中的殘燈好上多少。
「主將都沒有,不如逃命!」有人和著血絕望嘶聲:「打什麼?如何打得過……」
校尉垂著一臂,身上盡是淋漓血色,咬牙低吼:「奉軍令,叛逃者死!」
高大人吩咐,說是吃飽喝足明日交戰,誰也弄不清怎麼竟就變到了今日。
侍衛司安逸太久,這一批從營校到士兵幾乎都不曾正經打過仗。今夜不及防備,倉促應戰本就失了先機,叫襄王精銳一衝,幾乎立時潰不成軍。
校尉一刀劈了個奪命奔逃的潰兵,厲聲呵斥,盡力拖著人起身,身邊竟已沒一個能再握得住刀的。
黑鐵騎兵在夜色裡,沉默著一步步壓進,毫無抵抗地收割人命。
校尉緊閉了眼,要站直等死,忽然聽見鋒利弦聲嗡鳴,胸口一震,睜開眼睛。
為首的黑鐵騎甚至不及防備,當胸一箭,一頭栽落馬下。
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反應的間隙,就在隊伍愕然震驚的一瞬,又有三箭連發。精悍的大宛馬上,三名黑鐵騎叫箭矢穿胸而過,跌在地上。
始終沉默的黑鐵騎騷動一瞬,停在原地。
僅剩的一名頭領勒緊馬韁,胸口起伏幾次,面具後的眼睛牢牢釘在眼前的騎手身上。
校尉回頭,瞬間瞪圓了眼睛,身形晃了晃。他幾乎有些不可置信,臉上湧起些血色,喉嚨滾熱,「少……少將軍!」
雲琅低頭,「你認得我?」
「朔方軍忠捷營,前左前鋒嚴林。」校尉哽咽撲跪在馬下,「見過少將軍!」
雲琅攥了弓身,看著他身上血色,靜了片刻,「可還能戰?」
校尉嘶聲:「能戰!」
「好。」雲琅張弓,緩緩搭箭,「共守。」
御史中丞將大理寺翻了三遍,將雲琅的弓翻了出來,送回了琰王府。
五十年的桑木芯,鐵檀木弰,千捶的熟牛筋。
雲琅弓成滿月,泛著寒芒的箭尖巍然不動,遙遙釘在黑鐵騎僅剩的頭領喉間。
退一步,彼此整頓轉圜,再見再戰。
進一步,索命。
頭領對峙良久,用力一揮手,挾手下疾馳退去,投進夜色。
校尉一晃,「少將軍……」
「回去養傷。」雲琅並不看他,收箭斂弓,「權杖給我,你的人還有能站穩的,我要帶走。」
「屬下能戰!」校尉愴聲:「這不是北疆,是汴梁!」
「還能回去哪兒?端王歿了,屬下撿了條命,逃回了汴梁,混著醉生夢死……如今已是汴梁了!」
校尉嗓音嘶啞,幾乎瀝出血來,「少將軍,屬下的家就在這裡,屬下退不了了。」
夜深風寒,畏縮著的幾個人愣愣看著,聽著校尉絕望嘶吼,一時竟生出些赧然無措。
雲琅凝他良久,將手中勁弓遞過去。
校尉眼中一片赤紅,胸口激烈起伏,怔忡著抬頭。
「我的家也在這裡。」雲琅道:「起來,隨我拒敵。」
校尉狠狠抹去眼中水色,握了雲琅弓弰,攥緊腰刀,掙命起身。
雲琅收了弓,一言不發,策馬越過一地狼藉殘垣。
火光在他背後,捲著烈烈銀甲雪袍,似冰似火,凜冽灼灼。
灼盡了無數膽怯陰私的懦弱念頭。
校尉踉蹌著跟上,隔了幾息,又有人猛然站起身跟上去,握緊了手中的腰刀。
風勁雪寒。
夜風裡漫開血氣,捲著爆竹燃盡的碎皮,叫細碎雪粒打透了,栽進路旁泥濘。
往日繁盛的街景早已冷清,只餘開封府衙役忙碌穿梭,四處救火尋人。臨街勾欄砸毀大半,家家戶戶門窗緊閉,不見光亮不見人影。
汴梁城高牆深,遠在腹地不臨邊境,太久不曾見過戰火。
金水門外,襄王叛軍已盡數收到了訊息,人覆面、馬銜枚,由各處奔襲匯攏,聚在一處。
緊閉著的城門下,數不清的黑色鐵騎。
「滾木雷石!」都虞候守在城樓上,死死咬著牙,「盾牌在前,弓箭在後,聽令齊射!」
殿前司內,藏了不知多少叫蕭朔暗中護下的朔方軍舊部。這一仗沒人聽琰王殿下的,無論家小獨子,盡數豁命壓了上來。
人人死守,無一人肯退。
叛軍多是重甲騎兵,連馬身也披掛甲胄,尋常箭矢破不開五十斤的鐵甲,滾木雷石卻都極有限。
一旦耗盡,若援兵再不至,縱然所有人都死在城上,也守不住這一道薄薄的城門。
箭雨的間隙裡,連勝登上城樓。
「連將軍!」都虞候見他上來,隱約欣喜,「城中情形如何?侍衛司……」
連勝搖了搖頭,沉默著伸手,接過了身旁兵士的長弓。
都虞候怔住。
「我查了十三處侍衛司布防點。」連勝道:「都一戰即潰,有的甚至連交戰的痕跡也沒有……路上見了些逃命的流兵。」
連勝看著城樓下強攻的黑鐵騎,「援軍只怕不會來了。未戰先怯,士氣已竭,沒人能聚攏起這些嚇破膽的殘兵,除非……」
都虞候低聲:「除非什麼?」
「除非……」連勝靜了片刻,苦笑,「若再晚兩三個月就好了。」
都虞候忽然明白了他的話,心底一沉,在廝殺聲裡沉默下來。
若再晚兩三個月,雲琅身上的傷病便能養好大半,再無後顧之憂。
再晚兩三個月,琰王殿下就能想出辦法,轉圜朝堂,徐徐圖之,還他們一個攻無不克的少將軍。
夜色濃深更甚,風捲雪粒撲得人心頭冰涼
「既然援兵來不了……便不指望了。」都虞候道:「不論援兵來不來,我等都半步退不得。」
「此處與燕雲不同,破了金水門,就叫他們進了內城。」都虞候沉聲:「內城可有交戰?」
「有。」連勝道:「殿下正帶人死守右承天門,同他們激戰,我走得急看不清楚,不知少將軍在不在其中。」
兩人心中皆不由自主寒了寒,一時靜默下來。
內城守得最嚴,殿前司寧可錯殺不肯放過,篩子一樣過了六七次,叛軍絕不會出在外面。
是侍衛司內部有人倒戈。
皇上最信任的侍衛司,這些年要錢給錢、要糧給糧,兵強馬壯威風凜凜的禁軍精銳,潰逃的潰逃,叛逆的叛逆,如今只怕已再靠不住半分。
「內城無險可守,一馬平川,我們若攔不住,他們就會直取右承天門。」連勝道:「若與內城叛軍合在一處,就再無人能攔了。」
都虞候緊咬著牙,將無邊寒涼合著熱血嚥下去,奪過身旁兵士手中長槊,轉身下城。
連勝將他一把扯住,沉聲道:「做什麼?」
「金水門不是朔州城,城牆不是照著防攻城建的,若不出城死戰,遲早要被攻破。」都虞候道:「你我的命都是撿的,當年若無殿下,都死透了……今日好歹還一條。」
「要出城拒敵,也該我去!」連勝厲聲:「你是殿前司都虞候!殿下不在,你是此處主將,豈可任意輕離!」
都虞候:「正參領。」
連勝被他叫出昔日朔方軍中軍職,胸口一緊,立在原地。
「你善守城,我擅強攻。」都虞候握緊長槊,「搏一次,就當這是朔方長城……就當這是當年。」
「真想再回去一次。」都虞候低頭笑了笑,「端王爺還在,領著咱們攻無不克,少將軍奇兵突襲,沒有打不贏的仗。」
連勝說不出話,呼吸窒得胸肺生疼,叫風雪裹著,立在原地。
都虞候點了三百輕騎,下了城樓。
雙方力疲休戰的短暫間隙裡,金水門城門緩慢拉開。
黑鐵騎瞬間警醒,正要撲上,守在城樓的將軍斷然厲喝,沉重的滾木雷石鋪天蓋地砸下來。
重甲機動最差,不能硬抗,聽令立即後撤。輕甲騎兵與步兵才一補上來,尚未立穩,便迎上了鋪天蓋地的箭雨。
連勝親持長弓,死守在城頭,箭勢狠得像是飽浸了心頭鮮血。
箭雨之下,殿前司的輕甲兵悍不畏死地迎了上來。
「步兵三一圍重甲,不可戀戰!」都虞候高聲道:「輕騎兵隨我衝鋒!」
黑鐵騎一路不曾遇到這樣強橫的阻力,此時不由自主,陣營竟被硬生生豁開了個口子,一陣混亂。
三百輕甲皆是朔方軍出身,斬慣了戎狄的狼崽子,人人手下狠厲異常,與黑鐵騎撲在一處。
攻城勢頭暫緩下來,連勝霍然回身,將眼底滾熱死死逼回去,「徵調城中壯勇,加固城門,沙袋填豁!城中火油盡數匯攏,引井水上城!」
無險可守,無屏障可依,無援軍可待。
還剩血肉。
叛軍遭遇的第一次激烈衝鋒,主將心驚一瞬,立時重新排布,將重甲騎兵硬頂上來。
兩軍混戰在一處,城上便放不了滾木雷石。重甲兵的甲胄能護全身,只餘雙眼雙手,刀劈不開、槍刺不透,面對只著薄甲的對手,幾乎是單方面的屠殺。
殿前司的兵馬死命拚殺,卻畢竟軍備不足,勢單力薄,又只有區區三百人。
再激烈的戰局,也能靠碾壓的實力差距,將這一股頑抗的力量碾淨。
叛軍將領沉默注視著戰局,緩緩舉起手中長刀,向前斬落。
這是絞殺的手勢,都虞候握緊手中長槊,胸口激烈起伏,用力閉了閉眼。
這三百人,原本便是來送死的。
能攔住多少便攔住多少,能拚上性命殺一個,就少一個人去攻那搖搖欲墜的城。
都虞候手中長槊橫劈,正要下同歸於盡的死戰令,忽然狠狠一悸,盯住濃深夜空中斬出來的一線白光。
白磷火石,承雷令。
雲騎的承雷令。
都虞候眼中迸出難以置信的亮色。
叛軍將領心頭無端一寒,回頭看時,卻已叫一支足以穿金裂石的白羽箭生生穿透。
叛軍將領抬了抬手,滿眼錯愕不及褪去,斃命跌落馬下。
雲琅掛了弓,銀甲映雪一馬當先,帶了身後匯攏的近千侍衛司殘兵,持槍捲入敵陣,一槍挑了尚在驚恐愕然的副將參軍。
都虞候怔望著眼前驚變,一時竟不知是夢是真,喉嚨裡一片激盪血氣,「少將軍!」
雲琅抬眸,目光雪亮,落在他身上。
都虞候眼底狠狠一燙,用力揮了下手中長槊,「兩軍並一,入前鋒列陣,隨少將軍拒敵!」
叛軍再三折將,其餘能主事的又不及照應兼顧,一時亂成一團。
雲琅隨手撿來的長槍,極不趁手,一擊便折了槍尖,索性隨手拋了,勒馬朝城樓上抬頭一望。
連勝牢牢盯著城下情形,迎上雲琅眼中銳芒,撲回去取了殿前司的無鋒重劍。
將作監仿照古劍巨闕製了兩柄劍,看似無刃無鋒,其實都在蘸火藏拙之下,有倒鉤血槽,鋒利無匹。
這兩柄劍,在侍衛司的那一把,曾被拿在暗衛手中,留下了雲琅胸口的那一處沉傷。
雲琅接了城上拋落的寶劍,揚鞭催馬,直入敵陣。
重甲騎兵並非全無破綻,五十斤的重甲,百餘斤的人,加上馬的甲胄、人的兵器,一匹馬要載幾百斤的分量。
大宛馬是最好的戰馬,矯健勇猛,天性好戰通解人意,有汗血寶馬之稱,遠比夯笨的駑馬適合戰場。襄王當初也是為了這個,才煞費苦心,不惜花重金趁亂買去千匹大宛良馬,暗中打造了這支黑鐵騎兵。
可襄王終歸不是沙場戰將,也有一件事並不清楚。
人說好馬不駕轅,不僅是因為大宛馬拉車暴殄天物,更是因為大宛馬能疾奔千里,能馳風掣電,卻天生不善負重,耐力不足。
仗打到現在,這些裹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的重甲騎兵,縱然人尚有餘力,馬卻已支援不住了。
雲琅與都虞候照了個面,持劍橫攔,向下重重一斬。
都虞候陡然醒悟,高聲傳令:「輕甲步兵,三人一隊,斬馬鐮!」
殿前司眾人立即奉令,雲琅匯攏的侍衛司殘兵盡皆能戰,見同伴拿出鐮形彎刀,立時人人照做。
朔方軍長年與戎狄騎兵對峙,早總結出專對付騎兵的兵器。新月形的彎刀照著鐮刀鑄造,刃在內側,不斬人頭,只斷馬腿。
叛軍一陣騷動,隱有退卻之意,禁軍匯攏合圍,兩翼包攏,卻已將這一股鐵騎盡數封死在金水門前。
步兵滾在鮮血浸透的雪地裡,死咬著牙關,以彎刀專斬馬腿,有人跌落便立時三人撲上,掀開盔甲一擊斃命。
馬上騎兵慌亂,要以手中兵器擊殺這些不要命的禁軍,才舉起刀,眼前便叫一道雪亮劍芒劃開茫茫血色。
雲琅棄了馬,身法使到極處,劍光凜冽,只破鐵甲唯一護不住的空處。
劍映寒月,有死無傷。
局勢轉眼逆轉,離城門最近的一股黑鐵騎叫禁軍牢牢咬在門前,竟是連脫身撤退也已不能。
稍遠些的叛軍原本要來救援,竟也叫眼前情形所懾,一時竟不敢輕易上前。
風雪愈烈,最後一個重甲騎兵跌落馬下,雪已大得叫人睜不開眼。
叛軍首領終於不敢再進,鳴金聲起,後隊作前,暫且緩緩退入城中街巷。
連勝下城開門,將浴血的禁軍隊伍迎入城內,又將城門死死閉上。
雲琅殿後,回了馬上,最後一個入城,叫他扶了下馬站定。
人人精疲力竭,身上大小傷痕無數,血跡斑斑,眼裡卻燃著幾乎狂熱的凜凜戰意。
雲琅慢慢掃過一圈,笑了笑,抱拳拱手。
將士熱切,震呼以應。
「今日。」雲琅開口,叫發洩一般的呼聲掩去大半,無奈笑了下,慢慢道:「今日一戰,叛軍挫了銳氣,受驚退去,不會再輕易強攻。」
「此後幾日,叛軍大抵會圍而不攻,切斷內城與外城供給,意圖將我軍拖垮。」雲琅扶了馬背,「休養生息,將城內糧食收到一處,按人頭供給。城內青壯……」
「少將軍。」連勝無奈,「末將還在這兒。」
雲琅看他一眼,微微笑了,「我忘了,連將軍守過的城,比我砍的旗都多。」
他語氣輕鬆,眾人一時再忍不住,一齊哄笑起來。
連勝叫他調侃,一時苦笑連連,假意訓了幾句眾人不可起哄,與都虞候一併將雲琅引入了殿前司內營。
雲琅叫兩人扶著,背後營帳厚重布簾垂落,步勢一沉,嗆出口血,身形跟著墜在了連勝臂間。
連勝在城上盯得仔細,見雲琅戰時不肯開口多說話,便知不好,這才在帳外貿然出言打斷。看見那一口血,心底跟著狠狠一沉,匆忙將雲琅攙住,「少將軍!」
「喊什麼。」雲琅垂眸,聲音低緩:「扶我坐下。」
都虞候不知雲琅具體情形,興奮之意尚未退去,此時叫眼前情形駭得腦中嗡一聲響,慌忙伸手,同連勝一道扶著雲琅坐在榻上。
雲琅胸口血氣湧動,咳了兩聲,慢慢支撐著盤膝,將失控的內力壓下去。
連勝與都虞候對視一眼,急要上前,已有人掀開帳簾進來。
連勝心中焦灼,正要呵斥,忽然瞪大了眼睛,「殿……」
來人扳過雲琅身子,俐落卸了身上銀鎧,抬手抵在雲琅被汗水浸透的脊背上,護持住後心,將人穩穩托住。
雲琅察覺到這隻手也並不算暖,分神聽著身後氣息,蹙了蹙眉,低聲:「蕭朔。」
「專心些,你我都輕鬆。」蕭朔按住他幾處穴位,手上拿捏分寸,攔在雲琅眼前的手動了動,替雲琅拭去額間淋漓汗意。
雲琅只得閉了眼,借助蕭朔的力道,屏息凝神,將逸散的內勁條條理順。
隔了一刻,蕭朔神色微鬆,撤開手。
連勝與都虞候牢牢盯著情形,見狀一喜,上前要說話,被蕭朔以目光止住。
兩人反應都極快,忙閉緊了嘴,施了一禮,退出營帳忙碌去了。
雲琅稍放了些心,扯著蕭朔一併坐在榻上,長舒一口氣仰下去,閉了眼睛。
蕭朔側過頭,看著攤開手腳倒在榻上的雲琅。
雲少將軍眉眼明朗,自有皎皎鋒銳。激戰沾了些血色,幾乎像是一柄染血神兵,寒光凜冽,隱隱出鞘。
蕭朔知他疲累,握了握他的手,「雲琅。」
雲琅勉強睜開眼皮,「又攻城了?」
「……」蕭朔:「不曾。」
「那你叫我做什麼?」雲琅分辨了下,確認了自己拽的是蕭朔沒受傷那隻手,扯了扯,「躺下,睡覺。」
「洗一洗再睡。」蕭朔道:「都是血。」
雲琅心說蕭小王爺可太講究了,想了想臉上沾的血,鬆了手張牙舞爪嚇唬他一通,倒回去自顧自閉了眼。
蕭朔坐了一陣,起身要了些熱水,擰過布巾,替雲琅仔細拭了臉上血跡硝煙。
布巾溫熱舒適,雲琅不自覺貼了下,正埋進蕭朔掌心。
那雙手沒有平日的暖意,雲琅閉了眼睛,在蕭朔因為失血微涼的掌心裡埋了埋,「小王爺。」
蕭朔拾掇慣了雲琅,單手也仍有條不紊,將他扶在榻上,褪了戰袍戰靴,將雙手沾的血跡也仔細拭淨。
雲琅不想叫他費力,偏偏身上力氣已耗得涓滴不剩,此時心神一鬆,竟連動一動手指也極艱難。
「我知你累了。」蕭朔握了握雲琅的手,將他冰涼的手指攏在掌心,「安心,有我。」
雲琅勉力扯了扯嘴角,攏了攏發眩的目光,朝他盡力笑了下。
城內叛軍盡數剿除,文武百官與皇上雖還在宮裡憋著,有金吾衛駐守,總歸出不了亂子。
整個汴梁城能戰的精銳都已被雲琅匯攏,帶進了金水門,合力拒敵,叛軍首戰便被狠狠挫了銳氣,一時也再難重整旗鼓。
雲琅舒坦了,鬆了口氣,「我要睡覺。」
「再等一刻。」蕭朔拿過一併送來的薑湯,「喝了再睡。」
雲琅別過頭,「不喝。」
蕭朔扶住雲琅頸後,攬著雲琅,將人正過來。
雲琅只想睡覺,快被他煩死了,硬生生逼出力氣,扯著薄裘蒙住頭,「不喝不喝不喝不喝……」
「你今日頂風奔襲,冒雪激戰,已有寒氣侵體。」蕭朔吹了吹滾熱薑湯,「坐……」
雲少將軍把自己拿薄裘裹成了個小團,賭著氣骨碌碌滾到榻邊。
蕭朔眼看他滾錯了方向,伸手將人從榻下撈回來,「坐起來。」
雲琅:「……」
蕭朔見他抵死不配合,也不動怒,將雲琅裹著的薄裘剝開,單臂將人攬住,叫他靠在自己剛傷了的左肩上。
雲琅睜著眼睛,被蕭小王爺近在咫尺的傷處封印,一動也不敢動。
蕭朔拿過薑湯,含了一口,貼上雲琅幾乎已淡白的嘴唇,慢慢度過去。
雲琅:「唔?」
「這是你的帥帳,你的舊部隨時會進來。」蕭朔垂眸,「你若不自己喝,我便一口一口這樣餵你。」
雲琅想不通,「他們不也是你的新部嗎?」
蕭朔耳根微熱,神色卻仍鎮定,「先帝給我留了封手書……教會我了些東西。」
雲琅還被方才小王爺那一口餵得意亂神迷,此時聽見他說這個,心裡更愁,「完了完了,我就說有先帝的事……」
蕭朔深吸口氣,闔了闔眼,「少將軍。」
雲琅愁雲慘澹,「少將軍夫人。」
蕭朔:「……」
「餵吧!」雲琅橫了心,決心激將,「有人進來,就說這是少將軍新扛回來的夫人,來省親的,兼餵薑湯。」
蕭朔靜了一刻,「好。」
「……」雲琅:「啊?」
蕭朔含了第二口薑湯,慢慢度給雲琅,又去含第三口。
唇齒廝磨,熱意從薑湯點染到唇畔耳後。雲琅面紅耳赤,堪堪守著一線清明,勉強避開,「慢著……將軍夫人你也肯做?」
蕭朔道:「有何不好?」
雲琅一時也說不出有何不好,張口結舌,看著半點不知自矜身分的琰王殿下。
「你我心意相通。」蕭朔道:「誰歸於誰,並無分別,總歸攜手百年,來世仍做眷侶。」
雲琅受不了蕭小王爺這般直白,心底怦然,紅著臉埋在薑湯裡咕嘟咕嘟吐泡泡。
蕭朔看不慣他拿吃的尋開心,嘆了一聲,將薑湯放在一旁,「罷了。」
雲琅愣愣道:「不喝了?」
「不願喝便不喝了。」蕭朔道:「躺下,我替你暖。」
雲琅心說完了完了將軍夫人如今要侍寢了,話到嘴邊,瞄見蕭朔沉靜眸色,胸口熱意一蕩,終歸沒能說得出。
他素來喜歡開玩笑,嘴上占些便宜,心裡從來不曾當真。蕭朔自然清楚,卻從來都句句回得認真,沒有一句應付了事。
這些年,就在這般玩笑鬥嘴裡,也不知誆了蕭小王爺多少的真心話。
雲琅喉嚨輕動了下,由著蕭朔攬住肩背,仔細避開了蕭朔的傷處,讓他擁著躺在榻上。
拚殺一夜,此時夜色將盡晨光微明,風雪竟也暫歇下來,天開雲霽。
帳外井然有序,正安排防務,人人走動間經過帥帳,都會留意壓低聲音,不驚動了戰後歇息的少將軍與琰王殿下。
「小王爺。」雲琅閉了眼睛,埋進他肩頭衣物,「將軍夫人不好,不威風。」
蕭朔攬著他,聲音低柔輕緩,「想要什麼?」
「小王妃多厲害。」雲琅含混道:「回頭你自己給我弄一個,就王府正妃那個印,你記得嗎?上面還帶著同心結的……」
蕭朔微怔,慢慢撫上雲琅脊背,沒說話。
雲琅皺了皺眉,怕蕭朔又犯了敗興的毛病,事先堵他嘴,「你若要說不合規制……」
「不是。」蕭朔道:「我只當你不喜歡。」
雲琅茫然,「為什麼?」
蕭朔撫了撫雲琅額頂,將雲琅攬近,將身上熱意分過去,慢慢替他推撚背上穴位。
雲琅是上馬能戰的良將,待到改天換日,只憑身上這些戰功,也早該封侯拜將。他原本覺得先帝處置不妥,那一封玉牒,也並沒打算給雲琅再看。
但今日叫雲琅無意點破,才忽然想透。
誰歸於誰,雲琅都是只憑一人一馬就能重振士氣,單人獨騎便能力挽狂瀾的少將軍。
他的少將軍。
蕭朔攏著他,輕聲道:「母妃那枚印隨葬了,待此間事了,給你重做一個。」
雲琅此時已極睏倦,叫蕭朔身上暖意裹著,輕易便被拐走了念頭,打了個呵欠,「要羊脂玉的。」
蕭朔點了點頭,「好。」
雲琅奇思妙想,「再刻個兔子。」
蕭朔:「……」
「還能刻別的嗎?」雲琅埋在他胸口,念念叨叨:「就刻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都不死』……」
蕭朔實在聽不下去,停了推穴,低頭吻住了雲少將軍,將人護進懷間。
雲琅滿意了,舒舒服服讓小王爺親著,沒了動靜。
蕭朔眼看著雲琅沒心沒肺立地睡熟,按了按額頭,將袖中玉牒拿出來,稍一沉吟,還是重新仔細收好,避開傷處將人攬實。
按雲少將軍的打法,只怕不會拖得太久,至多三五日,就會設下誘餌引敵入甕,一戰定鼎勝局。
接下來的幾日,想必都再閒不下來。
大戰間隙,好生休養精神,才能應對之後的局面。
既然雲琅睡得這般安穩……這封玉牒,便也不急著交給御筆用印、明媒正娶的琰王府正妃了。
【第十章】今日一戰,我只聽喊殺聲便恨不能與你並肩
蕭朔是進宮來做什麼的,洪公公看不透,都虞候和連勝看不透,就連皇上預設立場、百般揣摩,只怕也想不明白。
宮變凶險,禍福難料。蕭朔慣了走一步看三步,縱然有九成九的把握,也要為了那一分,將後路替他鋪設妥當。
只要能叫皇上相信雲琅能替他守住當年事,便有可能叫皇上動搖,此時壓上蕭朔的立場,皇上無人可用,為安撫蕭朔,多半會選赦了雲琅死罪。
若今日能將雲琅身上的死罪推了……不論用什麼辦法,縱然明日不幸,蕭小王爺死在這宮變之中,雲琅也再不需王府庇佑。
蕭朔不攔雲琅同死同穴,卻要為了這一分可能,寧肯兵行險著,也要讓雲琅能以少將軍之名去北疆。
蕭朔要保證,縱然琰王今日身死,他的少將軍也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領他的兵、奪他的城。
「少將軍……好軍威。」蕭朔抬手,在雲琅眼尾輕輕一碰,「訓人竟也能將自己訓成這般架式。」
雲琅用力閉上眼睛,將眼底熱意逼回去,惡狠狠威脅,「再說一句。」
蕭朔及時住了口,靜了片刻,又輕聲道:「只是慣了思慮,將事做得周全些,你不必多想。」
雲少將軍不爭氣,又想起來時見蕭朔那一笑,徹底沒了半分軍威,緊閉著眼睛轉了個身。
「知錯了。」蕭朔輕撫他頸後,「如何能哄少將軍消氣?」
「去找你六大爺,叫他赦了我。」雲琅悶聲:「打一仗給你看軍威。」
蕭朔微啞,正要開口,殿外傳來極輕的兩下敲門聲。
「殿下。」隔了一息,洪公公的聲音自門外響起,「文德殿方才派人傳旨,說宗正寺來報,尋著了一封過往宗室玉牒。」
「天章閣閣老與虔國公親自辨認,上用玉璽,是先帝筆跡。」洪公公輕聲道:「玉牒上所載……是前雲麾將軍雲琅。」
雲琅:「……」
蕭朔靜坐著,掌心仍覆著他脖頸,看不清神色。
雲琅方才澎湃的心神漸漸熄了,心情有些複雜,撐坐起來。
兩人忙活半宿,為的無非就是這個,自然猜得到皇上會妥協設法赦他死罪。
死罪並不難免,雲琅只是受親族牽連,若非當年親手燒了豁罪明詔,為換琰王府安寧將性命親手交進了六皇子手中,這罪分明早就該一筆勾銷。
如今皇上既不得已退讓這一步,找個今年高興、大赦天下的藉口,罪便也免乾淨了。
誰也沒想起來……居然還有這個辦法。
雲琅還記著先帝那句「皇后養子」,一時心裡也頗沒底,訥訥:「小王爺。」
蕭朔坐得紋絲不動。
雲琅有點心虛,乾咳一聲,扯扯他袖子,「小皇孫。」
蕭朔坐得一片巍然。
雲琅鼓足勇氣,「大侄……」
蕭朔:「雲琅。」
雲琅當即牢牢閉嘴。
蕭朔深吸口氣,將一把火燒了祖廟的念頭壓下去,按按眉心,起身下榻開門,去接了那一封玉牒。
他也早已忘了此事,更想不到蔡太傅竟當真去找了,此時只覺分外頭痛,蹙緊眉打開看了一眼,卻忽然微怔。
雲琅輩分飄忽不定,頗為緊張,「寫的什麼?」
蕭朔看他一眼,將玉牒合上。
雲琅:「啊?」
蕭小王爺沒有心。雲琅火急火燎,自榻上跳下來,「給我看一眼!怎麼回事,莫非將我寫成端王養孫了?你怎麼還往高舉你這人……」
洪公公及時關了門,看著兩人鬧在一處爭搶那份玉牒,再壓不住笑意,欣然向後退了退。
雲琅蹦著高,眼看便要搶到那一封玉牒,神色忽然微變,鬆開手回過身。
洪公公一愣,「小侯爺,可是出了什麼事?」
蕭朔走到窗邊,將窗戶推開。
宮中仍寧靜,天邊卻一片通明,隱約可見耀眼爆竹焰色。
蕭朔與雲琅對視一眼,神色微沉,「是鼇山的爆竹聲。」
「大抵是我們這位皇上到底沉不住氣,打草驚蛇了……無妨,來得及。」
雲琅道:「我本想著今日在宮裡陪你一天,外頭安排好了,隨時能用。」
雲琅入宮前便已整頓好了殿前司,兩家親兵也並在一處,隨時待命。開封尹早備好了滅火活水、衙役各方守牢,虔國公的私兵也守在了京郊,隨時馳援。
本想有備無患,陰差陽錯,竟碰在了一處。
侍衛司異動,朝臣深夜入宮,終歸還是驚動了虎視眈眈的襄王,竟將宮變提前了整整一日。
此時正好盡數用上。
「不耽擱了,回頭同你說。」雲琅摸過蒙面巾,「你那盔甲穿好,流矢無眼,千萬當心。」
「小侯爺!」洪公公隱約聽明白了情形,心頭一懸,「您不可不披甲,宮中有盔甲,老奴帶您去。」
「不必。」雲琅一笑,「我剛從製衣局過來,一不小心,看見了套上好的雲錦短打,配的薄鐵淬火明光甲。」
雲琅已有了主意,緊了緊腕間袖箭機栝,「蕭朔。」
蕭朔點了點頭,緩聲道:「凡事謹慎,多加小心。」
「話還給你,多加小心。」雲琅笑道:「有件事我沒對你說過……我在御史臺獄,曾做過個夢。」
雲琅:「夢見我穿著那一身雲錦戰袍,去北疆打了一場仗,萬箭穿心,死在了北疆。」
蕭朔眼底光芒一悸,抬頭望他。
「我就剩了一個煙花,本想等到死而無憾的時候,給自己聽個響。」雲琅道:「放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居然有憾,還憾大發了……我惦記一個人,竟連他一眼都沒看見。」
雲琅:「若他在,我說一句疼,他定來哄我。」
「戰事在即。」蕭朔啞聲道:「不說這些。」
「就得說這些,老主簿說了,要說什麼等打完仗回來就把我扛回你府裡當小王妃之類的話,這就叫插旗。」
雲琅飛快含混道:「你聽我說,蕭朔。」
蕭朔叫他握住手,輕攥了下,抬起視線。
「我攀扯你,在刑場胡言亂語,是忽然想通了。」雲琅道:「我若死在你府上,就能有個歸處,半夜還能在你床底下睡覺。」
蕭朔靜了靜,抬頭道:「戰事在即……」
「我知道。」雲琅扯扯嘴角,低聲飛快道:「我今夜調息,又做了那個夢,夢裡有諸多不同。我想過是什麼兆頭,也想同你研究研究,後來見你醒來朝我笑,忽然想透了……蕭朔。」
窗外漆黑,夜色下蟄伏的凶險還尚未顯露,天邊明暗吞吐,雜著爆竹的鳴聲。
雲琅單手一撐,坐在窗沿上。
雲琅看著蕭朔,眼底已是一片刀光劍影的明銳鋒芒,卻又分明映著他的影子,「過來,這次輪到你。」
蕭朔靜看他良久,走過去。
雲琅握住他手臂用力一扯,伸手將蕭朔牢牢抱住,迎著夜風,肆無忌憚地吻他。
蕭朔胸口滾燙熱血轟鳴,氣息一滯,閉上眼睛。
雲少將軍輕薄了琰王殿下,笑意明淨,深深看了蕭朔一眼,再不廢話,擰身扎進了茫茫夜色。
**************
臘月廿九,大儺驅逐疫癘之鬼,焚天香於戶外。
消災祈福,除舊布新
鼇山轟鳴點亮的一刻,文德殿內也跟著一時靜寂。朝臣面面相覷,神色都隱約微變。
皇上用力按了按眉心,深吸口氣,慢慢呼出來。
高繼勳死得突然,蕭朔接掌侍衛司,原本也是此時唯一一條出路。
只是按照原本預計,赦了雲琅以安撫蕭朔,明早再勉勵一番,調動妥當從容安排,一日的時間恰好足夠。
襄王一黨偏偏在今夜點亮鼇山,勢成騎虎,待兵戈一起,再無退路。
「京城情勢與北疆不同,雲琅已多年沒帶過兵,未必能勝,不便執掌兵事。」皇上壓了壓念頭,「宣琰王……來文德殿吧。」
一刻後,琰王披掛入殿,奉了侍衛司銅牌令。
「非常之時,朕信不過旁人。」皇上穿過群臣,親手將蕭朔扶起,「禁軍各處皆已調配妥當,只缺人居中調動,你可有把握?」
「臣不知兵。」蕭朔道:「拚命而已。」
皇上頓了下,神色不變,緩聲道:「朕用人不疑,既用了你,便是信你能替朕剿除逆黨。」
話音未盡,又一聲震耳轟鳴。
方才那一聲在城中,離得尚遠,此時這一響震得地皮像是都跟著顫了一顫,竟彷彿近在咫尺。
窗外夜沉如水,仍靜得彷彿一片風平浪靜,夜風流動,卻飄來隱約炙烤的火藥氣息。
皇上倏而轉身,牢牢盯著窗外,神色驟沉。
蕭朔道:「上朝時,大都過宣德門、端禮門,再入文德門方到文德殿。可要來文德殿最便利的,其實並不是這幾座門。」
眾人面面相覷,對視一眼,臉色都不由變了變。
「情勢有變,臣請兵符。」蕭朔道:「右承天門若破,要毀文德殿,只要一把火。」
他語氣冷淡漠然,與平日無異,說出的話卻已在殿中掀開一片焦躁惶恐。
「你……你如何知道,他們會從右承天門殺進來?」樞密使顫巍巍道:「那裡不是正門,外有護城塹溝,城高牆深,區區叛軍如何進得來……」
「大人。」蕭朔慢慢道,「真正的叛軍,是不會裹挾幾個禁軍嘩變,在寢宮前鬧一場了事的。」
他此言對著樞密使,皇上的臉色卻忽然狠狠一白,沉聲道:「夠了,不必說了!」
蕭朔回身,垂頭拱手。
皇上深深盯他半晌,終歸將侍衛司的腰牌兵符取出來,遞給金吾衛,交在了蕭朔手中。
*****************
汴梁城中,火光四起。
開封尹未著官服,親自帶人撲火滅煙,身上已處處煙灰餘燼,「不可聚在一處,四處照應!敲淨街梆……」
話到一半,一條梁柱燒得毀去大半,當頭劈砸下來。
護衛撲救已來不及,喊劈了嗓子,要捨身撲過去,忽然聽見身後清亮馬嘶。
馬上將領白袍銀甲,掠過殘垣,一槍挑飛了仍烈烈燒著的梁柱,扯著開封尹衣領,拋進護衛群中。
開封尹被人七手八腳匆忙攙扶,倉促站穩,「雲將軍!」
「有勞。」雲琅勒馬,「叛軍在何處?」
開封尹定了定神,「四方都有,朝城西匯攏。方才聽見傳令,要破右承天門。」
雲琅:「百姓如何?」
「依將軍所言,這幾夜淨街宵禁。」開封尹道:「大都在家中,只是有民居燒毀,開封府正設法安置。」
雲琅心中大致有數,點了下頭,勒了勒手中馬韁。
開封尹是文人,不是戰將,能顧到這一步已是極限。如今在阻攔叛軍,與之激戰的,應當是周邊駐紮的禁軍。
禁軍布置他看過一圈,當年端王遺留下來的布防圖,水潑不透,若戰力足夠,叛軍理當束手無策。
若戰力足夠。
雲琅隨手拋了搶來的長槍,解下鞍後繫著的勁弓,握在手裡,凝神將城中各方布置戰力盤過一遍。
宮中忌憚蕭朔,卻又不得不用蕭朔,縱然交出侍衛司,也不會放蕭朔出城。
城中禁軍各自為戰,沒有將領主持,成了遊兵散勇。
「殿前司守在金水門!」開封尹忽然想起一事,上前一步急道:「是琰王留給將軍的部下,將軍若見了他們,便有兵了!」
「不急。」雲琅道:「金水門緊要,不可輕離。」
開封尹一怔,「可是……」
「衛大人斯文些,擦一擦臉。」雲琅朝他一笑,調轉馬頭,「我做將軍,幾時還沒有兵帶了?」
開封尹怔忡立著,不及開口,雲琅已揚鞭催馬,沒入了黑黢黢的夜色。
城中亂成一片,沿街門戶緊閉,越向西走,越見戰後狼藉。
血色刺目,混著硫磺火藥,在風裡熱熱刺著人的嗓子。
花燈碾爛了,毀去大半,破開精緻外膛,亮出一點細弱燭火。
侍衛司叫黑鐵騎兵絞著,一觸即潰,猶有勉力拚殺的,也已不比風中的殘燈好上多少。
「主將都沒有,不如逃命!」有人和著血絕望嘶聲:「打什麼?如何打得過……」
校尉垂著一臂,身上盡是淋漓血色,咬牙低吼:「奉軍令,叛逃者死!」
高大人吩咐,說是吃飽喝足明日交戰,誰也弄不清怎麼竟就變到了今日。
侍衛司安逸太久,這一批從營校到士兵幾乎都不曾正經打過仗。今夜不及防備,倉促應戰本就失了先機,叫襄王精銳一衝,幾乎立時潰不成軍。
校尉一刀劈了個奪命奔逃的潰兵,厲聲呵斥,盡力拖著人起身,身邊竟已沒一個能再握得住刀的。
黑鐵騎兵在夜色裡,沉默著一步步壓進,毫無抵抗地收割人命。
校尉緊閉了眼,要站直等死,忽然聽見鋒利弦聲嗡鳴,胸口一震,睜開眼睛。
為首的黑鐵騎甚至不及防備,當胸一箭,一頭栽落馬下。
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反應的間隙,就在隊伍愕然震驚的一瞬,又有三箭連發。精悍的大宛馬上,三名黑鐵騎叫箭矢穿胸而過,跌在地上。
始終沉默的黑鐵騎騷動一瞬,停在原地。
僅剩的一名頭領勒緊馬韁,胸口起伏幾次,面具後的眼睛牢牢釘在眼前的騎手身上。
校尉回頭,瞬間瞪圓了眼睛,身形晃了晃。他幾乎有些不可置信,臉上湧起些血色,喉嚨滾熱,「少……少將軍!」
雲琅低頭,「你認得我?」
「朔方軍忠捷營,前左前鋒嚴林。」校尉哽咽撲跪在馬下,「見過少將軍!」
雲琅攥了弓身,看著他身上血色,靜了片刻,「可還能戰?」
校尉嘶聲:「能戰!」
「好。」雲琅張弓,緩緩搭箭,「共守。」
御史中丞將大理寺翻了三遍,將雲琅的弓翻了出來,送回了琰王府。
五十年的桑木芯,鐵檀木弰,千捶的熟牛筋。
雲琅弓成滿月,泛著寒芒的箭尖巍然不動,遙遙釘在黑鐵騎僅剩的頭領喉間。
退一步,彼此整頓轉圜,再見再戰。
進一步,索命。
頭領對峙良久,用力一揮手,挾手下疾馳退去,投進夜色。
校尉一晃,「少將軍……」
「回去養傷。」雲琅並不看他,收箭斂弓,「權杖給我,你的人還有能站穩的,我要帶走。」
「屬下能戰!」校尉愴聲:「這不是北疆,是汴梁!」
「還能回去哪兒?端王歿了,屬下撿了條命,逃回了汴梁,混著醉生夢死……如今已是汴梁了!」
校尉嗓音嘶啞,幾乎瀝出血來,「少將軍,屬下的家就在這裡,屬下退不了了。」
夜深風寒,畏縮著的幾個人愣愣看著,聽著校尉絕望嘶吼,一時竟生出些赧然無措。
雲琅凝他良久,將手中勁弓遞過去。
校尉眼中一片赤紅,胸口激烈起伏,怔忡著抬頭。
「我的家也在這裡。」雲琅道:「起來,隨我拒敵。」
校尉狠狠抹去眼中水色,握了雲琅弓弰,攥緊腰刀,掙命起身。
雲琅收了弓,一言不發,策馬越過一地狼藉殘垣。
火光在他背後,捲著烈烈銀甲雪袍,似冰似火,凜冽灼灼。
灼盡了無數膽怯陰私的懦弱念頭。
校尉踉蹌著跟上,隔了幾息,又有人猛然站起身跟上去,握緊了手中的腰刀。
風勁雪寒。
夜風裡漫開血氣,捲著爆竹燃盡的碎皮,叫細碎雪粒打透了,栽進路旁泥濘。
往日繁盛的街景早已冷清,只餘開封府衙役忙碌穿梭,四處救火尋人。臨街勾欄砸毀大半,家家戶戶門窗緊閉,不見光亮不見人影。
汴梁城高牆深,遠在腹地不臨邊境,太久不曾見過戰火。
金水門外,襄王叛軍已盡數收到了訊息,人覆面、馬銜枚,由各處奔襲匯攏,聚在一處。
緊閉著的城門下,數不清的黑色鐵騎。
「滾木雷石!」都虞候守在城樓上,死死咬著牙,「盾牌在前,弓箭在後,聽令齊射!」
殿前司內,藏了不知多少叫蕭朔暗中護下的朔方軍舊部。這一仗沒人聽琰王殿下的,無論家小獨子,盡數豁命壓了上來。
人人死守,無一人肯退。
叛軍多是重甲騎兵,連馬身也披掛甲胄,尋常箭矢破不開五十斤的鐵甲,滾木雷石卻都極有限。
一旦耗盡,若援兵再不至,縱然所有人都死在城上,也守不住這一道薄薄的城門。
箭雨的間隙裡,連勝登上城樓。
「連將軍!」都虞候見他上來,隱約欣喜,「城中情形如何?侍衛司……」
連勝搖了搖頭,沉默著伸手,接過了身旁兵士的長弓。
都虞候怔住。
「我查了十三處侍衛司布防點。」連勝道:「都一戰即潰,有的甚至連交戰的痕跡也沒有……路上見了些逃命的流兵。」
連勝看著城樓下強攻的黑鐵騎,「援軍只怕不會來了。未戰先怯,士氣已竭,沒人能聚攏起這些嚇破膽的殘兵,除非……」
都虞候低聲:「除非什麼?」
「除非……」連勝靜了片刻,苦笑,「若再晚兩三個月就好了。」
都虞候忽然明白了他的話,心底一沉,在廝殺聲裡沉默下來。
若再晚兩三個月,雲琅身上的傷病便能養好大半,再無後顧之憂。
再晚兩三個月,琰王殿下就能想出辦法,轉圜朝堂,徐徐圖之,還他們一個攻無不克的少將軍。
夜色濃深更甚,風捲雪粒撲得人心頭冰涼
「既然援兵來不了……便不指望了。」都虞候道:「不論援兵來不來,我等都半步退不得。」
「此處與燕雲不同,破了金水門,就叫他們進了內城。」都虞候沉聲:「內城可有交戰?」
「有。」連勝道:「殿下正帶人死守右承天門,同他們激戰,我走得急看不清楚,不知少將軍在不在其中。」
兩人心中皆不由自主寒了寒,一時靜默下來。
內城守得最嚴,殿前司寧可錯殺不肯放過,篩子一樣過了六七次,叛軍絕不會出在外面。
是侍衛司內部有人倒戈。
皇上最信任的侍衛司,這些年要錢給錢、要糧給糧,兵強馬壯威風凜凜的禁軍精銳,潰逃的潰逃,叛逆的叛逆,如今只怕已再靠不住半分。
「內城無險可守,一馬平川,我們若攔不住,他們就會直取右承天門。」連勝道:「若與內城叛軍合在一處,就再無人能攔了。」
都虞候緊咬著牙,將無邊寒涼合著熱血嚥下去,奪過身旁兵士手中長槊,轉身下城。
連勝將他一把扯住,沉聲道:「做什麼?」
「金水門不是朔州城,城牆不是照著防攻城建的,若不出城死戰,遲早要被攻破。」都虞候道:「你我的命都是撿的,當年若無殿下,都死透了……今日好歹還一條。」
「要出城拒敵,也該我去!」連勝厲聲:「你是殿前司都虞候!殿下不在,你是此處主將,豈可任意輕離!」
都虞候:「正參領。」
連勝被他叫出昔日朔方軍中軍職,胸口一緊,立在原地。
「你善守城,我擅強攻。」都虞候握緊長槊,「搏一次,就當這是朔方長城……就當這是當年。」
「真想再回去一次。」都虞候低頭笑了笑,「端王爺還在,領著咱們攻無不克,少將軍奇兵突襲,沒有打不贏的仗。」
連勝說不出話,呼吸窒得胸肺生疼,叫風雪裹著,立在原地。
都虞候點了三百輕騎,下了城樓。
雙方力疲休戰的短暫間隙裡,金水門城門緩慢拉開。
黑鐵騎瞬間警醒,正要撲上,守在城樓的將軍斷然厲喝,沉重的滾木雷石鋪天蓋地砸下來。
重甲機動最差,不能硬抗,聽令立即後撤。輕甲騎兵與步兵才一補上來,尚未立穩,便迎上了鋪天蓋地的箭雨。
連勝親持長弓,死守在城頭,箭勢狠得像是飽浸了心頭鮮血。
箭雨之下,殿前司的輕甲兵悍不畏死地迎了上來。
「步兵三一圍重甲,不可戀戰!」都虞候高聲道:「輕騎兵隨我衝鋒!」
黑鐵騎一路不曾遇到這樣強橫的阻力,此時不由自主,陣營竟被硬生生豁開了個口子,一陣混亂。
三百輕甲皆是朔方軍出身,斬慣了戎狄的狼崽子,人人手下狠厲異常,與黑鐵騎撲在一處。
攻城勢頭暫緩下來,連勝霍然回身,將眼底滾熱死死逼回去,「徵調城中壯勇,加固城門,沙袋填豁!城中火油盡數匯攏,引井水上城!」
無險可守,無屏障可依,無援軍可待。
還剩血肉。
叛軍遭遇的第一次激烈衝鋒,主將心驚一瞬,立時重新排布,將重甲騎兵硬頂上來。
兩軍混戰在一處,城上便放不了滾木雷石。重甲兵的甲胄能護全身,只餘雙眼雙手,刀劈不開、槍刺不透,面對只著薄甲的對手,幾乎是單方面的屠殺。
殿前司的兵馬死命拚殺,卻畢竟軍備不足,勢單力薄,又只有區區三百人。
再激烈的戰局,也能靠碾壓的實力差距,將這一股頑抗的力量碾淨。
叛軍將領沉默注視著戰局,緩緩舉起手中長刀,向前斬落。
這是絞殺的手勢,都虞候握緊手中長槊,胸口激烈起伏,用力閉了閉眼。
這三百人,原本便是來送死的。
能攔住多少便攔住多少,能拚上性命殺一個,就少一個人去攻那搖搖欲墜的城。
都虞候手中長槊橫劈,正要下同歸於盡的死戰令,忽然狠狠一悸,盯住濃深夜空中斬出來的一線白光。
白磷火石,承雷令。
雲騎的承雷令。
都虞候眼中迸出難以置信的亮色。
叛軍將領心頭無端一寒,回頭看時,卻已叫一支足以穿金裂石的白羽箭生生穿透。
叛軍將領抬了抬手,滿眼錯愕不及褪去,斃命跌落馬下。
雲琅掛了弓,銀甲映雪一馬當先,帶了身後匯攏的近千侍衛司殘兵,持槍捲入敵陣,一槍挑了尚在驚恐愕然的副將參軍。
都虞候怔望著眼前驚變,一時竟不知是夢是真,喉嚨裡一片激盪血氣,「少將軍!」
雲琅抬眸,目光雪亮,落在他身上。
都虞候眼底狠狠一燙,用力揮了下手中長槊,「兩軍並一,入前鋒列陣,隨少將軍拒敵!」
叛軍再三折將,其餘能主事的又不及照應兼顧,一時亂成一團。
雲琅隨手撿來的長槍,極不趁手,一擊便折了槍尖,索性隨手拋了,勒馬朝城樓上抬頭一望。
連勝牢牢盯著城下情形,迎上雲琅眼中銳芒,撲回去取了殿前司的無鋒重劍。
將作監仿照古劍巨闕製了兩柄劍,看似無刃無鋒,其實都在蘸火藏拙之下,有倒鉤血槽,鋒利無匹。
這兩柄劍,在侍衛司的那一把,曾被拿在暗衛手中,留下了雲琅胸口的那一處沉傷。
雲琅接了城上拋落的寶劍,揚鞭催馬,直入敵陣。
重甲騎兵並非全無破綻,五十斤的重甲,百餘斤的人,加上馬的甲胄、人的兵器,一匹馬要載幾百斤的分量。
大宛馬是最好的戰馬,矯健勇猛,天性好戰通解人意,有汗血寶馬之稱,遠比夯笨的駑馬適合戰場。襄王當初也是為了這個,才煞費苦心,不惜花重金趁亂買去千匹大宛良馬,暗中打造了這支黑鐵騎兵。
可襄王終歸不是沙場戰將,也有一件事並不清楚。
人說好馬不駕轅,不僅是因為大宛馬拉車暴殄天物,更是因為大宛馬能疾奔千里,能馳風掣電,卻天生不善負重,耐力不足。
仗打到現在,這些裹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的重甲騎兵,縱然人尚有餘力,馬卻已支援不住了。
雲琅與都虞候照了個面,持劍橫攔,向下重重一斬。
都虞候陡然醒悟,高聲傳令:「輕甲步兵,三人一隊,斬馬鐮!」
殿前司眾人立即奉令,雲琅匯攏的侍衛司殘兵盡皆能戰,見同伴拿出鐮形彎刀,立時人人照做。
朔方軍長年與戎狄騎兵對峙,早總結出專對付騎兵的兵器。新月形的彎刀照著鐮刀鑄造,刃在內側,不斬人頭,只斷馬腿。
叛軍一陣騷動,隱有退卻之意,禁軍匯攏合圍,兩翼包攏,卻已將這一股鐵騎盡數封死在金水門前。
步兵滾在鮮血浸透的雪地裡,死咬著牙關,以彎刀專斬馬腿,有人跌落便立時三人撲上,掀開盔甲一擊斃命。
馬上騎兵慌亂,要以手中兵器擊殺這些不要命的禁軍,才舉起刀,眼前便叫一道雪亮劍芒劃開茫茫血色。
雲琅棄了馬,身法使到極處,劍光凜冽,只破鐵甲唯一護不住的空處。
劍映寒月,有死無傷。
局勢轉眼逆轉,離城門最近的一股黑鐵騎叫禁軍牢牢咬在門前,竟是連脫身撤退也已不能。
稍遠些的叛軍原本要來救援,竟也叫眼前情形所懾,一時竟不敢輕易上前。
風雪愈烈,最後一個重甲騎兵跌落馬下,雪已大得叫人睜不開眼。
叛軍首領終於不敢再進,鳴金聲起,後隊作前,暫且緩緩退入城中街巷。
連勝下城開門,將浴血的禁軍隊伍迎入城內,又將城門死死閉上。
雲琅殿後,回了馬上,最後一個入城,叫他扶了下馬站定。
人人精疲力竭,身上大小傷痕無數,血跡斑斑,眼裡卻燃著幾乎狂熱的凜凜戰意。
雲琅慢慢掃過一圈,笑了笑,抱拳拱手。
將士熱切,震呼以應。
「今日。」雲琅開口,叫發洩一般的呼聲掩去大半,無奈笑了下,慢慢道:「今日一戰,叛軍挫了銳氣,受驚退去,不會再輕易強攻。」
「此後幾日,叛軍大抵會圍而不攻,切斷內城與外城供給,意圖將我軍拖垮。」雲琅扶了馬背,「休養生息,將城內糧食收到一處,按人頭供給。城內青壯……」
「少將軍。」連勝無奈,「末將還在這兒。」
雲琅看他一眼,微微笑了,「我忘了,連將軍守過的城,比我砍的旗都多。」
他語氣輕鬆,眾人一時再忍不住,一齊哄笑起來。
連勝叫他調侃,一時苦笑連連,假意訓了幾句眾人不可起哄,與都虞候一併將雲琅引入了殿前司內營。
雲琅叫兩人扶著,背後營帳厚重布簾垂落,步勢一沉,嗆出口血,身形跟著墜在了連勝臂間。
連勝在城上盯得仔細,見雲琅戰時不肯開口多說話,便知不好,這才在帳外貿然出言打斷。看見那一口血,心底跟著狠狠一沉,匆忙將雲琅攙住,「少將軍!」
「喊什麼。」雲琅垂眸,聲音低緩:「扶我坐下。」
都虞候不知雲琅具體情形,興奮之意尚未退去,此時叫眼前情形駭得腦中嗡一聲響,慌忙伸手,同連勝一道扶著雲琅坐在榻上。
雲琅胸口血氣湧動,咳了兩聲,慢慢支撐著盤膝,將失控的內力壓下去。
連勝與都虞候對視一眼,急要上前,已有人掀開帳簾進來。
連勝心中焦灼,正要呵斥,忽然瞪大了眼睛,「殿……」
來人扳過雲琅身子,俐落卸了身上銀鎧,抬手抵在雲琅被汗水浸透的脊背上,護持住後心,將人穩穩托住。
雲琅察覺到這隻手也並不算暖,分神聽著身後氣息,蹙了蹙眉,低聲:「蕭朔。」
「專心些,你我都輕鬆。」蕭朔按住他幾處穴位,手上拿捏分寸,攔在雲琅眼前的手動了動,替雲琅拭去額間淋漓汗意。
雲琅只得閉了眼,借助蕭朔的力道,屏息凝神,將逸散的內勁條條理順。
隔了一刻,蕭朔神色微鬆,撤開手。
連勝與都虞候牢牢盯著情形,見狀一喜,上前要說話,被蕭朔以目光止住。
兩人反應都極快,忙閉緊了嘴,施了一禮,退出營帳忙碌去了。
雲琅稍放了些心,扯著蕭朔一併坐在榻上,長舒一口氣仰下去,閉了眼睛。
蕭朔側過頭,看著攤開手腳倒在榻上的雲琅。
雲少將軍眉眼明朗,自有皎皎鋒銳。激戰沾了些血色,幾乎像是一柄染血神兵,寒光凜冽,隱隱出鞘。
蕭朔知他疲累,握了握他的手,「雲琅。」
雲琅勉強睜開眼皮,「又攻城了?」
「……」蕭朔:「不曾。」
「那你叫我做什麼?」雲琅分辨了下,確認了自己拽的是蕭朔沒受傷那隻手,扯了扯,「躺下,睡覺。」
「洗一洗再睡。」蕭朔道:「都是血。」
雲琅心說蕭小王爺可太講究了,想了想臉上沾的血,鬆了手張牙舞爪嚇唬他一通,倒回去自顧自閉了眼。
蕭朔坐了一陣,起身要了些熱水,擰過布巾,替雲琅仔細拭了臉上血跡硝煙。
布巾溫熱舒適,雲琅不自覺貼了下,正埋進蕭朔掌心。
那雙手沒有平日的暖意,雲琅閉了眼睛,在蕭朔因為失血微涼的掌心裡埋了埋,「小王爺。」
蕭朔拾掇慣了雲琅,單手也仍有條不紊,將他扶在榻上,褪了戰袍戰靴,將雙手沾的血跡也仔細拭淨。
雲琅不想叫他費力,偏偏身上力氣已耗得涓滴不剩,此時心神一鬆,竟連動一動手指也極艱難。
「我知你累了。」蕭朔握了握雲琅的手,將他冰涼的手指攏在掌心,「安心,有我。」
雲琅勉力扯了扯嘴角,攏了攏發眩的目光,朝他盡力笑了下。
城內叛軍盡數剿除,文武百官與皇上雖還在宮裡憋著,有金吾衛駐守,總歸出不了亂子。
整個汴梁城能戰的精銳都已被雲琅匯攏,帶進了金水門,合力拒敵,叛軍首戰便被狠狠挫了銳氣,一時也再難重整旗鼓。
雲琅舒坦了,鬆了口氣,「我要睡覺。」
「再等一刻。」蕭朔拿過一併送來的薑湯,「喝了再睡。」
雲琅別過頭,「不喝。」
蕭朔扶住雲琅頸後,攬著雲琅,將人正過來。
雲琅只想睡覺,快被他煩死了,硬生生逼出力氣,扯著薄裘蒙住頭,「不喝不喝不喝不喝……」
「你今日頂風奔襲,冒雪激戰,已有寒氣侵體。」蕭朔吹了吹滾熱薑湯,「坐……」
雲少將軍把自己拿薄裘裹成了個小團,賭著氣骨碌碌滾到榻邊。
蕭朔眼看他滾錯了方向,伸手將人從榻下撈回來,「坐起來。」
雲琅:「……」
蕭朔見他抵死不配合,也不動怒,將雲琅裹著的薄裘剝開,單臂將人攬住,叫他靠在自己剛傷了的左肩上。
雲琅睜著眼睛,被蕭小王爺近在咫尺的傷處封印,一動也不敢動。
蕭朔拿過薑湯,含了一口,貼上雲琅幾乎已淡白的嘴唇,慢慢度過去。
雲琅:「唔?」
「這是你的帥帳,你的舊部隨時會進來。」蕭朔垂眸,「你若不自己喝,我便一口一口這樣餵你。」
雲琅想不通,「他們不也是你的新部嗎?」
蕭朔耳根微熱,神色卻仍鎮定,「先帝給我留了封手書……教會我了些東西。」
雲琅還被方才小王爺那一口餵得意亂神迷,此時聽見他說這個,心裡更愁,「完了完了,我就說有先帝的事……」
蕭朔深吸口氣,闔了闔眼,「少將軍。」
雲琅愁雲慘澹,「少將軍夫人。」
蕭朔:「……」
「餵吧!」雲琅橫了心,決心激將,「有人進來,就說這是少將軍新扛回來的夫人,來省親的,兼餵薑湯。」
蕭朔靜了一刻,「好。」
「……」雲琅:「啊?」
蕭朔含了第二口薑湯,慢慢度給雲琅,又去含第三口。
唇齒廝磨,熱意從薑湯點染到唇畔耳後。雲琅面紅耳赤,堪堪守著一線清明,勉強避開,「慢著……將軍夫人你也肯做?」
蕭朔道:「有何不好?」
雲琅一時也說不出有何不好,張口結舌,看著半點不知自矜身分的琰王殿下。
「你我心意相通。」蕭朔道:「誰歸於誰,並無分別,總歸攜手百年,來世仍做眷侶。」
雲琅受不了蕭小王爺這般直白,心底怦然,紅著臉埋在薑湯裡咕嘟咕嘟吐泡泡。
蕭朔看不慣他拿吃的尋開心,嘆了一聲,將薑湯放在一旁,「罷了。」
雲琅愣愣道:「不喝了?」
「不願喝便不喝了。」蕭朔道:「躺下,我替你暖。」
雲琅心說完了完了將軍夫人如今要侍寢了,話到嘴邊,瞄見蕭朔沉靜眸色,胸口熱意一蕩,終歸沒能說得出。
他素來喜歡開玩笑,嘴上占些便宜,心裡從來不曾當真。蕭朔自然清楚,卻從來都句句回得認真,沒有一句應付了事。
這些年,就在這般玩笑鬥嘴裡,也不知誆了蕭小王爺多少的真心話。
雲琅喉嚨輕動了下,由著蕭朔攬住肩背,仔細避開了蕭朔的傷處,讓他擁著躺在榻上。
拚殺一夜,此時夜色將盡晨光微明,風雪竟也暫歇下來,天開雲霽。
帳外井然有序,正安排防務,人人走動間經過帥帳,都會留意壓低聲音,不驚動了戰後歇息的少將軍與琰王殿下。
「小王爺。」雲琅閉了眼睛,埋進他肩頭衣物,「將軍夫人不好,不威風。」
蕭朔攬著他,聲音低柔輕緩,「想要什麼?」
「小王妃多厲害。」雲琅含混道:「回頭你自己給我弄一個,就王府正妃那個印,你記得嗎?上面還帶著同心結的……」
蕭朔微怔,慢慢撫上雲琅脊背,沒說話。
雲琅皺了皺眉,怕蕭朔又犯了敗興的毛病,事先堵他嘴,「你若要說不合規制……」
「不是。」蕭朔道:「我只當你不喜歡。」
雲琅茫然,「為什麼?」
蕭朔撫了撫雲琅額頂,將雲琅攬近,將身上熱意分過去,慢慢替他推撚背上穴位。
雲琅是上馬能戰的良將,待到改天換日,只憑身上這些戰功,也早該封侯拜將。他原本覺得先帝處置不妥,那一封玉牒,也並沒打算給雲琅再看。
但今日叫雲琅無意點破,才忽然想透。
誰歸於誰,雲琅都是只憑一人一馬就能重振士氣,單人獨騎便能力挽狂瀾的少將軍。
他的少將軍。
蕭朔攏著他,輕聲道:「母妃那枚印隨葬了,待此間事了,給你重做一個。」
雲琅此時已極睏倦,叫蕭朔身上暖意裹著,輕易便被拐走了念頭,打了個呵欠,「要羊脂玉的。」
蕭朔點了點頭,「好。」
雲琅奇思妙想,「再刻個兔子。」
蕭朔:「……」
「還能刻別的嗎?」雲琅埋在他胸口,念念叨叨:「就刻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都不死』……」
蕭朔實在聽不下去,停了推穴,低頭吻住了雲少將軍,將人護進懷間。
雲琅滿意了,舒舒服服讓小王爺親著,沒了動靜。
蕭朔眼看著雲琅沒心沒肺立地睡熟,按了按額頭,將袖中玉牒拿出來,稍一沉吟,還是重新仔細收好,避開傷處將人攬實。
按雲少將軍的打法,只怕不會拖得太久,至多三五日,就會設下誘餌引敵入甕,一戰定鼎勝局。
接下來的幾日,想必都再閒不下來。
大戰間隙,好生休養精神,才能應對之後的局面。
既然雲琅睡得這般安穩……這封玉牒,便也不急著交給御筆用印、明媒正娶的琰王府正妃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