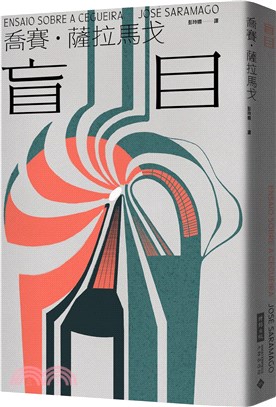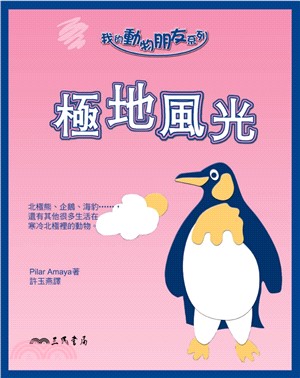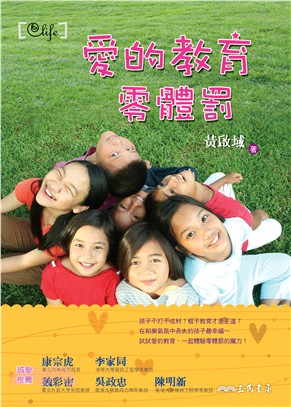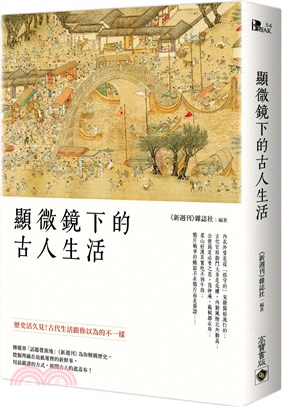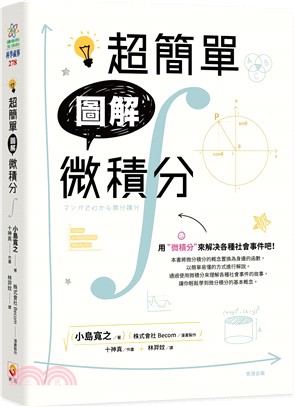盲目(世紀新版)
商品資訊
系列名:大師名作坊
ISBN13:9786263530720
替代書名:Ensaio sobre a cegueira
出版社:時報文化
作者:喬賽‧薩拉馬戈
譯者:彭玲嫻
出版日:2022/11/01
裝訂/頁數:平裝/312頁
規格:21cm*14.8cm*2cm (高/寬/厚)
版次:2
商品簡介
比盲目更黑暗的是人性。
一部對人類處境深刻審視的偉大寓言。
史上唯一葡萄牙語文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喬賽‧薩拉馬戈最受讀者歡迎傳世代表作,世紀新版
某個國家突然失明症肆虐,人民陸續失明,不知從何感染……
看不見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知道對方看不見……
比黑暗更黑暗,無法迴避的人性恐懼。
與《一九八四》《審判》《鼠疫》齊名的世界經典
名列《衛報》評選「史上百大最佳文學作品」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張淑英專文導讀,作家童偉格專文推薦
「他以想像力、同情心和諷刺力支撐的寓言,不斷使我們領悟到一個難以捉摸的現實。」──諾貝爾文學獎授獎獻辭
一名在大馬路上等待紅綠燈的駕駛,突然發現自己看不見,動彈不得的他由路人送回家後,眼見駕駛的妻子也喪失視力,便心生竊意,偷走盲眼駕駛人的車子,隨後小偷路人也失明了。一起失明疾病火速蔓延開來,連眼科醫生也看不見了,整座城市陷入一陣混亂,於是政府下令將所有盲人送進一間精神病院,並派遣武裝士兵看守。「生命在被遺棄時是多麼地脆弱。」那座遭世人遺棄的醫院,駭人聽聞的事件接連爆發,病院內發生的一切都落入醫生太太眼中,她為了照顧失明的丈夫,謊稱自己也是盲人,其實她看得見,卻無法迴避目睹這一切。
失去眼裡的光亮,也就失去了對人的尊重。
盲,是墮落之淵。
出身貧寒、教育程度不高的薩拉馬戈,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的異數。他身受政治迫害,年過五十歲才重回文壇,卻以創作實踐獨力挑戰國家和教會的規訓,無論面對歷史、世俗或神聖權威,一貫抱持破除迷信的「否定」姿態,堅定左翼立場,站在人民群眾這邊,關注政治並保持社會意識,完成他正直的寫作。《盲目》藉由一場不知名瘟疫的始末,讓讀者看見人性未曾曝光且暗不見底的深淵,最令人恐懼的地方,在於那恐怕是自己未曾發現的自己。為了追求公平理性的社會,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認為權力隱藏在看不見的地方,於是虛構出一個又一個幻想寓言,去反抗一切理念和教條,以充滿想像力的故事,為人類現況擔憂,正如書中作家所言:「不要迷失自己,千萬別讓自己迷失。」
「不可能的事物、夢想與幻覺的可能性,就是我的小說的主題。」──喬賽‧薩拉馬戈
若你看得到,就仔細看,
能仔細看,就好好觀察。
也許在盲目的世界中才能彰顯事物的真相。
作者簡介
喬賽‧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1922-2010)
一九二二年生於葡萄牙,曾經操持多種不同行業維持生計,包括技工、技術設計人員與編輯,從一九八○年起,全力投入創作。他的作品包含了戲劇、詩作、短篇故事、非小說與虛構小說,他的小說已經被翻譯為四十餘種語言。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修道院紀事》,讓他首度成為英語出版世界的焦點,《費城詢問報》讚美該部小說:「一部虛構而極富原創性的歷史小說,足以媲美馬奎斯顛峰時期作品」。以《詩人里卡多逝世的那一年》一書獲英國《獨立報》「國外小說創作獎」。一九九一年,出版《耶穌基督的福音》,因其大膽言論觸怒宗教世界而遭受葡萄牙官方干預,憤而自我放逐於西班牙,與妻子琵拉爾居住在蘭薩羅特島。一九九五年出版《盲目》,並於同年獲得葡萄牙文學最高獎項「卡蒙斯文學獎」;一九九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當今全球最知名的葡萄牙作家。另有代表作《所有的名字》、《里斯本圍城史》、《投票記》、《大象的旅程》、《葡萄牙之旅》等著作。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西班牙蘭薩羅特島辭世,享壽八十七歲。
譯者簡介
彭玲嫻
台大外文系畢業,英國諾丁罕大學英語研究,輔大翻譯學研究所肄業,曾任前新聞局《光華畫報雜誌》(今外交部《台灣光華雜誌》)英文編輯、《解讀時代》雜誌主筆,譯有《同名之人》、《凜冬將至》、《大地三部曲》、《黑鳥不哭》、《婚姻生活》、《投票記》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盲目》是一則寓言,諷喻現存的社會。薩拉馬戈藉著人性的『盲點』的譬喻點出人與人在求生存之際共生共榮的關係,從尊重與寬容來彰顯人性與道德,提醒世人省思視覺的『倫理責任』。」──張淑英(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專文導讀
●「醫生太太,毋寧是以獨自的文明,傷逝一般,帶我們預見了集體文明,能如何輕易地崩壞、再次成為殘酷廢墟,而後又建制起文明。」──童偉格(作家),專文推薦
●「再也沒有一本書對民主、對自由、對政治如此地直接介入。」──閻連科,作家
●「《盲目》是薩拉馬戈特別令人震驚和不安的作品。他那極具說服力的想像震撼人心,讓讀者深刻意識到,人類社會竟是如此脆弱、荒誕。這部作品必將永存。」──哈洛‧卜倫,《西方正典》作者、知名文學評論家
●「你很難想到比他更有想像力的小說家,他的書充滿幽默、人性和創造力。」──Margaret Jull Costa,知名英國西葡語譯者
●「在最近幾年出版的任何文字的小說中,《盲目》是最具挑戰性、發人深思與令人亢奮的作品。」──《出版人週刊》
●「既非憤世嫉俗,也非沒有主見,而是……一種誠實地以智慧命名的品質。我們應該感謝它把如此寬廣的世界呈現給讀者。」──《紐約時報書評》
●「一部卓越的作品,一部敢直面我們這個世紀全部恐怖的作品。」──《華盛頓郵報》
●「文學大師的震撼之作。」──《波士頓環球報》
●「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卡夫卡的《審判》以及卡繆的《鼠疫》並駕齊驅。」──《科克斯評論》
●「薩拉馬戈巧妙地展現了人性的脆弱,我們彼此息息相關,同時讓我們的盲目也成倍地放大。」──《書單雜誌》
●「《盲目》拓展了我對人性和小說可能性的看法。」──全國公共廣播電臺
●「薩拉馬戈成功地刻劃了人類的缺陷,創造出當今世界最卓越的一部作品。」──《泰晤士報》
●「薩拉馬戈不斷將當前迫切需求與未來的發展結合。這是他最具啟發性與最樂觀的一面。」──《獨立報》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推薦跋 隱匿之人 文│童偉格
導讀 盲目的明亮,明目的黑暗──薩拉馬戈的《盲目》 文│張淑英
書摘/試閱
綠燈終於亮了,車輛輕快地移動。但有個事實逐漸明朗──並非所有的車輛都同樣敏捷。中間車道的第一輛車停滯不前。一定是哪兒的機械故障了,油門踏板鬆了,排檔卡住了,電路出了問題。要不就是沒油了,這種事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下一批等候穿越馬路的行人看到靜止的車裡,駕駛人在擋風玻璃後揮手。後方車輛發狂也似地猛鳴喇叭,有些駕駛人已經下車來,準備要將這輛動彈不得的車推到一個不會阻礙交通的地方。他們憤怒地捶打緊閉的車窗,車裡的人把頭轉向他們,先轉向一側,又轉向另一側。他很明顯正在喊著什麼,從嘴形看來似乎是一直重複著幾個字。不是一個字,是三個字。等有個人終於把門打開後,才知他說的原來是,我瞎了。
誰會相信。乍看之下,這人的眼睛似乎完好無瑕,虹膜晶瑩閃亮,鞏膜潔白,密實如瓷器。他的雙眼圓睜,臉龐滿佈皺紋,眉毛突然皺了起來,任誰都看得出,這一切顯示著他痛苦難當。突然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所有看得到的一切都掩蓋在他緊握的拳頭之後,彷彿他極力想把他所捕捉的最後一幅影像留在腦中,那便是號誌燈上一枚渾圓的紅光。我瞎了,我瞎了。人們攙他下車,他絕望地複誦相同的字眼,如泉湧的淚映得他自稱已死的雙眼更加晶亮。有時就是有這種事,會過去的,你看著好了,有時是神經的問題,一個女人說。燈號又變了,一些多事的路人聚在四周,後方的駕駛人不知青紅皂白,只當是一般事故,撞壞了車燈或撞凹了擋泥板之類的,壓根兒不該引起這番騷動,因而抗議起來。叫警察來吧,他們喊著,把這糟老頭兒弄開,別擋路。拜託,瞎了眼的人懇求,誰帶我回家吧。認為可能是神經問題的女人主張該叫救護車來,把這可憐人送到醫院去。但盲人拒絕接受,沒有這個必要,他只希望有人能陪他到他家樓下大門口。我家就在附近,送我回家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忙。那車子怎麼辦,有人問。另一個聲音回答,鑰匙還插在裡面,就把車開到人行道上吧。不用,又有第三個聲音插嘴,我來處理車子,陪這人回家。贊同的聲音嗡嗡響起。盲人感覺到有人挽住他的手臂。來,跟我來。與方才相同的聲音在對他說話。一夥人緩緩把他弄上前座,替他繫好安全帶。我看不到,看不到,他咕噥著,淚仍婆娑。告訴我你住哪裡,那人問他。車窗外有貪婪的臉龐在窺視,熱切地想探得些消息。盲人把手舉在眼前比劃。什麼也看不到,就像是陷在霧中,或是掉進了渾濁的海裡。但瞎眼不是這樣的,另一人說,他們說盲人看到的是一片漆黑。但我看到的都是白的,那位太太可能說得對,可能就是神經的問題,都是神經害的。不用跟我講這些,這件事很不幸,的確不幸,拜託告訴我你住在哪裡。這時引擎發動了。失明似乎同時也損傷了他的記性,他期期艾艾道出住址。他說,我不知該說什麼來感謝你。另一人便回答,別多想了,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誰也不知我們會碰上什麼事。你說得對,今早我出門時,誰想得到會發生這等可怕的事。車仍靜止,盲人很困惑。我們為什麼不動,他問。現在是紅燈,另一人回答。自此開始,他再也不知何時是紅燈了。
盲人的家果如他所說,就在附近,但人行道塞滿了車,無處停放,不得不在附近小路另覓停車位。小路裡人行道狹窄,乘客那側的車身距牆僅有一隻手掌寬。為了不用擠過煞車桿和方向盤,難受地從乘客座爬到駕駛座,盲人只有在停好車前先下車。孤伶伶被遺棄在路中央,感受著腳下路面晃動,他努力想壓抑體內奔湧的著慌。他的手驚惶地在面前揮動,彷彿是在自己描述的那片渾濁汪洋中泅泳,而他的嘴已張開,就要出聲呼救,但他終於感覺到另一人的手溫柔地碰觸他的臂膀。別緊張,我牽著你了。兩人在人行道上緩緩行走,唯恐失足。盲人拖著腳步,卻因此被不平的路面絆得踉蹌。耐心點,快到了,另一人小聲地說。不一會兒,他又問,你家裡有沒有人可以照顧你。盲人回答,我不知道,我太太要下班才會回家。今天我提早出門,反而碰上這種事。你看著吧,這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我從沒聽說過有人突然失明的。何況我從前還自誇我連眼鏡都不用戴。你等著看,一定沒事的。兩人走到門前,住在附近的兩個婦人看見自己的鄰居讓人攙著手臂走路,好奇地注視,但誰也沒想到問一聲,你眼裡進了東西嗎。她們不曾想到,即便想到,盲人也不會回答,是的,進了東西,進了渾濁的海。進了大樓,盲人說,真感謝你,很抱歉給你添了這許多麻煩,我現在自己能應付了。不用道歉,我陪你上樓,就這麼把你丟在這兒我會於心不安。兩人艱難地擠進小小的電梯。你住幾樓。三樓,你無法想像我有多感激。別謝我,今天是你碰上困難。對,你說得對,說不定明天就是你。電梯停頓,兩人走出去。要不要我幫你開門。多謝你,這個我可以自己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小串鑰匙,一一摸索鋸齒狀的邊緣。他說,肯定是這支,然後用左手指尖摸索鑰匙孔,試圖開門。不是這支。我看看,我幫你。試到第三次時,門開了。盲人向屋裡喊,你在嗎。沒人回答,於是他說,我就說吧,她還沒回來。他伸長了手,摸索著穿過走廊,一會兒又小心翼翼回來,估量著另一人可能的所在位置,臉朝著他說,我該如何感謝你。小事一樁,別謝我。雪中送炭的好心人又加了一句,要不要我幫忙你安頓安頓,陪你等你太太回家。這番熱心忽然讓盲人起了疑。他當然不要請個素昧平生的人進屋來,天知道他此刻是否正算計著如何制伏這個手無寸鐵的可憐盲人,把他五花大綁,封了嘴,洗劫一切貴重物品。不用了,別麻煩,他說,我很好。他一面緩緩關門,一面叨叨念著,不用,不用。
聽見電梯下降的聲音,盲人鬆了一口氣。他忘了自己的處境,機械性地打開窺視孔蓋向外看。窺視孔的另一方彷彿有堵白牆。他感覺得到窺視孔的金屬框抵著他的眉,睫毛掃過小小的玻璃,但他望不出去,無法穿透的白掩蓋了一切。他知道他在自己家裡,他認得那氣味、那情調、那寂靜。他可以憑著觸感、憑著手指的輕撫,分辨出屋裡的家具和物件。但同時一切又彷彿消融入一種奇怪的次元,沒有方向,沒有參考點,沒有南北,沒有上下。他和多數人一樣,童年時曾假扮盲人以為遊戲。閉上雙眼五分鐘後,他就肯定失明固然無疑是種可怖的苦楚,但倘若這不幸的可憐人仍保有足夠的記憶,不只是顏色的記憶,還有形狀與平面、樣式與外表,那麼失明到底還是可以忍受的。前提自然是此人並非天生眼盲。他的推論甚至深遠到認為盲人所置身的黑暗不過就是沒有了光,而所謂的盲是一種遮掩了事物外型的東西,覆蓋在黑紗之下的一切是完好無缺的。然而如今卻是相反的,他驟然落入如此明亮而徹底的渾白之中。這白不是吸收,而是吞噬了所有的色彩、事物、所有的存在,因此一切又加倍地不可見。
他往客廳的方向移動,小心翼翼,手沿牆壁遲疑地摸索,並不預期會碰上任何東西,但還是意外把一只插了花的瓶子砸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全不記得有這麼一只花瓶,也或者是他妻子在出門上班前把花瓶擱在這兒,打算稍後再尋找更合適的地方來安置的。他彎下身估量損失有多嚴重。水潑了一地,淹漫在光滑的地板上。他想撿起花,卻忘了破碎的玻璃。一個碎片戳入他的手指,疼痛中,無助的淚水孩子氣地湧了滿眶。被渾白遮蔽視線的他置身於自己家的中央,夜幕緩緩低垂,屋裡漸趨昏暗。他緊握著花,感覺著鮮血流下,他扭著身,從口袋裡掏出手帕,盡可能妥善地纏裹在手指上,然後跌跌撞撞、笨手笨腳地摸索,繞著家具前進,小心翼翼地邁步,唯恐被地毯絆倒。好不容易來到平日和妻子坐著看電視的沙發。他坐下來,花擱在腿上,極其小心地解開手帕。摸起來黏膩的血令他憂心。他的血變成一種沒有顏色的黏稠物質,一種陌生而卻又屬於他的東西,像自己加諸於自己身上的威脅。他想這必定是由於自己看不到的緣故。他用沒有受傷的那隻手,緩緩地、輕輕地摸索,尋找插入手指的碎片。碎片尖利,像支小小的匕首。他把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併攏,抽出碎片,重新用手帕包裹受傷的手指,這回纏得緊緊的,以便止血,然後虛弱疲憊地靠在沙發上。一分鐘後,由於處於某種痛苦或絕望之中,身體在神經理當保持警醒與緊繃的時刻,採取了極其尋常的棄守策略,一股疲憊襲了上來。其實較像是睏倦而非真的疲憊,但也同樣沉重。他旋即夢見自己在假裝眼盲,夢見自己永恆地閉眼睜眼,回回都宛如遠行歸鄉,發現他所認識的世界裡,所有的色彩與形狀都堅定不移地等著他。在這份鼓舞人心的確定之下,他卻意識著無常隱隱糾纏。或許這是個誑人的夢,一個遲早終將醒轉,卻不知眼前橫陳著何種真相的夢。如果隨後二字也適用於疲憊只維持數秒而意識已落入即將醒轉的半機警狀態之時,他隨後開始認真思索耽溺於這種猶疑不決的狀態是否明智。我要醒嗎,不醒嗎,要醒嗎,不醒嗎。不得不冒險一試的時刻終會來到。我的膝上擱著花,雙眼緊閉猶如怯於睜開,究竟是在做什麼。你膝上擱著花睡在這裡,究竟是做什麼,妻子問他。
她沒有等他回答,逕自動手撿拾花瓶碎片,擦乾地板,咕噥著流露她無意掩飾的惱怒。你大可以自己收拾這一團混亂,別當事不干己似地呼呼大睡。他不發一語,把雙眼保護在緊閉的眼皮之後。突然一個思緒使他激動起來。如果我現在睜開眼睛呢,他自問。焦躁的希望攫住了他。女人近前來,注意到了血跡斑斑的手帕,憤怒轉瞬消失。可憐的傢伙,怎麼回事。她一面憐惜地問,一面解開急就章的繃帶。他用盡渾身的力氣,但願見到妻子跪在他跟前,就在他知道她在的那個地方,他睜開雙眼。終於醒了,我的瞌睡蟲,她微笑著說。一陣靜默。他說,我瞎了,我看不到。女人失去了耐性。別玩這種蠢遊戲,有些事情不能開玩笑。我多麼希望這是玩笑,但我真的瞎了,什麼也看不見。拜託,別嚇我,你看我,看著我,我在這裡,燈亮了。我知道你在那裡,我聽得見你的聲音,摸得到你,我可以想像你開了燈,但我瞎了。她開始哭泣,摟住他。不是真的,告訴我不是真的。花兒滑落到地板上,落在沾血的手帕上,受傷的手指重新開始淌血。他彷彿但願用其他的字眼來表達似地,喃喃地說,我最不擔心的就是那個,我的眼中什麼都是白的。他露出悲傷的微笑。女人在他身旁坐下,緊緊擁他,親吻他的額頭、臉頰,柔柔親吻眼睛。會過去的,你看著好了,你沒生過病,沒有人突然之間失明的。有可能。也許你可以告訴我這是怎麼發生的,是什麼時候,在哪兒發生的,當時感覺如何,不,等等,第一要務是找個眼睛專家請教請教,你知道什麼醫生嗎。我不知道,我們兩個都沒戴眼鏡。如果我帶你去醫院,大概不會有治療失明的急診。你說得對,不如直接找個醫生。我查查電話簿,找個附近的醫生。她站起身,仍繼續發問。你有察覺什麼異狀嗎。沒有,他回答。注意,我要關燈了,你可以告訴我,好。什麼也沒有。什麼叫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我還是看到一片白,就好像沒有夜晚一樣。
他聽得到妻子快速翻著電話簿,聽見她吸著鼻子忍住淚水,嘆息,最後說,這個應該可以,希望他願意見我們。她撥了電話,詢問那兒是不是診所,醫師在不在,她能不能和醫師說說話。不,不,醫師不認得我,我有很急的狀況,求求你,我瞭解,那我把情況告訴你,但求求你把我的話轉告醫師,是這樣的,我先生突然瞎了,對,對,突然之間,不,不,他不是醫師的病人,我先生沒戴眼鏡,從沒戴過,對,他視力很好,和我一樣,我的視力也好得不得了,啊,太謝謝你了,我可以等,我可以等,醫師,對,突然之間,他說什麼都變白的,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還沒來得及問他,我才剛到家,他就這樣了,要不要我問問他,啊,我太感激您了,醫師,我們馬上去,馬上就去。盲人站起來。等等,他妻子說,我先處理一下那根手指。她消失了一會兒,回來時帶著一瓶雙氧水、一瓶碘酒、棉花和一盒膏藥。她一面替他包紮,一面問,你把車停在哪兒了。突然間她質問起他,以你的情況不可能自己開車,或者事情發生時你已經回家了。不,是在街上,我在紅燈前停下來,有個人送我回家,車子停在隔壁街上。好吧,我們下樓去,我去找車,你在門口等我,鑰匙放在哪裡。我不知道,他沒還我。誰沒還你。送我回家的那個人,一個男的。他一定放在哪兒了,我找找看。不用找了,他沒進屋來。但鑰匙總該在什麼地方吧。可能他忘了,一不小心帶走了。運氣可真好。用你的鑰匙吧,回來再找。對,走吧,牽我的手。盲人說,如果一輩子都要這樣,還不如死了算了。拜託,別說傻話,事情已經夠糟了。失明的人是我,不是你,你不瞭解這感覺。醫生會有辦法治好的,你等著看好了。我會等。
(待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