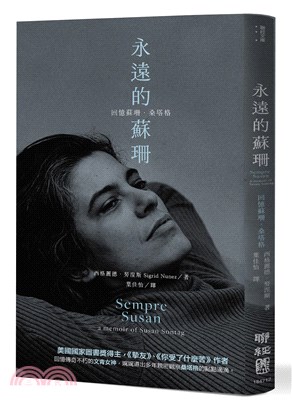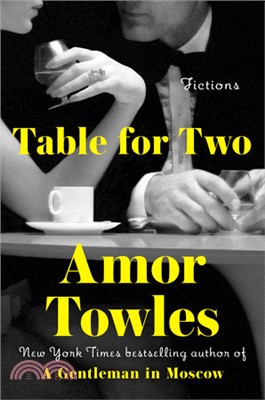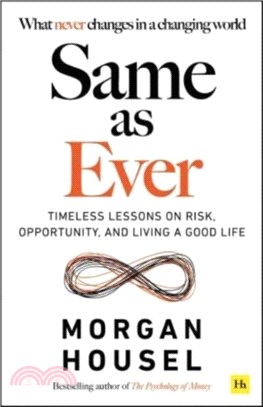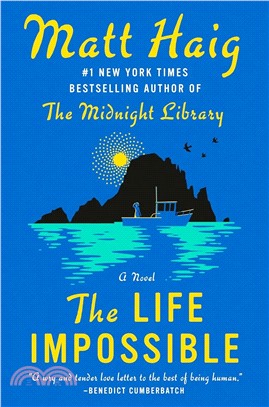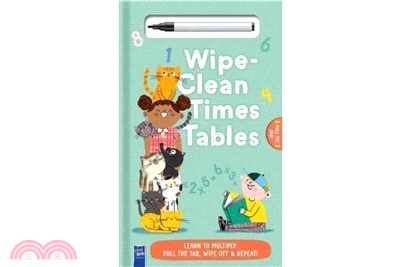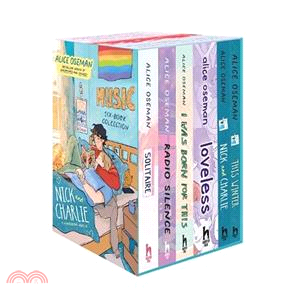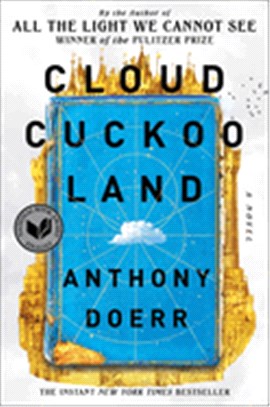永遠的蘇珊:回憶蘇珊.桑塔格
商品資訊
系列名:聯經文庫
ISBN13:9789570869651
替代書名:Sempre Susan: a memoir of Susan Sontag
出版社:聯經
作者:西格麗德.努涅斯
譯者:葉佳怡
出版日:2023/06/22
裝訂/頁數:平裝/248頁
規格:19cm*12.8cm*1.3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國際知名作家書寫傳奇不朽的文青女神──
回憶寫作中的代表之作
呈現更「蘇珊」的人性面向
一個躁動不安、才華洋溢的靈魂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摯友》、《你受了什麼苦》作者──西格麗德.努涅斯
懷抱著愛與敬意,記錄桑塔格的特立獨行
寫下兩人既親密又糾結的點點滴滴
這些年來,我見過或聽說許多人曾表示,他們是在年輕時讀了蘇珊.桑塔格的作品才想成為作家,而且這種人多到驚人。
──西格麗德.努涅斯
那年,傳奇大作家43歲,而她25歲。
努涅斯第一次見到桑塔格時還只是一位胸懷抱負的青年作家,而蘇珊已是文壇傳奇人物,以她的論戰文章、前衛的個人風格聞名全球。不久後,桑塔格將努涅斯介紹給她兒子──作家大衛.里夫,兩人開始約會。之後,努涅斯搬進里夫和桑塔格合住的公寓。如她寫道:
我們三人住在一起——蘇珊、她的兒子,還有我——這真的是個好主意嗎?難道大衛跟我不該自己找個地方住嗎?她說她找不到我們不能住在一起的理由,就算大衛跟我打算生孩子也一樣。若有必要,她說,她很樂意撫養我們所有人。當我表達疑慮時,她說:「別這麼保守。誰說我們一定要活得跟別人一樣?」
那些年,待在罹癌癒後的桑塔格身旁,努涅斯見證了當時眾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最風光的、最私密的、當然也有最怨懟的事。面對約會對象的母親、寫作前輩、同為聰明有想法的女性,她們之間除了良性的互動,亦少不了緊繃又糾結的時刻。如今努涅斯已是國際知名的小說家,在桑塔格過世後,她將這段深具意義的過往撰寫成書,回顧親身相處的傳奇人物,並獻上她深深的愛。
關於桑塔格,努涅斯的回憶包括:
.名字啊︒蘇珊向我坦承,獲得這樣一個無聊又平凡的名字始終讓她開心不起來。「妳看起來不像是叫蘇珊的人」,她會模仿那些對自己這麼說的人。
.某次跟她共進午餐,我意識到回去工作會遲到時,立刻從桌邊跳了起來,她態度訕笑,「坐下!妳不需要那麼準時。別活得那麼卑微。」卑微是她最喜歡講的詞彙之一。
.她的不安全感究竟跟性別有多少關係,我們無從得知。但想到這個驕傲、聰明又有野心的女人成長於女性解放的年代之前,以及她在日常生活中得面對多少的偏見,任何人都能想像她一路以來受過不少屈辱。
.你們那裡到底是什麼狀況?我記得有個朋友笑著說,「所有人都想像過各種最不道德的情節,但其實你們那裡的狀況很典型:占有欲強的控制狂母親,還有充滿罪惡感的兒子。」
國內外好評推薦
★ 關於桑塔格,寫得最好的書寫。
──艾德蒙.懷特|作家
★ 桑塔格目空一切,缺乏安全感,對美和愛毫無招架之力,卻又強烈不願妥協,不過,正如努涅斯在結尾處暗示的,她肯定是年輕作家所能遇到的最好的老師。
──《出版者周刊》
★ 在「我認識桑塔格」類型書寫之中,獨樹一格的回憶傑作。
──A.O. 史考特|《紐約時報書評》
★ 優雅、懷抱敬意、卻又令人疼痛的坦誠。
──《Kirkus書評》
★ 以不偏不倚的幽默、富有情感的敘述,詳盡又入微的觀察,道出公眾人物私下那複雜又矛盾的那一面。
──莉迪亞.戴維斯|作家、譯者
★ 桑塔格已經成為一種形象,但是這本小書讓我們看見桑塔格作為一個人。但是什麼是人呢,所謂的「人」並不一定是一種本質深刻的描述,而她痛很冷天氣、痛恨小提包、痛恨教書。這些瑣碎的事實儘管不能形成一種結構,然而或許人就是被這些片段所驅動,然後成為人。
──汪正翔|攝影師、作家
★ 哭有時,笑有時,哀悼有時。追憶蘇珊・桑塔格,也似如她本身一樣,無法一言以蔽之,縱使這本小書只是由短短兩年的時光切片所構成,卻依舊反射出萬千形象——那是她思想與論著之外,或許可以稱之為「心」的東西。
──盛浩偉|作家
汪正翔|攝影師、作家
柯裕棻|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作家
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盛浩偉|作家
蔣亞妮|作家
感動推薦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
生長在紐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巴拿馬華人。大學就讀巴納德學院,之後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藝術碩士(MFA)。畢業後陸續擔任《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巴黎評論》、《紐約客》等雜誌的撰稿人,並於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波士頓大學等校任教,更曾在多所大專院校擔任訪問或駐校作家。作品收錄於多本選集中,包括手推車獎選集與美籍華人文學選。曾獲2019美國最佳短篇故事獎、懷丁作家獎、羅馬文學獎、柏林獎學金。
近年代表作《摯友》獲得2018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殊榮,更入圍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法國費米娜獎、法國最佳外國圖書獎決選。現居紐約。
譯者簡介
葉佳怡
台北木柵人,曾為《聯合文學》雜誌主編,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長篇小說《聲音與憤怒》、《我彌留之際》、《激情》、《沼澤女孩》、《消失的他們》;短篇小說集《恐怖老年性愛》、《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人類學作品《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圖像小說《歡樂之家》等。
目次
.眾人的桑塔格,與她的蘇珊|盛浩偉
書摘/試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參加作家駐村活動。因為一個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的理由,我必須延後抵達的日期。我擔心遲到會惹人不悅,但蘇珊堅持那不是件壞事。「無論做什麼,打從一開始就打破規則準沒錯。」對她來說,遲到就是她的規則。「我唯一會擔心遲到的場合,只有搭飛機和看歌劇。」就算人們抱怨老是得等她,她也毫無歉意。「我就想,如果大家不夠聰明,不懂帶點什麼來讀的話……」(但若真有人如她一般通透這番道理,搞得她必須等對方時,她又不高興了。)
我對準時抱持一絲不苟的態度,這點讓她很受不了。某次跟她共進午餐,我意識到回去工作會遲到時,立刻從桌邊跳了起來,她態度訕笑,「坐下!妳不需要那麼準時。別活得那麼卑微。」卑微是她最喜歡講的詞彙之一。
所謂例外主義:我們三人住在一起——蘇珊、她的兒子,還有我——這真的是個好主意嗎?難道大衛跟我不該自己找個地方住嗎?她說她找不到我們不能住在一起的理由,就算大衛跟我打算生孩子也一樣。若有必要,她說,她很樂意撫養我們所有人。當我表達疑慮時,她說:「別這麼保守。誰說我們一定要活得跟別人一樣?」
(有一次,在聖馬克廣場上,她指向兩名舉止古怪的女子,其中一位是中年婦女,另一位已邁入老年,她們穿得像吉普賽人,還留著一頭飄逸灰髮。「老波西米亞人,」她說。然後又打趣地說,「這就是我們三十年後的樣子。」超過三十年過去了。她死了,現在也沒有波希米亞人了。)
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四十三歲,但在我看來非常老。部分原因是我當時二十五歲,在那個年紀,任何超過四十歲的人都讓我覺得很老。但其實也是因為當時她剛結束手段激進的乳房切除手術,身體正在恢復。(這裡她也打破了一條規則:她拒絕接受醫院方建議的復健運動時,一名同情她的護理師在她耳邊悄聲說,「哈皮.洛克斐勒 也不肯做。」)她的膚色蠟黃,而她的頭髮——很多人覺得她是刻意把黑髮中的部分髮絲漂白,這點總讓我迷惘,因為只有那些白髮是她的真實髮色,而且應該一看就知道才對。(是有名美髮師建議留下一部分不染,看起來才不會那麼假。)化療讓她的頭髮輕薄不少,卻沒有完全帶走那頭豐厚到驚人的黑髮,只是長回來的大多是白髮或灰髮。
所以,奇怪的是:我們剛見面時,她看起來比我認識她時實際年齡還要老。隨著她逐漸恢復健康,她看起來愈來愈年輕,而等到她決定染髮後,她看起來就更年輕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距離我讀完哥倫比亞大學的創意寫作學院將近一年。我住的地方在西106街,蘇珊就住在106街和河岸大道的轉角。她在病弱期間累積了大量未回覆的信件,正打算開始處理,所以要求朋友推薦可以幫忙的人,那些朋友是《紐約書評》 的編輯。在大學畢業準備讀研究所期間,我曾在那間雜誌社做過編輯助理。那些編輯知道我會打字,而且就住附近,所以建議她打給我。我當時想打的正是這種零工:不太會干擾我寫作的工作。
我去到河岸大道340號的第一天,天氣晴朗,整間公寓——那是間有許多巨大窗戶的頂樓公寓——明亮的刺眼。我們在蘇珊的臥室工作。我坐在她的書桌前用她那台龐大的IBM Selectric打字機打字,她則在一旁說出要我打下的內容,同時來回踱步或躺在床上。那個房間就跟公寓的其他空間一樣,裝潢非常簡樸,白色的牆面上什麼都沒有。正如她後來解釋,因為這是工作的地方,她想要儘可能處在白色的環境中,也希望儘量確保其中不要有書。我不記得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的照片(事實上,在那間公寓中,我無法回想起任何這類照片有被展示出來);相反的,那裡有幾張黑白照(就像出版社準備的公關資料袋中會附的那種照片),照片中是她的文學英雄:普魯斯特、王爾德、安托南(她才剛編完他的一部選集)、華特.班雅明。公寓的其他地方有幾張老電影明星的照片,而且都是著名黑白老電影中的定格畫面。(根據我的回憶,這些照片之前是紐約客電影院 的大廳的裝飾品,那間專門放老片的電影院位於88街和百老匯大道的交叉口。)
她穿著一件寬鬆的套頭衫、牛仔褲,還有胡志明輪胎橡膠製的夾腳拖鞋 ,那雙拖鞋我想應該是她某次去北越旅行帶回來的。因為癌症的關係,她試圖戒菸(她會嘗試,然後失敗,然後再嘗試,一次又一次)。她會一次吃掉一整罐炸玉米粒,同時從一加侖裝塑膠桶中大口大口狂喝水。
信件總是多到令人卻步,我們得花上好幾小時處理,但我們的進度之所以慢到如此荒謬的程度,是因為電話一直響起,而且她每次都會接起來閒聊(有幾次是真的聊了好一陣子),而我就是坐在一邊等她說完,同時當然也在聽她聊天,偶爾拍拍她兒子那條總愛討人關注的巨型愛斯基摩犬。打來的人大多是我聽過的名字。我逐漸發現大家聽說她罹癌時的反應讓她很受不了。(不過當時我還不知道,她已經在整理一些想法,準備之後寫成〈疾病的隱喻〉。)我記得她在提起癌症時,對著電話另一頭的人說那是一種「專橫的疾病。」我還聽她對好幾個人提到,萊昂內爾.特里林 和漢娜.鄂蘭 的死讓她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她提到有人說特里林難怪會癌症,畢竟他應該已經多年沒幹過他老婆了,她對此說法感到憤慨。(「還是學院裡的人說的話!」)她很不想承認,但最終還是勇敢地坦承:當她得知自己罹癌,首先出現的想法之一是,「我的性生活不夠頻繁嗎?」
有一次打電話來的是她兒子。大衛比我小一歲,當時剛從安默斯特學院 輟學沒多久,最近才回到學校讀書。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大二學生,在普林斯頓那邊有個住處,但每星期有大半時間都跟母親住在一起。他的臥室(很快就要變成我們的臥室)就在她的臥室旁邊。
工作讓她覺得無聊。我們才剛處理完幾封信,她就提議可以休息吃個午餐。我跟著她走到公寓另一頭,沿途經過擺滿書的走廊和用餐區,我讚嘆地看著用餐區那張優雅的木製長桌,以及搭配的木製長凳(她告訴我,那是一張老舊的法國農舍長桌),桌子後方的牆面掛著一張經典的好利獲得牌打字機 海報(「和火車一樣快」那張)。餐桌上通常擺滿書籍和紙張,真正要吃飯則大多是在廚房,用的是一張被人漆成深藍色的木製流理台桌。
她拿了金寶牌的蘑菇濃湯來加熱,我坐在台桌前高腳凳上感到很不自在。那罐湯再搭配一罐牛奶後足夠給兩個人喝。她很好聊,這點讓我驚訝。我已經習慣了《紐約書評》公司內上下分明的關係,那裡的編輯從不跟員工聊天。就在那天,我得知這間公寓的前任租客是她的朋友賈斯珀.瓊斯 ,幾年前,當約翰斯決定搬走時,蘇珊承接了他的租約。可惜的是,她不認為自己有辦法繼續待下去,因為這棟大樓的屋主想要自己住這間公寓。蘇珊想繼續住的理由很明顯:這間兩房的頂樓公寓很大,有兩間臥室,而且位於一棟好看的戰前建築內——租金也相當划算,根據我的記憶大約一個月是四百七十五美金。客廳的物件很少,導致原本就很大的客廳顯得更大(甚至有一點回音)。不過要是得搬走,她說,她最會想念的還是看出去的景觀:那條河,還有每天的日落。(在屋外看其實應該更棒,但露臺一團亂:那裡是狗日常排泄的地方。)在公寓兩間臥房的另一頭有個小很多的房間,曾經是給女僕住的,裡頭有半套衛浴。當時大衛有個朋友會在那裡過夜。
等我搬進去後,那裡就成了我的書房。(「妳是這間屋子裡唯一有兩個房間的人,」當我告訴她我要搬離「340號公寓」時,蘇珊這樣說,語氣又是受傷又是控訴。)
吃午餐時,她問了我很多問題,像是幫《紐約書評》的編輯羅伯特.席爾維斯 和芭芭拉.雅皮斯坦 工作是什麼感覺,還有成為伊莉莎白.哈德維克 的學生是什麼感覺,伊莉莎白.哈德維克是我在巴納德學院 的其中一名教授,也是《紐約書評》的編輯委員之一。顯然這三人讓蘇珊很感興趣——甚至是著迷——我後來也得知,他們的友誼及認可對她來說至關重要。這三人都是《紐約書評》於一九六三年創辦時創始成員之一。蘇珊認為《紐約書評》比美國的任何一本刊物都還要傑出——這本刊物是嘗試將美國的知識份子生活提升至最高標準的「英雄式」作為——而她打從第一期就開始為這本刊物撰稿,因此始終感到非常驕傲。她的文章都是由席爾維斯進行編輯:「他是我目前為止遇過最棒的編輯。」他是所有作家求之不得的頂尖編輯,她總會這麼說。就跟其他供稿者一樣,他對作家抱持的懇切敬重讓她讚嘆。她也讚嘆他的完美主義,以及為了刊出文章而孜孜不倦編修的努力。他是她遇過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之一,她這麼說——可能還是最認真工作的人,可說一週幾乎七天都能看到他在伏案工作,包括假日,而且一工作就是整天,甚至還會到深夜。他就是蘇珊最仰慕的那種人:他推崇紀律、對知識抱持熱情,行事又無比審慎,除了最值得敬佩的作家和藝術家之外,只有他能在她的內心激起這種崇敬之情。
為《紐約書評》撰稿讓她相當自豪,而唯一能讓她同樣引以為傲的,是能夠在法勒、施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社 出書。事實上,她那天講的電話中,時間最長且態度最親密的對象就是羅傑.施特勞斯,他是出版社的主導者,而且早在十三年前就出了她的第一本書,之後也持續出版她的其他著作。他們一天至少談話一次也不稀奇。當時的蘇珊還沒有文學經紀人,除了出版書籍之外,施特勞斯替她應付了一些出版商通常不會處理的工作,像是為她的短篇小說和文章尋求雜誌發表的機會。不過那不是一段基於生意的關係。他們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他們是彼此的知己,施特勞斯也參與了蘇珊無關寫作的許多生活面向,包含她生病的危機,還有後來必須找新公寓的過程。儘管蘇珊和施特勞斯剛認識時,大衛已經十歲了,施特勞斯還是常說大衛「可能是我的私生子吧。」很快地,他就會把大衛帶進公司,讓他成為許多作家的編輯,其中包括蘇珊。
蘑菇湯不夠喝。她在冰箱內尋找,裡面幾乎空蕩蕩的,雖然不是玉米的季節,冰箱裡卻有用塑膠包裝起來的一根根玉米。我們吃了玉米後,她說,「當然,我想要的根本不是這些。我真正想要的是來根菸。」我才剛戒菸,但之後一搬進來,我就又開始抽了。我們三人都抽菸,幾乎所有來這間公寓的人也都抽菸。
我那天離開時,太陽已經低垂在哈德遜河面上,但我們的成果非常有限。蘇珊要求我這幾天再找時間過來。我記得走回家的路上心想,她真的很隨興、開放——與其說是我母親那一輩的人,其實更像我的同齡人。不過她跟年輕人相處一直都是這樣,她跟兒子之間也沒有常見的代溝問題;她兒子甚至還沒上高中,她就開始把他當成成年人對待了,從來似乎也沒懷疑過應不應該這麼做。現在回想,我不禁也想起蘇珊之前說的一件事:在她的記憶中,童年就是無聊透頂的一段時光,她總是迫不及待地希望趕快結束。我一直無法了解這件事(怎麼可能有人的童年——就算是不怎麼快樂的童年——會被描述成「徹底的浪費時間」?),但她希望大衛的童年也能儘快結束。(事後證明,他也覺得自己童年是段悲慘的時光,而且會引用蘇珊常描述自己童年的說法:像在監獄服刑。)就彷彿她並不是真的相信童年有必要存在——又或者更好的說法是,她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價值可言。
對大衛來說,她在他還是個小孩時就成了「蘇珊」,而他的父親,也就是社會學家及文化評論家菲利普.里夫 則是「菲利普」;大衛告訴過我,他無法想像自己稱呼他們「媽」和「爸」。每次蘇珊和大衛談起他的父親時——那是她在十七歲時結婚的對象,當時她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而他是二十八歲的講師,接著兩人在七年後離婚——她也稱他為菲利普。大衛提起她時很少說「我母親」,我也覺得說「你母親」聽來很怪。她就是永遠的 「蘇珊」。(有一次,我剛開始在《紐約書評》工作沒多久,羅伯特.席爾維特說,「幫我打電話給蘇珊」。我伸手去拿旋轉名片架,說,「哪個蘇珊?」芭芭拉.雅皮斯坦當時也在場,她一聽就笑了。「哪個蘇珊?」她重複了一次,搖搖頭,我知道她在嘲笑我。)
名字啊。蘇珊向我坦承,獲得這樣一個無聊又平凡的名字始終讓她開心不起來。(「妳看起來不像是叫蘇珊的人,」她會模仿那些對自己這麼說的人。)只要有人叫她蘇,她就會全身帶刺地嚴詞糾正對方。普遍來說,她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略稱或暱稱,不過她還是常把大衛(她是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作品為他命名)暱稱為小衛(Dig)。
在那些年間,這對母子從未跟父親連絡。不過有一次,我們三人驅車前往費城,那次蘇珊獲邀去演講,而大衛的父親跟第二任妻子就住在那裡,在車上時,蘇珊從後座對駕駛座的大衛說:「我認為你該帶希格麗德去見菲利普。」所以到了隔天,在開車回紐約之前,我們去了菲利普.里夫的家。蘇珊表示要在車上等。我們沒有事先通知要來,按電鈴時無人回應,但透過前門鑲的小片玻璃可以剛好看見門後的區域,大衛指了指他父親收藏的那些拐杖給我看。
我從未見過菲利普.里夫。但二○○六年,讀到他過世的消息時,我立刻想到了那些拐杖收藏,內心感到一陣疼痛。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