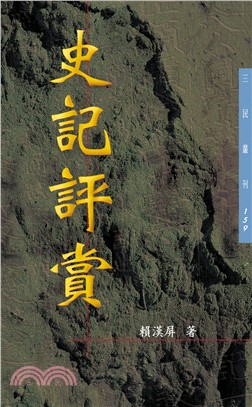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
商品資訊
系列名:木馬文化
ISBN13:9786263145177
替代書名:In einer dunklen Nacht ging ich aus meinem stillen Haus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彼得‧漢德克
譯者:彤雅立
出版日:2023/10/13
裝訂/頁數:精裝/352頁
規格:18.8cm*13.7cm*2.5cm (高/寬/厚)
適性閱讀分級:617【九年級】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當夢想殞落、關係斷裂,一個人如何重建世界?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
‧全新譯本,德文直譯:最貼近漢德克的實驗風格‧
虛幻、超現實……文字的魔域
寂靜、喃喃自語……情感的深淵
「夢想是如何停止的,大家通常會記得一清二楚。
至於夢想是如何開始的,幾乎沒人記得!」
一名孤絕的藥劑師,如何為了蕈菇痴狂,離開世俗構築的框架,走上無人理解的道路。在漆黑靜謐的小徑,他是否還有辦法尋覓到一絲的光明?
塔克桑,一處偏遠、幾乎沒有遊客的郊區,住著一名神祕的藥劑師。藥局是他唯一的堡壘,他日復一日開藥、指引病人,下班後,他不與病人招呼,不與妻子互動、不交談,各自棲居在住所。
直到他遇到兩名人士──詩人與曾經輝煌的奧運選手。他平淡的生活發展出奇異的改變:一名女人在暗夜中襲擊他;一場特殊的慶典正舉行著,他甚至找到了離異的家人。種種劇烈變化,使得他一度喪失語言的能力。而沒變的是,不同種類的蕈菇仍致命地吸引著他。
「我時常想,會不會是我對蕈菇的熱情,拆散了我與妻子?」
藥劑師告訴敘事者,這是一個關乎冒險與愛的故事。
而探險與愛的本質,必得穿越黑暗,挖掘深處。
彼得‧漢德克的語言冷靜帶有詩意、抽離表層情感,情節發展與文法遣詞,也經常背離大眾習慣的常態。然而,正是種種實驗、挑戰,使得漢德克的小說別具令人駐足並深思的特性。
《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之中,漢德克結合超現實、怪誕等氛圍,探索人與人之間,時而猛然斷裂、時而又瞬間接起的連結。在虛妄底下,顯露人們最真實、最純粹的渴求。也是一場尋回自我存在意義的偉大冒險。
「說故事,正是藉由陳述『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這個句子,來嚮導自己,離開自我緘默的密室。也於是,將一片寂靜地域,一再原地流轉,正是對此寂靜,最強悍的離境。」──童偉格(作家)
「很多地方都會忽然出現類似魔幻寫實的文句或場景,像是烏鴉忽然會說話,或是類似電影《地下社會》的荒謬慶典場面等,會像蕈菇一樣一個一個突然冒出來。可是隨著旅途的進程,小說文字愈到後面,愈是清澈,彷彿藥劑師經歷這段黑夜的靈魂之旅,找回愛的能力的同時,他看待世界的角度,變得更清楚及肯定【……】我相信閱讀《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就是一趟找回感受能力的靈修過程。」──耿一偉(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藥劑師從在漆黑的夜晚出發,離開了安靜的房子後,冒險的一切語言都失能了,世界剩下蕈菇,無窮無盡的蕈菇,大自然成為了一切的能指,作為對於現代世界的反抗。世界的意義只在於個人的視野以及興趣當中,只要幻想當中仍有未接觸部落,則處處皆為詩歌。」──沐羽(作家)
白樵、朱嘉漢、言叔夏、曹馭博、廖偉棠、鄭琬融、鴻鴻──聯合推薦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
‧全新譯本,德文直譯:最貼近漢德克的實驗風格‧
虛幻、超現實……文字的魔域
寂靜、喃喃自語……情感的深淵
「夢想是如何停止的,大家通常會記得一清二楚。
至於夢想是如何開始的,幾乎沒人記得!」
一名孤絕的藥劑師,如何為了蕈菇痴狂,離開世俗構築的框架,走上無人理解的道路。在漆黑靜謐的小徑,他是否還有辦法尋覓到一絲的光明?
塔克桑,一處偏遠、幾乎沒有遊客的郊區,住著一名神祕的藥劑師。藥局是他唯一的堡壘,他日復一日開藥、指引病人,下班後,他不與病人招呼,不與妻子互動、不交談,各自棲居在住所。
直到他遇到兩名人士──詩人與曾經輝煌的奧運選手。他平淡的生活發展出奇異的改變:一名女人在暗夜中襲擊他;一場特殊的慶典正舉行著,他甚至找到了離異的家人。種種劇烈變化,使得他一度喪失語言的能力。而沒變的是,不同種類的蕈菇仍致命地吸引著他。
「我時常想,會不會是我對蕈菇的熱情,拆散了我與妻子?」
藥劑師告訴敘事者,這是一個關乎冒險與愛的故事。
而探險與愛的本質,必得穿越黑暗,挖掘深處。
彼得‧漢德克的語言冷靜帶有詩意、抽離表層情感,情節發展與文法遣詞,也經常背離大眾習慣的常態。然而,正是種種實驗、挑戰,使得漢德克的小說別具令人駐足並深思的特性。
《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之中,漢德克結合超現實、怪誕等氛圍,探索人與人之間,時而猛然斷裂、時而又瞬間接起的連結。在虛妄底下,顯露人們最真實、最純粹的渴求。也是一場尋回自我存在意義的偉大冒險。
「說故事,正是藉由陳述『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這個句子,來嚮導自己,離開自我緘默的密室。也於是,將一片寂靜地域,一再原地流轉,正是對此寂靜,最強悍的離境。」──童偉格(作家)
「很多地方都會忽然出現類似魔幻寫實的文句或場景,像是烏鴉忽然會說話,或是類似電影《地下社會》的荒謬慶典場面等,會像蕈菇一樣一個一個突然冒出來。可是隨著旅途的進程,小說文字愈到後面,愈是清澈,彷彿藥劑師經歷這段黑夜的靈魂之旅,找回愛的能力的同時,他看待世界的角度,變得更清楚及肯定【……】我相信閱讀《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就是一趟找回感受能力的靈修過程。」──耿一偉(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藥劑師從在漆黑的夜晚出發,離開了安靜的房子後,冒險的一切語言都失能了,世界剩下蕈菇,無窮無盡的蕈菇,大自然成為了一切的能指,作為對於現代世界的反抗。世界的意義只在於個人的視野以及興趣當中,只要幻想當中仍有未接觸部落,則處處皆為詩歌。」──沐羽(作家)
白樵、朱嘉漢、言叔夏、曹馭博、廖偉棠、鄭琬融、鴻鴻──聯合推薦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出生於奧地利,著名小說家、劇作家。1961年曾於格拉茨大學攻讀法律,1965年退學。24歲即發表著名劇本《冒犯觀眾》,引起廣大迴響。他是當代德語文學重量級的作家之一,曾於1973年獲畢希納文學獎,2009年獲卡夫卡文學獎,2014年獲國際易卜生獎,被譽為「活著的經典」。作品風格以實驗性的語言著稱。
作品產量眾多,小說有《夢外之悲》、《守門員的焦慮》、《左撇子女人》、《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及《水果賊》(暫譯)等,其中多部曾改編成電影,如《守門員的焦慮》為與文‧溫德斯合作改編;《左撇子女人》則由漢德克本人執導,並獲坎城影展最佳影片提名。
譯者簡介
彤雅立
著有詩集,譯作若干。以翻譯、研究與寫作為業。德語譯作包括《夢外之悲》、《園圃之歌》、《帕帕拉吉!劃破天空的文明人》、《馬克思、愛情與資本論》、《分裂的天空》與《卡夫卡中短篇全集》等。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出生於奧地利,著名小說家、劇作家。1961年曾於格拉茨大學攻讀法律,1965年退學。24歲即發表著名劇本《冒犯觀眾》,引起廣大迴響。他是當代德語文學重量級的作家之一,曾於1973年獲畢希納文學獎,2009年獲卡夫卡文學獎,2014年獲國際易卜生獎,被譽為「活著的經典」。作品風格以實驗性的語言著稱。
作品產量眾多,小說有《夢外之悲》、《守門員的焦慮》、《左撇子女人》、《在漆黑的夜晚,我離開了我安靜的房子》及《水果賊》(暫譯)等,其中多部曾改編成電影,如《守門員的焦慮》為與文‧溫德斯合作改編;《左撇子女人》則由漢德克本人執導,並獲坎城影展最佳影片提名。
譯者簡介
彤雅立
著有詩集,譯作若干。以翻譯、研究與寫作為業。德語譯作包括《夢外之悲》、《園圃之歌》、《帕帕拉吉!劃破天空的文明人》、《馬克思、愛情與資本論》、《分裂的天空》與《卡夫卡中短篇全集》等。
名人/編輯推薦
作家/童偉格、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耿一偉──專文導讀
作家/沐羽──專文推薦
白樵、朱嘉漢、言叔夏、曹馭博、廖偉棠、鄭琬融、鴻鴻──聯合推薦
作家/沐羽──專文推薦
白樵、朱嘉漢、言叔夏、曹馭博、廖偉棠、鄭琬融、鴻鴻──聯合推薦
目次
導讀/訴說寂靜──童偉格
導讀/愛,帶我們走出心靈的黑夜──耿一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終章
推薦跋/冒險的意義在無限延伸的蕈菇之後──沐羽
彼得‧漢德克年表
導讀/愛,帶我們走出心靈的黑夜──耿一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終章
推薦跋/冒險的意義在無限延伸的蕈菇之後──沐羽
彼得‧漢德克年表
書摘/試閱
在這則故事所上演的時代,塔克桑幾乎是被遺忘的。鄰近城市薩爾斯堡的大多數居民,大概都說不出這個地方在哪裡。對許多人而言,這個名字聽來陌生。塔克桑?伯明罕?諾丁罕?事實上,戰後第一個足球俱樂部的名字就叫做「塔克桑森林」,直到從圈內最底層鹹魚翻身之後才更名,甚至更名為「FC薩爾斯堡」(這段時間或許又改回了原來的名字)。儘管市中心的人們早已習慣開往塔克桑的公車從身邊駛過──與其他公車相較,這條路線不太擠也不太空──卻幾乎不見一名城市人坐在裡面過。
與鄰近薩爾斯堡的那些古老村莊不一樣,塔克桑是戰後新建的,而且從來不是觀光勝地。那裡沒有吸引人的旅館與景點,就連令人卻步之處也沒有。儘管草地後面緊鄰著克萊斯罕城堡、賭場與國家禮賓處,塔克桑卻不是行政區、不是城郊、不是農田,與附近所有的地方相反,塔克桑總被略過不訪,無論是來自近處與遠方都無人參訪。
沒人會前來,即便只是匆匆經過,也不會有人看它一眼,更別說待上一晚。因為在塔克桑一間旅館都沒有,而這又是薩爾斯堡周邊城鎮的一項特點了。所謂的「客房」,其實只是壁龕、小房間,如果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空房,眼前這裡將是最後的避難所。塔克桑,這個地名亮晶晶地掛在公車上,行駛直到夜深,如鬼影穿梭在已然更漆黑、更寂靜的市中心,這麼多年來,從未有哪個人受到吸引而下車來到此地。就算有個見多識廣、心胸開闊的人,甚至是放眼世界滿懷胸襟之人,你向他打聽塔克桑,他會說:「不曉得。」或者就聳聳肩。
會去那裡超過一次的客人,或許就屬我跟我的朋友安德烈.魯蛇了,他是中古德語老師,還自稱是房屋門檻學家。當時我初來乍到塔克桑,在一條名叫「克萊斯罕大道」(一點也感受不到城堡與大道)的中心街道走進一間棚屋酒吧,裡面一個男人花了好幾個鐘頭發牢騷,說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幹掉誰:「就是得幹掉他!」一個冬夜,一間幾近空蕩蕩的薩爾斯堡機場餐廳(在那段時間,它幾乎比入境大廳還要大),安德烈.魯蛇在那裡,他湊到我的耳邊說:「看,塔克桑的藥劑師就坐在那裡!」
這段時間,吾友魯蛇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而我則是離開薩爾斯堡很久了。那時我們偶爾還會約出來聚聚的塔克桑藥劑師,在這則故事所上演的時代,也幾乎無人聞問──無論那是不是他的個性使然。
塔克桑那麼難以接近,是因為地理位置,不過也要歸咎於當地形成的街廓。
就像今天大家愈來愈常碰上的隨便哪個地方,打從一開始都有如下特點──與鄰近地帶明確隔開,或從附近的城鎮透過所有可能的交通路線,都難以抵達;步行或騎腳踏車想要到達,都是不可能的。與現在那些小村鎮截然相反的是,這些日子以來,塔克桑被愈來愈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橫切,乃至限縮了腹地,被強行推進一個詭異之境,並且在凡此種種的障礙中生成。雖然它位於雄偉江河的流域,並且是進入一座大城市之前的重要據點,也因此有著營區或兵營式的住宅區,事實上,塔克桑的周邊鄰近德國邊界,甚至有三個軍營,其中一個隸屬塔克桑的轄區。開往慕尼黑的遠程火車路線,是塔克桑其中一個邊界,它的存在比這座村子還要久遠。而高速公路也早在二戰之前就蓋好,稱為帝國高速公路(幾十年後,狹窄隧道入口鑲嵌的竣工日,旁邊刻著納粹卐字符的黨徽鷹爪)。同樣的,奧地利第一共和國期間建成的機場也形成屏障,使得後來在塔克桑形成的區域難以抵達。
塔克桑就建立在這個三角交通樞紐之中,唯有透過幾條艱困、繞遠路的彎路以及隧道才能抵達。如此一來,塔克桑可以說是一看便知,是個被重重包圍的境外領土。
被誰包圍?屬於哪裡?大概可以說,塔克桑確實比薩爾斯堡附近其他什麼地方都還要引人注目,一個戰爭難民、流離失所者與東歐德裔移民的僑居地。無論如何,這位藥劑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歸屬於某個來自東邊、經營藥品工廠的家庭,先是經歷過哈布斯堡的君主政體,接著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然後被德國占領。在此,我並不想知道有關他更詳細的故事,對此他說:「就這樣吧!讓一切隨風而去!」
這些新來的人,戰後來到這聯繫長途火車軌道、高速公路與飛機場的三角地帶,餘下的空間則是農田,上面掛著農莊招牌「塔克桑」。一直以來,他們不只是落地生根,同時也給自己添加了保護與屏障。
克服外在屏障之後,你會遇上第二道障礙,這些障礙並不是預先規畫好的,而是之後才蓋起的建築。無論是在鐵路路堤或是飛機跑道的柵欄後方,塔克桑的內部似乎又再度被包圍了,如果不是用鐵絲網隔絕,就是被高聳的樹籬隔開,在上方,幾乎只能看見戰後石砌天主教堂的方尖塔(新教教堂則不在視線之內)。
這兩道屏障,一道由外部強加,另一道則由內部增補;想要晃遊其間,無非只有足球場、能散步的草地或是蔓生的田野。每年都有幾天讓客座的馬戲團在空曠處演出,他們離開之後,地面留下一道蒼白的圓環,因而整體看來彷彿一座平地碉堡。
早在半世紀前,塔克桑就是許多新移民的新據點,今天我們稱呼這些區域為「新城」,即便規模非常小。並不容易進入,要走路或搭車出來,則又更難了。幾乎所有標明通往那裡的道路,後來就會轉彎,最後在成群的房屋與小花園之間又導回原處。或者這幾條路就結束在一排密林之前,空曠的田野與通往其他地方的景象在密林之中發出微光。這些新住民的街道甚至會以麥哲倫或者保時捷來命名。
像塔克桑那樣被密林包圍的大部分街道(毋寧說是聯外道路),由於鄰近機場,都以開拓先鋒的飛行員來命名,像是「齊柏林伯爵」、「奧托.馮.李林塔爾」或「馬歇爾.雷巴」,大概也沒有事先徵詢過戰後外來移民的意見,就強加行使──他們自己也許偏好「哥舍爾」或「錫本比根街」,但誰知道呢?有一回,我的朋友安德烈.魯蛇跟我說,唯一適合用來為這些街道命名的飛行員,就屬「諾葛塞與柯利」,這兩個人第一次試飛,從歐洲到美洲橫越大西洋,離開歐陸不久便失蹤了。
還有第三件事情,可以說是讓塔克桑一開始就超越了當時其他地方──今天我們愈來愈習以為常,居住與工作不在同一個地方。在這樣的三角地帶與密林包圍的僑居地中,有工作的人從五十年前起就依循這樣的規則,房子或公寓要在別處──可以鄰近塔克桑,但無論如何不要在同一個地方。就連商人或餐館老闆也只是白天來,只為了做生意。甚至是我頗熟悉的一個神父,他被指派來服務新住民,只專程來帶領彌撒,平時則住在城裡漫無目的地遊走(這些日子以來,他應該早就放棄這項職務了)。
藥劑師的住家也是一樣,位於塔克桑外圍的其中一戶農舍,靠近邊界的薩拉赫河,在這條河尚未流入薩爾察赫河之處。房子位於那裡一幢質樸的三角屋中,也可以說是一處「尖角」。
他喜歡賴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他的生活就是一串三角形的移動,介於河堤房屋、藥局與機場三者之間。當時我們在機場初次相遇──這裡曾經在另一段時期上演著他的故事──他固定在那裡吃晚餐,有時跟妻子,有時跟情人。
那間藥局是年紀大他很多的哥哥開的,曾經是戰後塔克桑新移民與難民移居區的第一家中小企業,實際上是第一家公開且便民的機構,創立時間早於學校與兩座教堂,甚至早於任何一個店家。沒有一家麵包店比那藥局早開張(以前的麵包最早是要去農舍採買的)。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這家藥局還是戰後新移民唯一的「民眾服務中心」。我認識的一個人如此形容,人們起初會嘲笑那間人跡罕至地帶的藥房,不過那裡漸漸成為臨時的社區活動中心。
即使過了幾十年,你還是可以感受得到──雖然如今農業景致已然消失,塔克桑藥局在鄰里的地位依舊屹立不搖,它隱身在教堂尖塔與超市之間,使人難以一眼看見,然而在大家的心目中,它仍然是這個地區的中心。
這樣的印象不是源自建築本身。這幢建築看起來像一間小小的書報雜貨攤,很適合賣菸草與報紙。裡面的擺設既不像許多歷史悠久的藥局陰暗、精心布置、充滿巧思、如博物館般富麗堂皇琳瑯滿目,卻也不明亮鮮豔──我到底置身何處呢?在一間日光室?還是一家香水店?或是一張沙灘日光浴椅?──有些新來的,或是更年輕的員工會這樣問。嚇人的是,裡面沒有色彩也毫無修飾,無論藥品或者牙膏,沒有一樣東西突出醒目,所有的一切退後到非常厚實笨重的屏障與陳列櫃深處,彷彿不是商品,不是任何可被購買之物,而是被禁止的兵器庫中那未獲授權的東西,前面有兩三個白衣警衛看守著。藥局門口甚至沒有特別的門檻,就像安德烈.魯蛇說的,幾乎全世界的藥局都有門檻。這裡讓人感受不到高度,也感受不到阻礙,它是圖畫、裝飾與圖案,比家中的玄關還要講究,凹面甚至比教堂門口還要深。你會發現自己沒有跨越任何檻,就這樣進入了這座藥品倉庫。
塔克桑的藥局名叫「老鷹之家」,是創始人的哥哥取的,他早已西遷,到巴伐利亞的穆瑙市,在那裡與兒女子孫於新開業的「紅豬藥局」安身立命。根據後來接手的人說,那家藥局看起來有點像書報雜貨攤,又有點像小家電行,因此取名「兔子之家」、「刺蝟之家」其實更好,或者也可以按照接手人的意願,譬如以祖先的鄉土來命名──「塔特拉藥局」。
不,這個平凡無奇的地方之所以顯得突兀,在塔克桑獨樹一幟,是因為位處村莊中央,村莊現在幾乎建造成了一座城鎮──它位處一片大草地的中央,那裡對於一幢茅屋而言是過大了。草地上稀疏地生長著低矮、年代久遠的樹木,以及那種彷彿昔日草原所遺留下來的灌木叢。「有時在早晨,我出門上班的路上,會看見炊煙從茅屋升起。」藥劑師以不那麼純粹的奧地利式語氣說著。
他也喜歡在街上來來回回,從河邊的房子到他越過森林邊緣的藥店,晚上再從這家藥店沿著田地的圍籬一直走,往飛機場的方向去,諸如此類(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這樣的諸如此類)。他不是步行就是駕著他其中一輛大車去上班──總是最新的車款──但他也曾經直挺挺地騎著腳踏車,黑色、沉重的「飛翔荷蘭人」品牌。有幾回,我在田間小路遇見騎機車的他,渾身被濺上汙泥,同時又若有所思,彷彿剛剛在野地打獵過(有一次,他在我的夢中出現,搭乘一架私人的齊柏林飛船,降落在藥局門口,攀著繩索而下,落在草原的綠地之中)。
與鄰近薩爾斯堡的那些古老村莊不一樣,塔克桑是戰後新建的,而且從來不是觀光勝地。那裡沒有吸引人的旅館與景點,就連令人卻步之處也沒有。儘管草地後面緊鄰著克萊斯罕城堡、賭場與國家禮賓處,塔克桑卻不是行政區、不是城郊、不是農田,與附近所有的地方相反,塔克桑總被略過不訪,無論是來自近處與遠方都無人參訪。
沒人會前來,即便只是匆匆經過,也不會有人看它一眼,更別說待上一晚。因為在塔克桑一間旅館都沒有,而這又是薩爾斯堡周邊城鎮的一項特點了。所謂的「客房」,其實只是壁龕、小房間,如果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空房,眼前這裡將是最後的避難所。塔克桑,這個地名亮晶晶地掛在公車上,行駛直到夜深,如鬼影穿梭在已然更漆黑、更寂靜的市中心,這麼多年來,從未有哪個人受到吸引而下車來到此地。就算有個見多識廣、心胸開闊的人,甚至是放眼世界滿懷胸襟之人,你向他打聽塔克桑,他會說:「不曉得。」或者就聳聳肩。
會去那裡超過一次的客人,或許就屬我跟我的朋友安德烈.魯蛇了,他是中古德語老師,還自稱是房屋門檻學家。當時我初來乍到塔克桑,在一條名叫「克萊斯罕大道」(一點也感受不到城堡與大道)的中心街道走進一間棚屋酒吧,裡面一個男人花了好幾個鐘頭發牢騷,說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幹掉誰:「就是得幹掉他!」一個冬夜,一間幾近空蕩蕩的薩爾斯堡機場餐廳(在那段時間,它幾乎比入境大廳還要大),安德烈.魯蛇在那裡,他湊到我的耳邊說:「看,塔克桑的藥劑師就坐在那裡!」
這段時間,吾友魯蛇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而我則是離開薩爾斯堡很久了。那時我們偶爾還會約出來聚聚的塔克桑藥劑師,在這則故事所上演的時代,也幾乎無人聞問──無論那是不是他的個性使然。
塔克桑那麼難以接近,是因為地理位置,不過也要歸咎於當地形成的街廓。
就像今天大家愈來愈常碰上的隨便哪個地方,打從一開始都有如下特點──與鄰近地帶明確隔開,或從附近的城鎮透過所有可能的交通路線,都難以抵達;步行或騎腳踏車想要到達,都是不可能的。與現在那些小村鎮截然相反的是,這些日子以來,塔克桑被愈來愈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橫切,乃至限縮了腹地,被強行推進一個詭異之境,並且在凡此種種的障礙中生成。雖然它位於雄偉江河的流域,並且是進入一座大城市之前的重要據點,也因此有著營區或兵營式的住宅區,事實上,塔克桑的周邊鄰近德國邊界,甚至有三個軍營,其中一個隸屬塔克桑的轄區。開往慕尼黑的遠程火車路線,是塔克桑其中一個邊界,它的存在比這座村子還要久遠。而高速公路也早在二戰之前就蓋好,稱為帝國高速公路(幾十年後,狹窄隧道入口鑲嵌的竣工日,旁邊刻著納粹卐字符的黨徽鷹爪)。同樣的,奧地利第一共和國期間建成的機場也形成屏障,使得後來在塔克桑形成的區域難以抵達。
塔克桑就建立在這個三角交通樞紐之中,唯有透過幾條艱困、繞遠路的彎路以及隧道才能抵達。如此一來,塔克桑可以說是一看便知,是個被重重包圍的境外領土。
被誰包圍?屬於哪裡?大概可以說,塔克桑確實比薩爾斯堡附近其他什麼地方都還要引人注目,一個戰爭難民、流離失所者與東歐德裔移民的僑居地。無論如何,這位藥劑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歸屬於某個來自東邊、經營藥品工廠的家庭,先是經歷過哈布斯堡的君主政體,接著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然後被德國占領。在此,我並不想知道有關他更詳細的故事,對此他說:「就這樣吧!讓一切隨風而去!」
這些新來的人,戰後來到這聯繫長途火車軌道、高速公路與飛機場的三角地帶,餘下的空間則是農田,上面掛著農莊招牌「塔克桑」。一直以來,他們不只是落地生根,同時也給自己添加了保護與屏障。
克服外在屏障之後,你會遇上第二道障礙,這些障礙並不是預先規畫好的,而是之後才蓋起的建築。無論是在鐵路路堤或是飛機跑道的柵欄後方,塔克桑的內部似乎又再度被包圍了,如果不是用鐵絲網隔絕,就是被高聳的樹籬隔開,在上方,幾乎只能看見戰後石砌天主教堂的方尖塔(新教教堂則不在視線之內)。
這兩道屏障,一道由外部強加,另一道則由內部增補;想要晃遊其間,無非只有足球場、能散步的草地或是蔓生的田野。每年都有幾天讓客座的馬戲團在空曠處演出,他們離開之後,地面留下一道蒼白的圓環,因而整體看來彷彿一座平地碉堡。
早在半世紀前,塔克桑就是許多新移民的新據點,今天我們稱呼這些區域為「新城」,即便規模非常小。並不容易進入,要走路或搭車出來,則又更難了。幾乎所有標明通往那裡的道路,後來就會轉彎,最後在成群的房屋與小花園之間又導回原處。或者這幾條路就結束在一排密林之前,空曠的田野與通往其他地方的景象在密林之中發出微光。這些新住民的街道甚至會以麥哲倫或者保時捷來命名。
像塔克桑那樣被密林包圍的大部分街道(毋寧說是聯外道路),由於鄰近機場,都以開拓先鋒的飛行員來命名,像是「齊柏林伯爵」、「奧托.馮.李林塔爾」或「馬歇爾.雷巴」,大概也沒有事先徵詢過戰後外來移民的意見,就強加行使──他們自己也許偏好「哥舍爾」或「錫本比根街」,但誰知道呢?有一回,我的朋友安德烈.魯蛇跟我說,唯一適合用來為這些街道命名的飛行員,就屬「諾葛塞與柯利」,這兩個人第一次試飛,從歐洲到美洲橫越大西洋,離開歐陸不久便失蹤了。
還有第三件事情,可以說是讓塔克桑一開始就超越了當時其他地方──今天我們愈來愈習以為常,居住與工作不在同一個地方。在這樣的三角地帶與密林包圍的僑居地中,有工作的人從五十年前起就依循這樣的規則,房子或公寓要在別處──可以鄰近塔克桑,但無論如何不要在同一個地方。就連商人或餐館老闆也只是白天來,只為了做生意。甚至是我頗熟悉的一個神父,他被指派來服務新住民,只專程來帶領彌撒,平時則住在城裡漫無目的地遊走(這些日子以來,他應該早就放棄這項職務了)。
藥劑師的住家也是一樣,位於塔克桑外圍的其中一戶農舍,靠近邊界的薩拉赫河,在這條河尚未流入薩爾察赫河之處。房子位於那裡一幢質樸的三角屋中,也可以說是一處「尖角」。
他喜歡賴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他的生活就是一串三角形的移動,介於河堤房屋、藥局與機場三者之間。當時我們在機場初次相遇──這裡曾經在另一段時期上演著他的故事──他固定在那裡吃晚餐,有時跟妻子,有時跟情人。
那間藥局是年紀大他很多的哥哥開的,曾經是戰後塔克桑新移民與難民移居區的第一家中小企業,實際上是第一家公開且便民的機構,創立時間早於學校與兩座教堂,甚至早於任何一個店家。沒有一家麵包店比那藥局早開張(以前的麵包最早是要去農舍採買的)。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這家藥局還是戰後新移民唯一的「民眾服務中心」。我認識的一個人如此形容,人們起初會嘲笑那間人跡罕至地帶的藥房,不過那裡漸漸成為臨時的社區活動中心。
即使過了幾十年,你還是可以感受得到──雖然如今農業景致已然消失,塔克桑藥局在鄰里的地位依舊屹立不搖,它隱身在教堂尖塔與超市之間,使人難以一眼看見,然而在大家的心目中,它仍然是這個地區的中心。
這樣的印象不是源自建築本身。這幢建築看起來像一間小小的書報雜貨攤,很適合賣菸草與報紙。裡面的擺設既不像許多歷史悠久的藥局陰暗、精心布置、充滿巧思、如博物館般富麗堂皇琳瑯滿目,卻也不明亮鮮豔──我到底置身何處呢?在一間日光室?還是一家香水店?或是一張沙灘日光浴椅?──有些新來的,或是更年輕的員工會這樣問。嚇人的是,裡面沒有色彩也毫無修飾,無論藥品或者牙膏,沒有一樣東西突出醒目,所有的一切退後到非常厚實笨重的屏障與陳列櫃深處,彷彿不是商品,不是任何可被購買之物,而是被禁止的兵器庫中那未獲授權的東西,前面有兩三個白衣警衛看守著。藥局門口甚至沒有特別的門檻,就像安德烈.魯蛇說的,幾乎全世界的藥局都有門檻。這裡讓人感受不到高度,也感受不到阻礙,它是圖畫、裝飾與圖案,比家中的玄關還要講究,凹面甚至比教堂門口還要深。你會發現自己沒有跨越任何檻,就這樣進入了這座藥品倉庫。
塔克桑的藥局名叫「老鷹之家」,是創始人的哥哥取的,他早已西遷,到巴伐利亞的穆瑙市,在那裡與兒女子孫於新開業的「紅豬藥局」安身立命。根據後來接手的人說,那家藥局看起來有點像書報雜貨攤,又有點像小家電行,因此取名「兔子之家」、「刺蝟之家」其實更好,或者也可以按照接手人的意願,譬如以祖先的鄉土來命名──「塔特拉藥局」。
不,這個平凡無奇的地方之所以顯得突兀,在塔克桑獨樹一幟,是因為位處村莊中央,村莊現在幾乎建造成了一座城鎮──它位處一片大草地的中央,那裡對於一幢茅屋而言是過大了。草地上稀疏地生長著低矮、年代久遠的樹木,以及那種彷彿昔日草原所遺留下來的灌木叢。「有時在早晨,我出門上班的路上,會看見炊煙從茅屋升起。」藥劑師以不那麼純粹的奧地利式語氣說著。
他也喜歡在街上來來回回,從河邊的房子到他越過森林邊緣的藥店,晚上再從這家藥店沿著田地的圍籬一直走,往飛機場的方向去,諸如此類(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這樣的諸如此類)。他不是步行就是駕著他其中一輛大車去上班──總是最新的車款──但他也曾經直挺挺地騎著腳踏車,黑色、沉重的「飛翔荷蘭人」品牌。有幾回,我在田間小路遇見騎機車的他,渾身被濺上汙泥,同時又若有所思,彷彿剛剛在野地打獵過(有一次,他在我的夢中出現,搭乘一架私人的齊柏林飛船,降落在藥局門口,攀著繩索而下,落在草原的綠地之中)。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