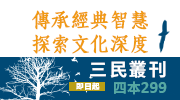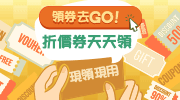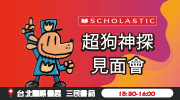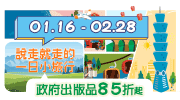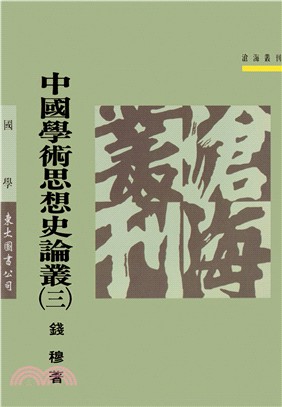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應重視詩詞體裁研究
(代 序)
盡管對中國的韻文學的研究對象、范圍、目的、方法應該是什么,大家的看法不盡一致,但韻文學是文學的一部分而且是就文學形式的體裁特點而言的,這大概不成問題吧。由此想到對古典詩詞的研究,體裁特點也是不應忽略的一個方面。
以往對詩詞的研究,多從一般文學發展史的角度進行,有人稱之為縱向研究;現在,又有人提出還應進行橫向研究,研究文學在這一時代與社會、政治、經濟以及其他意識形態的關系,然后把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結合起來。這自然是能使研究工作深入的很有卓見的建議。但我覺得這還不夠,還應該把文學的內容研究與形式研究結合起來。
詩歌形式的研究(包括研究它與內容的關系),我以為不能不注意詩歌的體裁。以往的研究,多半總是只注意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有用什么表現手法,諸如比喻、象征、想象、夸張,或者語言精煉含蓄,自然流暢、有節奏感,用典或白描,以及藝術風格如何等等,卻很少結合體裁特點加以論述,即使談到體裁,也只限于詩律學的范圍。似乎一首近體詩與一首古風的差別,就在于一則有字句限制、格律規定,一則沒有;律詩與絕句的差別,似乎只是律詩八句,絕句四句,“絕乃律之半”。這樣,就很難說明律、絕同是近體,為什么杜甫的律詩(尤其是七律)筆力勁健,人難匹敵。而他的絕句就未能稱雄于一時;李白寫絕句是拿手,而寫律詩(尤其是七律)則非其所長。邊塞詩派總擅長歌行,田園詩派多工于五言短詩。王維的《夷門歌》、《隴頭吟》、《老將行》、《燕支行》諸作,和他的《輞川集》、《皇甫岳云谿雜題》組詩,不但題材各別,風格迥異,選擇的體裁也是不同的。李白的古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與歌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都是極自負的話,可是一則從容和緩,一則奔放不羈。如此等等,也都與選擇詩的體裁特點有關,而決非平平仄仄的格律常識可說明的。
我國傳統的詩學是很講究體裁特點的,對詩的各體都有過不少論述,有的是說得相當精辟的。這也許與他們自身都有創作實踐經驗有關。現在研究詩詞換了路子,多不注意及此,這是一個缺陷。
京劇、越劇、歌劇、舞劇、話劇……雖然同是舞臺劇,如果不顧及它們各自的特點,而用同一尺度去衡量,比較和評論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是很難說得中肯的。研究詩歌,也必須弄清各體的特點和適應性,道理是一樣的。可惜這方面的研究,已長期被忽略、冷落了。我在杭大任教時,給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過“唐詩體裁研究”的課,就是想引導學生也注意這方面的研究。因為我發現上過中國古代文學課的學生,有的還弄不清樂府與古、近體詩究竟是什么關系。最近,讀到一篇發表出來的文章,在談唐詩的體裁種類時,把七言古體與歌行體分作兩類。其實,這是不妥當的。在唐代,歌行就是七古,七古都叫歌行,并非兩類。那時,五古、七古的名稱還沒有,所謂古體、往體、古風、古詩,是指唐以前就有的聲調未協的五言詩;而七言詩和長短句詩,唐以前除了個別詩人如鮑照等仿樂府歌行而作外,一般詩人都不寫或很少去寫,七言成為文人普遍創作的一種詩體還始于唐代,而長短句詩成為文人普遍創作形式則始于盛唐。所以唐人不把七言稱作古體,而只叫歌行。宋元之后,稱之為七古,那也只是因為樂府歌行對唐來說,是古已有之的。這一點,明代的唐詩學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簽》的《體凡》篇中已經提到了;我最近有一篇《什么是歌行?》的文章發表(《古典文學知識》1987年1期),也說了這方面的問題。
總之,我覺得詩歌體裁是應該充分利用前人取得的經驗與成果加以系統研究的一個領域,只要深入下去,一定會有很多發現的。我準備繼續在這方面下點功夫,同時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一起來共同研究它。
(原載《中國韻文學刊》總第1期“韻文筆談”欄目,題作《詩歌形式的研究不能不注意詩歌的體裁》)
治學雜談——讀懂并不容易
治學之道,人人各異,悟性高低,功力深淺,成就亦自不同。自知學淺識陋,應邀為文,不無慚愧。又所言多半常識,非有高見;片言斷想,不成系統,姑且稱之為雜談。
喜歡古典詩詞的年輕人,常以為讀懂詩詞容易,特別是在現在各種注釋本已出版得比較多的情況下,以為遇到難懂的詞句,看一下注釋就解決了,所以總把注意力集中在看人家如何評析鑒賞上,而忽略自己細心研讀原作。我以為這不是有效地提高自己對詩詞的閱讀和鑒賞能力的好辦法。出色的評析鑒賞,必須建立在正確理解作品的基礎上;除理解詞義外,還應包括作者為何要這樣寫。這一最基本的功夫,要做到家并不容易。翻看前人的詩評、詞評,就會發現有的評說由于對作品理解有偏誤,而說不到點子上;今人的鑒賞文章,情況更嚴重,一首幾十字的詩詞,可以寫上幾千字的文章,可仍不免在理解原文上出錯。試舉數例如下:陳與義《和張矩臣水墨梅》詩:“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玉妃,即楊貴妃,因其白凈而喻梅花。詩的后兩句用典,有注本引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朓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這都不錯。但說到句意時稱“這兩句是以梅花一塵不染的品格自勵”,就誤解了。其實,用此典是因為詩詠“水墨梅”的緣故。真梅是白的,畫梅是黑的,所以用素衣化緇典,同題后一首詩有“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語可證。
陸游《度浮橋至南臺》七律前半云:“客中多病廢登臨,聞說南臺試一尋。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系大江心。”南臺,島名,在福州外閩江中,亦稱“南臺山”。有人因“九軌(謂往來車多)”句寫“度浮橋”,便以為“千艘”句寫所見江上船只眾多景象,其實是誤解。原意兩句都寫浮橋,浮橋無墩,橋面架于一字排開的許多船上,故謂。可見,讀詩詞一點也粗心不得。其中近體詩、詞的題目、小序尤須留意,古人從不隨意題寫,有時那幾個字、一兩句話,便成一篇內容的綱。這一點,讀多了就會知道。
再如辛棄疾《滿江紅•題冷泉亭》詞,是題在杭州靈隱飛來峰腳下的冷泉亭上的,其結尾說:“恨此中、風物本吾家,今為客。”有箋注說:“‘吾家’,指濟南。”這是想當然的解說,是不對的,問題出在沒有弄懂句意。后來寫鑒賞文章的人便據此而說冷泉亭景物“有和作者家鄉(濟南)相似的地方”,作者是恨“故鄉永遠回歸不得,只能長期在南方作客”,是“觸景懷舊”等等。辛棄疾突騎渡江歸宋后,從未說過懷念淪陷的山東家鄉而可惜回不去的話,反而自辯道:“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水龍吟》)怎么現在卻恨起“在南方作客”來了呢?這是說不通的。再說“本吾家”三字也不能解成“似故鄉”,它是與“今為客”相連對舉的,意思是說,本來就是自己家里的,現在反而當作客人了。這指什么呢?指“此中風物”,即飛來峰。題冷泉亭,必詠飛來峰,亭在峰下,是一回事,此亭至今仍懸一楹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來?”相傳“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茲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印度)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淳祐臨安志》)故飛來峰又稱鷲嶺。辛詞上闋末云:“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是當年、玉斧削方壺,無人識。”已說不信峰從國外飛來。下闋結尾,照應此說,謂此山本自家所有,今反以外來客視之,所以為恨耳。這是在借題發揮,寫自己的牢騷。南宋當局歧視稼軒等南歸人士,稱他們為“歸正人”,時時防范并限制其職權。稼軒不滿,故借詞寓意,仿佛是說:我等本大宋臣民,冒死南歸報國,奈何執政強分正邪,視若外人,使我輩長寄人廊廡之下耶!
誤解文意,學者也在所難免,并非都是沒有根底的年輕人,故言讀懂并不容易,真正理解了,評析、鑒賞自然也就不難了。
(代 序)
盡管對中國的韻文學的研究對象、范圍、目的、方法應該是什么,大家的看法不盡一致,但韻文學是文學的一部分而且是就文學形式的體裁特點而言的,這大概不成問題吧。由此想到對古典詩詞的研究,體裁特點也是不應忽略的一個方面。
以往對詩詞的研究,多從一般文學發展史的角度進行,有人稱之為縱向研究;現在,又有人提出還應進行橫向研究,研究文學在這一時代與社會、政治、經濟以及其他意識形態的關系,然后把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結合起來。這自然是能使研究工作深入的很有卓見的建議。但我覺得這還不夠,還應該把文學的內容研究與形式研究結合起來。
詩歌形式的研究(包括研究它與內容的關系),我以為不能不注意詩歌的體裁。以往的研究,多半總是只注意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有用什么表現手法,諸如比喻、象征、想象、夸張,或者語言精煉含蓄,自然流暢、有節奏感,用典或白描,以及藝術風格如何等等,卻很少結合體裁特點加以論述,即使談到體裁,也只限于詩律學的范圍。似乎一首近體詩與一首古風的差別,就在于一則有字句限制、格律規定,一則沒有;律詩與絕句的差別,似乎只是律詩八句,絕句四句,“絕乃律之半”。這樣,就很難說明律、絕同是近體,為什么杜甫的律詩(尤其是七律)筆力勁健,人難匹敵。而他的絕句就未能稱雄于一時;李白寫絕句是拿手,而寫律詩(尤其是七律)則非其所長。邊塞詩派總擅長歌行,田園詩派多工于五言短詩。王維的《夷門歌》、《隴頭吟》、《老將行》、《燕支行》諸作,和他的《輞川集》、《皇甫岳云谿雜題》組詩,不但題材各別,風格迥異,選擇的體裁也是不同的。李白的古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與歌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都是極自負的話,可是一則從容和緩,一則奔放不羈。如此等等,也都與選擇詩的體裁特點有關,而決非平平仄仄的格律常識可說明的。
我國傳統的詩學是很講究體裁特點的,對詩的各體都有過不少論述,有的是說得相當精辟的。這也許與他們自身都有創作實踐經驗有關。現在研究詩詞換了路子,多不注意及此,這是一個缺陷。
京劇、越劇、歌劇、舞劇、話劇……雖然同是舞臺劇,如果不顧及它們各自的特點,而用同一尺度去衡量,比較和評論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是很難說得中肯的。研究詩歌,也必須弄清各體的特點和適應性,道理是一樣的。可惜這方面的研究,已長期被忽略、冷落了。我在杭大任教時,給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過“唐詩體裁研究”的課,就是想引導學生也注意這方面的研究。因為我發現上過中國古代文學課的學生,有的還弄不清樂府與古、近體詩究竟是什么關系。最近,讀到一篇發表出來的文章,在談唐詩的體裁種類時,把七言古體與歌行體分作兩類。其實,這是不妥當的。在唐代,歌行就是七古,七古都叫歌行,并非兩類。那時,五古、七古的名稱還沒有,所謂古體、往體、古風、古詩,是指唐以前就有的聲調未協的五言詩;而七言詩和長短句詩,唐以前除了個別詩人如鮑照等仿樂府歌行而作外,一般詩人都不寫或很少去寫,七言成為文人普遍創作的一種詩體還始于唐代,而長短句詩成為文人普遍創作形式則始于盛唐。所以唐人不把七言稱作古體,而只叫歌行。宋元之后,稱之為七古,那也只是因為樂府歌行對唐來說,是古已有之的。這一點,明代的唐詩學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簽》的《體凡》篇中已經提到了;我最近有一篇《什么是歌行?》的文章發表(《古典文學知識》1987年1期),也說了這方面的問題。
總之,我覺得詩歌體裁是應該充分利用前人取得的經驗與成果加以系統研究的一個領域,只要深入下去,一定會有很多發現的。我準備繼續在這方面下點功夫,同時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一起來共同研究它。
(原載《中國韻文學刊》總第1期“韻文筆談”欄目,題作《詩歌形式的研究不能不注意詩歌的體裁》)
治學雜談——讀懂并不容易
治學之道,人人各異,悟性高低,功力深淺,成就亦自不同。自知學淺識陋,應邀為文,不無慚愧。又所言多半常識,非有高見;片言斷想,不成系統,姑且稱之為雜談。
喜歡古典詩詞的年輕人,常以為讀懂詩詞容易,特別是在現在各種注釋本已出版得比較多的情況下,以為遇到難懂的詞句,看一下注釋就解決了,所以總把注意力集中在看人家如何評析鑒賞上,而忽略自己細心研讀原作。我以為這不是有效地提高自己對詩詞的閱讀和鑒賞能力的好辦法。出色的評析鑒賞,必須建立在正確理解作品的基礎上;除理解詞義外,還應包括作者為何要這樣寫。這一最基本的功夫,要做到家并不容易。翻看前人的詩評、詞評,就會發現有的評說由于對作品理解有偏誤,而說不到點子上;今人的鑒賞文章,情況更嚴重,一首幾十字的詩詞,可以寫上幾千字的文章,可仍不免在理解原文上出錯。試舉數例如下:陳與義《和張矩臣水墨梅》詩:“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玉妃,即楊貴妃,因其白凈而喻梅花。詩的后兩句用典,有注本引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朓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這都不錯。但說到句意時稱“這兩句是以梅花一塵不染的品格自勵”,就誤解了。其實,用此典是因為詩詠“水墨梅”的緣故。真梅是白的,畫梅是黑的,所以用素衣化緇典,同題后一首詩有“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語可證。
陸游《度浮橋至南臺》七律前半云:“客中多病廢登臨,聞說南臺試一尋。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系大江心。”南臺,島名,在福州外閩江中,亦稱“南臺山”。有人因“九軌(謂往來車多)”句寫“度浮橋”,便以為“千艘”句寫所見江上船只眾多景象,其實是誤解。原意兩句都寫浮橋,浮橋無墩,橋面架于一字排開的許多船上,故謂。可見,讀詩詞一點也粗心不得。其中近體詩、詞的題目、小序尤須留意,古人從不隨意題寫,有時那幾個字、一兩句話,便成一篇內容的綱。這一點,讀多了就會知道。
再如辛棄疾《滿江紅•題冷泉亭》詞,是題在杭州靈隱飛來峰腳下的冷泉亭上的,其結尾說:“恨此中、風物本吾家,今為客。”有箋注說:“‘吾家’,指濟南。”這是想當然的解說,是不對的,問題出在沒有弄懂句意。后來寫鑒賞文章的人便據此而說冷泉亭景物“有和作者家鄉(濟南)相似的地方”,作者是恨“故鄉永遠回歸不得,只能長期在南方作客”,是“觸景懷舊”等等。辛棄疾突騎渡江歸宋后,從未說過懷念淪陷的山東家鄉而可惜回不去的話,反而自辯道:“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水龍吟》)怎么現在卻恨起“在南方作客”來了呢?這是說不通的。再說“本吾家”三字也不能解成“似故鄉”,它是與“今為客”相連對舉的,意思是說,本來就是自己家里的,現在反而當作客人了。這指什么呢?指“此中風物”,即飛來峰。題冷泉亭,必詠飛來峰,亭在峰下,是一回事,此亭至今仍懸一楹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來?”相傳“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茲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印度)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淳祐臨安志》)故飛來峰又稱鷲嶺。辛詞上闋末云:“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是當年、玉斧削方壺,無人識。”已說不信峰從國外飛來。下闋結尾,照應此說,謂此山本自家所有,今反以外來客視之,所以為恨耳。這是在借題發揮,寫自己的牢騷。南宋當局歧視稼軒等南歸人士,稱他們為“歸正人”,時時防范并限制其職權。稼軒不滿,故借詞寓意,仿佛是說:我等本大宋臣民,冒死南歸報國,奈何執政強分正邪,視若外人,使我輩長寄人廊廡之下耶!
誤解文意,學者也在所難免,并非都是沒有根底的年輕人,故言讀懂并不容易,真正理解了,評析、鑒賞自然也就不難了。
作者簡介
蔡義江,1934年生。著名紅學家、學者、教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浙江寧波人。1954年畢業于杭州大學(現改為浙江大學),留校任教于中文系、新聞系。1978年借調至京,籌創《紅樓夢學刊》,成立中國紅學會。1986年,調任民革中央常委、宣傳部部長,創辦團結出版社,兼任社長、總編輯,兼教于京杭高校。為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委員。現為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中國古典文學普及研究會副會長。在唐宋詩詞、紅學研究方面成績卓著。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現稱《鑒賞》)、《論紅樓夢佚稿》、《紅樓夢》校注、《蔡義江論紅樓夢》、《紅樓夢叢書全編》、《稼軒長短句編年》(香港上海書局)、《辛棄疾年譜》、《唐宋詩詞探勝》、《清代文學概論》(日本每日交流社)、《宋詞三百首》詳析(臺灣建宏書局)等。
目次
應重視詩詞體裁研究(代序)
上編 詩詞體裁
古風
“古風”的所指
興起與演變
感遇詩
山水田園詩
新樂府
短古
長篇
與律詩的界線
歌行
歌行的名稱
歌行與樂府
歌行的流變
歌行的作法
律詩
律詩的題目
題目與內容必須完全一致
全詩必須始終環繞著題目寫
題目的每層意思都必須寫到
題目或主要題意須“開門見山”,即在首聯中便寫出
律詩的章法
首聯起
頷聯 承
頸聯 轉
尾聯合
律詩的句法字法
律詩的因拗取峭
絕句
絕句的名稱
絕句的興起
絕句的特點
少:時間上,過程短暫;空間上,畫面干凈
小:借細節或瑣事來表現詩旨
了:語言明白,一看就知,一聽就懂
常:常見、常有、帶普遍性的題材和表現形式
藏:含蓄,耐人尋味,不一覽無余,言有盡而意無窮
長:韻味悠長,情意綿長,一唱三嘆有余音
詞
詞的興起
詞的名稱
詞與樂府的根本區別
詞與詩在體裁特點上的區別
詞的發展與演變
曲
曲的名稱及其含義
曲的豪放派
曲的清麗派
……
下編 詩詞鑒賞
盛唐三大家詩探勝
宋詞解讀
附錄
雜論
乙夏承燾師
治學雜談
后記
上編 詩詞體裁
古風
“古風”的所指
興起與演變
感遇詩
山水田園詩
新樂府
短古
長篇
與律詩的界線
歌行
歌行的名稱
歌行與樂府
歌行的流變
歌行的作法
律詩
律詩的題目
題目與內容必須完全一致
全詩必須始終環繞著題目寫
題目的每層意思都必須寫到
題目或主要題意須“開門見山”,即在首聯中便寫出
律詩的章法
首聯起
頷聯 承
頸聯 轉
尾聯合
律詩的句法字法
律詩的因拗取峭
絕句
絕句的名稱
絕句的興起
絕句的特點
少:時間上,過程短暫;空間上,畫面干凈
小:借細節或瑣事來表現詩旨
了:語言明白,一看就知,一聽就懂
常:常見、常有、帶普遍性的題材和表現形式
藏:含蓄,耐人尋味,不一覽無余,言有盡而意無窮
長:韻味悠長,情意綿長,一唱三嘆有余音
詞
詞的興起
詞的名稱
詞與樂府的根本區別
詞與詩在體裁特點上的區別
詞的發展與演變
曲
曲的名稱及其含義
曲的豪放派
曲的清麗派
……
下編 詩詞鑒賞
盛唐三大家詩探勝
宋詞解讀
附錄
雜論
乙夏承燾師
治學雜談
后記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