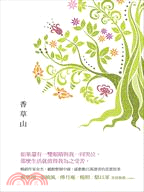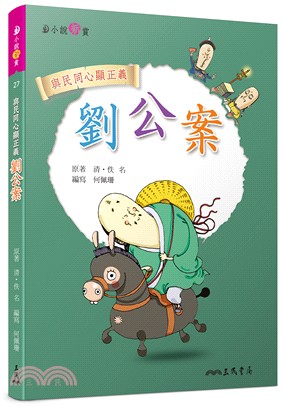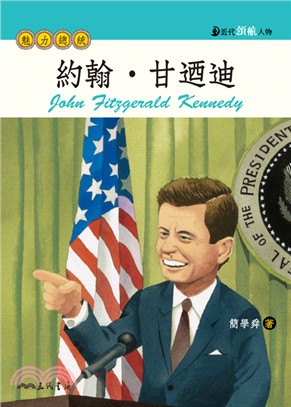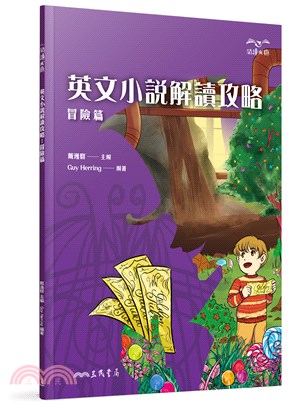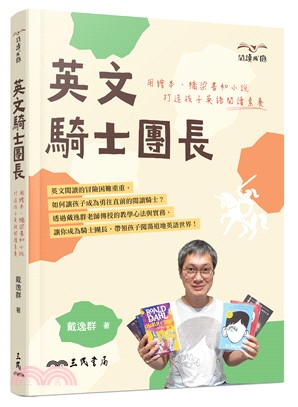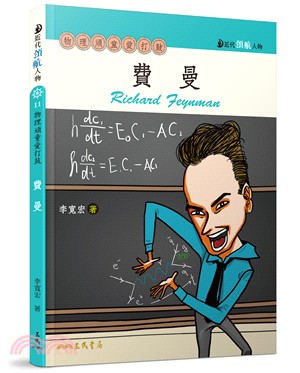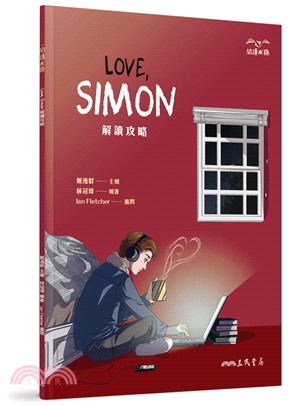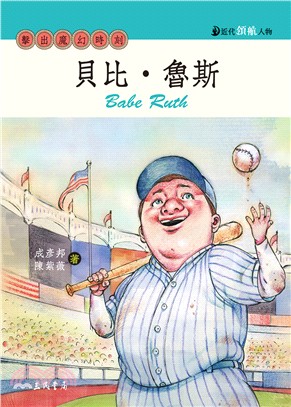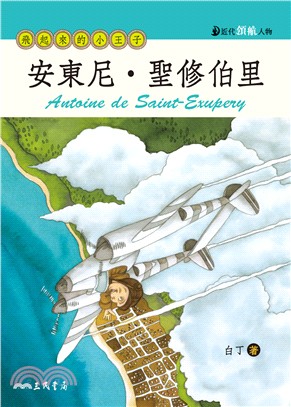商品簡介
「良人哪,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香草山」之名源自《聖經》最優美的情詩集《雅歌》,隱喻著一個純真而美好的、有信、有望、有愛的世界。作者希望藉由這部作品重燃世人對愛的信念,認識到在庸常的物質生活之上,還有一個不可征服的心靈與精神生活。
《香草山》以情書和日記為藍本,如實地記錄了余杰與妻子的生命軌跡與心靈地圖。它既是一個愛情故事,也是出生於七十年代的中國新生代的一部心靈史。書中描述了「天安門後一代」對愛情、理想和正義的執著求索,以及對社會黑暗的反思與批判。文體遊走於抒情和議論之間,對於善與惡、笑與淚,人間的苦難與人性的光輝,省思深刻,文辭雋永,許多優美靈動的段落更猶如獨立的散文詩,或富於哲思,或撫慰人心。
2002年,《香草山》由中國的長江文藝出版社首度發行,備受大學生和年輕人的喜愛,印行近五十萬冊。那段期間,在許多大學的學生宿舍裡幾乎是人手一冊。2011年,余杰針對海外讀者作了更大幅度的修訂,除了恢復簡體字版被刪除的禁忌話題,並在家族故事中增加大量細節,力求通過家族史來呈現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社會變遷與磨難。
作者簡介
余杰
1974年生於四川成都平原一個美麗的小鎮。聰慧早熟,十三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就讀北大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期間,創作了上百萬字的作品,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廣為流傳。
1998年以雜文集《火與冰》一書驚動文壇和學界,該書嚴厲批判中國大陸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等層面的弊端,迅即引起巨大迴響,印行上百萬冊,並榮獲中國最大的連鎖書店席殊書屋好書俱樂部「1998年十大好書」。
有「北大才子」之稱的余杰,以犀利的言論轟炸沉悶的知識界,引領一時風騷。有人將他的少年得志比為五四時期的胡適,有人將他喻為當代魯迅,更有不少人將他和八○後人氣最旺的青春作家韓寒並列。
因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宣揚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起著作全面遭禁。儘管如此,仍筆耕不輟,先後受邀到歐美及港台數十所大學和學術機構訪問,並曾獲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接見。近年來已在港台出版了十幾本政論集,成果豐碩,視野更廣。
名人/編輯推薦
在當代中國,余杰是一個不可不被認識的名字。他的聰明早慧,犀利又博學的文才,早已成為傳奇,而如今《香草山》則讓我們更貼近余杰的內心世界。這本書彷彿五四青年精神的再現,同樣勇於揭露自己的內心,也同樣充滿了對於時代的憤懣,吶喊與掙扎,堪稱是本世紀中國的最佳寫照。——郝譽翔,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作家
余杰的出現既是一個異數,也是一種必然——平庸的生存需要激情之思的衝擊,萬馬齊暗的輿論環境需要銳利吶喊的刺痛,刻意製造出的繁華盛世需要批判勇氣的警醒,被淘空的記憶需要真實歷史來餵養,靈魂荒漠需要良知信仰的滋潤,普遍的人性冷酷更需要愛的溫暖。——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年輕而又精英的男女主人公在相互喃喃細語愛的誓言的同時,以各自的家族史為紐軸,回顧文化大革命等殘酷的言論彈壓,同情現在都市失業者、農民的悲慘生活。在眾多的中國作家酣醉於高度經濟成長、忘卻人權問題、弱者敗者的救濟問題的今日,本書以主人公充滿正義感的社會批判,令人耳目一新。——藤井省三,日本著名漢學家、東京大學教授
《香草山》是一部情書和札記,盛載著二顆心的純真交往,記錄他們共同尋覓人生意義、愛與真理的心路歷程。作品從《聖經》擷取靈感,猶如作者書寫自己的《雅歌》,談論的內容廣闊,包括中外人物和故事,引用詩歌及典故,讀者享受甜美意境外,更如暢泳於壯闊的思想江瀾中。——香港湯清文藝獎獲獎評語
序
「我一直以為,支撐我生活的動力,便是羅素所稱的三種單純而又極其強烈的激情: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於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而在這樣的動力下生活,註定是孤獨的,無盡的、近於絕望的孤獨。」一封讀者的來信,字字句句敲擊著作者的心扉,於是讀者與作者之間,開始透過書信分享彼此的思想與情感、渴望與追尋,愛情翩然而至,他們也堅定了攜手共度人生的信念。
書為媒,對於一本書而言,何嘗不是它最美好的功用?
以美好的生命激勵美好的生命,不正是作家引以為豪的使命?
那麼,《香草山》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它不是情書,不是小說,不是自傳,它是一部誕生在浮華時代的澄明清澈的心靈史。
它彰顯了個人內心的強大,強大到足以戰勝一切外部環境的束縛。
在中國,《香草山》曾經是大學校園裡人手一冊的枕邊書,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不少讀者表示,《香草山》讓他們看到了愛情的美好、真理的可貴、正義的崇高,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帶給他們心靈深處的安慰,使他們有了繼續追求幸福的力量。
豆瓣讀書網站上,一位網友如此留言說:「這是一部看得人心底軟軟地疼,又淡淡地歡喜,同時心中充盈著清輝似的光芒的書。看它的感覺是如此寧靜、如此純潔;就像一條花瓣的小溪,夢幻般地在血管裡汨汨流動;又像是一隻破殼的小雞,在早春的槐花香中絨絨的一團。」
《香草山》不僅是一本書,香草山更是一個地名。那裡藍天白雲,水草豐美,如作家楊牧在〈自剖〉一文中所說:「香草山,那雲霧深處,那麼至美和平安樂的國度。我們將會動身前去,那個美麗無人的國度,看草原上的小花,看草原上的羊群和麋鹿。……世界上每個人都該有個完美的香草山,讓他們在那山裡沒有憂慮地徜徉,讓他們離開猜忌和怨毒的俗塵,讓他們帶著笑容入眠。」
這不單是個夢,如果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心,這就是觸手可及的現實。
《香草山》正體字版的問世,讓這本在中國無法再印行的書,能被台灣的讀者所知曉;而這段靜美而敞亮的生命,也多了一群新的分享者。
願這個故事成為您生命的祝福。
目次
第一章 信 9
那封信,像一顆小石子一樣擊中我的心
第二章 智齒 53
那顆智齒,讓我們一起疼痛
第三章 葡萄園 97
你如同一棵鳳仙花,來到我的葡萄園
第四章 蝴蝶 139
蝴蝶沒有死去,只是隱沒在夜色中
第五章 水井 185
從幽暗的水井中,打撈滿滿一水桶的星星
第六章 蘆葦 219
壓傷的蘆葦,它不折斷
第七章 睡蓮 257
此刻,你的身體和靈魂,像睡蓮一樣緩緩向我綻放
第八章 泉水 301
愛情像泉水一樣流淌,從此不再有死亡
第九章 蜂蜜 339
你從遠方來,我們一起採蜜築巢
書摘/試閱
寧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覺很冒昧給你寫信。我原是不能接受給陌生人寫信這樣冒昧行為的人。
我曾經有過數次被文字打動的經歷,也曾有過與這文字後面的心靈結識的衝動。但出於漠然悲觀的天性,最終寧肯默默地與文字交流。迄今為止從未寫過一封給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給了我極大的打擊,因為他就是我曾經想要寫信的人。而如今,信還在心裡醞釀,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體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與悔恨。
世事喧囂,人生寂寞。我一直以為,支撐我生活的動力,便是羅素所稱的三種單純而又極其強烈的激情: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於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而在這樣的動力下生活,註定是孤獨的,無盡的、近於絕望的孤獨。
我想,在這片已經不再蔚藍、不再純潔的天空下,如果還有一雙眼睛與我一同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吧。
於是,因為王小波,因為孤獨,因為生命的脆弱與無助,我終於提起了筆,給你,嚴重而真誠。
作個不恰當的對比,許廣平第一次冒昧給魯迅寫信的時候,提了一個大而無當的問題:人生遇到歧途怎麼辦?我自覺我這封信雖沒有提問,卻也大而無當,不知所云。可魯迅認真回答了許廣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卻從未絕望。你呢?還有一顆易感而真誠的心嗎?
最後,我要告訴你,我是個女孩,美麗,也還年輕。
寧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寧萱的日記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起床來鬼使神差地給一個陌生人寫了一封信—除了他寫的一本書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
很久沒有寫信了。雖然每天都坐在電腦前,但在鍵盤上敲出的都是與心靈無關的文字—是比八股還要八股的專案可行性報告、是格子裡填滿資料的報表、是給其他部門的例行公事的通知書……日復一日,這些文件已經塞滿了我的大腦。
忽然,我覺得很累、很累。我來到這家龐大的外資公司已經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個二十剛剛出頭的小女孩,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當上了部門經理。我上學得早,因為父母工作忙,沒有時間照料我,讓我五歲便上小學了。我在小學和中學又各跳了一級,所以上大學的時候只有十五歲。大學畢業還不到二十歲。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幾天的聚會上,畢業之後難得一聚的大學同學都異口同聲地這麼說。當年在我下鋪的女孩,還只是銀行的一個普通營業員。最有「出息」的男同學,也僅僅是政府部門的一個小科長。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這些不是我夢寐以求的。我內心有一種聲音在對我說:「你並不屬於這裡。」這個聲音每天都在心靈深處響起,由遠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紅的熔岩在幽暗的地殼中翻湧著。那麼,我的靈魂究竟屬於什麼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裡才能夠獲得寧靜和愉悅呢?
公司占據整個的一座大廈,我的部門在十樓,整層樓就是一間開放式的辦公室。每個職員有一個透明的隔間。幾十個職員,像一群家養的鴿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樣的「籠子」裡。
巨大的中央空調,每時每刻都在發散著無窮的能量,冬暖夏涼。我不喜歡空調,我寧願房間裡的溫度與外面的溫度一模一樣。無論冷也好,熱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溫度最好。可是,我們的皮膚已經適應了空調製造的虛假溫度,反而無法適應大自然本身真實的溫度。我們的肌膚在虛假的溫度之中麻木了,我們的心也一樣。我們親手把自己裝進一個虛假的盒子裡。
我每天對著電腦,用電子郵件和電話跟同事們聯繫。儘管大家同處一室,卻談不上有什麼心靈的溝通。這就是「現代化」的公司中的慣例。在公司安裝著藍色玻璃的辦公室裡,每個人各司其職: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處理事務,一動不動;或者匆匆地走來走去,沒有片刻時間左顧右盼。每個人都表情嚴肅,卻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然而,偌大的公司裡,沒有一個人能夠與我一起分享看風景時的心情。英國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說《窗外有藍天》,很久以前看過,書中具體的情節我已經記不清了,卻記得那個小小的、簡單的、窗外有片藍天的房間。
我沒有一個房間,但我有一個角落。
我經常往遠方眺望,遠方依稀可見煙雨迷濛的瘦西湖,瘦西湖邊上白塔的塔尖也還有模糊的輪廓。可惜,湖邊的高樓越來越多,視線也越來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把樓房越蓋越高,為什麼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人們把鴿子關進鳥籠,最後自己也住進了鳥籠。
我喜歡童年時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個小院子曾經就在瘦西湖的邊上。屋簷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跡,木梁上的燕子窩中有時落下一兩片羽毛。可是,在幾年前的房地產開發熱中,這個可愛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連同我童年溫軟的記憶。
我喜歡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歡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於同事對我說,你這麼年輕,為什麼總是穿著冰冷的、壓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對這樣的詢問,我笑而不答。心中卻隱隱作痛。黑色是內斂的、是悲哀的、是冷靜的、是堅強的。記得一篇小說中寫道:「很多有傷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為這樣不容易讓別人看到疼痛。」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願意讓旁人窺視到我的內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籬。我讓自己與外部世界保持著一分距離。像一隻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蟲,凝固,但是安全。
讀那本名叫《火與冰》的書,也有好長一段日子了。書中那些剛強的句子打動過我,更打動我的卻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邊沒有書。我當時讀的那本已經很破舊的書,並不屬於我。讀過之後,我也不想去書店買一本新的。因為讀過之後,這本書在「精神」的意義上就已屬於我了。書裡的好些句子我幾乎能夠背誦下來,也能夠感受到作者寫作時的心情。它們讓我如此牽腸掛肚。
從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著雨,天色灰濛濛的,像《紅樓夢》裡面那些讓作者和讀者一起哭泣的、所謂「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章節。此時此刻,我想起《火與冰》中那些憂憤的句子。在北國的風沙中,他有衝冠的怒髮嗎?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顆憂憤與感傷的心。
我給他寫信的時刻,不是我有意挑選的,卻恰好是一個孤獨與哀痛交織的時刻。他一定跟我一樣需要安慰。他身邊有安慰他的朋友嗎?
我不知道他的詳細地址以及與他有關的一切。然而,讀過一本他寫的書就足夠了—從「物質」的意義上來說,那本書我僅僅擁有過一天(更準確地說,一個夜晚)的時間。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進公司以後唯一一件「假公濟私」的事:我把這封用一頁便籤寫就的短信,放進一封特快專遞裡,填好他的姓名地址。在吩咐祕書寄出一大疊商業信件的時候,把它混在公司的信件中發了出去。我實在怕自己沒有勇氣走到郵局親手投出這封突發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顯示,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那麼,地址就簡單地寫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園讓我魂牽夢繞。中學時,我曾經沒日沒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後還是沒有能夠踏進去。就因為高考沒有發揮好,差了幾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樣,不情願地飄落到西湖邊上的那座校園裡。「暖風熏得遊人醉,西湖歌舞幾時休」,西湖美則美矣,卻不是一個念書的好地方。大學四年,濃濃的失落感一直伴隨著我。
畢業後,漸漸忘卻了有關校園裡的一切。照片都是會褪色的,記憶也一樣;花朵都是會飄落的,夢想也一樣。廷生的出現,重新勾起我昔日的夢想和創傷。他屬於那座校園,那座蔡元培和魯迅的校園,那座「五四」青年的長衫和白圍巾飄飄蕩蕩的校園,那座在血與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園。那座校園已經成為史詩,成為紀念碑,成為神話。北大的意義,早已經超越了一所大學。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麼的幸運啊。
他能否收到這封信,在我的信寫完以後,已經不重要了。寫信是對虛無的一種反抗。但寫完以後,我寧願忘記它,讓它像一個夢一樣在我的生命中消失。舉重若輕。
正如《世說新語》中那個有名的「雪中訪戴」的故事。我很喜歡這個古老的故事。長袖飄飄的王子猷、鵝毛般的雪花、披著蓑衣的船夫、劃在溪水中的木槳……我要是畫家,我會畫這樣的一幅神韻流動的水墨畫。那麼,我也來學學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還得去上班。睡吧,睡吧。今天的日記寫得太長了。
廷生的日記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每年六月初的這幾天,我都會離開校園。這幾天,空氣中瀰漫著血和鐵的味道,我不願待在這個麻木不仁的校園裡。十年前那個六月三日的深夜,我們全家人在收音機前聽「美國之音」,聽到裡面傳來的劈哩叭啦的槍聲。那一夜,我完成了我的成年禮;那一夜,我發誓要考北大。但是,當我真的考上北大之後,我才發現一切都變了,北大已經不再是北大。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真是兩個迥然不同的時代。
我「失蹤」四天之後回來,校園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東方」的課堂上,仍然是擁擠不堪。幾乎每個學生宿舍都有賺錢的妙招:有人賣速食麵,有人賣電影票,有人賣進口CD。誰都想成為鄧小平所說的那種「先富起來」的人。才十年的時間,這個校園就已經物換星移,滄海桑田。
我依舊去圖書館,去五樓的那間港台文獻中心。這間閱覽室少有人來,我獨自躲在角落裡,一個上午的時間一眨眼就過去了。這裡有不計其數的「反動書籍」,據說是一次國際書展之後,主辦單位將所有港台版的書籍全都贈送給了北大。我是偶然發現有這個大寶藏的,從此便每週都會來上三五次。這間閱覽室的書,只能在裡面看,不能外借,所以我經常到這裡一連看上三四個小時的書。這裡有台灣出版的與大陸觀點截然相反的近代史著作,有台灣早期「黨外運動」先驅者的傳記,我甚至找到了台灣出版的方勵之、劉曉波等八十年代風雲人物的著作。本來就有「反骨」的我,讀了這些反動書籍之後,就更加反動了。這間閱覽室給我的思想啟蒙,超過了北大的任何一個老師—八九之後的課堂上,大部分老師都謹言慎行,斟詞酌句。
比起當年的知青一代人來說,我能夠自由地閱讀這些「反動書籍」,簡直如同生活在天堂之中。六十年代,被放逐到農村的知青們,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弄到幾本「禁書」來讀。所謂「禁書」,就是「文革」前翻譯出版的一大批「內部讀物」,包括被稱為「灰皮書」的社科類書籍和被稱為「黃皮書」的外國文學書籍。當時在山西中部中山村當知青的作家鄭義,後來回憶說:「勞動是艱苦的。看書同樣是艱苦的。每天下了工,吃了飯,已經是筋疲力盡。又沒有電,連煤油燈都沒有。最初的日子裡,我們只有墨水瓶、藥瓶自製的『小煤油壺』,豆大的燈焰下,擠不了三四個人,於是只有輪流看。第一批從晚飯後看到十一、二點;第二批從十一、二點看到三、四點;再叫醒第三批接著看到天明。特別是當外村傳來好書,限定兩三天還,大家想自己做點筆記,唯一的辦法就是換班看,通宵達旦。回憶起來挺苦的,睡得正香,硬要掙扎著起來『換班兒』!只有走出窯洞,在雪地上捧把雪擦擦臉,看山區格外明亮的星星月亮,直到凍得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再趴到小炕桌上看。但那陣兒不覺得苦,因為不看這些書不知道該怎樣往下活!」
如今,我卻能在窗明几淨的圖書館,安安心心地讀這些好書。中文系的課程不多,有意思的課程更少,所以很多時間都可以由自己支配。窗外楊絮飄飄,如同六月的飛雪。讀書讀累了,就抬起頭來觀看一會兒滿天飛舞的楊絮。每片楊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們與人一樣,不由自主地在空氣裡飛翔,然後飛落塵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遠處,塔身被樹蔭簇擁著。它已灰塵滿面,像一個不合時宜的老人,冷冷地看著這個熱鬧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疊信件。有編輯寄來的刊物,有老朋友的來信,當然更多的是素不相識的讀者的來信。其中,顯得突兀的是一封來自揚州的特快專遞。誰寄來的?在記憶的倉庫裡搜尋了一陣,我在揚州確實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信封的後面留著一個外國公司的名稱和地址,以及一個有些模糊的「寧萱」的名字,它們讓我在心裡嘀咕了半天。我與公司之類的機構向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而「寧萱」卻又是一個充滿詩意的、讓人遐想聯翩的名字。
藍色的、硬皮的、碩大的特快專遞信封,仔細一掂量,裡面似乎空空如也。
這是誰寫來的信呢?這個「寧萱」究竟是誰?儘管差不多每天都會收到幾封陌生讀者的來信,卻很少是用特快專遞來郵寄的。讀者們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舊,也許是因為這路上顛簸太久的緣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遙遠的學校和鄉村,與高樓大廈無關。
撕開封口,原來是薄薄的一頁公司便籤,信的內容只寫了大半頁。字跡很小,很細,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卻一眼就能夠看出是女孩子的筆跡,每個字都帶著幾分柔媚的心思。
在學校裡的「家園」快餐廳裡,我買了一份速食,一邊吃,一邊懷著姑且讀讀的心態攤開信紙。剛剛讀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換了一種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來。因為,這封信的內容幾乎不忍卒讀—它像一塊小石子,準確地擊中了我的心臟。它沉重得讓我有窒息的感覺。
陽光從窗戶射進來,薄薄的信紙在陽光下是透明的。寫信人的心呢?
顯然,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著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著相同的創痛。在這些文字的背後,黑暗與光明兩種力量正在嚴峻地較量,悲哀與快樂兩種情緒正在劇烈地翻騰。一時間,兩種力量和兩種情緒都難分高下。這個關鍵時刻,正是需要外力來幫助的時刻。所以,她給遠方的、陌生的我寫信。她向我—一個她認為值得信賴的朋友,尋求精神上的幫助。
這個時代,還真有這樣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樣嚴酷的問題?
進入北大這些年,我已然是個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異端,不為大多數的同齡人所理解和認同。幸而,北大還有蔡元培時代的精神和學統零零星星的殘留,「寬容」是它最偉大的品質。所以,儘管不少人把我目為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時不時地加以嘲笑和調侃,卻也於我無害。
在這裡,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夠在這種「不干涉主義」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經很滿足了。在中國,這樣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麼,寫這封信的叫「寧萱」的女孩呢?她會不會也被周圍的人視為「異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獨。從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廈裡工作。那種摩天大廈好似遠古的恐龍,在那裡,她會受到傷害嗎?
我應該給她回信。我願意給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顆擱淺在沙灘上的貝殼。
廷生的信
寧萱:
你好。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
讀到你的信的時候,我剛剛從郊外返回學校。一路上,我正在想,離開校園好幾天了,平淡如水的學院生活,會不會發生些許的變化呢?我的郵件該堆積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門的郵件之中,我拆開了你的信。你的信深深地打動了我。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為王小波,因為魯迅與許廣平,更因為羅素的那句話。同時,你的信之所以打動我,還有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理由—因為我的孤獨和脆弱,因為你的「嚴重而真誠」。
文字是我與外界進行溝通的重要管道。在一個喧囂的時代裡,在一個人人都在談論「市場經濟」的時代裡,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極其困難。文字卻能穿越諸多的阻礙,連接起一顆又一顆陌生的心靈。這兩年來,我受到許許多多的干擾。有讚譽,也有辱罵,有「捧殺」,也有「棒殺」,卻很少獲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鳴。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夠在別人內心深處引發悠長的回音,是我生活中無法言喻的快樂。
今天,在你的這封信中,我發現了一種至誠至真的精神共鳴。謝謝你。
寫作的本質固然是孤獨的,但在寫作的過程中,人也在拚命地抗拒孤獨,就如同卡繆筆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石頭是否會再次掉下山,他並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樂、他的幸福,已經熔鑄在每一次的搬運、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個內心最幸福的悲劇演員。
然而,如果一個人永遠處於無邊無際的孤獨中,無論他有多麼堅強,他的寫作和生活都很難長久地堅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塊塊賞心悅目的綠洲。在孤獨的背後,支撐我的東西正像你信中所說,是「對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當然,在這沒有邊際的悲憫之中,首先是對自我這個無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憫。
你的信中提到許廣平給魯迅寫信的故事。當年,魯迅在一個不尊重人的國家和一個不尊重人的時代裡,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而戰鬥,儘管最後他還是被黑暗所吞沒。這黑暗既有外在的黑暗,也有他內心的黑暗。從他身上,才看到人內心的黑暗原來是深不可測的。我喜歡魯迅的散文集《野草》,如學者李劼所說,它有如荒涼的墳地,亂草在風中搖曳,天色晦暗不明,時空晨暮難辨。在誰也看不見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裝犧牲。
許廣平在信中提出的難題,魯迅在覆信時作出了回答。他說,「人生」的長途,最怕的是遇到兩大難關。一是「歧路」,二是「窮途」。我想,我們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窮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們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錯誤的路。我們的選擇很明瞭,也很堅定。因此,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存在真正的「歧途」、並不存在走錯路的危險。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正道已經走到了盡頭,無路可走的時候,該怎麼走呢?
王維的選擇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魯迅的選擇是:「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裡姑且走走」。我常勸說身邊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輕的弟妹們,不妨選擇王維的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輩子「在刺叢中求索」—荊棘會將我的赤腳扎得鮮血淋漓,會透到我的骨肉裡去。
這是我的命運,我不能、也不願違背。你呢?
我們這個時代的惡,並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比魯迅那個時代的惡要少;相反,我認為,我們時代的惡更加氾濫、更加凶險。當然,這種「惡」也存在於我們身上、我們心中。
我在對抗外部的惡的同時,也在清除著自己內在的惡。我在內外的夾擊中依然不願意放棄戰鬥。尤其是我自己內心的惡,它將伴隨我的生命始終,我也將不懈地與它戰鬥始終。
但是,我不會因為世上有太多的惡而感到沮喪。沒有惡,善也就沒有意義了。我也堅信,那些看上去無比強大的邪惡勢力,最後必然會衰弱、退縮,進而消亡。只要我們堅守內心的善,也許在一個漫長的黑夜之後醒來,那無所不在的惡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正如同《聖經》詩篇所說的:「作惡的,必被剪除……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這段經文帶給我很大的安慰。
這封信越寫越沉重。我幾乎都快忘掉你是一個「美麗,也還年輕」的女孩了。本來,你的來信就夠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為沉重的分量。就好像在一張漆黑的紙上再用濃墨寫字。可是,我實在寫不出輕鬆的句子來。就讓我們彼此分擔對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給我寫信的時候是四日的深夜。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日子,十年前的那一天,我十六歲的生命被徹底改變。
今年的六月,北京的天氣已經很熱了,就像一個巨大的蒸籠,讓人感到透不過氣。
北京是一個官與商的城市,北京是他們的天堂。六百年帶著血腥氣味的帝王都,像一隻恐龍一樣矗立在燕山的腳下。六百年了,無所不能的歲月可以改變一切。在這裡,流氓變帝王,文人變太監,優孟變大臣,少女變怨婦,無論出現怎樣的怪事,人們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多少個春夏秋冬,官與商們每天都在舉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許還有香噴噴的大盤人肉呈上。他們開懷暢飲,他們大口咀嚼。他們在餐桌上和床笫間隨意決定千萬子民的命運,這就叫「指點江山」。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將相們的幽靈會出來遊動,向後人傳授他們奪取權柄的計謀和殺戮敵人的勇氣。在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度裡,這些經驗永遠也不會過時。
世界變了,有車輛,有霓虹燈;世界沒有變,世界還是他們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門,只有在校園裡還遺留著幾分「家」的感覺。這個校園是城市西北角的一個孤島,它屏障了外部沸騰的波浪,讓我獲得了暫時的安寧。
校門外,車與人都是輪胎飛轉、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築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跡都沒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鮮血和文人的唾液。至於我,永遠都是一個漂泊者。我對北京沒有歸屬感,對已經離開七年的那座四川的小縣城也沒有歸屬感,每次回去,我都感到自己已經是一個外人了。我們真正的故鄉,離我們越來越遠。
這次出城,我選擇的是北京西南郊的檀柘寺。郁達夫在《故都的秋》裡寫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懷的美好景物,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鐘聲」。史書記載,當年檀柘寺人丁最興旺時,擁有僧眾數千人,號稱北方第一大寺。俗話說,先有檀柘寺,後有北京城,可見其歷史之悠久。
如今,這裡只有寂寂寥寥的幾個僧人。在午後的寂靜中,他們在寬敞的經室裡,閑看花開花落。檀柘寺少有遊人來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勝古跡,到處是鼎沸的人聲和旅遊團的小旗幟。和尚們並非身在紅塵外,他們抱怨說寺廟離城太遠,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較城裡的寺廟清苦許多。而我暗自竊喜,因為我此刻的心情正適合這樣淒冷的地方。
據說,這個雅致幽靜的院落,恭親王曾經來住過。
當年,權傾一時的恭親王試圖通過洋務運動富國強兵,卻被保守的「清流」派辱罵為「鬼子六」。後來,他被慈禧太后逼下台,到這荒郊野外的寺廟裡隱居了一段時間。
滿山的松樹,千姿百態。山間的石階,曲徑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處,能夠望到北京城金碧輝煌的宮殿和灰暗破敗的民居。可以想見,一百多年以前,恭親王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敗者,退居深山大廟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蕪、何等悲涼。也可以想見,他在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熱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的京城。時間像流水一樣消磨著人的意志。恭親王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冷冰冰的佛經,無論如何都是讀不下去的。他想拯救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老大帝國卻拋棄了他;他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卻不愛他。
中國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來,改革者和變法者們,哪一個有好下場呢?恭親王不過是他們當中的又一個犧牲品而已。幸虧他是皇族嫡系,喪失權力之後總還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後的譚嗣同們,就只能血灑菜市口了。而在那時,一度神采飛揚的恭親王,早已變成一個沉默寡言、唯唯諾諾的老人。唉,中國,中國,是一個考驗人耐性的地方,是一個把年輕人磨老的地方。
六月,城裡還是酷暑高溫,這裡卻已然有些凜冽的寒意。窗外,能聽見秋蟲的鳴叫。
就在你給我寫信的那個夜晚,我住在寺廟裡,心卻靜不下來,徹夜不眠。耳朵便有槍聲,炮聲,呼喊聲,哭泣聲。儘管十年之前的那個夜晚,我並不在北京,並不在現場,但又彷彿是一名親歷者。人民以膏血奉軍隊,軍隊以槍彈報人民,不圖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牛鬼蛇神之地獄!
後來,當我與「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丁子霖老師見面的時候,她送給我一本寫那些死難的孩子的書,其中包括她的兒子、十七歲的高中生蔣捷連罹難的經過。丁老師在扉頁寫道:「連兒如果在世,一定會跟你成為好朋友!」是的,那張照片上英姿颯爽的蔣捷連只比我大一歲,一定會是我的好朋友!而我又想,如果那個時候,我家在北京,我會不會跟他一樣,因愛國而上街,因上街而中彈,甚至變成躺臥在街頭的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呢?
此刻北大的校園,凝結的空氣像固體般,讓人無法呼吸;周圍一雙雙的眼睛,發出狼一樣的青光。我無法像身邊的同學那樣,若無其事地歡笑著去看電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上托福課。
我拒絕遺忘,因此記憶常常以噩夢的形式降臨在我的現實生活中。
我不願沉默,然而當我正要高聲呼喊的時候,卻發現自己依然失聲。
深夜,是比你寫信的時候更深呢,還是淺一些?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給我寫信以外,你還做了些什麼?
應該說,我比你幸運,我的身邊還有一個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卻只能在寂寞中面對紙和筆。不過,以後你將不再寂寞,你有了我這個朋友。
寫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選擇,或者僅僅是一個巧合而已。
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認識,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神啟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