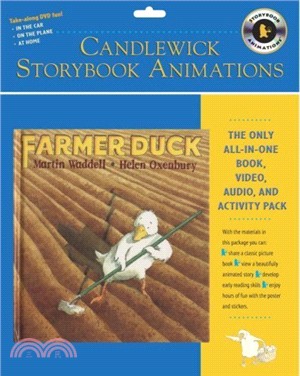商品簡介
《相約在書店》是我國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有關書、書店、出版的隨筆集。共分三卷,第一卷寫自己與書、書店、出版的故事;第二卷是對師友的回憶文章,大部分憶及與文化名人的書緣;第三卷乃作者為一些書撰寫的序言和出版說明。文章簡潔樸實,感情真摯,從容道來,掌故頻出,書香彌漫,可讀性強。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最初的夢
書店
買書結緣
為了讀書
重慶瑣憶
《電通》畫報一案
說“油印”
辦雜志起家
記籌辦《生活》半月刊
五十年前
回憶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
在孤島上海出版的三部名著
第一本書
給毛主席買書
得書日志
漫畫家的贈書贈畫
書香處處
開天窗
《傅雷家書》的出版
卷二
自得其樂
沙老師
一個小學生的懷念
長者贈聯
我的讀書觀
相約在書店
幾件往事
子夜驚魂
曾祺詩箋
我與丁聰
漫畫家與范用
衡宇相望成夢憶
——懷念一氓先生
懷念書友家英
忘不了愈之先生
公已無言遺教尚在
懷念胡繩
心里一片寧靜
——給寶權兄
詩人的題簽
恩師洛峰
永遠懷念雪寒先生
聶耳永生
鄭超麟及其回憶錄
感謝巴老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苦樂本相通 生涯似夢中
——悼祖光憶鳳霞
《天藍的生活》的歸來
——懷念羅蓀先生
卷三
《水》之歌
“大雁”之歌
我與蔣介石
一封感人的來信
談文學書籍裝幀和插圖
書話集裝幀
——致秀州書局
風景這邊獨好
——鐘芳玲的《書店風景》
《讀書》三百期
《新華文萃》——《新華文摘》
少年讀者知多少
——商務印書館百年感言
“漂亮小玩意兒”
——《我的藏書票之旅》代序
關于《莎士比亞畫冊》
《時代漫畫》選印本前言
“我熱愛中國”
——《西行漫記》重印本前言
《買書瑣記》前言
《愛看書的廣告》編者的話
《葉雨書衣》自序
為書籍的一生/汪家明
書摘/試閱
篇章選讀
最 初 的 夢
成為養老金領取者,終于閑了下來。沒事東想西想,想得最多的,是童年的日子。從能夠記事到現在,七十多年了,童年的事情,還很清楚。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潔之地,白紙一張,尚未污染,最可懷念。
甚至還想到老地方看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打來,瘋狂燒殺,我的家燒得精光,那地方早就變了樣,可是留在記憶中的,永遠變不了,永遠不會消失。
那地方,在長江下游,民國十幾年,算得上是個像樣的城市,有名的水陸碼頭。
從那里坐火車,可以東到上海,西到南京。江里來往的,有大輪船、小火輪,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
城里有條河通往長江,跟河道平行的,是條街,兩邊全是店鋪。挨著河的房屋,從窗戶可以往河里倒臟水,倒爛菜葉子,河水總是臟兮兮的,有時還漂浮著死貓,一到夏天,散發出一股味道。可是一到夜晚,住在附近的人,熱得睡不著,愿意到橋上乘涼,聊天。迎著橋的日新街,酒樓旅館,妓女清唱,夜晚比白天還熱鬧。
這座橋叫洋浮橋,北伐以前,往東不遠是租界,大概橋的式樣不同于老式的,所以有了這么個名字。十幾年前,舒告訴我,他的老太爺在租界里的海關當過“監督”,談起來,江邊一帶他很熟悉。
我家只有四口人,除了死掉的姐姐,就是外婆、爸爸、媽媽跟我,我很寂寞;到現在,我想起來,還有一種孤獨感。
外婆原先在洋浮橋邊開豆腐坊,掙了錢,開起百貨店,她是老板,爸爸是招女婿,用現在的說法,當經理。
我不喜歡在店里玩,一點不好玩,成天的的得得打算盤,買東西討價還價,煩死人。姑娘們買雙洋襪要挑揀半天,說話尖聲尖氣,我有點怕她們。
那時候,我已經認字,認方塊字,拿紅紙裁成一小塊一小塊,用毛筆寫上“人”、“天”、“大”、“小”……后來從書局買來成盒的方塊字,彩色印的,背面有畫兒,好看,我很喜歡。紅紙做的方塊字送給隔壁的小丫頭牙寶,她死要漂亮,學大人涂胭脂,吐點口水在紅紙上抹在嘴唇上,血紅血紅的,好怕人。人家說牙寶長大了做我的堂客,我才不要哩。
后來,上私塾念《三字經》、《百家姓》,日子過得很刻板,更加寂寞,只好自己找樂趣,我用好奇的充滿稚氣的眼光尋找樂趣。
我覺得最好的去處,是對門的那家小印刷鋪。鋪子不大,在我看起來卻很神氣,因為店里有兩部印刷機,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大的叫“對開架子”,小的叫“圓盤”,是后來到漢口進出版社當練習生跑印刷廠才知道。
印刷機就放在店堂里,在街上看得見,常有過路的鄉下人站在門口看機器印東西,看得發呆。圓盤轉動的時候會發出清脆的響聲,“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蠻好聽。三伏天,狗都不想動,街上靜悄悄,只聽見印刷機的聲音。
我每天都到印刷鋪子里玩,看一張張白紙,從機器這頭吃進去,那頭吐出來,上面就印滿了字。看工人用刮刀在圓盤上調油墨,綠的跟黃的摻在一起,變成草綠色,紅的跟白的摻在一起,變成粉紅色。我很想調調,當然不許,碰都不準碰。
后來,上小學了,我有了一盒馬頭牌水彩顏料,于是大調特調,隨我怎么調都可以,開心極了。
我把涂滿顏色的紙貼在墻上,自己欣賞。說不定抽象藝術,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藝術家,就是這么產生的。
印刷鋪有個小排字間,五六個字架,一張案桌。排字工人左手拿個狹長的銅盤,夾張稿子,右手從字架上揀字,他們叫“撮毛坯”。奇怪的是,他不看字架,好像手指有眼睛,能夠找到字,而且揀得飛快。我問他拿錯了怎么辦,他說“不關我的事”,原來另外有個戴眼鏡的老師傅專門對字。
上小學的時候,有個姓莊的同鄉的哥哥在一家報館當排字工人,我常到排字間玩,跟他做了朋友。我看他一天揀下來累得很,他教我唱一首歌:“做了八點鐘,又做八點鐘,還有八點鐘:吃飯,睡覺,撒尿,出恭。”“機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腦殼轟轟轟,再拿稿子來,操他的祖宗。”原來排字不是好玩的,很苦。
印刷鋪地上丟著印壞的紙片,上面有畫兒的,我就撿幾張。用紅紙綠紙印的電影說明書,我也撿。我認不得那么多的字,有人喜歡看說明書,我可以送給他,這也是一種樂趣。
我還撿地上的鉛字,撿到拼花邊用的五角星啊,小花兒啊,更開心。這不算偷,他們讓我撿,不在乎這幾個鉛字。排字工人還從字架上揀了“伏”“星”兩個頭號字送我,伏星是我的小名。
我把撿來的鉛字、花邊,拼起來用線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蓋在一張張紙上送人,盡管拼不成一句話,卻是我印的。
我把印有“伏星”兩個字的貼在墻上,東一張,西一張,到處是伏星,好像仁丹廣告。
在這條街上,還有家石印鋪,我也常常去玩。印的是廣告、京戲院的戲單,字很大。我看老師傅怎樣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頭上,還用毛筆細細描改,挺有看頭。就是始終不曉得為什么石頭是平面的,不像鉛字,用油墨滾一下就能印出字來,很奇怪。
那時候,傍晚街上有唱新聞的,邊唱邊賣:“小小無錫景啊,唱把那諸公聽……”唱詞也是用顏色紙石印的,兩個銅板一張。我買了不少張,攢起來借給人看。
還有一種石印的小唱本,叫做七字語,就是彈詞,唱本封面上有圖畫,花前月下公子小姐,兩三個銅板一本。
我看的第一本書,是在家里閣樓上放雜物的網籃里找到的一本《新學制國文》第一冊,爸爸念過的課本,油光紙印刷線裝,有字有圖。第一課的課文是:“夕陽西下,炊煙四起,三五童子,放學歸來。”畫上遠處有兩間小茅屋,煙囪在冒煙,還有柳樹,飛鳥,兩個背著書包的學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條拉犁的牛。這本課本,我看了好多遍,有的課文都背得出來。
八歲那年,不再上私塾,改上學堂,從此,看的書就多了,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課本,還在圖書室里看到《小朋友》、《兒童世界》、《新少年》這些雜志。到高年級,有兩位老師給我看了不少文學刊物,韜奮編的《大眾生活》、《生活星期刊》也看到了。
打這個時候起,我成了不折不扣的書迷。我找到新的天地。我覺得,沒有比書更可愛的東西了,書成了我的“通靈寶玉”。
不幸的是,小學快畢業,爸爸死了,外婆和媽媽沒有錢供我繼續升學,打算送我到一家寧波同鄉開的銀樓學手藝。我想來想去,要求讓我當印刷徒工,因為我看了《新少年》雜志登的茅盾的小說《少年印刷工》,那個叫元生的,姑父勸他去當印刷工,說排字這一種職業,剛好需要讀過小學的人去學,而且到底是接近書本子,從前學的那一點,也不至于拋荒。一本書,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排字工人可以說是最先讀到那部書的人。當印刷工人,一面學習生活技能,一面又可以滿足求知欲。還說,說不定將來也開一個印刷鋪。
元生聽了以后,晚上確也做了一個夢,但不是開印刷鋪子,而是坐在印刷機旁邊讀了許多書。
我也想做這個夢。不過后來外婆還是借了錢讓我考中學。
我不僅是書迷,還熱衷于出“號外”,出刊物,我不知道什么編輯、出版、發行,一個人干,唱獨角戲。
十歲那年,“一?二八”日本鬼子在上海開仗。那時候,中國人連小孩子都曉得要抗日,打東洋鬼子。我早就知道“五三慘案”,日本人在山東殺了蔡公時,挖掉他的眼睛。知道日本人占了東三省,像大桑葉的地圖從此缺了一大塊。上海打仗,人人都關心十九路軍打得怎樣了。每天下午三四點鐘,街上叫賣號外。我把人家看過的號外討來,用小張紙把號外的大標題抄寫五六份,送給人家看,不要錢。到現在我還記得寫過“天通庵”、“溫藻浜”這些地名,還有那不怕死的汽車司機胡阿毛。
號外盡是好消息,“殲敵三百”、“我軍固守”……看了,晚飯都要多喝一碗粥。
我送給想看號外又想省兩個銅板的人(兩個銅板可以買個燒餅),像茶水爐(上海叫老虎灶)的老師傅,剃頭店老板,救火會看門的,刻字鋪先生,都是這條街上的,他們挺高興。
媽媽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小伢子送號外,晚飯都不想吃了。”她不知道我抄號外要多長時間,抄錯了還要重寫。
小學五六年級,我編過一份叫做《大家看》的手抄刊物,材料來源是韜奮編的《生活星期刊》“據說”這一欄和《新少年》雜志“少年閱報室”這一欄。比如,停在鎮江的日本軍艦的水兵時常登陸“游覽”拍照,畫地圖,警察不僅不敢得罪,不干涉,還要保護,真是豈有此理!又比如,湖北有個地方,窮人賣兒賣女,兩三歲的男孩,三塊錢一個;七八歲的女孩,頂高的價錢是六塊錢;十五六歲以上“看貨論價”。我要讓小朋友們知道有這樣丟人的事情,這樣悲慘的事情。
刊物每期還抄一首陶行知作的詩歌,像:“小孩,小孩,小孩來!幾文錢,擦雙皮鞋?喊一個小孩,六個小孩來,把一雙腳兒圍住,搶著擦皮鞋。”誰讀了心里都很難過,都會想一想為什么?我的同學,就有家里很窮的,說不定將來也要擦皮鞋。
我還是個漫畫迷,辦了個漫畫刊物《我們的漫畫》,買張圖畫紙,折成課本那樣大小,用鐵絲騎馬釘,從報紙、雜志、畫報選一些漫畫,描在這本刊物上。原來黑白線條,我用蠟筆、水彩、粉畫筆著上顏色,更加好看,在同學之間傳閱。小朋友說“滑稽得很”,“好看得很”,他們還不懂得什么叫諷刺,只是覺得夸張的形象有趣,最愛看黃堯畫的《牛鼻子》。
這本手工漫畫刊物一共“出版”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蔣委員長”的漫畫頭像,那時他是領導抗戰的。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坦白交代。如果讓人知道,還了得。畫也不錯,給蔣介石戴上德國式的鋼盔,好像是胡考的手筆。
一九九二年,廖老冰兄送我一張我的漫畫像,寫了“熱戀漫畫數十年,地翻天覆情不變,范用兄亦漫畫之大情人也”,可以說是“婚外戀”。
暑假期間,請老師講文學作品,我跟幾個同學刻鋼板,油印“活葉文選”,印過夏衍的《包身工》、高爾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那時候,書店里賣《開明活葉文選》,很便宜,很受歡迎,現在沒有人做這種工作,為買不起書的讀者著想。
就這樣,我異想天開,抄抄摘摘,辦起了“出版”,自得其樂,其樂無窮。好在沒有人告我侵害版權,請我吃官司。
一九三七年,抗戰了,既沒有去當學徒,也沒有讀成書,而是逃難去了。逃到漢口,沒想到讀書生活出版社黃老板收我當練習生,有飯吃,有書讀,不是在印刷機旁邊讀,而是在出版社讀,真是天大的幸福!
在出版社,我還是有興趣跑印刷廠,喜歡聞油墨氣味,看工人排字、印書、裝訂。我跟工人做朋友,也跟印刷廠老板,甚至老板娘,老板的兒子女兒做朋友。
上海大華印刷廠有位叫“咬斷”(咬斷臍帶,鬼就拖不走了)的工人,印封面讓我和他一起調油墨,調得我滿意了才開印。解放以后,再也得不到這種樂趣。
跑印刷廠,多少學會一點揀字、拼版、改樣的技術。一九四三年在重慶,我代楚云、冬垠編《學習生活》雜志,常常帶著校樣,來回跑二十多里路,到化龍橋新華日報印刷車間,跟工人一起拼版,改樣子。我一直記得工人領班的名字,叫楊允庸,他為人可親,十分耐心,校樣怎么改都可以。前幾年我還見到過他,和我一樣,在過養老的日子。
進出版社不久,我寫的字,我設計的封面,居然印到書上,小時候的夢想真的實現了。
周立波從敵后到武漢,寫了一本《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他要我寫圖片說明文字:“小鬼!你來寫。”我大筆一揮,寫了“五臺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幾個帶有隸書味道的字,那是聶榮臻領導的邊區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立波說要寫娃娃體,我又歪歪倒倒地寫了“平津漢奸報廣告示例”,是一批剪報的說明。兩行字都印在書上,我看了又看,放在枕邊,這是我的字嗎?簡直難以相信,是不是做夢?
立波在書上題了“送給用,立波七月九日”。這本書跟隨我六十多年,沒有丟掉,成為珍貴的紀念品。啊!一九三八,激情的年代,意氣風發的年代,我還是個孩子。如今,立波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也老了。
說是有緣,機遇,或者命中注定吃出版這行飯,都可以。就這樣,從夢想到現實,我跟書打交道,過了愉快的一生。
我挨過不少批評,說我干出版不是“政治掛帥”,是憑個人愛好,個人興趣。我也鬧不清,我只知道:要做好工作,沒有一點興趣,行嗎?恐怕做人也不行。
上個月,暮春時節,我重到舊地,尋覓童年舊夢。那條河五十年前就給填了,沿河的房子全拆了,現在是條大馬路——中華路。我家開店鋪的房子還在,現在是一家旅社。此外,無影無蹤。
我親愛的外婆,爸爸,媽媽,你們在哪里?站在老地方,我似乎又感到孤獨,多么想再聽到那悅耳的印刷機轉動的聲音! 一九九七年,夏初
我 與 丁 聰
我怎么認識丁聰的?我是先認識(或者說“看上”)丁聰的畫,然后才認識“小丁”這個人。
上一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有兩本很有名的漫畫雜志,《時代漫畫》和《上海漫畫》。那時我還是小學生,就愛看這兩本漫畫雜志,是個“漫畫迷”。
不過,那時候丁聰的漫畫并沒有給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在“漫壇”剛剛出道,甚至還不能說出道。比起葉淺予、張光宇、魯少飛、汪子美,無論從畫的思想,還是畫的技巧來說,丁聰還嫩得很。不過倒是記住了“丁聰”這個名字;那時他還沒有用“小丁”這個名字。
抗戰開始,丁聰跑到香港去了,他在那里發表的作品,我見不到。
一九四六年,吳祖光、丁聰、龔之方辦了個刊物《清明》,登了一幅丁聰題為《花街》的漫畫。“花街”是成都的紅燈區。這是丁聰的一幅杰作。在他的筆下,妓女、老鴇、嫖客,人間地獄,慘不忍睹。直到現在,還歷歷在目。我打心里說:這幅畫了不起,丁聰了不起。
抗戰勝利了,這時的丁聰,以無畏無懼的斗士姿態出現在上海出版的進步刊物上。柯靈、唐弢、鄭振鐸主編的《周報》、《民主》,還有《文萃》,幾乎每期都有丁聰的作品,其矛頭直指獨夫民賊蔣介石,毫不隱晦,毫不含糊。鳳子主編的《人世間》,每期封面、插圖、題頭都由丁聰作畫。
解放以后我調到北京,丁聰也到了北京,我們還不相識。直到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誘使一大批“右派分子”入網,這才有機會與丁聰結識。
有一天,在文化部大廳批判右派分子(那時還只是揭發批判),丁聰被作為“二流堂”的一員在座。中午散會,丁聰走進東四青海餐廳吃包子,我尾隨其后,坐在一張桌子跟他套近乎。從此,我們算是認識了,進而成為朋友,臭味相投,沆瀣一氣。
一九七九年辦《讀書》雜志。要把《讀書》辦得有特色,我首先想到丁聰。點子之一每期發表一幅丁聰的新作。真是夠朋友,從創刊起,丁聰每期都給《讀書》畫一幅漫畫,從不脫期。不僅如此,還給《讀書》設計封面,畫版式。這樣的雜志,可以說沒有第二家。就這樣,丁聰給《讀書》畫了二十來年,現在還在畫。有時還每期兩幅。
由此,我們兩人來往就更密切了。每個星期丁聰都要大老遠由西城到東城,爬樓梯到五樓讀書編輯部。中午我們兩人下小館子,四小兩二鍋頭兩個小炒。我這個人有個怪毛病,點菜同時要兩碗米飯,大概是三年困難時期留下的后遺癥,總怕沒有飯吃。可是喝了酒吃了菜,飯吃不下,又不能退。這時丁聰就要教訓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浪費糧食是犯罪的行為。”然后替我把兩碗飯吃下肚。下一回,我照樣要兩碗米飯,他又照樣幫我吃掉。真是屢犯不改,孺子不可教也。
丁聰為什么如此善良?是因為有一個好“家長”夫人沈峻長期熏陶感化,才培養出一個可愛的小丁。只是小丁不識好歹,有時還要發牢騷講怪話。他作了一首《十勿起歌》“贈沈家長”。詩曰:
冷勿起熱勿起,飽勿起餓勿起,咸勿起淡勿起,辣勿起酸勿起,硬勿起軟勿起,響勿起輕勿起,累勿起歇勿起,曬勿起軋勿起,省勿起費勿起,捧勿起批勿起。
還注明:“如有不盡然處,得隨時修改補充之。”丁聰膽子不小,天沒有變,竟然造反了!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日《新民晚報》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范用同志:
信早收到。沒有回信,只是因為我的病。《隨想錄》能夠出合訂本,合訂本能夠印得這樣漂亮,我得感謝您和秀玉同志。說真話,我拿到這部書已經很滿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紙張,第一流的裝幀!是你們用輝煌的燈火把我這部多災多難的小著引進“文明”書市的。
譯文集付印時我也想寫篇“新記”。請告訴我最遲的交稿期。不過三、四月內恐怕寫不出來。
別的話下次再談。祝
好!
巴金三月九日
巴老的這封信寫于一九八七年,他收到《隨想錄》合訂本樣本。
為什么巴老說《隨想錄》是一部“多災多難的小著”?
《隨想錄》先是刊于香港“大公報”潘際坰兄主編的《大公園》副刊。在陸續發表的時候,內地就有人說三道四,以至于對際坰兄施加壓力,企圖腰斬《隨想錄》。香港向來言論出版自由,際坰兄理所當然予以拒絕。
我得知這一情況,十分氣憤。正好巴老來京,住在民族飯店,我打電話問候巴老,同時請求將《隨想錄》交三聯書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同意,我非常高興。
這樣,《隨想錄》先由香港三聯書店分冊出版,即《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
《隨想錄》精裝合訂本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由我設計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印了一百五十本編號特裝本,非賣品,供巴老贈送之用;巴老簽名贈我的一本為NO.132。正文用紙是《毛澤東選集》精裝本的特制紙張。我認為這種特制紙張,《毛選》可用,《隨想錄》也可用,當時我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長兼三聯書店總經理,手上有點小權,可以動用這種紙張。
華夏出版社又于一九九三年把香港三聯分冊出版的《隨想錄》,影印出版線裝本,五冊一函,函套用織錦,請冰心先生題簽。巴老為線裝本寫了一篇后記:
有人對我說:“你寫的書中印刷最多的是《隨想錄》,有九種印本,可是市里出售的很少。買不到書。”最近我同華夏出版社的朋友談起,他說“我還為你出一種線裝本,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我連聲說。我正想編一本新的《隨想錄》,這將是版本的第十種,我要把來不及收進合訂本的兩篇隨想也附印在里面。我不曾同哪一家出版社訂過合同,因此我還有這一點自由。
這次增補的兩篇文章是
懷念從文
懷念二叔。
巴金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
巴老說的華夏出版社的朋友即夏宗禹,我的摯友。
一九九○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巴老的《講真話的書》,里面收有《隨想錄》,卻出現了怪現象。其中《隨想錄》一四五《“文革”博物館》一文,在目錄頁上只標出“存目”兩字,正文頁里僅有標題,第一○二六頁整頁空白。
大家知道,在國民黨法西斯專政時期,報刊常有“開天窗”,報刊因為某篇文章或新聞被審查官“槍斃”了,編者故意讓它空著,讓讀者知道,以表示對審查的抗議。現在四川出版的這本《講真話的書》出現這種現象,又是為什么?
巴老在這篇文章里說的不過是:
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過去”,才能作“未來”的主人。
眾所周知,黨中央已經做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決定,難道巴老的意見犯了忌?
曾有一位溫姍先生在香港《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議論此事:
把巴老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極不可取;但是,編者仍然“存目”還有可取之處,至少他們有勇氣告訴讀者這里本來應有如此一篇文章,讓讀者去思索個“為什么”,而且引火燒身地招來對他們的批評。如果他們干脆連目錄都刪去,作者、讀者更是連話也說不出一句,豈不省事?
去年,楊苡同志在《鐘山》雙月刊發表《“文革”博物館在哪里?(重談一九七七年巴金的三封信)》一文,其中說:
“文革”博物館在哪里?在我們的親愛的祖國各地,無數無數的高樓在建成,竟沒有一座大樓掛上“文革”博物館的牌子!我現在只能說,它正在建成,或已經建成,它矗立在巴金老人的心里,在他的親朋好友心里,在所有經歷過十年浩劫的受難者的心里!歷史可以把一些發生過的事掩蓋,淡化,甚至歪曲。但歷史終歸是歷史,它不像是日歷、月歷或年歷,想撕掉就撕掉,而歲月留下的歷史蹤跡卻還能在記憶中永存。
我之所以在這里不厭其詳寫下這件事,只是想給研究中國現代出版史者提供一些資料。
三聯版《隨想錄》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沒有發生什么問題,平安無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也。
巴老信中所說的“譯文集”,即香港三聯書店于一九九○年出版的一套十本的“巴金譯文選集”:《草原故事及其他》(高爾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著)、《童話與散文詩》(王爾德著)、《遲開的薔薇》(斯托姆著)、《家庭的喜劇》(赫爾岑著)、《紅花集》(迦爾洵著)、《夜未央》(廖?抗夫著)、《散文詩》(屠格涅夫著)、《木木集》(屠格涅夫著)、《門檻》(屠格涅夫著)。是我用自己收藏的書選編的,每本十萬字左右,印小開本。臺灣東華書局又據香港三聯版印了精裝本,巴老也簽名送了我一套。
猶憶少年時,小學老師沙名鹿先生送我一本巴金的《家》作為生日禮物,自此,我就找巴金著作來讀,七十年了。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讀巴老的書成長的。巴老百歲華誕,寫這篇小文,略表我的感念之情。
原載《文匯讀書周報》,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