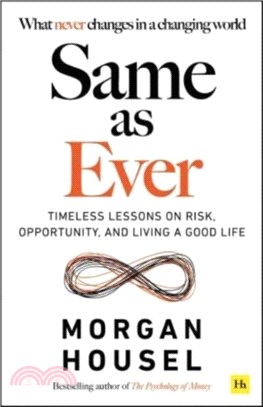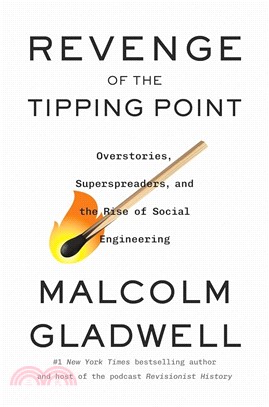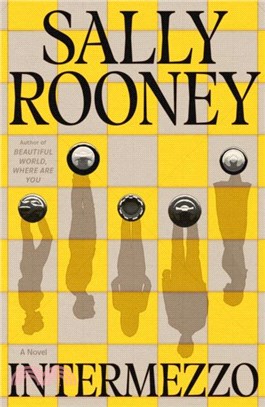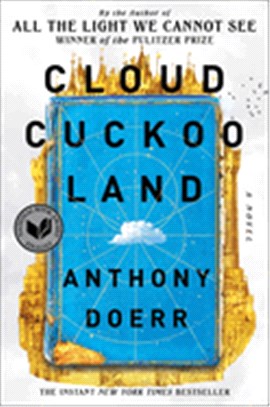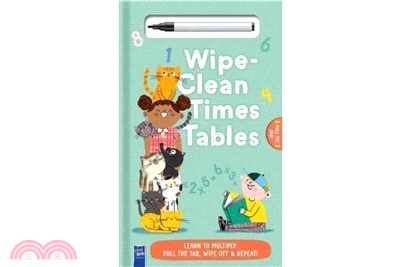人民幣定價:38 元
定價
:NT$ 228 元優惠價
:87 折 198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南方周末編著的《一頁沉重的歷史》選取劉心武、殘雪、肖復興、池莉白樺、陳祖芬、公劉等數十位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的往事回憶,按照舊夢、萍水、往事、親情、藝味的順序,精心輯錄成冊。這些短文,尺幅雖小而意義甚大,或描寫拼搏奮斗的艱辛和不屈,或抒發世事變遷的深沉感喟,或點撥生活中不為人所知的一些奇聞趣事,或于平凡瑣事中發現美的因子……這些小文,雖然僅是大千世相中的一些零屑側面,但從這一翎一爪、各具特色的生動描述中,讀者仍可以窺見生活的艱辛和生命的華麗,這種對生命的真實感悟是不以時代的變遷而衰減的;同時《一頁沉重的歷史》也因忠實地記錄了改革開放乃至跨世紀前後普通民眾的真實生活狀態,故也具有特殊的民間記史的作用。因此,《一頁沉重的歷史》特別適合生活節奏。
名人/編輯推薦
閱讀他們,傾聽他們,不同的面孔,不同的靈魂和不同的心態。有悲壯和崇高,有正義和痛苦,有愛以及恨……一些博大,一些精深,一些纖細,一些拙樸,那些跳動著的心!
南方周末編著的《一頁沉重的歷史》選取劉心武、殘雪、肖復興、池莉白樺、陳祖芬、公劉等數十位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的往事回憶,內容包括《一頁沉重的歷史》、《改寫寓言詩記》、《相撞》、《雪》、《野草莓》、《一頁沉重的歷史》、《與狼共眠》、《宰牛》、《方姑姑》、《兩個童養媳》、《大頭》、《春天的孩子》等。
南方周末編著的《一頁沉重的歷史》選取劉心武、殘雪、肖復興、池莉白樺、陳祖芬、公劉等數十位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的往事回憶,內容包括《一頁沉重的歷史》、《改寫寓言詩記》、《相撞》、《雪》、《野草莓》、《一頁沉重的歷史》、《與狼共眠》、《宰牛》、《方姑姑》、《兩個童養媳》、《大頭》、《春天的孩子》等。
序
那些漸行漸遠的名字
馬莉
大約15年前,我編過一本“芳草地”的結集,并寫過一個序,一晃,又一個15年將要過去了,再次把芳草地結集,我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感慨,不是感慨時間過得真快,而是感慨,我當年的那一批老作家,與我一起走過了20年的“芳草地”的老人,現在大多已經不復存在了,他們是馮亦代、張中行、蕭乾、梅志、綠原、藍翎、端木蕻良、何滿子、公劉、牧惠、許潔泯、李士非、陳荒煤、李佩芝、吳方……編輯這本集子時,重新看到他們的名字,再次閱讀他們的文章,回想起當年在電話中向他們約稿的情形,他們的音容笑貌,一下子浮現在眼前。我的眼睛有些濕潤。
這些都是當年我責編的“芳草地”版面的老作家,那時他們還不老,而我,還年輕,他們對我,對我編輯的這塊小小的“語言的家園”,倍加呵護,有求必應。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支撐起了我這個隨筆版面上空的一片藍天,我至今感恩這些老作家,沒有他們,我是編不好我的版面的,沒有這樣一群好的作家,我們的報紙是辦不成的。在這里,讓我向他們深深地鞠躬。
要說的話很多,就此打住罷,詩人聶魯達有句詩:“我喜歡你是寂靜的,好像你已遠去。”如今我離開我的編輯崗位,而他們,確實已越走越遠,那些我曾經熟悉的身影,正靜靜地睡在我耕耘過的,不,是我們一起耕耘過的清香的芳草地上。
我忍不住找回我15年前寫的序言,也放在這里,如此,對“芳草地”的敘說顯然就完整了——
“收集在這里的散文隨筆,大部分是《芳草地》版1995年所發表的作品精選。回想起來,編《芳草地》已是第5個年頭了,我大致算了一下,5年,大約270期吧,也就是200多萬字吧,這個數字饒有意味:5年,是半個世紀的十分之一,在時間的歷史長河中它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對于一個有限的生命而言,它卻不僅僅是短暫的一瞬了。
對于我而言,作為一個編輯,其責任不僅僅是編出令個人喜歡的好稿,也不僅僅是編出令讀者喜歡的好稿,做到這一點其實不難,但遠遠不夠。對于我而言,做到這一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個不思考的懶漢編輯。一直以來,我始終抱著這樣的信念——閱讀的信念,面對著當代那么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有什么理由不閱讀他們呢?
閱讀他們,傾聽他們,不同的面孔,不同的靈魂和不同的心態。有悲壯和崇高,有正義和痛苦,有愛以及恨……一些博大,一些精深,一些纖細,一些拙樸,那些跳動著的心!
我很驕傲我能站在本世紀末這樣一個很適合我的角度,去觀察和思考這個時代的場面和人物,這個時代的精神和氣質。
我想這將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時代吧。因為畢竟,這個時代保留了它應該保留的東西,譬如正義和偉大,譬如同情和關懷……譬如,這樣的一本書。
盡管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但,這還不夠嗎?
在這個世紀之末的黑暗之夜,我的朋友問我:我們還閱讀什么呢?
是啊,這也正是我思考的問題。
到處是燈紅酒綠和五彩繽紛,到處是嘈雜和熱鬧的聲音,到處是虛幻和偽裝。我想,面對這一切,閱讀就成為我們生存和謹慎選擇生存的第一需要了。
如果說,僅僅是閱讀這些優秀的篇章,那么5年,我已是閱讀了200多萬字了。這個數字當然不多,但,也不算少。
面對這些優秀的篇章,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結集成冊出版,讓下一個世紀的人們也能夠像我們一樣,滿懷著熱愛的心情去閱讀和欣賞呢?
我們有什么理由不讓未來的人們認識和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風貌呢?
我們沒有理由,我們也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2011年11月5日于宋莊
馬莉
大約15年前,我編過一本“芳草地”的結集,并寫過一個序,一晃,又一個15年將要過去了,再次把芳草地結集,我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感慨,不是感慨時間過得真快,而是感慨,我當年的那一批老作家,與我一起走過了20年的“芳草地”的老人,現在大多已經不復存在了,他們是馮亦代、張中行、蕭乾、梅志、綠原、藍翎、端木蕻良、何滿子、公劉、牧惠、許潔泯、李士非、陳荒煤、李佩芝、吳方……編輯這本集子時,重新看到他們的名字,再次閱讀他們的文章,回想起當年在電話中向他們約稿的情形,他們的音容笑貌,一下子浮現在眼前。我的眼睛有些濕潤。
這些都是當年我責編的“芳草地”版面的老作家,那時他們還不老,而我,還年輕,他們對我,對我編輯的這塊小小的“語言的家園”,倍加呵護,有求必應。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支撐起了我這個隨筆版面上空的一片藍天,我至今感恩這些老作家,沒有他們,我是編不好我的版面的,沒有這樣一群好的作家,我們的報紙是辦不成的。在這里,讓我向他們深深地鞠躬。
要說的話很多,就此打住罷,詩人聶魯達有句詩:“我喜歡你是寂靜的,好像你已遠去。”如今我離開我的編輯崗位,而他們,確實已越走越遠,那些我曾經熟悉的身影,正靜靜地睡在我耕耘過的,不,是我們一起耕耘過的清香的芳草地上。
我忍不住找回我15年前寫的序言,也放在這里,如此,對“芳草地”的敘說顯然就完整了——
“收集在這里的散文隨筆,大部分是《芳草地》版1995年所發表的作品精選。回想起來,編《芳草地》已是第5個年頭了,我大致算了一下,5年,大約270期吧,也就是200多萬字吧,這個數字饒有意味:5年,是半個世紀的十分之一,在時間的歷史長河中它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對于一個有限的生命而言,它卻不僅僅是短暫的一瞬了。
對于我而言,作為一個編輯,其責任不僅僅是編出令個人喜歡的好稿,也不僅僅是編出令讀者喜歡的好稿,做到這一點其實不難,但遠遠不夠。對于我而言,做到這一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個不思考的懶漢編輯。一直以來,我始終抱著這樣的信念——閱讀的信念,面對著當代那么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有什么理由不閱讀他們呢?
閱讀他們,傾聽他們,不同的面孔,不同的靈魂和不同的心態。有悲壯和崇高,有正義和痛苦,有愛以及恨……一些博大,一些精深,一些纖細,一些拙樸,那些跳動著的心!
我很驕傲我能站在本世紀末這樣一個很適合我的角度,去觀察和思考這個時代的場面和人物,這個時代的精神和氣質。
我想這將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時代吧。因為畢竟,這個時代保留了它應該保留的東西,譬如正義和偉大,譬如同情和關懷……譬如,這樣的一本書。
盡管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但,這還不夠嗎?
在這個世紀之末的黑暗之夜,我的朋友問我:我們還閱讀什么呢?
是啊,這也正是我思考的問題。
到處是燈紅酒綠和五彩繽紛,到處是嘈雜和熱鬧的聲音,到處是虛幻和偽裝。我想,面對這一切,閱讀就成為我們生存和謹慎選擇生存的第一需要了。
如果說,僅僅是閱讀這些優秀的篇章,那么5年,我已是閱讀了200多萬字了。這個數字當然不多,但,也不算少。
面對這些優秀的篇章,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結集成冊出版,讓下一個世紀的人們也能夠像我們一樣,滿懷著熱愛的心情去閱讀和欣賞呢?
我們有什么理由不讓未來的人們認識和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風貌呢?
我們沒有理由,我們也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2011年11月5日于宋莊
目次
一頁沉重的歷史
改寫寓言詩記
相撞
雪
野草莓
一頁沉重的歷史
與狼共眠
宰牛
方姑姑
兩個童養媳
大頭
春天的孩子
清道女
擦鞋的朋友
妮兒
笑麗的故事
十個一分鐘
賣刷把的婆婆
桔紅色背心
阿翠
十字街頭
謀生者
民工
街娃
偶過杭州
“吃草”
紅軍合唱團
看日本人的流淚表演
琴聲
在靜靜的樓道里
嚴復治學
晚節何以善終
近訪錢鐘書先生
讀懂本色
城墻失去之後
吳組緗瑣憶
憶楊騷
路翎走了
北大精神北大人
王小波之墓
形象與自我分離——湊趣談三毛一
這個曉聲
“小小謝”其人其詩
“不爭”與“不屑”
陳景潤一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一
兩個物理學家
“浪子”的啟示
功夫在琴外
敦煌的供養人
在靜靜的樓道里
長沙車站有個“知識分子”
冬日看海人
雨中
珍惜命運
一個人和他的林場
我在尋找什么
朋友——請節約用水
艾妮
回答
陌生的臺灣人
在貴州相識的臺灣人
—方白手帕
緣分
美麗幽默的德國小姐
到中國圓夢
東京小老弟在北京
腳的記憶
磚塔胡同
好人張德庭
虎根走了
徐老師
懷念珊珊
“俺們貧下中農”眼中的知青
小海
鄉村電影
“後學太師”
老易
收藏者
小三
杜鵑花
東方的古董
啊,朋友再見
一幅畫和一個人
一個朋友
看那個馬車夫犯錯誤
白樓
行俠
猴子
胡四臺記事
回老家
賈先生
看那個馬車夫犯錯誤
狼狗
龍虎斗
買鞋
你可不可以信任我一次
奇異的木板房——藝術家的境界
人與老鼠
死鬮
我的匣子
我也養過蠶
學游泳
眼睜睜地看著他走了
椰子
癖好
雪人
太陽花
雙色菊
胭脂
從未繁花
玉蘭花是這樣開的
花?轆錢兒
火繩
雪人
窗外的石榴花
木屐
冥幣
泡了水仙便過年
薔薇的感官
泥巴
狗
離散的記憶
父親
傻媽
外婆的墳墓
我的母親——《親情》系列之一
我的二舅——《親情》系列之二
我的大舅——《親情》系列之三
我的外祖父——《親情》系列之四
坐巴士回家
離散的記憶
相會
靜靜地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母親的保險箱
二十四雙布鞋
我的老父
蹬三輪車的父親
小舅的挽聯
我的外甥詹姆斯
致兒子
我和我的兒子
北京人喝酒
剃頭
文章作法
飛豆
遙迢獵戶
閨女掃墓
大眼睛,小眼睛
夜哭
客家的米酒
一日三餐
中午
一杯咖啡
聽味
喝而不醉
松子煮茶
烤白薯與烘山芋
草餅
思念油茶
“食欲”古今談
難忘野山椒
紅薯情節
玫瑰香兮
北京人喝酒
食葫蘆
肉味
吃好的不易
大食堂
改寫寓言詩記
相撞
雪
野草莓
一頁沉重的歷史
與狼共眠
宰牛
方姑姑
兩個童養媳
大頭
春天的孩子
清道女
擦鞋的朋友
妮兒
笑麗的故事
十個一分鐘
賣刷把的婆婆
桔紅色背心
阿翠
十字街頭
謀生者
民工
街娃
偶過杭州
“吃草”
紅軍合唱團
看日本人的流淚表演
琴聲
在靜靜的樓道里
嚴復治學
晚節何以善終
近訪錢鐘書先生
讀懂本色
城墻失去之後
吳組緗瑣憶
憶楊騷
路翎走了
北大精神北大人
王小波之墓
形象與自我分離——湊趣談三毛一
這個曉聲
“小小謝”其人其詩
“不爭”與“不屑”
陳景潤一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一
兩個物理學家
“浪子”的啟示
功夫在琴外
敦煌的供養人
在靜靜的樓道里
長沙車站有個“知識分子”
冬日看海人
雨中
珍惜命運
一個人和他的林場
我在尋找什么
朋友——請節約用水
艾妮
回答
陌生的臺灣人
在貴州相識的臺灣人
—方白手帕
緣分
美麗幽默的德國小姐
到中國圓夢
東京小老弟在北京
腳的記憶
磚塔胡同
好人張德庭
虎根走了
徐老師
懷念珊珊
“俺們貧下中農”眼中的知青
小海
鄉村電影
“後學太師”
老易
收藏者
小三
杜鵑花
東方的古董
啊,朋友再見
一幅畫和一個人
一個朋友
看那個馬車夫犯錯誤
白樓
行俠
猴子
胡四臺記事
回老家
賈先生
看那個馬車夫犯錯誤
狼狗
龍虎斗
買鞋
你可不可以信任我一次
奇異的木板房——藝術家的境界
人與老鼠
死鬮
我的匣子
我也養過蠶
學游泳
眼睜睜地看著他走了
椰子
癖好
雪人
太陽花
雙色菊
胭脂
從未繁花
玉蘭花是這樣開的
花?轆錢兒
火繩
雪人
窗外的石榴花
木屐
冥幣
泡了水仙便過年
薔薇的感官
泥巴
狗
離散的記憶
父親
傻媽
外婆的墳墓
我的母親——《親情》系列之一
我的二舅——《親情》系列之二
我的大舅——《親情》系列之三
我的外祖父——《親情》系列之四
坐巴士回家
離散的記憶
相會
靜靜地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母親的保險箱
二十四雙布鞋
我的老父
蹬三輪車的父親
小舅的挽聯
我的外甥詹姆斯
致兒子
我和我的兒子
北京人喝酒
剃頭
文章作法
飛豆
遙迢獵戶
閨女掃墓
大眼睛,小眼睛
夜哭
客家的米酒
一日三餐
中午
一杯咖啡
聽味
喝而不醉
松子煮茶
烤白薯與烘山芋
草餅
思念油茶
“食欲”古今談
難忘野山椒
紅薯情節
玫瑰香兮
北京人喝酒
食葫蘆
肉味
吃好的不易
大食堂
書摘/試閱
改寫寓言詩記
讀金克木先生《擬寓言詩記》後,想起我在三十四五年前干過一件類似的事。不過不是寫作寓言詩,而是根據散文體譯本的《克雷洛夫寓言》,把其中三首改寫成分行押韻的朗誦詩。
那是1962年12月10日,我正以“摘帽右派”之身份在一個劇團的創作組里混飯;總想寫點什么東西,好對得起一些後來被稱為“走資派”的領導干部對我的保護。時值中蘇分歧公開化,又恰在古巴危機之後,我改寫《誹謗者和毒蛇》《狼和杜鵑》《大老鼠論貓和獅子》三則,或“針對圍繞‘古巴事件’誹謗中國的一片營營之聲”,或“申述帝國主義本性何時何地都不會改變”,或“諷刺修正主義者被帝國主義嚇破了膽,無視人民革命力量必將勝利”,我當時自以為完全符合反帝反修的宣傳方針的。
四年以後,我怎么也沒想到,“文革”驟起,在關于我的“罪行材料”里,這三首“洋”、“古”人原作的寓言詩,定性為“反動透頂”,“含沙射影地攻擊和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把矛頭指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以《誹謗者和毒蛇》為例。定案材料說:“這首詩一開始,他(暗指邵某,不是克雷洛夫)就寫道:‘誰在人世間作惡頂多,誰下了地獄就能得上座。魔鬼的筵席上起了紛爭:誹謗者和毒蛇誰是頭名?’這是惡毒地攻擊黨的廬山會議。原作上寫的是魔鬼們要出去游行,爭站前列,邵燕祥卻給安排成在魔鬼的筵席上,從這里可以看出其用心之惡毒。他還寫誹謗者和毒蛇爭權奪利,魔王出來作結論,說他們都能殺傷人命,百咬百中,但是誹謗者無論遠近都能把人中傷,因此更值得重視,于是把誹謗者抬為上座。他把廬山會議誣蔑為爭權奪利,把我們偉大領袖和革命左派比做魔王和誹謗者,這是對我們偉大領袖和革命左派的最大的誣蔑和惡毒的攻擊。”
在1966年8月13日的斗爭會上,批判者就這首詩指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誹謗的專政,反右派就是誹謗者中傷(他)自己”以後,當場質問:“你矛頭指向誰?‘魔王’是誰?”這不是一定要給人以必死之罪嗎?——天可憐見,把偉大領袖跟“魔王”聯系起來,我可是從來想也沒想過的呀!
重提舊事,意不在辯誣,一是覺得當時批判者的心態耐人尋味,二是不免想一想:當時的被批判者如我,可悲何在?
記得80年代似是江西出版了吳巖先生以詩體翻譯的《克雷洛夫寓言》;至于我在60年代改寫時所據的散文體是不是吳巖先生的,記不清了。那時候在廣播系統,習慣于拿來就用,沒什么版權觀念。
相撞
許多年前的一天上午,我校讀了一陣自己的譯稿,腦子里裝滿了300年前一位法國貴族對人性的陰郁見解,快中午的時候,不想再做這件事了’就騎車去北大取預訂的書。外面明明好好的陽光,心里卻陰沉得緊,拐過中關村路口時急了點兒,又被警察訓了幾句,然後脫逃式地往前騎,正好遇見一個老頭兒,手里拿著飯盒,嘴上哼著京戲,自得其樂地橫過馬路。我趕緊往旁邊一讓,然而還是輕輕碰到了他的手臂,“當啷”一聲,一飯盒餃子掉地上了。
我心想真是倒霉,趕緊下車道歉,老頭兒先說要上醫院檢查身體,又說要去找警察,然後說要賠錢。我掏出身邊的零錢,他說不夠。我不太高興了,跟他爭執了幾句,突然又停住了嘴,因為周圍已經有一圈人了,他們開始說話,不用我再多說什么了。
我說我要趕去取書,老頭兒不放我走,旁邊有一個人遞過兩斤全國糧票給我說:“再給他些糧票,你走吧。”老頭兒還是不讓,于是有人熱心地數起餃子來,問他到底花了多少錢買的,他說了個數,這時我的心境已經發生了_一種微妙的變化,變得坦然了,甚至有點置身事外的感覺,零錢不夠,我想從購書款中給一張整的,旁邊一個人卻打抱不平了:“干嘛給這么多?”另一個塞過幾毛錢補上說:“這就齊了。”老頭兒這時其實也無所謂了,咧著嘴笑起來,也許是為這件事引起這么多人注意而感到高興。
一件小事,一件經常在街道上發生的小事,周圍的人很快散去了。目擊者誰也不會放在心上,包括那幾位掏錢、掏糧票的熱心人,然而就是這樣一些小事,時時糾正著我對于人類有時過于偏頗的看法。
雪
北方很久不雨,歲末忽來初雪。一夜間,滿天銀輝,“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頓覺神清氣爽,目明心喜。下雪時不免要賞雪,賞雪中又難免勾起人生境遇中的某些情景。我憶起了少年時,一個下雪的日子,母親命我拿著幾件舊衣,到當鋪中去典幾個錢買米,不料因衣服過于陳舊,當鋪拒絕收當,我無奈地挾著那包舊衣在雪地中悒怏而行。幼小的心靈懷著因貧窮而瀕于難拔困境的痛苦,我在雪地上長嚎,呼天不靈。我不知道怎么去告慰母親,我們的日子怎么過下去。自此後,下雪總是給我一種生之恐懼,給我對瘦弱的母親的憐愛號}不念。
此後的日子,凡遇下雪,似乎總是與我凄苦的生涯結下不解之緣。“文革”中的雪天,我不是在大雪紛飛中被揪斗,便是拉著沉重的煤車在雪地上傴僂而行。最使我愛心彌漫的年邁母親,也正是在一個下雪的夜晚溘然西去的。雪中的往事,能喚起我記憶的,往往是一些凄苦的事;歡樂的回憶縱然也有,但總是容易淡忘。有一件事最使我不能忘懷,在70年代末,我的一位最知心的友人,于一個冬雪的清晨忽然迫不及待地到我家里來,他劈頭一句話就告訴我,他的冤案拖了20多年,昨天已告平反。我聽後驚喜不勝,來不及敘舊,緊緊地抱住他不放。我看到他自此可以自由了,往日的冤屈已云消煙散,我的歡快之情幾乎無以復加;但想到他多年來的顛簸生涯,家庭破碎之狀,一種為他凄苦之思又油然而生。此時我的凄苦與歡快的情思交織在一起,我真辨不出那到底是歡樂還是苦楚的滋味。
如今年邁,憶及往日的冬雪種種,不勝欷噓。此刻我在雪地上漫走,雪止風息,路上皚白一片,我看見一群孩子正堆起一個雪人,臉部用墨炭勾畫出一個魔鬼像。他們各捏雪團若干,對雪魔群起而攻之,一時雪魔的臉面與全身被雪團擲得面目全非。孩子們邊擲邊叫,笑聲與叫聲混成一片,煞是熱鬧。這時,恰有一輛自行車飛馳而來,騎者是一少年,忽然他不慎翻車滑倒,砉然有聲。我還以為這少年受了傷,豈知他迅速爬起,躍身上車,疾馳而去。我目睹此情,驚嘆不止,那一派青春活力,揚起令人心喜的生命之火,那青春的魅力讓我感到這冬雪大地上增添了陣陣綠意。我忽然想起了杜甫的詩句:“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我在冬雪的嚴寒中,知曉了一點春天的消息。P2-7
讀金克木先生《擬寓言詩記》後,想起我在三十四五年前干過一件類似的事。不過不是寫作寓言詩,而是根據散文體譯本的《克雷洛夫寓言》,把其中三首改寫成分行押韻的朗誦詩。
那是1962年12月10日,我正以“摘帽右派”之身份在一個劇團的創作組里混飯;總想寫點什么東西,好對得起一些後來被稱為“走資派”的領導干部對我的保護。時值中蘇分歧公開化,又恰在古巴危機之後,我改寫《誹謗者和毒蛇》《狼和杜鵑》《大老鼠論貓和獅子》三則,或“針對圍繞‘古巴事件’誹謗中國的一片營營之聲”,或“申述帝國主義本性何時何地都不會改變”,或“諷刺修正主義者被帝國主義嚇破了膽,無視人民革命力量必將勝利”,我當時自以為完全符合反帝反修的宣傳方針的。
四年以後,我怎么也沒想到,“文革”驟起,在關于我的“罪行材料”里,這三首“洋”、“古”人原作的寓言詩,定性為“反動透頂”,“含沙射影地攻擊和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把矛頭指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以《誹謗者和毒蛇》為例。定案材料說:“這首詩一開始,他(暗指邵某,不是克雷洛夫)就寫道:‘誰在人世間作惡頂多,誰下了地獄就能得上座。魔鬼的筵席上起了紛爭:誹謗者和毒蛇誰是頭名?’這是惡毒地攻擊黨的廬山會議。原作上寫的是魔鬼們要出去游行,爭站前列,邵燕祥卻給安排成在魔鬼的筵席上,從這里可以看出其用心之惡毒。他還寫誹謗者和毒蛇爭權奪利,魔王出來作結論,說他們都能殺傷人命,百咬百中,但是誹謗者無論遠近都能把人中傷,因此更值得重視,于是把誹謗者抬為上座。他把廬山會議誣蔑為爭權奪利,把我們偉大領袖和革命左派比做魔王和誹謗者,這是對我們偉大領袖和革命左派的最大的誣蔑和惡毒的攻擊。”
在1966年8月13日的斗爭會上,批判者就這首詩指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誹謗的專政,反右派就是誹謗者中傷(他)自己”以後,當場質問:“你矛頭指向誰?‘魔王’是誰?”這不是一定要給人以必死之罪嗎?——天可憐見,把偉大領袖跟“魔王”聯系起來,我可是從來想也沒想過的呀!
重提舊事,意不在辯誣,一是覺得當時批判者的心態耐人尋味,二是不免想一想:當時的被批判者如我,可悲何在?
記得80年代似是江西出版了吳巖先生以詩體翻譯的《克雷洛夫寓言》;至于我在60年代改寫時所據的散文體是不是吳巖先生的,記不清了。那時候在廣播系統,習慣于拿來就用,沒什么版權觀念。
相撞
許多年前的一天上午,我校讀了一陣自己的譯稿,腦子里裝滿了300年前一位法國貴族對人性的陰郁見解,快中午的時候,不想再做這件事了’就騎車去北大取預訂的書。外面明明好好的陽光,心里卻陰沉得緊,拐過中關村路口時急了點兒,又被警察訓了幾句,然後脫逃式地往前騎,正好遇見一個老頭兒,手里拿著飯盒,嘴上哼著京戲,自得其樂地橫過馬路。我趕緊往旁邊一讓,然而還是輕輕碰到了他的手臂,“當啷”一聲,一飯盒餃子掉地上了。
我心想真是倒霉,趕緊下車道歉,老頭兒先說要上醫院檢查身體,又說要去找警察,然後說要賠錢。我掏出身邊的零錢,他說不夠。我不太高興了,跟他爭執了幾句,突然又停住了嘴,因為周圍已經有一圈人了,他們開始說話,不用我再多說什么了。
我說我要趕去取書,老頭兒不放我走,旁邊有一個人遞過兩斤全國糧票給我說:“再給他些糧票,你走吧。”老頭兒還是不讓,于是有人熱心地數起餃子來,問他到底花了多少錢買的,他說了個數,這時我的心境已經發生了_一種微妙的變化,變得坦然了,甚至有點置身事外的感覺,零錢不夠,我想從購書款中給一張整的,旁邊一個人卻打抱不平了:“干嘛給這么多?”另一個塞過幾毛錢補上說:“這就齊了。”老頭兒這時其實也無所謂了,咧著嘴笑起來,也許是為這件事引起這么多人注意而感到高興。
一件小事,一件經常在街道上發生的小事,周圍的人很快散去了。目擊者誰也不會放在心上,包括那幾位掏錢、掏糧票的熱心人,然而就是這樣一些小事,時時糾正著我對于人類有時過于偏頗的看法。
雪
北方很久不雨,歲末忽來初雪。一夜間,滿天銀輝,“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頓覺神清氣爽,目明心喜。下雪時不免要賞雪,賞雪中又難免勾起人生境遇中的某些情景。我憶起了少年時,一個下雪的日子,母親命我拿著幾件舊衣,到當鋪中去典幾個錢買米,不料因衣服過于陳舊,當鋪拒絕收當,我無奈地挾著那包舊衣在雪地中悒怏而行。幼小的心靈懷著因貧窮而瀕于難拔困境的痛苦,我在雪地上長嚎,呼天不靈。我不知道怎么去告慰母親,我們的日子怎么過下去。自此後,下雪總是給我一種生之恐懼,給我對瘦弱的母親的憐愛號}不念。
此後的日子,凡遇下雪,似乎總是與我凄苦的生涯結下不解之緣。“文革”中的雪天,我不是在大雪紛飛中被揪斗,便是拉著沉重的煤車在雪地上傴僂而行。最使我愛心彌漫的年邁母親,也正是在一個下雪的夜晚溘然西去的。雪中的往事,能喚起我記憶的,往往是一些凄苦的事;歡樂的回憶縱然也有,但總是容易淡忘。有一件事最使我不能忘懷,在70年代末,我的一位最知心的友人,于一個冬雪的清晨忽然迫不及待地到我家里來,他劈頭一句話就告訴我,他的冤案拖了20多年,昨天已告平反。我聽後驚喜不勝,來不及敘舊,緊緊地抱住他不放。我看到他自此可以自由了,往日的冤屈已云消煙散,我的歡快之情幾乎無以復加;但想到他多年來的顛簸生涯,家庭破碎之狀,一種為他凄苦之思又油然而生。此時我的凄苦與歡快的情思交織在一起,我真辨不出那到底是歡樂還是苦楚的滋味。
如今年邁,憶及往日的冬雪種種,不勝欷噓。此刻我在雪地上漫走,雪止風息,路上皚白一片,我看見一群孩子正堆起一個雪人,臉部用墨炭勾畫出一個魔鬼像。他們各捏雪團若干,對雪魔群起而攻之,一時雪魔的臉面與全身被雪團擲得面目全非。孩子們邊擲邊叫,笑聲與叫聲混成一片,煞是熱鬧。這時,恰有一輛自行車飛馳而來,騎者是一少年,忽然他不慎翻車滑倒,砉然有聲。我還以為這少年受了傷,豈知他迅速爬起,躍身上車,疾馳而去。我目睹此情,驚嘆不止,那一派青春活力,揚起令人心喜的生命之火,那青春的魅力讓我感到這冬雪大地上增添了陣陣綠意。我忽然想起了杜甫的詩句:“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我在冬雪的嚴寒中,知曉了一點春天的消息。P2-7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