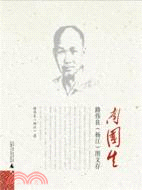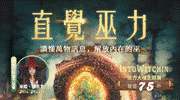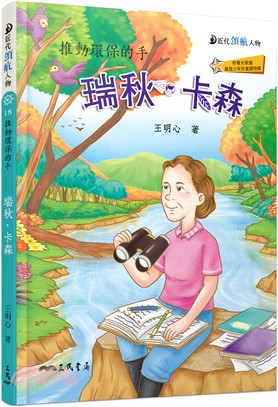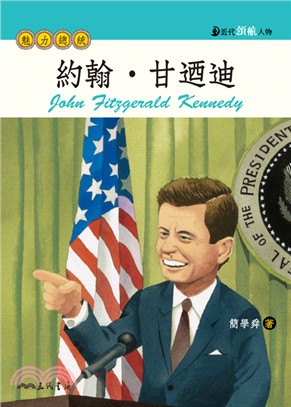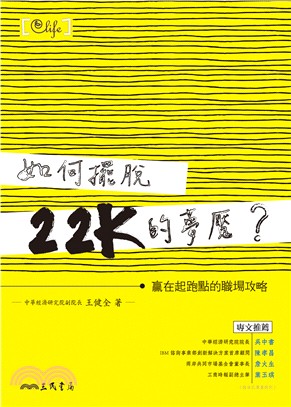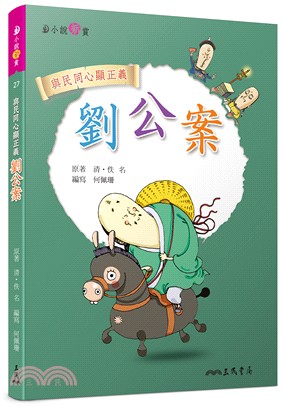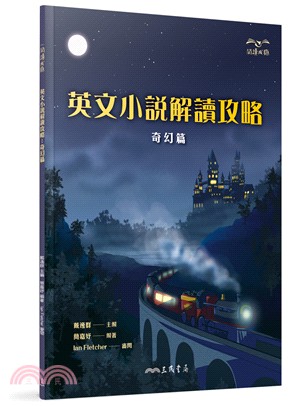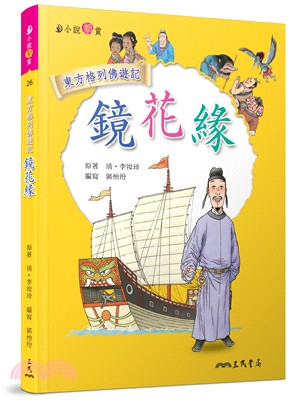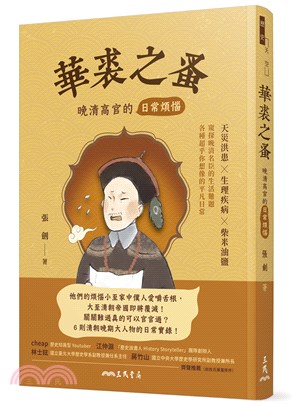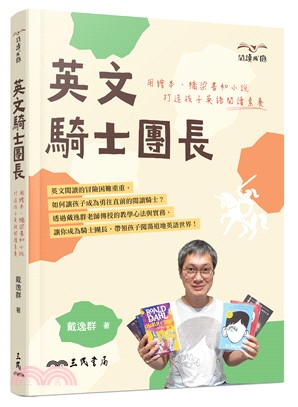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我們的父親以“楊江”這個化名--中共地下工作時的假名--行世,他的本名叫“路偉良”,這是廣西融水縣古鼎村路氏家族的“序列號”。
這個農民的兒子在大苗山做過先生,入廣西師專後學習唯物論,選擇革命救國之路,成為廣西早期中共地下黨員。
其後在粵、滇敵後打遊擊,創建滇桂黔羅盤區根據地,迎解放,任地委書記。50年代,在一機部任司長,搞經濟,後任廣西師院(今廣西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搞教育至“文革-前夕。
本書絕大部分內容以“文革”後發還的父親檔案材料為主,稟真據實,編綴而成。
《南國生》之名,取自母親生前最愛的小詩,詩雲“紅豆生南國……”,而父親讀大學的校園(桂林雁山西林公園)內,便曾有一株這種罕見的相思紅豆樹。
這個農民的兒子在大苗山做過先生,入廣西師專後學習唯物論,選擇革命救國之路,成為廣西早期中共地下黨員。
其後在粵、滇敵後打遊擊,創建滇桂黔羅盤區根據地,迎解放,任地委書記。50年代,在一機部任司長,搞經濟,後任廣西師院(今廣西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搞教育至“文革-前夕。
本書絕大部分內容以“文革”後發還的父親檔案材料為主,稟真據實,編綴而成。
《南國生》之名,取自母親生前最愛的小詩,詩雲“紅豆生南國……”,而父親讀大學的校園(桂林雁山西林公園)內,便曾有一株這種罕見的相思紅豆樹。
名人/編輯推薦
《南國生——路偉良(楊江)圖文存》為路偉良(又名:楊江)先生的遺稿和生前圖片結集。路偉良先生1911年生于一個貧寒的家庭,年青時期即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長為優秀而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新中國成立後,他投入祖國教育事業建設,為廣西師院(今廣西師范大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南國生——路偉良(楊江)圖文存》取名自“紅豆生南國”,表達路偉良先生對故土的眷戀之情。全書生動地反映了他飽經滄桑的一生,以個人奮斗史折射出中國現代百年歷史的風云變幻。
序
并不遙遠的記憶
父親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從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軍隊療養院那間寬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歸宿地與他過去的軍人身份挺相符。
父親一生里有過幾種截然不同的身份:25歲—35歲,他做過國民黨桂系軍校的教官、國民中學的校長,但隱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支部書記。35歲—41歲時,他已不必潛伏在敵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軍在云南的一支正規游擊隊里,擁有自己心愛的美式卡賓槍的司令員。直到1954年,當上一機部司長的父親,才上繳了那支隨身多年的勃朗寧小手槍,軍人情結似乎也到此為止。後來,他從北京調回廣西,身份是一所大學的黨委書記,搞教育、搞運動成了父親後半輩子的專業。不過,在伴隨我們成長的許多個周末里,父親也會技癢難耐,他帶著我們幾個小兵到郊外打鳥,槍也換過好幾種:小口徑、獵槍、氣槍。“文革”初起,紅衛兵給他戴了一頂奇怪的帽子:“打鳥書記”。
後來,當我開始翻檢那一大箱“文革”後退還父親的檔案材料時,我發現,盡管父親的身份幾十年中發生過很大轉換,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認同他那個時代的文學青年本色。這個秘密注釋就藏在一冊絳紅色的64開日記本的扉頁上,落筆時間是1949年11月16日:
在……中國人民可以子孫萬代享……幸福了。緯!將來我們……飛的計劃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著我們寫作……
這個被38歲的父親稱作“緯”的昆明姑娘叫張世緯,時年21歲,是父親任司令員的那支部隊里的一名教導員,畢業于著名的昆華女中,後來成了我們的母親。
早年就讀廣西師專時,父親就是墻報、校刊和《民國日報》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親在南寧養病,我隨侍身邊。一天,我在廣西圖書館查到一篇署名“蘆葦”,發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歲的父親依稀記得,這正是他當年常用的筆名之一。在父親的一篇回憶大學時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個發表苗山鄉村調查的“蘆葦”,一年之後(指1936年6月1日爆發的“兩廣事變”),同樣是在南寧,又成了《廣西學生軍宣言》的幾位起草人之
父親走了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墻壁上的鏡框——那是父親1957年離開北京回廣西前的照片——是母親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親,我們都會沐浴在父親的目光下。有時,與墻上的父親默默對視,那一刻,我感覺目光穿透了時空。但我分明意識到,假如父親仍與我們生活在同一時空,這種交流似乎要平淡許多。
也許這是一種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種血液遺傳里包含的溝通,是一種動物性很強的嗅覺,也是一種情感上的審視和仰望,卻似乎僅僅在家族成員缺席的情況下才被誘發出來。
其實,我們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記憶中,母親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隨左右。至今已屬于50後、60後的小同學之間那些親密無猜的日子里,最讓人記憶的場景,莫過于寒暑假時家中嘰嘰喳喳的學習小組了。那時,總是母親替我們張羅,噓寒問暖,遇到保姆煮了紅薯,包了餃子,乃至那幾甕泡菜缸又腌出酸蘿卜、茼筍、蒜苗、辣椒什么的,母親會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領發揮到極致。導致許多年後,我們的同學仍能大談在“楊書記家”吃的經歷……不過,每逢這種場面發生時,似乎父親總不在場,即便在,留給我們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親來去匆匆,秘書有時跟著進家門,見我們在後院打鬧,最多是秘書過來與母親打個招呼。如果哪一次父親也走到我們圍坐的小圓桌,同學們便怯生生地站起來,說一聲:“楊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聲了。
父親謹言少語,但我們并不害怕他。有時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纏著他,要求帶他們到郊外打烏,并且堅持自己扣動扳機,這時候,父親便會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來摸摸他們的小腦袋,用夾雜著普通話的桂林腔說道:“禮拜天我帶你們去鳥山……”所以,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許多鳥類的名字,如肥碩的斑鳩、敏捷的鷂鷹、傻乎乎的“包鳥”、謹慎的白鷺、小不點的綠豆鳥、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鷹等等。只有小妹超英從不參與這種“血腥”的活動。
好多年了,家里總是放著一兩支那種漆成深棗紅色的小口徑步槍,我們愛看父親擦槍的樣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來復線”為何是螺旋狀的。小口徑子彈裝在一種特制的紙盒里,打開抽屜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著黃銅和鉛做的槍彈,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
每當父親帶著我們,騎著那輛北京帶來的東德產倒閘自行車,興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鉆進當時人跡不多的樹林子,要不了多久,就會發現目標。把標尺缺口與準星連成一線,指向枝頭跳躍的斑鳩或小絨球似的綠豆鳥,指向水田里覓食的白鷺或獨秀峰上孤獨的老鷹時,我們的心臟就怦怦亂跳……最揪心的還是那“啪”的一聲,如同拍巴掌似的槍響——現在想起來還對那些無辜的生靈心有內疚。但當時最令我們興奮與困惑的便是“應聲倒下”這種畫面,因為我始終鬧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彈何以能讓數十米開外的獵物瞬間栽倒?
另一個與父親記憶有關的場景是游泳。
盡管長大以後對父親的“栽培”記憶猶新,按照順序,最先是學會游泳,其次是騎單車和打鳥,然後是照相。上小學,我們已懂得擺弄相機,初中時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遺憾的是,除了上述幾項生存本領,我不記得父親是否要求過我們練習書法或閱讀某一本書。
對于游泳,生長在南方的父親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從小就把游泳視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說,游泳的目的是鍛煉身體。“鍛煉”兩個字,也許是我們聽到的父親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我們非常樂意跟父親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見底的江水,鋪滿鵝卵石的沙灘,自由自在的嬉鬧正是我們童年的樂趣也!
……
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發生了轟動一時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賣,廣西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省工委副書記蘇曼、組織部長羅文坤(蘇曼夫人)、交通員張海萍三人,為保守黨的機密集體自殺身亡。蘇、羅、張被捕後曾被當作誘餌放回他們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學,準備抓捕前來聯系的人。第三天晨,蘇、羅、張被發現已在宿舍內自縊身亡。後來,地下黨內部傳達的通報是:蘇曼擔心羅、張兩女同志恐難承受敵人嚴刑逼供,三人議決用犧牲保住組織機密。當時,父親因先後擔任桂林兩所學校的地下黨支部書記,與蘇曼、張海萍均有秘密聯系,這些足以證明,由于戰友的獻身,當年31歲的父親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事件後,地下黨紛紛撤離桂林,而父親因未暴露身份而繼續潛伏,直到一年後,組織上對他重新審查,并派人接上關系。
第三次發生在1946年,當時父親的公開身份是廣西全州中學校長,由于內戰已開,桂系與中共對立,地下黨派人通知父親擇機撤出廣西,怎樣撤?自己想辦法也。父親的辦法是,先到重慶朋友所在的學校謀職過渡,以避免引起廣西的注意,然後再輾轉到香港,與組織接上關系。新中國成立後審干時父親才知道,通知他撤離廣西的人後已犧牲,在香港為他恢復關系的地下黨領導人也在新中國成立前病逝,這段“脫黨”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證人。 這些“脫黨”情節,顯然成了父親個人歷史中政治純潔程度的傷疤。我想,父親內心深處對那些傷疤一定保持著適當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從云南調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審干時填寫的履歷表副本,1957年他調回廣西前一機部對他作出的審查結論,以及1956年寫的《自傳》初稿等等,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脫黨”的,包括集體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問題,必不厭其煩,記錄在案,坦誠面對組織,不可謂不由衷。
關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這兩部分的手稿,都是當年的檢查認罪材料,語言風格是經歷過那個“急風暴雨”時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們原汁原味地留下來,恰恰是因為這是歷史原物,同樣的文字用不同的組詞造句習慣、不同的情緒和心態寫成文章,便保留了時代情狀和歷史現場的信息。為了讓更多的讀者能夠在閱讀的時候不至于太費勁,我盡可能地作出注釋和說明。
以我過去和現在對父親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許并不愿意讓研究者以外的後人看到這些文字,在他還活著并且還有預期心愿的時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後,人們已經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態,來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輩和扭曲的歷史。
揚三五
楊小肅(執筆)
楊小山
楊超英
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父親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從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軍隊療養院那間寬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歸宿地與他過去的軍人身份挺相符。
父親一生里有過幾種截然不同的身份:25歲—35歲,他做過國民黨桂系軍校的教官、國民中學的校長,但隱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支部書記。35歲—41歲時,他已不必潛伏在敵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軍在云南的一支正規游擊隊里,擁有自己心愛的美式卡賓槍的司令員。直到1954年,當上一機部司長的父親,才上繳了那支隨身多年的勃朗寧小手槍,軍人情結似乎也到此為止。後來,他從北京調回廣西,身份是一所大學的黨委書記,搞教育、搞運動成了父親後半輩子的專業。不過,在伴隨我們成長的許多個周末里,父親也會技癢難耐,他帶著我們幾個小兵到郊外打鳥,槍也換過好幾種:小口徑、獵槍、氣槍。“文革”初起,紅衛兵給他戴了一頂奇怪的帽子:“打鳥書記”。
後來,當我開始翻檢那一大箱“文革”後退還父親的檔案材料時,我發現,盡管父親的身份幾十年中發生過很大轉換,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認同他那個時代的文學青年本色。這個秘密注釋就藏在一冊絳紅色的64開日記本的扉頁上,落筆時間是1949年11月16日:
在……中國人民可以子孫萬代享……幸福了。緯!將來我們……飛的計劃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著我們寫作……
這個被38歲的父親稱作“緯”的昆明姑娘叫張世緯,時年21歲,是父親任司令員的那支部隊里的一名教導員,畢業于著名的昆華女中,後來成了我們的母親。
早年就讀廣西師專時,父親就是墻報、校刊和《民國日報》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親在南寧養病,我隨侍身邊。一天,我在廣西圖書館查到一篇署名“蘆葦”,發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歲的父親依稀記得,這正是他當年常用的筆名之一。在父親的一篇回憶大學時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個發表苗山鄉村調查的“蘆葦”,一年之後(指1936年6月1日爆發的“兩廣事變”),同樣是在南寧,又成了《廣西學生軍宣言》的幾位起草人之
父親走了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墻壁上的鏡框——那是父親1957年離開北京回廣西前的照片——是母親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親,我們都會沐浴在父親的目光下。有時,與墻上的父親默默對視,那一刻,我感覺目光穿透了時空。但我分明意識到,假如父親仍與我們生活在同一時空,這種交流似乎要平淡許多。
也許這是一種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種血液遺傳里包含的溝通,是一種動物性很強的嗅覺,也是一種情感上的審視和仰望,卻似乎僅僅在家族成員缺席的情況下才被誘發出來。
其實,我們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記憶中,母親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隨左右。至今已屬于50後、60後的小同學之間那些親密無猜的日子里,最讓人記憶的場景,莫過于寒暑假時家中嘰嘰喳喳的學習小組了。那時,總是母親替我們張羅,噓寒問暖,遇到保姆煮了紅薯,包了餃子,乃至那幾甕泡菜缸又腌出酸蘿卜、茼筍、蒜苗、辣椒什么的,母親會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領發揮到極致。導致許多年後,我們的同學仍能大談在“楊書記家”吃的經歷……不過,每逢這種場面發生時,似乎父親總不在場,即便在,留給我們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親來去匆匆,秘書有時跟著進家門,見我們在後院打鬧,最多是秘書過來與母親打個招呼。如果哪一次父親也走到我們圍坐的小圓桌,同學們便怯生生地站起來,說一聲:“楊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聲了。
父親謹言少語,但我們并不害怕他。有時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纏著他,要求帶他們到郊外打烏,并且堅持自己扣動扳機,這時候,父親便會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來摸摸他們的小腦袋,用夾雜著普通話的桂林腔說道:“禮拜天我帶你們去鳥山……”所以,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許多鳥類的名字,如肥碩的斑鳩、敏捷的鷂鷹、傻乎乎的“包鳥”、謹慎的白鷺、小不點的綠豆鳥、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鷹等等。只有小妹超英從不參與這種“血腥”的活動。
好多年了,家里總是放著一兩支那種漆成深棗紅色的小口徑步槍,我們愛看父親擦槍的樣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來復線”為何是螺旋狀的。小口徑子彈裝在一種特制的紙盒里,打開抽屜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著黃銅和鉛做的槍彈,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
每當父親帶著我們,騎著那輛北京帶來的東德產倒閘自行車,興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鉆進當時人跡不多的樹林子,要不了多久,就會發現目標。把標尺缺口與準星連成一線,指向枝頭跳躍的斑鳩或小絨球似的綠豆鳥,指向水田里覓食的白鷺或獨秀峰上孤獨的老鷹時,我們的心臟就怦怦亂跳……最揪心的還是那“啪”的一聲,如同拍巴掌似的槍響——現在想起來還對那些無辜的生靈心有內疚。但當時最令我們興奮與困惑的便是“應聲倒下”這種畫面,因為我始終鬧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彈何以能讓數十米開外的獵物瞬間栽倒?
另一個與父親記憶有關的場景是游泳。
盡管長大以後對父親的“栽培”記憶猶新,按照順序,最先是學會游泳,其次是騎單車和打鳥,然後是照相。上小學,我們已懂得擺弄相機,初中時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遺憾的是,除了上述幾項生存本領,我不記得父親是否要求過我們練習書法或閱讀某一本書。
對于游泳,生長在南方的父親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從小就把游泳視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說,游泳的目的是鍛煉身體。“鍛煉”兩個字,也許是我們聽到的父親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我們非常樂意跟父親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見底的江水,鋪滿鵝卵石的沙灘,自由自在的嬉鬧正是我們童年的樂趣也!
……
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發生了轟動一時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賣,廣西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省工委副書記蘇曼、組織部長羅文坤(蘇曼夫人)、交通員張海萍三人,為保守黨的機密集體自殺身亡。蘇、羅、張被捕後曾被當作誘餌放回他們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學,準備抓捕前來聯系的人。第三天晨,蘇、羅、張被發現已在宿舍內自縊身亡。後來,地下黨內部傳達的通報是:蘇曼擔心羅、張兩女同志恐難承受敵人嚴刑逼供,三人議決用犧牲保住組織機密。當時,父親因先後擔任桂林兩所學校的地下黨支部書記,與蘇曼、張海萍均有秘密聯系,這些足以證明,由于戰友的獻身,當年31歲的父親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事件後,地下黨紛紛撤離桂林,而父親因未暴露身份而繼續潛伏,直到一年後,組織上對他重新審查,并派人接上關系。
第三次發生在1946年,當時父親的公開身份是廣西全州中學校長,由于內戰已開,桂系與中共對立,地下黨派人通知父親擇機撤出廣西,怎樣撤?自己想辦法也。父親的辦法是,先到重慶朋友所在的學校謀職過渡,以避免引起廣西的注意,然後再輾轉到香港,與組織接上關系。新中國成立後審干時父親才知道,通知他撤離廣西的人後已犧牲,在香港為他恢復關系的地下黨領導人也在新中國成立前病逝,這段“脫黨”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證人。 這些“脫黨”情節,顯然成了父親個人歷史中政治純潔程度的傷疤。我想,父親內心深處對那些傷疤一定保持著適當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從云南調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審干時填寫的履歷表副本,1957年他調回廣西前一機部對他作出的審查結論,以及1956年寫的《自傳》初稿等等,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脫黨”的,包括集體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問題,必不厭其煩,記錄在案,坦誠面對組織,不可謂不由衷。
關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這兩部分的手稿,都是當年的檢查認罪材料,語言風格是經歷過那個“急風暴雨”時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們原汁原味地留下來,恰恰是因為這是歷史原物,同樣的文字用不同的組詞造句習慣、不同的情緒和心態寫成文章,便保留了時代情狀和歷史現場的信息。為了讓更多的讀者能夠在閱讀的時候不至于太費勁,我盡可能地作出注釋和說明。
以我過去和現在對父親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許并不愿意讓研究者以外的後人看到這些文字,在他還活著并且還有預期心愿的時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後,人們已經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態,來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輩和扭曲的歷史。
揚三五
楊小肅(執筆)
楊小山
楊超英
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目次
并不遙遠的記憶(代序)
自傳
陶保桓烈士傳
附一:從苗山中出來
附二:融縣羅城苗山拾零
廣西師專概況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關廣西地方建設干校的情況
附:我的歷史問題交代
我所了解的廣西地下黨的情況
我在廣東及云南工作情況的交代
附一:板橋日記
附二:錄音記錄
附三:鐘山鄉紀行
上海通信
附:對大量生產類型工廠工作的意見
“文革”前筆記
我在廣西師院幾年工作的初步檢查
附:十年歷程
我的檢查
附一:“文革”初期幾個問題的交代
附二:張云瑩逝世前後的情況匯報
關于三個問題的交代
附:關于處理秦似、趙佩瑩問題的檢查
思想匯報
附一:對支部大會所提意見的補充意見
附二:對楊江同志三次失掉組織關系及參加國民黨等問題的
審查結論
附三:關于楊江同志政治歷史問題的復查結論
附錄
往事的回憶
楊江與羅盤區
自傳
陶保桓烈士傳
附一:從苗山中出來
附二:融縣羅城苗山拾零
廣西師專概況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關廣西地方建設干校的情況
附:我的歷史問題交代
我所了解的廣西地下黨的情況
我在廣東及云南工作情況的交代
附一:板橋日記
附二:錄音記錄
附三:鐘山鄉紀行
上海通信
附:對大量生產類型工廠工作的意見
“文革”前筆記
我在廣西師院幾年工作的初步檢查
附:十年歷程
我的檢查
附一:“文革”初期幾個問題的交代
附二:張云瑩逝世前後的情況匯報
關于三個問題的交代
附:關于處理秦似、趙佩瑩問題的檢查
思想匯報
附一:對支部大會所提意見的補充意見
附二:對楊江同志三次失掉組織關系及參加國民黨等問題的
審查結論
附三:關于楊江同志政治歷史問題的復查結論
附錄
往事的回憶
楊江與羅盤區
書摘/試閱
賀縣中學、桂林師范和全州中學
當時,省教育廳是黃樸心當廳長,他是政學系的人物,廣西賀縣人。當時賀縣中學辦得不好,他要求物色一個能干的人去辦好賀中,我經過湯有雁——師專同學,大革命時脫黨,脫黨後傾向進步——的介紹,在1943年下半年到賀縣中學當校長。
由于“七九”事件後,蘇曼、羅文坤、張海萍自殺,偽省訓團的地下黨員分別離開,當時,我始終在偽省訓團工作,但組織上沒有人來聯系,我的組織關系也暫時中斷,直到我去賀縣中學後,吳贊之同志(現在南寧市委工作)到賀縣中學和我取得聯系,經過上級審查以後,繼續接上組織關系。
我到賀縣中學後,陸續請了一批進步教師到賀中,如陳貞嫻、蕭敏頌、曹國智、何明、馮娛修、吳帆波等來校教書。1944年桂林淪陷,賀縣中學處于敵後了。但賀縣八步有平樂專員公署,專員李新俊,他是李濟深的舊部,李濟深正醞釀在梧州、八步一帶搞武裝。當時,由桂林疏散到八步的,有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如陳此生、陳劭先、莫乃群、梁漱溟等,他們在昭平辦《廣西日報》(昭平版),也在積極活動。我黨也在平樂專區內搞農民組織工作。組織上當時給我的任務是,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逐步設法向偽政府搞一些槍支自衛,必要時,聽組織上指揮,組織學生搞武裝斗爭。
由于敵人始終未到賀縣,我也沒有暴露過。學校在情況緊張時,停課一下,在平靜時又復課教書。由于有進步教師在學校教課,地方反動勢力把我看成眼中釘一樣,他們幾次發動學生在校內鬧風潮,但由于黃樸心的關系以及地方進步力量的支持,他們沒有得逞。
在賀縣中學時期,處在淪陷區的形勢下,我們在學校的任務,是對學生進行抗戰必勝的教育,穩定敵後人心,做必要的準備,以便在敵人到達後發動武裝斗爭和敵人對抗。但日寇始終沒有到過周圍縣份,賀縣也沒有淪陷,一直搞到日寇投降,抗戰勝利。
當時組織上和我聯系的是吳贊之,吳贊之是我們融縣人。以後另派一個同志來,這個同志記不起名字了。粟稔當時在家,也和我聯系過。組織上和我都是個別聯系。在校工作的地下黨員有陳貞嫻、馮娛修(粟稔的愛人),她們和我都沒有組織聯系,我的組織關系,她們也不知道。 1945年下半年,我辭了賀縣中學校長職務,到桂林師范學校教書半年。湯有雁任桂林師范學校校長,在學生中我黨勢力占絕大優勢,學生們閱讀進步書刊,研究抗戰勝利後的實際問題,十分活躍。
在教師中,地下黨員有張鎮道、陶保恒、毛恣觀和我四個人。開始時,沒有建立支部,和學生也沒有聯系。後來,錢興同志和我聯系,他指定張鎮道當支書,建立教工中地下黨支部,逐漸與學生中黨員建立聯系,這時,我已離開桂師了。
我在桂師工作時間只一個學期,在桂師工作時,通過湯有雁的關系繼續得到黃樸心的保薦,1946年,我就到全州中學當校長去了。
全州中學是一個反動勢力控制比較強的學校,有偽專員陳恩元及蔣綜遜等反動勢力,充當學校反動教師的後臺,校內又有趙經武、趙欽武兄弟是中統特務。我初去時,即受到反動勢力的抵制,後來終于堅持進去了,安排了一些進步教師去教書,如王松(現云南新華報記者,共產黨員)、李仲良(云南寧洱地委宣傳部工作,共產黨員)等,反動勢力又發動學生來排擠王松等進步教師離校,斗爭是比較復雜的。
當時,組織上和我聯系的是陸翔和張鎮道同志。1946年下半年,張鎮道同志通知我,組織上要我考慮,如廣西無可靠後臺作依靠,即堅決撤出廣西:我研究的結果,認為我在廣西當了兩次校長,主要是靠湯有雁向黃樸心推薦的。此外,我還到偽中央訓練團受訓過。除此之外,并無什么靠山可以依靠。而且,我和黃樸心的關系,只是一般關系,他想利用我來辦好學校,作為他升官的工具而已。
考慮的結果,決定堅決執行組織上的決定,馬上離開廣西。當時正有朋友在重慶鄉村建設學院工作,經過他們的介紹,我在1946年7月左右,便辭了全州中學校長職務,到重慶鄉建學院去了。
我到香港後才知道是廣西省委書記錢興同志經過張鎮道(也是1946年從廣西撤退到廣東打游擊,他是一個主力團團長,在攻笆江時犧牲)通知我的。
重慶鄉建學院
重慶鄉村建設學院是晏陽初靠美元來辦的一個學校。這個學校的教務主任葉德光是一個進步人士(葉德光留美後,在解放後由美國回國,在我外交部工作。葉德光及其愛人都擅長英語,是否黨員不清楚,因我和他只有到鄉建學院時有過一面之識)。因此,他聘請了一批進步人士在那里教書。正因為他辦得比較進步,我到鄉建學院不久,晏陽初借故把他送到美國去留學,另派人來接替他的工作。在歡送葉德光去留美的歡送會開過不久,鄉建學院學生正掀起一個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反動政府即派來大批軍警,對進步學生與進步教師進行大逮捕。
當時,我到學校只有一個月左右,與學生、教師接觸不多,我的職務是講師兼注冊主任。後來,因許多進步教師與進步學生被捕,我即和進步教師的愛人及留校學生再組織起來,搞營救被捕師生的活動。那時,在學校搞營救運動的主要負責人是劉天行的愛人俞淑清。當時,晏陽初已新派一個教務主任來了,此人姓屈,什么名字記不清了,我被推選為留校師生代表之一去和他談判。當時,我們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師生,他答應同重慶警備司令部交涉。
後來,由此人擔保,當局釋放了鄉建學院被捕的一部分教授、講師及部分進步學生。我的朋友劉天行、徐堅等被釋放後,馬上搭飛機到香港。我亦被學校辭退。當營救運動得到一定效果後,我就和劉天行的愛人俞淑清等一道離開重慶,經廣州到香港。到香港後,通過粟捻介紹和錢興同志見面,接上了關系。
我在鄉建學院只搞了三個月的工作。在鄉建學院時期,和香港的粟稔同志有個別通訊聯系。在鄉建學院和劉天行、俞淑清夫婦有過工作關系,劉、俞都是共產黨員,現在廣東茂名縣工作,劉任文教局長,俞任衛生局長。
在十一年的廣西地下工作時期,我對于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搞革命還是不甚了了。廣西地下黨大革命以後的工作一直是浮在青年學生中,只在抗戰時期才有一部分轉到農民中去。因為沒有先進的革命根據地為基礎,斗爭就沒有力量。我在城市中工作,對長期隱蔽、蓄積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有所體會,但對武裝斗爭這一主要的方面,由于缺乏實踐知識,實在了解不多,對于如何利用敵人矛盾,發展我們的革命力量,如何逐步把敵人的統治推翻,我在廣西地下工作十一年,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P30-33
當時,省教育廳是黃樸心當廳長,他是政學系的人物,廣西賀縣人。當時賀縣中學辦得不好,他要求物色一個能干的人去辦好賀中,我經過湯有雁——師專同學,大革命時脫黨,脫黨後傾向進步——的介紹,在1943年下半年到賀縣中學當校長。
由于“七九”事件後,蘇曼、羅文坤、張海萍自殺,偽省訓團的地下黨員分別離開,當時,我始終在偽省訓團工作,但組織上沒有人來聯系,我的組織關系也暫時中斷,直到我去賀縣中學後,吳贊之同志(現在南寧市委工作)到賀縣中學和我取得聯系,經過上級審查以後,繼續接上組織關系。
我到賀縣中學後,陸續請了一批進步教師到賀中,如陳貞嫻、蕭敏頌、曹國智、何明、馮娛修、吳帆波等來校教書。1944年桂林淪陷,賀縣中學處于敵後了。但賀縣八步有平樂專員公署,專員李新俊,他是李濟深的舊部,李濟深正醞釀在梧州、八步一帶搞武裝。當時,由桂林疏散到八步的,有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如陳此生、陳劭先、莫乃群、梁漱溟等,他們在昭平辦《廣西日報》(昭平版),也在積極活動。我黨也在平樂專區內搞農民組織工作。組織上當時給我的任務是,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逐步設法向偽政府搞一些槍支自衛,必要時,聽組織上指揮,組織學生搞武裝斗爭。
由于敵人始終未到賀縣,我也沒有暴露過。學校在情況緊張時,停課一下,在平靜時又復課教書。由于有進步教師在學校教課,地方反動勢力把我看成眼中釘一樣,他們幾次發動學生在校內鬧風潮,但由于黃樸心的關系以及地方進步力量的支持,他們沒有得逞。
在賀縣中學時期,處在淪陷區的形勢下,我們在學校的任務,是對學生進行抗戰必勝的教育,穩定敵後人心,做必要的準備,以便在敵人到達後發動武裝斗爭和敵人對抗。但日寇始終沒有到過周圍縣份,賀縣也沒有淪陷,一直搞到日寇投降,抗戰勝利。
當時組織上和我聯系的是吳贊之,吳贊之是我們融縣人。以後另派一個同志來,這個同志記不起名字了。粟稔當時在家,也和我聯系過。組織上和我都是個別聯系。在校工作的地下黨員有陳貞嫻、馮娛修(粟稔的愛人),她們和我都沒有組織聯系,我的組織關系,她們也不知道。 1945年下半年,我辭了賀縣中學校長職務,到桂林師范學校教書半年。湯有雁任桂林師范學校校長,在學生中我黨勢力占絕大優勢,學生們閱讀進步書刊,研究抗戰勝利後的實際問題,十分活躍。
在教師中,地下黨員有張鎮道、陶保恒、毛恣觀和我四個人。開始時,沒有建立支部,和學生也沒有聯系。後來,錢興同志和我聯系,他指定張鎮道當支書,建立教工中地下黨支部,逐漸與學生中黨員建立聯系,這時,我已離開桂師了。
我在桂師工作時間只一個學期,在桂師工作時,通過湯有雁的關系繼續得到黃樸心的保薦,1946年,我就到全州中學當校長去了。
全州中學是一個反動勢力控制比較強的學校,有偽專員陳恩元及蔣綜遜等反動勢力,充當學校反動教師的後臺,校內又有趙經武、趙欽武兄弟是中統特務。我初去時,即受到反動勢力的抵制,後來終于堅持進去了,安排了一些進步教師去教書,如王松(現云南新華報記者,共產黨員)、李仲良(云南寧洱地委宣傳部工作,共產黨員)等,反動勢力又發動學生來排擠王松等進步教師離校,斗爭是比較復雜的。
當時,組織上和我聯系的是陸翔和張鎮道同志。1946年下半年,張鎮道同志通知我,組織上要我考慮,如廣西無可靠後臺作依靠,即堅決撤出廣西:我研究的結果,認為我在廣西當了兩次校長,主要是靠湯有雁向黃樸心推薦的。此外,我還到偽中央訓練團受訓過。除此之外,并無什么靠山可以依靠。而且,我和黃樸心的關系,只是一般關系,他想利用我來辦好學校,作為他升官的工具而已。
考慮的結果,決定堅決執行組織上的決定,馬上離開廣西。當時正有朋友在重慶鄉村建設學院工作,經過他們的介紹,我在1946年7月左右,便辭了全州中學校長職務,到重慶鄉建學院去了。
我到香港後才知道是廣西省委書記錢興同志經過張鎮道(也是1946年從廣西撤退到廣東打游擊,他是一個主力團團長,在攻笆江時犧牲)通知我的。
重慶鄉建學院
重慶鄉村建設學院是晏陽初靠美元來辦的一個學校。這個學校的教務主任葉德光是一個進步人士(葉德光留美後,在解放後由美國回國,在我外交部工作。葉德光及其愛人都擅長英語,是否黨員不清楚,因我和他只有到鄉建學院時有過一面之識)。因此,他聘請了一批進步人士在那里教書。正因為他辦得比較進步,我到鄉建學院不久,晏陽初借故把他送到美國去留學,另派人來接替他的工作。在歡送葉德光去留美的歡送會開過不久,鄉建學院學生正掀起一個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反動政府即派來大批軍警,對進步學生與進步教師進行大逮捕。
當時,我到學校只有一個月左右,與學生、教師接觸不多,我的職務是講師兼注冊主任。後來,因許多進步教師與進步學生被捕,我即和進步教師的愛人及留校學生再組織起來,搞營救被捕師生的活動。那時,在學校搞營救運動的主要負責人是劉天行的愛人俞淑清。當時,晏陽初已新派一個教務主任來了,此人姓屈,什么名字記不清了,我被推選為留校師生代表之一去和他談判。當時,我們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師生,他答應同重慶警備司令部交涉。
後來,由此人擔保,當局釋放了鄉建學院被捕的一部分教授、講師及部分進步學生。我的朋友劉天行、徐堅等被釋放後,馬上搭飛機到香港。我亦被學校辭退。當營救運動得到一定效果後,我就和劉天行的愛人俞淑清等一道離開重慶,經廣州到香港。到香港後,通過粟捻介紹和錢興同志見面,接上了關系。
我在鄉建學院只搞了三個月的工作。在鄉建學院時期,和香港的粟稔同志有個別通訊聯系。在鄉建學院和劉天行、俞淑清夫婦有過工作關系,劉、俞都是共產黨員,現在廣東茂名縣工作,劉任文教局長,俞任衛生局長。
在十一年的廣西地下工作時期,我對于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搞革命還是不甚了了。廣西地下黨大革命以後的工作一直是浮在青年學生中,只在抗戰時期才有一部分轉到農民中去。因為沒有先進的革命根據地為基礎,斗爭就沒有力量。我在城市中工作,對長期隱蔽、蓄積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有所體會,但對武裝斗爭這一主要的方面,由于缺乏實踐知識,實在了解不多,對于如何利用敵人矛盾,發展我們的革命力量,如何逐步把敵人的統治推翻,我在廣西地下工作十一年,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P30-33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