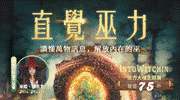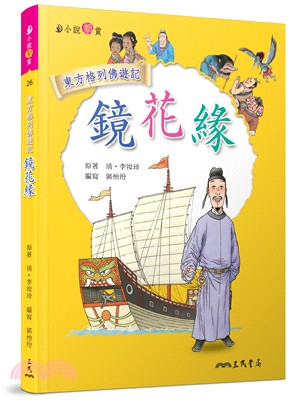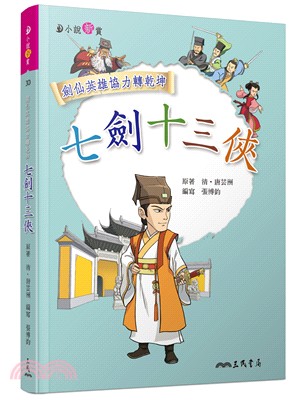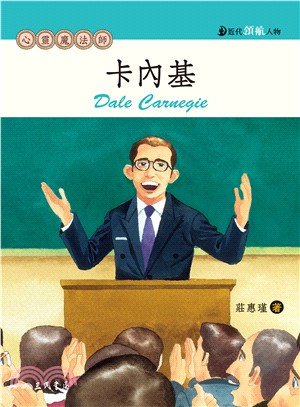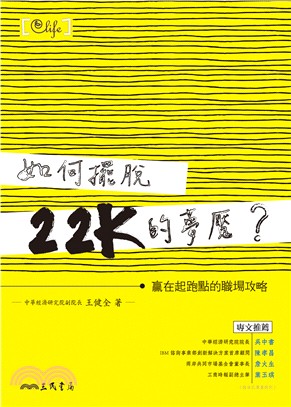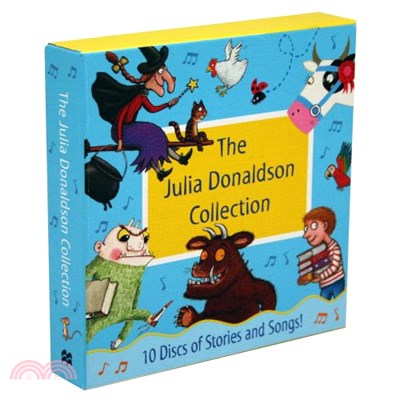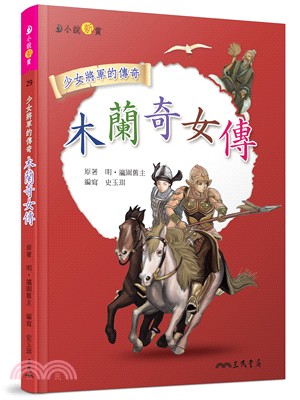商品簡介
十字軍運動其實尚未終止!
後冷戰時代,西方需要下一個敵人!
歐洲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辭彙,為歐亞大陸左側那片土地扮演政治認同其實是很晚近的發明!
「EUROPE」 一詞源自古希臘神話,不過在希臘人口中的EUROPE是指野蠻人居住之地;羅馬稱雄的時代,文明與野蠻的劃分是以是否分享羅馬文明為界,因此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是野蠻人。蠻族大遷徙的浪潮逐漸安定下來,基督教因為繼承了古代文明--猶太人的一神論、希臘的哲思雄辯、羅馬的帝國典章而得以馴化了蠻族,因此「基督教」成了這片土地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當東西教會公元1054年的分裂、1517年新教的出現,使得EUROPE歐洲成為團結這片土地的人為建構!
因此「歐洲」的出現不只是地理名詞更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工具,同時也需要外部「敵人」的協助進行內部的團結。歷史上扮演過這個外部敵人角色的有伊斯蘭、鄂圖曼土耳其、沙俄、蘇聯,正因為蘇聯使得大西洋兩岸達成空前的團結!
然而蘇聯解體了,西方(歐洲加上繼承歐洲文明美、加、澳、紐等等)能不再仰賴敵人的存在來掩飾彼此的差異甚至是抹滅彼此的差異嗎?歐洲作為西方的源頭未來只能是美帝的正當化工具、或是聯合國的橡皮圖章、或是馬前卒嗎?還是歐洲在經歷的兩次大戰與冷戰之後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景!
作者在本書不言而喻的判斷是,一旦歐洲企圖進行統一不論是以「宗教」之名、「帝國」或是「文明」帶給自己與其他人的反倒是災難,實情是歐洲分裂時反而開出進步的火花!
作者簡介
傑拉德.德朗提博士
為利物浦大學的社會系副教授。當前的研究興趣為現代性與社會理論,民主與社會運動。
譯者簡介
陳子瑜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歐洲研究碩士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士
序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百年,這也是適當的時刻讓我們反思史上最歷久不衰的主題之一,即「歐洲理念」(譯注:idea,從希臘文ideo而來,指一種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典範)。當許多以寬廣的歷史視點討論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書籍問世時,其中並沒有一本是以系統性與批判性的角度,去研究歐洲理念與當代政體中政治認同的關係。
「歐洲理念」是當代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面向,卻令人驚訝地有待探討。民族的神祕最終也臣服在眾多知識份子的批判下,但要打破作為一致化與普遍性計畫的歐洲迷思,仍未有任何批判見諸文字。
有人視歐洲是一種文化挑戰、一種哲學理想,或是地理概念,也有人側重歐洲的獨特性(韋伯)。我明白地將「歐洲」視為一種文化建構,並論證它不能被視為一個不證自明的整體,並破除歐洲的神祕性,以便評估在何種範圍內,歐洲理念可以在事實上藉由民族認同,以及「歐洲要塞」計畫這種沙文主義的狹隘規範性範疇,作為不受妨礙的集體認同基礎。
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是否能發展出不是基於族群—文化主義的集體認同,此一問題和那些涉及到經濟與政治整合的事項同等重要。本書旨在討論歐洲理念作為集體認同的基礎之限制與可能性。我所假設的答案是歐洲理念唯有在關注於新的公民身分概念上,才可成為規範性的集體認同基礎。
我的主旨為歐洲作為一種理念,它永遠都處於創造與再造的進程中,足球比賽的譬喻或許有助於概念化這點:球就是歐洲,球員們則是各種認同方案,而球場在本例中,便是地緣政治的實際運作場域。此項類比同時也強調了我的論點,即歐洲理念絕不是完全地被場上任一球員所控制;它佔據著由各種集體認同所競相爭奪的文化—象徵空間。歐洲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顆政治足球。
然而更進一步的延伸這譬喻,它並非沒有裁判的存在,因為實在的社會再生產同樣也涉及到規範性範疇;亦即是它可以被連結到擁有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權力的道德範疇。
目次
序言
謝辭
一.歐洲的矛盾性:本書理論導言
二.歐洲理念的起源:追溯歐洲理念在古典希臘羅馬時代的起源與萌芽
理論觀點/歐洲與古代人/基督受難向與伊斯蘭新月/基督教世界與歐洲
三.歐洲的西方化:「歐洲理念」與「基督教世界」之爭
理論觀點/歐洲政體之萌芽/十字軍意識形態的興起/歐洲認同與東方邊界歐洲
與日耳曼之形成/統一的神話/歐洲的西方化/歐洲認同與西方邊界
四.歐洲的界限:移轉中的邊界,西歐對歐洲理念的界定與佔有
理論觀點/作為邊疆之地的巴爾幹半島/居間之地/歐亞的創造
五.現代性時代裡的歐洲:西方體系民族國家的鞏固與歐洲理念的形成
理論觀點/歐洲認同的世俗化/歐洲與啟蒙運動/歐洲與法國大革命/歐洲與民
族理念歐洲的浪漫主義再發現
六.東方鏡像裡的歐洲:文明優越性的迷思與建構一個敵對世界體系必須的他者
理論觀點/東方的創造/文明與文化/歐洲與白人的重責大任
七.歐洲認同的危機:中歐的出現與法西斯主義
理論觀點/中歐(Mitteleuropa)的創造/歐洲的崩裂/歐洲悲觀主義/歐洲的法
西斯神話
八.作為冷戰建構物的歐洲:戰後重建與冷戰
理論觀點/美國的歐洲神話/歐洲與美國的對立依舊無解/歐洲與冷戰之起源/
市場的歐洲
九. 冷戰之後的歐洲:冷戰共識之瓦解對於歐洲理念的意涵探討
理論觀點/冷戰共識的終結/歐洲單點(EUROPE A LA CARTE)/歐洲主義的地緣政
治學/歐洲堡壘
十.結論:邁向後民族公民身分
書摘/試閱
歐洲認同的世俗化
義大利文意復興初期(Italian quattrocento,即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北歐的文藝復興形塑了通向一個新穎且久遠的歐洲認同意識之變遷。十五世紀以降,如我們所見,歐洲概念的使用頻率顯著地增加。這塊大陸的文化與地理之名不再彼此相符。基督教西方的理念,或基督教世界,開始失去之前的重要性,並慢慢被更世俗的歐洲意涵所取代。但這是個非常漸進的轉變。
第一步是由文藝復興及其人文主義理念所開始的。文藝復興可被視為一個整全的世界觀,提供歐洲認同在當代中的基礎。在一個民族主義尚未產生其影響的年代,文藝復興的文化使得全歐洲範圍的理念與風格之融合成為可能。但,由於其進化中的主要調解者是宗教改革,這使得它從來不曾是個完全世俗的認同。
正是宗教改革削弱了一種普世基督教秩序的理念,並為歐洲的世俗意涵之萌芽創造了空間,但儘管如此它仍緊緊地和基督教世界觀的殘留綁在一起。基督教整體在宗教改革後受到嚴重的打擊,所以並不難瞭解它是合乎情理地使用歐洲一詞而非基督教世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基督教就不重要了。帶來的結果是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古老對立被新的「文明的歐洲人」與「未開化的野蠻人」對立所取代。
對照的他者從小亞細亞轉到了美洲、非洲與剛贏取的亞洲。儘管土耳其威脅的想像在西方政治文化中仍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主題,它已逐漸不再佔有支配地位。事實上,除了法國之外,為了擊敗敵人而和土耳其人聯盟對西方政權來說並不罕見,例如哈布斯堡王朝便藉此和法國作戰。當歐洲取代基督教世界作為被認可的文化參考框架,奧圖曼人跟歐洲政權的關係在十七世紀結束時就變得越益世俗了。
一六四八年後基督教世界分裂為好幾個相互競爭的基督教派系:羅馬天主教、聖公會(Anglicanism,譯註:即英國國教)、路德宗、喀爾文宗及清教其他派系。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之後的階段與之前差異甚大。實際上走到盡頭的是統一的基督教世界之幻象。但這並不代表基督教不再像以前一樣重要,瞭解到這點是很重要的。實際上發生的是基督教不再是歐洲國家體系的疆域認同,變成以一種理性化之形式而存續下來的純粹宗教價值體系。
這個成長中的社會差異是那個時代其中一項影響最深遠的發展。一六四〇年代的英國內戰、一六八八年的光榮命與一六一八—四八的三十年宗教戰爭是歐洲世俗化的長期過程中,影響十分重大的事件。羅馬天主教本身也在反宗教改革後經歷一場主要的轉變,那時的它接受了時代的理性化精神。羅馬天主教在特倫托會議,即一五四五—六三年之前的年代和之後是非常不同的。要強調的是當宗教改革把歐洲分裂成清教徒北方與天主教南方時,基督教還是繼續作為文化認同的主要來源。
不應被遺忘的是,羅馬天主教與新教在西歐的分裂區從未像拉丁基督教跟希臘基督教的鴻溝那麼大。儘管有著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整體而言南北歐的聯繫仍比東西歐要來得緊密。再者,儘管一五七一年勒班陀之役後越來越不顯著,拉丁基督教因畏懼穆斯林威脅的緣故,仍是相當團結的。事實上我們發現宗教改革與反宗教改革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路德、喀爾文與羅耀拉(Loyola)都甚少使用歐洲一詞。他們所呼籲盼望要改革的,仍是基督教世界。但它在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後,不再有能力提供西方政體一個均一的政治文化。
邁向歐洲論述的過渡是個緩慢的過程,明顯地可從一五六一年企圖阻止這塊大陸以歐羅巴的異教神話命名中看出(Hale, 1993, pp. 48-9)。這也可從十七世紀末潘恩(Quaker William Penn)為歐洲統一所草擬的早期邦聯計畫之一而得證。和平主義者潘恩建議,為了保存基督教的完整並團結基督教世界以對抗土耳其人,歐洲的統一是必要的(Heather, 1992, p. 65)。基督教和歐洲之間的連結對他而言是相當清楚的,因為他認為在土耳其人被允許參與未來的歐洲聯合之前,他們首先必須放棄伊斯蘭並改宗基督教(Lewis, 1993a, p. 23)。諷刺的是當歐洲理念於十七世紀進入公眾意識時,歐洲在宗教戰爭中正經歷著一段顛覆時期。
歐洲理念顯露為世俗認同之定位的舞台因而佈置妥當。這在其演進中可說是關鍵階段;當時基督教世界理念已衰退,而民族理念尚未以自治之意涵出現。從文藝復興到美國與法國革命間的階段,歐洲理念是以西方文化模型而鞏固,而且就像其政治認同般日益重要。關鍵的交會點就是西方理念。當歐洲理念取代基督教世界作為主流的文化模型,東方概念便作為其指示物而被留下。歐洲理念就這樣變成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替代品。
因此,我的看法是歐洲理念所代表的是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對應物,並未與之決裂。基督教與人文主義間尚未解決的緊張形塑了數百年來的歐洲認同。基督教人文主義的人之神話、救贖的歷史哲學之想像,與新布爾喬亞價值系統的教化特質提供了接受其基督教遺緒的歐洲認同之基礎。當代歐洲文明的人類學普世價值有其天啟宗教之根源,且事實上該根源在宗教戰爭後以一種被強化的形式存續著。
歐洲可能在一六四八年後要比之前更相信真理的普世性、人本質的統一與歷史的救贖理念。和基督教過往的徹底斷裂之論點,因此是個非常有問題的概念。當義大利諸城的文化普遍地變得世俗,教皇也證明了自己無力阻止世俗主義之浪潮,但要說全歐洲都這樣則是錯的,特別是北方,例如斯圖亞特王朝下的不列顛,君權神授之學說曾復甦了一段時間。清教主義下高度理性化的世界,在強化基督教的現代化方面同樣有著巨大貢獻。指出這點是相當有趣的,即阿拉伯人從不把歐洲看待為世俗文明(Abu-Lughod, 1963, p. 159)。
一直到英國內戰結束(1649)與大陸上的三十年宗教戰爭終結(1648),一個伴隨著新的交流形式而出現的新共和國才誕生。基督教放棄了在西方文明中作為合一性主題的特權地位;正是在這空隙中歐洲理念取得了作為自治理念的第一個立足點。但,基督教的世俗化影響仍在。舉例來說,一六四八年後日漸高漲的反猶主義,便可被視為代表著歐洲意識的核心作為世俗化與反蒙昧主義版本的基督教世界觀。當宗教戰爭在十七世紀中葉來到尾聲時,正歷經第一波自中世紀驅逐以來的猶太人移入潮的西歐,找到了新的敵意焦點。
歐洲理念可在十七世紀中拉伯(Rabb, 1975)所謂「為穩定而鬥爭」的脈絡中被理解。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間的階段首次產生某種接近於世俗意識的東西,它為嶄新的社會組織提供了一組概念裝置。
歐洲布爾喬亞社會的基督教人文主義理想勝過了其他的意識形態競爭對手。沒有其他理想更有能力把布爾喬亞社會中形形色色的元素匯聚為一套整全的世界觀。歐洲認同的主要成份為進步理念、文明與基督教的贖罪。反猶主義就是和這些理念一同興盛起來,並賦予它們一個目標。以這些理念與理想武裝起來的歐洲,所面對的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
歐洲與啟蒙運動
那麼,到何種程度我們能論及與過去的斷裂?十七世紀晚期與十八世紀初期時,關於是否有著從古代開始的歷史進程的著名古今之爭,是最早有關與過去斷裂的世俗討論之一。當一個清晰的歐洲認同鞏固時,關於過去的批判卻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之前都未真正來到(Lively, 1981)。啟蒙思想家們首先察覺到一個世俗且充滿活力的時代精神。教會與國家不再被視為是共生的整體,而是各自分開的領域。啟蒙運動可被理解為完全成熟的歐洲認同之表現。理性主義與探索精神的世紀,充分地表現在一個國家與教會履行著不同角色,更為差異的社會中。
但世俗主義並不必然帶來與宗教的敵對。首先是國家教會裡的宗教制度化,教會因而與社會其他領域分開了,這就得以區辨出世俗社會。一如查德威克(Chadwick, 1993, p. 135)在他那關於十九世紀世俗主義之研究中所主張的,教會與國家之分離是政治上的必須,而非完全出於新的世界觀。它的首要功能並不只是捍衛國家免於教權主義之侵擾,還有在正取得國家支配權的反教權意識形態中保護基督教會。是故,國家教會的制度化捍衛了基督教免於啟蒙運動批判所帶來的全部後果。
許多歐洲國家像是大不列顛,是在反啟蒙運動與法國大命的革命原則下進入現代世界。世俗主義的年代並未延伸出拒絕基督教的偏見。它所做的僅僅是使其適應不同的世界觀,因此宗教只是諸多認知面向的其中一個。在許多國家中—蘇格蘭、英格蘭、德國與荷蘭—啟蒙運動在基督教會中尋得安身立命之所(Gilley, 1981, p. 104)。當科學、成文法與藝術正歷經著它們自己的獨立發展邏輯時,基督教世界觀仍是首要的文化之中心思想,藉此歐洲文明得以認出自己。
所以,或許在一個國家與教會間差異加大的社會中,宗教—及其身負重任的傳教士與對群眾異教的攻擊—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程度滲透進社會,並成為現代化的中介者。儘管教會失去了支配國家的權力,但仍在它視為對象主體的新專制權力機器的結構中,取得了控制家庭與學校的權力。換句話說,十九世紀的基督教並不是中世紀的剩餘,而是現代性的產物與再基督教化的過程:宗教被內在化了。
在這轉型中猶太人取代了穆斯林作為基督教的敵人。例如,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要求成為日耳曼民族的成員之標準,就是要身為基督徒(Katz, 1980, p. 77)。根據摩斯(Mosse, 1978)的研究,歐洲種族主義思潮出現於十八世紀的西歐與中歐;特別是啟蒙運動的新科學與基督教虔信派的復興演化成一種新舊混合物,並在理性化與逆現代化的反猶主義世界觀中找到它的表現方式。
歐洲理念作為一種文化模型,在十八世紀時開始成型。盧梭已預見一個時代,在那兒「不再有一個法國、一個德國、一個西班牙,甚至一個英國,有的只是歐洲人。有著相同的品味、相同的愛好、相同的生活方式」(Hampson, 1984, p. 71)。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為政治工程的烏托邦計畫打好了基礎。歐洲理念本身是社會契約的具體化,表現為各民族的聯盟。為了保存歐洲人民的獨立性,聖西蒙寫道他們將自己在新的政治框架中重組的必要性。
伏爾泰那時相信歐洲正在取代民族國家:「今日,不再有法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國人:不管人們怎麼說,他們就只是歐洲人—大夥都有著同樣的品味、同樣的感受、同樣的風俗,因為已沒有人經驗過任一特別的國族形式」(Dann and Dinwiddy, 1988, p. 14)。康德在1795年的《論永久和平》裡,為支持「自由國家聯邦」而提出其中一項最著名的主張。海涅(Heinrich Heine)將歐洲花園—巴黎,視為文明的中心。柏克(Edmund Burke)於一七九六年時寫下:「沒有歐洲人能在歐洲的任一地方成為流亡者」(Hay, 1957, p. 123)。然而,這個巍峨的理念並沒有幾分真實,只比作為上層階級旅遊之表現與布爾喬亞所嚮往的貴族社會大同主義要更豐富一些。
要一再強調的是,歐洲理念作為民族國家之外的另一選項,對當代人來說沒什麼意義。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太巨大了。啟蒙運動的普世主義從未將自己表現為強烈的歐洲主義之意涵,即使歐洲的文藝復興理念作為文化之中心正廣泛傳播著,並成為歐洲政治秩序的新烏托邦展望之基礎。啟蒙主義確實帶來的理念,是知識份子小團體的產物,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並不予理會(Anderson, 1988, pp.185-7)。他們的遺贈無疑是被誇大的。
以他們的歐洲理念而言,是徹頭徹尾的法國貨,並讚揚「歐洲宗教、白種人與法語的優越性」(de Rougement, 1966, p. 157)。整體的概念在其他文明中有著更多發展,像是中國。(Bozeman, 1960, p. 135; Dubs, 1944)。中國的世界秩序從未失卻其概括一切的文化整體之觀念(Fairbank, 1968, p. 5)。猶太傳統,帶著其宗教與國家間強烈的聯繫,亦能聲稱一個比基督教更堅固的文化整體之傳統,後者在文化上已更為分裂了。
在整個十八世紀和大半十九世紀,國際社會與法語及社會行為的法式標準有著緊密聯繫。正是法語取代了拉丁語 ,作為外交與政治社會的語言。要做個「歐洲人」,就要說法語。可理解的是外國政治人物並非渴望要使法國文化政治化,事實上它就真的只是國際語言而已。歐洲理念並未被鼓舞,因為許多有爭議的主張可能都是出於一己之利。是故俾斯麥駁斥了歐洲理念,因為這和普魯士的利益不相容。「我總是發現那些把『歐洲』掛在嘴上的政治人物,希望從外國勢力中拿到點什麼,卻從不敢鼓起勇氣以自己的名義去要求」(Crankshaw, 1982, p. 352)。依賴民族主義作為其正當性的統治者,鐵定是明確地反對泛歐洲的理念。
歐洲理念那搞分裂又愛引發論戰的特質,可在許多有關歐洲整體的初期理念中得到理解。其中啟蒙運動理念最著名的擁護者即是萊布尼茨與休謨,他們倡議歐洲國家聯盟的成形。隱藏在萊布尼茨的歐洲和平想像之下的基本概念,是那惡名昭彰的「埃及計畫」(Egyptian plan, 1672)。向路易十四所提的這個建議裡,他概述了其信念,即確保歐洲和平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由法國率領的歐洲聯合,侵略奧圖曼王朝治下的埃及(Foerster, 1967, pp. 151-60)。
這樣的戰爭或許對法國特別有吸引力,它彷彿因此就是「帶著正義之怒的復仇者、基督教世界之領導、歐洲與人類之喜悅」(Yapp, 1992, p. 146)。儘管該計畫從未以萊布尼茨所設想的方式實現過,它的確概括了位於歐洲合作之後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專注在非歐洲世界的西方戰爭機器。這就是隱藏在歐洲啟蒙運動中烏托邦主義之下的真實:為了打造帝國而有限度之歐洲內的和平。
歐洲與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對歐洲社會有著雙重意義。作為與舊秩序敵對的革命,它不僅僅是法國的,也是全歐洲的運動。但沒有東西可以掩蓋它也是個法國的革命這一事實。它所重視的普世主義者之理念與理想,最終是從屬於布爾喬亞階級的狹隘民族主義與督政府(Directory governemnt,譯註:法國大革命1795-1799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的帝國主義野心。從一七九三年以降,法國處於和全歐洲交戰的狀態,而「國家」的革命準則被改造成帝國主義的計畫。
在尊貴的專制主義最終被掃除於革命浪潮中之後,後革命國家將自身轉換為擴張運動。國家變成「偉大的國家」(la grande nation)且迅速地成了帝國。潛藏在拿破崙為了歐洲重建的計畫背後,是以法國的形象去創造歐洲的可能性(Woolf, 1991, p. 32)。起初法國人相當支持廢除最後一絲一毫封建主義殘餘,並在全歐洲都建立了共和政體的革命戰爭。歐洲正在邁向共和的路上。
法國大革命的普世主義理念既賦予了歐洲一個歐洲認同的意義,亦同時將之剝奪。至少有三項因素,要為革命在奠定長久歐洲認同之基礎的失敗負責。首先,如之前已提及的,約莫從一七九三年開始,革命便將自己改造成法國帝國主義計畫。拿破崙在一八〇四年取得法國皇帝頭銜,且對一七八九年理想的忠誠也變得和對法國的忠誠聯繫在一起。羅馬帝國因而以法蘭西帝國的形式復活。第二,開始於1793年的革命戰爭導致了西歐與東歐的重大衝突。
拿破崙的歐洲是以萊茵河作為其東部邊界的羅馬歐洲(Chanman, 1952, p. 68)。沒有比拿破崙在一八〇六年廢除的神聖羅馬帝國之案例能更明白的展現這點。取而代之的萊因邦聯,是西方與東方間的緩衝地帶,且有著自己的東方邊界,即古老的日耳曼—斯拉夫邊界。歐洲的東部區域並未經歷過和西歐同等程度的革命顛覆。在那兒啟蒙運動仍要比西方更具貴族氣息。再者,和革命之挑戰鬥爭時,東歐與俄羅斯的專制王權也比西方成功多了。
儘管波蘭是第一個賦予自己憲法的國家,卻也無法撐過時代的考驗並和自身在一七九三年第二次分割之後一同消失。第三,革命精神解開了新的疆域民族主義理念之束縛。然而直到甚晚之後為止,這些理念並未朝分離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而是成為立基於已建立的民族國家的歐洲秩序之基礎。
拿破崙曾試圖以法國之名製作歐洲,但失敗了。當他的對手們在一八一四年後企圖重建舊秩序時,所訴諸的正是歐洲理念。母需多言,這種歐洲的使用是一種反法國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種反西方的概念,因為神聖同盟將俄羅斯、普魯士與奧地利合併為以萊茵河作為其西部邊界,並以東方為基礎的權力集團(Cahnman, 1952, p. 609)。
觀察此一現象的有趣之處在於,歐洲理念開始進到國際政治的論述,精確地說,是歐洲整體作為地緣政治框架的崩潰,以及取代了共和主義革命工程的復辟王權之歐洲的結果。共和主義的失敗成為了歐洲理念史之後續的基本情境,後者在後革命階段中與復興的舊秩序之聯繫更加密切。
歐洲與民族理念
雖然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梅特涅所復辟的舊秩序確實戰勝了革命的挑戰,它仍必須將就某些之前已許諾的要求,以及大部份國家所同意的適度的憲法。後革命民族主義,是梅特涅舊秩序最大的威脅。一七八九年到一八四八年間,以共和主義為形式的民族主義普遍地和自由主義,以及對舊秩序的敵意聯繫在一起。但沒什麼可以改變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然來到這一事實,因此,在某種層面上來說歐洲理念碎裂成民族理想的排他主義。但這一點都不意味著新的民族國家體系不具規範。
當歐洲合併為少數卻較大的國家時,歐洲理念便承擔起作為調節性理念的規範性角色(Mann, 1993, pp. 35-6, 65, 254-5)。要做這件事,首先必須要使自己和民族主義和解。
自一八四八年以降,當自由派,或共和派的民族主義沒辦法組織一個與復辟舊秩序抗衡的有效革命時,民族主義便與原本的共和理念漸行漸遠。從一八四八年起民族主義拋棄了它較早之前的革命形式,並且變成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工具。極少數已保證自由主義的憲法,及大多數與之妥協的國家,轉而接受反動的保守主義,因此賦予了當代保守主義的誕生。
在一八六一年的義大利與一八七一年的德國統一之後,以民族愛國主義為形式的民族主義,日益變為一種既定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且不再是種解放的理想。另一方面,它也成為了一種傾向分離的運動,儘管一般來說這是比較後期的發展。在一八四八之前的階段中,它導致了早期於一八三〇年自奧圖曼帝國中獨立的希臘,以及於一八三一年脫離荷蘭的比利時,還有稍晚在柏林條約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賽爾維亞與黑山共和國於一八七八年、一九〇五年的挪威與一九一三年阿爾巴尼亞的實質建國。
所以我們要如何談論民族主義時代中,作為一種理念的歐洲呢?就十九世紀而言,從兩種面向去討論與較狹隘的民族主義理想相對的歐洲理想是有意義的。首先,有個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中發展的歐洲理念。這是基督教人文主義理想與一個基於理性、進步,與科學的普世價值體系的信念。
這些理想位於歐洲認同的核心,並體現在現代性理念中。第二,有個歐洲政治整體之理念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發展。基本上這是民族理想的改編版,它最知名的擁護者是馬志尼(Mazzini)。歐洲理念的這兩個方面—文化的與政治的—是相當獨立的,但儘管如此它們還是共同塑造了歐洲整體的現代理念。這時我所指的歐洲,作為西方基督教人文主義理念之化身,是牢牢固定在歐洲現代性的代理人,即民族國家之中的。所以,當西方文化具體呈現在作為文化模型的歐洲理念中時,正是由民族國家擔任歐洲現代性的承載者。隱藏於其後的是強烈的「人民」之概念。
「人民」理念是從法國大革命的原始概念逐漸發展而成,後者基本上是政治的,但卻變成文化的概念。民族共同體首先由知識份子所發現,且後續被愛國者與民族主義者之運動予以政治化(Hobsbawm, 1991b)。民族理想本應是種其定義隨語言而定的歷史共同體之表現,二十世紀初期時,宗教與種族特徵也被加到民族特性的清單上。歐洲認同的問題在於它有著如下之暗示,即更普世之特質的認同,或許必須讓自己接受文化的排他主義之假定。
關於民族文化對跨文化影響的敵意,反猶主義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十九世紀的文化民族主義者相信文明是奠基於民族—歷史的文化之上:歐洲的根基即為民族國家。猶太人被驅逐出國家共同體,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沒有國家的族群。然而十八世紀晚期的猶太人是以樂觀的角度去看待歐洲理念,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猶太人的歷史意識越益從歐洲與西方中除魅,而東方,特別是 一八七〇年後,則被許多人視作具有更大的潛能(Shavit, 1992)。猶太人對於歐洲的矛盾是與一八七〇年後民族性與反猶主義越來越緊密的連結有所相關,這點是可能的。
在十九世紀,由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規定的後拿破崙秩序之框架中,權力平衡體系使得一個實質的歐洲政治整體之概念是不可能的。維也納會議之後最有力的歐洲理念是權力平衡,即歐洲協商之本質,被視為歐洲(pax Europaea)和平的基礎。當它成為政治上的必需時,這理念便不只退回到啟蒙運動,更是專制主義之時代。
一般來說,歐洲理念是和單一國家的特殊利益有所關聯。對英國人來說,歐洲是跟法國連在一起的,然而對法國人而言,歐洲又意味著某種日耳曼人的東西。在拿破崙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寧願專注在它的殖民地上,而大致上對歐洲無甚興趣。對德國人來說,一方面歐洲跟法國的野心靠得太近。俾斯麥曾強烈地表達過這點,他反對歐洲秩序之理念,並抱持著歐洲理念是當時異端邪說其中一項的想法(Schieder, 1962)。
對梅特涅來說,歐洲是奧地利的必需品(Taylor, 1942, p. 34)。歐洲對法國與俄羅斯而言是個平衡槓桿,但此外便沒有進一步的用途。彼得大帝也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大概會有數十年需要歐洲,屆時我們便可背棄它了」(Szamuely, 1988, p. 136)。英國人是最反對歐洲理念的,它被認為是「歐洲大陸」。在其「光榮孤立」中,英國寧可繼續跟歐洲保持著外部聯繫,後者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意味著天主教專制統治。英國的民族認同自宗教改革以來,便被塑造為是與歐陸政權對立的,而且恐法症仍是英國民族認同所接受的形式中,最為廣泛流傳的。
十六世紀時,基督教共和國的理念已顯露為對查理五世(神聖羅馬皇帝,1519-1556。※)普世王權之企圖的反意識形態(Foerster, 1967, p. 107)。早期關於歐洲政治秩序的野心中,其中一項最著名的,就是由蘇利公爵在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七世紀初期時所構想的「亨利四世大藍圖(Grand Design of Henry IV)」。
蘇利預見了一個新的,但基本上卻是法國之延伸的歐洲(Souleyman, 1941)。該理念一個重要的面向是,對抗土耳其人的團結西方之概念。當歐洲理念在十六世紀與西班牙的世界展望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時,十七世紀和平的普世歐洲秩序之理念,則是強烈地與法國的抱負及黎胥留(Richelieu)的野心連在一起。路易十四渴望成為「歐洲的仲裁者」(Kennedy, 1989, p. 132)。
一六四二年時,上演了一幕名為歐洲的怪異劇碼,這是一齣被寫成帶有解釋黎胥留外交政策之目的的政治預言(Najam, 1956)。考慮到哈布斯堡王朝作為歐洲主宰的穩定關係之脈絡,代表著另一個競逐歐洲與歐洲理念,波旁王朝,特別是在一六四八年後,變得與反法國有著非常密不可分的關係(Burke, 1980)。然而,歐洲理念作為普世共和政體的言下之意是,歐洲無法透過任一政體之霸權而統一,儘管實際上這經常是一種競奪法國霸權地位的偽裝(Barraclough, 1963, p. 28)。
歐洲理念與英國威廉三世的抱負同樣有著強烈的聯繫。確實,十七世紀晚期,特別是由英國輝格黨所提倡的「歐洲自由」理念和清教徒緊密相連,而且奧蘭治的威廉三世正是以歐洲之名於一六八八年踏上英國土地(Schmidt, 1966)。歐洲理念稍後才在一七〇〇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反對由法國繼承西屬荷蘭)與一七〇一年後的漢諾威繼位(反對天主教的斯圖亞特王朝)之脈絡中,代表著清教徒的利益被召喚出來。
少數幾個國際組織,如一八五九年成立於日內瓦的紅十字會,以及一八七四年在伯恩建立的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這兩者是少數長期存在的歐洲合作之產物(Joll, 1980, p. 14; Lyons, 1963)。然而就是戰爭,以及永恆的戰前準備,才是歐洲社會的真實。政治上的歐洲是毀滅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歐洲理念依舊完全與政治脫節。如同我已論證的,國際政治並非全然沒有規範。
作為規範性理念的歐洲,在歐洲協調的協商體系中制度化了。這尤其是對十九世紀蓬勃發展的「國際社會」的回應,當它對歐洲政權控管世界舞台來說是日漸重要時。殖民地的爭奪以及把俄羅斯排擠在奧圖曼帝國疆域之外,這兩項因素使得它是更為必要的。其起源可從一六四八年的西發里利亞和約中尋得,並將三十年宗教戰爭帶向終結,而一七一三年的烏得勒支和約(Peace of Utrecht)則是結束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些事件構成了我的論點基礎。也就是歐洲理念並未反映著和平與統一,而是為了避免大陸被哈布斯堡王朝或波旁王朝所支配的一種規範性的必要。
歐洲協調,或是復辟舊秩序的協商體系,組成了一種負面的整體。某一政權的提升即意味著其他的下降。這是種國家間的平衡,而非一群國家的團結;其團結是由一種矛盾的能力所組成,即這些強國各自在單一個體中找到實行辦法,如果它沒有垮台的話,至少還能牽制其他國家。倘若歐洲理念真的存在,也是由它那十足的差異性所組成,就像一個易碎的差異整體。再者,假若歐洲協調有任何共同的目的,也是集中在帝國之建造與維持中歐的東方邊界,以及在離家近一點的地方反對自由主義民主與工人激進主義。
維也納會議確實為歐洲帶來了和平,但戰爭也因此被轉移到非洲與亞州。歐洲和平是殖民的前置條件。然而有個一直存在的危險,即強國間可能會在殖民問題上有摩擦,許多同盟正是透過帝國主義而成型:三國協約不僅僅是反德國的同盟,更是反對它們的殖民地人民之同盟(Kiernan, 1980, p. 45)。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一七七六年後的美國獨立。那一年可說是暗示了一個新文明的創建。一個先進的歐洲理念,試圖鍛造出獻給歐洲的新認同,作為介於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文明立場。同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新的歐洲聯邦理念於十九世紀出現(Foerster, 1967, pp. 266-71)。歐洲理念所顯露的全球脈絡是不能被忽略的。
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奧圖曼帝國最終加入了歐洲協調並接受與「基督教國家間的法律」被更名為「文明國家間的法律」—這同意是為了贏取土耳其的協助以對抗俄羅斯(Alting, 1975, p. 53)。歐洲與新國際政治規範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密切,前者提供給後者一個文化的參考框架。文明事實上意味著自由歐洲文明的規範,它取代了基督教世界作為文化框架,卻保留了後者的許多預設(Gong, 1984, p. 15)。
歐洲理念,如同它與文明標準的緊密關聯,因而也與國際法有著極大的結合。主要是聚焦於涉及到外交、商業與戰爭狀態的事項(Best, 1986, p. 215)。它一點都不是「國際」法,而是歐洲法,並渴求一個因為民族國家的興起而被掩蓋的道德普世主義(Best, 1986, p. 219)。但這是個扭曲的道德普世主義,被化約為西方理性主義與戰爭規範的道德律之變形。
甚至儘管歐洲理念在十九世紀中葉前是普遍使用的,它一般而言仍從屬於民族原則。十九世紀初期時,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啟蒙運動理念顯得過時,由民族公民所取代(Schlereth, 1977 and Meinecke, 1970)。遠比擔憂一個統一的大陸更能刺激各強國的是在邁索隆吉翁(Missolonghi)的一八二四年拜倫之死,一個象徵性地標示著現代民族主義之誕生的事件,當時各強國正在干預奧圖曼帝國,並為希臘獨立開啟了可能性,後者被聲稱是歐洲的縮影。
希臘獨立戰爭所解放的民族主義—與西歐的反革命保守主義恰好是同一時期—在團結歐洲以對抗亞洲與非洲的傳統敵人伊斯蘭方面,是個特別有力的文化工具(Bernal, 1987, p. 441)。歐洲秩序理念是受限於新生民族主義與權力平衡體系。然而,民族主義並不是對歐洲主義的否定,而正好是使其可能的條件。並且正是民族主義,讓諸強國最終於一九一四年時在理論與戰場上獻祭了歐洲。
甚至民族主義者自己也必須奮鬥,才能讓民族國家之理念廣為流傳。歷史的民族國家理念並不總是贏得人民的普遍支持。而對歐洲主義的熱忱就更少了,它從來就不曾是個主要的公共議題。雨果的「歐洲合眾國」理想或伏爾泰的「歐洲共和國」之展望,在民族主義的時代裡都只是個異例。這方面其中一項影響更為深遠的進展,就是由馬志尼於一八三四年在伯恩所建立的青年歐洲(Salvatorelli, 1964, pp. 339-47)。
就其真正的意義而言,此一運動的理念並不是要塑造一個統一的歐洲國家,而是打算支持歐洲民族主義運動之奮鬥,並成為未來自由國家的歐洲聯邦之基礎。順著統一的聯邦國家這條線,代表歐洲政治統一的理念一般來說是不受歡迎的。例如馬志尼的青年歐洲,僅持續了兩年且從未享有青年義大利般的成功,而且正是它啟發了民族主義運動,像是青年德國、青年法國與青年愛爾蘭。值得一提的是兩個有著最濃厚的歐洲主義傳統的國家,義大利與德國都還沒有統一。
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譯註:即義大利統一運動)與為了德國統一的努力都讚揚了歐洲理念。然而,一旦這些國家統一了,早期為了歐洲的熱忱就會變質為民族沙文主義與領土收復主義。與歐洲連結的普世主義原則便因民族文化的排他主義而黯然失色。
歐洲的浪漫主義再發現
十九世紀不僅僅是理性主義的時代,也是浪漫主義的時代。儘管這兩者緊密相連,在觀念上它們卻是相當不同的。最重要的是理性主義是種經常放眼未來的政治理念,而浪漫主義基本上卻是回顧往昔的非政治運動。浪漫主義把重點相當程度地放在對過去的再發現,並且在其突破性的形式中讚揚英雄般的自我認同概念。然而,在十九世紀的進程裡它與前者的聯繫要比後者的突破性形式來的更為密切。但它所引發的革命衝動,是一種隱藏在歐洲精神之下,動態且富創造性的力量之概念。
浪漫主義其中一項最著名的表現,就是諾伐利斯(Novalis)於一七九九年寫下的《基督教世界或歐洲》(Christendom or Europe, 1968)。對他來說,中世紀基督教是另一種相對於歐洲現代性及其世俗意識形態的烏托邦選項,他將世俗意識形態與宗教改革、哲學與啟蒙運動連結在一起。此外,他認為基督教世界和歐洲並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或許可以成為世上一股革新的力量。對諾伐利斯而言,歐洲暗示著某起某種分裂的東西,而基督教世界則象徵著統一的傳統。
透過反動的天主教浪漫主義對中世紀的再發現,是對於宗教改革的分裂與啟蒙運動之除魅的文化補償。歐洲理念作為基督教世界的衰微後嗣與歷史典範,明確表達於由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家施利格(Friedrich von Schlegel)主編的刊物歐羅巴,為世上最早的雜誌之一(de Rougement, 1966, p. 239)。
對費希特(Fichte)而言,德國是歐洲的發源地與拉丁文明的繼承者。德國人,在此他指的是普魯士人,是藉由控制歐洲來「為歐洲服務」(Taylor, 1988, p.38)。黑格爾視歐洲為基督教與日耳曼文化的綜合體,而後者在國家中得到了最高的體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代表著世界精神的歐洲在「歷史的終結」時變成了自我意識(Hegel, 1956, p. 103)。蘭克(Leopold von Ranke)相信拉丁民族與日耳曼民族間有著自然的羈絆,且這點構成了歐洲的本質(Schulin, 1985)。
語言與種族的連結在雅利安神話的建構中變得緊密了起來,該神話假定了一個原初種族,即日耳曼族,衍生為所有的歐洲民族。斯拉夫人因此被排除在歐洲種族之外。根據波力亞柯夫的說法(Poliakov, 1974, pp. 99-101),在其經典的雅利安神話研究中,日耳曼族在人類學上的一致性是作為不証自明的事實而為人接受,且經過一段時間後被認為是歐洲人或白種人的完美典範。日耳曼人因此開始把一個與雅利安神話連結的,倒退的文化理念強加在歐洲之上。
風行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理念,在其中懷舊扮演著主要角色。懷舊,特別是對往日的歐洲帝國,同樣是種過去的建構物。每個年代與每個國家都會認為自己和那些在自己之前就已消逝的東西有著密切聯繫。但在這種對過去的認同中,成了永久不衰的並不是往昔,而是被創造的過去。少數意識形態已經比浪漫主義更加影響著我們對於過去的想法。連續性在那兒僅僅被視為是種斷裂,而當代人對那些被景仰的偉大年代有著不同的理解。
已然從其中出現的虛幻之一,是歐洲過去的神秘性。所以考慮到歐洲政體其政治上分裂的特質,作為文化同質化概念的歐洲理念只有在文化層面上才有其意義。那麼在這意義中,歐洲文化傳統是被回溯地創造的。歐洲開始認同了它的文化人工產物:巍峨的教堂、歌劇院、咖啡館與皇室建築。浪漫主義為歐洲論述提供了一道記憶,沒有它,該論述或許只是個空泛的格言。
歐洲作為過去之化身的這種觀念同樣表現在新的文化旅遊業中。北歐的布爾喬亞社會,尤其是英國與德國,再次探索古希臘羅馬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奇觀。壯遊(Grand Tour)成為布爾喬亞紳士教育的基本成份,並賦予了帶有現代文明的浪漫主義時期的清教除魅,完整的表達方式。正在被重新探索的過去是歐洲王政復辟時期的產物。這是個反諷,因為是由清教北方去再次發現天主教南方的。
英國柏克所欽慕的並不是當代自由主義的歐洲,而是舊政權的。在其一七九〇年《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67, p. 76)的著作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可作為他的歐洲觀之總結:「…我們的風俗、我們的文明,以及所有與風俗及文明相關連的良善事物,在這個我們的歐洲世界中,長期以來仰賴兩個原則,而且的確是這兩者結合的結果:我指的是紳士精神與宗教精神。」
全球性的歐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一種美學的建構物,並且變成布爾喬亞文化機器的一部分。人文主義的意涵留存下來,成為歐洲書面文化的主要成份。它體現在歌德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之概念,與特殊的歐洲文學理念中。這是種趨勢,反映了以歐洲為名的書越來越多,以及歐洲文明史的概念開始廣泛流行。還有一種含義,歐洲主義在其中可說是作為一種體現在音樂裡的文化精神。
正是這種文化的整體,讓艾略特、雅斯培與瓦勒希等作家在稍後抵制了現代性作為歐洲傳統之整體這種說法。然而,遍及整個十九世紀,歐洲主義唯一的具體表現是在貴族的世界大同主義中—這在皇室家庭得到最好的證明,因為只有貴族與皇室超越了國境的限制。然而啟蒙運動以來的歐洲文化,無可否認地已經遺忘了文藝復興精神很長一段時間,並且隨著浪漫主義的催化,被编纂成了民族文化。
對保守主義者而言,歐洲也是政治的建構物。歐洲政治秩序的幻象有助於增強保守派對自由主義與共和民族主義的反抗。對反動的保守派來說,如果歐洲有意味任何東西的話,便是代表著已消失的舊秩序之歐洲。德.梅斯特禾(Joseph De Maistre)把歐洲跟教皇的管轄範圍劃上等號,並盼望著基督教世界的再興以抗衡自由主義。對梅特涅本人來說,法國大革命標誌著舊秩序的終結。他希望將歐洲視為是民族主義以外的另一個選擇。
歐洲已然是個國家,而義大利僅僅是「地理的表達方式」。歐洲理念與這種羅馬天主教專制統治的懷舊之聯繫變得密切起來。拿破崙時代之後,日耳曼浪漫主義者將歐洲視為過去。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興起,加強了歐洲曾一度存在但後來卻消失的這種理念。歐洲理念因而變成對於過去的保守的反革命詮釋,既非一種現在式的理論,也不是邁向未來的行動準則。諸如此類,它是個引人注目的對啟蒙運動理念的對比。歐洲因此再次擁抱了因啟蒙運動的批評,而被否定的過去。
所以普遍來說歐洲理念似乎是反革命的。群眾或許可以被團結起來對抗雅各賓主義、對抗「黃禍」、對抗民主(Barraclough, 1963, p. 41)。一如我們所理解,並非是歐洲理念之友的俾斯麥,在一八六三年時承諾要協助俄羅斯鎮壓叛亂,主張道這是「為了歐洲的利益」(Wittram, 1973, p. 105)。除了像是馬志尼與雨果這樣的人物之外,很難找到其他訴諸於歐洲理念的進步力量的範例。人們所得到的極為強烈的印象是,歐洲理念事實上被舊秩序強加於自由與民主運動,為了革新一個一度由基督教世界構成的整體之幻象。
現代性最終被理解為是屬於新世界的。套句布希亞(Baudrillard, 1988, pp. 73 and 76)的話,歐洲是「十九世紀布爾喬亞之夢」,而美洲則是「現代性的原初版本」。美國革命,相對於眾歐洲革命來說是成功的,當歐洲理念被許多歐洲人主張是代表過去的時候,新社會的自我意像在精神上來說是現代的。這種新舊世界的分別,在歐洲與美國於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時對日本的象徵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尋求著藉由訴諸以美國為模型的現代性圖像,以及歐洲作為西方精神文明與傳統之祖國,來讓自己「現代化」。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