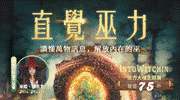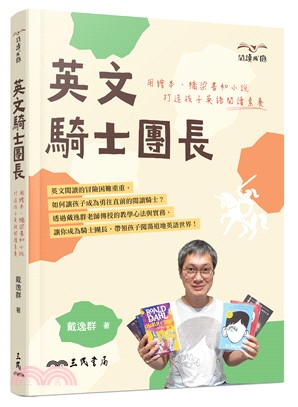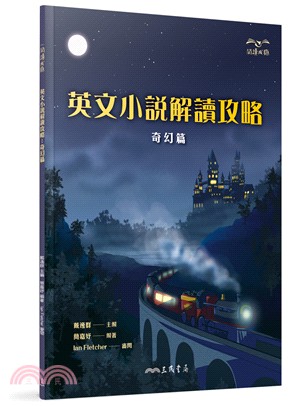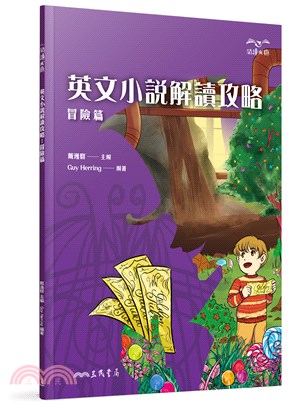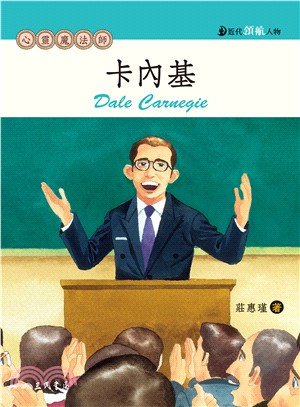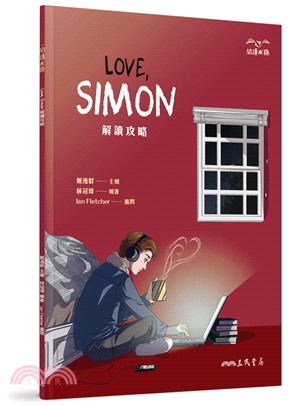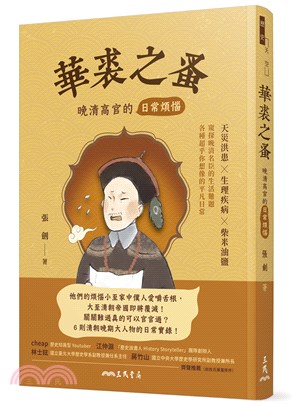定價
:NT$ 230 元優惠價
:90 折 207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瑾睿看著她欲哭又不敢哭,楚楚可憐的樣子一陣心疼,
玫果飛快的抓住那手緊緊握住,唯恐一鬆手他又再消失。
她害怕他一走了之,緊緊死命的反抱住他:「瑾睿,你以後再也不許丟下我。」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將她緊緊箍在懷裡,他怎麼能再捨得丟下她?
玫果的心一陣陣的涼,她都已經打算再也不回去,要和瑾睿平平凡凡的共度下半生,他們卻出現在自己的面前……
雖然她答應了要回弈園,可是就算人回去了,心真的能回得去嗎?經歷過了這麼多大起大落,她怎麼還能夠像以前一般無憂無慮,只知道開心的過日子?
回弈園途中,佩衿為了救玫果,卻讓玫果眼睜睜看著他被寒宮鈺凌虐,
那種熟悉又陌生的痛,一點點的在舔著她的心。
過去,從來沒有感覺到,如此深刻,如此激烈的痛,
也從來沒有這樣對自己如此怨恨,恨自己的無能為力,恨自己的逃避自私。
作者簡介
末果
我是生在酒鄉,卻是不懂得喝酒的異類。
小從夢想看盡天下美男,畫盡天下美人。
在服裝界漂泊十二年,只顧著畫皮,筆下美人卻寥寥無幾。
閒暇之於,開始用文字把所見所想描繪出來。
然後,自得其樂地愛著筆墨上的人物。
愛自己的,也愛他人的。
我是生在酒鄉,卻是不懂得喝酒的異類。
小從夢想看盡天下美男,畫盡天下美人。
在服裝界漂泊十二年,只顧著畫皮,筆下美人卻寥寥無幾。
閒暇之於,開始用文字把所見所想描繪出來。
然後,自得其樂地愛著筆墨上的人物。
愛自己的,也愛他人的。
書摘/試閱
玫果坐在院子裡把玩著一張請柬,忍不住的心中有些竊喜,那個銀杏終於要嫁人了,總算可以不再來糾纏瑾睿,竊喜之後又有點愧疚,人家要嫁給不喜歡的人,她卻在這兒偷著樂,實在有些不厚道。
瑾睿手中捏了本書從診堂裡出來,見她正攤開那張大紅的燙金請柬當著扇子搧風,搧了兩搧,舉起來對著光照了照。
自從人家把這請柬送來,她便一直在把玩,到現在差不多已有半個時辰,還樂此不疲,她玩得高興,他看著卻心酸,每次見她對光看時,心裡就一陣陣的揪痛。
放輕腳步,慢慢走到她面前,在她身邊坐下,凝看著她臉上燦爛的笑,自那晚以後,她臉上便多了許多笑容。
玫果不知自己身邊多了個人,仍孜孜不倦的反覆將那請柬對著太陽的方向,她沒告訴瑾睿,在拿到這張請柬時,無意中發現,對著光能隱約看到一團紅色,這是她醒來後,除了黑色以外唯一看到的顏色,這個發現讓她欣喜若狂,或者有一天,她能偷偷的看到他……
瑾睿看了她良久,視線才從她臉上移到手中書冊上:「人家出嫁,妳就能這麼開心?」
玫果正舉著那請柬,聽到他的聲音,就像是正在做壞事的小孩被大人捉了個當場,忙將手放了下來,老老實實的放在桌上:「我都不知道穿上紅喜服是什麼滋味。」
瑾睿抬眼看了看她,一身的白衫,這也是他看過她穿過的衣裳唯一的顏色,想像她穿上大紅喜服,應該會很美。
玫果一手撐著下巴,另一隻手的手指在請柬上輕刮,臉上的笑意褪了下去,如果不出那事,現在也該是她和弈風大婚的日子,拽地的大紅喜服是母親一早就備下的,不過卻沒有機會再穿了。
剛才的那份喜悅瞬間化成灰燼,消散的無影無蹤。
瑾睿見她眼裡陰晴不定,不知她又想去了哪裡,放下手中書冊:「改天我去市集上請人為妳做上一套,讓妳穿著過過癮?」
玫果小嘴一撇:「不如叫人做了全套,你陪著我過把成親癮,我這輩子好歹也算真真正正的嫁過一回。」
一回到這世界就已成為人婦,雖然那人說過她們拜過堂,成過親,但她終是沒有感覺。
男女之事雖然有過幾回,但哪次不像是偷吃的野鴛鴦?
瑾睿將手中書冊一合:「也好,就這麼定了,擇日不如撞日,反正現在閒著無事,天氣也是甚好,不如現在去市集上走一趟。」
玫果微微一愣:「當真?」
瑾睿將書冊收起,握了她的手,將她拉了起來,當真走向院外。
這些日子以來,他與她同榻而臥,但自那夜她解了他的衣衫,他阻止她進一步動作後,她睡覺就變得十分老實,雖然睡著後仍會緊緊偎在他懷裡,但不會再碰他一下。
過後他細細想來,只怕是自己怕傷了她腹中孩兒不肯碰她,而讓她誤會以為他對她仍有心結,所以才會連睡覺也顯得格外小心。
別看她白日裡顯得開朗,他知道她不過是不願他為她煩惱而強顏歡笑,內心深處卻是處處小心翼翼,唯恐稍有不慎引起他反感,她這樣的隱忍讓他心疼。
剛才見她把玩請柬便生出這個想法,或許只有讓她心裡承認自己是她的夫君,而並非口頭上說說,才會消除她這層心結。
到了市集的衣坊,掌櫃見他買下店中最好的喜服,又包了全套的紅燭幔帳,十分不解:「睿大夫,您這是給誰備下的?」
他不會聽錯傳聞,睿大夫拒絕了銀杏,銀杏大哭了一場後,答應了鎮中第一富賈家的提親,婚事也就在半個月後。
既然他不娶銀杏,備這婚嫁東西有什麼用處?
瑾睿看了看在店中東摸西摸的玫果:「我夫人嫌我娶她時,年紀太小,一切都是家中做主,自己沒有感覺,讓我重新補一回給她。」
玫果正摸著一個鳳冠上珠子在玩,聽了這話耳根子滾燙滾燙的,她不過是一句玩笑話,他就當了真,人家問起他就理所當然的推到了她頭上,好不厚道。
但那話的確出自自己之口,無力反駁只得立在那兒乾笑兩聲。
瑾睿面無表情,看著伙計收拾他買下的東西。
掌櫃愣了半天,自小由家中大人做主拜堂成親,是天經地義的事,哪曾見過後來再補多一回的說法,這位睿夫人年紀尚小胡鬧也就罷了,這位睿大夫竟然也就著她胡鬧,對這位夫人當真是寵上了天。
掌櫃夫人這時正好在店中,聽了這話,長嘆了口氣:「睿夫人真是好福氣,遇上這麼個疼愛自己的好夫君,我和我家相公也是娃娃親,長了這麼大,天天對著這些喜服,都不知自己穿上是個什麼樣子,這一生難免遺憾。」
玫果揚眉笑了,心裡某一處瞬間塌了下去,對著掌櫃夫人戲笑:「也叫掌櫃的補妳一回,反正妳們這兒,什麼東西都是現成的。」
掌櫃夫人看了掌櫃一眼,掌櫃已年過四十,老臉一紅:「我們一把年紀了,哪比得睿大夫和夫人風華正茂……」
掌櫃夫人雖然覺得遺憾,笑道:「我們孫子都有了,這時再補,人家只會當他納小。」語畢便吩咐著伙計,把東西穩穩當當的給瑾睿送回家去。
出了市集,玫果被瑾睿拖著手,喜滋滋的跟在他身後:「你該不會是看見銀杏成親,後悔沒答應娶她,所以才拿著我來過把癮?」
瑾睿突然收住腳,玫果一頭撞在他後背上,揉著被撞得酸痛的鼻子,正要使橫,握著她手的大手驀地一鬆。
她下意識的去抓卻抓了個空,呆愣在原地:「瑾睿。」
等了一會兒,不見回答,也聽不見他任何動靜,伸手摸了摸,不管哪個方向都尋不到他的一方衣角,他就像突然在自己身邊蒸發了,一陣心慌。
「瑾睿……」連喚了幾聲,仍是得不到回應,玫果臉色慢慢變白,再也笑不出來。
「瑾睿,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啊?」
瑾睿靜站在距她兩步之遙的地方,抿緊薄唇,眼裡帶著怒意冷眼看著她,任她怎麼急,硬是不出一聲。
不管她往哪兒走,他人影晃動隨她移動,但絕不容她摸到自己一縷髮絲。
玫果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不知為什麼他會突然不見了人,急得幾乎哭出來:「瑾睿你在哪裡?你回答我……」
「你怎麼了?你在哪兒?」她一邊喚,一邊往前摸索尋找,聲音啞了下來,帶著哭腔。
瑾睿俊美冷蕭的面頰繃得更緊,背著手凝看著她蒼白的小臉和她眼裡露出的恐懼與焦急,忍住不去握住她伸著的小手。
玫果心慌意亂,走出幾步又怕自己走開,他回來尋不到自己,又自退了回去,退來退去卻失去了方向,手觸到黃土小路邊的一株蘭竹,轉過身再也分不清自己在何處。
久違的恐懼感再次襲來,倚著竹竿滑蹲了下去,咬著唇忍著淚不湧出眼眶,喃喃的輕喚:「瑾睿你在哪裡?」
「不要玩了,快出來……」
「瑾睿你在哪裡?」
「瑾睿……」
瑾睿站在她身前,看著她欲哭又不敢哭的樣子,楚楚可憐,一陣心疼伸出手去扶她,尚沒碰到她的身子,握成拳又再縮回。
玫果聞到淡淡的竹香飄過,眼裡閃過驚喜,伸手來尋:「瑾睿,你在,是嗎?」
伸出的小手,握到的只是一片飄落的竹葉,笑意斂去,淚再也忍不住的滾落下來,抱著膝蓋輕泣:「瑾睿你在哪兒,我害怕……」
冰冷的手指拭去她臉上的淚珠。
玫果正抽著鼻子,僵了僵,飛快的抓住那隻冰冷的手緊緊握住,唯恐一鬆手他又再消失。
「瑾睿你去了哪裡?」
瑾睿這次沒再往後縮,任她緊緊握住,冷冷問道:「知錯了嗎?」
玫果怔住了,嘴動了動,咬緊唇瓣,沒敢出聲。
「別再跟我提別的女人,如果再有下次,我不介意如同以前一樣,一個人過。」他聲音冷得讓她從腳寒到背脊。
玫果感到他的手在慢慢抽離,慌忙死死拽住,帶著哭腔:「不要走,不要走。」
瑾睿輕嘆了口氣,將她摟進懷裡。
玫果害怕他一走了之,緊緊死命的反抱住他,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自她醒來,心裡再疼都不曾這樣放聲大哭過。
瑾睿也不勸,只是緊緊抱著她任她哭。
玫果剎時間,心裡壓抑著的所有傷痛與委屈盡數湧了上來,再也不顧其他,伏在他懷裡哭了個夠,眼淚鼻涕蹭了他一身。
他是極愛乾淨的人,此時對於玫果的所作所為卻絲毫不反感,只是將環抱著她的手臂緊了又緊,等她哭得沒了力氣,只剩下抽噎時,將她打橫抱起慢慢回走。
玫果緊緊攬著他的脖子,到了這時她才明白,不論是眼睛還是心,她都離不開他,正像他說的,他是她的眼睛。
「瑾睿,對不起。」
瑾睿低頭看了看懷裡的她,什麼也沒說,只是在她額頭上輕輕吻了吻。
回到家中,將她放進洗漱間,擰了濕巾拭淨她哭花的小臉,放下濕巾出去準備晚飯。
玫果自行重新梳洗乾淨,摸到廚房一角的小板凳上坐下,聽著他忙碌的聲音,心被塞得滿滿的,眼前隱約有火光跳動,可惜看不見他:「瑾睿。」
瑾睿回頭看了看她應了一聲。
玫果咬著唇,輕輕笑了笑,又喚了聲:「瑾睿。」
瑾睿又應了聲。
玫果又笑了笑,接著喚:「瑾睿。」
瑾睿終於沉不住氣:「怎麼?」
玫果抿抿嘴:「我怕你不要我了。」
瑾睿繃著的臉終於緩了下來,眼裡的冰霜慢慢融化,塞了裝著豆角的小竹箕到她手上:「去皮。」
玫果歡歡喜喜的接過,俐落的剝著豆角。
第二日,他當真佈置了房間,到處遍地的紅,桌上擺了紅燭,紅棗,桂圓……
一身紅衫掩去他身上的冰寒,俊美非常。
他低頭看著自己身上的紅裝,心裡不知是何滋味,過去的他幾時想過自己會有這麼一天?
再看身邊的玫果,紅衫紅裙,鳳冠,將她嬌小的身子緊緊包住,襯得一張雪白小臉,如粉團一般,黑眸在燭光下爍爍閃動。
他靜靜的看著,眼裡盡是柔情,忘了下面要做的事,只想這麼一直看著她。
玫果對著光,能隱約看到四處的紅,歡喜得小臉都放了光,將他扯到燭台前,隱約也能見個影子,更是喜得沒了魂,揚著闊袖腳尖輕點,身子旋轉翩翩起舞。
他立在原地看著,她一直就很美,這時卻美得讓他忘了思考,忘了一切,忘了自己還有著仇恨,只想這麼永遠和她一起過下去。
過了好一會兒才坐到榻邊,手指撫上琴,眼睛卻是留駐在她旋舞的紅影上,片刻不捨得離開。
有他伴奏,玫果舞得越加輕盈,歡快,直到曲畢才半蹲下身做了個謝禮,抬頭望向他所在方向只是笑。
瑾睿放下琴,握了她的小手,將她拽進懷裡,深深的吻上她的唇,過了良久才放開,牽了她的手,按著禮節一絲不漏的拜過天地。
將她重新攬在懷裡的時候,心裡再也沒有這許多年來的孤單,他知道自己以後的生命中多了個她,再也無法改變。
他不說話,玫果也不說,緊緊依偎在他懷裡,有他在以後再也不用怕。
過了不知多久,轉過身讓他對著燭光方向,伸手摸著他隱約的影子,臉上竟滿是溫柔,總有一天一定要再看看他,湊近他在他唇上輕輕吻了吻:「瑾睿,我們成親了,你以後再也不許丟下我。」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收緊手臂,將她緊緊箍在懷裡,吻上她的唇,他怎麼能再捨得丟下她……
那夜,他們誰都不捨得脫下那身喜服,相擁著依坐在榻上,整夜不捨得入睡。
瑾睿背靠著床角牆壁,手臂環過她的腰,輕撫著她的小腹:「可有想好為孩子取什麼名字?」
玫果將手覆在他手背上:「你說叫什麼好?既然你要他跟你姓,那名自然也該你取。」
瑾睿低頭沉思片刻,面頰貼著她的耳鬢:「叫不凡,可好?」
她不知他已從佩衿的來信中猜到她腹中孩兒是末凡的,深吸了口氣,咬咬牙:「不好!」
瑾睿早料到她會如此,吻吻她的耳廊,癢得她心中微泛起的酸楚很快消散,低聲道:「叫平凡吧!我想要他平平淡淡的過一生。」
她希望腹中的孩兒像個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過著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也只有平凡的人,才能過上平淡的生活。
像他親生父親那樣出色的人,注定不能過上平凡的生活。
過平凡的生活在她這一世成了夢,希望孩子能圓了她的夢。
瑾睿略為沉吟,淡淡的笑了笑:「也好,平凡就平凡吧!」
※
末凡為弈風渡完氣,全身疲憊不堪,濕漉漉地躺倒,頭枕著弈風的小腹,斜著眼睨視了雙目緊閉的弈風一眼:「你何時醒來,我們換上一換。」
他自然得不到回應,苦笑了笑,闔上眼,不想這一閉眼,竟睡了過去。
眼前煙霧繚繞,他站在原地轉了個圈,遠處像是一個繁華的村莊,他繞開村莊,正想離開,聽見遠處有小孩的哭聲,那聲音十分耳熟。
聲聲牽引著他內心最深處的某根弦,停下腳辨清了方向,尋著哭聲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撥開雲霧,看見一處簡樸的小院,院子裡晾著許多草藥,小茅屋內有炊煙冒起,一片祥和,他站在原處遠遠的望了許久,羨慕不已。
他做夢都會想起,她說過想開間醫坊,過平凡的生活,她說的生活只怕就是前面那戶人家那樣的吧?
良久,長嘆了口氣打算轉身離開,突然腳上被什麼東西緊緊纏住邁不動腳。
低下頭,見一個粉嫩嫩,團乎乎的嬰孩,扁著小嘴緊緊抱著他的腿,喚著:「爹爹。」
他從來不曾見過這麼漂亮的嬰孩,只以為是哪家的孩子走丟了,認不得人見了人便叫爹爹,但那聲爹爹卻叫得他全身酥軟,心裡生出愛意,蹲下身抱起他:「你為何叫我爹爹?」
嬰孩小嘴一扁卻像要哭:「娘壞,爹爹也壞。」
末凡樂了,捏著他的小臉:「我怎麼壞了?」話出了口才想起,忘了自己並不是他的爹爹。
嬰孩吸了吸鼻子:「爹爹不認孩兒。」
末凡更覺得有趣,又捏了捏他肉呼呼的小臉:「那你娘又怎麼壞了?」
嬰孩馬上露出一副可憐兮兮的委屈相:「我娘要給我改名叫平凡,我不喜歡平凡。」
末凡笑著摸摸他的頭:「平凡挺好。」
嬰孩見他這麼說,頓時惱了:「爹爹和娘一樣壞。」從他膝蓋上跳下去不見了。
末凡一個激靈醒了過來,原來是個夢,雖然明知是個夢,滿腦子都是那個夢中見到粉團團的嬰孩,心裡卻生出許多惆悵。
※
佩衿靠坐在桌案前,頭靠著身後牆壁,放在桌案上的右手將掌下白紙一把揉成團,緊緊拽成拳,面色慘白,閉上眼面頰因痛苦而扭曲,腦袋木訥的無法轉動,她一定不會有事……她不會有事的……
邁了一隻腳進書房門檻的離洛,應聞慕秋的話愣杵在了那兒,手中捧著的進出帳簿跌了一地也不自知,呆望著寒著一張臉立在桌案前的慕秋。
過了好一會兒,才晃了晃痛得欲裂的頭,確定自己剛才確實聽到了那番話,躍到慕秋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迫視著他:「你說那小妖精怎麼了?」
慕秋雙目赤紅,拂開揪著他胸前衣襟的手,深吸了口氣,令幾乎縮成一團的肺得以舒緩:「跳崖了,下落不明。」
離洛雙手猛的一推,抵著他的胸脯將他壓在桌邊牆壁上,嘶聲吼叫:「不可能!就算全世界的人死光了,她那種人也不會想死,她怎麼可能跳崖?」
慕秋反手將他推開,本不拘言笑的臉更加陰沉:「她親眼看著末凡殺死了弈風。」
離洛後退兩步,秀美的面頰慢慢變白,沉默了片刻,一揚手大聲吼道:「我不信。」
慕秋不再理會離洛,轉頭看向咬緊牙關,緊閉雙目一言不發的佩衿:「他讓你佈網搜索她的下落。」
佩衿無力的睜開眼,蒼白的唇抖了兩抖:「尋,一定要尋……」拋掉手中揉爛的紙張,抬眼看向慕秋:「他可還有說過什麼?」
「他說果兒是墜落冰湖。」慕秋那日放過末凡後,又在暗中監視他多日,也發現了那潭冰湖,那湖四面環山並無出路,他也下過水,但那水過於寒冷,以他的功力也抵不住,不能在水中久待,但四周環境卻是摸了個底,水中也無出暗渠出口,那水就是一潭死水。
他暗中監視的日子,見末凡日日下湖尋找均無所獲,不解末凡話中之意,但以他這般尋法,如果玫果真是葬身冰湖,不可能尋不到屍骨。
也正是見他對玫果這份心,才信了他的話,回了弈園尋找佩衿。
「冰湖?」佩衿也是微微一愕,他擅長打探,天下稱他無所不知,他自謙起名未必知卻當真不知那處還有一個冰湖。
慕秋尚未回答,離洛卻上前一步,雙手揪住他的衣衫,神色緊張:「你說的是碧水峰的冰潭?」
佩衿靈機一動,離洛是水族後人,早年水族遍佈蒼穹大陸,凡是有水的地方,便有他們的族人,對地上地下水道無不熟悉,掌管著所有水路交通運輸。
正因為如此,才成了各國君王心頭大忌,聯合起來誅殺水族,多年後水族人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離洛家族這一主脈,四處漂泊,最後在遇上圍剿官兵時,被鎮南王妃暗中派兵救下,隱姓埋名安居下來。
雖然那時離洛尚且年幼,但終是水族族長的後人,或許真知道些什麼。
佩衿仰頭看向離洛:「你知道那冰湖?」
離洛輕點了點頭,在桌邊坐下:「我聽祖父說過,碧水峰有一潭冰潭,那冰潭平日是一潭死水,但湖底有一道埋藏的暗流,只有當日光聚到那道暗流口徑處,才會開啟。難道小妖精進了暗流?」
佩衿和慕秋的心猛的一緊,對視了一眼。
「那暗流通向何處?」
離洛眉頭慢慢擰緊:「當年我先祖父為了弄清那冰潭暗流去向,特別製做了一百個牛皮袋,吩咐各處分壇約好時間守候,到了日光相聚的時候,將裝了砂石的牛皮袋拋入潭中,結果……」
佩衿抿緊薄唇,只怕不會那般輕鬆。
果然離洛頓了頓:「結果那一百個牛皮袋只有六十來個被族人尋到,而且分在不同河渠,後來先祖父又試過多次,總共拋了四百多個牛皮袋入潭,尋到的不到三百個。」
佩衿手揉了揉疼痛難忍的額頭:「這麼說來,那暗流出口遍佈蒼穹大陸?」
離洛鎖緊著眉峰:「是。」
佩衿又將額頭揉了揉:「尋到牛皮袋的河渠,可有什麼共同特點?」
離洛想了想:「均是冰水河,而且離碧水峰較遠的冰河收到的牛皮袋更多。」
佩衿點了點頭:「只要有線索,也不愁我的人尋不到一點蛛絲馬跡,只是難在並不知這些冰河分佈在何處,只怕時間……」咬了咬牙,站起身,往外走,一刻也不願再耽擱。
離洛猶豫了片刻,喚住佩衿:「等等,或許我能助你尋那妖精……」
佩衿轉過身,迷惑的看向他:「你有什麼辦法?」
離洛沉吟了片刻,才道:「水族……用我們水族的渠道搜索……」
「水族?」佩衿愣了愣:「水族不是早在多年前就……」
離洛眼裡閃過一抹恨意:「的確,不過水族的人眾多,豈是他們殺得完的,當年我們分佈在各地的族人,雖然被誅殺無數,但終是有人躲過那劫……」
佩衿眼裡露出驚詫:「你是說水族尚存?」
離洛點了點頭:「這些年來,我已經與各壇倖存的族人取得聯繫,重新佈下了水族暗網。」
為了族人的安危,他對這一秘密深埋心裡,不過也該是大家重新振作起來的時候了,水族不能再這麼沉淪下去。
佩衿絕望的心裂開一條細縫,縫中綻放出光芒:「此事王妃可知?」
離洛搖了搖頭:「無人知曉。」有了那次的大屠殺,他還會相信誰?還肯將這天大的秘密告訴他人?
佩衿握了他的肩膀,沉痛的眸子裡終於閃過一抹喜色:「如此甚好,你聯繫族人,我派我的人分佈到你各處族人之中,助他們尋找果兒。」
有水族引路,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查探方式,不管她是生是死,都會有個結果。
離洛點頭應了,與他雙雙外走。
慕秋長吁了口氣,提了烏金窄劍躍窗而出。
佩衿追到窗邊,喚住他:「你去哪裡?」
「我去盯著姓末的,他敢亂來,我先殺了他。」他口中雖狠,放不下心的卻是夜豹,雖然末凡與他是親兄弟,但他終是放心不下,再說他們身邊還有個寒宮雪,他不能不防。
再說,守著末凡便一定能有她的消息。
佩衿望著他如煙一般遠去的背影,點了點頭,如此安排甚好。
瑾睿手中捏了本書從診堂裡出來,見她正攤開那張大紅的燙金請柬當著扇子搧風,搧了兩搧,舉起來對著光照了照。
自從人家把這請柬送來,她便一直在把玩,到現在差不多已有半個時辰,還樂此不疲,她玩得高興,他看著卻心酸,每次見她對光看時,心裡就一陣陣的揪痛。
放輕腳步,慢慢走到她面前,在她身邊坐下,凝看著她臉上燦爛的笑,自那晚以後,她臉上便多了許多笑容。
玫果不知自己身邊多了個人,仍孜孜不倦的反覆將那請柬對著太陽的方向,她沒告訴瑾睿,在拿到這張請柬時,無意中發現,對著光能隱約看到一團紅色,這是她醒來後,除了黑色以外唯一看到的顏色,這個發現讓她欣喜若狂,或者有一天,她能偷偷的看到他……
瑾睿看了她良久,視線才從她臉上移到手中書冊上:「人家出嫁,妳就能這麼開心?」
玫果正舉著那請柬,聽到他的聲音,就像是正在做壞事的小孩被大人捉了個當場,忙將手放了下來,老老實實的放在桌上:「我都不知道穿上紅喜服是什麼滋味。」
瑾睿抬眼看了看她,一身的白衫,這也是他看過她穿過的衣裳唯一的顏色,想像她穿上大紅喜服,應該會很美。
玫果一手撐著下巴,另一隻手的手指在請柬上輕刮,臉上的笑意褪了下去,如果不出那事,現在也該是她和弈風大婚的日子,拽地的大紅喜服是母親一早就備下的,不過卻沒有機會再穿了。
剛才的那份喜悅瞬間化成灰燼,消散的無影無蹤。
瑾睿見她眼裡陰晴不定,不知她又想去了哪裡,放下手中書冊:「改天我去市集上請人為妳做上一套,讓妳穿著過過癮?」
玫果小嘴一撇:「不如叫人做了全套,你陪著我過把成親癮,我這輩子好歹也算真真正正的嫁過一回。」
一回到這世界就已成為人婦,雖然那人說過她們拜過堂,成過親,但她終是沒有感覺。
男女之事雖然有過幾回,但哪次不像是偷吃的野鴛鴦?
瑾睿將手中書冊一合:「也好,就這麼定了,擇日不如撞日,反正現在閒著無事,天氣也是甚好,不如現在去市集上走一趟。」
玫果微微一愣:「當真?」
瑾睿將書冊收起,握了她的手,將她拉了起來,當真走向院外。
這些日子以來,他與她同榻而臥,但自那夜她解了他的衣衫,他阻止她進一步動作後,她睡覺就變得十分老實,雖然睡著後仍會緊緊偎在他懷裡,但不會再碰他一下。
過後他細細想來,只怕是自己怕傷了她腹中孩兒不肯碰她,而讓她誤會以為他對她仍有心結,所以才會連睡覺也顯得格外小心。
別看她白日裡顯得開朗,他知道她不過是不願他為她煩惱而強顏歡笑,內心深處卻是處處小心翼翼,唯恐稍有不慎引起他反感,她這樣的隱忍讓他心疼。
剛才見她把玩請柬便生出這個想法,或許只有讓她心裡承認自己是她的夫君,而並非口頭上說說,才會消除她這層心結。
到了市集的衣坊,掌櫃見他買下店中最好的喜服,又包了全套的紅燭幔帳,十分不解:「睿大夫,您這是給誰備下的?」
他不會聽錯傳聞,睿大夫拒絕了銀杏,銀杏大哭了一場後,答應了鎮中第一富賈家的提親,婚事也就在半個月後。
既然他不娶銀杏,備這婚嫁東西有什麼用處?
瑾睿看了看在店中東摸西摸的玫果:「我夫人嫌我娶她時,年紀太小,一切都是家中做主,自己沒有感覺,讓我重新補一回給她。」
玫果正摸著一個鳳冠上珠子在玩,聽了這話耳根子滾燙滾燙的,她不過是一句玩笑話,他就當了真,人家問起他就理所當然的推到了她頭上,好不厚道。
但那話的確出自自己之口,無力反駁只得立在那兒乾笑兩聲。
瑾睿面無表情,看著伙計收拾他買下的東西。
掌櫃愣了半天,自小由家中大人做主拜堂成親,是天經地義的事,哪曾見過後來再補多一回的說法,這位睿夫人年紀尚小胡鬧也就罷了,這位睿大夫竟然也就著她胡鬧,對這位夫人當真是寵上了天。
掌櫃夫人這時正好在店中,聽了這話,長嘆了口氣:「睿夫人真是好福氣,遇上這麼個疼愛自己的好夫君,我和我家相公也是娃娃親,長了這麼大,天天對著這些喜服,都不知自己穿上是個什麼樣子,這一生難免遺憾。」
玫果揚眉笑了,心裡某一處瞬間塌了下去,對著掌櫃夫人戲笑:「也叫掌櫃的補妳一回,反正妳們這兒,什麼東西都是現成的。」
掌櫃夫人看了掌櫃一眼,掌櫃已年過四十,老臉一紅:「我們一把年紀了,哪比得睿大夫和夫人風華正茂……」
掌櫃夫人雖然覺得遺憾,笑道:「我們孫子都有了,這時再補,人家只會當他納小。」語畢便吩咐著伙計,把東西穩穩當當的給瑾睿送回家去。
出了市集,玫果被瑾睿拖著手,喜滋滋的跟在他身後:「你該不會是看見銀杏成親,後悔沒答應娶她,所以才拿著我來過把癮?」
瑾睿突然收住腳,玫果一頭撞在他後背上,揉著被撞得酸痛的鼻子,正要使橫,握著她手的大手驀地一鬆。
她下意識的去抓卻抓了個空,呆愣在原地:「瑾睿。」
等了一會兒,不見回答,也聽不見他任何動靜,伸手摸了摸,不管哪個方向都尋不到他的一方衣角,他就像突然在自己身邊蒸發了,一陣心慌。
「瑾睿……」連喚了幾聲,仍是得不到回應,玫果臉色慢慢變白,再也笑不出來。
「瑾睿,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啊?」
瑾睿靜站在距她兩步之遙的地方,抿緊薄唇,眼裡帶著怒意冷眼看著她,任她怎麼急,硬是不出一聲。
不管她往哪兒走,他人影晃動隨她移動,但絕不容她摸到自己一縷髮絲。
玫果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不知為什麼他會突然不見了人,急得幾乎哭出來:「瑾睿你在哪裡?你回答我……」
「你怎麼了?你在哪兒?」她一邊喚,一邊往前摸索尋找,聲音啞了下來,帶著哭腔。
瑾睿俊美冷蕭的面頰繃得更緊,背著手凝看著她蒼白的小臉和她眼裡露出的恐懼與焦急,忍住不去握住她伸著的小手。
玫果心慌意亂,走出幾步又怕自己走開,他回來尋不到自己,又自退了回去,退來退去卻失去了方向,手觸到黃土小路邊的一株蘭竹,轉過身再也分不清自己在何處。
久違的恐懼感再次襲來,倚著竹竿滑蹲了下去,咬著唇忍著淚不湧出眼眶,喃喃的輕喚:「瑾睿你在哪裡?」
「不要玩了,快出來……」
「瑾睿你在哪裡?」
「瑾睿……」
瑾睿站在她身前,看著她欲哭又不敢哭的樣子,楚楚可憐,一陣心疼伸出手去扶她,尚沒碰到她的身子,握成拳又再縮回。
玫果聞到淡淡的竹香飄過,眼裡閃過驚喜,伸手來尋:「瑾睿,你在,是嗎?」
伸出的小手,握到的只是一片飄落的竹葉,笑意斂去,淚再也忍不住的滾落下來,抱著膝蓋輕泣:「瑾睿你在哪兒,我害怕……」
冰冷的手指拭去她臉上的淚珠。
玫果正抽著鼻子,僵了僵,飛快的抓住那隻冰冷的手緊緊握住,唯恐一鬆手他又再消失。
「瑾睿你去了哪裡?」
瑾睿這次沒再往後縮,任她緊緊握住,冷冷問道:「知錯了嗎?」
玫果怔住了,嘴動了動,咬緊唇瓣,沒敢出聲。
「別再跟我提別的女人,如果再有下次,我不介意如同以前一樣,一個人過。」他聲音冷得讓她從腳寒到背脊。
玫果感到他的手在慢慢抽離,慌忙死死拽住,帶著哭腔:「不要走,不要走。」
瑾睿輕嘆了口氣,將她摟進懷裡。
玫果害怕他一走了之,緊緊死命的反抱住他,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自她醒來,心裡再疼都不曾這樣放聲大哭過。
瑾睿也不勸,只是緊緊抱著她任她哭。
玫果剎時間,心裡壓抑著的所有傷痛與委屈盡數湧了上來,再也不顧其他,伏在他懷裡哭了個夠,眼淚鼻涕蹭了他一身。
他是極愛乾淨的人,此時對於玫果的所作所為卻絲毫不反感,只是將環抱著她的手臂緊了又緊,等她哭得沒了力氣,只剩下抽噎時,將她打橫抱起慢慢回走。
玫果緊緊攬著他的脖子,到了這時她才明白,不論是眼睛還是心,她都離不開他,正像他說的,他是她的眼睛。
「瑾睿,對不起。」
瑾睿低頭看了看懷裡的她,什麼也沒說,只是在她額頭上輕輕吻了吻。
回到家中,將她放進洗漱間,擰了濕巾拭淨她哭花的小臉,放下濕巾出去準備晚飯。
玫果自行重新梳洗乾淨,摸到廚房一角的小板凳上坐下,聽著他忙碌的聲音,心被塞得滿滿的,眼前隱約有火光跳動,可惜看不見他:「瑾睿。」
瑾睿回頭看了看她應了一聲。
玫果咬著唇,輕輕笑了笑,又喚了聲:「瑾睿。」
瑾睿又應了聲。
玫果又笑了笑,接著喚:「瑾睿。」
瑾睿終於沉不住氣:「怎麼?」
玫果抿抿嘴:「我怕你不要我了。」
瑾睿繃著的臉終於緩了下來,眼裡的冰霜慢慢融化,塞了裝著豆角的小竹箕到她手上:「去皮。」
玫果歡歡喜喜的接過,俐落的剝著豆角。
第二日,他當真佈置了房間,到處遍地的紅,桌上擺了紅燭,紅棗,桂圓……
一身紅衫掩去他身上的冰寒,俊美非常。
他低頭看著自己身上的紅裝,心裡不知是何滋味,過去的他幾時想過自己會有這麼一天?
再看身邊的玫果,紅衫紅裙,鳳冠,將她嬌小的身子緊緊包住,襯得一張雪白小臉,如粉團一般,黑眸在燭光下爍爍閃動。
他靜靜的看著,眼裡盡是柔情,忘了下面要做的事,只想這麼一直看著她。
玫果對著光,能隱約看到四處的紅,歡喜得小臉都放了光,將他扯到燭台前,隱約也能見個影子,更是喜得沒了魂,揚著闊袖腳尖輕點,身子旋轉翩翩起舞。
他立在原地看著,她一直就很美,這時卻美得讓他忘了思考,忘了一切,忘了自己還有著仇恨,只想這麼永遠和她一起過下去。
過了好一會兒才坐到榻邊,手指撫上琴,眼睛卻是留駐在她旋舞的紅影上,片刻不捨得離開。
有他伴奏,玫果舞得越加輕盈,歡快,直到曲畢才半蹲下身做了個謝禮,抬頭望向他所在方向只是笑。
瑾睿放下琴,握了她的小手,將她拽進懷裡,深深的吻上她的唇,過了良久才放開,牽了她的手,按著禮節一絲不漏的拜過天地。
將她重新攬在懷裡的時候,心裡再也沒有這許多年來的孤單,他知道自己以後的生命中多了個她,再也無法改變。
他不說話,玫果也不說,緊緊依偎在他懷裡,有他在以後再也不用怕。
過了不知多久,轉過身讓他對著燭光方向,伸手摸著他隱約的影子,臉上竟滿是溫柔,總有一天一定要再看看他,湊近他在他唇上輕輕吻了吻:「瑾睿,我們成親了,你以後再也不許丟下我。」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收緊手臂,將她緊緊箍在懷裡,吻上她的唇,他怎麼能再捨得丟下她……
那夜,他們誰都不捨得脫下那身喜服,相擁著依坐在榻上,整夜不捨得入睡。
瑾睿背靠著床角牆壁,手臂環過她的腰,輕撫著她的小腹:「可有想好為孩子取什麼名字?」
玫果將手覆在他手背上:「你說叫什麼好?既然你要他跟你姓,那名自然也該你取。」
瑾睿低頭沉思片刻,面頰貼著她的耳鬢:「叫不凡,可好?」
她不知他已從佩衿的來信中猜到她腹中孩兒是末凡的,深吸了口氣,咬咬牙:「不好!」
瑾睿早料到她會如此,吻吻她的耳廊,癢得她心中微泛起的酸楚很快消散,低聲道:「叫平凡吧!我想要他平平淡淡的過一生。」
她希望腹中的孩兒像個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過著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也只有平凡的人,才能過上平淡的生活。
像他親生父親那樣出色的人,注定不能過上平凡的生活。
過平凡的生活在她這一世成了夢,希望孩子能圓了她的夢。
瑾睿略為沉吟,淡淡的笑了笑:「也好,平凡就平凡吧!」
※
末凡為弈風渡完氣,全身疲憊不堪,濕漉漉地躺倒,頭枕著弈風的小腹,斜著眼睨視了雙目緊閉的弈風一眼:「你何時醒來,我們換上一換。」
他自然得不到回應,苦笑了笑,闔上眼,不想這一閉眼,竟睡了過去。
眼前煙霧繚繞,他站在原地轉了個圈,遠處像是一個繁華的村莊,他繞開村莊,正想離開,聽見遠處有小孩的哭聲,那聲音十分耳熟。
聲聲牽引著他內心最深處的某根弦,停下腳辨清了方向,尋著哭聲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撥開雲霧,看見一處簡樸的小院,院子裡晾著許多草藥,小茅屋內有炊煙冒起,一片祥和,他站在原處遠遠的望了許久,羨慕不已。
他做夢都會想起,她說過想開間醫坊,過平凡的生活,她說的生活只怕就是前面那戶人家那樣的吧?
良久,長嘆了口氣打算轉身離開,突然腳上被什麼東西緊緊纏住邁不動腳。
低下頭,見一個粉嫩嫩,團乎乎的嬰孩,扁著小嘴緊緊抱著他的腿,喚著:「爹爹。」
他從來不曾見過這麼漂亮的嬰孩,只以為是哪家的孩子走丟了,認不得人見了人便叫爹爹,但那聲爹爹卻叫得他全身酥軟,心裡生出愛意,蹲下身抱起他:「你為何叫我爹爹?」
嬰孩小嘴一扁卻像要哭:「娘壞,爹爹也壞。」
末凡樂了,捏著他的小臉:「我怎麼壞了?」話出了口才想起,忘了自己並不是他的爹爹。
嬰孩吸了吸鼻子:「爹爹不認孩兒。」
末凡更覺得有趣,又捏了捏他肉呼呼的小臉:「那你娘又怎麼壞了?」
嬰孩馬上露出一副可憐兮兮的委屈相:「我娘要給我改名叫平凡,我不喜歡平凡。」
末凡笑著摸摸他的頭:「平凡挺好。」
嬰孩見他這麼說,頓時惱了:「爹爹和娘一樣壞。」從他膝蓋上跳下去不見了。
末凡一個激靈醒了過來,原來是個夢,雖然明知是個夢,滿腦子都是那個夢中見到粉團團的嬰孩,心裡卻生出許多惆悵。
※
佩衿靠坐在桌案前,頭靠著身後牆壁,放在桌案上的右手將掌下白紙一把揉成團,緊緊拽成拳,面色慘白,閉上眼面頰因痛苦而扭曲,腦袋木訥的無法轉動,她一定不會有事……她不會有事的……
邁了一隻腳進書房門檻的離洛,應聞慕秋的話愣杵在了那兒,手中捧著的進出帳簿跌了一地也不自知,呆望著寒著一張臉立在桌案前的慕秋。
過了好一會兒,才晃了晃痛得欲裂的頭,確定自己剛才確實聽到了那番話,躍到慕秋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迫視著他:「你說那小妖精怎麼了?」
慕秋雙目赤紅,拂開揪著他胸前衣襟的手,深吸了口氣,令幾乎縮成一團的肺得以舒緩:「跳崖了,下落不明。」
離洛雙手猛的一推,抵著他的胸脯將他壓在桌邊牆壁上,嘶聲吼叫:「不可能!就算全世界的人死光了,她那種人也不會想死,她怎麼可能跳崖?」
慕秋反手將他推開,本不拘言笑的臉更加陰沉:「她親眼看著末凡殺死了弈風。」
離洛後退兩步,秀美的面頰慢慢變白,沉默了片刻,一揚手大聲吼道:「我不信。」
慕秋不再理會離洛,轉頭看向咬緊牙關,緊閉雙目一言不發的佩衿:「他讓你佈網搜索她的下落。」
佩衿無力的睜開眼,蒼白的唇抖了兩抖:「尋,一定要尋……」拋掉手中揉爛的紙張,抬眼看向慕秋:「他可還有說過什麼?」
「他說果兒是墜落冰湖。」慕秋那日放過末凡後,又在暗中監視他多日,也發現了那潭冰湖,那湖四面環山並無出路,他也下過水,但那水過於寒冷,以他的功力也抵不住,不能在水中久待,但四周環境卻是摸了個底,水中也無出暗渠出口,那水就是一潭死水。
他暗中監視的日子,見末凡日日下湖尋找均無所獲,不解末凡話中之意,但以他這般尋法,如果玫果真是葬身冰湖,不可能尋不到屍骨。
也正是見他對玫果這份心,才信了他的話,回了弈園尋找佩衿。
「冰湖?」佩衿也是微微一愕,他擅長打探,天下稱他無所不知,他自謙起名未必知卻當真不知那處還有一個冰湖。
慕秋尚未回答,離洛卻上前一步,雙手揪住他的衣衫,神色緊張:「你說的是碧水峰的冰潭?」
佩衿靈機一動,離洛是水族後人,早年水族遍佈蒼穹大陸,凡是有水的地方,便有他們的族人,對地上地下水道無不熟悉,掌管著所有水路交通運輸。
正因為如此,才成了各國君王心頭大忌,聯合起來誅殺水族,多年後水族人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離洛家族這一主脈,四處漂泊,最後在遇上圍剿官兵時,被鎮南王妃暗中派兵救下,隱姓埋名安居下來。
雖然那時離洛尚且年幼,但終是水族族長的後人,或許真知道些什麼。
佩衿仰頭看向離洛:「你知道那冰湖?」
離洛輕點了點頭,在桌邊坐下:「我聽祖父說過,碧水峰有一潭冰潭,那冰潭平日是一潭死水,但湖底有一道埋藏的暗流,只有當日光聚到那道暗流口徑處,才會開啟。難道小妖精進了暗流?」
佩衿和慕秋的心猛的一緊,對視了一眼。
「那暗流通向何處?」
離洛眉頭慢慢擰緊:「當年我先祖父為了弄清那冰潭暗流去向,特別製做了一百個牛皮袋,吩咐各處分壇約好時間守候,到了日光相聚的時候,將裝了砂石的牛皮袋拋入潭中,結果……」
佩衿抿緊薄唇,只怕不會那般輕鬆。
果然離洛頓了頓:「結果那一百個牛皮袋只有六十來個被族人尋到,而且分在不同河渠,後來先祖父又試過多次,總共拋了四百多個牛皮袋入潭,尋到的不到三百個。」
佩衿手揉了揉疼痛難忍的額頭:「這麼說來,那暗流出口遍佈蒼穹大陸?」
離洛鎖緊著眉峰:「是。」
佩衿又將額頭揉了揉:「尋到牛皮袋的河渠,可有什麼共同特點?」
離洛想了想:「均是冰水河,而且離碧水峰較遠的冰河收到的牛皮袋更多。」
佩衿點了點頭:「只要有線索,也不愁我的人尋不到一點蛛絲馬跡,只是難在並不知這些冰河分佈在何處,只怕時間……」咬了咬牙,站起身,往外走,一刻也不願再耽擱。
離洛猶豫了片刻,喚住佩衿:「等等,或許我能助你尋那妖精……」
佩衿轉過身,迷惑的看向他:「你有什麼辦法?」
離洛沉吟了片刻,才道:「水族……用我們水族的渠道搜索……」
「水族?」佩衿愣了愣:「水族不是早在多年前就……」
離洛眼裡閃過一抹恨意:「的確,不過水族的人眾多,豈是他們殺得完的,當年我們分佈在各地的族人,雖然被誅殺無數,但終是有人躲過那劫……」
佩衿眼裡露出驚詫:「你是說水族尚存?」
離洛點了點頭:「這些年來,我已經與各壇倖存的族人取得聯繫,重新佈下了水族暗網。」
為了族人的安危,他對這一秘密深埋心裡,不過也該是大家重新振作起來的時候了,水族不能再這麼沉淪下去。
佩衿絕望的心裂開一條細縫,縫中綻放出光芒:「此事王妃可知?」
離洛搖了搖頭:「無人知曉。」有了那次的大屠殺,他還會相信誰?還肯將這天大的秘密告訴他人?
佩衿握了他的肩膀,沉痛的眸子裡終於閃過一抹喜色:「如此甚好,你聯繫族人,我派我的人分佈到你各處族人之中,助他們尋找果兒。」
有水族引路,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查探方式,不管她是生是死,都會有個結果。
離洛點頭應了,與他雙雙外走。
慕秋長吁了口氣,提了烏金窄劍躍窗而出。
佩衿追到窗邊,喚住他:「你去哪裡?」
「我去盯著姓末的,他敢亂來,我先殺了他。」他口中雖狠,放不下心的卻是夜豹,雖然末凡與他是親兄弟,但他終是放心不下,再說他們身邊還有個寒宮雪,他不能不防。
再說,守著末凡便一定能有她的消息。
佩衿望著他如煙一般遠去的背影,點了點頭,如此安排甚好。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