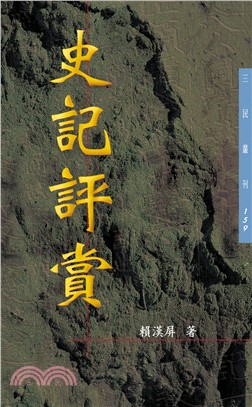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名家文庫:林徽因精選集(典藏版)》中的作品,從數量上來說,同徽因從事文藝寫作的漫長歲月確實是很不相稱的。一方面,這是由於她一生花了不少時間去當啦啦隊,鼓勵旁人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的興趣廣泛,文藝不過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學過建築,在耶魯大學還從名師貝克爾教授攻過舞臺設計。
名人/編輯推薦
《林徽因精選集(典藏版)(精》的作者林徽因是中國現代一個世紀的才女代表。她在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繪畫、翻譯等方面成就斐然,被胡適譽為“中國一代才女”。
本書收錄的就是她的散文、小說、詩歌、劇本作品,可供廣大文學愛好者閱讀欣賞。
本書收錄的就是她的散文、小說、詩歌、劇本作品,可供廣大文學愛好者閱讀欣賞。
序
1933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樓外的閱報欄去看報。那時我住在臨湖的六樓,是個剛從輔仁英文系轉到燕京新聞系的三年級生。報欄設在樓前,有兩架:一邊張貼著北平的《華北日報》和《晨報》,另一邊是天津的《大公報》和《益世報》。忽然,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版最底下一欄,看到《蠶》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給沈從文先生請他指教的,當時是準備經他指點以后再說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這么登了出來,我自是喜出望外。盡管那是把五千字的東西硬塞進三四千字的空間里——也就是說,排字工人把鉛條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擠成黑壓壓一片。其實,兩年前熊佛西編《晨報》副刊時,他也登過我的一些短文,記得有一篇是談愛爾蘭小劇院運動的。然而這畢竟是自己的創作第一次變成了鉛字,心里的滋味和感覺仿佛都很異樣。
然而還有更令我興奮的事等在后面呢!
幾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這信連同所有我心愛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蠶》,要請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來我這里,咱們一道去。
那幾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藍布大褂洗得干干凈凈,把一雙舊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過午飯我蹬上腳踏車,斜穿過大鐘寺進城了。兩小時后,我就羞怯怯地隨著沈先生從達子營跨進了總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如今回憶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動的心境和拘謹的神態,仍覺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后腿上,親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在去之前,原聽說這位小姐的肺病已經相當重了(還經常得臥床休息),而那時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癥那么可怕。我以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見我們呢!可那天她穿的卻是一套騎馬裝(她常和費正清與夫人威爾瑪去外國人俱樂部騎馬),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話講得又多又快又興奮。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連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兩位也只是坐在沙發上邊吧嗒著煙斗,邊點頭贊賞(徽因的健談絕不是結了婚的婦人的那種閑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她從不拐彎抹角,模棱兩可。這種純學術的批評,也從來沒有人記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過人的藝術悟性)。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沒提到一個“病”字。她比一個健康人精力還旺盛,還健談。
那以后,我們還常在朱光潛先生家舉行的“讀詩會”上見面。我也跟著大家稱她為“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種只會抿嘴嫣然一笑的嬌小姐,而是位學識淵博、思想敏捷,并且語言鋒利的評論家。她十分關心創作。當時南北方也頗有些文藝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細,并且對文章常有犀利和獨到的見解。對于好惡,她從不模棱兩可。同時,在批了什么一頓之后,往往又會指出某一點可取之處。一次我記得她當面對梁宗岱的一首詩數落了一通,梁詩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氣的。于是,在“讀詩會”的一角,他們抬起杠來。
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報》編刊物了。每個月我都到北平來,在來今雨軒舉行個二三十人的茶會,一半為了組稿,一半也為了聽取《文藝副刊》支持者們的意見。小姐幾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間必有一番宏論。
1936年我調到上海,同時編滬津兩地的《文藝副刊》。那是我一生從事文藝編輯工作最緊張、最興奮,也是最熱鬧的一年。那時,我三天兩頭地利用《答辭》欄同副刊的作者和讀者交談。為了使版面活躍,還不斷開辟各種“專欄”。我干得尤其起勁的,是從理論到實踐去推廣書評。什么好作品一問世,無論是《日出》還是《寶馬》,我都先在刊物上組織筆談,然后再請作者寫創作那部作品的經驗——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嘗試,徽因都熱烈支持,并且積極參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報》創刊十周年紀念的機會,除了舉辦文藝獎金,還想從《文藝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編一本《大公報小說選》。誰來編?只有徽因最適當,因為從副刊創辦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認真仔細。我寫信去邀請,她馬上慨然答應了,并且很快就把選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選了三十篇小說,有的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張天翼、凌叔華;有的如宋翰遲、楊寶琴、程萬孚、雋聞、威深等,當時并不大為人所知。
她還為這本選集寫了一篇“題記”,其中她指責有些作家“撇開自己熟識的生活不寫……因而顯露出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她號召作家們應“更有個性,更真誠地來刻畫這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個角度”。她還強調作品最主要的是誠實,她認為誠實比題材新鮮、結構完整和文字的流麗更為重要。
記得1936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薦我的《矮檐》時,曾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談這個“誠實”問題。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1966年8月化為灰燼了。這里我只好借用她在1936年5月7日從北平寫給她的美國好友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的一封信:
對,我了解你對工作的態度,我也正是那樣工作,雖然有時和你不盡相同。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里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現它才寫的,是我所發覺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經過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認真、誠懇地想把它傳達給旁人的。對我來說,“讀者”并不是“公眾”,而是比親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們很渴望聽我的訴說,并且在聽了之后,會喜,會悲。
從20世紀80年代張辛欣的小說看,家務同婦女的事業心之間的矛盾,似乎是永恒的。在同一封信里,30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惱著:
每當我做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于是,我趕快干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干不完,并且一樁樁地不斷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務,因為我的心總一半在旁處,并且一路上在詛咒我干著的活兒——然而我又很喜歡干這種家務,有時還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當我在認真寫著點什么或從事這一類工作,同時意識到我在怠慢了家務,我就一點也不感到不安。老實說,我倒挺快活,覺得我很明智,覺得我是在做著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只有當孩子們生了病或減輕了體重時,我才難過起來。有時午夜捫心自問,又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七七”事變那天,當日本軍人在盧溝橋全面發動侵略戰爭時,這對夫婦正在山西五臺山一座古廟里工作著呢。徽因談起來非常得意,因為那天是她從一座古寺的罩滿灰塵和蜘網的梁上,發現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結構的建造年月。
親愛的北平踐踏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了。思成和徽因當然決不肯留在淪陷區。像當時北平的許許多多教授學者一樣,他們也逃出了敵占區。
1937年深秋,我們見過一面,在武漢還是長沙,現在記不清了。當時我正在失業,準備隨楊振聲師和沈先生去大西南后方。那時同住在一起的,記得還有丁西林、朱自清和趙太侔三位先輩。后來買到了汽車票,我們就經益陽去了沅陵。
我們去湘西后不久,長沙就開始被炸。那時,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里。1937年11月她在致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寫道:
昨天是長沙第一次遭到空襲,我們住的房子被日本飛機炸了。炸彈就落在離我們住所的大門約十五碼的地方。我們臨時租了三間房。轟炸時,我媽媽、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還在床上生著病。我們對于會被炸,毫無準備,事先也完全沒發任何警報。
誰也不知道我們怎么沒被炸個血肉橫飛的。當我們聽到落在左近的兩顆炸彈的巨響時,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個孩子,趕緊奔向樓梯。隨后,我們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還沒走到底層,我就隨著彈聲摔下樓梯,懷里還抱著小弟。居然沒受傷!這時,房子開始坍塌,長沙的大門、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們身上墜落。我們趕緊沖出旁門——幸而院墻沒倒塌。我們逃到街上。這時四處黑煙彌漫。
當我們正撲向清華、北大、南開三家大學合挖的臨時防空壕時,空中又投下一顆炸彈。我們停下了腳步,心想,這回準跑不掉了。我們寧愿一家人在一起經歷這場悲劇,也不能走單了。這顆炸彈落在我們正跑著的巷子盡頭,但并沒爆炸。我們就從碎玻璃碴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幾件了)刨了出來,目前正東一處西一處地在朋友們家里借住。
抗戰期間,有個短時期我們曾同住在大后方的昆明。當時,我同楊振聲師、沈從文先生住在北門街,徽因、思成和張奚若等則住在翠湖邊上。她有個弟弟在空軍里。那時,她家里的常客多是些年輕的飛行員。徽因就像往時談論文學作品時那樣,充滿激情地談論著空軍英雄們的事跡。我也正是在她的鼓勵下,寫了《劉粹剛之死》。
1938年夏天我去香港繼續編《文藝副刊》,她仍然遙遙地給我指點和支持。1939年,我去英國了,這一別就是七年。
1947年我從上海飛到北平。事先她寫信來說,一定得留一個整天給她。于是,我去清華園探望她了。
當年清華管總務的可真細心,真愛護讀書人。老遠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豎了塊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寫的是:這里住著一位病人,遵醫囑她需要靜養,過往行人,請勿喧嘩。然而這位“病人”卻經常在家里接待賓客,一開講就滔滔不絕。 徽因早年在英國讀過書,對那里的一切她都熟稔,關切。我們真的足足聊了一個整天。
徽因是極重友情的。關于我在東方學院教的什么,在劍橋學的什么,在西歐戰場上的經歷,她都一一問到了,而她也把別后八年他們一家人的經歷,不厭其詳地講給我聽。
最令她傷心的一件事是:1937年他們全家南下逃難時,把多年來辛辛苦苦踏訪各地拍下的古建筑底片,全部存在天津一家銀行里。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換來的珍貴無比的學術成果。她告訴我,再也沒有想到,天津發大水時,它們統統被泡壞了。
關于友情,這里我想再引徽因在勝利后返北平之前,1946年2月28日從昆明寫給費慰梅的信:
我終于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里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但并非最不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并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后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在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處于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加深了我們久別后相互之間的了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情就重建起來并加深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和思想,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個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后方個人和社會的狀況。盡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對于勝利后國民黨發動內戰,徽因是深惡痛絕的。寫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1946年1月從重慶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里,談到自己當時的悲憤之情。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松。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閑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望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么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從這段話不難推想出,1949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樣的喜出望外。
開國前夕,我從香港趕到北平。當時思成和徽因正投入到國徽的設計中。他們住在清華園,每天都得進城來開會。幸而思成當時有輛小型轎車。他的殘疾就是在去美國留學前遇上車禍造成的,但他并沒有因此而害怕開車。兩個人就這樣滿懷激情,在為著革命大業而發揮著他們的才智。
我同徽因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二次文代會上。有一天在會場上,她老遠向我招手。我坐到她身邊,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聲:“小姐。”她不勝感慨地說:“哎呀,還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樣子啦。”語調怪傷感的。我安慰她說:“精神不老,就永遠也不會老。”
但僅僅過了一年,噩耗就傳來了。
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天資稟賦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災多難的歲月里,一輩子病魔纏身,戰爭期間顛沛流離,全國解放后只過了短短六年就溘然離去人間,怎能不令人心酸!我立即給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思成的回信我原以為早已燒毀于1966年8月那場火災,但據文潔若說,八年前(即1973年)它曾奇跡般地重新出現過一次。
1973年,文物局發還了一些十年動亂期間查抄的書物。當時我們全家人擠在東直門內一條小巷的一間八米斗室里,文潔若只得“以社為家”,住在辦公室,還把家中堆不下的書也放在一只破柜子里。一天,她偶然發現一本書中夾著這封信,她還重讀了一遍。信一共有兩頁,是用蠅頭小楷直書的,字跡非常工整。思成首先感謝我對他的慰問,并說他一直在害病,所以拖了這么久才寫回信。徽因與世長辭時,他自己也正住在同仁醫院,躺在她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以無限哀思回憶了他們共同生活和工作過來的幾十年,這是一位丈夫對亡妻真誠而感人的贊頌。可惜這次動手寫此文時,怎么也沒找到這封珍貴的信。
1983年我第三次訪美之際,除了在圣迭戈承卓以玉送來徽因年輕時的照片兩幀,又蒙費正清贈我一本他的自傳《五十年回憶錄》,其中有一段描繪抗戰期間他去李莊訪問思成和徽因的情景。
徽因瘦極了,但依舊那么充滿活力,并且在操持著家務,因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飯菜一樣樣端上。然后,我們就聊起來。主要是聽徽因一個人談。傍晚五點半,就得靠一支蠟燭或者一盞油燈來生活了。八點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覺。沒有電話,只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熱水瓶,可沒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沒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單,但缺少洗滌的肥皂。有筆,可沒有紙。有報紙,可都是幾天以前的。
最后,費正清慨嘆道:
住了一個星期,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患重感冒,只好躺在床上。我深深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于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這個集子里所收的作品,從數量上來說,同徽因從事文藝寫作的漫長歲月確實是很不相稱的。一方面,這是由于她一生花了不少時間去當啦啦隊,鼓勵旁人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的興趣廣泛,文藝不過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學過建筑,在耶魯大學還從名師貝克爾教授攻過舞臺設計。我在她家里曾見過她畫的水彩,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慳吝人》時,是她擔任的設計。
我不懂建筑學,但我隱約覺得徽因更大的貢獻,也許是在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無名英雄!試想以她那樣老早就被醫生宣布患有絕癥的瘦弱女子,卻不顧自己的健康狀況,陪伴思成在當時極為落后的窮鄉僻壤四處奔走,坐騾車,住雞毛小店,根據地方縣志的記載去尋訪早已被人們遺忘了的荒寺古廟。一個患有殘疾,一個身染重痼,這對熱愛祖國文化遺產的夫婦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滿積年塵埃的廟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處飛著蝙蝠)去丈量、測繪、探索我國古代建筑的營造法式。費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傳》中曾引用梁思成于1941年所寫而從未發表過的小結說:截至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營造學社已經踏訪了十五個省份里的兩百個縣,實地精細地研究了兩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大概都參加了。
徽因的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我經手發表的,如《模影零篇》。我不懂詩,但我十分愛讀她的詩。她的小說,半個世紀前讀的,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這里,我再一次表示遺憾:她寫得太少、太少了。每逢我聆聽她對文學、對藝術、對社會生活的細膩觀察和精辟見解時,我心里就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么精彩的一部書啊!
相信熱愛梁思成、林徽因這對夫婦的讀者,熱愛中國古典建筑的讀者會像我一樣,珍愛他們的文字,珍愛他們的文化情懷和文化操守。
然而還有更令我興奮的事等在后面呢!
幾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這信連同所有我心愛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蠶》,要請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來我這里,咱們一道去。
那幾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藍布大褂洗得干干凈凈,把一雙舊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過午飯我蹬上腳踏車,斜穿過大鐘寺進城了。兩小時后,我就羞怯怯地隨著沈先生從達子營跨進了總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如今回憶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動的心境和拘謹的神態,仍覺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后腿上,親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在去之前,原聽說這位小姐的肺病已經相當重了(還經常得臥床休息),而那時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癥那么可怕。我以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見我們呢!可那天她穿的卻是一套騎馬裝(她常和費正清與夫人威爾瑪去外國人俱樂部騎馬),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話講得又多又快又興奮。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連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兩位也只是坐在沙發上邊吧嗒著煙斗,邊點頭贊賞(徽因的健談絕不是結了婚的婦人的那種閑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她從不拐彎抹角,模棱兩可。這種純學術的批評,也從來沒有人記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過人的藝術悟性)。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沒提到一個“病”字。她比一個健康人精力還旺盛,還健談。
那以后,我們還常在朱光潛先生家舉行的“讀詩會”上見面。我也跟著大家稱她為“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種只會抿嘴嫣然一笑的嬌小姐,而是位學識淵博、思想敏捷,并且語言鋒利的評論家。她十分關心創作。當時南北方也頗有些文藝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細,并且對文章常有犀利和獨到的見解。對于好惡,她從不模棱兩可。同時,在批了什么一頓之后,往往又會指出某一點可取之處。一次我記得她當面對梁宗岱的一首詩數落了一通,梁詩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氣的。于是,在“讀詩會”的一角,他們抬起杠來。
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報》編刊物了。每個月我都到北平來,在來今雨軒舉行個二三十人的茶會,一半為了組稿,一半也為了聽取《文藝副刊》支持者們的意見。小姐幾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間必有一番宏論。
1936年我調到上海,同時編滬津兩地的《文藝副刊》。那是我一生從事文藝編輯工作最緊張、最興奮,也是最熱鬧的一年。那時,我三天兩頭地利用《答辭》欄同副刊的作者和讀者交談。為了使版面活躍,還不斷開辟各種“專欄”。我干得尤其起勁的,是從理論到實踐去推廣書評。什么好作品一問世,無論是《日出》還是《寶馬》,我都先在刊物上組織筆談,然后再請作者寫創作那部作品的經驗——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嘗試,徽因都熱烈支持,并且積極參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報》創刊十周年紀念的機會,除了舉辦文藝獎金,還想從《文藝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編一本《大公報小說選》。誰來編?只有徽因最適當,因為從副刊創辦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認真仔細。我寫信去邀請,她馬上慨然答應了,并且很快就把選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選了三十篇小說,有的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張天翼、凌叔華;有的如宋翰遲、楊寶琴、程萬孚、雋聞、威深等,當時并不大為人所知。
她還為這本選集寫了一篇“題記”,其中她指責有些作家“撇開自己熟識的生活不寫……因而顯露出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她號召作家們應“更有個性,更真誠地來刻畫這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個角度”。她還強調作品最主要的是誠實,她認為誠實比題材新鮮、結構完整和文字的流麗更為重要。
記得1936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薦我的《矮檐》時,曾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談這個“誠實”問題。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1966年8月化為灰燼了。這里我只好借用她在1936年5月7日從北平寫給她的美國好友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的一封信:
對,我了解你對工作的態度,我也正是那樣工作,雖然有時和你不盡相同。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里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現它才寫的,是我所發覺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經過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認真、誠懇地想把它傳達給旁人的。對我來說,“讀者”并不是“公眾”,而是比親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們很渴望聽我的訴說,并且在聽了之后,會喜,會悲。
從20世紀80年代張辛欣的小說看,家務同婦女的事業心之間的矛盾,似乎是永恒的。在同一封信里,30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惱著:
每當我做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于是,我趕快干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干不完,并且一樁樁地不斷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務,因為我的心總一半在旁處,并且一路上在詛咒我干著的活兒——然而我又很喜歡干這種家務,有時還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當我在認真寫著點什么或從事這一類工作,同時意識到我在怠慢了家務,我就一點也不感到不安。老實說,我倒挺快活,覺得我很明智,覺得我是在做著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只有當孩子們生了病或減輕了體重時,我才難過起來。有時午夜捫心自問,又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七七”事變那天,當日本軍人在盧溝橋全面發動侵略戰爭時,這對夫婦正在山西五臺山一座古廟里工作著呢。徽因談起來非常得意,因為那天是她從一座古寺的罩滿灰塵和蜘網的梁上,發現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結構的建造年月。
親愛的北平踐踏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了。思成和徽因當然決不肯留在淪陷區。像當時北平的許許多多教授學者一樣,他們也逃出了敵占區。
1937年深秋,我們見過一面,在武漢還是長沙,現在記不清了。當時我正在失業,準備隨楊振聲師和沈先生去大西南后方。那時同住在一起的,記得還有丁西林、朱自清和趙太侔三位先輩。后來買到了汽車票,我們就經益陽去了沅陵。
我們去湘西后不久,長沙就開始被炸。那時,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里。1937年11月她在致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寫道:
昨天是長沙第一次遭到空襲,我們住的房子被日本飛機炸了。炸彈就落在離我們住所的大門約十五碼的地方。我們臨時租了三間房。轟炸時,我媽媽、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還在床上生著病。我們對于會被炸,毫無準備,事先也完全沒發任何警報。
誰也不知道我們怎么沒被炸個血肉橫飛的。當我們聽到落在左近的兩顆炸彈的巨響時,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個孩子,趕緊奔向樓梯。隨后,我們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還沒走到底層,我就隨著彈聲摔下樓梯,懷里還抱著小弟。居然沒受傷!這時,房子開始坍塌,長沙的大門、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們身上墜落。我們趕緊沖出旁門——幸而院墻沒倒塌。我們逃到街上。這時四處黑煙彌漫。
當我們正撲向清華、北大、南開三家大學合挖的臨時防空壕時,空中又投下一顆炸彈。我們停下了腳步,心想,這回準跑不掉了。我們寧愿一家人在一起經歷這場悲劇,也不能走單了。這顆炸彈落在我們正跑著的巷子盡頭,但并沒爆炸。我們就從碎玻璃碴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幾件了)刨了出來,目前正東一處西一處地在朋友們家里借住。
抗戰期間,有個短時期我們曾同住在大后方的昆明。當時,我同楊振聲師、沈從文先生住在北門街,徽因、思成和張奚若等則住在翠湖邊上。她有個弟弟在空軍里。那時,她家里的常客多是些年輕的飛行員。徽因就像往時談論文學作品時那樣,充滿激情地談論著空軍英雄們的事跡。我也正是在她的鼓勵下,寫了《劉粹剛之死》。
1938年夏天我去香港繼續編《文藝副刊》,她仍然遙遙地給我指點和支持。1939年,我去英國了,這一別就是七年。
1947年我從上海飛到北平。事先她寫信來說,一定得留一個整天給她。于是,我去清華園探望她了。
當年清華管總務的可真細心,真愛護讀書人。老遠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豎了塊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寫的是:這里住著一位病人,遵醫囑她需要靜養,過往行人,請勿喧嘩。然而這位“病人”卻經常在家里接待賓客,一開講就滔滔不絕。 徽因早年在英國讀過書,對那里的一切她都熟稔,關切。我們真的足足聊了一個整天。
徽因是極重友情的。關于我在東方學院教的什么,在劍橋學的什么,在西歐戰場上的經歷,她都一一問到了,而她也把別后八年他們一家人的經歷,不厭其詳地講給我聽。
最令她傷心的一件事是:1937年他們全家南下逃難時,把多年來辛辛苦苦踏訪各地拍下的古建筑底片,全部存在天津一家銀行里。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換來的珍貴無比的學術成果。她告訴我,再也沒有想到,天津發大水時,它們統統被泡壞了。
關于友情,這里我想再引徽因在勝利后返北平之前,1946年2月28日從昆明寫給費慰梅的信:
我終于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里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但并非最不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并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后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在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處于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加深了我們久別后相互之間的了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情就重建起來并加深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和思想,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個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后方個人和社會的狀況。盡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對于勝利后國民黨發動內戰,徽因是深惡痛絕的。寫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1946年1月從重慶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里,談到自己當時的悲憤之情。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松。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閑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望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么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從這段話不難推想出,1949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樣的喜出望外。
開國前夕,我從香港趕到北平。當時思成和徽因正投入到國徽的設計中。他們住在清華園,每天都得進城來開會。幸而思成當時有輛小型轎車。他的殘疾就是在去美國留學前遇上車禍造成的,但他并沒有因此而害怕開車。兩個人就這樣滿懷激情,在為著革命大業而發揮著他們的才智。
我同徽因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二次文代會上。有一天在會場上,她老遠向我招手。我坐到她身邊,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聲:“小姐。”她不勝感慨地說:“哎呀,還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樣子啦。”語調怪傷感的。我安慰她說:“精神不老,就永遠也不會老。”
但僅僅過了一年,噩耗就傳來了。
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天資稟賦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災多難的歲月里,一輩子病魔纏身,戰爭期間顛沛流離,全國解放后只過了短短六年就溘然離去人間,怎能不令人心酸!我立即給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思成的回信我原以為早已燒毀于1966年8月那場火災,但據文潔若說,八年前(即1973年)它曾奇跡般地重新出現過一次。
1973年,文物局發還了一些十年動亂期間查抄的書物。當時我們全家人擠在東直門內一條小巷的一間八米斗室里,文潔若只得“以社為家”,住在辦公室,還把家中堆不下的書也放在一只破柜子里。一天,她偶然發現一本書中夾著這封信,她還重讀了一遍。信一共有兩頁,是用蠅頭小楷直書的,字跡非常工整。思成首先感謝我對他的慰問,并說他一直在害病,所以拖了這么久才寫回信。徽因與世長辭時,他自己也正住在同仁醫院,躺在她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以無限哀思回憶了他們共同生活和工作過來的幾十年,這是一位丈夫對亡妻真誠而感人的贊頌。可惜這次動手寫此文時,怎么也沒找到這封珍貴的信。
1983年我第三次訪美之際,除了在圣迭戈承卓以玉送來徽因年輕時的照片兩幀,又蒙費正清贈我一本他的自傳《五十年回憶錄》,其中有一段描繪抗戰期間他去李莊訪問思成和徽因的情景。
徽因瘦極了,但依舊那么充滿活力,并且在操持著家務,因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飯菜一樣樣端上。然后,我們就聊起來。主要是聽徽因一個人談。傍晚五點半,就得靠一支蠟燭或者一盞油燈來生活了。八點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覺。沒有電話,只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熱水瓶,可沒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沒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單,但缺少洗滌的肥皂。有筆,可沒有紙。有報紙,可都是幾天以前的。
最后,費正清慨嘆道:
住了一個星期,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患重感冒,只好躺在床上。我深深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于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這個集子里所收的作品,從數量上來說,同徽因從事文藝寫作的漫長歲月確實是很不相稱的。一方面,這是由于她一生花了不少時間去當啦啦隊,鼓勵旁人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的興趣廣泛,文藝不過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學過建筑,在耶魯大學還從名師貝克爾教授攻過舞臺設計。我在她家里曾見過她畫的水彩,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慳吝人》時,是她擔任的設計。
我不懂建筑學,但我隱約覺得徽因更大的貢獻,也許是在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無名英雄!試想以她那樣老早就被醫生宣布患有絕癥的瘦弱女子,卻不顧自己的健康狀況,陪伴思成在當時極為落后的窮鄉僻壤四處奔走,坐騾車,住雞毛小店,根據地方縣志的記載去尋訪早已被人們遺忘了的荒寺古廟。一個患有殘疾,一個身染重痼,這對熱愛祖國文化遺產的夫婦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滿積年塵埃的廟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處飛著蝙蝠)去丈量、測繪、探索我國古代建筑的營造法式。費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傳》中曾引用梁思成于1941年所寫而從未發表過的小結說:截至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營造學社已經踏訪了十五個省份里的兩百個縣,實地精細地研究了兩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大概都參加了。
徽因的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我經手發表的,如《模影零篇》。我不懂詩,但我十分愛讀她的詩。她的小說,半個世紀前讀的,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這里,我再一次表示遺憾:她寫得太少、太少了。每逢我聆聽她對文學、對藝術、對社會生活的細膩觀察和精辟見解時,我心里就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么精彩的一部書啊!
相信熱愛梁思成、林徽因這對夫婦的讀者,熱愛中國古典建筑的讀者會像我一樣,珍愛他們的文字,珍愛他們的文化情懷和文化操守。
目次
一代才女林徽因詩歌編“誰愛這不息的變幻”那一晚仍然一首桃花激昂笑深夜裡聽到樂聲情願蓮燈中夜鐘聲山中一個夏夜秋天,這秋天年關你是人間的四月天——一句愛的讚頌憶吊瑋德靈感城樓上深笑風箏別丟掉雨後天記憶靜院無題題剔空菩提葉黃昏過泰山晝夢八月的憂愁過楊柳冥思空想你來了“九一八”閑走藤花前——獨過靜心齋旅途中紅葉裡的信念山中靜坐十月獨行時間古城春景前後去春除夕看花給秋天人生展緩六點鐘在下午昆明即景一串瘋話病中雜詩(九首)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戰陣亡我們的雄雞春天田裡漫步破曉散文文論編悼志摩山西通信窗子以外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蛛絲和梅花彼此一片陽光惟其是脆嫩《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小說戲劇編窘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四篇)梅真同他們(四幕劇)夜鶯與玫瑰(譯作)書信編致胡適(八封)致沈從文(七封)致費正清、費慰梅(十封)致梁思莊給梁再冰致傅斯年致金岳霖致張兆和致梁思成(兩封)建築意編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平郊建築雜錄談北京的幾個文物建築我們的首都達.芬奇一具有偉大遠見的建築工程師和平禮物創作要目
書摘/試閱
十一月十九日,我們的好朋友,許多人都愛戴的新詩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慘酷的,在飛機上遇險而死去。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針刺觸到許多朋友的心上,頓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慟的咽哽鎖住每一個人的嗓子。
志摩……死……誰曾將這兩個句子連在一處想過!他是那樣活潑的一個人,那樣剛剛站在壯年的頂峰上的一個人。朋友們常常驚訝他的活動,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認真,誰又會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闖出我們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遠的靜寂,不給我們一點預告,一點準備,或是一個最后希望的余地。這種幾乎近于忍心的決絕,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現在那不能否認的事實,仍然無情地擋在我們前面。任憑我們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慘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夠仍然接觸到他原來的音容,事實是不會為體貼我們這悲念而有些許更改;而他也再不會為不忍我們這傷悼而有些許活動的可能!這難堪的永遠靜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殘酷處。
我們不迷信的,沒有宗教的望著這死的帷幕,更是絲毫沒有把握。張開口我們不會呼吁,閉上眼不會入夢,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邊沿,我們不能預期后會,對這死,我們只是永遠發怔,吞咽苦澀的淚;待時間來剝削這哀慟的尖銳,痂結我們每次悲悼的創傷。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許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適之先生家里嗎?但是除去拭淚相對,默然圍坐外,誰也沒有主意,誰也不知有什么話說,對這死!
誰也沒有主意,誰也沒有話說!事實不容我們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們不傷悼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們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對,默然圍坐……而志摩則仍是死去沒有回頭,沒有音訊,永遠的不會回頭,永遠的不會再有音訊。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命運之說的,但是對著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著那許多事實的痕跡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盡有定數?世事盡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么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們前邊展開的只是一堆堅質的事實:
“是的,他十九晨有電報來給我……
“十九早晨,是的!說下午三點準到南苑,派車接……
“電報是九時從南京飛機場發出的……
“剛是他開始飛行以后所發……
“派車接去了,等到四點半……說飛機沒有到……
“沒有到……航空公司說濟南有霧……很大……”只是一個鐘頭的差別;下午三時到南苑,濟南有霧!誰相信就是這一個鐘頭中便可以有這么不同事實的發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離平的前一晚我仍見到,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飛機改期過三次,他曾說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個茶會出來,在總布胡同口分手。在這茶會里我們請的是為太平洋會議來的一個柏雷博士,因為他是志摩生平最愛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兒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從柏雷口中得些關于曼殊斐兒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時間,我們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約會出去了,回來時很晚。聽差說他又來過,適遇我們夫婦剛走,他自己坐了一會兒,喝了一壺茶,在桌上寫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時飛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陣不痛快,卻忙給他一個電話。
“你放心。”他說,“很穩當的,我還要留著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跡呢,那能便死?……”
話雖是這樣說,他卻是已經死了整兩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會懂得,死去他這樣一個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現在這事實一天比一天更結實,更固定,更不容否認。志摩是死了,這個簡單殘酷的實際早又添上時間的色彩,一周,兩周,一直的增長下去……
我不該在這里語無倫次的盡管呻吟我們做朋友的悲哀情緒。歸根說,讀者抱著我們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請柏雷一樣,要從我們口里再聽到關于志摩的一些事。這個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們滿意,因為關于他的事,動聽的,使青年人知道這里有個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實在太多,決不是幾千字可以表達得完。誰也得承認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世間便不輕易有幾個的,無論在中國或是外國。
我認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時候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尚未去康橋。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認識到影響他遷學的狄更生先生。不用說他和我父親最談得來,雖然他們年歲上差別不算少,一見面之后便互相引為知己。他到康橋之后由狄更生介紹進了皇家學院,當時和他同學的有我姊丈溫君源寧。一直到最近兩個月中源寧還常在說他當時的許多笑話,雖然說是笑話,那也是他對志摩最早的一個驚異的印象。志摩認真的詩情,絕不含有絲毫矯偽,他那種癡,那種孩子似的天真實能令人驚訝。源寧說,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讀書,外邊下起了傾盆大雨——唯是英倫那樣的島國才有的狂雨——忽然他聽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門,外邊跳進一個被雨水淋得全濕的客人。不用說便是志摩,他一進門一把扯著源寧向外跑,說快來我們到橋上去等著。這一來把源寧怔住了,他問志摩等什么在這大雨里。志摩睜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興地說“看雨后的虹去”。源寧不止說他不去,并且勸志摩趁早將濕透的衣服換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國的濕氣豈是兒戲。志摩不等他說完,一溜煙的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問過志摩這故事的真確,他笑著點頭承認這全段故事的真實。我問: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橋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沒有?他說記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詫異的打斷他對那虹的描寫,問他:怎么他便知道,準會有虹的。他得意的笑答我說:“完全詩意的信仰!”
“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里哭了!也就是為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宿愿!“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運命!”他真對運命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的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苦,“我們不能輕易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但是我前邊說過最難堪的是這永遠的靜寂。我們生在這沒有宗教的時代,對這死實在太沒有把握了。這以后許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會有一點點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麗的詩意的信仰!
我個人的悲緒不禁又來擾亂我對他生前許多清晰的回憶,朋友們原諒。
詩人的志摩用不著我來多說,他那許多詩文便是估價他的天平。我們新詩的歷史才是這樣的短,恐怕他的判斷人尚在我們兒孫輩的中間。我要談的是詩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說志摩的為人只是不經意的浪漫,志摩的詩全是抒情詩,這斷語從不認識他的人聽來可以說很公平,從他朋友們看來實在是對不起他。志摩是個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華的卻是他對人的同情,和藹,和優容;沒有一個人他對他不和藹,沒有一種人,他不能優容,沒有一種的情感,他絕對的不能表同情。我不說了解,因為不是許多人愛說志摩最不解人情嗎?我說他的特點也就在這上頭。
我們尋常人就愛說了解,能了解的我們便同情,不了解的我們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們能了解的,我們以為很適當;不表同情于我們不能了解的,我們也認為很公平。志摩則不然,了解與不了解,他并沒有過分的夸張,他只知道溫存,和平,體貼。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無論出自何人,在何等情況下,他理智上認為適當與否,他全能表幾分同情,他真能體會原諒他人與他自己不相同處。從不會刻薄的單支出嚴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與他不同的人。他這樣的溫和,這樣的優容,真能使許多人慚愧,我可以忠實地說,至少他要比我們多數的人偉大許多。他覺得人類各種的情感動作全有它不同的,價值放大了的人類的眼光,同情是不該只限于我們劃定的范圍內。他是對的,朋友們,歸根說,我們能夠懂得幾個人,了解幾樁事,幾種情感?那一樁事,那一個人沒有多面的看法!為此說來志摩朋友之多,不是個可怪的事;凡是認得他的人不論深淺對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極為自然的結果。而反過來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過程中卻是很少得著同情的。不止如是,他還曾為他的一點理想的愚誠幾次幾乎不見容于社會。但是他卻未曾為這個鄙吝他給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為受了刺激而轉變刻薄暴戾過,誰能不承認他幾有超人的寬量。
P93-97
志摩……死……誰曾將這兩個句子連在一處想過!他是那樣活潑的一個人,那樣剛剛站在壯年的頂峰上的一個人。朋友們常常驚訝他的活動,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認真,誰又會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闖出我們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遠的靜寂,不給我們一點預告,一點準備,或是一個最后希望的余地。這種幾乎近于忍心的決絕,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現在那不能否認的事實,仍然無情地擋在我們前面。任憑我們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慘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夠仍然接觸到他原來的音容,事實是不會為體貼我們這悲念而有些許更改;而他也再不會為不忍我們這傷悼而有些許活動的可能!這難堪的永遠靜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殘酷處。
我們不迷信的,沒有宗教的望著這死的帷幕,更是絲毫沒有把握。張開口我們不會呼吁,閉上眼不會入夢,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邊沿,我們不能預期后會,對這死,我們只是永遠發怔,吞咽苦澀的淚;待時間來剝削這哀慟的尖銳,痂結我們每次悲悼的創傷。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許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適之先生家里嗎?但是除去拭淚相對,默然圍坐外,誰也沒有主意,誰也不知有什么話說,對這死!
誰也沒有主意,誰也沒有話說!事實不容我們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們不傷悼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們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對,默然圍坐……而志摩則仍是死去沒有回頭,沒有音訊,永遠的不會回頭,永遠的不會再有音訊。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命運之說的,但是對著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著那許多事實的痕跡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盡有定數?世事盡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么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們前邊展開的只是一堆堅質的事實:
“是的,他十九晨有電報來給我……
“十九早晨,是的!說下午三點準到南苑,派車接……
“電報是九時從南京飛機場發出的……
“剛是他開始飛行以后所發……
“派車接去了,等到四點半……說飛機沒有到……
“沒有到……航空公司說濟南有霧……很大……”只是一個鐘頭的差別;下午三時到南苑,濟南有霧!誰相信就是這一個鐘頭中便可以有這么不同事實的發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離平的前一晚我仍見到,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飛機改期過三次,他曾說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個茶會出來,在總布胡同口分手。在這茶會里我們請的是為太平洋會議來的一個柏雷博士,因為他是志摩生平最愛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兒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從柏雷口中得些關于曼殊斐兒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時間,我們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約會出去了,回來時很晚。聽差說他又來過,適遇我們夫婦剛走,他自己坐了一會兒,喝了一壺茶,在桌上寫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時飛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陣不痛快,卻忙給他一個電話。
“你放心。”他說,“很穩當的,我還要留著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跡呢,那能便死?……”
話雖是這樣說,他卻是已經死了整兩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會懂得,死去他這樣一個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現在這事實一天比一天更結實,更固定,更不容否認。志摩是死了,這個簡單殘酷的實際早又添上時間的色彩,一周,兩周,一直的增長下去……
我不該在這里語無倫次的盡管呻吟我們做朋友的悲哀情緒。歸根說,讀者抱著我們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請柏雷一樣,要從我們口里再聽到關于志摩的一些事。這個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們滿意,因為關于他的事,動聽的,使青年人知道這里有個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實在太多,決不是幾千字可以表達得完。誰也得承認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世間便不輕易有幾個的,無論在中國或是外國。
我認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時候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尚未去康橋。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認識到影響他遷學的狄更生先生。不用說他和我父親最談得來,雖然他們年歲上差別不算少,一見面之后便互相引為知己。他到康橋之后由狄更生介紹進了皇家學院,當時和他同學的有我姊丈溫君源寧。一直到最近兩個月中源寧還常在說他當時的許多笑話,雖然說是笑話,那也是他對志摩最早的一個驚異的印象。志摩認真的詩情,絕不含有絲毫矯偽,他那種癡,那種孩子似的天真實能令人驚訝。源寧說,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讀書,外邊下起了傾盆大雨——唯是英倫那樣的島國才有的狂雨——忽然他聽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門,外邊跳進一個被雨水淋得全濕的客人。不用說便是志摩,他一進門一把扯著源寧向外跑,說快來我們到橋上去等著。這一來把源寧怔住了,他問志摩等什么在這大雨里。志摩睜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興地說“看雨后的虹去”。源寧不止說他不去,并且勸志摩趁早將濕透的衣服換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國的濕氣豈是兒戲。志摩不等他說完,一溜煙的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問過志摩這故事的真確,他笑著點頭承認這全段故事的真實。我問: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橋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沒有?他說記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詫異的打斷他對那虹的描寫,問他:怎么他便知道,準會有虹的。他得意的笑答我說:“完全詩意的信仰!”
“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里哭了!也就是為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宿愿!“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運命!”他真對運命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的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苦,“我們不能輕易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但是我前邊說過最難堪的是這永遠的靜寂。我們生在這沒有宗教的時代,對這死實在太沒有把握了。這以后許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會有一點點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麗的詩意的信仰!
我個人的悲緒不禁又來擾亂我對他生前許多清晰的回憶,朋友們原諒。
詩人的志摩用不著我來多說,他那許多詩文便是估價他的天平。我們新詩的歷史才是這樣的短,恐怕他的判斷人尚在我們兒孫輩的中間。我要談的是詩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說志摩的為人只是不經意的浪漫,志摩的詩全是抒情詩,這斷語從不認識他的人聽來可以說很公平,從他朋友們看來實在是對不起他。志摩是個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華的卻是他對人的同情,和藹,和優容;沒有一個人他對他不和藹,沒有一種人,他不能優容,沒有一種的情感,他絕對的不能表同情。我不說了解,因為不是許多人愛說志摩最不解人情嗎?我說他的特點也就在這上頭。
我們尋常人就愛說了解,能了解的我們便同情,不了解的我們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們能了解的,我們以為很適當;不表同情于我們不能了解的,我們也認為很公平。志摩則不然,了解與不了解,他并沒有過分的夸張,他只知道溫存,和平,體貼。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無論出自何人,在何等情況下,他理智上認為適當與否,他全能表幾分同情,他真能體會原諒他人與他自己不相同處。從不會刻薄的單支出嚴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與他不同的人。他這樣的溫和,這樣的優容,真能使許多人慚愧,我可以忠實地說,至少他要比我們多數的人偉大許多。他覺得人類各種的情感動作全有它不同的,價值放大了的人類的眼光,同情是不該只限于我們劃定的范圍內。他是對的,朋友們,歸根說,我們能夠懂得幾個人,了解幾樁事,幾種情感?那一樁事,那一個人沒有多面的看法!為此說來志摩朋友之多,不是個可怪的事;凡是認得他的人不論深淺對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極為自然的結果。而反過來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過程中卻是很少得著同情的。不止如是,他還曾為他的一點理想的愚誠幾次幾乎不見容于社會。但是他卻未曾為這個鄙吝他給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為受了刺激而轉變刻薄暴戾過,誰能不承認他幾有超人的寬量。
P93-97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