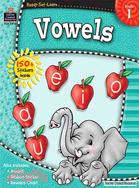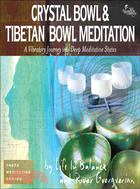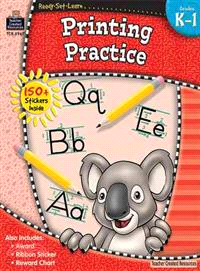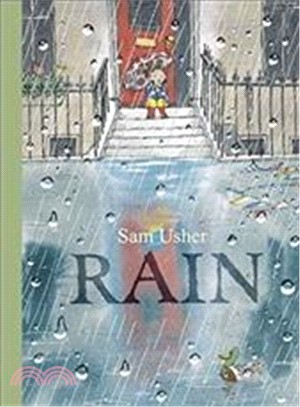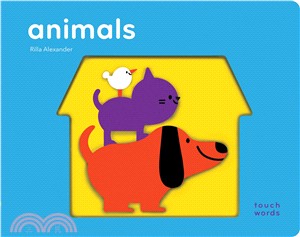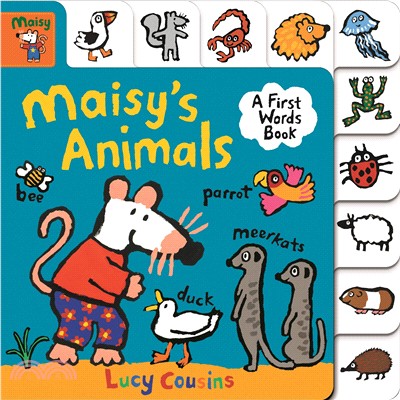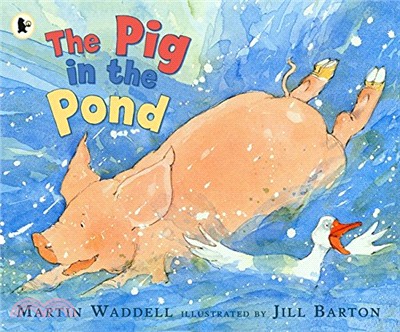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一位親戚是國民黨,
我當過共產黨的官員。
我的人生猶如走在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夾縫中
我的膚色較黑,至今仍殘留著印尼的赤道陽光。
戶口名簿上至今仍註明出生地:印尼。這個與生俱來的海外關係,在我人生的征途中成為沉重的包袱,在歷史的夾縫中艱難的遊走著。
回中國後不久遇上了土地改革,一夕間變成了「地主崽子」、「反動家屬」,小小年紀受盡歧視。幾十年錯雜、艱澀的人生路上,渴求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奢望。後因鄧小平一句「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突然包袱變成一種機遇,這幾十年終於走過來了,成為有點名氣的中學校長,又成為省級僑聯的秘書長,最後居然還成為一個「副廳級」幹部。
本書特色
本書傳主經歷種種磨難,但從未曾放棄過,終究從出身不好,最後卻仍可做到校長,甚至是「副廳級」幹部。給正在努力挑戰自我人生的讀者一點鼓勵。
作者簡介
生於印度尼西亞亞齊市,長於中國廣東梅縣,湖南長沙大學畢業。曾任中學教師、校長、湖南省僑聯處長、秘書長及雜誌社總編輯、社長,曾編著《湖南客家》等圖書。
序
前言
女兒、女婿去印尼巴厘島旅遊,帶回來一件玩具「木雕貓咪」。三個貓咪坐在沙發上,憨態可掬,做工稍顯粗糙但不失古樸。我喜歡。我出生於印尼。我的膚色較黑,至今仍殘留著印尼的赤道陽光。我叮囑他們「代我看看六十多年前生活過的地方」,他們完成了老爸的囑託,想讓老爸看著「印尼貓咪」喚起童年的記憶,以慰平生。
我家鄉廣東省梅縣是著名僑鄉。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迫於山多田少人稠,世事昏亂如麻,生活艱難困苦,梅縣客家人絡繹於途遠赴南洋(東南亞各國)謀取生路。我祖父赤貧,無以為生,忍痛讓年僅十三歲的父親,身上「僅繫一根皮帶」,先下汕頭做工,然後讓他跟著「水客」出南洋去了。「水客」是往返於家鄉與南洋之間,專事帶人帶錢帶物以為生計者。「水客」把他帶到了印尼亞齊市。
亞齊,地處蘇門答臘島西北部,就是二○○四年十二月發生大地震大海嘯的地方。我家鄉出南洋謀生的父老鄉親,以親帶親,以鄰幫鄰,大都到了那裡。家鄉窮,印尼也絕不是淘金之地,尤其是亞齊,那裡並不富庶,至今仍然落後貧窮。我父親在亞齊辛勤勞作近三十年,仍然是一名手工藝工人,家境很是一般。
父親是遵伯父之命回國的。伯父在國民黨軍隊和地方當過不大不小的官,家有薄產,元配不識字,於是叫我父親回來幫他打理家事。
父親帶著我們全家回國後,我在家鄉廣東梅縣讀小學、中學,接著到湖南長沙讀大學,之後在湖南工作近三十八年後退休。人生旅途一步步走過來,七十年了,時時處處覺得艱辛。一生奔波為稻粱謀,紛紛擾擾,擔驚受怕,無暇去思考人生的意義。
退休後,一次大學時的老同學聚會,有位舉杯慷慨陳詞,介紹他的退休生活座右銘:「忘記昨天,過好今天,不想明天。」一個人是只有這麼「三天」吧,但要按老同學酒酣耳熱之際倡導的那個活法,我不敢苟同。就拿「昨天」來說,「忘記」就很難。退休後賦閑在家,常常凝思「昨天」:我,一個極其平凡甚至近乎卑賤的人,從歷史的夾縫中艱難站起來,走過的是極不平凡、極為艱澀的人生道路。
我的戶口名簿上至今注明「出生地印尼」,白紙黑字抹不掉。這個與生俱來的「海外關係」,在我人生的漫漫征途中成為沉重的包袱,長時間蝸牛般背負著,在歷史的夾縫中艱難遊走。
回國不久碰上土地改革,父親與伯父家一起被劃為「官僚地主」成分,伯父在區裡一次群眾大會上被判「斬立決」。我一夜之間變為「地主崽子」、「反動家屬」。小小年紀便飽受歧視,年少已識盡愁滋味。幾十年錯雜、艱澀的人生路上,迷茫中無助地渴求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但似乎永遠是遙不可及的奢望。
精神上的重擊,生活上的折磨,使父親在一次並非不治之症的疾患中拋下了我們,這時他還未到知天命之年。一家大小生活全靠可憐的母親苦苦撐持。小學中學十二年,我寒窗苦讀,衣衫破舊,食不果腹,一餐飽飯只能在夢裡尋求。
也許是歷史的誤會,我竟然考上了大學,這是不幸中之萬幸。邁入大學校門,很快發現,我是全班唯一出身不好而且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報到不久即受到多次盤查,出身成分海外關係臺灣舅舅等疑難問題要我回答,弄得我惴惴不安。可是,之後卻沒有出現什麼事,我讀完了大學。
大學畢業,我表示「一切聽從黨安排」。結果,被層層發落,最終「安排」到據稱是「離鐵路最近」的一所鄉鎮中學教書。我言聽計從,風雪交加中形單影隻前往履職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文化大革命」中,因教案上引用流行詞句「被打倒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句子,卻不料被駐校軍宣隊隊長解讀為「階級人」,在大會上高喊「沒有階級人只有階級敵人」,點名批判我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由於忘記在一張大字報的「劉少奇」三字上畫一把紅叉,差點被「揪出來鬥垮鬥臭」。還被人莫名其妙地污蔑我明媒正娶的老婆「來歷不明」,無助的她被勒令退出藉以維生的臨時炊事員工作。
粉碎「四人幫」使我人生發生重大轉折,真所謂「撥開雲霧見太陽」,突然間喜事接踵而至:共產黨、致公黨都有人來找我談心,啟發我加入他們的組織;很快,我又成為了市政協常委;家鄉梅縣人民政府鄭重發文將我家的「地主」成分改為「華僑工人」,我的家庭出身一下由剝削階級變成了工人階級;土改時被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伯父經梅縣縣委重新定性為「起義投誠人員」予以平反;土改時被沒收的房屋被審定為「僑房」退回來了。
人生道路如此離奇。遲遲到來的「工人階級」出身,讓我悲喜交加。我還是我,但「出身」卻一下子變了,「出身不由己」這一次在我身上戲劇性地做出了證明。歷史給我一家開了個天大的玩笑,但是,我卻笑不起來。這個玩笑對於歷史來說可能是不經意的甚至是輕佻的一筆,但對於個人和家庭來說,代價實在太大了。這個在三十多年來無比嚮往的榮耀「出身」,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對於我已經沒有多大意義。
不過,也並不是一無好處,即如「歸國華僑」身分,因鄧小平一句「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就突然由包袱變成了一種機遇,我因而被「打著燈籠」找到,「榮調」到地區僑聯工作。此後較為順暢,到了省級機關,自己的一點聰明才智好像從牢籠中被釋放了,意氣風發,工作感到得心應手,受到稱讚,還幾次評定為「優秀共產黨員」;但是有一個大大的缺點,就是未熟諳官場規則和人情世故,從來不會無事找事挨進上級首長家噓寒問暖慶生賀節敬請笑納不成敬意諸如此類,有人揶揄我「太傳統」,有人鄙夷我「扮清高」……
然後,然後就老了,就退休了。
這幾十年,我終於走過來了,也就這麼走過來了。一個漂泊的海外遊子,一個貧賤的農村孩子,在錯雜的人生路上跌跌撞撞,幾經折騰,後來成為有點名氣的中學的一校之長,之後又成為省級僑聯的秘書長,還做過一個雜誌社的社長、總編輯,最後居然成為一個「副廳級」幹部,忝為末流「高幹」。「昨天」,不但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我現在就常常魂牽夢繞,揮之不去也!
記住昨天,是為了明天。對個人而言,明天是有限的,但是我們的國家、民族,卻有無數個明天。衷心祝願從昨天艱難曲折走過來的親愛的祖國,明天會不再折騰,切記以人為本,讓所有中國人順順當當堂而皇之地站起來。
走過了長長的人生旅途後,常常反思,我這一生,是怎麼走過來的呀?有自己的勤奮,有自己的才智,有自己的真誠,有自己的毅力,這些「自己」的東西固然重要,但似乎都不能視為成長的關鍵因素。關鍵的是歷史。歷史是人創造的,人是在歷史中行進的。新中國幾十年的歷史,給一些人「站起來」賦予了很多的機遇,也給一些人有意無意地設置了或多或少的障礙,致使遲遲不能「站起來」。我一生遇到的,更多的是障礙,誠然也得到了一些機遇。在人生的征途中,一些人走的是康莊大道,而我卻是在歷史的夾縫中離奇而艱澀地跋涉。在歷史的夾縫中,留下了我錯雜的人生足跡,刻下了我跌宕的人生印痕。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幸運的。一些開國功臣尚且人生多難,甚至死於非命,我一個平凡人盡可滿足了,夫復何求。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歷史與我,我與歷史,是怎麼糾纏在一起的;歷史是如何形成夾縫,我又如何能在夾縫中容身和成長直至站起來的——箇中情結,一言難盡。
俱往矣,人生應該回首,歷史不堪較真。我只是想客觀?說歷史中我錯雜、艱澀的人生,至於人生的意義,那就聽憑歷史來解讀吧。於是便有了這本書。
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平凡人的不平凡經歷,而我相信,我的不平凡人生經歷,並不單單是我一個人的遭遇,其意義也不屬於我個人所專有,它應該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歷史財富之一,即使它在浩瀚前行的歷史中不過是一個星點、一粒微塵。通過這本書,或許能對我們國家、民族豐富多彩的歷史,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透過一絲縫隙,另類地從而更深刻而全面地瞭解它,認識它。
最後,我恭敬地引用溫家寶總理的一段話作為本書「前言」的結尾,這段話或許也可作為對本書的詮釋。
溫家寶總理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日本國會的演說中說:
「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無論是正面經驗,或是反面教訓,都是寶貴財富,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學習,會來得更直接、更深刻、更有效,這是一個民族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對自己光明前途充滿自信的表現。」
目次
前 言
第一章 綿綿瓜瓞 海外飄萍(1941—1947)
一、客家梅州
二、葵嶺楊姓
三、僑鄉梅縣
四、漂泊海外
第二章 歷史磨難 悲苦一家(1947—1953)
一、顯赫伯父
二、「立功」悲劇
三、認識土改
四、敦厚父親
五、伯父一家
第三章 六年寒窗 柳暗花明(1953—1959)
一、幸運降臨
二、進入名校
三、中學苦旅
四、感謝恩師
五、火花閃爍
第四章 人生萬幸 大學陶冶(1959—1964)
一、歷史縫隙
二、艱難入學
三、名校折騰
四、艱苦磨礪
五、師生情懷
六、瀏陽情結
七、教育實習
第五章 山鄉中學 艱苦磨煉(1964—1976)
一、天降大任
二、小鎮名校
三、「文革」劫難
四、「文革」日記
五、勤懇勞作
第六章 歷史機遇 人生轉折(1976—1985)
一、小城躁動
二、恢復高考
三、光環加身
四、牛刀小試
五、歷史玩笑
第七章 工作異動 事關海外(1985—1989)
一、海外關係
二、五味雜陳
三、為僑服務
四、香港會親
第八章 僑聯工作 事業高峰(1989—2002)
一、非常時期
二、僑聯工作
三、《僑聲》雜誌
四、「出國考察」
五、北戴河記
第九章 退而未休 筆耕不輟(2002—2010)
一、退休前後
二、同學聚會
三、寫書出書
四、《湖南客家》
五、徜徉網路
六、結緣晚報
第十章 潔本還潔 平凡依舊(2010—)
一、回鄉之旅
二、團團圓圓
三、古稀之慶
四、喬遷喜憂
五、依舊平凡
六、含飴弄孫
附錄
平淡是真 知足常樂
——專訪湖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原秘書長楊宗錚 文/劉晶瑩
書摘/試閱
梅縣的土地改革是從一九五一年四月開始的,歷時兩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結束。
伯父家土改時被劃為「官僚地主」,理由當然為伯父是「偽官僚」,但沒有考慮到我父親的華僑身分。而因為我父親帶領妻子兒女回國後住在伯父家裡,並且替伯父打理家事,以「沒有分家」為由,因此也一併享受「官僚地主」待遇。
那時,我滿了十歲。初諳人事的我,知道這叫土改,但不知道土改是怎麼回事,不理解土改怎麼會把我家「改」成這個樣子。土改給我家至少三代人留下無法解脫的傷痛。我一輩子背著「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的沉重包袱,如牛負重,但一直沒有能去探究給自己帶來苦難的土地改革究竟是怎麼回事。
二○○九年,是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中央電視臺推出了「共和國檔案」系列報導。同年八月五日,播出了「土地改革運動」專題,轉錄如下:
根據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從一九五○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黨中央明確規定了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那就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
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和頒佈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從一九五○年冬開始,有領導地分期分批地進行。每期一般經歷了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和分配土地、復查總結等階段。
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到一九五二年九月為止,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外,我國大陸普遍實行了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分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生產資料,真正實現了農民數千年來得到土地的奮鬥目標,使農業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解放。
這三段話,應該是當今對土地改革的權威解釋,我能理解。從歷史的角度講,古代無論哪個王朝初建,現代無論哪個政黨執政,總要盡力爭取最廣大民眾的支持,迅速發展生產,以鞏固政權。土地改革,是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群眾運動,其目的也是喚起民眾,以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土地改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無疑是重要的一頁。
這是大而言之,土地改革意義重大。但是,任何一次群眾運動,總或多或少會存在一些問題。據搜索到的有關數據稱,土地改革中,還是存在一些偏差甚至錯誤的。例如,階級劃分的主觀色彩,其不確定性與隨意性,就傷害到了不少人。有些工作隊和基層幹部「抽肥補瘦」、「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單純經濟觀和政績觀,使得「提高成分」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貧雇農的平均主義要求,導致「有包就鏟、有凹就平」,矮子裡面拔高,一個村子總要整出那麼一兩個地主、富農來。
伯父家其實並沒有太多的田產和房產,早十幾二十年,家境還很清貧。據村裡老者說,伯父家土改前有三十多石穀田(多少石穀,是當地計算水田面積的一種方法)。據有關資料顯示,當時一般要擁有一百石穀田以上才評為地主。而且三十多石穀田裡面還有一部分是租耕的「公嘗田」(族中公田)。這些田地,很多都是由伯母自己耕種。當年伯母年輕,犁、耙、挑、鋤,種、割、收、曬,樣樣能行,具有客家婦女勤勞能幹的本質。
據說,劃為地主的條件之一是必須有長工、婢女。伯母一人在家,陸續收養了幾個男孩女孩。她為我父親前妻所生兒子泉曾所娶的童養媳阿清姊、她領養的小女孩阿芳姊(一九五二年時十五歲)被定為「婢女」;伯母從出賣嬰兒的擔子上買下的輝曾哥被定為「長工」。
伯父長年在外,在家鄉沒有任何劣蹟,村民尤其是楊姓族人還以他為榮;伯母是地道鄉民,絕對文盲,大字不識一筐,與同姓同族相處得很好,毫無「民憤」;只不過到了土改前,伯父家在村子裡算是生活過得較為寬裕的,矮子拔高,因此劃為地主成分。
還有一個因素:姓氏矛盾。葵嶺上村有兩大姓:楊姓和鄭姓。多年來,兩姓因水利、田土、山林等問題常有糾紛甚至爭鬥。鄭姓人家華僑多,生活上整體較楊姓富裕,甚至有比伯父更闊綽的人家。但是土改時村幹部中鄭姓人多。楊姓族人認為,鄭姓人較多地掌握了主導權和話語權,鬥爭對象也就偏向楊姓。長大後同我一樣在長沙讀書、工作的一位鄭姓同鄉,也持這個看法。
另外,也不排除有個人恩怨或者誤會等因素在起作用。有村民告訴我,對我父親與伯父是否應該分別對待,曾有過激烈的爭論。據村民說,有個別村幹部因小孩玩耍時產生糾紛,造成誤會,與我家有些恩怨,主張我家與伯父家「合二而一」,都是地主。
最近幾次返鄉,與村民閒聊中聽到一些土改前後的零星故事,很是耐人尋味。
土改時,伯母領養的小女孩阿芳姊被定為婢女。一次鬥爭會上,時年十五歲的她被叫上臺批鬥伯母,她上臺後竟然號啕大哭,只好叫她下臺,下臺後她仍然哭泣不止。村裡處分沒收伯父家的財產時,她分了一畝田、一間房。不久,她出嫁了,把分到的田和屋又送回給「地主婆」伯母。「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有時似乎很難用階級鬥爭理論解釋得清楚的。
一位貧農分到幾件衣服,其中有一條褲子,乾乾淨淨,折疊得整整齊齊,他打開一看,兩個膝蓋處竟然都有破洞。他自嘲地說:「地主的爛褲子比我的乾淨。」
我家養了一條心愛的黑色狗,毛色黑亮,忠實護家,家人叫它「噢必」(印尼話「狗」的意思)。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天早晨,父親起床後發現「噢必」不見了,屋簷下有一攤血跡。然後看見菜園的籬笆被踩倒,菜地裡有一串大大的老虎腳印,腳印斷斷續續延伸到溪邊上了山。父親說「噢必」被老虎吃了。
這也許是家遭厄運的一個不祥預兆。
這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伯父遭「處決」。幾天後,伯父家和我家家產被全部沒收。
那年我十一歲。當時情景,記憶很深,後來每每想起,都覺後怕。講給後代聽,他們都難以置信。寫這本書,我也不想過多地回憶當年的慘狀,因為這樣的回憶太令人難受了。
那是完全用得著「掃地出門」四字來形容。那一天,全家人被集中在門前禾坪。家裡湧進很多人,把全部東西搬空,以致「家徒四壁」。伯父收藏的書籍被丟棄滿地。我父親情急中穿了兩條長褲,內藏了兩個戒指和幾個耳環(是與我母親結婚時他親手打製的,那時他在印尼,是一個金飾店的手工藝工人),被發現後,強行脫去一條長褲,沒收了那些戒指和耳環。
「家徒四壁」的房屋,也被宣佈沒收。我家和伯父一家,被趕到收藏柴火、養豬養牛的老舊雜屋居住。
全部家什被一群人肩挑手提帶走,母親突然歇斯底里般追上前去,跪著說:「我們哪裡睡目(睡覺)啊?」於是留下了一張床。
當晚,在破舊的充滿黴味的黑洞洞的雜屋裡,我們一家五口擠在一張無被無墊的硬板床上。剛出生不久的弟弟仁曾哭吵了一晚。
「大難臨頭各自飛」。我家與伯父家這才分開,各自謀取活路。
家無隔夜糧,我們一家老小糠菜充饑。出生不久的最小的弟弟仁曾,父母不忍眼看著他餓死,忍痛送給了鄰村一戶未曾生育的葉姓人家,換來一斗米和一袋番薯乾。
鄰里鄉親不乏同情我家者,他們常常趁著夜色把一碗飯菜或幾個番薯、芋頭端到我們「新家」對面一間破爛的廁所牆腳,打著手勢,要我們去取。我通常是喜出望外,擔當起到廁所旁取食的任務。
父母每天以擔炭(挑煤)、砍柴、割茅草到縣城去賣得到的微薄收益竭力維持全家生命。我作為長兄,雖年僅十多歲,已經跟隨父母擔炭。凌晨三四點鐘起床,到十幾里地外一個叫雞籠坑的山間,從炭山擔炭到渡口運煤船上,小小年紀的我已經能挑上五六十斤,一天要挑五六個來回。妹妹金鳳比我小兩歲,弱小的身軀挑著一擔煤,上船時跳板搖搖晃晃,嚇得她大哭。累了一天還得走回家去(有時住在當地大姨家),回到家已是晚上十點左右。後來我在中學當班主任時率領學生挑煤能挑上百把斤七八里地不歇氣回到學校,就得益於這個時期的磨煉。
我家也分了田,但田在名叫「大水坑」和「蝦子塘」的地方,兩地相距十幾里地,而且都是峽谷密林中的「冷浸田」,產量很低。沒有牛,用人力耙田犁地。我和母親在前面拉,父親在後面掌著犁耙。
……
我本人是一名共產黨員,並且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最後還擔任過省級機關的黨委書記,是一位在幾十年中雖然受盡屈辱仍然堅定信仰共產主義的「地主崽子」。我的家庭在土改中的遭遇,用「空前慘烈」來形容也不為過。時過境遷,土地改革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共產黨員的立場,對共和國歷史的認知,加上時間的消磨,已經使我心靈的創傷逐漸被撫平,心態也日趨淡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