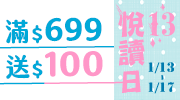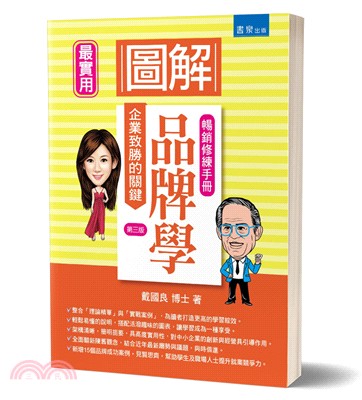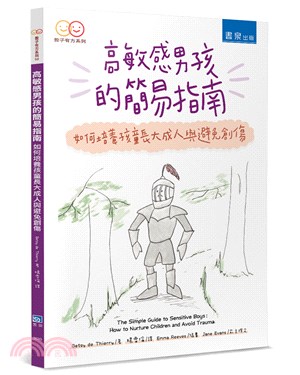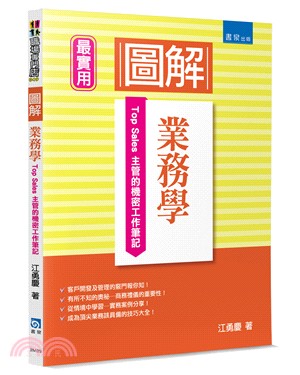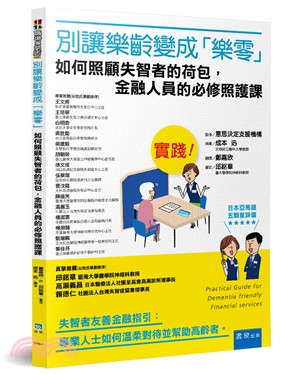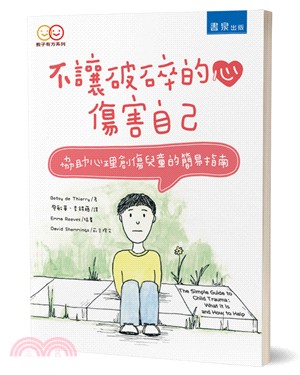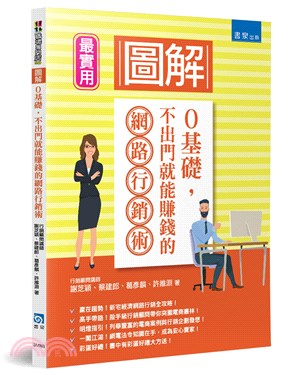梵學論集(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
ISBN13:9787516117743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作者:黃寶生
出版日:2013/01/01
裝訂/頁數:平裝/375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1
人民幣定價:72 元
定價
:NT$ 432 元優惠價
:87 折 376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梵學論集》體現了著作者在科學研究實踐中長期關注的某一專業方向或研究主題,歷時動態地展現了著作者在這一專題中不斷深化的研究路徑和學術心得,從中不難體味治學道路之銖積寸累、循序漸進、與時俱進、未有窮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學問有道夕修養理論、注重實證、堅持真理、服務社會的學者責任。
作者簡介
黃寶生,1942年7月出生,上海市人。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巴利文專業。1965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現任研究員。主要作品有專著:《印度古代文學》(1988)、《印度古典詩學》(1993)、《導讀》(2005)和《梵語文學讀本》(2010);譯著:《佛本生故事選》(合譯,1985)、《摩訶婆羅多》(合譯,2005)、《梵語詩學論著彙編》(2008)、《奧義書》(2010)和《薄伽梵歌》(2010);譯注:《梵漢對勘》(2011)、《梵漢對勘》(2011)和《梵漢對勘》(2011)。
序
代序
跋涉在梵學之路
梵語是印度古典語言,仿照“漢學”一詞,我在這里用“梵學”指稱古典印度學。印度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又與中國有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梵學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其深度和廣度也就可想而知。
我與梵語結緣,有很大的偶然性。1960年我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報到時,卻告知我已被調到了東語系。而到了東語系,又把我分配在梵文、巴利文專業。這是命運給予我的恩賜,使我得以在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教授親自執教下學習了五年。在這五年中,我們不僅學會了梵文、巴利文和英文這些語言工具,也對印度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有了深切認識。盡管我對印度古代社會、歷史、宗教和哲學的研究也懷有濃厚興趣,但我始終保持著對文學的強烈愛好。1965年學業結束,我如愿以償,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
進入研究所還不到一年,就遇上“文革”。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在“煉獄”中經受了痛苦的磨煉。因此,“文革”結束,能夠重新開始學術研究,倍感幸福。其實,在“文革”尚未正式結束之前,我們研究所在1973年就已開始非正式地恢復學術研究。馮至所長還親自寫信委托季羨林先生指導我的研究工作。殊不知當時先生尚未“解放”,我在北京大學一幢學生宿舍樓的值班室里找到了他。這次“非同尋常”的問學,先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做學問要從bibliography(目錄學)入手。”這樣,在此后幾年中,我經常查閱和瀏覽國內外學者的梵學研究成果。由此,我也養成閱讀書目的習慣,每年按照一定的經費額度,為圖書室訂購梵學圖書。經過年復一年的積累,圖書室收藏了從事梵學研究尤其是梵語文學研究的許多必備用書。
作為學術研究的準備階段,我在那幾年里讀了不少書。不僅讀梵語文學的書,也讀有關印度古代社會、歷史、宗教和哲學以及中國文史哲、西方文學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書。這是一種出于求知欲而無功利性的讀書,當時直接感受到的是知識的拓展和精神的愉悅。它的實際效用要到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才會真正顯現。因為在學術研究中,“專精”和“博通”構成辯證關系,每位學者在具體研究中都會有自己的專長,但在知識結構上必須兼顧這兩個方面。
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正軌后,我便開始撰寫和發表梵語文學研究論文。在治學方法上,我自然而然會受到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業師的影響。同時,我也自覺地向所內前輩學者學習,尤其是對錢鍾書先生的學術著作,都懷著敬仰的心情認真地讀過。打通中外文學,打通人文科學,這是我們在外國文學研究中應該努力追求的學術目標。如果說我是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先生的“受業弟子”的話,那么,我也自認是錢鍾書先生的“私淑弟子”。面對諸位先生的學術造詣,我深知自己在一生的學術道路上,必須虛心又虛心,容不得半點驕傲和自滿。
1983年至1986年期間,我參加了季羨林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印度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其中的梵語文學部分主要由我承擔,季先生只撰寫關于史詩《羅摩衍那》的一章。因為季先生當時剛剛完成這部史詩的翻譯工作,并撰有《羅摩衍那初探》一書。我聯想到季先生在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中,也是只撰寫他本人做過深入研究的一些條目。然而,按照我當時的情況,對梵語文學的概況雖有所了解,但對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深入研究才剛剛起步,發表的論文也有限。因此,嚴格地說,我還不適宜承擔《印度文學史》中梵語文學的撰寫任務。但出于工作需要,我只能邊干邊學,撰寫的主要方法是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注意吸收國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這次編寫工作,我對梵語文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一次系統深入的梳理,加固了自己的梵學根基。
1987年至1991年期間,我承擔了社科院重點項目《印度古典詩學》。在中國,向學術界介紹梵語文學理論的先驅者是金克木先生。早在1965年,他就為我們研究所編輯的《古典文學理論譯叢》選譯了一些梵語詩學名著的重要章節。而我在撰寫《印度文學史》中《梵語文學理論》一章時,真切地體會到這是一個有待開發的詩學寶庫。從那時開始,我就注意收集和訂購這方面的圖書。在資料基本齊備的基礎上,我用了兩年時間認真閱讀梵語詩學原著以及印度學者撰寫的各種梵語詩學研究著作,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并譯出許多需要引用的梵語詩學原始資料。然后,又用兩年時間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工作。這部著作依據豐富的原始資料,描述了印度古典詩學的源流、體系和結構,對它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形成的種種獨特的批評原則、概念和術語做了認真的闡釋。此書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文藝美學叢書”,出版后,受到國內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們的歡迎。
這部著作雖說有填補國內梵學研究中的學術空白的意義,但我決定從事這項研究也有現實的動因。當時國內文學理論界出現比較文學熱潮,并倡導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強調打破“歐洲文化中心論”,將廣大的東方納入比較文學視野,努力開展東西方文學比較和詩學比較。這當然是美好的學術愿望。可是,在國內,東方詩學研究一向是薄弱環節,所以,我發愿要寫一部印度古典詩學著作,為中國的比較詩學提供一些資源。
在這部著作的寫作過程中,我深深體驗到印度古典詩學雖然在表現形態上與中國和西方古典詩學迥然有別,但在文學原理上是相通的。我覺得各民族詩學中那些超越時空而相通的成分往往是文學理論的最可靠依據,代表人類文學的共同規律和基本原則,故而打通印度、中國和西方詩學,是一項富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基于這種想法,在完成《印度古典詩學》后,我準備“趁熱打鐵”,從事比較詩學研究。實際上,我也已經嘗試寫了兩篇論文:《印度古典詩學和西方現代文論》以及《禪和韻——中印詩學比較之一》。但這項研究沒有繼續下去,因為從1993年起,我接受了另一項學術任務,即主持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翻譯。
《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并稱為印度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已由季羨林先生譯出。而《摩訶婆羅多》的規模更宏大,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史詩,號稱有“十萬頌”(現代精校本約為八萬頌),篇幅為《羅摩衍那》的四倍。這項翻譯工作原本由趙國華邀請我們幾個老同學共同承擔。金克木先生為我們確定了翻譯體例,還親自翻譯了這部史詩的頭四章,為我們示范。然而,不幸的是,趙國華英年早逝,甚至沒有親眼見到于1993年先行出版的第一卷。這樣,出版社的領導找到我,希望我出面主持完成這項翻譯工作。我考慮到《摩訶婆羅多》本身的文化意義,也考慮到應該實現亡友的遺愿,便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個責任。這項工作也得到科研局的支持,于1996年列為院重點項目。
從1993年我接手主持這項工作,直至2002年完成全書的翻譯,前后花費了十年時間。在這十年中,我把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這項工作。作為項目主持人,我除了承擔較多的翻譯任務外,還負責全書譯稿的校訂和通稿工作,并為每卷譯文撰寫導言。隨著工作的展開,歲月的推移,我越來越感到這是一場“持久戰”,既是對自己學術能力的檢驗,更是對自己意志和毅力的考驗。正如我在譯后記中所說:“我有一種‘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勞累時,看到眼前已經完成的工作量,又會激發信心和力量。尤其是離最終目標越來越接近的一兩年中,我全神貫注,夜以繼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擱筆入睡后,夢中還在翻譯。在這些日子里,《摩訶婆羅多》仿佛已與我的生命合二而一,使我將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我能體驗到淡化身外之物給人帶來的精神愉悅,而這種精神愉悅又能轉化成超常的工作效率。我暗自將之稱為‘學問禪’,也就是進入了思維入定的‘三昧’境界。”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終于依靠集體的力量,完成了全書的翻譯(約四百萬字)。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也精心編輯和印制,于2005年出版,貢獻給國內學術界。
從學術上說,《摩訶婆羅多》起碼有印度學和史詩學兩方面的研究意義。在完成翻譯工作后,我完全可以接下去對這部史詩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但我決定還是回到我已放下很久的詩學課題上去,開始了中印古典詩學的比較研究。因為許多饒有興味的詩學問題始終縈繞在心,激發我的研究欲望。這項研究的預期成果分為兩部分:一是譯出幾部梵語詩學名著,二是寫出一部中印古典詩學比較研究專著。
這樣,我先翻譯梵語詩學名著,一鼓作氣譯出了《舞論》、《詩莊嚴論》、《詩鏡》、《韻光》、《詩光》和《文鏡》等十種,其中四種是選譯,六種是全譯。后來,它們結集為《梵語詩學論著匯編》(約八十萬字),作為《東方文化集成》叢書之一出版。在完成翻譯任務后,我進入中印古典詩學比較研究階段。我先對中印古典詩學的文化背景進行思考,撰寫了三篇中印古代文化傳統比較的論文:《歷史和神話》、《宗教和理性》和《語言和文學》。就在這項比較詩學研究進入正題之時,我的研究重心又身不由己地出現了轉移。
當時,有一些青年學者愿意跟隨我學梵文。我想到梵學研究資源豐富,而國內梵語人才稀缺,覺得自己也有必要擔起培養后繼人才這份責任。這樣,我于2007年夏至2009年夏開設了一個梵語研讀班。參加這個班的學員都已經具備梵語語法基礎知識,我的任務是帶領他們精讀梵語原典。因為只有真正學會閱讀梵語原典,將來才有可能獨立從事梵學各領域的研究工作。經過兩年的學習,學員們覺得收獲很大,并希望能將我們的教學成果保存下來,便于今后復習和參考,也為國內提供一部學習梵語的輔助讀物。于是,在學員們的協助下,我編了一部《梵語文學讀本》。所收篇目都是我講課用作教材的梵語文學名著。讀本內容包括梵語原文、漢語譯文和語法解析三個部分。這部讀本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而就在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接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執行這個項目。在培養人才方面,開設了一個學期為三年的梵文班。在研究方面,制定了有關梵學各領域的研究計劃。我一方面分擔梵文班教學任務,另一方面主持編輯出版《梵漢佛經對勘叢書》。梵漢佛經對勘研究不僅有助于讀解梵語佛經原典和古代漢譯佛經,也對佛教思想史、佛經翻譯史和佛教漢語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近代以來,我國前輩學者都很器重梵漢佛經對勘研究方法,只是由于國內缺少梵語人才,這方面的研究始終未能全面展開。現在,國內新的一代梵文學者正在成長起來,已有可能全面開拓這一研究領域。這樣,我近幾年的研究重點轉向了梵漢佛經對勘研究,先后完成了《入楞伽經》、《入菩提行論》和《維摩詰所說經》三部佛經的梵漢對勘,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回顧我這一生,跋涉在梵學路上,樂在其中。這部《梵學論集》中所收論文,我是按照它們發表年代的次序排列的,呈現出一路走來的足印。我一步一步行走著,我的生命也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步入了桑榆之年。但是,梵學研究對我的吸引力依然絲毫未減。我還惦記著我的中印古典詩學比較研究,希望自己能在梵漢佛經對勘研究告一段落后,再回到這個課題上來。
跋涉在梵學之路
梵語是印度古典語言,仿照“漢學”一詞,我在這里用“梵學”指稱古典印度學。印度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又與中國有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梵學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其深度和廣度也就可想而知。
我與梵語結緣,有很大的偶然性。1960年我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報到時,卻告知我已被調到了東語系。而到了東語系,又把我分配在梵文、巴利文專業。這是命運給予我的恩賜,使我得以在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教授親自執教下學習了五年。在這五年中,我們不僅學會了梵文、巴利文和英文這些語言工具,也對印度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有了深切認識。盡管我對印度古代社會、歷史、宗教和哲學的研究也懷有濃厚興趣,但我始終保持著對文學的強烈愛好。1965年學業結束,我如愿以償,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
進入研究所還不到一年,就遇上“文革”。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在“煉獄”中經受了痛苦的磨煉。因此,“文革”結束,能夠重新開始學術研究,倍感幸福。其實,在“文革”尚未正式結束之前,我們研究所在1973年就已開始非正式地恢復學術研究。馮至所長還親自寫信委托季羨林先生指導我的研究工作。殊不知當時先生尚未“解放”,我在北京大學一幢學生宿舍樓的值班室里找到了他。這次“非同尋常”的問學,先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做學問要從bibliography(目錄學)入手。”這樣,在此后幾年中,我經常查閱和瀏覽國內外學者的梵學研究成果。由此,我也養成閱讀書目的習慣,每年按照一定的經費額度,為圖書室訂購梵學圖書。經過年復一年的積累,圖書室收藏了從事梵學研究尤其是梵語文學研究的許多必備用書。
作為學術研究的準備階段,我在那幾年里讀了不少書。不僅讀梵語文學的書,也讀有關印度古代社會、歷史、宗教和哲學以及中國文史哲、西方文學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書。這是一種出于求知欲而無功利性的讀書,當時直接感受到的是知識的拓展和精神的愉悅。它的實際效用要到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才會真正顯現。因為在學術研究中,“專精”和“博通”構成辯證關系,每位學者在具體研究中都會有自己的專長,但在知識結構上必須兼顧這兩個方面。
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正軌后,我便開始撰寫和發表梵語文學研究論文。在治學方法上,我自然而然會受到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業師的影響。同時,我也自覺地向所內前輩學者學習,尤其是對錢鍾書先生的學術著作,都懷著敬仰的心情認真地讀過。打通中外文學,打通人文科學,這是我們在外國文學研究中應該努力追求的學術目標。如果說我是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先生的“受業弟子”的話,那么,我也自認是錢鍾書先生的“私淑弟子”。面對諸位先生的學術造詣,我深知自己在一生的學術道路上,必須虛心又虛心,容不得半點驕傲和自滿。
1983年至1986年期間,我參加了季羨林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印度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其中的梵語文學部分主要由我承擔,季先生只撰寫關于史詩《羅摩衍那》的一章。因為季先生當時剛剛完成這部史詩的翻譯工作,并撰有《羅摩衍那初探》一書。我聯想到季先生在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中,也是只撰寫他本人做過深入研究的一些條目。然而,按照我當時的情況,對梵語文學的概況雖有所了解,但對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深入研究才剛剛起步,發表的論文也有限。因此,嚴格地說,我還不適宜承擔《印度文學史》中梵語文學的撰寫任務。但出于工作需要,我只能邊干邊學,撰寫的主要方法是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注意吸收國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這次編寫工作,我對梵語文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一次系統深入的梳理,加固了自己的梵學根基。
1987年至1991年期間,我承擔了社科院重點項目《印度古典詩學》。在中國,向學術界介紹梵語文學理論的先驅者是金克木先生。早在1965年,他就為我們研究所編輯的《古典文學理論譯叢》選譯了一些梵語詩學名著的重要章節。而我在撰寫《印度文學史》中《梵語文學理論》一章時,真切地體會到這是一個有待開發的詩學寶庫。從那時開始,我就注意收集和訂購這方面的圖書。在資料基本齊備的基礎上,我用了兩年時間認真閱讀梵語詩學原著以及印度學者撰寫的各種梵語詩學研究著作,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并譯出許多需要引用的梵語詩學原始資料。然后,又用兩年時間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工作。這部著作依據豐富的原始資料,描述了印度古典詩學的源流、體系和結構,對它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形成的種種獨特的批評原則、概念和術語做了認真的闡釋。此書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文藝美學叢書”,出版后,受到國內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們的歡迎。
這部著作雖說有填補國內梵學研究中的學術空白的意義,但我決定從事這項研究也有現實的動因。當時國內文學理論界出現比較文學熱潮,并倡導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強調打破“歐洲文化中心論”,將廣大的東方納入比較文學視野,努力開展東西方文學比較和詩學比較。這當然是美好的學術愿望。可是,在國內,東方詩學研究一向是薄弱環節,所以,我發愿要寫一部印度古典詩學著作,為中國的比較詩學提供一些資源。
在這部著作的寫作過程中,我深深體驗到印度古典詩學雖然在表現形態上與中國和西方古典詩學迥然有別,但在文學原理上是相通的。我覺得各民族詩學中那些超越時空而相通的成分往往是文學理論的最可靠依據,代表人類文學的共同規律和基本原則,故而打通印度、中國和西方詩學,是一項富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基于這種想法,在完成《印度古典詩學》后,我準備“趁熱打鐵”,從事比較詩學研究。實際上,我也已經嘗試寫了兩篇論文:《印度古典詩學和西方現代文論》以及《禪和韻——中印詩學比較之一》。但這項研究沒有繼續下去,因為從1993年起,我接受了另一項學術任務,即主持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翻譯。
《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并稱為印度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已由季羨林先生譯出。而《摩訶婆羅多》的規模更宏大,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史詩,號稱有“十萬頌”(現代精校本約為八萬頌),篇幅為《羅摩衍那》的四倍。這項翻譯工作原本由趙國華邀請我們幾個老同學共同承擔。金克木先生為我們確定了翻譯體例,還親自翻譯了這部史詩的頭四章,為我們示范。然而,不幸的是,趙國華英年早逝,甚至沒有親眼見到于1993年先行出版的第一卷。這樣,出版社的領導找到我,希望我出面主持完成這項翻譯工作。我考慮到《摩訶婆羅多》本身的文化意義,也考慮到應該實現亡友的遺愿,便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個責任。這項工作也得到科研局的支持,于1996年列為院重點項目。
從1993年我接手主持這項工作,直至2002年完成全書的翻譯,前后花費了十年時間。在這十年中,我把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這項工作。作為項目主持人,我除了承擔較多的翻譯任務外,還負責全書譯稿的校訂和通稿工作,并為每卷譯文撰寫導言。隨著工作的展開,歲月的推移,我越來越感到這是一場“持久戰”,既是對自己學術能力的檢驗,更是對自己意志和毅力的考驗。正如我在譯后記中所說:“我有一種‘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勞累時,看到眼前已經完成的工作量,又會激發信心和力量。尤其是離最終目標越來越接近的一兩年中,我全神貫注,夜以繼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擱筆入睡后,夢中還在翻譯。在這些日子里,《摩訶婆羅多》仿佛已與我的生命合二而一,使我將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我能體驗到淡化身外之物給人帶來的精神愉悅,而這種精神愉悅又能轉化成超常的工作效率。我暗自將之稱為‘學問禪’,也就是進入了思維入定的‘三昧’境界。”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終于依靠集體的力量,完成了全書的翻譯(約四百萬字)。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也精心編輯和印制,于2005年出版,貢獻給國內學術界。
從學術上說,《摩訶婆羅多》起碼有印度學和史詩學兩方面的研究意義。在完成翻譯工作后,我完全可以接下去對這部史詩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但我決定還是回到我已放下很久的詩學課題上去,開始了中印古典詩學的比較研究。因為許多饒有興味的詩學問題始終縈繞在心,激發我的研究欲望。這項研究的預期成果分為兩部分:一是譯出幾部梵語詩學名著,二是寫出一部中印古典詩學比較研究專著。
這樣,我先翻譯梵語詩學名著,一鼓作氣譯出了《舞論》、《詩莊嚴論》、《詩鏡》、《韻光》、《詩光》和《文鏡》等十種,其中四種是選譯,六種是全譯。后來,它們結集為《梵語詩學論著匯編》(約八十萬字),作為《東方文化集成》叢書之一出版。在完成翻譯任務后,我進入中印古典詩學比較研究階段。我先對中印古典詩學的文化背景進行思考,撰寫了三篇中印古代文化傳統比較的論文:《歷史和神話》、《宗教和理性》和《語言和文學》。就在這項比較詩學研究進入正題之時,我的研究重心又身不由己地出現了轉移。
當時,有一些青年學者愿意跟隨我學梵文。我想到梵學研究資源豐富,而國內梵語人才稀缺,覺得自己也有必要擔起培養后繼人才這份責任。這樣,我于2007年夏至2009年夏開設了一個梵語研讀班。參加這個班的學員都已經具備梵語語法基礎知識,我的任務是帶領他們精讀梵語原典。因為只有真正學會閱讀梵語原典,將來才有可能獨立從事梵學各領域的研究工作。經過兩年的學習,學員們覺得收獲很大,并希望能將我們的教學成果保存下來,便于今后復習和參考,也為國內提供一部學習梵語的輔助讀物。于是,在學員們的協助下,我編了一部《梵語文學讀本》。所收篇目都是我講課用作教材的梵語文學名著。讀本內容包括梵語原文、漢語譯文和語法解析三個部分。這部讀本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而就在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接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執行這個項目。在培養人才方面,開設了一個學期為三年的梵文班。在研究方面,制定了有關梵學各領域的研究計劃。我一方面分擔梵文班教學任務,另一方面主持編輯出版《梵漢佛經對勘叢書》。梵漢佛經對勘研究不僅有助于讀解梵語佛經原典和古代漢譯佛經,也對佛教思想史、佛經翻譯史和佛教漢語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近代以來,我國前輩學者都很器重梵漢佛經對勘研究方法,只是由于國內缺少梵語人才,這方面的研究始終未能全面展開。現在,國內新的一代梵文學者正在成長起來,已有可能全面開拓這一研究領域。這樣,我近幾年的研究重點轉向了梵漢佛經對勘研究,先后完成了《入楞伽經》、《入菩提行論》和《維摩詰所說經》三部佛經的梵漢對勘,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回顧我這一生,跋涉在梵學路上,樂在其中。這部《梵學論集》中所收論文,我是按照它們發表年代的次序排列的,呈現出一路走來的足印。我一步一步行走著,我的生命也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步入了桑榆之年。但是,梵學研究對我的吸引力依然絲毫未減。我還惦記著我的中印古典詩學比較研究,希望自己能在梵漢佛經對勘研究告一段落后,再回到這個課題上來。
目次
代序論迦梨陀娑的《雲使》《本生經》淺論勝天的《牧童歌》古印度故事的框架結構印度古代神話發達的原因《管錐編》與佛經印度戲劇的起源印度古典詩學和西方現代文論梵語文學修辭例釋禪和韻——中印詩學比較之一在梵語詩學燭照下——讀馮至《十四行集》外國文學研究方法談佛經翻譯文質論書寫材料與中印文學傳統季羨林先生治學錄金克木先生的梵學成就——讀《梵竺廬集》《故事海選》譯本序《摩訶婆羅多》譯後記《摩訶婆羅多》前言神話和歷史——中印古代文化傳統比較之一宗教和理性——中印古代文化傳統比較之二語言和文學——中印古代文化傳統比較之三《梵語詩學論著彙編》導言《奧義書》導言《薄伽梵歌》導言《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梵漢對勘》導言《梵漢對勘》導言《梵漢對勘》導言
書摘/試閱
語言和文學
——中印古代文化傳統比較之三
梵語屬于印歐語系。現存《梨俱吠陀》是印歐語系中的最早文獻。漢語屬于漢藏語系。現存商周甲骨文是漢藏語系中的最早文獻。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漢字從甲骨文,經由小篆和隸書,演變成自東漢至今通用的楷書字體。而在印度的吠陀文獻中,找不到有關文字的記載。在吠陀神話中,語言被尊奉為女神,但沒有中國上古神話中蒼頡創制文字那樣的傳說。印度現存最早的、可以辨讀的文字見于吠陀時代之后,即公元三世紀的阿育王石刻銘文,使用婆羅米(Brhmī)和佉盧(Kharos?t?rī,或稱“驢唇體”)兩種字體。婆羅米字體由左往右書寫,后來演變成包括梵語天城體在內的印度各種語言的字體。佉盧字體由右往左書寫,顯然受西亞波斯字體影響,后來在印度消亡梁僧祐編撰的《出三藏記集》中提及印度古代這兩種文字:“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有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梵天創造文字的傳說出現在吠陀時代之后。。中國藏文字體約在七世紀借鑒梵語字體創制而成,八思巴蒙文字體則是借鑒藏文字體。還有,古代龜茲和焉耆吐火羅語也采用印度婆羅米字體。
通常情況下,人類上古時代的作品如果不依靠文字記錄,很難留存于世。埃及的《亡靈書》等作品書寫在紙草紙上,巴比倫的史詩《吉爾伽美什》等作品刻寫在泥版上,得以在近代考古發掘中重見天日;中國的“五經”書寫在簡帛上,得以傳承至今。而印度的四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達婆吠陀》,采用口頭方式創作印度學者達德(NSDatta)著有《〈梨俱吠陀〉作為口頭文學》(新德里,1999)一書,揭示《梨俱吠陀》作為口頭文學的特征,諸如慣用語、復沓和音步重復等。,于公元前十五世紀至公元前十世紀之間編訂成集后,不依靠文字書寫,代代相傳,歷久不變,完整地保存至今,不能不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其中的奧秘在于吠陀特殊的傳承方式。每首吠陀頌詩有五種誦讀方法:一、“本集誦讀”:按照詩律誦讀;二、“單詞誦讀”:拆開連聲,每個詞單獨發音;三、“相續誦讀”:每個詞依照ab、bc、cd、de……的次序誦讀;四、“發髻誦讀”:每個詞依照ab、ba、ab;bc、cb、bc……的次序誦讀;五、“緊密誦讀”:每個詞依照ab、ba、abc、cba、abc;bc、cb、bcd、dcb、bcd……的次序誦讀。這種傳承方式不憚繁瑣,旨在強化記憶。吠陀是婆羅門教的圣典。婆羅門祭司必須確保在宗教祭祀中吠陀頌詩的使用準確無誤。
吠陀的這種特殊傳承方式起到與文字記錄相同的作用。然而,吠陀語言保持不變,造成后人讀解的困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語言總是隨著時代變化發展的。這樣,在吠陀時代后期產生“六吠陀支”,即六種輔助吠陀的學科:禮儀學、語音學、語法學、詞源學、詩律學和天文學。其中的語音學、語法學和詞源學構成印度古代語言學。現存最早的一部詞源學著作是公元前五世紀耶斯迦的《尼錄多》。這部著作是對一部匯集《梨俱吠陀》中僻字和難字的辭書《尼犍豆》的注釋。其中也引用了十七位前賢的解釋,而他們之間的觀點常常互相牴牾。這說明在吠陀時代后期對吠陀詞語的讀解就已出現不少難點。耶斯迦在《尼錄多》中將詞分為四類:名詞、動詞、介詞和不變詞。他確立的詞源學原則是名詞源自動詞,即從所有的名詞中都能追溯出動詞詞根。《尼犍豆》和《尼錄多》相當于中國漢代的訓詁學著作《爾雅》和劉熙的《釋名》。從訓詁思想上看,《尼犍豆》以動詞為中心,而《爾雅》以名詞為中心。但《釋名》有所不同,饒宗頤先生曾指出:劉熙“利用同聲的語根以動詞解說名詞的法則”與耶斯迦的思想“暗合”饒宗頤:《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公元前四世紀,印度產生了著名的梵語語法著作《八章書》。作者是波你尼,故而這部著作又稱《波你尼經》。波你尼所處時代的語言已經不同于吠陀經典語言。這部著作便是分析和歸納當時通行語言的語法,予以規范化,為此后的古典梵語奠定基礎。《波你尼經》分為八章,總共3983個經句。它論述了梵語中的詞根、詞干、詞尾、前綴、后綴、派生詞和復合詞等語法現象,是一部完整而嚴密的梵語詞法學關于《波你尼經》的具體內容,可參閱金克木《印度文化論集》中的《梵語語法〈波你尼經〉概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但它采用口訣式的表述方式,語言高度濃縮,必須依靠老師講解,學生才能理解。這是印度古代經體著作的特點,用語力求簡略,便于記誦。因此,有位《波你尼經》注釋者說道:“語法家們覺得能省略半個音,好似生個兒子。”轉引自佩雷特(RWPerrett)編《印度哲學論集》(紐約,2001),第2卷,第187頁。公元前三世紀迦旃延那的《釋補》是對《波你尼經》的修訂補充。公元前二世紀波顛阇利的《大疏》是對《波你尼經》的疏解。《大疏》不僅是一部重要的梵語語法經典,也開創了印度后來流行的經疏文體。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第二)中將波你尼的語法著作稱為“聲明論”。據玄奘描述,波你尼接受自在天教導,“研精覃思,捃摭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中將波你尼的語法著作稱為“蘇呾啰”(即“經”字的音譯),并指出此經“是一切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千頌”。另外,慧立和彥悰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中將波你尼的語法著作稱為“聲明記論”,并記述其神話化的成書過程:“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萬頌,后至住劫,帝釋又略為十萬頌。其后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睹羅邑波膩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波你尼經》并非頌體,這里玄奘和義凈說它有一千頌,應該是轉換成頌,以折算字數。慧立和彥悰說它有八千頌,則不確。
根據中國佛教史料判斷,中國古代高僧一般都是通過《悉曇章》一類教材學習梵語的,估計未必直接研讀《波你尼經》。義凈將《悉曇章》解釋為“斯乃小學標章之稱”。這從日本入唐求法僧人的有關史料中也可以見出。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敘自己于會昌二年“五月十六日起首,于青龍寺天竺三藏寶月處,重學悉曇,親口受正音”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頁。。三善信行撰寫的《天臺宗延歷寺座主圓珍傳》中記載圓珍“于寺中遇天竺摩揭陀國大那蘭陀寺三藏般若怛羅,受學梵字《悉曇章》”。并稱“和尚(即圓珍)入唐,頻遇天竺諸三藏,習學悉曇”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歷抄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72頁。。這些表明在唐代的佛寺中,有教授“悉曇”的印度僧人。
在中國和印度,出于同樣的“解經”需求,首先出現的是詞源學或訓詁學著作。然后,隨著對語言本身加深認識,在印度出現包括語音學在內的語法學著作,以《波你尼經》為代表,而在中國出現文字學著作,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代表。其原因在于兩國的語言形態不同:梵語是屈折語,使用拼音文字;漢語是孤立語,使用表意文字。梵語的運用必須把握與詞干和詞綴變化相關的各種語法規則,諸如“界”(詞根)、“緣”(后綴)、“八囀聲”(名詞變格)、“十羅聲”(動詞變化)、“六釋”(復合詞)以及連聲、詞性(陽性、陰性和中性)和詞數(單數、雙數和復數)等。而漢語的運用與文字密切相關,正如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所說:“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許慎通曉漢字的發展演變,通過對字形結構的分析研究,總結出漢字的六種造字原則(“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許慎的《說文解字》不僅在漢代起到對漢字的統一規范作用,也為此后的漢語文字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兩漢之際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隨著譯經活動展開,梵語語音學也得到傳播。一旦認識到梵語的拼音特點,自然會促進對漢語音韻的研究。正如《隋書?經籍志》中所說:“自后漢佛法行于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這里,“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指梵語中以十四個元音與各種輔音組合成詞。而“八體六文”指漢語的八種字體和六種造字原則(即“六書”)。這樣,通過梵漢語言比較,啟發中國古人對漢語語音的辨析,促成漢語反切和四聲的發明以及等韻學的發展。
聲母、韻母和聲調是構成漢字語音的三要素。其中,聲母和韻母借鑒梵語的輔音和元音,很容易識別。而四聲發明的起源有點模糊。1934年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學報》上發表《四聲三問》,將四聲發明的起源追溯至吠陀語中的三種聲調(svara):“即指聲之高低言,英語所謂pitchaccent是也。”他認為“佛教輸入中國,其教徒轉讀經典時,此三聲之分別當亦隨之輸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頁。。此說影響很大,國內學術界曾廣泛引用。其實,陳先生的這個觀點存在缺陷,俞敏先生和饒宗頤先生已先后著文提出異議。除了佛教徒按照戒律不會采用婆羅門誦法誦經這一點之外,饒先生特別指出吠陀語和梵語不同,即吠陀語“三聲”已在梵語中消失參閱俞敏《俞敏語言學論文集》中的《后三國梵漢對音譜》,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饒宗頤《梵學集》中的《印度波儞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關于印度古代語言中的聲調或重音問題,這里可以稍作介紹。吠陀語中存在三種聲調,它們的使用涉及詞的意義。例如,indras'atru這個復合詞由“因陀羅”和“殺死”兩個詞組成。若重音在前,意思是“因陀羅殺死者”;若重音在后,意思是“殺死因陀羅者”。而在梵語中,誦讀時也有重音,但已經不涉及詞義。按照印度學者摩爾提(MSMurti)的說法:“古典語言(即梵語——引者注)廢棄音高重音法(pitchaccentuation),而轉向強調重音法(stressaccentuation)。”摩爾提(MSMurti):《梵語語言學導論》(德里,1984),第58頁。因此,梵語中的重音與吠陀語中的聲調有實質性的區別。與梵語中的重音不同,漢語中的四聲涉及詞義,但如上所述,對它們的發現也不可能是直接受到吠陀語影響。實際上,只要中國古人比照梵語,思考漢語語音問題,就必然會分辨出漢字的構成除了聲母和韻母之外,還有四聲。
這樣,印度古代語言學包含詞源學、語音學和語法學,而中國古代語言學包含訓詁學、文字學和音韻學。印度古代并無文字學,這與梵語是拼音文字有關。而梵語隨佛教輸入中國,催生了漢語音韻學,卻未促成漢語語法學的產生。這也與漢語是表意文字而無屈折變化有關。金克木先生曾以《波你尼經》和《說文解字》為例,指出“一個是以聲音為主的語詞網絡系統,一個是以形象為主的文字網絡系統”金克木:《梵佛探》,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也就是說,印度古人重語音,中國古人重文字。中國古人在“解經”實踐中,雖然也注意到漢語語法現象,并不斷予以總結,但在近代《馬氏文通》出現之前,沒有產生以語法結構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的語法學著作。
梵語屬于印歐語系,因而十九世紀歐洲學者一接觸到梵語以及《波你尼經》,無不推崇梵語,并贊嘆印度古代的語言學成就。馬克斯?繆勒(MaxMüller)說:“梵語肯定構成比較語文學惟一堅實的基礎。面對一切復雜現象,它始終是惟一可靠的向導。一位比較語文學家缺乏梵語知識,就像一位天文學家缺乏數學知識。”轉引自摩爾提(MSMurti)《梵語語言學導論》(德里,1984),第320頁。由此,歐洲學者積極借鑒梵語語言學,充實和完善歐洲語言學。直至二十世紀都是如此,如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LBloomfield)稱贊《波你尼經》“是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它極其詳細具體地描寫了作者本族言語的每一個詞的屈折變化、派生詞和合成的規則以及每一種句法的應用。直到今天,還沒有別的語言得到這樣完善的描寫”布龍菲爾德:《語言論》,袁家驊等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0頁。。
印度古人在語法學的基礎上,也對語言進行哲學思考。思考的重點是音和義的關系。波顛阇利在《大疏》中指出表達意義是詞的惟一目的。例如,一說出gauh?(“牛”)這個詞,我們的腦子里就會出現一種具有頸垂肉、角、蹄和尾的動物形象。他認為詞本身是原來存在的,恒定不變,不可分割。但它是由聲音展示的。他把這種詞本身稱作“常聲”(sphot?a)sphot?a一詞的本義是“綻開”或“展露”,意思是由“音”展示“義”。這里采用金克木先生的譯法,意譯為“常聲”。,即通過聲音展示的原本存在的詞。仍以gauh?(“牛”)為例,這個詞是原本存在的,但它是通過連續發出g、au和h?三個音素展示的。其中,任何一個單獨的音素都不能形成“牛”的詞義。而這三個音素也不可能同時發出。那只是依次發音至最后一個音素h?時,才能結合保留在印象中的前兩個音素g和au,形成“牛”的詞義。他把這種展示原本存在的詞的發音稱作“韻”(dhvani)。
波顛阇利的“常聲”論在伐致呵利(約七世紀)的《句詞論》(Vkyapadīya)中得到充分發揮。《句詞論》是一部梵語語言哲學著作,分為三章。其中的第一和第二章有作者本人的注疏。《句詞論》開宗明義指出:“無始、無終和不滅的梵,詞(‘音’)的本質,轉化為各種對象(‘義’),創造世界。”(11)伐致呵利將梵與語言的本質等同,既可說梵是語言的本質,也可說梵以語言為本質。梵是世界的本原。由此,他也將語言與世界的創造等同。伐致呵利的這一說法與《新約?約翰福音》異曲同工:“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InthebeginningwastheWorld;theWorldwaswithGod;andtheWordwasGod)
在伐致呵利看來,正如梵產生和呈現世界萬物,“常聲”(sphot?a)產生和呈現音和義。“常聲”代表語言的終極存在,原本完整而不可分割:“正如字母不分部分,詞也不分字母,同時,詞也不能與句分離。”(173)句分成詞,詞分成字母,只是為了便于理解。伐致呵利將語言的表現形式分成微妙、中介和粗糙三個層次。微妙形式是語言的絕對真實,音和義渾然一體。中介形式是微妙形式的展現,通過思想把握。粗糙形式是中介形式的進一步展現,即通過人體內的氣流運動,轉化為聲音,由發音器官說出,憑聽覺器官聽到。波顛阇利將這種發音稱為“韻”。而伐致呵利進一步區分,將“中介形式”稱為“原韻”,將“粗糙形式”稱為“變韻”。換言之,“原韻”是內在的思想展現,“變韻”是外在的聲音展現。誠如伐致呵利所說:“正如引火木上的光是另一種光的原因,思想中的詞是聞聽到的詞音的原因。思想中思考的詞在先,進入某種對象(‘意義’)在后,依靠發音(‘韻’)把握。”(146、47)在發音過程中,詞隨著詞中最后一個字母完成發音,而得到理解;同樣,句隨著句中最后一個詞完成發音,而得到理解。伐致呵利的“常聲”論讓我們聯想到索緒爾(Saussure)的“符號”論。索緒爾提出“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02頁。。據此,常聲便是符號(sign)。它呈現的音和義便是能指(即音響形象)和所指(即概念)。同時,也讓我們聯想到魏晉玄學家王弼在《老子道德經注》中對“大音希聲”的闡釋:“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據此,常聲便是大音,即不可得聞之音,也就是語言的絕對真實。一旦有聲,便分成字母和詞。這顯然是一種對語言本質的整體論認識。
伐致呵利推崇語言,將語言的本質等同于梵。他依據“梵我同一”的觀念指出:“語言是說話者的內在自我,人們稱它為偉大的如意神牛。誰通曉語言,就能達到至高靈魂(‘梵’);掌握語言活動本質,就能享有梵甘露。”(1131、132)由此,伐致呵利強調語法的重要:“語法最接近梵,是苦行中的最高苦行,吠陀的首要分支。”(111)他認為“詞與事物(‘意義’)活動的本質相連。離開語法,就無法理解詞的本質。語法展現解脫之門,在運用中治療語病,凈化一切學問。正如一切事類與詞類相連,語法這門學問是世上一切學問的根基”(113—15)。
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中介紹了伐致呵利的《句詞論》。義凈將《句詞論》(Vkyapadīya)音譯為《薄伽論》。按照義凈的描述:“《薄伽論》,頌有七百,釋有七千,亦是伐致呵利所造,敘圣教量及比量義。次有《萆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乃伐致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制。可謂窮天地之奧秘,極人理之精華矣。若人學至于此,方曰善解聲明,與九經百家相似。”對照現存的《句詞論》,義凈所說的“頌有七百”,相當于現存《句詞論》的前兩章,即第一章156頌,第二章485頌,合計641頌,接近“七百”頌。義凈所說《萆拏》實為現存《句詞論》第三章,別名Prakīrn?aka,可意譯為《雜論》。義凈譯為《萆拏》,顯然是截取詞頭Pra的音譯,如同他截取Vkyapadīya(《句詞論》)這個復合詞中的前一個詞,音譯為《薄伽論》。現存《句詞論》第三章有1323頌,與義凈所說“頌有三千”有差距。另外,義凈說這部分的注釋者是“護法論師”(Dharmapla),而現存文本的注釋者是海拉羅阇(Helrja)。
印度古代語言哲學注重音和義的關系。伐致呵利在《句詞論》中說:“大仙人們是經、注和疏的作者,認為音和義的結合是永恒的。”(123)而中國古人注重名和實的關系。《公孫龍子?名實論》中說:“夫名,實謂也。”《墨子?經說上》中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名實說和音義說有所不同。音和義是就語言內部結構而言,而名和實是就語言和外部事物而言。但也有相通之處,因為梵語中的“義”(artha)也含有對象或事物的意思。
莊子指出:“名,實之賓也。”(《莊子?逍遙游》)這里,確定了名和實的主賓關系:實為主,名為賓。這與印度古人對音義關系的看法一致。伐致呵利說:“一旦意義得到表達,作為輔助意義的表達者實現目的,就不再被人感知。”(154)也就是說,音輔助義,感知音是為了理解義。這也與莊子所謂“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相通。但莊子對名實關系的看法沒有停留在主賓關系上。在他看來,“名”并不能表達所有的“實”。他認為:“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莊子?秋水》)他將事物(“實”)分成“物之粗”、“物之精”和“不期精粗”三者,語言只能表達“物之粗”,也就是事物的“形與色”。而“物之精”只能意會。至于“不期精粗”,即“道”,既不能言說,也不能意會。這也就是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莊哲學思想中的“道”,與印度奧義書哲學中的“梵”相通,都是指稱世界的本原。莊子認為:“道不可聞,聞而非道也;道不可見,見而非道也;道不可言,言而非道也。”(《莊子?知北游》)同樣,奧義書哲學認為梵“不能用語言、思想和眼睛得知,除了說它存在之外,還能怎么得知?”(《伽陀奧義書》2312)或者說,梵“不可目睹,不可言說,不可執取,無特征,不可思議,不可名狀,以確信惟一自我為本質,滅寂戲論,平靜,吉祥,不二”(《蛙氏奧義書》7)。
印度大乘佛教也強調語言不能表達佛法:“般若波羅蜜不可說,禪那波羅蜜乃至一切法,若有為,若無為,若聲聞法,若辟支佛法,若菩薩法,若佛法,亦不可說。”(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方便品》)但為了教化眾生,又不得不說,于是,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觀派認為萬物因緣和合而成,并無“自性”,實質為“空”。龍樹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鳩摩羅什譯《中論》卷四)也就是說,因緣和合而成的萬物實質為“空”(s'ūnyat),因而關于它們的稱謂或言說只是“假名”(prajapti)。這里,既確認“空”,也確認“假名”,不偏執一端,故而是“中道”。因緣和合的萬物(“假名”)和實質(“空”)也可稱為“俗諦”和“真諦”。“真諦”本不可說,又不得不說,則借助“俗諦”。或通過“因緣、譬喻言辭”,或通過“遮詮”表達方式。“遮詮”(apoha)指否定式表述。如龍樹對“空”的表述:“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鳩摩羅什譯《中論》卷一)這與奧義書哲學中對“梵”的否定式表述(netineti)一脈相承。如《大森林奧義書》將不滅者(“梵”)表述為“不粗,不細,不短,不長,不紅,不濕,無影,無暗,無風,無空間,無接觸,無味,無香,無眼,無耳,無語,無思想,無光熱,無氣息,無嘴,無量,無內,無外”(388)。同樣,在老莊哲學中,“道”不可說,又不得不說,則借助“卮言”、“重言”和“寓言”(《莊子?天下》)。理解了印度奧義書哲學和大乘佛教以及中國老莊哲學的語言思想,對中國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及其說禪方式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中國古人對語言哲學的思考中,除了名和實、道和名(言)的關系之外,還有意、言和書的關系。《周易?系辭上傳》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莊子則說:“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莊子?天道》)這些論述中體現的意、言和書的等級次序,類似德里達所謂“邏各斯中心主義”中的“內在思想、口頭語言、書面文字之間的等級關系”參閱張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頁。。西方傳統認為“邏各斯”(logos)兼有“理性”(ratio)和“言說”(oratio)兩義。因此,“邏各斯中心主義”也可稱為“語音中心主義”。這樣,就“邏各斯”表示理性、思想或意義而言,接近中國古代語言哲學中的“意”,而就“邏各斯”表示語音或音和義的統一而言,接近印度古代語言哲學中的“常聲”(sphot?a)。然而,印度古人對語言的思考集中在音和義的關系,并不涉及書面文字。這不足為奇,因為輕視書寫是印度古代文化本身固有的特點。
雖然中國古代語言哲學涉及意、言和書的關系,但更多的思考還是集中在意和言的關系。意和言的關系不同于道和名(言)或梵和言。意和言的關系是能不能盡意和怎樣盡意,而道或梵已預設為不可言。中國儒家的主要傾向還是認為言可盡意。孔子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又說:“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周易?系辭上傳》)這里的“象”不僅指卦爻,也含有“形象”、“意象”和“象征”之意。由此,將意和言的關系擴充為意、象和言的關系。歐陽建則在《言盡意論》(《全晉文》卷一百九)中強調“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矣。茍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這里將言意不二比作“聲發響應”,類似印度的“常聲”說。無論是“言不盡意”論、“言盡意”論、“意象言”論或道家的“道不可言”論都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在中國古代詩學中得到運用,重視“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文心雕龍?隱秀》),充分激發語言潛藏的表現能力。而在印度古代詩學中,“常聲”論和“梵不可言”論也起到同樣的作用。梵語詩學家歡增就在《韻光》中將語法家稱為學問家中的“先驅”,指出:“他們把韻用在聽到的音素上。其他學者在闡明詩的本質時,遵循他們的思想,依據共同的暗示性,把表示義和表示者混合的詞的靈魂,即通常所謂的詩,也稱作韻。”(113注疏)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可以分成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文學也可以分成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書面文學的語言不同于口頭語言,這一點不言而喻。而口頭文學既然成為文學,其語言也不完全等同于口頭語言。郭紹虞先生曾將中國文學分成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以此歸納中國文學的演變:春秋以前為詩樂時代,戰國至漢為辭賦時代,魏晉南北朝為駢文時代,隋唐至北宋為古文時代,南宋至現代為語體時代。其中,“詩樂”是語言型文學,即接近口語的文學;“辭賦”是文字型文學,即脫離口語的文學;“駢文”是典型的文字型文學;“古文”和“語體”又回歸語言型文學參閱郭紹虞《中國語言與文字之分歧在文學史上的演變現象》,《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郭先生的這個歸納很有見地,揭示了中國文學語言演變的基本脈絡。在概念上,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與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有相通之處,但也不盡相同。口頭文學主要指依靠口頭創作和傳播的文學,書面文學主要指依靠文字創作和傳播的文學。從文學接受的角度看,前者主要是說和聽的關系,后者主要是寫和看的關系。而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的區別主要著眼于文學語言與口語的距離遠近。
印度古代的吠陀、史詩和往世書都屬于口頭文學。大約從公元前后不久開始,印度進入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吠陀使用的古梵語(或稱吠陀語),史詩和往世書使用的史詩梵語,都是與當時的口語接近的梵語。而古典梵語文學使用的古典梵語則是注重藻飾的梵語。印度古代現存最早的古典梵語詩學著作《詩莊嚴論》和《詩鏡》都是著重探討文學語言的修辭手法。古典梵語詩學家將那些裝飾語言的音和義的修辭手法視為文學語言不同于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的標志。當然,這并不是說吠陀、史詩和往世書中沒有修辭,只是相對地說,這些口頭文學中的修辭都比較質樸,而古典梵語文學中的修辭更趨精致。在七世紀的《詩莊嚴論》中論述的辭格為三十九種,此后不斷充實和發展,達到一百多種。追求藻飾是古典梵語文學的普遍特點。而其中的極端者,則以雕琢繁縟的文體和艱難奇巧的修辭為詩才,甚至近乎文字游戲。這樣的文學作品自然不能再像吠陀和史詩那樣依靠口頭創作和傳播,而必須依賴文字和書寫。因而,在王頂(九、十世紀)的詩學著作《詩探》中,在第十章論述“詩人的行為”時,提到“詩人的身邊經常有箱篋,有的裝有木片和白堊,有的裝有筆、墨水壺、棕櫚樹葉、樺樹皮、鐵針和多羅樹葉”。這些都是書寫的工具和材料,其中的“棕櫚樹葉”和“多羅樹葉”就是漢譯佛經中所稱的“貝葉”。
盡管如此,在古典梵語文學時期,依然存在口頭文學。兩大史詩的最后定型是在公元四、五世紀,各種往世書的最后定型則更晚。同時,許多故事文學作品也使用與口語接近的梵語。而且,在古代印度,除了梵語文學作品外,始終存在各種俗語文學作品。例如,于公元前三世紀結集的佛教經典《三藏》(Tipit?aka)使用的是巴利語(Pli),于公元五、六世紀結集的耆那教經典《阿笈摩》(gama)使用的是半摩揭陀語(Ardhamgadhī)。在古典梵語文學時期,佛教由小乘演變為大乘,佛教高僧們開始使用梵語撰寫佛經。出于口頭宣教的需要,大乘佛經使用的梵語大多也是接近口語的通俗梵語,但也有一些佛經效仿古典梵語“大詩”文體,注重文采和修辭。以各地方言為基礎的重要俗語還有摩訶剌陀語、修羅塞納語、摩揭陀語、畢舍遮語和阿波布朗舍語等。這些俗語后來發展成印度現代各種語言,如印地語、孟加拉語和旁遮普語等。而作為印度古代社會(尤其是上層社會)的通用語梵語,卻于十二世紀開始逐漸消亡。
印度古代語言的這種變化發展與拼音文字有關。拼音文字與語言的關系是文字依附語言,文字拼寫隨語言而變化。印度古代各地的方言隨著時間推移,在詞匯和語法上與通用語梵語的差異越來越大,最終拼寫出來,成了各自獨立的語言。而中國的漢語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漢字是表意文字。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推行“書同文”的語言政策。這樣,文字始終對語言起著管轄作用。各地方言可以有語音差別,但相對應的文字依然是統一的。語言作品中也可以或多或少攙雜方言,借用同音的漢字表達。然而,它們聽從歷史的選擇,或融入通用語,或被淘汰。在固定化的表意文字的統領下,各地方言不會發展成獨立的語言。因此,漢語沒有像使用拼音文字的梵語和拉丁語那樣在歷史發展中消亡,而成為世界語言之林中的常青樹。
在漢語中,還有文言和白話的區分,由此也形成文言文學和白話文學的區分。它們與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以及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也是在概念上既相通,又有差異。另外,白話文學也可稱為俗文學,但俗文學卻不能徑稱白話文學,因為在古代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和戲曲也可用文言創作。這類術語的多樣化體現不同的視角或立足點,也反映文學與語言關系本身的復雜性。
文言文是隨著戰國時期開始盛行書面文化而逐漸成型的。當時尚未發明造紙術,受書寫材料制約,簡牘嫌重,縑帛嫌貴,故而文言文的文體特點必定趨于簡約。在簡約的前提下,追求“辭達”、“辭巧”和“文質彬彬”。這樣,文言文逐漸形成有別于口語的詞匯和句法系統,并在使用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同時,文言文也適應實用需要,依據不同的內容和表達方式形成不同的文體和風格。如曹丕《典論?論文》中所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而劉勰《文心雕龍》中論述的文言文體達幾十種之多。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在文學觀念上有兩個重大發展:一是在“詩言志”的基礎上提出“詩緣情”;二是追求語言的藝術美,重視駢偶、聲律和藻飾。按陸機《文賦》中的說法,就是“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以“四聲八病”說為核心的永明聲律論揭示了漢詩音韻美的奧秘,奠定了漢詩格律的理論基礎。同時,在散文中也注重辭藻和聲韻,尤其鐘情駢偶,形成句式工整對稱(“駢四儷六”)的駢文。可以說,駢文代表中國古代散文語言藝術達到極致的文體形式。
而魏晉南北朝恰恰也是佛經翻譯昌盛的時期,故而在佛經翻譯活動中,關于佛經翻譯文體的文和質的討論貫穿始終。中國佛教高僧熟習簡約典雅的文言文體,這從他們為一些漢譯佛經撰寫的序文便可見出。乍一面對漢譯佛經質樸繁瑣的文體,自然會感到不適應,甚至心生疑惑。但隨著佛經翻譯實踐的深入,漸漸認識到漢譯佛經的這種文體符合佛經原典的本來面目。通過梵漢經籍文體的比較,得出“胡經尚質,秦人好文”(道安《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和“胡文委曲”,“秦人好簡”(僧睿《大智釋論序》)的結論。這并不難理解,因為佛經文體根植于口耳相傳的宣教方式,用語趨向通俗質樸,敘事說理也不憚繁瑣復沓。有了這樣的認識,他們也就不再忌諱使用白話或接近白話的文體翻譯佛經。有趣的是,他們還特別挑出儒家經典中文體接近口語的《尚書》和《詩經》為佛經文體撐腰:“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書》為質樸,而刪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道安《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這樣,在魏晉南北朝,一方面是駢文引領文言文體,另一方面是漢譯佛經推動白話文體,兩者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只有散見于典籍中的一些謠諺以及《詩經》和漢樂府中那些采自民間的歌謠,可以稱為白話或接近白話的文學。而此后,由佛經翻譯文體推波助瀾,白話文學與文言文學并駕齊驅,日益壯大。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唐代變文促進了中國古代通俗敘事文學的長足發展。變文采用韻散雜糅的白話文體,最初用于演說印度佛經故事,后來也用于演說中國歷史故事。韻散雜糅原本就是佛經的常用文體。在印度古典梵語敘事文學中,也有這類文體,稱為“占布”(Campu)。唐代變文后來演變成宋元話本(即白話小說)。宋元話本又演變成明清章回體白話長篇小說。
唐宋敘事文學的發展也為戲劇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中國古代戲劇誕生于宋元時期,明顯晚于希臘和印度。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國早期敘事文學不發達肯定是原因之一。古代希臘和印度的戲劇都產生在史詩之后,而且最初的戲劇題材大多取材于史詩中的故事和傳說。這說明有了以虛構為特征的敘事文學作為基礎,轉換成戲劇表演也就指日可待了。在中國古代,“傳奇”一詞既是唐宋小說的用名,也是元雜劇和明清戲曲的用名,也能印證這個道理。實際上,在元末明初的戲劇史料中,就有將傳奇視為戲曲源頭的說法。如夏庭芝說:“唐時有傳奇,皆文人所編,猶野史也,但資諧笑耳。宋之戲文,乃有唱念,有諢。”(《青樓集志》)陶宗儀說:“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南村輟耕錄》)
同時,從魏晉南北朝起,受漢譯佛經中偈頌的影響,佛教僧人也用白話寫詩。其中著名的詩人有南北朝的寶志和傅大士,唐代的王梵志、寒山、拾得和龐居士等,形成中國古代別開生面的佛教白話詩派。自然,他們也意識到白話詩不符合士大夫文人的詩藝標準。但他們仰仗有群眾基礎,充滿自信,認為自己的白話詩與文言詩享有同等地位。拾得在詩中表白說:“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全唐詩》卷八百七)寒山也說:“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全唐詩》卷八百六)另外,在唐代民間流行的詞曲或曲子詞,即配合樂曲歌唱的歌詞,是以長短句為特征的唐宋詞的先導。在這些詞曲中,也包含佛教詞曲。可以說,在唐代的白話文學運動中,佛教僧人始終是一支生力軍。
唐代變文還有一個更直接、更重要的演變發展方向是民間說唱文學。元明時民間流行的寶卷與變文一脈相承,說唱的內容可以分成佛經類和非佛經類,而以佛經類居多。元明時另一類說唱文學統稱為詞話,但留存于世的作品很少。因而,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一批明成化年間的詞話,顯得格外珍貴這批詞話于1973年由上海博物館影印出版。另有朱一玄校點本《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這批詞話共有十三種,其中講史類三種,公案類八種,神怪類兩種,說明說唱的內容已以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為主。另外,每種詞話都配有若干幅圖畫,說明還傳承著變文配圖說唱的原始精神。這類詞話的直接繼承者則是明清的長篇說唱文學鼓詞和彈詞。其中鼓詞流行于北方,彈詞流行于南方。
陳寅恪先生晚年目盲,曾依靠助手,聽讀彈詞《再生緣》,撰寫了《論再生緣》。《再生緣》出自清代女作家陳端生的手筆,字數達六十多萬。陳寅恪先生在文中稱《再生緣》“乃一敘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制也”。又說:“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而不知吾國也有此體。外國史詩中宗教哲學之思想,其精深博大,雖遠勝于吾國彈詞之所言,然止就文體立論,實未有差異。”參閱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陳先生的這一提示很有意義,也可以說是為比較文學點題。中國上古時代(先秦)沒有產生史詩一類長篇口頭敘事文學。而進入中古時代(唐宋),口頭說唱文學日趨發達,至近古時代(明清)達到鼎盛,涌現大量長篇說唱敘事文學。單就彈詞而言,“考諸各家書目所載,以及圖書館和私家藏書,估計至少有四百種”譚正璧、譚尋編著:《彈詞敘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其中,篇幅達數十萬字者不在少數,還有超過百萬字者。如《玉釧緣》一百二十萬字,《鳳雙飛》一百七十萬字,都超過約百萬字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而最長的一部彈詞是清代女作家李桂玉創作的《榴花夢》,近五百萬字,遠遠超過約四百萬字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令人驚嘆。這個有趣的文學現象,確實值得另外單獨列為專題,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中印古代文化傳統比較之三
梵語屬于印歐語系。現存《梨俱吠陀》是印歐語系中的最早文獻。漢語屬于漢藏語系。現存商周甲骨文是漢藏語系中的最早文獻。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漢字從甲骨文,經由小篆和隸書,演變成自東漢至今通用的楷書字體。而在印度的吠陀文獻中,找不到有關文字的記載。在吠陀神話中,語言被尊奉為女神,但沒有中國上古神話中蒼頡創制文字那樣的傳說。印度現存最早的、可以辨讀的文字見于吠陀時代之后,即公元三世紀的阿育王石刻銘文,使用婆羅米(Brhmī)和佉盧(Kharos?t?rī,或稱“驢唇體”)兩種字體。婆羅米字體由左往右書寫,后來演變成包括梵語天城體在內的印度各種語言的字體。佉盧字體由右往左書寫,顯然受西亞波斯字體影響,后來在印度消亡梁僧祐編撰的《出三藏記集》中提及印度古代這兩種文字:“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有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梵天創造文字的傳說出現在吠陀時代之后。。中國藏文字體約在七世紀借鑒梵語字體創制而成,八思巴蒙文字體則是借鑒藏文字體。還有,古代龜茲和焉耆吐火羅語也采用印度婆羅米字體。
通常情況下,人類上古時代的作品如果不依靠文字記錄,很難留存于世。埃及的《亡靈書》等作品書寫在紙草紙上,巴比倫的史詩《吉爾伽美什》等作品刻寫在泥版上,得以在近代考古發掘中重見天日;中國的“五經”書寫在簡帛上,得以傳承至今。而印度的四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達婆吠陀》,采用口頭方式創作印度學者達德(NSDatta)著有《〈梨俱吠陀〉作為口頭文學》(新德里,1999)一書,揭示《梨俱吠陀》作為口頭文學的特征,諸如慣用語、復沓和音步重復等。,于公元前十五世紀至公元前十世紀之間編訂成集后,不依靠文字書寫,代代相傳,歷久不變,完整地保存至今,不能不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其中的奧秘在于吠陀特殊的傳承方式。每首吠陀頌詩有五種誦讀方法:一、“本集誦讀”:按照詩律誦讀;二、“單詞誦讀”:拆開連聲,每個詞單獨發音;三、“相續誦讀”:每個詞依照ab、bc、cd、de……的次序誦讀;四、“發髻誦讀”:每個詞依照ab、ba、ab;bc、cb、bc……的次序誦讀;五、“緊密誦讀”:每個詞依照ab、ba、abc、cba、abc;bc、cb、bcd、dcb、bcd……的次序誦讀。這種傳承方式不憚繁瑣,旨在強化記憶。吠陀是婆羅門教的圣典。婆羅門祭司必須確保在宗教祭祀中吠陀頌詩的使用準確無誤。
吠陀的這種特殊傳承方式起到與文字記錄相同的作用。然而,吠陀語言保持不變,造成后人讀解的困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語言總是隨著時代變化發展的。這樣,在吠陀時代后期產生“六吠陀支”,即六種輔助吠陀的學科:禮儀學、語音學、語法學、詞源學、詩律學和天文學。其中的語音學、語法學和詞源學構成印度古代語言學。現存最早的一部詞源學著作是公元前五世紀耶斯迦的《尼錄多》。這部著作是對一部匯集《梨俱吠陀》中僻字和難字的辭書《尼犍豆》的注釋。其中也引用了十七位前賢的解釋,而他們之間的觀點常常互相牴牾。這說明在吠陀時代后期對吠陀詞語的讀解就已出現不少難點。耶斯迦在《尼錄多》中將詞分為四類:名詞、動詞、介詞和不變詞。他確立的詞源學原則是名詞源自動詞,即從所有的名詞中都能追溯出動詞詞根。《尼犍豆》和《尼錄多》相當于中國漢代的訓詁學著作《爾雅》和劉熙的《釋名》。從訓詁思想上看,《尼犍豆》以動詞為中心,而《爾雅》以名詞為中心。但《釋名》有所不同,饒宗頤先生曾指出:劉熙“利用同聲的語根以動詞解說名詞的法則”與耶斯迦的思想“暗合”饒宗頤:《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公元前四世紀,印度產生了著名的梵語語法著作《八章書》。作者是波你尼,故而這部著作又稱《波你尼經》。波你尼所處時代的語言已經不同于吠陀經典語言。這部著作便是分析和歸納當時通行語言的語法,予以規范化,為此后的古典梵語奠定基礎。《波你尼經》分為八章,總共3983個經句。它論述了梵語中的詞根、詞干、詞尾、前綴、后綴、派生詞和復合詞等語法現象,是一部完整而嚴密的梵語詞法學關于《波你尼經》的具體內容,可參閱金克木《印度文化論集》中的《梵語語法〈波你尼經〉概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但它采用口訣式的表述方式,語言高度濃縮,必須依靠老師講解,學生才能理解。這是印度古代經體著作的特點,用語力求簡略,便于記誦。因此,有位《波你尼經》注釋者說道:“語法家們覺得能省略半個音,好似生個兒子。”轉引自佩雷特(RWPerrett)編《印度哲學論集》(紐約,2001),第2卷,第187頁。公元前三世紀迦旃延那的《釋補》是對《波你尼經》的修訂補充。公元前二世紀波顛阇利的《大疏》是對《波你尼經》的疏解。《大疏》不僅是一部重要的梵語語法經典,也開創了印度后來流行的經疏文體。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第二)中將波你尼的語法著作稱為“聲明論”。據玄奘描述,波你尼接受自在天教導,“研精覃思,捃摭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中將波你尼的語法著作稱為“蘇呾啰”(即“經”字的音譯),并指出此經“是一切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千頌”。另外,慧立和彥悰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中將波你尼的語法著作稱為“聲明記論”,并記述其神話化的成書過程:“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萬頌,后至住劫,帝釋又略為十萬頌。其后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睹羅邑波膩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波你尼經》并非頌體,這里玄奘和義凈說它有一千頌,應該是轉換成頌,以折算字數。慧立和彥悰說它有八千頌,則不確。
根據中國佛教史料判斷,中國古代高僧一般都是通過《悉曇章》一類教材學習梵語的,估計未必直接研讀《波你尼經》。義凈將《悉曇章》解釋為“斯乃小學標章之稱”。這從日本入唐求法僧人的有關史料中也可以見出。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敘自己于會昌二年“五月十六日起首,于青龍寺天竺三藏寶月處,重學悉曇,親口受正音”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頁。。三善信行撰寫的《天臺宗延歷寺座主圓珍傳》中記載圓珍“于寺中遇天竺摩揭陀國大那蘭陀寺三藏般若怛羅,受學梵字《悉曇章》”。并稱“和尚(即圓珍)入唐,頻遇天竺諸三藏,習學悉曇”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歷抄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72頁。。這些表明在唐代的佛寺中,有教授“悉曇”的印度僧人。
在中國和印度,出于同樣的“解經”需求,首先出現的是詞源學或訓詁學著作。然后,隨著對語言本身加深認識,在印度出現包括語音學在內的語法學著作,以《波你尼經》為代表,而在中國出現文字學著作,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代表。其原因在于兩國的語言形態不同:梵語是屈折語,使用拼音文字;漢語是孤立語,使用表意文字。梵語的運用必須把握與詞干和詞綴變化相關的各種語法規則,諸如“界”(詞根)、“緣”(后綴)、“八囀聲”(名詞變格)、“十羅聲”(動詞變化)、“六釋”(復合詞)以及連聲、詞性(陽性、陰性和中性)和詞數(單數、雙數和復數)等。而漢語的運用與文字密切相關,正如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所說:“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許慎通曉漢字的發展演變,通過對字形結構的分析研究,總結出漢字的六種造字原則(“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許慎的《說文解字》不僅在漢代起到對漢字的統一規范作用,也為此后的漢語文字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兩漢之際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隨著譯經活動展開,梵語語音學也得到傳播。一旦認識到梵語的拼音特點,自然會促進對漢語音韻的研究。正如《隋書?經籍志》中所說:“自后漢佛法行于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這里,“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指梵語中以十四個元音與各種輔音組合成詞。而“八體六文”指漢語的八種字體和六種造字原則(即“六書”)。這樣,通過梵漢語言比較,啟發中國古人對漢語語音的辨析,促成漢語反切和四聲的發明以及等韻學的發展。
聲母、韻母和聲調是構成漢字語音的三要素。其中,聲母和韻母借鑒梵語的輔音和元音,很容易識別。而四聲發明的起源有點模糊。1934年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學報》上發表《四聲三問》,將四聲發明的起源追溯至吠陀語中的三種聲調(svara):“即指聲之高低言,英語所謂pitchaccent是也。”他認為“佛教輸入中國,其教徒轉讀經典時,此三聲之分別當亦隨之輸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頁。。此說影響很大,國內學術界曾廣泛引用。其實,陳先生的這個觀點存在缺陷,俞敏先生和饒宗頤先生已先后著文提出異議。除了佛教徒按照戒律不會采用婆羅門誦法誦經這一點之外,饒先生特別指出吠陀語和梵語不同,即吠陀語“三聲”已在梵語中消失參閱俞敏《俞敏語言學論文集》中的《后三國梵漢對音譜》,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饒宗頤《梵學集》中的《印度波儞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關于印度古代語言中的聲調或重音問題,這里可以稍作介紹。吠陀語中存在三種聲調,它們的使用涉及詞的意義。例如,indras'atru這個復合詞由“因陀羅”和“殺死”兩個詞組成。若重音在前,意思是“因陀羅殺死者”;若重音在后,意思是“殺死因陀羅者”。而在梵語中,誦讀時也有重音,但已經不涉及詞義。按照印度學者摩爾提(MSMurti)的說法:“古典語言(即梵語——引者注)廢棄音高重音法(pitchaccentuation),而轉向強調重音法(stressaccentuation)。”摩爾提(MSMurti):《梵語語言學導論》(德里,1984),第58頁。因此,梵語中的重音與吠陀語中的聲調有實質性的區別。與梵語中的重音不同,漢語中的四聲涉及詞義,但如上所述,對它們的發現也不可能是直接受到吠陀語影響。實際上,只要中國古人比照梵語,思考漢語語音問題,就必然會分辨出漢字的構成除了聲母和韻母之外,還有四聲。
這樣,印度古代語言學包含詞源學、語音學和語法學,而中國古代語言學包含訓詁學、文字學和音韻學。印度古代并無文字學,這與梵語是拼音文字有關。而梵語隨佛教輸入中國,催生了漢語音韻學,卻未促成漢語語法學的產生。這也與漢語是表意文字而無屈折變化有關。金克木先生曾以《波你尼經》和《說文解字》為例,指出“一個是以聲音為主的語詞網絡系統,一個是以形象為主的文字網絡系統”金克木:《梵佛探》,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也就是說,印度古人重語音,中國古人重文字。中國古人在“解經”實踐中,雖然也注意到漢語語法現象,并不斷予以總結,但在近代《馬氏文通》出現之前,沒有產生以語法結構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的語法學著作。
梵語屬于印歐語系,因而十九世紀歐洲學者一接觸到梵語以及《波你尼經》,無不推崇梵語,并贊嘆印度古代的語言學成就。馬克斯?繆勒(MaxMüller)說:“梵語肯定構成比較語文學惟一堅實的基礎。面對一切復雜現象,它始終是惟一可靠的向導。一位比較語文學家缺乏梵語知識,就像一位天文學家缺乏數學知識。”轉引自摩爾提(MSMurti)《梵語語言學導論》(德里,1984),第320頁。由此,歐洲學者積極借鑒梵語語言學,充實和完善歐洲語言學。直至二十世紀都是如此,如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LBloomfield)稱贊《波你尼經》“是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它極其詳細具體地描寫了作者本族言語的每一個詞的屈折變化、派生詞和合成的規則以及每一種句法的應用。直到今天,還沒有別的語言得到這樣完善的描寫”布龍菲爾德:《語言論》,袁家驊等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0頁。。
印度古人在語法學的基礎上,也對語言進行哲學思考。思考的重點是音和義的關系。波顛阇利在《大疏》中指出表達意義是詞的惟一目的。例如,一說出gauh?(“牛”)這個詞,我們的腦子里就會出現一種具有頸垂肉、角、蹄和尾的動物形象。他認為詞本身是原來存在的,恒定不變,不可分割。但它是由聲音展示的。他把這種詞本身稱作“常聲”(sphot?a)sphot?a一詞的本義是“綻開”或“展露”,意思是由“音”展示“義”。這里采用金克木先生的譯法,意譯為“常聲”。,即通過聲音展示的原本存在的詞。仍以gauh?(“牛”)為例,這個詞是原本存在的,但它是通過連續發出g、au和h?三個音素展示的。其中,任何一個單獨的音素都不能形成“牛”的詞義。而這三個音素也不可能同時發出。那只是依次發音至最后一個音素h?時,才能結合保留在印象中的前兩個音素g和au,形成“牛”的詞義。他把這種展示原本存在的詞的發音稱作“韻”(dhvani)。
波顛阇利的“常聲”論在伐致呵利(約七世紀)的《句詞論》(Vkyapadīya)中得到充分發揮。《句詞論》是一部梵語語言哲學著作,分為三章。其中的第一和第二章有作者本人的注疏。《句詞論》開宗明義指出:“無始、無終和不滅的梵,詞(‘音’)的本質,轉化為各種對象(‘義’),創造世界。”(11)伐致呵利將梵與語言的本質等同,既可說梵是語言的本質,也可說梵以語言為本質。梵是世界的本原。由此,他也將語言與世界的創造等同。伐致呵利的這一說法與《新約?約翰福音》異曲同工:“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InthebeginningwastheWorld;theWorldwaswithGod;andtheWordwasGod)
在伐致呵利看來,正如梵產生和呈現世界萬物,“常聲”(sphot?a)產生和呈現音和義。“常聲”代表語言的終極存在,原本完整而不可分割:“正如字母不分部分,詞也不分字母,同時,詞也不能與句分離。”(173)句分成詞,詞分成字母,只是為了便于理解。伐致呵利將語言的表現形式分成微妙、中介和粗糙三個層次。微妙形式是語言的絕對真實,音和義渾然一體。中介形式是微妙形式的展現,通過思想把握。粗糙形式是中介形式的進一步展現,即通過人體內的氣流運動,轉化為聲音,由發音器官說出,憑聽覺器官聽到。波顛阇利將這種發音稱為“韻”。而伐致呵利進一步區分,將“中介形式”稱為“原韻”,將“粗糙形式”稱為“變韻”。換言之,“原韻”是內在的思想展現,“變韻”是外在的聲音展現。誠如伐致呵利所說:“正如引火木上的光是另一種光的原因,思想中的詞是聞聽到的詞音的原因。思想中思考的詞在先,進入某種對象(‘意義’)在后,依靠發音(‘韻’)把握。”(146、47)在發音過程中,詞隨著詞中最后一個字母完成發音,而得到理解;同樣,句隨著句中最后一個詞完成發音,而得到理解。伐致呵利的“常聲”論讓我們聯想到索緒爾(Saussure)的“符號”論。索緒爾提出“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02頁。。據此,常聲便是符號(sign)。它呈現的音和義便是能指(即音響形象)和所指(即概念)。同時,也讓我們聯想到魏晉玄學家王弼在《老子道德經注》中對“大音希聲”的闡釋:“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據此,常聲便是大音,即不可得聞之音,也就是語言的絕對真實。一旦有聲,便分成字母和詞。這顯然是一種對語言本質的整體論認識。
伐致呵利推崇語言,將語言的本質等同于梵。他依據“梵我同一”的觀念指出:“語言是說話者的內在自我,人們稱它為偉大的如意神牛。誰通曉語言,就能達到至高靈魂(‘梵’);掌握語言活動本質,就能享有梵甘露。”(1131、132)由此,伐致呵利強調語法的重要:“語法最接近梵,是苦行中的最高苦行,吠陀的首要分支。”(111)他認為“詞與事物(‘意義’)活動的本質相連。離開語法,就無法理解詞的本質。語法展現解脫之門,在運用中治療語病,凈化一切學問。正如一切事類與詞類相連,語法這門學問是世上一切學問的根基”(113—15)。
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中介紹了伐致呵利的《句詞論》。義凈將《句詞論》(Vkyapadīya)音譯為《薄伽論》。按照義凈的描述:“《薄伽論》,頌有七百,釋有七千,亦是伐致呵利所造,敘圣教量及比量義。次有《萆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乃伐致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制。可謂窮天地之奧秘,極人理之精華矣。若人學至于此,方曰善解聲明,與九經百家相似。”對照現存的《句詞論》,義凈所說的“頌有七百”,相當于現存《句詞論》的前兩章,即第一章156頌,第二章485頌,合計641頌,接近“七百”頌。義凈所說《萆拏》實為現存《句詞論》第三章,別名Prakīrn?aka,可意譯為《雜論》。義凈譯為《萆拏》,顯然是截取詞頭Pra的音譯,如同他截取Vkyapadīya(《句詞論》)這個復合詞中的前一個詞,音譯為《薄伽論》。現存《句詞論》第三章有1323頌,與義凈所說“頌有三千”有差距。另外,義凈說這部分的注釋者是“護法論師”(Dharmapla),而現存文本的注釋者是海拉羅阇(Helrja)。
印度古代語言哲學注重音和義的關系。伐致呵利在《句詞論》中說:“大仙人們是經、注和疏的作者,認為音和義的結合是永恒的。”(123)而中國古人注重名和實的關系。《公孫龍子?名實論》中說:“夫名,實謂也。”《墨子?經說上》中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名實說和音義說有所不同。音和義是就語言內部結構而言,而名和實是就語言和外部事物而言。但也有相通之處,因為梵語中的“義”(artha)也含有對象或事物的意思。
莊子指出:“名,實之賓也。”(《莊子?逍遙游》)這里,確定了名和實的主賓關系:實為主,名為賓。這與印度古人對音義關系的看法一致。伐致呵利說:“一旦意義得到表達,作為輔助意義的表達者實現目的,就不再被人感知。”(154)也就是說,音輔助義,感知音是為了理解義。這也與莊子所謂“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相通。但莊子對名實關系的看法沒有停留在主賓關系上。在他看來,“名”并不能表達所有的“實”。他認為:“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莊子?秋水》)他將事物(“實”)分成“物之粗”、“物之精”和“不期精粗”三者,語言只能表達“物之粗”,也就是事物的“形與色”。而“物之精”只能意會。至于“不期精粗”,即“道”,既不能言說,也不能意會。這也就是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莊哲學思想中的“道”,與印度奧義書哲學中的“梵”相通,都是指稱世界的本原。莊子認為:“道不可聞,聞而非道也;道不可見,見而非道也;道不可言,言而非道也。”(《莊子?知北游》)同樣,奧義書哲學認為梵“不能用語言、思想和眼睛得知,除了說它存在之外,還能怎么得知?”(《伽陀奧義書》2312)或者說,梵“不可目睹,不可言說,不可執取,無特征,不可思議,不可名狀,以確信惟一自我為本質,滅寂戲論,平靜,吉祥,不二”(《蛙氏奧義書》7)。
印度大乘佛教也強調語言不能表達佛法:“般若波羅蜜不可說,禪那波羅蜜乃至一切法,若有為,若無為,若聲聞法,若辟支佛法,若菩薩法,若佛法,亦不可說。”(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方便品》)但為了教化眾生,又不得不說,于是,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觀派認為萬物因緣和合而成,并無“自性”,實質為“空”。龍樹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鳩摩羅什譯《中論》卷四)也就是說,因緣和合而成的萬物實質為“空”(s'ūnyat),因而關于它們的稱謂或言說只是“假名”(prajapti)。這里,既確認“空”,也確認“假名”,不偏執一端,故而是“中道”。因緣和合的萬物(“假名”)和實質(“空”)也可稱為“俗諦”和“真諦”。“真諦”本不可說,又不得不說,則借助“俗諦”。或通過“因緣、譬喻言辭”,或通過“遮詮”表達方式。“遮詮”(apoha)指否定式表述。如龍樹對“空”的表述:“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鳩摩羅什譯《中論》卷一)這與奧義書哲學中對“梵”的否定式表述(netineti)一脈相承。如《大森林奧義書》將不滅者(“梵”)表述為“不粗,不細,不短,不長,不紅,不濕,無影,無暗,無風,無空間,無接觸,無味,無香,無眼,無耳,無語,無思想,無光熱,無氣息,無嘴,無量,無內,無外”(388)。同樣,在老莊哲學中,“道”不可說,又不得不說,則借助“卮言”、“重言”和“寓言”(《莊子?天下》)。理解了印度奧義書哲學和大乘佛教以及中國老莊哲學的語言思想,對中國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及其說禪方式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中國古人對語言哲學的思考中,除了名和實、道和名(言)的關系之外,還有意、言和書的關系。《周易?系辭上傳》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莊子則說:“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莊子?天道》)這些論述中體現的意、言和書的等級次序,類似德里達所謂“邏各斯中心主義”中的“內在思想、口頭語言、書面文字之間的等級關系”參閱張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頁。。西方傳統認為“邏各斯”(logos)兼有“理性”(ratio)和“言說”(oratio)兩義。因此,“邏各斯中心主義”也可稱為“語音中心主義”。這樣,就“邏各斯”表示理性、思想或意義而言,接近中國古代語言哲學中的“意”,而就“邏各斯”表示語音或音和義的統一而言,接近印度古代語言哲學中的“常聲”(sphot?a)。然而,印度古人對語言的思考集中在音和義的關系,并不涉及書面文字。這不足為奇,因為輕視書寫是印度古代文化本身固有的特點。
雖然中國古代語言哲學涉及意、言和書的關系,但更多的思考還是集中在意和言的關系。意和言的關系不同于道和名(言)或梵和言。意和言的關系是能不能盡意和怎樣盡意,而道或梵已預設為不可言。中國儒家的主要傾向還是認為言可盡意。孔子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又說:“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周易?系辭上傳》)這里的“象”不僅指卦爻,也含有“形象”、“意象”和“象征”之意。由此,將意和言的關系擴充為意、象和言的關系。歐陽建則在《言盡意論》(《全晉文》卷一百九)中強調“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矣。茍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這里將言意不二比作“聲發響應”,類似印度的“常聲”說。無論是“言不盡意”論、“言盡意”論、“意象言”論或道家的“道不可言”論都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在中國古代詩學中得到運用,重視“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文心雕龍?隱秀》),充分激發語言潛藏的表現能力。而在印度古代詩學中,“常聲”論和“梵不可言”論也起到同樣的作用。梵語詩學家歡增就在《韻光》中將語法家稱為學問家中的“先驅”,指出:“他們把韻用在聽到的音素上。其他學者在闡明詩的本質時,遵循他們的思想,依據共同的暗示性,把表示義和表示者混合的詞的靈魂,即通常所謂的詩,也稱作韻。”(113注疏)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可以分成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文學也可以分成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書面文學的語言不同于口頭語言,這一點不言而喻。而口頭文學既然成為文學,其語言也不完全等同于口頭語言。郭紹虞先生曾將中國文學分成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以此歸納中國文學的演變:春秋以前為詩樂時代,戰國至漢為辭賦時代,魏晉南北朝為駢文時代,隋唐至北宋為古文時代,南宋至現代為語體時代。其中,“詩樂”是語言型文學,即接近口語的文學;“辭賦”是文字型文學,即脫離口語的文學;“駢文”是典型的文字型文學;“古文”和“語體”又回歸語言型文學參閱郭紹虞《中國語言與文字之分歧在文學史上的演變現象》,《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郭先生的這個歸納很有見地,揭示了中國文學語言演變的基本脈絡。在概念上,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與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有相通之處,但也不盡相同。口頭文學主要指依靠口頭創作和傳播的文學,書面文學主要指依靠文字創作和傳播的文學。從文學接受的角度看,前者主要是說和聽的關系,后者主要是寫和看的關系。而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的區別主要著眼于文學語言與口語的距離遠近。
印度古代的吠陀、史詩和往世書都屬于口頭文學。大約從公元前后不久開始,印度進入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吠陀使用的古梵語(或稱吠陀語),史詩和往世書使用的史詩梵語,都是與當時的口語接近的梵語。而古典梵語文學使用的古典梵語則是注重藻飾的梵語。印度古代現存最早的古典梵語詩學著作《詩莊嚴論》和《詩鏡》都是著重探討文學語言的修辭手法。古典梵語詩學家將那些裝飾語言的音和義的修辭手法視為文學語言不同于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的標志。當然,這并不是說吠陀、史詩和往世書中沒有修辭,只是相對地說,這些口頭文學中的修辭都比較質樸,而古典梵語文學中的修辭更趨精致。在七世紀的《詩莊嚴論》中論述的辭格為三十九種,此后不斷充實和發展,達到一百多種。追求藻飾是古典梵語文學的普遍特點。而其中的極端者,則以雕琢繁縟的文體和艱難奇巧的修辭為詩才,甚至近乎文字游戲。這樣的文學作品自然不能再像吠陀和史詩那樣依靠口頭創作和傳播,而必須依賴文字和書寫。因而,在王頂(九、十世紀)的詩學著作《詩探》中,在第十章論述“詩人的行為”時,提到“詩人的身邊經常有箱篋,有的裝有木片和白堊,有的裝有筆、墨水壺、棕櫚樹葉、樺樹皮、鐵針和多羅樹葉”。這些都是書寫的工具和材料,其中的“棕櫚樹葉”和“多羅樹葉”就是漢譯佛經中所稱的“貝葉”。
盡管如此,在古典梵語文學時期,依然存在口頭文學。兩大史詩的最后定型是在公元四、五世紀,各種往世書的最后定型則更晚。同時,許多故事文學作品也使用與口語接近的梵語。而且,在古代印度,除了梵語文學作品外,始終存在各種俗語文學作品。例如,于公元前三世紀結集的佛教經典《三藏》(Tipit?aka)使用的是巴利語(Pli),于公元五、六世紀結集的耆那教經典《阿笈摩》(gama)使用的是半摩揭陀語(Ardhamgadhī)。在古典梵語文學時期,佛教由小乘演變為大乘,佛教高僧們開始使用梵語撰寫佛經。出于口頭宣教的需要,大乘佛經使用的梵語大多也是接近口語的通俗梵語,但也有一些佛經效仿古典梵語“大詩”文體,注重文采和修辭。以各地方言為基礎的重要俗語還有摩訶剌陀語、修羅塞納語、摩揭陀語、畢舍遮語和阿波布朗舍語等。這些俗語后來發展成印度現代各種語言,如印地語、孟加拉語和旁遮普語等。而作為印度古代社會(尤其是上層社會)的通用語梵語,卻于十二世紀開始逐漸消亡。
印度古代語言的這種變化發展與拼音文字有關。拼音文字與語言的關系是文字依附語言,文字拼寫隨語言而變化。印度古代各地的方言隨著時間推移,在詞匯和語法上與通用語梵語的差異越來越大,最終拼寫出來,成了各自獨立的語言。而中國的漢語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漢字是表意文字。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推行“書同文”的語言政策。這樣,文字始終對語言起著管轄作用。各地方言可以有語音差別,但相對應的文字依然是統一的。語言作品中也可以或多或少攙雜方言,借用同音的漢字表達。然而,它們聽從歷史的選擇,或融入通用語,或被淘汰。在固定化的表意文字的統領下,各地方言不會發展成獨立的語言。因此,漢語沒有像使用拼音文字的梵語和拉丁語那樣在歷史發展中消亡,而成為世界語言之林中的常青樹。
在漢語中,還有文言和白話的區分,由此也形成文言文學和白話文學的區分。它們與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以及語言型文學和文字型文學也是在概念上既相通,又有差異。另外,白話文學也可稱為俗文學,但俗文學卻不能徑稱白話文學,因為在古代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和戲曲也可用文言創作。這類術語的多樣化體現不同的視角或立足點,也反映文學與語言關系本身的復雜性。
文言文是隨著戰國時期開始盛行書面文化而逐漸成型的。當時尚未發明造紙術,受書寫材料制約,簡牘嫌重,縑帛嫌貴,故而文言文的文體特點必定趨于簡約。在簡約的前提下,追求“辭達”、“辭巧”和“文質彬彬”。這樣,文言文逐漸形成有別于口語的詞匯和句法系統,并在使用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同時,文言文也適應實用需要,依據不同的內容和表達方式形成不同的文體和風格。如曹丕《典論?論文》中所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而劉勰《文心雕龍》中論述的文言文體達幾十種之多。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在文學觀念上有兩個重大發展:一是在“詩言志”的基礎上提出“詩緣情”;二是追求語言的藝術美,重視駢偶、聲律和藻飾。按陸機《文賦》中的說法,就是“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以“四聲八病”說為核心的永明聲律論揭示了漢詩音韻美的奧秘,奠定了漢詩格律的理論基礎。同時,在散文中也注重辭藻和聲韻,尤其鐘情駢偶,形成句式工整對稱(“駢四儷六”)的駢文。可以說,駢文代表中國古代散文語言藝術達到極致的文體形式。
而魏晉南北朝恰恰也是佛經翻譯昌盛的時期,故而在佛經翻譯活動中,關于佛經翻譯文體的文和質的討論貫穿始終。中國佛教高僧熟習簡約典雅的文言文體,這從他們為一些漢譯佛經撰寫的序文便可見出。乍一面對漢譯佛經質樸繁瑣的文體,自然會感到不適應,甚至心生疑惑。但隨著佛經翻譯實踐的深入,漸漸認識到漢譯佛經的這種文體符合佛經原典的本來面目。通過梵漢經籍文體的比較,得出“胡經尚質,秦人好文”(道安《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和“胡文委曲”,“秦人好簡”(僧睿《大智釋論序》)的結論。這并不難理解,因為佛經文體根植于口耳相傳的宣教方式,用語趨向通俗質樸,敘事說理也不憚繁瑣復沓。有了這樣的認識,他們也就不再忌諱使用白話或接近白話的文體翻譯佛經。有趣的是,他們還特別挑出儒家經典中文體接近口語的《尚書》和《詩經》為佛經文體撐腰:“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書》為質樸,而刪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道安《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這樣,在魏晉南北朝,一方面是駢文引領文言文體,另一方面是漢譯佛經推動白話文體,兩者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只有散見于典籍中的一些謠諺以及《詩經》和漢樂府中那些采自民間的歌謠,可以稱為白話或接近白話的文學。而此后,由佛經翻譯文體推波助瀾,白話文學與文言文學并駕齊驅,日益壯大。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唐代變文促進了中國古代通俗敘事文學的長足發展。變文采用韻散雜糅的白話文體,最初用于演說印度佛經故事,后來也用于演說中國歷史故事。韻散雜糅原本就是佛經的常用文體。在印度古典梵語敘事文學中,也有這類文體,稱為“占布”(Campu)。唐代變文后來演變成宋元話本(即白話小說)。宋元話本又演變成明清章回體白話長篇小說。
唐宋敘事文學的發展也為戲劇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中國古代戲劇誕生于宋元時期,明顯晚于希臘和印度。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國早期敘事文學不發達肯定是原因之一。古代希臘和印度的戲劇都產生在史詩之后,而且最初的戲劇題材大多取材于史詩中的故事和傳說。這說明有了以虛構為特征的敘事文學作為基礎,轉換成戲劇表演也就指日可待了。在中國古代,“傳奇”一詞既是唐宋小說的用名,也是元雜劇和明清戲曲的用名,也能印證這個道理。實際上,在元末明初的戲劇史料中,就有將傳奇視為戲曲源頭的說法。如夏庭芝說:“唐時有傳奇,皆文人所編,猶野史也,但資諧笑耳。宋之戲文,乃有唱念,有諢。”(《青樓集志》)陶宗儀說:“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南村輟耕錄》)
同時,從魏晉南北朝起,受漢譯佛經中偈頌的影響,佛教僧人也用白話寫詩。其中著名的詩人有南北朝的寶志和傅大士,唐代的王梵志、寒山、拾得和龐居士等,形成中國古代別開生面的佛教白話詩派。自然,他們也意識到白話詩不符合士大夫文人的詩藝標準。但他們仰仗有群眾基礎,充滿自信,認為自己的白話詩與文言詩享有同等地位。拾得在詩中表白說:“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全唐詩》卷八百七)寒山也說:“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全唐詩》卷八百六)另外,在唐代民間流行的詞曲或曲子詞,即配合樂曲歌唱的歌詞,是以長短句為特征的唐宋詞的先導。在這些詞曲中,也包含佛教詞曲。可以說,在唐代的白話文學運動中,佛教僧人始終是一支生力軍。
唐代變文還有一個更直接、更重要的演變發展方向是民間說唱文學。元明時民間流行的寶卷與變文一脈相承,說唱的內容可以分成佛經類和非佛經類,而以佛經類居多。元明時另一類說唱文學統稱為詞話,但留存于世的作品很少。因而,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一批明成化年間的詞話,顯得格外珍貴這批詞話于1973年由上海博物館影印出版。另有朱一玄校點本《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這批詞話共有十三種,其中講史類三種,公案類八種,神怪類兩種,說明說唱的內容已以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為主。另外,每種詞話都配有若干幅圖畫,說明還傳承著變文配圖說唱的原始精神。這類詞話的直接繼承者則是明清的長篇說唱文學鼓詞和彈詞。其中鼓詞流行于北方,彈詞流行于南方。
陳寅恪先生晚年目盲,曾依靠助手,聽讀彈詞《再生緣》,撰寫了《論再生緣》。《再生緣》出自清代女作家陳端生的手筆,字數達六十多萬。陳寅恪先生在文中稱《再生緣》“乃一敘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制也”。又說:“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而不知吾國也有此體。外國史詩中宗教哲學之思想,其精深博大,雖遠勝于吾國彈詞之所言,然止就文體立論,實未有差異。”參閱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陳先生的這一提示很有意義,也可以說是為比較文學點題。中國上古時代(先秦)沒有產生史詩一類長篇口頭敘事文學。而進入中古時代(唐宋),口頭說唱文學日趨發達,至近古時代(明清)達到鼎盛,涌現大量長篇說唱敘事文學。單就彈詞而言,“考諸各家書目所載,以及圖書館和私家藏書,估計至少有四百種”譚正璧、譚尋編著:《彈詞敘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其中,篇幅達數十萬字者不在少數,還有超過百萬字者。如《玉釧緣》一百二十萬字,《鳳雙飛》一百七十萬字,都超過約百萬字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而最長的一部彈詞是清代女作家李桂玉創作的《榴花夢》,近五百萬字,遠遠超過約四百萬字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令人驚嘆。這個有趣的文學現象,確實值得另外單獨列為專題,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