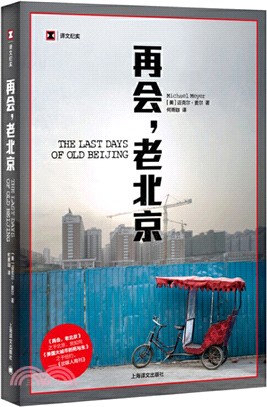再會,老北京:一座轉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譯文紀實
ISBN13:9787532761197
替代書名: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作者:(美)邁克爾‧麥爾
譯者:何雨珈
出版日:2018/06/01
裝訂/頁數:平裝/392頁
規格:20.8cm*14.6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我們愛上一座城,是因為愛上了那裡的一個人
我們懷念一座城,是因為懷念著這裡的一群人
一條胡同的因緣,一座城市的生死,一種歷史的記憶!
《華爾街日報》年度*佳亞洲圖書!
彼得·海斯勒、馮驥才、伊安·約翰遜聯合推薦!
新舊封面隨機發貨
北京,充滿活力的中國之都,變化是唯一不變的主題。
像紐約一樣,北京以國家的文化中心而驕傲;還是和紐約一樣,這座城市的歷史從沒有停止過活力。北京的朝代更替持續了近九個世紀,從蒙古人到漢族再到滿族,從帝王、軍閥、日本人到解放軍。
對中國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傳媒、教育、藝術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語言和時間。自北京建城以來,她就是吸引外來人口、商人、學者和探險者的魅力之地,也包括13世紀的馬可.波羅:這座城市內部以正方形和一種巧妙的、任何描述都不能夠表達的精確度向外擴張,就像一副棋盤。
這副"棋盤"的遺址仍留在北京古城裡,二十五平方英里的面積和曼哈頓區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狹窄巷子也依然存在,由灰牆和屋頂長草的平房庭院組成,縱橫交錯。幾個世紀以來,胡同是這個城市的文化特點;即使現在的巷子還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但在這些整齊格子裡的當地居民仍然堅持說東南西北,而不是左右。
作者簡介
邁克爾·麥爾(Michael Meyer)
1995年作為美國“和平隊”志願者首次來到中國,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訓英語教師。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並在清華大學學習中文。他的文章曾多次在《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諸多媒體上發表。邁克爾·麥爾曾獲得多個寫作獎項,其中包括古根海姆獎(Guggenheim),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New York Public Library),懷亭獎(Whiting), 和洛克菲勒·白拉及爾獎(Rockefeller Bellagio)。他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和香港大學教授紀實文學寫作。《再會,老北京》是他的首本書。
名人/編輯推薦
很少有作者能夠真正活在一部作品裡,融入當地的生活,並讓這種探究走向深處。兩年來,邁克爾·麥爾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書;在當今的英語寫作圈,沒有人比他更懂這個世界。
彼得·海斯勒(《江城》、《尋路中國》作者)
有回憶,有歷史,有旅行,也有對身體力行的呼籲,這本優美的處女作,表達了作者對老北京的戀慕,也是對一種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的輓歌……對於北京而言,麥爾的這部力作就如同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之於紐約。
《出版人周刊》
令人難忘地,麥爾記錄了一座城的死去。儘管看起來有些極端,但這絕不僅僅是北京的問題。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也是我們美國正在經歷的問題。
《紐約時報書評》
目次
第一章走過大前門
第二章叫我梅老師
第三章Mocky與我
第四章“告別危房”
第五章寒冬降臨
第六章拆之簡史一:燕都舊跡
第七章《北京晚報》
第八章幸福城中好時光
第九章把感覺留住
第十章春天
第十一章拆之簡史二:皇城興衰
第十二章“去貧化”的貧民窟
第十三章搶救老街
第十四章夏日大回收
第十五章過去時與將來時
第十六章拆之簡史三:民國首都的現代化之路
第十七章朱老師:樹的記憶
第十八章“他有病了你不給他治,是你的責任”
第十九章老寡婦的故事
第二十章拆之簡史四:“毛澤東時代”北京的工業浪潮
第二十一章回音壁
後記新北京,新奧運
致謝
譯名對照表
參考書目
譯後記一封寫給老北京的憂傷情書
書摘/試閱
第二章叫我梅老師
十年前,我作為一名“和平隊”(Peace Corps)的志願者,第一次來到中國。本來,我是希望能被派往拉丁美洲的,因為當時我在威斯康辛大學主修教育學,並準備拿西班牙語和英語的執教證書。工作日的上午,我在一所中學給九年級的孩子們當老師,接著則步履匆匆地走過麥迪遜生產奧斯卡?梅爾煙熏火腿的工廠,四十二個六年級孩子正等著和我共渡下午的一段上課時光。
這些實習教職都是沒有收入的,所以下課之後,我又兼職做起了特殊的接線員,充當需要打電話的聽力障礙人士與電話接聽人之間的橋樑。工作的時候,我戴一副耳機,面前擺著一台顯示器,把電話接聽人的話打成文字,同時把電話那頭聽力障礙人士的文字回答讀給接聽人。這場交流中沒有標點符號,“qq”代表一個問號,“ga”代表“請講”(go ahead),代表對方可以回話了。常會出現類似下面的句子:“薩拉你好,(語氣愉快),今天能和我共進晚餐嗎qq ga。”接線員們不過是一條條電話線,不能和通話雙方發生直接的對話。我只是重複對方的句子,然後說“請講”。這份偷窺狂們一定會夢寐以求的工作於我卻是個無可奈何的累贅,我得一邊上班,一邊看我給學生們佈置下去閱讀的小說,要比他們的進度提前一章,一邊還得不時停下來,將一個女人打出的字大聲讀給電話那頭的男人聽,有些內容讓人很是尷尬,比如,“寶貝兒我丈夫走了我現在就想要你——請講。”
一個春日的早晨,九年級學生們去參加一個名為“我們都是兄弟姐妹”的集會,而我則直挺挺地躺在教室裡冰涼的地板上。我的右眼失明了。“壓力大而已,”校醫院的護士下了簡單的結論,並且不以為意地聳聳肩。我抬眼看看那沉重得彷彿快要掉下來的天花板,發現其中一塊嵌板上用鉛筆工工整整地寫著幾個大字:“麥爾老師是個大笨蛋!”大廳的那頭,響起一陣及時雨般的電話鈴聲。
和平隊給了三個去向讓我選擇:中國、蒙古和海參崴(Vladivostok) 。我不會說中文。我用不慣筷子。但中國是我嚮往已久的地方。我曾經走進學校裡的一家旅行社,問去那裡的機票多少錢一張。對方給出個“天文數字”,瞟了我一眼,好像在說:去挖點兒金子吧你。
和平隊在電話裡告訴我,畢業三週以後就可以出發了。當天晚上會把各種表格快遞給我。結果聯邦快遞不給送貨上門,我輾轉去機場才拿到那封郵件。打開碩大的信封,我仔仔細細地翻看每一份文件:《志願者任務表》、各種體檢合格證明、眼鏡訂購套裝、《隱私法聲明》以及簽證申請,一切都真實可觸,我真的要去中國了。去吧(go ahead),眼前的郵件彷彿在說,這兩個字從未在我心裡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鳴:去吧,去吧,去吧。
那是1995年,中國當局對和平隊的戒心很重,認為其帶有某種政治目的。因此,我們這由十五個老師組成的隊伍換了個新名字,“中美友好志願者”。我的個人信息也被進行了一些“潤色”。在中文裡,我的姓Meyer讀起來音同“賣兒”,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貧窮父母在集市上叫賣兒子的淒涼畫面。在接受和平隊培訓期間,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在看見我名字之後低聲輕笑,給了我一個中文名字“梅英東”。我用這個名字向中國人介紹自己時,他們總會一陣竊笑。每當這時我就覺得,還是“賣兒”比較好。
和平隊來到中國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內江,位於大河沱江的一個拐彎處。這是個不怎麼發達和活泛的小城鎮,以甘蔗的出產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當地一個專愛揭露醜聞的作家在一本名為《天府之國魔與道》的著作中,對內江的毒品交易有過描述。
我在這個地方呆了兩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職業技術學校培訓英語教師。這所學校位於縣城外一座懸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滿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每天早上,我的“鬧鐘”就是窗外刺耳的豬叫。沒有手機電話,更無網可上,要和家里聯係了,就用學校裡提供的半透明紙,寫封家書,放進信封,用魚膠粘上郵票,再寄出去。校園窄窄的主路總是泥濘不堪,旁邊有一家餐館,地面是泥巴舖的,我就在那裡解決一日三餐。最忙的時候,我一周上八小時的課,向那些二十出頭,彷彿擁有無盡活力和智慧的學生們傳授知識。日常生活就是打籃球、讀小說和學中文。每月領八百塊錢工資的我能生活得不錯,這裡除了當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沒什麼好買的。我從來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為沒什麼壓力和必要。手錶從我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來暑往,以及學校的開學放假,就足以說明時間的變換了。
1997年,我作為一名“中美友好志願者”的服務期已滿,就來到北京,繼續教英語。在“鄉下”呆了整整兩年之後,北京於我,簡直就是個國際大都市。當時,這座城市也和其它中國城市完全不同。在這裡,市中心並不是一條條空蕩盪沒有人情味的寬闊林蔭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與寫字樓,而是一汪汪相連的湖水,周圍修著各式各樣看上去十分親切的建築,以及將它們聯繫起來的胡同。一條胡同的寬度一般和兩邊四合院院牆的高度一致。四川有著起伏的丘陵,其間間插著農田和開闊地,天空中總是飄著陰雲,一年到頭難見陽光。而北京則處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頭頂的天空總是清澈而高遠,這裡的氣候總讓我想起自己的故鄉明尼蘇達。我還在這裡遇到了未來的妻子。我對北京的感覺,一個詞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見鍾情。
世間的城市對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於登山隊員。然而,從小的經歷也讓我對城市充滿了懷疑與不信任。我母親童年時居住的底特律,曾經繁榮輝煌,現在則成為一座工業“廢城”,貧富階層分群而居。我父親的故鄉洛杉磯,一條條高速公路無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園,並且肆無忌憚地四處延伸。在我土生土長的明尼阿波利斯,人們竟然不得不在室內觀看職業棒球大賽。我在那裡的家位於城外一條偏僻得好似與世隔絕的泥路上,一排排榆樹和樺樹伸展著枝條立在兩邊。後院的柵欄只為美觀而設,一片片玉米地綿延好幾公頃。今天,那條路被鋪上了磚,樹木被修剪和砍伐,只為綠化某些公司的停車場而設。玉米地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別墅。一個教書匠微薄的薪水,是絕對買不起的。
中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甚至速度更快。每過幾年我都會回到和平隊生涯開始的內江,但最後一次去的時候,出租車司機轉過頭來,充滿懷疑地說,“你確定在這裡住過?你指的方向都讓我迷路啦!”我什麼都認不出來了。渡口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橋;河岸的峭壁也通了一條條公路;職業技術學校也升級成了一所大學。我下了車,站在一片霧霾之中。也不知過了多久,一個聲音響起,“梅教授?”原來是那時的郵遞員。他領著我,沿著鋪飾嶄新的人行道,來到我過去住的那座外牆舖有白瓷磚的樓房。那是十年前蓋的樓了,狀況仍然不錯。但已經被指定為需要拆除的房子,即將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賓館。過去的那個校園,那個我曾經渡過生命中兩年快樂時光的校園,早已經消失了。
不過,等我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審視這些變化時,也意識到這整體上是一件好事。我不是個刻意懷舊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沒有人應該生活在貧窮當中。新校園有現代化的教室,宿舍裡配有暖氣,鍛煉運動的場地也寬了許多,校園中的道路也鋪了瀝青,更加美觀和安全。學校申請到一些請外教的資金,不再單純依靠志願者了。
2001年,北京申奧的響亮口號中,第一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裡的時候,這個城市的美化和翻新運動就已經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了。一條條的胡同逐漸被大型購物超市、高層公寓樓和寬闊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歷史,留在老北京們心目中的地標正逐漸地消失著。可能你不久前還去吃過的老字號美味餐館,逛過的熱鬧露天市場,甚至是造訪過的溫馨社區,在短短幾週內就能面目全非,被夷為平地。這在北京已經是家常便飯。那些在這裡生活和工作過的人們去了哪裡呢?除了“反正不在這兒了,”沒有人能給出別的答案。
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新北京”一點兒也不陌生。這座城裡的第一家星巴克於1998年開張。九年後,城區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館,將近兩百家麥當勞和規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數十家必勝客,還有一家貓頭鷹餐廳。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寬,上面行駛的私家車也以一天約一千輛的速度增長。一家北京報紙驚呼《自行車王國一去不返!》。在曾經荒涼的郊區,一座座鱗次櫛比的高樓拔地而起,而高爾夫球場(11座)和滑雪度假村(12家)也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國際學校教書。學校位於北京正在蓬勃發展的郊區。這片區域處處是奢華貴氣,獨門獨院的別墅,因此被大家稱為“別墅之鄉”。我從市內乘車去上班的時候,總會經過一段佈滿購物中心的地帶,還能看見一家達美樂披薩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產項目,豪華的大門上寫著諸如“麗高王府”、“王朝花園”、“優勝美地”等富貴洋氣的名字。我總是睡意朦朧地靠著校車窗戶望出去,周圍的學生們則在爭論誰家的鄉下保姆更蠢笨,聲音有一搭沒一搭地飄進我耳朵裡。經過“美林香檳小鎮”的建築工地時,我的心情低落到極點。工地外的大廣告牌上有幾個豐滿高大,面帶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檳正在開懷暢飲。旁邊有一行英文:“同來喝香檳聖飲,一切煩惱遠離你。”我覺得牌子上那幾個人真是面目可憎。在“別墅之鄉”,一切的確看起來很遙遠,特別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裡的一切麻煩。正值“非典”肆虐,市民們幾乎中止了所有的戶外活動,只有建築工地還照常開工。在從學校返回曆史悠久的老城區時,校車會經過一座橋,橋上有個大大的電子計時牌,正為2008年奧運會的到來做著以“秒”為單位的倒計時。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數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變成了165,369,211。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著。
……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