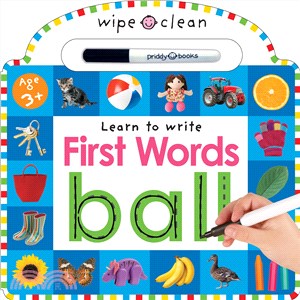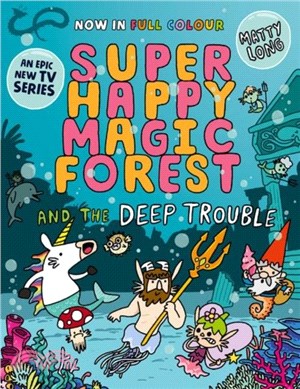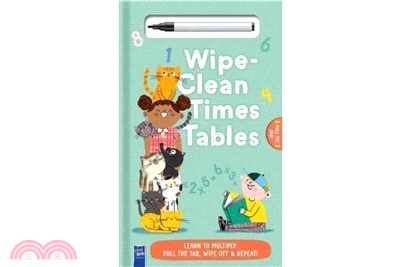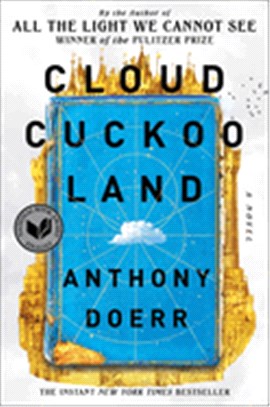給年輕記者的信
商品資訊
系列名:博雅文庫
ISBN13:9789571171715
替代書名: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
作者:塞繆爾.弗里德曼
出版日:2013/07/25
裝訂/頁數:平裝/184頁
規格:21cm*15cm (高/寬)
版次:2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在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本書作者在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兩方面都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本書中,他與年輕記者們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首先和讀者分享了自己從高中校刊做小記者到大學畢業後走向社會,直至成為著名記者的奮鬥經歷。在做這些工作時,他有對傳統的繼承,也有隨著時代發展的創新。無論是廣播採訪、電視報導、網路部落格,還是偏遠地方的冷僻新聞,作者的目標都是在採訪、寫作、思考、探究的過程中,塑造一個優秀記者的思維習慣。在當今社會,隨著媒介形式的巨大變化,新聞行業和新聞記者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而作者以他新奇的觀念和激動人心的故事,為已經或即將踏入新聞行業的人們提供了富有睿智的指導和靈感。
作者簡介
塞繆爾.弗里德曼(Samuel G. Freedman)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長達三十年。已出版過五本書,並為多家媒體撰稿,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全國廣播公司、《滾石雜誌》和《商業週刊》。曾獲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並榮獲美國猶太圖書獎。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長達三十年。已出版過五本書,並為多家媒體撰稿,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全國廣播公司、《滾石雜誌》和《商業週刊》。曾獲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並榮獲美國猶太圖書獎。
目次
致謝
序言
第一章 特性
作為人的新聞記者
忠誠誓言
我們要背叛嗎?
第二章 報導
做足功課
磨損的鞋
搶風航行
匿名的消息來源
打字與思考
第三章
寫作
寫作的階段
形式和功能
敬畏文字,尊重語言
有關我的書
愛與隔離
第四章
職業生涯
堅守你的立場
為漸進主義唱讚歌
迎難而上
圖書市場上的失敗
後記
序言
第一章 特性
作為人的新聞記者
忠誠誓言
我們要背叛嗎?
第二章 報導
做足功課
磨損的鞋
搶風航行
匿名的消息來源
打字與思考
第三章
寫作
寫作的階段
形式和功能
敬畏文字,尊重語言
有關我的書
愛與隔離
第四章
職業生涯
堅守你的立場
為漸進主義唱讚歌
迎難而上
圖書市場上的失敗
後記
書摘/試閱
作為人的新聞記者
要成為有道德的新聞記者,你必須永保仁慈之心。你大概會認為我正在說一個眾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客觀的理想狀態是新聞記者對於所採訪的對象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為了確保公正,新聞記者被要求不動感情。但我個人總是認為「客觀」是一個錯誤的辭彙,因為人不能迴避主觀。新聞記者所追求的就是怎樣更好地體現公正,這一主題本身值得我們稍後單獨討論。無論你把在新聞中保持距離稱為客觀還是公正,或是有其他什麼詞,新聞距離不能、也根本不應該超越人性的範疇。新聞是關於溝通情感的,而不是拒情感於千里之外。在一些罕見和非常的情況下,新聞是要突破障礙的,這障礙就是藝術界人士所說的「第四面牆」,所謂的「第四面牆」,把人與我們正在報導的事件截然分開。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
有兩張獲獎照片的故事和照片的拍攝者正好能說明我的觀點。如果你們研究過越南戰爭,那麼你可能看到過一張這樣的照片:一個越南女孩赤身裸體哭嚎著跑在一條路上。那個小女孩是美軍凝固汽油彈襲擊的犧牲品。這個痛苦的被燒灼的女孩的照片並沒有在美國引起深化反戰的作用,倒是使美聯社的攝影記者黃幼公獲得了普立茲獎。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黃幼公拍完那個名叫潘金淑的小女孩之後,他把小女孩帶上了一輛小公共汽車,命令那輛汽車去一家醫院,並在那裡懇求大夫立即進行治療。直到潘金淑上了手術臺,黃幼公才回到美聯社的辦公室去沖洗照片。潘金淑在二十八年之後的一個儀式上對英國女王談到了黃幼公:「他救了我的命。」我應當在這裡加上一句:他也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另一張攝於一九九三年的照片拍的是蘇丹的饑荒。照片抓到了正走向救濟所的一個瘦弱、蹣跚的孩子跌倒的瞬間,孩子的身後是一隻禿鷲。像黃幼公一樣,拍攝這張照片的自由撰稿人凱文.卡特吸引了公眾輿論對這一圖片形象的興趣。卡特也像黃幼公一樣,獲得了普立茲獎。不過他沒有像黃幼公那樣拯救照片中的主角。卡特在英國《衛報》的一位同事大衛.貝雷斯福德回憶當時質問他的情形:「你為這孩子做了什麼?」卡特回答說:「我什麼都沒做,那裡有成千上萬那樣的孩子。」(卡特的確說過他趕走了那隻禿鷲,還說他拍完照片後哭了幾個小時。)在獲得普立茲獎後不到四個月,卡特自殺了。你永遠不可能知道一個自殺者的確切想法,但事後許多卡特的同事不斷回憶著他作為新聞記者失去人性的那一天。
我知道關鍵時刻的抉擇對於像你們這樣年輕的人是多麼的困難,你們是專業上的新手,想要打造自己的特點,想要理解那些施加在你們良心上的矛盾要求。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二○○一年九月我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新聞報導導論課程。在「蓋達」組織發動襲擊的那個早晨,我的學生才上了一個月的課。他們立即被捲入了這起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新聞事件,儘管他們還在努力學習最基本的技巧。我並沒有像許多同事那樣把學生送到世貿中心所在的廢墟,讓他們感受對不安全的恐懼,但我讓學生們去進行紐約遭襲的後續報導,採訪紐約市的社區新聞。現在回顧起來,我可以說這種經歷使他們超越了自我。他們寫了多明尼加移民門房在「雙子星」大樓倒塌時遇難,寫了錫克教教徒由於被誤認為是阿拉伯人而被認為有犯罪的意圖,寫了殯儀員為眾多殘缺的屍體辦理喪葬事宜,還寫了消防部門的風笛手樂隊為葬禮和懷念儀式進行了數百次演奏,而他們已經失去了兩位自己的同事。
在報導那些事情的過程中,我的學生也碰到了一些令人極度痛苦而必須面對的問題。我的採訪對象哭了怎麼辦?我可以觸摸他們嗎?我可以擁抱他們嗎?我哭了又會怎麼樣?如果我哭的話算是個很糟糕的記者嗎?在我的課上當助教的《紐約時報》的米爾塔.奧吉托回答了這些問題。在紐約遭襲之後的幾周裡,米爾塔一直在寫〈罹難者介紹〉,這是《紐約時報》為那些被證實在襲擊中遇險的人開設的專欄。換句話說,就是她每一個工作日都在採訪倖存者。她對全班同學講,她在與失去兩個女兒的父親電話交談時如何失聲痛哭。她回憶了走進《紐約時報》的女廁時,發現一位同事由於極度緊張而在那裡抽泣的場面。米爾塔明白,作為記者,哭泣不會使她受到衝擊和傷害。如果長期不能感受寡婦和鰥夫的心痛,不能感受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痛,而且也不能傳達這種痛苦,這種對人性的疏遠就會導致新聞工作者的失敗。
那年秋天我和米爾塔教的學生中有個叫凱麗.謝里登的。她把那時寫的關於消防局樂隊的文章收集在二○○二年的一本名為《風笛兄弟》的書裡。凱麗與大多數新聞記者不一樣,她既考慮到職業需要,也注重個人道德,而且不得不親自去確定是否遵守了道德準則和職業規範。她想寫一本偉大的書,同時也希望能夠在晚上睡好覺。最近我問她有什麼可以對你們說的,她說:「在悲劇時代,界限變得模糊。關於如何保持人性,我給年輕記者的最佳忠告是順其自然。觀察,不張揚,盡力幫助別人,但不要把這些當做頭等大事。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如果你的家庭陷入同樣的境遇,你會有怎樣的感受。別忘了帶紙巾。」忠誠誓言
對於忠誠誓言我要特別給你們忠告。我不是指麥卡錫時期政府雇員被迫簽署的那種正式的忠誠誓言,我在這裡思考的是我們時代典型的那種暗示的、無需言傳的忠誠誓言,這種誓言具有來自道德、種族或宗教的熱情和共同政治目標的狂熱。你越感到是群體的一部分,特定的群體就越是認同你,為那個群體的利益服務的壓力就會越大。有人會期待你封鎖「壞消息」,不管那正好被人們認為是「壞消息」,還是一種新的有價值的意識形態思潮。
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做《紐約時報》記者時,恰巧被邀請參加一個逾越節聚會。當聽到我的姓氏和《紐約時報》的時候,有個來賓對我進行謾罵,說我是「最壞的那種自我仇恨的猶太人」,為了加重聲討的分量,他又說《紐約時報》反對以色列和猶太人。在經歷了挫折感和打擊之後,我開始意識到來賓是把我和湯瑪斯•弗里德曼混淆了。對我個人來說,我還從來沒有奢望過受到比這更高的讚賞。那時,弗里德曼如日中天,正因為報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走在通往普立茲獎的路上,而我正在報導康乃狄克州鄉下凌晨收垃圾的糾紛。我們名字的接近讓我收到了本來應寄給他的《高校曲棍球》雜誌。但這一切並不能使那個批評者有所緩和,即使我不是那個弗里德曼,我的猶太人身份也是不能抹殺的。
我當然能夠理解人的挫折感。他們感到好像被新聞體制擠壓以至於個性都被磨平了。拉美人、女同性戀者、福音教派基督徒,無論你能夠想到哪個組織,它都會把某個成員看做自己內部的人,它能魔術般地操縱那些槓桿和鞭子,而且很自然地希望那個人能代表組織掌控魔法。新聞工作者本身也無法避免這種誘惑。我認識的幾個黑人記者和編輯,他們深切地感受到想要報導黑人問題是如何使他們身心疲憊,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比白人在報導上更加敏感和細微,但卻拼命地避免成為那種只能報導黑人的固定角色。報導幾個月一次的政黨競選的記者、報導軍事行動的記者、報導整個賽季體育比賽的記者也都會遇到「忠誠」的問題。
實際上,一個記者必須永遠對職業、價值觀和讀者(或者聽眾和觀眾)負責。所以千萬別讓對集團的忠誠感或任何親密關係使你無法實話實說。但是,你的友誼和家族關係就會變得緊張甚至破裂;候選人、軍官、四分衛都可能稱你為在背後捅刀的人。所以,在這方面你不得不準備去適應這種孤獨狀態。
我的幾個新聞同行已經清楚地展示出這種精神氣質,你們也許能從他們的例子中獲取力量。我最好的編輯和導師之一是傑夫.施馬爾茲,他比我大幾歲,但在哥倫比亞大學上本科時就已在《紐約時報》做印刷工,不到三十歲就負責大多數都市報導的版面了。《紐約時報》編輯部有一些同性戀者,在一九八○年代早期那個排斥同性戀的氣候下,傑夫是主動公開性向的人之一。在他作為一個特殊人物全身心投入《紐約時報》的期間,從來沒有停止批評報紙的報導內容,其中包括缺乏同性戀問題的報導。我認為他寄望於一些採訪都市雇員新聞的記者能夠帶來變化。我在報社的第一年他就派我去採訪同性戀大遊行,在遊行隊伍中我碰到了高中的同班同學,我無意中在文章裡引用了他的話而暴露了他的同性戀身份。傑夫還派了一個叫邁克.諾曼的異性戀海軍退伍軍人去做紐約同性戀群體的重要系列報導,甚至告訴他應該深入哪些俱樂部或者澡堂。
所以當傑夫本人離開編輯部轉為記者,從事愛滋病的報導時,你或許會期待他能發揮模範、典型和為他的群體的人增光的作用,而他卻與自己的職業保持了距離。後來,在一九九○年代末,接踵而來的採訪任務使記者不堪重負。傑夫終於栽倒在新聞採訪室中,醫院的檢查表明他已染上嚴重的愛滋病。那時他身上已經沒有什麼淋巴細胞了,無法逃過這一劫。傑夫曾一度病情好轉,又回到了新聞工作中。同他採訪的對象在一起時,他有更多的激情,更少地去自我滿足,也更願意與他們分享擁抱和淚水。而且,他開始承受來自支援同性戀組織的難以承受的壓力,就像他在一篇值得紀念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那篇文章是傑夫去世的前一年發表的(他死於一九九三年,時年三十九歲)。他文章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在格林威治村為一名死於愛滋病的同性戀組織的領導人舉行的葬禮隊伍中,有個電視記者問我:「你是什麼人?」其實這個記者非常瞭解我:一個得了愛滋病的《紐約時報》的人。棺材並沒有蓋上,人們在雨中扛著這個敞開的「盒子」,拿著火把的送葬者在黃昏引導隊伍前行。單一節奏的輓歌伴著悼念隊伍的步伐,這個葬禮已經轉變成對布希處理愛滋病問題不當的抗議。
「你來這裡的身份是記者還是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電視記者繼續追問,麥克風在我的臉上晃來晃去,攝影機的燈光一直亮著。
我沒回答。人群在向我靠近,他們想知道答案。我也想知道。最後,答案有了,我說:「記者。」一些人表情厭惡地搖著頭,就差高呼「湯姆叔叔」了。他們需要支持者,而不是記者。我就站在那裡,一個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在一個愛滋病患者的葬禮上沒有位置,我只是我自身世界的一個局外人。
我在細雨中走了三十個街區回到了辦公室,一路思考著黑人報導黑人的事情,或者婦女報導婦女的事情,難度是多麼的大,而那種報導正是新聞工作中最富於挑戰的。有人認為那樣做新聞要受挫折,在那種情況下客觀往往被捨棄。但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記者的忠誠正是他們的痛苦所在,因為他們往往會受制於兩種忠誠。
我並沒有為這次葬禮遊行寫文章,因為這場遊行只要有一張照片和一段文字說明就足夠了。在那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通過了新聞業的考試,但卻沒有通過行動主義的考試。成為一個行動主義者意味著我只是個愛滋病人,而不是個新聞人。
要成為有道德的新聞記者,你必須永保仁慈之心。你大概會認為我正在說一個眾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客觀的理想狀態是新聞記者對於所採訪的對象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為了確保公正,新聞記者被要求不動感情。但我個人總是認為「客觀」是一個錯誤的辭彙,因為人不能迴避主觀。新聞記者所追求的就是怎樣更好地體現公正,這一主題本身值得我們稍後單獨討論。無論你把在新聞中保持距離稱為客觀還是公正,或是有其他什麼詞,新聞距離不能、也根本不應該超越人性的範疇。新聞是關於溝通情感的,而不是拒情感於千里之外。在一些罕見和非常的情況下,新聞是要突破障礙的,這障礙就是藝術界人士所說的「第四面牆」,所謂的「第四面牆」,把人與我們正在報導的事件截然分開。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
有兩張獲獎照片的故事和照片的拍攝者正好能說明我的觀點。如果你們研究過越南戰爭,那麼你可能看到過一張這樣的照片:一個越南女孩赤身裸體哭嚎著跑在一條路上。那個小女孩是美軍凝固汽油彈襲擊的犧牲品。這個痛苦的被燒灼的女孩的照片並沒有在美國引起深化反戰的作用,倒是使美聯社的攝影記者黃幼公獲得了普立茲獎。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黃幼公拍完那個名叫潘金淑的小女孩之後,他把小女孩帶上了一輛小公共汽車,命令那輛汽車去一家醫院,並在那裡懇求大夫立即進行治療。直到潘金淑上了手術臺,黃幼公才回到美聯社的辦公室去沖洗照片。潘金淑在二十八年之後的一個儀式上對英國女王談到了黃幼公:「他救了我的命。」我應當在這裡加上一句:他也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另一張攝於一九九三年的照片拍的是蘇丹的饑荒。照片抓到了正走向救濟所的一個瘦弱、蹣跚的孩子跌倒的瞬間,孩子的身後是一隻禿鷲。像黃幼公一樣,拍攝這張照片的自由撰稿人凱文.卡特吸引了公眾輿論對這一圖片形象的興趣。卡特也像黃幼公一樣,獲得了普立茲獎。不過他沒有像黃幼公那樣拯救照片中的主角。卡特在英國《衛報》的一位同事大衛.貝雷斯福德回憶當時質問他的情形:「你為這孩子做了什麼?」卡特回答說:「我什麼都沒做,那裡有成千上萬那樣的孩子。」(卡特的確說過他趕走了那隻禿鷲,還說他拍完照片後哭了幾個小時。)在獲得普立茲獎後不到四個月,卡特自殺了。你永遠不可能知道一個自殺者的確切想法,但事後許多卡特的同事不斷回憶著他作為新聞記者失去人性的那一天。
我知道關鍵時刻的抉擇對於像你們這樣年輕的人是多麼的困難,你們是專業上的新手,想要打造自己的特點,想要理解那些施加在你們良心上的矛盾要求。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二○○一年九月我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新聞報導導論課程。在「蓋達」組織發動襲擊的那個早晨,我的學生才上了一個月的課。他們立即被捲入了這起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新聞事件,儘管他們還在努力學習最基本的技巧。我並沒有像許多同事那樣把學生送到世貿中心所在的廢墟,讓他們感受對不安全的恐懼,但我讓學生們去進行紐約遭襲的後續報導,採訪紐約市的社區新聞。現在回顧起來,我可以說這種經歷使他們超越了自我。他們寫了多明尼加移民門房在「雙子星」大樓倒塌時遇難,寫了錫克教教徒由於被誤認為是阿拉伯人而被認為有犯罪的意圖,寫了殯儀員為眾多殘缺的屍體辦理喪葬事宜,還寫了消防部門的風笛手樂隊為葬禮和懷念儀式進行了數百次演奏,而他們已經失去了兩位自己的同事。
在報導那些事情的過程中,我的學生也碰到了一些令人極度痛苦而必須面對的問題。我的採訪對象哭了怎麼辦?我可以觸摸他們嗎?我可以擁抱他們嗎?我哭了又會怎麼樣?如果我哭的話算是個很糟糕的記者嗎?在我的課上當助教的《紐約時報》的米爾塔.奧吉托回答了這些問題。在紐約遭襲之後的幾周裡,米爾塔一直在寫〈罹難者介紹〉,這是《紐約時報》為那些被證實在襲擊中遇險的人開設的專欄。換句話說,就是她每一個工作日都在採訪倖存者。她對全班同學講,她在與失去兩個女兒的父親電話交談時如何失聲痛哭。她回憶了走進《紐約時報》的女廁時,發現一位同事由於極度緊張而在那裡抽泣的場面。米爾塔明白,作為記者,哭泣不會使她受到衝擊和傷害。如果長期不能感受寡婦和鰥夫的心痛,不能感受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痛,而且也不能傳達這種痛苦,這種對人性的疏遠就會導致新聞工作者的失敗。
那年秋天我和米爾塔教的學生中有個叫凱麗.謝里登的。她把那時寫的關於消防局樂隊的文章收集在二○○二年的一本名為《風笛兄弟》的書裡。凱麗與大多數新聞記者不一樣,她既考慮到職業需要,也注重個人道德,而且不得不親自去確定是否遵守了道德準則和職業規範。她想寫一本偉大的書,同時也希望能夠在晚上睡好覺。最近我問她有什麼可以對你們說的,她說:「在悲劇時代,界限變得模糊。關於如何保持人性,我給年輕記者的最佳忠告是順其自然。觀察,不張揚,盡力幫助別人,但不要把這些當做頭等大事。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如果你的家庭陷入同樣的境遇,你會有怎樣的感受。別忘了帶紙巾。」忠誠誓言
對於忠誠誓言我要特別給你們忠告。我不是指麥卡錫時期政府雇員被迫簽署的那種正式的忠誠誓言,我在這裡思考的是我們時代典型的那種暗示的、無需言傳的忠誠誓言,這種誓言具有來自道德、種族或宗教的熱情和共同政治目標的狂熱。你越感到是群體的一部分,特定的群體就越是認同你,為那個群體的利益服務的壓力就會越大。有人會期待你封鎖「壞消息」,不管那正好被人們認為是「壞消息」,還是一種新的有價值的意識形態思潮。
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做《紐約時報》記者時,恰巧被邀請參加一個逾越節聚會。當聽到我的姓氏和《紐約時報》的時候,有個來賓對我進行謾罵,說我是「最壞的那種自我仇恨的猶太人」,為了加重聲討的分量,他又說《紐約時報》反對以色列和猶太人。在經歷了挫折感和打擊之後,我開始意識到來賓是把我和湯瑪斯•弗里德曼混淆了。對我個人來說,我還從來沒有奢望過受到比這更高的讚賞。那時,弗里德曼如日中天,正因為報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走在通往普立茲獎的路上,而我正在報導康乃狄克州鄉下凌晨收垃圾的糾紛。我們名字的接近讓我收到了本來應寄給他的《高校曲棍球》雜誌。但這一切並不能使那個批評者有所緩和,即使我不是那個弗里德曼,我的猶太人身份也是不能抹殺的。
我當然能夠理解人的挫折感。他們感到好像被新聞體制擠壓以至於個性都被磨平了。拉美人、女同性戀者、福音教派基督徒,無論你能夠想到哪個組織,它都會把某個成員看做自己內部的人,它能魔術般地操縱那些槓桿和鞭子,而且很自然地希望那個人能代表組織掌控魔法。新聞工作者本身也無法避免這種誘惑。我認識的幾個黑人記者和編輯,他們深切地感受到想要報導黑人問題是如何使他們身心疲憊,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比白人在報導上更加敏感和細微,但卻拼命地避免成為那種只能報導黑人的固定角色。報導幾個月一次的政黨競選的記者、報導軍事行動的記者、報導整個賽季體育比賽的記者也都會遇到「忠誠」的問題。
實際上,一個記者必須永遠對職業、價值觀和讀者(或者聽眾和觀眾)負責。所以千萬別讓對集團的忠誠感或任何親密關係使你無法實話實說。但是,你的友誼和家族關係就會變得緊張甚至破裂;候選人、軍官、四分衛都可能稱你為在背後捅刀的人。所以,在這方面你不得不準備去適應這種孤獨狀態。
我的幾個新聞同行已經清楚地展示出這種精神氣質,你們也許能從他們的例子中獲取力量。我最好的編輯和導師之一是傑夫.施馬爾茲,他比我大幾歲,但在哥倫比亞大學上本科時就已在《紐約時報》做印刷工,不到三十歲就負責大多數都市報導的版面了。《紐約時報》編輯部有一些同性戀者,在一九八○年代早期那個排斥同性戀的氣候下,傑夫是主動公開性向的人之一。在他作為一個特殊人物全身心投入《紐約時報》的期間,從來沒有停止批評報紙的報導內容,其中包括缺乏同性戀問題的報導。我認為他寄望於一些採訪都市雇員新聞的記者能夠帶來變化。我在報社的第一年他就派我去採訪同性戀大遊行,在遊行隊伍中我碰到了高中的同班同學,我無意中在文章裡引用了他的話而暴露了他的同性戀身份。傑夫還派了一個叫邁克.諾曼的異性戀海軍退伍軍人去做紐約同性戀群體的重要系列報導,甚至告訴他應該深入哪些俱樂部或者澡堂。
所以當傑夫本人離開編輯部轉為記者,從事愛滋病的報導時,你或許會期待他能發揮模範、典型和為他的群體的人增光的作用,而他卻與自己的職業保持了距離。後來,在一九九○年代末,接踵而來的採訪任務使記者不堪重負。傑夫終於栽倒在新聞採訪室中,醫院的檢查表明他已染上嚴重的愛滋病。那時他身上已經沒有什麼淋巴細胞了,無法逃過這一劫。傑夫曾一度病情好轉,又回到了新聞工作中。同他採訪的對象在一起時,他有更多的激情,更少地去自我滿足,也更願意與他們分享擁抱和淚水。而且,他開始承受來自支援同性戀組織的難以承受的壓力,就像他在一篇值得紀念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那篇文章是傑夫去世的前一年發表的(他死於一九九三年,時年三十九歲)。他文章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在格林威治村為一名死於愛滋病的同性戀組織的領導人舉行的葬禮隊伍中,有個電視記者問我:「你是什麼人?」其實這個記者非常瞭解我:一個得了愛滋病的《紐約時報》的人。棺材並沒有蓋上,人們在雨中扛著這個敞開的「盒子」,拿著火把的送葬者在黃昏引導隊伍前行。單一節奏的輓歌伴著悼念隊伍的步伐,這個葬禮已經轉變成對布希處理愛滋病問題不當的抗議。
「你來這裡的身份是記者還是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電視記者繼續追問,麥克風在我的臉上晃來晃去,攝影機的燈光一直亮著。
我沒回答。人群在向我靠近,他們想知道答案。我也想知道。最後,答案有了,我說:「記者。」一些人表情厭惡地搖著頭,就差高呼「湯姆叔叔」了。他們需要支持者,而不是記者。我就站在那裡,一個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在一個愛滋病患者的葬禮上沒有位置,我只是我自身世界的一個局外人。
我在細雨中走了三十個街區回到了辦公室,一路思考著黑人報導黑人的事情,或者婦女報導婦女的事情,難度是多麼的大,而那種報導正是新聞工作中最富於挑戰的。有人認為那樣做新聞要受挫折,在那種情況下客觀往往被捨棄。但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記者的忠誠正是他們的痛苦所在,因為他們往往會受制於兩種忠誠。
我並沒有為這次葬禮遊行寫文章,因為這場遊行只要有一張照片和一段文字說明就足夠了。在那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通過了新聞業的考試,但卻沒有通過行動主義的考試。成為一個行動主義者意味著我只是個愛滋病人,而不是個新聞人。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