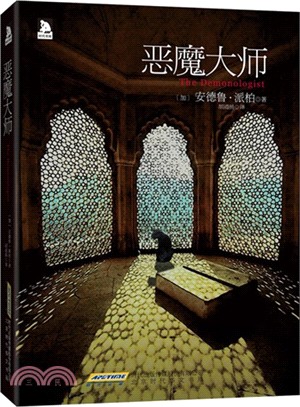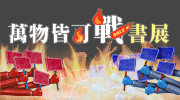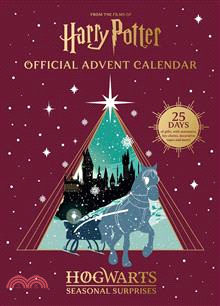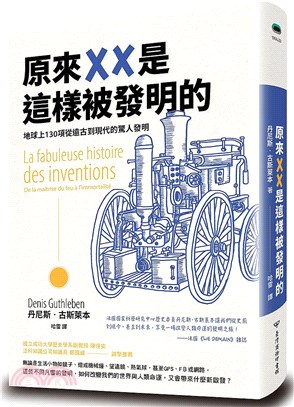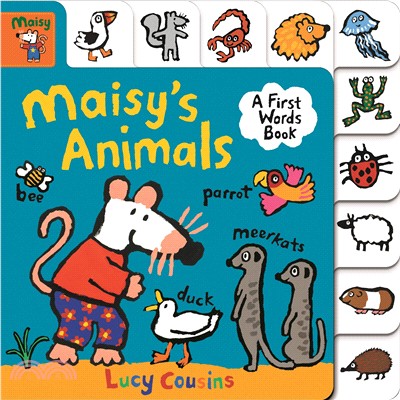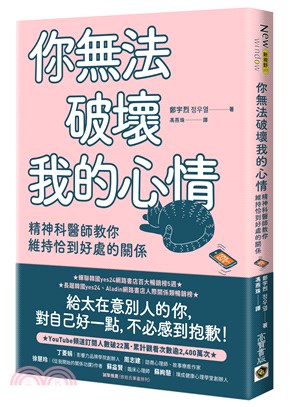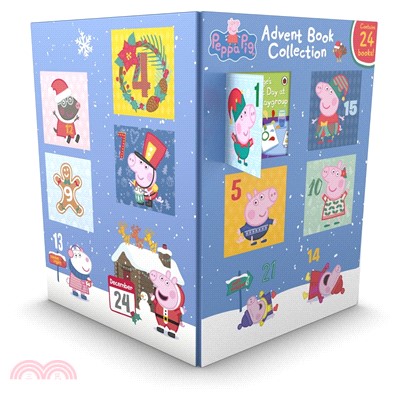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大衛·厄爾曼教授是惡魔學領域的專家,尤其對彌爾頓所著的《失樂園》一書研究頗深,他憑此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贊譽。不過大衛本人卻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也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
一天下午,他在學校辦公室意外迎來了一位訪客——她是個骨瘦嶙峋的女人,前來轉達一份口頭邀請:他被要求前往威尼斯,去見證一個“現象”并提出專業意見。作為報酬,他將獲得一筆可觀的收入。此時,大衛的生活在各個方面都陷入僵局(老婆出軌,女兒抑郁,情人患癌),為了拋開一切重新開始,他決定將這次旅行當作新的起點,于是帶著自己心愛的12歲的女兒泰絲前往了威尼斯。
在威尼斯發生的一切將大衛送上了一段難以想象的旅程,他開始相信惡魔可能真正存在,并最終從懷疑論者變成了真正的信徒。在《失樂園》字里行間所提及的符號及謎語的引導下,大衛開始了一段可怕的追尋,試圖將女兒從無名者手中救回。而這個無名者就是被魔鬼附身的實體,正是它將大衛選作了自己的信使,讓大衛成為了惡魔大師……
一天下午,他在學校辦公室意外迎來了一位訪客——她是個骨瘦嶙峋的女人,前來轉達一份口頭邀請:他被要求前往威尼斯,去見證一個“現象”并提出專業意見。作為報酬,他將獲得一筆可觀的收入。此時,大衛的生活在各個方面都陷入僵局(老婆出軌,女兒抑郁,情人患癌),為了拋開一切重新開始,他決定將這次旅行當作新的起點,于是帶著自己心愛的12歲的女兒泰絲前往了威尼斯。
在威尼斯發生的一切將大衛送上了一段難以想象的旅程,他開始相信惡魔可能真正存在,并最終從懷疑論者變成了真正的信徒。在《失樂園》字里行間所提及的符號及謎語的引導下,大衛開始了一段可怕的追尋,試圖將女兒從無名者手中救回。而這個無名者就是被魔鬼附身的實體,正是它將大衛選作了自己的信使,讓大衛成為了惡魔大師……
作者簡介
安德魯·派柏,是五部廣受贊譽小說的作者,其中包括:《消失的女孩》(Lost Girls)——全球暢銷書,并入選《紐約時報》年度值得關注作品;《殺人圓環》(The Killing Circle)——入選《紐約時報》年度最佳犯罪小說。他的幾部小說正在被改編為電影劇本,并投入拍攝,其中包括《惡魔大師》,其將由羅伯特·澤梅基斯的Image Movers和環球電影公司共同制作。
胡逍揚,北京大學學士、碩士,留學意大利,現為文學翻譯與自由撰稿人。
胡逍揚,北京大學學士、碩士,留學意大利,現為文學翻譯與自由撰稿人。
名人/編輯推薦
震撼美英各國的恐怖大作首次引進國內!與《別相信任何人》《消失的愛人》并稱當代驚悚小說巔峰的“三駕馬車”!歐美半年銷量近百萬冊!
好萊塢大導演將指導本書的同名電影,掀起恐怖浪潮!羅伯特·澤米吉斯的作品部部大賣,如《阿甘正傳》《回到未來》《荒島余生》《超時空接觸》!
厚積薄發!屌絲作者終成名家!《惡魔大師》一書讓作者安德魯·派柏從無人問津的作者成為了媒體口中的“斯蒂芬·金接班人”!
好萊塢大導演將指導本書的同名電影,掀起恐怖浪潮!羅伯特·澤米吉斯的作品部部大賣,如《阿甘正傳》《回到未來》《荒島余生》《超時空接觸》!
厚積薄發!屌絲作者終成名家!《惡魔大師》一書讓作者安德魯·派柏從無人問津的作者成為了媒體口中的“斯蒂芬·金接班人”!
目次
第一部 尚未創造出的夜晚
第二部 燃燒的湖泊
第三部 穿越伊甸園
……
第二部 燃燒的湖泊
第三部 穿越伊甸園
……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座位上的一排排面孔一學期比一學期更年輕。當然,這不過是因為比起那些來來去去的新生,我在一年年變老。這種錯覺,就像從轎車的后窗向外看,你會覺得是風景在離你而去,而不是你在離它而去。
我教授這門課已經太久了,久得可以一邊胡思亂想,一邊大聲給二百來個學生講課。現在該是總結的時候了。我差不多把畢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對這首長詩的研究中,現在是時候進行最后一次嘗試,看看能不能讓幾個把臉貼在筆記本電腦上的孩子體會到它的優美。
“現在,我們進行到了最后一部分,”我對大家說,并停頓了一下,等著他們把手指從電腦鍵盤上移開。像往常一樣,我深吸了一口教室中流通不暢的空氣,以便讓自己能夠應付在背誦詩歌最后幾句時流露的巨大悲傷。
他們落下了一些自然的眼淚,但是立刻把來揩去;世界全在他們面前,在那里要選擇他們休息的地方,神意是他們的導者:他們,手挽著手,以彷徨和遲緩的腳步,穿過伊甸走他們的孤寂的路程。
伴著這些詩句,我感到女兒就在身邊。從她出生以來——甚至在她出生之前,我就在想著自己希望擁有的這個孩子——我就在不可避免地想象著,泰絲就是和我相攜走出伊甸園的那個人。
“孤獨,”我接著說,“是整部作品的主題。不是善與惡的交鋒,也不是在宣揚‘上帝對人類做出的公正判決’。這是最有力的證明——甚至比《圣經》本身還要有說服力——證實地獄是真實存在的。地獄不是一個火坑,也不是一個存在于天上或地下的地方,而就在我們之中,在我們心里的某處。在那里,我們了解自己,知道必須忍耐永恒的孤獨,忍耐被驅逐,忍耐獨自流浪。原罪真正的果實是什么?是自我!我們這對可憐的新婚夫婦被留在了自我之中,雖然相互陪伴,但永遠會在自我意識中感到孤獨。他們現在能流浪去何處?蛇說:‘哪里都可以!整個世界都是他們的!’但他們只能選擇一條‘孤單的道路’,開始一段令人害怕、甚至充滿恐懼的旅程。但從那時起到現在,這都是一條每個人必須面對的道路。”
在這兒我又停頓了一下,比上一次時間更長,恐怕有些人會以為我講完了,會站起身來,合上電腦,或者開始咳嗽。但這些都沒發生。
“問問你們自己,”我接著說,并在想象中握緊了泰絲的手,“伊甸園的大門已經關上了,現在該何去何從?”
一只胳膊立刻從人群中舉了起來。那是坐在后排的一個孩子,我之前從沒叫過他,甚至沒注意到過他。
“你說。”
“這個問題會出現在考卷上嗎?”
我叫大衛?厄爾曼,在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系任職,是神話學、基督教與猶太教宗教故事方面的專家。但我的看家本領——讓我在常春藤中擁有終身教職,并被邀請參加世界各地無用學術會議的憑借——是彌爾頓的《失樂園》,是對墮落天使、來自蛇的誘惑、亞當和夏娃以及原罪的研究。《失樂園》是一首十七世紀的史詩,當中重述了《圣經》中的故事,卻有著一種狡猾的偏頗。它表達了對撒旦的同情,把它描述為一群叛亂天使的頭領,它們厭倦了上帝的暴戾和獨裁,逃離出來,以在人間制造麻煩為業。
這是個滑稽(那些虔誠的宗教信仰者甚至可能將之稱為偽善)的營生:我一生都在教授一件我并不相信的事情。我是一個持無神論的圣經學者,是個研究魔鬼的專家,但卻相信惡魔只是一種人造產物。我寫過眾多關于神跡的論文——痊愈的麻風病患者、水變成葡萄酒、驅魔等等,但卻從未看過任何一場讓我猜不透的魔術。我對這種矛盾所做出的解釋是,一些事雖然不真實存在,但卻擁有文化上的意義。魔鬼啊,天使啊,天堂啊,地獄啊,都是我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雖然我們從未,并且也不會看見、觸摸或是證實它們。它們是我們頭腦中激蕩的一些想法。
心是它自己的地方,并且在它自己里
能把地獄做成一個天堂,天堂做成一個地獄。
這是約翰?彌爾頓通過撒旦所說的話。我碰巧相信這個老家伙——這兩個老家伙——說的沒錯。
哥倫比亞大學莫寧賽德校區的空氣聞起來很濕潤,混雜著考試前的緊張氣氛和紐約一場只下了一半的雨。我剛上完春季學期的最后一節課,心里有種又苦又甜的寬慰感。甜是因為知道一學年終于結束了(備課、辦公時間和學生評估基本都完成了),苦是因為又一年過去了(個人里程表上令人沮喪地又前進了一格)。但是,和那些在教員大會時纏著我嬌嗔抱怨的同事不同,我還是挺喜歡教書的。我喜歡看學生第一次讀到成熟文學作品時的反應,雖然我知道,大部分人來這個學校的目的是為掙大錢、做醫生、做律師或者嫁個富翁做準備,但他們并沒因此變得完全無藥可救。不是被我,但至少是被詩歌拯救。
剛過下午三點,是時候穿過鋪滿石磚的小院,回到我位于哲學樓的辦公室去了。有人把一摞遲到的期末論文偷放在了講臺上,我準備把它們撂在辦公室,然后就去中央火車站和伊萊恩?奧布萊恩會合。我們會到牡蠣酒吧喝一杯,慶祝學期結束。
雖然伊萊恩在心理系教書,我和她的關系卻比和英語系的其他同事要近。說白了,在全紐約我就和她最親近。她和我年齡相同——四十三歲,恰好是壁球場的長度,半程馬拉松的距離。在我四年前到哥倫比亞大學時,她丈夫被一場莫名其妙的中風奪去了性命,留下她做了寡婦。她擁有被我稱之為“嚴肅的幽默感”的東西:不是說她常講笑話,而是說她能夠用智慧體察世界的荒謬,讓人充滿希望,又倍覺難堪。我得承認,她是個不言不語的美人,雖然這么說可能有悖于和我已婚男人的身份。而且,根據《學校行為規范》,對一位女同事表達這樣的贊美,并且時不時和她喝上一杯,雖然像其他一切人類的交往一樣,但卻是“不恰當的”。
可我和奧布萊恩之間的確沒發生過任何不恰當的事情。在她跳上紐黑文線列車回家之前,我從沒偷吻過她。我倆也從沒用調情的方式猜想過假如把我們放到市中心的一家旅館房間里去,到底會不會發生什么事情。我們不是在壓抑自己——至少我不這么覺得,也不是在對我的婚姻表示尊重(而且我倆都知道,我妻子一年前已經為了物理系那個得意洋洋的變態,那個假笑的字符理論家威爾?約格爾,拋棄了我們的婚姻誓言)。我相信,奧布萊恩(我只在三杯馬蒂尼下肚后才開始叫她伊萊恩)和我沒讓事情往那個方向發展,是怕它會破壞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我們現在擁有的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種我從童年結束后就沒有體會過的、深沉的、無涉性別的親密關系,而且大概在童年時候我也沒和誰有過這種關系。
不過,我感覺在我和奧布萊恩的關系中有一部分還是超越了友誼,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婚外情。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會談論一些我從未和黛安談過的事情。奧布萊恩會談談自己未來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她害怕自己會成為一個單身的老女人,另一方面,她意識到自己已經習慣了凡事靠自己,而且也挺享受這種任性和放縱。按她自己的話來說,她是個“越來越無法談婚論嫁”的女人了。
而我,會談談一直以來籠罩著我的抑郁愁云。我很不情愿把自己定義為抑郁癥——因為好像半個地球的人都對自己做出了類似診斷,抑郁癥也沒法很好地概括我的情況。我的事業運不錯,婚姻一開始也充滿希望,還擁有一個被我視為最大珍寶的孩子:她是個快樂且心腸柔軟的小女孩,在她出生前,所有醫生都診斷那次懷孕會以流產結束,但她卻成了我見證過的唯一神跡。拋去這些,我一生卻都在被一只無明憂郁的黑狗追逐著。泰絲降生后,黑狗消失了一陣。但當她結束嬰兒期,成為學齡兒童后,黑狗帶著更兇猛的饑餓回來了。雖然我很愛泰絲,雖然她會在睡前在我耳邊低語“爸爸,別悲傷”,這都無法拉住黑狗的韁繩。
總有種模模糊糊的感覺在提醒我,我在某些方面不太對。不是什么可以從外表上觀察出來的東西——說實話,我乍看上去非常“有教養”,起碼黛安在我們最初開始約會時是這么驕傲地形容我的。她現在還是這么形容我,只不過語調中充滿了尖酸的內涵。從個性上來說,我也不像一個非典型的終身教授那樣,總是自怨自艾,或是充滿了難以實現的野心。不,我心里的陰影來自一個難以捉摸的地方,不是用課本就能輕易解釋的。至于說我的癥狀,有時坐地鐵,我能看見車廂門上方貼著精神健康公共服務宣傳單,上面列出了一些危險癥狀,旁邊還留出讓人打勾的方框,我覺得我一項也不吻合。易怒或具有侵略性?只是在看新聞的時候會這樣。沒有胃口?不會。從大學畢業開始,我就在試著減掉十磅肉,至今還沒成功。無法集中精力?我可是靠讀“死白男”的詩和批改大學生論文為生——集中精力是我份內的事。
確切點兒說,我的病癥不是因缺失快樂引起的,而是由于感受到了一種無法定義的東西的存在。我能感覺到,有一個看不見的同伴一整天都跟隨著我,等待一個機會,好和我建立一種更親近的關系。童年時,我曾徒勞地試圖賦予它一種個性,把它當作其他孩子也會提起的那種“想象中的朋友”。但我的這位跟隨者所做的,就僅僅是跟著我——它從不和我玩,也不保護或者安慰我。到目前為止,它唯一的興趣就是在暗處陪著我,沉默中充滿敵意。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咬文嚼字,但它帶給我更多的是一種憂郁,而不是醫學診斷的抑郁所伴隨的那種化學物質分泌不平衡。在《憂郁的解剖》(四百年前出版,那時彌爾頓還在草稿上描繪他的撒旦)一書中,羅伯特?伯頓將其稱為一種“精神的煩躁”。那種感覺就是,我將終其一生受它折磨。
奧布萊恩已經放棄勸說我去看心理醫生了。她已經對我的答復見怪不怪:“我已經有你了,干嗎還去見他們?”
我想著這些,允許自己不自覺地笑了出來,但當我看見威爾?約格爾沿著舊圖書館的石頭臺階下來的時候,笑容立刻消失了。他沖我的方向揮揮手,就好像我和他是朋友似的。他似乎患了暫時性失憶,忘了自己在過去十個月里都在干我老婆。
“大衛!能跟你說句話嗎?”
這個男人看起來像什么?像一種極端狡猾的肉食動物,長著爪子的那種。
“又是一年。”一站到我跟前他就開口這么說,戲劇化地喘著粗氣。
他斜眼看著我,露出他的牙。大概這就是被黛安稱為“迷人”的那種表情了吧,他們第一次在瑜伽課后喝咖啡時,她就被他這副樣子迷住了。當我像所有戴綠帽子的丈夫那樣不能免俗地問出那個沒用的問題:為什么是他時,黛安就告訴了我這么一個詞。她聳了聳肩,好像挺奇怪我還要問出個緣由。“他很迷人。”最后她說,像蝴蝶選擇花朵一樣,她最終落在了這么一個詞上。
“聽著,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糟。”威爾開始了,“我很抱歉事情變成了這樣。”
“什么樣?”
“不好意思,你說什么?”
“我是說,事情變成了什么樣?”
他扯平了下嘴唇,擺出副受傷的表情。他教授的內容是弦理論,我猜他在和黛安滾完床單后給她講的也是這套東西。把任何物質層層剝開,會發現它們都是由難以置信的細小線狀“弦”組成的。我對物質一竅不通,但我覺著這理論說的對,威爾?約格爾的確是由弦構成的:一些看不見的線在牽著他的眉毛和嘴角往上抬,讓他看起來像是被大師操控的木偶。
“我只是想表現得像個成年人。”他說。
“你有孩子嗎,威爾?”
“孩子?沒有。”
“你當然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因為你就是個自私的孩子。”我邊說邊大口吸著濕潤的空氣。“想表現得像個成年人?去你媽的。你以為你是在演文藝片,把我老婆帶到村里去嗎?你以為你能像《泰晤士報》那幫人一樣紅口白牙地說謊嗎?在真實生活里我們都是糟糕的演員,是真正會受傷的笨蛋。你感覺不到,你當然感覺不到,但是你給我們——給我的家庭帶來了痛苦。我們的生活讓你給毀了,一切都是過去式了。”
“聽著,大衛。我……”
“我有個女兒,”我碾過他的話繼續說,“這個小女孩現在發現事情有點兒不對頭了,她開始把自己封閉起來,我都不知道該怎么幫她。你知道看著你的孩子——你生命的全部——變得四分五裂是種什么感覺嗎?你當然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個享有最高榮譽的混蛋,靠空談混吃混喝。什么看不見的弦!你就是個一無所知的專家,一具行尸走肉。”
我沒料到自己會說這么多,但很高興自己說出了這些話。不久之后,也許我會希望跳上時間機器回到剛才這一時刻,發表一通更為精心雕琢的羞辱。但是現在,我對自己的發言還算挺滿意。
“你這么說我其實挺可笑的。”他說。
“可笑?”
“挺諷刺的。也許這么說更恰當一些。”
“‘挺諷刺的’永遠不是個更恰當的詞。”
“順便說一句,我來找你聊聊這件事是黛安的主意。”
“你這個騙子。她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但你知道她是怎么看待你的嗎?”
木偶線被提起來了,威爾?約格爾露出個勝利的微笑。
“你不在這兒。”他說,“她是這么評價你的。‘大衛?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不在這兒。’”
我無言以對,因為這是實話。這給我們的婚姻判了死刑,而我卻無力修正自己的錯誤。把我們分開的不是對工作的狂熱,不是第三者引起的分心,不是一個過分著迷的愛好,也不是男人進入中年后企圖退回自我世界所引發的距離感。我的某個部分——恰恰是黛安需要的那個部分——已經不在這兒了。最近,雖然我倆同處一室,同睡一床,但當她伸手想抓住我時,卻感覺如同想抓住月亮那么困難。如果禱告有用的話,那我真想用禱告來得知我丟失的一部分究竟在哪里。我把什么丟在了身后?抑或我其實從來沒擁有過?那個在不知不覺中吞噬我的寄生物到底是什么?
太陽出來了,整個城市開始沐浴在水蒸氣當中,圖書館的臺階閃閃發光。威爾?約格爾皺皺他的鼻子。我終于想明白了,但一切已經太晚了:他是一只貓,是路過我面前的一只黑貓。
“估計又是炎熱的一天。”他說道,隨后消失在陽光里。
我路過羅丹的思想者銅像(“他看起來像是牙疼。”泰絲有一次正確地指出),進入了哲學樓。我的辦公室在三層。此刻我沿著掛在扶手上的臺階向上走,感覺像是虛脫了一樣。
當我拐了個彎,準備走向自己的辦公室時,一陣強烈的暈眩突然襲來,我趕快扶住了墻,身子貼在墻磚上。時不時,我會被焦慮襲中,變得暫時無法呼吸,用我母親的話來說就是遭受了“暈眩咒語”。但這回不太一樣。我有種正在墜落的感覺,不是從高處,而是在落入某個沒有邊界的空間里,像是在被深淵吞噬,整棟樓——甚至整個世界都變成了一張無情的血盆大口。
然后這感覺消失了。我暗自慶幸剛才沒人看見我抱墻的可笑舉動。
的確沒人看見,除了那個坐在我辦公室門外的女人。
她歲數挺大,不可能是學生;穿著太考究,也不太像學者。我一開始覺得她大概三十五六歲,但走近之后發現她顯得更老一點。她的一把骨頭讓她看起來很像個提前衰老的飲食紊亂癥患者。說實話,她看起來好像餓壞了,制作精良的套裝和染成黑色的長發都無法遮蓋住她的脆弱。
“厄爾曼教授?”
她帶有某種歐洲口音,可能來自法國、德國或是捷克。這種口音完美地掩飾了她的國籍。
“我今天沒有辦公時間。”
“當然,你門口的卡片上寫著呢。”
“你是為哪個學生來的嗎?你孩子選了我的課?”
我已經對這種情景習以為常了:一個直升機家長,為了讓孩子進個好學校不得不貸第三份款,還得替自己不上進的“希望之星”求情。雖然我這么問她,心里卻知道她不是為學生來的。她是為我來的。
“不,不是。”她一邊回答,一邊把誤入嘴中的一縷頭發撫到一邊,“我是來替人發出邀請的。”
“我的信箱在樓下。你可以把要交給我的東西留給看門人。”
“一個口頭邀請。”
她站起身來,比我想象中要高一些。雖然瘦得讓人擔心,但骨架子看起來卻并不柔弱。她的肩膀寬闊圓潤,尖尖的下巴指向天花板。
“我在市中心有個約會。”雖然這么說著,我的手已經伸向門把手準備開門,她也已經湊近過來,準備跟著我進去。
“就耽誤您一會兒時間,教授。”她說,“我保證不讓您遲到。”
我的辦公室本來就不大,成摞的論文和塞滿書的書架讓它看起來更小了,但這反倒使它挺舒服,看起來像個學者的老巢。但這個下午,當我坐在書桌后面,而那個瘦女人坐在一個古董板凳上時,屋里的氣氛讓人窒息。通常情況下,我的學生會坐在同樣的地方求我給論文延期,或者打高一點分數,但今天屋里的空氣變得稀薄,好像突然被搬到了一個高緯度地帶。
女人理理她的裙子。她的手指很長,佩戴的唯一首飾是大拇指上的扳指,可它太松了,手一動就跟著旋轉起來。
“按常理來說,您此刻應該自我介紹一下。”我說道,意外地發現自己語調里充滿敵意。我意識到這不是一種充滿力量的挑釁,而是出于自衛,就像一只小動物會在天敵面前營造一種兇猛的假象。
“很不巧,我不能提供給您我的真實姓名。”她說,“當然,我可以告訴您一個假名。但是任何一種方式的謊言都會讓我感覺不舒服,哪怕是出于社交禮儀的善意欺騙。”
“這讓您占了上風。”
“上風?但是教授,這并不是一場比賽。我們是一邊的。”
“我們是哪邊的?”
她笑了出來,發出一種病態的格格聲,聽起來很像一聲沒控制住的咳嗽。她迅速用雙手捂住了嘴。
“您的口音,我聽不出來是哪兒的。”她停止發笑,扳指也停止轉動后,我說。
“我在很多地方都待過。”
“一個旅客?”
“一個流浪者。這么說也許更恰當一些。”
“流浪意指缺乏目的。”
“是嗎?不太可能吧,因為流浪把我帶到了您這里。”
她向前滑了兩三英寸,坐到了板凳邊緣,但感覺上她好像坐在了我桌子上一樣。我們之間的距離近得讓人不舒服,我甚至都能聞到她的味道。那種味道讓人想起塞滿稻草的谷倉,以及擁擠在一起的牲口。有一秒鐘我甚至覺得再聞下去我就該惡心了。這時她開口說話了,聲音雖然沒能遮掩住味道,但多少讓我覺得氣味不再那么濃烈。
“我是代表一位十分謹慎的客戶到這里來的。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我只能向您透露一些最必要的信息。我想您將來會贊許這一點的。”
“就像原則須知一樣。”
“是的。”她揚起頭,好像從沒聽說過這個詞一樣,“只能告訴您您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是……?”
“我的客戶需要借助您的專業知識,去弄明白一件正在發生的事,這件事目前是我客戶的首要興趣。這就是我到這里來的原因。我們想邀請您做顧問,向我們提供您的專業知識、視角,或者任何您覺得相關的東西,來幫助我們弄明白……”說到這兒她停住了,好像是在尋找一個恰當的詞,并最終在有限的選項中做出了選擇,“一種現象。”
“現象?”
“我為我的含混不清而抱歉。”
“聽起來挺神秘的嘛。”
“如我所說,非這樣不可。”
她看著我,好像是我來向她提問的一樣。她在等待我繼續這場談話,我只好照做了。
“您提到一件‘事情’,它具體是關于什么的?”
“具體?這超過了我能說的范圍。”
“就因為這是個秘密?或者還是連你自己也搞不明白?”
“這個問題提得很公平。但如果回答了您,我就背叛了對客戶的承諾。”
“可您幾乎什么都沒說。”
“冒著越權的風險我也必須告訴您,那就是我真的沒有什么可告訴您的了。教授,您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可不是。我來這兒是向您尋求答案、征求意見的。我自己可沒什么看法。”
“您親眼見過這種現象嗎?”
她咽了咽口水,頸部的皮膚緊繃起來,我都能看見她喉嚨的蠕動,就像一只老鼠鉆過床單。
“是的,我見過。”她說。
“那您的觀點是什么?”
“觀點?”
“您怎么形容它?不要從專業角度,就從您個人的角度,您是怎么想的?”
“哦,這我不能說。”她搖搖頭,眼光低垂,好像我是在和她調情,我的關注讓她覺得很尷尬似的。
“為什么不能?”
她抬眼看著我。“因為我無法給它一個確切的名字。”她說。
我應該讓她離開。雖然最開始看見她在我辦公室門口時我有點好奇,但現在這種感覺全消失了。這樣的交談最終只能以一種更深的古怪感覺結束——不是在聽到一則有趣逸聞后會有的那種,不是你能事后在晚宴上和人講起的那種,說有個瘋女人曾經向我提出過一個瘋狂的建議。因為我知道她沒瘋。通常在和傷害不了你的怪人進行簡短交談時,你能感覺到有一層面紗在保護著你,但此刻,這個面紗被撩起來了,我有一種暴露在外的感覺。
“為什么你需要我?”但我發現自己還在繼續發問,“有那么多英語系教授呢。”
“他們中間可沒什么人是惡魔大師。”
“我可不會這么形容自己。”
“不是嗎?”她咧嘴笑了,似乎想用這種輕浮的幽默感來緩解她的嚴肅。“您是著名的宗教故事、神話學還有諸如此類事物的專家,不是嗎?你難道不是專門研究《圣經》中提到過的魔鬼的嗎?尤其是關于古時候魔鬼活動的可疑記錄。我的調查有錯嗎?”
“你說的都對。但在課本之外,我對魔鬼和諸如此類的人造產物一無所知。”
“這是當然!我們可沒指望您有親身經歷。”
“誰會有呢?”
“可不是,誰會有呢!不,教授,我們需要的只是你的學術造詣。”
“我覺得你可能沒聽明白。我不信那些。”
她皺起眉,明顯沒理解我的意思。
“我不是牧師,也不是神學家。我不相信魔鬼存在,就像不相信有圣誕老人一樣。”我接著解釋,“我不去教堂,也不認為《圣經》或者其他神圣書籍中記錄的事件真正發生過,尤其是其中超自然的部分。你想找個惡魔大師,我建議你聯系一下梵蒂岡,也許他們那兒還有在認真對待這種事情的人。”
“沒錯,”她又咧嘴笑了,“他們那兒的確有。”
“你是為教會工作嗎?”
“我為一家機構工作,他們有大量預算,而且被賦予了廣泛職責。”
“那我就當你給了我肯定的回答。”
她身子前傾,尖尖的胳膊肘碰到了膝蓋。“我知道您有個約會。您現在還有時間趕到中央車站去。所以,我現在可以開始把我客戶的邀請轉述給您了嗎?”
“等等,我沒告訴過你我要去中央車站。”
“對,您沒有。”
她一動不動,好像在用靜止強調些什么。
“我可以開始了嗎?”在感覺過了整整一分鐘后,她再次問道。
我靠回椅背,示意她繼續。不用再假裝了,在這件事上我好像沒的選擇。在最后這幾分鐘內她成功地擴大了自己在屋子中的存在感,堵住了門,好像夜店的門衛一樣。
“我們會在您最快能找到的方便時刻讓您乘飛機到威尼斯,最好是明天。您將住在老城最好的酒店里——順便插一句,這家店是我的最愛。一到那兒,您會得到一個地址。不需要您提供任何書面的文件或報告,事實上,除了當時在場的人以外,我們要求您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您看到的東西。大概就是這樣。當然了,全部花銷由我們提供。公務艙往返,您還將得到一筆希望能夠令您感覺合理的咨詢費。”
說完她站起身,跨了一步走到我桌子前,從咖啡杯中挑出一只筆,在電話旁的便簽紙上潦草寫下一個數字——超過了我年薪的三分之一。
“你們付我這樣一筆錢,而我要做的就是飛到威尼斯,拜訪某人的家,然后轉身飛回來?就是這樣?”
“大體就是這樣。”
“這真是個爛故事。”
“您質疑我的誠意?”
“希望您不會感覺受到了傷害。”
“一點兒不會。我有時候會忘記,對于一些人來說,得有真憑實據才行。”
她把手伸進外套的內兜,掏出一個白色公函信封放在我桌子上,上面沒寫姓名地址。
“這是什么?”
“機票,預付的酒店預訂函,保付支票,里面有我們所談的那個價錢的四分之一,剩下的要等您回來之后付清,還有您要去的那個地方的地址。”
我的手停留在信封上方,好像一觸碰它將開啟某種“關鍵時刻”。
“當然,我們很歡迎您帶家人一起前往,”她說,“您有妻子?有個女兒?”
“有個女兒沒錯,妻子我就不好說了。”
她抬頭看向天花板,接著閉上眼睛,背誦道:
歡迎呀,結婚的愛,神秘的法律,
人類子孫的真正的源泉,樂園里的唯一的禮儀,
否則在一切的事情里共通!
“你也是個研究彌爾頓的學者?”當她重新睜開眼時我問。
“和您沒法比,教授。我只是他的崇拜者罷了。”
“沒多少崇拜者能背誦他的詩。”
“過目不忘,這是我的天賦。雖然我從沒體會過詩人所描寫的東西。人類繁衍。我沒孩子。”
最后這句坦白讓人詫異。在所有狡詐過后,她毫無顧忌地——甚至有些悲傷地坦白了自己最大的個人隱私。
“彌爾頓是對的,兒女會帶來快樂。”我說,“但是相信我,他把婚姻和樂園聯系在一起,這就有點兒過火了。”
她點點頭,但好像不是沖著我的評論,而是在對另外的事情表示確信。或許她只是說完了該說的話,在等著我的回應。所以我做出了回答。
“我不能答應。不管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確挺吸引人,但又確實不在我能力范圍之內。我不可能接受。”
“您誤解我了,教授。我不是來這兒聽您的答案的。我是來這兒轉述邀請的,僅此而已。”
“好吧。但恐怕你的客戶要失望了。”
“這種事情幾乎從沒發生過。”
她輕巧轉身,邁出屋門。我等著她對我有所表示,說句“祝您一天愉快,教授”或者揮揮她骨瘦嶙峋的手什么的,但她已經穿過大廳向樓梯走去了。
當我從椅子上起身,把頭伸出門外找她時,她已經不見了。
……
座位上的一排排面孔一學期比一學期更年輕。當然,這不過是因為比起那些來來去去的新生,我在一年年變老。這種錯覺,就像從轎車的后窗向外看,你會覺得是風景在離你而去,而不是你在離它而去。
我教授這門課已經太久了,久得可以一邊胡思亂想,一邊大聲給二百來個學生講課。現在該是總結的時候了。我差不多把畢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對這首長詩的研究中,現在是時候進行最后一次嘗試,看看能不能讓幾個把臉貼在筆記本電腦上的孩子體會到它的優美。
“現在,我們進行到了最后一部分,”我對大家說,并停頓了一下,等著他們把手指從電腦鍵盤上移開。像往常一樣,我深吸了一口教室中流通不暢的空氣,以便讓自己能夠應付在背誦詩歌最后幾句時流露的巨大悲傷。
他們落下了一些自然的眼淚,但是立刻把來揩去;世界全在他們面前,在那里要選擇他們休息的地方,神意是他們的導者:他們,手挽著手,以彷徨和遲緩的腳步,穿過伊甸走他們的孤寂的路程。
伴著這些詩句,我感到女兒就在身邊。從她出生以來——甚至在她出生之前,我就在想著自己希望擁有的這個孩子——我就在不可避免地想象著,泰絲就是和我相攜走出伊甸園的那個人。
“孤獨,”我接著說,“是整部作品的主題。不是善與惡的交鋒,也不是在宣揚‘上帝對人類做出的公正判決’。這是最有力的證明——甚至比《圣經》本身還要有說服力——證實地獄是真實存在的。地獄不是一個火坑,也不是一個存在于天上或地下的地方,而就在我們之中,在我們心里的某處。在那里,我們了解自己,知道必須忍耐永恒的孤獨,忍耐被驅逐,忍耐獨自流浪。原罪真正的果實是什么?是自我!我們這對可憐的新婚夫婦被留在了自我之中,雖然相互陪伴,但永遠會在自我意識中感到孤獨。他們現在能流浪去何處?蛇說:‘哪里都可以!整個世界都是他們的!’但他們只能選擇一條‘孤單的道路’,開始一段令人害怕、甚至充滿恐懼的旅程。但從那時起到現在,這都是一條每個人必須面對的道路。”
在這兒我又停頓了一下,比上一次時間更長,恐怕有些人會以為我講完了,會站起身來,合上電腦,或者開始咳嗽。但這些都沒發生。
“問問你們自己,”我接著說,并在想象中握緊了泰絲的手,“伊甸園的大門已經關上了,現在該何去何從?”
一只胳膊立刻從人群中舉了起來。那是坐在后排的一個孩子,我之前從沒叫過他,甚至沒注意到過他。
“你說。”
“這個問題會出現在考卷上嗎?”
我叫大衛?厄爾曼,在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系任職,是神話學、基督教與猶太教宗教故事方面的專家。但我的看家本領——讓我在常春藤中擁有終身教職,并被邀請參加世界各地無用學術會議的憑借——是彌爾頓的《失樂園》,是對墮落天使、來自蛇的誘惑、亞當和夏娃以及原罪的研究。《失樂園》是一首十七世紀的史詩,當中重述了《圣經》中的故事,卻有著一種狡猾的偏頗。它表達了對撒旦的同情,把它描述為一群叛亂天使的頭領,它們厭倦了上帝的暴戾和獨裁,逃離出來,以在人間制造麻煩為業。
這是個滑稽(那些虔誠的宗教信仰者甚至可能將之稱為偽善)的營生:我一生都在教授一件我并不相信的事情。我是一個持無神論的圣經學者,是個研究魔鬼的專家,但卻相信惡魔只是一種人造產物。我寫過眾多關于神跡的論文——痊愈的麻風病患者、水變成葡萄酒、驅魔等等,但卻從未看過任何一場讓我猜不透的魔術。我對這種矛盾所做出的解釋是,一些事雖然不真實存在,但卻擁有文化上的意義。魔鬼啊,天使啊,天堂啊,地獄啊,都是我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雖然我們從未,并且也不會看見、觸摸或是證實它們。它們是我們頭腦中激蕩的一些想法。
心是它自己的地方,并且在它自己里
能把地獄做成一個天堂,天堂做成一個地獄。
這是約翰?彌爾頓通過撒旦所說的話。我碰巧相信這個老家伙——這兩個老家伙——說的沒錯。
哥倫比亞大學莫寧賽德校區的空氣聞起來很濕潤,混雜著考試前的緊張氣氛和紐約一場只下了一半的雨。我剛上完春季學期的最后一節課,心里有種又苦又甜的寬慰感。甜是因為知道一學年終于結束了(備課、辦公時間和學生評估基本都完成了),苦是因為又一年過去了(個人里程表上令人沮喪地又前進了一格)。但是,和那些在教員大會時纏著我嬌嗔抱怨的同事不同,我還是挺喜歡教書的。我喜歡看學生第一次讀到成熟文學作品時的反應,雖然我知道,大部分人來這個學校的目的是為掙大錢、做醫生、做律師或者嫁個富翁做準備,但他們并沒因此變得完全無藥可救。不是被我,但至少是被詩歌拯救。
剛過下午三點,是時候穿過鋪滿石磚的小院,回到我位于哲學樓的辦公室去了。有人把一摞遲到的期末論文偷放在了講臺上,我準備把它們撂在辦公室,然后就去中央火車站和伊萊恩?奧布萊恩會合。我們會到牡蠣酒吧喝一杯,慶祝學期結束。
雖然伊萊恩在心理系教書,我和她的關系卻比和英語系的其他同事要近。說白了,在全紐約我就和她最親近。她和我年齡相同——四十三歲,恰好是壁球場的長度,半程馬拉松的距離。在我四年前到哥倫比亞大學時,她丈夫被一場莫名其妙的中風奪去了性命,留下她做了寡婦。她擁有被我稱之為“嚴肅的幽默感”的東西:不是說她常講笑話,而是說她能夠用智慧體察世界的荒謬,讓人充滿希望,又倍覺難堪。我得承認,她是個不言不語的美人,雖然這么說可能有悖于和我已婚男人的身份。而且,根據《學校行為規范》,對一位女同事表達這樣的贊美,并且時不時和她喝上一杯,雖然像其他一切人類的交往一樣,但卻是“不恰當的”。
可我和奧布萊恩之間的確沒發生過任何不恰當的事情。在她跳上紐黑文線列車回家之前,我從沒偷吻過她。我倆也從沒用調情的方式猜想過假如把我們放到市中心的一家旅館房間里去,到底會不會發生什么事情。我們不是在壓抑自己——至少我不這么覺得,也不是在對我的婚姻表示尊重(而且我倆都知道,我妻子一年前已經為了物理系那個得意洋洋的變態,那個假笑的字符理論家威爾?約格爾,拋棄了我們的婚姻誓言)。我相信,奧布萊恩(我只在三杯馬蒂尼下肚后才開始叫她伊萊恩)和我沒讓事情往那個方向發展,是怕它會破壞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我們現在擁有的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種我從童年結束后就沒有體會過的、深沉的、無涉性別的親密關系,而且大概在童年時候我也沒和誰有過這種關系。
不過,我感覺在我和奧布萊恩的關系中有一部分還是超越了友誼,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婚外情。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會談論一些我從未和黛安談過的事情。奧布萊恩會談談自己未來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她害怕自己會成為一個單身的老女人,另一方面,她意識到自己已經習慣了凡事靠自己,而且也挺享受這種任性和放縱。按她自己的話來說,她是個“越來越無法談婚論嫁”的女人了。
而我,會談談一直以來籠罩著我的抑郁愁云。我很不情愿把自己定義為抑郁癥——因為好像半個地球的人都對自己做出了類似診斷,抑郁癥也沒法很好地概括我的情況。我的事業運不錯,婚姻一開始也充滿希望,還擁有一個被我視為最大珍寶的孩子:她是個快樂且心腸柔軟的小女孩,在她出生前,所有醫生都診斷那次懷孕會以流產結束,但她卻成了我見證過的唯一神跡。拋去這些,我一生卻都在被一只無明憂郁的黑狗追逐著。泰絲降生后,黑狗消失了一陣。但當她結束嬰兒期,成為學齡兒童后,黑狗帶著更兇猛的饑餓回來了。雖然我很愛泰絲,雖然她會在睡前在我耳邊低語“爸爸,別悲傷”,這都無法拉住黑狗的韁繩。
總有種模模糊糊的感覺在提醒我,我在某些方面不太對。不是什么可以從外表上觀察出來的東西——說實話,我乍看上去非常“有教養”,起碼黛安在我們最初開始約會時是這么驕傲地形容我的。她現在還是這么形容我,只不過語調中充滿了尖酸的內涵。從個性上來說,我也不像一個非典型的終身教授那樣,總是自怨自艾,或是充滿了難以實現的野心。不,我心里的陰影來自一個難以捉摸的地方,不是用課本就能輕易解釋的。至于說我的癥狀,有時坐地鐵,我能看見車廂門上方貼著精神健康公共服務宣傳單,上面列出了一些危險癥狀,旁邊還留出讓人打勾的方框,我覺得我一項也不吻合。易怒或具有侵略性?只是在看新聞的時候會這樣。沒有胃口?不會。從大學畢業開始,我就在試著減掉十磅肉,至今還沒成功。無法集中精力?我可是靠讀“死白男”的詩和批改大學生論文為生——集中精力是我份內的事。
確切點兒說,我的病癥不是因缺失快樂引起的,而是由于感受到了一種無法定義的東西的存在。我能感覺到,有一個看不見的同伴一整天都跟隨著我,等待一個機會,好和我建立一種更親近的關系。童年時,我曾徒勞地試圖賦予它一種個性,把它當作其他孩子也會提起的那種“想象中的朋友”。但我的這位跟隨者所做的,就僅僅是跟著我——它從不和我玩,也不保護或者安慰我。到目前為止,它唯一的興趣就是在暗處陪著我,沉默中充滿敵意。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咬文嚼字,但它帶給我更多的是一種憂郁,而不是醫學診斷的抑郁所伴隨的那種化學物質分泌不平衡。在《憂郁的解剖》(四百年前出版,那時彌爾頓還在草稿上描繪他的撒旦)一書中,羅伯特?伯頓將其稱為一種“精神的煩躁”。那種感覺就是,我將終其一生受它折磨。
奧布萊恩已經放棄勸說我去看心理醫生了。她已經對我的答復見怪不怪:“我已經有你了,干嗎還去見他們?”
我想著這些,允許自己不自覺地笑了出來,但當我看見威爾?約格爾沿著舊圖書館的石頭臺階下來的時候,笑容立刻消失了。他沖我的方向揮揮手,就好像我和他是朋友似的。他似乎患了暫時性失憶,忘了自己在過去十個月里都在干我老婆。
“大衛!能跟你說句話嗎?”
這個男人看起來像什么?像一種極端狡猾的肉食動物,長著爪子的那種。
“又是一年。”一站到我跟前他就開口這么說,戲劇化地喘著粗氣。
他斜眼看著我,露出他的牙。大概這就是被黛安稱為“迷人”的那種表情了吧,他們第一次在瑜伽課后喝咖啡時,她就被他這副樣子迷住了。當我像所有戴綠帽子的丈夫那樣不能免俗地問出那個沒用的問題:為什么是他時,黛安就告訴了我這么一個詞。她聳了聳肩,好像挺奇怪我還要問出個緣由。“他很迷人。”最后她說,像蝴蝶選擇花朵一樣,她最終落在了這么一個詞上。
“聽著,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糟。”威爾開始了,“我很抱歉事情變成了這樣。”
“什么樣?”
“不好意思,你說什么?”
“我是說,事情變成了什么樣?”
他扯平了下嘴唇,擺出副受傷的表情。他教授的內容是弦理論,我猜他在和黛安滾完床單后給她講的也是這套東西。把任何物質層層剝開,會發現它們都是由難以置信的細小線狀“弦”組成的。我對物質一竅不通,但我覺著這理論說的對,威爾?約格爾的確是由弦構成的:一些看不見的線在牽著他的眉毛和嘴角往上抬,讓他看起來像是被大師操控的木偶。
“我只是想表現得像個成年人。”他說。
“你有孩子嗎,威爾?”
“孩子?沒有。”
“你當然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因為你就是個自私的孩子。”我邊說邊大口吸著濕潤的空氣。“想表現得像個成年人?去你媽的。你以為你是在演文藝片,把我老婆帶到村里去嗎?你以為你能像《泰晤士報》那幫人一樣紅口白牙地說謊嗎?在真實生活里我們都是糟糕的演員,是真正會受傷的笨蛋。你感覺不到,你當然感覺不到,但是你給我們——給我的家庭帶來了痛苦。我們的生活讓你給毀了,一切都是過去式了。”
“聽著,大衛。我……”
“我有個女兒,”我碾過他的話繼續說,“這個小女孩現在發現事情有點兒不對頭了,她開始把自己封閉起來,我都不知道該怎么幫她。你知道看著你的孩子——你生命的全部——變得四分五裂是種什么感覺嗎?你當然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個享有最高榮譽的混蛋,靠空談混吃混喝。什么看不見的弦!你就是個一無所知的專家,一具行尸走肉。”
我沒料到自己會說這么多,但很高興自己說出了這些話。不久之后,也許我會希望跳上時間機器回到剛才這一時刻,發表一通更為精心雕琢的羞辱。但是現在,我對自己的發言還算挺滿意。
“你這么說我其實挺可笑的。”他說。
“可笑?”
“挺諷刺的。也許這么說更恰當一些。”
“‘挺諷刺的’永遠不是個更恰當的詞。”
“順便說一句,我來找你聊聊這件事是黛安的主意。”
“你這個騙子。她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但你知道她是怎么看待你的嗎?”
木偶線被提起來了,威爾?約格爾露出個勝利的微笑。
“你不在這兒。”他說,“她是這么評價你的。‘大衛?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不在這兒。’”
我無言以對,因為這是實話。這給我們的婚姻判了死刑,而我卻無力修正自己的錯誤。把我們分開的不是對工作的狂熱,不是第三者引起的分心,不是一個過分著迷的愛好,也不是男人進入中年后企圖退回自我世界所引發的距離感。我的某個部分——恰恰是黛安需要的那個部分——已經不在這兒了。最近,雖然我倆同處一室,同睡一床,但當她伸手想抓住我時,卻感覺如同想抓住月亮那么困難。如果禱告有用的話,那我真想用禱告來得知我丟失的一部分究竟在哪里。我把什么丟在了身后?抑或我其實從來沒擁有過?那個在不知不覺中吞噬我的寄生物到底是什么?
太陽出來了,整個城市開始沐浴在水蒸氣當中,圖書館的臺階閃閃發光。威爾?約格爾皺皺他的鼻子。我終于想明白了,但一切已經太晚了:他是一只貓,是路過我面前的一只黑貓。
“估計又是炎熱的一天。”他說道,隨后消失在陽光里。
我路過羅丹的思想者銅像(“他看起來像是牙疼。”泰絲有一次正確地指出),進入了哲學樓。我的辦公室在三層。此刻我沿著掛在扶手上的臺階向上走,感覺像是虛脫了一樣。
當我拐了個彎,準備走向自己的辦公室時,一陣強烈的暈眩突然襲來,我趕快扶住了墻,身子貼在墻磚上。時不時,我會被焦慮襲中,變得暫時無法呼吸,用我母親的話來說就是遭受了“暈眩咒語”。但這回不太一樣。我有種正在墜落的感覺,不是從高處,而是在落入某個沒有邊界的空間里,像是在被深淵吞噬,整棟樓——甚至整個世界都變成了一張無情的血盆大口。
然后這感覺消失了。我暗自慶幸剛才沒人看見我抱墻的可笑舉動。
的確沒人看見,除了那個坐在我辦公室門外的女人。
她歲數挺大,不可能是學生;穿著太考究,也不太像學者。我一開始覺得她大概三十五六歲,但走近之后發現她顯得更老一點。她的一把骨頭讓她看起來很像個提前衰老的飲食紊亂癥患者。說實話,她看起來好像餓壞了,制作精良的套裝和染成黑色的長發都無法遮蓋住她的脆弱。
“厄爾曼教授?”
她帶有某種歐洲口音,可能來自法國、德國或是捷克。這種口音完美地掩飾了她的國籍。
“我今天沒有辦公時間。”
“當然,你門口的卡片上寫著呢。”
“你是為哪個學生來的嗎?你孩子選了我的課?”
我已經對這種情景習以為常了:一個直升機家長,為了讓孩子進個好學校不得不貸第三份款,還得替自己不上進的“希望之星”求情。雖然我這么問她,心里卻知道她不是為學生來的。她是為我來的。
“不,不是。”她一邊回答,一邊把誤入嘴中的一縷頭發撫到一邊,“我是來替人發出邀請的。”
“我的信箱在樓下。你可以把要交給我的東西留給看門人。”
“一個口頭邀請。”
她站起身來,比我想象中要高一些。雖然瘦得讓人擔心,但骨架子看起來卻并不柔弱。她的肩膀寬闊圓潤,尖尖的下巴指向天花板。
“我在市中心有個約會。”雖然這么說著,我的手已經伸向門把手準備開門,她也已經湊近過來,準備跟著我進去。
“就耽誤您一會兒時間,教授。”她說,“我保證不讓您遲到。”
我的辦公室本來就不大,成摞的論文和塞滿書的書架讓它看起來更小了,但這反倒使它挺舒服,看起來像個學者的老巢。但這個下午,當我坐在書桌后面,而那個瘦女人坐在一個古董板凳上時,屋里的氣氛讓人窒息。通常情況下,我的學生會坐在同樣的地方求我給論文延期,或者打高一點分數,但今天屋里的空氣變得稀薄,好像突然被搬到了一個高緯度地帶。
女人理理她的裙子。她的手指很長,佩戴的唯一首飾是大拇指上的扳指,可它太松了,手一動就跟著旋轉起來。
“按常理來說,您此刻應該自我介紹一下。”我說道,意外地發現自己語調里充滿敵意。我意識到這不是一種充滿力量的挑釁,而是出于自衛,就像一只小動物會在天敵面前營造一種兇猛的假象。
“很不巧,我不能提供給您我的真實姓名。”她說,“當然,我可以告訴您一個假名。但是任何一種方式的謊言都會讓我感覺不舒服,哪怕是出于社交禮儀的善意欺騙。”
“這讓您占了上風。”
“上風?但是教授,這并不是一場比賽。我們是一邊的。”
“我們是哪邊的?”
她笑了出來,發出一種病態的格格聲,聽起來很像一聲沒控制住的咳嗽。她迅速用雙手捂住了嘴。
“您的口音,我聽不出來是哪兒的。”她停止發笑,扳指也停止轉動后,我說。
“我在很多地方都待過。”
“一個旅客?”
“一個流浪者。這么說也許更恰當一些。”
“流浪意指缺乏目的。”
“是嗎?不太可能吧,因為流浪把我帶到了您這里。”
她向前滑了兩三英寸,坐到了板凳邊緣,但感覺上她好像坐在了我桌子上一樣。我們之間的距離近得讓人不舒服,我甚至都能聞到她的味道。那種味道讓人想起塞滿稻草的谷倉,以及擁擠在一起的牲口。有一秒鐘我甚至覺得再聞下去我就該惡心了。這時她開口說話了,聲音雖然沒能遮掩住味道,但多少讓我覺得氣味不再那么濃烈。
“我是代表一位十分謹慎的客戶到這里來的。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我只能向您透露一些最必要的信息。我想您將來會贊許這一點的。”
“就像原則須知一樣。”
“是的。”她揚起頭,好像從沒聽說過這個詞一樣,“只能告訴您您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是……?”
“我的客戶需要借助您的專業知識,去弄明白一件正在發生的事,這件事目前是我客戶的首要興趣。這就是我到這里來的原因。我們想邀請您做顧問,向我們提供您的專業知識、視角,或者任何您覺得相關的東西,來幫助我們弄明白……”說到這兒她停住了,好像是在尋找一個恰當的詞,并最終在有限的選項中做出了選擇,“一種現象。”
“現象?”
“我為我的含混不清而抱歉。”
“聽起來挺神秘的嘛。”
“如我所說,非這樣不可。”
她看著我,好像是我來向她提問的一樣。她在等待我繼續這場談話,我只好照做了。
“您提到一件‘事情’,它具體是關于什么的?”
“具體?這超過了我能說的范圍。”
“就因為這是個秘密?或者還是連你自己也搞不明白?”
“這個問題提得很公平。但如果回答了您,我就背叛了對客戶的承諾。”
“可您幾乎什么都沒說。”
“冒著越權的風險我也必須告訴您,那就是我真的沒有什么可告訴您的了。教授,您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可不是。我來這兒是向您尋求答案、征求意見的。我自己可沒什么看法。”
“您親眼見過這種現象嗎?”
她咽了咽口水,頸部的皮膚緊繃起來,我都能看見她喉嚨的蠕動,就像一只老鼠鉆過床單。
“是的,我見過。”她說。
“那您的觀點是什么?”
“觀點?”
“您怎么形容它?不要從專業角度,就從您個人的角度,您是怎么想的?”
“哦,這我不能說。”她搖搖頭,眼光低垂,好像我是在和她調情,我的關注讓她覺得很尷尬似的。
“為什么不能?”
她抬眼看著我。“因為我無法給它一個確切的名字。”她說。
我應該讓她離開。雖然最開始看見她在我辦公室門口時我有點好奇,但現在這種感覺全消失了。這樣的交談最終只能以一種更深的古怪感覺結束——不是在聽到一則有趣逸聞后會有的那種,不是你能事后在晚宴上和人講起的那種,說有個瘋女人曾經向我提出過一個瘋狂的建議。因為我知道她沒瘋。通常在和傷害不了你的怪人進行簡短交談時,你能感覺到有一層面紗在保護著你,但此刻,這個面紗被撩起來了,我有一種暴露在外的感覺。
“為什么你需要我?”但我發現自己還在繼續發問,“有那么多英語系教授呢。”
“他們中間可沒什么人是惡魔大師。”
“我可不會這么形容自己。”
“不是嗎?”她咧嘴笑了,似乎想用這種輕浮的幽默感來緩解她的嚴肅。“您是著名的宗教故事、神話學還有諸如此類事物的專家,不是嗎?你難道不是專門研究《圣經》中提到過的魔鬼的嗎?尤其是關于古時候魔鬼活動的可疑記錄。我的調查有錯嗎?”
“你說的都對。但在課本之外,我對魔鬼和諸如此類的人造產物一無所知。”
“這是當然!我們可沒指望您有親身經歷。”
“誰會有呢?”
“可不是,誰會有呢!不,教授,我們需要的只是你的學術造詣。”
“我覺得你可能沒聽明白。我不信那些。”
她皺起眉,明顯沒理解我的意思。
“我不是牧師,也不是神學家。我不相信魔鬼存在,就像不相信有圣誕老人一樣。”我接著解釋,“我不去教堂,也不認為《圣經》或者其他神圣書籍中記錄的事件真正發生過,尤其是其中超自然的部分。你想找個惡魔大師,我建議你聯系一下梵蒂岡,也許他們那兒還有在認真對待這種事情的人。”
“沒錯,”她又咧嘴笑了,“他們那兒的確有。”
“你是為教會工作嗎?”
“我為一家機構工作,他們有大量預算,而且被賦予了廣泛職責。”
“那我就當你給了我肯定的回答。”
她身子前傾,尖尖的胳膊肘碰到了膝蓋。“我知道您有個約會。您現在還有時間趕到中央車站去。所以,我現在可以開始把我客戶的邀請轉述給您了嗎?”
“等等,我沒告訴過你我要去中央車站。”
“對,您沒有。”
她一動不動,好像在用靜止強調些什么。
“我可以開始了嗎?”在感覺過了整整一分鐘后,她再次問道。
我靠回椅背,示意她繼續。不用再假裝了,在這件事上我好像沒的選擇。在最后這幾分鐘內她成功地擴大了自己在屋子中的存在感,堵住了門,好像夜店的門衛一樣。
“我們會在您最快能找到的方便時刻讓您乘飛機到威尼斯,最好是明天。您將住在老城最好的酒店里——順便插一句,這家店是我的最愛。一到那兒,您會得到一個地址。不需要您提供任何書面的文件或報告,事實上,除了當時在場的人以外,我們要求您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您看到的東西。大概就是這樣。當然了,全部花銷由我們提供。公務艙往返,您還將得到一筆希望能夠令您感覺合理的咨詢費。”
說完她站起身,跨了一步走到我桌子前,從咖啡杯中挑出一只筆,在電話旁的便簽紙上潦草寫下一個數字——超過了我年薪的三分之一。
“你們付我這樣一筆錢,而我要做的就是飛到威尼斯,拜訪某人的家,然后轉身飛回來?就是這樣?”
“大體就是這樣。”
“這真是個爛故事。”
“您質疑我的誠意?”
“希望您不會感覺受到了傷害。”
“一點兒不會。我有時候會忘記,對于一些人來說,得有真憑實據才行。”
她把手伸進外套的內兜,掏出一個白色公函信封放在我桌子上,上面沒寫姓名地址。
“這是什么?”
“機票,預付的酒店預訂函,保付支票,里面有我們所談的那個價錢的四分之一,剩下的要等您回來之后付清,還有您要去的那個地方的地址。”
我的手停留在信封上方,好像一觸碰它將開啟某種“關鍵時刻”。
“當然,我們很歡迎您帶家人一起前往,”她說,“您有妻子?有個女兒?”
“有個女兒沒錯,妻子我就不好說了。”
她抬頭看向天花板,接著閉上眼睛,背誦道:
歡迎呀,結婚的愛,神秘的法律,
人類子孫的真正的源泉,樂園里的唯一的禮儀,
否則在一切的事情里共通!
“你也是個研究彌爾頓的學者?”當她重新睜開眼時我問。
“和您沒法比,教授。我只是他的崇拜者罷了。”
“沒多少崇拜者能背誦他的詩。”
“過目不忘,這是我的天賦。雖然我從沒體會過詩人所描寫的東西。人類繁衍。我沒孩子。”
最后這句坦白讓人詫異。在所有狡詐過后,她毫無顧忌地——甚至有些悲傷地坦白了自己最大的個人隱私。
“彌爾頓是對的,兒女會帶來快樂。”我說,“但是相信我,他把婚姻和樂園聯系在一起,這就有點兒過火了。”
她點點頭,但好像不是沖著我的評論,而是在對另外的事情表示確信。或許她只是說完了該說的話,在等著我的回應。所以我做出了回答。
“我不能答應。不管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確挺吸引人,但又確實不在我能力范圍之內。我不可能接受。”
“您誤解我了,教授。我不是來這兒聽您的答案的。我是來這兒轉述邀請的,僅此而已。”
“好吧。但恐怕你的客戶要失望了。”
“這種事情幾乎從沒發生過。”
她輕巧轉身,邁出屋門。我等著她對我有所表示,說句“祝您一天愉快,教授”或者揮揮她骨瘦嶙峋的手什么的,但她已經穿過大廳向樓梯走去了。
當我從椅子上起身,把頭伸出門外找她時,她已經不見了。
……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