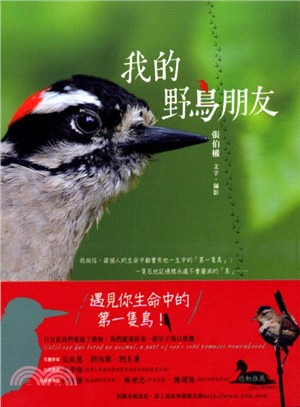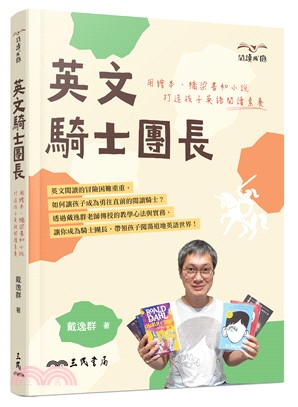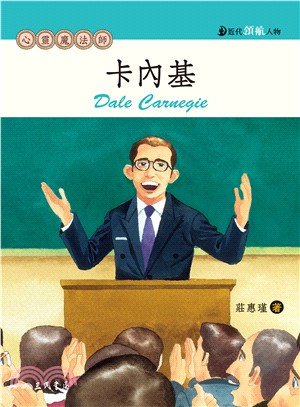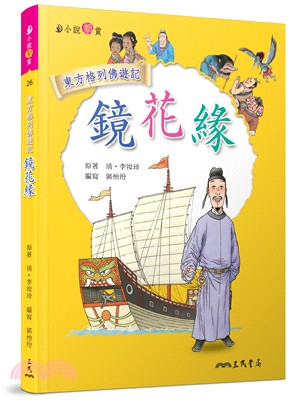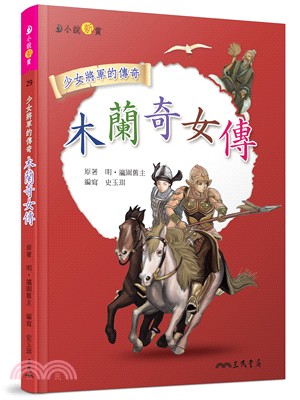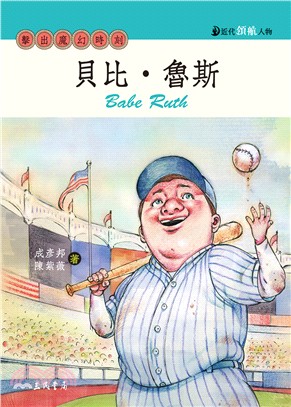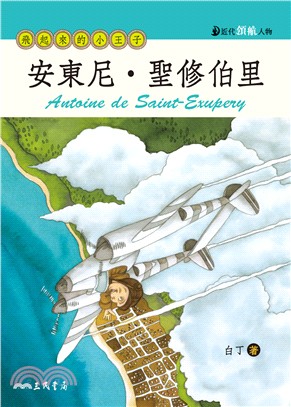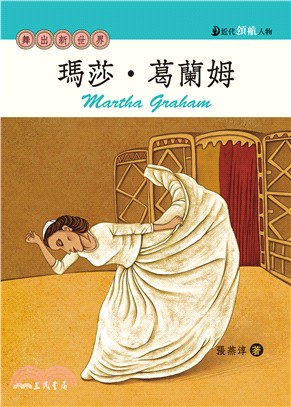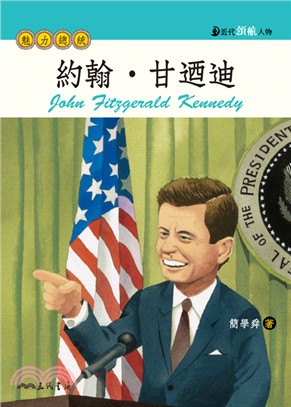我的野鳥朋友
商品資訊
系列名:生活館-Taiwan Style
ISBN13:9789573273431
出版社:遠流
作者:張伯權
出版日:2014/02/01
裝訂/頁數:平裝/240頁
規格:17cm*13cm*1.5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565【七年級】
商品簡介
★精采野鳥攝影近三百張,捕捉鳥類的一顰一笑、日常點滴
★有別於坊間鳥書,多著重科普硬知識的傳遞,本書從生活出發,以感性的文學筆調、生動的影像視覺,引領讀者走進充滿靈犀與哲思的野鳥世界。
★鳥事知多少:介紹書中野鳥不為人知的生活習性及傳奇故事等,如五色鳥的巢洞「裝潢」狀況如何、夜鷺為何在夜間行動、秧雞飛不飛、什麼叫做「猛禽」、翠鳥怎麼洗澡、撿到落地的小鳥怎麼辦等大大小小的知識整理。
作者簡介
張伯權
台北人,現旅居加拿大。
會走上「鳥」路,說是「意外」,也可以說是自己的「選擇」。念國小時候,對大自然就極為著迷。從年輕到現在,人文寫作與自然生態攝影,一直是他從未放棄的兩個最大興趣。
經過了長期觀察野鳥生態,從2007年起陸續於《講義》雜誌發表野鳥文章,分享他的快樂鳥日子。
著作/
文學筆記 (時報)
如何看懂美國廣告 (河馬文化)
聯副三十年世界文學大系《評論卷》(聯經)收入四篇評論:〈約伯的末裔-當代意第緒文學〉、〈旋風中的聲音-史特林堡〉、〈近代俄國流亡文學〉、〈彭巴草原的豐收季-南美新小說的風貌〉
譯作/
《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楓城)、《卡夫卡的故事》(時報) 、《噢,父親--卡夫卡給父親的信》(楓城)等。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一】
「真高興遇見你!」
生態作家 范欽慧
我們都知道,鳥兒有所謂的「銘印」現象,會把出生後第一個看到的動物視為母親。最初印象往往帶來最深的記憶,對人類來說也是如此。一隻在黑暗中發光的鳥,成為作者生命中的第一隻鳥。而我則是八歲時去南港玩,無意中發現了一隻五顏六色的鳥,立刻像是發現寶貝一樣,大聲吆喝家人來看,就在那瞬間,五色鳥從我眼中消失了,留下我無法解釋的迷惑與空洞。
長大後我也成了鳥友,並且熱愛聆聽鳥語,或許是為了要彌補當年的遺憾。對很多人來說,鳥兒就像是走進大自然的邀請卡,一但你開始學會看鳥,似乎很快的你就會注意到其他自然的布局。然而,要掌握一隻鳥的外觀,透過日益先進的攝影器材並非難事,但是要能夠對鳥寄情寓意,並抒發哲思,讓人能產生嚮往仰慕之情,此番閱歷實屬不同的創造層次。因為我們欣賞到的,不只是透過作者的見解,更是透過細膩的文字探微,與自我生命相融的獨特風景。這正好可以呼應作者所言:「你讀到的比我寫得更多。」
古人說,「情必近於痴而始真」,人生痴者,必定貪戀於美麗。於是尋尋覓覓的路上,不僅止於遊山玩水間的隨性相遇,更是專注於捕捉片刻光影所觸動的美麗音息。《我的野鳥朋友》所帶來的情趣,就在那份「痴」上。但是這番痴情,絕非懵懂年少所能體會,除非你有少年沈復的慧黠,能在童稚階段,便能發掘物外之趣,大部分的人,似乎要到中年之後,歷經了人生的起伏波動,才能逐漸領略更多的細節與情意,因此正處在生命秋季中的我,似乎更能感受到作者所描繪的平靜與虔誠。但是針對不同階段或需求的人,都能在這本書上獲得啟發,比如從鴛鴦所衍生的愛情經營理論,以至於黑冠麻鷺「自欺欺人」的獨門工夫,都會讓你拍案叫絕。
跟鳥兒做朋友,這樣的交心難免「一廂情願」,卻充滿著「自然療癒」的力量。如果對生命不夠敏感,或許也不會被這群飛羽所吸引而一路追隨,也因為對生命敏感,卻無法忍受紅塵間對生命的箝制與扭曲,於是走進這些生命的個別世界中,找到不同的彩虹或寶石,觀詳出不同的複雜與簡單,於是一隻小小山雀的身手,就能讓人開了眼、開了心,回過頭來,似乎更能明白自己當下所處的情境,也能從自然呼喚中,聽到自己內心的歌聲。就在萬物騷動間,自己的某些部分也就跟著甦醒了。
不論你是否原為賞鳥一族,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都能讓你在文字的風情間,欣賞到一部部精彩的「生態影片」。雖然這本書所記錄的鳥兒我都不陌生,但是很多篇章都讓我重新回味了在野外觀察的情節,甚至提供了更完整的劇情,尤其是當我讀了翠鳥釣魚的過程,黑冠麻鷺與蚯蚓的拉鋸戰,以及綠頭鴨的霸凌事件,都讓我身歷其境,情緒深受牽動與震撼。
我想不論對作者而言,或是對我自己來說,一但愛上鳥,那曾經相遇的鶯鶯燕燕,所留下的風韻傳奇只會更加豐富精彩。最後,我想透過一隻我最鍾愛的鳥兒「冠羽畫眉」作為結尾,牠是台灣的特有種鳥類,鳴叫聲也很像台語的「吐米酒」,但是有人說其實那是一句英文,我想藉此獻上此鳥語送給本書的作者,以及書中所有可愛的野鳥朋友們,那就是:Nice to meet you!(真高興遇見你!)
【推薦序二】
換個角度來「愛鳥及屋」
自然作家 劉伯樂
「去-去-去!沒有蟲了!」黃尾鴝從手中叼走了小蟲以後,老李狠下了決心。他做勢威嚇,甚至做出丟擊石塊的大動作驅趕黃尾鴝。我看著他眼角泛著淚水,騎上機車頭也不回掉頭離開。關渡老李因愛鳥而餵食野鳥,種下了人與鳥之間不應該有的感情。讓候鳥忘記北返的生理時間,成為關渡平原人人傳誦的軼事變文。
賞鳥、愛鳥、保護野鳥、攝影野鳥,諸多有關人與鳥之間以及野鳥環境相關情事,從黑面琵鷺到丹頂鶴事件,儼然已經是社會上膾炙人口的話題,也因此造就不少愛鳥達人。
《我的野鳥朋友》一書,讓我看見另一個執著鳥事的人,以攝影和寫作的方式愛鳥。
我並不認識本書作者,不知道他為何賞鳥?如何攝鳥?初讀本書,看著他拍攝的野鳥作品,讀了他的文章,知道作者對於野鳥的興趣,並不只是在乎那些網路上的攝鳥大師「睍睆黃鳥,載好其音」而已。有關鳥類的多樣性、獨特性,與環境的關係、人類的互動,更加上自己觀察得到的見解,舉凡鶯鶯燕燕,任何鳳毛鱗爪,鳥類的知識、賞鳥的心情、攝影心得,鉅細靡遺都在他的字裡行間斑斑可見,而且樂於和大家分享。再看那些圖片,記錄著野鳥的一舉一動,幀幀都是得來不易的生態佳作。如果和那些所謂「大師」的作品相比,始知「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我也是個愛鳥的人,喜歡野鳥生態繪畫。為了取得鳥類生態知識,也從事野鳥攝影。和作者一樣,用謙卑和求知若渴的心態去親近野鳥。舉凡和鳥類相關的環境、田野資訊,都要明察秋毫,也都必須事必躬親、身體力行。為達到這個目的,上山下海尋鳥蹤、求鳥影,想盡辦法取得野鳥的各種資訊自不用說。
藉著拍攝野鳥的過程,我也看到了環境、社會問題和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為什麼小水鴨喜歡聚集在華江橋下的河面上呢?想當然是為了食物。淡水河流域河水汙染由來已久,汙水孳生蚊蚋,魚蝦、水族聚集,於是雁鴨翔集覓食。當初設立「雁鴨公園」是為了要保護野鳥;但又期望「河清水清」還我一條乾淨的河流,如何兩全,恐得甚費思量。
作者愛鳥,把野鳥當作朋友。在野外遇見朋友,和朋友將心比心,關心自己也關心朋友。倘若我們不能「愛屋及鳥」,是不是也可以換個角度來「愛鳥及屋」?大家一起來愛鳥,交換不同的愛鳥心得,結交野鳥朋友,集合朋友一起來鞭策、改善環境,使人與鳥都可以安適而生存。
序
尋找第一隻鳥
我以為,每個人在塵世歲月的生命中,都應當去尋找他的「第一隻鳥」。
這隻鳥的種籽,常常不知在什麼時候埋進了我們的心底,也不知何時才會萌芽抽長。但是我深深相信,總有一天時間到了就會發生。
也許,就在你翻讀這本書,看到這篇序言之後。也或許有一天,當你第一次領著孩子走入野地、親近水邊、踏進林裏,不知不覺就在孩子的心田裏,埋下了那一顆他一生「第一隻鳥」的種籽。
許多年來,我在曠野裏認識了不少「野鳥」朋友,陸陸續續寫了幾篇「鳥」文章,說了一些「鳥」故事。現在,我把這些故事收集在這裏,成了一本書,迫不及待想與你分享。
走進大自然親近飛鳥,接觸各種大大小小的野生動物,始終帶給我心靈上極大的慰藉與喜悅。這些野地裏的生命,不僅鼓舞我度過生活中多個「低潮」,更讓我從牠們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重新「認識」了自己。反過來說,也讓我有能力,能夠重新審視這些以前被我疏忽的野生動物的生生息息;也逐漸明白了,在同一片藍天白雲下,牠們與我同時存在這同一個「時間」和「空間」的意義。
每次我在野地與野鳥相遇,每次總會學到一些事情。我從大自然、野鳥朋友身上學習來的,教導了我從今而後該如何重新在我的同類--「人」與「人」之間行走。如今,我不僅明白了應當如何輕輕撫摸一片葉子,也知道應該如何去握緊一個人的手--當這隻手需要我牽握的時候。
我把我的一些「思想」與「情感」,用心而努力地揉進了每一個字裏,至於說了些什麼,只有請正在翻閱這本書的你,從字裏行間去探索。我深深相信,你所「讀」到的會比我「寫」的更多。
※
當我們下定決心,要走進野地尋找生命裏的「第一隻鳥」時,請容我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時時刻刻莫忘記,人也是一種「動物」,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人,離開了大自然,並沒有因此離開了「野蠻」,反而失去了大自然的「包容」與「慰撫」。
如果此刻我們還無法接受,「其他動物與我們人類是對等的」這個觀念,至少我們應該勇於承認,其他動物也當擁有一些生命最基本的權利--譬如「生存」以及「免於懼怕」。雖然我不得不承認,即使今天的社會我們身邊仍然有一些「人」,在某些角落,為了這兩項最基本的權利,還在掙扎、奮鬥。
我誠心祝福你,很快就能夠找到你生命中的「第一隻鳥」。
我們會發現,從今而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原來,許多生命的「美麗」與「感動」,就發生在我們日常的身邊,猶如我們的家人與朋友,雖然與我們一樣的平凡,卻是如此的「真實」與「珍貴」。以前,也許因為「習以為常」或「理所當然」,所以看不見了。
我十分同意法國小說家法郎士說過的一句話,「只有當我們愛過了動物,我們靈魂的某一部分才得以甦醒。」(Until one has loved an animal, a part of one's soul remains unawakened.) 。這句話我認為更可以延伸為,「只有當我們懂得,而且也有了能力去愛別人的時候,我們的軀殼才具有了靈魂。」
※
除了台灣,我幸運地也能有機會在加拿大西岸的英屬哥倫比亞省觀察野鳥。這樣的機會,不僅擴大了我的視野與觀點,也豐富了我的野鳥經驗。英屬哥倫比亞省差不多有二十六個台灣那麼大,長期留棲在此繁殖的鳥類,大約有三百種左右。很多鳥兒我們台灣也有,但也有不少的鳥兒只有這裏才看得到。譬如夜鷺,雖然在這裏也看得見,不過最多時候,用不到五根手指就數盡了。又譬如知更鳥「旅鶇」,台灣看不到,不過如果有機會讓我們的赤腹鶇與知更鳥並棲樹頭,看到的人一定多數認為,牠們根本就是同父同母兄弟。
野鳥是沒有國界的。不管棲住地球上那個角落,牠們的家園沒有籬笆,也沒有圍牆,即使住在台灣同一個島嶼,也沒有哪一種鳥,專門隸屬於台南四草,或是宜蘭五十二甲;也沒有哪一種鳥的戶籍固定在台北關渡,或是屏東三地門。野鳥天生應該自由,所以才長有翅膀。不是嗎?
※
我時時告訴自己,野鳥固然美麗,不應該僅止於「欣賞」,我們應該跟牠們做朋友。一直以來,我對「賞鳥」一詞並不完全認同。我認為如果鳥兒只是用來「欣賞」,只是用來「看」得讓自己高興,那麼鳥兒不過是我們身外千千萬萬種的「物」之一。我們對待朋友,不會這樣的。我會想分享他的歡喜,也會想了解他的悲傷;如果可以,我很願意分擔。
我在野地裏,找到了我在人類社會裏一直在尋找,但卻不容易的「友情」。
※
最後,有幾個人我要向他們表示謝意。一位是《講義》雜誌社社長林獻章,因為《講義》我才有機會寫出這些「鳥」文章,一個月寫一篇,竟也連寫了好幾年。還有,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李傳理、出版二部總編輯兼總監黃靜宜,尤其主編張尊禎與美術編輯張小珊,謝謝他/她們讓這些「鳥」文章,變成了一本美麗精緻的「鳥」書。因為這本書的編輯,讓我深深體會了團隊工作的專業精神。還有,《講義》的胡佩瑛與蘇乃霙兩位主編,也要說一聲謝謝。
猶記得,當我寫〈似曾相似「燕」歸來〉這一篇的時候,心頭一直有一份極「特殊」的感覺。我母親,是麻豆鄉下長大的,姓林,單名「燕」。是她,在我的心田裏播下了我生命中「第一隻鳥」的種籽,雖然她並不知道。即使我跟她解釋了,她也不以為如此。可是,我可以感覺她心裏的高興。
前言:
《寫在前面的話》
走出荒野
終於我知道了,我走進大自然,
為的是要走出荒野。
回想自己多年來行走於大自然,放身無名的野外,追尋的就是實踐自我,希望做一個雙腳踩入大地--歲月的行者、時間的旅人。如今山林愈走愈遠,溪水愈涉愈深,路愈走愈荒野,但願一顆心也能愈走愈靜。
走進大自然,懷的是「尋找」的念頭
炎炎夏日吃西瓜的方式有好幾種,我想,人活著的方式也不應該只有一種。若干年來默默蜷跼城市的一角,無時無刻不在想望身邊的島嶼或遙遠的海角,有一片闃靜無聲的森林,除了風的嘆息、葉子的唏嗦,就只有自己偶爾踩斷枯枝的回響。而,我在一動一靜之間試圖攫住每一個機會,汲汲吸取那渴望已久、最原始也最粗野的「自由」氣息,深深地一口又一口。
我走進大自然,懷的是「尋找」的念頭,而非「征服」的妄想。我只是請求靜默的大地能夠張開雙臂接納我--至少暫時的「容納」我。我,不過是一個回頭浪子,藏著一顆虔誠知過但不能不說忐忑的「返鄉」心願--人本來就出自大自然,原本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我遺忘太久了。
我將簡單的需求,放進簡單的背囊裏。一顆8×25雙筒望遠鏡、幾瓶清水以及一點可以暫時止饑耐餓的乾糧,通常是幾顆家裏自己做的雜糧饅頭,也許再加一條巧克力或是幾粒黑糖。我在外衫右邊口袋插上一枝筆、一本小筆記,左邊放一只指北針。有時候看天氣,背囊裏再塞一件大外套或薄夾克。現在將近秋天時分,野外的天氣難以預測,雨水常常說來就來,風颳起來更是隨性。
走在曠野,我不必在意自己穿什麼衣服,戴什麼手錶,甚至用什麼名牌的鋼筆寫字。我要專注的是,如何避免破壞大自然,以及如何不讓自己在荒野遭受意外傷害,甚至喪失了生命。大自然很「美麗」,可也是很「無情」。
我深切感受,唯有在大自然的面前,人才獲得真正的「平等」與「自由」,我們在「人造社會」裏所擁有的身分與地位,有如口袋裏的紙鈔或信用卡,在這裏皆無可用之處。走進森林的深處,荒野裏隱密的溪谷,發覺只有自己獨與大自然面面相對、孑身相處。環顧周遭,沒有別人可以彰顯我們的「功名」,襯托我們的「財富」與「地位」,想來我們許多人一生所謂的「得意」,在荒野裏竟是顯得如此虛浮。
我在荒野與野鳥朋友相遇
我彳亍荒野,並非漫無目的。
在不知多少個清晨的微光裏,我凝視昨夜不知何時落下的葉子,被嚴霜凍僵了的薄弱軀體。這些葉子都是在一夕之間,措手不及,就以昨夜睡夢中的姿態蜷縮長眠。黃昏時候,我蹲下來撿拾被風吹落一地的葉子。我一片一片的挑撿,驀地驚覺,落地的葉子竟沒有一片是完整的。
好幾次,我在帶著寒意的迷霧中,追逐草原狼的足跡,總是巴巴看著影子閃進比人還高的芒欉裏,悵然望著牠走過後蘆草伏倒的痕跡。不過有一天,我們終於有了近距離四目相對的機會,直到今日,當時牠眈眈盯著我看的眼神,幾分「好奇」,幾分「疑懼」,還有幾分的「困惑」,一直深刻地烙在我的腦海裏,時不時出現與我互相凝視良久,彷彿在質問我 -- 我們究竟是兄弟,還是敵人?
※
又有一次,我來到被森林密密包圍的大湖澤邊緣,在零下的酷寒裏觀察各種大小鴨子的行為。我一邊做筆記,一邊拍攝記錄。野鴨子精力出奇地旺盛,活潑異常。我從觀景窗裏發覺牠們很多時候也在「觀察」我,眼睛閃閃射出一絲彷彿好奇的眼光。我以為「好奇心」的表現,永遠是動物最迷人之處。也許就在那一剎那,讓我興奮地以為動物跟我們一樣也有「感覺」,也會「思考」。也許在我的心底深處,幻想著能夠跨越那一條看不見的演化的鴻溝,可以與動物對話。我想,那是一種不自覺的渴望吧!我總覺得牠們的眼神裏,隱隱藏匿著一層我一直不十分明白的神秘。
這一大片湖澤以及周邊的林子,是許多鴨子的家。我來到湖邊是想看鴨子,卻看到了我。我原本想認識鴨子,卻很高興認識了自己。
※
記得一個風雨過後秋末的清晨,天色尚朦朧不清,我走在水邊,發現一隻春天才出生的年輕雌鴦,不知道什麼原因仆倒在泥濘裏。我看牠時而掙扎、時而困難地扭曲身軀。我看不出來牠的表情,不過那應該就是「痛苦」的表示。我不知不覺蹲了下來陪著牠,輕輕跟牠說話,說了些什麼自己也不知道。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牠將脖子最後一次扭平,美麗的眼睛直直瞠視著前方,一隻腳僵直在半空中,一動再也不動。
天空不知何時放了光明,我發現牠張得大大的眼睛映出了一片蔚藍的天空。我看見了那一眸最後的藍天,清清澈澈凝駐在牠黑色的眼珠裏--那一片藍得如此美麗,如此扣人心弦的天空,從此不再有升空飛翔的機會了。
憂傷,常常是美麗走過之後留下的痕跡。我的心頭,禁不住如此覺得。
※
有一種小鳥叫做黑頭山雀,你張開手掌伸出去,牠就會從樹上飛下來停落你的掌心。小山雀外表天真,個性溫和活潑。尤其一個長長的冬天,精神總是那麼抖擻,一副永遠不敗的模樣。每一次,我一個人逡巡酷寒砭骨的水邊,常常食指僵硬得無法按下快門,突然飛來數隻小山雀繞著我的身邊蹦上跳下,烏溜溜的眼睛不時與我相交遇,彷彿在為我打氣,讓我的身心不知不覺重新溫暖了起來。
從此以後每當心情低落,我就走進林子尋找牠們,聽過了牠們的聲音,看過了牠們的身影,我又能夠抬頭挺胸走出林子。
※
許多年前也是一個十月小陽春的清晨,太陽剛剛爬上山頭。我佇立在外雙溪婆婆橋上,面向上游望去。出乎意外發現溪中一塊塊的石頭,佇立著一隻隻的暗光鳥「夜鷺」,為數大概有六、七隻。每一隻胸前都毿毿飄垂著一把散亂的鬚毛,牠們的羽氅不僅鬆髶,甚至有些邋遢,一副滄桑歷盡,疲憊十分的模樣,跟我以前看過的美麗很不一樣。一隻踞守一塊石頭,凝然不動,無視眼前溪水不斷匆匆流過,從其姿態判斷顯然並非在等待游魚。我知道夜鷺的生命可以有二十年之長,也許這是牠們此生最後的一個階段。
那是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一幕。第一次,我看見了這般「古老」的暗光鳥。以前沒有,以後也一直未曾再見。
※
有一天,我一路追蹤記錄知更鳥完整的育雛過程。最後三隻幼鳥終於離巢,分別藏身在灌叢中。其中有一隻長得比較大,羽翮也比較完整,後來就站上了附近枝頭。大家都在等待親鳥最後幾次的餵食。兩天之後,兩隻親鳥就不再出現了,三隻小鳥也各自分奔前程,有朝一日若再相遇,恐怕彼此也不再相識。
不過,不同的經驗會有不一樣的心情。(配圖 L5 )
※
有一年我守在內雙溪大崙尾山上一棵大樟樹下,一邊忙著餵蚊子,一邊等待巢裏唯一一隻小五色鳥的離巢。樹大分枝,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我盯著巢窠洞口不敢稍稍眨眼。這一刻我反而無意舉起相機按啟快門,我要用自己的眼睛直接目送,我想凝結那一剎那讓它永遠顯影在自己的心版上。終於,一抹綠色影子急急衝出,在我的眼珠裏化成一道五色彩紅,很快地帶著我的期盼與祝福,消失在不遠的蓊鬱林子中。我知道,小五色鳥必須自己去尋找探索自己的世界。
※
長久以來,我幾乎每日一跬一步行走沒有名字的野地山林水邊,結識了不少野生動物朋友。晨曦暮色裏,時不時心頭總會想起以前讀過英國作家葛林 (Graham Greene) 說過的話:「人是唯一會推理的動物,推理使人絕望,所以人也是唯一會感覺『絕望』的動物。」意思大概如此。
不過我相信葛林只說出了一半。人不僅會推理,人還有一般科學甚至心理學家無法處理的「生存意志」,或是說「求生本能」,那是人在經過各種磨難與考驗,有朝一日終於釋然「接受」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無需言說的沈靜--宛若一條默默流過的大河,繼續前進,繼續面對風雨,繼續期待陽光再次出現的力量與勇氣。在一陣又一陣的傷痛過後,雙手撫摸著那慢慢消逝的傷口,甚至感覺自己一次比一次的強,一次比一次的勇。我相信這時候我們已經遠遠超過了「本能」,超越了「知命」。
我思忖,這應該是葛林沒有說出來的另外半句話吧!如果你仔細聆聽過貝多芬終於接受了耳聾事實之後的創作,相信會更明白我的意思,也更會同意我的看法。
終於我知道了,我走進大自然,為的是要努力走出荒野
目次
《目錄》
《推薦序一》「真高興遇見你!」 范欽慧
《推薦序二》換個角度來「愛鳥及屋」 劉伯樂
《自序》尋找第一隻鳥
《寫在前面的話》走出荒野
《我的20位野鳥朋友》
1. 飛翔的五色彩虹 五色鳥
2. 我的鄰居 綠繡眼
3. 一隻很會捕魚的狗 翠鳥
4. 香蒲草澤間的小隱士 鷦鷯
5. 荷葉梗上的漁夫 夜鷺
6. 那一眸最後的藍天 鴛鴦
7. 牠們一家都是雞 紅冠水雞與白冠雞
8. 永遠一雙鮮橘色的雨鞋 綠頭鴨
9. 青山碧水任遨遊 大蒼鷺
10. 沒見過這麼憨的鳥 黑冠麻鷺
11. 秋去春又回 燕子
12. 侏儸紀摩登鳥 鸕鶿
13. 橘紅胸脯的旅鶇 知更鳥
14. 策馬獨行草原遊騎兵 澤鷂
15. 優雅敏感的大鳥 鶴
16. 台灣客鳥 埃及聖鹮
17. 森林裏的鼓手 啄木鳥
18. 長尾山娘趕廟會 台灣藍鵲
19. 坪林的美麗飛羽傳奇 鷺鷥
20. 一隻鳥之死 黑頸鷿鷈、加拿大雁、綠頭鴨
書摘/試閱
【我的野鳥朋友1】
鷦鷯在一枝
我們要像鷦鷯那樣,昂首唱出心裏那一首埋藏了許久的歌。
總有一天,總有一個人,總會聽到我們的呼喚。
即使沒有,我們也要唱給自己聽。
鷦鷯,一種很會唱歌,以昆蟲為主食的小型禽鳥,屬於雀形目鷦鷯科。全世界共有十七屬七十七種,不過有四種幾乎接近絕種,另有十種可說已經瀕危。那麼多種不同的鷦鷯,大小不盡一樣,一般身長大概在十二公分上下,其中以冬鷦鷯最為嬌小,不超過十公分,比我們常見的麻雀還足足小了五公分,而尾翼差不多就占去了身長四分之一。
鷦鷯的棲地環境差異變化頗大,從乾旱的沙漠到茂密的林地,都有牠們的蹤跡,主要分布在美洲,但是叫做「冬鷦鷯」的鷦鷯,卻是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在台灣,我們看到的鷦鷯就是這一種;在歐洲看到的,也是就只有這一種。
身材嬌小、圓圓滾滾的冬鷦鷯
台灣的冬鷦鷯,通常活躍於兩千二百公尺以上,譬如合歡山的高海拔地區,經常進出於低矮的灌叢或箭竹藪之中,不少鳥友在松雪樓附近都曾經發現過,在台灣算是普遍的留鳥,為典型的高山鳥種。冬天時節,有時候可以看見幾隻偎聚在一起,彼此互相溫暖身體。
台灣鷦鷯的巢,一般結築於土壁草簷或岩縫之間。不過,也許是不同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型態,我在北美地區最常看見的鷦鷯,倒是生長在水邊的香蒲叢裏,也或許因為如此,當地人就稱牠做「沼澤鷦鷯」。
鷦鷯唱歌,聲音十分嘹亮,看牠身軀如此嬌弱,實在讓人難以想像。有人估算過,一隻冬鷦鷯如果跟一隻小公雞等重,其輸出功率大小竟然有小公雞的十倍。鷦鷯歌唱,不但腔調多變化,曲目更是繁多,從七十種到一百種不等。台灣原住民從前多以禽鳥鳴聲,做為日常活動進退的依據,鷦鷯也是原住民占卜的指標之一,《噶瑪蘭廳志》上說:「土蕃出草,聞(鷦鷯)聲則返。」像鷦鷯如此擅鳴的小鳥,我想帶給問卦者的,恐怕困擾多於明確的指示吧。
沼澤裏灌叢間的「小隱士」
我所認識許多禽鳥中,有好幾種可說天生「色淺體陋」、「形微處卑」,譬如歌聲十分迷人的歌麻雀 (Song Sparrow) ,其貌不僅不揚,其居所也多半是灌叢下黯淡的角落。每當我走在野地裏,看見小徑旁被我驚嚇到突然低飛竄走的歌麻雀,神態常彷若沿著牆腳弓身逃逸的小老鼠。我常在想,動物禽鳥是否具有「自我認識」的意念?意即不同的動物對自己形體的「大小」與「強弱」有所意識, 或是有所「感覺」--不然為何老虎、獅子幾乎什麼都不怕,白頭鷹昂頭藐視一切?即使同類之中,牠們也「知道」誰比較大,誰比較強。這樣的「認知」是從哪裏來的呢?
難道說,這是經過漫長演化的過程,已經寫進了基因裏頭?
我說歌麻雀「其貌不揚」,鷦鷯一身的羽色也差不多,大概以褐栗色為主調,再配上一點斑紋,經常與身邊環境混合為一,不易為人察覺,除非牠自己忍不住發出了聲音,或是晃動了枝葉。平常鷦鷯唱歌多半躲在灌叢低層,雖然看不見,但聽牠忽強忽弱,十分有勁的嗓音,不難想像昏暗的光線裏,聲音的主人一臉努力認真的模樣。一般說來,欲睹其廬山面目委實機會不多,說牠是沼澤裏灌叢間的「小隱士」,應不為過。
唯有在繁殖季節期間,為了宣示自己的領土、吸引伴侶,牠才會循著低矮灌木的枝椏,慢慢跳躍到頂端。首先調妥佇立的姿勢,甚至選好自己喜愛的方向,然後昂首翹尾,扯開嗓子盡情鳴唱。我想,這是鷦鷯最常拋頭露面的時刻。然而不管唱不唱歌,隨時不忘記把尾巴高高翹起,與身體成九十度,甚至超過九十度。這樣的姿勢正是鷦鷯的「正字標記」。
鷦鷯也許長得很平凡,可是每當牠站上枝頭高聲啁啾,全然無視咫尺之外的我。那樣的專心,那樣的忘情,驕傲的太陽下,那種抖擻不敗的精神,對於我是極具感染的力量,總是讓我看得忘神,聽到忘我。
有好幾次我看見牠一邊搧動著尾翼,一邊引頸高歌,唱到用心用力的地方,都會不禁然緊緊閉起了眼睛,那副陶醉的神情,幾乎就是義大利盲眼男高音波伽利的翻版。我見機不可失,趕緊按下快門,有圖為證。說真的,小鷦鷯唱得如此賣力、如此認真,實在憨得可愛。
「鷦鷯,巢於森林,不過一枝」
沼澤鷦鷯,嬌嬌小小,短短的一生究竟需要多少的土地,才能滿足生息的要求呢?這樣的問題,總會引起我心頭莫大的好奇,讓我不禁想起托爾斯泰的寓言小說《一個人需要多少的土地?》。鳥學專家說,一隻鷦鷯所宣示的土地,大概只有四分之一英畝,也就是大約一千平方公尺,換算成台灣甲,差不多十分之一甲,只等於「一分」的地--對於拍拍翅膀就可以隨意飛行的禽鳥而言,實在不算「大」,甚至可說「很小」。
是的,一個人短短有限的一生,究竟需要多少的「土地」,才夠「安身」,才算「立命」?中文有一句成語「鷦鷯一枝」,語出莊子《逍遙遊》,說鷦鷯所需要的,不過是一枝可以棲息的枝頭。一面比喻自己所求不多,一面也勸誡別人知足寡欲。
沼澤鷦鷯對繁殖領域有其特殊需求,一片片布滿香蒲的水澤邊緣,一塊塊長滿沼澤草的海邊濕地,只要有香蒲或沼澤草地區,就會有鷦鷯蒞臨。香蒲或沼澤草一旦枯萎,鷦鷯就不再出現。對鷦鷯而言,香蒲既是食物,更是重要的巢材。香蒲我們俗稱「水蠟燭」,西方人叫做「貓尾巴」,又稱「熱狗」,因為它圓筒狀雌性花穗,長得就是這個樣子。沼澤草不講究土質,但需要大量日照,即使鹽分極高的海邊潮間帶,依然可以茂密生長,不但提供了鳥類另一種生存空間,亦有凝聚流沙、保持水土的功能。
每隻鷦鷯占有的領地不但不大,彼此還常毗鄰而居,共有疆界。既然大家是鄰居,每天碰頭機會總是有,因此常可見兩隻鷦鷯煞有其事各據一方,拉開嗓門互別苗頭。通常由強勢一方先擺出擂臺接受鄰居的挑戰。一陣陣高歌,遙遙對唱完畢,彼此往往難免還要互相追逐一番。說是追逐,一旁的我看來,有時候倒是有七分像似在遊戲,一點看不出勝負的火氣。
鷦鷯一邊要演出爭逐領域、防禦疆土的戲碼,同時還要編築巢窠,更要日夜不停抽空飛上枝頭高聲歌唱,可想見這段日子有多麼忙碌,多麼辛苦。一般,我們總以為禽鳥也像我們人類,正午太陽太大了就要休憩,甚至還要移到樹蔭下打個盹。很多時候,為了記錄牠們難得的行為,我只有陪著一起曬烤,看誰先倒。
鷦鷯一次築巢不止一個,以展現自己的「能力」
領土一旦劃定,新房也一間一間建好,就等著新娘來鑑定挑選。
我說「一間一間」,表示一隻鷦鷯一次築巢不止一個。所以有此需要,除了用來混淆敵人視聽,算是「安全」考量的理由之外,也是雄鷦鷯對雌鳥展現自己「能力」的參考指標。好比人類男娶女嫁,男方拿出編了序號的房地產,向女方炫耀自己雄厚的經濟能力一樣。雌鳥一一檢視之後,乃以數量的多寡以及品質的優窳,來決定對方是否可以放心委身的對象。最後,牠卻一點不貪心,只選擇了其中最滿意的一個巢,自己再添加一點簡單但舒適的布置--就是牠們的新家了。
一般說來,鷦鷯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隻公的配二隻母的,算是常見現象,然而也並非每一隻公鷦鷯都是如此,有的還是維持「一夫一妻」。不過,雄性鷦鷯雖然行「一夫多妻」,一隻雌鳥卻是只事「一」夫。
有趣的是,共事一夫的兩隻雌鷦鷯卻是分別居住在同一塊領地相對的兩端--井水河水,互不相犯。甚且,兩隻雌鷦鷯下蛋的時間,通常也會相隔一至二個星期。否則,我揣想一身要兼顧兩個家,雄鷦鷯再有天大本事,單只餵哺兩窩加起來可能六到十八隻的雛鳥,外加猶若黑枕藍鶲一般進進出出傾倒便囊,半條小命不累死恐怕也很難。所幸,牠不必分擔臥巢孵蛋的工作。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指出,「鷦鷯,取茅葦毛毳而窠」。這些外殼用香蒲花穗的毛絮,或是葦草狹長的葉片編織而成的巢窠,從外表看似已經竣工,隨時可以遷居,其實內部「裝潢」皆尚未施作,只待未來女主人畫龍點睛。工程進行期間,雄鳥不時會暫且放下手邊工作,跑到枝頭高歌一曲,彷彿在殷切召喚:「快,快來啊,我的愛人--我已經準備好了新巢等著妳來。」如此唱了一遍又一遍。過了一會兒,見牠下到地面上來覓食,倒是默默無語,安靜得很。
雌鳥也許聽到了呼喚,飛了過來。牠會四處走走看看,逐一品鑑幾隻雄鳥辛苦的成果。這時,通常會有其中一隻雄鳥緊跟在旁,一邊依舊禁不住興奮繼續歌唱,一邊將身上的羽毛漲得膨鬆,顫抖不停。尾翼更是翹成了直角,垂直上天。雌鳥一旦選定其中一個,添加了一些襯裏,巢的主人即算雀屏中選,配對的儀式終於完成。沒有被選上的巢窠,則任其棄置一旁。因此我走在水澤邊,萋萋茂茂的蒲草裏或是灌叢中,隨時可見許多塌圮的鷦鷯巢,幾天日曬雨淋之後,看起來好像荒野裏遭人遺棄的小茅屋。
我想,我們有許多人猶如鷦鷯一般,生活在經濟競爭的底層,所擁有的生存空間甚至不如一隻小小的鷦鷯,然而縱使如此,我們也要像鷦鷯一樣,不時站上枝頭--我們所需要的只不過是「一」枝,昂首唱出心裏那一首埋藏了許久的歌。
總有一天,總有一個人,總會聽到我們的呼喚。即使沒有,我們也要唱給自己聽。
Box 鳥事知多少
雄鷦鷯一次築巢有幾個呢?
雄鷦鷯不辭辛勞,造築了不止一個的「求偶巢」,主要目的不外為了吸引雌鳥。平均來說,一隻雄鷦鷯一次築巢約五、六個,不過有人統計最多可達到二十七窠,手腳不但要俐落,其決心與毅力還真讓人忍不住大讚一聲佩服。一般情況,完成一個巢所需時間,大概快則一天,慢則三天;有時候也可以好幾個同時進行,有一次我觀察到有隻鷦鷯同時築兩個巢,忙碌的畫面十分有趣。
Box 鳥事知多少
鷦鷯家族中的「巨人」
鷦鷯身材嬌小,甚是可愛,不過在墨西哥靠近太平洋的海岸,卻有一種稱做「仙人掌鷦鷯」的鷦鷯,頭尾可以長達二十二公分,比我們島上的紅鳩略小,差不多有台灣夜鷹那麼大,簡直可以說是鷦鷯家族中的「巨人」。
【我的野鳥朋友2】
牠們一家都是雞 紅冠水雞與白冠雞
在人類的世界裏,有的人外表長得很搶眼,容易吸引別人的眼光;
有的人,也許第一眼沒什麼特別印象,卻慢慢愈看愈有味道。
我以為,鳥的世界也是一樣,紅冠水雞就屬於後者。
遠遠乍看,只是一團的灰黑,其實牠們身上的顏色,
少說也有六種主要的色調,一點不輸給五色鳥。
也許不是每一個人都養過「雞」,但是「每一個人都吃過雞,除非從小吃素」,這句話應該是真的。沒養過雞,但見過雞在地上奔跑啄食的模樣,相信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經驗。還有,牠們走路時候,一顆小小頭顱有韻有律,頻頻不斷向前搗捶的影像,也一定鮮活地刻印在我們的腦海裏。
在鶴形目中,有一科叫做「秧雞科」,歸屬在這一科裏頭的,都是外形長相彷彿雞,行為也頗似雞的中小型禽鳥,其中以「白腹秧雞」的名字最為響亮。說真的,牠們一家大小都很討人喜愛。這一次我想介紹的是,外形以及一些特有行為表現模式,比較接近的「紅冠水雞」與「白冠雞」這兩種,讓牠們一起登場作秀。
鴨不鴨,雞不雞--是鴨,還是雞?
在台灣,迷鳥不算,我們可以看見的秧雞大概有七種;其中六種算是走禽,只有一種屬於游禽。其實這樣子說,並非表示「走禽」只在陸地上走動,只有「游禽」才在水裏生活。大體而言,牠們這一家「雞」,無論在陸地穿梭或是在水裏涉足泅泳,說「自由自在」,絕對沒有問題。
「紅冠水雞」雖然叫做水雞,其實在陸地和水裏看到牠們的機會,一半一半。另一種大家都稱呼「白冠雞」,不過說實在的,每次看見牠們,總忍不住想要叫牠一聲「白冠水雞」。我不知道,為什麼牠的名字裏,獨獨漏掉了很重要的一個「水」字 -- 因為牠是「秧雞科」家族中,唯一被歸屬於游禽者,也是唯一一生大半時間都在水中討生活的「雞」。「『水』雞」這兩個字,放在牠的頭上,才是名副其實。
有很多人,第一次看見紅冠水雞或白冠「水」雞在水中划水的姿態,尤其看見牠們跟鴨子一樣,以倒插蔥的姿勢在水底覓食,都難以免除心頭的疑惑,驚聲叫道:「咦,那是鴨子,還是雞?」那樣「雞不雞、鴨不鴨」的猶疑,我真的很能夠體會。因為,那也是我自己初次看見白冠雞的第一個反應。
額板像似一面盾牌
紅冠水雞最引人注目的焦點,正是臉部正前方、兩眼之間,那一片寬長的「額板」。額板像似一面盾牌,紅妍得發亮,由上喙一直往上延伸至頭頂,渾渾厚厚、一體成型,只有三角形嘴尖部分呈青黃色,彷彿野草莓不小心沾了芥末醬,襯著一顆黑烏烏的頭,再配上兩粒紅眼珠,橫豎怎麼看都非常明顯,尤其當牠?在水裏划水前進,點頭如搗蒜,模樣更是可愛加有趣。
白冠雞的額板,就沒有紅冠水雞那般惹眼,只是一片素白,不過生長在美洲的比在台灣看見的,頂端多了一小塊暗紅色印記,接近嘴尖地方則有一圈斑環,除此之外沒有什麼不同。白冠雞終年只有一款衣裳,顏色只有深灰黑一種。有時候,看見兩三隻白冠雞,靜靜站在沒膝的水裏,也許光線昏暗的緣故,感覺彷彿童書裏所描繪的「半夜裏披著斗篷的小偷」。
這兩種水雞,不分雌雄,一律長得同一個樣子,除了雄雞的塊頭大了一點而已。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紅冠水雞的頭,是配合著腳在水裏向後推進的同時,用力向前一點。推一下,點一下;再推一下,再點一下,猶如雞在陸地上走路的模樣。白冠雞,亦復如此,一隻一隻的,宛如上了發條的玩具,尤其當牠們上百隻麇集湖面的光景,讓人不禁覺得,世上竟有這麼好笑的雞。
看似「無辜」也有「凶狠」的一面
秧雞科家族,個個長得像雞,但沒有一般雞的身材那麼肥胖大隻。白腹秧雞就是最好的例子,倘若從前面仔細端詳,其實有點「扁扁」的,那是因為白腹秧雞多半在草叢中活動,瘦瘦扁扁的身軀,正適合在草垛裏鑽進鑽出,極為方便。
紅冠水雞與白冠雞,因為生活環境與白腹秧雞不盡相同,體形倒沒有那麼「平扁」,也不需要那麼「平扁」。白冠雞甚至有些「圓滾」,畢竟這樣的身材,比較容易浮在水面上。論體格,白冠雞大概是台灣可見秧雞中,長得最「魁梧」的了,體重大約有紅冠水雞的兩倍多,有半公斤左右。
秧雞家族的棲地,因為多半在稠密的草叢中,即使像白冠雞那樣經常待在空曠的水域裏,彼此之間的聯繫,
主要靠的還是「聲音」而非「視覺」。有的天天都在叫喚,終年無休;有的平素緘默無語,繁殖季節一到,卻變得喋喋不休,這時候,領域意識變得尤其強烈。因此,每每可以看見兩隻紅冠水雞凶猛地在水面上捉雙廝殺,互相騰空踹踢,久久不停。有時候,甚至兩隻,通常是夫妻,聯手攻打一隻,場面激烈非常,雖然不至於打到你死我活,也夠讓人看得心驚肉跳。原來外表看起來,好像隨時等待被人宰殺的雞那樣的「無辜」,卻也有如此意外的「凶狠」。
侵略性更強的白冠雞,老遠看見對方剛剛踩入自己的領域,即使沒有挑釁的意味,天知道也許只是一時糊塗,卻也要即時發動攻擊,存的是「先下手為強」的心態。於是,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有一隻突然在前面落慌而逃,完全「小命只有一條」的驚慌神色,後面一隻則一路猛打窮追,好像打不到不甘心,趕跑了就得意洋洋。
保衛領域,就是保衛食物的來源;食物不足,生命就會受到威脅。有時候想一想,對於野生動物來說,偶爾的「凶狠」也是很自然的事。
一雙出奇的大腳ㄚ--小孩穿大人鞋子
紅冠水雞與白冠雞,就身體的比例而言,都有一雙出奇的特大號腳丫子,初次看見,沒有不在口裏或心裏大叫一聲,「哇,好大的腳!」-- 好似小孩子,穿著一雙很大很大的鞋子。其實,秧雞家族成員哪一個不是大腳丫?不過數來數去,還是白冠雞與紅冠水雞的最大。
紅冠水雞上岸覓食的時間算來也不少,牠們邊走邊啄食,有時候也撿些小石子,拌一些細砂,吃進肚子裏,用來幫助磨碎食物。腳趾長得這麼長,而且向四方大大張開,是方便在濕地泥灘上面走路,可以分散體重,以免陷入泥淖,因此我們也常常看到秧雞家族,走在荷葉或踩在水芙蓉的上面,卻是一派輕輕鬆鬆的模樣。
如果你留神觀察,白腹秧雞走路邁出步子之前,總先高高抬起一隻腳,收起腳趾,然後再慢慢伸張,再著地前進。這是為了適應草叢中草莖林立的環境,長久以來所養成的習慣。不過,走出了草隴,在開闊地裏遛達,還是不改習慣。一樣的模樣,看起來卻是說不出來的滑稽,好像擔心地上太滑怕跌跤,又像躡手躡腳怕吵了別人,或者引來「不必要的麻煩」的注意。
白冠雞,不僅腳長趾長,更是族群中唯一腳上長有蹼者,只是牠的蹼不像鴨子那樣,在趾間連結成一片,而是呈長條狀,像耳垂一般,分別附著在每一根長長腳趾的兩側,稱為「瓣蹼」。有了瓣蹼,白冠雞不但划水更有力,潛水也更加方便,成了大家族之中,唯一潛水覓食的秧雞,最深可以下潛二公尺。
紅冠水雞雖然沒有瓣蹼,但是一樣擅泳,因此西方人乾脆直呼牠為waterhen,在台灣則俗稱「田雞仔」,我想,也許是因為我們經常看見牠們在田裏跑來跑去,不管是水田還是旱田,甚至空心菜田。
我在陽明山山腳下觀察過,有的紅冠水雞一生幾乎就在田裏周轉,連巢都搭築在田地中央,孩子當然也在田裏出生。好心的農夫在收成之後,依然讓牠們的巢窠完整地留在原地,因為紅冠水雞有舊巢重複使用的習性,如果這隻母雞放棄了,別隻母雞也可能會跑過來撿,稍加一番修葺,湊合湊合著用。不過,如果你跑去台北植物園或大安公園觀察,恐怕不會將紅冠水雞與「田雞仔」聯想在一起,因為那裏沒有田地,只有一小汪子水池。
白冠雞的愛情,溫柔而浪漫
我們知道鴛鴦雌雄之間的關係極其親密,而紅冠水雞與白冠雞的「愛情故事」,也是一樣「浪漫」,只是無人傳述。
台灣的紅冠水雞,可說終年都是繁殖季節,一年可以高達三窩,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牠們也像台灣藍鵲一般,有「合作繁殖」的現象,先出生的兄姊,會幫助父母照顧初生的雛鳥。紅冠水雞雖然孩子生得多,折損率卻也不低,譬如植物園裏的小水雞,就經常被住在隔壁的夜鷺與鳳頭蒼鷹偷襲捕食。白冠雞因為是候鳥,一年只有一窩。直到目前,我們尚無法肯定牠們是否終身為伴,但至少在繁殖的當季,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牽繫,卻是十分的堅牢。
時間到了,紅冠雄水雞因為體內賀爾蒙的作祟,就會禁不住很勇敢地向母雞求愛,不管在陸地上,還是水中央。公雞會不停地閃現牠的尾巴,多少不無賣弄之嫌,嘴裏還啣著水草,一邊發聲、一邊獻給母雞,同時也獻上殷勤。
白冠雞則會互相以嘴尖,輕輕整理彼此頭頂、眼邊的絨羽。不知是因為「害羞」抑是「陶醉」,只見被啄的一方,一顆頭愈垂愈低,甚至慢慢垂入了水裏,只剩下半闔半張的紅眼睛浮在水面--如此的溫柔,如此的深情。
有一首台灣歌謠「桂花巷」,其中一句:「花朵再醜,也有綻開一次的時候」。我以為,再平凡的鳥,都有一些動人的故事;再如何普通,再長得不怎麼樣的鳥,也會有人欣賞疼愛。只要我們願意付出多一點的耐心和時間,去接近牠們、認識牠們,就會看見一些別人看不見的,或是自己以前看不到的「事」與「情」。
也許我們會發現,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差異,並沒有我們所認為的那般明顯;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距離,也沒有想像的那麼遙遠。
Box 鳥事知多少
哪裡可以看見紅冠水雞或白冠雞?
紅冠水雞,是全世界秧雞家族中分布最廣泛的一員, 除了極地、沙漠與熱帶雨林,以及澳洲、紐西蘭與附近的南太平洋諸島,到處都可以看見牠們忙碌覓食或匆忙逃避的身影。
在台灣,牠們算是很普遍的留鳥。我們可以在宜蘭五結鄉剛插了秧的稻田裏,瞥見牠們奔走的黑色影子;也可以在台北市陽明山山腳下,芝玉路旁的水圳,聽見牠們有點滑稽的短促叫聲。甚至,在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的南池,都可以看見成鳥領著成群的雛鳥,在荷花綠葉之間覓食戲水的畫面。
白冠雞,在台灣則屬於冬候鳥,比起紅冠水雞就沒有那般普遍。最容易看見的地方,是我曾經當過兵的金門。不過近幾年來,新北市的金山、新竹的金城湖、嘉義鰲鼓濕地、台南的柳營與四草、宜蘭的塭底與竹安河口、屏東恆春的龍鑾潭以及台東池上等等地區,也都可以發現牠們的蹤跡。
一般來說,秧雞家族多半生性「害羞」,容易緊張,稍有風吹草動,立刻往草叢裏一頭猛鑽,巴不得一身上下都是偽裝打扮,甚至隱形起來。因此比較起來,紅冠水雞可以說「大方」許多,雖然看見了人,還是一樣拔腳就跑,但在台灣幾種秧雞中,我們最容易看見的就是紅冠水雞。
Box 鳥事知多少
秧雞飛不飛?
一般人都以為秧雞不善飛行,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
一般秧雞,也許「很少飛行」,也「飛不高」,白冠雞與紅冠水雞翅膀圓而短,飛起或許有一點點笨拙,卻都飛得很好,否則牠們如何分布在世界各個角落?如何從苦寒冰封的冬地,遷徙到比較溫暖的南方?牠們起飛的時候,都像飛機一樣,需要一段助跑。也許你不知道,牠們白天很忙碌,其實晚上也沒有閒著。必須遷徙的時候,都是在夜間啟程動身,這也可能是我們所以很少看見牠們飛行的原因。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