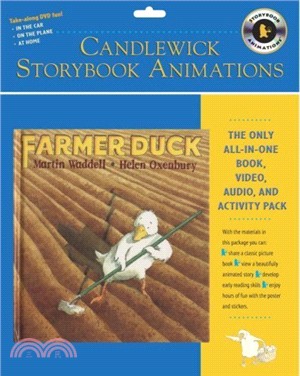父之罪
商品資訊
系列名:卜洛克馬修史卡德系列
ISBN13:9789862353226
替代書名:The Sins of the Fathers
出版社:臉譜文化
作者:勞倫斯.卜洛克
譯者:易萃雯
出版日:2014/02/25
裝訂/頁數:平裝/208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版次:2
商品簡介
我想過很久,對與錯之間總該有條界線,
可是實在很難知道該畫在哪裡。
通往地獄路徑,布滿善心
心懷至善、目標正當,還是不夠的
看似單純的一宗謀殺案,凶手理查.范得堡在監獄裡上吊自殺,結束短短二十年的年輕生命。而死者溫蒂.漢尼福,則是個離家多年的謎樣女子,她的養父為了填補這幾年對女兒生活的一無所知,委託史卡德調查溫蒂命案的前因後果。這個可憐的父親凱爾.漢尼福,在遭受如此大的打擊下,他想知道的並非結果,而是過程——到底,寶貝女兒過得是什麼樣的日子。
循著少得可憐的蛛絲馬跡,史卡德慢慢抽絲剝繭,而已經結案的案件,隨著許多跡象一一出現,增加了令人不解的謎團:溫蒂的金主為什麼全都是上了年紀的老男人?而與溫蒂同住一個屋簷下的理查,怎麼會是一個純情的男同志?理查的父親——身為牧師的馬丁,又為什麼口口聲聲說溫蒂是個罪該萬死的女惡魔?是因為她毀了兒子的美好前程?還是另有隱情?
有別於以往,在這次的探案過程中,史卡德更加深入地走進許多人的心靈深處,他傾聽那些無法說出口的孤寂和恐懼,分析潛意識所帶出來的特殊行為反應,他也透視了家庭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無法磨滅的深刻影響……終於,在一連串交叉對話的過程中,史卡德發現了令人驚駭不已的謀殺真相……
就在此時,深思熟慮後的史卡德,決定用他自己的方式,為整個故事找到一個「不得不」的終點。
目的正確手段錯誤,跟目的錯誤手段正確,到底哪個比較糟。
這不是我第一次思索這個問題,也不是最後一次。——史卡德
作者簡介
卜洛克的推理寫作,從「冷硬派」出發而予人以人性溫暖;屬「類型書寫」卻不拘一格,常見出格筆路。他的文思敏捷又勤於筆耕,自1957年正式出道以來,已出版超過50本小說,並寫出短篇小說逾百。遂將漢密特、錢徳勒所締建的美國犯罪小說傳統,推向另一個引人矚目的高度。
卜洛克一生獲獎無數。他曾七度榮獲愛倫坡獎、十次夏姆斯獎、四次安東尼獎、兩次馬爾他之鷹獎、2004年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以及法、德、日等國所頒發推理大獎。2002年,繼1994年愛倫坡獎當局頒發終身大師獎之後,他也獲得夏姆斯終身成就獎。2005年,知名線上雜誌Mystery Ink警察獎(Gumshoe Award)同樣以「終身成就獎」表彰他對犯罪推理小說的貢獻。
「馬修.史卡徳」是卜洛克最受歡迎的系列。透過一名無牌私家偵探的戒酒歷程,寫盡紐約的豐饒、蒼涼和深沉。此系列從一九七○年代一路寫到新世紀,在線性時間流淌聲裡,顯現人性的複雜明暗,以及人間命運交叉的種種因緣起滅。論者以為其勝處已超越犯罪小說範疇,而達於文學經典地位。
書摘/試閱
他塊頭不小,大約我的高度,但他粗重的骨架比我多了些肉。他彎彎的眉毛頗顯眼,還是黑的。他頭頂的毛髮是鐵灰色,直直往後梳,為他的巨顱帶出凜凜雄獅的味道。他原本戴著眼鏡,但此時已擱在我倆中間的橡木桌上。他深棕色的眼睛不斷梭巡我的臉孔,想找祕密訊息。就算他找到了,他的眼睛可沒透露。他的五官鐫刻得有稜有角——上鷹嘴鼻,豐潤的嘴,下巴的線條宛如危巖峭壁—但他臉孔引人側目,主要是因為它活似一塊空白石板,只等著別人刻下誡令。
他說:「我對你了解不多,史卡德。」
我對他所知甚少。他的名字叫凱爾.漢尼福,約莫五十五歲。他住在紐約州北部的悠堤卡,是批發藥商,擁有幾處房產。他有輛去年出廠的凱迪拉克停在外頭的路沿。他有個太太在卡來爾飯店的房間等他。
他有個女兒在市立太平間的一方冷鋼屜裡頭。
「也沒什麼好知道的,」我說,「我以前幹過警察。」
「表現優異,據柯勒副隊長說。」
我聳聳肩。
「而你現在是私家偵探。」
「不是。」
「我以為——」
「私家偵探領有執照。他們竊聽電話,跟蹤別人。他們填表格,他們存檔案,諸如此類的事。那些我全不幹。我只是偶爾幫人忙,然後他們給我禮物。」
「原來如此。」
我啜口咖啡。我喝的咖啡攙有波本。漢尼福面前擺的是杜華牌蘇格蘭威士忌和清水,但他興趣不大。我們坐在阿姆斯壯酒吧,牆壁嵌有暗木,配上錫紋天花板。此刻是一月的第二個禮拜二,下午兩點,這地方等於是我倆的天下。羅斯福醫院的幾個護士坐在吧台遠遠那端,護著酒杯細細品嚐;一個冒出幾根髭毛的孩子在靠窗的桌子吃漢堡。
他說:「實在很難跟你解釋,我想請你幫什麼忙。」
「我不確定我真能幫上什麼忙。我從報上得來的印象是:這案子不查自破,等於是看影片播放謀殺經過。」他的臉刷暗下來;他正在看那影片,刀子揮起落下。我趕緊開口道:「他們逮到他,把他扣押起來,然後踢進『死牢』。那天是禮拜四?」他點點頭。「然後禮拜六早上他們發現他吊死在牢房裡。結案。」
「你是這麼想嗎?案子已經結束?」
「從執法人員的觀點來看。」
「我不是這意思。警方當然必須從那個角度看。他們擒服凶手,而他已經不能接受法律制裁。」他上身前傾。「但有些事情我必須知道。」
「譬如?」
「我想知道她為什麼遇害。過去三年我跟溫蒂形同陌路。老天,我甚至連她是不是住紐約都不確定。」他的眼睛避開我的視線。「他們說她沒有工作,沒有明確的經濟來源。我看過她住的大樓。我想上樓進她公寓,可是我辦不到。她的房租每月將近四百塊錢,你說她錢從哪裡來?」
「有個男人幫她付。」
「她跟范得堡同住。殺她的男孩。他幫一個古董進口商做事,週薪大約一百二十五。如果有男人養她,他應該不會讓她找范得堡當室友,對不對?」他吸口氣。「我看她擺明了是妓女。警察沒有跟我明說,他們很小心。報紙可就不管了。」
這是他們的一貫作風,再說這案子又是報紙最愛炒作的那種題材。女孩漂亮,凶案發生在格林威治村,而且性意味濃厚。而且他們又逮到理查.范得堡渾身是血跑到街上。紐約稍微值幾個屁的老編,都不可能放過這個機會大顯身手。
他說:「史卡德,你知道為什麼這案子對我來說還沒結嗎?」
「大概吧。」我命令自己深深看入他幽暗的眼睛。「凶案為你打開了一扇門,你想知道房裡藏了什麼。」
「你的確了解。」
的確,何其不幸。我不想要這工作。我盡可能不接案子。我目前沒有必要工作,我不需要賺錢。我的房租便宜,我的日用花費很低。再說,我沒有理由討厭此人。我一向比較愛跟討厭的人收錢。
「柯勒副隊長搞不懂我要什麼。我敢說他給我你的名字,只是想禮貌的打發我走。」也不盡然,但我沒吭聲。「我非知道不可。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溫蒂到底變成了什麼人?而又為什麼有人會想殺她?」
為什麼有人會想殺人?紐約一天就有四、五起殺人案。去年夏天某個禮拜,數字更是高達五十三起。殺朋友,殺親人,殺戀人。長島有個男人亂刀砍死他兩歲的女兒,他幾個較大的孩子就那麼眼睜睜看他表演特技。人為什麼會變成野獸?
該隱弒兄後向上帝辯駁說,他不是亞伯的守護者。人只有這兩個選擇嗎,守護或者宰殺?
「你願意替我工作嗎,史卡德?」他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不,我該改個口。你願意幫我忙嗎?天大的忙。」
「我懷疑。」
「你的意思是?」
「那扇開了的門。房裡也許有些東西你不想看。」
「我曉得。」
「所以你才非看不可。」
「對。」
我喝完咖啡,我放下杯子,深吸一口氣。「好吧,」我說,「我姑且試試。」
他陷坐回他的椅子,掏了包菸出來點上一根。這是他進門後的頭一根。有些人緊張時得抽菸,有些人剛好相反。他現在比較自在,看來好像自覺完成了什麼使命。
∞
我眼前添了杯咖啡,記事本添了幾頁筆記。漢尼福還在跟同一杯酒奮戰。他跟我講了許多我根本無須知道的事——關於他女兒。不過話說回來,他說的任何事以後都有可能派上用場,只是難以預知是哪件事。我早就學到,不能漏聽別人想講的每一句話。
所以我得知溫蒂是獨生女,高中成績優異,人緣不錯但不常約會。我的腦中開始浮現她的圖像,雖然輪廓不清,但終究會與格林威治村又一名慘死的妓女合而為一。她離家到印第安納念大學以後,圖像模糊起來。他們顯然就是那時開始失去她的。她主修英文,輔修政治。畢業典禮前兩個月,她提了行李悄悄離開。
「學校通知了我們。我非常擔心,她的行為實在反常,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後我們收到一張明信片。她在紐約,有個工作,說是有些事情她必須理清頭緒。之後幾個月我們又收到邁阿密寄來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她是搬到那裡,或者只是去度假。」
然後就音訊杳然—直到電話鈴響,他們得知她的死訊。她高中畢業是十七歲,大學退學二十一,理查.范得堡割死她時二十四。她的生命到此劃下休止符,不會再長半歲。
他開始告訴我柯勒日後會提供更詳盡資料的事情。名字、地址、日期、時間。我讓他講下去。有個什麼叫我困惑不安,我擱在腦裡讓它慢慢成形。
他說:「殺她的男孩。理查.范得堡。他比她小,才二十歲。」他想到什麼,蹙起眉心。
「當初我一聽出了事,知道是他下的毒手,我恨不得殺了他。我要親手叫他死。」他緊握雙拳,然後緩緩鬆開。「但他自殺以後——不曉得,我裡頭有了改變,我意識到他也是受害者。他父親是牧師。」
「嗯,我曉得。」
「在布魯克林一間教堂。我有個衝動想找那人談談——雖然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打算跟他說些什麼。不過才考慮一下,我就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找他。只是——」
「你想了解那男孩,為的是要了解你女兒。」
他點點頭。
我說:「你知道嫌犯組合像吧,漢尼福先生?或許你在新聞報導上看過。通常警方找到目擊證人後,他們會用一組透明重疊膠片組合出嫌犯的長相。『鼻子是這樣嗎?耳.呢?哪對耳.最像?』如此這般,直到五官湊成一張臉孔。」
「噯,我見過。」
「那你或許也看過嫌犯本人的照片並排在組合像旁邊。它們其實不像—尤其對沒受過訓練的眼睛來說。但不可否認,五官分開來看是有部分雷同,而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官往往能充分加以利用。你懂我的意思?你想要你女兒和殺她那男孩的照片。這點我辦不到,沒人辦得到。我可以挖出足夠的事實,綜合多方問來的印象,為你拼湊出組合圖像,但結果可能跟你真正要的會有出入。」
「我了解。」
「你還是要我去查?」
「呃,當然。」
「我或許比那些響噹噹的大偵探社收費還高。他們為你工作,可以論日或者論時計酬,調查花費另計。我的方式是先收一筆款子,花費從中扣除。我不愛做記錄,不愛寫報告,也不會為了討好客戶定時跟他聯絡。」
「你要多少呢?」
我從來不知道該怎麼訂價。我的時間只有對我才有意義,它對別人能值多少我怎麼知道?如今我已經刻意調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盡可能不要介入別人的生活。那我又該跟強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我得先拿兩千。我不知道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你會不會突然決定不想再看那間暗房。這一路下去,或早或晚,甚至結束以後,我都有可能會再跟你收錢。當然,你也可以一個子兒也不給,主權在你。」
他突的一笑。「你做生意真是不按牌理出牌。」
「大概吧。」
「我從來沒聘過偵探,所以實在不知道一般手續是怎麼樣。開支票可以嗎?」
我告訴他我收支票,而他那頭在寫的時候,我想到早先困惑我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我說:「溫蒂退學以後,你一直沒僱私家偵探?」
「沒有。」他抬起頭。「我們沒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張明信片。我考慮過僱人追查,當然。但後來知道她沒事後,我就決定作罷。」
「但你們還是不曉得她人在哪裡,或者她過得怎樣。」
「對。」他垂下眼皮。「這是我來找你的部分原因,當然。我現在後悔莫及,工作全部停擺。」他的眼睛和我的碰個正著,那裡頭有個什麼我想避開不看,但做不到。「我得知道我該負多少責任。」
他真以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許可以為自己找到一個,但那絕不會是正確答案。那種問題永遠沒有正確解答。
他把支票寫好,交給我。該填我名字的地方他空著沒填,他說我或許想直接提現。我說指明付給我本人即可,於是他又拔下筆套,在右邊線上寫下「馬修.史卡德」。我把支票摺起,放進皮夾。
我說:「漢尼福先生,你有件事情略過沒提。你不認為那很重要,但這很難講,而你也知道這很難講。」
「你怎麼曉得?」
「直覺吧,我想。我有多年經驗,觀察別人苦苦無法決定到底自己願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需要跟我透露什麼,但——」
「唉,其實是不相干的事,史卡德。我沒提是因為我覺得和你的調查無關,但—唉,也罷。溫蒂不是我的親生女兒。」
「她是養女?」
「我收養了她。我太太是溫蒂的母親。溫蒂的父親在她出生前過世,他是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韓國仁川的時候遇難喪生。」他移開視線。「三年後我娶了溫蒂的母親。打從開始我就待她和親生女兒一樣。等我發現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以後,我對她更是加倍疼愛。就是這樣,說不說有關係嗎?」
「不知道,」我說,「也許沒關係。」但知道總是好的,現在我明白漢尼福為什麼自覺罪孽深重。
「史卡德?你還沒結婚吧?」
「離婚了。」
「有小孩嗎?」
我點點頭。他的嘴唇蠕動起來,欲言又止。我開始禱告上蒼快點讓他離開。
他說:「你當警察一定表現出眾。」
「還不賴。我有警察直覺,也學到動靜之間如何拿捏。這樣就已掌握了九成功夫。」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將近十六。」
「如果做滿二十年,不是有退休金什麼的能領嗎?」
「沒錯。」
他沒問下去。奇怪的是,這比他問了還叫我難堪。
我說:「我失去信念。」
「跟牧師一樣?」
「差不多吧。不過也不完全一樣。因為警察失去信念還繼續幹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打從進這行開始就只是想混。總之我辭掉,是因為我發現我已經不想再當警察。」或者當丈夫,或者當父親。或者當社會中堅分子。
「看盡局裡所有的貪污腐敗?」
「不,不。」腐敗從來沒有干擾到我。沒有腐敗我哪來足夠的錢養家。
「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嗎?也罷,反正也不是什麼祕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華盛頓高地山莊一處酒吧,那裡警察喝酒免費。有兩個孩子在那兒行搶,出門前一槍打中酒保心臟。我追了他們上街,打死其中一個,另一個打到大腿。他這輩子別想再好好走路。」
「我懂了。」
「不,我想你不懂。那不是我第一次殺人。死掉了一個我很高興,而且我很遺憾另一個最後復原了。」
「那——」
「有一槍失誤,反彈出去,擊中一個七歲小女孩的眼睛。子彈反彈,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吋的話,也許只會劃過她前額。有可能留下個疤痕破相,但沒有大礙。可是射進眼裡,都是軟綿綿的東西,自然就搗進腦內。他們告訴我她是當場斃命。」我看著我兩手。抖得不厲害——肉眼難以察覺。我拿起杯子,一飲而盡。我說:「不可能定我的罪。事實上,我還得到局裡嘉獎。然後我遞上辭呈。我不想再當警察。」
∞
他離開後,我多坐了幾分鐘。然後我迎上崔娜的視線,她為我端來另一杯攙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沒啥酒量。」她說。
我同意她的說法。我的音調八成洩漏了我的心情,因為她二話不說就坐上漢尼福的椅子,輕按我的手背。
「有麻煩嗎,馬修?」
「也不算。有事待辦,但我寧可不辦。」
「你寧可坐在這兒,把自己灌醉。」
我齜牙一笑。「妳什麼時候看我醉過?」
「從來沒有。不過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這樣對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纖長,摸來非常舒涼。「天下有什麼事是對誰有好處的?」我說。
「咖啡跟酒。奇怪的組合。」
「是嗎?」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搖搖頭。「咖啡從來沒法叫人清醒,它只能撐著你不睡。拿壺咖啡奉送酒鬼,兩個加到一塊只是個睜眼酒鬼。」
「這就是你的寫照嗎,寶貝?睜眼酒鬼?」
「我眼睛睜不開,但也沒醉倒,」我告訴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
四點過後不久,我抵達我存錢的銀行。漢尼福給的錢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領出現金。這是我今年元旦後第一次來此,所以他們在我的存款簿上加計利息。有台機器一眨眼工夫就算出多少,但數字小得實在不該勞動機器浪費時間。
我在五十七街上,踅回第九大道,然後往上城走去,一路經過阿姆斯壯酒吧跟羅斯福醫院,抵達聖保羅教堂。彌撒已近尾聲。我等在外頭,只見幾十個人三三兩兩步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婦女。然後我走進去,把四張五十元鈔票塞進濟貧箱裡。
我照《聖經》所說,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獻給神。不知道為什麼。我已養成習慣,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習慣。我是搬進旅館「定居」之後不久,開始這樣。
我喜歡教堂。我喜歡坐在那裡頭思考。目前這家,我是坐在中間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裡大概待了二十分鐘,也許更久。
兩千塊錢從凱爾.漢尼福那兒轉到我手上,兩百塊錢從我這兒轉到聖保羅的濟貧箱裡。我不知道這錢他們會怎麼花。也許買食物和衣服分送貧家,也許買林肯轎車給牧師代步。我其實並不在乎他們怎麼花。
天主教堂從我身上拿到的錢比別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為他們開門的時間較長。不是週末的話,基督教堂大部分都關了門不做生意。
天主教堂還有一個好處。可以點蠟燭。我一路出門時點了三根。一根給永遠活不到二十五的溫蒂.漢尼福,一根給永遠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范得堡。還有,當然,一根給永遠活不到八歲的艾提塔.里維拉。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