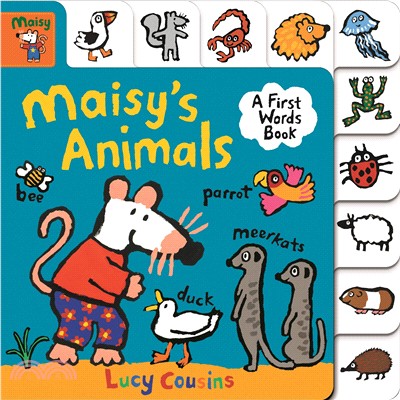商品簡介
初戀就像小倌的初夜,生澀但是純潔。
都說初戀是心上無法抹滅的刻痕,但煌吟的初戀情人究竟是誰?
當她被迫面對深埋心中的往日情懷時,命運的齒輪也開始轉動了!
★ 作者全新創作,從未在網路上曝光的內容,實體書獨家首發!
★ 女尊天后「逍遙紅塵」風華再現,展開另一段蕩氣迴腸、美男環伺、危機四伏的旅程!
天增歲月姐增夫,春滿乾坤爺滿門。老鴇變皇上,小倌理論成治國良方?
「哼,我是您的誰啊,豈敢勞您思念?」
「我男人!」
每一個傲嬌的小倌背後,都有一個死皮賴臉的恩客,面對寒蒔,唯有不要臉。
隨書附贈:
1.逍遙紅塵加碼全新創作「知音」獨家番外
2.貓君笑豬精心繪製「閣主和人爭風吃醋了?」人設海報
2.加大版書衣,「人物款」與「完整款」裡外兩款封面任君選擇
「如果我就是要留在這裡不走呢?」
「打斷你的腿,扛走!」
「妳能不能講點道理?」
「對你不用講理,講情。」
「我以前怎麼不知道妳是這樣的人?」
「在下端木煌吟,不知公子年齡幾何?許了人家沒有?」
「二十,沒有。」
「胡說!你嫁過人的,我親自用車拉你過門的,我還沒休夫呢,你休想賴!」
煌吟為了救治沈寒蒔身上的蠱毒,雖手刃仇人但也因此身受重傷,昏迷醒來後赫然發現自己身處山巔小屋中,再度全身癱瘓、武功盡失,只有一個毀容又不良於行的啞巴在照顧她。兩人朝夕相處後,煌吟漸漸發現這位照顧她的傷殘人士,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祕密而且跟她有關?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原來煌吟要武功盡失才能進階!才剛恢復功力,師傅青籬和神祕女子七葉先後現身,皆以能解蠱毒和她談條件,煌吟被迫和這兩人打交道,無意中發現他們身上的祕密。而青籬為了解蠱暫時無法動武,煌吟基於道義在旁照顧,終於結開多年來的師徒心結,但竟有一批黑衣人趁機偷襲他們,尚未查出這些人的幕後企圖,卻又接到容成鳳衣飛鴿傳書請煌吟儘速回國,究竟發生什麼連鳳后也無法決斷的緊急事件?身邊有越來越多的謎團發生,煌吟究竟會面臨怎樣的命運?
「妳……妳移情別戀就算了,我只能是第一個進門的,妳的鳳后、將軍、師傅都給我到後面排隊去!」
作者簡介
逍遙紅塵
自稱某狼;讀者第一次通常喚狼大,數日後變破狼,最終定格為殺破狼,據說其後母行為導致無數人咬牙切齒揪狼毛。實際上是超級無敵悲劇體質,三不五時就會上演掉水坑、卡鞋跟、臉著地、撞玻璃的情節。
貓君笑豬
畢業於川音美術學院油畫系,現為自由插畫家。
愛貓一族。喜歡音樂、旅遊,愛好一切美食。
曾為簡體版《星沉雁遠》《金風玉露》《簫月傾城》《幻想縱橫》與繁體版《美男十二宮》《藥窕淑女》《眸傾天下》《瀲灩江山》等小說繪製封面。出版個人畫集《曉見》、商業畫冊《花君宴》。
名人/編輯推薦
【讀者一致好評】
「狼大筆下的女主角們,傲立朝堂,生殺予奪,狂妄霸氣,令人折服;筆下的男主角們,風華絕代,性格分明,情深如許,令人嚮往。這就是狼大的文風,痞氣只是表面,那些角色深深印在腦海中,是豪情萬丈或似水纏綿,一筆一畫皆深刻,一刻一痕皆銷魂。這是女子可以主政的時代,女主角的能力才識確實擔得起國,擔得起家,也擔得起那些愛她的男子們。喜歡煌吟的自信與自傲,還有很多美人尚未出現,許多謎題還沒解開,期待狼大寫出後續發展。煌吟的荒淫美人路,嗯啊,很讓人期待的未來呢。」──讀者 pythagoras0314
「本書是《美男十二宮》的續作,但不用顧慮沒看過前作的話會不了解本作情節,因《公子們,接客了》乃是全新篇幅的展開。情節發展饒富意味,我總是很訝異作者能置入些令我實在想像不到的驚豔手法,彷若各色花朵遍路開,爭奇鬥豔,概而論之便是四字——出奇不意。本書女主角的個性是瀟灑氣概、敏智風流人物,而角色一開始的老鴇設定實在有趣,於角色身分的轉換上,作者也是別出心裁。而作者這次在老鴇這個身分當中又置入了一個畫龍點睛的元素──小倌理論,這可是其一將我逗得最樂的部分了,道理直白不呆板,實在是深得人心。本書中的美男,媚、柔、俊、美、勇,各色皆有,其中描寫之細緻玲瓏,似如品味美人瓷肌玉貌,帶來令人久而難忘的霽月雲雨。」──讀者 卿虎
「作者的故事架構依然讓人覺得龐大而深厚,文字間不時有氣勢磅礡之感,且用詞精妙,即便主角罵粗話竟也不覺突兀。且與上一套作品《美男十二宮》的故事設定有明顯不同,我一口氣看完了這本書,實在是讓人欲罷不能啊!目前出現的每個男角都很有魅力!不曉得這次女主角又會將幾位夫君金屋藏『嬌』呢?」──讀者 芴穎
「逍遙紅塵的作品都有一個共通點,故事中段以後劇情都會來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虐身又虐心,讓讀者的心情常常跟著劇情大起大落,也因為如此,我們這些書迷們才會如此地為她著迷。讓我最喜歡的片段就屬煌吟在回憶起過去的時候吧,那種哀傷、悲痛也深深地傳達給我,我在那段停留了十分鐘,遲遲不能緩解情緒。」──讀者 anna10tw
書摘/試閱
初醒,陌生之地
「嗡……嗡……嗡……」詭異的聲音一直在耳邊盤旋,吵得人崩潰,隨後就是癢,各種癢,全身每個地方都癢得難受。
再然後是冷,冷到我能感覺到自己皮膚上一粒粒突起的雞皮疙瘩,還有豎起的汗毛。
真的好冷,也真的好癢,誰他媽的能告訴我,為什麼這麼冷的天氣裡,居然會有蚊子?還這麼多!
沉睡的人硬生生被凍醒的滋味太難受了,當神志逐漸清醒,身體的疼痛也排山倒海地襲來。
重,身體沉重得就像一座山一樣,每一個骨節、每一寸皮肉都是痠痛的,無法比較哪個更疼、哪個更痠。那一波波抽搐般的疼,潮水似的湧了過來,撞擊著我,還來不及消散,更猛烈的一波就又襲來。
於是我就在痛、癢、冷的折磨裡死去活來、又活來死去之下,終於睜開了我沉重的眼皮,幾乎用盡了所有的力氣。
黑,一片的黑,什麼都看不見。
在全力施為之後,我這次的純氣不再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在筋脈裡肆虐,倒像是受了驚嚇的烏龜縮了起來,反正現在的我,是沒本事把它喚出來了。
沒有了武功,夜晚什麼都看不見,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也無法看清身邊都有些什麼。
大概死不了了!
要我死的人,沒必要救我;只是救我的人能不能專業點啊?這裡好冷好冷啊,我還是個病人呢,這樣下去要得風寒的。
當眼睛逐漸適應了黑暗,我隱隱約約地看到些事物,這是間不大的小木屋,沒有繁冗的裝飾,應該也不豪華,我依稀嗅到了木頭最原始的味道。房間也沒有多餘的擺設,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如果那幾塊木板拼起來的東西算是桌子和椅子的話。
破爛的門板不知道什麼時候被風吹開了,我可以直接看到天際的月華,月色下門外的小石坪上支著晾曬衣服的竹篙,幾個石塊權當做石凳了,兩株看不出什麼品種的樹木,再往前……
斷、斷崖?
我雖然沒內力,但是眼沒瞎,十五的月亮格外地明亮,小石坪上的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再往前卻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到的黑。
若非峭壁斷崖,不可能什麼也不見的。莫非我此刻身處在一個孤寒的高峰頂上?
角落裡傳來一絲極快的衣袂摩挲聲,像是人被驚醒後的猛然抬頭,還能聽到髮絲從肩頭落下的凌亂。
這屋子裡有人?
或許是武功暫時被禁制,也或許是體力尚未恢復,我居然沒發現角落裡蜷縮著一個人,黑沉沉的屋子裡沒有一絲光線,我無法看清對方的容顏,更無從判定身分。
大概不是敵人吧。
我在這人身上感受不到敵意,空氣裡沒有一點緊繃,如果是看守我的人,不可能有這樣清閒的心態。
我認識的人有限,能救我的,數來數去也不會超過一巴掌,這個人給我的感覺,絕不是這一個巴掌裡的。
被子被拾起覆上我的身體,我那凍僵的肌膚終於感受到了溫暖,還有被褥間殘留的陽光清香,這被子在白天裡被曬了很久呢。
那人一邊動作,髮絲也掃過我的臉頰,這算是唯一的接觸了。我還是無從判斷這人的身分,是男是女也無從推斷。
一盞油燈燃了起來,空氣裡生起淡淡的豆油味道,搖搖晃晃的燈光幾次被風壓得黯淡,又掙扎著燃了起來。
藉著微弱的燈光,我總算將那人看了個大概。有些瘦弱、髮絲凌亂隨意綁著,若不是那寬大的衣袍還是男子的服式,我幾乎難以判定他的性別。
那人蹣跚地走向門邊,動作緩慢而遲鈍,每一步都凝滯著、拖拉著,一隻腳落地,另外一隻腳再緩緩跟上,到門邊才幾步,竟走了許久。
應該是名男子吧,年紀只怕也不小了,推門關上的動作在他人來做只是隨手的事,而他竟然需要將身體微微靠上,以身體的重量將門推上。
當屋內不再有冷風,那燈光也不再跳動,漸漸安定了下來,我的耳邊也不再聽到嗡嗡的蚊子叫,心也平靜了。
當打量完整個屋子之後,我才發現,這間屋子比我最初想像的還要破敗,尋常人家即便是個茅草屋,至少也有一廳一屋。但我放眼四周,可以肯定這屋子就是全部了,一几、一桌、一床,角落裡放著米缸,堆著幾個馬鈴薯、南瓜等可以久放的食物,一兩塊臘肉香腸也是風醃的食材,幾乎可以想像平日裡的生活。
這老人家有些可憐啊……
如果說這裡的簡陋讓我心生憐憫的話,在當我看到角落裡貼牆席地的被褥時,心裡就只剩下愧疚了。
唯一的一張床讓給了我,倒把老人家擠到了地上,山中風露重,這樣睡幾日只怕會腰痠背痛了。
我想讓,但奈何說不出話,只能眼睜睜地看他拖拽著腳步,走到桌邊,在桌子的一角攤著一件衣裙。
有些刮破磨損的地方已經密布了針腳,縫補得仔細,有些地方則還維持破碎,這衣裙顯然只縫補到一半就被放在了那兒。
老人家,我對不起您,我不該腹誹您不會照顧人,把我光溜溜地扔在床上,看您老眼昏花還針腳還能如此細緻,看在不知道戳到多少次手指頭的份兒上,我也該感激一下的。
他背對著我,遮擋了油燈的刺眼光點,又恰巧留出了柔和的暈色,似乎是怕那光擾我休息而刻意地遮擋,讓我的感激又多了一分。
他緩緩地坐下,竹凳發出了吱嘎的聲音,他身體一緊,竹凳的聲音又更響了,像是就快要散開來。他手扶著桌子站了起來,那吱嘎聲終於止住了。
他一隻手拿起衣裙,一隻手顫巍巍地執起油燈,那手哆哆嗦嗦,油燈晃晃悠悠,濺了幾滴出來,落在他的衣袖上,我才發現他的衣袖很長,長得蓋住了手背,幾乎連手指都看不見,也幸虧衣袖長,不然這熱油就會燙到手了。
一步一顫,一步一跛,在幾聲單調重複的腳步聲裡,他挪到了角落的被褥旁,艱難地彎腰放下油燈,再放下衣裙,最後挪轉身體慢慢坐下去。
每一個動作都是緩慢的,可以看出他每一個動作都很仔細,從放下油燈的位置,到衣裙的平整,再到他笨拙卻無聲的動作,這是位心思周詳的老人家,我也隱約為什麼明白救我命的人會將我交由這樣一位老者來照顧了。
只可惜他一直低著頭,雪白的髮垂下,我完全看不到他的臉。
小小的屋子漸漸暖了起來,我與他各自占據著屋子的一角,他沒有抬頭看我,只專注於手中衣裙的縫補,我看了幾眼也就沒了興趣,我們就這麼疏遠而親近地和平相處著。
當感到溫暖,疼痛與疲累也一起湧上,我緩緩閉上眼睛,在柔柔的燭光中再度沉睡了過去。
這一覺睡得踏實而安穩,再醒來時,門縫下透著明亮的光,是一個明朗的白日。
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昨夜那老伯已經不見了蹤影,我轉動眼珠,只看到一盞燈油燃盡的油燈。
這燈,怕是燃了一夜吧。
想起老伯遲緩的行動,我又再度有點愧疚,為了我這一件破衣服,就讓人家熬了一夜。
衣服整整齊齊地疊好,就放在我的頭邊,有著和被褥一樣的陽光味道,不僅漿洗好了,還是剛剛晾曬後收下來的。
我走出屋門的時候,昨夜的猜測終於得到了印證,一方不大的平台是這山巔所有的活動空間,幾個簡陋的竹筒相連,引來山澗,滴滴答答的水落在水缸裡,倒也有些說不出的雅致,幾根竹篙撐出的晾衣架,幾塊石頭權當凳子,山崖的一角挖開小地,種著幾株花草,風掠過處,清幽的香氣伴隨著山頭的清涼,很是沁人心脾,奈何我看不出來是什麼花。
在人世浮華待得久了,對這樣的寧靜格外偏愛,如果換做當年的我,一心想著與木槿歸隱的我,只怕會嚮往這樣的地方,可現在……
我想回去。還不知道寒蒔的傷勢如何,鳳衣等不到我,又要擔憂了,還有那眉間有一抹血痕的男子,他的身分我還不知道。
太多心願未完,太多塵緣未了,已不容我在世外逍遙,更何況那曾許諾的人,也不在了。
看著四面如刀削一樣的峭壁,上寬下窄的走向,就算是有武功的我,上下也需小心謹慎,現在這孱弱的身軀,想要下去只有一個辦法——大頭朝下跳下去!
無論有多少想法,在此刻也只能是想法,這武功恢復就像一個壞脾氣的小倌,想什麼時候寵幸得看人家什麼時候高興。
我忽然回身,身後的人托著食案,被我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我尷尬了,「對不起,我只是聞到了飯菜香,沒想到會嚇到你。」
他匆忙低下頭,有些倉皇、胡亂地點著頭,將手中的食案放在石桌上,一樣樣地放著食物。
簡單到簡陋的菜色,幾片蒸的香腸臘肉、清炒的南瓜馬鈴薯,還有一個煨的地瓜,散發著濃烈的香氣,勾得饑腸轆轆的我猛吞口水。
他拿起小罐,慢慢掀起蓋子,我聞到了香甜的粥味,躺了幾日的人喝粥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意外的是……
「臘八粥?」
我嗅到了紅棗和松子、核桃的香味,於是在還未見到食物便脫口而出。隨後就發現是我想多了,大抵是為了替我補身體,所以粥裡放了一些補血益氣的藥材,倒與那記憶中的味道重合了。
他默默地將粥碗推到了我的面前。
我用勺子攪動著粥,香氣悠悠飄來,我的記憶又恍惚回到了那年,那冰雪中溫暖的香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臘八粥,今日這給我補身體的粥,如此奇異地巧合。
「是誰把我送到這裡來的?」
我抬頭望他,他又一次倉皇地低下了頭,動作大得白髮都揚了起來,散落在臉前。
他搖頭,本就凌亂的髮更是飛舞了起來。
「你不用瞞我,會讓你如此盡心照顧我,必然不會是敵人,我只想知道是誰,為什麼要將我放在這裡,而不是尋常的街巷裡。」我盡量將聲音放柔,希望不要再嚇到他。
他垂著臉,在長久的無聲後,他抬起了手,比了比自己的喉嚨。
我一愣,目光順著他的手指,看到了那隱藏在厚厚圍巾下的頸項,一道翻捲著的傷痕若隱若現,隨著他的動作倏忽閃著,看得不甚真切。
他竟連這裡也有傷?我無法想像這個男子是在怎樣的慘狀中存活下來的,甚至不敢想像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還有多少數不清的傷。
「那你會寫字嗎?」
他還是垂著臉,搖頭。
不能說,不能寫,看來把我送來的人不想讓我知道他的身分,才會安排這樣的人照顧我。
但我無法死心,到底是什麼人在裝神弄鬼?
「那我說話,你搖頭點頭可以嗎?」
這一次,他在沉默後輕輕點了點頭。
我看著那搖曳在面前的白髮,輕輕啜了口粥,「你其實很年輕,頂多二十歲上下吧?」
他正在布菜的手一抖,手中的碟子落在石桌上,裡頭的紅薯滾出來掉在地上,啪地一聲摔碎了。
我沒想到隨口一問會引起他這麼大的反應,愧疚又一次浮現,他倒是很快地鎮定下來,俯身拾起那紅薯,小心地剝去外面的皮,將髒的一面挖去。
他的動作很小心,也很優雅,卻還是能看到指尖的顫抖,這是筋脈受傷帶來的後遺症,我也有。
「我來吧。」我接過他手中的紅薯,指尖相碰,他鬆了手由了我,拿起另外一個小碗盛了碗粥,端起欲走。
「為什麼要走?」我開口攔住他,「怕嚇著我?」
他捧著碗,輕輕點頭。
「這是你的地方,你讓出床、守了我幾夜、為我縫補衣衫、做了飯食,我打擾了你的生活,沒理由讓你連吃飯都躲到角落裡。」
那欲走的人又重新坐了回來,輕柔的動作裡只聽到衣衫的簌簌聲,捧著他的碗。
從這些動作裡依稀可以感覺出,他是個性格極好的人。
「對不起,我沒想要探查你的祕密。」我有些歉意,「只是因為看到一些細節,想要求證一下。」
他的臉抬了起來,目光中透著疑問,又很快低下去。
我含了口粥緩緩嚥下,紅棗和核桃的香氣溢滿口,還有松子的清甜,「你的眼睛太亮了,若是上了年紀,眼珠會渾濁,這點不像。」
他很輕地頷首,粥捧到唇邊,保持著以髮遮顏的姿勢,無聲地喝著。
「還有你的手。」當我說出這幾個字的時候,他的手縮了縮,好像生怕自己藏得不夠似的,還摸了摸衣袖。
雖然他的手上布滿各種刀痕和傷疤,但是沒有疤痕的地方是細膩而緊致的,若是年邁的老者,只怕早皺成了老樹皮,當我看到他頸項的時候,更加確定了這個想法。
人最暴露年紀的地方,除了眼角、嘴角,就是頸項了,他連一絲頸紋都沒有,又怎麼可能會是上了年紀的人?
只能說我最初的誤會,是因為那頭雪白的髮和那蹣跚的步伐,如今想來卻有些明白了。
一個受過這麼重的傷的人,但凡露在外面可見之處都有疤痕的人,身上只怕也少不了傷處,走路又怎麼可能虎虎生風,而那頭白髮……
少年多情,青絲白髮,總是令人感慨而唏噓,其間的緣由,我不想多問。
即便是這樣的色澤,在陽光下還是泛起流光之采,隱隱滑著珠潤色澤,那順著肩頭落下的絹緞已近腿彎,一匹無瑕的白練,溫柔地貼合著身體。
我將剝好的紅薯放到他面前,他緊張地探出兩隻手指,將紅薯挪到自己面前,用勺子挖著送入口中。
手指上也是細細密密的傷痕,有大有小,看得我心悸。
我無法想像,究竟是怎麼樣的深仇大恨,才會對一名弱質少年下如此狠手,也無法想像,他是如何度過那段可怕的歲月。
拋去這些,僅僅那兩隻手指的長度和形狀,修長曼妙,手指尖尖,像是剛剛剝開外衣的春筍心。
那樣的眼神,那樣的髮,那樣的手,我眼前的人若在當年,應該也是顧盼生輝的人。
我忽然懂了他的瑟縮、他的遮掩,任誰都無法面對這樣的自己,也忽然明瞭了昨夜真正誤導我的那種死氣沉沉。
不是因為暮年,而是因為心灰意冷。
「一直獨自一人嗎?」這山巔的冷寒,孤苦的日子,在沒人陪伴的時候,越容易去回憶、去想。
寂寞的時光裡,最可怕的不是冷清,而是無法磨滅的記憶,越是無人時,錐心刺骨的往事越容易上心頭。
他的獨守山巔,又何嘗不是一夜夜的往事侵蝕。
他點頭,動作很平靜,氣息也很平靜,感受不到他身上的戾氣和怨懟,單純而乾淨。
在太多不甘與無望後,平靜才是最難得的,至少我沒有他的從容,這男子令我油然產生了敬佩。
「快四年了呢,一個人。」我感慨了聲,他一勺粥正送向唇邊,就這麼定定地頓在了空中。
我抬望目光,看向崖邊一株老松,上面有斑駁的刻痕,九道短痕之後,有一道中等長度的刻痕,兩道中等的痕跡和九道短痕下是一道長痕,十二道長痕後,便是另外新起的刻痕,可以輕易推斷出,這是他計算年月的方法,一共三個完整的,最後一個只得一半,應是今年的新痕,尤其最後一道還有木屑未落,是剛剛刻的。
我抱著被褥摔倒時,他大概正在刻日期吧,所以才來得這麼快。
不知是哪幾個字戳了他的心,我看到那手腕開始輕微地顫抖,勺中的粥晃了出來,落在他的衣衫上。
我又有了自抽嘴巴的衝動,誰叫我多話,誰叫我多事,誰叫我多嘴,真是混帳。
「對……」不起兩個字還沒說呢,他擺了擺手,表示他並不在意,端起了碗盞走向屋後,我跟著他的腳步,想要幫他清洗碗盞。
他又是擺手後是搖頭,直到那手推上我的肩頭,我拗不過他,唯有站在那兒發呆。
後屋比前院更沒有看頭,散亂地堆著些柴火,還有一個土堆堆起的包,說是墳太小,說是窖也不像,猜了半天,我也猜不出是什麼。
身後清洗的聲音小了下去,多了靠近的腳步,我側首時他已站在身邊,也同樣定定望著小包包,目光複雜,出神到忘了我在看他,忘記了隱藏自己的面孔。
他的手輕輕落在胸口,眼神溫柔如水,有釋然、有欣慰、有滿足。
這裡面葬著他的愛人?
可這土包太小了,放一具棺木顯然不夠,但我不敢問,怕刺了他。
不想打擾了他,我放緩腳步離開,在轉過屋角時,又忍不住回頭望了望,他站在那兒,遠方天際蒼茫,身姿孤寂,一抹殘陽斜影落在他的腳邊,拉長、拉長。
我蹲在花圃邊,撐著下巴想要看出個好歹,可惜我天生不懂得惜花憐草,看了半天只盯著一株發呆。
細細的莖,嫩嫩的綠葉,結著一粒粒紅色的小果子,豔豔的光華很是讓人喜歡,有的是圓圓的一顆,像粒瑪瑙珠子,有的已經冒出了小尖尖,細長細長的。
摸了摸,再摸了摸,我開始賤賤地想摘下來驗證自己的想法,礙於主人沒同意,只得按捺下,過一會兒又欠揍地去摳摳。
耳邊聽到杯盞輕放在石桌上的磕碰聲,我回頭衝他招招手,他腳步緩緩拉拽著走了過來。
我目光閃亮,有些期待、有些鬼祟,「這個是辣椒嗎?」
他怔了怔,點頭。
「那我能要求今日的馬鈴薯絲裡放點辣椒嗎?」我期待的目光變得熱切,只差雙目含淚了。
他的菜做得很好,這麼簡單的菜式能做得有滋有味已算是不錯的水準,可是沒辣椒,對我來說總覺得缺了什麼,好難受啊。
他悄悄別過臉,我能從他身上感覺到一縷快樂的氣息,這個傢伙在笑我!
他沒回答,但是他伸出了手,掐著蒂,一次摘一個,轉眼間手中多了七八個尖尖的小辣椒,這算是答應了吧?
「我來幫你洗,我來。」我幾近討好地說道,他只搖搖頭,朝石桌的方向指了指,示意我過去。
一個杯子、幾片茶葉、一壺熱水,看葉片被沖起、沉下,慢慢舒展開,再被推到我的面前。
「茶?」我眉頭微挑,半開玩笑,「我以為會是酒。」
我好茶,但是這個時代的女子多少都好幾口酒,一開始在屋內看到米缸旁放著幾個小罈,應該是他自釀的酒,山中露重,我以為他拿的會是酒呢。
他側目,髮絲下的目光裡有幾分複雜,糅著幾種情緒,讓我一時間難以捉摸。彷彿於他而言,我不該說這樣的話。又好像他根本沒想到我會討酒喝。
但是很快,他就搖搖手腕,指了指我。
我明白,他在說我身體未復原,莫要碰酒。我也順勢端起了茶盞,慢慢飲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簡陋的山巔小屋,連生活用具都少得可憐,這茶卻出奇的好,清香微甜,讓我不由得咂吧著嘴品味。
在我滿意的讚歎聲裡,他身上的氣息又柔和了幾分,執起了茶壺。
「我自己來吧。」我伸手,他也伸手,兩手指尖無意間相碰,他閃電般地縮了回去。
這是第二次他如此反應了,就連腳下也不自禁地退了兩步,與我保持距離。
我微怔了一下,就若無其事地拿起了壺,斟滿。
他也無聲地踏了回來,站在桌邊,就像什麼都沒發生般。
「我叫煌吟,你的朋友有告訴你嗎?」
他微微點頭。
「那你呢?」我苦著臉,「我總不能一直喊『喂』?」
這一次他沒動作,靜靜地站在那兒。
不能說,不會寫,想知道他的名字,真的有點難。
「不如這樣……」我想了想,「以後每天我想些字眼問你,若是你名字裡帶這個字,你就點頭,猜個十天半個月,總能猜出來的。」
我手指一點面前的茶盞,「茶!」
他搖頭。
再指,「水!」
還是搖頭。
「壺!」
「石頭!」
「辣椒!」
我說得飛快,他搖得也快,卻雅致。
「土疙瘩!」
「馬桶!」
他的喉嚨間發出細細的呼呼聲,嘴角扭曲得更加醜陋,倒是眼底,泛起了淺淺水幕。
笑出了眼淚?我猜得有這麼差嗎?
我無奈地捂上臉,為自己的想像力感到著急。
他悄然別開臉,目光遠遠落開。
此為精彩節錄,更多內容請見《公子們,接客了3》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