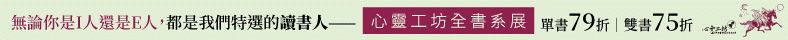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人生苦難、適應困難及由此氾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必然曾是大師們創見、洞見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此一意義而言,他們原來就都是「受傷的醫者」,他們「救人」先是為了「救己」……──林克明《受傷的醫者》
當走到生命貧乏處、被迫直視心靈傷口時,研究人類心靈的大師們會怎麼做?
醉心於人文思考的精神科醫師林克明,在接觸心理學之始,便是為了解開對人生的困惑。他試圖從傳記中尋找大師的人生智慧,卻驚訝地發現,這些所謂的「心理治療大師」,他們的人生其實滿布荊棘,或有童年創傷,或有成長挫折;成年後時常懷才不遇,事業發展一波三折。他們也許堅毅、進取、百折不撓,但當生命轉落困境時,也與我們同樣徬徨、沮喪、舉止無措;而憤怒、激情、勾心鬥角等人性面貌,更是經常上演的劇碼。
在《受傷的醫者》中,林克明記錄了心理治療界的大師生平、人生轉折、走上探索心靈祕境的原因、彼此從惺惺相惜到分道揚鑣的轉折歷程,清楚刻畫深刻的人性糾結。在作者筆下,大師們不僅是專業領域的典範,更是有血有肉、是非禍福懸於一念的凡人。經由這樣的「近身觀察」,我們得以藉其經驗反思己身,從苦難困頓中學習,走出自己的生命格局。
〔推薦〕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作家
文榮光──彰濱秀傳心理健康中心院長
宋維村──天主教若瑟醫院首席顧問
胡海國──臺灣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
符傳孝──紐約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陳芳明──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陳耀昌──臺灣大學醫學院血液腫瘤教授,《福爾摩沙三族記》作者
廖運範──長庚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賴其萬──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推薦語:
本書讓中文讀者輕鬆愉悅地解讀,全球百年來博大精深、震撼迷人、心靈療癒大師的真實人生。可說是出身台灣的作者在美國行醫、教學、研究、寫作與生活近四十年的精彩代表作,堪稱文化心理人類學田野研究的心血結晶。
──文榮光醫師(彰濱秀傳心理健康中心院長)
從大學時翻譯佛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開始,克明兄的每一本書都令人驚豔!他是光芒內斂的思想家,凡事都看得清楚想得透澈,話不多,但一開口必然語驚四座,論點令人折服。本書所評論的每一位醫者,克明兄都博覽群書,歸納其內容,以多年精神醫學的訓練和經驗加以評論。真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文獻。
──宋維村醫師(天主教若瑟醫院首席顧問)
《受傷的醫者》讓我們瞭解大師們也是人,一樣經歷生老病死, 悲歡離合。他們處理挫折,有時還不及常人。林克明教授用他幾十年在精神科的研究診療經驗,深入剖析。他用流暢的文筆,同理心的思維,把複雜曖昧的前因后果,有條不紊的娓娓道来。貼切的標題,畫龍點睛,瞄上一眼,就會讓人要先睹為快,欲罷不能。
──符傳孝醫師(紐約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當走到生命貧乏處、被迫直視心靈傷口時,研究人類心靈的大師們會怎麼做?
醉心於人文思考的精神科醫師林克明,在接觸心理學之始,便是為了解開對人生的困惑。他試圖從傳記中尋找大師的人生智慧,卻驚訝地發現,這些所謂的「心理治療大師」,他們的人生其實滿布荊棘,或有童年創傷,或有成長挫折;成年後時常懷才不遇,事業發展一波三折。他們也許堅毅、進取、百折不撓,但當生命轉落困境時,也與我們同樣徬徨、沮喪、舉止無措;而憤怒、激情、勾心鬥角等人性面貌,更是經常上演的劇碼。
在《受傷的醫者》中,林克明記錄了心理治療界的大師生平、人生轉折、走上探索心靈祕境的原因、彼此從惺惺相惜到分道揚鑣的轉折歷程,清楚刻畫深刻的人性糾結。在作者筆下,大師們不僅是專業領域的典範,更是有血有肉、是非禍福懸於一念的凡人。經由這樣的「近身觀察」,我們得以藉其經驗反思己身,從苦難困頓中學習,走出自己的生命格局。
〔推薦〕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作家
文榮光──彰濱秀傳心理健康中心院長
宋維村──天主教若瑟醫院首席顧問
胡海國──臺灣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
符傳孝──紐約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陳芳明──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陳耀昌──臺灣大學醫學院血液腫瘤教授,《福爾摩沙三族記》作者
廖運範──長庚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賴其萬──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推薦語:
本書讓中文讀者輕鬆愉悅地解讀,全球百年來博大精深、震撼迷人、心靈療癒大師的真實人生。可說是出身台灣的作者在美國行醫、教學、研究、寫作與生活近四十年的精彩代表作,堪稱文化心理人類學田野研究的心血結晶。
──文榮光醫師(彰濱秀傳心理健康中心院長)
從大學時翻譯佛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開始,克明兄的每一本書都令人驚豔!他是光芒內斂的思想家,凡事都看得清楚想得透澈,話不多,但一開口必然語驚四座,論點令人折服。本書所評論的每一位醫者,克明兄都博覽群書,歸納其內容,以多年精神醫學的訓練和經驗加以評論。真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文獻。
──宋維村醫師(天主教若瑟醫院首席顧問)
《受傷的醫者》讓我們瞭解大師們也是人,一樣經歷生老病死, 悲歡離合。他們處理挫折,有時還不及常人。林克明教授用他幾十年在精神科的研究診療經驗,深入剖析。他用流暢的文筆,同理心的思維,把複雜曖昧的前因后果,有條不紊的娓娓道来。貼切的標題,畫龍點睛,瞄上一眼,就會讓人要先睹為快,欲罷不能。
──符傳孝醫師(紐約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作者簡介
林克明
1946年生,1971年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譽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傑出終生資深會員。曾任臺灣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衛生及藥物成癮研究組主任、臺灣生物精神醫學及神經精神藥物學學會創會會長、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加州大學族群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主任、洛杉磯灣區及長堤亞太心理衛生中心創辦人。
研究興趣包括文化精神醫學、難民及移民之適應及心理衛生、心理史學、精神藥理學及基因體藥理學。著作包括學術論文兩百餘篇。譯著有《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性學三論》、《婚姻的幻象》、《精神分析術》等。現旅居舊金山,從事臨床工作、心理史學寫作及心理歷史小說創作。
1946年生,1971年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譽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傑出終生資深會員。曾任臺灣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衛生及藥物成癮研究組主任、臺灣生物精神醫學及神經精神藥物學學會創會會長、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加州大學族群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主任、洛杉磯灣區及長堤亞太心理衛生中心創辦人。
研究興趣包括文化精神醫學、難民及移民之適應及心理衛生、心理史學、精神藥理學及基因體藥理學。著作包括學術論文兩百餘篇。譯著有《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性學三論》、《婚姻的幻象》、《精神分析術》等。現旅居舊金山,從事臨床工作、心理史學寫作及心理歷史小說創作。
序
〔序〕
困而學之,學而知之
四十多年前進入臺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的時候,我對精神醫學這個領域所知其實非常有限。當時的心情,一方面是無盡的憧憬,同時也有更為深沈的惶恐。高中、大學時代之所以經常搜尋、涉獵心理學書籍,與其說是「為學問而學問」,不如說是源於對人生意義的茫然,源於對為人處世、日常生活的種種不安與惶惑。但是當時所能找到的有關心理學、心理治療學乃至精神分析學的著作,不論是原著還是轉述,都常不免讓人有莫測高深的感覺。大師們的自傳或傳記(如《佛洛伊德傳》、《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等),又總是讓人只能感覺到他們的才氣縱橫與他們堅忍不拔的驚人毅力。他們怎麼看怎麼像「超人」兼「完人」,把守著通往那神秘心靈世界的秘密鑰匙。為了要擺脫自己心靈的貧乏、走向富裕,我渴望著要去瞭解他們,尋求他們的秘密。
但是那也正是精神醫學轉型的年代。我在一九七四年轉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繼續進修時,原為精神分析師的舊主任剛下台不久,新的主任注重行為科學及生物精神醫學,反映的正是全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走向。第三版精神醫學診斷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 [DSM-III])在一九八零年出爐之後,精神動力學(psychodynamics)的概念遂逐漸爲「描述性」(”descriptive”)學說所取代。因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裡,精神分析學乃至其他種種心裡治療學正在逐漸淡出精神醫學界。在這樣的氛圍下,存身於大學臨床學術機構的我,擺盪於精神藥理學、社區精神醫學與文化精神醫學之間,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遂成了茶餘飯後助興的話題。當代掌權的「新克雷培林學派」(Neo-Kraepelinian)把「心靈」當成「黑箱」、「黑洞」,相信跳過這個黑箱,我們反而會更有餘裕去探討腦神經科學乃至分子基因學與行為、思考、情緒的關係。訓練結束後,我一直留在大學教學醫院與研究機構,三十年間忙於爲發展個人小小的學術事業而奔波,凝視心靈「黑箱」的時間,自然大減,但是對二十世紀初以來我們這個行業裡勇於探索人心的「祖師爺」們的人生際遇與心路歷程,則還是一直充滿好奇。
這期間有幸接觸到一些大師們的傳記,內容生動、考證詳實。經由作者們抽絲剝繭的敘述,我才真正體會,大師們的人生其實過得很辛苦。他們的童年常有嚴重的創傷;他們的成長過程充滿挫折;他們「懷才不遇」,事業發展一波三折。在傳統的「偉人」傳記裡,這樣的事跡通常會被用來做為反襯、彰顯偉人之所以成其為偉人的人格特質:堅毅、進取、自信、百折不撓。但是新一代的傳記,則比較容易不再那麼地「為賢者諱」。在這些作者的筆下,傳主面對人生苦難時的徬徨、沮喪、舉止失措,歷歷在目;傳主面對阻礙與爭議時表現出來的憤怒、激情乃至勾心鬥角的場面,也都無所遁形。這樣的書寫,當然有可能淪於流言蜚語的嫌疑。坊間有些書籍,的確明顯表露門戶之見,對異己者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但是真正嚴肅的「史家」在披陳傳主的癖性、弱點、缺失的時候,總是帶著淡淡的「哀矜勿喜」的態度。他們這種具體的「揭露」,其目的是要讓我們較有可能去貼近傳主,讓他們不再只是樣板,而是有血有肉、是非禍福懸於一念之間的人。也唯有經由這種貼近到幾乎可以感覺其呼吸的瞭解,我們才較有可能深刻體會大師們「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的歷程。
二零零九年我終於下定決心完全離開「學術機構」,重拾當初進入精神醫學領域時的初志,用餘生去尋求直接與人心交會的時光。而貼近人心,於我來說,就是兩條路徑:其一是去做個盡責的臨床精神科醫師,期待「病人」容許我走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其二是延續我從小對歷史人事的喜好,以古人為友,用我半生累積的知識與歷練去體會他們的人生抉擇,哀憐他們的無奈與困頓,讚賞他們的生命力、原創力,也由此開展我對寫作的熱情。
也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在醫學生時代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長、同學們共同集資創辦的《當代醫學》月刊,在走過三十餘年輝煌的歷史後,面臨因時代變遷等因素造成的瓶頸。同仁們幾經思考之後,決心將之持續至四十週年時圓滿閉幕。為了共襄盛舉,也為了一償去國多年、未曾為雜誌撰稿的歉疚,我於兩年前開闢了一個專欄,就取名爲「受傷的醫者」,每期介紹一位精神醫學界或心理學界的開拓者。當時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色彩最鮮豔、故事性最高,也或許就是爭議性最嚴重的幾位,如榮格(Carl G. Jung;1875-1961)、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等,原先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名單,只是想能寫幾篇就是幾篇。沒想到幾個月下來,每一個「主角」的背景資料牽引出許多我原所不知的、他們的同行者或敵對者(例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之於榮格)的「秘密」,於是乎有如原子爐的連鎖反應,名單越來越長,取捨居然成了問題。匆匆就是兩個寒暑,這個專欄,在見證《當代醫學》四十週年的慶祝盛典、圓滿謝幕後,也就畫下了句點。這期間勤跑圖書館,借閱書籍動輒十數百本,包括塵封多年的古稀珍本。有時為了求證解疑,幸運找到了專家學者或事件見證人的聯絡方式,居然還常得到善意的回應。大師們曲折豐富的人生,讓我有機會再度品嚐「做學問」的樂趣,也磨練說故事的能力,想來心裡就充滿感激。
本書記述的十五位傳主,每個人的成長、「成名」過程都極其艱辛,他們也多長期為種種身心症狀所苦(如果用現代的診斷標準來看,他們就正是名符其實的精神科病人)。就我所知,因篇幅所限,未包含在本書中的許多其他「先行者」,也多有類似的經歷。那麼是不是就可以說,我們出名的先輩,多半曾為明顯的精神疾患所苦呢?這個問題並不是本書所想要或有可能解答的:因為故事性的考量及個人的偏好,我的取樣絕對不會是客觀公正的。但是我相信的是,人生苦難、適應困難及由此氾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必然曾是大師們創見、洞見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此一意義而言,他們原來就都是「受傷的醫者」,他們「救人」先是為了「救己」。就如孔子自述,「我非生而知之者」,他們也不應該是天生的聖哲。因為「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他們的學問才會是彌足珍貴的「生命之學」。而我們後人,接踵其步,也必得「困而學之」,不止從書本與師長,更重要的是從他人(病人)及自身的煩惱、苦難中學習,才有可能終於「學而知之」。
這些陸續寫成的文章,其初並無預先擬定的章目或順序,大體以我當時對傳主熟悉的程度及手頭是否已有足夠資料為考量。在開始考慮成書時,重新排序成了一個難題。幸好心靈工坊的王桂花總編輯一聽之下,馬上想出了一個清楚的架構:將這本書分為兩輯。第一輯《「盛世」維也納》將重點放在佛洛伊德及他在「精神分析運動」初萌芽時最重要的夥伴兼宿敵 - 榮格與阿得勒(Alfred Adler;1870-1937) - 身上,試圖描畫他們各自的掙扎躓仆,他們一生的糾纏、恩怨,以及他們驚人的耐力與原創力。這一輯也包括幾位持續開展廣義定義下的「精神分析運動」的「第二代」俊傑之士,包括與佛洛伊德多年「情逾父子」的蘭克(Otto Rank;1884-1939)、企圖結合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而終至崩潰的賴克(Wilhelm Reich;1897-1957)、將精神分析學帶入英語世界的瓊思(A. Ernest Jones;1879-1958)、自認為是佛洛伊德正宗傳人的「客體關係理論」鼻祖克萊恩(Melanie R. Klein;1882-1960)、以及佛洛伊德聲譽的守護者,也與克萊恩同被尊為「兒童精神分析之母」的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這一輯以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Viktor E. Frankl;1905-1997)壓軸。先後受教於佛洛伊德與阿得勒的法蘭可,後來發現對人性的瞭解不應被侷限於「性」或「權位」,而只能經由「意義」的追尋才能來完成。令人感動的是,經過納粹集中營的劫難,九死一生的法蘭可竟能更加肯定生存的意義。他的身教言教,帶動了戰後迄今「存在/人本主義」(Existential-Humanistic )心理學的發展。
相對於第一輯完全以歐洲為主的事實(九位傳主裡有七位來自維也納,其他兩位分別來自瑞士與英國),第二輯《從大洋到大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之意)的重心則全在美國,六位傳主之中有四位生於美國,其他兩位的事業則在移民美國之後才得以開展。他們之中,萊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1889-1957)、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與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正是「人際關係精神分析學」(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及 「新佛洛伊德學派」(Neo-Freudians)的中堅份子。而這兩個學說的發展,反映的正是精神分析學及相關心理治療學說在從歐陸移植到「新世界」沃土的過程中,學者在新的文化環境下重新省思人心人性的成果。相較於上一代歐陸的學者,他們關注的重點,不再只是「內心世界」,而毋寧是個人與其環境,尤其是家庭、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建基於美式的樂觀與實用傾向,他們主張人性不是命定的,人的心理健康可以由環境的改造來促成。這樣的主張,一方面鼓動了全球推動社區心理衛生運動的風潮,同時也助長了如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萊克蔓之夫)等學者對當代社會剝奪人性自由的深刻批判。
雖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一生自詡為正宗的佛洛伊德傳人,他的許多摯友(例如米德)其實都是「新佛洛伊德學派」的人。他的人生八階段發展理論,強調的正是個人發展的社會背景,他以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及甘地(Mahatma Gandhi;1896-1948)為主題的鉅著,討論的也是社會、文化對個人認同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可以說艾瑞克森之所以成名,固然反映了他的才華與創見,但同時也因於他的想法呼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的心理需求。
另一位幾乎同姓的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son;1901-1980)則更是個來自中西部、身上同時流著維京人(Viking)與印地安人血液的「正宗」美國人。他「殘而不廢」,自信、樂觀、富於幽默。他不相信潛意識是洪水猛獸,而將之視為生機的泉源。也因為他,源遠流長但長期被誤解忽視的催眠療法才得以重見天日。
這一輯以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殿後,其實感覺上對他是有點委屈的。詹姆斯是本書所有傳主之中最年長者,年紀比佛洛伊德還大上一輪。當佛洛伊德與榮格及法朗克齊(Sandor Ferenczi;1873-1933)於1909年首次聯袂訪美時,最響往的就正是能與時已執美國心理學界牛耳的詹姆斯相見,並得到他的加持。詹姆斯雖然對新興的精神分析學不乏好感,他的興趣則始終放在「意識」的層面。他常年苦思人之所以為人的種種嚴肅議題,諸如自我意識的本質、自由意志與命定論(Determinism)並存的弔詭、靈魂與宗教情操的存在與屬性等。雖然伴隨這苦思的是大半生經年累月的極度憂鬱與種種嚴重身心症狀,他還是「甘之若飴」,勇往直前,晚年還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創立「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徹底經驗主義」(Radical Empiricism),流風所及,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世界的面貌。
如前所述,這本書從原初的構想到最後的成型,有說不盡的因緣。在許多關鍵點,如果沒有得到那麼多的支持與鼓勵,恐怕自己不管有多少熱情,也難以為繼。付梓前夕,感激之情,恐難盡述。不過首先最需要致謝的,就是《當代醫學》的編輯與同仁們,放心讓我開闢這個專欄。不僅如此,從一開始,我就有了這麼一群熱誠的「忠實讀者」:廖運範醫師(雜誌發行人)及其夫人黃妙珠醫師、賴其萬醫師(社長)、符傳孝醫師、張天鈞醫師(總編輯)及林欽沂總經理。他們都是筆者年少輕狂時代的老友,現在正處其各自事業、人生的巔峰,可謂名符其實的「日理萬機」,卻總是隨時把手邊的事情放下,用心與你對談。文稿一寄出,即時有回應,細讀、評點、加油打氣,依眉兒往往返返、字句琢磨。能有這樣的朋友,人生何憾!在此同時,也要感謝《當代醫學》的許翠玲小姐。沒有她的按時提醒、勤於催稿、並到最後一分鐘都不放棄,繼續追稿,這些稿件就沒有可能按月刊出、累積成冊。
感謝好友王浩威醫師這幾年對將這些篇章收集成書之構想的熱心回應與襄助;以及心靈工坊王桂花總編輯的企劃慧眼與積極推動。心靈工坊執行編輯陳乃賢小姐及行銷企劃許文薰小姐在本書編輯與出版過程中,竭盡心力。她們敬業與熱誠,我銘感於心。
在這麼多朋友及專業人士的關懷挹注之外,我何幸身邊還有一位「終生主編」的妻子宋文玲。身為臨床心理學博士並有多年執業經驗的文玲,對心理治療學的開創者們自然也都一直趣味盎然。雖然她只具名為本書中幾篇的共同作者,每篇文章從構思到完成,其實都得益於我們的反覆討論。 她也是本書每篇文稿「最初始」的讀者,改正多如牛毛的錯別字、推敲字句、修刪內容。我的為人雖然沈默寡言,為文卻常不免有過於渲染的毛病。凡事力求精準簡約的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複查資料來源、刪除與主題沒有直接關係的內容,有時大筆一揮,就刪掉好幾段,刪得我心疼,不免就偷偷又把它們放回去了。幾番來回反覆,終於發現,我寫文章就如我的飲食口味,喜歡「加油添醋」,而她習慣的則是「少油少鹽」。這樣的協調雖然難免有點辛苦,但也幸虧有她努力把關,這些成品才不至於如脫繮的野馬、橫衝直撞、失去重心。
本書的構思寫作,都是文玲與我在二零零九年遷居舊金山之後的事。正巧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女兒欣怡不約而同地也決定來此定居,讓我們很快就有了「落地生根」的感覺。我們的姊妹、親友的經常來訪,也更讓我們能安心地在這個城市「安居樂業」,繼續開展我們的新生涯,在此也一併致謝。
困而學之,學而知之
四十多年前進入臺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的時候,我對精神醫學這個領域所知其實非常有限。當時的心情,一方面是無盡的憧憬,同時也有更為深沈的惶恐。高中、大學時代之所以經常搜尋、涉獵心理學書籍,與其說是「為學問而學問」,不如說是源於對人生意義的茫然,源於對為人處世、日常生活的種種不安與惶惑。但是當時所能找到的有關心理學、心理治療學乃至精神分析學的著作,不論是原著還是轉述,都常不免讓人有莫測高深的感覺。大師們的自傳或傳記(如《佛洛伊德傳》、《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等),又總是讓人只能感覺到他們的才氣縱橫與他們堅忍不拔的驚人毅力。他們怎麼看怎麼像「超人」兼「完人」,把守著通往那神秘心靈世界的秘密鑰匙。為了要擺脫自己心靈的貧乏、走向富裕,我渴望著要去瞭解他們,尋求他們的秘密。
但是那也正是精神醫學轉型的年代。我在一九七四年轉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繼續進修時,原為精神分析師的舊主任剛下台不久,新的主任注重行為科學及生物精神醫學,反映的正是全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走向。第三版精神醫學診斷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 [DSM-III])在一九八零年出爐之後,精神動力學(psychodynamics)的概念遂逐漸爲「描述性」(”descriptive”)學說所取代。因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裡,精神分析學乃至其他種種心裡治療學正在逐漸淡出精神醫學界。在這樣的氛圍下,存身於大學臨床學術機構的我,擺盪於精神藥理學、社區精神醫學與文化精神醫學之間,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遂成了茶餘飯後助興的話題。當代掌權的「新克雷培林學派」(Neo-Kraepelinian)把「心靈」當成「黑箱」、「黑洞」,相信跳過這個黑箱,我們反而會更有餘裕去探討腦神經科學乃至分子基因學與行為、思考、情緒的關係。訓練結束後,我一直留在大學教學醫院與研究機構,三十年間忙於爲發展個人小小的學術事業而奔波,凝視心靈「黑箱」的時間,自然大減,但是對二十世紀初以來我們這個行業裡勇於探索人心的「祖師爺」們的人生際遇與心路歷程,則還是一直充滿好奇。
這期間有幸接觸到一些大師們的傳記,內容生動、考證詳實。經由作者們抽絲剝繭的敘述,我才真正體會,大師們的人生其實過得很辛苦。他們的童年常有嚴重的創傷;他們的成長過程充滿挫折;他們「懷才不遇」,事業發展一波三折。在傳統的「偉人」傳記裡,這樣的事跡通常會被用來做為反襯、彰顯偉人之所以成其為偉人的人格特質:堅毅、進取、自信、百折不撓。但是新一代的傳記,則比較容易不再那麼地「為賢者諱」。在這些作者的筆下,傳主面對人生苦難時的徬徨、沮喪、舉止失措,歷歷在目;傳主面對阻礙與爭議時表現出來的憤怒、激情乃至勾心鬥角的場面,也都無所遁形。這樣的書寫,當然有可能淪於流言蜚語的嫌疑。坊間有些書籍,的確明顯表露門戶之見,對異己者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但是真正嚴肅的「史家」在披陳傳主的癖性、弱點、缺失的時候,總是帶著淡淡的「哀矜勿喜」的態度。他們這種具體的「揭露」,其目的是要讓我們較有可能去貼近傳主,讓他們不再只是樣板,而是有血有肉、是非禍福懸於一念之間的人。也唯有經由這種貼近到幾乎可以感覺其呼吸的瞭解,我們才較有可能深刻體會大師們「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的歷程。
二零零九年我終於下定決心完全離開「學術機構」,重拾當初進入精神醫學領域時的初志,用餘生去尋求直接與人心交會的時光。而貼近人心,於我來說,就是兩條路徑:其一是去做個盡責的臨床精神科醫師,期待「病人」容許我走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其二是延續我從小對歷史人事的喜好,以古人為友,用我半生累積的知識與歷練去體會他們的人生抉擇,哀憐他們的無奈與困頓,讚賞他們的生命力、原創力,也由此開展我對寫作的熱情。
也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在醫學生時代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長、同學們共同集資創辦的《當代醫學》月刊,在走過三十餘年輝煌的歷史後,面臨因時代變遷等因素造成的瓶頸。同仁們幾經思考之後,決心將之持續至四十週年時圓滿閉幕。為了共襄盛舉,也為了一償去國多年、未曾為雜誌撰稿的歉疚,我於兩年前開闢了一個專欄,就取名爲「受傷的醫者」,每期介紹一位精神醫學界或心理學界的開拓者。當時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色彩最鮮豔、故事性最高,也或許就是爭議性最嚴重的幾位,如榮格(Carl G. Jung;1875-1961)、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等,原先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名單,只是想能寫幾篇就是幾篇。沒想到幾個月下來,每一個「主角」的背景資料牽引出許多我原所不知的、他們的同行者或敵對者(例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之於榮格)的「秘密」,於是乎有如原子爐的連鎖反應,名單越來越長,取捨居然成了問題。匆匆就是兩個寒暑,這個專欄,在見證《當代醫學》四十週年的慶祝盛典、圓滿謝幕後,也就畫下了句點。這期間勤跑圖書館,借閱書籍動輒十數百本,包括塵封多年的古稀珍本。有時為了求證解疑,幸運找到了專家學者或事件見證人的聯絡方式,居然還常得到善意的回應。大師們曲折豐富的人生,讓我有機會再度品嚐「做學問」的樂趣,也磨練說故事的能力,想來心裡就充滿感激。
本書記述的十五位傳主,每個人的成長、「成名」過程都極其艱辛,他們也多長期為種種身心症狀所苦(如果用現代的診斷標準來看,他們就正是名符其實的精神科病人)。就我所知,因篇幅所限,未包含在本書中的許多其他「先行者」,也多有類似的經歷。那麼是不是就可以說,我們出名的先輩,多半曾為明顯的精神疾患所苦呢?這個問題並不是本書所想要或有可能解答的:因為故事性的考量及個人的偏好,我的取樣絕對不會是客觀公正的。但是我相信的是,人生苦難、適應困難及由此氾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必然曾是大師們創見、洞見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此一意義而言,他們原來就都是「受傷的醫者」,他們「救人」先是為了「救己」。就如孔子自述,「我非生而知之者」,他們也不應該是天生的聖哲。因為「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他們的學問才會是彌足珍貴的「生命之學」。而我們後人,接踵其步,也必得「困而學之」,不止從書本與師長,更重要的是從他人(病人)及自身的煩惱、苦難中學習,才有可能終於「學而知之」。
這些陸續寫成的文章,其初並無預先擬定的章目或順序,大體以我當時對傳主熟悉的程度及手頭是否已有足夠資料為考量。在開始考慮成書時,重新排序成了一個難題。幸好心靈工坊的王桂花總編輯一聽之下,馬上想出了一個清楚的架構:將這本書分為兩輯。第一輯《「盛世」維也納》將重點放在佛洛伊德及他在「精神分析運動」初萌芽時最重要的夥伴兼宿敵 - 榮格與阿得勒(Alfred Adler;1870-1937) - 身上,試圖描畫他們各自的掙扎躓仆,他們一生的糾纏、恩怨,以及他們驚人的耐力與原創力。這一輯也包括幾位持續開展廣義定義下的「精神分析運動」的「第二代」俊傑之士,包括與佛洛伊德多年「情逾父子」的蘭克(Otto Rank;1884-1939)、企圖結合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而終至崩潰的賴克(Wilhelm Reich;1897-1957)、將精神分析學帶入英語世界的瓊思(A. Ernest Jones;1879-1958)、自認為是佛洛伊德正宗傳人的「客體關係理論」鼻祖克萊恩(Melanie R. Klein;1882-1960)、以及佛洛伊德聲譽的守護者,也與克萊恩同被尊為「兒童精神分析之母」的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這一輯以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Viktor E. Frankl;1905-1997)壓軸。先後受教於佛洛伊德與阿得勒的法蘭可,後來發現對人性的瞭解不應被侷限於「性」或「權位」,而只能經由「意義」的追尋才能來完成。令人感動的是,經過納粹集中營的劫難,九死一生的法蘭可竟能更加肯定生存的意義。他的身教言教,帶動了戰後迄今「存在/人本主義」(Existential-Humanistic )心理學的發展。
相對於第一輯完全以歐洲為主的事實(九位傳主裡有七位來自維也納,其他兩位分別來自瑞士與英國),第二輯《從大洋到大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之意)的重心則全在美國,六位傳主之中有四位生於美國,其他兩位的事業則在移民美國之後才得以開展。他們之中,萊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1889-1957)、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與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正是「人際關係精神分析學」(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及 「新佛洛伊德學派」(Neo-Freudians)的中堅份子。而這兩個學說的發展,反映的正是精神分析學及相關心理治療學說在從歐陸移植到「新世界」沃土的過程中,學者在新的文化環境下重新省思人心人性的成果。相較於上一代歐陸的學者,他們關注的重點,不再只是「內心世界」,而毋寧是個人與其環境,尤其是家庭、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建基於美式的樂觀與實用傾向,他們主張人性不是命定的,人的心理健康可以由環境的改造來促成。這樣的主張,一方面鼓動了全球推動社區心理衛生運動的風潮,同時也助長了如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萊克蔓之夫)等學者對當代社會剝奪人性自由的深刻批判。
雖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一生自詡為正宗的佛洛伊德傳人,他的許多摯友(例如米德)其實都是「新佛洛伊德學派」的人。他的人生八階段發展理論,強調的正是個人發展的社會背景,他以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及甘地(Mahatma Gandhi;1896-1948)為主題的鉅著,討論的也是社會、文化對個人認同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可以說艾瑞克森之所以成名,固然反映了他的才華與創見,但同時也因於他的想法呼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的心理需求。
另一位幾乎同姓的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son;1901-1980)則更是個來自中西部、身上同時流著維京人(Viking)與印地安人血液的「正宗」美國人。他「殘而不廢」,自信、樂觀、富於幽默。他不相信潛意識是洪水猛獸,而將之視為生機的泉源。也因為他,源遠流長但長期被誤解忽視的催眠療法才得以重見天日。
這一輯以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殿後,其實感覺上對他是有點委屈的。詹姆斯是本書所有傳主之中最年長者,年紀比佛洛伊德還大上一輪。當佛洛伊德與榮格及法朗克齊(Sandor Ferenczi;1873-1933)於1909年首次聯袂訪美時,最響往的就正是能與時已執美國心理學界牛耳的詹姆斯相見,並得到他的加持。詹姆斯雖然對新興的精神分析學不乏好感,他的興趣則始終放在「意識」的層面。他常年苦思人之所以為人的種種嚴肅議題,諸如自我意識的本質、自由意志與命定論(Determinism)並存的弔詭、靈魂與宗教情操的存在與屬性等。雖然伴隨這苦思的是大半生經年累月的極度憂鬱與種種嚴重身心症狀,他還是「甘之若飴」,勇往直前,晚年還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創立「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徹底經驗主義」(Radical Empiricism),流風所及,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世界的面貌。
如前所述,這本書從原初的構想到最後的成型,有說不盡的因緣。在許多關鍵點,如果沒有得到那麼多的支持與鼓勵,恐怕自己不管有多少熱情,也難以為繼。付梓前夕,感激之情,恐難盡述。不過首先最需要致謝的,就是《當代醫學》的編輯與同仁們,放心讓我開闢這個專欄。不僅如此,從一開始,我就有了這麼一群熱誠的「忠實讀者」:廖運範醫師(雜誌發行人)及其夫人黃妙珠醫師、賴其萬醫師(社長)、符傳孝醫師、張天鈞醫師(總編輯)及林欽沂總經理。他們都是筆者年少輕狂時代的老友,現在正處其各自事業、人生的巔峰,可謂名符其實的「日理萬機」,卻總是隨時把手邊的事情放下,用心與你對談。文稿一寄出,即時有回應,細讀、評點、加油打氣,依眉兒往往返返、字句琢磨。能有這樣的朋友,人生何憾!在此同時,也要感謝《當代醫學》的許翠玲小姐。沒有她的按時提醒、勤於催稿、並到最後一分鐘都不放棄,繼續追稿,這些稿件就沒有可能按月刊出、累積成冊。
感謝好友王浩威醫師這幾年對將這些篇章收集成書之構想的熱心回應與襄助;以及心靈工坊王桂花總編輯的企劃慧眼與積極推動。心靈工坊執行編輯陳乃賢小姐及行銷企劃許文薰小姐在本書編輯與出版過程中,竭盡心力。她們敬業與熱誠,我銘感於心。
在這麼多朋友及專業人士的關懷挹注之外,我何幸身邊還有一位「終生主編」的妻子宋文玲。身為臨床心理學博士並有多年執業經驗的文玲,對心理治療學的開創者們自然也都一直趣味盎然。雖然她只具名為本書中幾篇的共同作者,每篇文章從構思到完成,其實都得益於我們的反覆討論。 她也是本書每篇文稿「最初始」的讀者,改正多如牛毛的錯別字、推敲字句、修刪內容。我的為人雖然沈默寡言,為文卻常不免有過於渲染的毛病。凡事力求精準簡約的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複查資料來源、刪除與主題沒有直接關係的內容,有時大筆一揮,就刪掉好幾段,刪得我心疼,不免就偷偷又把它們放回去了。幾番來回反覆,終於發現,我寫文章就如我的飲食口味,喜歡「加油添醋」,而她習慣的則是「少油少鹽」。這樣的協調雖然難免有點辛苦,但也幸虧有她努力把關,這些成品才不至於如脫繮的野馬、橫衝直撞、失去重心。
本書的構思寫作,都是文玲與我在二零零九年遷居舊金山之後的事。正巧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女兒欣怡不約而同地也決定來此定居,讓我們很快就有了「落地生根」的感覺。我們的姊妹、親友的經常來訪,也更讓我們能安心地在這個城市「安居樂業」,繼續開展我們的新生涯,在此也一併致謝。
目次
第一輯 「盛世」維也納
「雪茄有時就只是雪茄」──佛洛伊德的成癮問題
最危險的治療方法──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
「兄友弟恭」愁殺人──個體心理學鼻祖阿德勒
生太飄零死亦難──蘭克的傳奇人生
從性格分析到呼風喚雨──賴克的輝煌與悲劇
佛洛依德的魔法師──將精神分析學帶入英語世界的瓊思
淒涼絢麗的人生──「客體關係理論」鼻祖梅蘭妮.克萊恩
當佛洛伊德遇上蒂凡妮──安娜.佛洛伊德與兒童精神分析學源起
浴火重生,大難致福──意義治療大師維克多.法蘭可
第二輯 從大洋到大洋
重訪玫瑰園──從《未曾許諾的玫瑰園》探討賴克蔓的一生
美國精神醫學史上的奇葩──蘇利文的大起大落
女兒眼中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與葛雷果理.貝特生的奇妙組合
甘地自甘地,路德自路德──流浪漢艾瑞克與心靈導師艾瑞克森
催眠大師音容宛在──米爾頓.艾瑞克森的傳奇
意識、情感與自由意志──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
「雪茄有時就只是雪茄」──佛洛伊德的成癮問題
最危險的治療方法──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
「兄友弟恭」愁殺人──個體心理學鼻祖阿德勒
生太飄零死亦難──蘭克的傳奇人生
從性格分析到呼風喚雨──賴克的輝煌與悲劇
佛洛依德的魔法師──將精神分析學帶入英語世界的瓊思
淒涼絢麗的人生──「客體關係理論」鼻祖梅蘭妮.克萊恩
當佛洛伊德遇上蒂凡妮──安娜.佛洛伊德與兒童精神分析學源起
浴火重生,大難致福──意義治療大師維克多.法蘭可
第二輯 從大洋到大洋
重訪玫瑰園──從《未曾許諾的玫瑰園》探討賴克蔓的一生
美國精神醫學史上的奇葩──蘇利文的大起大落
女兒眼中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與葛雷果理.貝特生的奇妙組合
甘地自甘地,路德自路德──流浪漢艾瑞克與心靈導師艾瑞克森
催眠大師音容宛在──米爾頓.艾瑞克森的傳奇
意識、情感與自由意志──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
書摘/試閱
〔摘文〕
最危險的治療方法──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
一九九三年我在現已倒閉的邊境書店(Borders)新書陳列櫃上第一次看到這本書,它的全名是《危險療程──心理學大師榮格、佛洛伊德,與她的故事》(A Most Dangerous Method—The Story of Jung, Freud and Sabina Spielrein )。此書最近再度引人注目,可能是因為據之改編的電影《危險療程》(A Dangerous Method )在不久前正式上映,頗獲好評。英文片名與書名一字之差,不知是否基於票房考量,還是顧慮到心理衛生界人士的反應。
雖然自大學以來我就一直對榮格(Carl G.Jung; 1875-1961)以及他與佛洛伊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十分好奇,但在讀這本書之前,所知其實非常有限。以前印象中的榮格,總是隔著一層神祕的面紗,讓人不免有霧裡看花的感覺。透過這本書,我才開始對榮格這個人本身及其思想的來龍去脈,有比較清楚的概念,也比較能夠體會,在神祕面紗下的榮格(以及佛洛伊德或其他的「偉人」),都不免時時身陷於七情六慾,不得不持續地掙扎、追尋、探索。他們原來也是活生生的人,言行常有瑕疵、思想難免矛盾。他們不是天縱英明,不應該是完美的偶像。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洞見,才會與我們有切身的關聯,才更彌足珍貴。
世紀大會面
大多數人談及榮格的生涯與事業時,總難免會把他在一九○七年與佛洛伊德的初次會面當作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那年已滿五十歲的佛洛伊德,其學說才終於開始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同時也引來日漸增多的攻擊。榮格雖然三十出頭,因追隨那個時代精神醫學泰斗尤金.布雷勒(Eugen Bleuler; 1857-1939)多年,已是瑞士蘇黎世大學伯格霍茲里(Burghölzli)精神專科醫院的第二把手。他的確才華橫溢,其時已因「字詞聯想」(word association)的研究而享譽歐美。
這個研究的目的,原初是為了要幫布雷勒收集「正常人」的資料,用以對照、了解精神科病人的思考過程。他意外地發現,「正常人」並不清楚自己因何從一個想法跳到另一個想法。同時,「皮膚電流反應」(Galvanic Skin Response)以及用精確的碼錶測量出來的「反應時間」,則顯示聯想的快慢與字詞所引發的情緒極有關聯。他由此而認定,心靈包含了比意識還多的領域,人的行為常被意識之外的力量所左右。
這種力量由何而來?布雷勒建議他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布雷勒其時在精神病理學方面的成就已與埃彌爾.克雷培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齊名。他首創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詞後來甚至取代了後者的「早發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延用至今。有趣的是,他比佛洛伊德(以及克雷培林)只小一歲,早年(1884)也遊學巴黎,同樣受教於神經醫學大師沙考,親眼見證催眠術對精神科病人的效力。其後他雖然一直留在精神專科療養院系統裡,卻持續對催眠現象及暗示作用保持高度的興趣。佛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第一本書《論歇斯底里》,就得到他很高的評價。一九○○年出爐的《夢的解析》,更讓他相信,佛洛伊德這位從未進入正統精神醫學殿堂的神經科學家兼心理治療師,的確極有創意,能言人之所未言。他開始在蘇黎世大學組織佛洛伊德學說研討會,並與佛氏正式接觸。佛洛伊德興奮莫名,隨即建議他可以用通信的方式為布雷勒做精神分析。佛洛伊德的意圖,是要經過蘇黎世大學傳播他的新見解。布雷勒則希望由親身的體驗,來檢視佛洛伊德理論的科學性與實用性。此後五年,兩人書信不斷。布雷勒把個人的身世與家庭資料,以及他的許多夢境,毫無保留地寄給佛洛伊德。但是他對佛洛伊德的分析卻常不能理解,也常抱怨佛氏苛求他人全盤接受他的整個理論體系。當佛洛伊德搬出他新發展的阻抗(resistance)理論來解釋布雷勒的不理解時,他就更歉難同意了。作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與醫學家,他非常情願、但也只願接受理論裡可以驗證或可以運用的部分。一九一二年他們終於分道揚鑣,當然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但是兩人立場如此不同,其結局應該是早就註定了吧!
正是在這蘇黎世與維也納「眉目傳情」的十年裡,榮格從早期對佛洛伊德理論抱持懷疑與批評的態度,蛻變成為精神分析運動的中堅與健將。一九○○年當布雷勒把《夢的解析》一書介紹給他時,他還抱怨此書深澀難解。一九○四年他在姑且一試的情況下,將佛洛伊德的「談話治療」應用於一個十分難纏的病人(也就是薩賓娜.史碧爾埃;詳後)身上,居然有效。但是一直到兩三年後,他對佛洛伊德的態度還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在他一九○六年出版的《早發性痴呆症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的序言裡,他在表達對佛氏理論的推崇的同時,還是不忘堅持理論不能當教條,特別標明他對「幼兒性慾」之類概念的不贊同。
繼布雷勒之後,榮格也在一九○六年開始與佛洛伊德通信。翌年他奉乃師之命,去維也納「探底」。未料兩人一見投緣,從下午一點一路談到次日清晨兩點,十三個小時裡廢寢忘食,幾無間斷。多年後,榮格追憶這個「世紀大會面」時說:「佛洛伊德是在我生命裡第一個真正重要的人。他與眾不同、充滿智慧、頗富機靈。但是他也讓我迷惑、捉摸不定。」榮格表達了他對佛氏性慾理論的疑慮,但是他「辯不過他」。榮格也坦承他從小對靈魂與通靈現象的興趣,佛洛伊德的臨別贈言卻是「請千萬不要放棄性慾理論,不要把青春拋擲在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上」。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於焉開展。在其後五年裡,兩人交換了七百多封熱情洋溢、挖心掏肺、也時或不免勾心鬥角的書信。
誰先昏倒
佛洛伊德當時正在尋找一個兒子。同時,不管是否自知,榮格也一直在尋覓父親。兩人由是一拍即合,其後關係有時「如膠似漆」。對佛洛伊德而言,榮格的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他精力充沛、聰穎過人,年紀輕輕就已享譽國際。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猶太人,他的加入,可以幫助精神分析術建立其普世性,使之不再被人認為「只是」猶太人的心理學。榮格的父親是個不怎麼成功的鄉村牧師,他的母親則是在巴塞爾(Basel)城裡長大的名門閨秀,從小嬌生慣養,不習慣鄉間生活。榮格的童年想必是非常地孤獨寂寞。他是獨子,上面的三個哥哥都活不過嬰兒期。他的母親常因不知名的疾病住院,一住就是幾個月,把他丟在娘家,
由單身的姨媽照顧。在家的時候,他的媽媽也還是非常冷漠疏遠,經常足不出戶,一個人待在臥房裡。雖然他的外祖父是位知名的牧師,他的母親與其他家人卻多有通靈的能力,常聚集討論神鬼附身等超自然現象。榮格對他們這種與亡魂溝通的秉賦又愛又怕,終其一生,一直在信與疑之間掙扎。
榮格童年時主要的安定力量來自父親,但是到了青春期,當他開始探索人生的意義與宇宙的奧祕之時,身為牧師的父親卻不能給他滿意的答案。「他叫我不要想,相信就好。」失望之餘,他拒絕繼續上教堂。二十歲的時候,父親病危,他卻沉浸於觀察、記錄附身於表姐妹們的「亡魂」的言行(後來成為他醫學博士論文的資料來源),對父親不聞不問。
在佛洛伊德身上,榮格似乎終於找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父親。在他寫給佛洛伊德的書信裡,榮格千方百計討好他,有時肉麻得讓人臉紅。他坦承自己對佛洛伊德有同性戀的愛慕傾向。他有時發揮佛氏的理論過了頭,有時也忍不住重提他對靈魂與玄學的興趣,但是一經指正,馬上就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似乎對佛洛伊德知無不言,其實在許多方面,當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或想法會遭受佛洛伊德的批評時,就不免刻意隱瞞,甚或堅決否認。
我們現在回溯這一段陳年往事,或許會直覺地以為榮格這樣的曲意奉承,是為了權位,其實並不盡然。榮格雖然年輕,他當時的學術地位已相當穩固。如果只是為了升遷,他完全沒有必要得到佛洛伊德的支持。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他與佛洛伊德的牽扯,毀了他在傳統學術界的生涯。他的確是因為佛洛伊德的支持,才順利成為新成立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會長(佛洛伊德原本提議要他做終生會長,後來因為太多人反對才萬般不情願地把「終生」這兩個字拿掉),可是佛洛伊德恐怕也別無選擇。比起佛洛伊德的維也納圈子,那時候的蘇黎世是更開放、更具國際性的。即使在一九一一年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帶著維也納幾乎一半的成員出走之前,蘇黎世的會眾,論質論量,都已比維也納為優。就客觀的情勢來講,其實是佛洛伊德更需要榮格,而不是榮格在利用佛洛伊德。
所以不管之前佛洛伊德幾乎清一色的猶太裔追隨者多嫉妒,榮格一開始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佛洛伊德的當然繼承人(heir apparent),他最優秀、寄望最深的兒子。但是就如佛洛伊德聞名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這個概念所呈現的,成器的兒子往往是父親最大的威脅,所以也就難怪佛洛伊德寫給榮格的信裡,也不免充滿心機,有時甚至不惜歪曲事實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佛洛伊德兩次昏倒中,非常具體地、戲劇化地表現出來。
佛洛伊德笫一次當著榮格的面昏倒,是在兩人應邀結伴同行去美國麻州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會集在不來梅(Bremen)等船的時候。其時考古學家在北歐許多沼澤裡發現保存完好的史前人遺體,面貌栩栩如生。榮格覺得他們可能是歐洲人的祖先,對他們非常有興趣,一路上不時提起。有一天晚飯後,他又開始談這些「沼澤人」,佛洛伊德忽然說:「你對他們這麼關注,是因為你潛意識裡有殺死我的慾望。」說完隨即昏倒(這只是你們亞利安人的事,可與我們猶太人無關,佛洛伊德在昏倒前,或許是這麼想的)。
兩個人的美洲之行都很成功。佛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美國當代心理學元老 ,包括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都趕來參與。他用德語講的五場演說,隨即被翻譯為英文,刊載於美國心理學雜誌,流傳至今。榮格也由此行而獲福旦大學(FordhamUniversity)邀請,次年再回美國作為時六週的講學。但是兩人的裂痕,在他們回歐洲的路上,卻已逐漸浮現。他們在船上不停地互相分析彼此的夢境。根據榮格後來的回憶,有一次到了非常重要的關鍵,佛洛伊德卻忽然停頓了下來,隔了一會兒才說,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需要維護我的權威。就像許多怨偶,他們的爭執從此時隱時現,又拖了三年多的時間,其間還穿插了許多似有意似無意的誤會,終於在一九一二年底引發了佛洛伊德的第二次當眾昏倒。這之後不久,戰火就急速表面化了。幾番言詞犀利的書信往返及無數次的反覆思量之後,佛洛伊德終於痛下決心,壯士斷腕,宣佈與榮格「絕交」。
佛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也與考古學以及父子關係有關。當時兩人及其他精神分析運動核心成員齊集在慕尼黑開會討論學會期刊編輯事宜,氣氛頗為緊張。午宴後有人把話題扯到古埃及的法老王阿曼諾費斯四世(Amenophis IV),主張他之所以改變傳統,首創一神信仰,源自他對其父親的複雜情結(father complex)。榮格強烈抗議,認為阿曼諾費斯四世的原創力與他的父親無關,他的一神信仰不是反抗父親的結果,阿曼諾費斯四世其實是很尊重他的父親的,可是為了「真理」,不得不銷毀父祖輩所崇拜的神祇塑像。榮格又說,所有其他的法老,固然沒有破壞其父親所崇拜的神像,但是「天無二日」,他們也就毫無例外地都以自己的名字及雕像取代其父輩留下的任何痕跡。榮格這一番話剛說完,佛洛伊德就從椅子上滑了下去,不省人事。榮格急忙將他抱起,放在躺椅上。過了好一陣子,佛洛伊德才回過神來,說「如果死亡這樣甜蜜的話,那也蠻不錯」。
榮格其實才是個很會昏倒的人。他在十二歲時因細故被一個同學揍了一頓之後就常常昏倒,被懷疑有癲癇症。有趣的是,在這「父子反目」的過程中,昏倒的卻不是他。或許他那時候,忙於反抗,並不清楚自己一旦被心目中理想的父親棄絕之後,面對的會是如何絕望的深淵。
禍水的名字就是女人嗎?
如前所述,一九○四年薩賓娜住進伯格霍茲里醫院,成為榮格第一個嘗試使用精神分析療法的實驗品。其時剛滿十八歲的薩賓娜是個來自俄國黑海岸邊的猶太女孩,嬌小美豔、聰慧敏感。在榮格的關注下,她多年不癒的歇斯底里症很快就好起來了,但是她同時也就愛上了他。那時新婚不久的榮格還是一個拘謹守禮、愛惜顏面的人。雖然被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迷人女孩深深吸引,榮格對她的痴情無從回應。但是在他的鼓勵下,她隔年就進入蘇黎世大學醫學院習醫。
幾年後,薩賓娜再度成為榮格的病人,也很快地就又愛上了他。她幻想他們會有一個結合猶太人與亞利安人的小孩,長大之後會成為救世英雄。榮格在接受與逃避之間來回擺盪,時而狂喜、時而愧疚,自承沒有醫德。但是「他的潛意識就握在她手裡」,他們的關係,也就繼續如萬花筒似地離離合合,流轉不息。她寫信向佛洛伊德投訴,他則抵死不認,堅持她處心積慮,硬是要引誘他,這一切都是她一廂情願的幻想。佛洛依德在一旁靜觀好戲,也樂得有這個把柄在手,必要時可以用來要脅榮格。直到一九一三年他已與榮格「絕交」,而薩賓娜也已結婚即將生育之時,佛洛伊德才鬆口對她說,「不管怎麼樣,我們都還是猶太人,他們永遠也不會了解我們、尊重我們」。
榮格在這兩次「治療」之間作風的轉變,固然可以有許多解讀,但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應該是來自他另外一位同事兼病人的影響。小榮格兩歲的奧圖.格羅斯(Otto Gross; 1877- 1920)是除了榮格以外,唯一被佛洛伊德認為是天才的精神分析師。格羅斯熱情洋溢、聰慧過人、人見人愛。他也是個放浪形骸,積年沉迷於嗎啡與古柯鹼不能自拔的人。他成天成夜流連於咖啡廳與酒廊,在那些地方結識、「治療」許多「前衞」文人、藝術家,也在那裡勾引一個又一個名女人,其中包括後來嫁給名作家D.H.勞倫斯(D. H. Laurence; 1885-1930),也就是《查泰萊夫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一書女主角原型的芭倫妮絲.弗莉達.馮.李奇特芬(Baroness Frieda von Richthofen; 1879-1956)。諷刺的是,奧圖的父親,漢斯.格羅斯(Hans Gross; 1847-1915),正是現代「犯罪學」之父,享譽國際。眼看著他的獨子即將掉落於萬丈深淵,漢斯同時寫信向布雷勒及佛洛伊德求援,兩人不約而同地推薦榮格。耐不住他們的央求,榮格勉強同意讓格羅斯入院,成為他的主治醫師。此後半年,榮格只得日日與這個他素所厭惡的人為伍。他分析格羅斯,急於向兩個老師表現他的治療能力。沒想到事隔不久,他就反而變成被格羅斯分析的人。他們同樣佩服尼采與佛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學將會改變世界。但是他也從格羅斯身上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格羅斯的性觀念讓他震驚,也讓他著迷。格羅斯認為,不論從演化論還是精神分析學的眼光來看,人的天性本來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性自由的。不論男女,都需要不同的性伴侶,禮教帶來的壓抑不合人性,是疾病之源。
兩個天才在一起相處半年,誰影響誰,誰贏誰輸,又有誰能說得定?但是這一次榮格的確是一敗塗地。他的慘敗,不單是因為格羅斯於半年後翻牆「越獄」出逃,一點都不給他面子。更為嚴重的是,格羅斯人是走了,卻留下人性裡有「多重配偶」(polygamous)傾向的這個觀念,繼續在榮格心中萌芽、滋長。當然,如果榮格的「潛意識」裡原本沒有這樣的慾望,他應該是不會這麼容易被「洗腦」的。當然到頭來格羅斯才是最大的輸家;他從此窮困潦倒,幾年後便如流星般消逝於天際。但是如果沒有格羅斯(加上薩賓娜)的出現,榮格的人生,大概會是很不一樣的。
最危險的治療方法──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
一九九三年我在現已倒閉的邊境書店(Borders)新書陳列櫃上第一次看到這本書,它的全名是《危險療程──心理學大師榮格、佛洛伊德,與她的故事》(A Most Dangerous Method—The Story of Jung, Freud and Sabina Spielrein )。此書最近再度引人注目,可能是因為據之改編的電影《危險療程》(A Dangerous Method )在不久前正式上映,頗獲好評。英文片名與書名一字之差,不知是否基於票房考量,還是顧慮到心理衛生界人士的反應。
雖然自大學以來我就一直對榮格(Carl G.Jung; 1875-1961)以及他與佛洛伊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十分好奇,但在讀這本書之前,所知其實非常有限。以前印象中的榮格,總是隔著一層神祕的面紗,讓人不免有霧裡看花的感覺。透過這本書,我才開始對榮格這個人本身及其思想的來龍去脈,有比較清楚的概念,也比較能夠體會,在神祕面紗下的榮格(以及佛洛伊德或其他的「偉人」),都不免時時身陷於七情六慾,不得不持續地掙扎、追尋、探索。他們原來也是活生生的人,言行常有瑕疵、思想難免矛盾。他們不是天縱英明,不應該是完美的偶像。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洞見,才會與我們有切身的關聯,才更彌足珍貴。
世紀大會面
大多數人談及榮格的生涯與事業時,總難免會把他在一九○七年與佛洛伊德的初次會面當作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那年已滿五十歲的佛洛伊德,其學說才終於開始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同時也引來日漸增多的攻擊。榮格雖然三十出頭,因追隨那個時代精神醫學泰斗尤金.布雷勒(Eugen Bleuler; 1857-1939)多年,已是瑞士蘇黎世大學伯格霍茲里(Burghölzli)精神專科醫院的第二把手。他的確才華橫溢,其時已因「字詞聯想」(word association)的研究而享譽歐美。
這個研究的目的,原初是為了要幫布雷勒收集「正常人」的資料,用以對照、了解精神科病人的思考過程。他意外地發現,「正常人」並不清楚自己因何從一個想法跳到另一個想法。同時,「皮膚電流反應」(Galvanic Skin Response)以及用精確的碼錶測量出來的「反應時間」,則顯示聯想的快慢與字詞所引發的情緒極有關聯。他由此而認定,心靈包含了比意識還多的領域,人的行為常被意識之外的力量所左右。
這種力量由何而來?布雷勒建議他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布雷勒其時在精神病理學方面的成就已與埃彌爾.克雷培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齊名。他首創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詞後來甚至取代了後者的「早發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延用至今。有趣的是,他比佛洛伊德(以及克雷培林)只小一歲,早年(1884)也遊學巴黎,同樣受教於神經醫學大師沙考,親眼見證催眠術對精神科病人的效力。其後他雖然一直留在精神專科療養院系統裡,卻持續對催眠現象及暗示作用保持高度的興趣。佛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第一本書《論歇斯底里》,就得到他很高的評價。一九○○年出爐的《夢的解析》,更讓他相信,佛洛伊德這位從未進入正統精神醫學殿堂的神經科學家兼心理治療師,的確極有創意,能言人之所未言。他開始在蘇黎世大學組織佛洛伊德學說研討會,並與佛氏正式接觸。佛洛伊德興奮莫名,隨即建議他可以用通信的方式為布雷勒做精神分析。佛洛伊德的意圖,是要經過蘇黎世大學傳播他的新見解。布雷勒則希望由親身的體驗,來檢視佛洛伊德理論的科學性與實用性。此後五年,兩人書信不斷。布雷勒把個人的身世與家庭資料,以及他的許多夢境,毫無保留地寄給佛洛伊德。但是他對佛洛伊德的分析卻常不能理解,也常抱怨佛氏苛求他人全盤接受他的整個理論體系。當佛洛伊德搬出他新發展的阻抗(resistance)理論來解釋布雷勒的不理解時,他就更歉難同意了。作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與醫學家,他非常情願、但也只願接受理論裡可以驗證或可以運用的部分。一九一二年他們終於分道揚鑣,當然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但是兩人立場如此不同,其結局應該是早就註定了吧!
正是在這蘇黎世與維也納「眉目傳情」的十年裡,榮格從早期對佛洛伊德理論抱持懷疑與批評的態度,蛻變成為精神分析運動的中堅與健將。一九○○年當布雷勒把《夢的解析》一書介紹給他時,他還抱怨此書深澀難解。一九○四年他在姑且一試的情況下,將佛洛伊德的「談話治療」應用於一個十分難纏的病人(也就是薩賓娜.史碧爾埃;詳後)身上,居然有效。但是一直到兩三年後,他對佛洛伊德的態度還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在他一九○六年出版的《早發性痴呆症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的序言裡,他在表達對佛氏理論的推崇的同時,還是不忘堅持理論不能當教條,特別標明他對「幼兒性慾」之類概念的不贊同。
繼布雷勒之後,榮格也在一九○六年開始與佛洛伊德通信。翌年他奉乃師之命,去維也納「探底」。未料兩人一見投緣,從下午一點一路談到次日清晨兩點,十三個小時裡廢寢忘食,幾無間斷。多年後,榮格追憶這個「世紀大會面」時說:「佛洛伊德是在我生命裡第一個真正重要的人。他與眾不同、充滿智慧、頗富機靈。但是他也讓我迷惑、捉摸不定。」榮格表達了他對佛氏性慾理論的疑慮,但是他「辯不過他」。榮格也坦承他從小對靈魂與通靈現象的興趣,佛洛伊德的臨別贈言卻是「請千萬不要放棄性慾理論,不要把青春拋擲在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上」。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於焉開展。在其後五年裡,兩人交換了七百多封熱情洋溢、挖心掏肺、也時或不免勾心鬥角的書信。
誰先昏倒
佛洛伊德當時正在尋找一個兒子。同時,不管是否自知,榮格也一直在尋覓父親。兩人由是一拍即合,其後關係有時「如膠似漆」。對佛洛伊德而言,榮格的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他精力充沛、聰穎過人,年紀輕輕就已享譽國際。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猶太人,他的加入,可以幫助精神分析術建立其普世性,使之不再被人認為「只是」猶太人的心理學。榮格的父親是個不怎麼成功的鄉村牧師,他的母親則是在巴塞爾(Basel)城裡長大的名門閨秀,從小嬌生慣養,不習慣鄉間生活。榮格的童年想必是非常地孤獨寂寞。他是獨子,上面的三個哥哥都活不過嬰兒期。他的母親常因不知名的疾病住院,一住就是幾個月,把他丟在娘家,
由單身的姨媽照顧。在家的時候,他的媽媽也還是非常冷漠疏遠,經常足不出戶,一個人待在臥房裡。雖然他的外祖父是位知名的牧師,他的母親與其他家人卻多有通靈的能力,常聚集討論神鬼附身等超自然現象。榮格對他們這種與亡魂溝通的秉賦又愛又怕,終其一生,一直在信與疑之間掙扎。
榮格童年時主要的安定力量來自父親,但是到了青春期,當他開始探索人生的意義與宇宙的奧祕之時,身為牧師的父親卻不能給他滿意的答案。「他叫我不要想,相信就好。」失望之餘,他拒絕繼續上教堂。二十歲的時候,父親病危,他卻沉浸於觀察、記錄附身於表姐妹們的「亡魂」的言行(後來成為他醫學博士論文的資料來源),對父親不聞不問。
在佛洛伊德身上,榮格似乎終於找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父親。在他寫給佛洛伊德的書信裡,榮格千方百計討好他,有時肉麻得讓人臉紅。他坦承自己對佛洛伊德有同性戀的愛慕傾向。他有時發揮佛氏的理論過了頭,有時也忍不住重提他對靈魂與玄學的興趣,但是一經指正,馬上就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似乎對佛洛伊德知無不言,其實在許多方面,當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或想法會遭受佛洛伊德的批評時,就不免刻意隱瞞,甚或堅決否認。
我們現在回溯這一段陳年往事,或許會直覺地以為榮格這樣的曲意奉承,是為了權位,其實並不盡然。榮格雖然年輕,他當時的學術地位已相當穩固。如果只是為了升遷,他完全沒有必要得到佛洛伊德的支持。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他與佛洛伊德的牽扯,毀了他在傳統學術界的生涯。他的確是因為佛洛伊德的支持,才順利成為新成立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會長(佛洛伊德原本提議要他做終生會長,後來因為太多人反對才萬般不情願地把「終生」這兩個字拿掉),可是佛洛伊德恐怕也別無選擇。比起佛洛伊德的維也納圈子,那時候的蘇黎世是更開放、更具國際性的。即使在一九一一年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帶著維也納幾乎一半的成員出走之前,蘇黎世的會眾,論質論量,都已比維也納為優。就客觀的情勢來講,其實是佛洛伊德更需要榮格,而不是榮格在利用佛洛伊德。
所以不管之前佛洛伊德幾乎清一色的猶太裔追隨者多嫉妒,榮格一開始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佛洛伊德的當然繼承人(heir apparent),他最優秀、寄望最深的兒子。但是就如佛洛伊德聞名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這個概念所呈現的,成器的兒子往往是父親最大的威脅,所以也就難怪佛洛伊德寫給榮格的信裡,也不免充滿心機,有時甚至不惜歪曲事實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佛洛伊德兩次昏倒中,非常具體地、戲劇化地表現出來。
佛洛伊德笫一次當著榮格的面昏倒,是在兩人應邀結伴同行去美國麻州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會集在不來梅(Bremen)等船的時候。其時考古學家在北歐許多沼澤裡發現保存完好的史前人遺體,面貌栩栩如生。榮格覺得他們可能是歐洲人的祖先,對他們非常有興趣,一路上不時提起。有一天晚飯後,他又開始談這些「沼澤人」,佛洛伊德忽然說:「你對他們這麼關注,是因為你潛意識裡有殺死我的慾望。」說完隨即昏倒(這只是你們亞利安人的事,可與我們猶太人無關,佛洛伊德在昏倒前,或許是這麼想的)。
兩個人的美洲之行都很成功。佛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美國當代心理學元老 ,包括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都趕來參與。他用德語講的五場演說,隨即被翻譯為英文,刊載於美國心理學雜誌,流傳至今。榮格也由此行而獲福旦大學(FordhamUniversity)邀請,次年再回美國作為時六週的講學。但是兩人的裂痕,在他們回歐洲的路上,卻已逐漸浮現。他們在船上不停地互相分析彼此的夢境。根據榮格後來的回憶,有一次到了非常重要的關鍵,佛洛伊德卻忽然停頓了下來,隔了一會兒才說,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需要維護我的權威。就像許多怨偶,他們的爭執從此時隱時現,又拖了三年多的時間,其間還穿插了許多似有意似無意的誤會,終於在一九一二年底引發了佛洛伊德的第二次當眾昏倒。這之後不久,戰火就急速表面化了。幾番言詞犀利的書信往返及無數次的反覆思量之後,佛洛伊德終於痛下決心,壯士斷腕,宣佈與榮格「絕交」。
佛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也與考古學以及父子關係有關。當時兩人及其他精神分析運動核心成員齊集在慕尼黑開會討論學會期刊編輯事宜,氣氛頗為緊張。午宴後有人把話題扯到古埃及的法老王阿曼諾費斯四世(Amenophis IV),主張他之所以改變傳統,首創一神信仰,源自他對其父親的複雜情結(father complex)。榮格強烈抗議,認為阿曼諾費斯四世的原創力與他的父親無關,他的一神信仰不是反抗父親的結果,阿曼諾費斯四世其實是很尊重他的父親的,可是為了「真理」,不得不銷毀父祖輩所崇拜的神祇塑像。榮格又說,所有其他的法老,固然沒有破壞其父親所崇拜的神像,但是「天無二日」,他們也就毫無例外地都以自己的名字及雕像取代其父輩留下的任何痕跡。榮格這一番話剛說完,佛洛伊德就從椅子上滑了下去,不省人事。榮格急忙將他抱起,放在躺椅上。過了好一陣子,佛洛伊德才回過神來,說「如果死亡這樣甜蜜的話,那也蠻不錯」。
榮格其實才是個很會昏倒的人。他在十二歲時因細故被一個同學揍了一頓之後就常常昏倒,被懷疑有癲癇症。有趣的是,在這「父子反目」的過程中,昏倒的卻不是他。或許他那時候,忙於反抗,並不清楚自己一旦被心目中理想的父親棄絕之後,面對的會是如何絕望的深淵。
禍水的名字就是女人嗎?
如前所述,一九○四年薩賓娜住進伯格霍茲里醫院,成為榮格第一個嘗試使用精神分析療法的實驗品。其時剛滿十八歲的薩賓娜是個來自俄國黑海岸邊的猶太女孩,嬌小美豔、聰慧敏感。在榮格的關注下,她多年不癒的歇斯底里症很快就好起來了,但是她同時也就愛上了他。那時新婚不久的榮格還是一個拘謹守禮、愛惜顏面的人。雖然被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迷人女孩深深吸引,榮格對她的痴情無從回應。但是在他的鼓勵下,她隔年就進入蘇黎世大學醫學院習醫。
幾年後,薩賓娜再度成為榮格的病人,也很快地就又愛上了他。她幻想他們會有一個結合猶太人與亞利安人的小孩,長大之後會成為救世英雄。榮格在接受與逃避之間來回擺盪,時而狂喜、時而愧疚,自承沒有醫德。但是「他的潛意識就握在她手裡」,他們的關係,也就繼續如萬花筒似地離離合合,流轉不息。她寫信向佛洛伊德投訴,他則抵死不認,堅持她處心積慮,硬是要引誘他,這一切都是她一廂情願的幻想。佛洛依德在一旁靜觀好戲,也樂得有這個把柄在手,必要時可以用來要脅榮格。直到一九一三年他已與榮格「絕交」,而薩賓娜也已結婚即將生育之時,佛洛伊德才鬆口對她說,「不管怎麼樣,我們都還是猶太人,他們永遠也不會了解我們、尊重我們」。
榮格在這兩次「治療」之間作風的轉變,固然可以有許多解讀,但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應該是來自他另外一位同事兼病人的影響。小榮格兩歲的奧圖.格羅斯(Otto Gross; 1877- 1920)是除了榮格以外,唯一被佛洛伊德認為是天才的精神分析師。格羅斯熱情洋溢、聰慧過人、人見人愛。他也是個放浪形骸,積年沉迷於嗎啡與古柯鹼不能自拔的人。他成天成夜流連於咖啡廳與酒廊,在那些地方結識、「治療」許多「前衞」文人、藝術家,也在那裡勾引一個又一個名女人,其中包括後來嫁給名作家D.H.勞倫斯(D. H. Laurence; 1885-1930),也就是《查泰萊夫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一書女主角原型的芭倫妮絲.弗莉達.馮.李奇特芬(Baroness Frieda von Richthofen; 1879-1956)。諷刺的是,奧圖的父親,漢斯.格羅斯(Hans Gross; 1847-1915),正是現代「犯罪學」之父,享譽國際。眼看著他的獨子即將掉落於萬丈深淵,漢斯同時寫信向布雷勒及佛洛伊德求援,兩人不約而同地推薦榮格。耐不住他們的央求,榮格勉強同意讓格羅斯入院,成為他的主治醫師。此後半年,榮格只得日日與這個他素所厭惡的人為伍。他分析格羅斯,急於向兩個老師表現他的治療能力。沒想到事隔不久,他就反而變成被格羅斯分析的人。他們同樣佩服尼采與佛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學將會改變世界。但是他也從格羅斯身上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格羅斯的性觀念讓他震驚,也讓他著迷。格羅斯認為,不論從演化論還是精神分析學的眼光來看,人的天性本來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性自由的。不論男女,都需要不同的性伴侶,禮教帶來的壓抑不合人性,是疾病之源。
兩個天才在一起相處半年,誰影響誰,誰贏誰輸,又有誰能說得定?但是這一次榮格的確是一敗塗地。他的慘敗,不單是因為格羅斯於半年後翻牆「越獄」出逃,一點都不給他面子。更為嚴重的是,格羅斯人是走了,卻留下人性裡有「多重配偶」(polygamous)傾向的這個觀念,繼續在榮格心中萌芽、滋長。當然,如果榮格的「潛意識」裡原本沒有這樣的慾望,他應該是不會這麼容易被「洗腦」的。當然到頭來格羅斯才是最大的輸家;他從此窮困潦倒,幾年後便如流星般消逝於天際。但是如果沒有格羅斯(加上薩賓娜)的出現,榮格的人生,大概會是很不一樣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