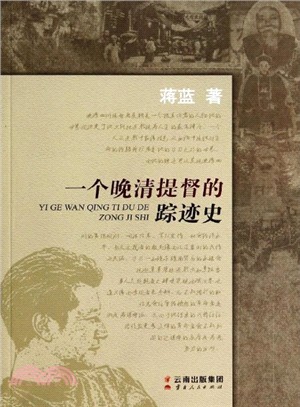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品以一個不見經傳的“二流歷史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為中心,通過他和曾經在四川歷史上風云一時的石達開、駱秉章、王闿運等縱橫交錯的關系,完成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歷史敘事。由唐友耕的蹤跡延伸開去,可以窺見晚清四川的軍隊實情、社會經濟水平以及當時的民情與民俗,等等。作品在坐實人物的歷史時空坐標之余,更為關注人物行蹤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與之相交錯的人際興衰、風物枯榮,彰顯了作品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文學底蘊,極具可讀性。
作者簡介
蔣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成都日報》高端訪談記者,《青年作家》主編。已出版《愛與欲望》、《復仇之書》、《人跡霜語錄》、《香格里拉精神史》、《拆骨為刀》、《思想存檔》、《動物論語》、《玄學獸》、《哲學獸》等文學、文化專著。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西部文學獎、布老虎散文獎。
名人/編輯推薦
序
我的出生地在川南鹽都自貢市,那里有一條沱江的支流滏溪河,為自貢市境內沱江段最大支流。河道曲如釜形,附會于水,成為河名。其源流有兩條:北源為威遠河,又稱清溪河,發源于威遠縣兩母山,全長94公里;西源為旭水河,又稱榮溪河,發源于榮縣西北榮隱山,全長73公里。兩河于鳳凰壩雙河口匯合后,始稱滏溪河,曲折蜿蜒流向東南,經貢井、自流井、仙灘、沿灘、鄧井關,于富順縣李家灣注入沱江,流程73.2公里。滏溪河城區段自雙河口起至金子凼堰閘總長8.5公里,是滏溪河的起始段,也是自貢市中心新舊城區的結合部和分界線。
在上千年采鹽的歷史中,井鹽成為了凝聚城市的動詞,那是有關井鹽蹤跡的延宕之波。本地井鹽的運銷與冷兵器時代相協調,處于肩挑、背馱狀態,架車、馬幫是常見的運輸方式,木船水運則是清中葉后自貢最先進的運輸形式。童年時的我,所有夏季都是在滏溪河里度過的。父親說,與其讓你偷偷下河送命,不如早點學會游泳。這樣在1970年,我五歲就可以獨自游泳過河了,因此可以與伙伴們在水里玩上幾個小時。比賽、打水仗、摸河底的蚌殼和螺螄,遇到運鹽巴的長長的櫓船隊,它們的動力是一艘小火輪,速度比游泳略快,但我們往往拼命追上櫓船,吊在尾舵上,直到開出兩里地,才入水游泳返回。最遠的一次,竟然到了一個叫金子凼的地方,才逆水游回來。從東興寺碼頭逆流而上,要經過關外碼頭、王爺廟到達張家沱碼頭。張家沱鹽業遺址位于自流井市區滏溪河南岸的富臺山下,是目前自貢市區內還保留舊貌的民居建筑群,同時因為一地同時修有三個祠廟而聞名。在張家沱南岸,有長數百丈的碼頭,如今全部浸泡在河水以下。在滏溪河河水清澈的年代,此地也是人們游泳的場所,碼頭則成為理想的跳臺。記得1970年中期我讀小學時,在一個灰蒙蒙的上午,特意到張家沱參加了全市紀念毛澤東暢游長江N周年的活動。數千人跳進河灣,暢游那八九百米距離,頗有“下餃子”的意味。對這段歷史的追憶和考索,我寫入到長文《有關井鹽的生活史》當中。
有言:“泰晤士河的每一滴水都是水的歷史。”崇尚知識惡力而現實行為不軌于正義的弗蘭西斯·培根自然注意到了被河流帶走的往事,他說:“名聲猶如河水,浮輕不浮重,載空不載實。”而歷史就是這樣的河流。但我高度懷疑那種宣稱擁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異能的人,你探頭入井,你能透過你的水面鏡像看到紅顏白骨、懶骨、忠骨、賊骨或者反骨嗎?也許你有,我沒這本事。
稍長,我在宜賓的金沙江、在牛佛渡口的沱江、在江陰的長江、在桂林的漓江、在樂山的大渡河與青衣江、在都江堰的岷江均下水暢游。記得2010年盛夏我到宜賓縣橫江鎮從事田野考察,又到橫江(橫江之上的朱提江,“朱提”的讀音在197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一書中標注為“shushi”,據考是僰人發音;橫江鎮人讀作“zhushi”;云南部分人讀作“shumo”,發音都較為接近)里小游了半個鐘頭。這里的水面、河坎間,距今150年前,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十幾萬兵馬與數量相當的官軍殊死一搏,雙方死亡近十萬人,二百多米寬的河道為之擁堵。當時,我就產生了鉤沉這段往事的念頭。
“鉤沉”的含義可上溯至《黃帝內經》。正常人的脈象會隨四時更替而相應變動,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難經》把石脈解釋為沉脈,創立“鉤沉”一詞的人必定熟悉于此,鉤應夏,沉應冬,“鉤沉”就是夏冬的意思。后來,逐漸成為“春秋”的另一說法。
歷史即是“人跡”鋪成。但主流史學觀認為,重大的往事才成為了“史跡”。而在個體生命與連續流動的歷史關系中,探尋歷史運行過程中個體生命的“蹤跡”,自然成了我的著手點。盡管汲深綆短,我當勉力為之。
陳嘉映先生在《事物,事實,論證》一文里指出,我們并不生活于一個事實世界,而是活在一個事情的世界。事實是事情的切片,是對事情的錘打和攤開,最終,事物、事實會構成對事情的“呈堂證供”。就是說,事情盡管神秘詭譎,但從來就不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在歷史的軌跡與個人的蹤跡之間,也許就映射了這樣的關系。歷史的軌跡是一種注重影響的呼嘯而至的宏大敘事,畛域立顯;而個人的蹤跡不過記錄的是一己的榮辱沉浮。蹤跡固然已經覆于歷史車輪的碾壓之下,但總還有一些殘剩的蛛絲馬跡存在于宏旨無心涉足的冷僻地隅,這就成為了我打撈個人蹤跡的采擷區。
如同發生的事情即是事實一樣,凡是發生的蹤跡都是軌跡。但唯有那些能夠說明歷史軌跡的人格蹤跡,才構成一種強力的個案蹤跡。
表面上看,蹤跡存留于歷史的縫隙,我們一旦將某個人的蹤跡鉤沉而出,將歷史碎片鋪開,歷史中不可解釋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靈的部分。所以,一個人的蹤跡史是把一個又一個的空間串聯并敞開,宛如我的書案上狂亂的筆觸,構成了一道插滿蒺藜與玻璃的山墻。他的思想與心跡,就像山墻上倏忽明滅的反光。第一,我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技術,才能安然通過;第二,我能夠感受到那些反光說蘊含的“能指”嗎?
當然了,回到對歷史的書寫,也并非一味在永續開放的變異中僅僅著眼于無規則沉淀。紛繁復雜的意識形態確實導致歷史的雜亂蹤跡,導致碎片化的歷史活動彌散在各個角落,但不可否認的是,總有一些基本的活動及其價值以規則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蹤跡縱然有豐富的活動和作用空間,但必定會通過觀念、知識以及相當的機制反映、制約和調節社會運行和歷史運動。雖然表面上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主觀愿望出發進行歷史活動,但他們的活動只能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下進行,而這就是歷史規律性的根源。就是說,利用所能見到的史料,進行低限度的推論與思想修復,是可行的。可惜的是,如今的歷史寫作者不是“修舊如舊”,而是一門心思進行著面目全非的臆造。
錯綜復雜的蹤跡,總是受到看不見的規律所左右,這個巨力就是社會存在。恩格斯所言:“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所以,我所關注的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一個人的“蹤跡史”,也可以說這一線索,是首先引我步入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從而帶出有關四川晚清時節的官場史、黑暗史、軍事戰爭史、執政史、民俗史、風物史等等,這就是我寫作兩年的長篇非虛構散文《一個晚清提督的蹤跡史——石達開、駱秉章、唐友耕、王閨運交錯的歷史》的初衷。這是一部旨在恢復漢語傳統文史哲三位一體的跨文體之書。一部無心取悅于文壇的非虛構之書。至于我是否能走出這一迷宮,朗然宣布:我來了我看見我說出,我沒有絕對的把握。
因而,蹤跡史與人物傳記的分野在我的視域就逐步清晰了:它與考據學派喜歡使用的研究法——諸如“名人行蹤考”也是貌合神離。
我心目中的蹤跡史,關注的是——
在盡量坐實人物的歷史時空坐標之余,更為關注其行蹤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與之相交錯的人際興衰、風物枯榮;
它偏重個人化視覺與文學敘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宏大歷史敘事所不屑的稗官野史與民間口述;
人物傳記關注的是通過人物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展示出來的心跡與思想變化,它傾心于小我之中見大我,并渴望自己對傳主的言路復原技術,躋身于正史,成為某種話語規范。這很難說孰輕孰重,不過是因角度而異。而這些汗牛充棟的傳記里,最讓人觸目驚心的即興發揮,莫過于圍繞魯迅先生的種種傳記,我稱之為“弱力的烏托邦傳”。
很清楚,我在這里談論的蹤跡,與德里達的“蹤跡論”南轅北轍。我所談論的蹤跡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不可能遁形而知天命,去關乎“在場”與否。本文所言的蹤跡接近刑事案件的偵破術——文學偵探學,這些蹤跡忠實地記錄著暴力曾經的“在場”。蹤跡在此既是進入事件主體過程的物質線索,同時也是衡定歷史的物證。
在德里達的視野中,他利用了蹤跡(有時也作“原跡”)之痕,為的是擾亂符號形而上學的決定論。但是他提示了我:蹤跡并不意味著存在一個本源,而表達了充分的、在場的意義的缺乏,蹤跡是“在場的幻影”,通過它“當下變成一種符號的符號,蹤跡的蹤跡”,這樣,文本就成了不斷書寫“蹤跡的蹤跡”的組合體。 從德里達繁復的表述中,我得到了不少啟示。暴力若得不到宣泄,它一旦獲得了比性交更充分的釋放,受害者一旦“死了”,詮釋暴力權威也就“死了”,一個時代充滿了暴徒的活力而四處飄零、無家可歸。整個歷史中心主義的宏大與在場因此徹底坍塌,剩下什么?我想,只有碎片,只有蹤跡。
我通過對唐友耕這樣一個復雜人物的蹤跡史考察,揭示個體與其存在的社會和文化的內在關系。進一步想的是,能否把思考擴展到“新社會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闕如的領域?在思想文化史與社會史之間,尋找一個中間地帶,能否如年鑒學派社會史學家所稱的“心性史”或文化史所稱的“意識史”?這的確是我心向往之的。章詒和曾經指出:“我們必須把個人記憶納入一個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個人記憶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空間里,個人記憶才有可能轉化為共同記憶,‘粉末’與‘碎片’才可能糅合成一個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和我們的后代子孫,也才可能通過這個公共空間承擔記憶,也承接記憶。”對此,我深以為然。
古人云:“一路腳跡進,一路腳跡出。”唐友耕的蹤跡把我引向了晚清時節的滇北、巴山蜀水的山野。一個沒有被歷史的手電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輩。在我看來,乃是他蟄伏于歷史的地表之下,安享他不便于見光的富貴和仙境。我將他從夢田里拉出來,我也許就成了他的敵人。而且從審美心理而言,在民國之前即使死亡還屬于絲織物,不像后來了,死亡全是化纖制品。
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是一個極具內容的人物,他的世界觀決定了他只能把殺戮視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個人從殺戮中獲得技藝,從血泊中提純對生命的經驗,并擴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由他的蹤跡可以發現晚清四川的官場規則、司法內幕、軍隊實情、社會經濟水平、起義反抗者的激烈緣由以及當時的民情與民俗。刀刃一如鏡子,鏡面背后的水銀會托起累累孽賬;殺戮亦如烹飪,當事人久處鮑魚之肆,嗅覺被油膩閉塞,味道只得由旁觀者來分辨。而不斷擢升的職位總會讓曾經憤怒的革命者逐漸成為保守派。又由于他付出的代價往往比收獲更多,這樣的革命者會不斷加固自己保守的底座,成為惡勢力的巨臂。
所以我說,最鋒利的刃,總是礪自墓碑。銹跡與石屑交替而下,個中更有無數幽魂,以沙粒的精光凝視你!
蘇軾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的確,歷史能夠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蹤跡已屬僥幸,歷史不再為之記下任何溢美之詞。如像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昭通農民起義軍靈魂人物李永和、藍大順、卯德興等人,如果說他們本就是歷史上的“箭垛式人物”,由原型到多元演化、總是引致不同時空的多層面觀照的話,那么唐友耕則是舉高這一箭垛到無蔽處的一塊石頭。所以,他偶爾也會被如像我這樣跑偏的箭頭“歪打正著”,撞出一連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為了勾勒箭垛的大豐收盛況。自然了,他們的生命原本不會像我等一樣毫無用處,他們更非插滿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們用腳下不斷涌出的血,譜寫出了“血的蹤跡”。其作用既不能證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自由的姿容,它只表明:倫理與權力需要更多的血去澆筑地盤,最后銹死板結成了歷史。
但愿從我追蹤到的“紅銹”里,可以偶爾聽見那些叫魂與梟鳴……
蔣藍
2013年1月30日于成都九眼橋
目次
被飛擲的李子與馬蹄突破的較場空間
虎帳人物的“出身論”
力摔奔馬
馬上對決
“花千總”之墓
唐友耕的寡情與重義
幾個江湖名號終于被女色策反
翠華鎮的“帽頂”大哥
屯上
一匹馬引發的血案
牛皮寨
南廣河與慶符縣
關河美女
花園庵的立場拷問
“帽頂”的詞源學
唐友耕像頑強的皰疹纏住了李藍大軍
奇人何崇政和他的祖墳
拉鋸戰中的精神勝利法
奸細如飄墜的枯葉蝶
《賊復至記略》中的“唐帽頂”手下
大山坡與獅子山的藿麻
犍為保衛戰
洼巖腔
蕭寺尋尸以及夢啟神力
丹棱縣的“大石包”
綿州內訌
用血磨刀,橫槊橫江
唐友耕從涪州城墻飛縱而下
梅花鎮的竹飆與脆蛇
清軍兵器譜
橫江鎮的陣勢
血氣浸淫的天地交感
花鳥異事
石城山
石門子的蘭花軼事
“王姑”與大壩高裝
血,漫漶于“武人貴相”之間
老鴉漩動石兒山
紫打地渡口
大渡河的河神與烏鴉
最后一個豹之夜
禹王宮與“鯨鯢封處”
“鯨鯢封處”碑
成都科甲巷
刑法的工藝化
書摘/試閱
一匹馬引發的血案
大關縣邊界與昭通市靖安鄉接壤,那一帶就是著名的黑石凹。從翠華鎮往南,“屯上”峭拔而上,乃是李藍起義的據點大旗山。在參加順天軍之前,年幼的唐友耕窮苦無計,到靖安的黑石凹將一個回族人的牛偷走,還舍不得殺了吃掉,交給父親牧放,準備賣個好價錢。黑石凹的失牛回民四處尋找,牛是認親的,他來到翠華鎮附近的山坡,那牛一見主人就叫喚不已,回民立即與唐友耕父親發生激烈爭執,一個說是自家的,一方說是偷來的,回民憤怒不已,將唐友耕的父親當場殺死。
但黑石凹距離唐友耕在大關縣翠花鎮的家不是一時半刻就能走到的,何況偷的是耕牛,不是一塊金子可以揣在兜里。昭通文史學者馬應良指出,唐友耕在黑石凹偷竊的是回民的馬匹,偷偷牽回大關家里,交給父親喂養,父親經常在大關城外的山坡上牧放馬匹。某天,昭通龍洞汛的經商回民恰巧在大關縣城外的山坡經過,見到了這匹失蹤的馬。恰巧馬的主人又是商人的親戚。馬主聞訊后,立即趕來與唐友耕的父親理論,幾句不和,回民把唐父當場殺死,牽馬而歸。(《清咸同年間昭通回民抗暴斗爭記》,《昭通文史資料》第一輯,2004年編印,231頁)
唐友耕并不知道這殺父仇人的名字。他還太孱弱,在一個奉武力為主旋律的年代他束手無策。他把殺父之仇的血吞回腸胃,一面刻苦練武,一面悄悄查訪兇手姓甚名誰。
就這樣,唐友耕和回民結下了血仇。為了既成的痛苦而痛苦,自然會招來更多的苦痛。這個痛苦的爆發點,不是自己的身體被三刀六洞貫透,就是在對方身體內爆炸,就像打翻的糞桶。
如此看來,后來發生在昭通咸豐年間的回漢之爭,最初的原因就是黑石凹的一頭牛。這引出了多年后唐友耕“奉旨”剿殺回民的血雨腥風。
對這段歷史,《唐公年譜》里臆造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故事,說是唐友根的父親、也是頂頭上司的“道西公”因有一匹駿馬被回民強賊馬某覬覦甚久,在一個猝不及防的時刻,強人暴起而奪馬殺人。這暗示了兩個背景:一是父親因良馬被殺,第二才是關鍵,點名父親是官府之人,那么,唐友耕念念有詞的復仇就具有了順應倫理與制度的合理性。唐友耕為道西公復仇,手刃馬某全家7口之后帶著妻子黃氏開始亡命江湖,做小生意糊口。他的母親龔太夫人攜帶襁褓中的小兒子唐友忠投靠敘府城內東大街的彭姓人家以避禍。這固然符合費行簡的記述,但是《年譜》將偷竊之“牛”替換成了被強人覬覦的“馬”,如此牛頭不對馬嘴,成何體統啊?
《年譜》記載的最大漏洞還在于:說咸豐七年(1857),唐友耕已經21歲(實際為17歲),當年冬十一月,他的弟弟唐友忠才出生,但何以從未再寫父親唐仁義(字道西)一些情況呢?他不是被殺了么?年齡相差如此之大,頗不可解。
在進入起義軍陣營之前,《年譜》臆造了一個短暫的逃亡期。但提到了那個叛黨麇集的大本營:大關縣牛皮寨,說唐友耕是去牛皮寨“投靠族兄”避禍。這險險的一筆,曲筆藏有萬般無奈,讓正統歷史為其捏了一把汗。他繼而帶老婆黃氏四處流浪。清末之際,各省反清的哥老會兄弟,尤其是犯了大案的,既不為體制所容,那就只有亡命江湖一條路可走,這叫做“避濠”,而這樣的“避濠”者逃往四川的特別多。唐友耕是久走江湖的,通往敘府的幾百里路他熟門熟路,人緣也廣,但是我估計,唐帽頂沒有遇到能夠接納他避禍的兄弟伙。這個原因,我在下文交代。
某日,來到敘府金流滾滾的金沙江邊,望著碧綠澄澈的橫江水匯入渾黃的金沙江,渾水很難摸魚,可惜出路不但不是那條魚,而且連想象的余地也斷絕了。這條被清代刑部尚書王士禎稱為“蠻江”的金沙江,它同樣以“黑水”“馬湖江”“麗水”等不同名字逶迤在歷史的地表,灌注的卻是一樣的咆哮濁流裹挾著不斷撕裂體制的鐵血之力,盡管讓文雅之士們膽寒,就像王士禎所謂“波濤三百里,猶是怯兵瀾”,可他們沒有料到的是,刀鋒倒卷,“蠻江”也往往是“蠻子”們的葬身所在!
絕望的黃夫人坐在江邊鵝卵石上,講了一番“大丈夫立建功名時不可失、勿以妾為念”之類的豪言后,轉身,她絕不投入“蠻江”,成為咆哮江流的浪花,而是選擇了符合傳統倫理的自殺形式——投繯!
這一番描繪,筆者沒有進行文學加工,而是《唐公年譜》為“尊者諱”的記載。想象一下吧,一個目不識丁且從未出過遠門的鄉下女人,隨夫亡命天涯,可惜天涯竟然才距家鄉區區幾百里,她的苦痛與驚懼被大江的咆哮聲所激發,她未嘗不是一直渴望著盡快結束這痛苦的延續。
這時,唐友耕空了。
傾空自己,不是棄力不是棄智,要成為老實巴焦的農民。傾空自己是把邪惡、善良以及未明的情緒全部傾倒出來,然后進行歸類,然后再把它們分門別類地裝回去。唯一的好處正是可以令一個人更接近事理。
唐友耕是一個喝水就可以打出一串酒飽嗝的人。他索性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輕身前進,自此毫無顧忌。
考察他的錯綜交叉的蹤跡,我不時獲得一些體悟。長期置身于恥辱之中的人,已經長出了日益強悍的道德厚繭。與其說是麻木不仁,不如說是一些列恥辱已經附著其心地之間成為了當事人的道德盾牌。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這種化攻擊為防守的異化,等于是把攻城者的尸體和武器,用來加固自己的城墻,這不能不是一種峭拔其上的底層智慧。過于脆性的富裕階級不明此理,只是在“不自由毋寧死”的二元對立中扭結,最后我發現多數“人上人”選擇了跪地求饒,這叫“茍全性命于亂世”;極少數殺身成仁,就成了烈士。
但關鍵在于,底層智慧往往是有毒的;而有毒的東西,還容易讓人上癮。
……
咸豐九年八月初(1859年10月初),因為昭通“煙幫”向敘府一帶走私煙土被官府發現。所謂“發現”,不過是一直走私煙土的煙幫這一次送上的賄賂數量甚少,大大令官府不滿,那么,殺一儆百方式不過是希望他們回到“知趣”的邏輯中來,但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簡單。著名歷史學家、四川省圖書館館長祝彥和在《蜀亂述聞》里稱,朝廷“聞奉批照屯積例斬,于是其黨聚眾起事”(見佚名輯《清代野史》第四卷,巴蜀書社1998年9月1版,2155頁)。其實,行幫本為較為團結的民間組織,聞名中外的天地會,最初就是閩廣一帶世代以肩挑負販為主的苦力秘密組織,而天地會眾人“結會目的,多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這樣的結社理由和起事的肇因,均是結社遭到毀滅性打擊后,不得不高懸異端的旗幟。
于是,李永和、藍大順遂在大關的屯上起事。唐友耕“雪夜上梁山”,他的兇悍與復仇經歷,以及他播散在負販行幫里的名聲,很快得到了兄弟們的欽佩,開始在藍大順的先鋒營里充任“尖刀”。
李永和時年23歲。我從“瓜面長身,外和內暴”的稗史描繪里,大體能感受到他的一些特性。因之近水樓臺的原因,他喜歡抽鴉片,而在川南、滇北一線,貨販子、馬幫、挑鹽匠等苦力均以為鴉片可以提神、緩解體乏,富人則騰云駕霧,超越女色、直搗癮癖的最深處……這種習俗一直沿襲到1950年易幟之前,劉文彩在宜賓1920—1930年的十年淘金記,全仗鴉片暴利。至于說到他“貪淫酗酒”,證據則來自于“偽”左護國軍政司、最具韜略的名山縣人何崇政的“勸諫”:“勿食洋煙,勿貪酒色”等語。可見,也許鴉片的提煉水平低劣,純度不高,李永和的癖好尚未登峰造極。因為全靠鴉片那騰云駕霧的縹緲托舉的人性,女色對他而言是全然無色無味的。
李永和的性情顯然與他從事的激烈反叛處于悖論狀態。他生性并不好動,起義軍里背后稱他為“李半年”,這個近于四川話里的“劉玄德”,由此可見他被鴉片馴化出來的疏懶與遲鈍。對立統一的原則暗示了藍大煙桿的異軍突起,就不是偶然的了。
大凡舉事者,多少總要有點墨水。李永和為昭通灑漁河柳樹灣人。他少時入私塾,因家貧而失學務農,后在昭通張鐵匠家當學徒。其時習武,結識藍朝鼎等眾多豪杰。因農蕪商敝,打鐵顯然打不出江山,李永和改行自組一支保鏢隊伍為滇川煙幫當護衛,居大關天星屯上為局。李永和力大無比,據說李家田的周圍都栽滿秧,牛無法進李家田中耙田,李永和便將水牛扛進扛出,至今灑漁河老年人中仍有“李短褡褡兒,力大如牛”的傳說。
在中國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比如革命往往始于頭發。李永和自幼不滿世俗,清時男性皆留長發辮,李永和卻偏要剪發齊肩,故人稱之“李短褡褡兒”。不滿于長辮子,但總要把根留住,不然就授人以柄。這一高標個性的叛逆發型,竟成為后來義軍反清的標志——凡參加義軍者皆去長辮留短發。走在山道上,李永和散開那鬃鬣似的頭發,落日穿過頭發,披光的事物逐一遙遠和澄清,幻象將被改編,成為邊際的霧氣與亮。
身為不羈的勇者,李永和就像一頭置身峻嶺深處的怪獸,以一根短辮子攪起的微風,引發了一場持續十幾年的血肉風暴。
昭通學者鄒長銘先生考證指出,藍大順又名藍朝鼎,昭通市守望鄉人。據藍氏祖墳墓碑銘文記載,祖籍陜西,雍正年間遷至貴州威寧。乾隆二十年后,藍大順的曾祖藍元吉徙居恩安縣城南八仙營,以耕種為業。后藍大順的祖父藍發貴“因家道未遂,復移居威寧稻田壩迤北丘”。藍大順父輩有7個弟兄,弟兄長成,藍大順的父親又遷回到八仙營藍家灣。其祖父死后也歸葬八仙營,現墓碑尚存。碑文記載藍大順一輩弟兄共24人,其中后來參加起義軍并有姓名可考者除藍大順外,還有藍朝璧、藍朝宏。1857年為逃避戰亂,謀求生計,李藍二人參加“煙幫”——這是一個受鴉片煙商雇用、保護煙商逃避官府查緝、盜匪搶掠的行幫組織。因為有心計,更有武藝,他仗義疏財,扶弱濟困而成為煙幫的管帶。《湘軍志》中也稱他們“自托商販,頗重身家,無反心”,“號為幫中巨擘”。(《昭通史話》,2000年第一版,昭通市政協文史資料文員會編印本)對這一考證,我有不同看法。這應該指的只是昭通藍氏“朝”字輩豪杰。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如颶風卷殘云。颶風固然攜帶讓體制畏懼的暴力,也裹挾火種。李、藍起義的根本原因則是地方官吏欲壑難填,他們承受不住了。起義之初的是只反貪官,不反皇上。叼著煙斗的斯大林好在講了一句名言:“農民反對地主,擁護皇帝。”其實是農民為自己日后的造反大業預留了后路:推翻皇帝,最后自己也過一把皇帝癮。他們心中只有來自封建宮闕的權力運行模式。陳勝吳廣是如此,黃巢是如此,李自成、張獻忠是如此,天平天國是如此,連孤陋寡聞、偏于青城山的王小波、李順,也是如此。
據說,牛皮寨眾頭領輪番拜旗,磕頭但不搗蒜,可惜旗幟睡而不起。只有李永和燒香焚香紙以拜,遂起風,“義旗刻張”,宛如張開的翅膀,大旗要把所有的旗穗連同李永和的一頭短發在逆風里發射出去,變成一支支奪命的飛箭。該山后來被稱為“拜旗堡”,至今尚存。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