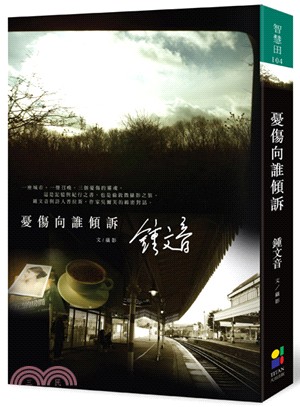商品簡介
一座城市。一聲召喚。三個憂傷的靈魂。
這是記憶與紀行之書,也是倫敦微攝影之旅。
鍾文音與詩人普拉斯,作家吳爾芙的綿密對話。
一趟旅程,可以是發現,也可以是終點。
一趟旅程,可以找到愛情,也可能找到了殺向自己的殺手。__鍾文音
這是生命的第幾場異鄉呢?
時時刻刻,踏著前行者的步伐,帶著想像與情懷,帶著憂傷和歡愉,
從童年,性別,寫作,愛情,異鄉為起點,以孤獨,決離,靜默為終點,
女子們熱烈情感在字裡行間飛揚,過往與現刻有了雙重,三重,四重,多重對話,
旅途上,分不清誰是普拉斯,誰是吳爾芙,或者誰是鍾文音……
新書專訪
我的文學經典情人,讓我的世界不寂寞
Q:請問《憂傷向誰傾訴》是如何被構思起來的?
A:對我來說,書寫小說是一種「吞噬」,大量的吞噬,等於生活都必須要被包覆在創作的小說中,生活中其他部分就會被擱置,就像一個膠囊或太空艙一樣,我在裡面全心書寫。所以想要找一種我能夠駕馭,而且可以很飽滿的文類。它很像一種對話,有心儀的對象,但對象不只是感情的客體,更是文學的經典情人。也因有這雙重客體的存在,讓我覺得世界並不寂寞。
而那些「前行者」──文學的經典情人,已經先經歷過那些我即將要經歷的事,無論是寫作的路途還是書出版後的銷售狀況。再者,我也很久沒有接觸這種文類,最後一次是三、四年前書寫艾蜜莉‧狄金生及普希金等,久了就又有「對話對象」匱乏的一種精神性的文學寂寞感生起,所以又寫這類文本,想要對話了。
當然,這必須要先有書寫客體出現,如我與朋友相約,有了前往倫敦的機會,在作家對話的系列作品中,我也沒寫過吳爾芙,這對我來說是一種缺憾,所以藉由《憂傷向誰傾訴》來完成我對話追尋的夢想。
所以,這部作品就被這樣構思起來,先有一座城市、一個情人、一個文學經典,接著就是,出發、抵達,然後書寫。
Q:《憂傷向誰請傾訴》從構思、醞釀到完成共歷時多長時間?
A:對我來說,這個結合旅行與自我觀照的寫作文類不需要醞釀太久,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這人生的大海究竟動盪多少次,例如你有沒有勇氣再出發,前往這片「大海」才是個問題。具體來說,我旅行過這麼多地方,要書寫100個作家、100座城市,都可以做得到,重點是,還有沒有勇氣再出發這才是難題。年輕時對於孤單的旅行非常熟悉,但到現在這個人生階段,會想「我還要一個人孤單的旅行嗎?」因為對這世界已經沒有具備那麼多好奇,可以很流浪、很便宜的過日子,並觀望這個世界,所以當要再前往倫敦,是很大的挑戰。
不過,我要在此定義「出國」,因為許多人可能會好奇,我一天到晚不是都在出國嗎?我指的是一個人超過三十天在國外飄盪、接觸陌生、再碰撞的過程,所以,說服自己前往時間可能會比書寫的時間還要長。不過,倫敦、吳爾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魅力,當然,與我相約倫敦的那個人也是出發的理由,是三重的召喚。所以,我準備去倫敦的「心理時間」大概是兩年,心裡很渴望能與吳爾芙對話,歸來後則利用半年時間完成作品。
書名則是暗渡俄國作家契可夫的作品,希望藉此向他致敬。契可夫擅長書寫底層人的憂傷。他曾寫過一個讓我覺得非常憂傷的故事,講述一個馬伕雖遭遇喪子之痛,但他還是必須工作,所以他很希望載客時可以像乘客訴說他的心事。沒想到,第一個上車的年輕人竟然對他說:「誰不會死啊?」讓他非常失望。好不容易有個軍官可以聽他說話,竟然一個閃神差點撞到東西,讓軍官命令他要好好駕車。最後,誰也無法聽他說話,他只好跟他的馬兒說⋯⋯契可夫是我寫短篇小說的模範,每個陌生人都有他的故事,所有人的哀愁都是我的憂傷。
對話、書寫是一種自我狀態的舉證與拼湊
Q:從過去到現在的作品,若在書中談到其他作家,都像在訴說自己的故事,在文字上充滿靈魂的共鳴。請問妳是如何與作家及其作品建立關係?而被談起的兩位女作家在書中又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A:與其說「共鳴」,還不如說「羨慕」。台灣給予的土壤養分,一直無法回到文學這棵樹,所以我在《憂傷向誰傾訴》中,就有提到吳爾芙自認自己是全英國最幸福的作家,她可以任意出版自己的作品,也有一個支持她的伴侶雷納德,在《大文豪與冰淇淋》(2008)提到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安娜的故事,都是同樣的用意,希望透過這些作家的點滴來拼湊我自己,也希望能有這樣的際遇,成為這樣的角色,後來就有讀者告訴我:「讓我們成為妳的小安娜!」
所以當我們在書寫的同時,也在暴露自己的不可能、台灣的匱乏,包括吳爾芙的世界、普拉斯的激情,很羨慕他們的能量,包括「死亡」這件事。雖然我不贊成自殺,但在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下,卻能孜孜不倦於寫作,這股創作能量讓我欽佩。透過與他們的對話,看見作家這個職業應有的模樣、文學原有重要性,當眾人失去對這些事的理解,就不會知道什麼才是好的作品。所以,我書寫吳爾芙或其他作家,就是在反證我的生命狀態,舉證我自己。這樣的創作,臨場感對我來說很重要,看著她們曾經寫作的書桌、走過的路,可能曾經喝茶、憂苦、咆哮的地方。就像我去拜訪普拉斯的故居,想像普拉斯對休斯咆哮,那感覺深深觸動了我。如果除卻了我在現場這件事,這個文本就會是空的,畢竟我不是評論家、報導者,
必須用我的眼睛觀察一切,感受現場的時間感,並且把「我」放進去,以「我」做為一種對照,自我揭露,對自己進行剖析,所以必須將筆墨航進自我的深海。
Q:《憂傷向誰傾訴》卷四〈一則虛構的對話〉擺在本書的用意,呼應前面三卷的基點何在?
A:因為我寫作不喜歡被規範,所以是故意將這段類似戀人一來一往的劇本感對話放進本書中,其實是呼應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戀人的對話很適合出現在旅館的房間裡。過去也有過這種嘗試,如《在河左岸》將有別於小說敘事方式的報導文體放在全書後,希望可以打破所謂的「整體性」。因為我發現台灣的文學很講求「整體性」、「明確性」,必須要很明確告訴讀者表達的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法國有許多文本雖然讀起來支離破碎,卻非常有魅力,我一直很想做這方面的挑戰,讓作品更加多元。雖然過去的作品也很多
元,加入了攝影、繪畫作品,不過這次更大膽,直接加入類似精神分析的戀人對話。
一旦風格確立,靈感就不會擱淺
Q:在採訪其他創作者的經驗中,「如何汲取靈感」、「沒有創作靈感怎麼辦」一定都會被列入提問中。但對於妳卻莫名不會有這種疑問,總覺得妳就是創作的代名詞,但這畢竟是我的想像。「靈感」會與其他創作者一樣,成為妳的煩惱嗎?
A:當作家想轉換到另一個風格時會比較辛苦,一旦風格確立,靈感就不會擱淺。另外,當作者到「文學市場」買材料時,遇見這麼多可能的可能,到底要不要寫進作品裡,或是寫進去了又被別人認為是同樣文類的再製。這也是為什麼在幾次的創作中,都會有一些「破格」之處,例如一則虛構的對話的書寫。也許國內很多人會認為,在文學世界裡小說很重要,但在西方世界,會看作者世界的本體,不會只有他在出書時才重要,當他旅行、被訪問時也都是作者的一部分,都很重要,所以他們才會這麼重視吳爾芙、莒哈絲等人,因為她們整個生命都是一種創作。
Q:新作品才剛產出,但對於書迷的我來說,已經迫不及待想知道,「那下一部作品呢?」請問,已經在構思下一部作品了嗎?或是有什麼題材是妳想書寫的?
A:目前手邊正準備著手書寫《最後的情人---莒哈絲海岸》、《在我們的海》關於馬偕夫人的傳奇故事。也去了廣島和南京等地,之後想嘗試「戰爭」的小說題材,廣義來說,就是「傷害」。我剛從越南回來,到過當地的博物館、舊戰地,看到一些關於戰爭的歷史,心裡覺得很多隱藏在人生船艙下的巨大傷害性的東西應該被打撈上岸,希望可以刻劃經歷戰爭或人與人之間互相傷害的一種「精神」狀態。最近看了電影《偷書賊》,那是一部反戰電影,它以「書」串起了整個故事,未來書寫小說也會多想思考這類的元素,而不只是憑直覺地寫。
作者簡介
淡江大傳系畢,曾赴紐約視覺藝術聯盟習油畫創作兩年。現專職創作,以小說和散文為主,兼擅攝影,以繪畫修身,周遊世界多年。
曾獲中時、聯合報、世界華文小說獎、林榮三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等多項重要文學獎。
二OO六年以《豔歌行》獲(開卷)中文創作十大好書獎。持續寫作不輟,已出版多部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及散文集。二O一一年出版百萬字鉅作:台灣島嶼三部曲《豔歌行》、《短歌行》、《傷歌行》,備受矚目與好評,並已出版簡體版、日文版及英文版。
出版圖文書《裝著心的行李》,攝影圖文書《暗室微光》、《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
目次
卷貳:守蜂者的女兒…………………………………………………………174
卷参:憂鬱的歐蘭朵…………………………………………………………262
卷肆:戀人的雙重房間--為愛翻譯 為愛扣問…………………………340
書摘/試閱
憂鬱的歐蘭朵
記住我們共同走過的歲月,
記住愛,
記住時光。
—維吉尼亞‧吳爾芙
我自己曾寫過這樣的一句話,現在看來,像是在為自己的生命做某種捍衛的詮釋:「或許多少年之後才能夠感受得到當時的一個舉動是多麼的驚天動地。」
比如二十幾歲時,突然有天醒來,告訴自己要離開,要到遙遠的國度,開始新的生活。那個國度是一座巨大的島,一座巨大的船艙,擠滿青春與不想老去的人。曼哈頓聳立的是高樓大廈切割成的峽谷,人如螻蟻是風光。
比如某天醒來,告訴自己要離開不斷施打的高劑量愛情毒素。
有種人是不該浪費生命在其身上的。
但那種逃離的驚天動地之舉,都是後來才能體會的。
即使只是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剎那的失心瘋,都會墜向深淵。廣島原子彈僅僅
幾秒,僅是一個按鍵時間就足以天崩地滅。
你在癲危時刻仍不忘和時光逆行,並給予歡樂與愛。
時時刻刻,吳爾芙—你啟發了後來的許多寫作者。
你那具有夢想家氣質的側臉,迷濛出世卻又極為入世。對自我與小說美學實驗的探視,瞬間捕捉流逝的心靈。
小說時間與真實時間,意識流流過精神的荒土,灌溉成一座奇花異草似的濕地,小說是人類前進的莽原,在歧路中探索,匍匐,為精神莽原的探勘傷痕累累而在所不惜。
戰將如是,武士精神,你也是刀刀劈進精神荒地,小說的荊棘重重,尤其在你的年代,女作家的騰空出世尤是天方夜譚的一顆明星。
你經歷了十九世紀末與二戰期間,看著大英帝國。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你走入隱士之屋附近的河流,跳入烏斯河(最想譯成:勿思河)。
你太瘦了,因此撿了許多石頭放在口袋以增加重量,好讓身體不會因為太輕而浮上來。一個會游泳者,如何在河裡拒絕求生的本能反應?你不再盡情感受這沒有答案的人生,毀滅將至,敵軍將戰車開入倫敦的日子不遠了。
「壯闊的心靈,卻落入令人窒息的凡間。筆端和命運對弈,到頭來卻難免成為一個輸家。」有朋友在臉書留言給我,因我提了你。但我以為你不是輸家,就生命某種程度而言你是,但就書寫而言,你不是,你是真正的贏家,贏得尊重,贏得價值,贏得精神。
大戰已臨,兵臨城下—你認為你最愛的城市倫敦將難逃德軍的魔掌,你不想活在那樣的戰火之中。
恐懼的想像往往是培植癲狂的養分,你害怕癲狂至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你知道會有那麼一天,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你,這一波比之前都強大。以前病發時,你不認得自己寫的文字了,這是對寫字者的最大凌遲,而凌遲是最大的罪。
你逐漸老去,深知這波強大激流襲擊,將連自己都會失去辨識自己的面目與文字。那麼自己將被這世界與文字徹底地隔離,自己隔絕在自我之外,因此你要自己快快出航,比這一天遠
航得更快更遠,寧可投入河神懷抱,以更激烈的荒涼方式讓自己不被俘虜。肉身可被燒盡,精
神不被摧毀。
盡情去感受這沒有答案的人生,你寫過的。五十九年,已經夠了,你夠盡情感受了,甚至這感受要崩毀失控了。
「寫作治病,寫作就是忘卻,文學是忽略生活最為愉快的方式。小說是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歷史,而戲劇是沒有敘述的小說。﹂哲學的戲劇化也是小說,以寫作剖析自我與扣問人生也是小說,以小說來疏離自我人生也是小說,小說有各種可能,各種可能都是小說。
創作猶如一趟旅程,創作成為致力完成自己的舟渡,一個發現之鑰。
寫作猶如縱走黑暗邊境,悠長緩慢,好似永遠踩不到底,但忽焉竟在筆中成形了。小說能比個人真實活過的人生更加真實,但也可能更加虛妄。
作品被完成時是如此地神祕,在文學的邊界,在人生的邊界,明亮與黑暗交織命運的房間。寫作猶如探勘,一個鑿光者。偉大的小說家都有個地獄,入地獄卻開出天堂之花。
慌走在靈魂的歧路花園。
起先的少女經驗是不愉悅的,你的兩個哥哥曾冒犯你,而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一種身體與性
的逾越。同時依戀母親的你,卻在十三歲時體驗到死亡,死神總是帶走所愛,你第一次精神崩
潰,腦中的精密儀器如琉璃,透明繽紛,卻不堪一擊。但琉璃粉碎仍可提煉成不同形狀,本質
還是你╲妳。
然而另一面的你也是頑強的,精密儀器如精工,摧毀的只是架構,只要重新組合,就可以重回你原初的本我。
之後,你幾乎年年與死神交戰,時勝時敗,努力四十多年,自動繳械。接受河神的盛宴,以肉體供養天地。你長期以河海作為象徵,接著是將自己變成小說的實體經驗。海洋是人類最初爬行至陸地的子宮母體,時刻相續的海浪也象徵著某種質量不變的永恆,浪是宇宙的心跳節拍。
生命最後有如你的作品︽海浪︾,敘事完全走入內心,一種心理的寫實或者不寫實,總之
不再受現實外在的細節綑綁。你也不再受軀殼的束縛,航進冰冷之海的苦痛想必深烈,但你知
道撐不過這一回。
繁複的低音暗自響徹整座如交響樂的海域,奇特的音波總是難以被聽見。
你曾經用「魚鰭」在寧靜遼闊的海洋上升起如蝶翅的象徵,帶著那樣亙古以來的孤獨寂
寥,寂靜的殘敗,與死亡的搏鬥,神祕而哀愁。
「汪洋大海中的一片魚鰭,我是一個隨時在我意識的邊緣記下一些話來以待將來作最後陳
述的人,現在我就記下這一句,以待在某個冬日的傍晚使用。」記下語句,雖然不知道何時會
用到它們。
「某個冬日的傍晚使用。」你說。
這真有意思,像是以為文字可以為冬日即將到來的傍晚取暖似的。
你有如海域裡最獨特的鯨魚聲音,聽來如鬼魂,也像低音號鳴奏。
據說這神祕聲音來自一隻名為赫茲的鯨魚,其歌聲太獨特了,獨特到只有牠自己才聽得見,獨一無二,因此找不到伴。
當然你一生都有朋友與夫為伴,但你心深處明白人最後都是孤獨的。
赫茲鯨魚是人的孤獨隱喻,每個人的終站都將化為赫茲鯨魚,人生春色凋零,孤獨涉
入冥河。
你是希臘的泰瑞西阿斯(Tiresias),盲人先知,卻具有兩性的生活經驗,失去性別,茫茫遊走繁華荒原。
有多少回了,你面對自己的精神生死交關,或者目睹他人肉體的生死交關,太多回了。
年輕時當你面對折磨父親的病魔時,你曾經這麼想著:「死神能否加快點腳步呢?」那時你才二十二歲第二次面對至親在和死神鏖戰,第一次是十三歲面對母親的死亡,你目擊著死亡的本身。表面看起來冰冷,一旦遇到所愛,內裡卻是如熔岩的炙燙。
父親過世,你和家人搬遷到南威爾斯。
那是一座介於大海與沙原之間的寂寥荒地,你常在懸崖高處往下眺望,沉思著未來。源於這段漫長的徒步生活,未來要書寫的材料也逐漸在你的腦海浮現。
你寫著日記,一直保有這個習慣。
後來你和姊姊還沒到布倫斯伯里(Bloomsbury)之前,你們去了義大利旅行。
在旅行裡,你觀看人的興致大過於看教堂,這也是寫小說者的奇異之眼。
在歐洲旅行時,到了巴黎,你和姊姊遇到克里夫‧貝爾,他還帶你們去參觀了雕塑家羅丹的畫室。貝爾這個人和你要好,但後來娶了你姊姊。
然而回到英國後,你卻瘋了一整個夏天。
陷在複雜的生命低潮,現實逐漸成了遙遠不可捉摸的狀態。
瘋狂的夏天,每個人都在等待你的康復。
瘋狂的生命風景永遠值得描述。這段無法書寫的時間,卻成為你往後不斷創作的生命基底,創傷若能轉化,就能成為生命的豐收。
失眠頭痛暈眩心悸……厭食,討厭人……你試圖自殺,所幸一九○四年五月到八月,三個月裡的關鍵性時間,你獲得了護士與專門神經科及家人的妥善照顧。
家人把你送到約克郡學院,因為那家學院的校長是你的表親,一來你可以療養,二來和其表親的妻子也就是校長夫人一起共度學校生活。在這段療養期間,你漸漸好轉,除了參加這些夫人們的茶會和教會活動外,在許多你不喜歡的學院場合時,你會到學校鄰近的高原荒地裡漫遊。在岩石間遊走,感受風的刺骨,荒煙蔓草的風土,品味幽微閃過的靈光詩語。
同時學院的氛圍也讓你不斷地自我淬鍊與琢磨書寫的技藝,為當一名職業作家的入門作進階的練習,為你日後的文學實驗創立新的敘事聲音。
私密的札記跳躍為社會的觀察者,書評的鑑賞者。
對於創作胚胎,你就像母親守候著未出生的嬰兒般,將現世風光轉化為奇魅書寫,你高昂的心性催發你的創造力,不斷鍛鍊與超越自我的窠臼。
這段時間是繁花盛開的金色年華,尤其從瘋狂的黑暗之谷步出後,你更明白時光不可浪擲,因為在時光之門的是一隻凶猛的獸,隨時匍匐在外,準備狠咬生命幾口。
陰暗與燦亮的兩端,你都歷歷行經,你不是關在象牙塔的小說家,你迎接社會種種,且參
與其中。
你甚至去倫敦為高齡窮人所設的莫利學院參與教學課程,熱情地教著寫作與文學等,甚至為學生寫課程大綱,但在教學上你的熱忱卻被學生們打敗,你發現賣力地教導著寫作與文學課程,但學生關心的卻和你不同。
比如你賣力地講著文藝復興,學生卻只關心旅館有沒有跳蚤。
於是後來你轉向參與文學沙龍的週四夜晚聚會,也是由你的姊姊凡妮莎發起的,沙龍是藝術聚會,不同創作媒材的藝術家以藝術議題為討論的聚會,即後來聞名英國的布倫斯伯里團體,將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和和平主義發揮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文學藝術結社。
你關心的女性是和你同一階層的女性,成員竭盡自己來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力。
你的愛是我唯一能確認的
生之悲苦,從生提煉死魂,你凝視死,早在十三歲時,就進而參與了死亡事件簿。你從神志清明到癲瘋狀態的見證者雷納德描述過那駭人模樣,你先是厭食,接著拒絕進食,抑鬱環繞不去,被罪惡感與絕望情緒淹沒,接著轉為興奮無明且又有如一頭失控野獸的狀態。你會對來照料你的護士行為粗暴,動粗相向,因為她們都在腦海裡形成幻影,身旁人變成惡魔。接著你會一直說話,從能夠被理解的字詞,逐漸進入分裂斷裂的無意識與不連貫字詞。
瘋癲者大約如此。
瘋狂之後,就像迷霧散去,你逐漸清醒,不僅記得泰半的經歷,且能進入理性的秩序思考。在你五十多年的生命裡,接二連三的瘋癲都沒有擊潰你,即使你曾經航進死神的懷抱,但所幸死神都把你隔離在外,好讓你能持續寫作,活在你所熱愛的世界裡。
你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沒能走過二戰。一九四一年,你深知這回過不去了。如果過去的瘋癲是大風大浪,那麼這回即將襲擊你神志的將是席捲一切的海嘯,你知道躲不過去,而你不想連累雷納德,你感到這一生虧欠太多了。
於是你寫好最後一封信,將信放在入門處。
最親愛的:
我知道我自己行將再度崩潰,我們再經歷一次類似的處境,而且這次我不會恢復,我開始幻聽並且無法專心,看來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解決之道。你給予我最極致的快樂,無人如同你一般,直到這可怖的病況再度來臨,我向來認為我們在一起最是快樂。我已經在損毀你的生命,沒有我在,你可以好生工作,我知道你可以的,你看我連寫這封信也不能寫得好,我現在甚至無法閱讀。我要告訴你的是,我生命的歡愉來自於你,你以最強烈的耐心與愛意。我要告訴你的是,假使有任何人能夠救我,那必然是你,縱使我已經分崩離析,你的愛仍是我唯一能確認的,我不要再繼續損壞你的時光了。
我認為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是兩個個體所能達到的最快樂的光陰。(註:此文摘自—《吳爾芙》貓頭鷹出版,二○○○。)
在你最後一本小說《海浪》的最後篇章文字,竟也成了作家最後的墓誌銘:「置身於你的懷抱,我依然不為所動,不受宰制,死亡啊!」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