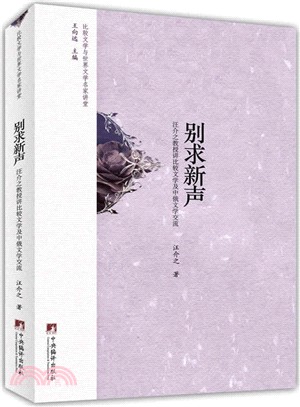別求新聲(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
ISBN13:9787511721709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作者:汪介之
出版日:2014/06/23
裝訂/頁數:平裝/386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別求新聲》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20卷叢書之一。中俄文學與文化交流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中國文學與文化對俄羅斯文學與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產生過多方面的影響。在歷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和作家的著述與作品中,都可以發現中國文化、哲學、藝術乃至宗教與倫理的廣泛滲透。俄羅斯知識界在研讀中國文學與文化的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頗具特色的“中國形象”。而同樣的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每一階段,也都顯示出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以至中國文學無論是反顧自己走過的路途,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確認自身的地位、成就和意義,還是更新自己的觀念,調整自己的思路,規劃未來的藍圖,幾乎都要把俄羅斯文學作為一種基本參照,在與這一文學的比較和對話中尋得支持、激勵、啟示或借鑒。中俄文學與文化交流還在繼續發展之中,也必然擁有廣闊的前景,而且,毫無疑問地將繼續成為整個中外文學關系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者簡介
汪介之(1952—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理事,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外文學關系、俄羅斯文學研究,已出版《選擇與失落:中俄文學關系的文化觀照》、《回望與沉思:俄蘇文論在20世紀中國文壇》、《文學接受與當代解讀——20世紀中國文學語境中的俄羅斯文學》、《遠逝的光華: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文化》、《流亡者的鄉愁:俄羅斯域外文學與本土文學關系述評》、《伏爾加河的呻吟——高爾基的最后20年》、《俄羅斯現代文學史》等專著10部,發表論文100余篇。目前正在研究的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詩學視域中的帕斯捷爾納克小說研究”。
名人/編輯推薦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著、比較文學學術論文集
該套叢書涉及了比較文學理論、外國文學、中外比較文學等研究領域,是作者長期的學術積淀,在國內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屬最新研究成果。
該套叢書涉及了比較文學理論、外國文學、中外比較文學等研究領域,是作者長期的學術積淀,在國內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屬最新研究成果。
目次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1
自序1
“世界文學”的命運與比較文學的前景
當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關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幾點思考
關于中俄文學關系的對話
中國文學接受俄羅斯文學的多元取向
俄羅斯文學精神與中國新文學總體格局的形成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1
自序1
“世界文學”的命運與比較文學的前景
當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關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幾點思考
關于中俄文學關系的對話
中國文學接受俄羅斯文學的多元取向
俄羅斯文學精神與中國新文學總體格局的形成
關于20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的反思
“蘇聯文學”:內涵、價值及其他
——“蘇聯文學再回首”筆談
百年俄蘇文論在中國的歷史回望與文化思考
中國文學接受20世紀俄國文論的回顧與沉思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理論行程
高爾基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在中國的接受
俄國形式主義在中國的接受
巴赫金的詩學理論及其在中國的流布
周揚與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的傳播
白銀時代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接受
新中國60年高爾基小說研究的歷史考察
高爾基之謎:“破解”還是曲解?
——《倒轉“紅輪”》第二章讀后質疑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的接受
帕斯捷爾納克與中國知識者的精神關聯
弗?索洛維約夫對中西文化的比較考察
高爾基筆下的“東方”與中國
阿赫瑪托娃等詩人與中國詩歌文化
巴赫金對中國文學的描述
[附]
與俄羅斯文學的相遇與相守
——汪介之教授訪談錄
后記
自序1
“世界文學”的命運與比較文學的前景
當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關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幾點思考
關于中俄文學關系的對話
中國文學接受俄羅斯文學的多元取向
俄羅斯文學精神與中國新文學總體格局的形成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1
自序1
“世界文學”的命運與比較文學的前景
當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關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幾點思考
關于中俄文學關系的對話
中國文學接受俄羅斯文學的多元取向
俄羅斯文學精神與中國新文學總體格局的形成
關于20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的反思
“蘇聯文學”:內涵、價值及其他
——“蘇聯文學再回首”筆談
百年俄蘇文論在中國的歷史回望與文化思考
中國文學接受20世紀俄國文論的回顧與沉思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理論行程
高爾基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在中國的接受
俄國形式主義在中國的接受
巴赫金的詩學理論及其在中國的流布
周揚與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的傳播
白銀時代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接受
新中國60年高爾基小說研究的歷史考察
高爾基之謎:“破解”還是曲解?
——《倒轉“紅輪”》第二章讀后質疑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的接受
帕斯捷爾納克與中國知識者的精神關聯
弗?索洛維約夫對中西文化的比較考察
高爾基筆下的“東方”與中國
阿赫瑪托娃等詩人與中國詩歌文化
巴赫金對中國文學的描述
[附]
與俄羅斯文學的相遇與相守
——汪介之教授訪談錄
后記
書摘/試閱
“世界文學”的命運與比較文學的前景
最近一個時期,關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學科的議論頗多。在全國性的本學科教學研討會或校際高層次座談上,一些學者就“世界文學”學科是否應當存在、“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兩個學科是否應當合并、“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等問題,暢談了自己的見解。這些議論,也引起了筆者對本學科設置的由來、合理性和前景的思考。現在,筆者不揣淺陋,也在此談談自己的看法,期望就正于同行專家學者。
“世界文學”:何去何從?
對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學科的名稱,特別是其中的“世界文學”,有些學者提出非議。有的學者甚至主張取消世界文學專業,一律改稱“外國文學”,并由外語系教師來承擔其教學任務。于是,世界文學學科便面臨著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
“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歌德在1827年與愛克曼的一次談話中提出來的。后來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解釋道:這個名稱 “似乎含有應該去研究從新西蘭到冰島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學這個意思”。但他們緊接著又說,“其實歌德并沒有這樣想。他用‘世界文學’這個名稱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國文學都將合而為一。這是一種要把各民族文學統起來成為一個偉大的綜合體的理想”。韋勒克和沃倫還指出:“‘世界文學’往往有第三種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偉大寶庫,如荷馬、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以及歌德,他們譽滿全球,經久不衰。這樣,‘世界文學’就變成了‘杰作’的同義詞,變成了一種文學作品選。”
或許是由于認同了韋勒克等對“世界文學”的第二種解釋,有學者指出:“世界文學”在今天,“還僅僅是先哲們對人類理想社會幻想中的一個夢”,既然是一個夢,怎么可以拿它來作為中國大學中的一個學科呢?
事實上,在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初至1997年以前,作為培養碩士研究生的學科名稱之一的“世界文學”,其內涵接近于上述韋勒克等的第一種解釋,而并不是把某種偉大的理想或幻想拿來當作學科的名稱。不過,這一學科通常不把中國文學作為自己教學和研究的對象,盡管從字面上看,“世界文學”無疑應當包括中國文學。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文學》刊物,一般不刊登中國的文學作品;我國歷史學科中的“世界史”專業,通常也不把中國歷史作為自己教學和研究的對象。這樣看來,“世界文學”其實就是外國文學。它主要研究除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國文學史的一般進程,注重考察各種文學思潮流派的交嬗演變、重要的文學現象和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力求探明各國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
如果說到作為一門課程的“世界文學”或“外國文學”,那么它在我國高校中文系的開設,則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以前。早在1917年,周作人就在北京大學文科、隨后又在中國文學系以中文講授歐洲文學史。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從1928年起,就提出“一方面注重于研究中國各體的文學,一方面也注重于研究外國文學各體的研究”。1932年秋朱自清接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同樣特別重視外國文學,“西洋文學史”一直被列為該系的必修課。1946年清華大學復員后,朱自清續任中文系主任,“世界文學史”課程由中文系開設,以中文講授,并讓學生大量閱讀世界文學名著的中文譯本。從50年代起,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四川大學、廈門大學、杭州大學(現已并入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暨南大學等絕大部分綜合性大學以及幾乎所有的師范大學的中文系,都先后設立了外國文學教研室。這些教研室的教師承擔著給中文系本科學生講授外國文學的任務。由于“文革”前我國的研究生培養制度不健全,當時中文系外國文學師資的來源,除了已有的老一代學者外,主要還有兩條渠道:其一,教育主管部門從中文系選拔一部分有較好的外國文學素養和一定外語水平的教師或本科畢業生,到外語院系脫產學習幾年外語,學完后回原系科從事外國文學教學;其二,從外文系教師中抽調一部分文學水平較高的教師,到中文系任教。這三部分人構成“文革”前和“文革”后一段時間內我國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師隊伍的主體。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很有造詣和影響的知名學者,如趙瑞蕻、朱維之、張月超、朱雯、許汝祉、王智量等。他們的外國文學教學、翻譯和研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和培養制度開始逐步走向健全。如同中文系各學科都要通過研究生制度培養自己的師資隊伍一樣,外國文學學科也面臨著這一任務。于是,從80年代初期起,經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批準,我國高校便開始有了作為二級學科的“世界文學”碩士學位點(1980年第一批正式建點的,有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暨南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從那時起陸續畢業于這一專業的一屆又一屆碩士生,是目前我國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師隊伍的骨干。當然,不斷補充著這支隊伍的,還有從外語院系各語種文學專業畢業的博士生、碩士生,以及到國外高校進修、訪學或獲得學位后歸國的學子。這支隊伍已經并且至今仍在發揮著它的作用。把這一學科的名稱改為“外國文學”,而不叫“世界文學”,也未嘗不可。不過,如果改稱“外國文學”,就有可能和設在外語院系的“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相混同。也許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混同,當初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才決定設立“世界文學”二級學科。
有的學者認為,我國高校中不必設立“世界文學”或“外國文學”學科,中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學任務,應當由外語系的教師來承擔。其理由是:外語系的教師精通外語和各語種(國別)文學,由他們來講外國文學,理所當然能講得更地道;而中文系的教師一般外語不行,怎么能講外國文學?
這一說法可能有些絕對化了。中文系不懂外語的外國文學教師確實有過,不過那主要存在于以往;今天如果還有,那也只是個別現象,決不能代表目前我國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師的主體。外語系絕大部分教師確實精通外語和與此種外語相聯系的國別文學。或許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我國有少數綜合性大學的中文系,至今沒有設立外國文學教研室,一直是請外語系教師給本系學生講授外國文學,具體講法是分別由英語(或其他西語)專業、俄語專業和掌握某一東方民族語言(如日語、阿拉伯語等)的教師講授西方文學、俄羅斯文學和東方文學。可是,這樣做的結果,其實和其他大部分高校由中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師自己來講授外國文學并沒有多少區別。因為,除了俄語專業的教師講授俄羅斯文學堪稱“地道”之外,在講授西方文學和東方文學時,無論外語系還是中文系的教師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教師一般只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并精通和此種外語相聯系的國別(語種)文學,但是他卻要給學生講授整個西方文學或東方文學。從各高校學生接受的實際效果來看,由外語系教師上課的未必就更好些。
還有的學者建議取消高校中文系的外國文學史課程,設置國別文學史,分別由外語系各語種的國別文學專家來講授,并讓學生盡可能地接觸作品原文。這是一種美好的設想。假若我們的大學都能夠提供分別精通希臘語、拉丁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德語、法語、英語、俄語、日語、阿拉伯語等各語種的國別文學教師,由他們分別來給學生講授古希臘文學、古羅馬文學、歐洲中世紀文學、意大利文學、西班牙文學、德語文學、法國文學、英美文學、俄羅斯文學、日本文學、阿拉伯文學等各語種、國別文學,那可能是學生們的一種幸運。但是,即便真的擁有如此雄厚的師資力量,這樣的課程恐怕也只能主要以漢語來講授,可以給學生提供的也只能是一、兩種外文資料,因為沒有哪一位學生可以聽懂十幾種語言,看懂十幾種外文資料。再者,外國文學,特別是歐洲文學,絕不是一系列國別文學的簡單相加。學生掌握了諸多國別文學史的知識,也未必能夠回答諸如“為什么說近代歐洲文學的主要體裁都在文藝復興時期奠定了基礎”、“18世紀的歐洲文學怎樣直接影響了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思潮”這類歐洲文學史中的基本問題。
順便說一句:目前國內有的大學外語系已不再開設外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課程。這樣做的結果之一是知識面的相對狹窄。于是,在我們的一些出版物中,謝林變成了“席令”(漓江版《彩色插圖世界文學史》);葉賽寧變成了“埃塞尼”,索爾仁尼琴變成了“索贊尼辛”(1998年5月2日《文匯讀書周報》);柏拉圖變成了“普拉東”,康德變成了“坎特”(學林版《彼得堡的冬天》),等等。這類現象,既和歐洲文學通史知識的缺乏有關,也與蔑視閱讀漢譯世界名著相聯系。世界文學名著的權威漢譯本在我國知識界、廣大作家和廣大讀者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在20世紀以來我國文化和文學發展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已有學者予以充分肯定,此處不復贅言。
問題又回到了由誰來講授歐洲文學史或外國文學史。依筆者的淺見,如果可以把外國文學史粗略地劃分為歐美文學(西方文學)和亞非文學(東方文學)兩大部分,那么,分別承擔這兩部分文學教學任務的教師,應當具備以下基本條件:熟練掌握一門外語,能順利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原文和外文研究資料;精通與其所掌握的外語相聯系的國別(語種)文學史(主要通過外文原文);閱讀過大量的該國別(語種)文學作品(主要通過外文原文);通曉這一國別(語種)文學所屬的歐美文學或亞非文學,包括既了解歐美或亞非文學通史,又了解分屬這兩個部分的各主要國別文學史(主要通過中文);系統閱讀過歐美文學史或亞非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主要通過權威譯本)。
培養具備上述基本條件的教師,正是多年來“世界文學”專業一直努力在做著的主要工作之一。圍繞上述基本目標,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實踐中,“世界文學”專業也已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和特色。毋庸諱言,由于目前我國高校“世界文學”專業大多數教師的外語語種,不外是英語、俄語或日語等少數幾種,掌握其他外語的教師還為數不多,所以“世界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或專業的欠缺之處無疑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局限,只能隨著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該學科重視程度的提高和學科自身建設的強化而逐步得到彌補。
對 “世界文學”學科或專業的懷疑和否定,當然不是始于今日。人們大概都還記得一位已故的英國文學專家的名言:誰能搞“世界文學”?是的,誰也不能搞“世界文學”,正如誰也不能搞“世界史”、“外國哲學”、“西方經濟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一樣,盡管這些學科都作為二級學科客觀存在。所有這些學科的專家,也都只能精通和他們的外語語種相聯系的某一國或少數幾國的哲學、經濟學、史學或語言學等。就“外國哲學”學科而言,分別掌握各種外語、分別精通某一國別哲學的專家們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外國哲學”學科隊伍。“世界史”、“西方經濟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以及“世界文學”學科,其實都是如此。對于可以視為“三級學科”的“西方文論”、“西方文學批評史”、“西方美學史”等,也應作如是觀。看來,至少是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內,所有的涉外學科,都存在一個外語語種的問題。學科名稱往往是很大的,但在這些學科中從事具體工作的人們所能精通的,則只能是和他所掌握的外語語種相聯系的那一小部分。在文學領域,無論是“世界文學”還是“外國語言文學”學科,也概莫能外。
如果我們能夠看到上述一系列事實,那么也許就會對“世界文學”何去何從的問題作出這樣的回答:它只能一如既往,和文學門類中的其他學科、和人文與社會科學門類中的其他涉外學科一起繼續前進。
合并既不是“歸順”,也不是“吞并”
1997年,“世界文學”學科的命運發生了某種變化。是年6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頒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在這一新《目錄》中,原有的“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被合并在一起,出現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引起更多爭議的學科名稱。
最近一個時期,關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學科的議論頗多。在全國性的本學科教學研討會或校際高層次座談上,一些學者就“世界文學”學科是否應當存在、“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兩個學科是否應當合并、“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等問題,暢談了自己的見解。這些議論,也引起了筆者對本學科設置的由來、合理性和前景的思考。現在,筆者不揣淺陋,也在此談談自己的看法,期望就正于同行專家學者。
“世界文學”:何去何從?
對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學科的名稱,特別是其中的“世界文學”,有些學者提出非議。有的學者甚至主張取消世界文學專業,一律改稱“外國文學”,并由外語系教師來承擔其教學任務。于是,世界文學學科便面臨著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
“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歌德在1827年與愛克曼的一次談話中提出來的。后來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解釋道:這個名稱 “似乎含有應該去研究從新西蘭到冰島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學這個意思”。但他們緊接著又說,“其實歌德并沒有這樣想。他用‘世界文學’這個名稱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國文學都將合而為一。這是一種要把各民族文學統起來成為一個偉大的綜合體的理想”。韋勒克和沃倫還指出:“‘世界文學’往往有第三種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偉大寶庫,如荷馬、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以及歌德,他們譽滿全球,經久不衰。這樣,‘世界文學’就變成了‘杰作’的同義詞,變成了一種文學作品選。”
或許是由于認同了韋勒克等對“世界文學”的第二種解釋,有學者指出:“世界文學”在今天,“還僅僅是先哲們對人類理想社會幻想中的一個夢”,既然是一個夢,怎么可以拿它來作為中國大學中的一個學科呢?
事實上,在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初至1997年以前,作為培養碩士研究生的學科名稱之一的“世界文學”,其內涵接近于上述韋勒克等的第一種解釋,而并不是把某種偉大的理想或幻想拿來當作學科的名稱。不過,這一學科通常不把中國文學作為自己教學和研究的對象,盡管從字面上看,“世界文學”無疑應當包括中國文學。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文學》刊物,一般不刊登中國的文學作品;我國歷史學科中的“世界史”專業,通常也不把中國歷史作為自己教學和研究的對象。這樣看來,“世界文學”其實就是外國文學。它主要研究除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國文學史的一般進程,注重考察各種文學思潮流派的交嬗演變、重要的文學現象和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力求探明各國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
如果說到作為一門課程的“世界文學”或“外國文學”,那么它在我國高校中文系的開設,則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以前。早在1917年,周作人就在北京大學文科、隨后又在中國文學系以中文講授歐洲文學史。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從1928年起,就提出“一方面注重于研究中國各體的文學,一方面也注重于研究外國文學各體的研究”。1932年秋朱自清接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同樣特別重視外國文學,“西洋文學史”一直被列為該系的必修課。1946年清華大學復員后,朱自清續任中文系主任,“世界文學史”課程由中文系開設,以中文講授,并讓學生大量閱讀世界文學名著的中文譯本。從50年代起,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四川大學、廈門大學、杭州大學(現已并入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暨南大學等絕大部分綜合性大學以及幾乎所有的師范大學的中文系,都先后設立了外國文學教研室。這些教研室的教師承擔著給中文系本科學生講授外國文學的任務。由于“文革”前我國的研究生培養制度不健全,當時中文系外國文學師資的來源,除了已有的老一代學者外,主要還有兩條渠道:其一,教育主管部門從中文系選拔一部分有較好的外國文學素養和一定外語水平的教師或本科畢業生,到外語院系脫產學習幾年外語,學完后回原系科從事外國文學教學;其二,從外文系教師中抽調一部分文學水平較高的教師,到中文系任教。這三部分人構成“文革”前和“文革”后一段時間內我國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師隊伍的主體。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很有造詣和影響的知名學者,如趙瑞蕻、朱維之、張月超、朱雯、許汝祉、王智量等。他們的外國文學教學、翻譯和研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和培養制度開始逐步走向健全。如同中文系各學科都要通過研究生制度培養自己的師資隊伍一樣,外國文學學科也面臨著這一任務。于是,從80年代初期起,經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批準,我國高校便開始有了作為二級學科的“世界文學”碩士學位點(1980年第一批正式建點的,有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暨南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從那時起陸續畢業于這一專業的一屆又一屆碩士生,是目前我國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師隊伍的骨干。當然,不斷補充著這支隊伍的,還有從外語院系各語種文學專業畢業的博士生、碩士生,以及到國外高校進修、訪學或獲得學位后歸國的學子。這支隊伍已經并且至今仍在發揮著它的作用。把這一學科的名稱改為“外國文學”,而不叫“世界文學”,也未嘗不可。不過,如果改稱“外國文學”,就有可能和設在外語院系的“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相混同。也許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混同,當初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才決定設立“世界文學”二級學科。
有的學者認為,我國高校中不必設立“世界文學”或“外國文學”學科,中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學任務,應當由外語系的教師來承擔。其理由是:外語系的教師精通外語和各語種(國別)文學,由他們來講外國文學,理所當然能講得更地道;而中文系的教師一般外語不行,怎么能講外國文學?
這一說法可能有些絕對化了。中文系不懂外語的外國文學教師確實有過,不過那主要存在于以往;今天如果還有,那也只是個別現象,決不能代表目前我國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師的主體。外語系絕大部分教師確實精通外語和與此種外語相聯系的國別文學。或許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我國有少數綜合性大學的中文系,至今沒有設立外國文學教研室,一直是請外語系教師給本系學生講授外國文學,具體講法是分別由英語(或其他西語)專業、俄語專業和掌握某一東方民族語言(如日語、阿拉伯語等)的教師講授西方文學、俄羅斯文學和東方文學。可是,這樣做的結果,其實和其他大部分高校由中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師自己來講授外國文學并沒有多少區別。因為,除了俄語專業的教師講授俄羅斯文學堪稱“地道”之外,在講授西方文學和東方文學時,無論外語系還是中文系的教師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教師一般只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并精通和此種外語相聯系的國別(語種)文學,但是他卻要給學生講授整個西方文學或東方文學。從各高校學生接受的實際效果來看,由外語系教師上課的未必就更好些。
還有的學者建議取消高校中文系的外國文學史課程,設置國別文學史,分別由外語系各語種的國別文學專家來講授,并讓學生盡可能地接觸作品原文。這是一種美好的設想。假若我們的大學都能夠提供分別精通希臘語、拉丁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德語、法語、英語、俄語、日語、阿拉伯語等各語種的國別文學教師,由他們分別來給學生講授古希臘文學、古羅馬文學、歐洲中世紀文學、意大利文學、西班牙文學、德語文學、法國文學、英美文學、俄羅斯文學、日本文學、阿拉伯文學等各語種、國別文學,那可能是學生們的一種幸運。但是,即便真的擁有如此雄厚的師資力量,這樣的課程恐怕也只能主要以漢語來講授,可以給學生提供的也只能是一、兩種外文資料,因為沒有哪一位學生可以聽懂十幾種語言,看懂十幾種外文資料。再者,外國文學,特別是歐洲文學,絕不是一系列國別文學的簡單相加。學生掌握了諸多國別文學史的知識,也未必能夠回答諸如“為什么說近代歐洲文學的主要體裁都在文藝復興時期奠定了基礎”、“18世紀的歐洲文學怎樣直接影響了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思潮”這類歐洲文學史中的基本問題。
順便說一句:目前國內有的大學外語系已不再開設外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課程。這樣做的結果之一是知識面的相對狹窄。于是,在我們的一些出版物中,謝林變成了“席令”(漓江版《彩色插圖世界文學史》);葉賽寧變成了“埃塞尼”,索爾仁尼琴變成了“索贊尼辛”(1998年5月2日《文匯讀書周報》);柏拉圖變成了“普拉東”,康德變成了“坎特”(學林版《彼得堡的冬天》),等等。這類現象,既和歐洲文學通史知識的缺乏有關,也與蔑視閱讀漢譯世界名著相聯系。世界文學名著的權威漢譯本在我國知識界、廣大作家和廣大讀者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在20世紀以來我國文化和文學發展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已有學者予以充分肯定,此處不復贅言。
問題又回到了由誰來講授歐洲文學史或外國文學史。依筆者的淺見,如果可以把外國文學史粗略地劃分為歐美文學(西方文學)和亞非文學(東方文學)兩大部分,那么,分別承擔這兩部分文學教學任務的教師,應當具備以下基本條件:熟練掌握一門外語,能順利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原文和外文研究資料;精通與其所掌握的外語相聯系的國別(語種)文學史(主要通過外文原文);閱讀過大量的該國別(語種)文學作品(主要通過外文原文);通曉這一國別(語種)文學所屬的歐美文學或亞非文學,包括既了解歐美或亞非文學通史,又了解分屬這兩個部分的各主要國別文學史(主要通過中文);系統閱讀過歐美文學史或亞非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主要通過權威譯本)。
培養具備上述基本條件的教師,正是多年來“世界文學”專業一直努力在做著的主要工作之一。圍繞上述基本目標,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實踐中,“世界文學”專業也已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和特色。毋庸諱言,由于目前我國高校“世界文學”專業大多數教師的外語語種,不外是英語、俄語或日語等少數幾種,掌握其他外語的教師還為數不多,所以“世界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或專業的欠缺之處無疑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局限,只能隨著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該學科重視程度的提高和學科自身建設的強化而逐步得到彌補。
對 “世界文學”學科或專業的懷疑和否定,當然不是始于今日。人們大概都還記得一位已故的英國文學專家的名言:誰能搞“世界文學”?是的,誰也不能搞“世界文學”,正如誰也不能搞“世界史”、“外國哲學”、“西方經濟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一樣,盡管這些學科都作為二級學科客觀存在。所有這些學科的專家,也都只能精通和他們的外語語種相聯系的某一國或少數幾國的哲學、經濟學、史學或語言學等。就“外國哲學”學科而言,分別掌握各種外語、分別精通某一國別哲學的專家們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外國哲學”學科隊伍。“世界史”、“西方經濟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以及“世界文學”學科,其實都是如此。對于可以視為“三級學科”的“西方文論”、“西方文學批評史”、“西方美學史”等,也應作如是觀。看來,至少是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內,所有的涉外學科,都存在一個外語語種的問題。學科名稱往往是很大的,但在這些學科中從事具體工作的人們所能精通的,則只能是和他所掌握的外語語種相聯系的那一小部分。在文學領域,無論是“世界文學”還是“外國語言文學”學科,也概莫能外。
如果我們能夠看到上述一系列事實,那么也許就會對“世界文學”何去何從的問題作出這樣的回答:它只能一如既往,和文學門類中的其他學科、和人文與社會科學門類中的其他涉外學科一起繼續前進。
合并既不是“歸順”,也不是“吞并”
1997年,“世界文學”學科的命運發生了某種變化。是年6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頒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在這一新《目錄》中,原有的“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被合并在一起,出現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引起更多爭議的學科名稱。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