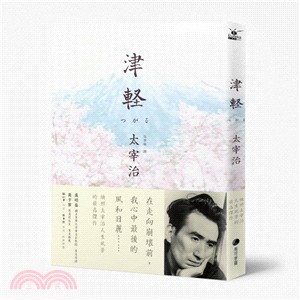商品簡介
在人生走向崩壞前,
我心中最後的風和日麗……
映照太宰治人生風景的最高傑作
「正因為我是津輕人,才能如此肆無忌憚大講津輕的壞話。
但如果其他地方的人聽到我講這些壞話因而全盤盡信並且瞧不起津輕,
我想自己還是會覺得不大高興。再怎麼說,我畢竟深愛著津輕。」───太宰治
★太宰治創作生涯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評論家盛讚「映照作家一生內心風景」的最高傑作!
★中譯版首度推出!作家吳明益專文導讀、舊香居吳卡密專文推薦,駱以軍、侯季然 推薦
「我問你,為什麼要去旅行呢?」
「因為苦悶啊!」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歲的太宰治展開久違的歸鄉之旅,他回到冷颼颼的津輕,偕友人剝蝦吃蟹、熱酒吟歌、登嶺遊寺,一場瀰漫著濃濃酒意、淡淡鄉愁的故鄉巡禮就此揭幕。太宰治以一貫的嘮叨自嘲、一本正經又令人捧腹的丑角精神,酣暢淋漓地描寫故鄉與故人。
如果說《人間失格》是太宰治人生的陰翳夜晚,《津輕》就是他難得愜意的午后時光。《津輕》為連結太宰治中期至晚期生涯的關鍵作品,也是他邁向戰後無賴派風格前最後的明亮之作。天生性格陰鬱的太宰治,試圖在本書以一貫幽默自嘲的文字展現努力的開朗,以及對故鄉既愛又恨的殷切情懷。文壇咸認此為太宰治文學的真正本色。
作者簡介
太宰治 Osamu Dazai(1909-1948)
日本現代知名作家,也是日本文學史上一位頗具爭議的傳奇作家。
本名津島修治,一九○九年六月十九日出生於日本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町的仕紳之家,父親曾任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經營銀行、鐵路等事業。中學時期,受芥川龍之介等人作品影響,立志成為一名作家。一九三○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就讀,師從井伏鱒二,後因參與左翼運動怠惰學業遭革除學籍。一九三三年開始以太宰治為筆名寫作,一九三五年以短篇《逆行》入選第一屆芥川賞決選名單,並於一九三九年以《女生徒》獲第四屆北村透谷獎,在他短暫的寫作生涯中總共創作了三十多部作品,包括《晚年》、《富嶽百景》、《津輕》、《斜陽》、《人間失格》等皆為日本家喻戶曉的經典作品。一九四八年,與情人山崎富榮於東京三鷹玉川上水投河自盡,結束其苦惱、矛盾而充滿傳奇性的一生。
太宰治的人生充滿濃郁的悲劇色彩,自二十歲起五度自殺,酗酒、女性關係複雜、還曾麻藥中毒,畢生寫作以自身為藍本,自傳體式的回憶貫穿文本,作品以負疚、否定、頹廢為底色,文字富哲思同時帶著幾分幽默,廣受文學愛好人士推崇。他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作家被視為日本戰後文學臻至巔峰的大師級巨匠。
譯者
吳季倫
曾任出版社編輯,選書精準,現專職譯述,譯有《無家可歸的中學生》(簡體版上海譯文出版社)、《父親的帽子》、《奢侈貧窮》、《東京下町古書店》系列(以上野人文化)、《津輕》(馬可孛羅文化)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回憶的開始
吳卡密 舊香居店主
對太宰治是一見鐘情。一如我喜歡的波特萊爾、普魯斯特,他們筆下的世界,「自我」永遠是一生的課題。誠實正直地面對自已,是太宰治最令人動容的一面。不斷與自我對話,挖掘、反省,徹底地自我批判、審視自己,期待成就更好的自己,信仰真理、憎恨偽善,讓他無法輕易隨波逐流。看似絶望、消極的態度,其實包含著對生命最熱切的嚮往,反反覆覆的迷失,正是真真切切尋求內在的必要過程,畢竟,誰又能一下子就搞定命運和人生呢?
或許是打小在生意場合穿梭,小學三年級就幫忙看店。以前沒有太多影音娛樂,買書看書的人也較今日來得多。每逢下班、假日時,店裡人來人往,至今常笑說:「除了書,看過的人應該也算多吧!」人來人往,讀書人怪癖多,學問好的,溫和有禮的;莫測高深,目中無人,驕傲自大;財大氣粗的;斤斤計較的,百百種的顧客,很容易觀察到人的不同面向和各種行為,這也是我童工生涯中最大的樂趣。從小與書為伍,說是喜歡閱讀、熱愛文學,倒不如說我對書頁間「起伏人性」更充滿好奇和喜愛,我喜歡以「自我」為中心的創作,赤裸真誠,不賣弄技巧、裝腔作勢地表達人性種種面向,如何坦白地面對自己,永遠是身為「人」,一生的課題!
每個人的秘密一說出口,就是一部私小說。 ——太宰治
一九〇九年,太宰治出生於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村。一九四四年,太宰治接受邀稿,再次回到家鄕,以各地所見所聞,伴隨年少回憶寫出《津輕》,他重訪「最熟悉,也是養成了我的性格,決定了我的命運的地方。」此時是他人生高峰期,創作穩定,不同於初期的他,企圖反抗所有一切成規的束縛,在錯亂與激情中表現自我。也不同於戰後的他,對社會改革、自我變革及自由主義的幻滅失望。那時的太宰治結婚生子,生活安定。他輕鬆愉快地回憶著,友情、親情自然流露,快意熱情地記錄旅程中的沿途風景、歷史場景、民俗典故。重遊舊地,回顧過往,童年往事、親情的疏離、人生原罪、家族的包袱,穿插登場,雖難免有陰鬱的情緒,卻已顯得自在清朗。行文間洋溢善意與溫度,偶爾自嘲也是合宜。提及兒時玩伴,他同樣能以明朗的態度去面對性格上的弱點,因為家族包袱始終是他無法逃脫的原罪。重回故鄉,尋友訪友,亦同時重新檢視自己與家人的關係。談及早逝的父親,他坦白自己是隨著年齡増長,對父親的一切突然產生亟欲了解的欲望──究竟,父親是個怎樣的人呢?
重返父親的故鄉「木造町」:
「這棟房子的隔間跟我那金木町的家非常相像。聽說,金木町現在的房子是我父親當了門婿之後不久,親自設計與大幅改建的。原來到了金木町的父親,只是把隔間改成與自己的老家一樣罷了。我好像可以明瞭身為門婿的父親當時的想法與感受,不由得會心一笑。有了這層體會後,就連院子裡的樹木和石頭的擺置,看上去都似曾相識。即便只是發現了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彷彿已經感受到死去父親『感性的一面』了。」
而這趟旅程的終站,也是《津輕》一書最精釆高潮的部分──小泊港,太宰治恍恍惚惚、抑鬱一生,藏在內心深處最甜蜜和痛苦的記憶,是代母哺育他的女傭阿竹──此行他最渴望見到的人。「三歲到八歲,都是由阿竹教育我的。某一天的早晨,我忽然醒過來,喚了阿竹,阿竹卻沒來。我吃了一驚,憑著直覺感到情況有異,立時放聲大哭。我哭得肝腸寸斷。」
終於來到小泊港,一開始尋找不到阿竹時,他近乎捉狂地咆哮:
「可說穿了,不就是個下人嘛!不就是個女佣嘛!難道你是女佣的孩子嗎?一個大男人,竟還苦苦思念兒時的女佣,說什麼非得見上一面的,你就是這樣才成不了材!也難怪哥哥們薄情地瞧不起你,當你是個低俗又陰柔的傢伙。這麼多兄弟們裡,就你一個怪胎!你怎會這般沒出息、卑鄙無恥、令人作嘔呢?你就不能振作起來嗎?」
多麼濃烈的思念啊!心中的澎湃、情緒化的發洩,長期的渴望和不安是這麼表露無遺。慌亂惶恐的心,在找到阿竹,得到安撫時,揮之不去的問號、遺憾都在阿竹身旁消散了。
「我伸直了雙腿,怔愣地看著運動會,心中沒有任何牽掛。也就是那種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無所謂、完全無憂無愁的心情。所謂的心靈平靜,大概就是指這種狀態吧。倘若確然如此的話,這時可說是我生平以來所體會到的內在寧靜了。」
與阿竹重逢的終章,讓我的眼眶不自覺濕了,他內心深處的種種壓抑和煩憂暫時雲散風消,在孕育、滋養他的故鄉找到安心的勇氣了。
從不同的作品重新建構作家人格的想像,也是另一種閱讀的喜悅。雖然太宰治自詡《津輕》是昭和年代的旅遊指南,但這本洋溢著希望、感謝、寬容的真情之作,不同以往大家熟悉的太宰治──軟弱、頹廢、憂鬱、黑暗、絶望……。這本津輕紀行釋放出的文字情感真摯細膩,太宰的年少時光更躍然紙上。除了展現文學本事,更讓讀者見識到他對生命的熱忱。當然,他依舊是大家記憶中瀟灑恣意的太宰治,仍會豪情率性說出:「即便一無所有,他,仍是崇奉真理和崇奉愛情的乞丐。」
《津輕》書末他寫下:「帶著勇氣向前走!切勿絕望!」即便他說過:「生而爲人,我很抱歉」、「活著,是很辛苦的。處處纏繞鎖錬,稍微一動,便有血噴出。」但對於文學的熱愛和信仰曾經讓他憧憬未來、擁抱世間、友愛眾生。闔上書,除了感動更有一番新的領會,我相信太宰治曾經踏踏實實、竭盡全力,努力認真地活在當下呀!
序
導讀
唯有再見才是人生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一九〇二年二十二歲的魯迅赴日,兩年後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成為仙台唯一的中國學生。二十年後,才有那篇知名的〈藤野先生〉,以及裡頭所回憶的「幻燈片事件」。
〈藤野先生〉裡魯迅陳述的日本經驗成為魯迅傳奇的一部分,文章中提及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的其中一張幻燈片,引起日本同學歡呼,讓魯迅意識到自己同胞的麻木病源,也成為他棄醫從文的關鍵。許多論者認為,魯迅後來到東京著手翻譯俄國與東歐文學,參與革命活動,寫出〈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都跟這個「幻燈片事件」有關。彼時一代文學家太宰治仍未出生。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歲的太宰治受日本內閣情報局與文學報國會將「大東亞五大宣言」予以小說化的委託,開始閱讀魯迅,並且於暮冬之際赴仙台探詢魯迅事蹟,翌年,日本戰敗,《惜別》出版。
太宰多數小說都有很濃厚的個人色彩,但《惜別》卻是「他傳」,寫的是魯迅在仙台的生活。太宰治虛構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醫師,在記者的來訪下,回憶和魯迅相處的點點滴滴。太宰為了寫作魯迅,將七卷本《大魯迅全集》(改造社)細讀過,成為他理解魯迅的基礎。小說中魯迅對田中的自白,內容顯然都來自於魯迅的作品。與此同時,太宰治還讀了兩本魯迅的傳記,分別是他評述「像春花一樣甘美」的《魯迅傳》(小田岳夫),以及「像秋霜一樣冷峻」的《魯迅》(竹內好)。
《惜別》在日本文學界的評價並不高,竹內好甚至批判太宰誤讀魯迅,但我卻認為它是一部極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於,這部受政府委託的著作裡,太宰藉魯迅之口,某種程度批判了軍國思想。其次是,太宰也藉由魯迅的文學觀,發揮了自己的文學觀。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託寫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書店之邀寫作故鄉,這就是你手中這部美麗的重訪(或告別)故鄉之書——《津輕》。
台灣讀者對太宰治的認識,多半建立在《人間失格》與《斜陽》這兩部作品上。放蕩酒色、心靈矛盾、哀傷為人的掙扎,是太宰文學的典型。而他五次自殺的經歷,也讓人常與小說聯想在一起。相對地,閱讀《津輕》將是完全不一樣的明亮經驗。
《津輕》分為「序文」,及「正文」(〈巡禮〉、〈蟹田〉、〈外濱〉、〈津輕平原〉、〈西海岸〉五章),乍看像是以地理與特色進行「導覽」的遊記,實質上則不然。太宰認真閱讀了大量地方歷史文獻,再穿插訪友經驗與回憶片段,寫出了這部「不只是遊記」的作品。
書中內容我自不必贅述,但不妨提醒讀者注意幾個部分:論者多半認為太宰治的憂鬱性格,與他的家族有關。選擇文學為志業的太宰,很想逃離父親與兄長的權力環境(他的父親津島源右衛門是地方名紳,也是縣議員、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同時經營銀行與鐵路),而《津輕》正好為此觀點,埋藏了情感線索。
其次,讀者當會發現,除了嘲弄、戲謔的「無賴派風格」外,太宰寫景與敘事都十分出色。《津輕》與《惜別》裡的景色都十分溫暖,那些小酒館、漁村巷弄、堤川、觀瀾山,在港口緩緩落下的粉雪、粒雪、綿雪、水雪、硬雪、糙雪、冰雪(只有雪國的子民才能分得清楚),以及水色淺、鹽分淡,還隱隱飄著海潮香味的蟹田海岸,他是如此努力想展示自己故鄉的美與自己文化氣質的根源。此外,太宰的歷史觀、文學觀與思想,也在這部書裡與故舊的飲宴討論中,很自然地鋪展開。
而我最被吸引的,當然是這部書裡太宰治顯示出的「月之亮面」:包括他和老友及照顧他的女傭阿竹間的情誼,以及對家鄉土地的感情。
比方說在與阿竹重逢的那段,太宰刻意把拉雜的尋人過程都寫出來,卻讓人緊張地期待。他提到「在兄弟姊妹當中,只有我一個的性情粗野而急躁,很遺憾地就是來自這位養育我的母親的影響」,指的就是十三歲起就照顧他的阿竹,這是對一個女傭的最高禮讚。而當他與好友N君談及故鄉的「歉收年表」,看到每隔幾年就出現的凶年,太宰不禁義憤。他說津輕人將歉收說成「饑渴」,而「我們的祖輩一生下來遇上了歉收,在艱難的困境中長大成人。這些熬過困境的祖輩們的血液,也必然在我們的體內流動著」,甚至大膽批判了政府無能。
引用京都名醫橘南谿《東遊記》中的幾則奇幻故事,更讓我彷彿看到眼神天真澄澈的少年太宰——畢竟太宰留下的照片,眼神總是如斯憂鬱。
太宰或許不能理解魯迅留學時所受到的歧視,以及做為一個沒落帝國的子民,在日俄戰爭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顯然很努力想理解這個影響中國的作家,並且與他在文學中對話。研究者藤井省三曾為文討論過太宰的《惜別》,提及小說裡魯迅寫了一段文章給「我」,內容正是〈摩羅詩力說〉的部分段落。「我」回應說:「我覺得,該短文的主旨,指出了與他從前說的那種『為幫助同胞的政治運動』的文藝多少有些差異的方向,不過,『不用之用』一詞讓人感到豐富的含蓄。終歸還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實際的政治運動那樣對民眾的強大指導性,而是漸漸地浸潤人心,發揮使其充實之用的東西。」「我」並進一步說:「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文藝這種東西,就會像注油少的車輪那樣,無論開始時怎樣流暢快速地運轉,也許馬上就會損毀。」
或許,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權力,對時局與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縱情慾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學是不斷滾動人生的潤滑,是無用卻能浸潤人心的物事。
太宰與魯迅與相似之處,還在於他們對父親形象的抵抗。在這特別的一年裡,或許短暫地讓他從多重的糾結情感抽身出來,體驗了人跟土地的純粹情感。
只是他終究選擇再次告別。
在太宰治的遺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詩:「人生足別離」。勸酒的人說,不要再推辭斟滿酒杯了啊,因為「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太宰說他有一位前輩將詩句翻譯成「唯有再見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悅轉瞬即逝,離別的傷心卻黯然銷魂、如影隨形,因此我們一生都得活在告別中。
我將《津輕》視為一部「告別」之作,因為那個太宰歸去的故鄉,正是他要道別的故鄉。而他寫魯迅的作品名為《惜別》(這是藤野送給魯迅照片背後的題字),則是太宰文學精神的另一面相: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與世界告別,在我看來,正是太宰「惜別」這個世間之故。那個他想離棄的生命,就是他燃燒的生命;而他離去的故鄉,正是他留戀的母土。關於這點,你手上的《津輕》正是美麗的明證。
目次
津輕雪花的種類
粉雪
粒雪
綿雪
水雪
硬雪
糙雪
冰雪
序章
正文
一 巡禮
二 蟹田
三 外濱
四 津輕平原
五 西海岸
書摘/試閱
正文
一 巡禮
「我問你,為什麼要去旅行呢?」
「因為苦悶啊!」
「你成天嚷嚷著苦悶呀苦悶的,這話誰信哪?」
「正岡子規三十六、尾崎紅葉三十七、齋藤綠雨三十八、國木田獨步三十八、長塚節三十七、芥川龍之介三十六、嘉村礒多三十七。」
「什麼意思?」
「那些傢伙死掉的年紀呀!他們就這麼一個接一個死了。算算,我也快到那個年紀了。身為一個作家,這個年紀正是緊要關頭。」
「那就是你所謂苦悶的時候嗎?」
「什麼呀?別瞎說了!妳多少總也明白一些吧?不說了,再講下去說就像故弄玄虛了。喂,我出門旅行啦!」
或許是我多少長了些年紀,總覺得向人解釋自己的感受,未免有裝腔作勢之嫌(況且那大都是些老生常談的虛偽文辭),因而什麼都不想說了。
某家出版社和我熟識的編輯從以前就問了我幾次:要不要寫一寫津輕呢?再加上我也想在有生之年看遍自己生長之地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就在某一年的春天,以一身乞丐般的裝束從東京出發了。
出發的日期是五月中旬。使用「乞丐般」這樣的形容,我想應該是一種主觀看法,可即便客觀來說,我的裝束也並不怎麼稱頭。我連一套西裝都沒有,只有勤勞服務的工作服,而且還不是去裁縫舖特別訂做的,只是妻子拿家裡現成的棉布塊染成藏青色後兜湊出來的夾克外套和長褲,成了看來頗為古怪的工作服。而且布料剛染完的顏色的確是藏青色沒錯,可穿上它外出一兩次後,馬上就變成了帶紫的奇怪顏色。即便是紫色的女用洋裝,也得穿在絕色佳人的身上才好看。我就在這條紫色的工作褲上,纏上人造羊毛短纖的綠色綁腿,再穿雙白粗麻布的膠底鞋,頭上戴的同樣是人造羊毛短纖的網球帽。向來注重衣著的我,人生中頭一遭以這副模樣出遊。不過,背包中到底還是塞進了用母親的遺物重新縫製、繡有家徽的單層外褂和大島綢的夾衣,還有一件仙台綢的褲裙。畢竟保不準會遇上什麼正式的場合,屆時就能派上用場了。
我搭乘十七點三十分由上野車站出發的快車。隨著夜色漸沉,寒意愈發襲人。我在那件貌似夾克外套底下只穿了兩件薄襯衫,而長褲裡面更只有一條褲叉。且不說我沒料到今晚的嚴寒,就連穿著冬季外套還備了毛毯蓋腿的人都嚷著「冷死了!今天晚上怎麼冷成這個樣子呀!」這個時節在東京,路上已可見到有些性急的人早早換上嗶嘰布料的單層和服了。我一時大意,竟忘了東北的嚴寒,只得盡量把全身縮成一團,成了如假包換的龜縮模樣,喃喃自語:正是!這就叫「滅卻心頭」的修行!然而愈近拂曉,凍寒更是有增無減。彼時的我已然放棄了「滅卻心頭」的修行念頭,滿腦子打轉的只有現實而庸俗的主意,一心巴望著快快到達青森,找個旅舍盤腿坐在暖爐旁,愜意地喝上熱酒。火車在早上八點鐘抵達了青森,T君來車站迎接。我早前已經事先捎信知會他了。
「我還以為您會穿和服來。」
「那已經過時了。」我盡量以談笑的語氣說道。
T君帶著女兒來接我。我這才猛然想到,早知道就該給孩子帶點禮物。
「總之,先去我家歇一下吧?」
「謝謝。不過,今天我想在中午之前趕到蟹田的N君家。」
「我知道,我聽N先生說了,他正在恭候大駕。總之,在開往蟹田的巴士發車之前,先到我家歇個腿吧!」
我先前那個盤坐在暖爐旁喝熱酒的庸俗願望,居然奇蹟似地實現了!到了T君家,屋裡的地爐已升起熊熊炭火,鐵壺裡也熱著一壺酒了。
「遠道而來,辛苦您了。」T君恭敬規矩地向我行禮,「您用啤酒嗎?」
「不,我喝清酒。」我輕聲乾咳。
T君曾待過我家,主要負責管理雞舍。他與我同齡,所以我們常一塊玩。我當時還曾聽過外祖母這樣批評T君:「那小子會罵女佣,真不知道該說他好還是壞。」後來T君去青森市上學,又進了青森市某家醫院工作,很受病患和同事們的信賴。前些年他曾出征到南方的孤島打仗,去年因病返鄉。病癒之後,又回到原來的那家醫院工作。
「你在戰地的時候,最高興的事是什麼?」
「當然是……」T君立即回答,「在戰地喝到滿滿一杯配給的啤酒。我會小心翼翼地一小口、一小口吸啜,喝到一半想離開杯緣喘口氣,可嘴脣卻牢牢巴著杯子不肯放,怎麼樣也沒法放開杯子。」
T君曾是一位嗜酒之人,現在卻滴酒不沾,還不時輕咳幾聲。
「你身子怎麼樣了?」
T君在很久以前曾患了肋膜炎,這次在戰地時又復發了。
「我從戰地回來,現在算是在後方服務。如果沒有那段自己生病受折磨的經歷,如今在醫院醫治病人時就無法面面俱到了。這回我可真有了深刻的體悟。」
「看來,你的醫德愈來愈崇高了!老實說,你那個胸疾……」我開始有了醉意,竟大放厥詞向醫生教起醫學來了,「根本是精神的疾病,只要忘了它,就會好起來的,有時候也得痛快地喝個夠呀!」
「您說得是,小酌怡情。」他說著,笑了起來。看來,我那毫無根據醫學論述並未得到正規醫生的認同。
「您要不要用些飯菜?只是青森這時節沒什麼當令的鮮魚。」
「不了,謝謝。」我心不在焉地望著一旁備妥的菜餚,「看起來都十分美味可口呀!給你添麻煩了,只不過我不大想吃東西。」
這趟津輕之旅,我在心中打定了主意,那就是對吃食要清心寡欲。我並非聖賢,一本正經地說這種話實在很難為情,但是東京人對食物的欲望實在超過限度了。可能我自己生性守舊,儘管覺得俗諺所說的「武士肚飢叼牙籤」那種近乎自暴自棄、打腫臉充胖子的愚蠢心態相當滑稽,卻依然深深地喜愛這句話。我覺得武士大可不必叼牙籤裝派頭,但這就叫男子漢的氣魄。所謂男子漢的氣魄,往往會以滑稽的形式呈現出來。聽說有些一沒骨氣二沒幹勁的東京人,到了鄉下就語氣誇張地哭訴住東京的人都快餓死了,然後央求鄉下人拿出白米做飯給他們,米飯上桌就千恩萬謝地扒飯大啖,同時不忘逢迎拍馬,堆出猥瑣的笑意涎著臉懇求:還有什麼可吃的嗎?有芋頭嗎?真是太好了,好幾個月沒吃到這麼美味的東西了!我還想順便帶點回家,能不能分一些給我呀?我確信每一個東京人都配給到份量相同的糧食,卻單單只有那些人抱怨快要餓死了,這實在很奇怪。也許他們的胃囊比別人大上一號吧。總而言之,哭求索討食物簡直不成體統。且不說值此非常時期,就該打著為國為民的大旗而自我犧牲,至少無論身在任何時代,都應當秉持一個人的尊嚴。我還聽說,就因為有少數例外的東京人去到外地就胡說一通,抱怨帝都糧食缺乏,因而外地人都瞧不起東京的來客,當他們全是一群來劫掠食物的傢伙。我這一趟可不是為了劫掠食物才來到津輕的。儘管我這身紫色的裝束真像個乞丐,可我是個崇奉真理和愛情的乞丐,絕不是討食白米飯的乞丐!──我不惜用上台講演的誇張語調、外帶擺個亮相說這段話以加強戲劇效果,也非得維護所有東京人的名譽不可!這是我這趟來到津輕前下定的決心。萬一有人對我說:「來來來,這是白米飯,儘管吃到撐破肚皮。聽說東京沒東西吃吧?」即便他是由衷的好意,我也只吃一小碗,還要回敬一段話:「大概是吃慣了吧,我覺得還是東京的米飯好吃。就連下飯菜,也恰好會在吃光的時候發了配給。我的胃好像也跟著縮小許多,吃一點就覺得飽了,妙哉妙哉!」
沒想到我那套乖僻的心思,可以說是完全白費了。我走訪了津輕各地的親朋好友,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我說:「這是白米飯呀,儘管吃到撐破肚皮!」尤其是我那位高齡八十八的外祖母,更是一臉正經地告訴我:「東京是個什麼好東西都吃得到的地方,就是想弄點好吃的給你,也想不出來該弄什麼才對。我本想給你吃點酒糟醃瓜,可不曉得怎麼回事,這陣子連酒糟都找不到了。」外祖母這番話讓我備感幸福。事實上,我這回見的都是些對吃食不怎麼在意的老實人。為此,我感恩老天爺賜予我的幸運。沒有人把美食特產硬塞給我,叫我這個也帶走、那個也帶走,多虧如此,我才得以一路輕裝,逍遙自在地繼續旅程;可當我回到東京家一看就傻了,因為此行所到之處的主人家,都已體貼地先我一步,把包裹寄到家裡來了。這些是題外話。總之,T君並沒有特別殷勤地勸酒讓菜,更絲毫沒有提及東京目前糧食供應的狀況。我們主要聊的話題,還是我們兩人以前在金木町的家中一起玩耍的往事。
「話說,我真把你當成好兄弟哩!」
這實在是粗魯、失禮、諷刺、裝腔又擺譜的狂妄之語。話一出口我就侷促不安了──我就找不到別句話好說的嗎?
「那樣反倒教人不愉快了。」T君像是也敏感地察覺到了。「我在金木町是你家的佣人,而你是主人。如果你不這樣想的話,我可不高興了。說來奇怪,日子都過二十年了,我到現在還常夢見你在金木町的家,連上戰場時也作過夢──完了!我忘了餵雞啦!然後就從夢裡驚醒。」
巴士發車的時間到了,T君陪我一起出了門。外頭已經不冷,天氣很好,再加上我喝了熱酒,別說不冷,額頭都還冒了汗呢。我們聊到了合浦公園現在正是櫻花盛開的時節。青森市的街道乾燥又潔白,噢不,醉眼惺忪看到的朦朧景象還是閉口不提才好。青森市目前正傾力發展造船工業。我半路順道去給中學時代照顧過我的豐田伯父上了墳,然後就趕去巴士車站了。假如是以前的我,可能會隨口邀T君同行:走吧,跟我一起去蟹田吧?可我畢竟長了些歲數,多少學會了一點人情世故,要不就是……哎,那種複雜的心情暫且按下不表。總之,我們雙方都已成為大人了。所謂大人,就得忍受孤獨,即使友情濃厚,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相互客套。為什麼非得小心翼翼不可呢?答案是,不為什麼。只因為已經遇過太多受騙上當、丟人現眼的事了。不能相信別人,這是從青年蛻變成大人的第一堂課。大人就是曾經受騙上當的青年所映出來的身影。我保持沉默,向前走去。這時,T君突然開了口:
「我明天會去蟹田。搭明天一早的第一班車去。我們就在N先生家碰面吧!」
「醫院那邊呢?」
「明天是星期天。」
「哎,原來如此!你怎麼不早點說啊?」
看來,我們心裡都還保有當年的那個純真少年。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