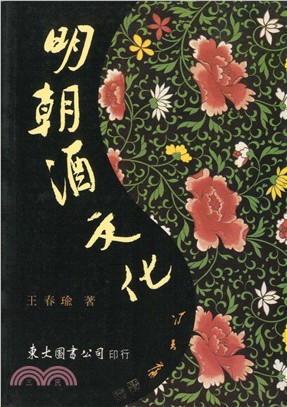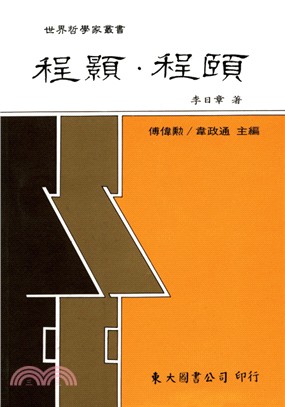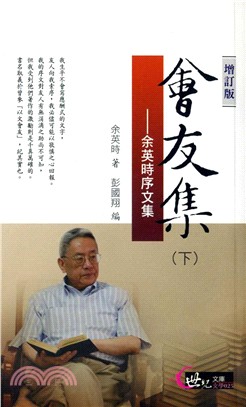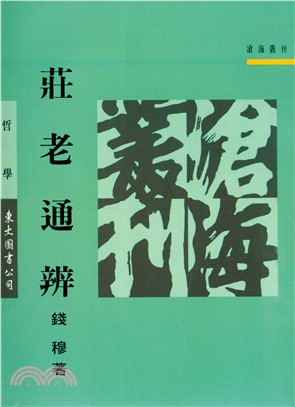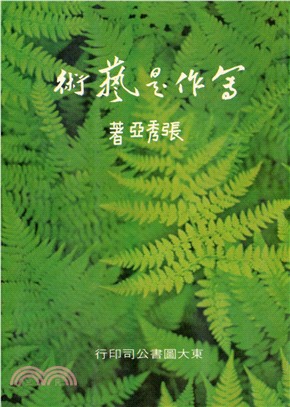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商市街》是蕭紅的散文集,創作完成于1935年5月15日,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二集第十二冊,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名悄吟。收入散文《歐羅巴旅館》、《雪天》、《他去追求職業》、《家庭教師》、《來客》、《當鋪》、《廣告員的夢想》、《家庭教師是強盜》、《十三天》、《拍賣家具》、《最后的一個星期》等41篇,后附郎華(蕭軍)《讀后記》1篇。
《回憶魯迅先生》是長篇紀實散文。1940年7月重慶婦女生活社初版,署名蕭紅。增加了蕭紅的《魯迅先生記(一)》、《魯迅先生記(二)》兩篇散文。
《回憶魯迅先生》是長篇紀實散文。1940年7月重慶婦女生活社初版,署名蕭紅。增加了蕭紅的《魯迅先生記(一)》、《魯迅先生記(二)》兩篇散文。
作者簡介
蕭紅, 1911年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著名女作家,被譽為“30年代文學洛神”。1935年發表了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東渡日本,并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抵達香港之后,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名人/編輯推薦
看許鞍華導演、湯唯主演的《黃金時代》 讀民國文學洛神蕭紅經典文字《商市街》完成于1935年5月,帶有明顯的自傳特色,但同時具有社會風情畫的特點。生動而真實描寫了城市里的貧富懸殊與對立,下層百姓境遇的悲慘,知識分子求職的艱難與謀生的不易,熱血青年的憂傷、歡笑和對人生道路的探尋與抉擇……
《回憶魯迅先生》初版于1940年7月,作者通過女性的細心體察,敏銳捕捉到了魯迅先生許多有靈性的生活細節,表現出魯迅超群的智慧、廣闊的胸襟和可親可敬的個性品質。是關于魯迅先生的諸多回憶錄中的珍品。
此外,本書還收錄了《魯迅先生記(一)》和《魯迅先生記(二)》兩篇散文。
在不到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她留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成為中國現代文壇一顆耀眼的明星,被稱為“文學洛神”。魯迅說,將來取代丁玲成為女作家中佼佼者的必定是蕭紅。
《回憶魯迅先生》初版于1940年7月,作者通過女性的細心體察,敏銳捕捉到了魯迅先生許多有靈性的生活細節,表現出魯迅超群的智慧、廣闊的胸襟和可親可敬的個性品質。是關于魯迅先生的諸多回憶錄中的珍品。
此外,本書還收錄了《魯迅先生記(一)》和《魯迅先生記(二)》兩篇散文。
在不到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她留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成為中國現代文壇一顆耀眼的明星,被稱為“文學洛神”。魯迅說,將來取代丁玲成為女作家中佼佼者的必定是蕭紅。
目次
目 錄
商市街
歐羅巴旅館
雪天
他去追求職業
家庭教師
來客
提籃者
餓
搬家
最末的一塊木
黑列巴和白鹽
度日
飛雪 目 錄
商市街
歐羅巴旅館
雪天
他去追求職業
家庭教師
來客
提籃者
餓
搬家
最末的一塊木
黑列巴和白鹽
度日
飛雪
他的上唇掛霜了
當鋪
借
買皮帽
廣告員的夢想
新識
牽牛房
十元鈔票
同命運的小魚
幾個歡快的日子
女教師
春意掛上了樹梢
小偷車夫和老頭
公園
夏夜
家庭教師是強盜
冊子
劇團
白面孔
又是冬天
門前的黑影
決意
一個南方的姑娘
生人
又是春天
患病
十三天
拍賣家具
最后的一個星期
讀后記/郎華
回憶魯迅先生回憶魯迅先生
附錄魯迅先生記(一)
魯迅先生記(二)
商市街
歐羅巴旅館
雪天
他去追求職業
家庭教師
來客
提籃者
餓
搬家
最末的一塊木
黑列巴和白鹽
度日
飛雪 目 錄
商市街
歐羅巴旅館
雪天
他去追求職業
家庭教師
來客
提籃者
餓
搬家
最末的一塊木
黑列巴和白鹽
度日
飛雪
他的上唇掛霜了
當鋪
借
買皮帽
廣告員的夢想
新識
牽牛房
十元鈔票
同命運的小魚
幾個歡快的日子
女教師
春意掛上了樹梢
小偷車夫和老頭
公園
夏夜
家庭教師是強盜
冊子
劇團
白面孔
又是冬天
門前的黑影
決意
一個南方的姑娘
生人
又是春天
患病
十三天
拍賣家具
最后的一個星期
讀后記/郎華
回憶魯迅先生回憶魯迅先生
附錄魯迅先生記(一)
魯迅先生記(二)
書摘/試閱
商市街商 市 街歐羅巴旅館
樓梯是那樣長,好像讓我順著一條小道爬上天頂。其實只是三層樓,也實在無力了,手扶著樓欄,努力拔著兩條顫顫地,不屬于我似的腿,升上幾步,手也開始和腿一般顫。
等我走進那個房間的時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著臉。
他——郎華,我的情人,那時候他還是我的情人,他問我了:
“你哭了嗎?”
“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淚呀!”
不知是幾分鐘過后,我才發現這個房間是如此的白,棚頂是斜坡的棚頂,除了一張床,地下有一張桌子,一圍藤椅。離開床沿用不到兩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開門時,那更方便,一張門扇躺在床上可以打開。住在這白色的小室,好像把我住在幔帳中一般。我口渴,我說:
“我應該喝一點水吧!”
他要為我倒水時,他非常著慌,兩條眉毛好像要連接起來,在鼻子的上端扭動了好幾下:
“怎樣喝呢?用什么喝?”
桌子上除了一塊潔白的桌布,干凈得連灰塵都不存在。
我有點昏迷,躺在床上聽他和茶房在過道說了些時,又聽到門響,他來到床邊。我想他一定舉著杯子在床邊,卻不,他的手兩面卻分張著:
“用什么喝?可以吧?用臉盆來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著才帶來的臉盆時,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發現,于是拿著刷牙缸走去。
旅館的過道是那樣寂靜,我聽他踏著地板來了。
正在喝著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單上,我用發顫的手指撫來撫去。他說: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撫來撫去,床單有突起的花紋,并且白得有些閃我的眼睛,心想:不錯的,自己正是沒有床單。我心想的話他卻說出了!
“我想我們是要睡空床板的,現在連枕頭都有。”
說著,他拍打我枕在頭下的枕頭。
“咯咯——”有人打門,進來一個高大的俄國女茶房,身后又進來一個中國茶房:
“也租鋪蓋嗎?”
“租的。”
“五角錢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說不租,郎華也說不租。
那女人動手去收拾:軟枕,床單,就連桌布她也從桌子扯下去。床單夾在她的腋下。一切夾在她的腋下。一秒鐘,這潔白的小室跟隨她花色的包頭巾一同消失去。
我雖然是腿顫,雖然肚子餓得那樣空,我也要站起來,打開柳條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樣,床上一張腫漲的草褥赤現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點和白圈顯露出來,大藤椅也好像跟著變了顏色。
晚飯以前,我們就在草褥上吻著抱著過的。
晚飯就在桌子上擺著黑“列巴”和白鹽。
晚飯以后事件就開始了:
開門進來三四個人,黑衣裳,掛著槍,掛著刀。進來先拿住郎華的兩臂,他正赤著胸膛在洗臉,兩手還是濕著。他們那些人,把箱子弄開,翻揚了一陣:
“旅館報告你帶槍,沒帶嗎?”那個掛刀的人問。隨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個長紙卷,里面卷的是一支劍。他打開,抖著劍柄的紅穗頭:
“你那里來的這個?”
停在門口那個去報告的俄國管事,揮著手,急得漲紅了臉。
警察要帶郎華到局子里去,他也預備跟他們去,嘴里不住說:“為什么單獨用這種方式檢查我?防害我?”
最后警察溫和下來,他的兩臂被放開,可是他忘記了穿衣裳,他濕水的手也干了。
原因日間那白俄來取房錢,一日兩元,一月六十元。我們只有五元錢。馬車錢來時去掉五角。那白俄說:
“你的房錢,給!”他好像知道我們沒有錢似的,他好像是很著忙,怕是我們跑走一樣。他拿到手中兩元票子又說:“六十元一月,明天給!”原來包租一月三十元,為了松花江漲水才有這樣的房價。如此,他搖手瞪眼的說:“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華說:“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經理——”
郎華從床下取出劍來,指著白俄:
“你快給我走開,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張著跑出去了,去報告警察所,說我們帶著兇器,其實劍裹在紙里,那人以為是大槍,而不知是一支劍。
結果警察帶劍走了,他說:“日本憲兵若是發現你有劍,那你非吃虧不可,了不得的,說你是大刀會,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來取。”
警察走了以后,閉了燈,鎖上門,街燈的光亮從小窗口跑下來,凄凄淡的,我們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國人,倒比日本憲兵強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從朋友處被逐出來是第二天了。雪天
我直直是睡了一個整天,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漸漸從灰色變做黑色。
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餓了。我下床開了燈,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間坐了坐,扒一扒頭發,揉擦兩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長和無底,好像把我放下一個煤洞去,并且沒有燈籠,使我一個人走沉下去。屋子雖然小,在我覺得和一個荒涼的廣場樣,屋子的墻壁隔離著我,比天還遠,那是說一切不和我發生關系;那是說我的肚子太空了!
一切街車街聲在小窗外鬧著。可是三層樓的過道非常寂靜。每走過一個人,我留意他的腳步聲,那是非常響亮的,硬底皮鞋踏過去,女人的高跟鞋更響亮而且焦急,有時成群的響聲,男男女女穿踏著過道一陣。我聽遍了過道上一切引誘我的聲音,可是不用開門看,我知道郎華還沒回來。
小窗那樣高,囚犯住的屋子一般,我仰起頭來,看見那一些紛飛的雪花從天空忙亂的跌落,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即刻就消融了!變成水珠滾動爬行著,玻璃窗被它畫成沒有意義無組織的條紋。
我想:雪花為什么要翩飛呢?多么沒有意義!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沒有意義嗎?坐在椅子里,兩手空著,什么也不做;口張著,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機器相像。
過道一響,我的心就非常跳,那該不是郎華的腳步?一種穿軟底鞋的聲音,擦擦來近門口,我仿佛是跳起來,我心害怕著:他凍得可憐了吧?他沒有帶回面包來吧!
開門看時,茶房站在那里:
“包夜飯嗎?”
“多少錢?”
“每份六角。包月十五元。”
“……”我一點都不遲疑搖著頭,怕是他把飯送進來強迫叫我吃似的,怕他強迫向我要錢似的。茶房走出,門又嚴肅的關起來。一切別的房中的笑聲,飯菜的香氣都斷絕了,就這樣用一道門,我與人間隔離著。
一直到郎華回來,他的膠皮底鞋擦在門限我才止住幻想。茶房手上的托盤,肉餅,炸黃的番薯,切成大片有彈力的面包……
郎華的夾衣上那樣濕了,已濕的褲管拖著泥。鞋底通了孔,使得襪子也濕了。
他上床暖一暖,腳伸在被子外面,我給他用一張破布擦著腳上冰涼的黑圈。
當他問我時,他和呆人一般直直的腰也不彎:
“餓了吧?”
我幾乎是哭了,我說:“不餓。”為了低頭,我的臉幾乎接觸到他冰涼的腳掌。
他的衣服完全濕透,所以我到馬路旁去買饅頭。就在光身的木桌上,刷牙缸冒著氣,刷牙缸伴著我們把饅頭吃完。饅頭既然吃完,桌上的銅板也要被吃掉似的。他問我:
“夠不夠?”
我說:“夠了。”我問他:“夠不夠?”
他也說:“夠了。”
隔壁的手風琴唱起來,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嗎?手風琴凄凄涼涼地唱呀!
登上桌子,把小窗打開。這小窗是通過人間的孔道:樓頂,煙囪,飛著雪沉重而濃黑的天,路燈,警察,街車,小販,乞丐,一切顯現在這小孔道,煩煩忙忙的市街發著響。
隔壁的手風琴在我們耳里不存在了。他去追求職業
他是一匹受凍受餓的犬呀!
在樓梯盡端,在過道長筒的那邊,他著濕的帽子被墻角隔住,他著濕的鞋子踏過發光的地板,一個一個排著腳踵的印泥。
這還是清早,過道的光線還不充足。可是有的房間門上已經掛好“列巴圈”了!送牛奶的人,輕輕帶著白色的,發熱的瓶子排在房間的門外。這非常引誘我,好像我已嗅到“列巴圈”的麥香,好像那成串肥胖的圓形的點心已經掛在我的鼻頭上。幾天沒有飽食,我是怎樣的需要啊!胃口在胸膛里面收縮,沒有錢買,讓那“列巴圈”們白白在虐待我。
過道漸漸響動起來。他們呼喚著茶房,關門開門,倒臉水。外國女人清早便高聲說笑。可是我的小室,沒有光線,連灰塵都看不見飛揚,靜得桌子在墻角欲睡了,藤椅在地板上伴著桌子睡;靜得棚頂和天空一般高,一切離得我遠遠,一切都厭煩我。
下午,郎華還不回來,我到過道口站了好幾次,外國女人紅色的裙子,藍色的裙子……一張張笑著的驕傲的紅嘴,走下樓梯,她們的高跟鞋打得樓梯清脆發響。圓胖而生著大胡子的男人那樣不相稱地捉著長耳環黑臉的和小雞一般瘦小的“基卜塞”女人上樓來。茶房在前面去給打開一個房間。長時間以后又上來一群外國孩子,他們嘴上剝著瓜子,多冰的鞋底在過道上擗擗拍拍的留下痕跡過去了。
看遍了這一些人,郎華總是不回來,我開始打旋子,經過每個房間,輕輕蕩來踱去,別人已當我是個偷兒,或是討乞的老婆,但我自己并不感覺。仍是帶著我蒼白的臉,退了色的藍布寬大的單衫踱蕩著。
忽然樓梯口跑上兩個一般高的外國姑娘。
“啊呀!”指點著向我說:“你的……真好看!”
另一個樣子像是為了我倒退了一步,并且那兩個不住翻著衣襟給我看:
“你的……真好看!”
我沒有理她們。心想:她們帽子上有水滴,不是又落雪?
跑回房間,看一看窗子究竟落雪不?郎華是穿著昨晚潮濕的衣裳走的。一開窗,雪花便滿窗倒傾下來。
郎華回來,他的帽沿滴著水,我接過來帽子問他:
“外面上凍了嗎?”
他把褲口擺給我看,我用手摸時,半段褲管又涼又硬。他抓住我在摸褲管的手說:
“小孩子,餓壞了吧!”
我說:“不餓。”我怎能說餓呢!為了追求食物他的衣服都結冰了。
過一會,他拿出二十元票子給我看。忽然使我癡呆了一刻,這是哪里來的呢?家庭教師
二十元票子,使他作了家庭教師。
這是第一天,他起得很早,并且臉上也像愉悅了些。我歡喜的跑到過道去倒臉水。心中埋藏不住這些愉快,使我一面折著被子,一面嘴里任意唱著什么歌的句子。而后坐到床沿,兩腿輕輕的跳動,單衫的衣角在腿下面抖蕩。我又跑出門外,看了幾次那個提籃賣面包的人,我想他應該吃些點心吧,八點鐘他要去教書,天寒,衣單,又空著肚子,那是不行的。
但是還不見那提著膨脹的籃子的人來到過道。
郎華作了家庭教師,大概他自己想也應該吃了。當我下樓時,他就自己在買,長形的大提籃已經擺在我們房間的門口。他仿佛一個大蝎虎樣,貪婪的,為著他的食欲,從籃子里往外捉取著面包,圓形的點心和“列巴圈”,他強健的兩臂,好像要把整個籃子抱到房間里才能滿足。最后他付過錢,下了最大的決心,舍棄了籃子跑回房中來吃。
還不到八點鐘,他就走了。九點鐘剛過他就回來。下午太陽快落時,他又去一次,一個鐘頭又回來。他已經慌慌忙忙像是生活有了意義似的。當他回來時,他帶回一個小包袱,他說那是才從當鋪取出的從前他當過的兩件衣裳。他很有興致的把一件長夾袍從包袱里解出來,還有一件小毛衣。
“你穿我的夾袍,我穿毛衣,”他吩咐著。
于是兩個人各自趕快穿上。他的毛衣很合適。惟有我穿著他的夾袍,兩只腳使我自己看不見,手被袖口吞沒去,寬大的袖口使我忽然感到我的肩膀一邊掛好一個口袋,就是這樣我覺得很合適,很滿足。
電燈照耀著滿城市的人家。鈔票帶在我的衣袋里,就這樣兩個人理直氣壯的走在街上,穿過電車道,穿過擾嚷著的那條破街。
一扇破碎的玻璃門,上面封了紙片,郎華拉開它,并且回頭向我說:“很好的小飯館,洋車夫和一切工人全在這里吃飯。”
我跟著進去。里面擺著三張大桌子,我有點看不慣,好幾部分食客都擠在一張桌上。屋子幾乎要轉不來身,我想:讓我坐在那里呢?三張桌子都是滿滿的人。我在袖口外面捏了一下郎華的手說:“一張空桌也沒有,怎么吃?”
樓梯是那樣長,好像讓我順著一條小道爬上天頂。其實只是三層樓,也實在無力了,手扶著樓欄,努力拔著兩條顫顫地,不屬于我似的腿,升上幾步,手也開始和腿一般顫。
等我走進那個房間的時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著臉。
他——郎華,我的情人,那時候他還是我的情人,他問我了:
“你哭了嗎?”
“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淚呀!”
不知是幾分鐘過后,我才發現這個房間是如此的白,棚頂是斜坡的棚頂,除了一張床,地下有一張桌子,一圍藤椅。離開床沿用不到兩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開門時,那更方便,一張門扇躺在床上可以打開。住在這白色的小室,好像把我住在幔帳中一般。我口渴,我說:
“我應該喝一點水吧!”
他要為我倒水時,他非常著慌,兩條眉毛好像要連接起來,在鼻子的上端扭動了好幾下:
“怎樣喝呢?用什么喝?”
桌子上除了一塊潔白的桌布,干凈得連灰塵都不存在。
我有點昏迷,躺在床上聽他和茶房在過道說了些時,又聽到門響,他來到床邊。我想他一定舉著杯子在床邊,卻不,他的手兩面卻分張著:
“用什么喝?可以吧?用臉盆來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著才帶來的臉盆時,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發現,于是拿著刷牙缸走去。
旅館的過道是那樣寂靜,我聽他踏著地板來了。
正在喝著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單上,我用發顫的手指撫來撫去。他說: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撫來撫去,床單有突起的花紋,并且白得有些閃我的眼睛,心想:不錯的,自己正是沒有床單。我心想的話他卻說出了!
“我想我們是要睡空床板的,現在連枕頭都有。”
說著,他拍打我枕在頭下的枕頭。
“咯咯——”有人打門,進來一個高大的俄國女茶房,身后又進來一個中國茶房:
“也租鋪蓋嗎?”
“租的。”
“五角錢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說不租,郎華也說不租。
那女人動手去收拾:軟枕,床單,就連桌布她也從桌子扯下去。床單夾在她的腋下。一切夾在她的腋下。一秒鐘,這潔白的小室跟隨她花色的包頭巾一同消失去。
我雖然是腿顫,雖然肚子餓得那樣空,我也要站起來,打開柳條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樣,床上一張腫漲的草褥赤現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點和白圈顯露出來,大藤椅也好像跟著變了顏色。
晚飯以前,我們就在草褥上吻著抱著過的。
晚飯就在桌子上擺著黑“列巴”和白鹽。
晚飯以后事件就開始了:
開門進來三四個人,黑衣裳,掛著槍,掛著刀。進來先拿住郎華的兩臂,他正赤著胸膛在洗臉,兩手還是濕著。他們那些人,把箱子弄開,翻揚了一陣:
“旅館報告你帶槍,沒帶嗎?”那個掛刀的人問。隨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個長紙卷,里面卷的是一支劍。他打開,抖著劍柄的紅穗頭:
“你那里來的這個?”
停在門口那個去報告的俄國管事,揮著手,急得漲紅了臉。
警察要帶郎華到局子里去,他也預備跟他們去,嘴里不住說:“為什么單獨用這種方式檢查我?防害我?”
最后警察溫和下來,他的兩臂被放開,可是他忘記了穿衣裳,他濕水的手也干了。
原因日間那白俄來取房錢,一日兩元,一月六十元。我們只有五元錢。馬車錢來時去掉五角。那白俄說:
“你的房錢,給!”他好像知道我們沒有錢似的,他好像是很著忙,怕是我們跑走一樣。他拿到手中兩元票子又說:“六十元一月,明天給!”原來包租一月三十元,為了松花江漲水才有這樣的房價。如此,他搖手瞪眼的說:“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華說:“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經理——”
郎華從床下取出劍來,指著白俄:
“你快給我走開,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張著跑出去了,去報告警察所,說我們帶著兇器,其實劍裹在紙里,那人以為是大槍,而不知是一支劍。
結果警察帶劍走了,他說:“日本憲兵若是發現你有劍,那你非吃虧不可,了不得的,說你是大刀會,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來取。”
警察走了以后,閉了燈,鎖上門,街燈的光亮從小窗口跑下來,凄凄淡的,我們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國人,倒比日本憲兵強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從朋友處被逐出來是第二天了。雪天
我直直是睡了一個整天,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漸漸從灰色變做黑色。
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餓了。我下床開了燈,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間坐了坐,扒一扒頭發,揉擦兩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長和無底,好像把我放下一個煤洞去,并且沒有燈籠,使我一個人走沉下去。屋子雖然小,在我覺得和一個荒涼的廣場樣,屋子的墻壁隔離著我,比天還遠,那是說一切不和我發生關系;那是說我的肚子太空了!
一切街車街聲在小窗外鬧著。可是三層樓的過道非常寂靜。每走過一個人,我留意他的腳步聲,那是非常響亮的,硬底皮鞋踏過去,女人的高跟鞋更響亮而且焦急,有時成群的響聲,男男女女穿踏著過道一陣。我聽遍了過道上一切引誘我的聲音,可是不用開門看,我知道郎華還沒回來。
小窗那樣高,囚犯住的屋子一般,我仰起頭來,看見那一些紛飛的雪花從天空忙亂的跌落,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即刻就消融了!變成水珠滾動爬行著,玻璃窗被它畫成沒有意義無組織的條紋。
我想:雪花為什么要翩飛呢?多么沒有意義!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沒有意義嗎?坐在椅子里,兩手空著,什么也不做;口張著,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機器相像。
過道一響,我的心就非常跳,那該不是郎華的腳步?一種穿軟底鞋的聲音,擦擦來近門口,我仿佛是跳起來,我心害怕著:他凍得可憐了吧?他沒有帶回面包來吧!
開門看時,茶房站在那里:
“包夜飯嗎?”
“多少錢?”
“每份六角。包月十五元。”
“……”我一點都不遲疑搖著頭,怕是他把飯送進來強迫叫我吃似的,怕他強迫向我要錢似的。茶房走出,門又嚴肅的關起來。一切別的房中的笑聲,飯菜的香氣都斷絕了,就這樣用一道門,我與人間隔離著。
一直到郎華回來,他的膠皮底鞋擦在門限我才止住幻想。茶房手上的托盤,肉餅,炸黃的番薯,切成大片有彈力的面包……
郎華的夾衣上那樣濕了,已濕的褲管拖著泥。鞋底通了孔,使得襪子也濕了。
他上床暖一暖,腳伸在被子外面,我給他用一張破布擦著腳上冰涼的黑圈。
當他問我時,他和呆人一般直直的腰也不彎:
“餓了吧?”
我幾乎是哭了,我說:“不餓。”為了低頭,我的臉幾乎接觸到他冰涼的腳掌。
他的衣服完全濕透,所以我到馬路旁去買饅頭。就在光身的木桌上,刷牙缸冒著氣,刷牙缸伴著我們把饅頭吃完。饅頭既然吃完,桌上的銅板也要被吃掉似的。他問我:
“夠不夠?”
我說:“夠了。”我問他:“夠不夠?”
他也說:“夠了。”
隔壁的手風琴唱起來,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嗎?手風琴凄凄涼涼地唱呀!
登上桌子,把小窗打開。這小窗是通過人間的孔道:樓頂,煙囪,飛著雪沉重而濃黑的天,路燈,警察,街車,小販,乞丐,一切顯現在這小孔道,煩煩忙忙的市街發著響。
隔壁的手風琴在我們耳里不存在了。他去追求職業
他是一匹受凍受餓的犬呀!
在樓梯盡端,在過道長筒的那邊,他著濕的帽子被墻角隔住,他著濕的鞋子踏過發光的地板,一個一個排著腳踵的印泥。
這還是清早,過道的光線還不充足。可是有的房間門上已經掛好“列巴圈”了!送牛奶的人,輕輕帶著白色的,發熱的瓶子排在房間的門外。這非常引誘我,好像我已嗅到“列巴圈”的麥香,好像那成串肥胖的圓形的點心已經掛在我的鼻頭上。幾天沒有飽食,我是怎樣的需要啊!胃口在胸膛里面收縮,沒有錢買,讓那“列巴圈”們白白在虐待我。
過道漸漸響動起來。他們呼喚著茶房,關門開門,倒臉水。外國女人清早便高聲說笑。可是我的小室,沒有光線,連灰塵都看不見飛揚,靜得桌子在墻角欲睡了,藤椅在地板上伴著桌子睡;靜得棚頂和天空一般高,一切離得我遠遠,一切都厭煩我。
下午,郎華還不回來,我到過道口站了好幾次,外國女人紅色的裙子,藍色的裙子……一張張笑著的驕傲的紅嘴,走下樓梯,她們的高跟鞋打得樓梯清脆發響。圓胖而生著大胡子的男人那樣不相稱地捉著長耳環黑臉的和小雞一般瘦小的“基卜塞”女人上樓來。茶房在前面去給打開一個房間。長時間以后又上來一群外國孩子,他們嘴上剝著瓜子,多冰的鞋底在過道上擗擗拍拍的留下痕跡過去了。
看遍了這一些人,郎華總是不回來,我開始打旋子,經過每個房間,輕輕蕩來踱去,別人已當我是個偷兒,或是討乞的老婆,但我自己并不感覺。仍是帶著我蒼白的臉,退了色的藍布寬大的單衫踱蕩著。
忽然樓梯口跑上兩個一般高的外國姑娘。
“啊呀!”指點著向我說:“你的……真好看!”
另一個樣子像是為了我倒退了一步,并且那兩個不住翻著衣襟給我看:
“你的……真好看!”
我沒有理她們。心想:她們帽子上有水滴,不是又落雪?
跑回房間,看一看窗子究竟落雪不?郎華是穿著昨晚潮濕的衣裳走的。一開窗,雪花便滿窗倒傾下來。
郎華回來,他的帽沿滴著水,我接過來帽子問他:
“外面上凍了嗎?”
他把褲口擺給我看,我用手摸時,半段褲管又涼又硬。他抓住我在摸褲管的手說:
“小孩子,餓壞了吧!”
我說:“不餓。”我怎能說餓呢!為了追求食物他的衣服都結冰了。
過一會,他拿出二十元票子給我看。忽然使我癡呆了一刻,這是哪里來的呢?家庭教師
二十元票子,使他作了家庭教師。
這是第一天,他起得很早,并且臉上也像愉悅了些。我歡喜的跑到過道去倒臉水。心中埋藏不住這些愉快,使我一面折著被子,一面嘴里任意唱著什么歌的句子。而后坐到床沿,兩腿輕輕的跳動,單衫的衣角在腿下面抖蕩。我又跑出門外,看了幾次那個提籃賣面包的人,我想他應該吃些點心吧,八點鐘他要去教書,天寒,衣單,又空著肚子,那是不行的。
但是還不見那提著膨脹的籃子的人來到過道。
郎華作了家庭教師,大概他自己想也應該吃了。當我下樓時,他就自己在買,長形的大提籃已經擺在我們房間的門口。他仿佛一個大蝎虎樣,貪婪的,為著他的食欲,從籃子里往外捉取著面包,圓形的點心和“列巴圈”,他強健的兩臂,好像要把整個籃子抱到房間里才能滿足。最后他付過錢,下了最大的決心,舍棄了籃子跑回房中來吃。
還不到八點鐘,他就走了。九點鐘剛過他就回來。下午太陽快落時,他又去一次,一個鐘頭又回來。他已經慌慌忙忙像是生活有了意義似的。當他回來時,他帶回一個小包袱,他說那是才從當鋪取出的從前他當過的兩件衣裳。他很有興致的把一件長夾袍從包袱里解出來,還有一件小毛衣。
“你穿我的夾袍,我穿毛衣,”他吩咐著。
于是兩個人各自趕快穿上。他的毛衣很合適。惟有我穿著他的夾袍,兩只腳使我自己看不見,手被袖口吞沒去,寬大的袖口使我忽然感到我的肩膀一邊掛好一個口袋,就是這樣我覺得很合適,很滿足。
電燈照耀著滿城市的人家。鈔票帶在我的衣袋里,就這樣兩個人理直氣壯的走在街上,穿過電車道,穿過擾嚷著的那條破街。
一扇破碎的玻璃門,上面封了紙片,郎華拉開它,并且回頭向我說:“很好的小飯館,洋車夫和一切工人全在這里吃飯。”
我跟著進去。里面擺著三張大桌子,我有點看不慣,好幾部分食客都擠在一張桌上。屋子幾乎要轉不來身,我想:讓我坐在那里呢?三張桌子都是滿滿的人。我在袖口外面捏了一下郎華的手說:“一張空桌也沒有,怎么吃?”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